陈北溪论“命”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283 |
| 颗粒名称: | 陈北溪论“命” |
| 分类号: | B244.7-55 |
| 页数: | 17 |
| 页码: | 134-150 |
| 摘要: | 陈淳命论的框架承袭自朱熹,但在部分话题上,或延伸、补充,或提出个人创见。其一,强调天命真诚无妄、非人为。其二,从表面与赋质两个层面讨论气禀清浊,形象而全面地解释了人之贤愚与气禀清浊的关系。其三,尤为强调天命的根源性,人与物之别、日用人伦万事万物均归根于天命,非人力所为。其四,较少讨论安身立命之道,主张修德因应横逆。 |
| 关键词: | 陈淳 命 根原 |
内容
陈淳(1159—1223),字安卿,福建龙溪县(今漳州市龙文区)人,人称北溪先生,为朱子高徒①。根据陈淳晚年讲学之讲义所整理的《北溪字义》,开篇以“命”字为首,可谓其早期探究根原的继续。陈荣捷先生指出:“《北溪字义》以命为首,此是其特色处。《朱子语类》《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均未以《命》字另为一门。陈淳之所以如此重视命者,盖以其寻觅源头处,穷到理而天理流行,以至于天命也。此并非与朱子哲学有殊,盖天命亦朱子之所重,只陈淳以之为其思想之中心而已。”①又指出,陈淳《北溪字义》中“命”一篇,可概括为四方面内容,均来自朱熹②。此说固然不假,陈淳论命整体框架确实来自朱熹,然而在具体话题上,或延伸或补充朱熹之说,并未完全祖述师说。
一、天命
在陈淳看来,在日用之间,事事均体现天命。庆元六年(1200),与廖子晦的书信中,陈淳言道:
大抵许多合做底道理,散在事物而总会于吾心,离心而论事,则事无本;离事而论理,则理为虚。须于人心之中,日用事物之际,见得所合做底,便只是此理,一一有去处,乃为实见。所合做底做得恰好,乃为实践。即此实见无复差迷,便是择善;即此实践更能耐久,便是固执。即此所合做底分来,便成中正仁义。即此所合做底见定浅深轻重,便是日用枝叶,即此所合做底浅深轻重,元有自然条理缝罅,非由人力安排,便是天命根原。③
用天理(命)统摄道,指出此理、此道贯穿于人心,体现于日用事物之际。强调天命乃天理自然非人力所安排。
嘉定十年(1217),其在严陵讲学,作《道学体统》言道:
盖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在心而言,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在人事而言,则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衣服饮食,大而礼乐刑政,财赋军师,凡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④
其将道纳入天命,指出道乃天理自然,为天命所定,在日用人伦万事间均有体现。即是说,人生中日用人伦万事所遵行的道,究其根源乃是天命。诚如学者所指出:“在这个概括中,陈淳清楚地用‘理’将心(性与情之统合)、身(自然生理与社会关系之统合)、行(个人行为与社会责任、日用琐事与家国大事之统合)统串为一体,使朱熹哲学呈现出结构完整而有机、层次清晰而相因的面相。”①
陈淳认为,天道真诚无妄。其言曰:“盖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有以天命本然言者,若‘诚者天之道’是也。”②因而,其讨论天命时,尤为强调其自然性与非人为性。
在这两段话中,陈淳不仅讨论天命的形而上含义,而且突出其在人事中的体现。可谓沿袭朱熹论命时重人事的倾向。
(一)理命、气命
朱熹以降、诰敕阐释命,然天无言,如何命令人呢?对此,陈淳解释道:“天岂‘谆谆然命之乎’?亦只是其理如此而已。”③又曰:“命,犹令也,如尊命、台命之类。天无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气到这物便生这物,气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④在理气化育万物的过程中,天便将命赋予万物包括人。当气到某物生某物时,天便赋予了万事万物这个理。即是说,天通过气赋予万事万物包括人,强调了气的作用。总之,天之命于万事万物,是在气化流行的过程中实现,并未有一个超乎理气之外的命令者。可见,其亦强调命为天所赋予,强调气化流行的过程。
陈淳曾问朱熹道:“‘命’字有专以理言者,有专以气言者。”朱熹答曰:“也都相离不得。盖天非气,无以命于人;人非气,无以受天所命。”⑤提点其不可分割看待理命、气命,强调理气不相离,理命与气命本质为一个命,并指出气的中介性质①。
基于此,陈淳亦就理、气两个层面讨论命。其言曰:
命一字有二义: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其实理不外乎气。盖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个气?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为之枢纽,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尝止息。所谓以理言者,非有离乎气,只是就气上指出个理,不杂乎气而为言耳。②
理不外乎气。在其看来,理为中枢枢纽,但言理不可离气。理之所以存在,乃是阴阳二气流行化育,其上需要一个主宰,于是便在气上指出一个理。可见,在他所论之理气关系中,气的作用更为重要,与朱熹明显不同③。由此出发,其更重视讨论气命。其言道:
如就气说,却亦有两般:一般说贫富贵贱、夭寿祸福,如所谓“死生有命”与“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气之短长厚薄不齐上论,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谓“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禀气之清浊不齐上论,是说人之智愚贤否。①
就气命而言,亦有两个方面:一以气之短长、厚薄差异上言为命分,如寿夭、生死、祸福、贫贱、富贵等均为其所定,此为通常所言之命运;一以气之清浊上言,如人之贤否、智愚即为其所定。其又言道:“若就人品类论,则上天所赋皆一般,而人随其所值,又各有清浊、厚薄之不齐。”②其将所值纳入气禀的讨论中,指出天赋与时,乃一视同仁、毫无二致,但因个体所值(所遇)不同,因而气禀才有清浊、厚薄之差异。朱熹论所值、所禀时,其所言之“气数”实有所值之意③。在此,陈淳明确用所值代替气数,可谓抓住要领。
在此基础上,陈淳详论所值对个体气禀之影响,进而讨论气禀对寿夭及人品高低、贤愚等之影响,并评价古今人物。值得注意的是,陈淳从气禀之清浊与气禀赋质之杂粹两个层面探讨。
首先,陈淳认为:“圣人得气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赋质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④其以尧、舜为例,二圣得气至清至粹,所以聪明神圣;得气清高而禀厚,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得气最长,所以享国皆百余岁。这是在天地之气至清至极的时代,到了孔子所处的时代,天地大气已经衰微,同为圣人的孔子情况便有很大的不同。天地大气已衰,孔夫子虽有至清至粹之气,有生知之智力,但气禀不高不厚,只能不为所用、周游列国,所得之气又不甚长,只得70余岁的中寿。颜回气禀亦是清明纯粹,仅次于圣人,但气不足,因而早夭而亡。
其次,“大抵得气之清者不隔蔽,那理义便呈露昭著。如银盏中满贮清水,自透见盏底银花子甚分明,若未尝有水然”⑤。人好比银盏子,禀受之理义即为盏底的银花子,气禀如同银盏子中盛的水。水之清浊决定盏底的银花子能否看得分明,气禀之清浊则决定理义是否被遮蔽,从而决定人之贤愚。因此,其言道:
贤人得清气多而浊气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聪明也易开发。自大贤而下,或清浊相半,或清底少浊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盏底银花子看不见,欲见得须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学,也解变化气质,转昏为明。①
贤人气禀清多浊少,浊气不能遮蔽其理义,因而智慧才智易开发。大贤以下之人,禀得浊气、清气参半,甚或浊气更多,其理义被遮蔽得较为严重,难以显现。若要驱除遮蔽,必须加以十分澄治之功。如果能够力学,亦能变化气质之性,转昏为明。尽管气命已前定人之贤愚,但是通过澄治之功,亦可转愚为贤。是知,贤愚虽为天命所定,但可通过人之主观能动性改变。与朱熹一样,陈淳亦肯定人能克服气禀清浊的限制,通过个人道德修养,改变前定的贤否智愚之别,追求圣贤的至清至粹的境界。
其又言道:
有一般人,禀气清明,于义理上尽看得出,而行之不笃,不能承载得道理,多杂诡谲去,是又赋质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贮在银盏裹面,亦透底清彻。但泉脉从淤土恶木根中穿过来,味不纯甘,以之煮白米则成赤饭,煎白水则成赤汤,烹茶则酸涩,是有恶味夹杂了。又有一般人,生下来于世味一切简淡,所为甚纯正,但与说到道理处,全发不来,是又赋质纯粹而禀气不清。比如井泉脉味纯甘绝佳,而有泥土浑浊了,终不透莹。②
还有一些人,气禀清明,但是天赋资质不粹。虽然能尽看得出义理,却不能笃行之。如同银盏子盛了清澈的泉水,盏底银花子完全看得分明;但是泉源不净,泉水味道不甘醇,不能用以饮食。又有一些人,天赋资质纯粹,但是气禀不清。虽然行为举止纯正合义理,却无法体贴义理。如同银盏子盛了甘甜味美的泉水,却夹杂泥土,终不能看分明盏底的银花子。是知,人之贤愚,除受气命影响外,亦与天赋资质相关。在其看来,司马光“恭俭力行,笃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资质,只缘少那至清之气,识见不高明”,即为第二种人。因而,二程屡用理义引导他,他却一向偏执固滞,不受启发。
陈淳指出,还有一些人,“甚好说道理,只是执拗,自立一家意见,是禀气清中被一条戾气冲拗了。如泉脉出来甚清,却被一条别水横冲破了,及或遭巉岩石头横截冲激,不帖顺去,反成险恶之流”①。这种人虽然禀受清气,却被一股戾气所冲,因而固执己见,执拗不化。如同泉源清澈,却被另一条水流冲破,掺杂在一起,或像是中途遭遇岩石,被横截冲击,清流反成而恶流。
最后,陈淳总结道:“看来人生气禀是有多少般样,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不可以一律齐。毕竟清明纯粹恰好底极为难得,所以圣贤少而愚不肖者多。”②人之气禀千差万别,难以整齐划一。而清明之气与纯粹之赋质毕竟难以同时兼得,因而圣贤少、愚不肖者多。
陈淳以水比喻气,以肉眼可见的清澈与否比喻气禀之清浊,以水之成分比喻气禀之赋质杂粹。将气禀成分的杂与粹纳入到人之贤愚的讨论中,而不仅仅停留在清浊层面上。可以说,陈淳所论气禀清浊可以分为表面与本质两个层面。其以水喻气,形象地展现了两个层面对人之贤愚的影响。增加气禀赋质的讨论,可谓陈淳气命说的一个新说。
(二)天、命、理之别
二程认为天、命、理、性等本质为一,朱熹则认为此四者即同又异,侧重点不同。陈淳祖述师说,并一步延伸阐发。
首先,陈淳亦讲天即理。其详论道:
天者,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处,大概皆是以理言之。程子曰:“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论语集注“获罪于天”曰:“天即理也。”易本义:“先天弗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又尝亲炙文公说:“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观此亦可见矣。故上而苍苍者,天之体也。上天之体以气言,“上天之载”以理言。③
理即是天,是主宰一切的上帝。讲“苍苍”,是就天之体言,即是以气言;上天之载以理言,即天道。
此外,二程认为循性曰道。朱熹则认为“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①。即是说命与道亦是即同又异。陈淳继承朱熹之说,言道:“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于物者。就元亨利贞之理而言,则谓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而赋予于物者而言,则谓之天命。”②事物从始至终之理为天道;此天道气化流行赋予万物,即为天命。此语可理解为,以理言之谓为天道,自人、物言之谓为天命,指出天道与天命是同一对象在不同角度上的指称,并用天道替代了朱熹之“天”。其仔细分析道:“若就造化上论,则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贞。此四者就气上论也得,就理上论也得。就气上论,则物之初生处为元,于时为春;物之发达处为亨,于时为夏;物之成遂处为利,于时为秋;物之敛藏处为贞,于时为冬。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则谓之正;自其敛藏者而言,故谓之固。就理上论,则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贞者生理之固。”③
其次,陈淳认为天与命略有区别。《孟子》言:“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熹注曰:“以理言之谓之天,自人言之谓之命,其实一而已。”有人问:“此处何以见二者之辨?”陈淳答曰:
天与命只一理,就其中却微有分别。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封此而反之,非人所为便是天。至以吉凶祸福地头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对此而反之,非人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体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谓之天”,是专就天之正面训义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谓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后见。故吉凶祸福自天来,到于人然后为命。乃是于天理中,截断命为一边,而言其指归尔。若只就天一边说,吉凶祸福,未有人受来,如何见得是命?④
在其看来,天与命虽只是一理,却有细微的差别。其一,天与命之相同处为非人为,自然无妄,强调非人力所为便是天。就吉凶祸福而言,因人自身行为招致者,乃是人力而非命;自然而然发生,非人力招致者才是命。其二,天以全体言,命则以妙用言。命乃天所赋予,但必须人禀受之后,才能见得命。强调命为人禀受所得,突出了人的主体性。
再次,陈淳亦讲性即理、性命非二物。其言道:
性即理也。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来具是理于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义礼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谓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谓之礼;得天命之利,在我谓之义;得天命之贞,在我谓之智。性与命本非二物,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①
其一,性即心中之理,因而性即理。元亨利贞四德之理,在人心即为仁义礼智。之所以称性,而不称理,乃是强调此理乃人心禀受于天而为我所有,强调其禀受性。其二,性乃天命赋予人,因而性、命本非二物,在天为命,在人为性。由此,命即理也。其又引程子曰:“天所付为命,人所受为性。”②是知,命强调赋予义,性则侧重禀受义。
其进一步言道:“性命只是一个道理,不分看则不分晓。只管分看不合看,又离了,不相干涉。须是就浑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乱。所以谓之命、谓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个理,须有个形骸方载得此理。其实理不外乎气,得天地之气成这形,得天地之理成这性。”③强调性命只是一个道理,不分开看不能区分。须从浑然一体的理中,看二者分界:命为赋予,性为禀受。又指出理气不相离,因而性、命均不能仅就理言,还需就气言。与朱熹“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气言之”的说法不同④。
最后,陈淳明确地将理一分殊说导入命论。其言道:
自一本而万殊,而体用一原也。合万殊而一统,而显微无间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虚灵不昧,则谓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无所不通,则谓之达道。尧舜与涂人同一禀也,孔子与十室均一赋也,圣人之所以为圣,生知安行乎此也。学者之所以为学,讲明践履乎此也。①
上至圣人,下至涂人,均禀受同一个理。此理乃上帝降衷于人,即天命于人。有人问:“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何故如彼之不齐?”既然天赋予时乃一视同仁,为何各人之命千差万别?陈淳回答道:
譬之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其雨则一,而江河受去,其流滔滔,不增不减;溪涧受去,则洪澜暴涨;沟浍受去,则朝盈暮涸。至放沼沚坎窟、盆瓮罂缶、螺杯蚬壳之属受去,或有斗斛之水,或只涓滴之水,或清甘,或污浊,或臭秽。随他所受,多少般样不齐,岂行雨者固为是区别哉?又譬之治一片地而播之菜子,其为播植一也,而有满园中森森成行伍出者,有掷之蹊旁而践蹂不出者,有未出为鸟雀啄者,有方芽为鸡鹅啮者,有稍长而芟去者,有既秀而连根拔者,有长留在园而旋取叶者,有日供常人而羹食者,有为菹于礼豆而荐神明者,有为齑于金盘而献上宾者,有丐子烹诸瓦盆而食者;有脆嫩而摘者,有壮茂而割者,有结实成子而研为齑汁用者,有藏为种子,到明年复生生不穷者。其参差如彼之不齐,岂播种者所能容心哉?故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自是不齐。亦自然之理,何疑焉!②
陈淳采用比喻手法进行解说,形象地指出天命毫无二致,而各人禀受所得不同,因而有千差万别之命。其一,用雨水作为比拟。同是禀受雨水,江河水流滔滔、不增不减;溪涧则水位暴涨;田间水道则朝盈暮涸;不同的容器受去,又有多少、污浊、清甘、臭秽之别。其二,用菜种子作为比拟,播种在不同地方,生长情况不同;收成后,作用又各种各样。之所以与这些差异,不是施雨者、播种者有意为之,而是禀受者各自禀受不同而导致。最后,又指出该现象亦是自然之理。
朱熹亦有以理一分殊的逻辑讨论命分各不相同,但并未明确地纳入讨论中。其言道:“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气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则又都一般。”③性仅就理言,命则兼就理气而言。气禀有多寡厚薄之别,个体之命因之而千差万别。人禀受理气而生,天赋与人之理是无差别,而人禀受之气则千差万别。这决定了人之命兼具理气而论,就理言之命应是相同的,而就气言之命则千差万别。陈淳明确地用理一分殊讲述命分差异,是对乃师之说的进一步拓展。
二、天命的根原性
临漳问学时,朱熹授以陈淳“根原”二字。朱熹离漳后,陈淳先后撰写《孝根原》《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事物根原》,并指出根原即天命。在此三篇文章中,陈淳将孝等道德范畴与天命对接。不仅指出道德范畴根源自天命,赋予其形而上的合法性,同时亦指出天命的道德性。
陈淳首论孝之根原为天命。在其看来,人之所以孝顺父母,并非父母要求使然,亦非出于畏惧父母,亦非希冀以孝行换取父母的什么回报,亦非自身想要如何,亦非圣人定下规则令人不得不如此,更不是由于畏惧神明遣告、乡党非议、朋友谴责才如此。究其根源,“皆天之所以命于人,而人之所以受乎天。其道当然诚,自有不容已处,非有一毫牵强矫伪于其间也”①。孝道乃天赋与人、人禀受自天。天道真诚无妄,孝道亦是如此,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牵强、虚假与伪装。由此,陈淳从天命的高度论证了孝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同时赋予其真诚性。
五伦以父子之伦为重,孝乃父子之伦的基本原则。孝根原自天命,真诚无妄,其他四伦自不待言。沿着此思路,陈淳将其根原论推之于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四伦。其开宗明义:“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其根原所自来,莫非天命自然,而非人所强为者。”②指出四伦均根原自天命,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强为。其详述道:
夫天之生人群然杂处,愚智不能皆齐不能以相安,必有才智杰然于中,为众所赖,以立者是君臣,盖天所命自然如此也。然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则君君臣臣之所以当义亦岂自外来乎?天之生人独阴不生独阳不成,必阴阳合德然后能生成,是夫妇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分固一定而不可乱,则夫夫妇妇之所以当别,亦岂自外来乎?天之生人虽由父母之胞胎,然决不能一时群生,而并出,必有先者焉,有后者焉,是兄弟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思乎此,则兄弟之所以当友,亦岂自外来乎?天之生人,人必与人为群,决不能脱去与鸟兽为伍,于是乎党类俦辈成焉,是朋友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思乎此则与人交之所以当信亦岂自外来乎?①
朱熹言:“人人有许多道理,盖自天降衷,万里皆具,仁义礼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自家一身都担在这里。”②陈淳此论,可谓是进一步具体论证了朱熹之说。
陈淳又将根原说推之于日用事物间,指出天命为万事万物之根原。其详述道:
夫天之生人,首不能如禽兽之秃其顶,则欲使人庄以冠;身不能如禽兽之氄其毛,则欲使人蔽以衣;趾不能如禽兽之刚其爪甲,则欲使人束其体则,正其衣襟冠履,乃天所以命于人如此也。若祼袒徒跣,则岂其天?而专事华靡之饰,亦岂其天哉?
天之生人,赋以臀欲使之能坐,赋以足欲使之能立。则坐当如尸,立当如齐,亦天所以命于人如此也。若箕踞跛踦,则岂其天?而专事释子之盘蹑,亦岂其天哉?
天于人,饥不能使之不食,渴不能使之不饮,则饮食者,乃天所以使人充饥渴之患者也。若厌之者为道家之辟谷,而溺之者又穷口腹之欲,则岂其天哉?
天于人,昼不能使如夜之晦,夜不能使如昼之明,则昼作而夜息,亦天所以使人顺阴阳之令者也。若昼而为宰予之寝,夜而为禅定之坐,则岂其天哉?
以至头容之所以当直,目容之所以当端,手容之所以当防,口容之所以当正,皆莫非天也。不然,则天于人必偏其头,侧其目,参差其手,飘摇其吻而生者矣。
视之所以当思明,听之所以当思聪,貌之所以当思防,言之所以当思忠,皆莫非天也。不然,则天于人必瞽其视,聋其听,槁其貌,瘖其言而言,而其所以视听言貌非礼之具,亦必元与形俱生矣。
又至冬之所以当裘,夏之所以当葛,出门之所以当如宾,承事之所以当如祭,见齐衰之所以当变冕,瞽者之所以当貌,乡党之所以当恂恂,宗庙之所以当便便,亦无一而非天也。不然,则天于人元必皆无是等事,而吾身之所接元亦必不复与是遇矣。①
在他看来,衣冠鞋帽、坐立之姿、饮食、昼起夜寝、容貌、视听言貌、冬裘夏葛,以及接待不同人采取不同的态度等等,均天命所定。其总结道:“由是而观,凡事物所当然,皆根原于天命之流行,非人之所强为,决不容以忽而易之者。人之所以周旋乎其间,只奉天命而共天职耳。苟于此而容其私心,便是悖天命而废厥职。”②世间万事万物均是天命流行化育而生,非人力违逆自然,勉强为之。因此,人生在天地间,只需遵奉天命,不容有些许私心以悖逆天命。
陈淳所述之事物均为礼仪细则,加上前述五伦,其将儒家之三纲五常、礼均纳入天命范围,为这些道德规范与仪轨确立了天命的先天根据,肯定其必然性与不可违抗性,并赋予其真诚无妄的特质。
通过此三篇根原说,陈淳将命确立为人世间日用人伦事物之根原、依据。其对命的这一发挥,十分切合朱熹理学的内涵。朱熹阅后,答书云:“所示卷子看得甚精密。”③同时又答陈淳岳父李公晦书云:“安卿书来,看得道理尽密,此间诸生皆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远,正为德门之庆。区区南官,亦喜为吾道得此人也。”④高度赞誉了陈淳的阐释。
陈淳的根原说,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陈淳借其根原说对佛道进行批判。其明确地指出,佛教之盘蹑、禅定以及道家之辟谷,均违反天命,企图从根原处否定佛道的正当性。其二,陈淳在陈述衣冠鞋帽根原时,实质上亦指出人与鸟兽之别的根原亦是天命。其教导斋生时,亦是从天命的层面论述了人与鸟兽之别,曰:
人之所以必具衣裳冠屦者,非圣人制为是礼以强人也,天之命于人者然也。盖天之生人,首不为鸟兽之露其顶,必欲使人庄以冠;身不为鸟兽之氄其毳,必欲使人庇以衣,趾不为鸟兽之刚其甲,必欲使人束以屦。表里相备,文质相称,夫然后有以全人之形,而贵于物,理甚昭昭,非由外得。是固无斯须之可去身,而亦无待于人之检防也,复何有寒暑隐显作辍之不常哉!①
值得注意的是,陈淳还从气命层面论证人与物之别,从而指出人、物差别的天命根原。其言曰:
人物之生,不出乎阴阳之气。本只是一气,分来有阴阳,阴阳又分来为五行。二与五只管分合运行,便有参差不齐,有清有浊,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论,同是一气,但人得气之正,物得气之偏,人得气之通,物得气之塞。且如人形骸,却与天地相应,头圆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极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合穴在顶心,却向后。日月来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两眼皆在前。海,碱水所归,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为得气之正。如物则禽兽头横,植物头向下,技叶却在上,此皆得气之偏处。人气通明,物气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为万物之灵。物气塞而不通,如火烟郁在里许,所以理义皆不通。②
各种生命之生成,均是乃阴阳二气与五行分合运行所化生。人与物,所禀本是一气,但因阴阳与五行的运行,便有参差不齐,有清浊、厚薄之别。人禀得气之通、正,因而人之形骸与天地、日月、大海相应;物禀得气之偏塞,因而禽兽、植物各部相同。人之气禀通明,禀得五行之秀,因而为万物之灵,通理义;物之气壅塞不通,因而不通理义。从气禀层面,陈淳给出了人与物不同的形而上根据。指出人之形骸别于物,人通理义,均是气禀所定,从而将人、物之别的根原归之于天命。其又言道:“人与物同得天地之气以生,天地之气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义礼智,粹然独与物异。物得气之偏,为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闭塞而不通。人物所以为理只一般,只是气有偏正,故理随之而有通塞尔。”③明确地指出,人与物禀受之理完全一致,亦禀受同一个气,只因人禀得之气正,理不被闭塞,得以明理义;物禀得之气偏,理被闭塞不通。更为圆融地解释了人通理义之故。
三、安身立命之道
陈淳对安身立命之道鲜少论及,但从字里行间亦可推知一二。
其一,知天命与听天命。其言曰:“如孔子志学,必至于不惑、知命,然后为精。”①说明知命乃是有志者必须达到的境界。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陈淳解释道:
至五十而后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盖专以理言,而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如君之所以当仁,臣之所以当敬,父之所以当慈,子之所以当孝,坐之所以当如尸,立之所以当如齐,视之所以当思明,听之所以当思聪之类,皆天之命我,而非人之所为者。吾皆知其根原所自来,无复遁情,至此则所知者又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以言之矣……至七十而后从心所欲不逾矩,至此,则心体莹彻,纯是天理,浑为一物,凡日用间一随吾意,欲之所之,皆莫非天理,大用流行,而自不越乎法度之外。声即为律,身即为度,所谓道心常为此身之主,而人心一听命矣。即《中庸》所谓“不勉而中”地位也。总而言之,志学所以造道也,而立所以成德也,自不惑、知命而耳顺,则义精之至也;从心所欲不逾矩,则仁熟之极也。②
其又言道:“如‘天命之谓性’,‘五十知天命’,‘穷理尽性至于命’,此等命字,皆是专指理而言。”③是知其所言知天命乃是指知义理之命,而非气命。天命是人伦日用事物之根原,是人与物差别之根原。因而,知命之后,人心又当听命,从而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境界。可见,陈淳讲知命,主要强调道德修养上的追求,而非安于命定之祸福吉凶、富贵贫贱等。
其二,顺受天命之正。陈淳尤为强调天命自然,真诚无妄,非人力所致。其论顺受正命时,亦十分强调人应该真诚顺受,不可有一丝矫揉造作、虚妄。
从理命而言,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四伦均是天命所必然,而非外力铄,人在天地间绝不可能一日离开此四者,因而应当“行乎其中,其所当义、当别、当友、当信,决不可不随处各有以自尽,思以奉天命而尽天职”①。如果不然,“惮于为义而事骄谄,则是不循天命之正为君臣,而以私意为君臣矣”,非天地统摄之权所赋予;“惮于为别而事狎昵,则是不循天命之正为夫妇,而以私意为夫妇矣”,非天地生化之根所令;“于为友而事争防,则是不循天命之正为兄弟,而以私意为兄弟矣”,非天地之序所定;“惮于为信而事机诈,则是不循天命之正为朋友,而以私意为朋友矣”,非天地并育并行之道所命②。
从气命而言,在贤愚层面上,陈淳则主张力行澄治之功,以变化气质,转昏为明;在命运层面上,陈淳突出天命自然而然,非人力所为。武王伐纣,前来孟津汇合、不期而至者有八百国,此乃天命所致,武王只是顺天应人罢了。其引唐陆贽“人事尽处,是谓天理”之言,指出“盖到人事已尽地头,赤见骨不容一点人力,便是天之所为”。即是说人尽了全力,仍不能改变现状,即是天命所为。是知天所定是命运,是不可违抗的。因而,他希望人们顺受其正,顺应天命自然,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其言道:“如桎梏死、岩墙死者非正命,是有致而然,乃人所自取而非天。若尽其道而死者为正命,盖到此时所值之吉凶祸福,皆莫之致而至,故可以天命言,而非人力之所取矣。”③与朱熹一样,其视桎梏而死、岩墙死为人力所致,并非正命。亦主张应当尽道而死,突出强调人的道德义务。
因此,其主张遭遇横逆时,应当反思自我。其言曰:
凡横逆之来,必吾有致之之隙。不然,亦必有近似之情,未有全无故而来者。君子视之,当如炼金之火,攻玉之错,于中有进德无穷之意焉,无恶也。盖使吾之自反,果无一不尽其理矣,而犹未也,恐吾出之有未中其节也;使吾出之果中其节矣,而犹未也,恐吾之全德未能充实而素孚于人也。使吾之全德果充实而素孚于人矣,而彼犹若是者,至此然后可以天地间一恶物视之,亦未可亟胜而峻灭,惟当公处而顺应。如暴来者待之以逊,毁来者待之以靖,诈来者待之以诚,慢来者待之以恭,一行吾天理之当然,若无闻无见焉。④
横逆并非是天命所定,而是人自身因素所致。君子应当将横逆看作炼金之火、攻玉之错,接受其考验,在其中经受磨练并日进于德。当遭遇横逆时,应当自我反思,反思自己是否尽理中节。做到这两点,还不够,还应反思自己的全德是否充实而素孚于人。如果做到这点,仍然遭遇横祸,方可视之为天地间之恶物,即是命中所定。面对此恶物,不必着急考虑克服它,而是应当坦然顺应它,一律以天理去面对它,仿佛并未遭遇横祸一般。只要能做到顺受其正,以天理待之,“则吾心无时而不休,吾身无日而不泰,地无适而不夷,事无接而不利也”①。可见,面对人生中的横逆及命定坏事,均应修德以应,以与生俱来的理去面对。这其中大概也有安于义理的含义。
综上,陈淳论命,基本继承了朱熹的思想框架,探讨了理命与气命、天命理关系等。其尤为突出天命真诚无妄的特质,着重论述“命”作为万事万物根原的形而上地位,少论知命、顺命、安命之类的安身立命之道。该特征与其一生问道旨趣密切相关②。其早期究心探究根源、穷究义理,分下学上达为二物,因而忽略了对安身立命、对待命的探讨;后期虽然已然糅合下学上达功夫,然注重讲学传道、护卫师门,因而亦疏于探讨安身立命之道。由陈淳论命,或可看出虽然在朱熹当头棒喝之下,陈淳已贯通上达下学,然而未必能渗透至方方面面的讨论。
一、天命
在陈淳看来,在日用之间,事事均体现天命。庆元六年(1200),与廖子晦的书信中,陈淳言道:
大抵许多合做底道理,散在事物而总会于吾心,离心而论事,则事无本;离事而论理,则理为虚。须于人心之中,日用事物之际,见得所合做底,便只是此理,一一有去处,乃为实见。所合做底做得恰好,乃为实践。即此实见无复差迷,便是择善;即此实践更能耐久,便是固执。即此所合做底分来,便成中正仁义。即此所合做底见定浅深轻重,便是日用枝叶,即此所合做底浅深轻重,元有自然条理缝罅,非由人力安排,便是天命根原。③
用天理(命)统摄道,指出此理、此道贯穿于人心,体现于日用事物之际。强调天命乃天理自然非人力所安排。
嘉定十年(1217),其在严陵讲学,作《道学体统》言道:
盖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在心而言,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在人事而言,则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衣服饮食,大而礼乐刑政,财赋军师,凡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④
其将道纳入天命,指出道乃天理自然,为天命所定,在日用人伦万事间均有体现。即是说,人生中日用人伦万事所遵行的道,究其根源乃是天命。诚如学者所指出:“在这个概括中,陈淳清楚地用‘理’将心(性与情之统合)、身(自然生理与社会关系之统合)、行(个人行为与社会责任、日用琐事与家国大事之统合)统串为一体,使朱熹哲学呈现出结构完整而有机、层次清晰而相因的面相。”①
陈淳认为,天道真诚无妄。其言曰:“盖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有以天命本然言者,若‘诚者天之道’是也。”②因而,其讨论天命时,尤为强调其自然性与非人为性。
在这两段话中,陈淳不仅讨论天命的形而上含义,而且突出其在人事中的体现。可谓沿袭朱熹论命时重人事的倾向。
(一)理命、气命
朱熹以降、诰敕阐释命,然天无言,如何命令人呢?对此,陈淳解释道:“天岂‘谆谆然命之乎’?亦只是其理如此而已。”③又曰:“命,犹令也,如尊命、台命之类。天无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气到这物便生这物,气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④在理气化育万物的过程中,天便将命赋予万物包括人。当气到某物生某物时,天便赋予了万事万物这个理。即是说,天通过气赋予万事万物包括人,强调了气的作用。总之,天之命于万事万物,是在气化流行的过程中实现,并未有一个超乎理气之外的命令者。可见,其亦强调命为天所赋予,强调气化流行的过程。
陈淳曾问朱熹道:“‘命’字有专以理言者,有专以气言者。”朱熹答曰:“也都相离不得。盖天非气,无以命于人;人非气,无以受天所命。”⑤提点其不可分割看待理命、气命,强调理气不相离,理命与气命本质为一个命,并指出气的中介性质①。
基于此,陈淳亦就理、气两个层面讨论命。其言曰:
命一字有二义: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其实理不外乎气。盖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个气?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为之枢纽,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尝止息。所谓以理言者,非有离乎气,只是就气上指出个理,不杂乎气而为言耳。②
理不外乎气。在其看来,理为中枢枢纽,但言理不可离气。理之所以存在,乃是阴阳二气流行化育,其上需要一个主宰,于是便在气上指出一个理。可见,在他所论之理气关系中,气的作用更为重要,与朱熹明显不同③。由此出发,其更重视讨论气命。其言道:
如就气说,却亦有两般:一般说贫富贵贱、夭寿祸福,如所谓“死生有命”与“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气之短长厚薄不齐上论,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谓“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禀气之清浊不齐上论,是说人之智愚贤否。①
就气命而言,亦有两个方面:一以气之短长、厚薄差异上言为命分,如寿夭、生死、祸福、贫贱、富贵等均为其所定,此为通常所言之命运;一以气之清浊上言,如人之贤否、智愚即为其所定。其又言道:“若就人品类论,则上天所赋皆一般,而人随其所值,又各有清浊、厚薄之不齐。”②其将所值纳入气禀的讨论中,指出天赋与时,乃一视同仁、毫无二致,但因个体所值(所遇)不同,因而气禀才有清浊、厚薄之差异。朱熹论所值、所禀时,其所言之“气数”实有所值之意③。在此,陈淳明确用所值代替气数,可谓抓住要领。
在此基础上,陈淳详论所值对个体气禀之影响,进而讨论气禀对寿夭及人品高低、贤愚等之影响,并评价古今人物。值得注意的是,陈淳从气禀之清浊与气禀赋质之杂粹两个层面探讨。
首先,陈淳认为:“圣人得气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赋质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④其以尧、舜为例,二圣得气至清至粹,所以聪明神圣;得气清高而禀厚,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得气最长,所以享国皆百余岁。这是在天地之气至清至极的时代,到了孔子所处的时代,天地大气已经衰微,同为圣人的孔子情况便有很大的不同。天地大气已衰,孔夫子虽有至清至粹之气,有生知之智力,但气禀不高不厚,只能不为所用、周游列国,所得之气又不甚长,只得70余岁的中寿。颜回气禀亦是清明纯粹,仅次于圣人,但气不足,因而早夭而亡。
其次,“大抵得气之清者不隔蔽,那理义便呈露昭著。如银盏中满贮清水,自透见盏底银花子甚分明,若未尝有水然”⑤。人好比银盏子,禀受之理义即为盏底的银花子,气禀如同银盏子中盛的水。水之清浊决定盏底的银花子能否看得分明,气禀之清浊则决定理义是否被遮蔽,从而决定人之贤愚。因此,其言道:
贤人得清气多而浊气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聪明也易开发。自大贤而下,或清浊相半,或清底少浊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盏底银花子看不见,欲见得须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学,也解变化气质,转昏为明。①
贤人气禀清多浊少,浊气不能遮蔽其理义,因而智慧才智易开发。大贤以下之人,禀得浊气、清气参半,甚或浊气更多,其理义被遮蔽得较为严重,难以显现。若要驱除遮蔽,必须加以十分澄治之功。如果能够力学,亦能变化气质之性,转昏为明。尽管气命已前定人之贤愚,但是通过澄治之功,亦可转愚为贤。是知,贤愚虽为天命所定,但可通过人之主观能动性改变。与朱熹一样,陈淳亦肯定人能克服气禀清浊的限制,通过个人道德修养,改变前定的贤否智愚之别,追求圣贤的至清至粹的境界。
其又言道:
有一般人,禀气清明,于义理上尽看得出,而行之不笃,不能承载得道理,多杂诡谲去,是又赋质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贮在银盏裹面,亦透底清彻。但泉脉从淤土恶木根中穿过来,味不纯甘,以之煮白米则成赤饭,煎白水则成赤汤,烹茶则酸涩,是有恶味夹杂了。又有一般人,生下来于世味一切简淡,所为甚纯正,但与说到道理处,全发不来,是又赋质纯粹而禀气不清。比如井泉脉味纯甘绝佳,而有泥土浑浊了,终不透莹。②
还有一些人,气禀清明,但是天赋资质不粹。虽然能尽看得出义理,却不能笃行之。如同银盏子盛了清澈的泉水,盏底银花子完全看得分明;但是泉源不净,泉水味道不甘醇,不能用以饮食。又有一些人,天赋资质纯粹,但是气禀不清。虽然行为举止纯正合义理,却无法体贴义理。如同银盏子盛了甘甜味美的泉水,却夹杂泥土,终不能看分明盏底的银花子。是知,人之贤愚,除受气命影响外,亦与天赋资质相关。在其看来,司马光“恭俭力行,笃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资质,只缘少那至清之气,识见不高明”,即为第二种人。因而,二程屡用理义引导他,他却一向偏执固滞,不受启发。
陈淳指出,还有一些人,“甚好说道理,只是执拗,自立一家意见,是禀气清中被一条戾气冲拗了。如泉脉出来甚清,却被一条别水横冲破了,及或遭巉岩石头横截冲激,不帖顺去,反成险恶之流”①。这种人虽然禀受清气,却被一股戾气所冲,因而固执己见,执拗不化。如同泉源清澈,却被另一条水流冲破,掺杂在一起,或像是中途遭遇岩石,被横截冲击,清流反成而恶流。
最后,陈淳总结道:“看来人生气禀是有多少般样,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不可以一律齐。毕竟清明纯粹恰好底极为难得,所以圣贤少而愚不肖者多。”②人之气禀千差万别,难以整齐划一。而清明之气与纯粹之赋质毕竟难以同时兼得,因而圣贤少、愚不肖者多。
陈淳以水比喻气,以肉眼可见的清澈与否比喻气禀之清浊,以水之成分比喻气禀之赋质杂粹。将气禀成分的杂与粹纳入到人之贤愚的讨论中,而不仅仅停留在清浊层面上。可以说,陈淳所论气禀清浊可以分为表面与本质两个层面。其以水喻气,形象地展现了两个层面对人之贤愚的影响。增加气禀赋质的讨论,可谓陈淳气命说的一个新说。
(二)天、命、理之别
二程认为天、命、理、性等本质为一,朱熹则认为此四者即同又异,侧重点不同。陈淳祖述师说,并一步延伸阐发。
首先,陈淳亦讲天即理。其详论道:
天者,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处,大概皆是以理言之。程子曰:“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论语集注“获罪于天”曰:“天即理也。”易本义:“先天弗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又尝亲炙文公说:“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观此亦可见矣。故上而苍苍者,天之体也。上天之体以气言,“上天之载”以理言。③
理即是天,是主宰一切的上帝。讲“苍苍”,是就天之体言,即是以气言;上天之载以理言,即天道。
此外,二程认为循性曰道。朱熹则认为“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①。即是说命与道亦是即同又异。陈淳继承朱熹之说,言道:“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于物者。就元亨利贞之理而言,则谓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而赋予于物者而言,则谓之天命。”②事物从始至终之理为天道;此天道气化流行赋予万物,即为天命。此语可理解为,以理言之谓为天道,自人、物言之谓为天命,指出天道与天命是同一对象在不同角度上的指称,并用天道替代了朱熹之“天”。其仔细分析道:“若就造化上论,则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贞。此四者就气上论也得,就理上论也得。就气上论,则物之初生处为元,于时为春;物之发达处为亨,于时为夏;物之成遂处为利,于时为秋;物之敛藏处为贞,于时为冬。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则谓之正;自其敛藏者而言,故谓之固。就理上论,则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贞者生理之固。”③
其次,陈淳认为天与命略有区别。《孟子》言:“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熹注曰:“以理言之谓之天,自人言之谓之命,其实一而已。”有人问:“此处何以见二者之辨?”陈淳答曰:
天与命只一理,就其中却微有分别。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封此而反之,非人所为便是天。至以吉凶祸福地头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对此而反之,非人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体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谓之天”,是专就天之正面训义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谓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后见。故吉凶祸福自天来,到于人然后为命。乃是于天理中,截断命为一边,而言其指归尔。若只就天一边说,吉凶祸福,未有人受来,如何见得是命?④
在其看来,天与命虽只是一理,却有细微的差别。其一,天与命之相同处为非人为,自然无妄,强调非人力所为便是天。就吉凶祸福而言,因人自身行为招致者,乃是人力而非命;自然而然发生,非人力招致者才是命。其二,天以全体言,命则以妙用言。命乃天所赋予,但必须人禀受之后,才能见得命。强调命为人禀受所得,突出了人的主体性。
再次,陈淳亦讲性即理、性命非二物。其言道:
性即理也。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来具是理于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义礼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谓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谓之礼;得天命之利,在我谓之义;得天命之贞,在我谓之智。性与命本非二物,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①
其一,性即心中之理,因而性即理。元亨利贞四德之理,在人心即为仁义礼智。之所以称性,而不称理,乃是强调此理乃人心禀受于天而为我所有,强调其禀受性。其二,性乃天命赋予人,因而性、命本非二物,在天为命,在人为性。由此,命即理也。其又引程子曰:“天所付为命,人所受为性。”②是知,命强调赋予义,性则侧重禀受义。
其进一步言道:“性命只是一个道理,不分看则不分晓。只管分看不合看,又离了,不相干涉。须是就浑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乱。所以谓之命、谓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个理,须有个形骸方载得此理。其实理不外乎气,得天地之气成这形,得天地之理成这性。”③强调性命只是一个道理,不分开看不能区分。须从浑然一体的理中,看二者分界:命为赋予,性为禀受。又指出理气不相离,因而性、命均不能仅就理言,还需就气言。与朱熹“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气言之”的说法不同④。
最后,陈淳明确地将理一分殊说导入命论。其言道:
自一本而万殊,而体用一原也。合万殊而一统,而显微无间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虚灵不昧,则谓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无所不通,则谓之达道。尧舜与涂人同一禀也,孔子与十室均一赋也,圣人之所以为圣,生知安行乎此也。学者之所以为学,讲明践履乎此也。①
上至圣人,下至涂人,均禀受同一个理。此理乃上帝降衷于人,即天命于人。有人问:“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何故如彼之不齐?”既然天赋予时乃一视同仁,为何各人之命千差万别?陈淳回答道:
譬之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其雨则一,而江河受去,其流滔滔,不增不减;溪涧受去,则洪澜暴涨;沟浍受去,则朝盈暮涸。至放沼沚坎窟、盆瓮罂缶、螺杯蚬壳之属受去,或有斗斛之水,或只涓滴之水,或清甘,或污浊,或臭秽。随他所受,多少般样不齐,岂行雨者固为是区别哉?又譬之治一片地而播之菜子,其为播植一也,而有满园中森森成行伍出者,有掷之蹊旁而践蹂不出者,有未出为鸟雀啄者,有方芽为鸡鹅啮者,有稍长而芟去者,有既秀而连根拔者,有长留在园而旋取叶者,有日供常人而羹食者,有为菹于礼豆而荐神明者,有为齑于金盘而献上宾者,有丐子烹诸瓦盆而食者;有脆嫩而摘者,有壮茂而割者,有结实成子而研为齑汁用者,有藏为种子,到明年复生生不穷者。其参差如彼之不齐,岂播种者所能容心哉?故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自是不齐。亦自然之理,何疑焉!②
陈淳采用比喻手法进行解说,形象地指出天命毫无二致,而各人禀受所得不同,因而有千差万别之命。其一,用雨水作为比拟。同是禀受雨水,江河水流滔滔、不增不减;溪涧则水位暴涨;田间水道则朝盈暮涸;不同的容器受去,又有多少、污浊、清甘、臭秽之别。其二,用菜种子作为比拟,播种在不同地方,生长情况不同;收成后,作用又各种各样。之所以与这些差异,不是施雨者、播种者有意为之,而是禀受者各自禀受不同而导致。最后,又指出该现象亦是自然之理。
朱熹亦有以理一分殊的逻辑讨论命分各不相同,但并未明确地纳入讨论中。其言道:“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气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则又都一般。”③性仅就理言,命则兼就理气而言。气禀有多寡厚薄之别,个体之命因之而千差万别。人禀受理气而生,天赋与人之理是无差别,而人禀受之气则千差万别。这决定了人之命兼具理气而论,就理言之命应是相同的,而就气言之命则千差万别。陈淳明确地用理一分殊讲述命分差异,是对乃师之说的进一步拓展。
二、天命的根原性
临漳问学时,朱熹授以陈淳“根原”二字。朱熹离漳后,陈淳先后撰写《孝根原》《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事物根原》,并指出根原即天命。在此三篇文章中,陈淳将孝等道德范畴与天命对接。不仅指出道德范畴根源自天命,赋予其形而上的合法性,同时亦指出天命的道德性。
陈淳首论孝之根原为天命。在其看来,人之所以孝顺父母,并非父母要求使然,亦非出于畏惧父母,亦非希冀以孝行换取父母的什么回报,亦非自身想要如何,亦非圣人定下规则令人不得不如此,更不是由于畏惧神明遣告、乡党非议、朋友谴责才如此。究其根源,“皆天之所以命于人,而人之所以受乎天。其道当然诚,自有不容已处,非有一毫牵强矫伪于其间也”①。孝道乃天赋与人、人禀受自天。天道真诚无妄,孝道亦是如此,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牵强、虚假与伪装。由此,陈淳从天命的高度论证了孝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同时赋予其真诚性。
五伦以父子之伦为重,孝乃父子之伦的基本原则。孝根原自天命,真诚无妄,其他四伦自不待言。沿着此思路,陈淳将其根原论推之于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四伦。其开宗明义:“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其根原所自来,莫非天命自然,而非人所强为者。”②指出四伦均根原自天命,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强为。其详述道:
夫天之生人群然杂处,愚智不能皆齐不能以相安,必有才智杰然于中,为众所赖,以立者是君臣,盖天所命自然如此也。然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则君君臣臣之所以当义亦岂自外来乎?天之生人独阴不生独阳不成,必阴阳合德然后能生成,是夫妇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分固一定而不可乱,则夫夫妇妇之所以当别,亦岂自外来乎?天之生人虽由父母之胞胎,然决不能一时群生,而并出,必有先者焉,有后者焉,是兄弟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思乎此,则兄弟之所以当友,亦岂自外来乎?天之生人,人必与人为群,决不能脱去与鸟兽为伍,于是乎党类俦辈成焉,是朋友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思乎此则与人交之所以当信亦岂自外来乎?①
朱熹言:“人人有许多道理,盖自天降衷,万里皆具,仁义礼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自家一身都担在这里。”②陈淳此论,可谓是进一步具体论证了朱熹之说。
陈淳又将根原说推之于日用事物间,指出天命为万事万物之根原。其详述道:
夫天之生人,首不能如禽兽之秃其顶,则欲使人庄以冠;身不能如禽兽之氄其毛,则欲使人蔽以衣;趾不能如禽兽之刚其爪甲,则欲使人束其体则,正其衣襟冠履,乃天所以命于人如此也。若祼袒徒跣,则岂其天?而专事华靡之饰,亦岂其天哉?
天之生人,赋以臀欲使之能坐,赋以足欲使之能立。则坐当如尸,立当如齐,亦天所以命于人如此也。若箕踞跛踦,则岂其天?而专事释子之盘蹑,亦岂其天哉?
天于人,饥不能使之不食,渴不能使之不饮,则饮食者,乃天所以使人充饥渴之患者也。若厌之者为道家之辟谷,而溺之者又穷口腹之欲,则岂其天哉?
天于人,昼不能使如夜之晦,夜不能使如昼之明,则昼作而夜息,亦天所以使人顺阴阳之令者也。若昼而为宰予之寝,夜而为禅定之坐,则岂其天哉?
以至头容之所以当直,目容之所以当端,手容之所以当防,口容之所以当正,皆莫非天也。不然,则天于人必偏其头,侧其目,参差其手,飘摇其吻而生者矣。
视之所以当思明,听之所以当思聪,貌之所以当思防,言之所以当思忠,皆莫非天也。不然,则天于人必瞽其视,聋其听,槁其貌,瘖其言而言,而其所以视听言貌非礼之具,亦必元与形俱生矣。
又至冬之所以当裘,夏之所以当葛,出门之所以当如宾,承事之所以当如祭,见齐衰之所以当变冕,瞽者之所以当貌,乡党之所以当恂恂,宗庙之所以当便便,亦无一而非天也。不然,则天于人元必皆无是等事,而吾身之所接元亦必不复与是遇矣。①
在他看来,衣冠鞋帽、坐立之姿、饮食、昼起夜寝、容貌、视听言貌、冬裘夏葛,以及接待不同人采取不同的态度等等,均天命所定。其总结道:“由是而观,凡事物所当然,皆根原于天命之流行,非人之所强为,决不容以忽而易之者。人之所以周旋乎其间,只奉天命而共天职耳。苟于此而容其私心,便是悖天命而废厥职。”②世间万事万物均是天命流行化育而生,非人力违逆自然,勉强为之。因此,人生在天地间,只需遵奉天命,不容有些许私心以悖逆天命。
陈淳所述之事物均为礼仪细则,加上前述五伦,其将儒家之三纲五常、礼均纳入天命范围,为这些道德规范与仪轨确立了天命的先天根据,肯定其必然性与不可违抗性,并赋予其真诚无妄的特质。
通过此三篇根原说,陈淳将命确立为人世间日用人伦事物之根原、依据。其对命的这一发挥,十分切合朱熹理学的内涵。朱熹阅后,答书云:“所示卷子看得甚精密。”③同时又答陈淳岳父李公晦书云:“安卿书来,看得道理尽密,此间诸生皆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远,正为德门之庆。区区南官,亦喜为吾道得此人也。”④高度赞誉了陈淳的阐释。
陈淳的根原说,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陈淳借其根原说对佛道进行批判。其明确地指出,佛教之盘蹑、禅定以及道家之辟谷,均违反天命,企图从根原处否定佛道的正当性。其二,陈淳在陈述衣冠鞋帽根原时,实质上亦指出人与鸟兽之别的根原亦是天命。其教导斋生时,亦是从天命的层面论述了人与鸟兽之别,曰:
人之所以必具衣裳冠屦者,非圣人制为是礼以强人也,天之命于人者然也。盖天之生人,首不为鸟兽之露其顶,必欲使人庄以冠;身不为鸟兽之氄其毳,必欲使人庇以衣,趾不为鸟兽之刚其甲,必欲使人束以屦。表里相备,文质相称,夫然后有以全人之形,而贵于物,理甚昭昭,非由外得。是固无斯须之可去身,而亦无待于人之检防也,复何有寒暑隐显作辍之不常哉!①
值得注意的是,陈淳还从气命层面论证人与物之别,从而指出人、物差别的天命根原。其言曰:
人物之生,不出乎阴阳之气。本只是一气,分来有阴阳,阴阳又分来为五行。二与五只管分合运行,便有参差不齐,有清有浊,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论,同是一气,但人得气之正,物得气之偏,人得气之通,物得气之塞。且如人形骸,却与天地相应,头圆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极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合穴在顶心,却向后。日月来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两眼皆在前。海,碱水所归,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为得气之正。如物则禽兽头横,植物头向下,技叶却在上,此皆得气之偏处。人气通明,物气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为万物之灵。物气塞而不通,如火烟郁在里许,所以理义皆不通。②
各种生命之生成,均是乃阴阳二气与五行分合运行所化生。人与物,所禀本是一气,但因阴阳与五行的运行,便有参差不齐,有清浊、厚薄之别。人禀得气之通、正,因而人之形骸与天地、日月、大海相应;物禀得气之偏塞,因而禽兽、植物各部相同。人之气禀通明,禀得五行之秀,因而为万物之灵,通理义;物之气壅塞不通,因而不通理义。从气禀层面,陈淳给出了人与物不同的形而上根据。指出人之形骸别于物,人通理义,均是气禀所定,从而将人、物之别的根原归之于天命。其又言道:“人与物同得天地之气以生,天地之气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义礼智,粹然独与物异。物得气之偏,为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闭塞而不通。人物所以为理只一般,只是气有偏正,故理随之而有通塞尔。”③明确地指出,人与物禀受之理完全一致,亦禀受同一个气,只因人禀得之气正,理不被闭塞,得以明理义;物禀得之气偏,理被闭塞不通。更为圆融地解释了人通理义之故。
三、安身立命之道
陈淳对安身立命之道鲜少论及,但从字里行间亦可推知一二。
其一,知天命与听天命。其言曰:“如孔子志学,必至于不惑、知命,然后为精。”①说明知命乃是有志者必须达到的境界。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陈淳解释道:
至五十而后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盖专以理言,而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如君之所以当仁,臣之所以当敬,父之所以当慈,子之所以当孝,坐之所以当如尸,立之所以当如齐,视之所以当思明,听之所以当思聪之类,皆天之命我,而非人之所为者。吾皆知其根原所自来,无复遁情,至此则所知者又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以言之矣……至七十而后从心所欲不逾矩,至此,则心体莹彻,纯是天理,浑为一物,凡日用间一随吾意,欲之所之,皆莫非天理,大用流行,而自不越乎法度之外。声即为律,身即为度,所谓道心常为此身之主,而人心一听命矣。即《中庸》所谓“不勉而中”地位也。总而言之,志学所以造道也,而立所以成德也,自不惑、知命而耳顺,则义精之至也;从心所欲不逾矩,则仁熟之极也。②
其又言道:“如‘天命之谓性’,‘五十知天命’,‘穷理尽性至于命’,此等命字,皆是专指理而言。”③是知其所言知天命乃是指知义理之命,而非气命。天命是人伦日用事物之根原,是人与物差别之根原。因而,知命之后,人心又当听命,从而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境界。可见,陈淳讲知命,主要强调道德修养上的追求,而非安于命定之祸福吉凶、富贵贫贱等。
其二,顺受天命之正。陈淳尤为强调天命自然,真诚无妄,非人力所致。其论顺受正命时,亦十分强调人应该真诚顺受,不可有一丝矫揉造作、虚妄。
从理命而言,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四伦均是天命所必然,而非外力铄,人在天地间绝不可能一日离开此四者,因而应当“行乎其中,其所当义、当别、当友、当信,决不可不随处各有以自尽,思以奉天命而尽天职”①。如果不然,“惮于为义而事骄谄,则是不循天命之正为君臣,而以私意为君臣矣”,非天地统摄之权所赋予;“惮于为别而事狎昵,则是不循天命之正为夫妇,而以私意为夫妇矣”,非天地生化之根所令;“于为友而事争防,则是不循天命之正为兄弟,而以私意为兄弟矣”,非天地之序所定;“惮于为信而事机诈,则是不循天命之正为朋友,而以私意为朋友矣”,非天地并育并行之道所命②。
从气命而言,在贤愚层面上,陈淳则主张力行澄治之功,以变化气质,转昏为明;在命运层面上,陈淳突出天命自然而然,非人力所为。武王伐纣,前来孟津汇合、不期而至者有八百国,此乃天命所致,武王只是顺天应人罢了。其引唐陆贽“人事尽处,是谓天理”之言,指出“盖到人事已尽地头,赤见骨不容一点人力,便是天之所为”。即是说人尽了全力,仍不能改变现状,即是天命所为。是知天所定是命运,是不可违抗的。因而,他希望人们顺受其正,顺应天命自然,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其言道:“如桎梏死、岩墙死者非正命,是有致而然,乃人所自取而非天。若尽其道而死者为正命,盖到此时所值之吉凶祸福,皆莫之致而至,故可以天命言,而非人力之所取矣。”③与朱熹一样,其视桎梏而死、岩墙死为人力所致,并非正命。亦主张应当尽道而死,突出强调人的道德义务。
因此,其主张遭遇横逆时,应当反思自我。其言曰:
凡横逆之来,必吾有致之之隙。不然,亦必有近似之情,未有全无故而来者。君子视之,当如炼金之火,攻玉之错,于中有进德无穷之意焉,无恶也。盖使吾之自反,果无一不尽其理矣,而犹未也,恐吾出之有未中其节也;使吾出之果中其节矣,而犹未也,恐吾之全德未能充实而素孚于人也。使吾之全德果充实而素孚于人矣,而彼犹若是者,至此然后可以天地间一恶物视之,亦未可亟胜而峻灭,惟当公处而顺应。如暴来者待之以逊,毁来者待之以靖,诈来者待之以诚,慢来者待之以恭,一行吾天理之当然,若无闻无见焉。④
横逆并非是天命所定,而是人自身因素所致。君子应当将横逆看作炼金之火、攻玉之错,接受其考验,在其中经受磨练并日进于德。当遭遇横逆时,应当自我反思,反思自己是否尽理中节。做到这两点,还不够,还应反思自己的全德是否充实而素孚于人。如果做到这点,仍然遭遇横祸,方可视之为天地间之恶物,即是命中所定。面对此恶物,不必着急考虑克服它,而是应当坦然顺应它,一律以天理去面对它,仿佛并未遭遇横祸一般。只要能做到顺受其正,以天理待之,“则吾心无时而不休,吾身无日而不泰,地无适而不夷,事无接而不利也”①。可见,面对人生中的横逆及命定坏事,均应修德以应,以与生俱来的理去面对。这其中大概也有安于义理的含义。
综上,陈淳论命,基本继承了朱熹的思想框架,探讨了理命与气命、天命理关系等。其尤为突出天命真诚无妄的特质,着重论述“命”作为万事万物根原的形而上地位,少论知命、顺命、安命之类的安身立命之道。该特征与其一生问道旨趣密切相关②。其早期究心探究根源、穷究义理,分下学上达为二物,因而忽略了对安身立命、对待命的探讨;后期虽然已然糅合下学上达功夫,然注重讲学传道、护卫师门,因而亦疏于探讨安身立命之道。由陈淳论命,或可看出虽然在朱熹当头棒喝之下,陈淳已贯通上达下学,然而未必能渗透至方方面面的讨论。
附注
*作者简介:李毅婷(1982—),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基金项目:2016年福建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礼下庶人视域下的陈淳礼学研究”(FJ2016C178);2016年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陈淳外王思想与漳州地方社会”。
①关于陈淳生卒年,学界有多种看法,今采张加才之说。具体可参看张加才:《关于北溪生平研究的几个问题》,《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26—31页、第37页。
①[美]陈荣捷:《最笃实之门徒——陈淳》,《朱子新探索》,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445页。
②[美]陈荣捷:《朱子言命》,《朱子新探索》,第246页。
③[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二《答廖师子晦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宋]陈淳:《严陵讲义·道学体统》,见陈氏著《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5页。
①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②《北溪大全集》卷二三《答陈寺丞师复二》。
③《北溪字义》卷上《命》,第4页。
④《北溪字义》卷上《命》,第1页。
⑤《朱子语类》卷四《性理一》,第76页。
①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指出:“理之命是就‘虽富贵之极,亦有品节限制’说,气之命是就贫贱说。但此两命义实不同,朱子混视之而为一命,亦非是。”〔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页。〕认为朱熹将气命、理命混视为一命,为后世学者分析朱熹命论定下了基本思路。如[美]陈荣捷:《朱子言命》,《朱子新探索》,第247—248页;史少博:《朱熹论“命”》,《管子学刊》2007年第3期,第107—109页、第125页;汪学群:《朱熹对命的思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26—34页。极少数学者认为,命分为理命、气命两种,把命分为两种。如魏义霞:《理气双重的审视维度和价值旨趣——朱熹性命之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第21—24页。赵金刚既反对朱熹将命分为两种的说法,且认为将命分为理命、气命分析不能成立:“不存在理命和气命两种命,命只是一个命,理和气综合起来才可以言命,虽然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命有两方面的内容,但这两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单独构成命。命在朱子那里不应该用‘理-气’这样的构架分属之,而应该像心一样,用‘易—道—神’的方式来看。”(赵金刚:《朱子论“命”》,《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3期,第103—110页。)朱熹论命依托其理气一元的宇宙论,因而必然从理受、气禀两个维度论命。朱熹不止一次指出:“命有二:有理,有气。”([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九九《张子之书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7页。)想彻底否定朱熹命论中存在“理—气”架构是不可能的。
②《北溪字义》卷上《命》,第1页。
③张加才:《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
①《北溪字义》卷上《命》,第1—2页。
②《北溪字义》卷上《命》,第2页。
③朱子言:“天地那里说我特地要生个圣贤出来!也只是气数到那里,恰相凑着,所以生出圣贤。及至生出,则若天之有意焉耳。”(《朱子语类》卷四《性理一》,第80页。)又言:“人之生,适遇其气,有得清者,有得浊者,贵贱寿夭皆然,故有参错不齐如此。圣贤在上,则其气中和;不然,则其气偏行。故有得其气清,聪明而无福禄者;亦有得其气浊,有福禄而无知者,皆其气数使然。”(《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第8页)可证。
④《北溪字义》卷上《命》,第2页。
⑤《北溪字义》卷上《命》,第2—3页。
①《北溪字义》卷上《命》,第3页。
②《北溪字义》卷上《命》,第3页。
①《北溪字义》卷上《命》,第3页。
②《北溪字义》卷上《命》,第3页。
③《北溪字义》卷上《命》,第5页。
①《朱子语类》卷五《性理二》,第82页。
②《北溪字义》卷上《命》,第1页。
③《北溪字义》卷上《命》,第3—4页。
④《北溪字义》卷上《命》,第4—5页。
①《北溪字义》卷上《性》,第6页。
②《北溪字义》卷上《性》,第6页。
③《北溪字义》卷上《性》,第6页。
④《朱子语类》卷四《性理一》,第77页。
①《严陵讲义·道学体统》,《北溪字义》,第75—76页。
②《北溪字义》卷上《命》,第5—6页。
③《朱子语类》卷四《性理一》,第77页。
①《北溪大全集》卷五《孝根原》。
②《北溪大全集》卷五《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
①《北溪大全集》卷五《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
②《朱子语类》卷一二一《朱子十八》,第2926页。
①《北溪大全集》卷五《事物根原》。
②《北溪大全集》卷五《事物根原》。
③《北溪大全集》卷五卷后。
④《北溪大全集》卷五卷后。
①《北溪大全集》卷一一《暑月喻斋生》。
②《北溪字义》卷上《命》,第2页。
③《北溪字义》卷上《性》,第6—7页。
①《北溪大全集》卷二三《答陈寺丞师复二》。
②《北溪大全集》卷一八《论语讲义》“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条。
③《北溪字义》卷上《命》,第1页。
①《北溪大全集》卷五《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
②《北溪大全集》卷五《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
③《北溪字义》卷上《命》,第4页。
④《北溪大全集》卷七《横逆自反》。
①《北溪大全集》卷七《横逆自反》。
②关于陈淳问道旨趣变迁,可参看拙文:《陈淳理学问道旨趣变迁——以“下学上达”为中心的讨论》,《闽台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第55—68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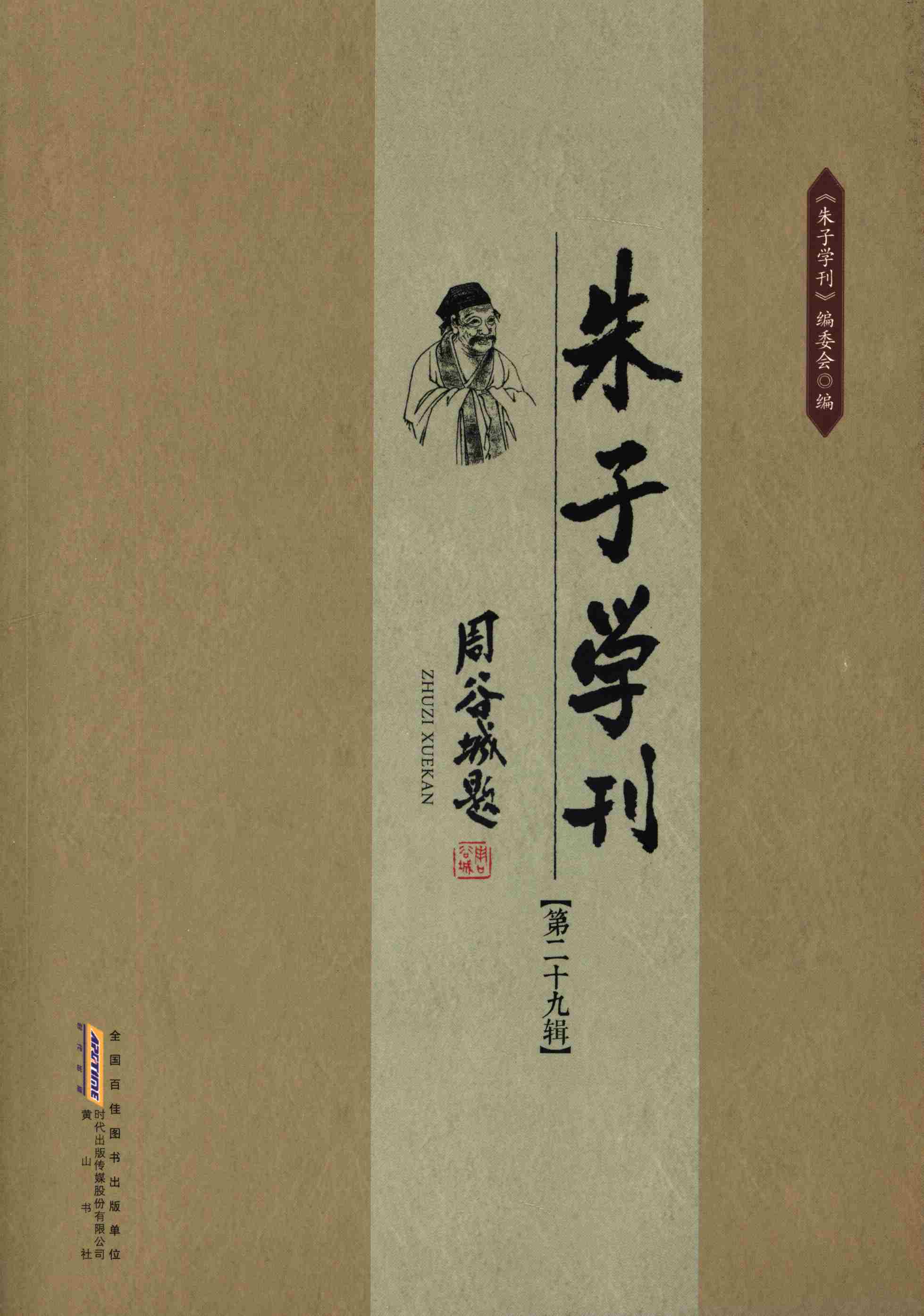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出版者:黄山书社
本书收录了《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学》《朱熹婚丧礼制的推行》《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戴震与朱熹关系平议》《陈北溪论“命”》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