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经传通解》编撰缘起新论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252 |
| 颗粒名称: | 《仪礼经传通解》编撰缘起新论 |
| 分类号: | B244.7-55 |
| 页数: | 16 |
| 页码: | 046-061 |
| 摘要: | 《仪礼经传通解》由朱子发起,历经朱子、黄榦、杨复三代学者前赴后继才编撰完成的礼学作品。朱子编撰《仪礼经传通解》的内在动力源自下学上达的工夫,而学术根源则是远承二程切问近思的治学方法,直接触发的原因则是宋代忽略礼学的学术偏差。正是三种因素促成朱子着手编撰《仪礼经传通解》。 |
| 关键词: | 编撰缘由 下学上达 切问近思 |
内容
《仪礼经传通解》(下文简称“《通解》”)历经朱子、黄榦、杨复三代学者主编而成,关于编撰的缘由,学者论述甚多,如殷慧博士学位论文《朱子礼学思想研究》认为《通解》的编撰缘由有两大方面:“学术层面:对宋代礼学研究的反思与纠偏……现实层面:礼制论争中屡屡受挫后的学术反思。”①潘斌《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缘由和学术影响》则认为有三方面原因:“为了继承和弘扬儒家的礼乐文化。……对王安石新政的文化政策所作之回应。……受到了吕祖谦、潘恭叔等人礼学观点的影响。”②他们都从不同层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也都部分指明朱子编撰《通解》的原因,但是殷慧的研究主要从外在的学术思潮和政治学术斗争来看待朱子编撰《通解》的缘由,而潘斌的研究则从朱子从事儒学研究的宏观目标与外在政治学术因素寻找问题的答案,都与朱子编撰《通解》的内在缘由存有一涧之隔,因为两者都未能把《通解》放置于朱子学术思想发展过程来考虑,尚未从朱子治学发展的变化过程来寻找其内外原因。正如蔡方鹿所说:
朱熹《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经传相分又相合的思想,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而与其理学思想有所出入。就其经学的逻辑言,是以《仪礼》为经,为本,为事,以《礼记》为传,为末,为理,经传的本末、事理之分,是其经学的内在逻辑。而就朱熹理学的逻辑而言,其理本论哲学不允许把理置于末和从属于事的位置,理作为宇宙的本体,是包括礼在内的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故就其理本论讲,理不依赖事物而存在,由此与其经学《礼记》之理安顿在《仪礼》之事的思想有所出入。①
蔡方鹿先生注意到了朱子经学与理学体系之间的差异,即经为本与理为本之间的矛盾关系,但未深入考察朱子礼学与理学之间的学术关系,而这却是朱子晚年编礼书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将从朱子的思想体系入手来讨论《通解》编撰的学术原因。
一、下学上达:由义理回归文本的内在动力
“下学上达”语出《论语·宪问第十四》“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朱子注曰:
不得于天不怨天,不合于人不尤人。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语意则见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之妙。盖在孔门,惟子贡之智几足以及此,故特语以发之,惜乎其犹有所未达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当如此。”又曰:“下学上达,意在言表。”又曰:“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②
朱子从文本内涵入手,认为“下学”工夫是“反己自修,循序渐进,无以甚异于人而致知也。”并未涉及“下学”所学的具体内容。因此,朱子保留程颐的观点来说明“下学”所学内容是人事。与下学相对的是“天理”,那么“天理”为何物?天理到底有没有存在?朱子晚年说:
圣人所谓上达,只是一举便都在此,非待下学后旋上达也。圣人便是天,人则不能如天。惟天无许多病败,故独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识能知,但圣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处独与之契合。①
此条为童伯羽庚戌所闻录(1190),朱子时年61岁,同年朱子在漳州首次刊刻《四书章句集注》②,朱子于《四书章句集注》中所言的天理正是指圣人所制作的规则,因此朱子把天理与人事合二而一,看作一个整体。能够实现天理与人事合二而一的人只有圣人,天理与人事之间的沟通的途径,正是圣人制作的规则,即礼。这是由朱子的礼学观念而获得的结论,《朱子语类》载有多处明文③,兹举一例如下:
问先生昔日礼是体,今乃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似非体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乡谈,才见分段,子便说道是用不是体,如说尺时无寸底是体。有寸底不是体便是用。如秤无星底是体,有星底不是体。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纸糊此便是体,人摇之便是用。”杨至之问体,曰:“合当底是体。”④
此文为甘节癸丑以后所闻录(1193)。上文虽是讨论体用关系,却始终没有离开“礼”来展开论述,而且礼处于“体”的位置,其实质性作用正是沟通天理与人事,因此,朱子所言的天理、人事实质上便是人遵循礼仪来开展活动。不论是下学还是上达,其实质都是以做事符合礼为中心。由此可见,编撰礼书为人的活动提供规则是其下学上达的治学思想的必然归宿。这可见于历史上有名的朱陆之辩。
朱陆之辩是学术史上的公案,《陆九渊年谱》借赵景昭之口总结朱子与陆九渊之间的差异: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人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①
鹅湖之会发生于宋孝宗淳熙二年乙未(1175),朱子时年46岁,陆九渊时年37岁②。虽然《陆九渊年谱》认为“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③,这件八百多年公案尚未定案,论著汗牛充栋。我们关注的只是赵景昭所概括内容,它是否符合朱子一贯的教学之法,还是误传之结果?兹证如下:
朱子教其弟子为学的顺序是从博学开始,根据人的年纪和自身精力的变化过程来安排学习进度,但是朱子教人读书之法并非要从博返约,而是依据年少者和年老者不同精力特征,读书方法应该有异。但是不论两者有何差异,朱子始终把读书落实到逐句逐字上作工夫,他说:
学者贪做工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读书须是子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理会未到,不知有疑尔。大抵为学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余,须用无书不读,无不究竟其义。若年齿向晚,却须择要用功,读一书便觉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会;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盖天下义理只有一个是与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着落,虽不再读,自然道理浃洽,省记不忘。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①
由此可见,朱子并非教人由博再返归约,而是要逐字逐句深究字义。但是居于朱子对年少者与年老者之间精力差异的认知,他要求年少者需“无书不读”的博学,而年老者须择要而读,两者的读书基础仍旧是要逐句逐字的精读,而非贪多务得,其内在精神是高度一致的。赵景昭误读了朱子,以至于朱陆之辩从一开始便是从误会开始。事实上,朱子教人读书的核心思想是要人精读,而其对应的方法便是熟读,《朱子语类·读书法上》甚至把熟读上升到读书的唯一方法,即“书只贵熟读,别无方法”②。这便再次证实了朱子并非要人先博而返约,而是要逐字逐句开始研读,日积月累达到透彻理解圣人之道。正是以求圣人之道为目标,朱子并非把学习典籍知识放在学习者所学内容的第一位,而是放在体悟自身内在道理的觉悟之后的。他几次三番地说到此问题,兹举一例如下:
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来。然圣人教人,须要读这书时,盖为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圣人说底,是他曾经历过来。③
此条为萧佐甲寅所闻(光宗绍熙五年即1194年)。读书是学子修身的第二义,而激发自己内在的人生道理才是第一义。人身修养不是外在的内容贯注于主体自身,而是由学子自身通过实践来辅助激发内在的人生道理。更重要的是朱子并非简单强调学者应该注重学习,而是要通过学习激发学子本已拥有的“道理”。这点与陆九渊的表述方式虽有差异,却都是强调以学者自身内在的道德为主体,并非如赵景昭所言的通过博观来返求实现,且朱子从始至终都否定赵景昭所言从博观到返求之间的内在学理。他说:
务反求者,以博观为外驰;务博观者,以内省为狭隘,堕于一偏。此皆学者之大病也。④
此条为杨道夫所载,朱子时年60岁了,上距鹅湖之会已经达十四年之久了,其学术思想已臻极致①。朱子在此断然否认了赵景昭所言的教人之法。虽然我们不能够准确推论出以上各言论的具体时间,但是鹅湖之会发生于淳熙二年乙未。“夏四月,东莱吕公伯恭来访,《近思录》成。偕东莱吕公至鹅湖。复斋陆子寿象山陆子静来会”②。由此可知,朱子此时虽有讲学活动,但更关注自身学术研究。此后,由于入仕,朱子的学术研究暂告一段落。细考《朱子语类》可知,《语类》所录朱子讲学的时间大约从1170年即乾道六年庚寅开始,但是所载此时段语录甚少③。虽有朱子声名未广的原因,亦有朱子学术思想尚处于不断精进的阶段,学术作品产量亦处于高峰阶段,并未广招生徒讲学所致。因此,前文朱子有关博约的观点显然是朱子自身观点的修正,不足以代表朱子在46岁时的真实想法。为此,我们不能够简单以赵景昭的观点为准,我们需要借助已经基本完成编年的《朱子文集》来深入研究朱子的学术观点进程,以免把朱子的学术思想当成一成不变的汇编,迷失于现象中。
正是以下学上达为治学的工夫,朱子在治学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以推究义理来源为目的,不断深入探索义理的经典文献基础,而《通解》的编撰目的正是为了落实礼义的“源”目标。
二、切问近思:朱子编撰《通解》的学术根源
下学上达是朱子编撰礼书的根本动力,那么如何贯彻下学上达工夫,经过朱子长期思考之后,最终形成以切问近思为实现“下学”工夫的思维方式。“切问近思”语出《论语·子张第十九》。其言曰: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何晏《集解》曰:“切问者,切问于己所学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也。况问所未学达,思所未达,则于所习者不精于所思者不解之。”①这个理念经由二程而进入朱子学术体系。《二程遗书》有多处记载,最具代表性的言论如下:
学只要鞭辟近里,著己而已。故“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②
朱子早年编撰《二程遗书》时,保留了很多有关切问近思的内容,但上引文献则是唯一被朱子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选录,我们虽难以断定这是朱子还是吕祖谦的意见,但是朱子亦赞同上引文献在二程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则毋庸置疑。而《近思录》在朱子治学方法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如陈淳所载:
《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③
又李闳祖载:
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④
陈淳是庚戌或者己未(1190或1199)所闻,朱子时年61岁或70岁,而李闳祖则是戊申以后所闻录(1188),即朱子时年59岁,两者均属朱子晚年的观点,更值得深入考察的是李闳祖的观点被《朱子语类》置于朱子讨论《近思录》相关语录内容的首条,显示了上引内容的重要性,又据《朱子语类》成书的过程,可知上文观点当属朱子学派的共识①,因此上引语录的观点当可代表朱子平生学术观点。与小学相对应的是大学,大学所学的应该是提炼小学所学修身之法的义理,而《近思录》则是详尽大学之道,可见《近思录》在朱子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切问近思的治学方法亦成为朱子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
虽然前文朱子有言《小学》具有“修身大法”的地位,但是在《朱子语类》中,朱子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作为小学之事或者修身的具体行为代名词。《朱子语类》载:
古人初学,只是教他“洒扫、应对、进退”而已,未便说到天理处。②
这亦是陈淳己未(1199)所闻③。初学即是小学阶段,洒扫应对便成为小学的代名词。为此,我们可以知道朱子对小学阶段极其重视,兹引如下:
“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今人既无本领,只去理会许多闲汩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④
此条语录完整呈现了朱子晚年对“小学”制度遗失的遗憾之情,而其原因是朱子对小学的功效期望甚高,即通过小学工夫可以达到“圣贤坯模”,且可以“养心”并能够“通达事物”。那么朱子对“小学教之以事”的具体内容包括哪一些呢?《朱子语类》载:
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①
此条为杨骧己酉、甲寅(1189或1194)所闻。朱子对小学所学之事有一个明确的见解,那就是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而大学所学的内容则是上述小学之事的内在之理。但是我们看到朱子所言小学制度永远和一个词相对,即“古者”,其言外之意是宋代教育已经失去了传统小学内容,由此造成了社会教育不再重视礼仪的具体内容的情形。朱子对上述情形进行深刻总结后,提出了以庄敬诚实为替代方法。他说:
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穷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但须庄敬诚实,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会道理。待此通透,意诚心正了,就切身处理会,旋旋去理会礼乐射御书数。今则无所用乎御。如礼乐射书数,也是合当理会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切身处理会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礼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己甚事。②
本条语录回顾了朱子讲学顺序先从抽象的大学之道开始讲起,教人立庄敬诚实之本,再通过致知格物来理会道理,达到正心诚意的修身效果,最后才是礼文制度。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朱子这样的教学次序实际上是出于无奈,因为在朱子时代,小学制度已经缺失了,难以从礼乐射御书数开始入手教育学生了,而只能从《大学》出发立庄敬诚实之本。
正是在小学制度已经崩溃的时代,朱子强调学者要从涵养庄敬之心着手开始修养进程,而涵养庄敬之心的根本是在行礼过程中,其思想根源正是上文所言切问近思的治学方式。朱子说:
“切问近思”,本只是讲学,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则仁在其中。此皆是教人只从这一路做去,且莫管那一边。然做得这一边,则那一边自在其中也。①
这是吕焘己未(1199)所闻录,他在文中注释“做得精则仁在其中”说:“如‘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皆是切己去做,方是求仁底事。”此处点明了朱子求仁的条件是“切己”。叶采在注《近思录》时对切问近思有精到的注解:“鞭辟入里著己者,切己之谓也。切问近思而不泛远则心德存矣。”②并指出其在学者修身中的地位:
切问近思者,致知之事也;言忠信笃敬者,力行之事也。说并见《论语》。③
切问近思固然是致知之事,但是忠信笃敬本身并不是力行之事,而是力行之事背后之理。但这并不影响切问近思对朱子学术思想的贡献,因为强调切问近思,朱子才发现小学的重要性,也正是小学工夫到了,才能够实现忠信笃敬。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切问近思的致知方式经由二程而进入朱子的思想体系。与此同时,朱子本人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小学的重要性,痛心小学制度的遗失,由此使用涵养庄敬之心的方法来弥补小学制度缺失后的弊端。但是涵养庄敬之心是义理范畴,仍旧缺少小学的功效。对此问题,朱子有着清醒的认识。《朱子语类》载:
问:“先生旧解以三者为‘修身之验,为政之本,非其平日庄敬诚实存省之功积之有素,则不能也’。专是做效验说。如此,则‘动’‘正’‘出’三字只是闲字。后来改本以‘验’为‘要’,‘非其’以下改为‘学者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顷刻之违者也’。如此,则工夫却在‘动’‘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说而不可以效验言矣。某疑‘动’‘正’‘出’三字,不可以为做工夫字。尚可说‘动’字、‘出’字岂可以为工夫耶?”曰:“这三字虽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处。正如着衣吃饭,其着其吃,虽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处。此意所争,只是丝发之间,要人自认得。旧来解以为效验,语似有病,故改从今说。盖若专以为平日庄敬持养方能如此,则不成未庄敬持养底人,便不要‘远暴慢’‘近信’‘远鄙倍’!便是旧说‘效验’字太深,有病。”①
此段为沈僩戊午(1198)以后所闻,虽非专门讲庄敬诚实之事,但是我们从此处看到庄敬诚实和做工夫两者之间的关系。朱子本人在教学过程中引用“庄敬持养”之法进入教育实践,实属是一个不得已的替代方法。正是从义理入手进行教育本身存在着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难以完全实现其内在实效。
正因“庄敬持养”替代小学工夫难以真正达到小学的实效,使得朱子在切问近思的治学方法的指导之下,重新寻找实现小学工夫之效的方法,而《通解》以整理古代礼仪为主体内容,礼仪与礼义并举的编撰方法,转变了单纯注重义理的学术偏好,正是朱子切问近思治学方法在礼仪方面的实际运用成果。
三、纠偏与发展:《仪礼经传通解》编撰的直接原因
前文已言下学上达与切问近思的研究方式是朱子编撰《通解》的内在动力和学术根源,但是学术思想落实到具体行为仍需要有历史因素的推波助澜。朱子编撰《通解》一书的行动便是朱子在学术思想基础上受历史环境影响而产生纠偏历史思潮的具体结果。
《通解》的编撰是处于王安石科举改革后的时代,正如朱子所言:
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②
朱子在讲学时亦念念不忘责备王安石废除《仪礼》之学,他说:“‘《礼》非全书,而《礼记》尤杂。今合取《仪礼》为正,然后取《礼记》诸书之说,以类相从,更取诸儒剖击之说各附其下,庶便搜阅。’又曰:‘前此《三礼》同为一经,故有《三礼》学究。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③诚然朱子所言的废《仪礼》而独存《礼记》的科举制度为《仪礼》被遗忘的重要原因,但是把《仪礼》传播不广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科举政策则有失公平,因为王安石执政期间不过从熙宁元年到熙宁九年,而司马光执政时期更是全部废除王安石执政期间的政治措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司马光执政的元祐四年的选举制度与王安石期间已经有了明显差异,但是《仪礼》依旧流传不广。《宋史·选举志》载:
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穀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穀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①
此文献所载内容发生的时间为元祐四年,宋神宗、王安石均已经离世,而此次科举考试正是在司马光全面主持朝局的情况下实行的政策,《仪礼》在诸经当中处于中经的地位,仍旧比《礼记》低一等。与熙宁时期完全相反的各项政策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有更多的科举政策,如:“(元祐)六年,诏复通礼科。初,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尝罢,至是始复。”②而这在宋哲宗亲政之后的绍圣四年,其举措不但没有废除礼学在经学中的地位,反而加强其经学地位,并于科举中大力扶持,《宋史·选举志一》载:
四年,诏礼部,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藉,遇试,颁付考官,以防复出。罢《春秋》科,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期半及他经。继而复立《春秋》博士,崇宁罢之。③
这是哲宗在绍圣四年所进行的选举改革,我们于此“二《礼》”,实难确证其为哪二《礼》,但是据宋哲宗亲政后以恢复神宗时期的政策为主基调而言,此“二《礼》”当指宋神宗时期保留的《周礼》与《礼记》二经。至于历史真实情况,因材料不足,暂时付之阙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还是以继承宋神宗改革意志的宋哲宗,他们都十分重视礼学,尤其是宋哲宗更是把礼经的科举录取名额占到总的录取名额的一半之多。虽然统治者大力提倡礼学,但事与愿违,无论是《礼记》《周礼》、通礼科均与《仪礼》一样被置于冷门的经学地位,朱子曾直言此种情况:
祖宗时有开宝通礼科,学究试默义,须是念得礼熟,是得礼官用此等人为之。介甫一切罢去,尽令做大义。故今之礼官,不问是甚人皆可做。某尝谓,朝廷须留此等专科,如史科亦尝有。①
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认为此处是朱子专门针对王安石废罢《仪礼》后对南宋礼学产生的重要影响②,明显为《朱子语类》所惑。前文已言,在宋神宗、王安石均已过世之后,司马光在元祐四年恢复了《仪礼》的经学地位,而《宋史》明言元祐六年恢复被王安石废罢的通礼一科。由此可见,朱子把宋代的礼学思潮发展方向归咎为王安石一人,明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朱子对礼学的学术思潮的概括则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即当时学术思潮是“尽令做大义”,而礼学人才凋零的情况甚至达到主管礼仪官员都对礼学十分陌生,更不用说其他普通的士人了。
虽然朱子极力把礼学的衰落归因于王安石,但是重视义理之学的社会思潮已经形成洪流,其本人也难以避免。我们以《朱子年谱》为检索对象,发现朱子本人的礼学作品只有早年的《祭仪》《家礼》,直到晚年庆元党禁时期才带领众多弟子着手编撰《通解》。其在礼学上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与其在四书学所作的工作,不可同日而语③。检索《朱子语类》中涉及四书学的内容与礼学内容的卷数与篇幅便可证实上述内容了①。如果以上还只是旁证,那么朱子生平对礼学的熟悉程度则可以直接证实朱子在礼学方面所花时间与精力的有限程度了。
绍熙五年(1194)秋,光宗内禅,宁宗即位,召朱熹赴行在。冬十月,朱熹奏乞讨论嫡孙承重之服。朱熹《乞讨论丧服劄子》一文有明确的阐述,但缺少明确的经文依据,朱熹此次上书以失败告终,后来在郑玄注找到文献依据。“这件事使朱熹深受震动,义理要想说服人,在国家礼制层面上的讨论还必须寻找经典依据”②。虽然三礼之学规模庞大,且朱子时代三礼的注、疏本尚未合刊,对朱子研读三礼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但正如前文所言,朱子治学是下学上达、切问近思的途径,其没有透彻研究礼学经典注疏,直接证实了朱子在礼学文献方面所花时间与精力不足的问题。假如朱子在研读礼学文献方面所花时间和精力足够多,当不会出现礼学文献不熟的问题。不论是朱子所花时间、精力还是注重礼学的义理的研讨,都显示了朱子对礼学文献的疏忽的情况。这绝非我们对朱子学术的吹毛求疵,因为朱子在平时讲学中不只一次强调学古礼,当求其内在的义理,并加以合符实际的应用。《朱子语类》载:
杨通老问《礼书》。曰:“看礼书见古人极有精密处,事无微细,各各有义理。然又须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见得度数文为之末,如此岂能识得深意?如将一碗干硬底饭来吃,有甚滋味?若白地将自家所见揣摸他本来意思不如此,也不济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会这个,下稍溺於器数,一齐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尽晓其意,且要识得大纲。”③
此条为叶贺孙辛亥(1191)以后所闻。除此之外,叶贺孙于同卷中尚录有多条相似内容的语录,当为可信。朱子在此主要强调学者要从礼书中看出古人的意思,而不是“度数文为之末”,换言之,朱子追求的是理解礼书的内在礼义,而非限于礼仪方面,更非“溺于器数”,事实上,朱子与宋代其他注重《礼记》的学者并没有根本区别,都是注重其内在学理。仅是朱子治学方法比其他宋儒更为严谨的强调学习者需要在学习礼书内在义理过程中,把握具体礼仪“大纲”,至于何为大纲则由行礼者根据自身工夫而定夺,可见朱子偏向于礼学的义理方面,则可确定了。至于具体礼仪内容,朱子则持可以损减的观点。《朱子语类》载:
今所集《礼书》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后人自去减杀,求其可行者而已。①
朱子所举例子为衣服观履不必如古,但是何者为大纲,何者为细节,而对礼学内容的减杀的标准为什么?朱子都未曾系统论述,亦与当时重视《礼记》的学者无本质的差别。
朱子生平著作等身,难以面面俱到,亦属正常。但是在四书学中,我们难以看到上述如此大的失误,亦显示出朱子对四书学重视程度远非礼学可比。甚至到了晚年,朱子对礼学典籍的整理难度或者重视程度仍旧缺少清晰的认识。他说:
古人自幼入小学,便教以礼;及长,自然在规矩之中。横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礼,也易学。今人乍见,往往以为难。某尝要取《三礼》编成一书,事多蹉过。若有朋友,只两年工夫可成。②
此条为邵浩丙午(1186)所闻录。朱子此时尚未充分认识礼书修撰的难度,这便导致《通解》一书最终只能以未完稿而嘱托于后学,其原因虽有多种,但是最为重要的当属朱子本人的学术兴趣更倾向于注重义理之学。
通过以上的略显烦琐的考论证实了:从北宋开始,学者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义理的研究方面,朱子亦是随时代大潮而发展。但是正是前文所言朱子本人的治学的方法论特质,才逐步把朱子的学术关注点引入到《通解》的编撰方面。朱子是宋学的典型代表,具有宋学的各种特征,但是其在深入学习宋学的基础上,通过归因于王安石罢废《仪礼》之学及自身的深刻反思纠正了宋代学者注重《礼记》之学,而罢废《仪礼》学的学术思潮,重新重视《仪礼》学,并以《仪礼》为主体内容,采编源自各种典籍的礼学资料,补充《仪礼》所缺之资料,重新构建礼仪与礼义并重的礼学资料体系,虽有逆时代学术思潮而动且有未完成编撰工作之遗憾,但是纠正宋学的弊端,发展宋学的优秀成果的目的却呈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推动《通解》的编撰工作克服各种不利因素而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通解》是朱子在下学上达、切问近思的学术思想指导下,逐渐克服宋学空疏的弊端,实现由宋代理学走向传统经学之路,并在纠正宋代礼学弊端,发展宋代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编撰《通解》,开创了后世编撰礼书的新典范。
朱熹《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经传相分又相合的思想,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而与其理学思想有所出入。就其经学的逻辑言,是以《仪礼》为经,为本,为事,以《礼记》为传,为末,为理,经传的本末、事理之分,是其经学的内在逻辑。而就朱熹理学的逻辑而言,其理本论哲学不允许把理置于末和从属于事的位置,理作为宇宙的本体,是包括礼在内的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故就其理本论讲,理不依赖事物而存在,由此与其经学《礼记》之理安顿在《仪礼》之事的思想有所出入。①
蔡方鹿先生注意到了朱子经学与理学体系之间的差异,即经为本与理为本之间的矛盾关系,但未深入考察朱子礼学与理学之间的学术关系,而这却是朱子晚年编礼书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将从朱子的思想体系入手来讨论《通解》编撰的学术原因。
一、下学上达:由义理回归文本的内在动力
“下学上达”语出《论语·宪问第十四》“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朱子注曰:
不得于天不怨天,不合于人不尤人。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语意则见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之妙。盖在孔门,惟子贡之智几足以及此,故特语以发之,惜乎其犹有所未达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当如此。”又曰:“下学上达,意在言表。”又曰:“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②
朱子从文本内涵入手,认为“下学”工夫是“反己自修,循序渐进,无以甚异于人而致知也。”并未涉及“下学”所学的具体内容。因此,朱子保留程颐的观点来说明“下学”所学内容是人事。与下学相对的是“天理”,那么“天理”为何物?天理到底有没有存在?朱子晚年说:
圣人所谓上达,只是一举便都在此,非待下学后旋上达也。圣人便是天,人则不能如天。惟天无许多病败,故独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识能知,但圣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处独与之契合。①
此条为童伯羽庚戌所闻录(1190),朱子时年61岁,同年朱子在漳州首次刊刻《四书章句集注》②,朱子于《四书章句集注》中所言的天理正是指圣人所制作的规则,因此朱子把天理与人事合二而一,看作一个整体。能够实现天理与人事合二而一的人只有圣人,天理与人事之间的沟通的途径,正是圣人制作的规则,即礼。这是由朱子的礼学观念而获得的结论,《朱子语类》载有多处明文③,兹举一例如下:
问先生昔日礼是体,今乃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似非体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乡谈,才见分段,子便说道是用不是体,如说尺时无寸底是体。有寸底不是体便是用。如秤无星底是体,有星底不是体。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纸糊此便是体,人摇之便是用。”杨至之问体,曰:“合当底是体。”④
此文为甘节癸丑以后所闻录(1193)。上文虽是讨论体用关系,却始终没有离开“礼”来展开论述,而且礼处于“体”的位置,其实质性作用正是沟通天理与人事,因此,朱子所言的天理、人事实质上便是人遵循礼仪来开展活动。不论是下学还是上达,其实质都是以做事符合礼为中心。由此可见,编撰礼书为人的活动提供规则是其下学上达的治学思想的必然归宿。这可见于历史上有名的朱陆之辩。
朱陆之辩是学术史上的公案,《陆九渊年谱》借赵景昭之口总结朱子与陆九渊之间的差异: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人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①
鹅湖之会发生于宋孝宗淳熙二年乙未(1175),朱子时年46岁,陆九渊时年37岁②。虽然《陆九渊年谱》认为“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③,这件八百多年公案尚未定案,论著汗牛充栋。我们关注的只是赵景昭所概括内容,它是否符合朱子一贯的教学之法,还是误传之结果?兹证如下:
朱子教其弟子为学的顺序是从博学开始,根据人的年纪和自身精力的变化过程来安排学习进度,但是朱子教人读书之法并非要从博返约,而是依据年少者和年老者不同精力特征,读书方法应该有异。但是不论两者有何差异,朱子始终把读书落实到逐句逐字上作工夫,他说:
学者贪做工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读书须是子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理会未到,不知有疑尔。大抵为学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余,须用无书不读,无不究竟其义。若年齿向晚,却须择要用功,读一书便觉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会;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盖天下义理只有一个是与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着落,虽不再读,自然道理浃洽,省记不忘。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①
由此可见,朱子并非教人由博再返归约,而是要逐字逐句深究字义。但是居于朱子对年少者与年老者之间精力差异的认知,他要求年少者需“无书不读”的博学,而年老者须择要而读,两者的读书基础仍旧是要逐句逐字的精读,而非贪多务得,其内在精神是高度一致的。赵景昭误读了朱子,以至于朱陆之辩从一开始便是从误会开始。事实上,朱子教人读书的核心思想是要人精读,而其对应的方法便是熟读,《朱子语类·读书法上》甚至把熟读上升到读书的唯一方法,即“书只贵熟读,别无方法”②。这便再次证实了朱子并非要人先博而返约,而是要逐字逐句开始研读,日积月累达到透彻理解圣人之道。正是以求圣人之道为目标,朱子并非把学习典籍知识放在学习者所学内容的第一位,而是放在体悟自身内在道理的觉悟之后的。他几次三番地说到此问题,兹举一例如下:
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来。然圣人教人,须要读这书时,盖为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圣人说底,是他曾经历过来。③
此条为萧佐甲寅所闻(光宗绍熙五年即1194年)。读书是学子修身的第二义,而激发自己内在的人生道理才是第一义。人身修养不是外在的内容贯注于主体自身,而是由学子自身通过实践来辅助激发内在的人生道理。更重要的是朱子并非简单强调学者应该注重学习,而是要通过学习激发学子本已拥有的“道理”。这点与陆九渊的表述方式虽有差异,却都是强调以学者自身内在的道德为主体,并非如赵景昭所言的通过博观来返求实现,且朱子从始至终都否定赵景昭所言从博观到返求之间的内在学理。他说:
务反求者,以博观为外驰;务博观者,以内省为狭隘,堕于一偏。此皆学者之大病也。④
此条为杨道夫所载,朱子时年60岁了,上距鹅湖之会已经达十四年之久了,其学术思想已臻极致①。朱子在此断然否认了赵景昭所言的教人之法。虽然我们不能够准确推论出以上各言论的具体时间,但是鹅湖之会发生于淳熙二年乙未。“夏四月,东莱吕公伯恭来访,《近思录》成。偕东莱吕公至鹅湖。复斋陆子寿象山陆子静来会”②。由此可知,朱子此时虽有讲学活动,但更关注自身学术研究。此后,由于入仕,朱子的学术研究暂告一段落。细考《朱子语类》可知,《语类》所录朱子讲学的时间大约从1170年即乾道六年庚寅开始,但是所载此时段语录甚少③。虽有朱子声名未广的原因,亦有朱子学术思想尚处于不断精进的阶段,学术作品产量亦处于高峰阶段,并未广招生徒讲学所致。因此,前文朱子有关博约的观点显然是朱子自身观点的修正,不足以代表朱子在46岁时的真实想法。为此,我们不能够简单以赵景昭的观点为准,我们需要借助已经基本完成编年的《朱子文集》来深入研究朱子的学术观点进程,以免把朱子的学术思想当成一成不变的汇编,迷失于现象中。
正是以下学上达为治学的工夫,朱子在治学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以推究义理来源为目的,不断深入探索义理的经典文献基础,而《通解》的编撰目的正是为了落实礼义的“源”目标。
二、切问近思:朱子编撰《通解》的学术根源
下学上达是朱子编撰礼书的根本动力,那么如何贯彻下学上达工夫,经过朱子长期思考之后,最终形成以切问近思为实现“下学”工夫的思维方式。“切问近思”语出《论语·子张第十九》。其言曰: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何晏《集解》曰:“切问者,切问于己所学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也。况问所未学达,思所未达,则于所习者不精于所思者不解之。”①这个理念经由二程而进入朱子学术体系。《二程遗书》有多处记载,最具代表性的言论如下:
学只要鞭辟近里,著己而已。故“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②
朱子早年编撰《二程遗书》时,保留了很多有关切问近思的内容,但上引文献则是唯一被朱子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选录,我们虽难以断定这是朱子还是吕祖谦的意见,但是朱子亦赞同上引文献在二程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则毋庸置疑。而《近思录》在朱子治学方法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如陈淳所载:
《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③
又李闳祖载:
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④
陈淳是庚戌或者己未(1190或1199)所闻,朱子时年61岁或70岁,而李闳祖则是戊申以后所闻录(1188),即朱子时年59岁,两者均属朱子晚年的观点,更值得深入考察的是李闳祖的观点被《朱子语类》置于朱子讨论《近思录》相关语录内容的首条,显示了上引内容的重要性,又据《朱子语类》成书的过程,可知上文观点当属朱子学派的共识①,因此上引语录的观点当可代表朱子平生学术观点。与小学相对应的是大学,大学所学的应该是提炼小学所学修身之法的义理,而《近思录》则是详尽大学之道,可见《近思录》在朱子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切问近思的治学方法亦成为朱子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
虽然前文朱子有言《小学》具有“修身大法”的地位,但是在《朱子语类》中,朱子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作为小学之事或者修身的具体行为代名词。《朱子语类》载:
古人初学,只是教他“洒扫、应对、进退”而已,未便说到天理处。②
这亦是陈淳己未(1199)所闻③。初学即是小学阶段,洒扫应对便成为小学的代名词。为此,我们可以知道朱子对小学阶段极其重视,兹引如下:
“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今人既无本领,只去理会许多闲汩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④
此条语录完整呈现了朱子晚年对“小学”制度遗失的遗憾之情,而其原因是朱子对小学的功效期望甚高,即通过小学工夫可以达到“圣贤坯模”,且可以“养心”并能够“通达事物”。那么朱子对“小学教之以事”的具体内容包括哪一些呢?《朱子语类》载:
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①
此条为杨骧己酉、甲寅(1189或1194)所闻。朱子对小学所学之事有一个明确的见解,那就是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而大学所学的内容则是上述小学之事的内在之理。但是我们看到朱子所言小学制度永远和一个词相对,即“古者”,其言外之意是宋代教育已经失去了传统小学内容,由此造成了社会教育不再重视礼仪的具体内容的情形。朱子对上述情形进行深刻总结后,提出了以庄敬诚实为替代方法。他说:
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穷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但须庄敬诚实,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会道理。待此通透,意诚心正了,就切身处理会,旋旋去理会礼乐射御书数。今则无所用乎御。如礼乐射书数,也是合当理会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切身处理会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礼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己甚事。②
本条语录回顾了朱子讲学顺序先从抽象的大学之道开始讲起,教人立庄敬诚实之本,再通过致知格物来理会道理,达到正心诚意的修身效果,最后才是礼文制度。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朱子这样的教学次序实际上是出于无奈,因为在朱子时代,小学制度已经缺失了,难以从礼乐射御书数开始入手教育学生了,而只能从《大学》出发立庄敬诚实之本。
正是在小学制度已经崩溃的时代,朱子强调学者要从涵养庄敬之心着手开始修养进程,而涵养庄敬之心的根本是在行礼过程中,其思想根源正是上文所言切问近思的治学方式。朱子说:
“切问近思”,本只是讲学,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则仁在其中。此皆是教人只从这一路做去,且莫管那一边。然做得这一边,则那一边自在其中也。①
这是吕焘己未(1199)所闻录,他在文中注释“做得精则仁在其中”说:“如‘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皆是切己去做,方是求仁底事。”此处点明了朱子求仁的条件是“切己”。叶采在注《近思录》时对切问近思有精到的注解:“鞭辟入里著己者,切己之谓也。切问近思而不泛远则心德存矣。”②并指出其在学者修身中的地位:
切问近思者,致知之事也;言忠信笃敬者,力行之事也。说并见《论语》。③
切问近思固然是致知之事,但是忠信笃敬本身并不是力行之事,而是力行之事背后之理。但这并不影响切问近思对朱子学术思想的贡献,因为强调切问近思,朱子才发现小学的重要性,也正是小学工夫到了,才能够实现忠信笃敬。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切问近思的致知方式经由二程而进入朱子的思想体系。与此同时,朱子本人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小学的重要性,痛心小学制度的遗失,由此使用涵养庄敬之心的方法来弥补小学制度缺失后的弊端。但是涵养庄敬之心是义理范畴,仍旧缺少小学的功效。对此问题,朱子有着清醒的认识。《朱子语类》载:
问:“先生旧解以三者为‘修身之验,为政之本,非其平日庄敬诚实存省之功积之有素,则不能也’。专是做效验说。如此,则‘动’‘正’‘出’三字只是闲字。后来改本以‘验’为‘要’,‘非其’以下改为‘学者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顷刻之违者也’。如此,则工夫却在‘动’‘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说而不可以效验言矣。某疑‘动’‘正’‘出’三字,不可以为做工夫字。尚可说‘动’字、‘出’字岂可以为工夫耶?”曰:“这三字虽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处。正如着衣吃饭,其着其吃,虽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处。此意所争,只是丝发之间,要人自认得。旧来解以为效验,语似有病,故改从今说。盖若专以为平日庄敬持养方能如此,则不成未庄敬持养底人,便不要‘远暴慢’‘近信’‘远鄙倍’!便是旧说‘效验’字太深,有病。”①
此段为沈僩戊午(1198)以后所闻,虽非专门讲庄敬诚实之事,但是我们从此处看到庄敬诚实和做工夫两者之间的关系。朱子本人在教学过程中引用“庄敬持养”之法进入教育实践,实属是一个不得已的替代方法。正是从义理入手进行教育本身存在着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难以完全实现其内在实效。
正因“庄敬持养”替代小学工夫难以真正达到小学的实效,使得朱子在切问近思的治学方法的指导之下,重新寻找实现小学工夫之效的方法,而《通解》以整理古代礼仪为主体内容,礼仪与礼义并举的编撰方法,转变了单纯注重义理的学术偏好,正是朱子切问近思治学方法在礼仪方面的实际运用成果。
三、纠偏与发展:《仪礼经传通解》编撰的直接原因
前文已言下学上达与切问近思的研究方式是朱子编撰《通解》的内在动力和学术根源,但是学术思想落实到具体行为仍需要有历史因素的推波助澜。朱子编撰《通解》一书的行动便是朱子在学术思想基础上受历史环境影响而产生纠偏历史思潮的具体结果。
《通解》的编撰是处于王安石科举改革后的时代,正如朱子所言:
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②
朱子在讲学时亦念念不忘责备王安石废除《仪礼》之学,他说:“‘《礼》非全书,而《礼记》尤杂。今合取《仪礼》为正,然后取《礼记》诸书之说,以类相从,更取诸儒剖击之说各附其下,庶便搜阅。’又曰:‘前此《三礼》同为一经,故有《三礼》学究。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③诚然朱子所言的废《仪礼》而独存《礼记》的科举制度为《仪礼》被遗忘的重要原因,但是把《仪礼》传播不广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科举政策则有失公平,因为王安石执政期间不过从熙宁元年到熙宁九年,而司马光执政时期更是全部废除王安石执政期间的政治措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司马光执政的元祐四年的选举制度与王安石期间已经有了明显差异,但是《仪礼》依旧流传不广。《宋史·选举志》载:
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穀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穀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①
此文献所载内容发生的时间为元祐四年,宋神宗、王安石均已经离世,而此次科举考试正是在司马光全面主持朝局的情况下实行的政策,《仪礼》在诸经当中处于中经的地位,仍旧比《礼记》低一等。与熙宁时期完全相反的各项政策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有更多的科举政策,如:“(元祐)六年,诏复通礼科。初,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尝罢,至是始复。”②而这在宋哲宗亲政之后的绍圣四年,其举措不但没有废除礼学在经学中的地位,反而加强其经学地位,并于科举中大力扶持,《宋史·选举志一》载:
四年,诏礼部,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藉,遇试,颁付考官,以防复出。罢《春秋》科,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期半及他经。继而复立《春秋》博士,崇宁罢之。③
这是哲宗在绍圣四年所进行的选举改革,我们于此“二《礼》”,实难确证其为哪二《礼》,但是据宋哲宗亲政后以恢复神宗时期的政策为主基调而言,此“二《礼》”当指宋神宗时期保留的《周礼》与《礼记》二经。至于历史真实情况,因材料不足,暂时付之阙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还是以继承宋神宗改革意志的宋哲宗,他们都十分重视礼学,尤其是宋哲宗更是把礼经的科举录取名额占到总的录取名额的一半之多。虽然统治者大力提倡礼学,但事与愿违,无论是《礼记》《周礼》、通礼科均与《仪礼》一样被置于冷门的经学地位,朱子曾直言此种情况:
祖宗时有开宝通礼科,学究试默义,须是念得礼熟,是得礼官用此等人为之。介甫一切罢去,尽令做大义。故今之礼官,不问是甚人皆可做。某尝谓,朝廷须留此等专科,如史科亦尝有。①
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认为此处是朱子专门针对王安石废罢《仪礼》后对南宋礼学产生的重要影响②,明显为《朱子语类》所惑。前文已言,在宋神宗、王安石均已过世之后,司马光在元祐四年恢复了《仪礼》的经学地位,而《宋史》明言元祐六年恢复被王安石废罢的通礼一科。由此可见,朱子把宋代的礼学思潮发展方向归咎为王安石一人,明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朱子对礼学的学术思潮的概括则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即当时学术思潮是“尽令做大义”,而礼学人才凋零的情况甚至达到主管礼仪官员都对礼学十分陌生,更不用说其他普通的士人了。
虽然朱子极力把礼学的衰落归因于王安石,但是重视义理之学的社会思潮已经形成洪流,其本人也难以避免。我们以《朱子年谱》为检索对象,发现朱子本人的礼学作品只有早年的《祭仪》《家礼》,直到晚年庆元党禁时期才带领众多弟子着手编撰《通解》。其在礼学上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与其在四书学所作的工作,不可同日而语③。检索《朱子语类》中涉及四书学的内容与礼学内容的卷数与篇幅便可证实上述内容了①。如果以上还只是旁证,那么朱子生平对礼学的熟悉程度则可以直接证实朱子在礼学方面所花时间与精力的有限程度了。
绍熙五年(1194)秋,光宗内禅,宁宗即位,召朱熹赴行在。冬十月,朱熹奏乞讨论嫡孙承重之服。朱熹《乞讨论丧服劄子》一文有明确的阐述,但缺少明确的经文依据,朱熹此次上书以失败告终,后来在郑玄注找到文献依据。“这件事使朱熹深受震动,义理要想说服人,在国家礼制层面上的讨论还必须寻找经典依据”②。虽然三礼之学规模庞大,且朱子时代三礼的注、疏本尚未合刊,对朱子研读三礼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但正如前文所言,朱子治学是下学上达、切问近思的途径,其没有透彻研究礼学经典注疏,直接证实了朱子在礼学文献方面所花时间与精力不足的问题。假如朱子在研读礼学文献方面所花时间和精力足够多,当不会出现礼学文献不熟的问题。不论是朱子所花时间、精力还是注重礼学的义理的研讨,都显示了朱子对礼学文献的疏忽的情况。这绝非我们对朱子学术的吹毛求疵,因为朱子在平时讲学中不只一次强调学古礼,当求其内在的义理,并加以合符实际的应用。《朱子语类》载:
杨通老问《礼书》。曰:“看礼书见古人极有精密处,事无微细,各各有义理。然又须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见得度数文为之末,如此岂能识得深意?如将一碗干硬底饭来吃,有甚滋味?若白地将自家所见揣摸他本来意思不如此,也不济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会这个,下稍溺於器数,一齐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尽晓其意,且要识得大纲。”③
此条为叶贺孙辛亥(1191)以后所闻。除此之外,叶贺孙于同卷中尚录有多条相似内容的语录,当为可信。朱子在此主要强调学者要从礼书中看出古人的意思,而不是“度数文为之末”,换言之,朱子追求的是理解礼书的内在礼义,而非限于礼仪方面,更非“溺于器数”,事实上,朱子与宋代其他注重《礼记》的学者并没有根本区别,都是注重其内在学理。仅是朱子治学方法比其他宋儒更为严谨的强调学习者需要在学习礼书内在义理过程中,把握具体礼仪“大纲”,至于何为大纲则由行礼者根据自身工夫而定夺,可见朱子偏向于礼学的义理方面,则可确定了。至于具体礼仪内容,朱子则持可以损减的观点。《朱子语类》载:
今所集《礼书》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后人自去减杀,求其可行者而已。①
朱子所举例子为衣服观履不必如古,但是何者为大纲,何者为细节,而对礼学内容的减杀的标准为什么?朱子都未曾系统论述,亦与当时重视《礼记》的学者无本质的差别。
朱子生平著作等身,难以面面俱到,亦属正常。但是在四书学中,我们难以看到上述如此大的失误,亦显示出朱子对四书学重视程度远非礼学可比。甚至到了晚年,朱子对礼学典籍的整理难度或者重视程度仍旧缺少清晰的认识。他说:
古人自幼入小学,便教以礼;及长,自然在规矩之中。横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礼,也易学。今人乍见,往往以为难。某尝要取《三礼》编成一书,事多蹉过。若有朋友,只两年工夫可成。②
此条为邵浩丙午(1186)所闻录。朱子此时尚未充分认识礼书修撰的难度,这便导致《通解》一书最终只能以未完稿而嘱托于后学,其原因虽有多种,但是最为重要的当属朱子本人的学术兴趣更倾向于注重义理之学。
通过以上的略显烦琐的考论证实了:从北宋开始,学者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义理的研究方面,朱子亦是随时代大潮而发展。但是正是前文所言朱子本人的治学的方法论特质,才逐步把朱子的学术关注点引入到《通解》的编撰方面。朱子是宋学的典型代表,具有宋学的各种特征,但是其在深入学习宋学的基础上,通过归因于王安石罢废《仪礼》之学及自身的深刻反思纠正了宋代学者注重《礼记》之学,而罢废《仪礼》学的学术思潮,重新重视《仪礼》学,并以《仪礼》为主体内容,采编源自各种典籍的礼学资料,补充《仪礼》所缺之资料,重新构建礼仪与礼义并重的礼学资料体系,虽有逆时代学术思潮而动且有未完成编撰工作之遗憾,但是纠正宋学的弊端,发展宋学的优秀成果的目的却呈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推动《通解》的编撰工作克服各种不利因素而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通解》是朱子在下学上达、切问近思的学术思想指导下,逐渐克服宋学空疏的弊端,实现由宋代理学走向传统经学之路,并在纠正宋代礼学弊端,发展宋代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编撰《通解》,开创了后世编撰礼书的新典范。
附注
*作者简介:王志阳,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朱子学、福建地方文献研究。
本文是2017年武夷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仪礼经传通解》与朱子学派礼学思想衍变过程及其影响研究”(YJ201707)阶段性成果。
①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92—100页。
②潘斌:《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缘由和学术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①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页。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5页。
②据王懋竑《朱子年谱》:“(光宗绍熙元年庚戌,六十一岁)刻《四经》《四子书》于郡。”《朱子文集》收录了《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一文落款为:“绍熙改元腊月庚寅新安朱熹书于临漳郡斋。”参见王懋竑撰,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9页。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6页。
③《朱子语类》卷二十五、卷三十六、卷四十一、卷四十二均讨论到礼为“天理之节文”。参见《朱子语类》,第880页、第1340页、第1452页、第1494页。
④《朱子语类》,第239—240页。
①陆九渊:《象山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②王懋竑《朱子年谱》也引用了《象山集》中的《附象山年谱》的此处文辞。为此,此处公历时间据中华书局点校本王懋竑《朱子年谱》所用时间。参见《朱熹年谱》,第67—89页,《象山集》卷三十六。
③《象山集》卷三十六。
①《朱子语类》,第323页。
②《朱子语类》,第323—324页。
③《朱子语类》,第313页、第313页、第313—314页。
④《朱子语类》,第312页。
①据《朱子语录姓氏》所载,杨道夫,字仲思,建宁人,己酉以后所闻。己酉为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朱子时年六十岁。参见《朱子语录姓氏》,《朱子语类》,第4347页。《朱熹年谱》,第197页。
②《朱熹年谱》,第67页、第69页。
③依据《朱子语录姓氏》中明确的记录时间,最早的语录时间是杨方庚寅所闻(1170),朱子时年41,但是王懋竑《朱子年谱》(绍兴)二十三年癸酉条引《行状》云:“职兼学事……年方逾冠,闻其风者,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则朱子的讲学时间当是早在同安主簿任上已经开始讲学,则《朱子语录姓氏》所载何镐乙未以前所闻,则其最早时间则可能早至1153年,因资料不足,难以确考。故我们取杨方庚寅所闻为最早。参见《朱子语录姓氏》,《朱子语类》,第4346—4352页。《朱熹年谱》,第10页。
①何晏:《论语注疏》卷十,四部丛刊影日本正平本。
②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朱子语类》,第3450页。
④《朱子语类》,第3449页。
①《朱子语类》附录二收录了清光绪庚辰十二月贺瑞麟《重刻朱子语类序》及黄干《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李性传《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蔡杭《饶州刊朱子语后录后序》、吴坚《建安刊朱子语别录后序》、黄士毅《朱子语类后序》、魏了翁《眉州刊朱子语类序》、蔡杭《徽州刊朱子语类后序》、王佖《徽州刊朱子语续类后序》,由这些序言可知黎靖德《朱子语类》的收集整理过程。参见《朱子语类》,第4355—4383页。
②《朱子语类》,第1665页。
③据《朱子语录姓氏》可知,陈淳所载语录的时间有两段:一是庚戌年(1190),一是己未年(1199)。而叶贺孙所载语录为辛亥以后所闻(1191),两者叠加的时间段是己未年(1199),由此可知,陈淳此条所闻录的时间为己未年(1199)。参见《朱子语录姓氏》,《朱子语类》,第4348页;《朱子语类》,第1665页。
④《朱子语类》,第296页。
①《朱子语类》,第268页。
②《朱子语类》,第269页。
①《朱子语类》,第860—861页。
②叶采:《近思录集解》卷二,元刻明修本。
③叶采:《近思录集解》卷二。
①《朱子语类》,第1283—1284页。
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687页。
③《朱子语类》,第2870—2871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同),第2620—3621页。
②《宋史》,第3621页。
③《宋史》,第3622页。
①《朱子语类》,第2883页。
②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第93页。
③据王懋竑《朱子年谱》统计,隆兴元年癸未(1163)完成《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到朱子四书学的经典形态《四书章句集注》的首次刊刻绍熙元年庚戌(1190),则已有27年之久,而此后直到庆元六年三月辛酉(1200)“改《大学诚意》章”,则朱子研究四书学的时间则长达37年。与之相比,朱子早年虽有编撰《家礼》,但是直到庆元二年(1196)“始修礼书”才正式着手编撰《通解》,虽然期间有断断续续的讨论编撰《通解》的内容,但是其所用时间则是从庆元二年方才全面集中精力来编撰《通解》。虽然上述时间段并非连续时间,但是仍可看出朱子用于研究四书学的时间至少是用于研究礼学时间的十倍之多。参见《朱熹年谱》,第22—23页、第209页、第265页、第258页。
①在《朱子语类》中,明确标为礼乐的内容从卷八十四至卷九十二共有9卷,而“四书”的内容则从卷十四至卷六十四有51卷,至于其他零散的内容涉及礼乐或者四书的内容不计在内,两者的数量之悬殊已可见一斑了。这个现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朱子平生着力点和学术兴趣点持续时间最长的当是《四书》学,故讲学内容涉及四书学的内容最多;二是《朱子语类》以对话形式出现,从上述统计数量可知,朱门弟子问学的内容亦较多集中在四书学方面。这两个原因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参见《朱子语类卷目》,《朱子语类》,第10—62页、第81—86页。
②参看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第103页。
③《朱子语类》,第2887页。
①《朱子语类》,第2886页。
②《朱子语类》,第3111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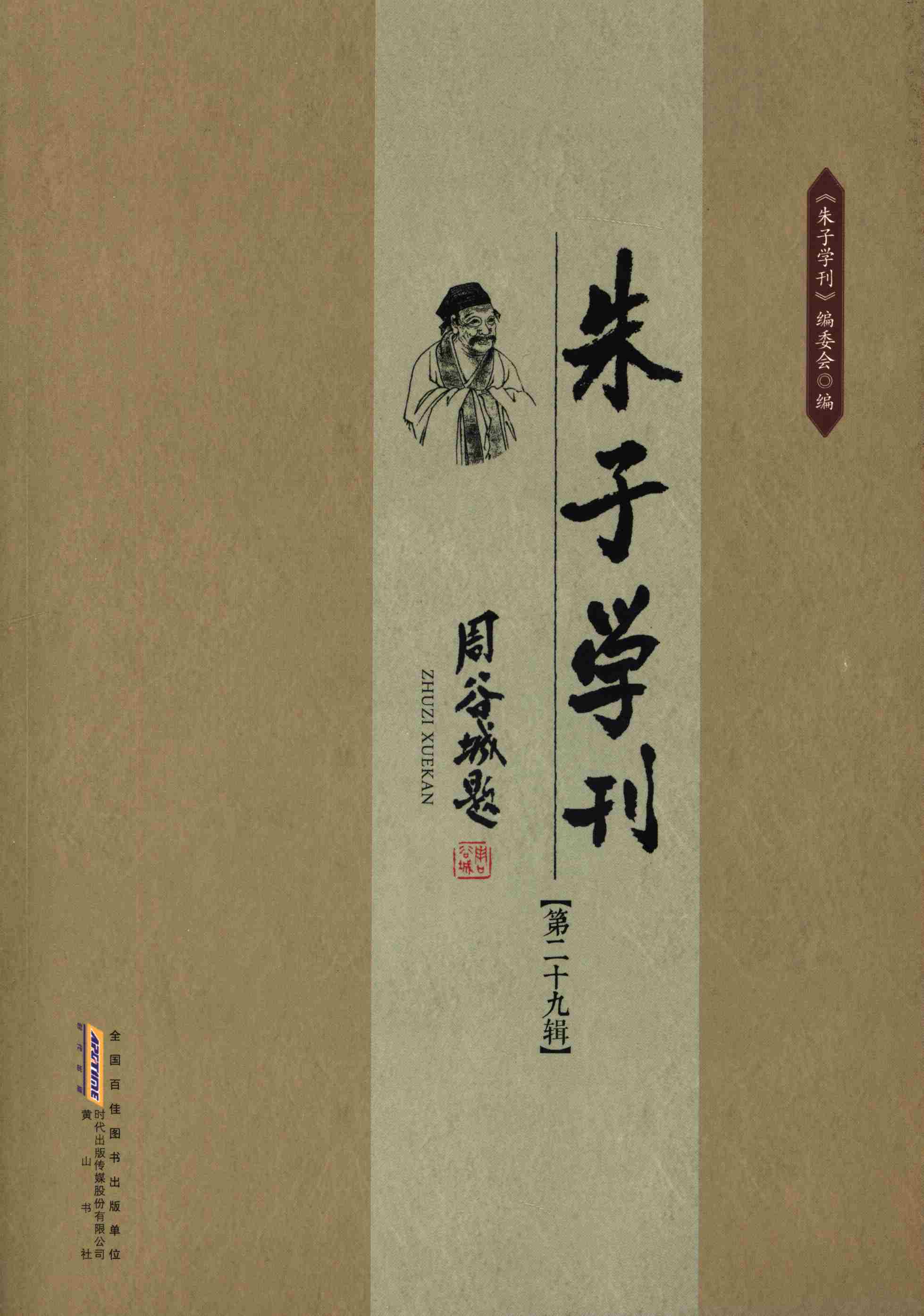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出版者:黄山书社
本书收录了《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学》《朱熹婚丧礼制的推行》《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戴震与朱熹关系平议》《陈北溪论“命”》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