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解》礼文博征注文的影响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251 |
| 颗粒名称: | 四、《通解》礼文博征注文的影响 |
| 分类号: | B244.7-55 |
| 页数: | 4 |
| 页码: | 042-045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清代前期学者对《仪礼》类诠释文献的博征礼文前贤注文之诠释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
| 关键词: | 清代礼经 著述体例 注释风格 |
内容
作为一部通释体著作,《通解》一书并不以精深的礼文注释见长,不以发覆礼文内容的心得见解为主要诠释手段。对于收录《通解》经、传两大块的各种文献原文的诠释,朱熹往往采用随文训诂的方式,收录郑玄注、贾公彦疏、孔颖达疏等历代前贤的诠释成说,然后再以“今按”“今详”的形式,对各家说法加以评点、申述或补充。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通解》在注文方面,一是保留了汉唐注疏的内容,特别是对郑玄《三礼注》的全文照录,被后人看作朱子‘服膺郑学’的体现。同时又多有评说、疑义和申述,常称‘疏说恐非’‘疏说非’‘疑孔说是’等,并且吸收和称引当时礼家之言见解,如称引‘程子曰’‘陈氏曰’‘陆氏说为是’‘张子曰’,就是对诸如陆佃、吕大临、张载、陈祥道、程子、张淳、吕希哲等宋代学者的观点有所吸收。很显然,朱熹是以自己的礼学判断对前人的见解和说法加以辨析和继承的。”
受这一博征礼文前贤注文之诠释方式的影响,清代颇有不少学者取用这一诠释手段。例如,清初浙江秀水学者盛世佐(1719—1755)所撰《仪礼集编》一书,便颇能彰显这一风格,具有如下几重特点:一是引书数量众多,涉及面广。据该书《凡例》称云,采自先秦迄于清代学者共197家著作,其中全解《仪礼》之作仅十数家,其余有关文集、语类、杂说及其他经解与《仪礼》相发明者,“务摭而录之,志在博收兼存异义,不专主一家言”。二是众说编排次第颇有讲究,“一以时代为序,二说略同则录前而置后,后足以发前所未备,始兼录之”。三是摭录众说但求详备,不求芟除异说。“京山郝氏尤好立异,所著《节解》一书掊击郑、贾不遗余力,而考据未精,穿凿已甚。今并录诸家之说,断以己意,亦欲去讲其非而求是耳,非敢与先儒角长短也”。四是引用贾《疏》往往有所删改。《凡例》云:“朱子尝谓《仪礼疏》说得不甚分明,故《通解》所引用往往加以润色,后儒因之,于贾《疏》各有删改,今掇其胜于原文者著于篇而分注其下,曰从某书节本,盖不没其所自也。若其未经删改者及他讲师之说,则但去其冗长而已,不敢妄加增损致乖本旨。”也就是说,《集编》引据贾《疏》情况不一,或据朱熹等人删改后的贾《疏》加以转引,或盛氏根据需要自行缩减冗长的贾《疏》之文加以引据,皆以不乖违贾《疏》本旨为要务。五是在援引郑《注》上,一般来说盛氏不予节省,但遇有重复之嫌的情况则删节之,用他的话说就是:“《乡射礼》文有与《乡饮酒礼》同者,《大射仪》有与《燕礼》《乡射礼》同者,郑氏各为之注,未免前后复出,今遇此等处,概从节去。”六是在引用前人说解的同时,亦不排除引据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张尔岐、万斯大、朱彝尊、汪琬、毛奇龄、阎若璩、姜兆锡等人的著述研究见解,在《集编》中亦多有摭引。
又如,直隶博野学者尹嘉铨(1711—1782)所著《仪礼探本》亦是如此。对于所要诠释的礼经文本,尹氏《探本》的注解大都来源于前贤的相关文献注释。从文献研读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其文字释音,主要节录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语料;就行文释义情况而言,则主要撷取郑玄《仪礼注》《礼记注》、贾公彦《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敖继公《仪礼集说》、方苞《仪礼析疑》《礼记析疑》、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等书,同时兼采历代其他学者研究成果汇纂而成。其中郑注一般出现在经文之后或《经典释文》之后,贾公彦《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朱熹《通解》的释语一般径称“疏曰”,方苞的释语一般径称“方子曰”,等等。此外,注释语料的出处还涉及其他一些学者,明代及之前的注家如崔灵恩、吕坤、邱濬、吴澄等,清代的注家如张尔岐、徐乾学、任启运等,但整体上都称引得很少。简言之,尹氏《探本》不以广征博引为著述要旨,一般征引自身认同的前人诠释观点,不同意见的则不予征引。另外,在同一经文的不同注释语之间,尹氏往往用“O”的标志分别开来,使读者不至于混淆。
又如,江苏常州学者秦蕙田(1702—1764)所著《五礼通考》亦是如此。和朱熹《通解》一样,秦氏《五礼通考》不以个性化的经文诠释考证为长,他对《仪礼》各篇经文的诠释,主要是通过征引汉代以来各家诠释文来实现的。从所引注释文献的来源看,秦氏征引最多的注释文献,清代以前主要有郑《注》、贾《疏》、朱熹《通解》、杨复《仪礼图》、敖继公《集说》、郝敬《集解》、陈祥道《礼书》;清代前期礼学著作援引最多的,则属张尔岐《句读》、盛世佐《集说》、蔡德晋《礼经本义》《钦定仪礼义疏》等几种出现最为频繁。而且,其援引敖继公《集说》、郝敬《集解》二家之说,并未像清初以来的许多学者那样,持所谓批判的诠释眼光,更多属于正面援引。
除各类私家著述受朱氏《通解》这一博征礼文前贤注文之诠释方式影响之外,清代乾隆年间官修之作《钦定仪礼义疏》同样受其影响。《仪礼义疏》采掇群言分为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七个义例,对于历代礼学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分析,然后胪列于每一义例之下,这样就使得全书的类目非常清晰,编著者的立论与各种不同见解都得到妥善的安置,即使是纂修者所不拟采信之说,也都列于“存疑”“存异”之中,大体上反映出了前人已有的各种成说,颇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其搜罗之功亦不可没。与此编纂义例相应,该书在书写上采取大小写相分别的方式,“贾《疏》释《注》者双行小书,各分附本注之下,后儒说有与《注》、《疏》相证相足者亦然。其推阐经义者,仍大书特列”。举凡历代申解郑《注》之训语,皆用小字列出,其余则用大字书写。另外,《义疏》中注音及郑《注》中有关古今异文部分的内容,亦用小字书写,一并附于《仪礼》正文各句之后。
不过,清代也有少数“张扬朱学派”学者在礼文注释的征引上,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其中尤以江苏武进学者胡抡最为突出。在胡抡看来,“经传注解之繁简详略,颇费筹蹰。太略,诚恐读之者不得明晓,不受穷经之益;太详,又恐言之者不能醇粹,不免雅郑之差”。胡氏所著《礼乐通考》嫌朱子《通解》征引古注过于烦琐,故没有延续朱子《通解》大量征引前贤文献注释的做法,其注释大量辑录之文献,更为强调“详而不失之于繁,简而不病于其略,斯为美耳”,释义表述更趋简洁明了。在先秦典籍的古注认知上,胡氏亦有自己的合理价值判断:“慎之哉,考古之不可忽也!礼著于经,经牵于注,后世去古既远,非古注无以得其门,泥古注又苦于其杂,惟以经为主,而以理断之,不为旧说所惑,乃得考古之益耳。”在胡抡看来,古注既有可取之处,所谓“非古注无以得其门”也;但亦不可全盘采录信从之,所谓“泥古注又苦于其杂”。因而,最为合理、科学的对待态度便是“惟以经为主,而以理断之,不为旧说所惑”。从这一认知观出发,胡抡对于所辑录之文献注释,包括《仪礼》经文的诠释在内,《通考》皆很少照搬古注,而是在参考糅合前贤诠释成果的基础上,另行用简洁的行文加以诠释说明。例如,《觐礼》:“侯氏裨冕,释币于祢。”郑注:“将觐,质明时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为上,其余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诸侯亦服焉。上公衮无升龙,侯伯鷩,子男毳,孤,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祢,谓行主迁主矣而云祢,亲之也。释币者,告将觐也。其释币,如聘大夫将受命释币于祢之礼。既则祝藏其币,归乃埋之于祧西阶之东。今文冕皆作絻。”而胡氏《通考》则小字注释云:“将觐之,质明时也。裨冕者,衮冕以下,五冕之通称也。祢,谓行主迁主矣而云祢,亲之也。释币者,告将觐也。”将二者加以对比便可发现,胡氏的训释语源自郑玄《注》文,但表义更趋简洁,尽管如此,胡氏并未标明“郑《注》云”等一类字样。总体观察来看,《通考》的此类注释语,更多趋向于诠释礼经的礼节情况,而较少关注字词的意义诠释。
综上各部分可见,朱熹的礼经学认知及其著述《仪礼经传通解》,对清代学者的《仪礼》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特别是《通解》“纂集重构”的著述方式和著述手段,更是在清代前期、中期催生了“张扬朱学派”,影响甚为深远。无怪乎陈澧发出“朱子《通解》之书,纯是汉唐注疏之学”的感慨。
受这一博征礼文前贤注文之诠释方式的影响,清代颇有不少学者取用这一诠释手段。例如,清初浙江秀水学者盛世佐(1719—1755)所撰《仪礼集编》一书,便颇能彰显这一风格,具有如下几重特点:一是引书数量众多,涉及面广。据该书《凡例》称云,采自先秦迄于清代学者共197家著作,其中全解《仪礼》之作仅十数家,其余有关文集、语类、杂说及其他经解与《仪礼》相发明者,“务摭而录之,志在博收兼存异义,不专主一家言”。二是众说编排次第颇有讲究,“一以时代为序,二说略同则录前而置后,后足以发前所未备,始兼录之”。三是摭录众说但求详备,不求芟除异说。“京山郝氏尤好立异,所著《节解》一书掊击郑、贾不遗余力,而考据未精,穿凿已甚。今并录诸家之说,断以己意,亦欲去讲其非而求是耳,非敢与先儒角长短也”。四是引用贾《疏》往往有所删改。《凡例》云:“朱子尝谓《仪礼疏》说得不甚分明,故《通解》所引用往往加以润色,后儒因之,于贾《疏》各有删改,今掇其胜于原文者著于篇而分注其下,曰从某书节本,盖不没其所自也。若其未经删改者及他讲师之说,则但去其冗长而已,不敢妄加增损致乖本旨。”也就是说,《集编》引据贾《疏》情况不一,或据朱熹等人删改后的贾《疏》加以转引,或盛氏根据需要自行缩减冗长的贾《疏》之文加以引据,皆以不乖违贾《疏》本旨为要务。五是在援引郑《注》上,一般来说盛氏不予节省,但遇有重复之嫌的情况则删节之,用他的话说就是:“《乡射礼》文有与《乡饮酒礼》同者,《大射仪》有与《燕礼》《乡射礼》同者,郑氏各为之注,未免前后复出,今遇此等处,概从节去。”六是在引用前人说解的同时,亦不排除引据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张尔岐、万斯大、朱彝尊、汪琬、毛奇龄、阎若璩、姜兆锡等人的著述研究见解,在《集编》中亦多有摭引。
又如,直隶博野学者尹嘉铨(1711—1782)所著《仪礼探本》亦是如此。对于所要诠释的礼经文本,尹氏《探本》的注解大都来源于前贤的相关文献注释。从文献研读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其文字释音,主要节录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语料;就行文释义情况而言,则主要撷取郑玄《仪礼注》《礼记注》、贾公彦《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敖继公《仪礼集说》、方苞《仪礼析疑》《礼记析疑》、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等书,同时兼采历代其他学者研究成果汇纂而成。其中郑注一般出现在经文之后或《经典释文》之后,贾公彦《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朱熹《通解》的释语一般径称“疏曰”,方苞的释语一般径称“方子曰”,等等。此外,注释语料的出处还涉及其他一些学者,明代及之前的注家如崔灵恩、吕坤、邱濬、吴澄等,清代的注家如张尔岐、徐乾学、任启运等,但整体上都称引得很少。简言之,尹氏《探本》不以广征博引为著述要旨,一般征引自身认同的前人诠释观点,不同意见的则不予征引。另外,在同一经文的不同注释语之间,尹氏往往用“O”的标志分别开来,使读者不至于混淆。
又如,江苏常州学者秦蕙田(1702—1764)所著《五礼通考》亦是如此。和朱熹《通解》一样,秦氏《五礼通考》不以个性化的经文诠释考证为长,他对《仪礼》各篇经文的诠释,主要是通过征引汉代以来各家诠释文来实现的。从所引注释文献的来源看,秦氏征引最多的注释文献,清代以前主要有郑《注》、贾《疏》、朱熹《通解》、杨复《仪礼图》、敖继公《集说》、郝敬《集解》、陈祥道《礼书》;清代前期礼学著作援引最多的,则属张尔岐《句读》、盛世佐《集说》、蔡德晋《礼经本义》《钦定仪礼义疏》等几种出现最为频繁。而且,其援引敖继公《集说》、郝敬《集解》二家之说,并未像清初以来的许多学者那样,持所谓批判的诠释眼光,更多属于正面援引。
除各类私家著述受朱氏《通解》这一博征礼文前贤注文之诠释方式影响之外,清代乾隆年间官修之作《钦定仪礼义疏》同样受其影响。《仪礼义疏》采掇群言分为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七个义例,对于历代礼学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分析,然后胪列于每一义例之下,这样就使得全书的类目非常清晰,编著者的立论与各种不同见解都得到妥善的安置,即使是纂修者所不拟采信之说,也都列于“存疑”“存异”之中,大体上反映出了前人已有的各种成说,颇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其搜罗之功亦不可没。与此编纂义例相应,该书在书写上采取大小写相分别的方式,“贾《疏》释《注》者双行小书,各分附本注之下,后儒说有与《注》、《疏》相证相足者亦然。其推阐经义者,仍大书特列”。举凡历代申解郑《注》之训语,皆用小字列出,其余则用大字书写。另外,《义疏》中注音及郑《注》中有关古今异文部分的内容,亦用小字书写,一并附于《仪礼》正文各句之后。
不过,清代也有少数“张扬朱学派”学者在礼文注释的征引上,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其中尤以江苏武进学者胡抡最为突出。在胡抡看来,“经传注解之繁简详略,颇费筹蹰。太略,诚恐读之者不得明晓,不受穷经之益;太详,又恐言之者不能醇粹,不免雅郑之差”。胡氏所著《礼乐通考》嫌朱子《通解》征引古注过于烦琐,故没有延续朱子《通解》大量征引前贤文献注释的做法,其注释大量辑录之文献,更为强调“详而不失之于繁,简而不病于其略,斯为美耳”,释义表述更趋简洁明了。在先秦典籍的古注认知上,胡氏亦有自己的合理价值判断:“慎之哉,考古之不可忽也!礼著于经,经牵于注,后世去古既远,非古注无以得其门,泥古注又苦于其杂,惟以经为主,而以理断之,不为旧说所惑,乃得考古之益耳。”在胡抡看来,古注既有可取之处,所谓“非古注无以得其门”也;但亦不可全盘采录信从之,所谓“泥古注又苦于其杂”。因而,最为合理、科学的对待态度便是“惟以经为主,而以理断之,不为旧说所惑”。从这一认知观出发,胡抡对于所辑录之文献注释,包括《仪礼》经文的诠释在内,《通考》皆很少照搬古注,而是在参考糅合前贤诠释成果的基础上,另行用简洁的行文加以诠释说明。例如,《觐礼》:“侯氏裨冕,释币于祢。”郑注:“将觐,质明时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为上,其余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诸侯亦服焉。上公衮无升龙,侯伯鷩,子男毳,孤,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祢,谓行主迁主矣而云祢,亲之也。释币者,告将觐也。其释币,如聘大夫将受命释币于祢之礼。既则祝藏其币,归乃埋之于祧西阶之东。今文冕皆作絻。”而胡氏《通考》则小字注释云:“将觐之,质明时也。裨冕者,衮冕以下,五冕之通称也。祢,谓行主迁主矣而云祢,亲之也。释币者,告将觐也。”将二者加以对比便可发现,胡氏的训释语源自郑玄《注》文,但表义更趋简洁,尽管如此,胡氏并未标明“郑《注》云”等一类字样。总体观察来看,《通考》的此类注释语,更多趋向于诠释礼经的礼节情况,而较少关注字词的意义诠释。
综上各部分可见,朱熹的礼经学认知及其著述《仪礼经传通解》,对清代学者的《仪礼》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特别是《通解》“纂集重构”的著述方式和著述手段,更是在清代前期、中期催生了“张扬朱学派”,影响甚为深远。无怪乎陈澧发出“朱子《通解》之书,纯是汉唐注疏之学”的感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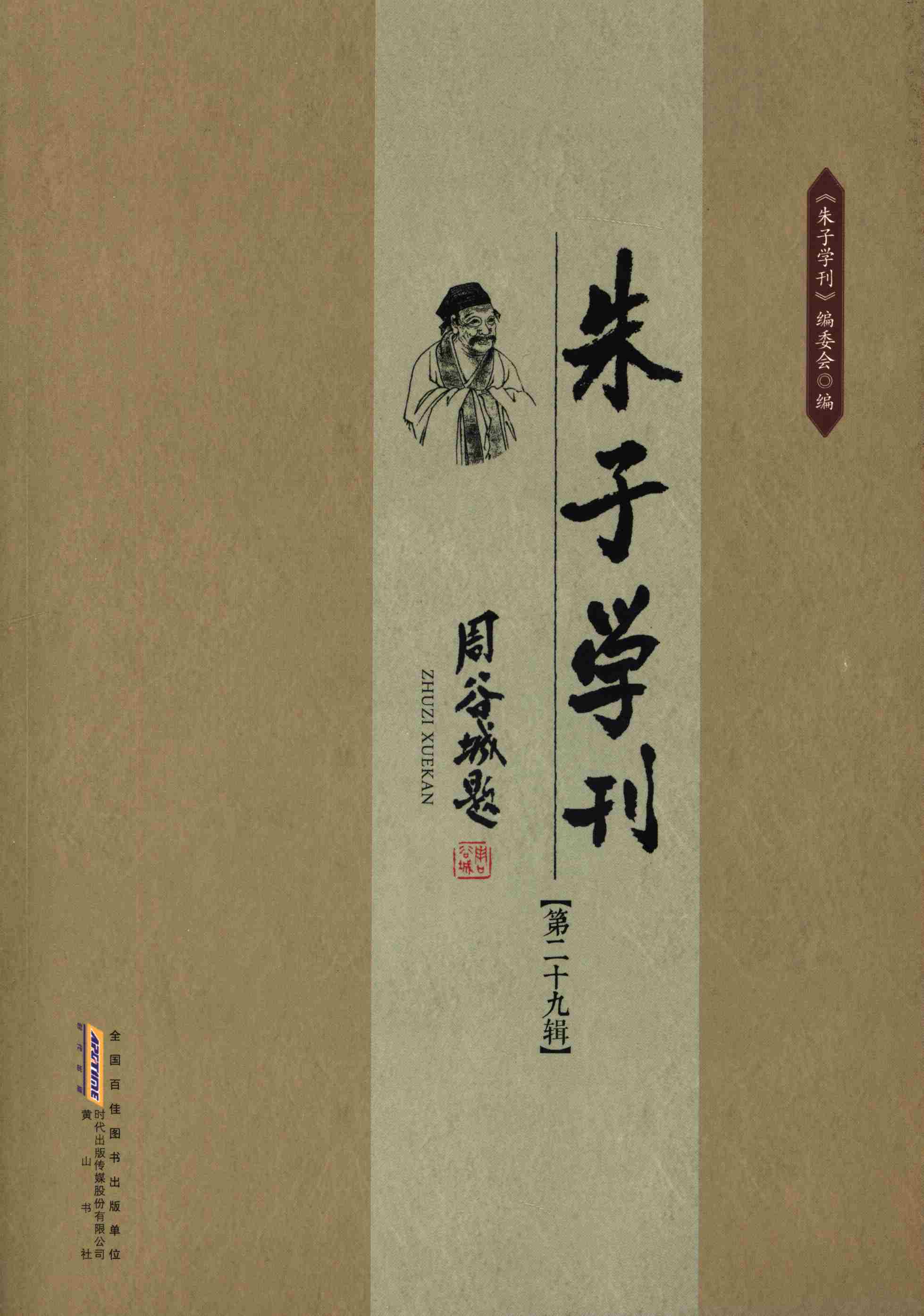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出版者:黄山书社
本书收录了《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学》《朱熹婚丧礼制的推行》《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戴震与朱熹关系平议》《陈北溪论“命”》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邓声国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