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解》通释体类体式的影响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249 |
| 颗粒名称: | 二、《通解》通释体类体式的影响 |
| 分类号: | B244.7-55 |
| 页数: | 6 |
| 页码: | 034-039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体例,包括篇章设计、内容编排和文献来源等方面。 |
| 关键词: | 清代礼经 著述体例 注释风格 |
内容
从文献整理体式情况看,朱氏《通解》主要采取通释体的编纂体式著述而成。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在篇章设计上,《通解》并没有以《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所称述的“吉、凶、宾、军、嘉”的“五礼”分类模式进行编排,而是以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的模式进行篇章编排的,这大体是对《仪礼》各篇进行分类之后而确定的模式,即以《士冠礼》《士昏礼》为家礼,以《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为乡礼,以《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为邦国礼,以《觐礼》为王朝礼,以《丧服》《士丧礼》《士虞礼》归于丧礼,以《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归于祭礼。这和东汉的郑玄开始将《仪礼》各章分别归于五礼系统的思路全然不同。究其目的而言,在于通过调整全书的篇章结构次序,“以达到建构礼学思想体系的目的”这样一种诠释策略。
二是在内容编排上,《通解》各篇大多以“经”“传”(或“记”)、“注”三方面的内容成篇。对于《仪礼》诸篇,朱熹尤其强调与之相关的“义”篇的延续与重构。例如,《通解》为《士冠礼》篇编纂《冠义》一篇,不仅吸纳了《小戴礼·冠义》一篇礼文,同时又因《孔子家语·冠颂篇》略见天子、诸侯、大夫之礼,《小戴礼·曾子问》中有变礼,《春秋》内外传有事证,故朱氏据此糅合而成此篇。再如,《通解》纂辑《昏义》一文时,不仅吸收了《小戴礼·昏义》一篇礼文,同时又将《礼记·郊特牲》、《坊记》、《曾子问》及《诗经》、《春秋》内外传、《白虎通义》、《说苑》所说婚礼之义及其变节合之,糅合而成此篇。
三是在各类礼文的文献来源上,往往不拘于《仪礼》十七篇篇目的内容,突破经传的界限分别,贯通《三礼》,融会诸子史书,扩大古礼文献资料和解说材料的选取范围,从而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经补传、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就成为《通解》的一个鲜明特点。
受朱熹、黄榦、杨复等《通解》《通解续》这一著述体式特点的影响,清代前期、中期“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治学纷纷据此进行效仿,以纂集重构出符合自身礼制思想的一部新的礼经学著作。例如,姜兆锡所著《仪礼经传内外编》便是一部相类似的著作。姜兆锡在该书《自序》中就说:“兹编实奉朱子遗训,以其所编家乡邦国王朝之礼,用勉斋丧、祭二礼之例以通之,不袭其迹而师其意。”这就点明了《内外编》在体例上源于《通解》和《续通解》,但姜氏却又有所调整变动。若分类言之,该书的编纂著述体例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全面观照:
其一,从“五礼”的分章布局情况来看。《内编》23卷,前22卷依次为嘉礼、军礼、宾礼、凶礼、吉礼,其中嘉礼、军礼、凶礼三者皆举纲统目,嘉礼分冠昏之礼、饮食之礼、飨燕之礼、宾射之礼、脤膰之礼、贺庆之礼,军礼分大封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师之礼,凶礼分丧礼、荒礼、吊礼、禬礼、恤礼;而宾礼、吉礼二者皆第举目,宾礼约以朝、聘之属统之,而吉礼约以人鬼天神地示之属统之,具体而言,则宾礼分朝觐之属之礼、聘问之属之礼,吉礼分享人鬼礼、祀天神礼、祭地示礼、因事之祭、类祭之事、因祭之事。第23卷,附庶民入小学礼、国子入小学礼、国子暨民俊入大学礼、弟子职礼、凡小学、大学简升礼、世子豫教礼、诸侯元年即位礼、王元年即位礼等九礼。《外编》5卷,卷一、卷二为《丧服》上下,卷三《丧服补》,别采经四篇;后附《五礼分合图考》,包括嘉礼图考、军礼图考、宾礼图考、凶礼图考、吉礼图考、后附图考、五礼总图考。
其二,从具体礼类的编排情况来看,《内外编》有源于《通解》《通解续》之处,但姜氏却又有所调整变动。例如,该书“丧礼”部分,《通解续》尝采《丧大记》及各经传之属,通将王侯大夫等丧礼、虞礼总汇为一篇,名之曰《丧大记》,又通将王侯大夫等卒哭祔练祥禫各礼汇为一篇,名之曰《卒哭祔练祥记》,而于王侯大夫等未以类分编;而姜兆锡《内编》卷十四、卷十五则参考其文,分丧礼为《大夫丧礼》《诸侯丧礼》《王丧礼》三类,而虞礼及卒哭祔练祥禫各礼之不可考者,仍总次为《记》,并略加参议其间。又如“馈食礼”部分,姜氏《内编》分《上大夫馈食礼》和《下大夫馈食礼》两类目,分别载于《内编》之卷十九和卷二十。凡此之类,都体现出姜氏在全书分门别类方面更趋细密、合理。
其三,从《仪礼》十七篇经文的整合情况来看。姜氏根据十七篇经文的礼类归属情况,依次将其归入相应的部类之下,《仪礼》中的《记》文也不再出现在对应十七篇经文之后,而是作为“本记”条文,附之于相应仪节经文之后。例如,《士冠礼》一文,本经保留了相对的完整性,姜氏只是将其中诸辞及《记》文作为“本记”之文,归附在各分节的具体仪文之后;至于《燕礼》《公食大夫礼》《士相见礼》诸篇经文,姜氏以为“每篇当分为诸礼,不得相统”,故而原有完整的经文不再保留篇目经文的完整性,而是被分解到相应的礼类之下。如《燕礼》一篇,姜氏将其拆分为“诸侯燕大夫礼”和“诸侯燕聘大夫礼”二礼类,分别为之分章节次。
其四,从各大礼类的文献重构情况来看。姜兆锡对各大礼类的文献重构,完全统一于具体礼制建构的需要,从各类经书和准经书中去寻找与摘录文献素材,而被列入其中的文献材料经过新的排列组合,相当程度上具有了经的权威性,姜氏将这类经文称之为“参补之经”。例如,《内编》卷十“宾礼”之“诸侯会同礼”,礼文原本阙而不备,姜氏汇考《周官·司仪》《掌客》诸职,参补为经,由此得以稍存“会同”之遗制;又“王时巡受朝礼”,礼文本阙,姜氏参《虞书》《周礼》《孔丛子》之文补足之;又“诸侯膳王礼”,礼文亦阙,姜氏取《周官·掌客》篇文补以为经。倘若某一礼类在传世文献当中无法找到具体的仪制记载,姜氏则阙而不录。如“饮食之礼”中的士族饮礼、大夫族饮礼、王食大夫礼、王食聘大夫礼、王食诸侯礼、王食牧伯礼、王食国宾礼,“飨燕之礼”中的本国大夫相飨礼、王大夫飨聘大夫礼、王大夫飨诸侯礼、诸侯飨大夫礼、王飨诸侯礼,等等,皆有细目而无正文。按照姜兆锡的说法,“参补之经”有四种情况:“有逸见他经而体例当升为经者,曰采补;虽见他经,而体稍不合者,曰参补;旁见书传,而体有未合者,曰姑补;散之书传,而合为编次者,曰汇补。”这种文献重构的做法,与黄勉斋《通解续》单纯补经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亦更趋合理。
再如,山西绛州学者梁万方(?—1725)所著《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一书,卷帙浩繁,全书69卷,完全以朱子、黄榦《通解》《通解续》之书为宗,“梁君本其尊人遗稿,复加讨论编次,朱墨咿嚘中搜罗宏富,抉择精严,竭数十年之力,凡三脱稿而后成,洵可谓先圣之功臣、紫阳之嫡派矣”。该书在著述体式上具有以下诸方面特点:
其一,从全书结构体例布局来看,大致承袭了《通解》的做法。梁氏“大致据杨复《序》文,谓朱子称黄榦所续丧、祭二礼‘规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书’而未暇,遂以榦之体例更朱子之体例,与榦书合为一编。补其阙文,删其冗复,正其讹误”,因而他的《重刊》也延续了《通解》及《通解续》的编纂体例,其中《家礼》5卷、《乡礼》3卷、《学礼》12卷、《邦国礼》5卷、《王朝礼》15卷、《丧礼》16卷、《祭礼》13卷,凡69卷90篇。梁氏《凡例》云:“朱子原本于《觐礼》以下初名《仪礼集传集注》,亦无编次名目;黄先生于《丧》、《祭》二编加‘续’字另序篇次,今悉遵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式法,《觐礼》篇接前至《祭义》,共为九十篇,前后通彻,合成一书。”(第4条)由此可见,梁氏并未更改朱子、黄氏之书的著述体例与主体编排结构。
其二,从《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诸类目的各自礼篇设置上,完全相同于朱子《通解》,而且在《仪礼》各篇之后,均仿朱氏的做法,每一篇之后设置一篇《义》文,如《士冠礼》之后,从小戴《礼记》之移入《冠义》之文;《燕礼》之后,从小戴《礼记》之移入《燕义》之文。倘若《礼记》没有《义》篇,则仍沿袭朱子的做法,从其他儒家经传删节补入,如《学礼》部分,《学制》一文之后,没有现存的《学义》文可以照搬,朱子乃“集诸经传凡言教法之意者补之,以释上篇之义”,而梁氏《重刊》亦据此加以仿效编订其文;又如,梁氏补《丧服义》篇,乃谓“礼篇如《冠》《昏》《饮》《射》《燕》《食》《聘》《朝》皆有《义》,皆汉儒所造以释礼者,既列于经,今观小戴《丧服四制》、《三年问》、《服问》等篇,大抵皆要其义言之者,故悉取其文并他篇书记之言《丧服》起义者合之为此篇”。
其三,对于《通解》《通解续》的缺额部分,梁氏深以为憾,他有意仿照朱熹《通解》的编撰体例进行了增补,诚如《重刊》中《凡例》部分第3条云:“旧本自《践阼》至《王制》之癸,共30篇,序、题皆缺;又《丧》、《祭》二礼亦多缺,今细探本篇之阃奥,联络上下篇之旨趣,以统贯其所采经书,仿朱子前式而补之。总书于纲领者,使学者一览而全义可洞悉也;后仍逐篇录入卷首者,所以使学者每读一篇,先领会其大义也。”
其四,考该书《凡例》第5条云:“此书旧名《仪礼经传通解》,今间有删订,亦悉本朱子之意;其附入诸家说及补注附按者,皆体会朱子平时所言之意旨,以发明经传之义理耳,不敢有更张也。”可见,在对待《通解》《通解续》原本辑录之材料和注释按语的处置方式上,梁氏《重刊》并未完全舍弃不用,而是略加删订而成,即使是需要补充其他文献材料及相关注释者,亦尽可能效仿原书编排之体例,不做大的改动。
其五,在自身注释语注释方式的编排上,梁氏《重刊》亦强调沿袭朱子《通解》的做法:“经义内注疏所解有未熨帖者,有旁及他说拘滞而乖大义者,朱子皆发明订正,冠以‘今按’二字。今敬仿之,用‘附按’字为别。”(《凡例》第11条)一个“敬仿之”的处置态度,亦表露出万方对于朱熹治学态度的推崇和敬重。
此外,为了体现自身治学对于朱氏学术的尊崇与重视,梁氏还将朱子有关诸经的注释成果吸纳到《重刊》中来,诚如万方在该书《凡例》第13条所说:“朱子前编引《四书》注皆用《集注》,《续》编犹有系《注疏》者,今悉改从朱注。又引《诗》皆改附朱子《集传》,引《易》改附朱子《本义》,引《书》改附九峰蔡氏《传》,一皆以至是为宗。”另外,第18条也说:“朱子凡有说《三礼》及《语类》所载说经传语,今皆各随其条下录入,而周子、程子、张子语亦然。若诸家精微之说,即皆采入,用一‘附’字别其原本。”
不过,清代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这一类治学方式的艰难,他们指出,这种文献的大批量纂集重构的方式极易于陷入“汙漫之书抄”的治学困境,需要治学者拥有高超的学术识见。如汪绂(1692—1759)在给江永的信中就颇有饬议之言:“大抵有明先辈,类多融贯全经,故时艺非必引用经文,而无非六经精义。后人专求工于时艺,而无暇以穷经,故满纸引用经言,究无当于经义。……今人因时艺而讲经学,亦已傎矣。况乃弃经学不讲,而从事于汙漫之书抄,不亦伤乎?”认为当时的许多这类书籍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污漫之书抄”,其实质是“弃经学不讲”的一种做法。因为在汪氏看来,如果无法形成一种有价值的礼学体系,这种纂集重构就形同于彻底失败了。另外,清初学者姚际恒对于这一类诠释策略之作亦颇不认同,并大加抵斥说:“吾实不解作者意指,以为尊《仪礼》耶?全录《注疏》毫无发明,一抄书吏可为也,尊之之义安在?以裁割《礼记》《周礼》史传等书附益之为能耶?检摘事迹可相类者合于一处,不别是非同异,粗识文字童子亦可为也,又何以为能?其于无可合者则分家、乡、学、邦国、王朝等名,凭臆变乱,牵强填塞,此全属纂辑类书伎俩,使经义破碎支离,何益于学?何益于治?”姚氏的这一番话似有失公允,他忽略了群经与《仪礼》之间具有互贯融通的学术特征,因而并未得到当时学者的积极响应,清代前期、中期“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治学风格便颇具强大的学术生命力,涌现了不少此类著述。
一是在篇章设计上,《通解》并没有以《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所称述的“吉、凶、宾、军、嘉”的“五礼”分类模式进行编排,而是以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的模式进行篇章编排的,这大体是对《仪礼》各篇进行分类之后而确定的模式,即以《士冠礼》《士昏礼》为家礼,以《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为乡礼,以《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为邦国礼,以《觐礼》为王朝礼,以《丧服》《士丧礼》《士虞礼》归于丧礼,以《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归于祭礼。这和东汉的郑玄开始将《仪礼》各章分别归于五礼系统的思路全然不同。究其目的而言,在于通过调整全书的篇章结构次序,“以达到建构礼学思想体系的目的”这样一种诠释策略。
二是在内容编排上,《通解》各篇大多以“经”“传”(或“记”)、“注”三方面的内容成篇。对于《仪礼》诸篇,朱熹尤其强调与之相关的“义”篇的延续与重构。例如,《通解》为《士冠礼》篇编纂《冠义》一篇,不仅吸纳了《小戴礼·冠义》一篇礼文,同时又因《孔子家语·冠颂篇》略见天子、诸侯、大夫之礼,《小戴礼·曾子问》中有变礼,《春秋》内外传有事证,故朱氏据此糅合而成此篇。再如,《通解》纂辑《昏义》一文时,不仅吸收了《小戴礼·昏义》一篇礼文,同时又将《礼记·郊特牲》、《坊记》、《曾子问》及《诗经》、《春秋》内外传、《白虎通义》、《说苑》所说婚礼之义及其变节合之,糅合而成此篇。
三是在各类礼文的文献来源上,往往不拘于《仪礼》十七篇篇目的内容,突破经传的界限分别,贯通《三礼》,融会诸子史书,扩大古礼文献资料和解说材料的选取范围,从而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经补传、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就成为《通解》的一个鲜明特点。
受朱熹、黄榦、杨复等《通解》《通解续》这一著述体式特点的影响,清代前期、中期“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治学纷纷据此进行效仿,以纂集重构出符合自身礼制思想的一部新的礼经学著作。例如,姜兆锡所著《仪礼经传内外编》便是一部相类似的著作。姜兆锡在该书《自序》中就说:“兹编实奉朱子遗训,以其所编家乡邦国王朝之礼,用勉斋丧、祭二礼之例以通之,不袭其迹而师其意。”这就点明了《内外编》在体例上源于《通解》和《续通解》,但姜氏却又有所调整变动。若分类言之,该书的编纂著述体例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全面观照:
其一,从“五礼”的分章布局情况来看。《内编》23卷,前22卷依次为嘉礼、军礼、宾礼、凶礼、吉礼,其中嘉礼、军礼、凶礼三者皆举纲统目,嘉礼分冠昏之礼、饮食之礼、飨燕之礼、宾射之礼、脤膰之礼、贺庆之礼,军礼分大封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师之礼,凶礼分丧礼、荒礼、吊礼、禬礼、恤礼;而宾礼、吉礼二者皆第举目,宾礼约以朝、聘之属统之,而吉礼约以人鬼天神地示之属统之,具体而言,则宾礼分朝觐之属之礼、聘问之属之礼,吉礼分享人鬼礼、祀天神礼、祭地示礼、因事之祭、类祭之事、因祭之事。第23卷,附庶民入小学礼、国子入小学礼、国子暨民俊入大学礼、弟子职礼、凡小学、大学简升礼、世子豫教礼、诸侯元年即位礼、王元年即位礼等九礼。《外编》5卷,卷一、卷二为《丧服》上下,卷三《丧服补》,别采经四篇;后附《五礼分合图考》,包括嘉礼图考、军礼图考、宾礼图考、凶礼图考、吉礼图考、后附图考、五礼总图考。
其二,从具体礼类的编排情况来看,《内外编》有源于《通解》《通解续》之处,但姜氏却又有所调整变动。例如,该书“丧礼”部分,《通解续》尝采《丧大记》及各经传之属,通将王侯大夫等丧礼、虞礼总汇为一篇,名之曰《丧大记》,又通将王侯大夫等卒哭祔练祥禫各礼汇为一篇,名之曰《卒哭祔练祥记》,而于王侯大夫等未以类分编;而姜兆锡《内编》卷十四、卷十五则参考其文,分丧礼为《大夫丧礼》《诸侯丧礼》《王丧礼》三类,而虞礼及卒哭祔练祥禫各礼之不可考者,仍总次为《记》,并略加参议其间。又如“馈食礼”部分,姜氏《内编》分《上大夫馈食礼》和《下大夫馈食礼》两类目,分别载于《内编》之卷十九和卷二十。凡此之类,都体现出姜氏在全书分门别类方面更趋细密、合理。
其三,从《仪礼》十七篇经文的整合情况来看。姜氏根据十七篇经文的礼类归属情况,依次将其归入相应的部类之下,《仪礼》中的《记》文也不再出现在对应十七篇经文之后,而是作为“本记”条文,附之于相应仪节经文之后。例如,《士冠礼》一文,本经保留了相对的完整性,姜氏只是将其中诸辞及《记》文作为“本记”之文,归附在各分节的具体仪文之后;至于《燕礼》《公食大夫礼》《士相见礼》诸篇经文,姜氏以为“每篇当分为诸礼,不得相统”,故而原有完整的经文不再保留篇目经文的完整性,而是被分解到相应的礼类之下。如《燕礼》一篇,姜氏将其拆分为“诸侯燕大夫礼”和“诸侯燕聘大夫礼”二礼类,分别为之分章节次。
其四,从各大礼类的文献重构情况来看。姜兆锡对各大礼类的文献重构,完全统一于具体礼制建构的需要,从各类经书和准经书中去寻找与摘录文献素材,而被列入其中的文献材料经过新的排列组合,相当程度上具有了经的权威性,姜氏将这类经文称之为“参补之经”。例如,《内编》卷十“宾礼”之“诸侯会同礼”,礼文原本阙而不备,姜氏汇考《周官·司仪》《掌客》诸职,参补为经,由此得以稍存“会同”之遗制;又“王时巡受朝礼”,礼文本阙,姜氏参《虞书》《周礼》《孔丛子》之文补足之;又“诸侯膳王礼”,礼文亦阙,姜氏取《周官·掌客》篇文补以为经。倘若某一礼类在传世文献当中无法找到具体的仪制记载,姜氏则阙而不录。如“饮食之礼”中的士族饮礼、大夫族饮礼、王食大夫礼、王食聘大夫礼、王食诸侯礼、王食牧伯礼、王食国宾礼,“飨燕之礼”中的本国大夫相飨礼、王大夫飨聘大夫礼、王大夫飨诸侯礼、诸侯飨大夫礼、王飨诸侯礼,等等,皆有细目而无正文。按照姜兆锡的说法,“参补之经”有四种情况:“有逸见他经而体例当升为经者,曰采补;虽见他经,而体稍不合者,曰参补;旁见书传,而体有未合者,曰姑补;散之书传,而合为编次者,曰汇补。”这种文献重构的做法,与黄勉斋《通解续》单纯补经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亦更趋合理。
再如,山西绛州学者梁万方(?—1725)所著《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一书,卷帙浩繁,全书69卷,完全以朱子、黄榦《通解》《通解续》之书为宗,“梁君本其尊人遗稿,复加讨论编次,朱墨咿嚘中搜罗宏富,抉择精严,竭数十年之力,凡三脱稿而后成,洵可谓先圣之功臣、紫阳之嫡派矣”。该书在著述体式上具有以下诸方面特点:
其一,从全书结构体例布局来看,大致承袭了《通解》的做法。梁氏“大致据杨复《序》文,谓朱子称黄榦所续丧、祭二礼‘规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书’而未暇,遂以榦之体例更朱子之体例,与榦书合为一编。补其阙文,删其冗复,正其讹误”,因而他的《重刊》也延续了《通解》及《通解续》的编纂体例,其中《家礼》5卷、《乡礼》3卷、《学礼》12卷、《邦国礼》5卷、《王朝礼》15卷、《丧礼》16卷、《祭礼》13卷,凡69卷90篇。梁氏《凡例》云:“朱子原本于《觐礼》以下初名《仪礼集传集注》,亦无编次名目;黄先生于《丧》、《祭》二编加‘续’字另序篇次,今悉遵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式法,《觐礼》篇接前至《祭义》,共为九十篇,前后通彻,合成一书。”(第4条)由此可见,梁氏并未更改朱子、黄氏之书的著述体例与主体编排结构。
其二,从《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诸类目的各自礼篇设置上,完全相同于朱子《通解》,而且在《仪礼》各篇之后,均仿朱氏的做法,每一篇之后设置一篇《义》文,如《士冠礼》之后,从小戴《礼记》之移入《冠义》之文;《燕礼》之后,从小戴《礼记》之移入《燕义》之文。倘若《礼记》没有《义》篇,则仍沿袭朱子的做法,从其他儒家经传删节补入,如《学礼》部分,《学制》一文之后,没有现存的《学义》文可以照搬,朱子乃“集诸经传凡言教法之意者补之,以释上篇之义”,而梁氏《重刊》亦据此加以仿效编订其文;又如,梁氏补《丧服义》篇,乃谓“礼篇如《冠》《昏》《饮》《射》《燕》《食》《聘》《朝》皆有《义》,皆汉儒所造以释礼者,既列于经,今观小戴《丧服四制》、《三年问》、《服问》等篇,大抵皆要其义言之者,故悉取其文并他篇书记之言《丧服》起义者合之为此篇”。
其三,对于《通解》《通解续》的缺额部分,梁氏深以为憾,他有意仿照朱熹《通解》的编撰体例进行了增补,诚如《重刊》中《凡例》部分第3条云:“旧本自《践阼》至《王制》之癸,共30篇,序、题皆缺;又《丧》、《祭》二礼亦多缺,今细探本篇之阃奥,联络上下篇之旨趣,以统贯其所采经书,仿朱子前式而补之。总书于纲领者,使学者一览而全义可洞悉也;后仍逐篇录入卷首者,所以使学者每读一篇,先领会其大义也。”
其四,考该书《凡例》第5条云:“此书旧名《仪礼经传通解》,今间有删订,亦悉本朱子之意;其附入诸家说及补注附按者,皆体会朱子平时所言之意旨,以发明经传之义理耳,不敢有更张也。”可见,在对待《通解》《通解续》原本辑录之材料和注释按语的处置方式上,梁氏《重刊》并未完全舍弃不用,而是略加删订而成,即使是需要补充其他文献材料及相关注释者,亦尽可能效仿原书编排之体例,不做大的改动。
其五,在自身注释语注释方式的编排上,梁氏《重刊》亦强调沿袭朱子《通解》的做法:“经义内注疏所解有未熨帖者,有旁及他说拘滞而乖大义者,朱子皆发明订正,冠以‘今按’二字。今敬仿之,用‘附按’字为别。”(《凡例》第11条)一个“敬仿之”的处置态度,亦表露出万方对于朱熹治学态度的推崇和敬重。
此外,为了体现自身治学对于朱氏学术的尊崇与重视,梁氏还将朱子有关诸经的注释成果吸纳到《重刊》中来,诚如万方在该书《凡例》第13条所说:“朱子前编引《四书》注皆用《集注》,《续》编犹有系《注疏》者,今悉改从朱注。又引《诗》皆改附朱子《集传》,引《易》改附朱子《本义》,引《书》改附九峰蔡氏《传》,一皆以至是为宗。”另外,第18条也说:“朱子凡有说《三礼》及《语类》所载说经传语,今皆各随其条下录入,而周子、程子、张子语亦然。若诸家精微之说,即皆采入,用一‘附’字别其原本。”
不过,清代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这一类治学方式的艰难,他们指出,这种文献的大批量纂集重构的方式极易于陷入“汙漫之书抄”的治学困境,需要治学者拥有高超的学术识见。如汪绂(1692—1759)在给江永的信中就颇有饬议之言:“大抵有明先辈,类多融贯全经,故时艺非必引用经文,而无非六经精义。后人专求工于时艺,而无暇以穷经,故满纸引用经言,究无当于经义。……今人因时艺而讲经学,亦已傎矣。况乃弃经学不讲,而从事于汙漫之书抄,不亦伤乎?”认为当时的许多这类书籍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污漫之书抄”,其实质是“弃经学不讲”的一种做法。因为在汪氏看来,如果无法形成一种有价值的礼学体系,这种纂集重构就形同于彻底失败了。另外,清初学者姚际恒对于这一类诠释策略之作亦颇不认同,并大加抵斥说:“吾实不解作者意指,以为尊《仪礼》耶?全录《注疏》毫无发明,一抄书吏可为也,尊之之义安在?以裁割《礼记》《周礼》史传等书附益之为能耶?检摘事迹可相类者合于一处,不别是非同异,粗识文字童子亦可为也,又何以为能?其于无可合者则分家、乡、学、邦国、王朝等名,凭臆变乱,牵强填塞,此全属纂辑类书伎俩,使经义破碎支离,何益于学?何益于治?”姚氏的这一番话似有失公允,他忽略了群经与《仪礼》之间具有互贯融通的学术特征,因而并未得到当时学者的积极响应,清代前期、中期“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治学风格便颇具强大的学术生命力,涌现了不少此类著述。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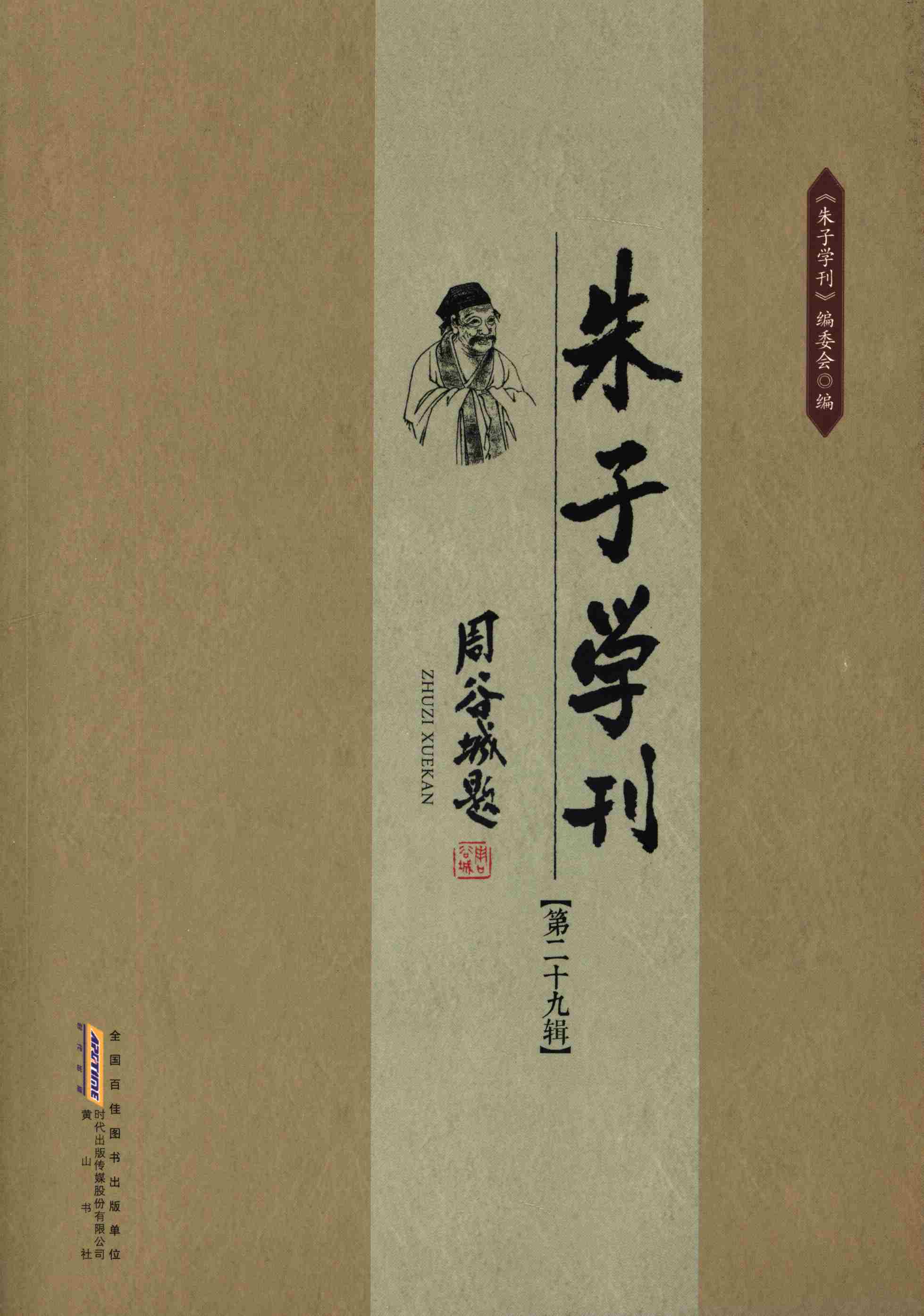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出版者:黄山书社
本书收录了《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学》《朱熹婚丧礼制的推行》《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戴震与朱熹关系平议》《陈北溪论“命”》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邓声国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