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朱熹《通解》对清代礼经研究的影响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243 |
| 颗粒名称: | 试论朱熹《通解》对清代礼经研究的影响 |
| 分类号: | B244.7-55 |
| 页数: | 16 |
| 页码: | 030-045 |
| 摘要: | 朱熹及其门人弟子黄榦、杨复等人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通解续》通过纂辑大量文献材料,借以重构一套新的礼学经传体系的治学方式,在礼学思想的传承与扬弃、著述的编纂体例、礼文分节、礼文取材、注释风格等多个方面,对清代前期和中期的《仪礼》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催生了“张扬朱学派”这一独特的诠释流派。 |
| 关键词: | 清代礼经 著述体例 注释风格 |
内容
朱熹及其门人弟子黄榦、杨复等人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下多称朱氏《通解》)、《仪礼经传通解续》(下多称《通解续》)问世后,对此后的礼经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清代前期和中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礼经学著作,如姜兆锡《仪礼经传内外编》、任启运《肆献裸馈食礼》、盛世佐《仪礼集编》、胡抡《礼乐通考》、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杨丕复《仪礼经传通解》、秦蕙田《五礼通考》、尹嘉铨《仪礼探本》等,都是同一类型的礼经学著作。这些礼经学著作,通过纂辑大量文献材料,重构一套新的礼学经传体系,使之符合著述者自身的礼学思想,并且援引历朝历代学者的注释语料,对这些新的经文、传文进行注释,这就与东汉郑玄注释《仪礼》的传统诠释体系迥然不同,成为一个新的文献类别群体——《通解》类《仪礼》文献。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清代前期、中期各家礼经学文献著述,就朱氏《通解》在清代礼经学研究的影响情况,逐一从礼学思想、著述体例、礼文分节、礼文取材、注释风格等多个方面,作一次粗线条式的考察分析。
一、朱熹礼经学思想的传承与影响
(一)朱熹关于《仪礼》成书问题之认知及影响
《朱子语类》卷八十五当中,提及朱熹对《仪礼》一书的成书问题的看法:“《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极细密,极周经处。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换言之,朱熹认为,今本所习《仪礼》十七篇并非成于一人制定而成,“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在逐渐赢得社会人士的认同之后,“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①。他所说的“圣人”,虽然没有说明具体是谁,推测可能是指周公、孔子之流。清代之时,遂有张尔岐、李光坡、蔡德晋、胡培翚、曹元弼等人坚持《仪礼》为周公所作说。例如,凌廷堪就指出:《仪礼》十七篇,乃是“礼之本经也”,“信非大圣人不能作也”②,“非周公制礼,则后世将无人伦”③。惠栋在《周易述》中也声称:“孔子当春秋之世,有天德而无天位,故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④晚清学者邵懿辰也指出,《仪礼》“本非一时一世而成,积久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旁皇周浃而曲得其次序,大体固周公为之也。其愈久而增多,则非尽周公为之也”⑤,“夫《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所谓《经礼》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时即礼文废阙,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汉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为定礼乐者,独取此十七篇以为教,配六艺而垂万世,则正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为天下之达礼耳”⑥。诸如此类的撰作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
至于《仪礼》经文所附的《传》《记》之文成书问题,《朱子语类》当中记载朱氏说:“子升问:‘《仪礼》《传》《记》是谁作?’曰:‘《传》是子夏作,《记》是子夏以后人作。’”①至于具体依据,朱氏没有详说,今人无从考述。然亦可考见,朱熹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比较传统的。清代之时,遂有《记》文不同撰者之说,如盛世佐、马的“汉儒窜入经师说”,刘沅的“汉儒纂辑遗文”说,黄以周的“七十子后学所记后仓所传”说,又有曹元弼的《传》文“子夏所作”说,等等。
(二)朱熹关于《仪礼》是否完本问题之认知及影响
《朱子语类》当中,提及朱熹对《仪礼》是否完本问题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礼书如仪礼,尚完备如他书”,但同时又指出:“先王之礼,今存者无几。”“今《仪礼》多是士礼,天子诸侯丧祭之礼皆不存,其中不过有些小朝聘燕飨之礼。自汉以来,凡天子之礼,皆是将士礼来增加为之。河间献王所得礼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诸侯之礼,故班固谓‘愈于推士礼以为天子、诸侯之礼者’。”“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十七篇同。郑康成注此十七篇,多举古文作某,则是他当时亦见此壁中之书。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无传焉!”②由这一番话语来看,朱熹是主张今本《仪礼》十七篇并非完本的。
受其影响,清代颇有一些学者亦主张《仪礼》非完帙之书。例如,《仪礼经传内编》卷九“士大夫投壶礼”下,姜兆锡申论说:“此亦燕以为乐而因以观德之礼,《周礼》不载,《小戴礼》之第四十篇实载之,而《大戴礼》亦有此篇。按:此当为《仪礼》经文而逸之耳,故今以类而附于射礼之后云。”③依姜氏看来,对《仪礼》经文性质的认定,并不局限于士礼的范畴,他以为汉初高堂生所传《仪礼》十七篇,当初就是残缺不全的,大小戴《礼记》所载“士大夫投壶礼”之文,其实当为“《仪礼》经文而逸之耳”,本质上讲,其实就是原本《仪礼》经文的一部分。盛世佐《仪礼集编·凡例》中也说:“礼书之存于今者,惟此经称完备,惜古文增多三十九篇,佚不传。然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修之司徒以节民性,为士大夫日用所不可阙者具在是矣,所亡惟军礼耳。”④盛氏以为,较之《周礼》,今本《仪礼》十七篇更称完备,其所“亡者惟军礼”之篇耳,只不过所亡佚的军礼部分在汉代便已无人传习,散佚至今不复可见。将二氏之说与朱熹的话语进行对比便能发现,他们之间的说法是大体一致的。
(三)朱熹关于《仪礼》与《礼记》关系之认知及影响
《仪礼》与《礼记》之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礼经学问题。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朱子语类》多次言及朱熹关于二者的认知观点:“《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①“《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无《士相见义》。后来刘原父补成一篇。”②“《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许多理皆无安著处。”③朱熹的这些观点,在清初学者当中不乏认同者,如浙江鄞县学者万斯大(1633—1683)认为:“《仪礼》一经,与《礼记》相表里。考仪文,则《仪礼》为备;言义理,则《礼记》为经。在圣人即吾心之义理而渐著之为仪文,在后人必通达其仪文而后得明其义理。故读《礼记》而不知《仪礼》,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也。悬空无据,岂能贯通。”④此一认识,可谓是对朱熹思想的承继与发挥。因而,在其《仪礼》学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仪礼》与《礼记》相发明,强调以《礼记》解《仪礼》,“《仪礼》之义,固有即《仪礼》而可考者,况又有《礼记》可相发明哉?”而对《周礼》,则不甚强调,以为“《仪礼》、《礼记》与《周礼》决不可通,故置弗论不宣。”⑤另外,江永的外甥李光地也认为:“礼有经有传,《仪礼》,礼之经也;《礼记》,礼之传也。”⑥可以看出,这一思想无疑与万斯大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承续了朱熹在此问题上的主张、意见。
(四)朱熹《仪礼》与《周礼》之关系认知及影响
对于《仪礼》与《周礼》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朱熹曾经在《乞修三礼剳子》当中指出:“《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⑦受其影响,清代也有少数学者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如清初儒臣方苞就明确主张:“《仪礼》所详,礼之细目也;《周官》所布,礼之大纲也。”①稍晚于方苞的江苏无锡学者蔡德晋与之看法大致相类:“《周官》为礼之纲领,《仪礼》为礼之条目。”②据此,不少学者在对《仪礼》经文的诠释当中,往往注重《周礼》与《仪礼》礼文的互证工作,通过《周礼》相关文献材料的考察,发明《仪礼》经义所在。
二、《通解》通释体类体式的影响
从文献整理体式情况看,朱氏《通解》主要采取通释体的编纂体式著述而成。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在篇章设计上,《通解》并没有以《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所称述的“吉、凶、宾、军、嘉”的“五礼”分类模式进行编排,而是以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的模式进行篇章编排的,这大体是对《仪礼》各篇进行分类之后而确定的模式,即以《士冠礼》《士昏礼》为家礼,以《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为乡礼,以《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为邦国礼,以《觐礼》为王朝礼,以《丧服》《士丧礼》《士虞礼》归于丧礼,以《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归于祭礼。这和东汉的郑玄开始将《仪礼》各章分别归于五礼系统的思路全然不同。究其目的而言,在于通过调整全书的篇章结构次序,“以达到建构礼学思想体系的目的”③这样一种诠释策略。
二是在内容编排上,《通解》各篇大多以“经”“传”(或“记”)、“注”三方面的内容成篇。对于《仪礼》诸篇,朱熹尤其强调与之相关的“义”篇的延续与重构。例如,《通解》为《士冠礼》篇编纂《冠义》一篇,不仅吸纳了《小戴礼·冠义》一篇礼文,同时又因《孔子家语·冠颂篇》略见天子、诸侯、大夫之礼,《小戴礼·曾子问》中有变礼,《春秋》内外传有事证,故朱氏据此糅合而成此篇。再如,《通解》纂辑《昏义》一文时,不仅吸收了《小戴礼·昏义》一篇礼文,同时又将《礼记·郊特牲》、《坊记》、《曾子问》及《诗经》、《春秋》内外传、《白虎通义》、《说苑》所说婚礼之义及其变节合之,糅合而成此篇。
三是在各类礼文的文献来源上,往往不拘于《仪礼》十七篇篇目的内容,突破经传的界限分别,贯通《三礼》,融会诸子史书,扩大古礼文献资料和解说材料的选取范围,从而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经补传、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就成为《通解》的一个鲜明特点。
受朱熹、黄榦、杨复等《通解》《通解续》这一著述体式特点的影响,清代前期、中期“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治学纷纷据此进行效仿,以纂集重构出符合自身礼制思想的一部新的礼经学著作。例如,姜兆锡所著《仪礼经传内外编》便是一部相类似的著作。姜兆锡在该书《自序》中就说:“兹编实奉朱子遗训,以其所编家乡邦国王朝之礼,用勉斋丧、祭二礼之例以通之,不袭其迹而师其意。”①这就点明了《内外编》在体例上源于《通解》和《续通解》,但姜氏却又有所调整变动。若分类言之,该书的编纂著述体例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全面观照:
其一,从“五礼”的分章布局情况来看。《内编》23卷,前22卷依次为嘉礼、军礼、宾礼、凶礼、吉礼,其中嘉礼、军礼、凶礼三者皆举纲统目,嘉礼分冠昏之礼、饮食之礼、飨燕之礼、宾射之礼、脤膰之礼、贺庆之礼,军礼分大封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师之礼,凶礼分丧礼、荒礼、吊礼、禬礼、恤礼;而宾礼、吉礼二者皆第举目,宾礼约以朝、聘之属统之,而吉礼约以人鬼天神地示之属统之,具体而言,则宾礼分朝觐之属之礼、聘问之属之礼,吉礼分享人鬼礼、祀天神礼、祭地示礼、因事之祭、类祭之事、因祭之事。第23卷,附庶民入小学礼、国子入小学礼、国子暨民俊入大学礼、弟子职礼、凡小学、大学简升礼、世子豫教礼、诸侯元年即位礼、王元年即位礼等九礼。《外编》5卷,卷一、卷二为《丧服》上下,卷三《丧服补》,别采经四篇;后附《五礼分合图考》,包括嘉礼图考、军礼图考、宾礼图考、凶礼图考、吉礼图考、后附图考、五礼总图考。
其二,从具体礼类的编排情况来看,《内外编》有源于《通解》《通解续》之处,但姜氏却又有所调整变动。例如,该书“丧礼”部分,《通解续》尝采《丧大记》及各经传之属,通将王侯大夫等丧礼、虞礼总汇为一篇,名之曰《丧大记》,又通将王侯大夫等卒哭祔练祥禫各礼汇为一篇,名之曰《卒哭祔练祥记》,而于王侯大夫等未以类分编;而姜兆锡《内编》卷十四、卷十五则参考其文,分丧礼为《大夫丧礼》《诸侯丧礼》《王丧礼》三类,而虞礼及卒哭祔练祥禫各礼之不可考者,仍总次为《记》,并略加参议其间。又如“馈食礼”部分,姜氏《内编》分《上大夫馈食礼》和《下大夫馈食礼》两类目,分别载于《内编》之卷十九和卷二十。凡此之类,都体现出姜氏在全书分门别类方面更趋细密、合理。
其三,从《仪礼》十七篇经文的整合情况来看。姜氏根据十七篇经文的礼类归属情况,依次将其归入相应的部类之下,《仪礼》中的《记》文也不再出现在对应十七篇经文之后,而是作为“本记”条文,附之于相应仪节经文之后。例如,《士冠礼》一文,本经保留了相对的完整性,姜氏只是将其中诸辞及《记》文作为“本记”之文,归附在各分节的具体仪文之后;至于《燕礼》《公食大夫礼》《士相见礼》诸篇经文,姜氏以为“每篇当分为诸礼,不得相统”,故而原有完整的经文不再保留篇目经文的完整性,而是被分解到相应的礼类之下。如《燕礼》一篇,姜氏将其拆分为“诸侯燕大夫礼”和“诸侯燕聘大夫礼”二礼类,分别为之分章节次。
其四,从各大礼类的文献重构情况来看。姜兆锡对各大礼类的文献重构,完全统一于具体礼制建构的需要,从各类经书和准经书中去寻找与摘录文献素材,而被列入其中的文献材料经过新的排列组合,相当程度上具有了经的权威性,姜氏将这类经文称之为“参补之经”。例如,《内编》卷十“宾礼”之“诸侯会同礼”,礼文原本阙而不备,姜氏汇考《周官·司仪》《掌客》诸职,参补为经,由此得以稍存“会同”之遗制;又“王时巡受朝礼”,礼文本阙,姜氏参《虞书》《周礼》《孔丛子》之文补足之;又“诸侯膳王礼”,礼文亦阙,姜氏取《周官·掌客》篇文补以为经。倘若某一礼类在传世文献当中无法找到具体的仪制记载,姜氏则阙而不录。如“饮食之礼”中的士族饮礼、大夫族饮礼、王食大夫礼、王食聘大夫礼、王食诸侯礼、王食牧伯礼、王食国宾礼,“飨燕之礼”中的本国大夫相飨礼、王大夫飨聘大夫礼、王大夫飨诸侯礼、诸侯飨大夫礼、王飨诸侯礼,等等,皆有细目而无正文。按照姜兆锡的说法,“参补之经”有四种情况:“有逸见他经而体例当升为经者,曰采补;虽见他经,而体稍不合者,曰参补;旁见书传,而体有未合者,曰姑补;散之书传,而合为编次者,曰汇补。”①这种文献重构的做法,与黄勉斋《通解续》单纯补经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亦更趋合理。
再如,山西绛州学者梁万方(?—1725)所著《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一书,卷帙浩繁,全书69卷,完全以朱子、黄榦《通解》《通解续》之书为宗,“梁君本其尊人遗稿,复加讨论编次,朱墨咿嚘中搜罗宏富,抉择精严,竭数十年之力,凡三脱稿而后成,洵可谓先圣之功臣、紫阳之嫡派矣”②。该书在著述体式上具有以下诸方面特点:
其一,从全书结构体例布局来看,大致承袭了《通解》的做法。梁氏“大致据杨复《序》文,谓朱子称黄榦所续丧、祭二礼‘规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书’而未暇,遂以榦之体例更朱子之体例,与榦书合为一编。补其阙文,删其冗复,正其讹误”①,因而他的《重刊》也延续了《通解》及《通解续》的编纂体例,其中《家礼》5卷、《乡礼》3卷、《学礼》12卷、《邦国礼》5卷、《王朝礼》15卷、《丧礼》16卷、《祭礼》13卷,凡69卷90篇。梁氏《凡例》云:“朱子原本于《觐礼》以下初名《仪礼集传集注》,亦无编次名目;黄先生于《丧》、《祭》二编加‘续’字另序篇次,今悉遵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式法,《觐礼》篇接前至《祭义》,共为九十篇,前后通彻,合成一书。”(第4条)由此可见,梁氏并未更改朱子、黄氏之书的著述体例与主体编排结构。
其二,从《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诸类目的各自礼篇设置上,完全相同于朱子《通解》,而且在《仪礼》各篇之后,均仿朱氏的做法,每一篇之后设置一篇《义》文,如《士冠礼》之后,从小戴《礼记》之移入《冠义》之文;《燕礼》之后,从小戴《礼记》之移入《燕义》之文。倘若《礼记》没有《义》篇,则仍沿袭朱子的做法,从其他儒家经传删节补入,如《学礼》部分,《学制》一文之后,没有现存的《学义》文可以照搬,朱子乃“集诸经传凡言教法之意者补之,以释上篇之义”②,而梁氏《重刊》亦据此加以仿效编订其文;又如,梁氏补《丧服义》篇,乃谓“礼篇如《冠》《昏》《饮》《射》《燕》《食》《聘》《朝》皆有《义》,皆汉儒所造以释礼者,既列于经,今观小戴《丧服四制》、《三年问》、《服问》等篇,大抵皆要其义言之者,故悉取其文并他篇书记之言《丧服》起义者合之为此篇”③。
其三,对于《通解》《通解续》的缺额部分,梁氏深以为憾,他有意仿照朱熹《通解》的编撰体例进行了增补,诚如《重刊》中《凡例》部分第3条云:“旧本自《践阼》至《王制》之癸,共30篇,序、题皆缺;又《丧》、《祭》二礼亦多缺,今细探本篇之阃奥,联络上下篇之旨趣,以统贯其所采经书,仿朱子前式而补之。总书于纲领者,使学者一览而全义可洞悉也;后仍逐篇录入卷首者,所以使学者每读一篇,先领会其大义也。”
其四,考该书《凡例》第5条云:“此书旧名《仪礼经传通解》,今间有删订,亦悉本朱子之意;其附入诸家说及补注附按者,皆体会朱子平时所言之意旨,以发明经传之义理耳,不敢有更张也。”可见,在对待《通解》《通解续》原本辑录之材料和注释按语的处置方式上,梁氏《重刊》并未完全舍弃不用,而是略加删订而成,即使是需要补充其他文献材料及相关注释者,亦尽可能效仿原书编排之体例,不做大的改动。
其五,在自身注释语注释方式的编排上,梁氏《重刊》亦强调沿袭朱子《通解》的做法:“经义内注疏所解有未熨帖者,有旁及他说拘滞而乖大义者,朱子皆发明订正,冠以‘今按’二字。今敬仿之,用‘附按’字为别。”(《凡例》第11条)一个“敬仿之”的处置态度,亦表露出万方对于朱熹治学态度的推崇和敬重。
此外,为了体现自身治学对于朱氏学术的尊崇与重视,梁氏还将朱子有关诸经的注释成果吸纳到《重刊》中来,诚如万方在该书《凡例》第13条所说:“朱子前编引《四书》注皆用《集注》,《续》编犹有系《注疏》者,今悉改从朱注。又引《诗》皆改附朱子《集传》,引《易》改附朱子《本义》,引《书》改附九峰蔡氏《传》,一皆以至是为宗。”另外,第18条也说:“朱子凡有说《三礼》及《语类》所载说经传语,今皆各随其条下录入,而周子、程子、张子语亦然。若诸家精微之说,即皆采入,用一‘附’字别其原本。”
不过,清代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这一类治学方式的艰难,他们指出,这种文献的大批量纂集重构的方式极易于陷入“汙漫之书抄”的治学困境,需要治学者拥有高超的学术识见。如汪绂(1692—1759)在给江永的信中就颇有饬议之言:“大抵有明先辈,类多融贯全经,故时艺非必引用经文,而无非六经精义。后人专求工于时艺,而无暇以穷经,故满纸引用经言,究无当于经义。……今人因时艺而讲经学,亦已傎矣。况乃弃经学不讲,而从事于汙漫之书抄,不亦伤乎?”①认为当时的许多这类书籍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污漫之书抄”,其实质是“弃经学不讲”的一种做法。因为在汪氏看来,如果无法形成一种有价值的礼学体系,这种纂集重构就形同于彻底失败了。另外,清初学者姚际恒对于这一类诠释策略之作亦颇不认同,并大加抵斥说:“吾实不解作者意指,以为尊《仪礼》耶?全录《注疏》毫无发明,一抄书吏可为也,尊之之义安在?以裁割《礼记》《周礼》史传等书附益之为能耶?检摘事迹可相类者合于一处,不别是非同异,粗识文字童子亦可为也,又何以为能?其于无可合者则分家、乡、学、邦国、王朝等名,凭臆变乱,牵强填塞,此全属纂辑类书伎俩,使经义破碎支离,何益于学?何益于治?”①姚氏的这一番话似有失公允,他忽略了群经与《仪礼》之间具有互贯融通的学术特征,因而并未得到当时学者的积极响应,清代前期、中期“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治学风格便颇具强大的学术生命力,涌现了不少此类著述。
三、《通解》礼经“分节”的影响
清人陈澧曾经说:“《仪礼》难读。昔人读之之法,略有数端:一曰分节,二曰绘图,三曰释例。今人生古人后,得其法以读之,通次经不难矣。”②为经文划分章节是礼经仪制训诂的一种特殊方式,正所谓“章次不分,则礼之始终度数与宾尸介绍,冠服玉帛牲牢尊俎之陈,如满屋散钱,毫无条贯”③。考察历代《仪礼》类诠释文献,注释家对《仪礼》采用“分节”的注释方式,起源较早。
关于《仪礼》本经的分节源始,清初学者盛世佐认为:“分节法昉于《通解》,而后之说《仪礼》者多遵之,以其便于读者也。”④然而后来广东番禺学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仪礼篇》中纠正其说称:“《士冠礼》:‘筮于庙门。’贾《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毕”一节,论将行冠礼,先筮取日之事。’贾《疏》全部皆如此。此读《仪礼》第一要法也。《有司彻》郑《注》屡言‘自某句至某句’,此贾《疏》分节之法所自出也。”⑤据此,则是郑玄《仪礼注》第一次采用这一方法对《仪礼》经文进行分节,但仅仅限于少数篇目,而贾公彦《仪礼疏》则是全部采用“分节”之法诠释礼经十七篇。
倘若将贾公彦《仪礼疏》和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进行比对,就能发现,在标注分节的位置上,二者是有差异的。贾公彦《疏》往往在每一节的第一句话之后,标云“自此至某句,论某事”;而朱熹《通解》则在每一节经文的末端,另起一行标云“右某事”,如该书卷一《士冠礼》篇,朱氏《通解》屡称“右筮日”“右戒宾”“右筮宾”“右宿宾”之类。从形式上看,朱熹《通解》的分节诠释功能特征更加鲜明,而贾《疏》的“分节”更类似于现代中学语文课分段和概括段落大意的做法。
根据陈澧《东塾读书记·仪礼篇》的考察,贾公彦《仪礼疏》的“分节”就已经相当细密了。例如《聘礼》一篇,贾氏《疏》屡云,“自此尽‘官具’,论聘人及用币之事”,“自此尽‘受书以行’,论陈币付使者之事”,“自此尽‘亦如之’,论宾与上介将行告祢之事”,等等。更有甚者,《特牲馈食礼》篇贾《疏》有分节者称:“自此尽‘卒复位’,论宾长献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妇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内,乃有十一爵:宾献尸,一也;主妇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妇,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妇,四也;主妇酢主人,五也;尸举奠爵酢宾长,六也;宾长献祝,七也;又献佐食,八也;宾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妇,十也;宾献主人酢,十一也。”①贾氏不仅总括此节主旨,更将此节经文的“献酢”活动,总结分解为十一环节,极其细密。针对贾氏这种分节的注解方式,陈澧感慨地说:“此一科而分十一节也。《有司彻》疏,如此类者最多,不可枚举。其分析细密,使读之者心目俱朗彻矣。”②
至于朱熹《通解》,其各篇的分节较之贾氏《疏》更加细密。以《士冠礼》一篇为例,贾《疏》仅分11节,已经称得上是颇为细密的了,然而朱子《通解》则更为详细具体,共分为筮日、戒宾、筮宾、宿宾、为期、陈器服、即位、迎宾、始加、再加、三加、醴冠者、冠者见母、字冠者、宾出就次、冠者见兄弟姑姊、奠挚于君乡大夫乡先生、醴宾、醮、杀、孤子冠、庶子冠、母不在、女子笄,凡24节。更能彰显朱子《通解》“分节”解经功能的是,朱熹将《士冠礼》一篇原本属于经文的“戒宾辞”“宿宾辞”“始加祝辞”“再加祝辞”“三加祝辞”“字辞”“醮辞”等,完全放置在相应一节概述性文字(指“右筮日”“右戒宾”)的后面,二者之间用“O”隔离开,既彰显出这些“辞”的解经性质,又对帮助理解具体某一节经文有很大的裨益。
朱熹《通解》给《仪礼》经文分节并在节段后面标注节旨的做法,对清代前期、中期学者的治学影响较大,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江永《礼书纲目》、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等诸多礼经文献,均延续了《通解》的这一注释方式。以《仪礼郑注句读》中《燕礼》一篇的分节情况为例,张氏将该篇经文分成五个部分,自首句至“公升就席”为第一部分,张氏在首句下说:“自此之‘公升就席’,皆燕初戒备之事,有戒与设具,有纳诸臣立于其位,有命大夫为宾,有请命执役,有纳宾,凡五节。”自“宾升自西阶,主人亦升自西阶”至“以虚爵降,奠于篚”为第二部分,张氏云:“自此至‘以虚爵降,奠于篚’,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献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宾,二人媵觯于公,公取媵觯酬宾,遂旅酬,凡七节,此初燕之盛礼也。”自“主人洗,升,实散,献卿于西阶上”至“降奠于篚”为第三部分,张氏在该部分首句下云:“自此至‘降奠于篚’,主人献卿,又二大夫媵觯于公,公又举媵酬宾若长,遂旅酬,凡三节。”自“射人自阼阶下请立司正”至“无算乐”为第四部分,张氏云:“自此至‘无算乐’,皆坐燕尽欢之事,既立司正安宾,次主人献士及旅食,次或射以乐宾,次宾媵觯于公为士举旅酬,次主人献庶子以下诸臣,乃行无算爵无算乐,凡六节,而燕礼备。”自“公与客燕”至经正文结束为第五部分,张氏又云:“此下言国君将与异国臣燕,使大夫就馆戒宾,及客应对之辞,其仪节与燕本国诸臣同,唯戒宾为异,故于礼末见之。”除了在每一部分首句下解释段落划分情况外,张氏还在每一部分各小节正文下,另起一行总结每小节之大旨,与整个部分的划分相呼应,使全文纲举目张,层次分明,增强了可读性。考察吴廷华《仪礼章句》、江永《礼书纲目》、徐乾学《读礼通考》等礼类文献的经文分节情况,亦大多类似此书的做法。
至于《仪礼·记》文的分节之源始,则并非始于朱熹等人的《通解》《通解续》之书。盛世佐在《仪礼集编·凡例》中申称:“《记》文旧不分章,张氏《句读》始分之。”①考贾公彦《仪礼疏》,尽管他对《仪礼》经文有具体“分节”,但在注释《记》文时,却未进行分节。至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更是将《记》文分解开来,放置到相应的经文分节文段总括语之后,用“○”隔开,将其和《礼记》之类解经性质的语料放置一块,便利于读者深层次理解经义。简言之,朱子并未对《仪礼·记》文分节。因此,盛氏谓《记》文分章始于张尔岐著述《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应该是可信的。
以《特牲馈食礼》篇为例,张尔岐将该篇《记》文,共分为8节,依次为“记祭时衣冠”,“记器具品物陈设之法”,“记事尸之礼”,“记佐食所事因及宗人佐食齿列”,“记设内尊与内兄弟面位旅酬赞荐诸仪”,“记祭灶之节”,“记宾送尸反位之节”,“记诸俎牲体之名数”②。较之贾公彦《仪礼疏》不分节《记》文的做法,张氏《句读》要合理得多;较之朱熹《通解》将《记》文附载在各节之后的做法,张氏《句读》更突出了《记》文自身的独立性,但从彰显《记》文原本补充注释经文的功能来说,张氏《句读》这一处置方式可能还不如朱熹《通解》更加直观便利。
至于各家“张扬朱学派”学者的同类之作,亦大致相类似,纷纷强调对礼经经文的“分节”诠释工作。例如,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纂集之各篇礼文部分,梁氏亦延续朱子《通解》的做法,仿效章句体著作的编纂方式,厘析经文划分章节次第,每一节之后题云右某事之类,“旧本分截章法,但云右某某,今仿朱子分《中庸》之例,每篇自第一章起,次第至末,凡若干章;又于篇下统注几章,每章细注几条,及章下分注又几条,总期贯彻详明”(《凡例》第17条)。
至于清代中期以后的许多著作,由于著述大多以“释难解纷”“订误质疑”为治学要务,不再以强调对礼文的“纂集重构”,“从结构入手,通过调整全书的篇章结构次序,以达到建构礼学思想体系的目的”①为诠释策略手段,朱氏《通解》给礼经“分节”的做法影响才渐趋淡化,不再成为一种著述时尚。
四、《通解》礼文博征注文的影响
作为一部通释体著作,《通解》一书并不以精深的礼文注释见长,不以发覆礼文内容的心得见解为主要诠释手段。对于收录《通解》经、传两大块的各种文献原文的诠释,朱熹往往采用随文训诂的方式,收录郑玄注、贾公彦疏、孔颖达疏等历代前贤的诠释成说,然后再以“今按”“今详”的形式,对各家说法加以评点、申述或补充。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通解》在注文方面,一是保留了汉唐注疏的内容,特别是对郑玄《三礼注》的全文照录,被后人看作朱子‘服膺郑学’的体现。同时又多有评说、疑义和申述,常称‘疏说恐非’‘疏说非’‘疑孔说是’等,并且吸收和称引当时礼家之言见解,如称引‘程子曰’‘陈氏曰’‘陆氏说为是’‘张子曰’,就是对诸如陆佃、吕大临、张载、陈祥道、程子、张淳、吕希哲等宋代学者的观点有所吸收。很显然,朱熹是以自己的礼学判断对前人的见解和说法加以辨析和继承的。”②
受这一博征礼文前贤注文之诠释方式的影响,清代颇有不少学者取用这一诠释手段。例如,清初浙江秀水学者盛世佐(1719—1755)所撰《仪礼集编》一书,便颇能彰显这一风格,具有如下几重特点:一是引书数量众多,涉及面广。据该书《凡例》称云,采自先秦迄于清代学者共197家著作,其中全解《仪礼》之作仅十数家,其余有关文集、语类、杂说及其他经解与《仪礼》相发明者,“务摭而录之,志在博收兼存异义,不专主一家言”①。二是众说编排次第颇有讲究,“一以时代为序,二说略同则录前而置后,后足以发前所未备,始兼录之”②。三是摭录众说但求详备,不求芟除异说。“京山郝氏尤好立异,所著《节解》一书掊击郑、贾不遗余力,而考据未精,穿凿已甚。今并录诸家之说,断以己意,亦欲去讲其非而求是耳,非敢与先儒角长短也”③。四是引用贾《疏》往往有所删改。《凡例》云:“朱子尝谓《仪礼疏》说得不甚分明,故《通解》所引用往往加以润色,后儒因之,于贾《疏》各有删改,今掇其胜于原文者著于篇而分注其下,曰从某书节本,盖不没其所自也。若其未经删改者及他讲师之说,则但去其冗长而已,不敢妄加增损致乖本旨。”④也就是说,《集编》引据贾《疏》情况不一,或据朱熹等人删改后的贾《疏》加以转引,或盛氏根据需要自行缩减冗长的贾《疏》之文加以引据,皆以不乖违贾《疏》本旨为要务。五是在援引郑《注》上,一般来说盛氏不予节省,但遇有重复之嫌的情况则删节之,用他的话说就是:“《乡射礼》文有与《乡饮酒礼》同者,《大射仪》有与《燕礼》《乡射礼》同者,郑氏各为之注,未免前后复出,今遇此等处,概从节去。”⑤六是在引用前人说解的同时,亦不排除引据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张尔岐、万斯大、朱彝尊、汪琬、毛奇龄、阎若璩、姜兆锡等人的著述研究见解,在《集编》中亦多有摭引。
又如,直隶博野学者尹嘉铨(1711—1782)所著《仪礼探本》亦是如此。对于所要诠释的礼经文本,尹氏《探本》的注解大都来源于前贤的相关文献注释。从文献研读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其文字释音,主要节录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语料;就行文释义情况而言,则主要撷取郑玄《仪礼注》《礼记注》、贾公彦《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敖继公《仪礼集说》、方苞《仪礼析疑》《礼记析疑》、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等书,同时兼采历代其他学者研究成果汇纂而成。其中郑注一般出现在经文之后或《经典释文》之后,贾公彦《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朱熹《通解》的释语一般径称“疏曰”,方苞的释语一般径称“方子曰”,等等。此外,注释语料的出处还涉及其他一些学者,明代及之前的注家如崔灵恩、吕坤、邱濬、吴澄等,清代的注家如张尔岐、徐乾学、任启运等,但整体上都称引得很少。简言之,尹氏《探本》不以广征博引为著述要旨,一般征引自身认同的前人诠释观点,不同意见的则不予征引。另外,在同一经文的不同注释语之间,尹氏往往用“O”的标志分别开来,使读者不至于混淆。
又如,江苏常州学者秦蕙田(1702—1764)所著《五礼通考》亦是如此。和朱熹《通解》一样,秦氏《五礼通考》不以个性化的经文诠释考证为长,他对《仪礼》各篇经文的诠释,主要是通过征引汉代以来各家诠释文来实现的。从所引注释文献的来源看,秦氏征引最多的注释文献,清代以前主要有郑《注》、贾《疏》、朱熹《通解》、杨复《仪礼图》、敖继公《集说》、郝敬《集解》、陈祥道《礼书》;清代前期礼学著作援引最多的,则属张尔岐《句读》、盛世佐《集说》、蔡德晋《礼经本义》《钦定仪礼义疏》等几种出现最为频繁。而且,其援引敖继公《集说》、郝敬《集解》二家之说,并未像清初以来的许多学者那样,持所谓批判的诠释眼光,更多属于正面援引。
除各类私家著述受朱氏《通解》这一博征礼文前贤注文之诠释方式影响之外,清代乾隆年间官修之作《钦定仪礼义疏》同样受其影响。《仪礼义疏》采掇群言分为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七个义例①,对于历代礼学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分析,然后胪列于每一义例之下,这样就使得全书的类目非常清晰,编著者的立论与各种不同见解都得到妥善的安置,即使是纂修者所不拟采信之说,也都列于“存疑”“存异”之中,大体上反映出了前人已有的各种成说,颇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其搜罗之功亦不可没。与此编纂义例相应,该书在书写上采取大小写相分别的方式,“贾《疏》释《注》者双行小书,各分附本注之下,后儒说有与《注》、《疏》相证相足者亦然。其推阐经义者,仍大书特列”②。举凡历代申解郑《注》之训语,皆用小字列出,其余则用大字书写。另外,《义疏》中注音及郑《注》中有关古今异文部分的内容,亦用小字书写,一并附于《仪礼》正文各句之后。
不过,清代也有少数“张扬朱学派”学者在礼文注释的征引上,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其中尤以江苏武进学者胡抡最为突出。在胡抡看来,“经传注解之繁简详略,颇费筹蹰。太略,诚恐读之者不得明晓,不受穷经之益;太详,又恐言之者不能醇粹,不免雅郑之差”①。胡氏所著《礼乐通考》嫌朱子《通解》征引古注过于烦琐,故没有延续朱子《通解》大量征引前贤文献注释的做法,其注释大量辑录之文献,更为强调“详而不失之于繁,简而不病于其略,斯为美耳”②,释义表述更趋简洁明了。在先秦典籍的古注认知上,胡氏亦有自己的合理价值判断:“慎之哉,考古之不可忽也!礼著于经,经牵于注,后世去古既远,非古注无以得其门,泥古注又苦于其杂,惟以经为主,而以理断之,不为旧说所惑,乃得考古之益耳。”③在胡抡看来,古注既有可取之处,所谓“非古注无以得其门”也;但亦不可全盘采录信从之,所谓“泥古注又苦于其杂”。因而,最为合理、科学的对待态度便是“惟以经为主,而以理断之,不为旧说所惑”。从这一认知观出发,胡抡对于所辑录之文献注释,包括《仪礼》经文的诠释在内,《通考》皆很少照搬古注,而是在参考糅合前贤诠释成果的基础上,另行用简洁的行文加以诠释说明。例如,《觐礼》:“侯氏裨冕,释币于祢。”郑注:“将觐,质明时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为上,其余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诸侯亦服焉。上公衮无升龙,侯伯鷩,子男毳,孤,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祢,谓行主迁主矣而云祢,亲之也。释币者,告将觐也。其释币,如聘大夫将受命释币于祢之礼。既则祝藏其币,归乃埋之于祧西阶之东。今文冕皆作絻。”而胡氏《通考》则小字注释云:“将觐之,质明时也。裨冕者,衮冕以下,五冕之通称也。祢,谓行主迁主矣而云祢,亲之也。释币者,告将觐也。”④将二者加以对比便可发现,胡氏的训释语源自郑玄《注》文,但表义更趋简洁,尽管如此,胡氏并未标明“郑《注》云”等一类字样。总体观察来看,《通考》的此类注释语,更多趋向于诠释礼经的礼节情况,而较少关注字词的意义诠释。
综上各部分可见,朱熹的礼经学认知及其著述《仪礼经传通解》,对清代学者的《仪礼》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特别是《通解》“纂集重构”的著述方式和著述手段,更是在清代前期、中期催生了“张扬朱学派”,影响甚为深远。无怪乎陈澧发出“朱子《通解》之书,纯是汉唐注疏之学”⑤的感慨。
一、朱熹礼经学思想的传承与影响
(一)朱熹关于《仪礼》成书问题之认知及影响
《朱子语类》卷八十五当中,提及朱熹对《仪礼》一书的成书问题的看法:“《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极细密,极周经处。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换言之,朱熹认为,今本所习《仪礼》十七篇并非成于一人制定而成,“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在逐渐赢得社会人士的认同之后,“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①。他所说的“圣人”,虽然没有说明具体是谁,推测可能是指周公、孔子之流。清代之时,遂有张尔岐、李光坡、蔡德晋、胡培翚、曹元弼等人坚持《仪礼》为周公所作说。例如,凌廷堪就指出:《仪礼》十七篇,乃是“礼之本经也”,“信非大圣人不能作也”②,“非周公制礼,则后世将无人伦”③。惠栋在《周易述》中也声称:“孔子当春秋之世,有天德而无天位,故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④晚清学者邵懿辰也指出,《仪礼》“本非一时一世而成,积久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旁皇周浃而曲得其次序,大体固周公为之也。其愈久而增多,则非尽周公为之也”⑤,“夫《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所谓《经礼》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时即礼文废阙,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汉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为定礼乐者,独取此十七篇以为教,配六艺而垂万世,则正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为天下之达礼耳”⑥。诸如此类的撰作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
至于《仪礼》经文所附的《传》《记》之文成书问题,《朱子语类》当中记载朱氏说:“子升问:‘《仪礼》《传》《记》是谁作?’曰:‘《传》是子夏作,《记》是子夏以后人作。’”①至于具体依据,朱氏没有详说,今人无从考述。然亦可考见,朱熹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比较传统的。清代之时,遂有《记》文不同撰者之说,如盛世佐、马的“汉儒窜入经师说”,刘沅的“汉儒纂辑遗文”说,黄以周的“七十子后学所记后仓所传”说,又有曹元弼的《传》文“子夏所作”说,等等。
(二)朱熹关于《仪礼》是否完本问题之认知及影响
《朱子语类》当中,提及朱熹对《仪礼》是否完本问题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礼书如仪礼,尚完备如他书”,但同时又指出:“先王之礼,今存者无几。”“今《仪礼》多是士礼,天子诸侯丧祭之礼皆不存,其中不过有些小朝聘燕飨之礼。自汉以来,凡天子之礼,皆是将士礼来增加为之。河间献王所得礼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诸侯之礼,故班固谓‘愈于推士礼以为天子、诸侯之礼者’。”“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十七篇同。郑康成注此十七篇,多举古文作某,则是他当时亦见此壁中之书。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无传焉!”②由这一番话语来看,朱熹是主张今本《仪礼》十七篇并非完本的。
受其影响,清代颇有一些学者亦主张《仪礼》非完帙之书。例如,《仪礼经传内编》卷九“士大夫投壶礼”下,姜兆锡申论说:“此亦燕以为乐而因以观德之礼,《周礼》不载,《小戴礼》之第四十篇实载之,而《大戴礼》亦有此篇。按:此当为《仪礼》经文而逸之耳,故今以类而附于射礼之后云。”③依姜氏看来,对《仪礼》经文性质的认定,并不局限于士礼的范畴,他以为汉初高堂生所传《仪礼》十七篇,当初就是残缺不全的,大小戴《礼记》所载“士大夫投壶礼”之文,其实当为“《仪礼》经文而逸之耳”,本质上讲,其实就是原本《仪礼》经文的一部分。盛世佐《仪礼集编·凡例》中也说:“礼书之存于今者,惟此经称完备,惜古文增多三十九篇,佚不传。然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修之司徒以节民性,为士大夫日用所不可阙者具在是矣,所亡惟军礼耳。”④盛氏以为,较之《周礼》,今本《仪礼》十七篇更称完备,其所“亡者惟军礼”之篇耳,只不过所亡佚的军礼部分在汉代便已无人传习,散佚至今不复可见。将二氏之说与朱熹的话语进行对比便能发现,他们之间的说法是大体一致的。
(三)朱熹关于《仪礼》与《礼记》关系之认知及影响
《仪礼》与《礼记》之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礼经学问题。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朱子语类》多次言及朱熹关于二者的认知观点:“《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①“《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无《士相见义》。后来刘原父补成一篇。”②“《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许多理皆无安著处。”③朱熹的这些观点,在清初学者当中不乏认同者,如浙江鄞县学者万斯大(1633—1683)认为:“《仪礼》一经,与《礼记》相表里。考仪文,则《仪礼》为备;言义理,则《礼记》为经。在圣人即吾心之义理而渐著之为仪文,在后人必通达其仪文而后得明其义理。故读《礼记》而不知《仪礼》,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也。悬空无据,岂能贯通。”④此一认识,可谓是对朱熹思想的承继与发挥。因而,在其《仪礼》学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仪礼》与《礼记》相发明,强调以《礼记》解《仪礼》,“《仪礼》之义,固有即《仪礼》而可考者,况又有《礼记》可相发明哉?”而对《周礼》,则不甚强调,以为“《仪礼》、《礼记》与《周礼》决不可通,故置弗论不宣。”⑤另外,江永的外甥李光地也认为:“礼有经有传,《仪礼》,礼之经也;《礼记》,礼之传也。”⑥可以看出,这一思想无疑与万斯大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承续了朱熹在此问题上的主张、意见。
(四)朱熹《仪礼》与《周礼》之关系认知及影响
对于《仪礼》与《周礼》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朱熹曾经在《乞修三礼剳子》当中指出:“《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⑦受其影响,清代也有少数学者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如清初儒臣方苞就明确主张:“《仪礼》所详,礼之细目也;《周官》所布,礼之大纲也。”①稍晚于方苞的江苏无锡学者蔡德晋与之看法大致相类:“《周官》为礼之纲领,《仪礼》为礼之条目。”②据此,不少学者在对《仪礼》经文的诠释当中,往往注重《周礼》与《仪礼》礼文的互证工作,通过《周礼》相关文献材料的考察,发明《仪礼》经义所在。
二、《通解》通释体类体式的影响
从文献整理体式情况看,朱氏《通解》主要采取通释体的编纂体式著述而成。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在篇章设计上,《通解》并没有以《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所称述的“吉、凶、宾、军、嘉”的“五礼”分类模式进行编排,而是以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的模式进行篇章编排的,这大体是对《仪礼》各篇进行分类之后而确定的模式,即以《士冠礼》《士昏礼》为家礼,以《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为乡礼,以《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为邦国礼,以《觐礼》为王朝礼,以《丧服》《士丧礼》《士虞礼》归于丧礼,以《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归于祭礼。这和东汉的郑玄开始将《仪礼》各章分别归于五礼系统的思路全然不同。究其目的而言,在于通过调整全书的篇章结构次序,“以达到建构礼学思想体系的目的”③这样一种诠释策略。
二是在内容编排上,《通解》各篇大多以“经”“传”(或“记”)、“注”三方面的内容成篇。对于《仪礼》诸篇,朱熹尤其强调与之相关的“义”篇的延续与重构。例如,《通解》为《士冠礼》篇编纂《冠义》一篇,不仅吸纳了《小戴礼·冠义》一篇礼文,同时又因《孔子家语·冠颂篇》略见天子、诸侯、大夫之礼,《小戴礼·曾子问》中有变礼,《春秋》内外传有事证,故朱氏据此糅合而成此篇。再如,《通解》纂辑《昏义》一文时,不仅吸收了《小戴礼·昏义》一篇礼文,同时又将《礼记·郊特牲》、《坊记》、《曾子问》及《诗经》、《春秋》内外传、《白虎通义》、《说苑》所说婚礼之义及其变节合之,糅合而成此篇。
三是在各类礼文的文献来源上,往往不拘于《仪礼》十七篇篇目的内容,突破经传的界限分别,贯通《三礼》,融会诸子史书,扩大古礼文献资料和解说材料的选取范围,从而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经补传、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就成为《通解》的一个鲜明特点。
受朱熹、黄榦、杨复等《通解》《通解续》这一著述体式特点的影响,清代前期、中期“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治学纷纷据此进行效仿,以纂集重构出符合自身礼制思想的一部新的礼经学著作。例如,姜兆锡所著《仪礼经传内外编》便是一部相类似的著作。姜兆锡在该书《自序》中就说:“兹编实奉朱子遗训,以其所编家乡邦国王朝之礼,用勉斋丧、祭二礼之例以通之,不袭其迹而师其意。”①这就点明了《内外编》在体例上源于《通解》和《续通解》,但姜氏却又有所调整变动。若分类言之,该书的编纂著述体例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全面观照:
其一,从“五礼”的分章布局情况来看。《内编》23卷,前22卷依次为嘉礼、军礼、宾礼、凶礼、吉礼,其中嘉礼、军礼、凶礼三者皆举纲统目,嘉礼分冠昏之礼、饮食之礼、飨燕之礼、宾射之礼、脤膰之礼、贺庆之礼,军礼分大封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师之礼,凶礼分丧礼、荒礼、吊礼、禬礼、恤礼;而宾礼、吉礼二者皆第举目,宾礼约以朝、聘之属统之,而吉礼约以人鬼天神地示之属统之,具体而言,则宾礼分朝觐之属之礼、聘问之属之礼,吉礼分享人鬼礼、祀天神礼、祭地示礼、因事之祭、类祭之事、因祭之事。第23卷,附庶民入小学礼、国子入小学礼、国子暨民俊入大学礼、弟子职礼、凡小学、大学简升礼、世子豫教礼、诸侯元年即位礼、王元年即位礼等九礼。《外编》5卷,卷一、卷二为《丧服》上下,卷三《丧服补》,别采经四篇;后附《五礼分合图考》,包括嘉礼图考、军礼图考、宾礼图考、凶礼图考、吉礼图考、后附图考、五礼总图考。
其二,从具体礼类的编排情况来看,《内外编》有源于《通解》《通解续》之处,但姜氏却又有所调整变动。例如,该书“丧礼”部分,《通解续》尝采《丧大记》及各经传之属,通将王侯大夫等丧礼、虞礼总汇为一篇,名之曰《丧大记》,又通将王侯大夫等卒哭祔练祥禫各礼汇为一篇,名之曰《卒哭祔练祥记》,而于王侯大夫等未以类分编;而姜兆锡《内编》卷十四、卷十五则参考其文,分丧礼为《大夫丧礼》《诸侯丧礼》《王丧礼》三类,而虞礼及卒哭祔练祥禫各礼之不可考者,仍总次为《记》,并略加参议其间。又如“馈食礼”部分,姜氏《内编》分《上大夫馈食礼》和《下大夫馈食礼》两类目,分别载于《内编》之卷十九和卷二十。凡此之类,都体现出姜氏在全书分门别类方面更趋细密、合理。
其三,从《仪礼》十七篇经文的整合情况来看。姜氏根据十七篇经文的礼类归属情况,依次将其归入相应的部类之下,《仪礼》中的《记》文也不再出现在对应十七篇经文之后,而是作为“本记”条文,附之于相应仪节经文之后。例如,《士冠礼》一文,本经保留了相对的完整性,姜氏只是将其中诸辞及《记》文作为“本记”之文,归附在各分节的具体仪文之后;至于《燕礼》《公食大夫礼》《士相见礼》诸篇经文,姜氏以为“每篇当分为诸礼,不得相统”,故而原有完整的经文不再保留篇目经文的完整性,而是被分解到相应的礼类之下。如《燕礼》一篇,姜氏将其拆分为“诸侯燕大夫礼”和“诸侯燕聘大夫礼”二礼类,分别为之分章节次。
其四,从各大礼类的文献重构情况来看。姜兆锡对各大礼类的文献重构,完全统一于具体礼制建构的需要,从各类经书和准经书中去寻找与摘录文献素材,而被列入其中的文献材料经过新的排列组合,相当程度上具有了经的权威性,姜氏将这类经文称之为“参补之经”。例如,《内编》卷十“宾礼”之“诸侯会同礼”,礼文原本阙而不备,姜氏汇考《周官·司仪》《掌客》诸职,参补为经,由此得以稍存“会同”之遗制;又“王时巡受朝礼”,礼文本阙,姜氏参《虞书》《周礼》《孔丛子》之文补足之;又“诸侯膳王礼”,礼文亦阙,姜氏取《周官·掌客》篇文补以为经。倘若某一礼类在传世文献当中无法找到具体的仪制记载,姜氏则阙而不录。如“饮食之礼”中的士族饮礼、大夫族饮礼、王食大夫礼、王食聘大夫礼、王食诸侯礼、王食牧伯礼、王食国宾礼,“飨燕之礼”中的本国大夫相飨礼、王大夫飨聘大夫礼、王大夫飨诸侯礼、诸侯飨大夫礼、王飨诸侯礼,等等,皆有细目而无正文。按照姜兆锡的说法,“参补之经”有四种情况:“有逸见他经而体例当升为经者,曰采补;虽见他经,而体稍不合者,曰参补;旁见书传,而体有未合者,曰姑补;散之书传,而合为编次者,曰汇补。”①这种文献重构的做法,与黄勉斋《通解续》单纯补经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亦更趋合理。
再如,山西绛州学者梁万方(?—1725)所著《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一书,卷帙浩繁,全书69卷,完全以朱子、黄榦《通解》《通解续》之书为宗,“梁君本其尊人遗稿,复加讨论编次,朱墨咿嚘中搜罗宏富,抉择精严,竭数十年之力,凡三脱稿而后成,洵可谓先圣之功臣、紫阳之嫡派矣”②。该书在著述体式上具有以下诸方面特点:
其一,从全书结构体例布局来看,大致承袭了《通解》的做法。梁氏“大致据杨复《序》文,谓朱子称黄榦所续丧、祭二礼‘规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书’而未暇,遂以榦之体例更朱子之体例,与榦书合为一编。补其阙文,删其冗复,正其讹误”①,因而他的《重刊》也延续了《通解》及《通解续》的编纂体例,其中《家礼》5卷、《乡礼》3卷、《学礼》12卷、《邦国礼》5卷、《王朝礼》15卷、《丧礼》16卷、《祭礼》13卷,凡69卷90篇。梁氏《凡例》云:“朱子原本于《觐礼》以下初名《仪礼集传集注》,亦无编次名目;黄先生于《丧》、《祭》二编加‘续’字另序篇次,今悉遵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式法,《觐礼》篇接前至《祭义》,共为九十篇,前后通彻,合成一书。”(第4条)由此可见,梁氏并未更改朱子、黄氏之书的著述体例与主体编排结构。
其二,从《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诸类目的各自礼篇设置上,完全相同于朱子《通解》,而且在《仪礼》各篇之后,均仿朱氏的做法,每一篇之后设置一篇《义》文,如《士冠礼》之后,从小戴《礼记》之移入《冠义》之文;《燕礼》之后,从小戴《礼记》之移入《燕义》之文。倘若《礼记》没有《义》篇,则仍沿袭朱子的做法,从其他儒家经传删节补入,如《学礼》部分,《学制》一文之后,没有现存的《学义》文可以照搬,朱子乃“集诸经传凡言教法之意者补之,以释上篇之义”②,而梁氏《重刊》亦据此加以仿效编订其文;又如,梁氏补《丧服义》篇,乃谓“礼篇如《冠》《昏》《饮》《射》《燕》《食》《聘》《朝》皆有《义》,皆汉儒所造以释礼者,既列于经,今观小戴《丧服四制》、《三年问》、《服问》等篇,大抵皆要其义言之者,故悉取其文并他篇书记之言《丧服》起义者合之为此篇”③。
其三,对于《通解》《通解续》的缺额部分,梁氏深以为憾,他有意仿照朱熹《通解》的编撰体例进行了增补,诚如《重刊》中《凡例》部分第3条云:“旧本自《践阼》至《王制》之癸,共30篇,序、题皆缺;又《丧》、《祭》二礼亦多缺,今细探本篇之阃奥,联络上下篇之旨趣,以统贯其所采经书,仿朱子前式而补之。总书于纲领者,使学者一览而全义可洞悉也;后仍逐篇录入卷首者,所以使学者每读一篇,先领会其大义也。”
其四,考该书《凡例》第5条云:“此书旧名《仪礼经传通解》,今间有删订,亦悉本朱子之意;其附入诸家说及补注附按者,皆体会朱子平时所言之意旨,以发明经传之义理耳,不敢有更张也。”可见,在对待《通解》《通解续》原本辑录之材料和注释按语的处置方式上,梁氏《重刊》并未完全舍弃不用,而是略加删订而成,即使是需要补充其他文献材料及相关注释者,亦尽可能效仿原书编排之体例,不做大的改动。
其五,在自身注释语注释方式的编排上,梁氏《重刊》亦强调沿袭朱子《通解》的做法:“经义内注疏所解有未熨帖者,有旁及他说拘滞而乖大义者,朱子皆发明订正,冠以‘今按’二字。今敬仿之,用‘附按’字为别。”(《凡例》第11条)一个“敬仿之”的处置态度,亦表露出万方对于朱熹治学态度的推崇和敬重。
此外,为了体现自身治学对于朱氏学术的尊崇与重视,梁氏还将朱子有关诸经的注释成果吸纳到《重刊》中来,诚如万方在该书《凡例》第13条所说:“朱子前编引《四书》注皆用《集注》,《续》编犹有系《注疏》者,今悉改从朱注。又引《诗》皆改附朱子《集传》,引《易》改附朱子《本义》,引《书》改附九峰蔡氏《传》,一皆以至是为宗。”另外,第18条也说:“朱子凡有说《三礼》及《语类》所载说经传语,今皆各随其条下录入,而周子、程子、张子语亦然。若诸家精微之说,即皆采入,用一‘附’字别其原本。”
不过,清代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这一类治学方式的艰难,他们指出,这种文献的大批量纂集重构的方式极易于陷入“汙漫之书抄”的治学困境,需要治学者拥有高超的学术识见。如汪绂(1692—1759)在给江永的信中就颇有饬议之言:“大抵有明先辈,类多融贯全经,故时艺非必引用经文,而无非六经精义。后人专求工于时艺,而无暇以穷经,故满纸引用经言,究无当于经义。……今人因时艺而讲经学,亦已傎矣。况乃弃经学不讲,而从事于汙漫之书抄,不亦伤乎?”①认为当时的许多这类书籍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污漫之书抄”,其实质是“弃经学不讲”的一种做法。因为在汪氏看来,如果无法形成一种有价值的礼学体系,这种纂集重构就形同于彻底失败了。另外,清初学者姚际恒对于这一类诠释策略之作亦颇不认同,并大加抵斥说:“吾实不解作者意指,以为尊《仪礼》耶?全录《注疏》毫无发明,一抄书吏可为也,尊之之义安在?以裁割《礼记》《周礼》史传等书附益之为能耶?检摘事迹可相类者合于一处,不别是非同异,粗识文字童子亦可为也,又何以为能?其于无可合者则分家、乡、学、邦国、王朝等名,凭臆变乱,牵强填塞,此全属纂辑类书伎俩,使经义破碎支离,何益于学?何益于治?”①姚氏的这一番话似有失公允,他忽略了群经与《仪礼》之间具有互贯融通的学术特征,因而并未得到当时学者的积极响应,清代前期、中期“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治学风格便颇具强大的学术生命力,涌现了不少此类著述。
三、《通解》礼经“分节”的影响
清人陈澧曾经说:“《仪礼》难读。昔人读之之法,略有数端:一曰分节,二曰绘图,三曰释例。今人生古人后,得其法以读之,通次经不难矣。”②为经文划分章节是礼经仪制训诂的一种特殊方式,正所谓“章次不分,则礼之始终度数与宾尸介绍,冠服玉帛牲牢尊俎之陈,如满屋散钱,毫无条贯”③。考察历代《仪礼》类诠释文献,注释家对《仪礼》采用“分节”的注释方式,起源较早。
关于《仪礼》本经的分节源始,清初学者盛世佐认为:“分节法昉于《通解》,而后之说《仪礼》者多遵之,以其便于读者也。”④然而后来广东番禺学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仪礼篇》中纠正其说称:“《士冠礼》:‘筮于庙门。’贾《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毕”一节,论将行冠礼,先筮取日之事。’贾《疏》全部皆如此。此读《仪礼》第一要法也。《有司彻》郑《注》屡言‘自某句至某句’,此贾《疏》分节之法所自出也。”⑤据此,则是郑玄《仪礼注》第一次采用这一方法对《仪礼》经文进行分节,但仅仅限于少数篇目,而贾公彦《仪礼疏》则是全部采用“分节”之法诠释礼经十七篇。
倘若将贾公彦《仪礼疏》和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进行比对,就能发现,在标注分节的位置上,二者是有差异的。贾公彦《疏》往往在每一节的第一句话之后,标云“自此至某句,论某事”;而朱熹《通解》则在每一节经文的末端,另起一行标云“右某事”,如该书卷一《士冠礼》篇,朱氏《通解》屡称“右筮日”“右戒宾”“右筮宾”“右宿宾”之类。从形式上看,朱熹《通解》的分节诠释功能特征更加鲜明,而贾《疏》的“分节”更类似于现代中学语文课分段和概括段落大意的做法。
根据陈澧《东塾读书记·仪礼篇》的考察,贾公彦《仪礼疏》的“分节”就已经相当细密了。例如《聘礼》一篇,贾氏《疏》屡云,“自此尽‘官具’,论聘人及用币之事”,“自此尽‘受书以行’,论陈币付使者之事”,“自此尽‘亦如之’,论宾与上介将行告祢之事”,等等。更有甚者,《特牲馈食礼》篇贾《疏》有分节者称:“自此尽‘卒复位’,论宾长献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妇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内,乃有十一爵:宾献尸,一也;主妇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妇,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妇,四也;主妇酢主人,五也;尸举奠爵酢宾长,六也;宾长献祝,七也;又献佐食,八也;宾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妇,十也;宾献主人酢,十一也。”①贾氏不仅总括此节主旨,更将此节经文的“献酢”活动,总结分解为十一环节,极其细密。针对贾氏这种分节的注解方式,陈澧感慨地说:“此一科而分十一节也。《有司彻》疏,如此类者最多,不可枚举。其分析细密,使读之者心目俱朗彻矣。”②
至于朱熹《通解》,其各篇的分节较之贾氏《疏》更加细密。以《士冠礼》一篇为例,贾《疏》仅分11节,已经称得上是颇为细密的了,然而朱子《通解》则更为详细具体,共分为筮日、戒宾、筮宾、宿宾、为期、陈器服、即位、迎宾、始加、再加、三加、醴冠者、冠者见母、字冠者、宾出就次、冠者见兄弟姑姊、奠挚于君乡大夫乡先生、醴宾、醮、杀、孤子冠、庶子冠、母不在、女子笄,凡24节。更能彰显朱子《通解》“分节”解经功能的是,朱熹将《士冠礼》一篇原本属于经文的“戒宾辞”“宿宾辞”“始加祝辞”“再加祝辞”“三加祝辞”“字辞”“醮辞”等,完全放置在相应一节概述性文字(指“右筮日”“右戒宾”)的后面,二者之间用“O”隔离开,既彰显出这些“辞”的解经性质,又对帮助理解具体某一节经文有很大的裨益。
朱熹《通解》给《仪礼》经文分节并在节段后面标注节旨的做法,对清代前期、中期学者的治学影响较大,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江永《礼书纲目》、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等诸多礼经文献,均延续了《通解》的这一注释方式。以《仪礼郑注句读》中《燕礼》一篇的分节情况为例,张氏将该篇经文分成五个部分,自首句至“公升就席”为第一部分,张氏在首句下说:“自此之‘公升就席’,皆燕初戒备之事,有戒与设具,有纳诸臣立于其位,有命大夫为宾,有请命执役,有纳宾,凡五节。”自“宾升自西阶,主人亦升自西阶”至“以虚爵降,奠于篚”为第二部分,张氏云:“自此至‘以虚爵降,奠于篚’,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献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宾,二人媵觯于公,公取媵觯酬宾,遂旅酬,凡七节,此初燕之盛礼也。”自“主人洗,升,实散,献卿于西阶上”至“降奠于篚”为第三部分,张氏在该部分首句下云:“自此至‘降奠于篚’,主人献卿,又二大夫媵觯于公,公又举媵酬宾若长,遂旅酬,凡三节。”自“射人自阼阶下请立司正”至“无算乐”为第四部分,张氏云:“自此至‘无算乐’,皆坐燕尽欢之事,既立司正安宾,次主人献士及旅食,次或射以乐宾,次宾媵觯于公为士举旅酬,次主人献庶子以下诸臣,乃行无算爵无算乐,凡六节,而燕礼备。”自“公与客燕”至经正文结束为第五部分,张氏又云:“此下言国君将与异国臣燕,使大夫就馆戒宾,及客应对之辞,其仪节与燕本国诸臣同,唯戒宾为异,故于礼末见之。”除了在每一部分首句下解释段落划分情况外,张氏还在每一部分各小节正文下,另起一行总结每小节之大旨,与整个部分的划分相呼应,使全文纲举目张,层次分明,增强了可读性。考察吴廷华《仪礼章句》、江永《礼书纲目》、徐乾学《读礼通考》等礼类文献的经文分节情况,亦大多类似此书的做法。
至于《仪礼·记》文的分节之源始,则并非始于朱熹等人的《通解》《通解续》之书。盛世佐在《仪礼集编·凡例》中申称:“《记》文旧不分章,张氏《句读》始分之。”①考贾公彦《仪礼疏》,尽管他对《仪礼》经文有具体“分节”,但在注释《记》文时,却未进行分节。至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更是将《记》文分解开来,放置到相应的经文分节文段总括语之后,用“○”隔开,将其和《礼记》之类解经性质的语料放置一块,便利于读者深层次理解经义。简言之,朱子并未对《仪礼·记》文分节。因此,盛氏谓《记》文分章始于张尔岐著述《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应该是可信的。
以《特牲馈食礼》篇为例,张尔岐将该篇《记》文,共分为8节,依次为“记祭时衣冠”,“记器具品物陈设之法”,“记事尸之礼”,“记佐食所事因及宗人佐食齿列”,“记设内尊与内兄弟面位旅酬赞荐诸仪”,“记祭灶之节”,“记宾送尸反位之节”,“记诸俎牲体之名数”②。较之贾公彦《仪礼疏》不分节《记》文的做法,张氏《句读》要合理得多;较之朱熹《通解》将《记》文附载在各节之后的做法,张氏《句读》更突出了《记》文自身的独立性,但从彰显《记》文原本补充注释经文的功能来说,张氏《句读》这一处置方式可能还不如朱熹《通解》更加直观便利。
至于各家“张扬朱学派”学者的同类之作,亦大致相类似,纷纷强调对礼经经文的“分节”诠释工作。例如,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纂集之各篇礼文部分,梁氏亦延续朱子《通解》的做法,仿效章句体著作的编纂方式,厘析经文划分章节次第,每一节之后题云右某事之类,“旧本分截章法,但云右某某,今仿朱子分《中庸》之例,每篇自第一章起,次第至末,凡若干章;又于篇下统注几章,每章细注几条,及章下分注又几条,总期贯彻详明”(《凡例》第17条)。
至于清代中期以后的许多著作,由于著述大多以“释难解纷”“订误质疑”为治学要务,不再以强调对礼文的“纂集重构”,“从结构入手,通过调整全书的篇章结构次序,以达到建构礼学思想体系的目的”①为诠释策略手段,朱氏《通解》给礼经“分节”的做法影响才渐趋淡化,不再成为一种著述时尚。
四、《通解》礼文博征注文的影响
作为一部通释体著作,《通解》一书并不以精深的礼文注释见长,不以发覆礼文内容的心得见解为主要诠释手段。对于收录《通解》经、传两大块的各种文献原文的诠释,朱熹往往采用随文训诂的方式,收录郑玄注、贾公彦疏、孔颖达疏等历代前贤的诠释成说,然后再以“今按”“今详”的形式,对各家说法加以评点、申述或补充。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通解》在注文方面,一是保留了汉唐注疏的内容,特别是对郑玄《三礼注》的全文照录,被后人看作朱子‘服膺郑学’的体现。同时又多有评说、疑义和申述,常称‘疏说恐非’‘疏说非’‘疑孔说是’等,并且吸收和称引当时礼家之言见解,如称引‘程子曰’‘陈氏曰’‘陆氏说为是’‘张子曰’,就是对诸如陆佃、吕大临、张载、陈祥道、程子、张淳、吕希哲等宋代学者的观点有所吸收。很显然,朱熹是以自己的礼学判断对前人的见解和说法加以辨析和继承的。”②
受这一博征礼文前贤注文之诠释方式的影响,清代颇有不少学者取用这一诠释手段。例如,清初浙江秀水学者盛世佐(1719—1755)所撰《仪礼集编》一书,便颇能彰显这一风格,具有如下几重特点:一是引书数量众多,涉及面广。据该书《凡例》称云,采自先秦迄于清代学者共197家著作,其中全解《仪礼》之作仅十数家,其余有关文集、语类、杂说及其他经解与《仪礼》相发明者,“务摭而录之,志在博收兼存异义,不专主一家言”①。二是众说编排次第颇有讲究,“一以时代为序,二说略同则录前而置后,后足以发前所未备,始兼录之”②。三是摭录众说但求详备,不求芟除异说。“京山郝氏尤好立异,所著《节解》一书掊击郑、贾不遗余力,而考据未精,穿凿已甚。今并录诸家之说,断以己意,亦欲去讲其非而求是耳,非敢与先儒角长短也”③。四是引用贾《疏》往往有所删改。《凡例》云:“朱子尝谓《仪礼疏》说得不甚分明,故《通解》所引用往往加以润色,后儒因之,于贾《疏》各有删改,今掇其胜于原文者著于篇而分注其下,曰从某书节本,盖不没其所自也。若其未经删改者及他讲师之说,则但去其冗长而已,不敢妄加增损致乖本旨。”④也就是说,《集编》引据贾《疏》情况不一,或据朱熹等人删改后的贾《疏》加以转引,或盛氏根据需要自行缩减冗长的贾《疏》之文加以引据,皆以不乖违贾《疏》本旨为要务。五是在援引郑《注》上,一般来说盛氏不予节省,但遇有重复之嫌的情况则删节之,用他的话说就是:“《乡射礼》文有与《乡饮酒礼》同者,《大射仪》有与《燕礼》《乡射礼》同者,郑氏各为之注,未免前后复出,今遇此等处,概从节去。”⑤六是在引用前人说解的同时,亦不排除引据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张尔岐、万斯大、朱彝尊、汪琬、毛奇龄、阎若璩、姜兆锡等人的著述研究见解,在《集编》中亦多有摭引。
又如,直隶博野学者尹嘉铨(1711—1782)所著《仪礼探本》亦是如此。对于所要诠释的礼经文本,尹氏《探本》的注解大都来源于前贤的相关文献注释。从文献研读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其文字释音,主要节录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语料;就行文释义情况而言,则主要撷取郑玄《仪礼注》《礼记注》、贾公彦《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敖继公《仪礼集说》、方苞《仪礼析疑》《礼记析疑》、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等书,同时兼采历代其他学者研究成果汇纂而成。其中郑注一般出现在经文之后或《经典释文》之后,贾公彦《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朱熹《通解》的释语一般径称“疏曰”,方苞的释语一般径称“方子曰”,等等。此外,注释语料的出处还涉及其他一些学者,明代及之前的注家如崔灵恩、吕坤、邱濬、吴澄等,清代的注家如张尔岐、徐乾学、任启运等,但整体上都称引得很少。简言之,尹氏《探本》不以广征博引为著述要旨,一般征引自身认同的前人诠释观点,不同意见的则不予征引。另外,在同一经文的不同注释语之间,尹氏往往用“O”的标志分别开来,使读者不至于混淆。
又如,江苏常州学者秦蕙田(1702—1764)所著《五礼通考》亦是如此。和朱熹《通解》一样,秦氏《五礼通考》不以个性化的经文诠释考证为长,他对《仪礼》各篇经文的诠释,主要是通过征引汉代以来各家诠释文来实现的。从所引注释文献的来源看,秦氏征引最多的注释文献,清代以前主要有郑《注》、贾《疏》、朱熹《通解》、杨复《仪礼图》、敖继公《集说》、郝敬《集解》、陈祥道《礼书》;清代前期礼学著作援引最多的,则属张尔岐《句读》、盛世佐《集说》、蔡德晋《礼经本义》《钦定仪礼义疏》等几种出现最为频繁。而且,其援引敖继公《集说》、郝敬《集解》二家之说,并未像清初以来的许多学者那样,持所谓批判的诠释眼光,更多属于正面援引。
除各类私家著述受朱氏《通解》这一博征礼文前贤注文之诠释方式影响之外,清代乾隆年间官修之作《钦定仪礼义疏》同样受其影响。《仪礼义疏》采掇群言分为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七个义例①,对于历代礼学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分析,然后胪列于每一义例之下,这样就使得全书的类目非常清晰,编著者的立论与各种不同见解都得到妥善的安置,即使是纂修者所不拟采信之说,也都列于“存疑”“存异”之中,大体上反映出了前人已有的各种成说,颇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其搜罗之功亦不可没。与此编纂义例相应,该书在书写上采取大小写相分别的方式,“贾《疏》释《注》者双行小书,各分附本注之下,后儒说有与《注》、《疏》相证相足者亦然。其推阐经义者,仍大书特列”②。举凡历代申解郑《注》之训语,皆用小字列出,其余则用大字书写。另外,《义疏》中注音及郑《注》中有关古今异文部分的内容,亦用小字书写,一并附于《仪礼》正文各句之后。
不过,清代也有少数“张扬朱学派”学者在礼文注释的征引上,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其中尤以江苏武进学者胡抡最为突出。在胡抡看来,“经传注解之繁简详略,颇费筹蹰。太略,诚恐读之者不得明晓,不受穷经之益;太详,又恐言之者不能醇粹,不免雅郑之差”①。胡氏所著《礼乐通考》嫌朱子《通解》征引古注过于烦琐,故没有延续朱子《通解》大量征引前贤文献注释的做法,其注释大量辑录之文献,更为强调“详而不失之于繁,简而不病于其略,斯为美耳”②,释义表述更趋简洁明了。在先秦典籍的古注认知上,胡氏亦有自己的合理价值判断:“慎之哉,考古之不可忽也!礼著于经,经牵于注,后世去古既远,非古注无以得其门,泥古注又苦于其杂,惟以经为主,而以理断之,不为旧说所惑,乃得考古之益耳。”③在胡抡看来,古注既有可取之处,所谓“非古注无以得其门”也;但亦不可全盘采录信从之,所谓“泥古注又苦于其杂”。因而,最为合理、科学的对待态度便是“惟以经为主,而以理断之,不为旧说所惑”。从这一认知观出发,胡抡对于所辑录之文献注释,包括《仪礼》经文的诠释在内,《通考》皆很少照搬古注,而是在参考糅合前贤诠释成果的基础上,另行用简洁的行文加以诠释说明。例如,《觐礼》:“侯氏裨冕,释币于祢。”郑注:“将觐,质明时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为上,其余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诸侯亦服焉。上公衮无升龙,侯伯鷩,子男毳,孤,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祢,谓行主迁主矣而云祢,亲之也。释币者,告将觐也。其释币,如聘大夫将受命释币于祢之礼。既则祝藏其币,归乃埋之于祧西阶之东。今文冕皆作絻。”而胡氏《通考》则小字注释云:“将觐之,质明时也。裨冕者,衮冕以下,五冕之通称也。祢,谓行主迁主矣而云祢,亲之也。释币者,告将觐也。”④将二者加以对比便可发现,胡氏的训释语源自郑玄《注》文,但表义更趋简洁,尽管如此,胡氏并未标明“郑《注》云”等一类字样。总体观察来看,《通考》的此类注释语,更多趋向于诠释礼经的礼节情况,而较少关注字词的意义诠释。
综上各部分可见,朱熹的礼经学认知及其著述《仪礼经传通解》,对清代学者的《仪礼》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特别是《通解》“纂集重构”的著述方式和著述手段,更是在清代前期、中期催生了“张扬朱学派”,影响甚为深远。无怪乎陈澧发出“朱子《通解》之书,纯是汉唐注疏之学”⑤的感慨。
附注
*作者简介:邓声国,井冈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清代礼学。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8页。
②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六《礼经释例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1—24页。
③凌廷堪:《拜周公言》,《校礼堂文集》卷五,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0页。
④惠栋:《周易述》卷十一《象传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册,第119页。
⑤邵懿辰:《论孔子定<礼>〈乐〉》,载《礼经通论》,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13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1页。
⑥邵懿辰:《论〈礼〉十七篇当从大戴之次本无阙佚》,载《礼经通论》,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13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0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四,《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89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99页。
③姜兆锡:《仪礼经传内外编》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87册,第310页。
④盛世佐:《仪礼集编》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5—6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四,《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88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99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朱子全书》第17册,第2940页。
④万斯大:《与陈令升书》,《仪礼商》附录所附。
⑤万斯大:《与陈令升书》,《仪礼商》附录所附。
⑥李光地:《礼记纂编序》,《榕村全集》卷二十,道光九年刊本。
⑦朱熹:《乞修三礼剳子》,《朱子全书》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①方苞:《仪礼析疑》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册,第122页。
②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③曾军:《义理与考据——清中期<礼记〉诠释的两种策略》,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3页。
①姜兆锡:《仪礼经传内外编》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87册,第169页。
①姜兆锡:《仪礼经传内外编》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87册,第177页。
②陈世倌:《<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序》,载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2册,第536页。
①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22页。
②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仪礼经传目录》卷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③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目录》,载《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2册,第564页。
①汪绂:《与江慎修论学书》,《双池文集》卷之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
①姚际恒:《仪礼通论·论旨》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86册,第30—31页。
②陈澧著,杨志刚点校:《东塾读书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8页。
③吴廷华此语系其子吴寿祺转述之语,见《皇清经解》本《仪礼章句》卷首。
④盛世佐:《仪礼集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5页。
⑤陈澧著,杨志刚点校:《东塾读书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8页。
①贾公彦:《仪礼注疏》卷四十五,《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85页。
②陈澧著,杨志刚点校:《东塾读书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9页。
①盛世佐:《仪礼集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5页。
②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卷十五,载刘晓东、杜泽逊编《清经解三编》第8册,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39—41页。
①曾军:《义理与考据——清中期〈礼记>诠释的两种策略》,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3页。
②王启发:《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及其礼学价值》,《炎黄文化研究》第3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①盛世佐:《仪礼集编》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3页。
②盛世佐:《仪礼集编》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3页。
③盛世佐:《仪礼集编》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4页。
④盛世佐:《仪礼集编》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4页。
⑤盛世佐:《仪礼集编》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4页。
①三礼馆诸儒在纂修《义疏》时,特别拟定了七大“义例”:“一曰正义,乃直解经义确然无疑者;二曰辨正,乃后儒驳正旧说至当不易者;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有所推阐;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又或已经驳论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废;六曰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起阵,或创为一说,虽未惬人心而不得不姑存之以资考辨;七曰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全篇而论之。”
②见《钦定仪礼义疏·凡例》。
①胡抡:《礼乐通考·凡例》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1册,第275页。
②胡抡:《礼乐通考·凡例》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1册,第275页。
③胡抡:《礼乐通考》卷之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1册,第291页。
④胡抡:《礼乐通考·宾礼·觐礼》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1册,第509页。
⑤陈澧著,杨志刚校点:《东塾读书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1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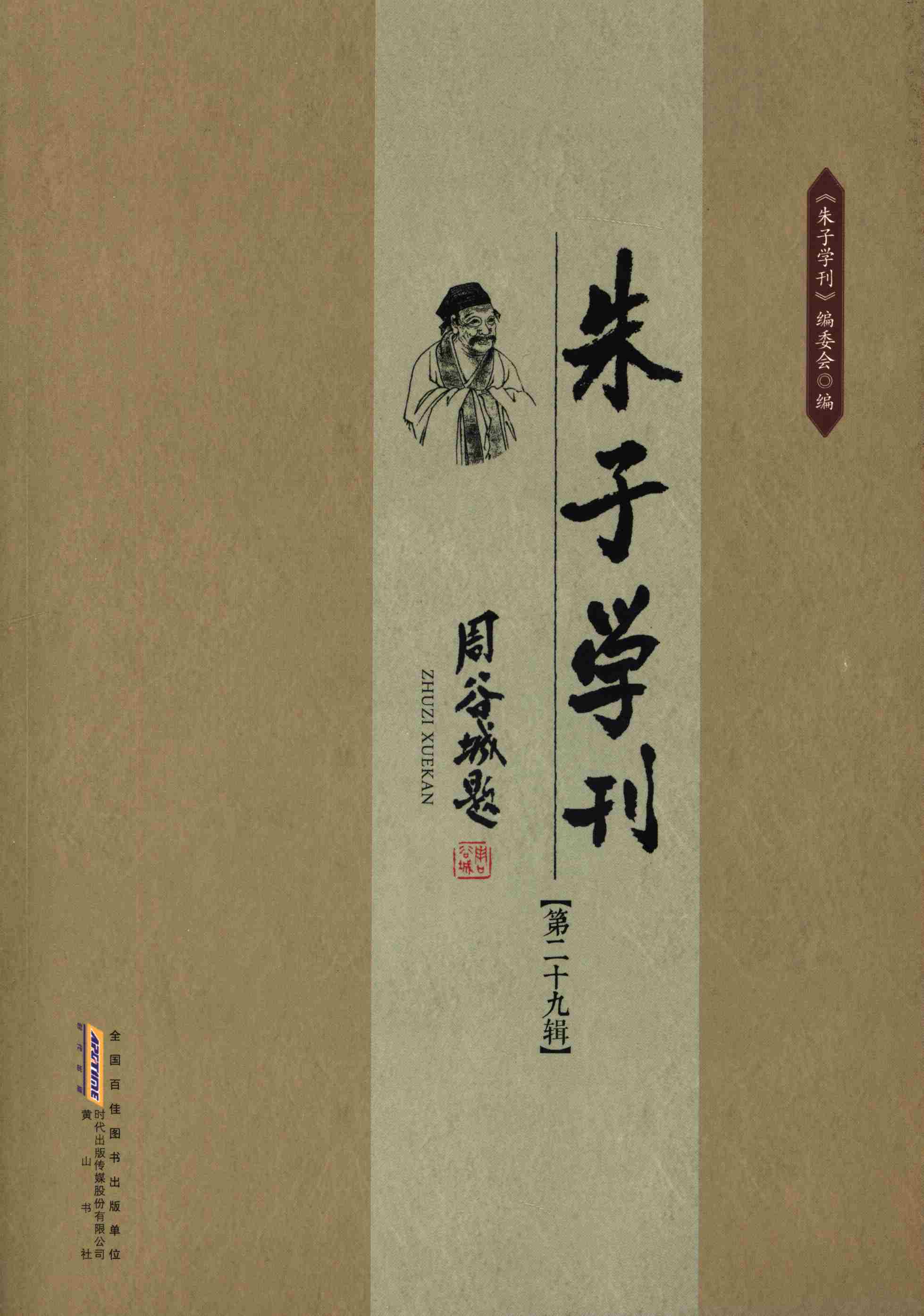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出版者:黄山书社
本书收录了《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学》《朱熹婚丧礼制的推行》《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戴震与朱熹关系平议》《陈北溪论“命”》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