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子建构体系的方法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227 |
| 颗粒名称: | 一、朱子建构体系的方法 |
| 分类号: | B244.7-55 |
| 页数: | 12 |
| 页码: | 013-024 |
| 摘要: | 本文主要讨论了朱子在建构自己的学问体系时所采用的方法学,特别是“以义理领导训诂”的方法。朱子以程子的理学为方向,选取和结合了四书、易学、周子之学等经典,并注入了自己的理学。通过比较法的方式,可以看出朱子的方法特色和其理学体系与其他学派的差异。 |
| 关键词: | 朱子 理气论 矛盾 |
内容
(一)“以义理领导训诂”
朱子之学问建构以“四书”为中心,一方面,对于四本书的选取与结合,此中便已预设了方法;另一方面,在“四书”的诠释中,又注入了理学。而对“四书”进行体系建构之后,又扩展到《易经》诠释、周子之学的诠释、北宋四子等人的诠释,以此为中心遂而开展出其自家体系。朱子所采方法有增字诠释、有以外部经典为据而为诠释,如以《大学》诠释《论》《孟》等等,然归结其重点,即是“以义理领导训诂”,至于其中心义理,就是理气论,也可以说是一种体用论。这是先秦所无,而为理学家的创新体系。下文将一一述之。
若将朱子于经典的诠释与清儒相比,则有汉、宋之争的不同。经典之原意当该只有一种,为何在各家诠释下会有不同,而不能归一?笔者以为,若以经典之原意为判准,则朱子学常不是原意,而是一种体系的建构,此体系之建构是顺着二程而来的理学,而把理气论置入于经典之中,包括“四书”、《易经》等。其方法即是“以义理领导训诂”,例如,格物的“格”字当该如何训解,则以合于理学的字义诠释者为佳。
至于理气论,也是一种体用义,亦是建构而来。先秦虽有“体”“用”二字,但两者并不对待,例如,《易经》的“用九”,并无“体九”与之对待,“君子体仁”,并无“君子用仁”与之对待;又如老子言“当其无,有车之用”,并无“车之体”与之为对。
故此体用之义可溯源至佛、老,如《大乘起信论》言“体大、用大、相大”。更早本是魏晋玄学为了解决“自然”与“名教”之冲突而来,把“自然”“无为”放在体处,“名教”放在用处;如王弼的“崇本举末”,因着“道”与“德”的自然无为,故可以举仁义礼智,仁义之有为,以无为之体为根,则能无所不为。故仁而无为,则为上仁,大德不德、大仁不仁。此是魏晋玄义的发展。到了宋代则广泛使用,如《易程传·序》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说,张子批佛老“体用殊绝”,而这体用之说朱子宗之。
因此,朱子的经典诠释之设计,是把理学置入于经典中,而此理学又是先秦所无。虽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子的理学是一种精神,理气等字义虽先秦少言,但其精神是合于先秦儒家的。笔者对此并不表认可。例如,于孟、告之辨,孟子所言性善,是人类为性善,犬牛则无可谓性善。而到了朱子的创造性诠释,却是犬牛亦为性善,只是气昏,表现得少,表现得少而不可说无性善。故朱子喜谈羔羊跪乳之说,代表动物亦有孝,亦有性善。
总之,朱子的学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其建构方法是把经典与理气论结合,采取“以义理领导训诂”的方式,而将自家义理置入其中。以下,试举出几点,以见其字义之诂训具有选择性,若是其他诠释家则未必采取朱子的说法。
(二)删改原文
在《四库全书》提要,提到杨慈湖之易学时,认为杂有佛老,于是言“存之,正所以废之”(指保存慈湖之书,以让后人见识到他真受佛老影响)。其中引到朱子之说,曰:“昔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不删郑康成所引谶纬之说,谓存之正所以废之,盖其名既重,不存其说,人无由知其失也。”这里提到,朱子解《仪礼》时,保存了郑玄之说,以郑玄之说杂有谶纬迷信,不删正以明示后人,所谓的“存之,正所以废之”,以其说掺有神道天文地理的迷信之言,朱子自信其说必废,而不消假于自手,存之以示世人,世人必将废之。
朱子在面对郑玄的著作时,有如此的自信,信其必废,为何在面对其他著作时却不愿保留?例如,于《南轩文集》,朱子略删,而称之为“淳熙甲辰本”;又对胡宏的《知言》亦有疑,与张栻、吕祖谦之书信往来商讨,而作《知言疑义》,建议删去部分文字;又面对周子《太极图说》版本问题,保留“无极而太极”本,却要删掉“自无极而为太极”版本。
这些作品,朱子都有意要删除一些文字,与其面对郑玄之杂有谶纬作品时,态度不同。何以不同?朱子认为郑玄之说,存之足以废之,而面对南轩、五峰、及另一版本《太极图说》,却无此自信,则是存之不足以废之,存之适足以反对自家见解,故朱子不如删之。
朱子为何取“无极而太极”而不取“自无极而为太极”呢?乃因理气论可用以诠释《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之见解,而与“自无极而为太极”之说则有抵触。如此一来,则朱子所尊之二程理学可以保留下来,而二程之师周子亦可顺理成章地成为理学宗师。此外,也因为与梭山、象山的无极太极论辩,若保留七字版“自无极而为太极”,此则为“无生有”,恰与老子的学说相似,则将造成《太极图说》不是理学作品、不是儒家作品,反倒近于象山所言《太极图说》是近于道家、道教的作品了。故朱子有必要做此删改。
又如面对胡宏的《知言》,朱子所做的《知言疑义》亦是如此。《知言》一书所删之处,主要是不合于朱子的体系,朱子做《知言疑义》,往复与吕祖谦、张栻书信之中而做讨论,其中张栻常为朱子所转,顺朱子之说而提议删改,至于吕祖谦则较为厚道,认为应多保留原文。
朱子提到《知言》时的评论是:“《知言》疑义,大端有八;性无善恶,心为已发,仁以用言,心以用尽,不事涵养,先务知识,气象迫狭,语论过高。”以上这些看法刚好与朱子的见解抵触,试分析如下:
1.“性无善恶”:朱子认为性即理,天理至善而不可言无善无恶。
2.“心为已发”:胡宏所言“心为已发”,乃朱子的中和旧说,性体心用,
心为用,故为已发。但后来朱子改正其说,“新说”视心统性情,情可言已发,而心则不见得已发,如本心,其为未发之中,乃心具理的原初状态,此不一定是已发。
3.“仁以用言”:在朱子,仁是体,不是用,故本于伊川“性中只有仁义礼智,何尝有孝弟”之说,而来批评胡宏,因为仁是性、是体,不可以用言。
4.“心以用尽”:胡宏的“尽心以成性”,朱子视为“心以用尽”。朱子以为,心不只是用,心有其体,有其用,情是心之用,性是心之体。
5.“不事涵养,先务知识”:此说亦与朱子不合,朱子认为,八岁入小学,先学一段涵养工夫,十五岁入大学,才学格物致知的工夫,故要先涵养,再求知识。
6.“气象迫狭,语论过高”:朱子的中和新说成立以后,心性情三分,用来涵养工夫,而为一种渐教,格物穷理亦是要天天积累;而胡宏的尽心成性,性体心用,没有涵养气象,没有工夫修养,而尽心就想知性,近于顿教,而被朱子视为“语论过高”,气象亦不悠游涵泳,而期于必悟,故为迫狭,指其没有下学上达之修养。
以上,都可说明朱子的取舍标准,是自己的理学;以理学体系为标准,来对其他见解或版本予以取舍,合于己者存,不合于己者则不见得要存,存之若不足以废之,则不存,因为存了胡宏某些话语,或是存了“自无极而为太极”的版本,适足以破坏了朱子体系。可见朱子正是以其体系为标准以建构哲学,这体系便是理气论!
(三)以改本《大学》重释《论》《孟》《庸》
《朱子语类》记载:
因言:“欲养浩然之气,则在于直。要得直,则在于集义。集义者,事事要得合义也。事事合义,则仰不愧,俯不怍。”赵又问:“‘夫有所受之也’是如何?”曰:“公如此看文字不得。且须逐项理会,理会这一项时,全不知有那一项,始得。读《大学》时,心只在《大学》上;读《论语》时,心只在《论语》上,更不可又去思量别项。”
此乃朱子与赵丞的对话,二人论及《不动心章》,而赵丞却语出“夫有所受之也”是如何?这已经超越了此章的范围,因为此句是《孟子》的另一章。而朱子认为,如此读书不切问近思,容易有误。若以朱子教人的读书法自是如此,面对一章一节,则不愿思其外。但若以《孟子》解《孟子》,也许赵丞之发问还不至于离谱。
然朱子自己立的法,即读此章则不思其外的方法,朱子自身是否遵守呢?例如,朱子的体系便是以《大学》诠释《论语》《孟子》,如此做法便已越出各部经典之外,已属外部诠释。再者,《大学》真的可以用来诠释《论》《孟》吗?
《大学》本是《礼记》一篇,有人视《礼记》为荀学系统,如船山认为《礼记·乐记》视乐为外来,而与孟子的“仁义礼智乐”为内在者不同。故以《大学》或《礼记》不见得能诠解《论语》《孟子》。
又伊藤仁斋认为,《论语》与《大学》有多处不合:
1.朱子的大学、小学之分于《论语》无据。在论述《论语·子夏之门人小子》处,朱子认为:“子游讥子夏弟子,于威仪容节之间则可矣。然此小学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学正心诚意之事,则无有。”即子夏只知教学生以小学的洒扫应对进退,而不知教之以大学正心诚意。而伊藤仁斋的质疑是,两人(子游、子夏)同学于孔门,而子夏知有小学、大学之分,而子张不知,岂真如此乎?此看出朱子以《大学》解《论语》之不恰当。
2.又《论语》提到“子在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依《大学》的标准,则孔子是心不正、心不在焉,以至于食而不知其味,故《大学》《论语》二书难以相入。
以上说明,朱子虽反对学生于章节之外做思考,要人读书专一于一处,不愿乎其外,于其所即之一段处切问,自己却以《大学》解《论》《孟》!这也看出,朱子的体系建构,即是置入理气论。朱子主张“四书”的修学顺序,要从《大学》入手,便是为配合自家以《大学》作为骨架,而填充入《论》《孟》《中庸》的体系建构。
而其方法,即是以义理领导训诂,其义理是理学,以理学领导训诂,故诠释“四书”时都以合于理学的方式来做建构。先在《大学》处删补经文以合于其体系(如格物穷理),再以《大学》为标准,而把《论》《孟》《中庸》都诠释为理学。
(四)增字诠释
朱子的体系建构,常常增字诠释。例如朱子与象山之争辩处,朱子对于“无极而太极”的诠释是无形而有理,而象山反对。象山针对朱子通过“然”与“所以然”的增字诠释法,用以诠释阴阳与太极,提出驳斥,象山言:
后书又谓“无极即是无形,太极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故着无极二字以明之”。《大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极乎!
若以《易传》诠释《易传》,此为内在建构,则不用取外在建构。朱子以《大学》解《孟子》,其实已是一种外在建构,若真以古本《大学》解《孟子》亦属接近,然朱子对《大学》所做修改太多,而启人疑窦。又若以《易传》诠释《易传》,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其中的“一阴一阳”与“形而上者”都是道,二者等同,亦即“一阴一阳”是为“形而上者”,而朱子却谓“一阴一阳”是“形而下者”,即视太极为形上、阴阳为形下!
朱子于书信中反驳象山,朱子的回答是:
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岂真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故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行,则谓之道。
面对象山对朱熹“形而上”“一阴一阳”解释的质疑,朱子以为都与本义有出入。朱子指出,阴阳不是形而上者,阴阳属形器而为形而下,于形而下(阴阳)之中,得以见所以然的形上之理(太极)。可见朱子对一阴一阳的诠释,乃是依于理气论而成,而此理气论又是依于二程的理论建构而来,故世称程朱理学。阴阳,器也,也同等于气;所以阴阳,道也,理也。但是《易传》原文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并未明言“所以阴阳者道也”,此以“然”与“所以然”的体系建构,是由程朱做成。
“然”与“所以然”的概念曾出现在《庄子》。《庄子·齐物论》谈到: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道家盛言自然,而不追问所以然;而朱子为儒家建构,于事物格物穷理,追问其所以然,即追问其天理,天理系理一分殊,落于事物,故即于世物上穷究之,事物是“然”,即是“如此”,于“如此”的事物上追问其背后的天理原因,即是其“所以然”。在此可从朱子与象山二人的诠释方法学比较中看出,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诠释而言,象山是以《易传》诠释《易传》,而朱子遵守程子之说,故用了外在诠释,以“然”与“所以然”的方法做诠释。这也是朱子的体系建构方法。
又举朱子于《论语·性相近章》增字诠释的例子,其注言: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孔子只说性相近,而朱子以气质之性诠释此相近之性,朱子已把性分别为两种,一种是天地之性,一种是气质之性,然这种区别必未是孔、孟的意思。朱子何以认为此处的相近之性是气质之性呢?因为他依于伊川见解,伊川认为天地之性,性即理,性是天理人人“相同”,何“相近”之有?若言相近,必不是谈天地之性,因为天地之性只能视为相同,而不可言相近,故相近也者,是为气质之性。此乃程朱的理气论置入于《论语》中而产生的创造性诠释,而且是一种增字诠释,把孔子所言之“性”,增字而为“气质之性”。
(五)析分一性而为二性
朱子析分一性而为二性的做法,除见于《论语》,尚可见于《孟子》。在诠释《孟子·生之谓性章》时,朱子言:
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
此处朱子将孟子的性义,诠释为有一种是性之为理,另一种是性之为气,孟子识性之为理,而告子不知,却以气为性。这又是把理气论置入于《孟子》诠释之中了。
又朱子于《告子上》前几章处,谈到荀子、扬雄、佛氏、告子、苏氏、胡氏、韩愈等人,视这些人都以气为性。由此亦看出朱子用二层的性以诠释《孟子》经典。天地之性,此性即理,是体、是天理;至于气质之性,则是此性落于气质之中,而此气质则为形下,是气。此以二元方式区分性的做法,未必是先秦的意思。若相比于戴震,戴震以性为血气心知,性亦是一元,而不必区分为二。
又如黄宗羲的见解,其顺着孙慎行之说,反对有二性,黄宗羲言:
别教有云:“丈夫食少金刚,终竟不消,要穿出身外,何以故?金刚不与身中杂秽同止。”故天命之性,岂特如金刚?一切清浊偏正刚柔缓急,皆拘他不得。如谓水本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不净器盛之则臭,以污泥之器盛之则浊,本然之清,未尝不在,但既臭浊,猝难得清。果若是,则水一性也,器一性也。性之夹杂如此,安所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乎!
黄宗羲认为,“天地之性”若能离于“气质”,则此取喻近于“金刚”不与“污秽”同处一般。此乃反对朱子二性之说,一种是天地之性,一种是气质之性,黄氏认为若如此区分,则性为挟杂,岂能称得上是“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可见黄宗羲对朱子学二性说的质疑。
朱子学的二性说确实非先秦原意,而是一种理学的建构,从另一角度看,此种建构能使儒学的生命化腐朽为神奇,从儒、佛、道之相遇中碰撞出新的火花,而为新儒学;也因着朱子的开展,成就了宋明儒学的道统新生命之延续。宋明儒者,无论宗朱、反朱,都围绕着朱子学问而开展,而朱子的学问核心,就在理气论。
于此再看一段孟子的原文,孟子谈到:
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孟子此段谈到“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亦是说孟子视“口之于味”也是“性”,只有一性,此一性担负了仁义之端及耳目口鼻之食色。故阳明视性是理气(道德与食色)合,较朱子为准确。
王船山亦视性是理气合。船山于注解张子《正蒙》“性其总,合两也”一段言:“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船山的气论认为,“盈天地皆器也”,天命之落于人而为性,性是理气合,而非如朱子所言,性只有理而无气(性即理,又说孟子不备气)。性中有理有气,其为理者,为仁义礼智;其为气者,为声色臭味。这也是船山的两端一致之说,合理、欲而为一性。故船山解张子所言的“性之合两”,即是合仁义道德与声色臭味而为一性,故亦可用一性以诠释孟子,而不用如朱子的二性说。
性之为一,而不需如朱子以二性诠释,于孟子原文已可明见。上文所引《富岁章》谈到,“口之于味”是“性”,故不必如朱子把“气化”区隔于性之外,而独成一天地之性;依于朱子,此性为理,纯善而无恶,又恶是气质后天所造成,乃天地之性落于气质中所造成。
朱子的二性区分可谓多此一举。先把气质隔于天地之性外,然后又说“孟子论性,终是不备”,而以程子之意为补充,补足其气质之性。笔者认为,朱子此举也可说是他所处时代之课题,其重视人的气质对人的影响,如魏晋的才性论之课题、如刘劭《人物志》之课题,视人之才性是否合于中正,而能力能否胜任官职以相人。又当时面对佛教的习气、无明等课题,而于儒家义理亦加入气质之性以扩充,此朱子从张子(气质之性)与二程(才)的义理发展而来。
又如朱子注《论语·其为人也孝弟章》,把其体用论注入于其中,其言: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程子曰:“……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
朱子认为,仁是“心之德,爱之理”,仁是性,是爱之情的所以然之理,是为体,而不是用,仁是性理中的一部分,故“为仁”只能解为“行仁”,而不可解为“是仁”,因为仁为体,最为根本,不能在仁之上还有一个孝弟作为其根本。也因为孝弟是用,而不是体,故性中只有仁义礼智,是为体,体中无用,孝弟是用,故性中无孝弟。这也是顺着程朱理气论之体系,因此“为仁”只能解为“行仁”。
为何说朱子的诠释是建构而成的呢?此与伊藤仁斋(1627—1705)之见解比较即可得知。伊藤乃江户时期日本古义派学者,用心于恢复《论语》古义,而认为朱子的诠释不是古义。于此章,其以《论语》解《论语》的内在建构,认为“本立道生”“孝弟为仁之本”,故“本”者为“孝弟”,“道”是指“仁”。如此,则不用如程朱所言仁为体为本,而孝弟为用为末,即不用如程子以仁论性,而为孝弟之本。
在伊藤仁斋而言,仁是道、也是德,是修己安人之道,是德之完成。心者、性者只有仁之端,而不是仁之全部体现。此乃伊藤对于仁说的诠释,而与朱子的仁是体是性、是形而上者不同。
由上可知,朱子的方法论是从外部引入理气论而来诠释《论语》,至于伊藤仁斋研究《论语》的方法则不高深穷微,而是平议地以《论语》解《论语》,最多以《孟子》解《论语》。朱子的做法乃是以理气论领导训诂,后来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之书写,即不取朱子的方法学,改以先秦时的字义来训解《孟子》。
(六)断句释文及先知后行
又朱子在断句时,也是以理气论领导训诂,朱子的《大学》设计,先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乃是一种先知后行的系统,但在《论语》,似有先行后知的说法,如《论语》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先行,而后学文,乃先行后知之说。而朱子不同意,故于此章注言:“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此诠释与《论语》语势完全不合,但合于朱子的理气论下的先知后行系统。
又《子贡问君子章》,孔子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程子的断句是:“先行,其言而后行之。”朱子不从,认为该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理由是,若断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乃为先行后言,或称为先行后知,与朱子的先知后行冲突。若改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则在行之时已有言,行与言(知)可为同时,则不至于成了“先行后知”之系统。于此可见朱子理论之选取,与其体系息息相关。
朱子之学问建构以“四书”为中心,一方面,对于四本书的选取与结合,此中便已预设了方法;另一方面,在“四书”的诠释中,又注入了理学。而对“四书”进行体系建构之后,又扩展到《易经》诠释、周子之学的诠释、北宋四子等人的诠释,以此为中心遂而开展出其自家体系。朱子所采方法有增字诠释、有以外部经典为据而为诠释,如以《大学》诠释《论》《孟》等等,然归结其重点,即是“以义理领导训诂”,至于其中心义理,就是理气论,也可以说是一种体用论。这是先秦所无,而为理学家的创新体系。下文将一一述之。
若将朱子于经典的诠释与清儒相比,则有汉、宋之争的不同。经典之原意当该只有一种,为何在各家诠释下会有不同,而不能归一?笔者以为,若以经典之原意为判准,则朱子学常不是原意,而是一种体系的建构,此体系之建构是顺着二程而来的理学,而把理气论置入于经典之中,包括“四书”、《易经》等。其方法即是“以义理领导训诂”,例如,格物的“格”字当该如何训解,则以合于理学的字义诠释者为佳。
至于理气论,也是一种体用义,亦是建构而来。先秦虽有“体”“用”二字,但两者并不对待,例如,《易经》的“用九”,并无“体九”与之对待,“君子体仁”,并无“君子用仁”与之对待;又如老子言“当其无,有车之用”,并无“车之体”与之为对。
故此体用之义可溯源至佛、老,如《大乘起信论》言“体大、用大、相大”。更早本是魏晋玄学为了解决“自然”与“名教”之冲突而来,把“自然”“无为”放在体处,“名教”放在用处;如王弼的“崇本举末”,因着“道”与“德”的自然无为,故可以举仁义礼智,仁义之有为,以无为之体为根,则能无所不为。故仁而无为,则为上仁,大德不德、大仁不仁。此是魏晋玄义的发展。到了宋代则广泛使用,如《易程传·序》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说,张子批佛老“体用殊绝”,而这体用之说朱子宗之。
因此,朱子的经典诠释之设计,是把理学置入于经典中,而此理学又是先秦所无。虽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子的理学是一种精神,理气等字义虽先秦少言,但其精神是合于先秦儒家的。笔者对此并不表认可。例如,于孟、告之辨,孟子所言性善,是人类为性善,犬牛则无可谓性善。而到了朱子的创造性诠释,却是犬牛亦为性善,只是气昏,表现得少,表现得少而不可说无性善。故朱子喜谈羔羊跪乳之说,代表动物亦有孝,亦有性善。
总之,朱子的学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其建构方法是把经典与理气论结合,采取“以义理领导训诂”的方式,而将自家义理置入其中。以下,试举出几点,以见其字义之诂训具有选择性,若是其他诠释家则未必采取朱子的说法。
(二)删改原文
在《四库全书》提要,提到杨慈湖之易学时,认为杂有佛老,于是言“存之,正所以废之”(指保存慈湖之书,以让后人见识到他真受佛老影响)。其中引到朱子之说,曰:“昔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不删郑康成所引谶纬之说,谓存之正所以废之,盖其名既重,不存其说,人无由知其失也。”这里提到,朱子解《仪礼》时,保存了郑玄之说,以郑玄之说杂有谶纬迷信,不删正以明示后人,所谓的“存之,正所以废之”,以其说掺有神道天文地理的迷信之言,朱子自信其说必废,而不消假于自手,存之以示世人,世人必将废之。
朱子在面对郑玄的著作时,有如此的自信,信其必废,为何在面对其他著作时却不愿保留?例如,于《南轩文集》,朱子略删,而称之为“淳熙甲辰本”;又对胡宏的《知言》亦有疑,与张栻、吕祖谦之书信往来商讨,而作《知言疑义》,建议删去部分文字;又面对周子《太极图说》版本问题,保留“无极而太极”本,却要删掉“自无极而为太极”版本。
这些作品,朱子都有意要删除一些文字,与其面对郑玄之杂有谶纬作品时,态度不同。何以不同?朱子认为郑玄之说,存之足以废之,而面对南轩、五峰、及另一版本《太极图说》,却无此自信,则是存之不足以废之,存之适足以反对自家见解,故朱子不如删之。
朱子为何取“无极而太极”而不取“自无极而为太极”呢?乃因理气论可用以诠释《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之见解,而与“自无极而为太极”之说则有抵触。如此一来,则朱子所尊之二程理学可以保留下来,而二程之师周子亦可顺理成章地成为理学宗师。此外,也因为与梭山、象山的无极太极论辩,若保留七字版“自无极而为太极”,此则为“无生有”,恰与老子的学说相似,则将造成《太极图说》不是理学作品、不是儒家作品,反倒近于象山所言《太极图说》是近于道家、道教的作品了。故朱子有必要做此删改。
又如面对胡宏的《知言》,朱子所做的《知言疑义》亦是如此。《知言》一书所删之处,主要是不合于朱子的体系,朱子做《知言疑义》,往复与吕祖谦、张栻书信之中而做讨论,其中张栻常为朱子所转,顺朱子之说而提议删改,至于吕祖谦则较为厚道,认为应多保留原文。
朱子提到《知言》时的评论是:“《知言》疑义,大端有八;性无善恶,心为已发,仁以用言,心以用尽,不事涵养,先务知识,气象迫狭,语论过高。”以上这些看法刚好与朱子的见解抵触,试分析如下:
1.“性无善恶”:朱子认为性即理,天理至善而不可言无善无恶。
2.“心为已发”:胡宏所言“心为已发”,乃朱子的中和旧说,性体心用,
心为用,故为已发。但后来朱子改正其说,“新说”视心统性情,情可言已发,而心则不见得已发,如本心,其为未发之中,乃心具理的原初状态,此不一定是已发。
3.“仁以用言”:在朱子,仁是体,不是用,故本于伊川“性中只有仁义礼智,何尝有孝弟”之说,而来批评胡宏,因为仁是性、是体,不可以用言。
4.“心以用尽”:胡宏的“尽心以成性”,朱子视为“心以用尽”。朱子以为,心不只是用,心有其体,有其用,情是心之用,性是心之体。
5.“不事涵养,先务知识”:此说亦与朱子不合,朱子认为,八岁入小学,先学一段涵养工夫,十五岁入大学,才学格物致知的工夫,故要先涵养,再求知识。
6.“气象迫狭,语论过高”:朱子的中和新说成立以后,心性情三分,用来涵养工夫,而为一种渐教,格物穷理亦是要天天积累;而胡宏的尽心成性,性体心用,没有涵养气象,没有工夫修养,而尽心就想知性,近于顿教,而被朱子视为“语论过高”,气象亦不悠游涵泳,而期于必悟,故为迫狭,指其没有下学上达之修养。
以上,都可说明朱子的取舍标准,是自己的理学;以理学体系为标准,来对其他见解或版本予以取舍,合于己者存,不合于己者则不见得要存,存之若不足以废之,则不存,因为存了胡宏某些话语,或是存了“自无极而为太极”的版本,适足以破坏了朱子体系。可见朱子正是以其体系为标准以建构哲学,这体系便是理气论!
(三)以改本《大学》重释《论》《孟》《庸》
《朱子语类》记载:
因言:“欲养浩然之气,则在于直。要得直,则在于集义。集义者,事事要得合义也。事事合义,则仰不愧,俯不怍。”赵又问:“‘夫有所受之也’是如何?”曰:“公如此看文字不得。且须逐项理会,理会这一项时,全不知有那一项,始得。读《大学》时,心只在《大学》上;读《论语》时,心只在《论语》上,更不可又去思量别项。”
此乃朱子与赵丞的对话,二人论及《不动心章》,而赵丞却语出“夫有所受之也”是如何?这已经超越了此章的范围,因为此句是《孟子》的另一章。而朱子认为,如此读书不切问近思,容易有误。若以朱子教人的读书法自是如此,面对一章一节,则不愿思其外。但若以《孟子》解《孟子》,也许赵丞之发问还不至于离谱。
然朱子自己立的法,即读此章则不思其外的方法,朱子自身是否遵守呢?例如,朱子的体系便是以《大学》诠释《论语》《孟子》,如此做法便已越出各部经典之外,已属外部诠释。再者,《大学》真的可以用来诠释《论》《孟》吗?
《大学》本是《礼记》一篇,有人视《礼记》为荀学系统,如船山认为《礼记·乐记》视乐为外来,而与孟子的“仁义礼智乐”为内在者不同。故以《大学》或《礼记》不见得能诠解《论语》《孟子》。
又伊藤仁斋认为,《论语》与《大学》有多处不合:
1.朱子的大学、小学之分于《论语》无据。在论述《论语·子夏之门人小子》处,朱子认为:“子游讥子夏弟子,于威仪容节之间则可矣。然此小学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学正心诚意之事,则无有。”即子夏只知教学生以小学的洒扫应对进退,而不知教之以大学正心诚意。而伊藤仁斋的质疑是,两人(子游、子夏)同学于孔门,而子夏知有小学、大学之分,而子张不知,岂真如此乎?此看出朱子以《大学》解《论语》之不恰当。
2.又《论语》提到“子在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依《大学》的标准,则孔子是心不正、心不在焉,以至于食而不知其味,故《大学》《论语》二书难以相入。
以上说明,朱子虽反对学生于章节之外做思考,要人读书专一于一处,不愿乎其外,于其所即之一段处切问,自己却以《大学》解《论》《孟》!这也看出,朱子的体系建构,即是置入理气论。朱子主张“四书”的修学顺序,要从《大学》入手,便是为配合自家以《大学》作为骨架,而填充入《论》《孟》《中庸》的体系建构。
而其方法,即是以义理领导训诂,其义理是理学,以理学领导训诂,故诠释“四书”时都以合于理学的方式来做建构。先在《大学》处删补经文以合于其体系(如格物穷理),再以《大学》为标准,而把《论》《孟》《中庸》都诠释为理学。
(四)增字诠释
朱子的体系建构,常常增字诠释。例如朱子与象山之争辩处,朱子对于“无极而太极”的诠释是无形而有理,而象山反对。象山针对朱子通过“然”与“所以然”的增字诠释法,用以诠释阴阳与太极,提出驳斥,象山言:
后书又谓“无极即是无形,太极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故着无极二字以明之”。《大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极乎!
若以《易传》诠释《易传》,此为内在建构,则不用取外在建构。朱子以《大学》解《孟子》,其实已是一种外在建构,若真以古本《大学》解《孟子》亦属接近,然朱子对《大学》所做修改太多,而启人疑窦。又若以《易传》诠释《易传》,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其中的“一阴一阳”与“形而上者”都是道,二者等同,亦即“一阴一阳”是为“形而上者”,而朱子却谓“一阴一阳”是“形而下者”,即视太极为形上、阴阳为形下!
朱子于书信中反驳象山,朱子的回答是:
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岂真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故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行,则谓之道。
面对象山对朱熹“形而上”“一阴一阳”解释的质疑,朱子以为都与本义有出入。朱子指出,阴阳不是形而上者,阴阳属形器而为形而下,于形而下(阴阳)之中,得以见所以然的形上之理(太极)。可见朱子对一阴一阳的诠释,乃是依于理气论而成,而此理气论又是依于二程的理论建构而来,故世称程朱理学。阴阳,器也,也同等于气;所以阴阳,道也,理也。但是《易传》原文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并未明言“所以阴阳者道也”,此以“然”与“所以然”的体系建构,是由程朱做成。
“然”与“所以然”的概念曾出现在《庄子》。《庄子·齐物论》谈到: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道家盛言自然,而不追问所以然;而朱子为儒家建构,于事物格物穷理,追问其所以然,即追问其天理,天理系理一分殊,落于事物,故即于世物上穷究之,事物是“然”,即是“如此”,于“如此”的事物上追问其背后的天理原因,即是其“所以然”。在此可从朱子与象山二人的诠释方法学比较中看出,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诠释而言,象山是以《易传》诠释《易传》,而朱子遵守程子之说,故用了外在诠释,以“然”与“所以然”的方法做诠释。这也是朱子的体系建构方法。
又举朱子于《论语·性相近章》增字诠释的例子,其注言: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孔子只说性相近,而朱子以气质之性诠释此相近之性,朱子已把性分别为两种,一种是天地之性,一种是气质之性,然这种区别必未是孔、孟的意思。朱子何以认为此处的相近之性是气质之性呢?因为他依于伊川见解,伊川认为天地之性,性即理,性是天理人人“相同”,何“相近”之有?若言相近,必不是谈天地之性,因为天地之性只能视为相同,而不可言相近,故相近也者,是为气质之性。此乃程朱的理气论置入于《论语》中而产生的创造性诠释,而且是一种增字诠释,把孔子所言之“性”,增字而为“气质之性”。
(五)析分一性而为二性
朱子析分一性而为二性的做法,除见于《论语》,尚可见于《孟子》。在诠释《孟子·生之谓性章》时,朱子言:
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
此处朱子将孟子的性义,诠释为有一种是性之为理,另一种是性之为气,孟子识性之为理,而告子不知,却以气为性。这又是把理气论置入于《孟子》诠释之中了。
又朱子于《告子上》前几章处,谈到荀子、扬雄、佛氏、告子、苏氏、胡氏、韩愈等人,视这些人都以气为性。由此亦看出朱子用二层的性以诠释《孟子》经典。天地之性,此性即理,是体、是天理;至于气质之性,则是此性落于气质之中,而此气质则为形下,是气。此以二元方式区分性的做法,未必是先秦的意思。若相比于戴震,戴震以性为血气心知,性亦是一元,而不必区分为二。
又如黄宗羲的见解,其顺着孙慎行之说,反对有二性,黄宗羲言:
别教有云:“丈夫食少金刚,终竟不消,要穿出身外,何以故?金刚不与身中杂秽同止。”故天命之性,岂特如金刚?一切清浊偏正刚柔缓急,皆拘他不得。如谓水本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不净器盛之则臭,以污泥之器盛之则浊,本然之清,未尝不在,但既臭浊,猝难得清。果若是,则水一性也,器一性也。性之夹杂如此,安所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乎!
黄宗羲认为,“天地之性”若能离于“气质”,则此取喻近于“金刚”不与“污秽”同处一般。此乃反对朱子二性之说,一种是天地之性,一种是气质之性,黄氏认为若如此区分,则性为挟杂,岂能称得上是“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可见黄宗羲对朱子学二性说的质疑。
朱子学的二性说确实非先秦原意,而是一种理学的建构,从另一角度看,此种建构能使儒学的生命化腐朽为神奇,从儒、佛、道之相遇中碰撞出新的火花,而为新儒学;也因着朱子的开展,成就了宋明儒学的道统新生命之延续。宋明儒者,无论宗朱、反朱,都围绕着朱子学问而开展,而朱子的学问核心,就在理气论。
于此再看一段孟子的原文,孟子谈到:
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孟子此段谈到“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亦是说孟子视“口之于味”也是“性”,只有一性,此一性担负了仁义之端及耳目口鼻之食色。故阳明视性是理气(道德与食色)合,较朱子为准确。
王船山亦视性是理气合。船山于注解张子《正蒙》“性其总,合两也”一段言:“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船山的气论认为,“盈天地皆器也”,天命之落于人而为性,性是理气合,而非如朱子所言,性只有理而无气(性即理,又说孟子不备气)。性中有理有气,其为理者,为仁义礼智;其为气者,为声色臭味。这也是船山的两端一致之说,合理、欲而为一性。故船山解张子所言的“性之合两”,即是合仁义道德与声色臭味而为一性,故亦可用一性以诠释孟子,而不用如朱子的二性说。
性之为一,而不需如朱子以二性诠释,于孟子原文已可明见。上文所引《富岁章》谈到,“口之于味”是“性”,故不必如朱子把“气化”区隔于性之外,而独成一天地之性;依于朱子,此性为理,纯善而无恶,又恶是气质后天所造成,乃天地之性落于气质中所造成。
朱子的二性区分可谓多此一举。先把气质隔于天地之性外,然后又说“孟子论性,终是不备”,而以程子之意为补充,补足其气质之性。笔者认为,朱子此举也可说是他所处时代之课题,其重视人的气质对人的影响,如魏晋的才性论之课题、如刘劭《人物志》之课题,视人之才性是否合于中正,而能力能否胜任官职以相人。又当时面对佛教的习气、无明等课题,而于儒家义理亦加入气质之性以扩充,此朱子从张子(气质之性)与二程(才)的义理发展而来。
又如朱子注《论语·其为人也孝弟章》,把其体用论注入于其中,其言: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程子曰:“……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
朱子认为,仁是“心之德,爱之理”,仁是性,是爱之情的所以然之理,是为体,而不是用,仁是性理中的一部分,故“为仁”只能解为“行仁”,而不可解为“是仁”,因为仁为体,最为根本,不能在仁之上还有一个孝弟作为其根本。也因为孝弟是用,而不是体,故性中只有仁义礼智,是为体,体中无用,孝弟是用,故性中无孝弟。这也是顺着程朱理气论之体系,因此“为仁”只能解为“行仁”。
为何说朱子的诠释是建构而成的呢?此与伊藤仁斋(1627—1705)之见解比较即可得知。伊藤乃江户时期日本古义派学者,用心于恢复《论语》古义,而认为朱子的诠释不是古义。于此章,其以《论语》解《论语》的内在建构,认为“本立道生”“孝弟为仁之本”,故“本”者为“孝弟”,“道”是指“仁”。如此,则不用如程朱所言仁为体为本,而孝弟为用为末,即不用如程子以仁论性,而为孝弟之本。
在伊藤仁斋而言,仁是道、也是德,是修己安人之道,是德之完成。心者、性者只有仁之端,而不是仁之全部体现。此乃伊藤对于仁说的诠释,而与朱子的仁是体是性、是形而上者不同。
由上可知,朱子的方法论是从外部引入理气论而来诠释《论语》,至于伊藤仁斋研究《论语》的方法则不高深穷微,而是平议地以《论语》解《论语》,最多以《孟子》解《论语》。朱子的做法乃是以理气论领导训诂,后来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之书写,即不取朱子的方法学,改以先秦时的字义来训解《孟子》。
(六)断句释文及先知后行
又朱子在断句时,也是以理气论领导训诂,朱子的《大学》设计,先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乃是一种先知后行的系统,但在《论语》,似有先行后知的说法,如《论语》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先行,而后学文,乃先行后知之说。而朱子不同意,故于此章注言:“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此诠释与《论语》语势完全不合,但合于朱子的理气论下的先知后行系统。
又《子贡问君子章》,孔子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程子的断句是:“先行,其言而后行之。”朱子不从,认为该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理由是,若断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乃为先行后言,或称为先行后知,与朱子的先知后行冲突。若改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则在行之时已有言,行与言(知)可为同时,则不至于成了“先行后知”之系统。于此可见朱子理论之选取,与其体系息息相关。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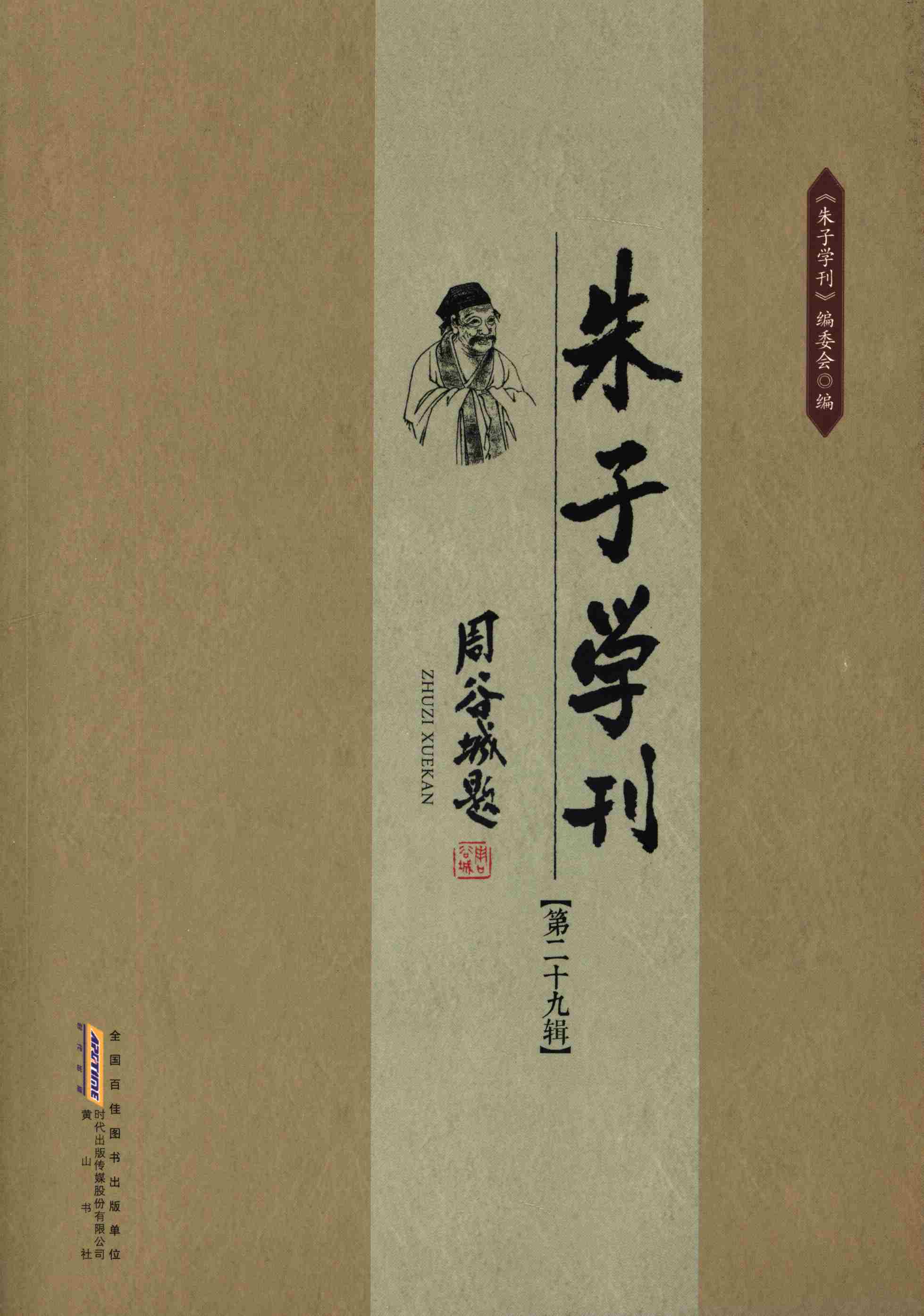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出版者:黄山书社
本书收录了《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学》《朱熹婚丧礼制的推行》《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戴震与朱熹关系平议》《陈北溪论“命”》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蔡家和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