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子“智藏”观与山崎闇斋的宣扬
| 内容出处: |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048 |
| 颗粒名称: | 一 朱子“智藏”观与山崎闇斋的宣扬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7 |
| 页码: | 477-483 |
| 摘要: | 本文以日本江户时代的崎门朱子学者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了他们对于朱熹晚年思想中的“智藏”观点的重视。文章将以三宅尚斋所编写的《智藏说》为基础,详细阐明了崎门派“智藏说”的具体内容和逻辑结构,以及在崎门派朱子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文章还探讨了崎门派朱子学者对“智藏”观点的重视与发展,以及该观点在日本朱子学传播中的一侧面,以及中、日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等问题。该研究填补了现有研究对于崎门派“智藏说”的概略性说明的不足。 |
| 关键词: | 日本 朱子学 研究对象 |
内容
如上所述,朱熹晚年的思想中有所谓“智藏”这一观点。朱熹是在六十五岁时所讲授过的《玉山讲义》中,首次将之提出。《玉山讲义》中如下说道:
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于此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义,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义”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①
在此《玉山讲义》中,朱熹除了将“智”规定为“仁之分别”之外,将“智”对应到四时(春夏秋冬)中的“冬”而将它视为具有“生之藏”“义之藏”之意。
在此《讲义》,朱熹的关注点就在仁、义,尤其是“仁”之生意通贯周流于四德之中这一点。虽然在这当中,“智”的重要性还没有凸显,但朱熹在给陈器之的书信中回答关于《玉山讲义》内容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四德中“智”的特别角色以及其重要意义。朱熹如此说:
“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始终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①
在此,朱熹将四德的主轴从“仁义”转移到“仁智”,说明“智”德的特别性、重要性。据朱熹所言,“智”没有像其他三德(仁、义、礼)具有能看到的具体作用,它的功能只是分别以及收藏、翕聚而已。但朱熹认为这种收藏、翕聚的功能才是重要的。根据《易》学思想中的阴阳循环之理,有“始”(首)则有“终”(末),有“终”(末)才有“始”(首),因为有收藏、翕聚,所以才能发散、伸展。因此,“仁”的生意原来都是根据“智”的收藏、翕聚的。若没有“智”的收藏,就没有“仁”的元气。朱熹所以说“智能成始,能成终”“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的理由就在这里。朱熹的“智藏”这一观点,在以下的文献中也能看到。
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觉而无运用,冬之象也。①
贺孙问:“孟子四端,何为以知为后?”曰:“孟子只循环说。智本来是藏仁义礼,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礼义都藏在智里面。如元亨利贞,贞是智,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里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长、秋成意思在里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见,到一阳初动,这生意方从中出,也未发露,十二月也未发尽露。只管养在这里,到春天方发生,到夏天一齐都长,秋渐成,渐藏,冬依旧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终始’亦见得,无终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②
四端,仁智最大。无贞,则元无起处。无智,则如何是仁。《易》曰:
“大明终始。”有终便有始。智之所以大者,以其有知也。③
如此,朱熹在晚年非常重视“智”,而提出如上所述的“智藏”观点。④然而此一“智藏”观,如上所述,古来并未受到中、韩两国朱子学者的重视,因此几乎都没有任何中、韩朱子学者针对“智藏”的问题开展深入讨论。但在日本江户时代,以山崎闇斋为开山祖师的崎门朱子学者们,却非常重视朱熹的这一“智藏”观,并留下了许多有关“智藏”观的学说主张。
山崎闇斋在《近思录序》中说:“仁爱之有味,智藏之无迹,先生(引者按,朱熹)丁宁开示之。”⑤提到朱熹思想中有“智藏”这一重要观点。闇斋又受到朱熹上述“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一句的启发,撰写“仁智交际间,万化同出自,虽孔朱后生,不过启此秘”⑥这一首诗。
会津藩主保科正之(1611—1672)乃是山崎闇斋的弟子之一。保科正之与闇斋两人刊行的《玉山讲义附录》就是收集《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中有关《玉山讲义》的资料编辑而成的。而保科正之与山崎闇斋两人编辑、刊行这一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阐发朱熹思想中的“智藏”之说。这一点,我们由以下所列的闇斋文章可以获知。
尝使嘉(引者按,闇斋)读《玉山讲义》,为之附录。则举其要曰:“仁之生意亲切之味,即未发之爱一意,一理而万物之所以为一体也。”又曰:“智藏而无迹。识此而后可以语道体,可以论鬼神。”又曰:“仁智交际,万化机轴。此合天人之道也。”呜呼,可谓说约矣。知此要约者,朱门蔡季通、仲默、真希元之后,未有斯人也。①
又玩索《玉山讲义》而使嘉搜《朱子文集》《语类》之说可与此相发明者。反复之,分其类,为附录三卷。上之一明太极阴阳,二明健顺五常,三明仁义仁智。中明四德五常。下之一明仁,二明智,三明气禀死生。玉讲之义,精之如是者未之有。而性命之说之详,至于此无复以加焉。而未发之爱之为仁,无迹之藏之为智,而仁智交际之间则其独见默契处。朱门西山并九峰之外,人之所得而不识也。②
在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闇斋认为能够真正体会、了解朱熹“智藏”观之奥秘的人,在中国只有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蔡沉(1167—1230,字仲
默,号九峰)、真德秀(1178—1235,字希原,号西山)等人。③对闇斋而言,自己以及其弟子保科正之才是真正体会朱熹“智藏”观之真意的人。这就意味着真正继承朱子学根本精神的,无非是日本的闇斋(崎门)学派这个学统。于是,闇斋的弟子们也特别重视“智藏”观。
闇斋虽然特别发扬“智藏”观,但以“述而不作”为宗旨,他本人针对“智藏”发表的相关言论并不多,无法掌握其整体面貌。因此,若要了解崎门“智藏”论的全貌,就必须依据弟子们留下的相关数据。据笔者的调查,崎门学者直接探讨“智藏”这一议题的相关资料有三宅尚斋(1662—1741):《智藏说》、三宅尚斋:《智藏论笔札》、久米订斋(1699—1784):《读智藏说笔记》、若林强斋(1679—1732):《玉山讲义师说》、幸田子善(1720—1792):《玉山讲义笔记》等。
在前人研究当中,已经对山崎闇斋、保科正之、三宅尚斋、楠本端山的“智藏”相关言论进行了概略性的说明。管见所及,针对崎门的“智藏”论有所介绍、分析、讨论的研究,有以下论著:(1)冈田武彦:《朱子と智藏》(《朱子与智藏》),收入《中國思想しこおしナる理想と現實》(《中国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东京:木耳社,1983年);(2)冈田武彦:《朱子の智藏說とその由來および繼承》(《朱子的智藏说及其由来与继承》),收入《中國思想しこおしナる理想と現實》(《中国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东京:木耳社,1983年);(3)冈田武彦:《山崎闇齋》(东京:明德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山崎闇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4)冈田武彦:《楠本端山》(东京:明德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马安东译:《楠本端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5)海老田辉已:《三宅尚齋》(东京:明德出版社,1990年);(6)高岛元洋:《山崎闇齋——日本朱子學と垂加神道》(《山崎闇斋——日本朱子学与垂加神道》,东京:ぺりかん社,1992年);(7)难波征男:《朱子學“智藏說”の變遷と展開》(《朱子学“智藏说”的变迁与展开》,《福冈女学院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纪要·人文学研究》第四辑,2001年3月)。以下简单回顾这些研究的内容。
在学界第一位发现在朱熹以及崎门学中的“智藏说”的重要性,并进行相关探讨、研究的学者可能是冈田武彦。冈田在论文(1)中指出:“在历来的朱子学研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学说被忽略了。一是‘全体大用论’,二是‘智藏说’。关于前者,幸好恩师楠本正继教授已经阐明了其本质以及全貌;但关于后者,很遗憾地几乎都没有人进行深入探讨。”①在此问题意识之下,为了补充历来研究的不足,冈田在(1)(2)的文章中详细介绍朱熹的“智藏”这一观点。透过(1)(2)论文,我们可以知道:朱子在晚年65岁时撰写的《玉山讲义》中,第一次提出“智藏”这一观点,而其“智藏”观的具体内容、意义在《答陈器之书问玉山讲义书》(《朱子文集》卷五十八)中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冈田在文章(2)(3)中,除了介绍、说明朱熹的“智藏”观之外,还介绍朱熹的“智藏”观流传到日本,受到崎门派的朱子学者重视而被继承的情况。透过(2)(3)文章,我们可以知道:闇斋所编的《玉山讲义附录》《程书抄略》《张书抄略》等书都是为了发扬“智藏说”而编的,闇斋的高徒佐藤直方、浅见絅斋、三宅尚斋都相当重视“智藏说”,对“智藏”意义做详细的解说,其中最热心研究“智藏说”的乃是三宅尚斋,幕末维新期的崎门派朱子学者楠本端山也非常重视“智藏说”。冈田在文章(4)介绍楠本端山的“智藏说”,而将“智藏说”从朱熹到端山的流传过程做以下整理:“智藏说最先是朱子说起的,来自《易》的东西。将朱子的智藏说公诸于世的,是山崎闇斋,这是元明诸儒及其他学派未曾论及过的。……取朱子的智藏说又将之公诸于世的,是闇斋,这主旨也传至门人。继承这体系的,是三宅尚斋。这从他著有《智藏说》可知。……端山很好地继承了朱子以及誾斋、尚斋的智藏主旨,努力于体认。”②
海老田在《三宅尚斋》一书中的第四节介绍尚斋的“智藏说”。尚斋特别注重“知”,认为“知”先于“行”。尚斋将“知”理解为“心之德”、“思、知、意、虑”等精神作用,或运用万物之“理”的本体。本书虽然独立提到三宅的“智藏说”,但偏向于文献性的说明,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尚斋“智藏说”的具体内容以及思想意义。
高岛在《山崎誾齋——日本朱子學と垂下神道》第一部第七章《德と智藏說》中,独立探讨闇斋的“智藏说”。高岛将朱熹的“智藏”观与闇斋的“智藏”观详细比较,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别。本书中出现将“智藏说”与神道说加以联结并检讨的观点,值得参考。但关于三宅尚斋等其他崎门派学者的“智藏说”,在该文当中仍未见作者阐明。
难波《朱子學“智藏說”の變遷と展開》一文,基本上是根据冈田的研究,其见解也并未超出冈田研究的范围。但其中引用韩国朴洋子教授的《<天命圖>しこ見る退溪の智藏說しこついて》(《在<天命图>中看退溪的智藏说》),指出在李退溪思想中也能看到智藏说,提出崎门派的“智藏说”可能受到退溪学的影响之新见解,值得注意。
这些研究虽然注意“智藏”论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根据上列的文献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剖析、阐明崎门“智藏说”。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崎门“智藏说”的研究还停留在概略性、部分性的程度。因此,以下根据上列的相关资料,来深入分析、探讨崎门学者“智藏说”的具体内容以及其思想特色。
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于此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义,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义”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①
在此《玉山讲义》中,朱熹除了将“智”规定为“仁之分别”之外,将“智”对应到四时(春夏秋冬)中的“冬”而将它视为具有“生之藏”“义之藏”之意。
在此《讲义》,朱熹的关注点就在仁、义,尤其是“仁”之生意通贯周流于四德之中这一点。虽然在这当中,“智”的重要性还没有凸显,但朱熹在给陈器之的书信中回答关于《玉山讲义》内容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四德中“智”的特别角色以及其重要意义。朱熹如此说:
“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始终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①
在此,朱熹将四德的主轴从“仁义”转移到“仁智”,说明“智”德的特别性、重要性。据朱熹所言,“智”没有像其他三德(仁、义、礼)具有能看到的具体作用,它的功能只是分别以及收藏、翕聚而已。但朱熹认为这种收藏、翕聚的功能才是重要的。根据《易》学思想中的阴阳循环之理,有“始”(首)则有“终”(末),有“终”(末)才有“始”(首),因为有收藏、翕聚,所以才能发散、伸展。因此,“仁”的生意原来都是根据“智”的收藏、翕聚的。若没有“智”的收藏,就没有“仁”的元气。朱熹所以说“智能成始,能成终”“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的理由就在这里。朱熹的“智藏”这一观点,在以下的文献中也能看到。
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觉而无运用,冬之象也。①
贺孙问:“孟子四端,何为以知为后?”曰:“孟子只循环说。智本来是藏仁义礼,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礼义都藏在智里面。如元亨利贞,贞是智,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里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长、秋成意思在里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见,到一阳初动,这生意方从中出,也未发露,十二月也未发尽露。只管养在这里,到春天方发生,到夏天一齐都长,秋渐成,渐藏,冬依旧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终始’亦见得,无终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②
四端,仁智最大。无贞,则元无起处。无智,则如何是仁。《易》曰:
“大明终始。”有终便有始。智之所以大者,以其有知也。③
如此,朱熹在晚年非常重视“智”,而提出如上所述的“智藏”观点。④然而此一“智藏”观,如上所述,古来并未受到中、韩两国朱子学者的重视,因此几乎都没有任何中、韩朱子学者针对“智藏”的问题开展深入讨论。但在日本江户时代,以山崎闇斋为开山祖师的崎门朱子学者们,却非常重视朱熹的这一“智藏”观,并留下了许多有关“智藏”观的学说主张。
山崎闇斋在《近思录序》中说:“仁爱之有味,智藏之无迹,先生(引者按,朱熹)丁宁开示之。”⑤提到朱熹思想中有“智藏”这一重要观点。闇斋又受到朱熹上述“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一句的启发,撰写“仁智交际间,万化同出自,虽孔朱后生,不过启此秘”⑥这一首诗。
会津藩主保科正之(1611—1672)乃是山崎闇斋的弟子之一。保科正之与闇斋两人刊行的《玉山讲义附录》就是收集《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中有关《玉山讲义》的资料编辑而成的。而保科正之与山崎闇斋两人编辑、刊行这一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阐发朱熹思想中的“智藏”之说。这一点,我们由以下所列的闇斋文章可以获知。
尝使嘉(引者按,闇斋)读《玉山讲义》,为之附录。则举其要曰:“仁之生意亲切之味,即未发之爱一意,一理而万物之所以为一体也。”又曰:“智藏而无迹。识此而后可以语道体,可以论鬼神。”又曰:“仁智交际,万化机轴。此合天人之道也。”呜呼,可谓说约矣。知此要约者,朱门蔡季通、仲默、真希元之后,未有斯人也。①
又玩索《玉山讲义》而使嘉搜《朱子文集》《语类》之说可与此相发明者。反复之,分其类,为附录三卷。上之一明太极阴阳,二明健顺五常,三明仁义仁智。中明四德五常。下之一明仁,二明智,三明气禀死生。玉讲之义,精之如是者未之有。而性命之说之详,至于此无复以加焉。而未发之爱之为仁,无迹之藏之为智,而仁智交际之间则其独见默契处。朱门西山并九峰之外,人之所得而不识也。②
在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闇斋认为能够真正体会、了解朱熹“智藏”观之奥秘的人,在中国只有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蔡沉(1167—1230,字仲
默,号九峰)、真德秀(1178—1235,字希原,号西山)等人。③对闇斋而言,自己以及其弟子保科正之才是真正体会朱熹“智藏”观之真意的人。这就意味着真正继承朱子学根本精神的,无非是日本的闇斋(崎门)学派这个学统。于是,闇斋的弟子们也特别重视“智藏”观。
闇斋虽然特别发扬“智藏”观,但以“述而不作”为宗旨,他本人针对“智藏”发表的相关言论并不多,无法掌握其整体面貌。因此,若要了解崎门“智藏”论的全貌,就必须依据弟子们留下的相关数据。据笔者的调查,崎门学者直接探讨“智藏”这一议题的相关资料有三宅尚斋(1662—1741):《智藏说》、三宅尚斋:《智藏论笔札》、久米订斋(1699—1784):《读智藏说笔记》、若林强斋(1679—1732):《玉山讲义师说》、幸田子善(1720—1792):《玉山讲义笔记》等。
在前人研究当中,已经对山崎闇斋、保科正之、三宅尚斋、楠本端山的“智藏”相关言论进行了概略性的说明。管见所及,针对崎门的“智藏”论有所介绍、分析、讨论的研究,有以下论著:(1)冈田武彦:《朱子と智藏》(《朱子与智藏》),收入《中國思想しこおしナる理想と現實》(《中国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东京:木耳社,1983年);(2)冈田武彦:《朱子の智藏說とその由來および繼承》(《朱子的智藏说及其由来与继承》),收入《中國思想しこおしナる理想と現實》(《中国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东京:木耳社,1983年);(3)冈田武彦:《山崎闇齋》(东京:明德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山崎闇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4)冈田武彦:《楠本端山》(东京:明德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马安东译:《楠本端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5)海老田辉已:《三宅尚齋》(东京:明德出版社,1990年);(6)高岛元洋:《山崎闇齋——日本朱子學と垂加神道》(《山崎闇斋——日本朱子学与垂加神道》,东京:ぺりかん社,1992年);(7)难波征男:《朱子學“智藏說”の變遷と展開》(《朱子学“智藏说”的变迁与展开》,《福冈女学院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纪要·人文学研究》第四辑,2001年3月)。以下简单回顾这些研究的内容。
在学界第一位发现在朱熹以及崎门学中的“智藏说”的重要性,并进行相关探讨、研究的学者可能是冈田武彦。冈田在论文(1)中指出:“在历来的朱子学研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学说被忽略了。一是‘全体大用论’,二是‘智藏说’。关于前者,幸好恩师楠本正继教授已经阐明了其本质以及全貌;但关于后者,很遗憾地几乎都没有人进行深入探讨。”①在此问题意识之下,为了补充历来研究的不足,冈田在(1)(2)的文章中详细介绍朱熹的“智藏”这一观点。透过(1)(2)论文,我们可以知道:朱子在晚年65岁时撰写的《玉山讲义》中,第一次提出“智藏”这一观点,而其“智藏”观的具体内容、意义在《答陈器之书问玉山讲义书》(《朱子文集》卷五十八)中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冈田在文章(2)(3)中,除了介绍、说明朱熹的“智藏”观之外,还介绍朱熹的“智藏”观流传到日本,受到崎门派的朱子学者重视而被继承的情况。透过(2)(3)文章,我们可以知道:闇斋所编的《玉山讲义附录》《程书抄略》《张书抄略》等书都是为了发扬“智藏说”而编的,闇斋的高徒佐藤直方、浅见絅斋、三宅尚斋都相当重视“智藏说”,对“智藏”意义做详细的解说,其中最热心研究“智藏说”的乃是三宅尚斋,幕末维新期的崎门派朱子学者楠本端山也非常重视“智藏说”。冈田在文章(4)介绍楠本端山的“智藏说”,而将“智藏说”从朱熹到端山的流传过程做以下整理:“智藏说最先是朱子说起的,来自《易》的东西。将朱子的智藏说公诸于世的,是山崎闇斋,这是元明诸儒及其他学派未曾论及过的。……取朱子的智藏说又将之公诸于世的,是闇斋,这主旨也传至门人。继承这体系的,是三宅尚斋。这从他著有《智藏说》可知。……端山很好地继承了朱子以及誾斋、尚斋的智藏主旨,努力于体认。”②
海老田在《三宅尚斋》一书中的第四节介绍尚斋的“智藏说”。尚斋特别注重“知”,认为“知”先于“行”。尚斋将“知”理解为“心之德”、“思、知、意、虑”等精神作用,或运用万物之“理”的本体。本书虽然独立提到三宅的“智藏说”,但偏向于文献性的说明,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尚斋“智藏说”的具体内容以及思想意义。
高岛在《山崎誾齋——日本朱子學と垂下神道》第一部第七章《德と智藏說》中,独立探讨闇斋的“智藏说”。高岛将朱熹的“智藏”观与闇斋的“智藏”观详细比较,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别。本书中出现将“智藏说”与神道说加以联结并检讨的观点,值得参考。但关于三宅尚斋等其他崎门派学者的“智藏说”,在该文当中仍未见作者阐明。
难波《朱子學“智藏說”の變遷と展開》一文,基本上是根据冈田的研究,其见解也并未超出冈田研究的范围。但其中引用韩国朴洋子教授的《<天命圖>しこ見る退溪の智藏說しこついて》(《在<天命图>中看退溪的智藏说》),指出在李退溪思想中也能看到智藏说,提出崎门派的“智藏说”可能受到退溪学的影响之新见解,值得注意。
这些研究虽然注意“智藏”论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根据上列的文献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剖析、阐明崎门“智藏说”。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崎门“智藏说”的研究还停留在概略性、部分性的程度。因此,以下根据上列的相关资料,来深入分析、探讨崎门学者“智藏说”的具体内容以及其思想特色。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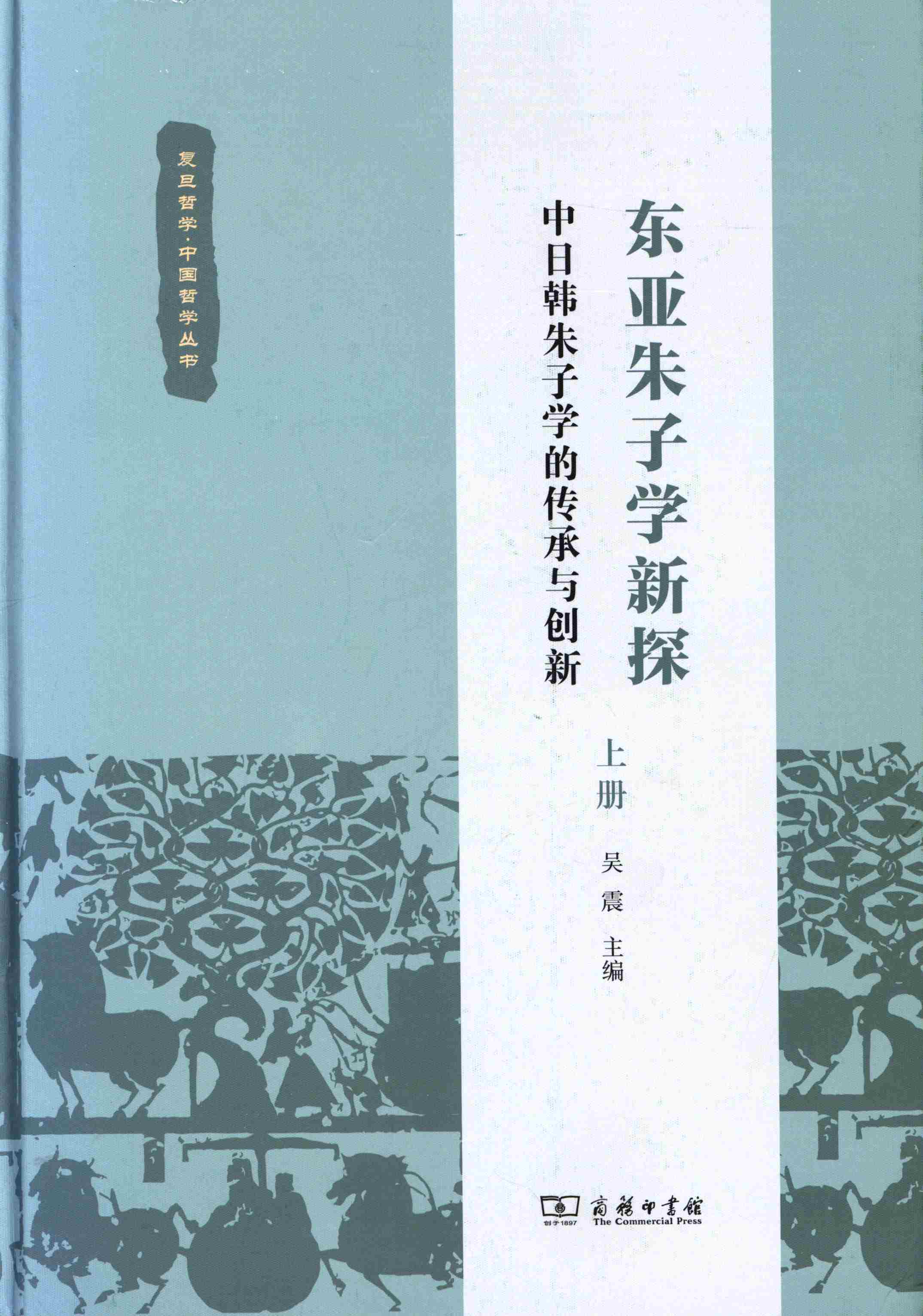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这部《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是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的结项成果,并于今年被认定为是成果。全书共由四篇三十七章组成,近九十万字,吴震教授主编,由海内外中国哲学领域的一线学者组成的性团队合作分篇撰写,代表了当代朱子学研究的前沿的成果。本书的四篇结构是:一、“东亚儒学与中国朱子学”;二、“日本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三、“韩国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比较研究与回顾综述”;后是两篇“附录”,分别是“近十年来日本朱子学研究论著简目”、“近十年来韩国朱子学研究论著简目”。本书进一步拓展了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深度与广度,可以认为,通过本书的出版,“东亚朱子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有充分理由得以成立(如同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东亚儒学”或“东亚哲学”已渐形成一般),进而,本书的出版也得以重新展现了中国哲学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