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1》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6779 |
| 颗粒名称: | 历代对《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 |
| 其他题名: | 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9 |
| 页码: | 060-068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论语·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的是君子与小人在道德上的对立。汉唐时期的解读者对于“和”与“同”的解释存在差异,有将“和”解读为“和谐”的,也有将其解读为“心不争”的。朱熹认为君子尚义,所以“和而不同”,而小人追求利益,所以“同而不和”。君子与小人的对立不仅在于“和”与“同”,更体现在公私与义利之间。 |
| 关键词: | 朱子学 论语 解读 |
内容
《论语·子路》载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明显是就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而言。然而,当今学者的解读,大都以西周末史伯批评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并且讲“和而不同”以及春秋末齐国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将其中的“和”解读为“和谐”。李泽厚《论语今读》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君子和谐却不同一,小人同一却不和谐。”①同时还特别强调:“‘和’的前提是承认、赞成、允许彼此有差异、有区别、有分歧,然后使这些差异、区别、分歧调整、配置、处理到某种适当的地位、情况、结构中,于是各得其所,而后整体便有‘和’——和谐或发展。”②问题是,能够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吗?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果这里的“和”解读为“和谐”,是否意味着君子与小人也应当“和谐”?在孔子那里,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能够“和谐”吗?孔子讲“道不同,不相为谋”,讲的就是君子与小人不应当“和谐”。可见,孔子之所以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中还需要做更多、更为深入的解读。
一、汉唐时期的两种不同解读
《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仅讲君子与小人在道德上相互对立,而且讲“和而不同”“同而不和”,讲“和”与“同”的区别。关于“和”与“同”的区别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国语·郑语》记西周末史伯对周幽王“去和而取同”的批评。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③这里将“和”与“同”区别开来,强调“以多物,务和同”,讲由“多”而“和”,反对“同”而“一”,讲“和而不同”,无疑具有“和谐”之意。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是先王“和而不同”,而不是讲君子“和而不同”。
又据《晏子春秋》载,春秋末齐国晏婴与齐景公论“和”与“同”的区别,说:“和如羹焉,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①应当说,晏婴讲“和如羹”而反对“专一”,与史伯讲先王“和而不同”,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对于“和”与“同”的区别的讨论,其中的“和”也具有“和谐”之意,且同样只是讲先王“济五味、和五声”;至于所谓“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其中的“君子”应当是指君王。
东汉荀悦《申鉴》推崇《晏子春秋》所谓“和如羹”,并引出《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说: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咸甘苦不同,嘉味以济,谓之和羹;宫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谓之和声。臧否损益不同,中正以训,谓之和言;趋舍动静不同,雅度以平,谓之和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一声,谁能听之?’《诗》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无言,时靡有争。’此之谓也。”②这里讲“君子食和羹”,“纳和言以平其政”,所谓“君子”指的是君王;接着又讲《论语》的“君子和而不同”,似乎是把《论语》“君子和而不同”中的“和”解读为不同事物的相互和谐。
另据《后汉书·刘梁传》载,刘梁著《辩和同之论》,说:“君子之于事也,无适无莫,必考之以义焉。得由和兴,失由同起。故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春秋传》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剂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③显然,这里的解读也是以晏婴讲“和如羹”解《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和”即“和谐”。
应当说,无论是史伯讲“和而不同”,还是晏婴讲“和如羹”,都是就先王而言,要求君王讲“和谐”,并不涉及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如果据此解读《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将其中的“和”解读为“和谐”,强调“和”的价值而否定“同”,很可能会消解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不合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蕴含的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之意。
与此不同,三国时何晏《论语集解》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南北朝的皇侃《论语义疏》疏曰:“和,谓心不争也。不同,谓立志各异也。君子之人千万,千万其心和如一,而所习立之志业不同也。……小人为恶如一,故云‘同’也。好斗争,故云‘不和’也。”①后来,北宋的邢昺《论语注疏》疏曰:“此章别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则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②应当说,何晏、皇侃以及邢昺的解读,从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讲“和”与“同”,突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对立,不同于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对于“和谐”的推崇,较为合乎《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意。
然而,何晏、皇侃等的解读,在“和”与“同”的概念界定上,尚存在着某些不自洽。何晏《论语集解》讲“和”,把君子之“和”解读为君子之心的“和”,把小人之“不和”解读为小人“各争其利”;讲“同”,则把君子之“不同”解读为君子“所见各异”,把小人之“同”解读为小人“所嗜好者同”。皇侃《论语义疏》明确把君子的“和”“不同”与小人的“同”“不和”分别开来界定:就君子而言,“和,谓心不争也。不同,谓立志各异也”;就小人而言,“小人为恶如一,故云‘同’也。好斗争,故云‘不和’也”。也就是说,在何晏、皇侃等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中,无论是“和”的内涵,还是“同”的内涵,都不是统一的。
由此可见,汉唐时期对于《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解读,既有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而将其中的“和”解为“和谐”,实际上消解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也有何晏、皇侃等的解读,突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但尚没有就“和”与“同”的概念内涵做出自洽的解读。
二、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③这里从心性层面将“和”解读为“无乖戾之心”,将“同”解读为“阿比之意”,也就是认为君子“无乖戾之心”,因而无“阿比之意”;小人有“阿比之意”,因而有“乖戾之心”。显然,这样的解读,与何晏、皇侃等的解读一样,突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重要的是,朱熹的解读还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义利联系起来,认为君子尚义,所以“和而不同”,小人尚利,所以“同而不和”。朱熹还说:“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盖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会这一个公当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个私意,故虽相与阿比,然两人相聚也便分个彼己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纷争而不和也。”①也就是说,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不只在“和”与“同”的区别,更在于“公”与“私”的对立,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区别。朱熹门人辅广对《论语集注》引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做了讨论,说:“尹氏本意,虽只是以义利二字说不同、不和之意,然细推之,则君子之于事,唯欲合于义,故常和。然义有可否,故有不同;小人徇利之意则固同矣,然利起争夺,安得而和?”②显然,辅广进一步强调君子尚义,所以“和而不同”;小人尚利,所以“同而不和”。
与何晏、皇侃等的解读相比,朱熹的解读明显具有两大优势:其一,正如以上所述,何晏、皇侃等的解读尚没有就“和”与“同”的概念内涵做出自洽的解读,与此不同,朱熹的解读特别重视并明确给出了对于“和”与“同”的概念的统一界定;其二,何晏、皇侃等的解读讲君子与小人具有“和”与“不和”、“不同”与“同”的对立,但由于没有就“和”与“同”的概念内涵做出自洽的解读,这样的对立是含混的,与此不同,朱熹的解读对“和”与“同”的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统一界定,并进一步强调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对立,突出了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对立,因而是对何晏、皇侃等的解读的发展和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不仅从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的角度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而且明确反对依据晏婴“和如羹”所做的解读。朱熹《论孟精义》收录了吕、杨、侯氏的解读:
吕曰:“和则可否相济,同则随彼可否。调羹者五味相合为和,以水济水为同。”
……
杨曰:“五味调之而后和,而五味非同也。如以咸济咸,则同而已,非所以为和也。君子有可否以相济,故其发必中节,犹之五味相得也。小人以同为说,犹之以咸济咸耳,尚何和之有?”
侯曰:“和非同也,和则虽有可不可之异,济其美而已,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同非和也,同恶相济,如以水济水,安能和哉?故曰:‘小人同而不和。’”③
对此,朱熹《论语或问》说:“吕、杨、侯氏说,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则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状而言,似不可引以为证也。盖此所论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协恭,而无乖争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无阿谀党比之风。若小人则反是焉。此二者,外虽相似,而内实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状之隐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轨,非圣人不能究极而发明之也。……如此说,则君子之心,无同异可否之私,而惟欲必归于是;若晏子之说,则是必于立异,然后可以为和而不同也,岂非矫枉过直之论哉!”①这里对以晏婴“和如羹”来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出了批评,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朱熹看来,晏婴所谓“和如羹”,是“就事而言”,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就“君子小人之情状而言”,是就人的内在道德品质而言,所以“不可引以为证”。晏婴强调听取不同意见,所谓“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又讲“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济也”。然而,可否相济,只是“就事而言”,并非就道德上的君子小人而言,换言之,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做到可否相济,而在于内在道德品质的截然相反。
第二,朱熹认为,君子小人“外虽相似,而内实相反”,所以对于“和”与“同”的界定,不可只是从事物表面上看,而应当从人的内在心性看。朱熹《论语集注》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又进一步讲公私义利,以此把君子与小人对立起来;《论语或问》则讲“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协恭,而无乖争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无阿谀党比之风。若小人则反是焉”。显然,对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朱熹的解读强调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对立,而以晏婴“和如羹”为依据的解读则只是讲君子与小人在做事上的“和”与“同”的区别。
第三,朱熹认为,对于各种不同的事物,君子应当“必归于是”,而晏婴“和如羹”要求“必于立异,然后可以为和而不同”,过多讲不同事物之“和而不同”,属于“矫枉过直之论”。朱熹《论语集注》注“道不同,不相为谋”,曰:“不同,如善恶邪正之异。”②并且认为,“君子小人决无一事之可相为谋者也”。③应当说,在朱熹的话语中,天理、人欲、公私、义利,乃至君子小人,正如邪正、善恶,都是对立的,而不可“和而不同”,如果用晏婴“和如羹”来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实际上包含了对于小人的“和而不同”,必然会消解君子与小人的对立,那么君子就不是与小人对立的君子,也就不成其为君子,因而就会陷于悖论,所以用“和如羹”解“君子和而不同”是不可能的。
三、朱熹之后的讨论
朱熹解《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心性层面将“和”解读为“无乖戾之心”,将“同”解读为“阿比之意”,是就人的道德品质而言,并非“就事而言”。然而,人的道德品质与做事又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朱熹之后,有不少学者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既从心性的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又讲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
元代陈天祥《四书辨疑》不满足于朱熹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的解读,说:“和则固无乖戾之心,只以无乖戾之心为和,恐亦未尽。若无中正之气,专以无乖戾为心,亦与阿比之意相邻,和与同未易辨也。中正而无乖戾,然后为和。凡在君父之侧,师长、朋友之间,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可者献之,否者替之,结者解之,离者合之,此君子之和也。而或巧媚阴柔,随时俯仰,人曰可,己亦曰可,人曰否,己亦曰否,惟言莫违,无唱不和,此小人之同也。晏子辨梁丘据非和,以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此论辨析甚明,宜引以证此章之义。”①陈天祥的解读试图在朱熹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的基础上,引入“中正之气”,并进一步以晏婴的“和如羹”区别君子之和与小人之同,实际上是把朱熹的解读与晏婴讲“和如羹”结合起来。
明代程敏政也解释说:“和是无乖戾之心,同是有阿比的意思。孔子说君子的心术公正,专一尚义,凡与人相交,必同寅协恭,无乖戾之心。然事当持正处,又不能不与人辩论,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的心术私邪,专一尚利,凡与人相交,便巧言令色,有阿比之意。然到不得利处,必至于争竞,故曰‘小人同而不和’。”②后来王夫之作了训释,说:“君子以义为尚,所与共事功者,皆君子也。事无所争,情无所猜,心志孚而坦然共适,和也。若夫析事理于毫芒,而各欲行其所是,非必一唱众和而无辨者也,不同也……小人以利为趋,所与相议论者,小人也。以权相附,以党相依,依阿行而聚谋不逞,同也。乃其挟己私之各异,而阴图以相倾,则有含忌蓄疑而难平者也,不和也。”③应当说,程敏政、王夫之的解释,合乎朱熹《论语集注》之意。
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引述何晏所言:“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并指出:“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义者宜也,各适其宜,未有方体,故不同。然不同因乎义,而非执己之见,无伤于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务于是,则有争心,故同而不和。此即君子、小人之异也。”①显然,这里以义、利讲“和”与“同”,并由此从心性的层面讲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这与朱熹《论语集注》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引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是相通的。在讲君子与小人相互对立的基础上,刘宝楠《论语正义》又讲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的“和如羹”,从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引申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
清末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和康有为《论语注》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出一辙,都是先引述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的“和如羹”,然后引申出君子与小人的相互对立。简朝亮说:“由是言之,和则不乖戾,同则惟阿比,其义不昭然乎?”②康有为说:“盖君子之待人也,有公心爱物,故和;其行己也,独立不惧,各行其是,故不同。小人之待人也,媚世易合,故同;其行己也,争利相忮,不肯少让,故不和。”③这明显更为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
直到现代钱穆《论语新解》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故不能和。或说:和如五味调和成食,五声调和成乐,声味不同,而能相调和。同如以水济水,以火济火,所嗜好同,则必互争。”④显然,这样的解读都是从朱熹的解读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出发,并进一步引申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
四、余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于《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既有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而将其中的“和”解为“和谐”,又有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以及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朱熹之后的学者大多既从心性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又由此引申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应当说,在这些解读中,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并进一步讲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对立,发展并完善了何晏、皇侃等的解读,超越了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的解读。
首先,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是就先王而言,以此为依据解读《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将圣王与君子混为一谈。据《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也就是说,君子首先在于“修己以敬”,如果在“修己以敬”的基础上做到“修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和谐,就是尧舜也不容易做好。显然,在孔子看来,君子与圣王是有区别的。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讲的是圣王“和而不同”,而不是君子“和而不同”,因而不能用于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此不同,朱熹的解读强调的是君子的内在品质,更为合乎《论语》讲君子“修己以敬”,并与圣王有所区别之意。
其次,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是就做事而言,而《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就做人而言,做事与做人不可混为一谈。《论语》讲君子与小人,首先是就人的内在品质而言,《论语·宪问》讲“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与此不同,史伯讲“和而不同”,强调“以他平他”,反对“以同裨同”,又讲“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显然是就做事而言;同样,晏婴讲“和如羹”,讲不同事物的“相成”“相济”,反对“以水济水”,也是就做事而言。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实际上是将做事与做人混为一谈,而朱熹的解读揭示君子“和而不同”的内在品质,更为合乎《论语》的君子之意。
再次,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由于只是就先王而言,就做事而言,因而不是就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小人而言,史伯以“和而不同”批评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并不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所以,以此为依据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必定会带来对于君子与小人对立的消解,甚至会陷于以“和”来解读道德上君子与小人的对立所引起的理论矛盾。与此不同,较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更为完善的朱熹的解读,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从心性层面强调了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因而更为合乎《论语》讲君子与小人相互对立之意。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荻生徂徕解《论语》,强调其中的“君子”“小人”主要是“以位言”。他说:“君子者,在上之称也。……君者治下者也,士大夫皆以治民为职,故君尚之子以称之,是以位言之者也。虽在下位,其德足为人上,亦谓之君子,是以德言之者也。”“小人,亦民之称也,民之所务,在营生,故其所志在成一己,而无安民之心,是谓之小人,其所志小故也。虽在上位,其操心如此,亦谓之小人;经传所言,或主位言之,或主德言之。所指不同,而其所为称小人之意,皆不出此矣。”①在荻生徂徕看来,《论语》中的“君子”为上层官员,“小人”为下层百姓,“君子”与“小人”是相须关系,而不是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他的《论语征》以晏婴的“和如羹”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反对何晏以“君子心和”、朱熹以“无乖戾之心”解其中的“和”,说:“何晏曰‘君子心和’、朱子曰‘无乖戾之心’,皆徒求诸心而失其义焉。盖古之君子学先王之道,譬诸规矩准绳,故能知其可否。苟不知可否之所在,其心虽和乎,乌能相成相济,如羹与乐乎?亦可谓之同已。”①他认为何晏讲“君子心和”、朱熹讲“无乖戾之心”,并非“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义,而君子之为君子在于知道事之可否,而使之达到相互和谐。问题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并不在于能否知道事之可否,讲事物之和谐,而在于内在的心性道德。
《论语》中的“君子”“小人”,确有一些并不是讲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②,但是,由此而像荻生徂徕那样,以为《论语》中的“君子”“小人”大都不是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尤其是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的“君子”“小人”并非就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而言,或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讨论。
当今不少学者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将《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的“和”解为“和谐”,并将“和谐”解为“由‘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所构成的‘普遍和谐’”,又进一步认为“儒家关于‘和谐’的观念是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作为起点的”。③这里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与人之外部的和谐统一起来,并以“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为起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实际上就是朱熹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言“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今人所讲的“普遍和谐”,实际上正是朱熹之后不少学者既讲君子之“和”在“无乖戾之心”,因而无“阿比之意”,又讲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的“和如羹”,引申出人之外部事物的和谐,而朱熹讲“无乖戾之心”,因而无“阿比之意”,正是这一“普遍和谐”的起点。由此可以看出,朱熹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不仅更为合乎《论语》之意,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6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一、汉唐时期的两种不同解读
《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仅讲君子与小人在道德上相互对立,而且讲“和而不同”“同而不和”,讲“和”与“同”的区别。关于“和”与“同”的区别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国语·郑语》记西周末史伯对周幽王“去和而取同”的批评。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③这里将“和”与“同”区别开来,强调“以多物,务和同”,讲由“多”而“和”,反对“同”而“一”,讲“和而不同”,无疑具有“和谐”之意。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是先王“和而不同”,而不是讲君子“和而不同”。
又据《晏子春秋》载,春秋末齐国晏婴与齐景公论“和”与“同”的区别,说:“和如羹焉,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①应当说,晏婴讲“和如羹”而反对“专一”,与史伯讲先王“和而不同”,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对于“和”与“同”的区别的讨论,其中的“和”也具有“和谐”之意,且同样只是讲先王“济五味、和五声”;至于所谓“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其中的“君子”应当是指君王。
东汉荀悦《申鉴》推崇《晏子春秋》所谓“和如羹”,并引出《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说: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咸甘苦不同,嘉味以济,谓之和羹;宫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谓之和声。臧否损益不同,中正以训,谓之和言;趋舍动静不同,雅度以平,谓之和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一声,谁能听之?’《诗》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无言,时靡有争。’此之谓也。”②这里讲“君子食和羹”,“纳和言以平其政”,所谓“君子”指的是君王;接着又讲《论语》的“君子和而不同”,似乎是把《论语》“君子和而不同”中的“和”解读为不同事物的相互和谐。
另据《后汉书·刘梁传》载,刘梁著《辩和同之论》,说:“君子之于事也,无适无莫,必考之以义焉。得由和兴,失由同起。故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春秋传》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剂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③显然,这里的解读也是以晏婴讲“和如羹”解《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和”即“和谐”。
应当说,无论是史伯讲“和而不同”,还是晏婴讲“和如羹”,都是就先王而言,要求君王讲“和谐”,并不涉及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如果据此解读《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将其中的“和”解读为“和谐”,强调“和”的价值而否定“同”,很可能会消解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不合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蕴含的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之意。
与此不同,三国时何晏《论语集解》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南北朝的皇侃《论语义疏》疏曰:“和,谓心不争也。不同,谓立志各异也。君子之人千万,千万其心和如一,而所习立之志业不同也。……小人为恶如一,故云‘同’也。好斗争,故云‘不和’也。”①后来,北宋的邢昺《论语注疏》疏曰:“此章别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则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②应当说,何晏、皇侃以及邢昺的解读,从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讲“和”与“同”,突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对立,不同于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对于“和谐”的推崇,较为合乎《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意。
然而,何晏、皇侃等的解读,在“和”与“同”的概念界定上,尚存在着某些不自洽。何晏《论语集解》讲“和”,把君子之“和”解读为君子之心的“和”,把小人之“不和”解读为小人“各争其利”;讲“同”,则把君子之“不同”解读为君子“所见各异”,把小人之“同”解读为小人“所嗜好者同”。皇侃《论语义疏》明确把君子的“和”“不同”与小人的“同”“不和”分别开来界定:就君子而言,“和,谓心不争也。不同,谓立志各异也”;就小人而言,“小人为恶如一,故云‘同’也。好斗争,故云‘不和’也”。也就是说,在何晏、皇侃等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中,无论是“和”的内涵,还是“同”的内涵,都不是统一的。
由此可见,汉唐时期对于《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解读,既有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而将其中的“和”解为“和谐”,实际上消解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也有何晏、皇侃等的解读,突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但尚没有就“和”与“同”的概念内涵做出自洽的解读。
二、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③这里从心性层面将“和”解读为“无乖戾之心”,将“同”解读为“阿比之意”,也就是认为君子“无乖戾之心”,因而无“阿比之意”;小人有“阿比之意”,因而有“乖戾之心”。显然,这样的解读,与何晏、皇侃等的解读一样,突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重要的是,朱熹的解读还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义利联系起来,认为君子尚义,所以“和而不同”,小人尚利,所以“同而不和”。朱熹还说:“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盖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会这一个公当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个私意,故虽相与阿比,然两人相聚也便分个彼己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纷争而不和也。”①也就是说,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不只在“和”与“同”的区别,更在于“公”与“私”的对立,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区别。朱熹门人辅广对《论语集注》引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做了讨论,说:“尹氏本意,虽只是以义利二字说不同、不和之意,然细推之,则君子之于事,唯欲合于义,故常和。然义有可否,故有不同;小人徇利之意则固同矣,然利起争夺,安得而和?”②显然,辅广进一步强调君子尚义,所以“和而不同”;小人尚利,所以“同而不和”。
与何晏、皇侃等的解读相比,朱熹的解读明显具有两大优势:其一,正如以上所述,何晏、皇侃等的解读尚没有就“和”与“同”的概念内涵做出自洽的解读,与此不同,朱熹的解读特别重视并明确给出了对于“和”与“同”的概念的统一界定;其二,何晏、皇侃等的解读讲君子与小人具有“和”与“不和”、“不同”与“同”的对立,但由于没有就“和”与“同”的概念内涵做出自洽的解读,这样的对立是含混的,与此不同,朱熹的解读对“和”与“同”的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统一界定,并进一步强调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对立,突出了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对立,因而是对何晏、皇侃等的解读的发展和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不仅从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的角度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而且明确反对依据晏婴“和如羹”所做的解读。朱熹《论孟精义》收录了吕、杨、侯氏的解读:
吕曰:“和则可否相济,同则随彼可否。调羹者五味相合为和,以水济水为同。”
……
杨曰:“五味调之而后和,而五味非同也。如以咸济咸,则同而已,非所以为和也。君子有可否以相济,故其发必中节,犹之五味相得也。小人以同为说,犹之以咸济咸耳,尚何和之有?”
侯曰:“和非同也,和则虽有可不可之异,济其美而已,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同非和也,同恶相济,如以水济水,安能和哉?故曰:‘小人同而不和。’”③
对此,朱熹《论语或问》说:“吕、杨、侯氏说,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则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状而言,似不可引以为证也。盖此所论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协恭,而无乖争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无阿谀党比之风。若小人则反是焉。此二者,外虽相似,而内实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状之隐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轨,非圣人不能究极而发明之也。……如此说,则君子之心,无同异可否之私,而惟欲必归于是;若晏子之说,则是必于立异,然后可以为和而不同也,岂非矫枉过直之论哉!”①这里对以晏婴“和如羹”来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出了批评,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朱熹看来,晏婴所谓“和如羹”,是“就事而言”,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就“君子小人之情状而言”,是就人的内在道德品质而言,所以“不可引以为证”。晏婴强调听取不同意见,所谓“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又讲“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济也”。然而,可否相济,只是“就事而言”,并非就道德上的君子小人而言,换言之,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做到可否相济,而在于内在道德品质的截然相反。
第二,朱熹认为,君子小人“外虽相似,而内实相反”,所以对于“和”与“同”的界定,不可只是从事物表面上看,而应当从人的内在心性看。朱熹《论语集注》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又进一步讲公私义利,以此把君子与小人对立起来;《论语或问》则讲“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协恭,而无乖争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无阿谀党比之风。若小人则反是焉”。显然,对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朱熹的解读强调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对立,而以晏婴“和如羹”为依据的解读则只是讲君子与小人在做事上的“和”与“同”的区别。
第三,朱熹认为,对于各种不同的事物,君子应当“必归于是”,而晏婴“和如羹”要求“必于立异,然后可以为和而不同”,过多讲不同事物之“和而不同”,属于“矫枉过直之论”。朱熹《论语集注》注“道不同,不相为谋”,曰:“不同,如善恶邪正之异。”②并且认为,“君子小人决无一事之可相为谋者也”。③应当说,在朱熹的话语中,天理、人欲、公私、义利,乃至君子小人,正如邪正、善恶,都是对立的,而不可“和而不同”,如果用晏婴“和如羹”来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实际上包含了对于小人的“和而不同”,必然会消解君子与小人的对立,那么君子就不是与小人对立的君子,也就不成其为君子,因而就会陷于悖论,所以用“和如羹”解“君子和而不同”是不可能的。
三、朱熹之后的讨论
朱熹解《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心性层面将“和”解读为“无乖戾之心”,将“同”解读为“阿比之意”,是就人的道德品质而言,并非“就事而言”。然而,人的道德品质与做事又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朱熹之后,有不少学者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既从心性的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又讲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
元代陈天祥《四书辨疑》不满足于朱熹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的解读,说:“和则固无乖戾之心,只以无乖戾之心为和,恐亦未尽。若无中正之气,专以无乖戾为心,亦与阿比之意相邻,和与同未易辨也。中正而无乖戾,然后为和。凡在君父之侧,师长、朋友之间,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可者献之,否者替之,结者解之,离者合之,此君子之和也。而或巧媚阴柔,随时俯仰,人曰可,己亦曰可,人曰否,己亦曰否,惟言莫违,无唱不和,此小人之同也。晏子辨梁丘据非和,以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此论辨析甚明,宜引以证此章之义。”①陈天祥的解读试图在朱熹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的基础上,引入“中正之气”,并进一步以晏婴的“和如羹”区别君子之和与小人之同,实际上是把朱熹的解读与晏婴讲“和如羹”结合起来。
明代程敏政也解释说:“和是无乖戾之心,同是有阿比的意思。孔子说君子的心术公正,专一尚义,凡与人相交,必同寅协恭,无乖戾之心。然事当持正处,又不能不与人辩论,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的心术私邪,专一尚利,凡与人相交,便巧言令色,有阿比之意。然到不得利处,必至于争竞,故曰‘小人同而不和’。”②后来王夫之作了训释,说:“君子以义为尚,所与共事功者,皆君子也。事无所争,情无所猜,心志孚而坦然共适,和也。若夫析事理于毫芒,而各欲行其所是,非必一唱众和而无辨者也,不同也……小人以利为趋,所与相议论者,小人也。以权相附,以党相依,依阿行而聚谋不逞,同也。乃其挟己私之各异,而阴图以相倾,则有含忌蓄疑而难平者也,不和也。”③应当说,程敏政、王夫之的解释,合乎朱熹《论语集注》之意。
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引述何晏所言:“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并指出:“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义者宜也,各适其宜,未有方体,故不同。然不同因乎义,而非执己之见,无伤于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务于是,则有争心,故同而不和。此即君子、小人之异也。”①显然,这里以义、利讲“和”与“同”,并由此从心性的层面讲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这与朱熹《论语集注》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引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是相通的。在讲君子与小人相互对立的基础上,刘宝楠《论语正义》又讲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的“和如羹”,从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引申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
清末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和康有为《论语注》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出一辙,都是先引述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的“和如羹”,然后引申出君子与小人的相互对立。简朝亮说:“由是言之,和则不乖戾,同则惟阿比,其义不昭然乎?”②康有为说:“盖君子之待人也,有公心爱物,故和;其行己也,独立不惧,各行其是,故不同。小人之待人也,媚世易合,故同;其行己也,争利相忮,不肯少让,故不和。”③这明显更为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
直到现代钱穆《论语新解》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故不能和。或说:和如五味调和成食,五声调和成乐,声味不同,而能相调和。同如以水济水,以火济火,所嗜好同,则必互争。”④显然,这样的解读都是从朱熹的解读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出发,并进一步引申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
四、余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于《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既有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而将其中的“和”解为“和谐”,又有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以及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朱熹之后的学者大多既从心性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又由此引申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应当说,在这些解读中,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并进一步讲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对立,发展并完善了何晏、皇侃等的解读,超越了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的解读。
首先,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是就先王而言,以此为依据解读《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将圣王与君子混为一谈。据《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也就是说,君子首先在于“修己以敬”,如果在“修己以敬”的基础上做到“修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和谐,就是尧舜也不容易做好。显然,在孔子看来,君子与圣王是有区别的。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讲的是圣王“和而不同”,而不是君子“和而不同”,因而不能用于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此不同,朱熹的解读强调的是君子的内在品质,更为合乎《论语》讲君子“修己以敬”,并与圣王有所区别之意。
其次,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是就做事而言,而《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就做人而言,做事与做人不可混为一谈。《论语》讲君子与小人,首先是就人的内在品质而言,《论语·宪问》讲“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与此不同,史伯讲“和而不同”,强调“以他平他”,反对“以同裨同”,又讲“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显然是就做事而言;同样,晏婴讲“和如羹”,讲不同事物的“相成”“相济”,反对“以水济水”,也是就做事而言。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实际上是将做事与做人混为一谈,而朱熹的解读揭示君子“和而不同”的内在品质,更为合乎《论语》的君子之意。
再次,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由于只是就先王而言,就做事而言,因而不是就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小人而言,史伯以“和而不同”批评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并不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所以,以此为依据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必定会带来对于君子与小人对立的消解,甚至会陷于以“和”来解读道德上君子与小人的对立所引起的理论矛盾。与此不同,较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更为完善的朱熹的解读,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从心性层面强调了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因而更为合乎《论语》讲君子与小人相互对立之意。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荻生徂徕解《论语》,强调其中的“君子”“小人”主要是“以位言”。他说:“君子者,在上之称也。……君者治下者也,士大夫皆以治民为职,故君尚之子以称之,是以位言之者也。虽在下位,其德足为人上,亦谓之君子,是以德言之者也。”“小人,亦民之称也,民之所务,在营生,故其所志在成一己,而无安民之心,是谓之小人,其所志小故也。虽在上位,其操心如此,亦谓之小人;经传所言,或主位言之,或主德言之。所指不同,而其所为称小人之意,皆不出此矣。”①在荻生徂徕看来,《论语》中的“君子”为上层官员,“小人”为下层百姓,“君子”与“小人”是相须关系,而不是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他的《论语征》以晏婴的“和如羹”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反对何晏以“君子心和”、朱熹以“无乖戾之心”解其中的“和”,说:“何晏曰‘君子心和’、朱子曰‘无乖戾之心’,皆徒求诸心而失其义焉。盖古之君子学先王之道,譬诸规矩准绳,故能知其可否。苟不知可否之所在,其心虽和乎,乌能相成相济,如羹与乐乎?亦可谓之同已。”①他认为何晏讲“君子心和”、朱熹讲“无乖戾之心”,并非“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义,而君子之为君子在于知道事之可否,而使之达到相互和谐。问题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并不在于能否知道事之可否,讲事物之和谐,而在于内在的心性道德。
《论语》中的“君子”“小人”,确有一些并不是讲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②,但是,由此而像荻生徂徕那样,以为《论语》中的“君子”“小人”大都不是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尤其是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的“君子”“小人”并非就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而言,或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讨论。
当今不少学者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将《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的“和”解为“和谐”,并将“和谐”解为“由‘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所构成的‘普遍和谐’”,又进一步认为“儒家关于‘和谐’的观念是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作为起点的”。③这里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与人之外部的和谐统一起来,并以“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为起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实际上就是朱熹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言“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今人所讲的“普遍和谐”,实际上正是朱熹之后不少学者既讲君子之“和”在“无乖戾之心”,因而无“阿比之意”,又讲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的“和如羹”,引申出人之外部事物的和谐,而朱熹讲“无乖戾之心”,因而无“阿比之意”,正是这一“普遍和谐”的起点。由此可以看出,朱熹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不仅更为合乎《论语》之意,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6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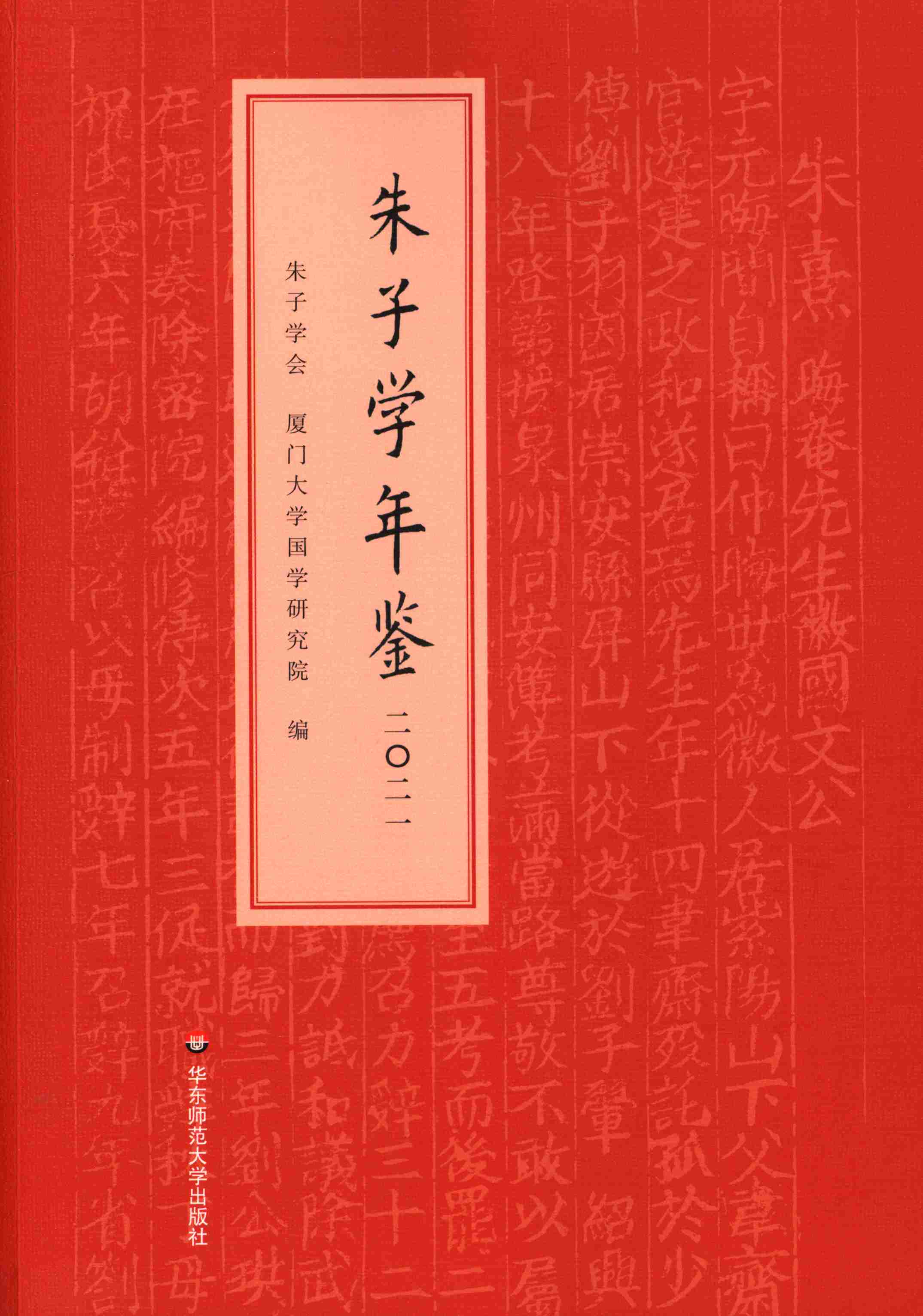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1》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共9部分: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学界概况、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收录《融突和合论——中国哲学元理》《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2021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简介》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乐爱国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