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研究新视野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1》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6776 |
| 颗粒名称: | 朱子学研究新视野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4 |
| 页码: | 047-110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明清朱子学作为宋明理学研究新增长点的地位,分析了《四书》学的忧乐情怀与宋儒内圣之道的关联,以及历代对《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同时,文章还讨论了朱熹对程颢思想的创造性诠释以及戴震与朱子对《孟子》性论诠释的差异。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 宋明理学 |
内容
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
陈来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教授主编的《陆陇其全集》。陆陇其是清初的朱子学家,号称理学名臣。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清初朱子学的研究将会有重要的推动。进而言之,我觉得明清朱子学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将会成为未来新的增长点。
回顾我们四十年来宋明理学的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完成了朱子哲学研究爬坡的任务。所谓爬坡,就是我们要经过攀登,然后占据包括东亚在内的整个世界朱子哲学研究的高地。在第一个十年之中,这个任务我们达成了。到了第二个十年,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完成了攀爬、占领世界学术领域里面王阳明哲学研究的高地。
然后,到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宋明理学研究的增长点是朱子学和阳明学之“后学”的研究,比如阳明后学的相关文献整理。江南地区的学者,浙江、上海的很多学者都参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特别是浙江的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阳明后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支朱子后学,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开始阶段主要是我跟朱杰人教授等人一起推动的,以南昌大学为基地进行系统的朱子后学的研究,现在正在开始慢慢地开花结果。但细致地看,目前朱子后学的研究课题,截止范围大概是在元代(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其截止的断代是在元代),很多朱子门人、后学的研究都是到元代为止,这是其研究范围。
然而,广义地讲朱子后学,当然就应延伸到明代、清代。因此这个朱子“后学”的课题,还需要在明清时代的朱子学之中继续发展,也就是说,想要完整地呈现整个的朱子学、朱子后学的研究,新的增长点就在明代、清代。甚至可以说,明清朱子学的重要性绝不低于宋末和元代的朱子学。这个时期,有大量的朱子学者以及朱子学的文献,所以说诸如陆陇其等明清朱子学相关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
特别是,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还与另一个线索的研究很有关系,就是说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们除了朱子学、阳明学以外,还有一条线索就是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研究。这一时段其实也是我自己比较关切的,比如说我在1986年曾撰文讨论“二陆”,就是陆世仪、陆陇其。陆世仪是明末清初的,陆陇其是清初的。陆陇其强调实行实学,反对空谈心性,反对太极玄想,要求使学问向人的道德实践方面发展,表现出他与早期朱学的差别,可以说他是属于清初理学内部的实践派。我自己对陆世仪的评价比较高,认为他是明末清初诸大家之一。原来我们讲三大家,其实应该是四大家,如果缺了陆世仪是不完整的。因为从刘宗周下来,黄宗羲还是顺着心学的脉络进行学术总结的;王船山的独立性很强,但是他的后期还是顺着张横渠;顺着朱子学下来进行的总结性的研究,那就是陆世仪。所以说,我一直认为陆世仪是明代朱子学之中具有总结性、代表性的人物。另外我也研究了黄道周,他是明末的“二周”之一,后来有些学者做了后续的研究,明清哲学中专门的研究我后来选择了王船山。明清之际这个阶段的研究,不仅对我自己而言,就是对整个中国学术界来讲,也可以说是除了朱子学、阳明学以外,一个独立的重要领域。
明清朱子学跟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在时间段上是有交叉的,像陆世仪,既是明清朱子学的,也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所以研究这一时段,从我们宋明理学整个学科的布局来说,是不断发展下去的有效的新的增长点。就宋明理学领域来讲,明清朱子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明代中期开始的这段朱子学,我们以前的研究也不是很清楚。如果这段朱子学研究得不清楚,不仅对朱子学的发展线索不能清楚地了解,对阳明学本身也不能清楚地了解。也就是说,阳明学有些细部的了解,必须对应着朱子学的研究。比如王阳明中年时期在北京、在南京,跟朱子学者有着复杂交流,这些问题一直就没被很好地研究过,最近几年开始有学者来做研究了。
所以说,明清朱子学的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这些工作也可以算作江南儒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因为明清朱子学里头有很大一块,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学者,有很多都是属于江南儒学的研究范围。因此,对于现在江南的学者,以浙江和上海地区为主的年轻学者来说,这个新的有效增长点更需要认真把握,也应当能够做得更加成功,比如《陆陇其全集》的顺利出版,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1月20日,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四书》学的忧乐情怀与宋儒的内圣之道
朱汉民
中国哲学是以人文关怀、人生意义为出发点。宋儒既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又追求“孔颜乐处”的超然境界。理学家通过挖掘《四书》的思想资源,以表达自己对人文世界的忧患与喜乐的进一步思考,进而建构一种既有人文关怀、又有精神超越的内圣之道。质而言之,宋代士大夫推动儒家内圣之道的哲学建构,其出发点正是一种与忧乐相关的人文关怀。
一、《四书》的忧患意识与宋儒的社会关切
宋代士大夫普遍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既有《四书》记载的儒家士人的精神传统,又有着现实的社会政治原因。
首先考察《四书》的士人精神传统。在早期儒家的子学著作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孔子及其弟子们对君王无德、士人无耻、天下无道的强烈忧患。孔子深刻表达了他对天下无道的关切,他一直强调“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进一步思考天下无道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社会普遍缺乏仁爱精神,而仁爱精神的推广又离不开教育。所以,孔子《论语·述而》反复强调:“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卫灵公》记载:“君子忧道不忧贫。”可见,孔子已经将自己对社会政治的忧患,转化为对文化教育的忧患。《孟子·离娄下》也大量记载了孟子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方面的种种忧患,他进一步指出忧患意识的价值与意义:“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孟子相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而君子不能够消极地等待忧患灾患的来临,而是要保持积极的防患于未然的心理准备。所以,忧患意识的重要价值,就是要强调持久、不变的戒惕心理,即所谓保持一种“终身之忧”的精神状态,最终才达到“无一朝之患”的结果。《孟子·告子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是强调忧患的精神状态是为了使人提高警觉,心存戒惕而临危不乱。
《四书》元典奠定了的儒家士人的精神传统,特别是对宋代士大夫形成的忧患意识有直接影响。
如果说汉唐时期的儒家士族衍化为因文化垄断而成为既得利益的“准贵族”的话,宋代士大夫主要是来自于白衣秀才,他们是一个从民间士人上升到庙堂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的社会群体,他们与先秦儒家诸子既有着相近的精神文化的血缘联系,又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文化情怀,故而自然和早期儒家士人的人格精神十分一致。他们从《四书》元典中寻找人格典范、思想资源,《论语》《子思子》《孟子》表达出来的士君子的忧患意识和人格精神,成为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源泉与效法典范。早期儒家士人表现出来的关怀现实、心忧天下的人格精神,对宋代士大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然,宋代士大夫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还与两宋面临的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分不开。宋代有一个政治现象值得注意:士大夫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两宋时期,恰恰面临内忧外患的严重政治局面。士大夫群体在承担与君主“共治天下”政治权力的同时,相应也就承担了重大的政治责任,这一重大政治责任很快也转化为士大夫群体对内忧外患局面的忧患意识。一方面,宋朝面临严重的内忧,宋初为了防范割据势力和各种政治力量篡权,强化中央集权而推动政治、军事、科举等方面的变革,他们在防止地方割据势力而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积弊,特别是出现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等问题,逐渐导致国力贫弱、民生艰难;另一方面宋朝面临“外患”,宋开国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却又相继陷入了辽、西夏、金和蒙政权的威胁,宋朝立国后的数百年间,始终受到外患的侵扰,游牧民族的南下侵夺始终是两宋的大患。所以,在宋朝建国后不久,“内忧”“外患”的矛盾开始显现,处于政治中心的宋代士大夫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普遍持有一种浓厚的忧患意识。本来,两宋时期士大夫群体是凭借自己拥有的文化知识、政治理念、价值信仰而参与政治的,并且获得了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机遇,所以,他们能够成为参与朝政的政治主体,而且往往会成为一种政治清流,而并不会像其他如军阀、后宫、宦官等权贵政治力量一样,容易导致对权力的贪婪与对民众的傲慢;相反,当士大夫群体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价值理念,必然会积极推动对内忧外患严峻现实的变革。所以,士大夫越是成为政治主体,他们感到的责任也越大,随之他们的忧患意识也越强。两宋以来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确实引发了士大夫的强烈忧患与革新意识。范仲淹向仁宗帝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变法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办法。范仲淹“立朝益务劲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欣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①王安石一直怀有很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顾内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而风俗日以衰坏。”②他主导的熙宁变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常恐天下之不久安”的严重忧患。
由于《四书》就是一套充满士人忧患意识的儒家经典,宋儒可以通过诠释《四书》,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在宋儒对《四书》的诠释传统中,特别强调士人的人文情怀、政治责任,也特别强调士人的家国情怀、天下担当,希望能够唤起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二程将《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子由、颜子等人表现出来的责任承担及其忧患意识,统统理解为“圣贤气象”:
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如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由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子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观此数句,便见圣贤气象大段不同。①
孔子、子由、颜子等人表现出来的无非是士人从政所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与忧患情怀,但是,二程将这一种本来是士人期望承担的政治责任与忧患意识,提升为一种“圣贤气象”,以作为士大夫效法的人格典范,宋儒的这一看法其实是有重要的现实原因的。
由此可见,宋代士大夫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崛起,他们拥有的强烈政治责任、忧患意识,一方面与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身份的提升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与他们自觉继承先秦儒家士人的人格精神有密切关系。宋儒在诠释早期儒家士人的子学典籍即《四书》元典时,实现了在现实中面临的内忧外患与《四书》文本忧患意识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对话。两宋以来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是宋代士大夫激发起忧患意识的现实原因;而一千多年前儒家士君子的人格精神,则是宋代士大夫激发起忧患意识的精神源泉。所以,追溯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精神渊源,可以在先秦儒家士人的子学系统及经典传记之中找到,特别是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中找到。宋代士大夫从早期儒家子学中获得相关的思想资源,《论语》《子思子》《孟子》表现出来的士人精神传统,既为宋代士大夫精神崛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激发了宋代士大夫重建与自己精神契合的《四书》学。由此可见,以《四书》学为代表的宋学之所以蓬勃兴起,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知识传统的建构,更加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新的士大夫精神传统的建构。
所以,宋儒一方面仍然关怀现实、心忧天下,希望实现博施济众的经世事业,故而仍然关注国家政治治理;另一方面,宋儒的学术旨趣重心已经从汉代的“外王”转向宋代的“内圣”,宋儒往往相互劝勉、自我期许要成为“圣人”,普遍向往、追求“圣贤气象”的人格理想,使宋学具有“内圣之学”的特点。所谓“宋学精神”,其实也就是宋代士大夫精神。宋代士大夫坚持对知识、道德和功业的不懈追求,倡导一种有体有用的学术精神,特别强调由士大夫掌控的“道统”要主导由朝廷掌控的“治统”,这一切,均体现出宋代士大夫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由于宋学兴起代表了士大夫的文化自觉,他们无论是在庙堂执政,还是在学府执教,均表现出鲜明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他们倡导、建构一种体现士大夫主体意识的道统论,其实正是在推动一场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宋学运动。
二、《论语》的孔颜之乐与宋儒的精神超越
宋代士大夫追求的“圣贤气象”,还表现出另外一个侧面,即对“孔颜乐处”的精神超越、人格理想无限向往与不懈追求。在宋儒对“圣贤气象”的诠释中,“圣贤”不仅仅追求“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更应该具有“孔颜之乐”的超越精神和人格特质。宋代士大夫对“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人格理想的追求,也是通过《四书》学的诠释来完成的。特别是《论语》《孟子》中记载了早期儒者积极入世的乐观精神和人生境界,往往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向往、仿效的典范。
“孔颜乐处”源于《论语》。《论语·述而》中有多处记载孔子对精神快乐的追求,如孔子曾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雍也》记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述而》记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这里可以看到,孔子并不因为事业困局、颠沛流离而忧伤、痛苦,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士君子应该将快乐学习、快乐生活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特别是《论语·雍也》孔子对学生颜回有一段评价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非常欣赏颜回能够超越物质生活条件、达到一种纯粹精神快乐的人生境界,肯定这一种“乐”的状态高于“忧”。“孔颜乐处”代表了作为个体存在、感性生命的儒家士人,一直将“乐”作为自己的生命本真和人生理想。
在汉唐儒家那里,并没有对孔子、颜回关于人生之乐表达出特别的关注。但是,原始儒家追求“乐”的人生境界,在宋代士大夫那里得到强烈的呼应。《论语》中有关“孔颜之乐”的问题,很快成为一个士大夫普遍关注、热烈讨论的重大问题。从两宋开始,士大夫群体普遍盛行以“孔颜之乐”的人生境界相劝勉,而且他们也将“孔颜之乐”作为求圣之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的学术问题。
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思想史现象,即北宋那些著名的、有创造性的新儒家学者,他们进入圣门,似乎都是从体悟“孔颜之乐”开始的。他们对“孔颜之乐”境界的体悟,又总是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宋学学者群体中,几位有创始之功的学者,诸如范仲淹、胡瑗、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他们进入圣学门槛、建构道学学术,往往总是与“孔颜乐处”的问题思考相关。张载年少时喜谈兵,范仲淹告诫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范仲淹还将《中庸》作为领悟“名教可乐”的主要经典。胡瑗主讲太学时就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试诸生。道学宗师周敦颐,就是一个追求“孔颜之乐”的士大夫,史书记载他“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①周敦颐也以这一种人生境界启发、培养弟子,程颢、程颐兄弟十四五岁从学于理学开山周敦颐,周子教他们“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②程颢、程颐由“孔颜之乐”的人生追求而走向道德性命的义理建构,而成为理学的奠基人。
为什么“孔颜之乐”会成为这些宋学重要开拓者普遍关注、深入思考、引发创新的重要学术问题?这一学术问题的思想史意义在哪里?宋代士大夫对“孔颜之乐”的普遍追求,使他们往往将是否达到“乐”的境界作为得道与否的标志,表达的恰恰是这些承担着沉重政治责任、社会忧患的士大夫群体另一精神面向和思想追求。他们认定,从孔子、颜回到子思、孟子,都无不追求这种“心下快活”的人生境界,从个体存在、感性生命的角度来看,宋代士大夫同样会积极寻求爱莲观草、吟风弄月的快乐人生。宋儒认为,要达到这种精神上的“快乐”“气象”,离不开《四书》体系的学术资源,包括身心修炼工夫与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四书》学之所以在宋代兴起,恰恰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宋代士大夫寻求“圣贤气象”“社会忧患”“孔颜之乐”的精神需求,成为这一个时代能够表达时代精神的经典依据。
正因为作为政治精英的士大夫不仅仅是社会角色,还是感性个体,他们也会面临个人的是非、得失、生死问题,他们意识到,个人的忧、苦、烦、闷等消极情绪,其实源于自己对得失是非荣辱的偏执。那么,他们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个人的忧虑、烦恼等消极情感等问题?佛老之学提供的方案是以自己的内心平和为最高目标,故而主张通过精神修炼,以能够在面临是非、得失、生死问题时达到“不动心”“无情”“空寂”的精神状态与心理状态;但是,儒家思想的最高目标是以内圣与外王为一体,通过“正心诚意”的内圣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所以,儒家人格理想的“圣贤”“君子”,总是会充满家国情怀、天下牵挂。理学家胡宏谈到“圣人”时,认为他们和凡人一样有着丰富的个人情感与人生体验:“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有害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人以术为伤德也,圣人不弃术;人以忧为非达也,圣人不忘忧;人以怨为非宏也,圣人不释怨。”③他认为,圣人和众人一样,也是一个有着情、才、欲、忧、怨的个体存在,特别是儒家的圣贤、士君子必须承担起社会关切、家国情怀的忧患意识与外王事业,他们常常感到需要学习佛老的精神超越境界,面对人间不平、痛苦而自己却保持“不动心”“无情”甚至是“空寂”的精神状态与心理状态。所以,儒家的圣贤、士君子作为个体存在,他们需要有一套处理忧患、痛苦等不良情绪的修炼方法和精神境界。唐宋以来,儒家士大夫也一直在深入思考,如何化解个人的忧、怨等不良情绪,提升喜、乐等积极情感。
应该说,魏晋隋唐以来,佛道对这些问题均有过深入的思考和实践,其中佛教更是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随着魏晋隋唐佛教的大规模传入和发展,主张通过精神修炼而化解个体的不良情绪,对士大夫精神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进一步引导宋儒更加关切通过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以化解忧怨等不良情绪和提升喜乐等积极情感。所以,从个体存在来说,新儒家精神修炼的目标就是所谓“寻乐”“心下快活”,北宋儒林流行“寻孔颜乐处”,以及他们在修身中以是否“乐”为目标,即所谓“反身而诚,乃为大乐”。①这些所谓的“乐”,其实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忧、苦、烦、闷等各种消极情绪,从而达到身心的安泰、自在、舒展、洒落的超越境界,这一超越人生境界与天理论的人文信仰、哲学建构有关。宋儒罗大经说:“吾辈学道,须是打叠教心下快活。古曰无闷,曰不愠,曰乐则生矣,曰乐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饮水之乐,颜子有陋巷箪瓢之乐,曾点有浴沂咏归之乐,曾参有履穿肘见、歌若金石之乐,周程有爱莲观草、弄月吟风、傍花随柳之乐。”罗大经将修身目的确定为“教心下快活”,这既是一种“爱莲观草、弄月吟风、傍花随柳”的感性快乐,又是个人实现了对自己感性生命的超越,是考察一个人是否“得道”的重要标志。所以,宋儒的“寻孔颜乐处”,首先必须能够超越个人忧、苦、烦、闷的消极情绪,通过修身使自己“世间一切声色嗜好洗得净,一切荣辱得失看得破”②,这一精神超越的思想根基必然是哲学与信仰。
故而在两宋时期,《四书》学成为宋代士大夫特别关注、热烈讨论的核心经典。因为宋代士大夫特别在意是否达到“圣贤气象”的崇高境界,是否在承担重要政治责任的同时还能够具有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心境。他们通过阅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中的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圣先贤对“乐”的追求,进一步表达出自己对自由、自在、自得、自乐的向往与追求。理学开山祖周敦颐在《通书·颜子》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③在这里,周敦颐通过对《论语》中“颜子之乐”的诠释,认为这是一种“见其大而忘其小”,其实是指颜回达到了人与天道合一的精神境界。这一个“大”,恰恰是周敦颐在《太极图说》《通书》中建构起来的“太极”“诚”的宇宙本体。所以,这里所谓的“颜子之乐”,其实就是依据于“圣贤之道”而达到的崇高境界。譬如程颢也是通过挖掘《论语》《孟子》和《中庸》的思想资源,而建构这样一种“颜子之乐”的精神境界,他在描述仁者精神境界时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①仁本来是《论语》中的核心道德思想,而宋儒进一步将仁提升为一种哲学意义的形而上之本体。我们注意到,程颢建构的仁学本体论,其首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仁学提供一种知识学依据,更是为他们满足“孔颜之乐”的情感需求,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乃为大乐”提供一种安顿精神的依据。所以,为了达到“浑然与物同体”“反身而诚”的“乐”之心灵境界,程颢等道学家从早期儒家士人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对“乐”的追求中,找到了自己精神安顿的依据,并由此走向内圣之道的哲学建构。
三、宋儒的忧乐意识与内圣之道建构
从北宋开始,士大夫群体非常向往“圣贤气象”的人格理想,通过追求一种“孔颜乐处”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境界来体现这一种“圣贤气象”。宋儒强调“圣贤气象”的最重要标志不是外在的政治功业之“用”,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之“体”。这一“内圣”的心理状态、精神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从宋儒的学术论述和现实追求来看,“圣贤气象”往往体现为情感心理、精神情怀的忧与乐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宋儒之所以需要建构出一套有关内圣外王之道,其实是源于生活世界的忧乐人生,宋儒哲学建构的精神动力、价值源泉是他们的人文世界。
首先,宋儒之所以将自己的忧乐情怀归结为一种内圣之道,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前提与价值承担,即他们的忧乐应该是与天下苍生休戚相关的情怀。在宋儒看来,尽管一切人均有忧与乐的情感,而圣贤、士君子表达出来的忧与乐,应该是不同于常人的。普通常人的忧与乐可能是源于自己个人的利欲、需求与境遇,而圣贤、士君子的忧乐却总是直接关联人民幸福、国家安泰、天下和美。所以,北宋时期的许多儒家士大夫,总是将圣贤、君子的忧与乐与天下的忧与乐联系起来。欧阳修曾经谈到圣人的忧乐情感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众人之豫,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②欧阳修所推崇的“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正是强调圣人并不执着于个人的忧与乐,而是将天下的忧与乐看作是自己的忧与乐。北宋时期士大夫普遍推崇的道德精神与人格理想,在范仲淹著名的《岳阳楼记》中表达得更是特别充分,也就是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这一类思想观点,均是强调圣贤、士君子的社会担当、天下情怀的责任意识,要求士大夫要有君子、圣贤的社会责任和天下情怀,将个人的忧乐和天下的忧乐联系起来。这其实恰恰是宋儒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
但是,宋代士大夫不仅仅是强调要将个人忧乐与天下忧乐联系起来,我们进一步探究时还可以追问:宋儒为什么会以“忧”与“乐”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感描述“圣贤气象”?这两种不同类型情感分别体现出什么不同的人文意义?
两宋时期的儒家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进入历史舞台,他们总是对自己的政治责任、社会使命有强烈的承担意识,所以,他们对两宋的内忧外患十分敏感,他们追求现实的外王事业,完全有可能因此而沉溺于忧虑、痛苦、烦恼等消极情绪之中而难以自拔。从宋儒的思想言论和生活实践中会发现,当他们在追求外王事业的过程中,必然会承担社会之苦、国家之难的沉重压力,故而忧患必然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焦点和重心。许多现代学者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儒家人格理想、中国文化特征是忧患意识。但是,为什么宋代士大夫总是不得不经历这样的人生磨难和生命悲苦?宋儒并不相信我们的生活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极乐世界,他们不能够依赖因果报应、上帝赏罚的宗教信仰来解决、化解他们面临的严峻精神问题。要如何才能够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以回归到生命本质的心灵平静、精神愉悦、身心安泰?
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一旦落实在世俗的生活世界,他们也必须处理个体存在、感性生命具有的消极情感,他们当然希望回归心灵平静、精神愉悦、身心安泰的生命状态,并以此作为根本精神导向,这时候,“乐以忘忧”“曾点之志”“乐是心之本体”等思想观念就成为他们情感世界的追求和目标。可以说,宋代新儒家之所以追求“孔颜之乐”,恰恰在于他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精神向度,就是解决他们在社会关切、家国情怀中产生的忧患问题。他们之所以需要寻乐,是根源于他们从事外王事业必然面临的入世之忧;而他们也需要化解、超越内心沉重的忧患,故而迫切需要一种超然之乐。所以,“圣贤气象”既能够凸显宋代士大夫的责任意识,同时也能够表达士大夫的超然境界。许多现代学者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儒家人格理想、中国文化特征是乐的精神。所以,宋代士大夫“圣贤气象”的精神追求,既可能体现为“忧患意识”,更应该体现为“孔颜之乐”。宋代士大夫并不希望永远陷于“忧患”之苦,也不希望溺于一己之“乐”,故而只能够是兼顾社会责任的忧患意识与个体生命本真的乐天精神,最终达到一种忧乐圆融的精神境界与理想人格。
宋儒不仅仅是拥有强烈的忧乐情怀,还以此忧乐情怀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心性哲学。人们往往认为哲学是理性智慧的产物,而宋儒“致广大、尽精微”的高深哲学为什么会与“忧”与“乐”的情感世界相关联?
这时,我们就来到理学“内圣之道”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核心。宋代士大夫在积极入世中为什么会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他们又为什么能够在忧患处境中寻“孔颜乐处”?其实两者均与“士志于道”的精神信仰有关。儒家士人的信仰是道,但恰恰是魏晋隋唐以来,儒家信仰之道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许多有事业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士大夫往往是出入佛老,在佛道的宗教信仰和空无哲学中寻求精神宁静。宋儒必须为自己的“忧患意识”“孔颜乐处”找到信仰、哲学的依据,这样他们才能够超越“忧患意识”带来的困扰,才能够真正实现“孔颜之乐”的精神升华。所以,《周易》的宇宙哲学成为宋儒建构信仰依据、哲学依据的重要典籍。
这里举宋儒解释《周易》中《困卦》的一个例子,能够使我们看到宋儒的宇宙哲学与忧乐意识的密切关系。《困》似乎象征作为政治主体的两宋士大夫面临的历史困局,他们一旦进入现实世界就不能不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但是,宋儒希望一切“志于道”的圣贤、士君子,能够在困局与忧患中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范仲淹对于《困卦》的“泽无水”,他主张“困于险而又不改其说,其惟君子乎,能困穷而乐道哉”。①胡瑗也是如此:“惟君子处于穷困,则能以圣贤之道自为之乐,又能取正于大有德之人以为法则,故所行无不得其道,所以获吉而无咎矣。”②程颐进一步强调:“大人处困,不唯其道自吉,乐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③“君子当困穷之时……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④可见,范仲淹、胡瑗、程颐在诠释《困卦》的卦义时,均强调两点:其一,任何穷塞祸患的困境均不可动摇士君子坚守道义、不改志向的决心;其二,必须要在“君子困穷”的境遇中坚持以道自乐。可见,宋儒对《困卦》卦义的阐发,已经深入到理学内圣之道的核心问题,即如何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解决多灾多难的现实困局。程颐认为:“以卦才言处困之道也。下险而上说,为处险而能说,虽在困穷艰险之中,乐天安义,自得其说乐也。时虽困也,处不失义,则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时当困而反亨,身虽亨,乃其道之困也。”⑤君子虽然处于困穷艰险的时势中,他无法获得个人命运的亨通,但是他仍然应该通过坚守道义、乐天安义并自得其乐,这就是所谓的“孔颜之乐”。
为了坚定自己的“乐道”精神,宋儒重新建构了内圣之道,即建立一套以无极太极、理气道器的宇宙论为哲学基础的心性之学。宋儒建构了天人一体的心性之学与居敬穷理的修身工夫,他们坚持一切人均可通过心性修养而获得“圣贤气象”,这是宋代士大夫能够获得精神上的自我救赎的唯一可能。宋儒特别是在《四书》的经典文本中,找到了他们迫切需要的如何能够达到忧中有乐、乐不忘忧、忧乐圆融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的哲学依据。
宋学本来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宋儒当然希望在内圣之道和外王之道两方面均有进一步拓展;但在宋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宋儒越来越意识到内圣的根本性,特别是宋代士大夫的忧乐情怀和对理想人格的向往,故而逐渐将内外兼顾的宋学转型为以内圣为主导的性理之学。什么是“性理之学”?元代理学家吴澄说:“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①当一个人体认到“吾之性”即是“天地之理”,由自我的内在心性可上达宇宙之理,他承担的“忧患意识”就具有了崇高的精神价值,而他的“孔颜之乐”才能够提升到一种真正的精神超越境界。所以,追求内圣之道的宋儒更加热衷于形而上维度的思想建构,对理气、道器、人心道心、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问题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们将《周易》的宇宙哲学与《四书》的人格哲学结合起来,建立起形而上性理与形而下生活紧密相连的内圣之道。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历代对《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
——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
乐爱国
《论语·子路》载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明显是就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而言。然而,当今学者的解读,大都以西周末史伯批评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并且讲“和而不同”以及春秋末齐国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将其中的“和”解读为“和谐”。李泽厚《论语今读》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君子和谐却不同一,小人同一却不和谐。”①同时还特别强调:“‘和’的前提是承认、赞成、允许彼此有差异、有区别、有分歧,然后使这些差异、区别、分歧调整、配置、处理到某种适当的地位、情况、结构中,于是各得其所,而后整体便有‘和’——和谐或发展。”②问题是,能够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吗?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果这里的“和”解读为“和谐”,是否意味着君子与小人也应当“和谐”?在孔子那里,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能够“和谐”吗?孔子讲“道不同,不相为谋”,讲的就是君子与小人不应当“和谐”。可见,孔子之所以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中还需要做更多、更为深入的解读。
一、汉唐时期的两种不同解读
《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仅讲君子与小人在道德上相互对立,而且讲“和而不同”“同而不和”,讲“和”与“同”的区别。关于“和”与“同”的区别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国语·郑语》记西周末史伯对周幽王“去和而取同”的批评。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③这里将“和”与“同”区别开来,强调“以多物,务和同”,讲由“多”而“和”,反对“同”而“一”,讲“和而不同”,无疑具有“和谐”之意。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是先王“和而不同”,而不是讲君子“和而不同”。
又据《晏子春秋》载,春秋末齐国晏婴与齐景公论“和”与“同”的区别,说:“和如羹焉,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①应当说,晏婴讲“和如羹”而反对“专一”,与史伯讲先王“和而不同”,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对于“和”与“同”的区别的讨论,其中的“和”也具有“和谐”之意,且同样只是讲先王“济五味、和五声”;至于所谓“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其中的“君子”应当是指君王。
东汉荀悦《申鉴》推崇《晏子春秋》所谓“和如羹”,并引出《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说: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咸甘苦不同,嘉味以济,谓之和羹;宫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谓之和声。臧否损益不同,中正以训,谓之和言;趋舍动静不同,雅度以平,谓之和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一声,谁能听之?’《诗》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无言,时靡有争。’此之谓也。”②这里讲“君子食和羹”,“纳和言以平其政”,所谓“君子”指的是君王;接着又讲《论语》的“君子和而不同”,似乎是把《论语》“君子和而不同”中的“和”解读为不同事物的相互和谐。
另据《后汉书·刘梁传》载,刘梁著《辩和同之论》,说:“君子之于事也,无适无莫,必考之以义焉。得由和兴,失由同起。故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春秋传》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剂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③显然,这里的解读也是以晏婴讲“和如羹”解《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和”即“和谐”。
应当说,无论是史伯讲“和而不同”,还是晏婴讲“和如羹”,都是就先王而言,要求君王讲“和谐”,并不涉及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如果据此解读《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将其中的“和”解读为“和谐”,强调“和”的价值而否定“同”,很可能会消解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不合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蕴含的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之意。
与此不同,三国时何晏《论语集解》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南北朝的皇侃《论语义疏》疏曰:“和,谓心不争也。不同,谓立志各异也。君子之人千万,千万其心和如一,而所习立之志业不同也。……小人为恶如一,故云‘同’也。好斗争,故云‘不和’也。”①后来,北宋的邢昺《论语注疏》疏曰:“此章别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则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②应当说,何晏、皇侃以及邢昺的解读,从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讲“和”与“同”,突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对立,不同于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对于“和谐”的推崇,较为合乎《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意。
然而,何晏、皇侃等的解读,在“和”与“同”的概念界定上,尚存在着某些不自洽。何晏《论语集解》讲“和”,把君子之“和”解读为君子之心的“和”,把小人之“不和”解读为小人“各争其利”;讲“同”,则把君子之“不同”解读为君子“所见各异”,把小人之“同”解读为小人“所嗜好者同”。皇侃《论语义疏》明确把君子的“和”“不同”与小人的“同”“不和”分别开来界定:就君子而言,“和,谓心不争也。不同,谓立志各异也”;就小人而言,“小人为恶如一,故云‘同’也。好斗争,故云‘不和’也”。也就是说,在何晏、皇侃等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中,无论是“和”的内涵,还是“同”的内涵,都不是统一的。
由此可见,汉唐时期对于《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解读,既有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而将其中的“和”解为“和谐”,实际上消解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也有何晏、皇侃等的解读,突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但尚没有就“和”与“同”的概念内涵做出自洽的解读。
二、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③这里从心性层面将“和”解读为“无乖戾之心”,将“同”解读为“阿比之意”,也就是认为君子“无乖戾之心”,因而无“阿比之意”;小人有“阿比之意”,因而有“乖戾之心”。显然,这样的解读,与何晏、皇侃等的解读一样,突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重要的是,朱熹的解读还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义利联系起来,认为君子尚义,所以“和而不同”,小人尚利,所以“同而不和”。朱熹还说:“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盖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会这一个公当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个私意,故虽相与阿比,然两人相聚也便分个彼己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纷争而不和也。”①也就是说,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不只在“和”与“同”的区别,更在于“公”与“私”的对立,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区别。朱熹门人辅广对《论语集注》引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做了讨论,说:“尹氏本意,虽只是以义利二字说不同、不和之意,然细推之,则君子之于事,唯欲合于义,故常和。然义有可否,故有不同;小人徇利之意则固同矣,然利起争夺,安得而和?”②显然,辅广进一步强调君子尚义,所以“和而不同”;小人尚利,所以“同而不和”。
与何晏、皇侃等的解读相比,朱熹的解读明显具有两大优势:其一,正如以上所述,何晏、皇侃等的解读尚没有就“和”与“同”的概念内涵做出自洽的解读,与此不同,朱熹的解读特别重视并明确给出了对于“和”与“同”的概念的统一界定;其二,何晏、皇侃等的解读讲君子与小人具有“和”与“不和”、“不同”与“同”的对立,但由于没有就“和”与“同”的概念内涵做出自洽的解读,这样的对立是含混的,与此不同,朱熹的解读对“和”与“同”的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统一界定,并进一步强调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对立,突出了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对立,因而是对何晏、皇侃等的解读的发展和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不仅从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的角度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而且明确反对依据晏婴“和如羹”所做的解读。朱熹《论孟精义》收录了吕、杨、侯氏的解读:
吕曰:“和则可否相济,同则随彼可否。调羹者五味相合为和,以水济水为同。”
……
杨曰:“五味调之而后和,而五味非同也。如以咸济咸,则同而已,非所以为和也。君子有可否以相济,故其发必中节,犹之五味相得也。小人以同为说,犹之以咸济咸耳,尚何和之有?”
侯曰:“和非同也,和则虽有可不可之异,济其美而已,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同非和也,同恶相济,如以水济水,安能和哉?故曰:‘小人同而不和。’”③
对此,朱熹《论语或问》说:“吕、杨、侯氏说,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则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状而言,似不可引以为证也。盖此所论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协恭,而无乖争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无阿谀党比之风。若小人则反是焉。此二者,外虽相似,而内实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状之隐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轨,非圣人不能究极而发明之也。……如此说,则君子之心,无同异可否之私,而惟欲必归于是;若晏子之说,则是必于立异,然后可以为和而不同也,岂非矫枉过直之论哉!”①这里对以晏婴“和如羹”来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出了批评,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朱熹看来,晏婴所谓“和如羹”,是“就事而言”,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就“君子小人之情状而言”,是就人的内在道德品质而言,所以“不可引以为证”。晏婴强调听取不同意见,所谓“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又讲“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济也”。然而,可否相济,只是“就事而言”,并非就道德上的君子小人而言,换言之,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做到可否相济,而在于内在道德品质的截然相反。
第二,朱熹认为,君子小人“外虽相似,而内实相反”,所以对于“和”与“同”的界定,不可只是从事物表面上看,而应当从人的内在心性看。朱熹《论语集注》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又进一步讲公私义利,以此把君子与小人对立起来;《论语或问》则讲“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协恭,而无乖争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无阿谀党比之风。若小人则反是焉”。显然,对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朱熹的解读强调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对立,而以晏婴“和如羹”为依据的解读则只是讲君子与小人在做事上的“和”与“同”的区别。
第三,朱熹认为,对于各种不同的事物,君子应当“必归于是”,而晏婴“和如羹”要求“必于立异,然后可以为和而不同”,过多讲不同事物之“和而不同”,属于“矫枉过直之论”。朱熹《论语集注》注“道不同,不相为谋”,曰:“不同,如善恶邪正之异。”②并且认为,“君子小人决无一事之可相为谋者也”。③应当说,在朱熹的话语中,天理、人欲、公私、义利,乃至君子小人,正如邪正、善恶,都是对立的,而不可“和而不同”,如果用晏婴“和如羹”来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实际上包含了对于小人的“和而不同”,必然会消解君子与小人的对立,那么君子就不是与小人对立的君子,也就不成其为君子,因而就会陷于悖论,所以用“和如羹”解“君子和而不同”是不可能的。
三、朱熹之后的讨论
朱熹解《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心性层面将“和”解读为“无乖戾之心”,将“同”解读为“阿比之意”,是就人的道德品质而言,并非“就事而言”。然而,人的道德品质与做事又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朱熹之后,有不少学者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既从心性的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又讲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
元代陈天祥《四书辨疑》不满足于朱熹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的解读,说:“和则固无乖戾之心,只以无乖戾之心为和,恐亦未尽。若无中正之气,专以无乖戾为心,亦与阿比之意相邻,和与同未易辨也。中正而无乖戾,然后为和。凡在君父之侧,师长、朋友之间,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可者献之,否者替之,结者解之,离者合之,此君子之和也。而或巧媚阴柔,随时俯仰,人曰可,己亦曰可,人曰否,己亦曰否,惟言莫违,无唱不和,此小人之同也。晏子辨梁丘据非和,以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此论辨析甚明,宜引以证此章之义。”①陈天祥的解读试图在朱熹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的基础上,引入“中正之气”,并进一步以晏婴的“和如羹”区别君子之和与小人之同,实际上是把朱熹的解读与晏婴讲“和如羹”结合起来。
明代程敏政也解释说:“和是无乖戾之心,同是有阿比的意思。孔子说君子的心术公正,专一尚义,凡与人相交,必同寅协恭,无乖戾之心。然事当持正处,又不能不与人辩论,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的心术私邪,专一尚利,凡与人相交,便巧言令色,有阿比之意。然到不得利处,必至于争竞,故曰‘小人同而不和’。”②后来王夫之作了训释,说:“君子以义为尚,所与共事功者,皆君子也。事无所争,情无所猜,心志孚而坦然共适,和也。若夫析事理于毫芒,而各欲行其所是,非必一唱众和而无辨者也,不同也……小人以利为趋,所与相议论者,小人也。以权相附,以党相依,依阿行而聚谋不逞,同也。乃其挟己私之各异,而阴图以相倾,则有含忌蓄疑而难平者也,不和也。”③应当说,程敏政、王夫之的解释,合乎朱熹《论语集注》之意。
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引述何晏所言:“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并指出:“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义者宜也,各适其宜,未有方体,故不同。然不同因乎义,而非执己之见,无伤于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务于是,则有争心,故同而不和。此即君子、小人之异也。”①显然,这里以义、利讲“和”与“同”,并由此从心性的层面讲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这与朱熹《论语集注》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引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是相通的。在讲君子与小人相互对立的基础上,刘宝楠《论语正义》又讲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的“和如羹”,从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引申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
清末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和康有为《论语注》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出一辙,都是先引述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的“和如羹”,然后引申出君子与小人的相互对立。简朝亮说:“由是言之,和则不乖戾,同则惟阿比,其义不昭然乎?”②康有为说:“盖君子之待人也,有公心爱物,故和;其行己也,独立不惧,各行其是,故不同。小人之待人也,媚世易合,故同;其行己也,争利相忮,不肯少让,故不和。”③这明显更为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
直到现代钱穆《论语新解》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故不能和。或说:和如五味调和成食,五声调和成乐,声味不同,而能相调和。同如以水济水,以火济火,所嗜好同,则必互争。”④显然,这样的解读都是从朱熹的解读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出发,并进一步引申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
四、余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于《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既有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而将其中的“和”解为“和谐”,又有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以及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朱熹之后的学者大多既从心性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又由此引申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应当说,在这些解读中,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并进一步讲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对立,发展并完善了何晏、皇侃等的解读,超越了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的解读。
首先,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是就先王而言,以此为依据解读《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将圣王与君子混为一谈。据《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也就是说,君子首先在于“修己以敬”,如果在“修己以敬”的基础上做到“修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和谐,就是尧舜也不容易做好。显然,在孔子看来,君子与圣王是有区别的。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讲的是圣王“和而不同”,而不是君子“和而不同”,因而不能用于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此不同,朱熹的解读强调的是君子的内在品质,更为合乎《论语》讲君子“修己以敬”,并与圣王有所区别之意。
其次,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是就做事而言,而《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就做人而言,做事与做人不可混为一谈。《论语》讲君子与小人,首先是就人的内在品质而言,《论语·宪问》讲“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与此不同,史伯讲“和而不同”,强调“以他平他”,反对“以同裨同”,又讲“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显然是就做事而言;同样,晏婴讲“和如羹”,讲不同事物的“相成”“相济”,反对“以水济水”,也是就做事而言。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实际上是将做事与做人混为一谈,而朱熹的解读揭示君子“和而不同”的内在品质,更为合乎《论语》的君子之意。
再次,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由于只是就先王而言,就做事而言,因而不是就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小人而言,史伯以“和而不同”批评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并不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所以,以此为依据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必定会带来对于君子与小人对立的消解,甚至会陷于以“和”来解读道德上君子与小人的对立所引起的理论矛盾。与此不同,较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更为完善的朱熹的解读,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从心性层面强调了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因而更为合乎《论语》讲君子与小人相互对立之意。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荻生徂徕解《论语》,强调其中的“君子”“小人”主要是“以位言”。他说:“君子者,在上之称也。……君者治下者也,士大夫皆以治民为职,故君尚之子以称之,是以位言之者也。虽在下位,其德足为人上,亦谓之君子,是以德言之者也。”“小人,亦民之称也,民之所务,在营生,故其所志在成一己,而无安民之心,是谓之小人,其所志小故也。虽在上位,其操心如此,亦谓之小人;经传所言,或主位言之,或主德言之。所指不同,而其所为称小人之意,皆不出此矣。”①在荻生徂徕看来,《论语》中的“君子”为上层官员,“小人”为下层百姓,“君子”与“小人”是相须关系,而不是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他的《论语征》以晏婴的“和如羹”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反对何晏以“君子心和”、朱熹以“无乖戾之心”解其中的“和”,说:“何晏曰‘君子心和’、朱子曰‘无乖戾之心’,皆徒求诸心而失其义焉。盖古之君子学先王之道,譬诸规矩准绳,故能知其可否。苟不知可否之所在,其心虽和乎,乌能相成相济,如羹与乐乎?亦可谓之同已。”①他认为何晏讲“君子心和”、朱熹讲“无乖戾之心”,并非“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义,而君子之为君子在于知道事之可否,而使之达到相互和谐。问题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并不在于能否知道事之可否,讲事物之和谐,而在于内在的心性道德。
《论语》中的“君子”“小人”,确有一些并不是讲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②,但是,由此而像荻生徂徕那样,以为《论语》中的“君子”“小人”大都不是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尤其是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的“君子”“小人”并非就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而言,或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讨论。
当今不少学者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将《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的“和”解为“和谐”,并将“和谐”解为“由‘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所构成的‘普遍和谐’”,又进一步认为“儒家关于‘和谐’的观念是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作为起点的”。③这里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与人之外部的和谐统一起来,并以“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为起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实际上就是朱熹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言“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今人所讲的“普遍和谐”,实际上正是朱熹之后不少学者既讲君子之“和”在“无乖戾之心”,因而无“阿比之意”,又讲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的“和如羹”,引申出人之外部事物的和谐,而朱熹讲“无乖戾之心”,因而无“阿比之意”,正是这一“普遍和谐”的起点。由此可以看出,朱熹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不仅更为合乎《论语》之意,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6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皇极与教化——朱子、象山皇极说新论
许家星
《洪范》篇在《尚书》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历来得到学者高度重视,近来更成为儒家政治哲学讨论的热门话题。目前学界对朱、陆“皇极”解的认识大体有两种观点:一是余英时、吴震、丁四新、王博等所持的政治文化范畴说,此为主流意见。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专辟“皇权与皇极”章,强调理学家通过对皇极概念的重新解释来表达关于政治秩序的新理念。①吴震大体认同余氏之说,认为“皇极诠释之争不仅是概念问题,更是当时的政治问题”。②丁四新则通过探讨以五行畴和皇极畴为中心的《洪范》政治哲学,从皇极本意的角度批评朱熹充满理学家趣味的解释并未切中其的。③王博肯定了皇极是古典时代政治思想的集中表达,着力讨论了与皇极密切相关的太极、无极。④二是陈来所持的经典解释说,他力排众议,认为把朱子皇极解当作一个政治文化范畴虽可成立,但并非朱子主要用心所在。对朱子而言,“皇极”更多的仍是一个学术思想、经典诠释问题。“朱熹的皇极讨论,不会只是针对政治的发言……‘论时事’和‘求训解’在朱子是不同的,这一点还是要加以分别的。”⑤
上述两派之说皆言之成理。然朱陆皇极之解,无论是政治问题说或经典解释说,其实皆不离“德性教化”这一主旨,政治是不离教化的政治,解释则以工夫教化为指归。朱陆皇极解皆再三强调了皇极“正心”“保心”的精神教化意义,皆推崇先知觉后知的以上化下之教,彰显了儒家哲学以教化为根本的精神特质,此是二者之同。然在落实教化的具体途径上二者则各有特色。朱子对皇极提出新解,认为皇极指君王以一身树立大中至极之标准,从而具有圣人般的德行,成为天下效仿之对象,此解具有责君行道的意义。象山则恪守以大中解皇极的传统之义,通过对德福关系的新解,突出了对民众的保心之教,以期达到承流宣化的效果,体现了化民行道的思想,此是二者之殊。概言之,朱陆皇极解皆认可责君上行道与化下民行道两种教化途径,不过因针对对象之异,而各自突出了化君与化民。二者相较,朱子皇极解更为复杂精密,其皇极思想有一明显的变化,反映了他晚年对教化、立极思想的重视。
一、“民视君以为至极之标准而从其化”
朱子皇极解经过反复沉潜而成,留下了初本与改本之别;朱子对自家之解充满自信,认为此解足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之解,特重文义训释,而归本于立人极的德性教化。以下从皇极新义、民从上化、立极于上、上之化为皇极、以身立极、为治心法、极中之辨七个方面依次论述之。
(一)“四外望之以取正”。朱子一反传统的皇极为大中之义,而主张君王树立至极标准,以为四方取正效法之义,体现了以德立极,以极化民的教化观点。①《皇极辨》中“化”字出现6次,包括“观感而化”“从其化”“下之从化”“所以化”“上之化”(2次),“教”字出现3次,反映出朱子着眼“下从上化”的理念。朱子说:
故自《孔氏传》训“皇极”为“大中”,而诸儒皆祖其说,余独尝以经之文义语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盖皇者,君之称也;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诗》所谓“四方之极”者(按:初本无此句),于皇极之义为尤近……既居天下之至中,则必有天下之纯德,而后可以立至极之标准……语其孝,则极天下之孝,而天下之为孝者莫能尚也,是则所谓皇极者也。由是而……考其祸福于人,如挈裘领,岂有一毛之不顺哉……《洪范》之畴所以虽本于五行,究于福极,而必以皇极为之主也。②
此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批评皇极旧说,表达新解,提出皇极是指君王居中,因其纯德至极,而为天下极致准则,故为四方取法。第二层指出君王树立至极之标准并非易事,须有天下至纯之德方可,具体落实为由五行五事以修身,八政五纪以齐政,方能卓然立极。特别以仁、孝为例,强调只有做到极致,方是皇极。①第三层认为,在做到至极基础上,方能顺天应人,合于鬼神而审乎祸福。《洪范》九畴虽以五行为开端,以福德关系为究竟,却须以皇极为根本来统帅之,道出了皇极为《洪范》之本的观点。新解突出了“四外望之以取正”的上行下效的德化意义,其根本宗旨就是要求人君通过修身以树立一个天下瞻仰效法的道德典范,从而达到教化天下的效果。
此处定本与初本差别甚大,二、三两层义皆为初本所无,改后更显周全严密。首句“余独尝以经之文义”句初本为“予尝考之”,“独”字之补,颇显朱子自负之意;“经之文义”之补则见出朱子紧扣章句文本表达创见的治学风格。
(二)“使民观感而化焉”。紧接“皇极”的是“皇建其有极”,朱子解为人君以己之一身为天下树立至极标准。“皇建其有极云者,则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极之标准于天下也。”树立这个“至极标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民观感而化”。君王的“建极”,是一个自利而利他的行为:建极之君因自身光辉的德行而享有长寿、富贵等五种幸福,而这种五福聚集所带来的光环又吸引了民众,民众在对建极之君德福一体的崇高道德典范之观摩中,获得内心的感动和灵魂的教化,这就是建极之君将自身所聚之福广布于民众之中的利他行为。此中君民之福传递授受之关键有二:一是君王必须能“建极”;二是民众必须能“观感而化”,即它建立在君民之间道德感应、德行转化的基础上,否则这种赐福于民是不可实现的。
人君能建其极,则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观感而化焉,则是又能布此福而与其民也。②
朱子将“建极”与“敛福”联系起来,强调德福一致,合乎《中庸》大德必得之说。又把“感化”与“赐福”相关联,认为接受德教者即是接受“福报”,被道德感化之人,即是有福纳福之人。此皆体现了朱子以德论福的德福观。应提出的是,“使民观感而化”,初本为“推以化民”,“推”字有用力勉强之意,改本更强调了感化之自然无形,同于《论语集注》“道之以德”解的“观感而兴”的潜默之化。
不仅是君“布福于民”,民同样会“还福于君”,朱子在“锡汝保极”解中提出:
夫民视君以为至极之标准而从其化,则是复以此福还锡其君,而使之长为至极之标准也。③
所谓“保极”,指民众以君王为至极标准而顺从其教化,此即还君王所布之福于君之身,使君永为至极标准,可谓“常建其极”。民之反哺、还福其君的实质是以君王至极之德为标准,顺从君之德化,使自身亦拥有同样之德。朱子指出“惟皇作极”表达的亦是君王作极的典型示范意义,对于民之感化向善具有关键效果。“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为至极之标准也。”①朱子还从全篇整体指出“皇建其有极”以下皆围绕君王修身立极,以观天下,天下自然而化之义展开。“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极’以下,是总说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标准以观天下,而天下化之之义。”②
(三)“立极于上而下之从化”。朱子于“皇则受之”句特别阐发了立极教化思想。他认为,君王立极于上,则下民受其感应从其教化,自然有快慢深浅之别,对虽有不完全顺从教化但却未过于违背者,仍当宽容接受之。他说:
夫君既立极于上,而下之从化,或有浅深迟速之不同……其或未能尽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当受之而不拒也。③
学者多注意太极与皇极关系,于“立(人)极”似罕见论及。《皇极辨》中“立极”出现3次,分别为“君既立极于上”“圣人所以立极乎上”“人君以身立极”,意指君王当以圣人为标准来要求自我,做到“王而圣”“君为师”“政即教”的合一。朱子在此将“成圣”作为君应有状态和必要素质,表达出君应为圣的儒家政治要求,此不仅关乎君王一身之资质,实系乎天下治理之根本。
立极内含继天、立人极、立教三层含义。作为君王至极标准的极有一个超越的来源,那就是继天而来,极的根源其实在天。天在朱子看来,其实为“理”,故立极的实质就是要君王成为天理的体现,成为圣人,只有圣人才做到了“浑然天理”。故此处“立极于上”通乎朱子《学庸章句序》“继天立极”说,《大学章句序》提出伏羲等上古圣神是“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故能继天命而立人极。④《中庸章句序》再次表达伏羲等上古圣神是“继天立极”者,将之与“道统”联系起来,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立极”其实是“立人极”的简称,《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朱子指出,圣人即是“太极之全体,一动一静,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圣人就是太极在人道上的表现,就是人极。皇极、太极、人极三个概念互涵相通。太极图自开篇言阴阳造化,中间言人禀受造化之灵,最后以圣人立人极结束,昭示圣人得乎太极全体,而合乎天地,此前后恰好构成一个首尾相因,脉络贯通的整体,显出人极乃太极说内在结穴所在,体现出太极图即天道而言人道的天人贯通。前贤已注意朱子“皇极”是太极论的自然展开,但《皇极辨》并未出现“太极”,“立(人)极”则出现多次。盖皇极要求人君建立其极,是为民立极,人极的内容如朱子弟子方宾所言,即是仁义之道,“而仁义礼智所以立人极也”。①朱子曾要求孝宗放弃功利之心,罢免求和之议,通过对仁义三纲之道的体验扩充,来“建人极”,树立作为君王应有的天下道德表率,如此方是重振国事的关键。“而以穷理为先,于仁义之道,三纲之本,少加意焉,体验扩充,以建人极。”②人极作为普遍永恒而又日用常行的人伦之道,具有大中至正的极则意义。圣人以仁义中正为立人极,其实即是仁义礼智,不过中正较礼智更亲切而已。“圣人立人极,不说仁义礼智,却说仁义中正者,中正尤亲切。”③
立极与立教密不可分,立极是树立至极之准则,是立教之前提,立教则是立极的落实和展开。朱子多次将“立极”与“立教”联系起来,早在《杂学辨》中即认为“修道之谓教”就是“圣人所以立极”所在。④《君臣服议》亦言宋朝开国确定的三年丧制具有立极导民之效,“则其所以立极导民者,无所难矣。”《大学章句序》指出,继天立极的圣人通过设立司徒典乐等官职开展对百姓的礼乐教化,以复其性。儒家之道其实就是“立极”之道,天生圣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圣人通过继天立极,来修道立教,教化百姓。“问继天立极……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⑤
(四)“上之化也,所谓皇极者也”。朱子在“惟皇之极”句的解释中提出了民众“革面从君”与“以君为极”的思想。
夫人之有能革面从君,而以好德自名,则虽未必出于中心之实,人君亦当因其自名而与之以善。则是人者,亦得以君为极而勉其实也。⑥
若有人能受君之感化而改除旧习,从君之教,尽管其心出于好名而诚意不够,但君王亦当因任其好名之心而善待勉励之。此显示圣人设教“至宽至广”“与人为善”“一视同仁”的广大包容,合乎夫子“有教无类”,孟子“归斯受之”的教化理念。
朱子对“凡厥正人”句的诠释,强调了君王立极至为严密,而待人极为宽广的原则。
是以圣人所以立极乎上者,至严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宽至广。虽彼之所以化于此者,浅深迟速……长养涵育,其心未尝不一也。①
朱子首先阐发了《论语》“富之教之”及《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先富后善的教化原则,要求君王先安顿民众生活,否则难以教化诱导民众于善。如民众因生活所迫陷于不义再加以教化,则事倍功半,无济于事。此体现了朱子视民生保障为教化前提的立场。强调对作为立极施教的君王,应给予最为严格细密的要求;但对被教化者则又应持“至宽至广”的宽大包容原则,面对民众接受教化效果所存在的深浅快慢之差异,应始终抱有抚育涵养之心。这一对在上者严格与对在下者的宽容体现了差别化视角。
朱子对“无偏无陂”句的解释突出了在上之化的意义。他说:
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从乎上之化,而会归乎至极之标准也……王之义、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谓皇极者也。②
天下之人皆不敢徇一己私情而自觉顺从于王者教化,会归于君王所立至极之标准。通过王者以自身所践行之正义、正道、正路教化民众,化除人之私欲而使之归于荡荡平平正直之则,此义、道、路作为在上之教化,即是皇极。可见朱子皇极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在上之化的教化之道。
(五)“人君以身立极而布命于下”。朱子对皇极章最后三句的诠释,着重突出君王立极布命的身教思想,并将立极、伦常、天理、降衷贯通为一。一方面,作为施行教化者的人君,应当“以身立极”,人君所发布的天下教令即是天理伦常和上帝降衷之体现。
则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极而布命于下,则其所以为常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异乎上帝之降衷也。③
此“以身立极”即“继天立极”,对君王而言,其身本自继天而来,德性上应实现与天为一,才有资格、有能力成为万民取法的教化者。初本“立极”本是“为表”,改后突出了“立极”这一中心主旨。“天之理”初本为“循天之理”,删此“循”字,表明立极之君所立之伦常教化,即是天理,突出了君王作为立极者的自我立法,与理为一的神圣法则意义。
朱子强烈责求作为立极者的君王,理应成为纯乎天理的圣人。对受教的天下之民,要求接受君王教化之命,恪守遵行,以不偏离天理伦常而直接感化于君王德教之光华。
朱子又解“天子作民父母”句为:
则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极之标准,所以能作亿兆之父母而为天下之王也。不然,则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统御人群,而履天下之极尊矣。①
“人君能立至极之标准”初本为“能建其有极”,改本紧扣“立极”而论,显豁了“皇极”的“立至极标准”义。“亿兆”初本为“民”,改为“作亿兆之父母”正同乎《大学章句序》“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亦证明朱子《皇极辨》始终着眼于君师复性之教。“首出庶物,统御人群”,初本为“建立标准,子育元元”,改为《乾卦》“首出庶物”及“统御”后,强调了君王首先应该履行作为一国之首应有的仪范天下之责,如此才能“统御人群”。即他不仅在地位上是万人之上,更应该在德性上“首出庶物”,做到“中心安仁”。此是再次扣紧“立人极”而论。②表明天子之所以为天子,关键在“德”而非位。仅有位无德者,不足以履天子之位。《中庸》认为,德位分离者,皆不能制作礼乐以行其教化,只有德位兼备的圣人天子方可制作礼乐。
(六)“此是人君为治之心法”。朱子还以“心法”论定“皇极”,彰显了“皇极”作为道的意义,也揭示了宋代“皇极”畴取代五行畴的原因。
问:皇极。曰:此是人君为治之心法。如周公一书(按:指《尚书·周书》),只是个八政而已。③
朱子将皇极与八政比较,认为皇极才是人君治国心法,而《周书》不过是讨论具体政治措施之作,仅是“为治”,皇极才是更深层的决定“为治”的“心法”,此心法即是道之义。它直接作用人君之心,实非八政可比。皇极作为心法的意义在于:君王能以极为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成为天下民众之道德标准、行为表率,使得民众皆有以兴起并效法之,以成就修身化民之效。君王能否成为天下所取法的对象,事关天下治理成败,故君王之心实为天下根本之要。可见朱子的皇极新解,与他格君心的道德教化思想一致。“心法”在朱子语境中,具有不同所指,但皆无外乎修身内圣与治国外王义,具有统率本体与工夫的道统意义。皇极心法与允执厥中、克己复礼之心法一脉相承,不过表述有所不同而已。
君王如能通过修身工夫皇建其极,那就是把握了政治根本。因天下大事,皆无外乎是从君王一心之法流淌而出,如其心正大光明,则其事自然正大光明。“古人纪纲天下,凡措置许多事,都是心法。从这里流出,是多少正大!”①皇极心法说的意义表明朱子的道统论并非仅限于狭义的内在心性之学,而实际亦包含了治平天下的外王之道。
(七)中、极误解与“修身立政”。朱子对皇极章的逐句解释,体现了其“皇极”思想实是以责君立极化民为中心,并未涉及任何具体时政。此诚如陈来先生所言,朱子的皇极解首先或者说主要是一个经典命题的解释问题。朱子之解可能涉及政治的部分仅作为一段补充性质的短文被置于正文之后,且完全以“修身”立论,它以“修身立道之本”始,以“不知修身以立政”之告诫终。朱子说:
但先儒未尝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误训“皇极”为“大中”;又见其词多为含洪宽大之言,因复误认“中”为含胡苟且,不分善恶之意……乃以误认之“中”为误训之“极”,不谨乎至严至密之体,而务为至宽至广之量,其弊将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堕于汉元帝之优游、唐代宗之姑息。②
朱子此段文字虽兼具学术、政治、教化三重意义,但仍是紧密围绕“中”“极”的字义之辨展开。在他看来,先儒误训“极”为“中”的原因是未能理会“皇极”之说意在确立“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由此引发“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的严重政治后果。时人不仅解“极”为“中”有误,且对“中”的理解亦有误。“中”本是“无过不及”之义,并非所误认的居中调停,“含糊苟且,不分善恶之意”,这种误解导致君王修身上的“恕己”,用人上的“君子小人并用”的姑息、放纵。③朱子特别反对以“宽恕”解释“恕”。认为恕当正解为“如心”,而非苟且姑息之义,恕只可对人,不可于己,批评范纯仁“恕己之心恕人”说虽心存厚道,为世所称,其实不合本义,后果严重。如郅恽对光武帝的“恕己”解将引发逢君之恶、贼君之罪的恶劣后果。④朱子“皇极”解“一破千古之惑”的意义建立在对“中”“恕”字义重新理解的基础上,表明对经典文义的理解之正误,将对修身治国带来重大影响。此即朱子皇极解“破惑”的意义所在。
朱子皇极解的重心实不在政治文化领域,而归本于君王修身化民的道德教化义。朱子强调皇极的“至严至密”“极则”“准则”义,与其“格君心之非”“正心诚意”之学是完全一致的。朱子皇极解其实是以修身教化为主的一套道德治国论,而修身、正身、修己工夫,五福、六极效验,完全落实在“人君之心”这一根本上,此为君王所承担重任所在。他说:“人君端本,岂有他哉……其本皆在人君之心,其责亦甚重矣。”①故一切工夫皆终归于治心的教化之学。
二、“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
象山皇极解既是其化民成俗具体实践的产物,又是其平治天下的理论纲领,体现了象山学鲜明的以心为教的特色,具有理事相融的色彩。以下从以道觉民、承流宣化、保心保极、心正是福、以心教化、皇极根心六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以斯道觉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极也”。象山为改变荆门上元节设醮祈福的陋习,代以宣讲《洪范》“敛福赐民”章,试图通过对“皇极”的解释来达到端正民心,改变民风的教化目的。此是象山以“正人心”为治荆首务的落实。②象山以其天生的演讲能力,阐述了发明本心,自求多福的思想,使听者大受震动,深为信服,以至有感激哭泣者。《年谱》载:
讲《洪范》敛福赐民一章,以代醮事。发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晓然有感于中,或为之泣。
《讲义》并未对《洪范》皇极展开全面阐发,而仅就其前三句作一论说,即“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象山对“皇极”采用汉唐通行的“大中”说,并未自创新解。其实在经典解释上,朱子甚喜提出迥异于前人之新说,而象山往往遵循成说,此即一例也。象山说:
皇,大也。极,中也。《洪范》九畴,五居其中,故谓之极。是极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万物以此而育。③
此以皇为大,中为极,皇极为九畴之五,故居其中。并以“充塞宇宙”来表明“极”之广大,此乃象山标志语,以之形容“极”之广大,可见“极”在象山思想中具有特殊地位。象山又采《中庸》致中和说,以位天地、育万物显示“极”之效用。象山又指出:
古先圣王,皇建其极,故能参天地,赞化育。当此之时,凡厥庶民,皆能保极,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叶气嘉生,薰为太平”,向用五福,此之谓也。①
皇极大中构成参赞化育功效的前提,古代圣王能够做到皇建其极,故能参赞化育。在此皇极之中,民众受其教化熏陶,而能遵循中道。由此达到天下比屋可封,人皆君子的德行教化大兴之治。阴阳调和,风雨时至,太和之气带来祥瑞之物,化为太平世界,此即享用五福。
象山认为在圣王建极与民众保极之间存在上教下化关系,在天道太平与人道和谐之间具有内在感应关系。②并意识到“皇极”并非是一定能确保建立者,如在无道之世,人心不善,豪杰无有,则皇极不建。“逮德下衰,此心不竞,豪杰不兴,皇极不建。”③皇极之能否建,关乎民众之能否觉悟。他说:
皇建其有极,即是敛此五福以锡庶民。舍“极”而言福,是虚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极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极。但其气禀有清浊,智识有开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以斯道觉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极”也,即“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也。④
“皇建其有极”就是聚福以赐给百姓,但百姓能否接受所“赐”之福,则取决于自身能否“保有其极”。象山坚持以“极”论“福”,强调“极”“福”不可割裂,得“福”的关键在“保极”,无极则无福,无极而言福,必为虚妄之谈,必是不明事理之论。又引《汤诰》“降衷于民”说,指出“衷”即是“极”,“极”又是“中”,此不同于孔安国解“极”为“善”。以此证明人皆同样秉有上天所赐之极,凡民与圣人同体无隔,而实不可自弃。然又因气的清浊、智的通塞等客观限制,导致凡民不能明了自身所禀赋之“极”。⑤只有极少数先知先觉之士,方能明乎此上天降衷之极而觉乎此道,并以之觉悟后知后觉。象山一方面指出“凡民之生均有是极”,将凡民往上提升至与圣人同样禀赋天降之极;另一方面强调“古先圣贤与民同类”,圣贤亦不过是《孟子》所言“天民先觉”而已,可见圣凡同体。他强调“以道觉民”的教化、开发民众之意,表明宋代理学并非株守“得君行道”一途。事实上,朱陆真正的政治生涯皆极短,他们将主要精力用在发明斯道和以道化民的教化工作上,由此重视书院讲习活动的展开。明代阳明学“觉民行道”亦是对理学此项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展开而已。①在象山看来,不管是在上之皇极还是在下之五福,皆离不开对道的觉悟,皆围绕如何觉道展开。象山此处论证逻辑极似朱子《大学章句序》思路。②
(二)“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象山将“宣化”与“宣福”等同之。他说:
皇建其极,“是彝是训,于帝其训”,无非敛此五福,以锡尔庶民。郡守县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为圣天子以锡尔庶民也。凡尔庶民,知爱其亲,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圣天子所锡之福也。
圣上德性光明在上,足以洞察幽明,智照四方,故能替天治民,奉天从事,立大中之道,此伦常中道既是民众所当遵循之法则,亦同样是帝王所当行之法则,皇能建其极,则自能聚集五福以锡庶民。各级官员秉承圣意,宣扬教化,就是替天子赐五福于民。“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说把官员开展教化当作赐民之福,把德性之教与人生幸福结合之,表达了以教为福的思想,明确了开展化民易俗的教化工作乃官员应尽之职责。③于民众而言,如能做到爱亲敬兄的孝悌之道,即是实现了“皇降之衷”,即承受了天子所赐之福。可见,象山之教化以父子兄弟的孝悌爱敬之情为中心,将所谓祈福归结为个人的内在德性修养,此福不在天,不在王,而是在个人当下可行的内在之道,是人人本有的孝悌仁爱之心。象山指出特意开设本讲,乃是针对官府设立法会祈福之举的一项改革,“谨发明《洪范》敛福锡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几承流宣化之万一。”指出天子以皇极君临天下,地方官员理应与民众践履皇极之义,从而接近天子之光辉。故以此讲代替法会,意在达到承流宣化之目的。列九畴于《讲义》之后,希望民众能转变观念,做到以善为福。所谓“自求多福”之福乃是自我当下即可把握者,求福即在求心,福在心内非在外也。
象山始终认为,宣扬教化乃是为官本职。他在尚未上任荆州时所作《石湾祷雨文》中,即批评官员不以宣化为职,反而一味以吏事、催科、簿书等为务,放弃了作为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承流宣化之责,表明了以承流宣化作为执政首务的理念及革新弊政的用心。“论道经邦,承流宣化,徒为空言;簿书期会,狱讼财计,斯为实事,为日久矣。”①在《宜章县学记》中,象山大量引用《尚书》以为立论根据,充分表达了承流宣化、各负其责的教化思想。他说:
汉董生曰:“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斯民之责于天者,君也。分君之责者,吏也。民之弗率,吏之责也。吏之不良,君之责也。《书》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君任其责者也。可以为吏而不任其责乎?②
上帝不仅降生民之中,还任命君师对民众施其政教,行其化育。由此内设朝廷,外置邦邑,皆以尽心辅助天子之教化为务。周公告诫成王三宅三俊说,当以三德教化百姓;成王告诫康叔,应以五常教化百姓。董仲舒“承流宣化”说,指出郡守、县令等官,承担着宣扬君德,教化民众之责。故向上天承担保养教化民众之责者为君王,分担君王之责者为官吏。如民众不遵循教导,则当责备官吏;如官吏品行不端,则追究君王责任。可见君臣上下之间,各自承担着教化官吏与民众之职。天下有罪,百姓有错,君王当负其总责。然作为官吏者亦当承担所负有之职责,而不可推诿于民众与风俗之难治难移。
象山将有无教化之道,视为夷狄之国与中国的差别所在。据夫子君子化陋俗为良治之思想,批评官员推脱治化之责于风土民情者乃自欺之言。引曾子、孟子、孔子之言,表明民情处饥渴无助情形之下,反而最易推行治化之道。称赞吴镒通过学校教育子弟,使老幼皆受教化而自然回心向善,证明开展治理教化工作,于此民风不竞之世更为容易。又以周道大行为例,对教化提出了应达到“民日迁善远罪而不知为之者”的自然而化境界。特别抨击功利之说、百家之言对于人心的遮蔽和教化的阻碍,教化关键在自我挺立,践履仁义,扩充四端。
夷狄之国……无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顾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责,而惟民是尤,则斯人之为吏可知也……于其所谓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③
(三)“若能保有是心,即为保极”。象山将保极、五福皆落实为保心。说:
若能保有是心,即为保极,宜得其寿……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圣天子所锡之福也。身或不寿,此心实寿……杀身成仁,亦为考终命。④
象山认为,如能保养此心不失,即是保极,就当享有富寿康宁等五福。福不是外在之事,而纯为内心存养;它本无关肉体,即使肉体消亡,此心仍可常存。如杀身成仁者,身虽亡而命常在。故百姓如能明乎君臣上下之义,中国夷狄、善恶是非之分,践行父慈子孝五伦之道,即做到了皇降之衷,即能承受天子所赐五福。①象山谈到了如何面对德福不一。他区分了心之福与身之福,认为如能行五常之教,其心实已享有了五福之报。此种福报完全是“心福”而非“身福”,如能存养、践履此道德之心,即是最大之福,外界富寿等,皆不足与计。此体现了象山以“心”为核心解释人生的思想。《贵溪重修县学记》则明确提出以本心为教,对民众教化本乎尧舜之道,皆不过使之不失本心。“庠序之教,抑申斯义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②然据《中庸》“大德必得”之论,“心福”应与“身福”一致。
(四)“实论五福,但当论人一心”。象山进一步申论了以心论福的“心福”立场。说:
实论五福,但当论人一心,此心若正,无不是福。此心若邪,无不是祸……不知富贵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恶,是逆天地……若于此时更复自欺自瞒,是直欲自绝灭其本心也……虽在贫贱患难中,心自亨通。正人达者观之,即是福德。③
象山提出论福实为论心,心正为福,心邪为祸,区别了德富背离和一致两种情况。一者大富之人,如其心邪事恶,则是违背天地鬼神,背离圣贤之训,君师之教。若自加反思,真实面对自我,必能意识到其中实有不可自我欺骗隐瞒者所在。若于此仍是自我欺瞒,不肯面对本真之我,则必是自绝灭其本心之人。况且富贵实非人生所当追求,自正人君子而观之,富贵非但不可羡慕,反而可怜鄙视之极,实乃身处监狱污秽之中而不自觉。反之,身处患难之中,如能心正事善,不违天地鬼神,君师圣贤之教,则必赢得庇佑和肯定。虽处贫贱,而心实富有通达。自正人君子观之,此即福德。象山以正邪、贫富、善恶之对比,突出“福德”的“德福”义,是因“德”而“福”而非因“富”而德,以消解民众以富为德的观念。世俗之福并非真福,唯有有道德者方是真幸福。当然,此处象山强调了观察者的身份——自正人观之,否则就不正之人观之,其判断必有所不同。
象山引《尚书》说论证“自考其心”的求福之法,批评求神拜佛无益。
但自考其心,则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随形,如响应声,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迁善远罪,但贪求富贵,却祈神佛以求福。④
伊尹告诫太甲上帝无常,灾祸吉祥因人善恶而降。《坤卦》说积善余庆,强调善祥恶殃的德福一致。祸福善恶端在自家之心,故当“自考其心”,如能自求自考,则见祸福如形影声响之必然而不可违逆。批评愚人贪恋富贵而妄求神佛保佑赐福,但却不知神自有其福善祸淫之原则,而不被人所收买,故不能予福德于不善之人。真求福德之法,乃在对治自身,迁善改过,远离罪恶。象山完全是从道德本心的角度阐发以善为福的思想,批评了求神拜佛思想的荒谬性。
象山之论,合乎其义利之辨的精神,他教化民众当以义为利,而不是以利为利。他曾据《尚书·仲虺之诰》区别内心动机与外在效果的同一与差异两种情况,略相当于康德的合法性与道德性之别。判定行为是否具有道德,关键是看其心之所主,而不是看其行之是否合乎所是。如心主于义,则其行为义;主于利,则行为利。故后世行为虽有合乎礼义者,然却是出于利害之心。反之,古人虽是考虑利害,却是出于道义之行。这样使得一切行为的价值皆当“凭心而论”,而不是就事而论,故官吏处理财会、诉讼等杂务就完全具有了正当性和必要性;同样,出于求利之心的祈福之举,则不具有了道德性。
后世贤者处心处事,亦非尽无礼义,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礼义行之耳。后世所以大异于古人者,正在于此。①
对民众而言,功利的态度尤表现在事鬼神上。象山虽肯定怪力鬼神实有,所看重者,则是鬼神所具有的教化百姓之效用。②象山以“聪明正直”作为对神的要求,认为民众对神的祭祀应祭所当祭,非所当祭而祭,即是淫祀。对神而言,亦不应享有不当祭之祭,否则非神。他以此为准则来改革旧俗祭神之误,体现了化民成俗教化思想的实践。象山曾多次求雨,但却体现了很强的理性精神,毫无祈求姿态,批评山川之神素餐不治,劝告诸神既然享民之祭,理应替民分忧,救民旱灾。把山川之神视为自己的“同僚”,共同承担庇护一方百姓的使命,如不能消除灾害,对神来说,亦意味着失职。“旱干水溢,实与守臣同其责。”③
(五)“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象山提出了以心为教说。
皇极在《洪范》九畴之中,乃《洪范》根本……“敛时五福,锡尔庶民”者,即是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以发明尔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尔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恶,即为保极。可以报圣天子教育之恩,长享五福,更不必别求神佛也。
象山肯定“皇极”在整个《洪范》九畴之中的根本地位。天子“建用皇极”,赐五福于百姓,其实质是以皇极之心施于政事教化,以阐发显明百姓内在本有的天降之中,使之不至陷溺。庶民如能保全此本心,即做到了保极。则可上报君恩,长享五福,而不必别求神佛。象山此处亦是以“心”论福,以心论“极”,天子赐福于民者无他,不过是施教者以大中之心教化民众,使民众能自觉其大中之心,存养此心而不陷溺也。对受教化者而言,则保全大中之心纯正无邪,即是保养此极。无论赐福、保极皆是一心之教化。象山之心,并不离乎理。他指出福其实不可赐,所谓赐福,乃是指此理之遍布宇宙。象山主心即理,故此理充塞,其实亦是此心充塞。“福如何锡得?只是此理充塞宇宙。”①
(六)“皇极之建,根乎人心”。象山指出,《洪范》九畴之教关乎彝伦之存废,箕子曾对武王讲述《洪范》九畴,当鲧治水失败后,帝大怒而不授《洪范》,导致伦常败坏;在大禹接替治水工作后,方才赐予《洪范》,使得伦常有序。作为《洪范》核心的皇极大中之建立,事关彝伦兴废,此是普遍不易之理。但此“中”“常”并不神秘,不可仅从政治上加以理解,实则“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大中常道既内在根本于人心,又超越充塞于天地,表达了以人心论“皇极”的教化思想。“皇极之建,彝伦之叙,反是则非,终古不易。是极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
象山的教化思想,特别重视先知先觉的引导之功。他指出,先知先觉的意义在于明理导民。盖理虽遍在天地,但若无先知先觉开导引诱,则人必然限于黑暗摸索之中,而无法明乎此理。只有明觉之人方才可以论理。学不明理,只是凭一己武断论述天下是非,不自量力,此显出象山对于“理”之重视。“是理之在天下无间然也,然非先知先觉为之开导,则人固未免于暗。”②上古圣贤先觉此道以觉悟斯民,后世学者无学,道亦无传,故民无所归。批评士人未能明道,导致教化不行,斯道不明。可见士之先觉乃是教化推行之前提。故象山反复致意于“以道觉民”。“上古圣贤,先知此道,以此道觉此民。后世学绝道丧,邪说蜂起……而号称学者,又复如此,道何由而明哉!”③
在象山看来,所谓先知先觉实质就是师友之教,象山认为有无师友之教,是决定学道成败的关键。先知先觉之觉悟后知后觉,乃是天理必然。有师之教与无师之教,效果截然不同。先知先觉者承担培育天下人才之重任,故天下没有人才,责任在于作为先知先觉者的师友未能尽其教化之功。“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要当有任其责者。”④象山讨论了先知先觉所教与学者所习之异同,指出所谓先知先觉之教并非口耳言语之教、“意见之教”,乃是事实之教,人伦之道,是言教与身教的统一。此有针对朱子意味。
朱子对象山皇极说甚为关切,听闻象山解“保极为存心”,要求学者对其说加以判定,提出应对照经文,逐句落实其解,方能判定象山得失。朱子判定象山的皇极解不过是敛六极,“陆子静《荆门军晓谕》乃是敛六极也”①。所谓六极乃是与五福相对的六种不好之遭遇:“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其意谓象山把敛五福解读成了敛灾祸。象山提出“舍极无福”“保有是心即为保极”“实论五福,但当论人一心”的以心为福说,注重教化民众不可执着世俗之祸福,其目的亦是“使天下之民归于正”,实在具有转化民风的教化意义。朱子颇为忌惮其将此等外在祸福完全收归于“心”,而置现实祸福于不顾之论,故发此批评,实不相应而有失严苛。学者已指出朱子所言不妥。②
三、结语:皇极与教化
朱子、象山对皇极字义及其思想的阐发,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在基本精神旨趣上彼此相通,皆以推行教化为共同宗旨。朱子皇极之解,自辟新见,其指向却在责君行道,要求君王修身诚意,以立人极,通过树立圣人般的典范人格,成为天下四方效法取正的法则,以达到下民感兴而化的教化效果。朱子以治经学的严谨态度,对皇极文本,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就其文本前后修改等来看,体现了越来越突出教化、立极的意味。而象山的皇极讲义则完全是有感而作,是为了解决一个转移风俗,改变民心的实际问题。故象山的皇极解只是选取首三句而发,不如朱子皇极解严密完整。为了转变民众祈神求福的功利之心,象山开出了保心、保极,以心为福之方,教化民众当在自家德性用功,树立德福一致,以德为福的思想,体现了心学的教化理论,产生了明显的现实效果,彰显了象山学义理与事功贯通的“实学”特质。简言之,朱陆皇极解所针对对象,所设定任务皆有所不同,朱子可谓是责君成圣以化民的上层路线,象山则是化民之心以行道的下层路线,但二者皆同归于儒家的教化之道。
儒家的这一教化思想在当代仍具有新的理论活力。当代儒家教化哲学的代表学者李景林指出,儒学的根本特质就是一种教化的哲学。儒学作为一种工夫教化,它不脱离于哲学;另一方面,儒学作为哲学义理,它扎根于工夫教化。儒学的“教化”观念,取形式与实质、内在与超越一体的思路,经由“工夫”来引发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转变。儒家哲学的教化还借助于中国古代社会固有的礼仪、仪式系统,经过形上学的诠释、点化、提升,巧妙地切合和影响于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之样式,这种教化带有浓厚的哲学的意味,这是它“哲学义的教化”一面。①李景林强调,经典传习、礼乐教化、重视家庭教育作为的儒家教化方法,于今日落实儒学的教化之道仍具有重要意义。他提醒教化儒学的未来发展要注意三个方面:理论形态的重建、儒学和社会生活联系的重建、“以身体道”群体的培育。②可见,从教化的角度来解读儒学的过去与重建儒学的未来,可以超越以心性或政治论儒学的分歧,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中国哲学传统,开拓中国哲学新境,这是宋代儒者皇极解留给我们的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论题。
(原载《学术界》2021年第1期,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心性情”与“易道神”:朱熹对程颢思想的创造性诠释
翟奎凤
《二程遗书》卷一有下面一段话:
“忠信所以进德”,“终日乾乾”,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疑事,则只曰“诚之不可掩如此夫”。彻上彻下,不过如此。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
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①一般认为,这段话是程颢说的,最后几句论形而上下、道器的话非常有名,相对来说,“彻上彻下,不过如此”之前的文字关注讨论得不多。实际上,朱熹与其门人在谈话中对这段文字前面所论“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有非常集中而且相当深刻的研讨。朱熹的基本观点是:以心、性、情来对应这里的易、道、神。朱熹关于“易、道、神”的讨论成为构成其心统性情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乾乾”的意思是刚健精进,也有慎独、戒惧之意,“对越在天”是讲对上天的敬畏。朱熹认为前三句话“只是解一个‘终日乾乾’”②,而“下面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云云,便是说许多事,都只是一个天”(同上)。具体而言,“易、道、神”是“就天上说”,而“性、道、教”则是“就人身上说”(同上)。总体上来看,朱熹认为程颢所说这段话“皆是明道体无乎不在。名虽不同,只是一理发出,是个无始无终底意”(同上,第3189页)。朱熹关于“易、道、神”的讨论也是其道体思想的重要体现。
一、天人相应:“心性情”与“易道神”
1168年(39岁)朱熹在《答范伯崇》论程颐“随时变易以从道”③时说“‘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潜、见、跃、飞之类观之,则‘随时变易以从道’者可见矣”(《文集》卷三十九,《朱子全书》第22册,第1774页)。1171年(42岁)在《答方伯谟》信中又进一步发挥说:“随时变易以从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潜’‘见’‘飞’‘跃’观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当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而伊川又谓‘变易而后合道,易字与道字不相似也’。”(《文集》卷四十四,《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08页)这是朱熹较早引述到程颢“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一语,但这里还没有把“易、道”与心、性关联对应起来,只是以变易流行与定理当然来解释“易”与“道”。但其实在1170年,41岁的朱子在与张栻的通信中已把“心”与“易”作了关联,他说:
心具众理,变化感通,生生不穷,故谓之易。此其所以能开物成务而冐天下也。圆神、方知变易,二者阙一则用不妙,用不妙则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心”正谓其无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众理必具而无朕可名,其“密”之谓欤?必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动也,如此立语如何?(《文集》卷三十二,《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95页)
朱子这里以“心”解“易”,心、易皆有变化感通、生生、圆神方知、变易等特点。《易传·系辞上》说:“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圆神、方知本来是讲蓍卦之德,朱子这里转用来讲心之德。《易传·说卦传》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朱子也以“妙”为心之用。《易传·系辞上》还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朱子在40岁己丑之悟中和新说之后,确立了心统性情的思想,心可以有未发(性)、已发(情)两种状态,认为未发为寂、已发为感。易学话语下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也被朱子用来论心的静与动两种状态。但是这封信没有引述程子“易、道、神”之说。
1172年(43岁)朱熹在答吴德夫的信中说①:
“易”之为义,乃指流行变易之体而言。此体生生,元无间断,但其间一动一静相为始终耳。程子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此体在人,则心是已。其理则所谓性,其用则所谓情,其动静则所谓未发、已发之时也。此其为天人之分虽殊,然静而此理已具,动而此用实行,则其为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则是易之有太极者。(《文集》卷四十五,《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70—2071页)
这里也强调“易”为流行变易之体,此体生生不息。接着就引出了程子所说“易、道、神”,认为此“体”在人为心,相应地,“理”“道”对应“性”,“用”“神”对应“情”。在朱熹看来,“易、道、神”本是讲天道自然界的变化,相应于人,可以对应心、性、情。寂静之时,具此性理,感通之时为用之实行。寂感、动静、体用合起来又可以表述为“易有太极”,太极为理,易为变易流行之总体。
在答吴德夫信前后或同时,朱熹还有《元亨利贞说》短文一则,其中也说到: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文集》卷六十七,《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54页)
这些都贯穿了朱熹心统性情、心主性情的思想,“理”“道”为性、“用”“神”为情,“体”“易”为心。心统性情之统有心包性情、心主性情二义,相应地,似也可说易统道神、易包道神、易主道神。
《朱子语类》中关于“易、道、神”的讨论相当多,相对文集来说,也更加详细深入。在与弟子万人杰论“易、道、神”时,朱子说“就人一身言之:易,犹心也;道,犹性也;神,犹情也”。对此,万人杰问说:“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朱子回答说“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摄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为春夏,所以为秋冬之理是也;至发育万物者,即其情也”(《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88页)。这里突出了“心”的主宰性。这条材料为万人杰自记,黄㽦也记录了万人杰与朱子的类似对话:
正淳问:“‘其体则谓之易’,只屈伸往来之义是否?”曰:“义则不是。只阴阳屈伸,便是形体。”又问:“昨日以天地之心、情、性在人上言之,今却以人之心、性、情就天上言之,如何?”曰:“春夏秋冬便是天地之心;天命流行有所主宰,其所以为春夏秋冬,便是性;造化发用便是情。”又问:“恐心大性小?”曰:“此不可以小大论。若以能为春夏秋冬者为性,亦未是。只是所以为此者,是合下有此道理。谓如以镜子为心,其光之照见物处便是情,其所以能光者是性。因甚把木板子来,却照不见?为他元没这光底道理。”(同上)
“正淳”即是万人杰,此条语录记于朱子59岁时。朱熹强调“只阴阳屈伸”便是形体,显然,若说“屈伸往来之义”就指向性理了。易、道、神是从天(春夏秋冬)的角度来说,心、性、情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易、道、神为天地之心、性、情①。这里“春夏秋冬便是天地之心”的“心”是连着心、性、情来说,强调春夏秋冬、四季转换流行之体,就相当于人的心。因此,这里“天地之心”,与一般所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是不同的。这里“天命流行有所主宰”实际上又强调性对心的主宰,性理是根据,规范着心流行生生。与前面一条强调心对性的主宰、管摄义又有所不同。心主宰性,反过来也可以说,性主宰心,所揭示的思想意义不同。这条材料最后又以镜子来比喻心,“所以能光者是性”,镜子有光能照物的原理根据是性,光所照见之物为情。
黄㽦还记载了另外一条相关材料:
“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功用则谓之鬼神。”易是阴阳屈伸,随时变易。大抵古今只是大阖辟,小阖辟,今人说《易》,都无着摸。圣人便于六十四卦,只以阴阳奇耦写出来。至于所以为阴阳,为古今,乃是此道理。及至忽然生物,或在此,或在彼,如花木之类蓦然而出,华时都华,实时都实,生气便发出来,只此便是神。如在人,仁义礼智,恻隐羞恶,心便能管摄。其为喜怒哀乐,即情之发用处。(《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88—3189页)
这条材料也是记于朱子59岁时,这里把“其用则谓之神”表述为“其功用则谓之鬼神”。以阴阳、屈伸、阖辟、往来解释易,为朱子一贯思路,其背后的所以然、根据为道和理;其发用功能、生机展现,为神。以心统性情之说,心能主宰、管摄性与情,照此逻辑,也可以说“易”能主宰、管摄道与神。朱子还说:
盖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发见者言。明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发见亦如此。如后段所谓“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某尝谓,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是情。缘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来个个亦如此。一本故也。①(同上,第3199—3200页)要见得分晓,但看明道云:“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此天地之心、性、情也。②(《语类》卷五,《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3页)
程子曰:“其体谓之道,其用谓之神。”而其理属之人,则谓之性;其体属之人,则谓之心;其用属之人,则谓之情。③(《语类》卷一百,《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50页)
可见,大概是从43岁中年开始,一直到晚年,以心性情论易道神,是朱子常说的话语。那么,朱子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把两者对应关联起来进行论说呢?朱子非常重视宇宙生化论、重视天道,同时认为天地之道与人道有对应、呼应性,人道的根源在天道,在这一点,相对程子来说,他受到周敦颐、邵雍的影响更大。朱子在40岁提出中和新说,确立心统性情思想之后,应该说他就开始潜在地寻求心统性情思想的天道论根据或本体论表述,在把心与易对应之后,对程子思想非常熟悉的他自然进而把心性情与易道神对应起来。这样在天之易道神,在人即为心性情,心统性情思想的主体论表述也就有了天道论的支撑,就更加具有权威性。
二、易体:道体而非形体
“其体则谓之易”,这里的体是变化流行的总体、统体,非体用之体,对此,朱熹有反复强调。但此体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抑或包体用,不分形而上下。就《语类》材料来看,朱子的表述有前后矛盾之处。统观来看,朱子所诠释的“其体则谓之易”之体应是该体用、形而上下浑融的道体。
朱熹曾把体理解为形体,为形而下的存在。如程端蒙所记语录说:
“其体则谓之易”,在人则心也;“其理则谓之道”,在人则性也;“其用则谓之神”,在人则情也。所谓易者,变化错综,如阴阳昼夜,雷风水火,反复流转,纵横经纬而不已也。人心则语默动静,变化不测者是也。体,是形体也。言体,则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则形而上者也。故程子曰“易中只是言反复往来上下”,亦是意也。①(《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87页)
易、心皆为变化、错综、不测、流转不息的存在,这是朱熹经常说的。但是他这里说“体是形体”,而且直接说成是形而下的存在,与形而上之理相对。那么,这样的话,照此逻辑类比,就是心与性相对,心为形下存在。但是这显然与朱子本人心统性情的根本思想是矛盾的。因此,这条材料不能视为朱子的究竟之说。原文“体,是形体也”下有小注曰“贺孙录云:体,非‘体、用’之谓。”“贺孙”是指叶贺孙(字味道,括苍人,居永嘉)。贺孙所录为辛亥(1191年,朱子62岁)以后所闻。那么,据此推理,则端蒙此条所录也可能在1191年即62岁时(他与朱子过从密切,在去世前还曾写信与朱子诀别)。
《语类》中载有弟子辅广所记朱子论“其体谓之易”的一段话:
问:昨日先生说:“程子谓:‘其体则谓之易。’体,犹形体也,乃形而下者,《易》中只说个阴阳交易而已。”然先生又尝曰:“在人言之,则其体谓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是个动静感应而已,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是也。看那几个字便见得。”因言:“易是互相博易之义,观《先天图》便可见。东边一画阴,便对西边一画阳,盖东一边本皆是阳,西一边本皆是阴,东边阴画皆是自西边来,西边阳画都是自东边来。姤在西,是东边五画阳过;复在东,是西边五画阴过,互相博易而成。《易》之变虽多般,然此是第一变。”
广云:“程子所谓‘易中只说反复、往来、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
曰:“看得来程子之意又别。邵子所谓《易》,程子多理会他底不得。盖他只据理而说,都不曾去问他。”(《语类》卷六十五,《朱子全书》第16册,第2171页)
这段话中不少语句与上面程端蒙所记材料类似。辅广所记朱子语录在朱子65岁之后。如果拉近与上面程端蒙条材料的距离,那么辅广这条材料可系在朱子65岁时。可以尝试推测,在朱子62岁至65岁时,似乎他多次把“其体谓之易”中的体理解为形而下的形体。当然,就上面这段材料中朱子的讲话内容来看,他强调了心的动静感应,与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状态类似,接着又发挥了“易”的互相博易之易,以复、姤为重卦乾坤第一变,类似八卦中震、巽为其“一索”之第一变。这段话应该是进一步解释他所说的“易中只说个阴阳交易而已”。这是以邵雍先天易学的思想来解释互相博易。辅广问:程子所说的“易中只说反复、往来、上下”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其实程子这句话,在程端蒙所记材料中,朱子本人也有引用到。但在这条语录中,朱子明显站在邵雍一边,对程子有些微词,认为他只是单纯从“理”的角度非常抽象地来讲“往来上下”,没有去理会邵雍先天易学交互变易的精蕴。
显然,若把“体”理解为形而下的形体,这与朱子心统性情的基本思想是无法贯通的。实际上,朱子对这种说法也有明确否定过。我们看下面万人杰所记语录:
黄敬之有书,先生示人杰。
人杰云:“其说名义处,或中或否。盖彼未有实功,说得不济事。”
曰:“也须要理会。若实下功夫,亦须先理会名义,都要着落。彼谓‘易者心之妙用,太极者性之本体’,其说有病。如伊川所谓‘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方说得的当。然伊川所谓‘体’字与‘实’字相似,乃是该体、用而言。如阴阳动静之类,毕竟是阴为体,阳为用,静而动,动而静,是所以为易之体也。”
人杰云:“向见先生云,体是形体,却是着形气说,不如说该体、用者为备耳。”
曰:“若作形气说,然却只说得一边。惟说作该体、用,乃为全备,却统得下面‘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两句。”(《语类》卷一百二十,《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78页)。
“黄敬之”为弟子黄显子。朱熹批评了黄敬之“易者心之妙用,太极者性之本体”的思想,重申对程子“易、道、神”思想的肯定。但是这里强调“体”是“该体用”,与“实”字相似。接下来,他亲自否定了自己之前把这里的体理解为形气、形体的说法,认为只有理解为“该体用”才完备,才能统得下面的“道、神”。显然,这里内在地贯穿着其心统性情的思想,只有心该体用,才能统得性、情。如果易、心只是形气,统不了性情。万人杰在朱子51岁时过来学习,直到朱子70岁时,仍与朱子过从甚密。综合来看,这条材料应该是在朱子65岁之后,可能在68岁左右。
朱熹强调“体”与“实”字相似,又说是“体质”之体,“犹言骨子”:
问:“‘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如何看“体”字?
曰:“体,是体质之‘体’,犹言骨子也。易者,阴阳错综,交换代易之谓,如寒暑昼夜,阖辟往来。天地之间,阴阳交错,而实理流行,盖与道为体也。寒暑昼夜,阖辟往来,而实理于是流行其间,非此,则实理无所顿放。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实理寓焉。故曰‘其体则谓之易’,言易为此理之体质也。”(《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86—3187页)
这条材料为弟子董铢于朱子67岁以后所记。关于“体质”之说,朱子在回答叶贺孙问“其体则谓之易”时也强调“体不是‘体用’之‘体’,恰似说‘体质’之‘体’,犹云‘其质则谓之易’”。那么,体质之体是不是就是形而下的形体、形气呢?总体上来看,应该不是。这里实际上是引入“道体”的观念来解释“易体”。董铢这条材料最后有小注:“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集注》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即是此意。”(同上)
把易体与道体关联起来,在弟子甘节所录材料中也有体现:
周元兴问“与道为体”。曰:“天地日月,阴阳寒暑,皆‘与道为体’。”又问:“此‘体’字如何?”曰:“是体质。道之本然之体不可见,观此则可见无体之体,如阴阳五行为太极之体。”又问:“太极是体,二五是用?”曰:“此是无体之体。”叔重曰:“如‘其体则谓之易’否?”曰:“然。”(《语类》卷二十六,《朱子全书》第15册,第1356页)
“叔重”即董铢。这条材料录于朱子64岁以后。综合董、甘所录这两则非常相关的材料来看,体质、道体、易体是在一个层面来说的。
陈来先生在《仁学本体论》中对朱子的道体思想有深刻揭示,他指出:
从朱子学的立场来说,道体即是实体,也是最高实体。在程颐的说法里,道本无体,是无体之体,必须借助事物作为体才能为人所了解。但朱子已经与程颐不同,他不再说道之本然之体不可见,而直指川流,认为这就是道体之本然;他进而认为,天地之生化流行,就是道体之本然,可见他已经从程颐的观念摆脱出来,进至实体的观念了。①
在这个意义上,道体就是“其体则谓之易”的体,乃变化生生流行不已
之总体。至于此体之中寓有理,这是理学思维特别重视的地方。①因此,全面来看,朱子所说“其体则谓之易”的易体是该体用的道体。这样的易体、道体是理气浑融不分的。这种道体论、实体论,究其实,也是一种境界论。
《易传·系辞》还说到“神无方而易无体”,朱子认为“无体”是说“或自阴而阳,或自阳而阴,无确定底”,而“其体谓之易”之体,“是说个阴阳,动静辟阖,刚柔消长”(《语类》卷七十四,《朱子全书》第16册,第2522页),两者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无体”之体谓没有形而下的固定形体,“其体”之体为道体、变易流行之总体,可以说,“易”因其无体,乃成道体,为无体之体。
三、神用:功用而非妙用
在朱子看来,“其体则谓之易”为该体用之道体,非仅形下之形体。这可以作为定论。只有这样,“易、道、神”,才能与“心、性、情”对应协调起来。然而,以“神”对应“情”,仍有不少让人费解之处,以至于让我们怀疑朱子以心、性、情来解易、道、神,到底恰不恰当?与程子的原意是否一致?
在朱子心统性情的思想中,性与情对,为体用关系,情为心的一种活动状态。情总是关联着具体的人与事,关联着气,有具象性,有形下性。但是在一般意义上来说,“神”是超越性的形上存在。那为什么朱子把“其用则谓之神”对应于情呢?
这需要我们回到程子说的另外一句话以及朱子的解读。程颐说“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谓之神,以性情言之谓之乾”(《遗书》卷二十二上,第343页)。学生经常就“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谓之神”来向朱子请教前后两个神的区别。朱子认为“鬼神者,有屈伸往来之迹,如寒来暑往,日往月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见也。忽然而来,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测知,鬼神之妙用也”(《语类》卷六十八,《朱子全书》第16册,第2258页),“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无迹底。妙用是其所以然者”(同上,第2259页),“功用兼精粗而言,是说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测。天地是体,鬼神是用。鬼神是阴阳二气往来屈伸。天地间,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同上),“鬼神之神,此神字说得粗”②(《语类》卷六十七,《朱子全书》第16册,第2218页)、“言鬼神,自有迹者而言之;言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测识”(同上,第2087页)。综合来看,似功用之鬼神是形而下的(粗或兼精粗),而妙用之神是形而上的(精),朱子用“所以然”一词值得注意。《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程颐认为“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遗书》卷三,第118页),那么,套此逻辑,功用之鬼神为一阴一阳之屈伸变化,而妙用之神乃功用阴阳鬼神的根据或动力。
可见,实际上朱子是把“其用则谓之神”与“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等同起来。据黄㽦所记语录,朱子就曾直接说过“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功用则谓之鬼神”①,他直接把“其用则谓之神”中的“用”理解为“功用”,“神”理解为“鬼神”②。程颐曾说“鬼神者,造化之迹”,显然这也是从阴阳、形下的角度来理解功用和鬼神。朱子还说“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说起。虽是‘无声无臭’,其阖辟变化之体,则谓之易;然所以能阖辟变化之理,则谓之道;其功用著见处,则谓之神”(《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85页)。“阖辟变化之体”是易体、道体,其变化之理、道是本体、根据,这种意义上的理、道可以理解为太极。“其功用著见处,则谓之神”,“功用”意思是功能展现,是可见的表象世界。
结合这些来看,可以说朱子所理解的“其用则谓之神”之“用”主要是指各种自然现象、造化之迹,“神”是鬼神、阴阳二气屈伸往来之变化表象。“其体则谓之易”是讲变易流行的统体、总体,包含体用,而“其用则谓之神”则是表象、现象世界;当然,这个现象、表象也是体之功用表现,是用不离体、体用不二的。而“其理则谓之道”则是变化的根据、原理,是形而上的。
朱子反复以心、性、情来对解易道神。但是当以情释神,视神为情时,就会关联到心与神的关系,在此思维框架下,心“神”竟被视为气,为形而下的存在。我们看下面一段语录:
(直卿)又问:“神是气之至妙处,所以管摄动静。十年前,曾闻先生说:神亦只是形而下者。”贺孙问:“神既是管摄此身,则心又安在?”曰:“神即是心之至妙处,滚在气里说,又只是气,然神又是气之精妙处,到得气,又是粗了。精又粗,形又粗。至于说魂说魄,皆是说到粗处。”(贺孙)(寓录云:“直卿云:‘看来神字本不专说气,也可就理上说。先生只就形而下者说。’先生曰:‘所以某就形而下说,毕竟就气处多发出光彩便是神。’味道问:‘神如此说,心又在那里?’曰:‘神便在心里,凝在里而为精,发出光彩为神。精属阴,神属阳。说到魂魄鬼神,又是说到大段粗处。’”)(同上,第3186页)
这些话也是由以“心性情”讨论程子“易、道、神”话语引起的。牟宗三据此认为“无论叶贺孙录或徐寓录,皆表示朱子视神为神气、神采之神,与鬼神之神同。心、神、鬼神、魂魄、精、形等俱属于气,俱是形而下者”,并强调“心理学的心、习心、识心、成心,可视为气,为形而下者,而道德的、应然的本心则不可视为气,视为形而下者。神气、神采、鬼神之神可视为气,形而下者,而诚体之神,寂感真几之神则不可视为气,视为形而下者。由心理学的心到道德的本心,由鬼神之神到诚体之神,俱不能一条鞭地、直线地、形式地直通上去,而一是皆以气视之也”①,并批评说“朱子以如此实在论的态度一条鞭地视心与神为气,则其视道体为‘只是理’亦是很逻辑地一贯者,此见其心思清明、煞有工夫,而足以决定成另一系统,即吾所谓主观地说是静涵静摄系统,客观地说是‘本体论的存有’之系统”②。
牟宗三也承认神气、神采、识心、成心可视为气,同时他也指出诚体之神、道德本心的超越性,不可视为气。但是就“心性情”对应“易道神”话语来看,“情”对应“神”,这里的神为功用之鬼神,为具体的情感心理活动,类似于自然现象界的阴阳错综变化。在上面一段对话中,朱子所说的心与神,多是就神识、情识活动而言。实际上,在心神问题上,朱子的表述也相当复杂。当学生问“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时,朱子说“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若今学者所论操存舍亡之心,自是神明不测”(《语类》卷五,《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1页),陈来先生指出“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心脏之心实有一物,可以谓之形而下,但哲学意义上的心并非实有一物,其特质为‘神明不测’,故不能说是形而下。心既然不属形而下,当然意味着心不属气”③。在《孟子集注》中朱子解释“尽心”时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孟子集注》卷十三,《朱子全书》第6册,第425页),在《大学或问》中又说“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大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11页)。这两处关于“神明”的表述看起来很相似,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前者从总体上讲“心”是“人之神明”,这个神明偏于形而上,而后者讲“知”是“心之神明”,有具体形下性。吴震认为“在他(朱熹)看来,既然人心主要是一种意识知觉,具有虚灵不昧、湛然虚明、神明不测等特征,因而我们就不能用形上形下这套观念模式来定义”④。心与神、神明的关系相当复杂,在一个层面上,心、神为易体、道体,是理气合一的统体,在另一个层面又为偏于气的情识、神识。全面来看朱子的心,它是包性与情的,在寂然不动的本心层面,心近于性,在感而遂通的发用层面,心又表现为情。性与情皆为心所统、所包,近于性的本心通于形而上,表现为情的心识又近于形下之气。所以朱子也说“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朱子语类》卷五,《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1页),“灵”为神明性存在,相对气,有超越性、贯通性。在这个意义上,说灵说神,又是本体性理功能的展现。①但是在易道神话语下,在朱子的诠释下,神是有迹的功用之鬼神,为神气、神识,有形而下的气性特征。而牟宗三由此引申论证朱子的心为形下之存在,这种观点,显然又失之简单。
陈来先生指出“以‘心统性情’为代表的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构的表达、描述常常使用的模式并不是‘理/气’的模式,而是‘易/道/神’的模式。因为心性系统是一个功能系统,而不是存在实体”。②“在朱子的哲学中,知觉神明之心是作为以知觉为特色的功能总体,而不是存在实体,故不能把对存在实体的形上学分析(理/气)运用于对功能总体的了解。在功能系统中质料的概念找不到它的适当地位。另一方面,形上学的‘理/气’分析把事物分解为形式、质料的要素,而‘心’是统括性情的总体性范畴,并不是要素。这些都决定了存在论的形上学分析不能无条件地生搬硬套在朱子哲学中对‘心’的把握上面。”③陈先生的这个看法深刻精彩。也许朱子本人也感觉到用理气分析模式很难解释说明其心统性情的思想,所以引入程子“易道神”话语,并予以创造性转化诠释,用来说明其心统性情的思想,应该说他本人对这种解释模式还是很满意的,所以反复以心、性、情来论易道神,把易道神作为一种理想的解释模式来说明其心统性情的思想。陈来先生认为,“按朱熹的理解,二程的这个思想揭示了一个方法论的模式,即易(体)—道(理)—神(用),可以广泛用于说明一切具有一定功能的、自身运动变化的系统,就是说从三个要素来把握一个系统的总体关联,一个是系统的总体,一个是系统工作的原理,一个是系统的作用。朱熹发挥的这个思想,应当承认,具有相当深刻的含义。”④
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朱子的解读就是程子的原意呢?笔者更倾向于这是朱子的创造性诠释,是借用程子的话语来更好地表述其心统性情的思想,也就是说这未必或很难说就是程子的原意。牟宗三认为“‘其理则谓之道’,此理是与神为一之理。全道体即是一神,即是一理,但其为理是超越的、动态的、既存有亦活动的生化之理,不只是超越的、静态的、只存有而不活动的形式的所以然。朱子唯将此理视为静态的形式的所以然(当然亦是超越的、形而上的所以然),故将易体与神用俱视为气,但属于形而下者,而唯理才是形而上者。如此说理尤显非明道说此语之意”①、“至于‘其用则谓之神’,用即是道体生物不测之神用。‘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神即是寂感之神,亦曰诚体之神,皆即指道体自己说:全道体即是一神用,全神用即是道体之自己。此神用之用非是如普通之可以分解为体用,而体用各有所当属之用也:此神用不与体对,神即是体;道体亦不与神用对,体即是神”②。朱熹将神用视为气与情识,大体上可以这么讲,但是牟宗三说在朱熹,易体也是形下之气,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这不符合朱子原意。但是笔者倾向认可牟宗三“在明道,易体、神用、理道皆是说的道体自己”的看法,“其体、其理、其用,皆指‘上天之载’本身说,即皆指无声无臭、生物不测之天道本身说,是故易、道、神亦是此天道本身之种种名,所指皆一实体也”。③
总结来说,朱子把心性情与易道神进行对应,虽不一定符合程子原意,但不失为一种创造性诠释。尽管把情与神用进行对应造成不少理解上的困难,但总体上来说,用易道神来说明其心统性情的思想,还是有其理论上的自洽性,可以深化人们对其心统性情思想的理解。
(原载《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2期,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戴震与朱子对《孟子》性论诠释之差异
蔡家和
一、前言
朱子可谓宋学之集大成者,其依二程之理学思想而发扬光大,初始对于汉学亦是不满的!如于《大学章句序》提到:“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①这里的“自是以来”,指的是从孟子之后。
朱子的道统观视孟子之后,唯二程能够绍继,而其间(孟子之后至二程之前)的主流学说,大致上特点有二,亦是朱子所批评的:(1)佛、老二家之虚无寂灭教说;(2)专务章句训诂之俗儒,亦指经学之儒,此指汉儒之注经,徒务章句之诵读,而不知更深层且直指生命的学问。
朱子对于汉儒之不满,亦显示于《四书章句集注》之中,其所收集的注解虽亦包含了汉儒之说,但大致仍以宋代道南派为主,即程子弟子之传承,而朱子编有《论孟精义》,诠释上亦多宗于宋儒,即程子一系。之后,朱学盛行,历宋、元、明、清不衰,或多或少皆占有一席之地,影响所及遍于东北亚、东南亚,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而在中国,如朱子的《论语集注》既兴,而汉学何晏所编的《论语集解》即废,官学、科举考试等亦以朱子注书为依据。不过,到了明、清以后,朱学之影响力有了变化。先是明朝中叶,阳明学派兴起,其一主旨便是反对朱子学,欲与朱学一争正统,不过大致上,仍不出宋儒之视角,其采朱学之形式义而不采内容义,争辩于心即理或不即理的问题。到了清代,戴震可谓反朱之巨子,就连朱子之形式义亦不取,不信朱子的“性即理”之说,而改依《礼记》,定义“性”只是血气心知。②
清代学风之兴,有回到朴学、古学、实学的趋势,亦被称为汉学,概以汉学为宗,而反对朱学,或以朱学为主的宋学。其视宋学已杂有佛老,虽可谓性命之学,却离先秦古义甚远。方法学上,朱子主张“以义理领导训诂”③,不过,戴震则以先秦字义为准则,如其《孟子字义疏证》之作。
《孟子字义疏证》为戴震之重要作品,由此作,亦可看出汉学与宋学两种治学宗旨之大相径庭,汉学可称为相偶论,宋学则为体用论,如此不同观点,亦同时显现于其他“四书”“五经”之诠释上。
由于系统庞大,本文即聚焦于《孟子》之论性一处,借此比较二派对于孟子之性善说有何不同诠释?最后再做一总结,以孔孟为准,检视二派说法有何特点?谁较能接近孔孟之说?
二、戴震与朱子之性论
(一)戴震:性是血气心知
关于“性”字之诠释,学界向来有分歧,许是因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如《中庸》“天命之谓性”一句,两派对此诠释即不同。朱子解曰:天之所命令者,在人而为仁、义、礼、智之性,性即理也!而戴震认为:万物分于道而为运命,人道即不同于物道,人性与物性即不相同。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将“性”解为血气心知:
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气化生人生物以后,各以类滋生久矣,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气化曰阴阳、曰五行,而阴阳五行之成化也,杂糅万变,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虽一类之中又复不同。凡分形气于父母,即为分于阴阳五行,人物以类滋生,皆气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谓性。”以生而限于天,故曰天命。《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分于道者,分于阴阳五行也,一言乎分,则其限之于始,有偏全、厚薄、清浊、昏明之不齐,各随所分而形于一,各成其性也。然性虽不同,大致以类为之区别,故《论语》曰“性相近也”,此就人与人相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言同类之相似,则异类之不相似明矣,故诘告子“生之谓性”曰:“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明乎其必不可混同言之也。天道,阴阳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咸分于道,成其各殊者而已矣。①
这里,戴震举《大戴礼记》语而来证明:性乃血气心知!《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分于天道之阴阳五行,即为命!借此诠释《中庸》的“天命之谓性”。《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属《小戴礼记》,而与《大戴礼记》相近。
依于此说,则“天命之谓性”的“命”字,有其分道,则所受者亦有所限,人有德性,而物则无。然反观之,人亦有不及于物者,如人的眼力、嗅觉不及于鹰、犬等,以分于道而有所限之故。故此“命”义乃指命限,有所禀、运气上的不同。至于“形于一,谓之性”一句,意思是,个体成形即有其性,某甲有甲之人性,而牛则有牛之物性。
此说的重点,乃“性”一字,有分类上的不同,如人性这一类,与牛性这一类,两类不同。这里的类概念,不只是生物学上的区别,更是存有论与德性论上的;人之存在属类,不会同于牛一般,而人之食色,亦不同于牛之食色,人是道德之存有,而牛则不是。
孟子亦曾有类概念之说,其曰: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孟子·告子上》)
同类则为相似,不同类则不相似,如某甲与某乙同类,则为相似,唯孔子虽属人类,却能成为圣贤,能够出于其类而拔乎其萃!一般来说,如果不知对方的脚有多大(需穿多大的鞋),只要依于同类之概念而来推测或制作,大致也就不会相差太多了。又如人之口味、味觉,彼此之间,便较犬、马等之口味更接近,马食刍草,人却不然。同类之人性较为相近,食色亦相近,道德性也相似。在戴震而言,食色亦是性,属于血气之性。
至于心知之性,戴震认为:
孟子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当于理义,其心气必畅然自得,悖于理义,心气必沮丧自失,以此见心之于理义,一同乎血气之于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义非他,可否之而当,是谓理义。然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异强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①
这里明言,“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非喻言也”(《孟子·告子上》),指理义悦心与刍豢悦口之间,并非比喻的关系,而是指两者都属于人性。部分学者因“犹”字,联想到“性犹湍水”云云,认为此自为比喻无误,然理义悦心与刍豢悦口之间却非比喻,例如“牛之性犹人之性”一句中的“犹”字,即等同的意思。
心知即如君官,心官能思、能知,能依于物之则、人道、义理等而来导正;人道,即是义之道,心官悦于义理、人道,如同依于光之照明,而能中理不谬;心官依其本性,而能悦于仁义之道!
此处所引之文,尚有一个重点,即对于孟子“天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之正解,戴震的说法是:“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参看《孟子》原文: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
关于这段话,汉、宋学二派解法不同。汉学家方面,视天下之性乃千古如是,人类、犬类、牛类等各类之性、血气心知等,从古至今,不曾稍改。而宋学家中,朱子所解之“故”,谓依其旧理、故理①,此为“性即理”;牛之理千古以来不曾稍改,人之理亦然。
朱子视性即理,而戴震则以性为血气心知,这似乎是孟子性论诠释中的理、气之争。要注意的是,戴震此中的血气心知并非属于形下层次;形上与形下二者,需要两两对立才能成立,若无气化之外或气化之内的区别,又何来形上与形下之切割?戴震的血气心知,并非如朱子所定义的形下之气,而是即于形下形上、无分气化内或外之气。形上与形下在戴氏而言也只是成形前与成形后之说不同,不可以朱子的形上形下之说用在戴震身上。
(二)朱子:性即理
朱子所主张的“性即理”之说,传承自伊川,而戴震则提出质疑,问如下:
问:《论语》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自程子朱子始别之,以为截然各言一性。(朱子于《论语》引程子云,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反取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为合于孔子。②
这里质问:依于程朱,则《孟子》之性善论,与《论语》“性相近”说,两者所说之“性”竟不同?不过,程朱的气质之性(张载亦如此发明)与天地之性,其实是同一个性。所谓的气质之性,只是本然天地之性落于气质之中,以至于所表现出的本然之性,有多寡程度上的不同,即使在动物上,天理、天性亦同,亦为性善,只是动物气质浊劣,只得表现其偏,如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等,证明动物亦具有性善、道德性之部分。而戴震则不如此认为。那么,戴震为何要说,若依程朱,则《论语》的“性相近”与《孟子》的性善论,将为二性?这可参看《论语集注》中,朱子对“性相近”的诠释,曰: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①
程朱诠释孟子之性善论,定义为:性即理,故无有不善。不过,程朱以为,《孟子》一书中所言之“性”,却是要随文看,即有时是指天理之性,有时却是气质之性。若言性善,只能是天性、天理,人、物皆同,又怎可言“相近”?若言“相近”,只能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亦是源自本然之性,但因所秉、客观环境不同,致使气质有美、恶之分,有时甚至相距亦远。
程朱认为,《论语》既言“性相近”,那么也就只能是气质之性;而在其他著作中,也提到告子之说亦是气质之性,这便让戴震怀疑,若依程朱,则反而告子合于孔子,而孟子不合孔子。在戴震“反取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为合于孔子”一语下有小注云:
程子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此止是言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性安有缓急,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又云:“凡言性处,须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止论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为孟子问他,他说便不是也。”②
此戴震抄自伊川之言,用以证明程朱之论,似乎以告子合于孔子,而孟子反远于孔子?那么,朱子对于告子的“生之谓性”,又是如何理解的呢?其曰: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③
前面戴震共引伊川的两段话。第一段,“性相近”云云,与“生之谓性”之说,皆指所禀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乃本然之性堕于气质之中而来,遂有善恶、美丑之判,而本然之性亦常为气质之性所掩,致其表现不出本然之性善。
而这里,朱子主张孟子所论之性,乃纯粹之天地之性,性即理也;而告子则不知以性为理,而以气当之,此只是形下之气,不比本然性善的仁义礼智的形上之理;而形下之气所杂的气质之性,主要以知觉运动为主,乃指人之食、色等动物性。
戴震依此朱子义理,而与伊川的气质之性比配,认为若依程朱之说,则反而导致告子能同于孔子,而孟子反不能同于孔子的结果,因为告子与孔子所论之性都是气质之性。
三、程朱对孟子之翻案
(一)二程论性已不同孟子
程朱理学揭橥“性即理”说,亦称为理气论,性即天理,而天理无所不善,则关于“恶”的出口,便只能推向另一边的“气质之性”。这应该就是程朱创立“气质之性”的原因,于是形成了二分之性的格局。再者,也正因性之二分,程朱可把历来诸如告子、荀子、扬雄、释氏、胡氏(五峰父子)等人说法,都判定为“误把气质之性认作天地之性”一类,这类人以气当理、认气为性,于是有性善恶混、性可善可不善、性空等说,是则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矣!
程朱学派认为,因着理气之二分,儒家便得以归纳历来关于性论之学派,以便杜荀、扬等辈之口,战国时期的孟子无法做到,如今程朱却办到了,则历史争论至于程朱,或许可以稍歇!不过,戴震却不以为然,评曰:
创立名目曰“气质之性”,而以理当孟子所谓善者为生物之本,(程子云:“孟子言性,当随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谓性’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后谓之性耳,故不同,继之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然不害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极本穷源之性。”)人与禽兽得之也同,(程子所谓“不害为一”,朱子于《中庸》“天命之谓性”释之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而致疑于孟子,(朱子云:“孟子言‘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欠中间一转语,须着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异”始得,恐孟子见得人性同处,自是分晓直截,却于这些子未甚察。”)是谓性即理,于孟子且不可通矣,其不能通于《易》《论语》固宜,孟子闻告子言“生之谓性”,则致诘之,程朱之说,不几助告子而议孟子欤?①
这里引了伊川之说。伊川认为,一来,孟子书中的“性”,须要随文看,有时指本然之性,有时指气质之性,二性并存,一是先天本然之性,二是后天落在气质中的性。二来,告子的“生之谓性”,并非全错。告子的“生之谓性”也是性,只不过是指受生之后的性,也就是气质之性,不同于孟子所强调的本然之性。只要区分出《孟子》书中的两种性,则孟、告争议即可平息。①而伊川的这些想法,其兄明道早已言及。明道言: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灭若敖氏之类),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②
明道以为,人生而静之上不容说者,乃本然之性;可说者,即是气质之性,这也可比配于告子的“生之谓性”。此气质之性,性即于气,气即于性,原来只是本然之性落于气中者,如此一来,则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本性虽善,但因落于恶的气质之中,也就表现不出其本善。前面伊川的话,便是对其兄明道思想之阐发,而明道此段,大致也可用伊川“气质之性”的理念来做诠释。
伊川又说,犬之性、人之性、牛之性,虽在显现上不同,但不害其本性为一。这样的说法,其实已经翻了孟子的案了。如《孟子》原文:“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孟子·告子上》)意思是,此三性并不同,犬性亦不同于牛性,虽都是动物,但本性不同。
而伊川却说“不害其为一”,此所谓“理一分殊”,如月印万川,天下海、湖之月影稍异,然本源为同一之月、同一之天理,天理即性,万物皆同具本然之性,而性即理也。万物虽同具一个性理,但因人、牛、犬等所禀气质不同,所表现出的本性之程度也就不同。人得其秀而最灵,人的气质中所表现出的本然之性较多;动物则较少,亦有些微道德性之表现,如羔羊跪乳、蜂蚁有君臣之义等。这些论调已与孟子不同,当是一种创造性之诠释,或可用以解决历来各家论性之争议,如荀、扬等人之说。
(二)朱子对二程之承继
程子尝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③而朱子继之而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孟子终是未备,所以不能杜绝荀、扬之口。”④论性不论气者,指孟子,而论气不论性者,指荀、扬。亦是说,性论之所以历来分歧,无法定于一尊,乃因各家所言之性不一,孟子所言,乃终极的天地之性,而荀、扬则是以气为性。直到程子,才算真正解决各家之纷争,而得以杜绝荀、扬之口。
然如船山质疑程朱此说,曰:“程子固以孟子言性未及气禀为不备矣,是孟子之终不言气禀可知已。”①船山意思是:若以孟子性论有所不备,则知孟子终究未曾言及气禀呀!
不过,朱子于《孟子集注》中,仍是以气禀之说来做诠释。如《孟子·告子上》“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一段,关于“命”者,概有所禀与所值,禀其气清,则行义也易。此所言“命”,亦同于“天命之谓性”一处,天命者,本然之性也,而此性亦在气中。
故朱子注“天命之谓性”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②人、物各率其性,人率人性,马率马性,都是天理之生,而表现在气禀之中。朱子又言:“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③于是要人修道、进德修业。这便是程朱的气禀义。
戴震于“人与禽兽得之也同”一句后面,又引朱子《中庸》“天命之谓性”之注,即朱子所注,业已视人、物之间是本根、同性,故不害其为一,即人性、物性源于同一性。
朱子这些说法,亦曾在韩国儒学界引发著名的“湖洛论争”,主要争辩人、物性之同或异?依于朱子,人、物性是为同一性,所谓“不害其为一”者,皆源于同一个天理;不过,朱子亦说人、物性分殊,此因后天所禀气质不同,致使所表现出的“理一”多寡有别。而即便是动物,亦有健顺五常之德,只是气禀较偏,只能微性(道德性)之表现,不若人之周全,然人、物性却是本源同一的!四、性中有无食色?
(一)戴震:性中有食
依朱子“气质之性”说,性善为本然之性,性中没有食色,食色者,气质之性也。朱子注“告子曰:食色性也”处言:“告子以人之知觉运动者为性,故言人之甘食悦色者即其性。”④若再加上伊川之语,则可知“食色性也”亦是“生之谓性”之性,亦同于《论语》的“性相近”,皆属气禀之性。总之,在“性即理”中,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没有孝悌,更没有食色。
然戴震有不同看法,他主张“唯有血气心知之一性”,合于血气与心知而为一性,是为“一本说”。性中自有血气、嗜欲、食色……如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又如上文提到,戴震认为“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云云,此非比喻之说,而是指即便是“刍豢之悦我口”,亦是性!
此如韩国儒学古学派之代表人物丁茶山所言“性是嗜欲”,以为所谓的“动心忍性”,其中的性何以要忍?以性即是欲故,当须用忍,不容私欲之任意勃发。孟子也有“可欲之谓善”的说法,这也近于戴震的“性中有食色”。
再来参看戴震以下之诠释:
问: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张子云:“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云:“仁义礼智,天道在人,则赋于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浊,然而性善可学而尽,故不之命。”宋儒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本于《孟子》此章,以气质之性君子不谓之性,故专取义理之性,岂性之名君子得以意取舍欤?
曰:非也,性者,有于己者也,命者,听于限制也,谓性犹云借口于性耳,君子不借口于性之自然以求遂其欲,不借口于命之限之而不尽其材,后儒未详审文义,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谓性,非不谓之性,不谓命,非不谓之命。①
这里,问者因张子“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之言,视张子亦只说天地之性,而不谈气质,于是将张子等同于程朱,皆以天地之性为本性,而排除了气质。
然而,张子亦言:“性其总,合两也。”合于天地之性与声色之性。又曰:“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②而张子对于《孟子·告子上》“口之于味”章的诠释,也颇为地道,其言:“养则付命于天,道则责成于人。”③此甚得孟子之旨。
(二)唐君毅:以道德引导食
关于戴震上述说法,可以参看唐君毅先生之评论,其言:
清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以《礼记》之血气心知之性释孟子,谓声色臭味之欲,根于血气,仁义礼智为心知,并皆为性,乃以借口释谓字,说孟子立言之旨,非不谓声色臭味之欲为性,而只言人不当借口于性以逞其欲,此亦明反于孟子之“不谓性”之明言,亦与孟子他处言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处处即心言性,不即声色臭味之欲言性之旨相违。④
看来,唐先生并不苟同戴震之说法,认为其说将有违于孟子之旨。不过,唐先生也不赞成朱子之解法,如言:
朱子承程子之言,于上一命字,以品节限制释之,而于下一命字,则曰谓仁义礼智之性,所禀有厚薄清浊,故曰命,此又以人之天生之气质之性之差别为命,对同一章之命字,先后异训,即自不一致。朱子尝谓气质之说,起于张、程,又何能谓孟子已有此说?①
同一“命”字,于同一章内,却有前后不同意思,如此说法,显得牵强。再者,由既有文献来看,可以说“气质之性”一语,起于张子、程子,又怎能牵扯上孟子早有气质之说呢?对此,唐先生亦是颇不以为然的。
唐先生倾向于一种做法——撷取各家之长,或凡合于孔孟之旨者,便来导出他所认为合宜之诠释。从侧重的角度来看,唐先生亦是将血气之性与道德之性合而为一,再以道德之性而来引导食色之性,这种方式最终还是与戴震一致。只不过戴震是先将二性合一而论,先总说一性;唐先生则是先分解为二性,而后再将二性合一。
若回到《孟子》原文,心官则思,应当从其大体,继以大体引领小体,以德性引导食色,孟子本义如此,戴震亦不敢违背。戴震“君子不谓性”之诠说,应是指:君子不会借口食色亦是天性,而随意放纵,在命之不可得时,亦能随遇而安。
五、物性之辨
(一)人性、物性之辨
依朱子的“性即理”说,人性、物性本源同一,彼此之不同,只在于禀气之殊异,人得其秀而最为灵气,性理之表现亦多,而动物却因气禀所限较多,仅能部分表现道德性。至于戴震则有不同见解,他认为,人是道德之存有,其心知可以知仁义,而悦于仁义,然动物则缺,以物之类种与人不同之故,并非道德之存有一类,无法表现仁义。
此外,戴震所定义的性,将随种类之不同而不同;人性与牛性不同,牛性与犬性也不同。关于后者的牛性、犬性之异,朱子则不强调,于是戴震批评朱子这点,其曰:
朱子释《孟子》有曰:“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如其说,孟子但举人、物诘之可矣,又何分牛之性、犬之性乎?犬与牛之异,非有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不得谓孟子以仁义礼智诘告子明矣。在告子,既以知觉运动为性,使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告子何不可直应之曰“然”?斯以见知觉运动不可概人物,而目为蠢然同也。②
这里举了朱子注《孟子·告子上》“生之谓性”章一段,表示人与物之同者,在于食、色等动物性,统称为知觉运动,人、物皆能知觉,皆能运动。不过,朱子此说,与孟子之说稍异;若依孟子,人、物虽都有动物性,都能知觉运动,但其中之内容毕竟有别,如孟子尝言:“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孟子·告子上》)此则显示人、马于性类上之殊途。且口味亦性也。
(二)物性之辨
上文引言,戴震更强调物物亦别的概念,以物与物之间应是分属于不同类种,亦如《孟子》原文:“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若只是分辨人与物之不同,则孟子只要举例“牛之性”犹如“人之性”便罢,为何还多了一句“犬之性犹牛之性”?
戴震这里的言下之意,似乎在凸显,朱子之所诠无法契合于孟子原意;孟子所表达的,当是一种类概念,即不只人、牛不同,至于犬、牛亦不同。朱子只是大要地说:知觉运动之蠢然,人与物同,而仁义礼智之粹然,人与物异。孟子此章,只谈人、物之辨,而不提犬、牛之辨。
若回到《孟子》原文,则孟子亦看到牛性与犬性之间的殊异,此由犬能看门而牛能耕作之不同表现上看出,可见牛与犬并不同类,性亦不同。则朱子此章之诠,便显得不够周全。
戴震以为,若孟子只谈人、物之异,则只要说一句“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就好,“犬之性犹牛之性”云云,则为多余,但朱子似未认清物性之间亦有不同这点,其过失归根结底即在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性之分说,以及把“性”定义为天理、仁义礼智等说法有其弊病。
六、结语与反思
历来汉宋之争,宋儒之于汉学,总认定汉学仅是一种训诂之学,如朱子曰:“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①不过,朱子自己对于汉儒文献之抄录与批判,甚少下过功夫。既然缺乏论据,则朱子的批评也就难以服人。若是清儒,如戴震——作为汉学之一派,对于宋学程朱学派之批评,则用功甚多,他将宋儒作品逐条抄出,而后进行评判及论证,如此做法,说服力较高。②
到了近代之“当代新儒家”,其立场则又倾向于宋学,同时也对汉学特别是清代汉学做出批评。个中翘楚,如唐君毅先生认为,戴震视“理”为分理、文理、肌理,只看到先秦于“理”之区分处,而不见其整全,只见于“理”之静态性,而不知其动态性。总之,将“理”视为文理、分理,并非先秦之唯一说法。
唐先生之相关批评,收于其著《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约20页之篇幅①,其论述甚是有力。他举出戴震之缺失有三:
其一,孟子乃“即心言性”,如孟子言:“仁义礼智根于心。”不过,依笔者拙见,孟子除了“即心言性”之外,亦有“即生言性”②,如告子提出“生之谓性”处,孟子不辩,而只辩其义外。
其二,《孟子》原文“口之于味”等等,“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唐先生认为在性中有命的,如口味,这得之不得有命,故在君子而言,不谓此为性。此处也是唐先生对戴震的反驳,因为他举出,孟子都视口味等,在君子不谓性了。然笔者认为,《孟子》原文也有提到“性也,有命焉”,但仍是性。而唐先生最后以道德之真性可包括口味之次味,则亦是融入戴震之说了。
其三,戴震谓,性乃血气心知,而能达情遂欲。唐先生则问,则由此血气心知,如何达到仁义?若是后者,当需自觉主宰,方能达办,此与达情遂欲,恐怕已是两层问题,而非戴震之一元气论所能解决。③唐先生强调,这里要有一股精神之转折,方能由己情之达,而生同理心之自立立人、已达达人,自己若无其情,则不能知晓他人之情。这是发生顺序之义理,而非以性理来领导生理。
唐先生的第三点,可说非常有力。但若站在戴震立场,当须掌握达情遂欲之中相感相通之情,而将此情上看、高看即可。因戴震只是气论之一层、一元,其情将不同凡响、不能低看,总只有这一层,而须即情即理。乃一种依心知而能自觉,从一般之情,而为理想感通之情。
唐先生亦以为,朱子之论性,所谓“性即理”,乃是依于伊川之发明,而朱子之“心统性情”,则是来自张子,并于其性论之建构,区分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这一连串的发展,难以溯及孔孟之说。④若强以此套建构来诠释孔孟之性,则非孔孟原意。朱子的确需要回答戴震之质问,除了戴震之外,明清之际的许多学者,如阮元、焦循等,以及日本之江户学者伊藤仁斋等,都对程朱有所批评。
唐先生最后以“即心言性”来包括“即生言性”,同理,是否也可把朱子的“性即理”,用以收摄性即气之一面?另一方面,戴震的血气心知、情欲,是否亦能上提而收摄同理心?然无论如何,都不能违反大体摄小体的原则。这些做法,或许更能接近孟子原意。大致上,唐先生似有调和汉宋之意,视两派各有优缺点,而欲平彰汉宋,各美其美。笔者以为,唐先生之论证力道,足以抗衡汉学,而为新宋学之坚强学者,值得吾辈关注。
(原载《孔学堂》2021年第2期,作者单位: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
陈来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教授主编的《陆陇其全集》。陆陇其是清初的朱子学家,号称理学名臣。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清初朱子学的研究将会有重要的推动。进而言之,我觉得明清朱子学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将会成为未来新的增长点。
回顾我们四十年来宋明理学的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完成了朱子哲学研究爬坡的任务。所谓爬坡,就是我们要经过攀登,然后占据包括东亚在内的整个世界朱子哲学研究的高地。在第一个十年之中,这个任务我们达成了。到了第二个十年,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完成了攀爬、占领世界学术领域里面王阳明哲学研究的高地。
然后,到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宋明理学研究的增长点是朱子学和阳明学之“后学”的研究,比如阳明后学的相关文献整理。江南地区的学者,浙江、上海的很多学者都参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特别是浙江的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阳明后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支朱子后学,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开始阶段主要是我跟朱杰人教授等人一起推动的,以南昌大学为基地进行系统的朱子后学的研究,现在正在开始慢慢地开花结果。但细致地看,目前朱子后学的研究课题,截止范围大概是在元代(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其截止的断代是在元代),很多朱子门人、后学的研究都是到元代为止,这是其研究范围。
然而,广义地讲朱子后学,当然就应延伸到明代、清代。因此这个朱子“后学”的课题,还需要在明清时代的朱子学之中继续发展,也就是说,想要完整地呈现整个的朱子学、朱子后学的研究,新的增长点就在明代、清代。甚至可以说,明清朱子学的重要性绝不低于宋末和元代的朱子学。这个时期,有大量的朱子学者以及朱子学的文献,所以说诸如陆陇其等明清朱子学相关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
特别是,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还与另一个线索的研究很有关系,就是说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们除了朱子学、阳明学以外,还有一条线索就是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研究。这一时段其实也是我自己比较关切的,比如说我在1986年曾撰文讨论“二陆”,就是陆世仪、陆陇其。陆世仪是明末清初的,陆陇其是清初的。陆陇其强调实行实学,反对空谈心性,反对太极玄想,要求使学问向人的道德实践方面发展,表现出他与早期朱学的差别,可以说他是属于清初理学内部的实践派。我自己对陆世仪的评价比较高,认为他是明末清初诸大家之一。原来我们讲三大家,其实应该是四大家,如果缺了陆世仪是不完整的。因为从刘宗周下来,黄宗羲还是顺着心学的脉络进行学术总结的;王船山的独立性很强,但是他的后期还是顺着张横渠;顺着朱子学下来进行的总结性的研究,那就是陆世仪。所以说,我一直认为陆世仪是明代朱子学之中具有总结性、代表性的人物。另外我也研究了黄道周,他是明末的“二周”之一,后来有些学者做了后续的研究,明清哲学中专门的研究我后来选择了王船山。明清之际这个阶段的研究,不仅对我自己而言,就是对整个中国学术界来讲,也可以说是除了朱子学、阳明学以外,一个独立的重要领域。
明清朱子学跟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在时间段上是有交叉的,像陆世仪,既是明清朱子学的,也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所以研究这一时段,从我们宋明理学整个学科的布局来说,是不断发展下去的有效的新的增长点。就宋明理学领域来讲,明清朱子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明代中期开始的这段朱子学,我们以前的研究也不是很清楚。如果这段朱子学研究得不清楚,不仅对朱子学的发展线索不能清楚地了解,对阳明学本身也不能清楚地了解。也就是说,阳明学有些细部的了解,必须对应着朱子学的研究。比如王阳明中年时期在北京、在南京,跟朱子学者有着复杂交流,这些问题一直就没被很好地研究过,最近几年开始有学者来做研究了。
所以说,明清朱子学的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这些工作也可以算作江南儒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因为明清朱子学里头有很大一块,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学者,有很多都是属于江南儒学的研究范围。因此,对于现在江南的学者,以浙江和上海地区为主的年轻学者来说,这个新的有效增长点更需要认真把握,也应当能够做得更加成功,比如《陆陇其全集》的顺利出版,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1月20日,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四书》学的忧乐情怀与宋儒的内圣之道
朱汉民
中国哲学是以人文关怀、人生意义为出发点。宋儒既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又追求“孔颜乐处”的超然境界。理学家通过挖掘《四书》的思想资源,以表达自己对人文世界的忧患与喜乐的进一步思考,进而建构一种既有人文关怀、又有精神超越的内圣之道。质而言之,宋代士大夫推动儒家内圣之道的哲学建构,其出发点正是一种与忧乐相关的人文关怀。
一、《四书》的忧患意识与宋儒的社会关切
宋代士大夫普遍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既有《四书》记载的儒家士人的精神传统,又有着现实的社会政治原因。
首先考察《四书》的士人精神传统。在早期儒家的子学著作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孔子及其弟子们对君王无德、士人无耻、天下无道的强烈忧患。孔子深刻表达了他对天下无道的关切,他一直强调“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进一步思考天下无道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社会普遍缺乏仁爱精神,而仁爱精神的推广又离不开教育。所以,孔子《论语·述而》反复强调:“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卫灵公》记载:“君子忧道不忧贫。”可见,孔子已经将自己对社会政治的忧患,转化为对文化教育的忧患。《孟子·离娄下》也大量记载了孟子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方面的种种忧患,他进一步指出忧患意识的价值与意义:“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孟子相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而君子不能够消极地等待忧患灾患的来临,而是要保持积极的防患于未然的心理准备。所以,忧患意识的重要价值,就是要强调持久、不变的戒惕心理,即所谓保持一种“终身之忧”的精神状态,最终才达到“无一朝之患”的结果。《孟子·告子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是强调忧患的精神状态是为了使人提高警觉,心存戒惕而临危不乱。
《四书》元典奠定了的儒家士人的精神传统,特别是对宋代士大夫形成的忧患意识有直接影响。
如果说汉唐时期的儒家士族衍化为因文化垄断而成为既得利益的“准贵族”的话,宋代士大夫主要是来自于白衣秀才,他们是一个从民间士人上升到庙堂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的社会群体,他们与先秦儒家诸子既有着相近的精神文化的血缘联系,又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文化情怀,故而自然和早期儒家士人的人格精神十分一致。他们从《四书》元典中寻找人格典范、思想资源,《论语》《子思子》《孟子》表达出来的士君子的忧患意识和人格精神,成为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源泉与效法典范。早期儒家士人表现出来的关怀现实、心忧天下的人格精神,对宋代士大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然,宋代士大夫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还与两宋面临的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分不开。宋代有一个政治现象值得注意:士大夫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两宋时期,恰恰面临内忧外患的严重政治局面。士大夫群体在承担与君主“共治天下”政治权力的同时,相应也就承担了重大的政治责任,这一重大政治责任很快也转化为士大夫群体对内忧外患局面的忧患意识。一方面,宋朝面临严重的内忧,宋初为了防范割据势力和各种政治力量篡权,强化中央集权而推动政治、军事、科举等方面的变革,他们在防止地方割据势力而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积弊,特别是出现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等问题,逐渐导致国力贫弱、民生艰难;另一方面宋朝面临“外患”,宋开国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却又相继陷入了辽、西夏、金和蒙政权的威胁,宋朝立国后的数百年间,始终受到外患的侵扰,游牧民族的南下侵夺始终是两宋的大患。所以,在宋朝建国后不久,“内忧”“外患”的矛盾开始显现,处于政治中心的宋代士大夫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普遍持有一种浓厚的忧患意识。本来,两宋时期士大夫群体是凭借自己拥有的文化知识、政治理念、价值信仰而参与政治的,并且获得了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机遇,所以,他们能够成为参与朝政的政治主体,而且往往会成为一种政治清流,而并不会像其他如军阀、后宫、宦官等权贵政治力量一样,容易导致对权力的贪婪与对民众的傲慢;相反,当士大夫群体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价值理念,必然会积极推动对内忧外患严峻现实的变革。所以,士大夫越是成为政治主体,他们感到的责任也越大,随之他们的忧患意识也越强。两宋以来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确实引发了士大夫的强烈忧患与革新意识。范仲淹向仁宗帝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变法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办法。范仲淹“立朝益务劲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欣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①王安石一直怀有很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顾内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而风俗日以衰坏。”②他主导的熙宁变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常恐天下之不久安”的严重忧患。
由于《四书》就是一套充满士人忧患意识的儒家经典,宋儒可以通过诠释《四书》,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在宋儒对《四书》的诠释传统中,特别强调士人的人文情怀、政治责任,也特别强调士人的家国情怀、天下担当,希望能够唤起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二程将《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子由、颜子等人表现出来的责任承担及其忧患意识,统统理解为“圣贤气象”:
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如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由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子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观此数句,便见圣贤气象大段不同。①
孔子、子由、颜子等人表现出来的无非是士人从政所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与忧患情怀,但是,二程将这一种本来是士人期望承担的政治责任与忧患意识,提升为一种“圣贤气象”,以作为士大夫效法的人格典范,宋儒的这一看法其实是有重要的现实原因的。
由此可见,宋代士大夫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崛起,他们拥有的强烈政治责任、忧患意识,一方面与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身份的提升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与他们自觉继承先秦儒家士人的人格精神有密切关系。宋儒在诠释早期儒家士人的子学典籍即《四书》元典时,实现了在现实中面临的内忧外患与《四书》文本忧患意识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对话。两宋以来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是宋代士大夫激发起忧患意识的现实原因;而一千多年前儒家士君子的人格精神,则是宋代士大夫激发起忧患意识的精神源泉。所以,追溯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精神渊源,可以在先秦儒家士人的子学系统及经典传记之中找到,特别是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中找到。宋代士大夫从早期儒家子学中获得相关的思想资源,《论语》《子思子》《孟子》表现出来的士人精神传统,既为宋代士大夫精神崛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激发了宋代士大夫重建与自己精神契合的《四书》学。由此可见,以《四书》学为代表的宋学之所以蓬勃兴起,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知识传统的建构,更加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新的士大夫精神传统的建构。
所以,宋儒一方面仍然关怀现实、心忧天下,希望实现博施济众的经世事业,故而仍然关注国家政治治理;另一方面,宋儒的学术旨趣重心已经从汉代的“外王”转向宋代的“内圣”,宋儒往往相互劝勉、自我期许要成为“圣人”,普遍向往、追求“圣贤气象”的人格理想,使宋学具有“内圣之学”的特点。所谓“宋学精神”,其实也就是宋代士大夫精神。宋代士大夫坚持对知识、道德和功业的不懈追求,倡导一种有体有用的学术精神,特别强调由士大夫掌控的“道统”要主导由朝廷掌控的“治统”,这一切,均体现出宋代士大夫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由于宋学兴起代表了士大夫的文化自觉,他们无论是在庙堂执政,还是在学府执教,均表现出鲜明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他们倡导、建构一种体现士大夫主体意识的道统论,其实正是在推动一场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宋学运动。
二、《论语》的孔颜之乐与宋儒的精神超越
宋代士大夫追求的“圣贤气象”,还表现出另外一个侧面,即对“孔颜乐处”的精神超越、人格理想无限向往与不懈追求。在宋儒对“圣贤气象”的诠释中,“圣贤”不仅仅追求“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更应该具有“孔颜之乐”的超越精神和人格特质。宋代士大夫对“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人格理想的追求,也是通过《四书》学的诠释来完成的。特别是《论语》《孟子》中记载了早期儒者积极入世的乐观精神和人生境界,往往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向往、仿效的典范。
“孔颜乐处”源于《论语》。《论语·述而》中有多处记载孔子对精神快乐的追求,如孔子曾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雍也》记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述而》记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这里可以看到,孔子并不因为事业困局、颠沛流离而忧伤、痛苦,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士君子应该将快乐学习、快乐生活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特别是《论语·雍也》孔子对学生颜回有一段评价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非常欣赏颜回能够超越物质生活条件、达到一种纯粹精神快乐的人生境界,肯定这一种“乐”的状态高于“忧”。“孔颜乐处”代表了作为个体存在、感性生命的儒家士人,一直将“乐”作为自己的生命本真和人生理想。
在汉唐儒家那里,并没有对孔子、颜回关于人生之乐表达出特别的关注。但是,原始儒家追求“乐”的人生境界,在宋代士大夫那里得到强烈的呼应。《论语》中有关“孔颜之乐”的问题,很快成为一个士大夫普遍关注、热烈讨论的重大问题。从两宋开始,士大夫群体普遍盛行以“孔颜之乐”的人生境界相劝勉,而且他们也将“孔颜之乐”作为求圣之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的学术问题。
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思想史现象,即北宋那些著名的、有创造性的新儒家学者,他们进入圣门,似乎都是从体悟“孔颜之乐”开始的。他们对“孔颜之乐”境界的体悟,又总是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宋学学者群体中,几位有创始之功的学者,诸如范仲淹、胡瑗、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他们进入圣学门槛、建构道学学术,往往总是与“孔颜乐处”的问题思考相关。张载年少时喜谈兵,范仲淹告诫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范仲淹还将《中庸》作为领悟“名教可乐”的主要经典。胡瑗主讲太学时就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试诸生。道学宗师周敦颐,就是一个追求“孔颜之乐”的士大夫,史书记载他“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①周敦颐也以这一种人生境界启发、培养弟子,程颢、程颐兄弟十四五岁从学于理学开山周敦颐,周子教他们“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②程颢、程颐由“孔颜之乐”的人生追求而走向道德性命的义理建构,而成为理学的奠基人。
为什么“孔颜之乐”会成为这些宋学重要开拓者普遍关注、深入思考、引发创新的重要学术问题?这一学术问题的思想史意义在哪里?宋代士大夫对“孔颜之乐”的普遍追求,使他们往往将是否达到“乐”的境界作为得道与否的标志,表达的恰恰是这些承担着沉重政治责任、社会忧患的士大夫群体另一精神面向和思想追求。他们认定,从孔子、颜回到子思、孟子,都无不追求这种“心下快活”的人生境界,从个体存在、感性生命的角度来看,宋代士大夫同样会积极寻求爱莲观草、吟风弄月的快乐人生。宋儒认为,要达到这种精神上的“快乐”“气象”,离不开《四书》体系的学术资源,包括身心修炼工夫与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四书》学之所以在宋代兴起,恰恰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宋代士大夫寻求“圣贤气象”“社会忧患”“孔颜之乐”的精神需求,成为这一个时代能够表达时代精神的经典依据。
正因为作为政治精英的士大夫不仅仅是社会角色,还是感性个体,他们也会面临个人的是非、得失、生死问题,他们意识到,个人的忧、苦、烦、闷等消极情绪,其实源于自己对得失是非荣辱的偏执。那么,他们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个人的忧虑、烦恼等消极情感等问题?佛老之学提供的方案是以自己的内心平和为最高目标,故而主张通过精神修炼,以能够在面临是非、得失、生死问题时达到“不动心”“无情”“空寂”的精神状态与心理状态;但是,儒家思想的最高目标是以内圣与外王为一体,通过“正心诚意”的内圣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所以,儒家人格理想的“圣贤”“君子”,总是会充满家国情怀、天下牵挂。理学家胡宏谈到“圣人”时,认为他们和凡人一样有着丰富的个人情感与人生体验:“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有害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人以术为伤德也,圣人不弃术;人以忧为非达也,圣人不忘忧;人以怨为非宏也,圣人不释怨。”③他认为,圣人和众人一样,也是一个有着情、才、欲、忧、怨的个体存在,特别是儒家的圣贤、士君子必须承担起社会关切、家国情怀的忧患意识与外王事业,他们常常感到需要学习佛老的精神超越境界,面对人间不平、痛苦而自己却保持“不动心”“无情”甚至是“空寂”的精神状态与心理状态。所以,儒家的圣贤、士君子作为个体存在,他们需要有一套处理忧患、痛苦等不良情绪的修炼方法和精神境界。唐宋以来,儒家士大夫也一直在深入思考,如何化解个人的忧、怨等不良情绪,提升喜、乐等积极情感。
应该说,魏晋隋唐以来,佛道对这些问题均有过深入的思考和实践,其中佛教更是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随着魏晋隋唐佛教的大规模传入和发展,主张通过精神修炼而化解个体的不良情绪,对士大夫精神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进一步引导宋儒更加关切通过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以化解忧怨等不良情绪和提升喜乐等积极情感。所以,从个体存在来说,新儒家精神修炼的目标就是所谓“寻乐”“心下快活”,北宋儒林流行“寻孔颜乐处”,以及他们在修身中以是否“乐”为目标,即所谓“反身而诚,乃为大乐”。①这些所谓的“乐”,其实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忧、苦、烦、闷等各种消极情绪,从而达到身心的安泰、自在、舒展、洒落的超越境界,这一超越人生境界与天理论的人文信仰、哲学建构有关。宋儒罗大经说:“吾辈学道,须是打叠教心下快活。古曰无闷,曰不愠,曰乐则生矣,曰乐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饮水之乐,颜子有陋巷箪瓢之乐,曾点有浴沂咏归之乐,曾参有履穿肘见、歌若金石之乐,周程有爱莲观草、弄月吟风、傍花随柳之乐。”罗大经将修身目的确定为“教心下快活”,这既是一种“爱莲观草、弄月吟风、傍花随柳”的感性快乐,又是个人实现了对自己感性生命的超越,是考察一个人是否“得道”的重要标志。所以,宋儒的“寻孔颜乐处”,首先必须能够超越个人忧、苦、烦、闷的消极情绪,通过修身使自己“世间一切声色嗜好洗得净,一切荣辱得失看得破”②,这一精神超越的思想根基必然是哲学与信仰。
故而在两宋时期,《四书》学成为宋代士大夫特别关注、热烈讨论的核心经典。因为宋代士大夫特别在意是否达到“圣贤气象”的崇高境界,是否在承担重要政治责任的同时还能够具有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心境。他们通过阅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中的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圣先贤对“乐”的追求,进一步表达出自己对自由、自在、自得、自乐的向往与追求。理学开山祖周敦颐在《通书·颜子》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③在这里,周敦颐通过对《论语》中“颜子之乐”的诠释,认为这是一种“见其大而忘其小”,其实是指颜回达到了人与天道合一的精神境界。这一个“大”,恰恰是周敦颐在《太极图说》《通书》中建构起来的“太极”“诚”的宇宙本体。所以,这里所谓的“颜子之乐”,其实就是依据于“圣贤之道”而达到的崇高境界。譬如程颢也是通过挖掘《论语》《孟子》和《中庸》的思想资源,而建构这样一种“颜子之乐”的精神境界,他在描述仁者精神境界时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①仁本来是《论语》中的核心道德思想,而宋儒进一步将仁提升为一种哲学意义的形而上之本体。我们注意到,程颢建构的仁学本体论,其首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仁学提供一种知识学依据,更是为他们满足“孔颜之乐”的情感需求,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乃为大乐”提供一种安顿精神的依据。所以,为了达到“浑然与物同体”“反身而诚”的“乐”之心灵境界,程颢等道学家从早期儒家士人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对“乐”的追求中,找到了自己精神安顿的依据,并由此走向内圣之道的哲学建构。
三、宋儒的忧乐意识与内圣之道建构
从北宋开始,士大夫群体非常向往“圣贤气象”的人格理想,通过追求一种“孔颜乐处”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境界来体现这一种“圣贤气象”。宋儒强调“圣贤气象”的最重要标志不是外在的政治功业之“用”,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之“体”。这一“内圣”的心理状态、精神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从宋儒的学术论述和现实追求来看,“圣贤气象”往往体现为情感心理、精神情怀的忧与乐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宋儒之所以需要建构出一套有关内圣外王之道,其实是源于生活世界的忧乐人生,宋儒哲学建构的精神动力、价值源泉是他们的人文世界。
首先,宋儒之所以将自己的忧乐情怀归结为一种内圣之道,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前提与价值承担,即他们的忧乐应该是与天下苍生休戚相关的情怀。在宋儒看来,尽管一切人均有忧与乐的情感,而圣贤、士君子表达出来的忧与乐,应该是不同于常人的。普通常人的忧与乐可能是源于自己个人的利欲、需求与境遇,而圣贤、士君子的忧乐却总是直接关联人民幸福、国家安泰、天下和美。所以,北宋时期的许多儒家士大夫,总是将圣贤、君子的忧与乐与天下的忧与乐联系起来。欧阳修曾经谈到圣人的忧乐情感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众人之豫,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②欧阳修所推崇的“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正是强调圣人并不执着于个人的忧与乐,而是将天下的忧与乐看作是自己的忧与乐。北宋时期士大夫普遍推崇的道德精神与人格理想,在范仲淹著名的《岳阳楼记》中表达得更是特别充分,也就是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这一类思想观点,均是强调圣贤、士君子的社会担当、天下情怀的责任意识,要求士大夫要有君子、圣贤的社会责任和天下情怀,将个人的忧乐和天下的忧乐联系起来。这其实恰恰是宋儒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
但是,宋代士大夫不仅仅是强调要将个人忧乐与天下忧乐联系起来,我们进一步探究时还可以追问:宋儒为什么会以“忧”与“乐”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感描述“圣贤气象”?这两种不同类型情感分别体现出什么不同的人文意义?
两宋时期的儒家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进入历史舞台,他们总是对自己的政治责任、社会使命有强烈的承担意识,所以,他们对两宋的内忧外患十分敏感,他们追求现实的外王事业,完全有可能因此而沉溺于忧虑、痛苦、烦恼等消极情绪之中而难以自拔。从宋儒的思想言论和生活实践中会发现,当他们在追求外王事业的过程中,必然会承担社会之苦、国家之难的沉重压力,故而忧患必然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焦点和重心。许多现代学者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儒家人格理想、中国文化特征是忧患意识。但是,为什么宋代士大夫总是不得不经历这样的人生磨难和生命悲苦?宋儒并不相信我们的生活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极乐世界,他们不能够依赖因果报应、上帝赏罚的宗教信仰来解决、化解他们面临的严峻精神问题。要如何才能够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以回归到生命本质的心灵平静、精神愉悦、身心安泰?
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一旦落实在世俗的生活世界,他们也必须处理个体存在、感性生命具有的消极情感,他们当然希望回归心灵平静、精神愉悦、身心安泰的生命状态,并以此作为根本精神导向,这时候,“乐以忘忧”“曾点之志”“乐是心之本体”等思想观念就成为他们情感世界的追求和目标。可以说,宋代新儒家之所以追求“孔颜之乐”,恰恰在于他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精神向度,就是解决他们在社会关切、家国情怀中产生的忧患问题。他们之所以需要寻乐,是根源于他们从事外王事业必然面临的入世之忧;而他们也需要化解、超越内心沉重的忧患,故而迫切需要一种超然之乐。所以,“圣贤气象”既能够凸显宋代士大夫的责任意识,同时也能够表达士大夫的超然境界。许多现代学者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儒家人格理想、中国文化特征是乐的精神。所以,宋代士大夫“圣贤气象”的精神追求,既可能体现为“忧患意识”,更应该体现为“孔颜之乐”。宋代士大夫并不希望永远陷于“忧患”之苦,也不希望溺于一己之“乐”,故而只能够是兼顾社会责任的忧患意识与个体生命本真的乐天精神,最终达到一种忧乐圆融的精神境界与理想人格。
宋儒不仅仅是拥有强烈的忧乐情怀,还以此忧乐情怀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心性哲学。人们往往认为哲学是理性智慧的产物,而宋儒“致广大、尽精微”的高深哲学为什么会与“忧”与“乐”的情感世界相关联?
这时,我们就来到理学“内圣之道”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核心。宋代士大夫在积极入世中为什么会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他们又为什么能够在忧患处境中寻“孔颜乐处”?其实两者均与“士志于道”的精神信仰有关。儒家士人的信仰是道,但恰恰是魏晋隋唐以来,儒家信仰之道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许多有事业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士大夫往往是出入佛老,在佛道的宗教信仰和空无哲学中寻求精神宁静。宋儒必须为自己的“忧患意识”“孔颜乐处”找到信仰、哲学的依据,这样他们才能够超越“忧患意识”带来的困扰,才能够真正实现“孔颜之乐”的精神升华。所以,《周易》的宇宙哲学成为宋儒建构信仰依据、哲学依据的重要典籍。
这里举宋儒解释《周易》中《困卦》的一个例子,能够使我们看到宋儒的宇宙哲学与忧乐意识的密切关系。《困》似乎象征作为政治主体的两宋士大夫面临的历史困局,他们一旦进入现实世界就不能不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但是,宋儒希望一切“志于道”的圣贤、士君子,能够在困局与忧患中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范仲淹对于《困卦》的“泽无水”,他主张“困于险而又不改其说,其惟君子乎,能困穷而乐道哉”。①胡瑗也是如此:“惟君子处于穷困,则能以圣贤之道自为之乐,又能取正于大有德之人以为法则,故所行无不得其道,所以获吉而无咎矣。”②程颐进一步强调:“大人处困,不唯其道自吉,乐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③“君子当困穷之时……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④可见,范仲淹、胡瑗、程颐在诠释《困卦》的卦义时,均强调两点:其一,任何穷塞祸患的困境均不可动摇士君子坚守道义、不改志向的决心;其二,必须要在“君子困穷”的境遇中坚持以道自乐。可见,宋儒对《困卦》卦义的阐发,已经深入到理学内圣之道的核心问题,即如何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解决多灾多难的现实困局。程颐认为:“以卦才言处困之道也。下险而上说,为处险而能说,虽在困穷艰险之中,乐天安义,自得其说乐也。时虽困也,处不失义,则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时当困而反亨,身虽亨,乃其道之困也。”⑤君子虽然处于困穷艰险的时势中,他无法获得个人命运的亨通,但是他仍然应该通过坚守道义、乐天安义并自得其乐,这就是所谓的“孔颜之乐”。
为了坚定自己的“乐道”精神,宋儒重新建构了内圣之道,即建立一套以无极太极、理气道器的宇宙论为哲学基础的心性之学。宋儒建构了天人一体的心性之学与居敬穷理的修身工夫,他们坚持一切人均可通过心性修养而获得“圣贤气象”,这是宋代士大夫能够获得精神上的自我救赎的唯一可能。宋儒特别是在《四书》的经典文本中,找到了他们迫切需要的如何能够达到忧中有乐、乐不忘忧、忧乐圆融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的哲学依据。
宋学本来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宋儒当然希望在内圣之道和外王之道两方面均有进一步拓展;但在宋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宋儒越来越意识到内圣的根本性,特别是宋代士大夫的忧乐情怀和对理想人格的向往,故而逐渐将内外兼顾的宋学转型为以内圣为主导的性理之学。什么是“性理之学”?元代理学家吴澄说:“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①当一个人体认到“吾之性”即是“天地之理”,由自我的内在心性可上达宇宙之理,他承担的“忧患意识”就具有了崇高的精神价值,而他的“孔颜之乐”才能够提升到一种真正的精神超越境界。所以,追求内圣之道的宋儒更加热衷于形而上维度的思想建构,对理气、道器、人心道心、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问题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们将《周易》的宇宙哲学与《四书》的人格哲学结合起来,建立起形而上性理与形而下生活紧密相连的内圣之道。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历代对《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
——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
乐爱国
《论语·子路》载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明显是就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而言。然而,当今学者的解读,大都以西周末史伯批评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并且讲“和而不同”以及春秋末齐国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将其中的“和”解读为“和谐”。李泽厚《论语今读》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君子和谐却不同一,小人同一却不和谐。”①同时还特别强调:“‘和’的前提是承认、赞成、允许彼此有差异、有区别、有分歧,然后使这些差异、区别、分歧调整、配置、处理到某种适当的地位、情况、结构中,于是各得其所,而后整体便有‘和’——和谐或发展。”②问题是,能够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吗?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果这里的“和”解读为“和谐”,是否意味着君子与小人也应当“和谐”?在孔子那里,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能够“和谐”吗?孔子讲“道不同,不相为谋”,讲的就是君子与小人不应当“和谐”。可见,孔子之所以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中还需要做更多、更为深入的解读。
一、汉唐时期的两种不同解读
《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仅讲君子与小人在道德上相互对立,而且讲“和而不同”“同而不和”,讲“和”与“同”的区别。关于“和”与“同”的区别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国语·郑语》记西周末史伯对周幽王“去和而取同”的批评。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③这里将“和”与“同”区别开来,强调“以多物,务和同”,讲由“多”而“和”,反对“同”而“一”,讲“和而不同”,无疑具有“和谐”之意。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是先王“和而不同”,而不是讲君子“和而不同”。
又据《晏子春秋》载,春秋末齐国晏婴与齐景公论“和”与“同”的区别,说:“和如羹焉,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①应当说,晏婴讲“和如羹”而反对“专一”,与史伯讲先王“和而不同”,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对于“和”与“同”的区别的讨论,其中的“和”也具有“和谐”之意,且同样只是讲先王“济五味、和五声”;至于所谓“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其中的“君子”应当是指君王。
东汉荀悦《申鉴》推崇《晏子春秋》所谓“和如羹”,并引出《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说: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咸甘苦不同,嘉味以济,谓之和羹;宫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谓之和声。臧否损益不同,中正以训,谓之和言;趋舍动静不同,雅度以平,谓之和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一声,谁能听之?’《诗》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无言,时靡有争。’此之谓也。”②这里讲“君子食和羹”,“纳和言以平其政”,所谓“君子”指的是君王;接着又讲《论语》的“君子和而不同”,似乎是把《论语》“君子和而不同”中的“和”解读为不同事物的相互和谐。
另据《后汉书·刘梁传》载,刘梁著《辩和同之论》,说:“君子之于事也,无适无莫,必考之以义焉。得由和兴,失由同起。故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春秋传》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剂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③显然,这里的解读也是以晏婴讲“和如羹”解《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和”即“和谐”。
应当说,无论是史伯讲“和而不同”,还是晏婴讲“和如羹”,都是就先王而言,要求君王讲“和谐”,并不涉及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如果据此解读《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将其中的“和”解读为“和谐”,强调“和”的价值而否定“同”,很可能会消解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不合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蕴含的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之意。
与此不同,三国时何晏《论语集解》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南北朝的皇侃《论语义疏》疏曰:“和,谓心不争也。不同,谓立志各异也。君子之人千万,千万其心和如一,而所习立之志业不同也。……小人为恶如一,故云‘同’也。好斗争,故云‘不和’也。”①后来,北宋的邢昺《论语注疏》疏曰:“此章别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则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②应当说,何晏、皇侃以及邢昺的解读,从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讲“和”与“同”,突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对立,不同于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对于“和谐”的推崇,较为合乎《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意。
然而,何晏、皇侃等的解读,在“和”与“同”的概念界定上,尚存在着某些不自洽。何晏《论语集解》讲“和”,把君子之“和”解读为君子之心的“和”,把小人之“不和”解读为小人“各争其利”;讲“同”,则把君子之“不同”解读为君子“所见各异”,把小人之“同”解读为小人“所嗜好者同”。皇侃《论语义疏》明确把君子的“和”“不同”与小人的“同”“不和”分别开来界定:就君子而言,“和,谓心不争也。不同,谓立志各异也”;就小人而言,“小人为恶如一,故云‘同’也。好斗争,故云‘不和’也”。也就是说,在何晏、皇侃等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中,无论是“和”的内涵,还是“同”的内涵,都不是统一的。
由此可见,汉唐时期对于《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解读,既有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而将其中的“和”解为“和谐”,实际上消解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也有何晏、皇侃等的解读,突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但尚没有就“和”与“同”的概念内涵做出自洽的解读。
二、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③这里从心性层面将“和”解读为“无乖戾之心”,将“同”解读为“阿比之意”,也就是认为君子“无乖戾之心”,因而无“阿比之意”;小人有“阿比之意”,因而有“乖戾之心”。显然,这样的解读,与何晏、皇侃等的解读一样,突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重要的是,朱熹的解读还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义利联系起来,认为君子尚义,所以“和而不同”,小人尚利,所以“同而不和”。朱熹还说:“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盖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会这一个公当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个私意,故虽相与阿比,然两人相聚也便分个彼己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纷争而不和也。”①也就是说,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不只在“和”与“同”的区别,更在于“公”与“私”的对立,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区别。朱熹门人辅广对《论语集注》引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做了讨论,说:“尹氏本意,虽只是以义利二字说不同、不和之意,然细推之,则君子之于事,唯欲合于义,故常和。然义有可否,故有不同;小人徇利之意则固同矣,然利起争夺,安得而和?”②显然,辅广进一步强调君子尚义,所以“和而不同”;小人尚利,所以“同而不和”。
与何晏、皇侃等的解读相比,朱熹的解读明显具有两大优势:其一,正如以上所述,何晏、皇侃等的解读尚没有就“和”与“同”的概念内涵做出自洽的解读,与此不同,朱熹的解读特别重视并明确给出了对于“和”与“同”的概念的统一界定;其二,何晏、皇侃等的解读讲君子与小人具有“和”与“不和”、“不同”与“同”的对立,但由于没有就“和”与“同”的概念内涵做出自洽的解读,这样的对立是含混的,与此不同,朱熹的解读对“和”与“同”的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统一界定,并进一步强调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对立,突出了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对立,因而是对何晏、皇侃等的解读的发展和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不仅从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的角度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而且明确反对依据晏婴“和如羹”所做的解读。朱熹《论孟精义》收录了吕、杨、侯氏的解读:
吕曰:“和则可否相济,同则随彼可否。调羹者五味相合为和,以水济水为同。”
……
杨曰:“五味调之而后和,而五味非同也。如以咸济咸,则同而已,非所以为和也。君子有可否以相济,故其发必中节,犹之五味相得也。小人以同为说,犹之以咸济咸耳,尚何和之有?”
侯曰:“和非同也,和则虽有可不可之异,济其美而已,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同非和也,同恶相济,如以水济水,安能和哉?故曰:‘小人同而不和。’”③
对此,朱熹《论语或问》说:“吕、杨、侯氏说,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则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状而言,似不可引以为证也。盖此所论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协恭,而无乖争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无阿谀党比之风。若小人则反是焉。此二者,外虽相似,而内实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状之隐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轨,非圣人不能究极而发明之也。……如此说,则君子之心,无同异可否之私,而惟欲必归于是;若晏子之说,则是必于立异,然后可以为和而不同也,岂非矫枉过直之论哉!”①这里对以晏婴“和如羹”来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出了批评,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朱熹看来,晏婴所谓“和如羹”,是“就事而言”,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就“君子小人之情状而言”,是就人的内在道德品质而言,所以“不可引以为证”。晏婴强调听取不同意见,所谓“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又讲“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济也”。然而,可否相济,只是“就事而言”,并非就道德上的君子小人而言,换言之,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做到可否相济,而在于内在道德品质的截然相反。
第二,朱熹认为,君子小人“外虽相似,而内实相反”,所以对于“和”与“同”的界定,不可只是从事物表面上看,而应当从人的内在心性看。朱熹《论语集注》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又进一步讲公私义利,以此把君子与小人对立起来;《论语或问》则讲“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协恭,而无乖争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无阿谀党比之风。若小人则反是焉”。显然,对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朱熹的解读强调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对立,而以晏婴“和如羹”为依据的解读则只是讲君子与小人在做事上的“和”与“同”的区别。
第三,朱熹认为,对于各种不同的事物,君子应当“必归于是”,而晏婴“和如羹”要求“必于立异,然后可以为和而不同”,过多讲不同事物之“和而不同”,属于“矫枉过直之论”。朱熹《论语集注》注“道不同,不相为谋”,曰:“不同,如善恶邪正之异。”②并且认为,“君子小人决无一事之可相为谋者也”。③应当说,在朱熹的话语中,天理、人欲、公私、义利,乃至君子小人,正如邪正、善恶,都是对立的,而不可“和而不同”,如果用晏婴“和如羹”来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实际上包含了对于小人的“和而不同”,必然会消解君子与小人的对立,那么君子就不是与小人对立的君子,也就不成其为君子,因而就会陷于悖论,所以用“和如羹”解“君子和而不同”是不可能的。
三、朱熹之后的讨论
朱熹解《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心性层面将“和”解读为“无乖戾之心”,将“同”解读为“阿比之意”,是就人的道德品质而言,并非“就事而言”。然而,人的道德品质与做事又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朱熹之后,有不少学者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既从心性的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又讲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
元代陈天祥《四书辨疑》不满足于朱熹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的解读,说:“和则固无乖戾之心,只以无乖戾之心为和,恐亦未尽。若无中正之气,专以无乖戾为心,亦与阿比之意相邻,和与同未易辨也。中正而无乖戾,然后为和。凡在君父之侧,师长、朋友之间,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可者献之,否者替之,结者解之,离者合之,此君子之和也。而或巧媚阴柔,随时俯仰,人曰可,己亦曰可,人曰否,己亦曰否,惟言莫违,无唱不和,此小人之同也。晏子辨梁丘据非和,以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此论辨析甚明,宜引以证此章之义。”①陈天祥的解读试图在朱熹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的基础上,引入“中正之气”,并进一步以晏婴的“和如羹”区别君子之和与小人之同,实际上是把朱熹的解读与晏婴讲“和如羹”结合起来。
明代程敏政也解释说:“和是无乖戾之心,同是有阿比的意思。孔子说君子的心术公正,专一尚义,凡与人相交,必同寅协恭,无乖戾之心。然事当持正处,又不能不与人辩论,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的心术私邪,专一尚利,凡与人相交,便巧言令色,有阿比之意。然到不得利处,必至于争竞,故曰‘小人同而不和’。”②后来王夫之作了训释,说:“君子以义为尚,所与共事功者,皆君子也。事无所争,情无所猜,心志孚而坦然共适,和也。若夫析事理于毫芒,而各欲行其所是,非必一唱众和而无辨者也,不同也……小人以利为趋,所与相议论者,小人也。以权相附,以党相依,依阿行而聚谋不逞,同也。乃其挟己私之各异,而阴图以相倾,则有含忌蓄疑而难平者也,不和也。”③应当说,程敏政、王夫之的解释,合乎朱熹《论语集注》之意。
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引述何晏所言:“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并指出:“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义者宜也,各适其宜,未有方体,故不同。然不同因乎义,而非执己之见,无伤于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务于是,则有争心,故同而不和。此即君子、小人之异也。”①显然,这里以义、利讲“和”与“同”,并由此从心性的层面讲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这与朱熹《论语集注》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引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是相通的。在讲君子与小人相互对立的基础上,刘宝楠《论语正义》又讲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的“和如羹”,从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引申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
清末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和康有为《论语注》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出一辙,都是先引述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的“和如羹”,然后引申出君子与小人的相互对立。简朝亮说:“由是言之,和则不乖戾,同则惟阿比,其义不昭然乎?”②康有为说:“盖君子之待人也,有公心爱物,故和;其行己也,独立不惧,各行其是,故不同。小人之待人也,媚世易合,故同;其行己也,争利相忮,不肯少让,故不和。”③这明显更为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
直到现代钱穆《论语新解》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故不能和。或说:和如五味调和成食,五声调和成乐,声味不同,而能相调和。同如以水济水,以火济火,所嗜好同,则必互争。”④显然,这样的解读都是从朱熹的解读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出发,并进一步引申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
四、余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于《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既有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而将其中的“和”解为“和谐”,又有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以及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朱熹之后的学者大多既从心性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又由此引申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应当说,在这些解读中,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并进一步讲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对立,发展并完善了何晏、皇侃等的解读,超越了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的解读。
首先,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是就先王而言,以此为依据解读《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将圣王与君子混为一谈。据《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也就是说,君子首先在于“修己以敬”,如果在“修己以敬”的基础上做到“修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和谐,就是尧舜也不容易做好。显然,在孔子看来,君子与圣王是有区别的。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讲的是圣王“和而不同”,而不是君子“和而不同”,因而不能用于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此不同,朱熹的解读强调的是君子的内在品质,更为合乎《论语》讲君子“修己以敬”,并与圣王有所区别之意。
其次,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是就做事而言,而《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就做人而言,做事与做人不可混为一谈。《论语》讲君子与小人,首先是就人的内在品质而言,《论语·宪问》讲“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与此不同,史伯讲“和而不同”,强调“以他平他”,反对“以同裨同”,又讲“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显然是就做事而言;同样,晏婴讲“和如羹”,讲不同事物的“相成”“相济”,反对“以水济水”,也是就做事而言。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实际上是将做事与做人混为一谈,而朱熹的解读揭示君子“和而不同”的内在品质,更为合乎《论语》的君子之意。
再次,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由于只是就先王而言,就做事而言,因而不是就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小人而言,史伯以“和而不同”批评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并不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所以,以此为依据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必定会带来对于君子与小人对立的消解,甚至会陷于以“和”来解读道德上君子与小人的对立所引起的理论矛盾。与此不同,较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更为完善的朱熹的解读,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从心性层面强调了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因而更为合乎《论语》讲君子与小人相互对立之意。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荻生徂徕解《论语》,强调其中的“君子”“小人”主要是“以位言”。他说:“君子者,在上之称也。……君者治下者也,士大夫皆以治民为职,故君尚之子以称之,是以位言之者也。虽在下位,其德足为人上,亦谓之君子,是以德言之者也。”“小人,亦民之称也,民之所务,在营生,故其所志在成一己,而无安民之心,是谓之小人,其所志小故也。虽在上位,其操心如此,亦谓之小人;经传所言,或主位言之,或主德言之。所指不同,而其所为称小人之意,皆不出此矣。”①在荻生徂徕看来,《论语》中的“君子”为上层官员,“小人”为下层百姓,“君子”与“小人”是相须关系,而不是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他的《论语征》以晏婴的“和如羹”解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反对何晏以“君子心和”、朱熹以“无乖戾之心”解其中的“和”,说:“何晏曰‘君子心和’、朱子曰‘无乖戾之心’,皆徒求诸心而失其义焉。盖古之君子学先王之道,譬诸规矩准绳,故能知其可否。苟不知可否之所在,其心虽和乎,乌能相成相济,如羹与乐乎?亦可谓之同已。”①他认为何晏讲“君子心和”、朱熹讲“无乖戾之心”,并非“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义,而君子之为君子在于知道事之可否,而使之达到相互和谐。问题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并不在于能否知道事之可否,讲事物之和谐,而在于内在的心性道德。
《论语》中的“君子”“小人”,确有一些并不是讲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②,但是,由此而像荻生徂徕那样,以为《论语》中的“君子”“小人”大都不是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尤其是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的“君子”“小人”并非就道德上相互对立的君子与小人而言,或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讨论。
当今不少学者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将《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的“和”解为“和谐”,并将“和谐”解为“由‘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所构成的‘普遍和谐’”,又进一步认为“儒家关于‘和谐’的观念是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作为起点的”。③这里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与人之外部的和谐统一起来,并以“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为起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实际上就是朱熹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言“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今人所讲的“普遍和谐”,实际上正是朱熹之后不少学者既讲君子之“和”在“无乖戾之心”,因而无“阿比之意”,又讲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的“和如羹”,引申出人之外部事物的和谐,而朱熹讲“无乖戾之心”,因而无“阿比之意”,正是这一“普遍和谐”的起点。由此可以看出,朱熹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不仅更为合乎《论语》之意,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6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皇极与教化——朱子、象山皇极说新论
许家星
《洪范》篇在《尚书》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历来得到学者高度重视,近来更成为儒家政治哲学讨论的热门话题。目前学界对朱、陆“皇极”解的认识大体有两种观点:一是余英时、吴震、丁四新、王博等所持的政治文化范畴说,此为主流意见。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专辟“皇权与皇极”章,强调理学家通过对皇极概念的重新解释来表达关于政治秩序的新理念。①吴震大体认同余氏之说,认为“皇极诠释之争不仅是概念问题,更是当时的政治问题”。②丁四新则通过探讨以五行畴和皇极畴为中心的《洪范》政治哲学,从皇极本意的角度批评朱熹充满理学家趣味的解释并未切中其的。③王博肯定了皇极是古典时代政治思想的集中表达,着力讨论了与皇极密切相关的太极、无极。④二是陈来所持的经典解释说,他力排众议,认为把朱子皇极解当作一个政治文化范畴虽可成立,但并非朱子主要用心所在。对朱子而言,“皇极”更多的仍是一个学术思想、经典诠释问题。“朱熹的皇极讨论,不会只是针对政治的发言……‘论时事’和‘求训解’在朱子是不同的,这一点还是要加以分别的。”⑤
上述两派之说皆言之成理。然朱陆皇极之解,无论是政治问题说或经典解释说,其实皆不离“德性教化”这一主旨,政治是不离教化的政治,解释则以工夫教化为指归。朱陆皇极解皆再三强调了皇极“正心”“保心”的精神教化意义,皆推崇先知觉后知的以上化下之教,彰显了儒家哲学以教化为根本的精神特质,此是二者之同。然在落实教化的具体途径上二者则各有特色。朱子对皇极提出新解,认为皇极指君王以一身树立大中至极之标准,从而具有圣人般的德行,成为天下效仿之对象,此解具有责君行道的意义。象山则恪守以大中解皇极的传统之义,通过对德福关系的新解,突出了对民众的保心之教,以期达到承流宣化的效果,体现了化民行道的思想,此是二者之殊。概言之,朱陆皇极解皆认可责君上行道与化下民行道两种教化途径,不过因针对对象之异,而各自突出了化君与化民。二者相较,朱子皇极解更为复杂精密,其皇极思想有一明显的变化,反映了他晚年对教化、立极思想的重视。
一、“民视君以为至极之标准而从其化”
朱子皇极解经过反复沉潜而成,留下了初本与改本之别;朱子对自家之解充满自信,认为此解足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之解,特重文义训释,而归本于立人极的德性教化。以下从皇极新义、民从上化、立极于上、上之化为皇极、以身立极、为治心法、极中之辨七个方面依次论述之。
(一)“四外望之以取正”。朱子一反传统的皇极为大中之义,而主张君王树立至极标准,以为四方取正效法之义,体现了以德立极,以极化民的教化观点。①《皇极辨》中“化”字出现6次,包括“观感而化”“从其化”“下之从化”“所以化”“上之化”(2次),“教”字出现3次,反映出朱子着眼“下从上化”的理念。朱子说:
故自《孔氏传》训“皇极”为“大中”,而诸儒皆祖其说,余独尝以经之文义语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盖皇者,君之称也;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诗》所谓“四方之极”者(按:初本无此句),于皇极之义为尤近……既居天下之至中,则必有天下之纯德,而后可以立至极之标准……语其孝,则极天下之孝,而天下之为孝者莫能尚也,是则所谓皇极者也。由是而……考其祸福于人,如挈裘领,岂有一毛之不顺哉……《洪范》之畴所以虽本于五行,究于福极,而必以皇极为之主也。②
此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批评皇极旧说,表达新解,提出皇极是指君王居中,因其纯德至极,而为天下极致准则,故为四方取法。第二层指出君王树立至极之标准并非易事,须有天下至纯之德方可,具体落实为由五行五事以修身,八政五纪以齐政,方能卓然立极。特别以仁、孝为例,强调只有做到极致,方是皇极。①第三层认为,在做到至极基础上,方能顺天应人,合于鬼神而审乎祸福。《洪范》九畴虽以五行为开端,以福德关系为究竟,却须以皇极为根本来统帅之,道出了皇极为《洪范》之本的观点。新解突出了“四外望之以取正”的上行下效的德化意义,其根本宗旨就是要求人君通过修身以树立一个天下瞻仰效法的道德典范,从而达到教化天下的效果。
此处定本与初本差别甚大,二、三两层义皆为初本所无,改后更显周全严密。首句“余独尝以经之文义”句初本为“予尝考之”,“独”字之补,颇显朱子自负之意;“经之文义”之补则见出朱子紧扣章句文本表达创见的治学风格。
(二)“使民观感而化焉”。紧接“皇极”的是“皇建其有极”,朱子解为人君以己之一身为天下树立至极标准。“皇建其有极云者,则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极之标准于天下也。”树立这个“至极标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民观感而化”。君王的“建极”,是一个自利而利他的行为:建极之君因自身光辉的德行而享有长寿、富贵等五种幸福,而这种五福聚集所带来的光环又吸引了民众,民众在对建极之君德福一体的崇高道德典范之观摩中,获得内心的感动和灵魂的教化,这就是建极之君将自身所聚之福广布于民众之中的利他行为。此中君民之福传递授受之关键有二:一是君王必须能“建极”;二是民众必须能“观感而化”,即它建立在君民之间道德感应、德行转化的基础上,否则这种赐福于民是不可实现的。
人君能建其极,则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观感而化焉,则是又能布此福而与其民也。②
朱子将“建极”与“敛福”联系起来,强调德福一致,合乎《中庸》大德必得之说。又把“感化”与“赐福”相关联,认为接受德教者即是接受“福报”,被道德感化之人,即是有福纳福之人。此皆体现了朱子以德论福的德福观。应提出的是,“使民观感而化”,初本为“推以化民”,“推”字有用力勉强之意,改本更强调了感化之自然无形,同于《论语集注》“道之以德”解的“观感而兴”的潜默之化。
不仅是君“布福于民”,民同样会“还福于君”,朱子在“锡汝保极”解中提出:
夫民视君以为至极之标准而从其化,则是复以此福还锡其君,而使之长为至极之标准也。③
所谓“保极”,指民众以君王为至极标准而顺从其教化,此即还君王所布之福于君之身,使君永为至极标准,可谓“常建其极”。民之反哺、还福其君的实质是以君王至极之德为标准,顺从君之德化,使自身亦拥有同样之德。朱子指出“惟皇作极”表达的亦是君王作极的典型示范意义,对于民之感化向善具有关键效果。“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为至极之标准也。”①朱子还从全篇整体指出“皇建其有极”以下皆围绕君王修身立极,以观天下,天下自然而化之义展开。“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极’以下,是总说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标准以观天下,而天下化之之义。”②
(三)“立极于上而下之从化”。朱子于“皇则受之”句特别阐发了立极教化思想。他认为,君王立极于上,则下民受其感应从其教化,自然有快慢深浅之别,对虽有不完全顺从教化但却未过于违背者,仍当宽容接受之。他说:
夫君既立极于上,而下之从化,或有浅深迟速之不同……其或未能尽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当受之而不拒也。③
学者多注意太极与皇极关系,于“立(人)极”似罕见论及。《皇极辨》中“立极”出现3次,分别为“君既立极于上”“圣人所以立极乎上”“人君以身立极”,意指君王当以圣人为标准来要求自我,做到“王而圣”“君为师”“政即教”的合一。朱子在此将“成圣”作为君应有状态和必要素质,表达出君应为圣的儒家政治要求,此不仅关乎君王一身之资质,实系乎天下治理之根本。
立极内含继天、立人极、立教三层含义。作为君王至极标准的极有一个超越的来源,那就是继天而来,极的根源其实在天。天在朱子看来,其实为“理”,故立极的实质就是要君王成为天理的体现,成为圣人,只有圣人才做到了“浑然天理”。故此处“立极于上”通乎朱子《学庸章句序》“继天立极”说,《大学章句序》提出伏羲等上古圣神是“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故能继天命而立人极。④《中庸章句序》再次表达伏羲等上古圣神是“继天立极”者,将之与“道统”联系起来,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立极”其实是“立人极”的简称,《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朱子指出,圣人即是“太极之全体,一动一静,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圣人就是太极在人道上的表现,就是人极。皇极、太极、人极三个概念互涵相通。太极图自开篇言阴阳造化,中间言人禀受造化之灵,最后以圣人立人极结束,昭示圣人得乎太极全体,而合乎天地,此前后恰好构成一个首尾相因,脉络贯通的整体,显出人极乃太极说内在结穴所在,体现出太极图即天道而言人道的天人贯通。前贤已注意朱子“皇极”是太极论的自然展开,但《皇极辨》并未出现“太极”,“立(人)极”则出现多次。盖皇极要求人君建立其极,是为民立极,人极的内容如朱子弟子方宾所言,即是仁义之道,“而仁义礼智所以立人极也”。①朱子曾要求孝宗放弃功利之心,罢免求和之议,通过对仁义三纲之道的体验扩充,来“建人极”,树立作为君王应有的天下道德表率,如此方是重振国事的关键。“而以穷理为先,于仁义之道,三纲之本,少加意焉,体验扩充,以建人极。”②人极作为普遍永恒而又日用常行的人伦之道,具有大中至正的极则意义。圣人以仁义中正为立人极,其实即是仁义礼智,不过中正较礼智更亲切而已。“圣人立人极,不说仁义礼智,却说仁义中正者,中正尤亲切。”③
立极与立教密不可分,立极是树立至极之准则,是立教之前提,立教则是立极的落实和展开。朱子多次将“立极”与“立教”联系起来,早在《杂学辨》中即认为“修道之谓教”就是“圣人所以立极”所在。④《君臣服议》亦言宋朝开国确定的三年丧制具有立极导民之效,“则其所以立极导民者,无所难矣。”《大学章句序》指出,继天立极的圣人通过设立司徒典乐等官职开展对百姓的礼乐教化,以复其性。儒家之道其实就是“立极”之道,天生圣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圣人通过继天立极,来修道立教,教化百姓。“问继天立极……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⑤
(四)“上之化也,所谓皇极者也”。朱子在“惟皇之极”句的解释中提出了民众“革面从君”与“以君为极”的思想。
夫人之有能革面从君,而以好德自名,则虽未必出于中心之实,人君亦当因其自名而与之以善。则是人者,亦得以君为极而勉其实也。⑥
若有人能受君之感化而改除旧习,从君之教,尽管其心出于好名而诚意不够,但君王亦当因任其好名之心而善待勉励之。此显示圣人设教“至宽至广”“与人为善”“一视同仁”的广大包容,合乎夫子“有教无类”,孟子“归斯受之”的教化理念。
朱子对“凡厥正人”句的诠释,强调了君王立极至为严密,而待人极为宽广的原则。
是以圣人所以立极乎上者,至严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宽至广。虽彼之所以化于此者,浅深迟速……长养涵育,其心未尝不一也。①
朱子首先阐发了《论语》“富之教之”及《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先富后善的教化原则,要求君王先安顿民众生活,否则难以教化诱导民众于善。如民众因生活所迫陷于不义再加以教化,则事倍功半,无济于事。此体现了朱子视民生保障为教化前提的立场。强调对作为立极施教的君王,应给予最为严格细密的要求;但对被教化者则又应持“至宽至广”的宽大包容原则,面对民众接受教化效果所存在的深浅快慢之差异,应始终抱有抚育涵养之心。这一对在上者严格与对在下者的宽容体现了差别化视角。
朱子对“无偏无陂”句的解释突出了在上之化的意义。他说:
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从乎上之化,而会归乎至极之标准也……王之义、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谓皇极者也。②
天下之人皆不敢徇一己私情而自觉顺从于王者教化,会归于君王所立至极之标准。通过王者以自身所践行之正义、正道、正路教化民众,化除人之私欲而使之归于荡荡平平正直之则,此义、道、路作为在上之教化,即是皇极。可见朱子皇极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在上之化的教化之道。
(五)“人君以身立极而布命于下”。朱子对皇极章最后三句的诠释,着重突出君王立极布命的身教思想,并将立极、伦常、天理、降衷贯通为一。一方面,作为施行教化者的人君,应当“以身立极”,人君所发布的天下教令即是天理伦常和上帝降衷之体现。
则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极而布命于下,则其所以为常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异乎上帝之降衷也。③
此“以身立极”即“继天立极”,对君王而言,其身本自继天而来,德性上应实现与天为一,才有资格、有能力成为万民取法的教化者。初本“立极”本是“为表”,改后突出了“立极”这一中心主旨。“天之理”初本为“循天之理”,删此“循”字,表明立极之君所立之伦常教化,即是天理,突出了君王作为立极者的自我立法,与理为一的神圣法则意义。
朱子强烈责求作为立极者的君王,理应成为纯乎天理的圣人。对受教的天下之民,要求接受君王教化之命,恪守遵行,以不偏离天理伦常而直接感化于君王德教之光华。
朱子又解“天子作民父母”句为:
则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极之标准,所以能作亿兆之父母而为天下之王也。不然,则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统御人群,而履天下之极尊矣。①
“人君能立至极之标准”初本为“能建其有极”,改本紧扣“立极”而论,显豁了“皇极”的“立至极标准”义。“亿兆”初本为“民”,改为“作亿兆之父母”正同乎《大学章句序》“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亦证明朱子《皇极辨》始终着眼于君师复性之教。“首出庶物,统御人群”,初本为“建立标准,子育元元”,改为《乾卦》“首出庶物”及“统御”后,强调了君王首先应该履行作为一国之首应有的仪范天下之责,如此才能“统御人群”。即他不仅在地位上是万人之上,更应该在德性上“首出庶物”,做到“中心安仁”。此是再次扣紧“立人极”而论。②表明天子之所以为天子,关键在“德”而非位。仅有位无德者,不足以履天子之位。《中庸》认为,德位分离者,皆不能制作礼乐以行其教化,只有德位兼备的圣人天子方可制作礼乐。
(六)“此是人君为治之心法”。朱子还以“心法”论定“皇极”,彰显了“皇极”作为道的意义,也揭示了宋代“皇极”畴取代五行畴的原因。
问:皇极。曰:此是人君为治之心法。如周公一书(按:指《尚书·周书》),只是个八政而已。③
朱子将皇极与八政比较,认为皇极才是人君治国心法,而《周书》不过是讨论具体政治措施之作,仅是“为治”,皇极才是更深层的决定“为治”的“心法”,此心法即是道之义。它直接作用人君之心,实非八政可比。皇极作为心法的意义在于:君王能以极为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成为天下民众之道德标准、行为表率,使得民众皆有以兴起并效法之,以成就修身化民之效。君王能否成为天下所取法的对象,事关天下治理成败,故君王之心实为天下根本之要。可见朱子的皇极新解,与他格君心的道德教化思想一致。“心法”在朱子语境中,具有不同所指,但皆无外乎修身内圣与治国外王义,具有统率本体与工夫的道统意义。皇极心法与允执厥中、克己复礼之心法一脉相承,不过表述有所不同而已。
君王如能通过修身工夫皇建其极,那就是把握了政治根本。因天下大事,皆无外乎是从君王一心之法流淌而出,如其心正大光明,则其事自然正大光明。“古人纪纲天下,凡措置许多事,都是心法。从这里流出,是多少正大!”①皇极心法说的意义表明朱子的道统论并非仅限于狭义的内在心性之学,而实际亦包含了治平天下的外王之道。
(七)中、极误解与“修身立政”。朱子对皇极章的逐句解释,体现了其“皇极”思想实是以责君立极化民为中心,并未涉及任何具体时政。此诚如陈来先生所言,朱子的皇极解首先或者说主要是一个经典命题的解释问题。朱子之解可能涉及政治的部分仅作为一段补充性质的短文被置于正文之后,且完全以“修身”立论,它以“修身立道之本”始,以“不知修身以立政”之告诫终。朱子说:
但先儒未尝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误训“皇极”为“大中”;又见其词多为含洪宽大之言,因复误认“中”为含胡苟且,不分善恶之意……乃以误认之“中”为误训之“极”,不谨乎至严至密之体,而务为至宽至广之量,其弊将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堕于汉元帝之优游、唐代宗之姑息。②
朱子此段文字虽兼具学术、政治、教化三重意义,但仍是紧密围绕“中”“极”的字义之辨展开。在他看来,先儒误训“极”为“中”的原因是未能理会“皇极”之说意在确立“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由此引发“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的严重政治后果。时人不仅解“极”为“中”有误,且对“中”的理解亦有误。“中”本是“无过不及”之义,并非所误认的居中调停,“含糊苟且,不分善恶之意”,这种误解导致君王修身上的“恕己”,用人上的“君子小人并用”的姑息、放纵。③朱子特别反对以“宽恕”解释“恕”。认为恕当正解为“如心”,而非苟且姑息之义,恕只可对人,不可于己,批评范纯仁“恕己之心恕人”说虽心存厚道,为世所称,其实不合本义,后果严重。如郅恽对光武帝的“恕己”解将引发逢君之恶、贼君之罪的恶劣后果。④朱子“皇极”解“一破千古之惑”的意义建立在对“中”“恕”字义重新理解的基础上,表明对经典文义的理解之正误,将对修身治国带来重大影响。此即朱子皇极解“破惑”的意义所在。
朱子皇极解的重心实不在政治文化领域,而归本于君王修身化民的道德教化义。朱子强调皇极的“至严至密”“极则”“准则”义,与其“格君心之非”“正心诚意”之学是完全一致的。朱子皇极解其实是以修身教化为主的一套道德治国论,而修身、正身、修己工夫,五福、六极效验,完全落实在“人君之心”这一根本上,此为君王所承担重任所在。他说:“人君端本,岂有他哉……其本皆在人君之心,其责亦甚重矣。”①故一切工夫皆终归于治心的教化之学。
二、“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
象山皇极解既是其化民成俗具体实践的产物,又是其平治天下的理论纲领,体现了象山学鲜明的以心为教的特色,具有理事相融的色彩。以下从以道觉民、承流宣化、保心保极、心正是福、以心教化、皇极根心六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以斯道觉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极也”。象山为改变荆门上元节设醮祈福的陋习,代以宣讲《洪范》“敛福赐民”章,试图通过对“皇极”的解释来达到端正民心,改变民风的教化目的。此是象山以“正人心”为治荆首务的落实。②象山以其天生的演讲能力,阐述了发明本心,自求多福的思想,使听者大受震动,深为信服,以至有感激哭泣者。《年谱》载:
讲《洪范》敛福赐民一章,以代醮事。发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晓然有感于中,或为之泣。
《讲义》并未对《洪范》皇极展开全面阐发,而仅就其前三句作一论说,即“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象山对“皇极”采用汉唐通行的“大中”说,并未自创新解。其实在经典解释上,朱子甚喜提出迥异于前人之新说,而象山往往遵循成说,此即一例也。象山说:
皇,大也。极,中也。《洪范》九畴,五居其中,故谓之极。是极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万物以此而育。③
此以皇为大,中为极,皇极为九畴之五,故居其中。并以“充塞宇宙”来表明“极”之广大,此乃象山标志语,以之形容“极”之广大,可见“极”在象山思想中具有特殊地位。象山又采《中庸》致中和说,以位天地、育万物显示“极”之效用。象山又指出:
古先圣王,皇建其极,故能参天地,赞化育。当此之时,凡厥庶民,皆能保极,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叶气嘉生,薰为太平”,向用五福,此之谓也。①
皇极大中构成参赞化育功效的前提,古代圣王能够做到皇建其极,故能参赞化育。在此皇极之中,民众受其教化熏陶,而能遵循中道。由此达到天下比屋可封,人皆君子的德行教化大兴之治。阴阳调和,风雨时至,太和之气带来祥瑞之物,化为太平世界,此即享用五福。
象山认为在圣王建极与民众保极之间存在上教下化关系,在天道太平与人道和谐之间具有内在感应关系。②并意识到“皇极”并非是一定能确保建立者,如在无道之世,人心不善,豪杰无有,则皇极不建。“逮德下衰,此心不竞,豪杰不兴,皇极不建。”③皇极之能否建,关乎民众之能否觉悟。他说:
皇建其有极,即是敛此五福以锡庶民。舍“极”而言福,是虚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极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极。但其气禀有清浊,智识有开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以斯道觉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极”也,即“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也。④
“皇建其有极”就是聚福以赐给百姓,但百姓能否接受所“赐”之福,则取决于自身能否“保有其极”。象山坚持以“极”论“福”,强调“极”“福”不可割裂,得“福”的关键在“保极”,无极则无福,无极而言福,必为虚妄之谈,必是不明事理之论。又引《汤诰》“降衷于民”说,指出“衷”即是“极”,“极”又是“中”,此不同于孔安国解“极”为“善”。以此证明人皆同样秉有上天所赐之极,凡民与圣人同体无隔,而实不可自弃。然又因气的清浊、智的通塞等客观限制,导致凡民不能明了自身所禀赋之“极”。⑤只有极少数先知先觉之士,方能明乎此上天降衷之极而觉乎此道,并以之觉悟后知后觉。象山一方面指出“凡民之生均有是极”,将凡民往上提升至与圣人同样禀赋天降之极;另一方面强调“古先圣贤与民同类”,圣贤亦不过是《孟子》所言“天民先觉”而已,可见圣凡同体。他强调“以道觉民”的教化、开发民众之意,表明宋代理学并非株守“得君行道”一途。事实上,朱陆真正的政治生涯皆极短,他们将主要精力用在发明斯道和以道化民的教化工作上,由此重视书院讲习活动的展开。明代阳明学“觉民行道”亦是对理学此项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展开而已。①在象山看来,不管是在上之皇极还是在下之五福,皆离不开对道的觉悟,皆围绕如何觉道展开。象山此处论证逻辑极似朱子《大学章句序》思路。②
(二)“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象山将“宣化”与“宣福”等同之。他说:
皇建其极,“是彝是训,于帝其训”,无非敛此五福,以锡尔庶民。郡守县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为圣天子以锡尔庶民也。凡尔庶民,知爱其亲,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圣天子所锡之福也。
圣上德性光明在上,足以洞察幽明,智照四方,故能替天治民,奉天从事,立大中之道,此伦常中道既是民众所当遵循之法则,亦同样是帝王所当行之法则,皇能建其极,则自能聚集五福以锡庶民。各级官员秉承圣意,宣扬教化,就是替天子赐五福于民。“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说把官员开展教化当作赐民之福,把德性之教与人生幸福结合之,表达了以教为福的思想,明确了开展化民易俗的教化工作乃官员应尽之职责。③于民众而言,如能做到爱亲敬兄的孝悌之道,即是实现了“皇降之衷”,即承受了天子所赐之福。可见,象山之教化以父子兄弟的孝悌爱敬之情为中心,将所谓祈福归结为个人的内在德性修养,此福不在天,不在王,而是在个人当下可行的内在之道,是人人本有的孝悌仁爱之心。象山指出特意开设本讲,乃是针对官府设立法会祈福之举的一项改革,“谨发明《洪范》敛福锡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几承流宣化之万一。”指出天子以皇极君临天下,地方官员理应与民众践履皇极之义,从而接近天子之光辉。故以此讲代替法会,意在达到承流宣化之目的。列九畴于《讲义》之后,希望民众能转变观念,做到以善为福。所谓“自求多福”之福乃是自我当下即可把握者,求福即在求心,福在心内非在外也。
象山始终认为,宣扬教化乃是为官本职。他在尚未上任荆州时所作《石湾祷雨文》中,即批评官员不以宣化为职,反而一味以吏事、催科、簿书等为务,放弃了作为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承流宣化之责,表明了以承流宣化作为执政首务的理念及革新弊政的用心。“论道经邦,承流宣化,徒为空言;簿书期会,狱讼财计,斯为实事,为日久矣。”①在《宜章县学记》中,象山大量引用《尚书》以为立论根据,充分表达了承流宣化、各负其责的教化思想。他说:
汉董生曰:“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斯民之责于天者,君也。分君之责者,吏也。民之弗率,吏之责也。吏之不良,君之责也。《书》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君任其责者也。可以为吏而不任其责乎?②
上帝不仅降生民之中,还任命君师对民众施其政教,行其化育。由此内设朝廷,外置邦邑,皆以尽心辅助天子之教化为务。周公告诫成王三宅三俊说,当以三德教化百姓;成王告诫康叔,应以五常教化百姓。董仲舒“承流宣化”说,指出郡守、县令等官,承担着宣扬君德,教化民众之责。故向上天承担保养教化民众之责者为君王,分担君王之责者为官吏。如民众不遵循教导,则当责备官吏;如官吏品行不端,则追究君王责任。可见君臣上下之间,各自承担着教化官吏与民众之职。天下有罪,百姓有错,君王当负其总责。然作为官吏者亦当承担所负有之职责,而不可推诿于民众与风俗之难治难移。
象山将有无教化之道,视为夷狄之国与中国的差别所在。据夫子君子化陋俗为良治之思想,批评官员推脱治化之责于风土民情者乃自欺之言。引曾子、孟子、孔子之言,表明民情处饥渴无助情形之下,反而最易推行治化之道。称赞吴镒通过学校教育子弟,使老幼皆受教化而自然回心向善,证明开展治理教化工作,于此民风不竞之世更为容易。又以周道大行为例,对教化提出了应达到“民日迁善远罪而不知为之者”的自然而化境界。特别抨击功利之说、百家之言对于人心的遮蔽和教化的阻碍,教化关键在自我挺立,践履仁义,扩充四端。
夷狄之国……无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顾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责,而惟民是尤,则斯人之为吏可知也……于其所谓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③
(三)“若能保有是心,即为保极”。象山将保极、五福皆落实为保心。说:
若能保有是心,即为保极,宜得其寿……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圣天子所锡之福也。身或不寿,此心实寿……杀身成仁,亦为考终命。④
象山认为,如能保养此心不失,即是保极,就当享有富寿康宁等五福。福不是外在之事,而纯为内心存养;它本无关肉体,即使肉体消亡,此心仍可常存。如杀身成仁者,身虽亡而命常在。故百姓如能明乎君臣上下之义,中国夷狄、善恶是非之分,践行父慈子孝五伦之道,即做到了皇降之衷,即能承受天子所赐五福。①象山谈到了如何面对德福不一。他区分了心之福与身之福,认为如能行五常之教,其心实已享有了五福之报。此种福报完全是“心福”而非“身福”,如能存养、践履此道德之心,即是最大之福,外界富寿等,皆不足与计。此体现了象山以“心”为核心解释人生的思想。《贵溪重修县学记》则明确提出以本心为教,对民众教化本乎尧舜之道,皆不过使之不失本心。“庠序之教,抑申斯义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②然据《中庸》“大德必得”之论,“心福”应与“身福”一致。
(四)“实论五福,但当论人一心”。象山进一步申论了以心论福的“心福”立场。说:
实论五福,但当论人一心,此心若正,无不是福。此心若邪,无不是祸……不知富贵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恶,是逆天地……若于此时更复自欺自瞒,是直欲自绝灭其本心也……虽在贫贱患难中,心自亨通。正人达者观之,即是福德。③
象山提出论福实为论心,心正为福,心邪为祸,区别了德富背离和一致两种情况。一者大富之人,如其心邪事恶,则是违背天地鬼神,背离圣贤之训,君师之教。若自加反思,真实面对自我,必能意识到其中实有不可自我欺骗隐瞒者所在。若于此仍是自我欺瞒,不肯面对本真之我,则必是自绝灭其本心之人。况且富贵实非人生所当追求,自正人君子而观之,富贵非但不可羡慕,反而可怜鄙视之极,实乃身处监狱污秽之中而不自觉。反之,身处患难之中,如能心正事善,不违天地鬼神,君师圣贤之教,则必赢得庇佑和肯定。虽处贫贱,而心实富有通达。自正人君子观之,此即福德。象山以正邪、贫富、善恶之对比,突出“福德”的“德福”义,是因“德”而“福”而非因“富”而德,以消解民众以富为德的观念。世俗之福并非真福,唯有有道德者方是真幸福。当然,此处象山强调了观察者的身份——自正人观之,否则就不正之人观之,其判断必有所不同。
象山引《尚书》说论证“自考其心”的求福之法,批评求神拜佛无益。
但自考其心,则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随形,如响应声,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迁善远罪,但贪求富贵,却祈神佛以求福。④
伊尹告诫太甲上帝无常,灾祸吉祥因人善恶而降。《坤卦》说积善余庆,强调善祥恶殃的德福一致。祸福善恶端在自家之心,故当“自考其心”,如能自求自考,则见祸福如形影声响之必然而不可违逆。批评愚人贪恋富贵而妄求神佛保佑赐福,但却不知神自有其福善祸淫之原则,而不被人所收买,故不能予福德于不善之人。真求福德之法,乃在对治自身,迁善改过,远离罪恶。象山完全是从道德本心的角度阐发以善为福的思想,批评了求神拜佛思想的荒谬性。
象山之论,合乎其义利之辨的精神,他教化民众当以义为利,而不是以利为利。他曾据《尚书·仲虺之诰》区别内心动机与外在效果的同一与差异两种情况,略相当于康德的合法性与道德性之别。判定行为是否具有道德,关键是看其心之所主,而不是看其行之是否合乎所是。如心主于义,则其行为义;主于利,则行为利。故后世行为虽有合乎礼义者,然却是出于利害之心。反之,古人虽是考虑利害,却是出于道义之行。这样使得一切行为的价值皆当“凭心而论”,而不是就事而论,故官吏处理财会、诉讼等杂务就完全具有了正当性和必要性;同样,出于求利之心的祈福之举,则不具有了道德性。
后世贤者处心处事,亦非尽无礼义,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礼义行之耳。后世所以大异于古人者,正在于此。①
对民众而言,功利的态度尤表现在事鬼神上。象山虽肯定怪力鬼神实有,所看重者,则是鬼神所具有的教化百姓之效用。②象山以“聪明正直”作为对神的要求,认为民众对神的祭祀应祭所当祭,非所当祭而祭,即是淫祀。对神而言,亦不应享有不当祭之祭,否则非神。他以此为准则来改革旧俗祭神之误,体现了化民成俗教化思想的实践。象山曾多次求雨,但却体现了很强的理性精神,毫无祈求姿态,批评山川之神素餐不治,劝告诸神既然享民之祭,理应替民分忧,救民旱灾。把山川之神视为自己的“同僚”,共同承担庇护一方百姓的使命,如不能消除灾害,对神来说,亦意味着失职。“旱干水溢,实与守臣同其责。”③
(五)“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象山提出了以心为教说。
皇极在《洪范》九畴之中,乃《洪范》根本……“敛时五福,锡尔庶民”者,即是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以发明尔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尔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恶,即为保极。可以报圣天子教育之恩,长享五福,更不必别求神佛也。
象山肯定“皇极”在整个《洪范》九畴之中的根本地位。天子“建用皇极”,赐五福于百姓,其实质是以皇极之心施于政事教化,以阐发显明百姓内在本有的天降之中,使之不至陷溺。庶民如能保全此本心,即做到了保极。则可上报君恩,长享五福,而不必别求神佛。象山此处亦是以“心”论福,以心论“极”,天子赐福于民者无他,不过是施教者以大中之心教化民众,使民众能自觉其大中之心,存养此心而不陷溺也。对受教化者而言,则保全大中之心纯正无邪,即是保养此极。无论赐福、保极皆是一心之教化。象山之心,并不离乎理。他指出福其实不可赐,所谓赐福,乃是指此理之遍布宇宙。象山主心即理,故此理充塞,其实亦是此心充塞。“福如何锡得?只是此理充塞宇宙。”①
(六)“皇极之建,根乎人心”。象山指出,《洪范》九畴之教关乎彝伦之存废,箕子曾对武王讲述《洪范》九畴,当鲧治水失败后,帝大怒而不授《洪范》,导致伦常败坏;在大禹接替治水工作后,方才赐予《洪范》,使得伦常有序。作为《洪范》核心的皇极大中之建立,事关彝伦兴废,此是普遍不易之理。但此“中”“常”并不神秘,不可仅从政治上加以理解,实则“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大中常道既内在根本于人心,又超越充塞于天地,表达了以人心论“皇极”的教化思想。“皇极之建,彝伦之叙,反是则非,终古不易。是极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
象山的教化思想,特别重视先知先觉的引导之功。他指出,先知先觉的意义在于明理导民。盖理虽遍在天地,但若无先知先觉开导引诱,则人必然限于黑暗摸索之中,而无法明乎此理。只有明觉之人方才可以论理。学不明理,只是凭一己武断论述天下是非,不自量力,此显出象山对于“理”之重视。“是理之在天下无间然也,然非先知先觉为之开导,则人固未免于暗。”②上古圣贤先觉此道以觉悟斯民,后世学者无学,道亦无传,故民无所归。批评士人未能明道,导致教化不行,斯道不明。可见士之先觉乃是教化推行之前提。故象山反复致意于“以道觉民”。“上古圣贤,先知此道,以此道觉此民。后世学绝道丧,邪说蜂起……而号称学者,又复如此,道何由而明哉!”③
在象山看来,所谓先知先觉实质就是师友之教,象山认为有无师友之教,是决定学道成败的关键。先知先觉之觉悟后知后觉,乃是天理必然。有师之教与无师之教,效果截然不同。先知先觉者承担培育天下人才之重任,故天下没有人才,责任在于作为先知先觉者的师友未能尽其教化之功。“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要当有任其责者。”④象山讨论了先知先觉所教与学者所习之异同,指出所谓先知先觉之教并非口耳言语之教、“意见之教”,乃是事实之教,人伦之道,是言教与身教的统一。此有针对朱子意味。
朱子对象山皇极说甚为关切,听闻象山解“保极为存心”,要求学者对其说加以判定,提出应对照经文,逐句落实其解,方能判定象山得失。朱子判定象山的皇极解不过是敛六极,“陆子静《荆门军晓谕》乃是敛六极也”①。所谓六极乃是与五福相对的六种不好之遭遇:“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其意谓象山把敛五福解读成了敛灾祸。象山提出“舍极无福”“保有是心即为保极”“实论五福,但当论人一心”的以心为福说,注重教化民众不可执着世俗之祸福,其目的亦是“使天下之民归于正”,实在具有转化民风的教化意义。朱子颇为忌惮其将此等外在祸福完全收归于“心”,而置现实祸福于不顾之论,故发此批评,实不相应而有失严苛。学者已指出朱子所言不妥。②
三、结语:皇极与教化
朱子、象山对皇极字义及其思想的阐发,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在基本精神旨趣上彼此相通,皆以推行教化为共同宗旨。朱子皇极之解,自辟新见,其指向却在责君行道,要求君王修身诚意,以立人极,通过树立圣人般的典范人格,成为天下四方效法取正的法则,以达到下民感兴而化的教化效果。朱子以治经学的严谨态度,对皇极文本,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就其文本前后修改等来看,体现了越来越突出教化、立极的意味。而象山的皇极讲义则完全是有感而作,是为了解决一个转移风俗,改变民心的实际问题。故象山的皇极解只是选取首三句而发,不如朱子皇极解严密完整。为了转变民众祈神求福的功利之心,象山开出了保心、保极,以心为福之方,教化民众当在自家德性用功,树立德福一致,以德为福的思想,体现了心学的教化理论,产生了明显的现实效果,彰显了象山学义理与事功贯通的“实学”特质。简言之,朱陆皇极解所针对对象,所设定任务皆有所不同,朱子可谓是责君成圣以化民的上层路线,象山则是化民之心以行道的下层路线,但二者皆同归于儒家的教化之道。
儒家的这一教化思想在当代仍具有新的理论活力。当代儒家教化哲学的代表学者李景林指出,儒学的根本特质就是一种教化的哲学。儒学作为一种工夫教化,它不脱离于哲学;另一方面,儒学作为哲学义理,它扎根于工夫教化。儒学的“教化”观念,取形式与实质、内在与超越一体的思路,经由“工夫”来引发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转变。儒家哲学的教化还借助于中国古代社会固有的礼仪、仪式系统,经过形上学的诠释、点化、提升,巧妙地切合和影响于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之样式,这种教化带有浓厚的哲学的意味,这是它“哲学义的教化”一面。①李景林强调,经典传习、礼乐教化、重视家庭教育作为的儒家教化方法,于今日落实儒学的教化之道仍具有重要意义。他提醒教化儒学的未来发展要注意三个方面:理论形态的重建、儒学和社会生活联系的重建、“以身体道”群体的培育。②可见,从教化的角度来解读儒学的过去与重建儒学的未来,可以超越以心性或政治论儒学的分歧,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中国哲学传统,开拓中国哲学新境,这是宋代儒者皇极解留给我们的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论题。
(原载《学术界》2021年第1期,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心性情”与“易道神”:朱熹对程颢思想的创造性诠释
翟奎凤
《二程遗书》卷一有下面一段话:
“忠信所以进德”,“终日乾乾”,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疑事,则只曰“诚之不可掩如此夫”。彻上彻下,不过如此。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
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①一般认为,这段话是程颢说的,最后几句论形而上下、道器的话非常有名,相对来说,“彻上彻下,不过如此”之前的文字关注讨论得不多。实际上,朱熹与其门人在谈话中对这段文字前面所论“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有非常集中而且相当深刻的研讨。朱熹的基本观点是:以心、性、情来对应这里的易、道、神。朱熹关于“易、道、神”的讨论成为构成其心统性情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乾乾”的意思是刚健精进,也有慎独、戒惧之意,“对越在天”是讲对上天的敬畏。朱熹认为前三句话“只是解一个‘终日乾乾’”②,而“下面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云云,便是说许多事,都只是一个天”(同上)。具体而言,“易、道、神”是“就天上说”,而“性、道、教”则是“就人身上说”(同上)。总体上来看,朱熹认为程颢所说这段话“皆是明道体无乎不在。名虽不同,只是一理发出,是个无始无终底意”(同上,第3189页)。朱熹关于“易、道、神”的讨论也是其道体思想的重要体现。
一、天人相应:“心性情”与“易道神”
1168年(39岁)朱熹在《答范伯崇》论程颐“随时变易以从道”③时说“‘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潜、见、跃、飞之类观之,则‘随时变易以从道’者可见矣”(《文集》卷三十九,《朱子全书》第22册,第1774页)。1171年(42岁)在《答方伯谟》信中又进一步发挥说:“随时变易以从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潜’‘见’‘飞’‘跃’观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当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而伊川又谓‘变易而后合道,易字与道字不相似也’。”(《文集》卷四十四,《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08页)这是朱熹较早引述到程颢“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一语,但这里还没有把“易、道”与心、性关联对应起来,只是以变易流行与定理当然来解释“易”与“道”。但其实在1170年,41岁的朱子在与张栻的通信中已把“心”与“易”作了关联,他说:
心具众理,变化感通,生生不穷,故谓之易。此其所以能开物成务而冐天下也。圆神、方知变易,二者阙一则用不妙,用不妙则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心”正谓其无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众理必具而无朕可名,其“密”之谓欤?必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动也,如此立语如何?(《文集》卷三十二,《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95页)
朱子这里以“心”解“易”,心、易皆有变化感通、生生、圆神方知、变易等特点。《易传·系辞上》说:“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圆神、方知本来是讲蓍卦之德,朱子这里转用来讲心之德。《易传·说卦传》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朱子也以“妙”为心之用。《易传·系辞上》还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朱子在40岁己丑之悟中和新说之后,确立了心统性情的思想,心可以有未发(性)、已发(情)两种状态,认为未发为寂、已发为感。易学话语下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也被朱子用来论心的静与动两种状态。但是这封信没有引述程子“易、道、神”之说。
1172年(43岁)朱熹在答吴德夫的信中说①:
“易”之为义,乃指流行变易之体而言。此体生生,元无间断,但其间一动一静相为始终耳。程子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此体在人,则心是已。其理则所谓性,其用则所谓情,其动静则所谓未发、已发之时也。此其为天人之分虽殊,然静而此理已具,动而此用实行,则其为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则是易之有太极者。(《文集》卷四十五,《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70—2071页)
这里也强调“易”为流行变易之体,此体生生不息。接着就引出了程子所说“易、道、神”,认为此“体”在人为心,相应地,“理”“道”对应“性”,“用”“神”对应“情”。在朱熹看来,“易、道、神”本是讲天道自然界的变化,相应于人,可以对应心、性、情。寂静之时,具此性理,感通之时为用之实行。寂感、动静、体用合起来又可以表述为“易有太极”,太极为理,易为变易流行之总体。
在答吴德夫信前后或同时,朱熹还有《元亨利贞说》短文一则,其中也说到: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文集》卷六十七,《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54页)
这些都贯穿了朱熹心统性情、心主性情的思想,“理”“道”为性、“用”“神”为情,“体”“易”为心。心统性情之统有心包性情、心主性情二义,相应地,似也可说易统道神、易包道神、易主道神。
《朱子语类》中关于“易、道、神”的讨论相当多,相对文集来说,也更加详细深入。在与弟子万人杰论“易、道、神”时,朱子说“就人一身言之:易,犹心也;道,犹性也;神,犹情也”。对此,万人杰问说:“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朱子回答说“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摄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为春夏,所以为秋冬之理是也;至发育万物者,即其情也”(《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88页)。这里突出了“心”的主宰性。这条材料为万人杰自记,黄㽦也记录了万人杰与朱子的类似对话:
正淳问:“‘其体则谓之易’,只屈伸往来之义是否?”曰:“义则不是。只阴阳屈伸,便是形体。”又问:“昨日以天地之心、情、性在人上言之,今却以人之心、性、情就天上言之,如何?”曰:“春夏秋冬便是天地之心;天命流行有所主宰,其所以为春夏秋冬,便是性;造化发用便是情。”又问:“恐心大性小?”曰:“此不可以小大论。若以能为春夏秋冬者为性,亦未是。只是所以为此者,是合下有此道理。谓如以镜子为心,其光之照见物处便是情,其所以能光者是性。因甚把木板子来,却照不见?为他元没这光底道理。”(同上)
“正淳”即是万人杰,此条语录记于朱子59岁时。朱熹强调“只阴阳屈伸”便是形体,显然,若说“屈伸往来之义”就指向性理了。易、道、神是从天(春夏秋冬)的角度来说,心、性、情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易、道、神为天地之心、性、情①。这里“春夏秋冬便是天地之心”的“心”是连着心、性、情来说,强调春夏秋冬、四季转换流行之体,就相当于人的心。因此,这里“天地之心”,与一般所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是不同的。这里“天命流行有所主宰”实际上又强调性对心的主宰,性理是根据,规范着心流行生生。与前面一条强调心对性的主宰、管摄义又有所不同。心主宰性,反过来也可以说,性主宰心,所揭示的思想意义不同。这条材料最后又以镜子来比喻心,“所以能光者是性”,镜子有光能照物的原理根据是性,光所照见之物为情。
黄㽦还记载了另外一条相关材料:
“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功用则谓之鬼神。”易是阴阳屈伸,随时变易。大抵古今只是大阖辟,小阖辟,今人说《易》,都无着摸。圣人便于六十四卦,只以阴阳奇耦写出来。至于所以为阴阳,为古今,乃是此道理。及至忽然生物,或在此,或在彼,如花木之类蓦然而出,华时都华,实时都实,生气便发出来,只此便是神。如在人,仁义礼智,恻隐羞恶,心便能管摄。其为喜怒哀乐,即情之发用处。(《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88—3189页)
这条材料也是记于朱子59岁时,这里把“其用则谓之神”表述为“其功用则谓之鬼神”。以阴阳、屈伸、阖辟、往来解释易,为朱子一贯思路,其背后的所以然、根据为道和理;其发用功能、生机展现,为神。以心统性情之说,心能主宰、管摄性与情,照此逻辑,也可以说“易”能主宰、管摄道与神。朱子还说:
盖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发见者言。明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发见亦如此。如后段所谓“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某尝谓,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是情。缘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来个个亦如此。一本故也。①(同上,第3199—3200页)要见得分晓,但看明道云:“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此天地之心、性、情也。②(《语类》卷五,《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3页)
程子曰:“其体谓之道,其用谓之神。”而其理属之人,则谓之性;其体属之人,则谓之心;其用属之人,则谓之情。③(《语类》卷一百,《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50页)
可见,大概是从43岁中年开始,一直到晚年,以心性情论易道神,是朱子常说的话语。那么,朱子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把两者对应关联起来进行论说呢?朱子非常重视宇宙生化论、重视天道,同时认为天地之道与人道有对应、呼应性,人道的根源在天道,在这一点,相对程子来说,他受到周敦颐、邵雍的影响更大。朱子在40岁提出中和新说,确立心统性情思想之后,应该说他就开始潜在地寻求心统性情思想的天道论根据或本体论表述,在把心与易对应之后,对程子思想非常熟悉的他自然进而把心性情与易道神对应起来。这样在天之易道神,在人即为心性情,心统性情思想的主体论表述也就有了天道论的支撑,就更加具有权威性。
二、易体:道体而非形体
“其体则谓之易”,这里的体是变化流行的总体、统体,非体用之体,对此,朱熹有反复强调。但此体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抑或包体用,不分形而上下。就《语类》材料来看,朱子的表述有前后矛盾之处。统观来看,朱子所诠释的“其体则谓之易”之体应是该体用、形而上下浑融的道体。
朱熹曾把体理解为形体,为形而下的存在。如程端蒙所记语录说:
“其体则谓之易”,在人则心也;“其理则谓之道”,在人则性也;“其用则谓之神”,在人则情也。所谓易者,变化错综,如阴阳昼夜,雷风水火,反复流转,纵横经纬而不已也。人心则语默动静,变化不测者是也。体,是形体也。言体,则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则形而上者也。故程子曰“易中只是言反复往来上下”,亦是意也。①(《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87页)
易、心皆为变化、错综、不测、流转不息的存在,这是朱熹经常说的。但是他这里说“体是形体”,而且直接说成是形而下的存在,与形而上之理相对。那么,这样的话,照此逻辑类比,就是心与性相对,心为形下存在。但是这显然与朱子本人心统性情的根本思想是矛盾的。因此,这条材料不能视为朱子的究竟之说。原文“体,是形体也”下有小注曰“贺孙录云:体,非‘体、用’之谓。”“贺孙”是指叶贺孙(字味道,括苍人,居永嘉)。贺孙所录为辛亥(1191年,朱子62岁)以后所闻。那么,据此推理,则端蒙此条所录也可能在1191年即62岁时(他与朱子过从密切,在去世前还曾写信与朱子诀别)。
《语类》中载有弟子辅广所记朱子论“其体谓之易”的一段话:
问:昨日先生说:“程子谓:‘其体则谓之易。’体,犹形体也,乃形而下者,《易》中只说个阴阳交易而已。”然先生又尝曰:“在人言之,则其体谓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是个动静感应而已,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是也。看那几个字便见得。”因言:“易是互相博易之义,观《先天图》便可见。东边一画阴,便对西边一画阳,盖东一边本皆是阳,西一边本皆是阴,东边阴画皆是自西边来,西边阳画都是自东边来。姤在西,是东边五画阳过;复在东,是西边五画阴过,互相博易而成。《易》之变虽多般,然此是第一变。”
广云:“程子所谓‘易中只说反复、往来、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
曰:“看得来程子之意又别。邵子所谓《易》,程子多理会他底不得。盖他只据理而说,都不曾去问他。”(《语类》卷六十五,《朱子全书》第16册,第2171页)
这段话中不少语句与上面程端蒙所记材料类似。辅广所记朱子语录在朱子65岁之后。如果拉近与上面程端蒙条材料的距离,那么辅广这条材料可系在朱子65岁时。可以尝试推测,在朱子62岁至65岁时,似乎他多次把“其体谓之易”中的体理解为形而下的形体。当然,就上面这段材料中朱子的讲话内容来看,他强调了心的动静感应,与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状态类似,接着又发挥了“易”的互相博易之易,以复、姤为重卦乾坤第一变,类似八卦中震、巽为其“一索”之第一变。这段话应该是进一步解释他所说的“易中只说个阴阳交易而已”。这是以邵雍先天易学的思想来解释互相博易。辅广问:程子所说的“易中只说反复、往来、上下”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其实程子这句话,在程端蒙所记材料中,朱子本人也有引用到。但在这条语录中,朱子明显站在邵雍一边,对程子有些微词,认为他只是单纯从“理”的角度非常抽象地来讲“往来上下”,没有去理会邵雍先天易学交互变易的精蕴。
显然,若把“体”理解为形而下的形体,这与朱子心统性情的基本思想是无法贯通的。实际上,朱子对这种说法也有明确否定过。我们看下面万人杰所记语录:
黄敬之有书,先生示人杰。
人杰云:“其说名义处,或中或否。盖彼未有实功,说得不济事。”
曰:“也须要理会。若实下功夫,亦须先理会名义,都要着落。彼谓‘易者心之妙用,太极者性之本体’,其说有病。如伊川所谓‘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方说得的当。然伊川所谓‘体’字与‘实’字相似,乃是该体、用而言。如阴阳动静之类,毕竟是阴为体,阳为用,静而动,动而静,是所以为易之体也。”
人杰云:“向见先生云,体是形体,却是着形气说,不如说该体、用者为备耳。”
曰:“若作形气说,然却只说得一边。惟说作该体、用,乃为全备,却统得下面‘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两句。”(《语类》卷一百二十,《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78页)。
“黄敬之”为弟子黄显子。朱熹批评了黄敬之“易者心之妙用,太极者性之本体”的思想,重申对程子“易、道、神”思想的肯定。但是这里强调“体”是“该体用”,与“实”字相似。接下来,他亲自否定了自己之前把这里的体理解为形气、形体的说法,认为只有理解为“该体用”才完备,才能统得下面的“道、神”。显然,这里内在地贯穿着其心统性情的思想,只有心该体用,才能统得性、情。如果易、心只是形气,统不了性情。万人杰在朱子51岁时过来学习,直到朱子70岁时,仍与朱子过从甚密。综合来看,这条材料应该是在朱子65岁之后,可能在68岁左右。
朱熹强调“体”与“实”字相似,又说是“体质”之体,“犹言骨子”:
问:“‘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如何看“体”字?
曰:“体,是体质之‘体’,犹言骨子也。易者,阴阳错综,交换代易之谓,如寒暑昼夜,阖辟往来。天地之间,阴阳交错,而实理流行,盖与道为体也。寒暑昼夜,阖辟往来,而实理于是流行其间,非此,则实理无所顿放。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实理寓焉。故曰‘其体则谓之易’,言易为此理之体质也。”(《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86—3187页)
这条材料为弟子董铢于朱子67岁以后所记。关于“体质”之说,朱子在回答叶贺孙问“其体则谓之易”时也强调“体不是‘体用’之‘体’,恰似说‘体质’之‘体’,犹云‘其质则谓之易’”。那么,体质之体是不是就是形而下的形体、形气呢?总体上来看,应该不是。这里实际上是引入“道体”的观念来解释“易体”。董铢这条材料最后有小注:“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集注》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即是此意。”(同上)
把易体与道体关联起来,在弟子甘节所录材料中也有体现:
周元兴问“与道为体”。曰:“天地日月,阴阳寒暑,皆‘与道为体’。”又问:“此‘体’字如何?”曰:“是体质。道之本然之体不可见,观此则可见无体之体,如阴阳五行为太极之体。”又问:“太极是体,二五是用?”曰:“此是无体之体。”叔重曰:“如‘其体则谓之易’否?”曰:“然。”(《语类》卷二十六,《朱子全书》第15册,第1356页)
“叔重”即董铢。这条材料录于朱子64岁以后。综合董、甘所录这两则非常相关的材料来看,体质、道体、易体是在一个层面来说的。
陈来先生在《仁学本体论》中对朱子的道体思想有深刻揭示,他指出:
从朱子学的立场来说,道体即是实体,也是最高实体。在程颐的说法里,道本无体,是无体之体,必须借助事物作为体才能为人所了解。但朱子已经与程颐不同,他不再说道之本然之体不可见,而直指川流,认为这就是道体之本然;他进而认为,天地之生化流行,就是道体之本然,可见他已经从程颐的观念摆脱出来,进至实体的观念了。①
在这个意义上,道体就是“其体则谓之易”的体,乃变化生生流行不已
之总体。至于此体之中寓有理,这是理学思维特别重视的地方。①因此,全面来看,朱子所说“其体则谓之易”的易体是该体用的道体。这样的易体、道体是理气浑融不分的。这种道体论、实体论,究其实,也是一种境界论。
《易传·系辞》还说到“神无方而易无体”,朱子认为“无体”是说“或自阴而阳,或自阳而阴,无确定底”,而“其体谓之易”之体,“是说个阴阳,动静辟阖,刚柔消长”(《语类》卷七十四,《朱子全书》第16册,第2522页),两者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无体”之体谓没有形而下的固定形体,“其体”之体为道体、变易流行之总体,可以说,“易”因其无体,乃成道体,为无体之体。
三、神用:功用而非妙用
在朱子看来,“其体则谓之易”为该体用之道体,非仅形下之形体。这可以作为定论。只有这样,“易、道、神”,才能与“心、性、情”对应协调起来。然而,以“神”对应“情”,仍有不少让人费解之处,以至于让我们怀疑朱子以心、性、情来解易、道、神,到底恰不恰当?与程子的原意是否一致?
在朱子心统性情的思想中,性与情对,为体用关系,情为心的一种活动状态。情总是关联着具体的人与事,关联着气,有具象性,有形下性。但是在一般意义上来说,“神”是超越性的形上存在。那为什么朱子把“其用则谓之神”对应于情呢?
这需要我们回到程子说的另外一句话以及朱子的解读。程颐说“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谓之神,以性情言之谓之乾”(《遗书》卷二十二上,第343页)。学生经常就“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谓之神”来向朱子请教前后两个神的区别。朱子认为“鬼神者,有屈伸往来之迹,如寒来暑往,日往月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见也。忽然而来,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测知,鬼神之妙用也”(《语类》卷六十八,《朱子全书》第16册,第2258页),“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无迹底。妙用是其所以然者”(同上,第2259页),“功用兼精粗而言,是说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测。天地是体,鬼神是用。鬼神是阴阳二气往来屈伸。天地间,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同上),“鬼神之神,此神字说得粗”②(《语类》卷六十七,《朱子全书》第16册,第2218页)、“言鬼神,自有迹者而言之;言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测识”(同上,第2087页)。综合来看,似功用之鬼神是形而下的(粗或兼精粗),而妙用之神是形而上的(精),朱子用“所以然”一词值得注意。《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程颐认为“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遗书》卷三,第118页),那么,套此逻辑,功用之鬼神为一阴一阳之屈伸变化,而妙用之神乃功用阴阳鬼神的根据或动力。
可见,实际上朱子是把“其用则谓之神”与“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等同起来。据黄㽦所记语录,朱子就曾直接说过“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功用则谓之鬼神”①,他直接把“其用则谓之神”中的“用”理解为“功用”,“神”理解为“鬼神”②。程颐曾说“鬼神者,造化之迹”,显然这也是从阴阳、形下的角度来理解功用和鬼神。朱子还说“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说起。虽是‘无声无臭’,其阖辟变化之体,则谓之易;然所以能阖辟变化之理,则谓之道;其功用著见处,则谓之神”(《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85页)。“阖辟变化之体”是易体、道体,其变化之理、道是本体、根据,这种意义上的理、道可以理解为太极。“其功用著见处,则谓之神”,“功用”意思是功能展现,是可见的表象世界。
结合这些来看,可以说朱子所理解的“其用则谓之神”之“用”主要是指各种自然现象、造化之迹,“神”是鬼神、阴阳二气屈伸往来之变化表象。“其体则谓之易”是讲变易流行的统体、总体,包含体用,而“其用则谓之神”则是表象、现象世界;当然,这个现象、表象也是体之功用表现,是用不离体、体用不二的。而“其理则谓之道”则是变化的根据、原理,是形而上的。
朱子反复以心、性、情来对解易道神。但是当以情释神,视神为情时,就会关联到心与神的关系,在此思维框架下,心“神”竟被视为气,为形而下的存在。我们看下面一段语录:
(直卿)又问:“神是气之至妙处,所以管摄动静。十年前,曾闻先生说:神亦只是形而下者。”贺孙问:“神既是管摄此身,则心又安在?”曰:“神即是心之至妙处,滚在气里说,又只是气,然神又是气之精妙处,到得气,又是粗了。精又粗,形又粗。至于说魂说魄,皆是说到粗处。”(贺孙)(寓录云:“直卿云:‘看来神字本不专说气,也可就理上说。先生只就形而下者说。’先生曰:‘所以某就形而下说,毕竟就气处多发出光彩便是神。’味道问:‘神如此说,心又在那里?’曰:‘神便在心里,凝在里而为精,发出光彩为神。精属阴,神属阳。说到魂魄鬼神,又是说到大段粗处。’”)(同上,第3186页)
这些话也是由以“心性情”讨论程子“易、道、神”话语引起的。牟宗三据此认为“无论叶贺孙录或徐寓录,皆表示朱子视神为神气、神采之神,与鬼神之神同。心、神、鬼神、魂魄、精、形等俱属于气,俱是形而下者”,并强调“心理学的心、习心、识心、成心,可视为气,为形而下者,而道德的、应然的本心则不可视为气,视为形而下者。神气、神采、鬼神之神可视为气,形而下者,而诚体之神,寂感真几之神则不可视为气,视为形而下者。由心理学的心到道德的本心,由鬼神之神到诚体之神,俱不能一条鞭地、直线地、形式地直通上去,而一是皆以气视之也”①,并批评说“朱子以如此实在论的态度一条鞭地视心与神为气,则其视道体为‘只是理’亦是很逻辑地一贯者,此见其心思清明、煞有工夫,而足以决定成另一系统,即吾所谓主观地说是静涵静摄系统,客观地说是‘本体论的存有’之系统”②。
牟宗三也承认神气、神采、识心、成心可视为气,同时他也指出诚体之神、道德本心的超越性,不可视为气。但是就“心性情”对应“易道神”话语来看,“情”对应“神”,这里的神为功用之鬼神,为具体的情感心理活动,类似于自然现象界的阴阳错综变化。在上面一段对话中,朱子所说的心与神,多是就神识、情识活动而言。实际上,在心神问题上,朱子的表述也相当复杂。当学生问“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时,朱子说“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若今学者所论操存舍亡之心,自是神明不测”(《语类》卷五,《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1页),陈来先生指出“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心脏之心实有一物,可以谓之形而下,但哲学意义上的心并非实有一物,其特质为‘神明不测’,故不能说是形而下。心既然不属形而下,当然意味着心不属气”③。在《孟子集注》中朱子解释“尽心”时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孟子集注》卷十三,《朱子全书》第6册,第425页),在《大学或问》中又说“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大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11页)。这两处关于“神明”的表述看起来很相似,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前者从总体上讲“心”是“人之神明”,这个神明偏于形而上,而后者讲“知”是“心之神明”,有具体形下性。吴震认为“在他(朱熹)看来,既然人心主要是一种意识知觉,具有虚灵不昧、湛然虚明、神明不测等特征,因而我们就不能用形上形下这套观念模式来定义”④。心与神、神明的关系相当复杂,在一个层面上,心、神为易体、道体,是理气合一的统体,在另一个层面又为偏于气的情识、神识。全面来看朱子的心,它是包性与情的,在寂然不动的本心层面,心近于性,在感而遂通的发用层面,心又表现为情。性与情皆为心所统、所包,近于性的本心通于形而上,表现为情的心识又近于形下之气。所以朱子也说“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朱子语类》卷五,《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1页),“灵”为神明性存在,相对气,有超越性、贯通性。在这个意义上,说灵说神,又是本体性理功能的展现。①但是在易道神话语下,在朱子的诠释下,神是有迹的功用之鬼神,为神气、神识,有形而下的气性特征。而牟宗三由此引申论证朱子的心为形下之存在,这种观点,显然又失之简单。
陈来先生指出“以‘心统性情’为代表的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构的表达、描述常常使用的模式并不是‘理/气’的模式,而是‘易/道/神’的模式。因为心性系统是一个功能系统,而不是存在实体”。②“在朱子的哲学中,知觉神明之心是作为以知觉为特色的功能总体,而不是存在实体,故不能把对存在实体的形上学分析(理/气)运用于对功能总体的了解。在功能系统中质料的概念找不到它的适当地位。另一方面,形上学的‘理/气’分析把事物分解为形式、质料的要素,而‘心’是统括性情的总体性范畴,并不是要素。这些都决定了存在论的形上学分析不能无条件地生搬硬套在朱子哲学中对‘心’的把握上面。”③陈先生的这个看法深刻精彩。也许朱子本人也感觉到用理气分析模式很难解释说明其心统性情的思想,所以引入程子“易道神”话语,并予以创造性转化诠释,用来说明其心统性情的思想,应该说他本人对这种解释模式还是很满意的,所以反复以心、性、情来论易道神,把易道神作为一种理想的解释模式来说明其心统性情的思想。陈来先生认为,“按朱熹的理解,二程的这个思想揭示了一个方法论的模式,即易(体)—道(理)—神(用),可以广泛用于说明一切具有一定功能的、自身运动变化的系统,就是说从三个要素来把握一个系统的总体关联,一个是系统的总体,一个是系统工作的原理,一个是系统的作用。朱熹发挥的这个思想,应当承认,具有相当深刻的含义。”④
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朱子的解读就是程子的原意呢?笔者更倾向于这是朱子的创造性诠释,是借用程子的话语来更好地表述其心统性情的思想,也就是说这未必或很难说就是程子的原意。牟宗三认为“‘其理则谓之道’,此理是与神为一之理。全道体即是一神,即是一理,但其为理是超越的、动态的、既存有亦活动的生化之理,不只是超越的、静态的、只存有而不活动的形式的所以然。朱子唯将此理视为静态的形式的所以然(当然亦是超越的、形而上的所以然),故将易体与神用俱视为气,但属于形而下者,而唯理才是形而上者。如此说理尤显非明道说此语之意”①、“至于‘其用则谓之神’,用即是道体生物不测之神用。‘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神即是寂感之神,亦曰诚体之神,皆即指道体自己说:全道体即是一神用,全神用即是道体之自己。此神用之用非是如普通之可以分解为体用,而体用各有所当属之用也:此神用不与体对,神即是体;道体亦不与神用对,体即是神”②。朱熹将神用视为气与情识,大体上可以这么讲,但是牟宗三说在朱熹,易体也是形下之气,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这不符合朱子原意。但是笔者倾向认可牟宗三“在明道,易体、神用、理道皆是说的道体自己”的看法,“其体、其理、其用,皆指‘上天之载’本身说,即皆指无声无臭、生物不测之天道本身说,是故易、道、神亦是此天道本身之种种名,所指皆一实体也”。③
总结来说,朱子把心性情与易道神进行对应,虽不一定符合程子原意,但不失为一种创造性诠释。尽管把情与神用进行对应造成不少理解上的困难,但总体上来说,用易道神来说明其心统性情的思想,还是有其理论上的自洽性,可以深化人们对其心统性情思想的理解。
(原载《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2期,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戴震与朱子对《孟子》性论诠释之差异
蔡家和
一、前言
朱子可谓宋学之集大成者,其依二程之理学思想而发扬光大,初始对于汉学亦是不满的!如于《大学章句序》提到:“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①这里的“自是以来”,指的是从孟子之后。
朱子的道统观视孟子之后,唯二程能够绍继,而其间(孟子之后至二程之前)的主流学说,大致上特点有二,亦是朱子所批评的:(1)佛、老二家之虚无寂灭教说;(2)专务章句训诂之俗儒,亦指经学之儒,此指汉儒之注经,徒务章句之诵读,而不知更深层且直指生命的学问。
朱子对于汉儒之不满,亦显示于《四书章句集注》之中,其所收集的注解虽亦包含了汉儒之说,但大致仍以宋代道南派为主,即程子弟子之传承,而朱子编有《论孟精义》,诠释上亦多宗于宋儒,即程子一系。之后,朱学盛行,历宋、元、明、清不衰,或多或少皆占有一席之地,影响所及遍于东北亚、东南亚,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而在中国,如朱子的《论语集注》既兴,而汉学何晏所编的《论语集解》即废,官学、科举考试等亦以朱子注书为依据。不过,到了明、清以后,朱学之影响力有了变化。先是明朝中叶,阳明学派兴起,其一主旨便是反对朱子学,欲与朱学一争正统,不过大致上,仍不出宋儒之视角,其采朱学之形式义而不采内容义,争辩于心即理或不即理的问题。到了清代,戴震可谓反朱之巨子,就连朱子之形式义亦不取,不信朱子的“性即理”之说,而改依《礼记》,定义“性”只是血气心知。②
清代学风之兴,有回到朴学、古学、实学的趋势,亦被称为汉学,概以汉学为宗,而反对朱学,或以朱学为主的宋学。其视宋学已杂有佛老,虽可谓性命之学,却离先秦古义甚远。方法学上,朱子主张“以义理领导训诂”③,不过,戴震则以先秦字义为准则,如其《孟子字义疏证》之作。
《孟子字义疏证》为戴震之重要作品,由此作,亦可看出汉学与宋学两种治学宗旨之大相径庭,汉学可称为相偶论,宋学则为体用论,如此不同观点,亦同时显现于其他“四书”“五经”之诠释上。
由于系统庞大,本文即聚焦于《孟子》之论性一处,借此比较二派对于孟子之性善说有何不同诠释?最后再做一总结,以孔孟为准,检视二派说法有何特点?谁较能接近孔孟之说?
二、戴震与朱子之性论
(一)戴震:性是血气心知
关于“性”字之诠释,学界向来有分歧,许是因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如《中庸》“天命之谓性”一句,两派对此诠释即不同。朱子解曰:天之所命令者,在人而为仁、义、礼、智之性,性即理也!而戴震认为:万物分于道而为运命,人道即不同于物道,人性与物性即不相同。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将“性”解为血气心知:
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气化生人生物以后,各以类滋生久矣,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气化曰阴阳、曰五行,而阴阳五行之成化也,杂糅万变,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虽一类之中又复不同。凡分形气于父母,即为分于阴阳五行,人物以类滋生,皆气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谓性。”以生而限于天,故曰天命。《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分于道者,分于阴阳五行也,一言乎分,则其限之于始,有偏全、厚薄、清浊、昏明之不齐,各随所分而形于一,各成其性也。然性虽不同,大致以类为之区别,故《论语》曰“性相近也”,此就人与人相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言同类之相似,则异类之不相似明矣,故诘告子“生之谓性”曰:“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明乎其必不可混同言之也。天道,阴阳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咸分于道,成其各殊者而已矣。①
这里,戴震举《大戴礼记》语而来证明:性乃血气心知!《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分于天道之阴阳五行,即为命!借此诠释《中庸》的“天命之谓性”。《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属《小戴礼记》,而与《大戴礼记》相近。
依于此说,则“天命之谓性”的“命”字,有其分道,则所受者亦有所限,人有德性,而物则无。然反观之,人亦有不及于物者,如人的眼力、嗅觉不及于鹰、犬等,以分于道而有所限之故。故此“命”义乃指命限,有所禀、运气上的不同。至于“形于一,谓之性”一句,意思是,个体成形即有其性,某甲有甲之人性,而牛则有牛之物性。
此说的重点,乃“性”一字,有分类上的不同,如人性这一类,与牛性这一类,两类不同。这里的类概念,不只是生物学上的区别,更是存有论与德性论上的;人之存在属类,不会同于牛一般,而人之食色,亦不同于牛之食色,人是道德之存有,而牛则不是。
孟子亦曾有类概念之说,其曰: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孟子·告子上》)
同类则为相似,不同类则不相似,如某甲与某乙同类,则为相似,唯孔子虽属人类,却能成为圣贤,能够出于其类而拔乎其萃!一般来说,如果不知对方的脚有多大(需穿多大的鞋),只要依于同类之概念而来推测或制作,大致也就不会相差太多了。又如人之口味、味觉,彼此之间,便较犬、马等之口味更接近,马食刍草,人却不然。同类之人性较为相近,食色亦相近,道德性也相似。在戴震而言,食色亦是性,属于血气之性。
至于心知之性,戴震认为:
孟子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当于理义,其心气必畅然自得,悖于理义,心气必沮丧自失,以此见心之于理义,一同乎血气之于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义非他,可否之而当,是谓理义。然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异强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①
这里明言,“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非喻言也”(《孟子·告子上》),指理义悦心与刍豢悦口之间,并非比喻的关系,而是指两者都属于人性。部分学者因“犹”字,联想到“性犹湍水”云云,认为此自为比喻无误,然理义悦心与刍豢悦口之间却非比喻,例如“牛之性犹人之性”一句中的“犹”字,即等同的意思。
心知即如君官,心官能思、能知,能依于物之则、人道、义理等而来导正;人道,即是义之道,心官悦于义理、人道,如同依于光之照明,而能中理不谬;心官依其本性,而能悦于仁义之道!
此处所引之文,尚有一个重点,即对于孟子“天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之正解,戴震的说法是:“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参看《孟子》原文: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
关于这段话,汉、宋学二派解法不同。汉学家方面,视天下之性乃千古如是,人类、犬类、牛类等各类之性、血气心知等,从古至今,不曾稍改。而宋学家中,朱子所解之“故”,谓依其旧理、故理①,此为“性即理”;牛之理千古以来不曾稍改,人之理亦然。
朱子视性即理,而戴震则以性为血气心知,这似乎是孟子性论诠释中的理、气之争。要注意的是,戴震此中的血气心知并非属于形下层次;形上与形下二者,需要两两对立才能成立,若无气化之外或气化之内的区别,又何来形上与形下之切割?戴震的血气心知,并非如朱子所定义的形下之气,而是即于形下形上、无分气化内或外之气。形上与形下在戴氏而言也只是成形前与成形后之说不同,不可以朱子的形上形下之说用在戴震身上。
(二)朱子:性即理
朱子所主张的“性即理”之说,传承自伊川,而戴震则提出质疑,问如下:
问:《论语》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自程子朱子始别之,以为截然各言一性。(朱子于《论语》引程子云,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反取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为合于孔子。②
这里质问:依于程朱,则《孟子》之性善论,与《论语》“性相近”说,两者所说之“性”竟不同?不过,程朱的气质之性(张载亦如此发明)与天地之性,其实是同一个性。所谓的气质之性,只是本然天地之性落于气质之中,以至于所表现出的本然之性,有多寡程度上的不同,即使在动物上,天理、天性亦同,亦为性善,只是动物气质浊劣,只得表现其偏,如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等,证明动物亦具有性善、道德性之部分。而戴震则不如此认为。那么,戴震为何要说,若依程朱,则《论语》的“性相近”与《孟子》的性善论,将为二性?这可参看《论语集注》中,朱子对“性相近”的诠释,曰: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①
程朱诠释孟子之性善论,定义为:性即理,故无有不善。不过,程朱以为,《孟子》一书中所言之“性”,却是要随文看,即有时是指天理之性,有时却是气质之性。若言性善,只能是天性、天理,人、物皆同,又怎可言“相近”?若言“相近”,只能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亦是源自本然之性,但因所秉、客观环境不同,致使气质有美、恶之分,有时甚至相距亦远。
程朱认为,《论语》既言“性相近”,那么也就只能是气质之性;而在其他著作中,也提到告子之说亦是气质之性,这便让戴震怀疑,若依程朱,则反而告子合于孔子,而孟子不合孔子。在戴震“反取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为合于孔子”一语下有小注云:
程子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此止是言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性安有缓急,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又云:“凡言性处,须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止论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为孟子问他,他说便不是也。”②
此戴震抄自伊川之言,用以证明程朱之论,似乎以告子合于孔子,而孟子反远于孔子?那么,朱子对于告子的“生之谓性”,又是如何理解的呢?其曰: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③
前面戴震共引伊川的两段话。第一段,“性相近”云云,与“生之谓性”之说,皆指所禀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乃本然之性堕于气质之中而来,遂有善恶、美丑之判,而本然之性亦常为气质之性所掩,致其表现不出本然之性善。
而这里,朱子主张孟子所论之性,乃纯粹之天地之性,性即理也;而告子则不知以性为理,而以气当之,此只是形下之气,不比本然性善的仁义礼智的形上之理;而形下之气所杂的气质之性,主要以知觉运动为主,乃指人之食、色等动物性。
戴震依此朱子义理,而与伊川的气质之性比配,认为若依程朱之说,则反而导致告子能同于孔子,而孟子反不能同于孔子的结果,因为告子与孔子所论之性都是气质之性。
三、程朱对孟子之翻案
(一)二程论性已不同孟子
程朱理学揭橥“性即理”说,亦称为理气论,性即天理,而天理无所不善,则关于“恶”的出口,便只能推向另一边的“气质之性”。这应该就是程朱创立“气质之性”的原因,于是形成了二分之性的格局。再者,也正因性之二分,程朱可把历来诸如告子、荀子、扬雄、释氏、胡氏(五峰父子)等人说法,都判定为“误把气质之性认作天地之性”一类,这类人以气当理、认气为性,于是有性善恶混、性可善可不善、性空等说,是则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矣!
程朱学派认为,因着理气之二分,儒家便得以归纳历来关于性论之学派,以便杜荀、扬等辈之口,战国时期的孟子无法做到,如今程朱却办到了,则历史争论至于程朱,或许可以稍歇!不过,戴震却不以为然,评曰:
创立名目曰“气质之性”,而以理当孟子所谓善者为生物之本,(程子云:“孟子言性,当随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谓性’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后谓之性耳,故不同,继之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然不害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极本穷源之性。”)人与禽兽得之也同,(程子所谓“不害为一”,朱子于《中庸》“天命之谓性”释之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而致疑于孟子,(朱子云:“孟子言‘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欠中间一转语,须着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异”始得,恐孟子见得人性同处,自是分晓直截,却于这些子未甚察。”)是谓性即理,于孟子且不可通矣,其不能通于《易》《论语》固宜,孟子闻告子言“生之谓性”,则致诘之,程朱之说,不几助告子而议孟子欤?①
这里引了伊川之说。伊川认为,一来,孟子书中的“性”,须要随文看,有时指本然之性,有时指气质之性,二性并存,一是先天本然之性,二是后天落在气质中的性。二来,告子的“生之谓性”,并非全错。告子的“生之谓性”也是性,只不过是指受生之后的性,也就是气质之性,不同于孟子所强调的本然之性。只要区分出《孟子》书中的两种性,则孟、告争议即可平息。①而伊川的这些想法,其兄明道早已言及。明道言: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灭若敖氏之类),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②
明道以为,人生而静之上不容说者,乃本然之性;可说者,即是气质之性,这也可比配于告子的“生之谓性”。此气质之性,性即于气,气即于性,原来只是本然之性落于气中者,如此一来,则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本性虽善,但因落于恶的气质之中,也就表现不出其本善。前面伊川的话,便是对其兄明道思想之阐发,而明道此段,大致也可用伊川“气质之性”的理念来做诠释。
伊川又说,犬之性、人之性、牛之性,虽在显现上不同,但不害其本性为一。这样的说法,其实已经翻了孟子的案了。如《孟子》原文:“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孟子·告子上》)意思是,此三性并不同,犬性亦不同于牛性,虽都是动物,但本性不同。
而伊川却说“不害其为一”,此所谓“理一分殊”,如月印万川,天下海、湖之月影稍异,然本源为同一之月、同一之天理,天理即性,万物皆同具本然之性,而性即理也。万物虽同具一个性理,但因人、牛、犬等所禀气质不同,所表现出的本性之程度也就不同。人得其秀而最灵,人的气质中所表现出的本然之性较多;动物则较少,亦有些微道德性之表现,如羔羊跪乳、蜂蚁有君臣之义等。这些论调已与孟子不同,当是一种创造性之诠释,或可用以解决历来各家论性之争议,如荀、扬等人之说。
(二)朱子对二程之承继
程子尝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③而朱子继之而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孟子终是未备,所以不能杜绝荀、扬之口。”④论性不论气者,指孟子,而论气不论性者,指荀、扬。亦是说,性论之所以历来分歧,无法定于一尊,乃因各家所言之性不一,孟子所言,乃终极的天地之性,而荀、扬则是以气为性。直到程子,才算真正解决各家之纷争,而得以杜绝荀、扬之口。
然如船山质疑程朱此说,曰:“程子固以孟子言性未及气禀为不备矣,是孟子之终不言气禀可知已。”①船山意思是:若以孟子性论有所不备,则知孟子终究未曾言及气禀呀!
不过,朱子于《孟子集注》中,仍是以气禀之说来做诠释。如《孟子·告子上》“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一段,关于“命”者,概有所禀与所值,禀其气清,则行义也易。此所言“命”,亦同于“天命之谓性”一处,天命者,本然之性也,而此性亦在气中。
故朱子注“天命之谓性”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②人、物各率其性,人率人性,马率马性,都是天理之生,而表现在气禀之中。朱子又言:“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③于是要人修道、进德修业。这便是程朱的气禀义。
戴震于“人与禽兽得之也同”一句后面,又引朱子《中庸》“天命之谓性”之注,即朱子所注,业已视人、物之间是本根、同性,故不害其为一,即人性、物性源于同一性。
朱子这些说法,亦曾在韩国儒学界引发著名的“湖洛论争”,主要争辩人、物性之同或异?依于朱子,人、物性是为同一性,所谓“不害其为一”者,皆源于同一个天理;不过,朱子亦说人、物性分殊,此因后天所禀气质不同,致使所表现出的“理一”多寡有别。而即便是动物,亦有健顺五常之德,只是气禀较偏,只能微性(道德性)之表现,不若人之周全,然人、物性却是本源同一的!四、性中有无食色?
(一)戴震:性中有食
依朱子“气质之性”说,性善为本然之性,性中没有食色,食色者,气质之性也。朱子注“告子曰:食色性也”处言:“告子以人之知觉运动者为性,故言人之甘食悦色者即其性。”④若再加上伊川之语,则可知“食色性也”亦是“生之谓性”之性,亦同于《论语》的“性相近”,皆属气禀之性。总之,在“性即理”中,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没有孝悌,更没有食色。
然戴震有不同看法,他主张“唯有血气心知之一性”,合于血气与心知而为一性,是为“一本说”。性中自有血气、嗜欲、食色……如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又如上文提到,戴震认为“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云云,此非比喻之说,而是指即便是“刍豢之悦我口”,亦是性!
此如韩国儒学古学派之代表人物丁茶山所言“性是嗜欲”,以为所谓的“动心忍性”,其中的性何以要忍?以性即是欲故,当须用忍,不容私欲之任意勃发。孟子也有“可欲之谓善”的说法,这也近于戴震的“性中有食色”。
再来参看戴震以下之诠释:
问: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张子云:“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云:“仁义礼智,天道在人,则赋于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浊,然而性善可学而尽,故不之命。”宋儒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本于《孟子》此章,以气质之性君子不谓之性,故专取义理之性,岂性之名君子得以意取舍欤?
曰:非也,性者,有于己者也,命者,听于限制也,谓性犹云借口于性耳,君子不借口于性之自然以求遂其欲,不借口于命之限之而不尽其材,后儒未详审文义,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谓性,非不谓之性,不谓命,非不谓之命。①
这里,问者因张子“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之言,视张子亦只说天地之性,而不谈气质,于是将张子等同于程朱,皆以天地之性为本性,而排除了气质。
然而,张子亦言:“性其总,合两也。”合于天地之性与声色之性。又曰:“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②而张子对于《孟子·告子上》“口之于味”章的诠释,也颇为地道,其言:“养则付命于天,道则责成于人。”③此甚得孟子之旨。
(二)唐君毅:以道德引导食
关于戴震上述说法,可以参看唐君毅先生之评论,其言:
清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以《礼记》之血气心知之性释孟子,谓声色臭味之欲,根于血气,仁义礼智为心知,并皆为性,乃以借口释谓字,说孟子立言之旨,非不谓声色臭味之欲为性,而只言人不当借口于性以逞其欲,此亦明反于孟子之“不谓性”之明言,亦与孟子他处言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处处即心言性,不即声色臭味之欲言性之旨相违。④
看来,唐先生并不苟同戴震之说法,认为其说将有违于孟子之旨。不过,唐先生也不赞成朱子之解法,如言:
朱子承程子之言,于上一命字,以品节限制释之,而于下一命字,则曰谓仁义礼智之性,所禀有厚薄清浊,故曰命,此又以人之天生之气质之性之差别为命,对同一章之命字,先后异训,即自不一致。朱子尝谓气质之说,起于张、程,又何能谓孟子已有此说?①
同一“命”字,于同一章内,却有前后不同意思,如此说法,显得牵强。再者,由既有文献来看,可以说“气质之性”一语,起于张子、程子,又怎能牵扯上孟子早有气质之说呢?对此,唐先生亦是颇不以为然的。
唐先生倾向于一种做法——撷取各家之长,或凡合于孔孟之旨者,便来导出他所认为合宜之诠释。从侧重的角度来看,唐先生亦是将血气之性与道德之性合而为一,再以道德之性而来引导食色之性,这种方式最终还是与戴震一致。只不过戴震是先将二性合一而论,先总说一性;唐先生则是先分解为二性,而后再将二性合一。
若回到《孟子》原文,心官则思,应当从其大体,继以大体引领小体,以德性引导食色,孟子本义如此,戴震亦不敢违背。戴震“君子不谓性”之诠说,应是指:君子不会借口食色亦是天性,而随意放纵,在命之不可得时,亦能随遇而安。
五、物性之辨
(一)人性、物性之辨
依朱子的“性即理”说,人性、物性本源同一,彼此之不同,只在于禀气之殊异,人得其秀而最为灵气,性理之表现亦多,而动物却因气禀所限较多,仅能部分表现道德性。至于戴震则有不同见解,他认为,人是道德之存有,其心知可以知仁义,而悦于仁义,然动物则缺,以物之类种与人不同之故,并非道德之存有一类,无法表现仁义。
此外,戴震所定义的性,将随种类之不同而不同;人性与牛性不同,牛性与犬性也不同。关于后者的牛性、犬性之异,朱子则不强调,于是戴震批评朱子这点,其曰:
朱子释《孟子》有曰:“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如其说,孟子但举人、物诘之可矣,又何分牛之性、犬之性乎?犬与牛之异,非有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不得谓孟子以仁义礼智诘告子明矣。在告子,既以知觉运动为性,使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告子何不可直应之曰“然”?斯以见知觉运动不可概人物,而目为蠢然同也。②
这里举了朱子注《孟子·告子上》“生之谓性”章一段,表示人与物之同者,在于食、色等动物性,统称为知觉运动,人、物皆能知觉,皆能运动。不过,朱子此说,与孟子之说稍异;若依孟子,人、物虽都有动物性,都能知觉运动,但其中之内容毕竟有别,如孟子尝言:“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孟子·告子上》)此则显示人、马于性类上之殊途。且口味亦性也。
(二)物性之辨
上文引言,戴震更强调物物亦别的概念,以物与物之间应是分属于不同类种,亦如《孟子》原文:“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若只是分辨人与物之不同,则孟子只要举例“牛之性”犹如“人之性”便罢,为何还多了一句“犬之性犹牛之性”?
戴震这里的言下之意,似乎在凸显,朱子之所诠无法契合于孟子原意;孟子所表达的,当是一种类概念,即不只人、牛不同,至于犬、牛亦不同。朱子只是大要地说:知觉运动之蠢然,人与物同,而仁义礼智之粹然,人与物异。孟子此章,只谈人、物之辨,而不提犬、牛之辨。
若回到《孟子》原文,则孟子亦看到牛性与犬性之间的殊异,此由犬能看门而牛能耕作之不同表现上看出,可见牛与犬并不同类,性亦不同。则朱子此章之诠,便显得不够周全。
戴震以为,若孟子只谈人、物之异,则只要说一句“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就好,“犬之性犹牛之性”云云,则为多余,但朱子似未认清物性之间亦有不同这点,其过失归根结底即在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性之分说,以及把“性”定义为天理、仁义礼智等说法有其弊病。
六、结语与反思
历来汉宋之争,宋儒之于汉学,总认定汉学仅是一种训诂之学,如朱子曰:“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①不过,朱子自己对于汉儒文献之抄录与批判,甚少下过功夫。既然缺乏论据,则朱子的批评也就难以服人。若是清儒,如戴震——作为汉学之一派,对于宋学程朱学派之批评,则用功甚多,他将宋儒作品逐条抄出,而后进行评判及论证,如此做法,说服力较高。②
到了近代之“当代新儒家”,其立场则又倾向于宋学,同时也对汉学特别是清代汉学做出批评。个中翘楚,如唐君毅先生认为,戴震视“理”为分理、文理、肌理,只看到先秦于“理”之区分处,而不见其整全,只见于“理”之静态性,而不知其动态性。总之,将“理”视为文理、分理,并非先秦之唯一说法。
唐先生之相关批评,收于其著《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约20页之篇幅①,其论述甚是有力。他举出戴震之缺失有三:
其一,孟子乃“即心言性”,如孟子言:“仁义礼智根于心。”不过,依笔者拙见,孟子除了“即心言性”之外,亦有“即生言性”②,如告子提出“生之谓性”处,孟子不辩,而只辩其义外。
其二,《孟子》原文“口之于味”等等,“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唐先生认为在性中有命的,如口味,这得之不得有命,故在君子而言,不谓此为性。此处也是唐先生对戴震的反驳,因为他举出,孟子都视口味等,在君子不谓性了。然笔者认为,《孟子》原文也有提到“性也,有命焉”,但仍是性。而唐先生最后以道德之真性可包括口味之次味,则亦是融入戴震之说了。
其三,戴震谓,性乃血气心知,而能达情遂欲。唐先生则问,则由此血气心知,如何达到仁义?若是后者,当需自觉主宰,方能达办,此与达情遂欲,恐怕已是两层问题,而非戴震之一元气论所能解决。③唐先生强调,这里要有一股精神之转折,方能由己情之达,而生同理心之自立立人、已达达人,自己若无其情,则不能知晓他人之情。这是发生顺序之义理,而非以性理来领导生理。
唐先生的第三点,可说非常有力。但若站在戴震立场,当须掌握达情遂欲之中相感相通之情,而将此情上看、高看即可。因戴震只是气论之一层、一元,其情将不同凡响、不能低看,总只有这一层,而须即情即理。乃一种依心知而能自觉,从一般之情,而为理想感通之情。
唐先生亦以为,朱子之论性,所谓“性即理”,乃是依于伊川之发明,而朱子之“心统性情”,则是来自张子,并于其性论之建构,区分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这一连串的发展,难以溯及孔孟之说。④若强以此套建构来诠释孔孟之性,则非孔孟原意。朱子的确需要回答戴震之质问,除了戴震之外,明清之际的许多学者,如阮元、焦循等,以及日本之江户学者伊藤仁斋等,都对程朱有所批评。
唐先生最后以“即心言性”来包括“即生言性”,同理,是否也可把朱子的“性即理”,用以收摄性即气之一面?另一方面,戴震的血气心知、情欲,是否亦能上提而收摄同理心?然无论如何,都不能违反大体摄小体的原则。这些做法,或许更能接近孟子原意。大致上,唐先生似有调和汉宋之意,视两派各有优缺点,而欲平彰汉宋,各美其美。笔者以为,唐先生之论证力道,足以抗衡汉学,而为新宋学之坚强学者,值得吾辈关注。
(原载《孔学堂》2021年第2期,作者单位: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
附注
①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文》卷六一〇,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58页。
②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8页。
①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上,《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4页。
①黄庭坚:《濂溪诗》,《全宋文》第104册卷二二七九,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
②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上册,第16页。
③胡宏:《知言疑义》,《胡宏集》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33页。
①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上册,第17页。
②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0页。
③周敦颐:《通书·颜子第二十三》,《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2—33页。
①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上册,第17—18页。
②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一,《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109页。
①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七《易义·困》,《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
②胡瑗:《周易口义》卷八《困》,《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03页。
③程颐:《周易程氏传》卷四《经下·困》,《二程集》下册,第940页。
④程颐:《周易程氏传》卷四《经下·困》,《二程集》下册,第941页。
⑤程颐:《周易程氏传》卷四《经下·困》,《二程集》下册,第941页。
①黄宗羲、全祖望:《草庐学案·草庐精语》,《宋元学案》卷九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38页。
①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55页。
②李泽厚:《论语今读》,第256页。
③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70—472页。
①卢守助:《晏子春秋译注》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7—238页。
②荀悦:《申鉴》,《诸子集成新编》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页。
③范晔:《后汉书》第9册,卷八十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35—2636页。
①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44页。
②何晏、邢昺:《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五,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49页。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48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三,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11页。
②辅广:《辅广集辑释》中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907页。
③朱熹:《论孟精义》,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64页。
①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819—820页。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0页。
③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864页。
①陈天祥:《四书辨疑》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3页。
②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31页。
③王夫之:《四书训义》,《船山全书》第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759页。
①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45页。
②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436页。
③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2页。
④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46页。
①荻生徂徕:《辨名·君子小人》,《荻生徂徕全集》第1卷,东京: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第459页。
①荻生徂徕:《论语征》,松平赖宽:《论语征集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029页。
②参见乐爱国:《朱熹解<论语>中的“君子”“小人”》,《江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③汤一介:《略论儒学的和谐观念》,《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①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849页。
②吴震:《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极”解释——以朱熹<皇极辨>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③丁四新:《再论(尚书·洪范)的政治哲学——以五行畴和皇极畴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④王博:《从皇极到无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此外,刘增光《皇极根于人心——陆九渊的洪范学》亦纳象山皇极之教于政治哲学范畴,载《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会议论文集》,第510—522页。
⑤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①陈来已提及朱子皇极解的根本目的就是使民“归心教化”,但并未展开论述。参见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53—3454页(本文涉及朱子文献,皆是《朱子全书》2002年版,以下不再标注)。作为初本的《皇极辨初稿》本段内容与改本差别较大,初本无“顺五行、厚八政,极仁极孝”等说。载《朱子全书》第26册,第727页。
①在《皇极辨》初本第一个补记中,朱子已以孝、悌为例来阐明至极:“以孝言之,而天下之孝至此无以加;以弟言之,则天下之弟至此而无小过也。”《朱子全书》第26册,第730页。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认为朱子此处已经“把初本的补记一的思想增写在这里。”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55页。
③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55页。末句中的“至极”,初本为“天下”,改后更加扣紧皇极和对应全文。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55页。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2025页。
③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55页。
④唐仲友亦言:“‘建用皇极’者,善民之习而复其性也。”《帝王经世图谱》卷三《皇极建用之图》,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927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9页。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2655页。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635页。
③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136页。
④朱子《静江府虞帝庙碑》中认为舜是配天立极,“熹窃惟帝之所以配天立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八,《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99页。《武夷七咏·天柱峰》“只说乾坤大,谁知立极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朱子全书》第20册,第455页。朱子指出,司马光等人反驳王安石以僖祖为不祧之祖的观点是“以为太祖受命立极,当为始祖”,可见“立极”与“皇极”一并,已成为宋代学者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观点。《面奏祧庙札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朱子全书》第20册,第726页。
⑤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17册,第431页。
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55页。初本无“从君”,初本“教以修身求福之道”被改为“因其自名而与之以善”,更扣紧文本。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55页。末句初本为:“虽彼之所以移于此者,迟速真伪、才德高下有万不同;而吾之所以应于彼者,矜怜抚奄,恳恻周尽,未尝不一也。”《朱子全书》第26册,第729页。文字主要差别除“移”改为“化”外,把“真伪”改为“浅深”,表明这是程度问题,与“宽广”保持一致,亦与前文“因其自名而与之以善”相贯通。去除“才德高下”。改“矜怜抚奄,恳恻周尽”为“长养涵育”,突出养而育之的教养义。最后一句补充“心”字,体现了以心为教的特色。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56页。初本为:“言民皆不溺于己之私”,与改本同为“化私”之意。《语类》亦指出君王立极与民观而化是上下一体,教政合一,以教为本。“言王者之身可以为下民之标准也。貌之恭,言之从,视明听聪,则民观而化之。……敛者,非取之于外,亦自吾身先得其正,然后可以率天下之民以归于正,此锡福之道也。”《朱子语类》卷七十九,第2710页。
③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56页。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56页。
②“首出庶物”之说已见于《皇极辨》初本:“故惟曰聪明睿智,首出庶物,如所谓‘天下一人而已’者。”《朱子全书》第二十六册,第730—731页。
③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2704页。
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867页。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56—3457页。
③朱子说:“今人说中,只是含胡依违,善不必尽赏,恶不必尽罚。如此,岂得谓之中!”《朱子语类》卷七十九,第2706页。
④“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则不患不至于圣贤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称之者,但恕字之义,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于人,而不可以施之于己。……若汉之光武,亦贤君也,一旦以无罪黜其妻,其臣郅恽不能力陈大义以救其失,而姑为缓辞以慰解之……光武乃谓恽为善恕己量主,则其失又甚远,而大启为人臣者不肯责难陈善以贼其君之罪。一字之义,有所不明,而其祸乃至于此,可不谨哉!”朱熹:《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38页。
①《朱子语类》卷七十九,第2708页。象山亦特别重视格君心之非,反复致意于此,此是其与朱子之同处。如“格君心之非,引之于当道,安得不用其极”。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5页。“今时人臣逢君之恶,长君之恶则有之矣。所谓格君心之非,引君当道,邈乎远哉!”《陆九渊集》,第179页。
②符叙舜功云:“象山在荆门,上元须作醮,象山罢之。劝谕邦人以福不在外,但当求之内心。于是日入道观,设讲座,说‘皇极’,令邦人聚听之。次日,又画为一图以示之。”《朱子语类》卷七十九,第2712页。有学者认为象山《讲义》具有明心学、倡教化、回应朱子的三重目的。方旭东认为象山上元讲皇极与道教有关。《上元醮与皇极——陆九渊(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发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③陆九渊:《陆九渊集》,第28页。
①陆九渊:《陆九渊集》,第284页。
②朱子曾反思之前自己亦曾以天道、人道思想阐发《洪范》,后觉不妥而放弃之。“向来亦将天道人事分配为之,后来觉未尽,遂已之。”《朱子语类》卷七十九,第2714页。
③陆九渊:《陆九渊集》,第235页。
④陆九渊:《陆九渊集》,第284页。
⑤陆九渊《宜章县学记》提到“降衷”被堵的情况:“功利之习入于骨髓,杨朱、墨翟、告子、许行之徒,又各以其说,从而诬之。帝降之衷,茅塞甚矣。”《陆九渊集》,第230页。
①余英时认为阳明心学由“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王阳明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我们不妨称之为‘觉民行道’,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190页。吴震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的导论中着重从儒家德福之道及天人感应的角度讨论了皇极。
②如“上帝降衷于下民”通乎《大学章句序》“天降生民以仁义礼智之性”,指人性之善本自天赋;气禀、智识论通乎气禀不齐,不全乎性说,解释现实人性之不善;“以斯道觉斯民”通乎“为君师之教以复性”说,落实为圣贤教化之道,使人皆能保全降衷之性。可见象山与朱子皇极解不仅有别,实亦有同。
③陆九渊:《陆九渊集》,第113页。
①陆九渊:《陆九渊集》,第308页。
②陆九渊:《陆九渊集》,第228页。
③陆九渊:《陆九渊集》,第229—230页。
④陆九渊:《陆九渊集》,第284页。
①象山此处特别提及“中国夷狄”之分,可能与荆门彼时为“次边”之地有关,“中国夷狄”之分具有激发民众抗敌爱国之情的意味。另一种可能是思想文化之别,象山不满荆门设醮祈福之风,希望以儒家德性教化之学来扭转风气,激发民众归本儒学之教的用意。
②陆九渊:《陆九渊集》,第237页。
③陆九渊:《陆九渊集》,第284页。
④陆九渊:《陆九渊集》,第285页。
①陆九渊:《陆九渊集》,第422页。
②牟宗三亦以心论德福一致。“一切存在之状态随心转,事事如意而无所谓不如意,这是福。这样,德即存在,存在即德,德与福通过这样的诡谲的相即,便形成德福浑是一事。”牟宗三:《圆善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249页。
③陆九渊:《陆九渊集》,第306页。
①陆九渊:《陆九渊集》,第435页。
②陆九渊:《陆九渊集》,第270页。
③陆九渊:《陆九渊集》,第127页。
④陆九渊:《陆九渊集》,第239页。
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10页。
②陈来指出,“陆九渊这一儒家文化实践是值得赞赏的。”“朱子这个批评似不恰当,盖陆氏是对民众施行教化,不是解经论学,应不必在此处进行学术辨析。”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吴震《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极”解释——以朱熹<皇极辨>为中心》亦指出,朱熹对陆九渊之论乃“一酷评”,“未免说得有点过重”。
①李景林:《教化的哲学·绪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李景林:《教化论视域中的儒学·绪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①程颢、程颐撰,潘富恩导读:《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②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85页。
③程颐在其《易传》自序中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
①系年据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787页。
①刘砥于朱子61岁所记语录也有一条说:“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此天地之心、性、情也。”(《语类》卷五,《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3页)
①此条为李闳祖记于朱子59岁以后。
②此条为刘砥记于朱子61岁时,为在论及才、性、情、心关系时所说。
③此条为曾祖道记于朱子68岁时。按:《朱子全书》此条把从“其体谓之道”到“则谓之情”都引为程子的话,标点当有误。“而其理属之人”后实际上是朱子的发挥。底本把程子的话引为“其体谓之道,其用谓之神”有脱字,与程子原话“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比较,如果“则”视为省略字,当脱“谓之易,其理”五字。诸《语类》整理本此条标点皆有误,皆未注意到此。
①此条为程端蒙所记,时间在朱子50岁至62岁期间。
①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9—20页。
①陈来:《仁学本体论》,第214页。
②但是前面又说“功用兼精粗而言,是说造化”。
①牟宗三说:“此第三语又随意加一‘鬼’字,非是。”(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页)笔者认为若联系程颐所说“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那么加“功”字、“鬼”字非随意,当是有意为之。
②朱子把“其用则谓之神”理解为“鬼神”,可能也是联系到程子原文引述到《中庸》“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第25页。
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第25页。
③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7页。
④吴震:《朱子思想再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19页。
①张卫红认为:“朱子心论的重点实为气之‘灵’,从形质构成、认知功能以及心识的生成结构来看,心都具有形而上下之间的特性,处于未受气禀私欲遮蔽的经验心之先,朱子称为‘本然之体’‘心之全体’等。本然心具有超越性,是经验心的真正根源,也是中和新说、心统性情等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础。”(《朱子“心论”的层面与超越性特质:兼与阳明“心论”比较》,《中国文化》2020年第1期)
②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192页。
③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194页。
④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94页。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第21—22页。
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第21页。
③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第20页。
①朱熹:《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第2页。
②见其《孟子字义疏证》之作:“性”者,依《礼记·乐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一段,解为血气心知。
③如注疏《论语》,其中的代名词,如“学而时习之”的“之”,多以“理”字填充。到了朱子弟子陈淳的《北溪字义》,虽亦精于训诂,但仍以朱子之说为宗,以理学进行建构。
①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汤志钧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91—292页。
①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第272页。
①“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者也。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朱熹:《孟子集注》卷八,《四书章句集注》,第297页)
②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第292页。
①朱熹:《论语集注》卷九,《四书章句集注》,第175—176页。
②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第292页。
③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四书章句集注》,第326页。
①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第292—293页。
①其实,孟子正是反对告子的“生之谓性”,性是类的原则,若一律以生释之,则牛性同于人性,亦同犬性,皆有其生之故,个别类则不显。
②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程集》,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第10页。
③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六,《二程集》,第81页。
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九,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38页。
①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139页。
②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17页。
③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17页。
④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四书章句集注》,第326页。
①戴震:《绪言上》,《戴震集》,第369—370页。
②张载:《正蒙》,《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2、63页。
③见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四书章句集注》,第370页。
④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唐君毅全集》第15卷,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22页。
①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唐君毅全集》第15卷,第21—22页。
②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第294页。
①朱熹:《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2页。既然缺乏论据,则朱子的批评也就令人难以服气。
②笔者以为,章句训诂未必不好,亦能融沁身心而成为性命之学,宋儒若真欲批评,理应确实指出汉儒于义理上有何偏差,而借此昭告世人,以为简择。如唐君毅先生指出汉儒、清儒于孟子义理中的自觉、自证、自我提点的工夫义,常只是视而不见。
①可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唐君毅全集》第12卷,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27—46页。
②如孟子言:“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此为即生言性。
③可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唐君毅全集》第12卷,第84—87页。
④程朱为何区分二性?一来是因理学之建构、理气论之构思,二者,则欲借此解决历代之性论分歧,而杜荀、扬等辈之口。不过,如此做法反而引发后世纷争,不甚完备。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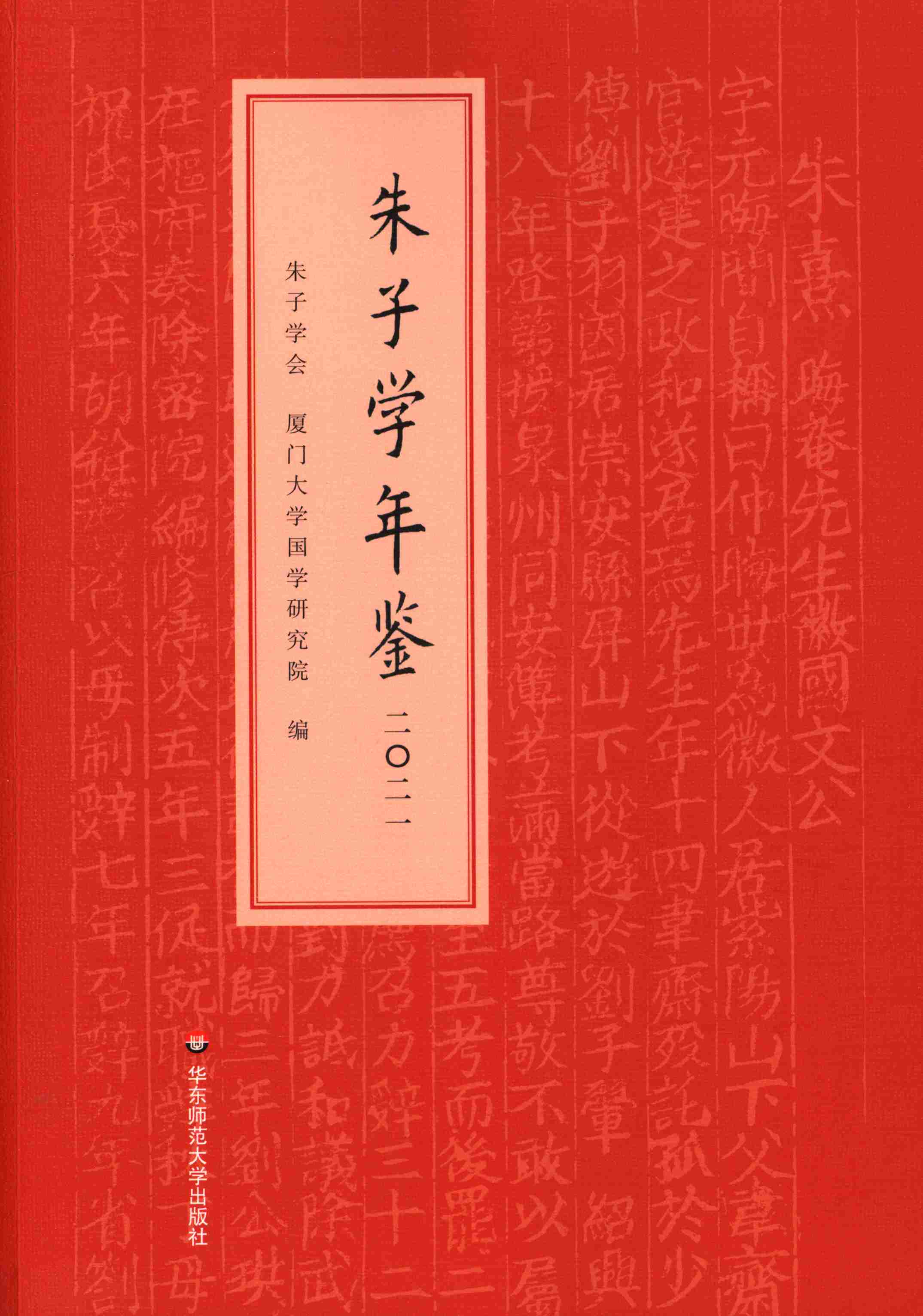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1》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共9部分: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学界概况、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收录《融突和合论——中国哲学元理》《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2021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简介》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