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理双彰:朱熹论礼、理关系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与朱子后学》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6718 |
| 颗粒名称: | 礼理双彰:朱熹论礼、理关系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4 |
| 页码: | 139-16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礼和理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礼是理的具体表现形式,而理是涵盖一切自然、社会、人生、事物规律、法则的本体概念。朱熹强调实践和内心的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礼和理的关系。同时,他也认为礼必须是人性的自然发用,也即是“心之所安”。 |
| 关键词: | 朱熹 儒学 宋代 |
内容
“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①这是皮锡瑞对经学史上汉、宋学术特点的总概括。借用“礼”“理”二字,我们来分析朱熹的礼学思想,就不难发现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朱熹多言理,而少论礼吗?朱熹是怎样认识对待礼、理关系的?朱熹是在怎样的学术思想背景下论述礼、理关系的?
事实上,朱熹关于礼、理关系的思想综合了先秦和宋代诸儒的意见,在继承和批评的基础上形成了礼、理双彰的思想。朱熹的礼、理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既重视高明的形上学理论建构,又强调下学工夫的践履,既重视理的本体理论综合,又重视礼的工夫论。朱熹礼、理双彰的思想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体现,也是其思想能够深远影响中国以及东亚政治和社会的根本原因。
一、以理释礼——形上本体的礼
“礼者,理也。”这一观念,实为二程、张载以来理学家的共识②。朱熹也以理来释礼。他说:“礼只是理,只是看合当恁地。”③礼是理应然的体现。对《离娄章句下》中“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朱熹这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朱熹礼学研究”(09BZS03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宋礼学研究”(18AZX010)。
样解释:“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则随事而顺理,因时而处宜,岂为是哉?”①理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早已成为一个涵盖一切自然、社会、人生、事物规律、法则的本体概念,它统摄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彰显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②礼无疑就是天理、天道中的一件,天理是礼文制度中的礼义精髓。“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则谓之道,以其各有条理而言则谓之理。其目则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其实无二物也。”③同时朱熹还指出,“《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④。也就是说,礼经、乐经也同样是天理的体现与承载。
再者,朱熹认为礼是天理之自然。以“节文”“仪则”来释礼,强调礼的约束、规范意义,朱熹也的确注意到礼中严格的等级差异,礼数、礼容、礼器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严毅不可侵犯之处。朱子说“礼是严敬之意”⑤,甚至说“礼如此之严,分明是分毫不可犯”⑥。可是这样的论述怎样才能与理学家所宣扬的人主动对礼的服膺联系起来呢?黄榦曾说:“观《玉藻》《乡党》所载,则臣之事君,礼亦严矣。……如‘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谓至严矣!”⑦朱熹赶紧强调严与和都应统一在礼中:“至严之中,便是至和处,不可分做两截去看。”⑧“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⑨也就是说,礼是天理的自然流露,没有丝毫强人之处。
但朱子并不同意以“天经地义”的观念阐释“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之言:“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子太叔又继而阐发子产此义:“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①在朱熹看来,将“礼”看作“天经地义”的准则,而要人委曲自己的情感以求合于“礼”,是将人的情感与礼截然二分。如子产、子太叔所言,“礼”是外在于人且毋庸置疑的准则。朱子对《左传》所载这段议论提出异议,他认为子产、子太叔所言“只说是人做这个去合那天之度数”“都是做这个去合那天,都无那自然之理”②。“自然之理”,即所谓“理”“天理”。“礼乐者,皆天理之自然。节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乐也是天理自然有底。……所谓礼乐,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则无不可行也。”③这里的“自然”之意仍然强调礼乃是对宇宙秩序的模仿,人的个体性情和社会名分都是天秩、天序的条理的展现,因此礼的本源就是自然。朱熹说:
盖圣人制礼,无一节是强人,皆是合如此。……尝谓吕与叔说得数句好,云:“自斩至缌,衣服异等,九族之情无所撼;自王公至皂隶,仪章异制,上下之分莫敢争。皆出于性之所有,循而行之,无不中节也。”此言礼之出于自然,无一节强人。须要知得此理,则自然和。④
因为礼是圣人综合考虑天、人的特点及其关系所制定出来的,量身定制的礼怎么会是强迫人的呢?天理的自然本来就是差序等级的体现,万物参差不齐,各得其所,人间秩序也是如此。人知得此礼,内心充满恭敬,同时行得此礼,自然和乐。
“礼”之合于天理,即是说礼必须是人性的自然发用,也即是“心之所安”。《论语·阳货》所载孔子回答宰我对“三年之丧”的质问时说:“女安,则为之。”①这一回答最可说明礼必须在与本心相应的情况下,才能显现其价值。朱子也从人内心的真情实感谈礼的意义,《朱子语类》中记载:
或问:“哀慕之情,易得间断,如何?”曰:“此如何问得人?孝子丧亲,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岂待抑勒,亦岂待问人?只是时时思慕,自哀感。所以说‘祭思敬,丧思哀’。只是思着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别人如何抑勒得他?”因举“宰我问三年之丧”云云,曰:“‘女安则为之!’圣人也只得如此说,不当抑勒他,教他须用哀。只是从心上说,教他自感悟。”②
如果只是依从别人的指挥,而没有真切的情感,则礼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换言之,礼的真实意义,即外在举止与内心情感的充分和谐。
在朱熹看来,礼作为天理之自然,本身就是表里如一、内外交流的自然状态。朱子说:“礼是恭敬底物事,尔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许多般模样;乐是和乐底物事,尔心中自不和乐,外面强做和乐,也不得。心里不恁地,外面强做,终是有差失。纵饶做得无差失,也只表里不相应,也不是礼乐。”③而人们认识到礼是天理之自然,才能知行合一,内外交融。又说:“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铿锵鼓舞,许多劳攘,当不得那礼乐。”④总之,朱熹都在强调礼文繁密丰富,需要学者操存持守、笃实践履的地方很多,但是如果能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就能达到与天理自然合一的境界,而根本不知规矩、规范为何物。朱熹说:“所谓礼者,正以礼文而言,其所以为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若曰循理而天理自然合,则又何规矩之可言哉?”①朱熹论礼为天理之自然,表面上看来在论证礼的属性,而最终目的是在强调人必须通过修养心性而主动践履礼仪的必要性。
朱熹以理释礼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追求礼治秩序的重建,他对秩序的认识仍然是承袭张载、二程的观点。程颐说:“《书》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②朱熹在此基础上继续阐发说: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当处者,谓之叙;因其叙而与之以其所当得者,谓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天秩,便是那天叙里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这个叙,便是他这个自然之秩。③
朱熹通过阐释天叙、天秩都是自然的次序,具有恒久的稳定性和不可抗逆的属性,从而强调人伦关系和礼制等级的天然性。在人间社会实行的典礼,都产生于天叙天秩之下,但凡礼文、礼制、礼乐都不是圣人自出机杼制作的,而是天定的。朱熹说:
“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悙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许多典礼,都是天叙天秩下了,圣人只是因而敕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谓冠昏丧祭之礼,与夫典章制度,文物礼乐,车舆衣服,无一件是圣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圣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将去。如推个车子,本自转将去,我这里只是略扶助之而已。④朱熹这一思想与荀子不依据天道观念以建立人道的思想,把礼乐视为人道而非天道的思想不同。荀子在吸收批判老庄思想的基础上认为,自然之天与人为各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不能借崇拜自然来反对人为,同样也不能以自然的无为来反对礼乐。在荀子的思想中,既然天是无可取法的,又不能示人以典范,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礼义法度,就只有仰赖君子与圣人来发明创造。荀子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①荀子认为是圣人立礼义法度用来制约、适应后天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并非来自先天的自然性。“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②这些思想是与其性伪之分,天人之分的观点相应的。朱熹则继承二程、张载天人合一的主张,认为人性善,性即理,天道与人道有着一致性。
二、不以理易礼——下学工夫的礼
朱熹用天理来阐释礼,既是基于宇宙本体论来统括指导礼治社会,也是对人间礼制秩序形而上的提升。这是理学家孜孜以求的建构儒学本体论的需要,也是理学心性理论发展的最终目标,沟通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从而重建社会秩序。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朱熹也有不用天理说礼处。在朱熹看来,礼虽隶属、表现天理,但礼、理并非可以相互替代。朱熹强调不能以理易礼主要表现在解释“克己复礼归仁”和“约之以礼”两句上。朱熹说:
“克己复礼”,不可将“理”字来训“礼”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复天理。不成克己后,便都没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这里恰好着精细底工夫,故必又复礼,方是仁。圣人却不只说克己为仁,须说“克己复礼为仁”。见得礼,便事事有个自然底规矩准则。③
“约之以礼”,“礼”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节文处。①
之所以不能用“理”来代替“礼”,关键在于说“复理”“约理”就会脱离现实精细的践履工夫,会导致学者们学无持守。“复礼”“约礼”,才能在实践中认识到事事有个自然的规矩准则,才能依照确定的规范礼仪行事持守。有门人问朱熹:“所以唤做札而不谓之理者,莫是礼便是实了,有准则,有着实处?”朱子回答说:“只说理却空去了。这个礼是那天理节文,教人有准则处。”②朱熹认为,光说理而不复礼,会少一节践履工夫。而此点正是儒家与佛教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在朱熹看来,儒、佛都讲克己,但强调“复礼”的教化却是儒家显著的特征之一。他说:
若是佛家,侭有能克己者,虽谓之无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复得礼也。圣人之教,所以以复礼为主。若但知克己,则下梢必堕于空寂,如释氏之为矣。③
然而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礼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谓之有私欲。只是他元无这礼,克己私了,却空荡荡地。他是见得这理元不是当。克己了,无归着处。④
释氏之学,只是克己,更无复礼工夫,所以不中节文……吾儒克己便复礼,见得工夫精粗。⑤
佛家克己而不能复礼,因此容易陷入空虚寂寥之处,而无所依归。儒家既克己又复礼,个人对私欲的抑制与对礼仪的践履成为修身的基本工夫,着眼点还是在现实社会人生中寻求安顿。
早在《克斋记》中朱熹就指出:“予惟‘克’‘复’之云,虽若各为一事,其实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故克己者,乃所以复礼,而非克己之外别有复礼之功也。”①为了能将这一思想更加明确,朱熹索性用复礼来论克己,说:
礼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说个“复”,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复礼。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复得这一分天理来;克得那二分己去,便复得这二分礼来。且如箕踞非礼,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虽未能如尸,便复得这些个来。②
且如坐当如尸,立当如齐,此礼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则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齐,方合礼也。③
朱熹强调礼是内在于人本身的秩序和准则,克己和复礼并非有明确的先后顺序,而是同时进行的。“克己便是复礼,不是克己了,方待复礼,不是做两截工夫。”④克己复礼本属一项工夫,不得分作两项说。“克己,则礼自复;闲邪,则诚自存。非克己外别有复礼,闲邪外别有存诚。”⑤所谓克己,实际上只不过是天理战胜人欲,克去非礼自然就能复礼。《论语集注》:“私胜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而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之流行矣。”⑥
依据朱熹是否用“理”释“礼”,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在对待礼、理关系上的两层考虑。首先,朱熹认为“礼是那天地自然之理”,此理可以贯通“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所代表的繁文缛节,千条万绪的曲礼、威仪都是天理的体现⑦。这是体察到了礼的形而上层面。其次,朱熹不以“理”训“礼”在于强调礼是“归宿处”,是持守用力节文处①。这是强调礼所具备的形而下的践履工夫层面。朱熹对礼、理关系的认识正可以这样概括,既要认识到礼所具有的天理、心性的内涵,又要能在实践中忠实履行。当有人问“这‘礼’字恁地重看”时,朱熹回答说:
只是这个道理,有说得开朗底,有说得细密底。“复礼”之“礼”,说得较细密。“博文、约礼”,“知崇、礼卑”,“礼”字都说得细密。知崇是见得开朗,礼卑是要确守得底。②
用理来释礼,就是说得“开朗处”。不用理来训礼,是因为认识到礼有“细密”的节文,最终目的是要践履确守。用朱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得个正当道理而有所归宿尔”③。
朱熹关于礼、理关系的两重论述是否正如清儒所说,存在中、晚年礼学思想转型的问题呢?阮元认为:“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故理必附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④除去清儒张扬礼学的一般成见外,阮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朱熹讲礼、理关系存在一定的变化。翻检有关资料,我们也能发现一些材料说明此点。1170年,朱熹在给林用中的信中提到:
程子言敬,必以整齐严肃、正衣冠、尊瞻视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论。而先圣说克己复礼,寻常讲说,于“礼”字每不快意,必训作“理”字然后已,今乃知其精微缜密,非常情所及耳。⑤
这说明朱熹在四十岁左右认识到的“克己复礼”之说,是服膺程颐以理训礼的,主张复礼就是复天理。1192年,赵致道给朱熹的信中提到:“不曰理而曰礼者,盖言理则隐而无形,言礼则实而有据。礼者,理之显设而有节文者也,言礼则理在其中矣。”①朱熹对此论表示肯定。“礼便是节文升降揖逊是也。但这个‘礼’字又说得阔,凡事物之常理皆是。”②这说明朱熹确实有从理回归到礼的趋向。前面《朱子语类》中的晚年之论,也是主张不能以理训礼,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呢?
实际上,朱熹之所以强调不能以理训礼,主要针对陆九渊心学,意在纠正二程及后学的礼、理观。这些批评直接集中在对“克己复礼归仁”一句的解释上。譬如陆九渊在论“克己复礼”时就认为“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而且“只是有一念要做圣贤”就可。朱熹认为“此等议论,恰如小儿则剧一般,只管要高去,圣门何尝有这般说话!”③在朱熹看来,二程及其后学同陆学一样,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悬空说理的势头,重克己之说,轻复礼之实,远离了儒学平易、踏实的践履工夫,必须从理论上予以扭转。
程颢自从体贴出天理来之后,与其弟子论学都不免以“天理”“天道”来重新解释儒家的一般概念范畴。比如以“道”解“仁”,认为克己就是得道。他与弟子韩持国有一番讨论:
明道尝论克己复礼,韩持国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错否?”曰:“如公所言,只是说道也。克己复礼,乃所以为道也。”
又韩持国尝论:“克己复礼以谓克,却不是道。”先生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国又言:“道则不须克。”先生言:“道则不消克,却不是持国事,在圣人则无事可克,今日持国须克得己,然后复礼。”又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积习侭有功,礼在何处。”又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于礼非有异也。”又曰:“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①
在韩持国看来,道既然是无所不在也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应该是自足而无欠缺的,也就无须“克”来修持体验道。如果在事上克己,也就不能称其为道了。程颢指出韩持国在论道时应该顾及为道之方的层面。《论语》中的主题“为仁之方”,在程颢理学的诠释框架中已经悄然地为“为道之方”所替代。程颢指出道不是可以自然而然就能获得的,必须通过“修道之谓教”的修养工夫。但是,程颢在解释“四勿”时,又不免将仁与礼混为一谈,不自觉地偏向强调“克己”的内在面。钱穆先生曾指出,朱熹偶有将克己复礼分作两项说的时候,乃“依违于明道之说而未达十分之定见”②。但朱熹最终还是认为程颢所论“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礼文,而礼意已得”,认为这个“说得不相似”,“说得忒高了”。在朱熹看来克己、复礼“是合掌说底”,不能执于一偏③。
程颢以道释仁,范祖禹则以理代礼。范祖禹这样解释“克己复礼”:
克己,自胜其私也,胜己之私则至于理。礼者,理也,至于理则能复礼矣。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克己也。不迁怒,不贰过,复礼也。夫正与是出于理,不正不是则非理也。视听言动无非礼者,正心而已矣。为仁由己,在内故也。克己复礼,时天下之善皆在于此矣。天下之善在己,则行之一日可使天下之仁归焉。夫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则非颜子所及,而尧舜修身以治天下,亦惟视听言动无非礼而已矣。④
在此段中范祖禹虽然认识到尧舜修身治天下皆本于礼,可谓认识到了礼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至于理则能复礼”,未免说得过于轻松随意。而且他以知行、是非是否合理来论礼,认为正心即可复礼,说得笼统轻巧,没有切实的下手工夫。难怪朱熹一针见血地指出:“范氏之说则其疏甚矣。”①
谢良佐(1050—1103)继承和发展了程颢的仁说思想,以知觉言仁。他强调礼的重要性,但认为遵循天理就可以上达而天,下学至礼。整体上强调天理以及合理的优先性。
曰:“礼者,摄心之规矩。循理而天,则动作语默无非天也。内外如一,则视听言动无非我矣。”或问:“言动非礼则可以正,视听如何得合礼?”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则多非礼,故仁者先难而后获。所谓难者,以我视、以我听、以我言、以我动也。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视听不以我也,胥失之矣。”或问:“视听言动合理,而与礼文不相合,如何?”曰:“言动犹可以礼,视听有甚礼文。以斯视、以斯听,自然合理,合理便合礼文,循理便是复礼。”或问:“求仁如何下工夫?”曰:“如颜子视听言动上做亦得,如曾子颜色容貌上做亦得。出辞气者,犹佛所谓从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诺,若不从心中出,便是不识痛痒。古人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不见不闻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汉不识痛痒了。又如仲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如见大宾如承大祭底心在,便长识痛痒。”又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就性上看。”又曰:“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克己之私,则心虚见理矣。”②
谢良佐认为礼是制约和统摄“心”的规矩。但谢良佐着重论述了心的作用和功能:心可以领悟到天理,在克尽一己性之偏私后能够“心虚见理”;心可以管摄视听言动,循心而可以体验到仁;以我心去视听言动,就能自然合理、复礼。朱熹称赞谢良佐对礼的定义和认识,认为“善矣”。但朱熹紧接着批评:
然必以理易礼而又有“循理而天自然合礼”之说焉,亦未免失之过高而无可持循之实。盖圣人所谓礼者,正以礼文而言,其所以为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若曰循理而天,自然合理,则又何规矩之可言哉。其言克己之效则又但曰“克己之私则心虚见理”,则是其所以用力于此者,不以为修身践履之当然,特以求夫知之而已也。①
朱熹认为谢良佐礼、理说的最大弊病还是在于“以理易礼”:重视天理之体验,忽视礼文之规矩;重视知克己之理,忽视行复礼之实。朱熹认为谢良佐和吕大临一样,都是“所论失之过高而无可持循之实”。
游酢(1053—1123)为二程高弟,同样主张万物一体为仁。游酢强调心之本体就是仁,明确提出仁是本心,仁为心之本体的思想,主张人能反其本心,便能达到万物一体的仁之境界。游酢说:
孟子曰:“仁,人心也。”则仁之为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体则喜怒哀乐之未发者是也。惟其徇己之私,则汩于忿欲,而人道熄矣。诚能胜人心之私,以还道心之公,则将视人如己,视物如人,而心之本体见矣。自此而亲亲,自此而仁民,自此而爱物,皆其本心,随物而见者然也,故曰克己复礼为仁。礼者,性之中也。且心之本体一而已矣,非事事而为之,物物而爱之,又非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也。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无适而非仁矣。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天下归仁,取足于身而已,非有藉于外也,故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请事斯语,至于非礼勿动则不离于中,其诚不息而可久矣,故能三月不违仁。虽然,三月不违者,其心犹有所操也。至于中心安仁,则纵目之所视,更无乱色。纵耳之所听,更无奸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发育万物,弥纶天地,而何克己复礼,三月不违之足言哉?此圣人之能事,而对时育万物者,所以博施济众也。仁至于此,则仲尼所不敢居,而且罕言也。然则仁与圣乌乎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则为贤,纵之则为圣。苟未至于纵心,则于博施济众未能无数数然也。”①
游酢认为礼本来体现的就是人性中和的一面,不必日积月累于事事、物物中求之,只要修持心性就能达到仁。游酢此论心性比吕大临、谢良佐更为直截简易,因而遭致朱熹的严厉批评:
游氏之说以为视人如己,视物如人,则其失近于吕氏,而无天序天秩之本,且谓人与物等则,其害于分殊之义为尤甚。以为非必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无适而非仁者,则又陷于释氏顿悟之说,以启后学侥幸躐等之心。以为安仁则纵目所视而无乱色,纵耳所听而无奸声,则又生于庄周、列御寇荒唐之论。②
朱熹认为高妙与落实是分辨异端与儒学的关键。朱熹之所以痛切批评吕、游之说,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儒者如果一味说得高妙,就容易与异端如佛、道、墨、法等家同流而失却根基。在朱熹看来,游酢所论“视人如己、视物如人”,就是只认识到理一之处,而没有认识到儒家所论分殊之处,没有明确辨析合同的亲亲原则与别异的尊尊原则,就失去了对天秩天序下分殊之理的认识。朱熹还指出游酢释“非礼勿动”,只不过将“中”“诚”等好字拼凑总聚,表现出种种晦涩之处③。朱熹认识到这些都是悬空说理或义理所带来的流弊,因此朱熹力求回到礼的节文形态,主张将儒学“复礼”说得着实明白。
程门高弟中,杨时(1053—1135)因独邀耆寿而对南宋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比起其他程门学者来说,杨时更为注重“求仁之学”。杨时注重孟子“仁者人也”的说法,主张于静中体验求仁之方,此论对朱熹的老师李侗影响很深。杨时所论“克己复礼为仁说”为:
仁,人心也。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而已。放而不知求,则人欲肆而天理灭矣。杨子曰:“胜己之私谓之克。”克己所以胜私欲而收放心也。虽收放心,闲之为艰,复礼所以闲之也。能常操而存者,天下与吾一体耳,孰非吾仁乎?颜渊其复不远,庶乎仁者也,故告之如此,若夫动容周旋中礼,则无事乎复矣。①
杨时强调克己求放心的求仁工夫,认为收放心即可,复礼实际上是“无事”的闲工夫。朱熹认为复礼正是儒学精微、切实的下学工夫,因而批评杨时“以为先克己而后复礼以闲之,则其违圣人之意远矣”②。针对杨时所论“道非礼,则荡而无止;礼非道,则梏于仪章器数之末”,朱熹说:
盖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礼者道体之节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后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礼为德,而欲以凝夫道,则既误矣。而又曰:“道非礼,则荡而无止;礼非道,则梏于仪章器数之末,而有所不行。”则是所谓道者,乃为虚无恍惚元无准则之物,所谓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于道也,其诸老氏之言乎,误益甚矣。③
杨时原意也是欲沟通道与礼,强调两者相互影响、依赖的关系,在朱熹看来,“杨氏以为先克己,而后复礼以闲之,则其违圣人之意远矣”④。杨时认为克己、复礼两分为先后顺序,朱熹认为此言有将道与礼割裂的趋势,言道则为“虚无恍惚,元无准则”,言礼、德则有待于道才能成,又有流于道家的危险,因而需要加以批判。杨时门下的张九成(1092—1159)也祖述程颐的礼、理观念,其论“克己复礼”云:“己者,何也?人欲也。礼者,何也?天理也。灭天理,穷人欲,何由而得仁?灭人欲尽天理,于是乃为仁。”①朱熹认为这是杜撰学问、脱空狂妄之论,只以念虑论礼,而没有强调“居处恭,执事敬”“坐如尸,立如齐”等具体应该履行的礼,实际上就不是礼,也就不能真正理解礼的内涵和作用②。总之,朱熹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厘清礼、理关系,就有可能会不自觉流入释老。只有强调平实亲切的以礼文为依托的日用常行工夫,才能真正掌握儒学发展的命脉。
尹焞(1061—1132)在论述礼、理关系时表现出谨遵师说之处:
弟子问仁者多矣,唯对颜子为尽。问何以至于仁,曰复礼则仁矣。礼者,理也,去私欲则复天理。复天理者,仁也。礼不可以徒复,唯能克己所以复也。又问克己之目,语以视听言动者。夫然,则为仁在内,何事于外乎?盖难胜莫如己私,由乎中而应乎外,制其外所以养其中。视听言动必以礼,而其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是之谓复天理。颜子事斯言而进乎圣人,它弟子所不能及也。③
朱熹认同尹焞所论“由乎中而应乎外,制其外所以养其中。视听言动必以礼,而其心不正者未之有也”。但是朱熹认为这也是“庶几近之”,主要的毛病还是表现在“以理易礼”,特别是“以复礼为仁”之说,“亦失程子之意矣”④。有门人曾问及朱熹在编《集注》时为何没有取尹焞之说,朱熹回答说:“不欲其只说复理而不说‘礼’字。盖说复礼,即说得着实;若说作理,则悬空,是个甚物事?”⑤这说明朱熹已经严格地将礼、理关系进行了界定,并以此为标准对二程及其后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与批评。
应该指出的是,程门弟子对“克己复礼归仁”说做出的种种诠释都是在天理论建构中的理学思想,均致力于以天理来重新整合儒学传统中的概念、范畴,目的都是形成有宋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他们强调克己的内圣工夫,注重对天理的体悟,这都是理学倾向“内在”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新儒学特色之所在。虽然他们做出的种种努力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朱熹,但朱熹站在学术思想发展的新起点上,出于健全理学体系的需要,才尽心剖析于“浅深、疏密、毫厘之间”①。
在礼、理关系上,朱熹最终还是服膺于程颐之说,一方面朱熹替程颐“礼即是理也”的说法进行辩护,认为程颐的本义是“礼之属乎天理,以对己之属乎人欲,非以礼训理,而谓真可以此易彼也”②。朱熹的意思是程颐强调“礼即理”,并非“以理易礼”,后学直接论“复礼”为“复天理”,撇开复礼环节,只重视克己灭人欲存天理,实际上是误解了程颐之意。另一方面,朱熹在编撰《集注》时全文抄录程颐之说,强调克己复礼的践履工夫:
程子曰:“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颜渊事斯语,所以进于圣人。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视箴》曰:“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其《听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其《言箴》曰:“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伤烦则支。己肆物忤,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其《动箴》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①
程颐为礼、理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格局,礼是天理体现于人间的秩序,克己是胜己之私,消除内心的蔽障和偏失的欲望才能体会到天理。同时礼并不完全是外在的束缚,而是发自内在本性的应对事物的中和行为。视听言动正是克己复礼的下手之处。程颐的《四箴》正是体现了既克己又复礼的切实可循的下学工夫。强调克己是持久的不能间断的工夫,也是需要大毅力、大勇气去恪守的道德规范。《四箴》中“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正是表达了这种内外交相发用,反身存诚,习与性成的修养工夫。克己只有用礼作为衡量标准时,才能真正达到仁的境界。程颐强调“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只有礼时,方始是仁处”。朱熹在阅读程颐此论时特亲笔注明:“克己复礼为仁,言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是乃仁也。”②朱熹正是看到程颐不仅很好地沟通礼、仁、理三者的关系,同时又提供了具体可以操作的克己复礼的修养条目,体现了儒学所著力的根本所在。朱熹对程门后学“以理易礼”说的批评正基于他们或多或少偏离了程学精义,朱熹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使得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确做到了采众人之长,折流俗之谬,明圣传之统。
三、朱子的礼学:以理事、体用释礼
朱熹对礼的理解,最终可以用“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来概括,此两句出自《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一章朱子的注解③。“节文”一词见于《礼记·坊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檀弓下》也说:“辟踊,哀之至也;有筭,为之节文也。”孔颖达将“节文”解作“准节文章”①,也就是“调节与文饰”之意。“节文”二字,又见于《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朱熹在《集注》中将“节文”解释为“品节文章”。
在其他一些注释中,朱熹主要倾向于以“节文”定义礼:“礼,节文也。”②在释《中庸》“亲亲之大,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时,认为礼是亲亲尊贤的节文,礼是节文仁义的体现③。在释“非天子不议礼”时认为,“礼,亲疏贵贱相接之体也”④。释《论语·为政篇》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时,朱熹认为“礼,谓制度品节也”⑤。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时,认为“礼,即理之节文也”⑥。释“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时,说“礼,谓义理之节文”⑦。总的来说,朱熹倾向于用内蕴天理的“制度”“节文”来释礼。
曾祖道曾这样理解“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谓“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见其大概之所宜,然到礼上方见其威仪法则之详也。节文仪则,是曰事宜”。曾祖道侧重挖掘礼为文、为事的内涵,朱熹则提醒他“更就天人上看”⑧。这说明在朱熹的理解中,礼正是沟通天人的有效手段,体现天人合一的现实载体。
关于此句,陈淳的解释似乎最得师意,他以体用先后关系来分析礼的内涵:
文公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以两句对言之,何也?盖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于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见于人事,人事在外而根于中。天理其体而人事其用也。“仪”谓容仪而形见于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与“文”字相应。“则”谓法则、准则,是个骨子,所以存于中者乃确然不易之意,与“节”字相应。“文”而后“仪”,“节”而后“则”,必有“天理之节文”而后有“人事之仪则”,言须尽此二者,意乃圆备。①
首先,陈淳指出天理与人事之间的关联,天理只是人事中的理,天理是人事的中心,天理在内,人事在外,天理为礼之体,人事为礼之用。这样从天理、人事的角度理解了礼。接着陈淳指出“仪”“文”同有外在显现之容制,“则”“节”共为内在确定不易之准则。最后此两句之间是有着先后顺序的,“天理之节文”是“人事之仪则”的条件,这样强调礼之内在精义的优先性。经过陈淳的阐释,朱熹关于礼的内涵似乎已经很完备了,可是用体用先后关系来论礼,符合朱熹的原意吗?
的确,朱熹早年曾用“体”来说礼。后来换用“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来论礼,这期间有什么微妙的变化吗?我们再来看一段朱熹与弟子们关于此句的讨论:
问:“先生昔曰‘礼是体’。今乃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似非体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乡谈,才见分段子,便说道是用,不是体。如说尺时,无寸底是体,有寸底不是体,便是用;如秤,无星底是体,有星底不是体,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纸糊,此便是体;人摇之,便是用。”杨至之问体,曰:“合当底是体。”②此处朱熹虽然没有直接回答礼是体还是用的问题,但根据朱熹对体用的认识,他的主旨还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礼兼备体用。礼无疑是“体”,“当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体,故仁义礼智为体”①。礼同时兼具体用两面,“如尺与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铢,则体也;将去秤量物事,则用也”②。礼是道理与用处的结合,“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③。在朱熹看来,礼既是应该如此的道理,又是可以权衡、践履的标准和工夫。“礼者,道体之节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后乃能行之也。”④礼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朱子曾说:“学者学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则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⑤从这些讨论来看,在早年朱熹多强调礼为体的一面,因而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朱熹则强调礼兼备体用,沟通天人,是形上道理和形下人事的有机结合。
朱熹认为礼同时具备理和文两方面属性。他说:“所因之礼是天做底,万世不可易;所损益之礼,是人做底,故随时更变。”⑥礼中蕴含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都是不变的天理,是礼相因袭而不能轻易变更的根据,而礼文制度则是损益变化的已然之迹。朱熹说:“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则自今以往,或者继周而王者,虽百世之远,所因所革亦不过此,岂但十世而已乎!”⑦但从偏正结构“天理之节文”的描述来看,朱熹似又更强调礼作为“节文”的属性。
朱熹认为所谓文章就是“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①。“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②朱熹也肯定陈淳所言“文”大要就是“文理可观之谓”③。朱熹重视礼文,认为动容周旋的礼文就是礼之实体,就是礼的体现。“五声十二律,不可谓乐之末,犹揖逊周旋,不可谓礼之末。若不是揖逊周旋,又如何见得礼在那里?”④在秩序亟待重建的南宋社会,朱熹认为重视礼文也是对礼之本的追求。朱熹认为孔子答林放问礼之本,“然俭戚亦只是礼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当文时,不可一向以俭戚为是”⑤。正如颜炳罡所指出的:“朱熹直接挑战孔子,似乎处处与孔子相反。孔子时代,礼乐的危机主要是形式化的危机,礼乐还存在,朱熹的时代,礼乐不再是形式化的危机,而是没有几人精通古礼了,所以他要求重建礼乐的形式——揖逊周旋。”⑥朱熹在其解说《论语·子罕》中颜渊所说的“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一句时,朱熹说:“圣人教人,只此两事。博文工夫固多,约礼只是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则是天理。礼者,天理之节文。节谓等差,文谓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乡党》一篇乃圣人动容周旋皆中礼处。”⑦总的来说,朱熹既重视礼的内涵,又强调礼的形式。
为什么朱熹会用理事关系来论礼呢?这里有必要结合理学思想的发展来解释。为了反对二氏哲学中“体用殊绝”,程颐在继承张载学说的基础上特别指出:“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①这一论述是指《周易》深奥的义理蕴含于错综复杂的卦象之中,理与象不能分割,同出一源。程颐所说的体,是指事物内藏而不彰显的原理和根源,用是指各种现象。后来程颐进一步拓展此思想,说:“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②这说明在程颐看来,理是事物的本质,事物是理的表现,两者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相互统一的。程颐以理为事物内部深奥而微妙的原理,把事物看作理的表征,以理为体,以事为用,认为体用是统一的,强调本体和现实的密切联系。后来朱熹、陈淳用理事、体用论礼都受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
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事的体用一源的思想。他说:“‘体用一源’者,自理而观,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显微无间’者,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③同时朱熹从“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上”这一思想明确化,讨论了理、事的先后问题。这就是说,在一切事物尚未产生时,事物的规律、原理、法则就已经存在,理不因事物存在、出现与否而有所改变。如果要探寻永恒存在的理,就必须通由事才能得到。同样,朱熹关于礼的定义就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不可否认的是,朱熹以“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来名礼,也的确抓住了礼有礼义精微、礼制彰显的两面,为新儒学的礼教体系提供了有之可循的制度仪则,引发了儒者们对礼的内涵的重视与探讨。
这里还有必要讨论一下的是清儒对朱熹用理、事论礼的批评。清代以凌廷堪为代表的经史学家,特标举“以礼代理”的旗帜反攻理学。他们认为以“理”来名学就缺乏合理性,根本不是正统儒家学术的表述。凌廷堪说:“考《论语》及《大学》皆未尝有理字,徒因释氏以理事为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义,是以宋儒论学,往往理事并称。……无端于经文所未有者,尽援释氏以立帜。……故鄙儒遂误以理学为圣学矣。”①凌氏意在指责理学乃是借用佛学之绪余,而非圣学。所言“宋儒论学往往理事并称”,实际上是在讽刺朱熹言礼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虽然学者们早就有结论,程朱理学受华严宗的影响很深②,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理学家正是在借用佛教思想体系和范畴的过程中通过反思儒学,同时在批判佛道的基础上才确立新儒学精致的哲学思想体系。他们的立场仍然是坚定不移的儒学立场。因此,虽然清儒对朱熹有诸多批判,但也遮蔽不了我们真实了解学术思想史的目光。
事实上,朱熹关于礼、理关系的思想综合了先秦和宋代诸儒的意见,在继承和批评的基础上形成了礼、理双彰的思想。朱熹的礼、理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既重视高明的形上学理论建构,又强调下学工夫的践履,既重视理的本体理论综合,又重视礼的工夫论。朱熹礼、理双彰的思想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体现,也是其思想能够深远影响中国以及东亚政治和社会的根本原因。
一、以理释礼——形上本体的礼
“礼者,理也。”这一观念,实为二程、张载以来理学家的共识②。朱熹也以理来释礼。他说:“礼只是理,只是看合当恁地。”③礼是理应然的体现。对《离娄章句下》中“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朱熹这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朱熹礼学研究”(09BZS03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宋礼学研究”(18AZX010)。
样解释:“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则随事而顺理,因时而处宜,岂为是哉?”①理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早已成为一个涵盖一切自然、社会、人生、事物规律、法则的本体概念,它统摄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彰显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②礼无疑就是天理、天道中的一件,天理是礼文制度中的礼义精髓。“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则谓之道,以其各有条理而言则谓之理。其目则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其实无二物也。”③同时朱熹还指出,“《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④。也就是说,礼经、乐经也同样是天理的体现与承载。
再者,朱熹认为礼是天理之自然。以“节文”“仪则”来释礼,强调礼的约束、规范意义,朱熹也的确注意到礼中严格的等级差异,礼数、礼容、礼器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严毅不可侵犯之处。朱子说“礼是严敬之意”⑤,甚至说“礼如此之严,分明是分毫不可犯”⑥。可是这样的论述怎样才能与理学家所宣扬的人主动对礼的服膺联系起来呢?黄榦曾说:“观《玉藻》《乡党》所载,则臣之事君,礼亦严矣。……如‘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谓至严矣!”⑦朱熹赶紧强调严与和都应统一在礼中:“至严之中,便是至和处,不可分做两截去看。”⑧“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⑨也就是说,礼是天理的自然流露,没有丝毫强人之处。
但朱子并不同意以“天经地义”的观念阐释“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之言:“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子太叔又继而阐发子产此义:“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①在朱熹看来,将“礼”看作“天经地义”的准则,而要人委曲自己的情感以求合于“礼”,是将人的情感与礼截然二分。如子产、子太叔所言,“礼”是外在于人且毋庸置疑的准则。朱子对《左传》所载这段议论提出异议,他认为子产、子太叔所言“只说是人做这个去合那天之度数”“都是做这个去合那天,都无那自然之理”②。“自然之理”,即所谓“理”“天理”。“礼乐者,皆天理之自然。节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乐也是天理自然有底。……所谓礼乐,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则无不可行也。”③这里的“自然”之意仍然强调礼乃是对宇宙秩序的模仿,人的个体性情和社会名分都是天秩、天序的条理的展现,因此礼的本源就是自然。朱熹说:
盖圣人制礼,无一节是强人,皆是合如此。……尝谓吕与叔说得数句好,云:“自斩至缌,衣服异等,九族之情无所撼;自王公至皂隶,仪章异制,上下之分莫敢争。皆出于性之所有,循而行之,无不中节也。”此言礼之出于自然,无一节强人。须要知得此理,则自然和。④
因为礼是圣人综合考虑天、人的特点及其关系所制定出来的,量身定制的礼怎么会是强迫人的呢?天理的自然本来就是差序等级的体现,万物参差不齐,各得其所,人间秩序也是如此。人知得此礼,内心充满恭敬,同时行得此礼,自然和乐。
“礼”之合于天理,即是说礼必须是人性的自然发用,也即是“心之所安”。《论语·阳货》所载孔子回答宰我对“三年之丧”的质问时说:“女安,则为之。”①这一回答最可说明礼必须在与本心相应的情况下,才能显现其价值。朱子也从人内心的真情实感谈礼的意义,《朱子语类》中记载:
或问:“哀慕之情,易得间断,如何?”曰:“此如何问得人?孝子丧亲,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岂待抑勒,亦岂待问人?只是时时思慕,自哀感。所以说‘祭思敬,丧思哀’。只是思着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别人如何抑勒得他?”因举“宰我问三年之丧”云云,曰:“‘女安则为之!’圣人也只得如此说,不当抑勒他,教他须用哀。只是从心上说,教他自感悟。”②
如果只是依从别人的指挥,而没有真切的情感,则礼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换言之,礼的真实意义,即外在举止与内心情感的充分和谐。
在朱熹看来,礼作为天理之自然,本身就是表里如一、内外交流的自然状态。朱子说:“礼是恭敬底物事,尔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许多般模样;乐是和乐底物事,尔心中自不和乐,外面强做和乐,也不得。心里不恁地,外面强做,终是有差失。纵饶做得无差失,也只表里不相应,也不是礼乐。”③而人们认识到礼是天理之自然,才能知行合一,内外交融。又说:“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铿锵鼓舞,许多劳攘,当不得那礼乐。”④总之,朱熹都在强调礼文繁密丰富,需要学者操存持守、笃实践履的地方很多,但是如果能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就能达到与天理自然合一的境界,而根本不知规矩、规范为何物。朱熹说:“所谓礼者,正以礼文而言,其所以为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若曰循理而天理自然合,则又何规矩之可言哉?”①朱熹论礼为天理之自然,表面上看来在论证礼的属性,而最终目的是在强调人必须通过修养心性而主动践履礼仪的必要性。
朱熹以理释礼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追求礼治秩序的重建,他对秩序的认识仍然是承袭张载、二程的观点。程颐说:“《书》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②朱熹在此基础上继续阐发说: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当处者,谓之叙;因其叙而与之以其所当得者,谓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天秩,便是那天叙里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这个叙,便是他这个自然之秩。③
朱熹通过阐释天叙、天秩都是自然的次序,具有恒久的稳定性和不可抗逆的属性,从而强调人伦关系和礼制等级的天然性。在人间社会实行的典礼,都产生于天叙天秩之下,但凡礼文、礼制、礼乐都不是圣人自出机杼制作的,而是天定的。朱熹说:
“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悙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许多典礼,都是天叙天秩下了,圣人只是因而敕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谓冠昏丧祭之礼,与夫典章制度,文物礼乐,车舆衣服,无一件是圣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圣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将去。如推个车子,本自转将去,我这里只是略扶助之而已。④朱熹这一思想与荀子不依据天道观念以建立人道的思想,把礼乐视为人道而非天道的思想不同。荀子在吸收批判老庄思想的基础上认为,自然之天与人为各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不能借崇拜自然来反对人为,同样也不能以自然的无为来反对礼乐。在荀子的思想中,既然天是无可取法的,又不能示人以典范,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礼义法度,就只有仰赖君子与圣人来发明创造。荀子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①荀子认为是圣人立礼义法度用来制约、适应后天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并非来自先天的自然性。“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②这些思想是与其性伪之分,天人之分的观点相应的。朱熹则继承二程、张载天人合一的主张,认为人性善,性即理,天道与人道有着一致性。
二、不以理易礼——下学工夫的礼
朱熹用天理来阐释礼,既是基于宇宙本体论来统括指导礼治社会,也是对人间礼制秩序形而上的提升。这是理学家孜孜以求的建构儒学本体论的需要,也是理学心性理论发展的最终目标,沟通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从而重建社会秩序。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朱熹也有不用天理说礼处。在朱熹看来,礼虽隶属、表现天理,但礼、理并非可以相互替代。朱熹强调不能以理易礼主要表现在解释“克己复礼归仁”和“约之以礼”两句上。朱熹说:
“克己复礼”,不可将“理”字来训“礼”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复天理。不成克己后,便都没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这里恰好着精细底工夫,故必又复礼,方是仁。圣人却不只说克己为仁,须说“克己复礼为仁”。见得礼,便事事有个自然底规矩准则。③
“约之以礼”,“礼”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节文处。①
之所以不能用“理”来代替“礼”,关键在于说“复理”“约理”就会脱离现实精细的践履工夫,会导致学者们学无持守。“复礼”“约礼”,才能在实践中认识到事事有个自然的规矩准则,才能依照确定的规范礼仪行事持守。有门人问朱熹:“所以唤做札而不谓之理者,莫是礼便是实了,有准则,有着实处?”朱子回答说:“只说理却空去了。这个礼是那天理节文,教人有准则处。”②朱熹认为,光说理而不复礼,会少一节践履工夫。而此点正是儒家与佛教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在朱熹看来,儒、佛都讲克己,但强调“复礼”的教化却是儒家显著的特征之一。他说:
若是佛家,侭有能克己者,虽谓之无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复得礼也。圣人之教,所以以复礼为主。若但知克己,则下梢必堕于空寂,如释氏之为矣。③
然而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礼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谓之有私欲。只是他元无这礼,克己私了,却空荡荡地。他是见得这理元不是当。克己了,无归着处。④
释氏之学,只是克己,更无复礼工夫,所以不中节文……吾儒克己便复礼,见得工夫精粗。⑤
佛家克己而不能复礼,因此容易陷入空虚寂寥之处,而无所依归。儒家既克己又复礼,个人对私欲的抑制与对礼仪的践履成为修身的基本工夫,着眼点还是在现实社会人生中寻求安顿。
早在《克斋记》中朱熹就指出:“予惟‘克’‘复’之云,虽若各为一事,其实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故克己者,乃所以复礼,而非克己之外别有复礼之功也。”①为了能将这一思想更加明确,朱熹索性用复礼来论克己,说:
礼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说个“复”,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复礼。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复得这一分天理来;克得那二分己去,便复得这二分礼来。且如箕踞非礼,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虽未能如尸,便复得这些个来。②
且如坐当如尸,立当如齐,此礼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则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齐,方合礼也。③
朱熹强调礼是内在于人本身的秩序和准则,克己和复礼并非有明确的先后顺序,而是同时进行的。“克己便是复礼,不是克己了,方待复礼,不是做两截工夫。”④克己复礼本属一项工夫,不得分作两项说。“克己,则礼自复;闲邪,则诚自存。非克己外别有复礼,闲邪外别有存诚。”⑤所谓克己,实际上只不过是天理战胜人欲,克去非礼自然就能复礼。《论语集注》:“私胜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而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之流行矣。”⑥
依据朱熹是否用“理”释“礼”,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在对待礼、理关系上的两层考虑。首先,朱熹认为“礼是那天地自然之理”,此理可以贯通“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所代表的繁文缛节,千条万绪的曲礼、威仪都是天理的体现⑦。这是体察到了礼的形而上层面。其次,朱熹不以“理”训“礼”在于强调礼是“归宿处”,是持守用力节文处①。这是强调礼所具备的形而下的践履工夫层面。朱熹对礼、理关系的认识正可以这样概括,既要认识到礼所具有的天理、心性的内涵,又要能在实践中忠实履行。当有人问“这‘礼’字恁地重看”时,朱熹回答说:
只是这个道理,有说得开朗底,有说得细密底。“复礼”之“礼”,说得较细密。“博文、约礼”,“知崇、礼卑”,“礼”字都说得细密。知崇是见得开朗,礼卑是要确守得底。②
用理来释礼,就是说得“开朗处”。不用理来训礼,是因为认识到礼有“细密”的节文,最终目的是要践履确守。用朱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得个正当道理而有所归宿尔”③。
朱熹关于礼、理关系的两重论述是否正如清儒所说,存在中、晚年礼学思想转型的问题呢?阮元认为:“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故理必附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④除去清儒张扬礼学的一般成见外,阮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朱熹讲礼、理关系存在一定的变化。翻检有关资料,我们也能发现一些材料说明此点。1170年,朱熹在给林用中的信中提到:
程子言敬,必以整齐严肃、正衣冠、尊瞻视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论。而先圣说克己复礼,寻常讲说,于“礼”字每不快意,必训作“理”字然后已,今乃知其精微缜密,非常情所及耳。⑤
这说明朱熹在四十岁左右认识到的“克己复礼”之说,是服膺程颐以理训礼的,主张复礼就是复天理。1192年,赵致道给朱熹的信中提到:“不曰理而曰礼者,盖言理则隐而无形,言礼则实而有据。礼者,理之显设而有节文者也,言礼则理在其中矣。”①朱熹对此论表示肯定。“礼便是节文升降揖逊是也。但这个‘礼’字又说得阔,凡事物之常理皆是。”②这说明朱熹确实有从理回归到礼的趋向。前面《朱子语类》中的晚年之论,也是主张不能以理训礼,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呢?
实际上,朱熹之所以强调不能以理训礼,主要针对陆九渊心学,意在纠正二程及后学的礼、理观。这些批评直接集中在对“克己复礼归仁”一句的解释上。譬如陆九渊在论“克己复礼”时就认为“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而且“只是有一念要做圣贤”就可。朱熹认为“此等议论,恰如小儿则剧一般,只管要高去,圣门何尝有这般说话!”③在朱熹看来,二程及其后学同陆学一样,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悬空说理的势头,重克己之说,轻复礼之实,远离了儒学平易、踏实的践履工夫,必须从理论上予以扭转。
程颢自从体贴出天理来之后,与其弟子论学都不免以“天理”“天道”来重新解释儒家的一般概念范畴。比如以“道”解“仁”,认为克己就是得道。他与弟子韩持国有一番讨论:
明道尝论克己复礼,韩持国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错否?”曰:“如公所言,只是说道也。克己复礼,乃所以为道也。”
又韩持国尝论:“克己复礼以谓克,却不是道。”先生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国又言:“道则不须克。”先生言:“道则不消克,却不是持国事,在圣人则无事可克,今日持国须克得己,然后复礼。”又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积习侭有功,礼在何处。”又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于礼非有异也。”又曰:“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①
在韩持国看来,道既然是无所不在也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应该是自足而无欠缺的,也就无须“克”来修持体验道。如果在事上克己,也就不能称其为道了。程颢指出韩持国在论道时应该顾及为道之方的层面。《论语》中的主题“为仁之方”,在程颢理学的诠释框架中已经悄然地为“为道之方”所替代。程颢指出道不是可以自然而然就能获得的,必须通过“修道之谓教”的修养工夫。但是,程颢在解释“四勿”时,又不免将仁与礼混为一谈,不自觉地偏向强调“克己”的内在面。钱穆先生曾指出,朱熹偶有将克己复礼分作两项说的时候,乃“依违于明道之说而未达十分之定见”②。但朱熹最终还是认为程颢所论“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礼文,而礼意已得”,认为这个“说得不相似”,“说得忒高了”。在朱熹看来克己、复礼“是合掌说底”,不能执于一偏③。
程颢以道释仁,范祖禹则以理代礼。范祖禹这样解释“克己复礼”:
克己,自胜其私也,胜己之私则至于理。礼者,理也,至于理则能复礼矣。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克己也。不迁怒,不贰过,复礼也。夫正与是出于理,不正不是则非理也。视听言动无非礼者,正心而已矣。为仁由己,在内故也。克己复礼,时天下之善皆在于此矣。天下之善在己,则行之一日可使天下之仁归焉。夫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则非颜子所及,而尧舜修身以治天下,亦惟视听言动无非礼而已矣。④
在此段中范祖禹虽然认识到尧舜修身治天下皆本于礼,可谓认识到了礼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至于理则能复礼”,未免说得过于轻松随意。而且他以知行、是非是否合理来论礼,认为正心即可复礼,说得笼统轻巧,没有切实的下手工夫。难怪朱熹一针见血地指出:“范氏之说则其疏甚矣。”①
谢良佐(1050—1103)继承和发展了程颢的仁说思想,以知觉言仁。他强调礼的重要性,但认为遵循天理就可以上达而天,下学至礼。整体上强调天理以及合理的优先性。
曰:“礼者,摄心之规矩。循理而天,则动作语默无非天也。内外如一,则视听言动无非我矣。”或问:“言动非礼则可以正,视听如何得合礼?”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则多非礼,故仁者先难而后获。所谓难者,以我视、以我听、以我言、以我动也。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视听不以我也,胥失之矣。”或问:“视听言动合理,而与礼文不相合,如何?”曰:“言动犹可以礼,视听有甚礼文。以斯视、以斯听,自然合理,合理便合礼文,循理便是复礼。”或问:“求仁如何下工夫?”曰:“如颜子视听言动上做亦得,如曾子颜色容貌上做亦得。出辞气者,犹佛所谓从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诺,若不从心中出,便是不识痛痒。古人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不见不闻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汉不识痛痒了。又如仲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如见大宾如承大祭底心在,便长识痛痒。”又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就性上看。”又曰:“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克己之私,则心虚见理矣。”②
谢良佐认为礼是制约和统摄“心”的规矩。但谢良佐着重论述了心的作用和功能:心可以领悟到天理,在克尽一己性之偏私后能够“心虚见理”;心可以管摄视听言动,循心而可以体验到仁;以我心去视听言动,就能自然合理、复礼。朱熹称赞谢良佐对礼的定义和认识,认为“善矣”。但朱熹紧接着批评:
然必以理易礼而又有“循理而天自然合礼”之说焉,亦未免失之过高而无可持循之实。盖圣人所谓礼者,正以礼文而言,其所以为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若曰循理而天,自然合理,则又何规矩之可言哉。其言克己之效则又但曰“克己之私则心虚见理”,则是其所以用力于此者,不以为修身践履之当然,特以求夫知之而已也。①
朱熹认为谢良佐礼、理说的最大弊病还是在于“以理易礼”:重视天理之体验,忽视礼文之规矩;重视知克己之理,忽视行复礼之实。朱熹认为谢良佐和吕大临一样,都是“所论失之过高而无可持循之实”。
游酢(1053—1123)为二程高弟,同样主张万物一体为仁。游酢强调心之本体就是仁,明确提出仁是本心,仁为心之本体的思想,主张人能反其本心,便能达到万物一体的仁之境界。游酢说:
孟子曰:“仁,人心也。”则仁之为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体则喜怒哀乐之未发者是也。惟其徇己之私,则汩于忿欲,而人道熄矣。诚能胜人心之私,以还道心之公,则将视人如己,视物如人,而心之本体见矣。自此而亲亲,自此而仁民,自此而爱物,皆其本心,随物而见者然也,故曰克己复礼为仁。礼者,性之中也。且心之本体一而已矣,非事事而为之,物物而爱之,又非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也。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无适而非仁矣。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天下归仁,取足于身而已,非有藉于外也,故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请事斯语,至于非礼勿动则不离于中,其诚不息而可久矣,故能三月不违仁。虽然,三月不违者,其心犹有所操也。至于中心安仁,则纵目之所视,更无乱色。纵耳之所听,更无奸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发育万物,弥纶天地,而何克己复礼,三月不违之足言哉?此圣人之能事,而对时育万物者,所以博施济众也。仁至于此,则仲尼所不敢居,而且罕言也。然则仁与圣乌乎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则为贤,纵之则为圣。苟未至于纵心,则于博施济众未能无数数然也。”①
游酢认为礼本来体现的就是人性中和的一面,不必日积月累于事事、物物中求之,只要修持心性就能达到仁。游酢此论心性比吕大临、谢良佐更为直截简易,因而遭致朱熹的严厉批评:
游氏之说以为视人如己,视物如人,则其失近于吕氏,而无天序天秩之本,且谓人与物等则,其害于分殊之义为尤甚。以为非必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无适而非仁者,则又陷于释氏顿悟之说,以启后学侥幸躐等之心。以为安仁则纵目所视而无乱色,纵耳所听而无奸声,则又生于庄周、列御寇荒唐之论。②
朱熹认为高妙与落实是分辨异端与儒学的关键。朱熹之所以痛切批评吕、游之说,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儒者如果一味说得高妙,就容易与异端如佛、道、墨、法等家同流而失却根基。在朱熹看来,游酢所论“视人如己、视物如人”,就是只认识到理一之处,而没有认识到儒家所论分殊之处,没有明确辨析合同的亲亲原则与别异的尊尊原则,就失去了对天秩天序下分殊之理的认识。朱熹还指出游酢释“非礼勿动”,只不过将“中”“诚”等好字拼凑总聚,表现出种种晦涩之处③。朱熹认识到这些都是悬空说理或义理所带来的流弊,因此朱熹力求回到礼的节文形态,主张将儒学“复礼”说得着实明白。
程门高弟中,杨时(1053—1135)因独邀耆寿而对南宋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比起其他程门学者来说,杨时更为注重“求仁之学”。杨时注重孟子“仁者人也”的说法,主张于静中体验求仁之方,此论对朱熹的老师李侗影响很深。杨时所论“克己复礼为仁说”为:
仁,人心也。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而已。放而不知求,则人欲肆而天理灭矣。杨子曰:“胜己之私谓之克。”克己所以胜私欲而收放心也。虽收放心,闲之为艰,复礼所以闲之也。能常操而存者,天下与吾一体耳,孰非吾仁乎?颜渊其复不远,庶乎仁者也,故告之如此,若夫动容周旋中礼,则无事乎复矣。①
杨时强调克己求放心的求仁工夫,认为收放心即可,复礼实际上是“无事”的闲工夫。朱熹认为复礼正是儒学精微、切实的下学工夫,因而批评杨时“以为先克己而后复礼以闲之,则其违圣人之意远矣”②。针对杨时所论“道非礼,则荡而无止;礼非道,则梏于仪章器数之末”,朱熹说:
盖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礼者道体之节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后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礼为德,而欲以凝夫道,则既误矣。而又曰:“道非礼,则荡而无止;礼非道,则梏于仪章器数之末,而有所不行。”则是所谓道者,乃为虚无恍惚元无准则之物,所谓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于道也,其诸老氏之言乎,误益甚矣。③
杨时原意也是欲沟通道与礼,强调两者相互影响、依赖的关系,在朱熹看来,“杨氏以为先克己,而后复礼以闲之,则其违圣人之意远矣”④。杨时认为克己、复礼两分为先后顺序,朱熹认为此言有将道与礼割裂的趋势,言道则为“虚无恍惚,元无准则”,言礼、德则有待于道才能成,又有流于道家的危险,因而需要加以批判。杨时门下的张九成(1092—1159)也祖述程颐的礼、理观念,其论“克己复礼”云:“己者,何也?人欲也。礼者,何也?天理也。灭天理,穷人欲,何由而得仁?灭人欲尽天理,于是乃为仁。”①朱熹认为这是杜撰学问、脱空狂妄之论,只以念虑论礼,而没有强调“居处恭,执事敬”“坐如尸,立如齐”等具体应该履行的礼,实际上就不是礼,也就不能真正理解礼的内涵和作用②。总之,朱熹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厘清礼、理关系,就有可能会不自觉流入释老。只有强调平实亲切的以礼文为依托的日用常行工夫,才能真正掌握儒学发展的命脉。
尹焞(1061—1132)在论述礼、理关系时表现出谨遵师说之处:
弟子问仁者多矣,唯对颜子为尽。问何以至于仁,曰复礼则仁矣。礼者,理也,去私欲则复天理。复天理者,仁也。礼不可以徒复,唯能克己所以复也。又问克己之目,语以视听言动者。夫然,则为仁在内,何事于外乎?盖难胜莫如己私,由乎中而应乎外,制其外所以养其中。视听言动必以礼,而其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是之谓复天理。颜子事斯言而进乎圣人,它弟子所不能及也。③
朱熹认同尹焞所论“由乎中而应乎外,制其外所以养其中。视听言动必以礼,而其心不正者未之有也”。但是朱熹认为这也是“庶几近之”,主要的毛病还是表现在“以理易礼”,特别是“以复礼为仁”之说,“亦失程子之意矣”④。有门人曾问及朱熹在编《集注》时为何没有取尹焞之说,朱熹回答说:“不欲其只说复理而不说‘礼’字。盖说复礼,即说得着实;若说作理,则悬空,是个甚物事?”⑤这说明朱熹已经严格地将礼、理关系进行了界定,并以此为标准对二程及其后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与批评。
应该指出的是,程门弟子对“克己复礼归仁”说做出的种种诠释都是在天理论建构中的理学思想,均致力于以天理来重新整合儒学传统中的概念、范畴,目的都是形成有宋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他们强调克己的内圣工夫,注重对天理的体悟,这都是理学倾向“内在”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新儒学特色之所在。虽然他们做出的种种努力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朱熹,但朱熹站在学术思想发展的新起点上,出于健全理学体系的需要,才尽心剖析于“浅深、疏密、毫厘之间”①。
在礼、理关系上,朱熹最终还是服膺于程颐之说,一方面朱熹替程颐“礼即是理也”的说法进行辩护,认为程颐的本义是“礼之属乎天理,以对己之属乎人欲,非以礼训理,而谓真可以此易彼也”②。朱熹的意思是程颐强调“礼即理”,并非“以理易礼”,后学直接论“复礼”为“复天理”,撇开复礼环节,只重视克己灭人欲存天理,实际上是误解了程颐之意。另一方面,朱熹在编撰《集注》时全文抄录程颐之说,强调克己复礼的践履工夫:
程子曰:“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颜渊事斯语,所以进于圣人。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视箴》曰:“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其《听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其《言箴》曰:“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伤烦则支。己肆物忤,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其《动箴》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①
程颐为礼、理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格局,礼是天理体现于人间的秩序,克己是胜己之私,消除内心的蔽障和偏失的欲望才能体会到天理。同时礼并不完全是外在的束缚,而是发自内在本性的应对事物的中和行为。视听言动正是克己复礼的下手之处。程颐的《四箴》正是体现了既克己又复礼的切实可循的下学工夫。强调克己是持久的不能间断的工夫,也是需要大毅力、大勇气去恪守的道德规范。《四箴》中“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正是表达了这种内外交相发用,反身存诚,习与性成的修养工夫。克己只有用礼作为衡量标准时,才能真正达到仁的境界。程颐强调“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只有礼时,方始是仁处”。朱熹在阅读程颐此论时特亲笔注明:“克己复礼为仁,言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是乃仁也。”②朱熹正是看到程颐不仅很好地沟通礼、仁、理三者的关系,同时又提供了具体可以操作的克己复礼的修养条目,体现了儒学所著力的根本所在。朱熹对程门后学“以理易礼”说的批评正基于他们或多或少偏离了程学精义,朱熹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使得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确做到了采众人之长,折流俗之谬,明圣传之统。
三、朱子的礼学:以理事、体用释礼
朱熹对礼的理解,最终可以用“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来概括,此两句出自《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一章朱子的注解③。“节文”一词见于《礼记·坊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檀弓下》也说:“辟踊,哀之至也;有筭,为之节文也。”孔颖达将“节文”解作“准节文章”①,也就是“调节与文饰”之意。“节文”二字,又见于《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朱熹在《集注》中将“节文”解释为“品节文章”。
在其他一些注释中,朱熹主要倾向于以“节文”定义礼:“礼,节文也。”②在释《中庸》“亲亲之大,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时,认为礼是亲亲尊贤的节文,礼是节文仁义的体现③。在释“非天子不议礼”时认为,“礼,亲疏贵贱相接之体也”④。释《论语·为政篇》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时,朱熹认为“礼,谓制度品节也”⑤。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时,认为“礼,即理之节文也”⑥。释“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时,说“礼,谓义理之节文”⑦。总的来说,朱熹倾向于用内蕴天理的“制度”“节文”来释礼。
曾祖道曾这样理解“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谓“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见其大概之所宜,然到礼上方见其威仪法则之详也。节文仪则,是曰事宜”。曾祖道侧重挖掘礼为文、为事的内涵,朱熹则提醒他“更就天人上看”⑧。这说明在朱熹的理解中,礼正是沟通天人的有效手段,体现天人合一的现实载体。
关于此句,陈淳的解释似乎最得师意,他以体用先后关系来分析礼的内涵:
文公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以两句对言之,何也?盖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于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见于人事,人事在外而根于中。天理其体而人事其用也。“仪”谓容仪而形见于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与“文”字相应。“则”谓法则、准则,是个骨子,所以存于中者乃确然不易之意,与“节”字相应。“文”而后“仪”,“节”而后“则”,必有“天理之节文”而后有“人事之仪则”,言须尽此二者,意乃圆备。①
首先,陈淳指出天理与人事之间的关联,天理只是人事中的理,天理是人事的中心,天理在内,人事在外,天理为礼之体,人事为礼之用。这样从天理、人事的角度理解了礼。接着陈淳指出“仪”“文”同有外在显现之容制,“则”“节”共为内在确定不易之准则。最后此两句之间是有着先后顺序的,“天理之节文”是“人事之仪则”的条件,这样强调礼之内在精义的优先性。经过陈淳的阐释,朱熹关于礼的内涵似乎已经很完备了,可是用体用先后关系来论礼,符合朱熹的原意吗?
的确,朱熹早年曾用“体”来说礼。后来换用“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来论礼,这期间有什么微妙的变化吗?我们再来看一段朱熹与弟子们关于此句的讨论:
问:“先生昔曰‘礼是体’。今乃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似非体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乡谈,才见分段子,便说道是用,不是体。如说尺时,无寸底是体,有寸底不是体,便是用;如秤,无星底是体,有星底不是体,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纸糊,此便是体;人摇之,便是用。”杨至之问体,曰:“合当底是体。”②此处朱熹虽然没有直接回答礼是体还是用的问题,但根据朱熹对体用的认识,他的主旨还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礼兼备体用。礼无疑是“体”,“当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体,故仁义礼智为体”①。礼同时兼具体用两面,“如尺与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铢,则体也;将去秤量物事,则用也”②。礼是道理与用处的结合,“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③。在朱熹看来,礼既是应该如此的道理,又是可以权衡、践履的标准和工夫。“礼者,道体之节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后乃能行之也。”④礼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朱子曾说:“学者学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则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⑤从这些讨论来看,在早年朱熹多强调礼为体的一面,因而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朱熹则强调礼兼备体用,沟通天人,是形上道理和形下人事的有机结合。
朱熹认为礼同时具备理和文两方面属性。他说:“所因之礼是天做底,万世不可易;所损益之礼,是人做底,故随时更变。”⑥礼中蕴含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都是不变的天理,是礼相因袭而不能轻易变更的根据,而礼文制度则是损益变化的已然之迹。朱熹说:“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则自今以往,或者继周而王者,虽百世之远,所因所革亦不过此,岂但十世而已乎!”⑦但从偏正结构“天理之节文”的描述来看,朱熹似又更强调礼作为“节文”的属性。
朱熹认为所谓文章就是“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①。“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②朱熹也肯定陈淳所言“文”大要就是“文理可观之谓”③。朱熹重视礼文,认为动容周旋的礼文就是礼之实体,就是礼的体现。“五声十二律,不可谓乐之末,犹揖逊周旋,不可谓礼之末。若不是揖逊周旋,又如何见得礼在那里?”④在秩序亟待重建的南宋社会,朱熹认为重视礼文也是对礼之本的追求。朱熹认为孔子答林放问礼之本,“然俭戚亦只是礼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当文时,不可一向以俭戚为是”⑤。正如颜炳罡所指出的:“朱熹直接挑战孔子,似乎处处与孔子相反。孔子时代,礼乐的危机主要是形式化的危机,礼乐还存在,朱熹的时代,礼乐不再是形式化的危机,而是没有几人精通古礼了,所以他要求重建礼乐的形式——揖逊周旋。”⑥朱熹在其解说《论语·子罕》中颜渊所说的“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一句时,朱熹说:“圣人教人,只此两事。博文工夫固多,约礼只是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则是天理。礼者,天理之节文。节谓等差,文谓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乡党》一篇乃圣人动容周旋皆中礼处。”⑦总的来说,朱熹既重视礼的内涵,又强调礼的形式。
为什么朱熹会用理事关系来论礼呢?这里有必要结合理学思想的发展来解释。为了反对二氏哲学中“体用殊绝”,程颐在继承张载学说的基础上特别指出:“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①这一论述是指《周易》深奥的义理蕴含于错综复杂的卦象之中,理与象不能分割,同出一源。程颐所说的体,是指事物内藏而不彰显的原理和根源,用是指各种现象。后来程颐进一步拓展此思想,说:“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②这说明在程颐看来,理是事物的本质,事物是理的表现,两者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相互统一的。程颐以理为事物内部深奥而微妙的原理,把事物看作理的表征,以理为体,以事为用,认为体用是统一的,强调本体和现实的密切联系。后来朱熹、陈淳用理事、体用论礼都受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
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事的体用一源的思想。他说:“‘体用一源’者,自理而观,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显微无间’者,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③同时朱熹从“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上”这一思想明确化,讨论了理、事的先后问题。这就是说,在一切事物尚未产生时,事物的规律、原理、法则就已经存在,理不因事物存在、出现与否而有所改变。如果要探寻永恒存在的理,就必须通由事才能得到。同样,朱熹关于礼的定义就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不可否认的是,朱熹以“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来名礼,也的确抓住了礼有礼义精微、礼制彰显的两面,为新儒学的礼教体系提供了有之可循的制度仪则,引发了儒者们对礼的内涵的重视与探讨。
这里还有必要讨论一下的是清儒对朱熹用理、事论礼的批评。清代以凌廷堪为代表的经史学家,特标举“以礼代理”的旗帜反攻理学。他们认为以“理”来名学就缺乏合理性,根本不是正统儒家学术的表述。凌廷堪说:“考《论语》及《大学》皆未尝有理字,徒因释氏以理事为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义,是以宋儒论学,往往理事并称。……无端于经文所未有者,尽援释氏以立帜。……故鄙儒遂误以理学为圣学矣。”①凌氏意在指责理学乃是借用佛学之绪余,而非圣学。所言“宋儒论学往往理事并称”,实际上是在讽刺朱熹言礼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虽然学者们早就有结论,程朱理学受华严宗的影响很深②,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理学家正是在借用佛教思想体系和范畴的过程中通过反思儒学,同时在批判佛道的基础上才确立新儒学精致的哲学思想体系。他们的立场仍然是坚定不移的儒学立场。因此,虽然清儒对朱熹有诸多批判,但也遮蔽不了我们真实了解学术思想史的目光。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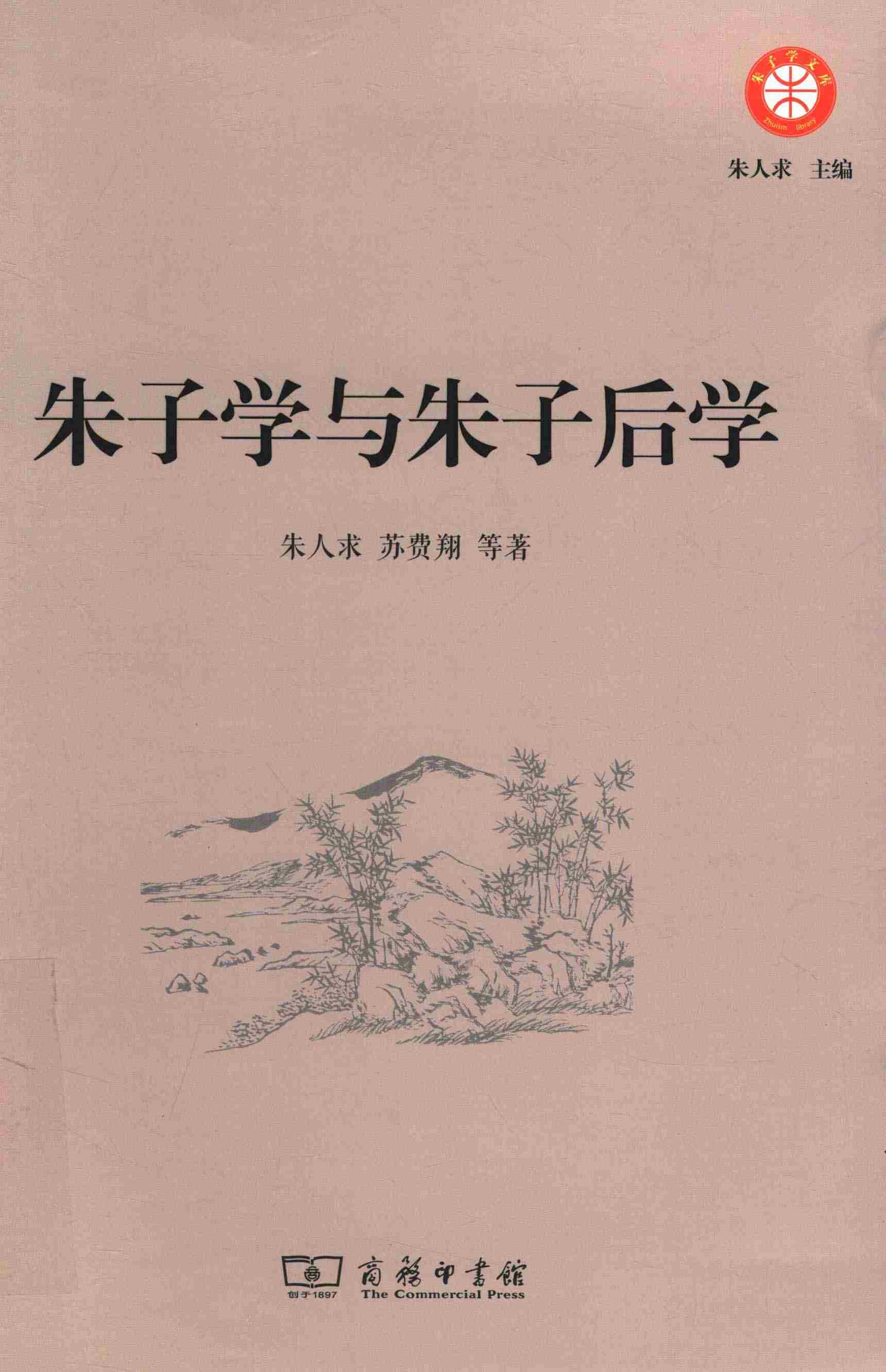
《朱子学与朱子后学》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收录了来自美国、德国、法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知名朱子学者近作14篇,内容涉及朱子的道统论、礼学、气论、诗论、格物致知论、人心道心、家国天下等问题,时间上从南宋跨越到现代,空间上从中国走向东亚世界,以点带面,简单勾勒了朱子思想的多元面向,介绍了朱子学的思想理念、政治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