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栗谷人心道心说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与朱子后学》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6717 |
| 颗粒名称: | 四、栗谷人心道心说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8 |
| 页码: | 131-138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东亚儒学传统中关于人心和道心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两种善问题”。该问题源于朱熹的哲学思想,卢稣斋和李栗谷等人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分析了这些学者的观点和思想,并提出了对“两种善问题”的再思考。 |
| 关键词: | 朱子学 东亚儒学 李栗谷 |
内容
在分析完栗谷的人心道心说的三个方面后,本文不拟从当代儒学的观点来评价栗谷的人心道心说②,而是接下来考察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两种善问题。笔者把这个问题命名为卢稣斋-李栗谷难题。
1.两种善问题的提出(卢稣斋-李栗谷难题)
卢稣斋是东亚第一个以长篇论文的形式阐发人心道心问题的人。此前,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阐发了其人心道心思想。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本,《中庸章句序》并非仅仅只谈人心道心问题,它还涵盖了其他问题。①不管是罗钦顺、湛若水,还是王阳明,都没有专门的论文来阐述人心道心问题。故而,从东亚儒学的视角来看,卢氏的《人心道心辨》便是第一篇专门论述人心道心问题的论文。该文长达三千三百余字,作于1559年。②就整个人心道心的诠释史而言,卢氏的下述观点值得重视:“人心为人欲,则道心为已发可也。人心为善恶,则道心为未发可也。”③朱熹曾经持有人心乃人欲的观点,但其晚年定论则是人心不是人欲,人心可善可恶。如果根据卢氏的看法,那么当人心的道德属性是恶的情况下,则道心就不能不是道德属性为善的已发之心。只有这样,作为已发的人心道心才能分别是恶和善。反之,当人心本身兼善恶的情况下,纯善的道心就不能是已发的心,而必须是未发的性了。④这个观点比较有意思,其实质在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人心本身兼善恶,那么道心(纯善)和人心之善是何种关系?也就是说,会形成人心之善、人心之恶、道心之善,这么三种善恶关系,也就是卢氏所说的“作三截看而已”。在他看来,“殊不思善恶属人心,则性命之发,已自在其中矣”。也就是说,人心之善,其实就体现了性命之发,因而也就是道心。卢氏认为,如果形成人心之善和道心同时并存的局面,那么道心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很大程度上就被消解了。为了避免被消解,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道心作为未发的性,而人心则继续是已发的兼善恶的心。于是,道心人心便顺理成章地构成了体用关系。应该说,卢氏的构想,从他的论证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后,李栗谷在提出四端是指道心和人心之善者时,就面临着道心和人心之善是两种善还是一种善的理论难题。而罗、卢氏的道心人心体用论,则相当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难题。因而从东亚儒学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关于善的一本还是二本说总结为一个难题:卢稣斋-李栗谷难题。在李栗谷晚年的《人心道心图说》一文中,提出了“七情即人心道心善恶之总名也。孟子就七情中剔除善一边,目之以四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①。卢稣斋认为,人心之善和道心是同一种类型的善,因而是实质同一的。他坚持善的一本性,为了避免出现人心之善和道心同时存在,即为了避免二善,于是他就只好把道心本体化,从而形成了道心人心体用说。而李栗谷在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中,能够和卢氏保持相同的思路,即把人心人欲化,故而成为恶,以便和纯善的道心并列且对立起来。此时,他很好地坚持了善的一本性。而当他意识到了在朱熹的晚年定论那里,人心是可善可恶的时候,栗谷就抛弃了人心为恶的观点,而走向了人心兼善恶。与此同时,他仍然基于朱熹的基本观点,人心道心均是已发,故而于此他就和卢氏分道扬镳了。为了避免二善(两种善)的尴尬,卢氏走向了道心人心体用论,而背离了朱熹道心人心说的基本立场。而李栗谷则拒绝选择罗、卢的道心人心体用论,在坚持朱学道心人心说基本立场的同时,却掉进了二善的陷阱。②
2.问题的深化:一本还是二本?
和朱学相同,李栗谷的人心道心说也是建立在对人心概念的规定基础之上的。在前说中,人心是恶,于是道心人心便对立,从而形成了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在后说中,人心有善有恶,于是就形成了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的人心道心统一说。从理论形态来看,前说和后说明显不同,后说是对前说的摒弃与新开展。但是,在后说中,虽然理论类型相同,但是也还存在一个明显不同。后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文本中:《圣学辑要》③与《人心道心图说》。在前者中,四端专指道心,二者之间是可以画等号的。但是,在后者(《人心道心图说》)中,四端却既指道心,又指人心之善者。也就是说,四端=道心+人心之善者。因而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回答:第一,栗谷是如何实现从“四端=道心”到“四端=道心+人心之善者”这个重要转变的,其理由何在?第二,道心(纯善)与人心之善是何种关系?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可以简单说明如下。栗谷告诉我们,“四端只是善情之别名”①。在前说中,由于人心是恶,故而四端只能专指纯善的道心。在后说中,由于人心兼善恶,故而四端就必须同时指称道心以及人心之善者。在《圣学辑要》中,就人心道心说而言,已经取得巨大突破,那就是人心不再是人欲。但是,在人心道心与四端七情的关联问题上,栗谷还在旧有的惯性的影响下,得出了四端专指道心的错误看法。即便如此,却并不影响《圣学辑要》的重要地位。而在《人心道心图说》中,他终于认识到了这个缺陷,于是就调整为四端同时指道心与人心之善者。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则可以转变为如下问题:是否存在不同于道心的独立的人心之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构成了两种善。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道心与人心之善,就实际上是同一种善。正如屏溪(尹凤九,1681—1767)所言,“善则一也。人心既善,则即道心之善云尔”②。要是这样的话,人心之善就等价于道心,人心之善就是道心,或者说道心与人心之善者乃异名而同指,因而不存在独立的人心之善。
栗谷在《人心道心图说》中所体现的人心道心说,即“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的观点,和朱熹的思想保持着一定距离。在朱熹哲学中,人心之恶就是人欲,但是人心不即是人欲。就此而言,人心就其自身而言应该是中性的,而善恶则是人心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发展的后果本身,似乎就不再是人心自身了。笔者在对朱熹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基于此提出了人心通孔说。③这个学说的要点是:人心本身具有独立性;就其发展后果天理/道心与人欲而言,人心就意味着潜能。于是,道心/天理、人欲与人心就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现实与潜能的关系。根据朱学,四端属于善,道心也属于善,而人心则可善可恶。栗谷则认为,人心也有善者,这个善似乎不是朱学意义上的作为潜能的善,而是现实的善。于是心便具有两种善,道心和人心之善。从四端七情的角度看,它们都属于四端,从而具有某种统一性,故而可以视为同一种类型的善。这种看法认为,从语言形式上看虽有道心和人心之善者这两种善,但实质上是一种善。但是,从已发之心的角度来看,既然使用了不同的词语来表述善,以及强调人心与道心之区别,则明显存在着两种善。栗谷非常强调一性、一心等所谓的一本,道心之善和人心之善的表述,是否是对这一原则的突破呢?
根据李明辉的研究,类似于人心之善的气质之性的“之”字,具有三种不同含义。①根据这个思想,人心之善者就具有如下几层意思:第一,人心的善;第二,在人心中的善;第三,人心善。根据人心之善者是和人心之恶者并列,以及刚才的区分,可以认为,栗谷所说的“人心之善者”应指的是第二层意思,即人心中具有(或表现出来)的善。由于人心乃生于形气之私,故而人心之善者也可以视为形气之善者。就此而言,朱熹有一个说法比较有启发性。“季通以书问《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气’。先生曰:‘形气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气亦皆有善。’不知形气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则形气善;不由道心,一付于形气,则为恶。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船无柁,纵之行,有时入于波涛,有时入于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运之,则虽入波涛无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乃形气,则乃理也。”②对于朱熹来说,形气既是限制原则,也是表现原则。故而,它一方面可以表现出善,即“形气之有善”;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现出恶。对于我们来说,前者才是关注的对象。朱熹认为:“形气之有善,皆自道心出。”也就是说,不存在独立的形气之善,相反,形气之善本身就是道心的产物,或者说就是道心。故而,对于朱熹来说,“由道心”与“不由道心”的结果迥然不同,分别是形气善与恶。“由道心”也就是道心主宰,而“不由道心”则是道心失去或没有主宰。可以说,在朱熹那里,人心之善者,皆自道心出,故而和道心乃同一的。不存在不同于道心的独立的人心之善。故而,善必须是一。这就是善的一本说。不难发现,善的一本说与人心通孔说,是逻辑一致的。
相对于朱熹而言,栗谷之四端=道心+人心之善者的公式,意味着什么呢?①且看下面的材料。
许晟甫问:“人心有善有恶,道心纯善无恶,人心之善亦道心也。”
振纲答曰:“人心之善,亦可谓之道心也。虽然,忠于君,孝于亲,道心之属,而原于性命之正。饥欲食,寒欲衣,人心之属,而生于形气之私。人心道心,各有所主而言也。若以人心之善,专谓之道心,则圣人只有道心而已。朱子何以曰‘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也哉?’”②
先生曰:“是。”
许晟甫秉承善的一本说,认为既然人心有善有恶,而道心纯善,所以可以得出人心之善的实质就是道心的结论。针对人心之善即是道心的话语,栗谷的某门徒提出了反驳。在他看来,人心之善可视为道心而不是道心。其根据是:人心是有善有恶的,如果把人心之善归入道心的范畴,则人心就只剩下有恶这个层面了。这是栗谷的人心道心后说所无法接受的,因为他明确认为人心乃上智所不能无者,但圣人当然可以没有流于恶的人心。这两种说法不能并存,于是人心之善和道心有明显区别,就是一个必然的结论了。一定意义上,在朱熹和栗谷之间,出现了善的一本说和二本说的对峙:朱熹是一本说,而栗谷则是二本说。
3.问题解决的关键:人心之独立性问题以及人心能否自持其独立?
栗谷和朱熹之所以存在这一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人心的特性的看法,是不同的。因而,问题在于,人心是独立的吗?或进一步追问,人心之善恶是独立的吗?具体来说,朱熹认为人心是通孔,本身在道德哲学中是没有独立意义的,但道心/天理和人欲,却是通过人心而实现的。因而,就善恶而言,人心自身是无善无恶的,也就是说,是中性的。但是,儒家伦理学是严格强调善与恶的冲突并为善去恶的,于是作为中性的人心本身就不能真正保持其独立性。①其只有两种结局:要么上达为道心/天理,要么下达徇人欲。就这么两种结局(善恶)而言,它们是现实性,而作为其出发点和源头的人心,就是一种潜能。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朱熹对于人心的规定何以是可善可恶了。换言之,“可善可恶”就意味着作为潜能本身的人心的发展具有两种相反可能性。因而,人心通孔说必然意味着人心是可善可恶的。元代的许东阳(谦),也能够理解朱熹人心道心思想的这个关节点,所以他对人心的看法也是可善可恶。②但对于李栗谷来说,则不是这样的,他对于人心的看法是“有善有恶”。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栗谷和朱熹人心道心说之基本差异就是人心有善有恶和人心可善可恶。朱熹认为人心之善就是道心,不存在独立的人心之善。栗谷的人心有善有恶主要是从现实表现上说的,而朱熹的人心可善可恶则是从潜能上说的。前者容易把人心实体化,而后者则更容易凸显人心为通孔。当然,李栗谷也不是完全没有从潜能的角度分析人心,比如,他说道:“人心易流于人欲,故虽善亦危。”从潜能来看,人心确实容易流于恶的人欲,或者说人心流于人欲的可能性要比上达为天理的可能性更大,故而甚“危”。可以发现,李栗谷存在前后不一致之处。但从现实表现而不是潜能上说人心之善恶,似乎是其主导倾向。因而,对于人心与天理人欲是否在同一逻辑层(平)面的问题,对于朱熹和栗谷来说,至关重要。对此问题,朱熹的答案是否定的,而栗谷的则是较为肯定的。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垂直与水平两个向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朱熹而言,人心与天理人欲是立体的垂直关系。而对于栗谷来说,则是水平的平面关系。
《中庸》里有“致广大、尽精微”之语。在笔者看来,李栗谷在剖析人心道心问题时,条分缕析,在不少细节方面明显超越了朱熹,从而达到了精微之境。在李退溪看来,从理发的四端与从气发的七情,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情感(善)。故而,二善对于主张理有活动性的李退溪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主张理不动因而只有一种情的李栗谷来说,就是不可以的。李明辉认为,四端是形而上的情感,七情是形而下的情感,所以四端七情是不同种类(异质)的情。①这个论述对于道心人心也是适用的,基于此,栗谷的看法就是错误的,因为后者混淆了两种情感。也就是说,李氏是不会同意人心之善者和道心都是同一种形而上的情感(纯善的四端)的。看来二善问题并不应该是李栗谷学说的宿命,他或许可以以辩证的方式走出这个困境。似乎可以依据李栗谷对理气之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理解,从而认为道心与人心之善者,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从道心与人心不离的角度来看,道心乃人心之合理状态,因而人心之善即是道心,此乃一;从道心与人心不杂的角度来看,道心是道心,人心之善是人心,故而是二。诚如钱穆所言,“人心道心只是一体两分,又是两体合一”②。当然了,解决难题的最佳方案还是回归朱熹的人心通孔说,从而把现实化的人心转变为作为潜能的人心。
1.两种善问题的提出(卢稣斋-李栗谷难题)
卢稣斋是东亚第一个以长篇论文的形式阐发人心道心问题的人。此前,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阐发了其人心道心思想。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本,《中庸章句序》并非仅仅只谈人心道心问题,它还涵盖了其他问题。①不管是罗钦顺、湛若水,还是王阳明,都没有专门的论文来阐述人心道心问题。故而,从东亚儒学的视角来看,卢氏的《人心道心辨》便是第一篇专门论述人心道心问题的论文。该文长达三千三百余字,作于1559年。②就整个人心道心的诠释史而言,卢氏的下述观点值得重视:“人心为人欲,则道心为已发可也。人心为善恶,则道心为未发可也。”③朱熹曾经持有人心乃人欲的观点,但其晚年定论则是人心不是人欲,人心可善可恶。如果根据卢氏的看法,那么当人心的道德属性是恶的情况下,则道心就不能不是道德属性为善的已发之心。只有这样,作为已发的人心道心才能分别是恶和善。反之,当人心本身兼善恶的情况下,纯善的道心就不能是已发的心,而必须是未发的性了。④这个观点比较有意思,其实质在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人心本身兼善恶,那么道心(纯善)和人心之善是何种关系?也就是说,会形成人心之善、人心之恶、道心之善,这么三种善恶关系,也就是卢氏所说的“作三截看而已”。在他看来,“殊不思善恶属人心,则性命之发,已自在其中矣”。也就是说,人心之善,其实就体现了性命之发,因而也就是道心。卢氏认为,如果形成人心之善和道心同时并存的局面,那么道心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很大程度上就被消解了。为了避免被消解,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道心作为未发的性,而人心则继续是已发的兼善恶的心。于是,道心人心便顺理成章地构成了体用关系。应该说,卢氏的构想,从他的论证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后,李栗谷在提出四端是指道心和人心之善者时,就面临着道心和人心之善是两种善还是一种善的理论难题。而罗、卢氏的道心人心体用论,则相当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难题。因而从东亚儒学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关于善的一本还是二本说总结为一个难题:卢稣斋-李栗谷难题。在李栗谷晚年的《人心道心图说》一文中,提出了“七情即人心道心善恶之总名也。孟子就七情中剔除善一边,目之以四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①。卢稣斋认为,人心之善和道心是同一种类型的善,因而是实质同一的。他坚持善的一本性,为了避免出现人心之善和道心同时存在,即为了避免二善,于是他就只好把道心本体化,从而形成了道心人心体用说。而李栗谷在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中,能够和卢氏保持相同的思路,即把人心人欲化,故而成为恶,以便和纯善的道心并列且对立起来。此时,他很好地坚持了善的一本性。而当他意识到了在朱熹的晚年定论那里,人心是可善可恶的时候,栗谷就抛弃了人心为恶的观点,而走向了人心兼善恶。与此同时,他仍然基于朱熹的基本观点,人心道心均是已发,故而于此他就和卢氏分道扬镳了。为了避免二善(两种善)的尴尬,卢氏走向了道心人心体用论,而背离了朱熹道心人心说的基本立场。而李栗谷则拒绝选择罗、卢的道心人心体用论,在坚持朱学道心人心说基本立场的同时,却掉进了二善的陷阱。②
2.问题的深化:一本还是二本?
和朱学相同,李栗谷的人心道心说也是建立在对人心概念的规定基础之上的。在前说中,人心是恶,于是道心人心便对立,从而形成了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在后说中,人心有善有恶,于是就形成了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的人心道心统一说。从理论形态来看,前说和后说明显不同,后说是对前说的摒弃与新开展。但是,在后说中,虽然理论类型相同,但是也还存在一个明显不同。后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文本中:《圣学辑要》③与《人心道心图说》。在前者中,四端专指道心,二者之间是可以画等号的。但是,在后者(《人心道心图说》)中,四端却既指道心,又指人心之善者。也就是说,四端=道心+人心之善者。因而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回答:第一,栗谷是如何实现从“四端=道心”到“四端=道心+人心之善者”这个重要转变的,其理由何在?第二,道心(纯善)与人心之善是何种关系?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可以简单说明如下。栗谷告诉我们,“四端只是善情之别名”①。在前说中,由于人心是恶,故而四端只能专指纯善的道心。在后说中,由于人心兼善恶,故而四端就必须同时指称道心以及人心之善者。在《圣学辑要》中,就人心道心说而言,已经取得巨大突破,那就是人心不再是人欲。但是,在人心道心与四端七情的关联问题上,栗谷还在旧有的惯性的影响下,得出了四端专指道心的错误看法。即便如此,却并不影响《圣学辑要》的重要地位。而在《人心道心图说》中,他终于认识到了这个缺陷,于是就调整为四端同时指道心与人心之善者。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则可以转变为如下问题:是否存在不同于道心的独立的人心之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构成了两种善。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道心与人心之善,就实际上是同一种善。正如屏溪(尹凤九,1681—1767)所言,“善则一也。人心既善,则即道心之善云尔”②。要是这样的话,人心之善就等价于道心,人心之善就是道心,或者说道心与人心之善者乃异名而同指,因而不存在独立的人心之善。
栗谷在《人心道心图说》中所体现的人心道心说,即“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的观点,和朱熹的思想保持着一定距离。在朱熹哲学中,人心之恶就是人欲,但是人心不即是人欲。就此而言,人心就其自身而言应该是中性的,而善恶则是人心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发展的后果本身,似乎就不再是人心自身了。笔者在对朱熹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基于此提出了人心通孔说。③这个学说的要点是:人心本身具有独立性;就其发展后果天理/道心与人欲而言,人心就意味着潜能。于是,道心/天理、人欲与人心就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现实与潜能的关系。根据朱学,四端属于善,道心也属于善,而人心则可善可恶。栗谷则认为,人心也有善者,这个善似乎不是朱学意义上的作为潜能的善,而是现实的善。于是心便具有两种善,道心和人心之善。从四端七情的角度看,它们都属于四端,从而具有某种统一性,故而可以视为同一种类型的善。这种看法认为,从语言形式上看虽有道心和人心之善者这两种善,但实质上是一种善。但是,从已发之心的角度来看,既然使用了不同的词语来表述善,以及强调人心与道心之区别,则明显存在着两种善。栗谷非常强调一性、一心等所谓的一本,道心之善和人心之善的表述,是否是对这一原则的突破呢?
根据李明辉的研究,类似于人心之善的气质之性的“之”字,具有三种不同含义。①根据这个思想,人心之善者就具有如下几层意思:第一,人心的善;第二,在人心中的善;第三,人心善。根据人心之善者是和人心之恶者并列,以及刚才的区分,可以认为,栗谷所说的“人心之善者”应指的是第二层意思,即人心中具有(或表现出来)的善。由于人心乃生于形气之私,故而人心之善者也可以视为形气之善者。就此而言,朱熹有一个说法比较有启发性。“季通以书问《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气’。先生曰:‘形气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气亦皆有善。’不知形气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则形气善;不由道心,一付于形气,则为恶。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船无柁,纵之行,有时入于波涛,有时入于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运之,则虽入波涛无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乃形气,则乃理也。”②对于朱熹来说,形气既是限制原则,也是表现原则。故而,它一方面可以表现出善,即“形气之有善”;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现出恶。对于我们来说,前者才是关注的对象。朱熹认为:“形气之有善,皆自道心出。”也就是说,不存在独立的形气之善,相反,形气之善本身就是道心的产物,或者说就是道心。故而,对于朱熹来说,“由道心”与“不由道心”的结果迥然不同,分别是形气善与恶。“由道心”也就是道心主宰,而“不由道心”则是道心失去或没有主宰。可以说,在朱熹那里,人心之善者,皆自道心出,故而和道心乃同一的。不存在不同于道心的独立的人心之善。故而,善必须是一。这就是善的一本说。不难发现,善的一本说与人心通孔说,是逻辑一致的。
相对于朱熹而言,栗谷之四端=道心+人心之善者的公式,意味着什么呢?①且看下面的材料。
许晟甫问:“人心有善有恶,道心纯善无恶,人心之善亦道心也。”
振纲答曰:“人心之善,亦可谓之道心也。虽然,忠于君,孝于亲,道心之属,而原于性命之正。饥欲食,寒欲衣,人心之属,而生于形气之私。人心道心,各有所主而言也。若以人心之善,专谓之道心,则圣人只有道心而已。朱子何以曰‘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也哉?’”②
先生曰:“是。”
许晟甫秉承善的一本说,认为既然人心有善有恶,而道心纯善,所以可以得出人心之善的实质就是道心的结论。针对人心之善即是道心的话语,栗谷的某门徒提出了反驳。在他看来,人心之善可视为道心而不是道心。其根据是:人心是有善有恶的,如果把人心之善归入道心的范畴,则人心就只剩下有恶这个层面了。这是栗谷的人心道心后说所无法接受的,因为他明确认为人心乃上智所不能无者,但圣人当然可以没有流于恶的人心。这两种说法不能并存,于是人心之善和道心有明显区别,就是一个必然的结论了。一定意义上,在朱熹和栗谷之间,出现了善的一本说和二本说的对峙:朱熹是一本说,而栗谷则是二本说。
3.问题解决的关键:人心之独立性问题以及人心能否自持其独立?
栗谷和朱熹之所以存在这一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人心的特性的看法,是不同的。因而,问题在于,人心是独立的吗?或进一步追问,人心之善恶是独立的吗?具体来说,朱熹认为人心是通孔,本身在道德哲学中是没有独立意义的,但道心/天理和人欲,却是通过人心而实现的。因而,就善恶而言,人心自身是无善无恶的,也就是说,是中性的。但是,儒家伦理学是严格强调善与恶的冲突并为善去恶的,于是作为中性的人心本身就不能真正保持其独立性。①其只有两种结局:要么上达为道心/天理,要么下达徇人欲。就这么两种结局(善恶)而言,它们是现实性,而作为其出发点和源头的人心,就是一种潜能。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朱熹对于人心的规定何以是可善可恶了。换言之,“可善可恶”就意味着作为潜能本身的人心的发展具有两种相反可能性。因而,人心通孔说必然意味着人心是可善可恶的。元代的许东阳(谦),也能够理解朱熹人心道心思想的这个关节点,所以他对人心的看法也是可善可恶。②但对于李栗谷来说,则不是这样的,他对于人心的看法是“有善有恶”。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栗谷和朱熹人心道心说之基本差异就是人心有善有恶和人心可善可恶。朱熹认为人心之善就是道心,不存在独立的人心之善。栗谷的人心有善有恶主要是从现实表现上说的,而朱熹的人心可善可恶则是从潜能上说的。前者容易把人心实体化,而后者则更容易凸显人心为通孔。当然,李栗谷也不是完全没有从潜能的角度分析人心,比如,他说道:“人心易流于人欲,故虽善亦危。”从潜能来看,人心确实容易流于恶的人欲,或者说人心流于人欲的可能性要比上达为天理的可能性更大,故而甚“危”。可以发现,李栗谷存在前后不一致之处。但从现实表现而不是潜能上说人心之善恶,似乎是其主导倾向。因而,对于人心与天理人欲是否在同一逻辑层(平)面的问题,对于朱熹和栗谷来说,至关重要。对此问题,朱熹的答案是否定的,而栗谷的则是较为肯定的。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垂直与水平两个向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朱熹而言,人心与天理人欲是立体的垂直关系。而对于栗谷来说,则是水平的平面关系。
《中庸》里有“致广大、尽精微”之语。在笔者看来,李栗谷在剖析人心道心问题时,条分缕析,在不少细节方面明显超越了朱熹,从而达到了精微之境。在李退溪看来,从理发的四端与从气发的七情,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情感(善)。故而,二善对于主张理有活动性的李退溪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主张理不动因而只有一种情的李栗谷来说,就是不可以的。李明辉认为,四端是形而上的情感,七情是形而下的情感,所以四端七情是不同种类(异质)的情。①这个论述对于道心人心也是适用的,基于此,栗谷的看法就是错误的,因为后者混淆了两种情感。也就是说,李氏是不会同意人心之善者和道心都是同一种形而上的情感(纯善的四端)的。看来二善问题并不应该是李栗谷学说的宿命,他或许可以以辩证的方式走出这个困境。似乎可以依据李栗谷对理气之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理解,从而认为道心与人心之善者,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从道心与人心不离的角度来看,道心乃人心之合理状态,因而人心之善即是道心,此乃一;从道心与人心不杂的角度来看,道心是道心,人心之善是人心,故而是二。诚如钱穆所言,“人心道心只是一体两分,又是两体合一”②。当然了,解决难题的最佳方案还是回归朱熹的人心通孔说,从而把现实化的人心转变为作为潜能的人心。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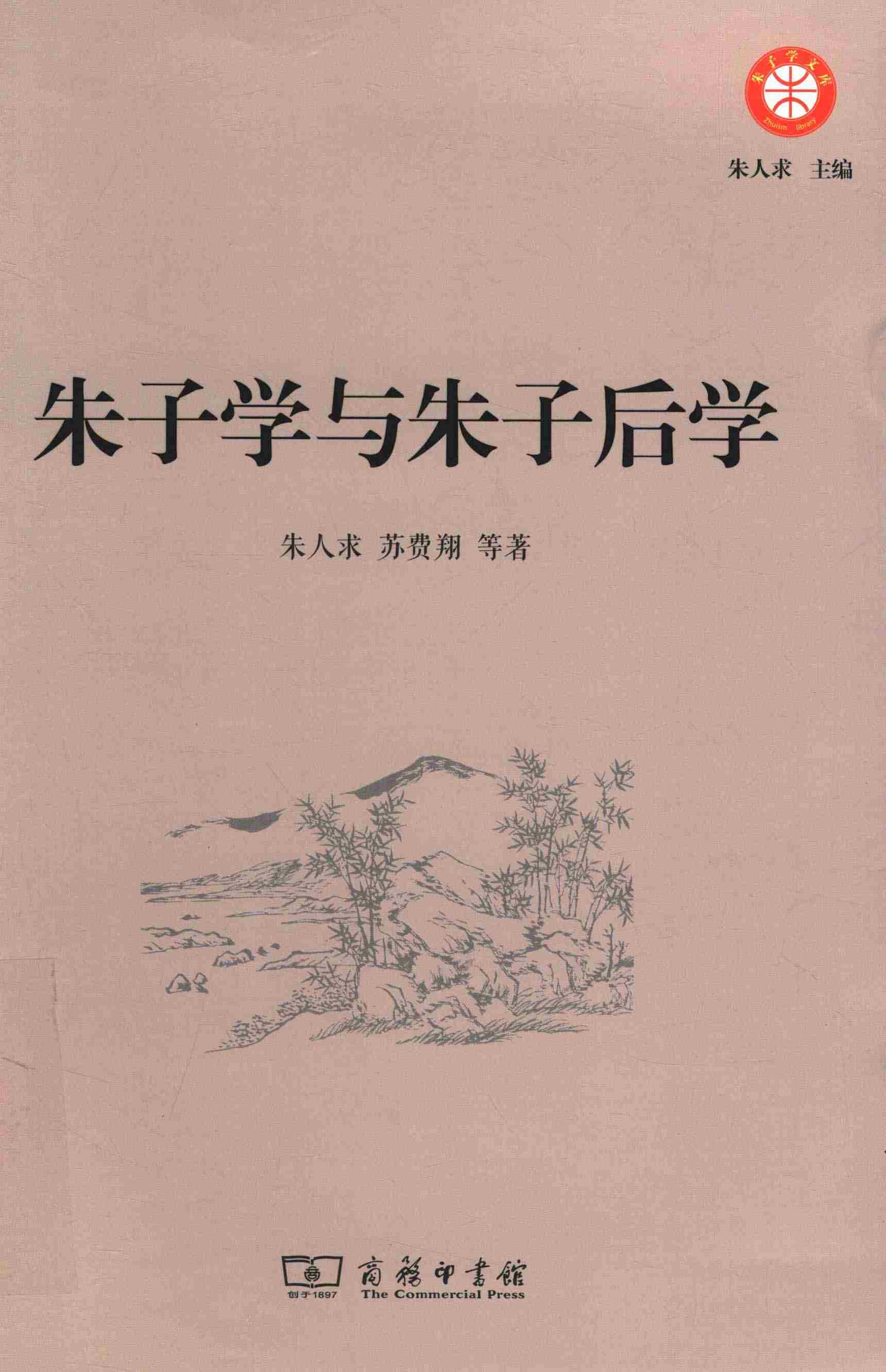
《朱子学与朱子后学》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收录了来自美国、德国、法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知名朱子学者近作14篇,内容涉及朱子的道统论、礼学、气论、诗论、格物致知论、人心道心、家国天下等问题,时间上从南宋跨越到现代,空间上从中国走向东亚世界,以点带面,简单勾勒了朱子思想的多元面向,介绍了朱子学的思想理念、政治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