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在《〈大学〉或问》中对“格物致知”的补传及其对门人后学的影响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与朱子后学》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6706 |
| 颗粒名称: | 论朱熹在《〈大学〉或问》中对“格物致知”的补传及其对门人后学的影响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2 |
| 页码: | 99-120 |
| 摘要: | 本文讨论了朱熹对《大学》中“格物致知”这一概念的理解和阐释。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指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和理解,获得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基于对事物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解,而不是仅仅通过抽象思考或经验积累得到的。因此,朱熹强调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即物而穷其理”,通过实际观察和思考来获得真知。 |
| 关键词: | 朱熹 格物致知 认识论 |
内容
一、序论
朱熹曾对《礼记·大学》进行过订正,其中对“格物致知”这一命题的阐释尤为着力,并对该节进行了系统的补正。朱熹的补正文字即《“格物致知”补传》,又称《格物章补文》《补致知章》或《〈大学〉补亡》。
朱熹补文的开篇为一段简短的序文,主要说明《大学》注文第五章存在着的阙文。朱熹开宗明义,说明他是基于程子说法据以增补的。朱熹曰:
此谓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此谓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此章旧本通下章,误在经文之下。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①
序文之后,是朱熹为增补《大学》正文所作的阐释性注文。注文如下: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①
这段共134字(如不计“此谓知之至也”,共128字)的文字已成为与《大学》正文等量齐观的重要论述,从而使之具有了经文的地位,而朱熹本人也由此跻身于孔、孟、曾子等古代圣贤之列。该段文字简要概括了朱熹关于知识学习的思想,同时也是对其认识论的总结。诚如朱熹所言,他的这一看法是在程子思想的直接启发下形成的。
在《朱子语类》第十六卷(《大学》三),朱熹对该节文字的补正情况做了几处详细说明。第十六卷有四页的内容是对《大学》注文第五章的讨论,题名为《传五章释格物致知》,主要讨论“格物”和“致知”两个观念。从朱熹回答弟子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对《大学五章》注文第五章的补正可能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事实上,在朱熹门人引述乃师的文字中,至少有一处是与上引文字不同的。这句话在朱熹《〈大学〉章句》中的原话是“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但其弟子引述的却是“理之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分别取舍无不切”。②
另外,朱熹在对该章进行补正时,并没有刻意去模仿《大学》的古奥文风,而是有意用宋代的语言去表达。在回答弟子为何不用《大学》之文体时,朱熹坦承自己过去确实曾努力为之,但却无法做到:
问:“所补‘致知’章,何不效其文体?”
[朱熹]曰:“亦曾效而为之,竟不能成。刘原父却会效古人为文,其集中有数篇论,全似《礼记》。”③
《朱子语类》第十六卷《传五章释格物致知》的四页文字在篇幅上要比《〈大学〉或问》少。在《朱子全书》第十八卷中,共有四十二页专论《〈大学〉或问》①,其中约有十页的篇幅专论上文中提到的格物节补注②。《朱子语类》第十八卷《大学五·或问下》几乎全是朱熹的《〈大学〉补注》及朱熹对《〈大学〉或问》的阐释。③因此,《朱子语类》第十六与十八两卷关于《大学》第五节的总篇幅共达四十五页,几乎占《语类》全书的百分之一。如果再加上朱熹在《〈大学〉或问》中讨论格物致知的十页,可以说朱熹是用了相当的篇幅对之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这里,我将首先介绍朱熹在《〈大学〉或问》中所作的补注内容,然后再介绍《〈大学〉或问》在朱熹给弟子的答文及为宁宗所作《经筵讲义》中所起的作用。
二、《〈大学〉或问》中关于《“格物致知”补传》的解释
在《朱子语类》第十八卷中,朱熹把《〈大学〉或问》十页的补注内容分为三个部分(这一分法不见于《〈大学〉或问》本文),并把《〈大学〉或问》中门人所问问题的首句作为标题,即:
1.“独其所谓格物致知”一段
2.“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
3.“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一段
首段(“独其所谓格物致知”一段)涵盖了《〈大学〉或问》三页的内容。一位门人就朱熹“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句提问如下:
[或问]曰:“此经之序,自诚意以下,其义明而传悉矣。独其所谓格物致知者,字义不明,而传复阙焉,且为最初用力之地,而无复上文语绪之可寻也。子乃自谓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则程子之言,何以见其必合于经意,而子之言,又似不尽出于程子,何耶?”①
朱熹在答文中首先引用了程氏兄弟三个部分共十七句(第一部分两句,第二部分十句,第三部分五句)论述,而后总结说:
凡程子之为说者,不过如此,其于“格物致知”之传详矣。今也寻其义理既无可疑,考其字义亦皆有据。至以他书论之,则《文言》所谓“学聚问辩”,《中庸》所谓“明善择善”,《孟子》所谓“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验夫大学始教之功为有在乎此也。愚尝反复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窃取其意,以补传文之阙,不然,则又安敢犯不韪之罪,为无证之言,以自托于圣经贤传之间乎?②
朱熹《〈大学〉或问》第二段(“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涉及了朱熹的一些哲学观点,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该段共685字,几乎全是朱熹回答两个门人问题的文字。第一个问题是:
[或问于朱熹]曰:“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闻之乎?”③
《朱子语类》第十八卷即以“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为篇名。朱熹的回答分为两个层次,中间还引用了九句经典文献,在整体上阐释了自己的一些哲学主张。朱熹解答的全文如下:
吾闻之也,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则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理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各有攸主,而不可乱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则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则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也;远而至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也;极其大,则天地之运,古今之变,不能外也;尽于小,则一尘之微,一息之顷,不能遗也。是乃
上帝所降之衷①
《烝民》所秉之彝②
刘子所谓天地之中③
夫子所谓性与天道④
子思所谓天命之性
孟子所谓仁义之心
程子所谓天然自有之中
张子所谓万物之一原
邵子所谓道之形体者[性]⑤
但其气质有清浊偏正之殊,物欲有浅深厚薄之异,是以人之与物,贤之与愚,相与悬绝而不能同耳。
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于天下万物之理无不能知;以其禀之异,故于其理或有所不能穷也。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知有不尽,则其心之所发,必不能纯于义理,而无杂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诚,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国家不可得而治也。
昔者圣人盖有忧之,是以于其始教,为之小学,而使之习于诚敬,则所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者,已无所不用其至矣。
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极,则吾之知识,亦得以周徧精切而无不尽也。
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①,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②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
此愚之所以补乎本传阙文之意,所不能尽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归,则不合者鲜矣,读者其亦深考而实识之哉!③
该文简要论述了朱熹在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方面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熹在这里以更为清晰的语言对《〈大学〉补传》中的注文进行了表述。《〈大学〉补传》中关于此节的文字是: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①
《〈大学〉或问》第二段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
[或问于朱熹]曰:“然则子之为学,不求诸心,而求诸迹,不求之内,而求之外,吾恐圣贤之学,不如是之浅近而支离也。”②朱熹的答复如下:
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然或不知此心之灵,而无以存之,则昏昧杂扰,而无以穷众理之妙。不知众理之妙,而无以穷之,则偏狭固滞,而无以尽此心之全。此其理势之相须,盖亦有必然者。是以圣人设教,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辩之际,以致尽心之功。巨细相涵,动静交养,初未尝有内外精粗之择,及其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则亦有以知其浑然一致,而果无内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为浅近支离,而欲藏形匿景,别为一种幽深恍惚、艰难阻绝之论,务使学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言论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后可以得之,则是近世佛学诚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乱古人明德新民之实学,其亦误矣。③
这段答文也显示了朱熹把哲学思想运用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性,由此也反驳了陆九渊等对朱熹学理“支离”的指责。
《〈大学〉或问》最后一段是关于《〈大学〉补传》的。该段在《朱子语类》中题为“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包括门人的三个问题及朱熹的回答,内容主要是反驳宋代学者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朱熹在文中逐一反驳了温公司马光(1019—1086)及程颐六弟子的观点,后六人即与叔吕大临(1040—1092)、上蔡谢良佐(1050—1103)、龟山杨时(1053—1135)、和靖尹惇(1071—1142)、文定胡安国(1074—1138)和五峰胡宏(1106—1162)。在《〈大学〉或问》中,虽然朱熹对七人的观点一一进行了反驳,但并未举出他们的名号。但在《朱子语类》第十八卷第三节“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一段,他却逐一介绍这七人的论点,并标出其名号或地望。
《或问》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说”曰:
“格,犹扦也,御也,能扦御外物,而后能知至道。”温公
“必穷物之理同出于一为格物。”吕与叔
“穷理只是寻个是处。”上蔡
“天下之物不可胜穷,然皆备于我而非从外得。”龟山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为非程子之言。”和靖
“物物致察,宛转归己。”胡文定
“即事即物,不厌不弃,而身亲格之。”五峰①
在《〈大学〉或问》中,朱熹对程颐及其门人后学的观点做了总结性的批驳:
程子之言,其答问反复之详且明也如彼,而其门人之所以为说者乃如此,虽或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于犹有所未尽也,是亦不待七十子丧而大义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发而有助于后学哉!②
在结论中,朱熹引用了本师李侗(延平先生,1093—1163)关于“为学”的观念:
间独惟念昔文延平先生之教,以为“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①
朱熹对李侗的观点做了如下评论:
详味此言,虽其规模之大,条理之密,若不逮于程子,然其功夫之渐次,意味之深切,则有非他说所能及者。惟尝实用力于此者,为能有以识之,未易以口舌争也。②
综上所述,朱熹对《大学》第五节的补注分三个层次:一是阐明朱熹自己的补文(134字)来源有自,贴合了程子的说法;二是阐述了其中有关“理”的哲学观点;三是反驳了司马光等人的指责,并介绍了自己与先师有关的哲学观点。
三、《朱子语类》中有关《〈大学〉或问》和《大学》补文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回到《朱子语类》第十八卷讨论《〈大学〉或问》的四十页内容上。该卷有朱熹为“格物”所加的注文,另在回答门人提问的答文中,也有多处论述“格物”的重要内容。③如上所述,《朱子语类》这四十页的内容被分为“独其所谓格物致知”“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及“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三段。
第一段有《〈大学〉或问》中引用的程子十七句引文。我们特别注意到该节有朱熹主要论敌陆九渊对“格物”论的不同看法,同时朱熹也在和江西人黄义刚的讨论中做了进一步的申论,黄义刚指责陆九渊反对程颐的“格物”观。
陈淳(字安卿,1153—1217)也纪录了上述朱、黄关于“格物”的讨论,但没有提到陆九渊的名字:
黄毅然[黄义刚]问:“程子说‘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而先生说要随事理会。恐精力短,如何?
[朱熹]曰:“也须用理会。不成精力短后,话便信口开,行便信脚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
[黄义刚]又问:“无事时见得是如此,临事又做错了,如何?”
[朱熹]曰:“只是断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闲时理会,不是要临时理会。闲时看得道理分晓,则事来时断置自易。格物只是理会未理会得底,不是从头都要理会。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蹈,何曾有错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会当蹈水火与不当蹈水火,临事时断置教分晓。程子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亦是如此。且如看文字,圣贤说话粹,无可疑者。若后世诸儒之言,唤做都不是,也不得;有好底,有不好底;好底里面也有不好处,不好底里面也有好处;有这一事说得是,那一件说得不是;有这一句说得是,那一句说得不是;都要恁地分别。如临事,亦要如此理会那个是,那个不是。若道理明时,自分晓。有一般说,汉、唐来都是;有一般说,汉、唐来都不是;恁地也不得。且如董仲舒、贾谊说话,何曾有都不是底,何曾有都是底。须是要见得他那个议论是,那个议论不是。如此,方唤做格物。如今将一个物事来,是与不是见得不定,便是自家这里道理不通透。若道理明,则这样处自通透。”①
黄义刚本人则以典型的对话体更详尽地纪录了二人讨论的内容,收录在《朱子语类》中陈淳的记录之后。
黄义刚首先以陆九渊对程颐格物观无用的议论开始:
[黄义刚]问:“陆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说。若以为随事讨论,则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则无所不照,其说亦似省力。”
[朱熹]曰:“不去随事讨论后,听他胡做,话便信口说,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
义刚曰:“平时明知此事不是,临时却做错了,随即又悔。此毕竟是精神短后,照烛不逮。”
[朱熹]曰:“只是断制不下。且如有一人牵你出去街上行,不成不管后,只听他牵去。须是知道那里不可去,我不要随他去。”
义刚曰:“事卒然在面前,卒然断制不下,这须是精神强,始得。”
[朱熹]曰:“所以格物,便是要闲时理会,不是要临时理会。如水火,人知其不可蹈,自是不去蹈,何曾有人错去蹈水火来。若是平时看得分明时,卒然到面前,须解断制。若理会不得时,也须临事时与尽心理会。十分断制不下,则亦无奈何。然亦岂可道晓不得后,但听他。如今有十人,须看他那个好,那个不好。好人也有做得不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处得那件是,那件不是。处得是,又有曲折处。而今人读书,全一例说好底,固不是。但取圣人书,而以为后世底皆不足信,也不是。如圣人之言,自是纯粹。但后世人也有说得是底,如汉[董]仲舒之徒。说得是底还他是。然也有不是处,也自可见。须是如此去穷,方是。但所谓格物,也是格未晓底,已自晓底又何用格。如伊川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是说那难理会底。”①
《朱子语类》第十八卷还多次述及朱熹在《〈大学〉或问》中谈到的“所当然”“所以为然”这两个说法。《〈大学〉或问》第二段(“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曾三次提及这两个说法:
1.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所能为也。②
2.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③
3.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①
另外,在《〈大学〉或问》第一段中,朱熹把这一对说法简略地跟“理”联系起来:
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②
对这两个说法,朱熹在答文中做了如下解释:
[周谟]问:“《或问》物有当然之则,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
[朱熹]曰:“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是当然之则。然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则不是论其所以然矣。”③
在另一处文字中,朱熹对门人辅广的回答是:
[辅广]问:“[《或问》]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先生[朱熹]问:“每常如何看?”
[辅]广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
[朱熹]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已者,然又当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见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其事所当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个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学者但止见一边。如去见人,只见得他冠冕衣裳,却元不曾识得那人。且如为忠,为孝,为仁,为义,但只据眼前理会得个皮肤便休,都不曾理会得那彻心彻髓处。以至于天地间造化,固是阳长则生,阴消则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万事,一事各有一理,须是一一理会教彻。不成只说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万物万事,吾知其为万物万事而已。’明道诗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观他此语,须知有极至之理,非册子上所能载者。”
[辅]广曰:“大至于阴阳造化,皆是‘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所谓‘太极’,则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朱熹]曰:“固是。人须是自向里入深去理会。此个道理,才理会到深处,又易得似禅。须是理会到深处,又却不与禅相似;方是。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入禅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觉走入番界去定也。只如程门高第游氏(游酢),则分明是投番了。虽上蔡(谢良佐)、龟山(杨时)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终看他未破;时时去他那下探头探脑,心下也须疑它那下有个好处在。大凡为学,须是四方八面都理会教通晓,仍更理会向里来。”①
朱熹的答文又一次清楚地阐释了“所以然”的观念。朱熹最后还指责了受禅宗影响的程颐门人游酢(1053—1123)。尽管程颐的其他弟子如谢良佐(1050—1103)和杨时(1053—1135)并不信禅,但他们的思考方式与禅思的机制并无二致。朱熹在这里以幽默的方式把“入禅”的思考方式比作宋金界河的淮河,“入禅”即越过淮河进入番境,“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觉走入番界去定也”。
《〈大学〉或问》的第二段(“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列举了九句自《尚书》至邵雍的语句,用以解释以“格物致知”为目的的形而上之理。《朱子语类》第十八卷对上述引文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以使读者进一步理解朱熹的思想。朱熹在文中回答了门人关于《尚书》《左传》和“衷”“中”意义的提问。在朱熹看来,“衷”是人们获得的天赐,而《尚书》中所谓的“上帝降衷”意即“折中”,亦即“正中”:
[黄卓]问“上帝降衷”。
[朱熹]曰:“衷,只是中也。”
又曰:“是恰好处。如折衷,是折两者之半而取中之义。”①
“衷”是上天所降,在“接受”了“天命”的人看来,其所“受”之“衷”或“命”,就是他们身上的“性”。
[朱熹]曰:“天降衷者,衷降此。以降言,为命;以受言,为性。”②
这也是为什么在朱熹看来,“衷”即天降到人身上的“性”,也等同于人所“受”的“中”:
[朱熹]曰:“‘衷’字,看来只是个无过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个个有一副当恰好、无过不及底道理降与你。与程子所谓天然自有之中,[《左传》]刘子(刘康公)所谓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相似;与《诗》所谓秉彝,张子(张载)所谓万物之一原又不同。须各晓其名字训义之所以异,方见其所谓同。(一云:若说降衷便是秉彝,则不可。若说便是万物一原,则又不可。万物一原,自说万物皆出此也。若统论道理,固是一般,圣贤何故说许多名字?)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去声)者,以中为准则而取正也。[《诗经·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则’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个当然之则,故民执之以为常道,所以无不好此懿德。”③
在朱熹的形而上体系中,“衷”“中”“则”是上天对人类的赐予,在人看来,是天降之“命”。这些由天所“与”、由物所“受”的概念,多多少少都是与“性”“理”“道”甚或“太极”相对应的说法。
[朱熹]曰:“如‘降衷于下民’,这紧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则谓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则谓之性。如云‘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则谓之性,而不谓之衷。所以不同,缘各据他来处与所受处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据天之所与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据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绥厥猷’,猷即道,道者性之发用处,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说得道理如此缜密,处处皆合。”①
朱熹的一个门人曾问及是否可以在《左传》“天地之中”的说法与周敦颐的“太极”之间进行对比。朱熹在答文中认为二者名称虽异,所指本为一物:
陈问:“[《左传》]刘子(刘康公)所谓天地之中,即周子(周敦颐)所谓太极否?”
[朱熹]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处。上帝降衷,亦是恰好处。极不是中,极之为物,只是在中。如这烛台,中央簪处便是极。从这里比到那里,也恰好,不曾加些;从那里比到这里,也恰好,不曾减些。”②
最后,朱熹对《左传》的“天地之中”与程子的“天然自有之中”二句进行了比较。在朱熹看来,《左传》里的“中”是“未发”之中,即尚未表现出来的现象,而程子的“中”是“适中”,是“已发”之中,即业已成形的事物。
[曾祖道]问:“[《左传》]天地之中,[程子]天然自有之中,同否?”
[朱熹]曰:“[《左传》]天地之中,是未发之中;[程子]天然自有之中,是时中。”
[曾祖道]曰:“然则天地之中是指道体,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
[朱熹]曰:“然。”①
四、朱熹对陈淳“《或问》所引书降衷以下八言”立论的答复
《〈大学〉或问》中所引以《尚书》“上帝所降之衷”为开头的九句引文,清楚地阐明了朱熹关于“理”的“当然之则”的说法。这些引文引起朱熹门人陈淳的极大兴趣。在陈淳写给乃师的一封长信中,他力图为解释九句引文的次序而构建一个理论。陈淳写道:
《或问》所引《书》“降衷”以下八言,虽皆所以证夫“理”,而其相次莫以有序否?尝试推之:降衷自天赋于人而言,秉彝自人禀于天而言。衷者,理之至善而无妄也,彝则理之一定而有常也。常即善之所为,因有是善,故能常。衷者统言,彝则指定言。此二句方举其大纲,而下文则详之。
[左传]“天地之中”,统言天地间实理浑然大中,无所偏倚,为万邦之极,而万物之生莫不以是为枢纽也。此比所谓衷则又加确矣。
[中庸]“天命之性”,指是理降而在人,为赋生之全体,而性则实即夫天理之中,而非有二者。是二言者,一言天,一言自天而人,又所以兼明夫天赋于人而详其降衷之意也。
[孟子]“仁义之心”,仁义乃即天命之性,指其实理,而心则包具焉以为体而主于身者也。此比所谓彝则又加实矣。
[程子]“天然自有之中”,又细言是理之散于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之则,无过无不及,皆天之所为而非人之力①者。“而其实,又不外于其心”②,此二句又就性而言,合衷、彝而结之。盖万物虽各有当然无过不及之理,然总其根源之所自,则只是一大本而同为一理也。此理人物所共由,天地间所公共,所以谓之道。而其体则统会于吾之性,非泛然事物之间而不根于其内也。
窃以此下更宜以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以包天人、事物、体用、动静、内外、终始一贯为说,似于八言之下其意尤为圆也。而不之取,不审何也?③
陈淳在上文中对九句引文所涉及的复杂结构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试图阐释每句引文所包含的义理,同时也在整体上把九句引文和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无极而太极”的概念联系起来。有趣的是,朱熹并不赞同陈淳对这些概念所做的深度发掘,而是在答复中给后者的理论热情浇了一盆冷水。朱熹说,这九句引文的次序只是按自古及今的年代进行排列,并无他意:
当时只以古今为次第,未有此意。周子语意差远,故不得引以为证,恐却费注解也。④
朱熹以“费批注”为由,表明陈淳的过度解释纯属画蛇添足之举。在笔者看来,陈淳的这一解读颇类似于康德对“知识激情”(Schw?rmerei)一词的过度解读,这对哲学家来说是危险的。朱熹通过看似轻描淡写的说明,让进行大胆解释的弟子冷静了下来。其实,朱熹通过这种简单的年代排序,只是要体现引文在内容上的纯粹的“模拟”特征,他要揭示的是引语中所涉及的超感觉世界,仅限于《中庸》中的“性”或《左传》中“民受天地之中”的“中”。陈淳则试图打破朱熹的简单模拟关系,建立细密和学术式的知性构建。但是,在朱熹看来,这一序列并无任何特定的意义。陈淳所寻找的,是为九句引语建立逻辑联系,这正是朱熹要摒弃的。
五、《〈大学〉或问》《经筵讲义》与《格物致知补传》的关系
绍熙五年(1194),宁宗登基,朱熹平生第一次在首都临安出任官职。同年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三日,朱熹在宫廷为宁宗做了七次《大学》讲座。十二月三日,当第七次课结束之时,朱熹向宁宗面呈《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札中力谏宁宗放弃“独断”的行为。朱熹呈递该札的直接后果是断送了自己刚刚开始的仕途,黯然返乡。朱熹七次讲座的内容后被编为《经筵讲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朱熹被突然罢官,因此这七次讲座也不是他对《大学》的全文讲评。另外,就师生关系而言,宁宗可以说是朱熹最显赫的门生。
《经筵讲义》中有四页内容出自《格物致知补传》。我们注意到,《经筵讲义》其实是《〈大学〉或问》的简本,其中的一些段落甚至是一字不动的照录,也有一些内容是为了引起宁宗的注意特意做了调整。
在《经筵讲义》中,朱熹首先对《大学》中的缺文做了如下解释:
此谓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谓知之至也。臣熹曰:“此句之上当有阙文。”①
朱熹进而详细阐述了自己认定存在缺文的理由:
臣谨按:此传之五章,其次当释物格知至之义,今亡其辞,而独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结语也。臣尝窃考此篇之旨,其纲领有三,其条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为先务。今乃独遗其本传之文,不知其所以发明此旨者果为何说,甚可惜也。然而尚赖程氏之言,有可以补其亡者。①
其后,朱熹对《朱子语类·大学或问》中的三段内容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对《〈大学〉或问》“独所谓格物致知”一段,朱熹引用了原补注十七句引文中的六句,有的是全文照录,有的则做了调整,如《经筵讲义》中的第一段引文就是把《〈大学〉或问》中程子的两句引文合二为一。《〈大学〉或问》的两句引文是:
(1)又有问[于程子]进修之术何先者。
程子曰:“[学]莫先于正心诚意,然欲诚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尽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穷而至之,所谓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②
(2)[或问于程子]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将止格一物,而万理皆通耶?”
[程子]曰:“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③《经筵讲义》整合后的引文是:
[程子曰]:“学莫先于正心诚意,然欲正心诚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尽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穷而至之,所谓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但能今日[而]格一件[物焉],明日又格一件[物焉],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④
另外,朱熹在《经筵讲义》中增加五条《〈大学〉或问》中没有的引文,其中前三条为程子文:
“学道以知为先,致知以敬为本。”
“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
“但庄整齐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①
后两条为程子门人谢良佐和尹悙之语:
至其门人谢良佐之言,则曰:“敬是常惺惺法。”
尹惇之言则曰:“人能收敛其心,不容一物,则可以谓之敬矣。”②
对《〈大学〉或问》“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一段,朱熹则没有收入《经筵讲义》中。这可能是由于这段文字争议较大,在该段中,朱熹对一些字句的解释与司马光等学者的解释多有不同,如对“格”字的解释,司马光认为“格”即“捍”,意即“抵御、抵抗”,但朱熹却解释为“达到、臻至”。另外,朱熹还反驳了上引谢良佐和尹悙对“格物致知”的解释。由此看来,《经筵讲义》应该说是朱熹对《〈大学〉或问》进行整合和折中后形成的版本。
对“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经筵讲义》中除了几个地方小有不同外,几乎是照单全录。朱熹明确指出,由“当然之则”所界定的“规则”是出自人心的。在“当然之则”后,他还特意加上了《〈大学〉或问》中没有的“具于人心”的说法,以便更清楚地说明天理的内在概念:
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具于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也。③
另外,《经筵讲义》也没有引录《〈大学〉或问》中第二段第二节的问答文字:
[或问于朱熹]曰:“然则子之为学,不求诸心,而求诸迹,不求之内,而求之外,吾恐圣贤之学,不如是之浅近而支离也。”①
在《经筵讲义》中,朱熹还向宁宗阐述了下面一大段《〈大学〉或问》中没有的内容:
凡此推演,虽出管窥,然实皆圣经贤传之意、造道入德之方也。抑臣闻之,治古之世,天下无不学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为尤密。盖自其为赤子之时,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傅,则又有小学之学。及其齿于胄子,则又有大学之学。凡所以涵养其本原、开导其知识之具,已先熟于为臣为子之时,故其内外凝肃、思虑通明之効,有以见于君临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执要,酬酢从容,取是舍非,赏善罚恶,而奸言邪说无足以乱其心术也。
降及后世,教化不修,天下之人例不知学,而尊且贵者为尤甚。盖幼而不知小学之教,故其长也无以进乎大学之道。凡平日所以涵养其本原、开导其知识者,既已一切卤莽而无法,则其一旦居尊而临下,决无所恃以应事物之变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后,始欲学于小学,以为大学之基,则已过时而不暇矣。
夫手握天下之图,身据兆民之上,可谓安且荣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术,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于前,骋其拟议窥觎于后,是则岂不反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于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励,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从今日从事于敬,以求放心,则犹可以涵养本原而致其精明,以为穷理之本。
伏惟陛下深留圣意,实下工夫,不可但崇空言,以应故事而已也。臣义切爱君,不觉烦读,下情无任恐惧恳激之至。②
这段论述同时涵盖了朱熹的政治观与认识论,是对《〈大学〉章句·序》中一些命题的进一步申论。①
六、结论
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原文的补注是其在程颐思想的基础上长期思考并提炼升华的结果,并在《〈大学〉或问》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其中与门人就“格物致知”进行的诸多问答和解释都收入《朱子语类》的第十六和第十八卷。在答文中,朱熹为阐释《大学》中的知识起源论而增加了许多要素。朱熹在淳熙四年(1177)完成了《〈大学〉或问》的解释内容,而后于绍熙五年(1194)为宁宗做御前讲座,并编成《经筵讲义》。应该说,宁宗是朱熹最显赫的弟子。令人称奇的是,在南宋时代,像朱熹这样重要的哲学家是可以亲自向皇帝传授如《〈大学〉或问》这样精深细微的哲学思想的,但不可否认,为讲授起见,朱熹在《经筵讲义》中删节了某些内容。
朱熹曾对《礼记·大学》进行过订正,其中对“格物致知”这一命题的阐释尤为着力,并对该节进行了系统的补正。朱熹的补正文字即《“格物致知”补传》,又称《格物章补文》《补致知章》或《〈大学〉补亡》。
朱熹补文的开篇为一段简短的序文,主要说明《大学》注文第五章存在着的阙文。朱熹开宗明义,说明他是基于程子说法据以增补的。朱熹曰:
此谓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此谓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此章旧本通下章,误在经文之下。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①
序文之后,是朱熹为增补《大学》正文所作的阐释性注文。注文如下: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①
这段共134字(如不计“此谓知之至也”,共128字)的文字已成为与《大学》正文等量齐观的重要论述,从而使之具有了经文的地位,而朱熹本人也由此跻身于孔、孟、曾子等古代圣贤之列。该段文字简要概括了朱熹关于知识学习的思想,同时也是对其认识论的总结。诚如朱熹所言,他的这一看法是在程子思想的直接启发下形成的。
在《朱子语类》第十六卷(《大学》三),朱熹对该节文字的补正情况做了几处详细说明。第十六卷有四页的内容是对《大学》注文第五章的讨论,题名为《传五章释格物致知》,主要讨论“格物”和“致知”两个观念。从朱熹回答弟子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对《大学五章》注文第五章的补正可能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事实上,在朱熹门人引述乃师的文字中,至少有一处是与上引文字不同的。这句话在朱熹《〈大学〉章句》中的原话是“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但其弟子引述的却是“理之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分别取舍无不切”。②
另外,朱熹在对该章进行补正时,并没有刻意去模仿《大学》的古奥文风,而是有意用宋代的语言去表达。在回答弟子为何不用《大学》之文体时,朱熹坦承自己过去确实曾努力为之,但却无法做到:
问:“所补‘致知’章,何不效其文体?”
[朱熹]曰:“亦曾效而为之,竟不能成。刘原父却会效古人为文,其集中有数篇论,全似《礼记》。”③
《朱子语类》第十六卷《传五章释格物致知》的四页文字在篇幅上要比《〈大学〉或问》少。在《朱子全书》第十八卷中,共有四十二页专论《〈大学〉或问》①,其中约有十页的篇幅专论上文中提到的格物节补注②。《朱子语类》第十八卷《大学五·或问下》几乎全是朱熹的《〈大学〉补注》及朱熹对《〈大学〉或问》的阐释。③因此,《朱子语类》第十六与十八两卷关于《大学》第五节的总篇幅共达四十五页,几乎占《语类》全书的百分之一。如果再加上朱熹在《〈大学〉或问》中讨论格物致知的十页,可以说朱熹是用了相当的篇幅对之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这里,我将首先介绍朱熹在《〈大学〉或问》中所作的补注内容,然后再介绍《〈大学〉或问》在朱熹给弟子的答文及为宁宗所作《经筵讲义》中所起的作用。
二、《〈大学〉或问》中关于《“格物致知”补传》的解释
在《朱子语类》第十八卷中,朱熹把《〈大学〉或问》十页的补注内容分为三个部分(这一分法不见于《〈大学〉或问》本文),并把《〈大学〉或问》中门人所问问题的首句作为标题,即:
1.“独其所谓格物致知”一段
2.“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
3.“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一段
首段(“独其所谓格物致知”一段)涵盖了《〈大学〉或问》三页的内容。一位门人就朱熹“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句提问如下:
[或问]曰:“此经之序,自诚意以下,其义明而传悉矣。独其所谓格物致知者,字义不明,而传复阙焉,且为最初用力之地,而无复上文语绪之可寻也。子乃自谓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则程子之言,何以见其必合于经意,而子之言,又似不尽出于程子,何耶?”①
朱熹在答文中首先引用了程氏兄弟三个部分共十七句(第一部分两句,第二部分十句,第三部分五句)论述,而后总结说:
凡程子之为说者,不过如此,其于“格物致知”之传详矣。今也寻其义理既无可疑,考其字义亦皆有据。至以他书论之,则《文言》所谓“学聚问辩”,《中庸》所谓“明善择善”,《孟子》所谓“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验夫大学始教之功为有在乎此也。愚尝反复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窃取其意,以补传文之阙,不然,则又安敢犯不韪之罪,为无证之言,以自托于圣经贤传之间乎?②
朱熹《〈大学〉或问》第二段(“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涉及了朱熹的一些哲学观点,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该段共685字,几乎全是朱熹回答两个门人问题的文字。第一个问题是:
[或问于朱熹]曰:“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闻之乎?”③
《朱子语类》第十八卷即以“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为篇名。朱熹的回答分为两个层次,中间还引用了九句经典文献,在整体上阐释了自己的一些哲学主张。朱熹解答的全文如下:
吾闻之也,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则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理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各有攸主,而不可乱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则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则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也;远而至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也;极其大,则天地之运,古今之变,不能外也;尽于小,则一尘之微,一息之顷,不能遗也。是乃
上帝所降之衷①
《烝民》所秉之彝②
刘子所谓天地之中③
夫子所谓性与天道④
子思所谓天命之性
孟子所谓仁义之心
程子所谓天然自有之中
张子所谓万物之一原
邵子所谓道之形体者[性]⑤
但其气质有清浊偏正之殊,物欲有浅深厚薄之异,是以人之与物,贤之与愚,相与悬绝而不能同耳。
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于天下万物之理无不能知;以其禀之异,故于其理或有所不能穷也。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知有不尽,则其心之所发,必不能纯于义理,而无杂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诚,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国家不可得而治也。
昔者圣人盖有忧之,是以于其始教,为之小学,而使之习于诚敬,则所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者,已无所不用其至矣。
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极,则吾之知识,亦得以周徧精切而无不尽也。
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①,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②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
此愚之所以补乎本传阙文之意,所不能尽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归,则不合者鲜矣,读者其亦深考而实识之哉!③
该文简要论述了朱熹在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方面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熹在这里以更为清晰的语言对《〈大学〉补传》中的注文进行了表述。《〈大学〉补传》中关于此节的文字是: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①
《〈大学〉或问》第二段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
[或问于朱熹]曰:“然则子之为学,不求诸心,而求诸迹,不求之内,而求之外,吾恐圣贤之学,不如是之浅近而支离也。”②朱熹的答复如下:
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然或不知此心之灵,而无以存之,则昏昧杂扰,而无以穷众理之妙。不知众理之妙,而无以穷之,则偏狭固滞,而无以尽此心之全。此其理势之相须,盖亦有必然者。是以圣人设教,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辩之际,以致尽心之功。巨细相涵,动静交养,初未尝有内外精粗之择,及其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则亦有以知其浑然一致,而果无内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为浅近支离,而欲藏形匿景,别为一种幽深恍惚、艰难阻绝之论,务使学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言论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后可以得之,则是近世佛学诚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乱古人明德新民之实学,其亦误矣。③
这段答文也显示了朱熹把哲学思想运用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性,由此也反驳了陆九渊等对朱熹学理“支离”的指责。
《〈大学〉或问》最后一段是关于《〈大学〉补传》的。该段在《朱子语类》中题为“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包括门人的三个问题及朱熹的回答,内容主要是反驳宋代学者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朱熹在文中逐一反驳了温公司马光(1019—1086)及程颐六弟子的观点,后六人即与叔吕大临(1040—1092)、上蔡谢良佐(1050—1103)、龟山杨时(1053—1135)、和靖尹惇(1071—1142)、文定胡安国(1074—1138)和五峰胡宏(1106—1162)。在《〈大学〉或问》中,虽然朱熹对七人的观点一一进行了反驳,但并未举出他们的名号。但在《朱子语类》第十八卷第三节“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一段,他却逐一介绍这七人的论点,并标出其名号或地望。
《或问》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说”曰:
“格,犹扦也,御也,能扦御外物,而后能知至道。”温公
“必穷物之理同出于一为格物。”吕与叔
“穷理只是寻个是处。”上蔡
“天下之物不可胜穷,然皆备于我而非从外得。”龟山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为非程子之言。”和靖
“物物致察,宛转归己。”胡文定
“即事即物,不厌不弃,而身亲格之。”五峰①
在《〈大学〉或问》中,朱熹对程颐及其门人后学的观点做了总结性的批驳:
程子之言,其答问反复之详且明也如彼,而其门人之所以为说者乃如此,虽或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于犹有所未尽也,是亦不待七十子丧而大义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发而有助于后学哉!②
在结论中,朱熹引用了本师李侗(延平先生,1093—1163)关于“为学”的观念:
间独惟念昔文延平先生之教,以为“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①
朱熹对李侗的观点做了如下评论:
详味此言,虽其规模之大,条理之密,若不逮于程子,然其功夫之渐次,意味之深切,则有非他说所能及者。惟尝实用力于此者,为能有以识之,未易以口舌争也。②
综上所述,朱熹对《大学》第五节的补注分三个层次:一是阐明朱熹自己的补文(134字)来源有自,贴合了程子的说法;二是阐述了其中有关“理”的哲学观点;三是反驳了司马光等人的指责,并介绍了自己与先师有关的哲学观点。
三、《朱子语类》中有关《〈大学〉或问》和《大学》补文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回到《朱子语类》第十八卷讨论《〈大学〉或问》的四十页内容上。该卷有朱熹为“格物”所加的注文,另在回答门人提问的答文中,也有多处论述“格物”的重要内容。③如上所述,《朱子语类》这四十页的内容被分为“独其所谓格物致知”“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及“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三段。
第一段有《〈大学〉或问》中引用的程子十七句引文。我们特别注意到该节有朱熹主要论敌陆九渊对“格物”论的不同看法,同时朱熹也在和江西人黄义刚的讨论中做了进一步的申论,黄义刚指责陆九渊反对程颐的“格物”观。
陈淳(字安卿,1153—1217)也纪录了上述朱、黄关于“格物”的讨论,但没有提到陆九渊的名字:
黄毅然[黄义刚]问:“程子说‘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而先生说要随事理会。恐精力短,如何?
[朱熹]曰:“也须用理会。不成精力短后,话便信口开,行便信脚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
[黄义刚]又问:“无事时见得是如此,临事又做错了,如何?”
[朱熹]曰:“只是断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闲时理会,不是要临时理会。闲时看得道理分晓,则事来时断置自易。格物只是理会未理会得底,不是从头都要理会。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蹈,何曾有错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会当蹈水火与不当蹈水火,临事时断置教分晓。程子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亦是如此。且如看文字,圣贤说话粹,无可疑者。若后世诸儒之言,唤做都不是,也不得;有好底,有不好底;好底里面也有不好处,不好底里面也有好处;有这一事说得是,那一件说得不是;有这一句说得是,那一句说得不是;都要恁地分别。如临事,亦要如此理会那个是,那个不是。若道理明时,自分晓。有一般说,汉、唐来都是;有一般说,汉、唐来都不是;恁地也不得。且如董仲舒、贾谊说话,何曾有都不是底,何曾有都是底。须是要见得他那个议论是,那个议论不是。如此,方唤做格物。如今将一个物事来,是与不是见得不定,便是自家这里道理不通透。若道理明,则这样处自通透。”①
黄义刚本人则以典型的对话体更详尽地纪录了二人讨论的内容,收录在《朱子语类》中陈淳的记录之后。
黄义刚首先以陆九渊对程颐格物观无用的议论开始:
[黄义刚]问:“陆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说。若以为随事讨论,则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则无所不照,其说亦似省力。”
[朱熹]曰:“不去随事讨论后,听他胡做,话便信口说,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
义刚曰:“平时明知此事不是,临时却做错了,随即又悔。此毕竟是精神短后,照烛不逮。”
[朱熹]曰:“只是断制不下。且如有一人牵你出去街上行,不成不管后,只听他牵去。须是知道那里不可去,我不要随他去。”
义刚曰:“事卒然在面前,卒然断制不下,这须是精神强,始得。”
[朱熹]曰:“所以格物,便是要闲时理会,不是要临时理会。如水火,人知其不可蹈,自是不去蹈,何曾有人错去蹈水火来。若是平时看得分明时,卒然到面前,须解断制。若理会不得时,也须临事时与尽心理会。十分断制不下,则亦无奈何。然亦岂可道晓不得后,但听他。如今有十人,须看他那个好,那个不好。好人也有做得不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处得那件是,那件不是。处得是,又有曲折处。而今人读书,全一例说好底,固不是。但取圣人书,而以为后世底皆不足信,也不是。如圣人之言,自是纯粹。但后世人也有说得是底,如汉[董]仲舒之徒。说得是底还他是。然也有不是处,也自可见。须是如此去穷,方是。但所谓格物,也是格未晓底,已自晓底又何用格。如伊川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是说那难理会底。”①
《朱子语类》第十八卷还多次述及朱熹在《〈大学〉或问》中谈到的“所当然”“所以为然”这两个说法。《〈大学〉或问》第二段(“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曾三次提及这两个说法:
1.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所能为也。②
2.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③
3.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①
另外,在《〈大学〉或问》第一段中,朱熹把这一对说法简略地跟“理”联系起来:
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②
对这两个说法,朱熹在答文中做了如下解释:
[周谟]问:“《或问》物有当然之则,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
[朱熹]曰:“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是当然之则。然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则不是论其所以然矣。”③
在另一处文字中,朱熹对门人辅广的回答是:
[辅广]问:“[《或问》]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先生[朱熹]问:“每常如何看?”
[辅]广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
[朱熹]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已者,然又当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见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其事所当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个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学者但止见一边。如去见人,只见得他冠冕衣裳,却元不曾识得那人。且如为忠,为孝,为仁,为义,但只据眼前理会得个皮肤便休,都不曾理会得那彻心彻髓处。以至于天地间造化,固是阳长则生,阴消则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万事,一事各有一理,须是一一理会教彻。不成只说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万物万事,吾知其为万物万事而已。’明道诗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观他此语,须知有极至之理,非册子上所能载者。”
[辅]广曰:“大至于阴阳造化,皆是‘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所谓‘太极’,则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朱熹]曰:“固是。人须是自向里入深去理会。此个道理,才理会到深处,又易得似禅。须是理会到深处,又却不与禅相似;方是。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入禅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觉走入番界去定也。只如程门高第游氏(游酢),则分明是投番了。虽上蔡(谢良佐)、龟山(杨时)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终看他未破;时时去他那下探头探脑,心下也须疑它那下有个好处在。大凡为学,须是四方八面都理会教通晓,仍更理会向里来。”①
朱熹的答文又一次清楚地阐释了“所以然”的观念。朱熹最后还指责了受禅宗影响的程颐门人游酢(1053—1123)。尽管程颐的其他弟子如谢良佐(1050—1103)和杨时(1053—1135)并不信禅,但他们的思考方式与禅思的机制并无二致。朱熹在这里以幽默的方式把“入禅”的思考方式比作宋金界河的淮河,“入禅”即越过淮河进入番境,“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觉走入番界去定也”。
《〈大学〉或问》的第二段(“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列举了九句自《尚书》至邵雍的语句,用以解释以“格物致知”为目的的形而上之理。《朱子语类》第十八卷对上述引文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以使读者进一步理解朱熹的思想。朱熹在文中回答了门人关于《尚书》《左传》和“衷”“中”意义的提问。在朱熹看来,“衷”是人们获得的天赐,而《尚书》中所谓的“上帝降衷”意即“折中”,亦即“正中”:
[黄卓]问“上帝降衷”。
[朱熹]曰:“衷,只是中也。”
又曰:“是恰好处。如折衷,是折两者之半而取中之义。”①
“衷”是上天所降,在“接受”了“天命”的人看来,其所“受”之“衷”或“命”,就是他们身上的“性”。
[朱熹]曰:“天降衷者,衷降此。以降言,为命;以受言,为性。”②
这也是为什么在朱熹看来,“衷”即天降到人身上的“性”,也等同于人所“受”的“中”:
[朱熹]曰:“‘衷’字,看来只是个无过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个个有一副当恰好、无过不及底道理降与你。与程子所谓天然自有之中,[《左传》]刘子(刘康公)所谓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相似;与《诗》所谓秉彝,张子(张载)所谓万物之一原又不同。须各晓其名字训义之所以异,方见其所谓同。(一云:若说降衷便是秉彝,则不可。若说便是万物一原,则又不可。万物一原,自说万物皆出此也。若统论道理,固是一般,圣贤何故说许多名字?)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去声)者,以中为准则而取正也。[《诗经·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则’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个当然之则,故民执之以为常道,所以无不好此懿德。”③
在朱熹的形而上体系中,“衷”“中”“则”是上天对人类的赐予,在人看来,是天降之“命”。这些由天所“与”、由物所“受”的概念,多多少少都是与“性”“理”“道”甚或“太极”相对应的说法。
[朱熹]曰:“如‘降衷于下民’,这紧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则谓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则谓之性。如云‘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则谓之性,而不谓之衷。所以不同,缘各据他来处与所受处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据天之所与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据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绥厥猷’,猷即道,道者性之发用处,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说得道理如此缜密,处处皆合。”①
朱熹的一个门人曾问及是否可以在《左传》“天地之中”的说法与周敦颐的“太极”之间进行对比。朱熹在答文中认为二者名称虽异,所指本为一物:
陈问:“[《左传》]刘子(刘康公)所谓天地之中,即周子(周敦颐)所谓太极否?”
[朱熹]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处。上帝降衷,亦是恰好处。极不是中,极之为物,只是在中。如这烛台,中央簪处便是极。从这里比到那里,也恰好,不曾加些;从那里比到这里,也恰好,不曾减些。”②
最后,朱熹对《左传》的“天地之中”与程子的“天然自有之中”二句进行了比较。在朱熹看来,《左传》里的“中”是“未发”之中,即尚未表现出来的现象,而程子的“中”是“适中”,是“已发”之中,即业已成形的事物。
[曾祖道]问:“[《左传》]天地之中,[程子]天然自有之中,同否?”
[朱熹]曰:“[《左传》]天地之中,是未发之中;[程子]天然自有之中,是时中。”
[曾祖道]曰:“然则天地之中是指道体,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
[朱熹]曰:“然。”①
四、朱熹对陈淳“《或问》所引书降衷以下八言”立论的答复
《〈大学〉或问》中所引以《尚书》“上帝所降之衷”为开头的九句引文,清楚地阐明了朱熹关于“理”的“当然之则”的说法。这些引文引起朱熹门人陈淳的极大兴趣。在陈淳写给乃师的一封长信中,他力图为解释九句引文的次序而构建一个理论。陈淳写道:
《或问》所引《书》“降衷”以下八言,虽皆所以证夫“理”,而其相次莫以有序否?尝试推之:降衷自天赋于人而言,秉彝自人禀于天而言。衷者,理之至善而无妄也,彝则理之一定而有常也。常即善之所为,因有是善,故能常。衷者统言,彝则指定言。此二句方举其大纲,而下文则详之。
[左传]“天地之中”,统言天地间实理浑然大中,无所偏倚,为万邦之极,而万物之生莫不以是为枢纽也。此比所谓衷则又加确矣。
[中庸]“天命之性”,指是理降而在人,为赋生之全体,而性则实即夫天理之中,而非有二者。是二言者,一言天,一言自天而人,又所以兼明夫天赋于人而详其降衷之意也。
[孟子]“仁义之心”,仁义乃即天命之性,指其实理,而心则包具焉以为体而主于身者也。此比所谓彝则又加实矣。
[程子]“天然自有之中”,又细言是理之散于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之则,无过无不及,皆天之所为而非人之力①者。“而其实,又不外于其心”②,此二句又就性而言,合衷、彝而结之。盖万物虽各有当然无过不及之理,然总其根源之所自,则只是一大本而同为一理也。此理人物所共由,天地间所公共,所以谓之道。而其体则统会于吾之性,非泛然事物之间而不根于其内也。
窃以此下更宜以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以包天人、事物、体用、动静、内外、终始一贯为说,似于八言之下其意尤为圆也。而不之取,不审何也?③
陈淳在上文中对九句引文所涉及的复杂结构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试图阐释每句引文所包含的义理,同时也在整体上把九句引文和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无极而太极”的概念联系起来。有趣的是,朱熹并不赞同陈淳对这些概念所做的深度发掘,而是在答复中给后者的理论热情浇了一盆冷水。朱熹说,这九句引文的次序只是按自古及今的年代进行排列,并无他意:
当时只以古今为次第,未有此意。周子语意差远,故不得引以为证,恐却费注解也。④
朱熹以“费批注”为由,表明陈淳的过度解释纯属画蛇添足之举。在笔者看来,陈淳的这一解读颇类似于康德对“知识激情”(Schw?rmerei)一词的过度解读,这对哲学家来说是危险的。朱熹通过看似轻描淡写的说明,让进行大胆解释的弟子冷静了下来。其实,朱熹通过这种简单的年代排序,只是要体现引文在内容上的纯粹的“模拟”特征,他要揭示的是引语中所涉及的超感觉世界,仅限于《中庸》中的“性”或《左传》中“民受天地之中”的“中”。陈淳则试图打破朱熹的简单模拟关系,建立细密和学术式的知性构建。但是,在朱熹看来,这一序列并无任何特定的意义。陈淳所寻找的,是为九句引语建立逻辑联系,这正是朱熹要摒弃的。
五、《〈大学〉或问》《经筵讲义》与《格物致知补传》的关系
绍熙五年(1194),宁宗登基,朱熹平生第一次在首都临安出任官职。同年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三日,朱熹在宫廷为宁宗做了七次《大学》讲座。十二月三日,当第七次课结束之时,朱熹向宁宗面呈《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札中力谏宁宗放弃“独断”的行为。朱熹呈递该札的直接后果是断送了自己刚刚开始的仕途,黯然返乡。朱熹七次讲座的内容后被编为《经筵讲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朱熹被突然罢官,因此这七次讲座也不是他对《大学》的全文讲评。另外,就师生关系而言,宁宗可以说是朱熹最显赫的门生。
《经筵讲义》中有四页内容出自《格物致知补传》。我们注意到,《经筵讲义》其实是《〈大学〉或问》的简本,其中的一些段落甚至是一字不动的照录,也有一些内容是为了引起宁宗的注意特意做了调整。
在《经筵讲义》中,朱熹首先对《大学》中的缺文做了如下解释:
此谓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谓知之至也。臣熹曰:“此句之上当有阙文。”①
朱熹进而详细阐述了自己认定存在缺文的理由:
臣谨按:此传之五章,其次当释物格知至之义,今亡其辞,而独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结语也。臣尝窃考此篇之旨,其纲领有三,其条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为先务。今乃独遗其本传之文,不知其所以发明此旨者果为何说,甚可惜也。然而尚赖程氏之言,有可以补其亡者。①
其后,朱熹对《朱子语类·大学或问》中的三段内容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对《〈大学〉或问》“独所谓格物致知”一段,朱熹引用了原补注十七句引文中的六句,有的是全文照录,有的则做了调整,如《经筵讲义》中的第一段引文就是把《〈大学〉或问》中程子的两句引文合二为一。《〈大学〉或问》的两句引文是:
(1)又有问[于程子]进修之术何先者。
程子曰:“[学]莫先于正心诚意,然欲诚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尽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穷而至之,所谓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②
(2)[或问于程子]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将止格一物,而万理皆通耶?”
[程子]曰:“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③《经筵讲义》整合后的引文是:
[程子曰]:“学莫先于正心诚意,然欲正心诚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尽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穷而至之,所谓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但能今日[而]格一件[物焉],明日又格一件[物焉],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④
另外,朱熹在《经筵讲义》中增加五条《〈大学〉或问》中没有的引文,其中前三条为程子文:
“学道以知为先,致知以敬为本。”
“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
“但庄整齐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①
后两条为程子门人谢良佐和尹悙之语:
至其门人谢良佐之言,则曰:“敬是常惺惺法。”
尹惇之言则曰:“人能收敛其心,不容一物,则可以谓之敬矣。”②
对《〈大学〉或问》“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一段,朱熹则没有收入《经筵讲义》中。这可能是由于这段文字争议较大,在该段中,朱熹对一些字句的解释与司马光等学者的解释多有不同,如对“格”字的解释,司马光认为“格”即“捍”,意即“抵御、抵抗”,但朱熹却解释为“达到、臻至”。另外,朱熹还反驳了上引谢良佐和尹悙对“格物致知”的解释。由此看来,《经筵讲义》应该说是朱熹对《〈大学〉或问》进行整合和折中后形成的版本。
对“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一段,《经筵讲义》中除了几个地方小有不同外,几乎是照单全录。朱熹明确指出,由“当然之则”所界定的“规则”是出自人心的。在“当然之则”后,他还特意加上了《〈大学〉或问》中没有的“具于人心”的说法,以便更清楚地说明天理的内在概念:
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具于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也。③
另外,《经筵讲义》也没有引录《〈大学〉或问》中第二段第二节的问答文字:
[或问于朱熹]曰:“然则子之为学,不求诸心,而求诸迹,不求之内,而求之外,吾恐圣贤之学,不如是之浅近而支离也。”①
在《经筵讲义》中,朱熹还向宁宗阐述了下面一大段《〈大学〉或问》中没有的内容:
凡此推演,虽出管窥,然实皆圣经贤传之意、造道入德之方也。抑臣闻之,治古之世,天下无不学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为尤密。盖自其为赤子之时,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傅,则又有小学之学。及其齿于胄子,则又有大学之学。凡所以涵养其本原、开导其知识之具,已先熟于为臣为子之时,故其内外凝肃、思虑通明之効,有以见于君临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执要,酬酢从容,取是舍非,赏善罚恶,而奸言邪说无足以乱其心术也。
降及后世,教化不修,天下之人例不知学,而尊且贵者为尤甚。盖幼而不知小学之教,故其长也无以进乎大学之道。凡平日所以涵养其本原、开导其知识者,既已一切卤莽而无法,则其一旦居尊而临下,决无所恃以应事物之变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后,始欲学于小学,以为大学之基,则已过时而不暇矣。
夫手握天下之图,身据兆民之上,可谓安且荣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术,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于前,骋其拟议窥觎于后,是则岂不反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于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励,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从今日从事于敬,以求放心,则犹可以涵养本原而致其精明,以为穷理之本。
伏惟陛下深留圣意,实下工夫,不可但崇空言,以应故事而已也。臣义切爱君,不觉烦读,下情无任恐惧恳激之至。②
这段论述同时涵盖了朱熹的政治观与认识论,是对《〈大学〉章句·序》中一些命题的进一步申论。①
六、结论
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原文的补注是其在程颐思想的基础上长期思考并提炼升华的结果,并在《〈大学〉或问》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其中与门人就“格物致知”进行的诸多问答和解释都收入《朱子语类》的第十六和第十八卷。在答文中,朱熹为阐释《大学》中的知识起源论而增加了许多要素。朱熹在淳熙四年(1177)完成了《〈大学〉或问》的解释内容,而后于绍熙五年(1194)为宁宗做御前讲座,并编成《经筵讲义》。应该说,宁宗是朱熹最显赫的弟子。令人称奇的是,在南宋时代,像朱熹这样重要的哲学家是可以亲自向皇帝传授如《〈大学〉或问》这样精深细微的哲学思想的,但不可否认,为讲授起见,朱熹在《经筵讲义》中删节了某些内容。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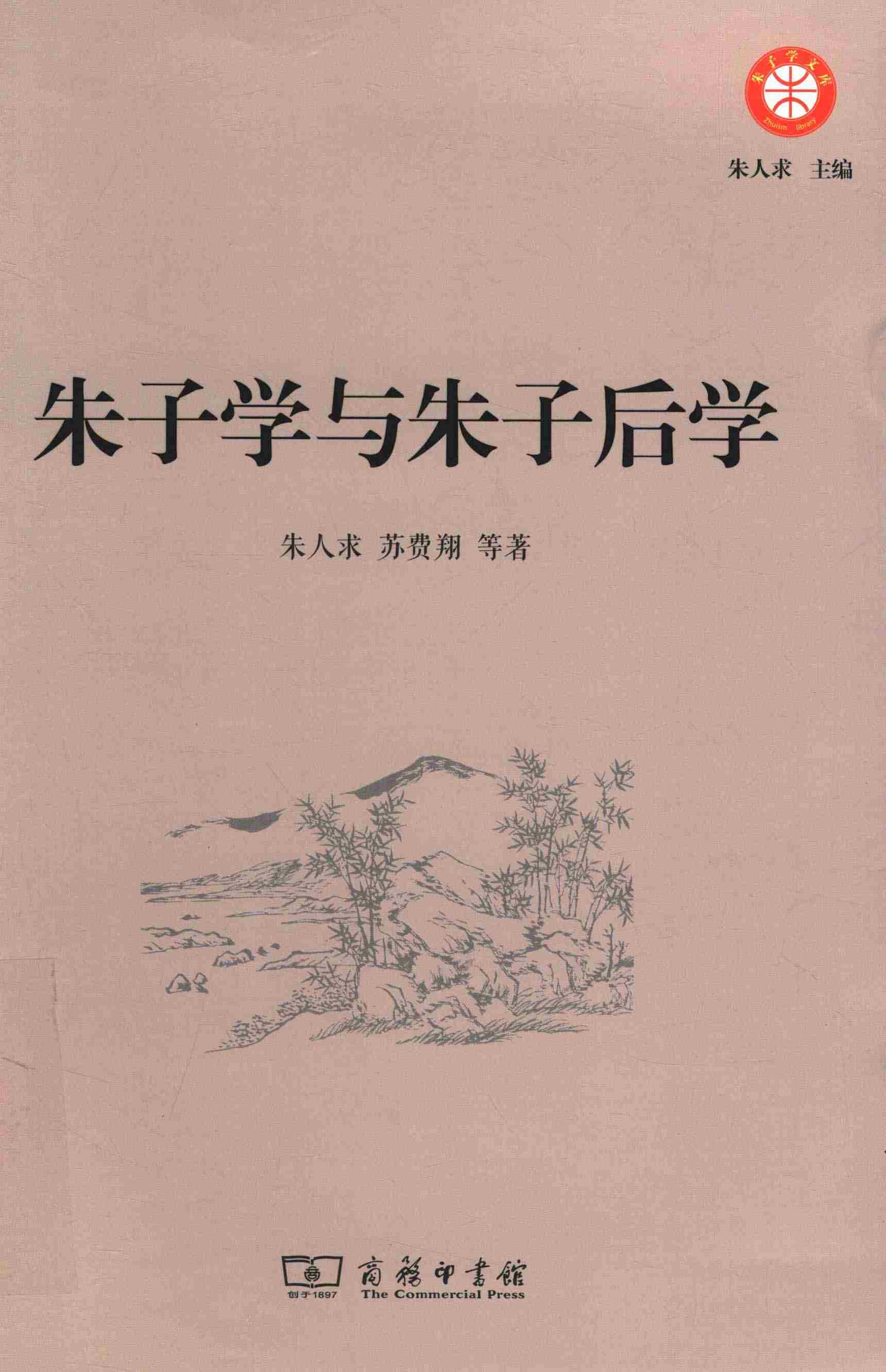
《朱子学与朱子后学》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收录了来自美国、德国、法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知名朱子学者近作14篇,内容涉及朱子的道统论、礼学、气论、诗论、格物致知论、人心道心、家国天下等问题,时间上从南宋跨越到现代,空间上从中国走向东亚世界,以点带面,简单勾勒了朱子思想的多元面向,介绍了朱子学的思想理念、政治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