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谢良佐与杨时对道学话语的构建
| 内容出处: | 《《诸儒鸣道集》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5197 |
| 颗粒名称: | 第八章 谢良佐与杨时对道学话语的构建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31 |
| 页码: | 294-322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 |
| 关键词: | 道学话语 谢良佐 杨时 |
内容
在一定程度上,二程弟子们在对其师学术的光大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程弟子们虽然在思想的原创性上并没有取得突破,但是却能够融会与发扬师说,积极寻求在政治和学术领域上扩大乃师的影响。显然,洛学之所以没有像朔学、王学、关学、蜀学那样昙花一现,而且还能够开出道南、湖湘学派交相辉映的盛况,二程之能“后继有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二程诸弟子,当以杨时和谢良佐最为代表。
谢良佐和杨时之于二程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在“接着讲”,虽然他们在对待佛老的态度上、在具体的工夫论层面,还是有所不同的。事实上,谢、杨所关注的问题已经明显偏于了工夫论的层面,表现出学理建构与工夫论选择二者之间的息息相关(考虑学理对如何做工夫的影响)。再者,二程诸弟子的学说更加转向心境化、内在化,也都表现出与佛老之学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性(这种关联,可以是外在的),这也招致了朱子的严厉批评。但是,仅就谢、杨二人来说,他们都有着鲜明的道统意识,仍不失儒者之风范。
全祖望以为,“明道喜龟山,伊川喜上蔡,盖其气象相似也”,①但其实从学术的角度说,虽然二人都有融会二程思想于一体的痕迹,但是谢良佐(谢上蔡)与明道思想更为接近,而杨时(龟山)与伊川思想更接近。
在二程的诸弟子中,朱子受谢、杨的影响最大,而对他们的批评也较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朱子思想也是在对二人思想的扬弃上,走向成熟的。
一谢良佐的高远之学
黄宗羲和全祖望都曾指出,谢良佐(下文简称为“上蔡”)为二程诸位弟子之首。实际上,上蔡对后世的影响也为二程的其他弟子所不及。据目前资料而言,后来对上蔡思想能提出全面而具有建设性回应的,莫过于朱子,而上蔡影响之大,确有赖于朱子之推波助澜也。
我们知道,朱子与上蔡之间有着很深的思想渊源。虽然后人多渲染朱子为道南四传,但是朱子对杨时和罗从彦的关注却远远不及对谢的关注。朱子在二十岁之前,曾至少三次精读上蔡的《论语解》,后来又精心编订《上蔡语录》,而他与张栻等湖南学者的往复学术论辩,许多就是围绕上蔡所提出的某些话头来展开的。相对来说,朱子对龟山的关心就少多了,更很少提到罗从彦。为什么朱子最早接触的是上蔡而非龟山的著作①?这个问题目前很难说清楚。不过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朱子在早年对上蔡有着特殊的兴趣,也颇为上蔡学说所吸引,这一点毫无疑义。朱子后来也承认,“熹自少年妄意为学,既赖先生之言以发其趣”②。可以说,上蔡是朱子早年思想发展的重要引路人之一(另外一个是李侗)。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后来对上蔡思想的扬弃,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朱子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正因为如此,在二程的诸弟子中,朱子对上蔡的批评最多,也最深刻。总之,我们不能过度宣扬朱子的所谓“道南之传”,却看不到朱子对前贤思想的广泛吸取。在这一点上,钱穆先生的看法无疑是睿智的。
朱子曾概括谢良佐的思想为:“以生意论仁,以实理论诚,以常惺惺论敬,以求是论穷理,其命理皆精当,而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则于夫子(二程)教人之法又最为得其纲领”③,这表明朱子对上蔡的思想颇多肯定。对此,陈来在《宋明理学》一书中已经有详细的论述,本文则重在考察上蔡与朱子思想之间的“跨带交流”,以对陈来的论述做出补充。
朱子对上蔡总的批评
朱子对上蔡的认识,有一个从早年全力推崇在到中晚年之后批评有加的复杂演变过程,而其中的转折点基本就是标志着朱子思想趋于成熟的“中和乙丑之悟”:朱子的“中和新说”首先是针对湖湘学派而起,而其批判的锋芒自然也会延伸到作为湖湘学派思想源头的谢上蔡身上。
朱子对上蔡的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视其为“禅学”。正如陈来所指出的,朱子所理解的“禅说”,泛指在外部特征上与佛家相类似各种学说和主张。这些外部特征包括:重内遗外、趋于简易、兀然期悟、弃除文字、张狂颠绝,①乃至忽略理而论心,对心理解知觉化、感觉化,言语高妙、不懈卑近等等。我们知道,朱子主张儒学与佛学的本质区别在于虚实之辨,上面所提到的“禅说”的特征,都表现出“虚”的一面。朱子对上蔡“禅说”的指责,也集中在这些方面上。再者,朱子对上蔡的批评,更注意上蔡学术对后世学风的“负面”导向上,而这又主要体现在工夫论的层面。
再者,朱子对上蔡的批评,也明显有突出儒学的德性价值观,反对上蔡主张心之无著、自由、活泼的一面。这与他主张辟佛老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在一定程度上,朱子对上蔡思想的批判,交织着对自己早年思想发展历程的反思,交织着他对于张九成、湖南诸学者、陆九渊及其后学们之间思想互动的反思和批判,也交织着朱子在面对上蔡与明道思想一致性之时的复杂心情,交织着他对于儒学与佛老之学关系问题的警觉。由此,朱子对上蔡思想的扬弃,所面对的就不只是已成为历史的上蔡文本,而是包含有赋予历史性的话题以当下意义的因素在内。我们在注意到朱子对上蔡的批评往往失之太过的同时,也要对朱子的特别用心有同情的理解。
求仁为急
谢良佐的仁说基本上承明道的仁说而来,但是对伊川的说法也有所继承。明道特别强调“体仁”,而上蔡则进一步把明道的说法发挥为要去察识、体会“生意”和“知觉”,以此来体认仁。他的观点又被概括为“只要见得此心,便以为仁”②、“心有所觉谓之仁”③、“有知觉、认痛痒,便唤作仁”①、“活者为仁”②等。对于谢的这一说法,后人或褒或贬,差距很大。赞同者强调其与明道“仁说”的一致性,而攻击者如朱子则直接视之为禅说。其实,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讲,朱子并不是没有看到上蔡与明道在仁说上的关联性,他也承认上蔡“以生意论仁”之说是“命理精当”。但是,他更关注的问题有点:一是认为以知觉论仁很难和佛家的说法相区分,二是这一说法或对后来学者产生负面的导向作用。在当时特定情景下,朱子的担心不能算是多虑。
先来说第一个方面:我们能很容易地在佛教文献中找出以知觉和“作用”为佛性的例子,而单纯地视“知觉”和“生意”为仁,就不足以揭示出儒学仁说的根本特性所在。在上蔡的文献中,他对上述界限并未做出严格的区分(也可以说对此问题未有自觉)。比如,谢上蔡曾提到:“仁是四肢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识痛痒,仁是识痛痒(曾本此下云‘儒之仁、佛之觉’)。”③又如他提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学佛者知此,谓之见性,遂以为了,故终归妄诞。圣门学者见此消息,必加功焉……仁,操则存,舍则亡……”④,这两种说法很容易混淆佛与儒学的界限。朱子尤其是担心,在对仁的理解上只强调个体化的感觉,而忽视理而只谈心,这会影响人们对仁的明晰的、可通约的理解,也会混淆性与情的界限。朱子的态度很明确,只有在心所知觉的对象是理的情况下,才可以称之为仁:“须是分作三截看,那不闻痛痒底是不仁,只觉得痛痒、不觉得理底,虽会于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须是觉这理方是。”①
朱子批评上蔡的“仁说”,就集中在其近“禅”上。如,针对上蔡在对《论语》“孝悌,其为仁之本”节的注释中,认为“夫仁之为道,非惟举之莫能胜、而行之莫能至,而语之亦难。其语愈博,其去仁愈远。古人语此者多矣,然而终非仁也……为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可以论仁者莫如人心,人心之不伪者莫如事亲、从兄……但孝弟可以为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间。盖仁之道,古人犹难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实欲知仁,则在力行,自省察吾事亲从兄时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则知仁矣”②的说法,朱子指出,上蔡“孝悌非仁”的说法是“盖谓别有一物是仁,如此则性外有物也”③“其意不主乎为仁,而主乎知仁”④。不仅如此,朱子还从上蔡的这一说法中读出了禅说的味道:“必如其说,则是方其事亲从兄之际,又以一心察此一心,而求识夫活物,其所重者乃在乎活物而不在乎父兄,其所以事而从之,特以求夫活物,而初非以为吾事之当然也。此盖源于佛学之余习而非圣门之本意。观其论此,而吕进伯以为犹释氏之所谓禅,彼乃欣然受之而不辞,则可见矣。”⑤于朱子,主张“以心察心”就是禅说(其实佛学内部也反对二心之说)。从文本上看,朱子对上蔡的指责未必恰当,但是当我们把考察的范围扩展到上蔡后学对其说法的扩展上时,我们或许能明白朱子的真正用心所指:
顷年张子韶之论,以为当事亲,便当体认取那事亲者是何物,方识所谓仁;当事兄,便当体认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识所谓义。某说若如此,则前面方推这心去事亲,随手又便去背后寻摸取这个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随手又便著一心去寻摸取这个义,是二心矣,禅家便是如此……,某尝举子韶之说以问李先生,曰:“当事亲便要体认取个仁,当事兄便要体认取个义,如此则事亲事兄却是没紧要底事,且姑借此来体认取个仁义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问:“上蔡爱说个觉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张子韶初间便是上蔡之说,只是后来又展上蔡之说,说得来放肆无收煞了。”或曰:“南轩初间也有以觉训仁之病。”曰:“大概都是自上蔡处来。”①
在这里,朱子就明确指出了上蔡仁说的负面影响——张九成对上蔡说法的引申,更像是主张“以心察心”。不只如此,朱子更担心上述说法会导致后人把仁理解为隐藏在背后的、独立的“神秘之物”,进而引申出是内非外、只在心上做工夫的做法。在朱子看来,后者的禅意要更浓,代表者就是陆九渊。
再说第二个方面,谢上蔡明确指出求仁当为学者之急务:“心有所觉谓之仁,仁则心与事为一……此善学者所以急急于求仁也”②,不独如此,他还认为:“世人说仁,只管着爱说,怎生见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关爱甚事?何故却近仁?”③这里,上蔡也明确提到了践履的重要性,但是从朱子上文中的批判来看,他显然认为即使上蔡主张力行,也是建立在主张先去“知仁”之上的,并把“知仁”化约为以“觉知”为根本工夫。朱子所批评上蔡的,不在于其无工夫,而在于其工夫之偏。
需要说明的是,正如陈来所指出的,上蔡在具体的求仁工夫上很明显地吸收了伊川“整齐严肃”以持敬的做法。因此,就谢本人而言,早年确实有张狂的毛病,但是在二程的敲打下,他在随后的二十年中还是保持了对此相当的警觉。他对于在工夫层面上放与守之辩证关系的认识也较恰当。而朱子所担心的,更在于上蔡上述说法对后学的影响:上蔡以求仁为急务,还不废其他的工夫,而湖南学者们主张在心之动念处体仁,却很少提到格物致知,这是对上蔡说法的极端化约。④朱子认为,这样做会失之急迫,乃至轻视下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把“急于求仁”变成了“急迫于求仁”,其流弊显而易见。
对朱子来说,他已经把上述流弊和谢的观点联系起来(甚至还上溯到明道那里),并下大力气来扭转这一风气。如,针对有弟子提问:“世有因谢氏之说而推之者,曰:‘人能自观其过,则知其所以观此者即吾之仁,是说如何?’”朱子就明确回答:
(朱子)曰:“此说最为新奇而可喜,吾亦尝闻而悦之矣。然尝以质之于师(李侗),而曰‘不然’,既又验诸行事之实,而后知其果不然也。盖方其无事之时,不务涵养本原,而必欲求过以为观省之资,及其观之之际,则又不务速改其过,而徒欲藉之以为知仁之地,是既失其所以求仁之方矣。且其观之而欲知观者之为仁也,方寸之地、俄顷之间,有过者焉、有观者焉、有知者焉,更相攫挐,迭相排逐,烦扰猝迫,应接不暇,盖不胜其险薄狂怪,而于仁之意味愈不得其彷佛,原其所以然者,盖亦生于‘以觉为仁,而谓爱非仁’之说耳。夫有是性必有是情,故仁之爱、知之觉,犹水之寒、火之热也。程子谓不可以爱为仁,盖曰不可以情为性,犹不可以寒为水而已,然其所谓以仁为爱,体爱为仁用,则于其血脉之所系,未尝不使之相为流通也。故于有子之言、以及此章之,未尝不以爱为言,至于以觉训仁,则盖尝明斥其非矣。今宗本程氏而不深考于此,乃直谓觉为仁、而深疾夫爱之说,则是谓热为水而恶言水之寒也。溺于新奇而不自知其陷于异端,诚以是说推之,则庶乎其有改矣。”①
显然,朱子对上蔡仁说的批评,更多是基于其对后学之导向的忧虑,而他对“因谢氏之说而推之者”(主要指湖南学者)的批评,也基本落脚在工夫论的层面。这其实正能反映出朱子在经历了长期徘徊于杨时学派(道南学派)与谢良佐学派(湖湘学派)之间,苦苦寻求为学工夫之后的一个基本结论。不过,朱子在指责谢的仁说为禅说之同时,也必须正视谢的说法与明道仁说的关联。事实上,是批评二程后学的同时,如何回护二程与其后学思想的一致性,这个问题始终是朱子需要认真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在为学之序上的纠结
朱子对上蔡的批评,还集中在“为学之序”的问题上。上蔡的为学工夫基本不出二程的范围,却有将其简易、内化、趋高的倾向,这也引起了朱子的极大忧虑。
上蔡主张“学者且须是穷理”①,而对于这个“理”字,又被他进一步限定为“天理”、“是处”。②这是对二程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不过,上蔡之穷理说也有其特殊之点:
(谢曰)学者且须是穷理,物物皆有理。穷理则能知天之所为,知天之所为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无往而非理也。穷理则是寻个是处。有我不能穷理,人谁识真我?何者为我?理便是我。穷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曰:“理必物物而穷之乎?”
(谢)曰:“必穷其大者,理一而已。一处理穷,触处皆通。恕其穷理之本欤(曾本此句为‘物虽细者亦有理也’)?”③
上蔡主张穷理要穷其大者,并认为“一处理穷”则能“触处皆通”。这一点是朱子所最为反对的。④事实上,在上蔡那里,理之“大者”只能是指心上之理,而认为“大者通则触处通”,无疑会导向工夫论层面的“不懈卑近”,甚至只是去穷心上之理、务内遗外(这也正是朱子与陆九渊的重要分歧之点)。朱子认为,必如上蔡所说,只去穷“大”的理,这样所见的理会也失之笼统。他有时也以曾点曾参父子为比,认为前者只是见到了理的大而虚的轮廓,而后者则步步为营,所见皆是实理,最终得以有“一以贯之”之境界。朱子强调,正是由于所见之理虚与实的不同,曾点“终不及他的儿子”。
事实上,朱子早年在阅读上蔡《语录》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疑问:既然“理无大小”,那么在穷理工夫上就不应该有所“拣择”,但是前人或主张要“为学有序”,或主张“穷其大者”,这一矛盾确实让朱子困惑了很久。
在李侗“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在分殊耳”的引导下,朱子经过艰苦的反思,明确反对主张只在一处穷理,并希望由此能触处皆通的说法,而是主张由积累而贯通说,其《格物补传》就是明证。朱子的态度很明确:因为理无大小,所以不能刻意拣择穷理的对象;又因为事上有分别,所以在穷理时又应该以切近者为先,此之谓“为学有序”,①这完全出于自然,而非拣择。
我们再以一个具体的例子对此详加说明。从二程到上蔡再到朱子,他们都关心一个问题:下学与上达或者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之间的关系。于朱子,他则在这个问题中注意到了上蔡的说法有颠倒“为学之序”的弊端:
谢子曰:“道须是下学而上达始得。不见古人就‘洒扫应对’上做起?”
(问)曰:“‘洒扫应对’上学,却似太琐屑,不展拓。”
(谢)曰:“凡事不必须要高远,且从小处看。只如将一金与人,与将天下与人,虽大小不同,其实一也。我若有轻物底心,将天下与人如一金与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将一金与人如天下与人相似。又若行千尺台边心便恐惧,行平地上心却安稳,我若去得恐惧底心,虽履千仞之险亦只与行平地上一般。只如洒扫不著此心,怎洒扫得?应对不著此心,怎应对得?故曾子欲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为此。古人须要就‘洒扫应对’上养取诚意出来。”②
下学而极其道则上达矣,然上达师无与焉。洒扫应对进退,乃动容貌、出辞气之事,必正心诚意而后能,与酬酢祐神之事何以异?孰以为可而先传?孰以为不可而后倦?如草木区以别矣,其为曲直一也。所以圣人克勤小物而必有始卒,盖本末无二道。③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上蔡的上述说法并不存在什么问题,而对于上蔡的上述说法,朱子却在《论语或问》和《语类》中有连篇累牍的抨击。当然,他也不忘突出上蔡此说与二程说法的区别所在:
……且如洒扫应对,子游便忽略了,子夏便只就这上做工夫。又曰:“谢氏说此章甚差。”①
上蔡之学,初见其无碍,甚喜之,然细观之,终不离禅底见解。如洒扫应对处,此只是小子之始学,程先生因发明虽始学,然其终之大者亦不离此。上蔡于此类处,便说的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终,若如此说时(即谢主张在下学上养诚意),便是不安于其小者初者,必知其有所谓大者方安为之……上蔡于小处,说的亦大了……上蔡大率张皇不安贴。②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个“思无邪”便了,便略了那诗三百,圣人须是从诗三百逐一篇理会了,然后理会思无邪,此所谓下学而上达也。今人止务上达,自要免得下学,如说道洒扫应对进退便有天道,③都不去做那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到得洒扫则不安于洒扫,进退则不安于进退,应对则不安于应对,那里面曲折去处都鹘突无理会了。这个须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贯通到这里,方是一贯。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习而但求察。④
“谢说则源于程子之意而失之远矣,夫下学而极其道固上达矣,然此方论下学之始为,未遽及夫极其道而上达之意也。上达固非师之所能与,然此方论为师教人之序,未遽及夫师无与焉之妙也。不吝之心一也,而一金天下则其捐之有难易之殊;不惧之心一也,而平地高台则其习之有先后之序。必如谢氏之说,将使学者先获而后难,不安于下学而妄意于上达,且谓为学之道尽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而无复格物、致知、修身、齐家之事也。其与子夏程子之意正相反矣。”曰:“程子亦常以理无大小,而洒扫应对精义入神者不异,何以异于谢氏之意?而以为相反,何也?”(朱子)曰:“程子所谓必有所以然者,以为同出于理之自然也。谢氏以必正心诚意而后能者,则以为同出于心之使然也。程子所谓慎独者,则不敢忽其小者,以求其理之所当。谢氏独以著心为言,则又如其论颜子克己、曾子贵道之说,初不问理之是非,而唯吾心之所欲为也。然此其失之小者耳。程子虽以理无大小为言,然其意则以明夫小不谨则将害其大,小不尽则不可以进于大,而欲使人谨其小者,以驯致其大者耳。如谢氏之云,则反使人恃其小者以自大,而谓夫大者之真不过如此也。此岂非相反之尤者哉?”曰:“其与子夏相反者,又何也?”(朱子)曰:“子夏正以次序为言,而谢氏以为无次序;子夏以草木为区别,而谢氏乃以为曲直则一;子夏以唯圣人为有始卒,而谢氏则无圣人众人之分,此其相反亦可见矣。”①
二程曾提出“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独”②,甚至主张“后人便将性命别作一般事说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统底事,就孝弟中便可尽性至命。至如洒扫应对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统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却被后来人言性命者别作一般高远说”③,上蔡的说法基本上是对此的“忠实“发挥。
表面上看,主张下学而上达是上蔡与朱子之间的共识,因此朱子对上蔡的批评颇令人感到不知所谓。但是就朱子的立场来说,他对上蔡的批评有以下几点:
其一,下学就是下学,上达就是上达,二者之间的分界不可混淆。因此,试图在“洒扫应对进退”这些下学之事上“著心”,认为只有在正心诚意之后才能做好洒扫应对进退之事的说法,就是“不安下学”、“妄意上达”,就是急于求知、急于求察。
其二,认为“下学而极其道则上达”的说法,也会导出“谓为学之道尽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不去做其他工夫的结论。其实,朱子的上述担心并不为过,上蔡不是提到过“一处理穷”则“触处皆通”吗?依照他的思路,在洒扫应对上做好了,就可以实现精义入神,自然就“无复格物、致知、修身、齐家之事也”了。
其三,上蔡总有把小事说大的毛病,这是其“狂者胸次”的体现。
其四,朱子还刻意强调了上蔡此说与二程说法的区别:二程的意思是强调理无大小,上蔡则强调心之所欲为;二程是在强调谨小以致大,上蔡则“恃其小者以自大”。
总之,朱子对上蔡的三点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其为学无次序(或次序不当),混淆了下学与上达之分。我们则认为,朱子对上蔡的批评,往往是基于他对上蔡学说的前见(事先形成的总体判断)使然。就文本来说,朱子的批评往往是在自说自话,未必都能抓住上蔡的本意。但是若是从同情之理解的角度来看,我们未尝不能从中看出朱子对于上蔡学说对后学潜在的引导作用的担心。事实上,朱子的上述担心又会在和湖南学者陆九渊及其弟子们的接触中一再被放大,并最终激化。
心无所著之“气象”
在上蔡的文献中,与“境界”一词内涵大致相当的“气象”一词频繁出现,而上蔡也比周、张、二程等人更为重视探讨圣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问题。上蔡的“气象论”自然也成为朱子之境界论的形成过程中,大力扬弃的对象。
有趣的是,上蔡的“气象论”也与明道的主张有直接的关联。明道的文献中时常有对“优游”、“心闲”和“无事”的吟咏,甚至有“太山为高矣,然太山顶上已不属太山。虽尧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①的说法,上蔡对此则有进一步的引申:
道以无所倚为至,……曾点之学,虽禹稷之事故可以优为。②
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才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点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然易做,只是无心近乎忘。③
把来作用弄,便是做两般看当了,是将此事横在肚里,一如子路、冉求相似,便被他曾点冷眼看,他只管独对春风吟咏,肚里混没些能解,岂不快活!①
显然,上蔡提倡的“无著”与明道提到的“无事”有内在的关联。但是从明道的《定性说》来看,明道所说的“无事”,是指“物来而顺应”,还是要强调去“应物”,而上蔡这段文字中的“无著”,就变成了“肚里混没些能解”的一味快活,成了真正的无所事事,这一点是朱子难以容忍的。朱子不止针对《论语》中“曾点言志”一段,强调“学固着学,然事亦岂可废也?若都不就事上学,只要便如曾点样快活,将来却恐狂了人去也”②,还就此引出了对上蔡的批评:
圣贤之心所以异于佛老者,正以无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谓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旷然无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则亦何以异于虚无寂灭之学,而岂圣人之事哉?抑观其直以异端无实之妄言(指列子御风)为比,则其得失亦可见矣。③
上蔡“尧舜事业横在胸中”之说,若谓尧舜自将已做了底事业横在胸中,则世间无此等小器量底尧舜,若说学者,则凡圣贤一言一行皆当潜心玩索,要识得他底蕴,自家分上一一要用,岂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丧志”之说,盖是箴上蔡记诵博识而不理会道理之病,渠得此语,遂一向扫荡,直要得胸中旷然、无一毫所能,则可谓矫枉过其正矣。观其论曾点事,遂及列子御风,以为易做,则可见也。大抵明道所谓‘与学者语,如扶醉人’,真是如此。④
这里,朱子对上蔡的批评显然是过了。上蔡所说的不著一事,本意还是要突出顺理之自然:如他又提到“尧舜汤武做底事业,只是与天理合一,几曾做作,横在肚里?见他做出许多掀天动地盖世底功业,如太空中一点浮云相似,他把做甚么……孔子便不然……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为,更不作用”①。就此而言,上蔡的说法仍不出明道“定心”之说的范围,而又点出“不著心”的实质是“与天理合一”,这是对明道说法的合理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再次转换视角,尤其是聚焦朱子晚年时人竞相谈论“与点之乐”的现实,就会明白朱子之指责上蔡此说的现实用心所在。②
以常惺惺论敬
朱子对上蔡的观点并非一味地批评,尤其是对于上蔡借用佛家“主人翁是常惺惺”的说法而提出“敬是常惺惺法”③的做法,朱子却是完全肯定的:“谢良佐之言则曰‘敬是常惺惺法’……此皆切至之言,深得圣经之旨。”④为什么这一次,以辟佛著称的朱子,却对于上蔡化用佛教的词汇不以为意呢?道理很简单,上蔡的这一说法完全是在强调“敬的要义就在于持续不懈的明觉状态”,这也就是朱子自己所说的“静中有个觉处”的意思,这虽在字面上与佛教一致,但是却无碍上蔡表达自己思想的清晰性(上蔡的本意是在强调儒家之敬与庄子心斋的区别:前者是要时时关注,后者则是要事事放下)。同时,上蔡的说法与朱子后来希望以敬来统摄自己心性修养工夫的努力也是一致的。如,朱子在著名的“中和新说”中就提到:“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心主乎一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是以君子之于敬,亦无动静语默而不用其力焉。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艮》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有以主乎静中之动,是以寂而未尝不感;有以察乎动中之静,是以感而未尝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贯彻而无一息之不仁也。”①在这里,“知觉不昧”即是上蔡“常惺惺”之确解,它是贯通动静的,而主敬也恰恰成为朱子在多年探求习性修养工夫之后的最终结论。在此意义上,他对上蔡的说法当然是肯定的。
总论
朱子曾指出,上蔡是张无垢和陆象山的思想源头,但是从陆九渊的立场看,其实上蔡对他的影响甚微(陆九渊的著作中并未提及上蔡)。反之,上蔡对朱子的影响却始终挥之不去:朱子对上蔡思想不只是有批判,更有吸收。在不同的时期,我们都能在朱子的文献中找到他首肯上蔡某观点的文字,虽然越是到了晚年,他批评上蔡的文字也越多起来。可以说,上蔡在后世的最大贡献,就是引起了朱子的积极回应,从而使得上蔡所关注的许多问题一变成为理学的热点问题。当然,《上蔡语录》之所以能在后世广为流传,也是与朱子的整理分不开的。
二杨时之学趋于简易
与上蔡相比,杨时(下文简称龟山)与佛老的关系更近,甚至还注释过庄、列的著作,而朱子对龟山的批评也更为直接。上蔡的所谓“禅说”,还只是与佛学的某些外部特征相类似,而龟山的许多说法,却是真正的禅说,如全祖望(谢山)引宋儒黄震(东发)语即指出:
祖望谨案:慈溪黄氏曰:“龟山气象和平,议论醇正,说经旨极切,论人物极严,可以垂训万世。使不间流于异端,岂不诚醇儒哉?乃不料其晚年竟溺于佛氏。如云:‘总老言经中说十识,第八庵摩罗识,唐言(田按,即汉语称为)白净无垢,第九阿赖邪识,唐言善恶种子。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又云:‘庞居士谓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此即尧舜之道在行止疾徐间。’又云:‘《圆觉经》言作、止、任灭是四病。作即所谓助长,止即所谓不耘苗,任灭即是无事。’又云:‘谓形色为天性,亦犹所谓色即是空。’又云:‘《维摩经》云真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又云:‘庄子《逍遥游》所谓无入不自得,《养生主》所谓行其所无事’,如此数则,可骇可叹。”黄氏之言,真龟山之诤臣也,故附于此(本段文字的点断,以中华书局版为准)。①
全祖望此文颇能揭示龟山晚年溺佛的状况(其实龟山早年也有溺佛的经历),但是查对黄震的原文,谢的引文与东发的原文出入较大(或许是点校者的错误使然,或许是谢山对东发的文字有所总结):
(针对龟山的几条“禅说”)按附合至此,可怪可骇。人心一至溺,是非即成颠倒,前辈尚不能免,后学可不自惧乎?夫龟山本忠门之高第也(田按,下疑有脱文)。
龟山气象平和,议论醇正,说经旨甚切,论人物极严,事必于其正理,而凡挟数用术苟就功名者,决不许之,可以垂训万世。使不间流于异端,岂不诚醇儒哉?横渠思索高深,往往非后学之所宜先,似不若龟山之平直,动可人意。然其精到之语,必前此圣贤之所未发,斥绝异端,一语不流。高明者多自立,浑厚者易迁变,此任道之有贵于刚大哉。②
无论如何,龟山晚年溺佛的程度要远远超过上蔡,其引佛老语以解经的程度也是上蔡所不及的。不过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却认为,“但是无论如何,至少在批判王学的场合,杨时并不在佛教面前丢盔弃甲:‘夫儒佛不两立久矣,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王氏乃不会起是非邪正,尊其人,师其道……’”③,此话或许过重,杨时在涉及儒佛的根本区别之处,还是能坚持儒者立场的。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黎昕先生所言,“据陈荣捷教授统计,《四书集注》共用了32个学者的731条语录,而其中引杨时语录就达73条之多,仅次于二程和尹淳之后(二程为225条,尹焞为90条),位居第三”。①这一事实颇能说明,较之于上蔡的高妙之言,朱子更喜欢龟山对四书的平实解读,认为其立场与二程更为接近。
在很大程度上,龟山是二程的祖述者,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龟山还是有自己特色的。
理与气
二程对理气关系问题讨论的不多,龟山对此问题则有所关注。他对理与气的说明比较微妙:既有“通天下一气”的说法,也有“天下只是一理”的说法,但是却没有明确地对理与气之关系如何予以明确的说明。事实上,似乎理气关系也并不是二程及其弟子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在龟山,对理这一概念的讨论并不多,而引人注意的倒是其对“通天下一气”这一观点的多次强调。龟山并毫不掩饰这一说法与庄子思想的渊源关系(至少在《踵息庵记》一文中,“通天下一气耳”的说法与庄子有莫大的关系,而张载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过类似的说法)——虽然龟山这一说法也是受到孟子和张载影响的产物。关于这个问题,土田健次郎先生即认为,只有在朱熹那里,“气”才是始终与“理”相对置的概念,而理气关系论也才成为贯穿于宇宙论、人性论、道德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在二程及其弟子们那里,情况还不是如此。他以程颐为例,指出,“在程颐的有关文献中,将‘理’字与‘气’字明确对置的例子几乎没有……仅从字面上讲,可以说程颐还没有理气之论”②。我们认为,土田健次郎先生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在二程及其弟子们那里,的确还没有把理气关系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模式,也可以说,他们对理的关注要远远优先于气。
在龟山那里,对作为本体意义的“理”字提到的甚少,更没有将理与气对置的例子。毋宁说,龟山对理和气的认识基本上是因袭前人之论,由此,学界讨论龟山究竟是理一元论者,还是气一元论者,还是理气二元论者的问题虽然很热烈,却始终难有定论。
就《龟山语录》文本而言,龟山论“气”的内容相对固定:较之张载区分气之本然和气之客形、朱子能从气的感性的殊象中提炼出作为一般的“气”之概念这样的新意来说,龟山对气的理解毫无新意可言。与此相对,出现在《龟山语录》中的“理”字的含义却比较复杂,但是主要还是在集中在“规律”的意义上,进而提出“乘理”、“任理”、“循理”等概念,却基本上没有像二程那样在本根、本体的意义上使用过理字。这种情况,以下面的这则材料最具代表性:
语仲素(罗从彦):“《西铭》只是发明一个事天底道理,所谓事天者,循天理而巳。”①
“事天”,就是要循天之理,在这里,“理”还是仅仅是规律的含义。陈来指出,龟山的格物论有摇摆于理学与心学之间的一面,其实龟山在对理气关系的说明上,未尝没有摇摆的因素存在。龟山学说的特色就是杂众说,还并没有凝聚成清晰、有系统的自家理论。
性论
龟山持性善论立场,这一点当无异议。他在对《中庸》首章的诠释中即指出:
“‘天命之谓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谓道’,离性非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则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盖原于此。谓性有不善者,诬天也。性无不善,则不可加损也,无俟乎修焉,率之而已。”②
龟山此文提倡“性不假修”,这难以得到朱子的认同,但是龟山这里所持的性善论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不过,龟山对性的理解也颇受佛家的影响:他曾直接以佛学术语比附性善论来反驳王安石“性无善恶”的性论:
通揔老言:“经中说十识,第八庵摩罗识,唐言白净无垢,第九阿頼耶识,唐言善恶种子。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谓探其本;言善恶混,乃是于善恶巳萌处看。”荆公盖不知此。①
按照揔老的意思,只有就人的善恶念头已经萌生之时说,才能说善恶混,而就性之本(本源、本质、本然)来说,则性为善,龟山所取于他的,也仅仅只是这一点。不过,这一说法在朱子那里显然是无法接受的:这无异于是说“本然之善不与恶对”,也很自然会被引申成为性超善恶的观点,对之的批判尤为严厉。但是我们从这段文字本身来看,龟山还是意在强调“性善是本”,有善有恶是末的观点。
又如,龟山也曾以“具足圆成、本无亏欠”、“性无变坏”等词汇来诠释性,并由此提出“性不假修”的说法。我们认为,类似这样的说法在儒家典籍中是没有先例的,只能是受到佛说影响下的产物。我们知道,在朱子之前,宋儒们对于心与性并未做出过严格的区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张载和明道所讨论的定性问题,其实应该称为“定心”才更为恰当。因此,龟山以性为“具足”、“无亏”云云,其实是在另一意义上提出了本心的提法。此外,龟山明确提出过“性、命、道,一体而异名”②的说法,颇有把“性”上推到天之层面的意思(即认为性在人欲之先),这实际上是开了湖南学者尤其是胡宏将“性”本体化之先河。
虽然龟山的性论受到了“禅说”的影响,但是其根本处并未走出儒家的藩篱,这又有表现为龟山在论性上对孟子道性善的反复强调,也表现在其多次宣扬明道所主张的、以“循天理”来诠释“率性”的观点。同时,针对张载气质之性的说法,龟山则极力将其与孟子的性善说统一起来:
仲素问:“横渠云气质之性,如何?”曰:“人所资禀固有不同者,若论其本,则无不善。盖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无不善,而人则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时而恶矣。犹人之生也,气得其和则为安乐人,及其有疾也,以气不和而然也。然气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则反(天按,当为返字)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说气质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刚柔缓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谓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于湛浊,则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①
龟山上述观点很独特,他是用常态和非常态之分来统合孟子与张载的观点,其立论是基于性气不分的一元思路。对龟山而言,性只有一个(龟山所理解的性,表述为心更合适),其常态、本然是善,恶则只是性之偶然的、非本然的状态。龟山的这一说法和张载以气之未形、已形的两分来论性不同,也与朱子对气质之性的理解不同:对朱子来说,只能以理为善,龟山的说法是混淆了理与气、性与情之别:“阴阳,气也。不能无不善,唯所以阴阳者,则是所谓道,而无不善也。今既以阴阳为无不善,而不能必其无不善,则又曰‘善者其常而亦有时而恶焉’,则非所以语性之善矣。”②再者,朱子显然认为,人作为理与气的合体,必然会受到气禀的影响,气质之性与生俱来,也不可摆脱,朱子认为这才是常。由此,人所能做的,就不是要去根除气质之性,而是要努力变化气质,直到人的行动皆能发于天理之公,直到气质完全听从天理的指挥为止。但是从龟山的这段话来看,他显然认为气质之性是应该“去除”的。正因为龟山不注意区分性与气、性与情的界限,因此他又会主张“口之于味等,性中本来有这个,若不是性中有,怎生发得出来”①之说,这一说法也是朱子难以赞同的。龟山的这一说法与清代学者尤其是戴震的看法颇为类似
龟山对孟子与张载性论的统合,显然尚且处在感性和经验层面,但这却足以保证其儒者的基本立场。
格物说
龟山的格物说也颇具特色:他将格物与明善和诚身联系起来,有明显强调内在优先性的倾向,这一点却遭到了朱子的严厉批评。但是龟山的说法并非没有所本,在很大程度上,龟山的格物说是对明道说法的进一步引申。
明道的格物说特别强调反身、强调学文与进德的不同,而庞万里先生也把这一点作为明道与伊川格物说的显要不同之处。如,明道就很强调:
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所守不约,泛滥无功。②
致知,但知止于至善……不须外面。只务观物理,汎然正如游骑无所归也。③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于至善”,反己守约是也。④
明道强调内(我)之对于外(物理)的优先性。相对而言,伊川则在强调明善的同时,指出明善不能离开明理,尤其是穷物理:
人患事系,思虑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在乎格物穷理。穷至于物理,则渐久后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⑤
伊川与明道不同之处,在于突出“明善在于格物穷理”,因为二者其实“只是一理”,强调了二者同等的重要性。
龟山对于二程的格物说都有所继承,但主要还是以明道说为主,而更趋于“简易直接”,甚至提出“物固不可胜穷,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①的说法。这就和明道主张以我为本来通物我的说法有所偏离。龟山屡屡强调“一”(一气、一理、一身)以及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而对“理一分殊”原则未必有明确的理解,这是导致上述偏离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伊川之强调“理一分殊”,是在先承认分殊的前提下,再去求其贯通之处的“理之一”,此即所谓在积累中以求贯通,由此,对外物之殊性的认识就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在“理一分殊”的模式下,人之善与物之理都是作为“一”之理的体现,其本则同,因此明善与格物就不再是不相关的了。在明道,虽然很强调以我为主的格物观,但也强调“物来顺应”,强调要不系于我而系于物。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容纳了对外物的关注。
而在龟山,则仅仅以“凡形色之具于吾身,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目之于色,耳之于省,口鼻之于美味,接乎外耳不到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②云云以为说明。对此,朱子明确予以反驳:
程子曰:“所谓穷理者,非必尽穷天下之物,又非只穷一物而众理皆通,但要积累多后,脱然有贯通处”。又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不必言因见物而反求诸身也。然语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③
反身而诚者,物格知至而反之于身,则所明之善无不实,有如前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无内外隐显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则反之而不诚者多矣,安得直谓但能反求诸身,则不待求之于外,而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而无不诚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离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尤非大学之本意矣。①
于朱子而言,认为反身而诚就可以穷尽天下之理也属于“禅说”之属,这与陆象山的说法没有区别。朱子也注意到,龟山并没有认为只要“反身而诚”就够了,而同时也强调学习典章的重要性:
(问)曰:“杨氏之说有‘虚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
(答)曰:“固也。是其前段主于诚意,故以为有法度而无诚意则法度为虚器,正言以发之也。其后段主于格物,故以为若但知诚意,而不知治天下国家之道,则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为虚器而不之讲,反语以诘之也。此其不同审矣。”②
朱子意谓,龟山是从一正一反两方面来说明:诚意固然是主导,但是诚意并不能代替格外物,二者不可偏废。这表明,龟山毕竟不同于与后世主张只在心上做工夫者,与伊川的格物说并无根本冲突。但是在总体上,龟山在格物与诚身之间,更重视的是后者。朱子注意龟山的,主要是这一点。
“诚”不仅是龟山格物说的核心,还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意义:
盖惟圣人与天同德者为能诚焉。③
自一身之修推而至于天下,无二道也,本诸诚意而已。④
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⑤
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诚意为主。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也。⑥
大致说来,诚意之于龟山,相当于敬之于二程,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但是,龟山以诚意说来统摄为学工夫,其重内在、重简易的特色也更为明显。
对《中庸》的诠释
在许多学者看来,对《中庸》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未发”问题的关注,是以龟山为代表的道南学派的主要特色所在,这也是推动朱子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从文本上看,这些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如龟山就认为:
《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①
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②
龟山这里对《中庸》的赞叹,足以表明其对《中庸》的推许要远在《论》、《孟》、《大学》之上。龟山的《中庸解》久已遗失,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宋人卫湜在《礼记集说》中对龟山《中庸解》的摘录,以及朱子对龟山中庸说的批评性资料而一窥其大概。③在此方面,复旦大学的郭晓东教授已有《论杨龟山对〈中庸〉的诠释及朱子的批评》④一文有专门的论述。本文则仅结合朱子对龟山“中庸义”的批判,具体来看龟山与二程之观点上的细微差异之处。
总的说来,朱子对龟山的中庸说之批评要大于肯定,并多次明确指其为“禅说”。如,针对龟山对《中庸》中“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矣”、“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段的解释中,提出“无适而非道”的说法,朱子即认为:
杨氏“无适非道”之云则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尽……若便指物以为道,而曰“人不能顷刻而离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则是不惟昧于形而上下之别,而堕于释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学者误谓“道无不在,虽欲离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则虽猖狂妄行,亦无适而不为道”,则其为害将有不可胜言者,不但文义之失而已也。①
朱子的意思,龟山的“无适非道”说,在被理解为“所谓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间不能违物而独立,是以无适而不有义理之准则,不可顷刻去之而不由”的情况下,这是可以成立的。但是,龟山此说也可以被理解为事道不分乃至“作用见性”的“禅说”,朱子更忧虑这一点。从龟山的文本来看,其本意恰恰就是朱子所批评的后一种情况。但是,龟山此一说发显然来自二程:
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一作敬),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分于道也远矣……彼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为隘也。吾道则不然,率性而已。②
……夫道不可须臾离也,以其无适而非道也。故于不闻不睹必恐惧戒慎焉,所以慎其独也。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其充此之谓乎。夫如是,诚之至也,故合乎神天,而卒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盖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天,兹其所以为至也……③
我们认为,龟山的上述说法虽然本于二程,不过二程的说法主要是针对儒释之别而发,所要突出的是“直内与方外”的统一,与朱子的第一种解释意思大致一致;而龟山的说法则引向了慎独说,强调恐惧戒慎,突出的是人的内在性工夫。就这点来说,朱子对龟山的指责非常牵强。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龟山从“无适非道”说中挥进一步推出“率性”说,并进一步导出“寒而衣,饥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视听,手足之举履,无非道也……夫尧舜之道,岂有物可玩而乐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农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乐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谓知之者也”①以及“尧舜之道曰孝弟,不过行止疾徐之间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日出而作,晦而息,无非道者,譬之莫不饮食而知味者鲜类”②的说法,就会明白朱子反感龟山此说的深层原因:朱子既指出龟山的说法混淆了形上形下之别,会导致“认欲为理”、“不问理之是非”之流弊,也与“禅说”无法区分(俱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二)。朱子的此处担忧也不是没有理由。
如果说朱子上面对龟山的指责还显牵强的话,那么他对龟山的“未发”说则给予了不加掩饰的指责:
杨氏所谓“未发之时,以心验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则发必中节矣”,又曰“须于未发之际能礼所谓中”,其曰验之、体之、执之,则亦吕氏之失也。③其曰“其恸其喜,中固自若”,疑与程子所云“言和则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细推之,则程子之意,正谓喜怒哀乐已发之处见得未发之理发见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无偏倚、过不及之差,乃时中之中而非浑然在中之中也。若杨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庄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则是以为圣人方当喜怒哀乐之时,其心漠然同于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为,皆不复出于中心之诚矣。大抵杨氏之言多杂于佛老,故其失类如此。④
朱子所批判龟山文字的原文颇长,其核心部分为:
……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验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发而中节,中固未尝忘也。孔子之恸、孟子之喜,因其可恸可喜也,于孔孟何有哉?其恸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鉴之茹物,因物而异形,而鉴之明未尝异也。庄生所谓“出怒不怒则怒出于不怒,出为无为则为出于不为”,亦此意也。若圣人而无喜怒哀乐,则天下之达道废矣……故于是四者,当论其中节、不中节,不当论其有无也。或问:“正心诚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后世自是无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一念之间毫发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圣人始得。且如吾辈,还敢便道自已心得其正否?此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于喜怒哀乐己发之后,能得所谓和。致中和,则天地可位、万物可育,其于平天下何有?”①
从龟山的这段文字可见,可以说龟山此说与明道的《定性说》颇有类似之处,但也可以说是龟山受到了邵雍乃至佛老的影响,朱子之批评,不可谓无的放矢。此外,二程都不主张去体验未发之中,甚至二程在与弟子们讨论中和问题之时,都不曾涉及如何做工夫论的问题。就这一点说,主张在工夫论层面“体验未发”,的确是所谓龟山“道南旨诀”的特色所在。
朱子之批评龟山的,主要集中在龟山主张去“验之、体之、执之”上,颇有主张去“察识”中或是“求中于未发之先”的嫌疑,难怪土田健次郎会认为,湖湘的胡氏主张“察识”已发之端倪论,也是受到了龟山的影响。②总的看来,龟山并不主张纯粹静的工夫,在这一点上龟山与后来学者罗从彦、李侗的主张还是很有差距的。我们在提到“道南旨诀”之时,也要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两次的“中和之悟”是朱子实现思想飞跃的关键点,而对龟山及李侗所主张的“体验未发”说之扬弃,则是朱子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朱子,一味着意去“体验未发”和一味去“察识心之动处”的弊端都是一样的,二者虽然在表面上截然相反,却都属于“禅说”之属。
又如,针对龟山对《中庸》里“中庸不可能”的解释,朱子更是认为:
游氏以舜为绝学无为,而杨氏亦谓:“有能斯有为之者,其违道远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无事焉,夫何能之有?”则皆老佛之余绪。而杨氏下章所论“不知不能,为道远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学于程氏之门号称高第,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晓也已。①
明道对《中庸》这句话的解释为:“克己最难,故中庸不可能也”②,与龟山强调“无为”和“无事”相对照,显然明道更强调做工夫的说法,更合朱子的口味。
再如,针对龟山对《中庸》二十七章的解释,朱子强调:
杨氏之说亦不可晓,盖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礼者道体之节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后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礼为德,而欲以凝夫道则既误矣,而又曰“道非礼则荡而无止、礼非道则梏于仪章器数之末而有所不行”,则是所谓道者,乃为虚无恍惚元无准则之物,所谓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于道也,其诸老氏之言乎?误益甚矣。③
龟山注释的原文如下:
道之峻极于天,道之至也,无礼以范围之,则荡然无止,而天地之化或过矣。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所以体道而范围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谓至德者,礼其是乎?夫礼,天所秩也。后世或以为忠信之薄,或以为伪,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后行”,盖道非礼不止,礼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资也。苟非其人而梏于仪章、器数之末,则愚不肖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
龟山此段释文与二程的说法也有很大的差距:主要是突出的所谓道与礼的内在关系。但是在朱子看来,龟山的说法有认为“道是离开礼而独立存在的空虚之物”的嫌疑。
比较而言,对《中庸》的诠释是龟山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受到朱子批评最多的部分(朱子对龟山之性论、诚意论的批评都属于对中庸义的批评)。在朱子那里,龟山与二程在诠释《中庸》上的差异被刻意放大了。这又被纳入到了其扬弃二程后学之流弊以实现统一学术的大思路下,成为其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龟山之释《论语》
龟山对《论语》、《孟子》的诠释,影响远不及其对《中庸》的诠释。原因就在于,龟山的论、孟解缺少自身的特色吧。龟山的《论语解》、《孟子解》同样早已遗失,但是在朱子的《论孟精义》和《四书或问》中还保存了一些内容。据《论语或问》,龟山的《论语解》有初本、次本、三本之说,①于此可见龟山在《论语解》上也耗费了不少工夫。
在龟山的《论语解》中,他对仁的诠释最引人注目:虽说基本上是对二程仁说的发挥,但是却融合了理一分殊的思路:
道二,仁与不仁而已,故修道必以仁。仁者,人也,合天下之公,非私于一己者也。盖无公天下之诚心,而任一己之私意,则违道远矣。然仁者人也,爱有差等则亲亲为大;义者行吾敬而已,时措之宜则尊贤为大……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事亲,仁之实也,故修身以事亲为本。仁者人也,非私于一己者也。事亲而不知人,则其锡类不广矣。视天下无一物之非仁也,其知人乎?知人而不知天,则夷子之二本也。盖五品之差,天叙也。先王惇五典而有厚薄隆杀之别焉,明天叙而已。②
龟山从“理一分殊”的模式论仁,可谓发二程之所未发:既强调了公天下之心是仁之本;又突出了次等(天叙)是仁之施,是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只有把公天下之心和具体实施层面的爱有次等贯通起来才谓之仁。龟山进而指出,“视天下无一物非仁”的说法是“不知人(之特殊性)”,而不讲次等的说法是“不知天(秩序)”。龟山这一说法力图贯通天和人,一和殊之的关系,颇有创见,也颇受朱子的肯定。
我们知道,“父子相隐”问题始终是儒学的一大困扰。对此的回答,势必要在情理法之间选取一个优先者,而舍去另一方。但是,如果刻意把情与理的矛盾对立起来,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难说圆满。
龟山对此的回答就是完全突出一个情字:“父子相隐,人之情也,若其情,则直在其中矣。子证其父,岂人情也哉?逆而为之,曲孰甚焉”、“父子之真情,岂欲相暴其恶哉!行其真情,乃所谓直。反情以为直,则失其所以直矣。乞酰之不得为直,亦犹是也”。①龟山的意思,情与直是同一的,任情就能保证直。对此,朱子表示并不赞同:
杨氏之说本乎情,谢侯氏尹氏之说本乎理,皆有所不同也。今试以身处之,则所谓情者可体而易见,所谓理者近于泛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见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则人情之或邪或正,初无准则,若之何其必顺此而皆可以为直也邪?苟顺其情而皆可谓之直,则霍光之夫妇相隐可以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皆咈其情而反陷于曲矣,而可乎哉。②
龟山所说的情,当指真情。但无论如何,情与直是不能直接等同的。在朱子,性无不善,而情则或有不善。真情过当也会流于私,所以在重视真情的同时,也还是要讲到准则,讲到理以为限定。于朱子来说,行动本乎人情固然很重要,但还是要做到依乎天理,虽然在朱子那里,情和理之间的界限未必就十分清楚。
朱子对龟山论、孟注释的肯定颇多,甚至不乏“独得之”、“至矣”这样的赞语,但在一些涉及思想性内容的领域(往往是上文提到的几个方面,朱子对龟山的批评依然尖锐)。抛开龟山对一些细节问题的论述,我们注意到朱子所肯定龟山的,往往是其注释平实之处,而对其近禅、新奇、过高,疏阔之论则持批评立场。
例如,龟山对“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解释为:“会物于一己,而后能公天下之好恶,而不为私焉。”①对此,朱子直言龟山的说法本于僧肇,与儒家的说法不类:
杨氏会物于一已者,僧肇之言也。夫谓无私心而自无物我之间,可也。若有意会物而又必于已焉,则是物我未忘,率彼以合乎此也。且物之与己,又若之何而可会哉?此记佛者之言而较之,犹未得为极至之论,况杨氏以儒者而数称之,则不可晓矣。②
龟山此说是否本于僧肇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龟山这一主张泯除物我痕迹的说法,这显然是朱子不能接受的。类似的例证极多,此不赘述。
龟山著述很多,但是在道学史上留下影响的内容并不多。这多少也是诸二程弟子的宿命:处在北宋五子与朱子之间,学术基本以述为主,自身特色不足(即便稍有己见,也多成为朱子批评的对象)。随着朱子影响的扩大,二程诸弟子只有被朱子的光环所笼罩。在很大意义上,他们的价值就在于一度成为朱子思想发展的引路人乃或批评对象,从而促进了朱子思想的飞跃。
谢良佐和杨时之于二程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在“接着讲”,虽然他们在对待佛老的态度上、在具体的工夫论层面,还是有所不同的。事实上,谢、杨所关注的问题已经明显偏于了工夫论的层面,表现出学理建构与工夫论选择二者之间的息息相关(考虑学理对如何做工夫的影响)。再者,二程诸弟子的学说更加转向心境化、内在化,也都表现出与佛老之学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性(这种关联,可以是外在的),这也招致了朱子的严厉批评。但是,仅就谢、杨二人来说,他们都有着鲜明的道统意识,仍不失儒者之风范。
全祖望以为,“明道喜龟山,伊川喜上蔡,盖其气象相似也”,①但其实从学术的角度说,虽然二人都有融会二程思想于一体的痕迹,但是谢良佐(谢上蔡)与明道思想更为接近,而杨时(龟山)与伊川思想更接近。
在二程的诸弟子中,朱子受谢、杨的影响最大,而对他们的批评也较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朱子思想也是在对二人思想的扬弃上,走向成熟的。
一谢良佐的高远之学
黄宗羲和全祖望都曾指出,谢良佐(下文简称为“上蔡”)为二程诸位弟子之首。实际上,上蔡对后世的影响也为二程的其他弟子所不及。据目前资料而言,后来对上蔡思想能提出全面而具有建设性回应的,莫过于朱子,而上蔡影响之大,确有赖于朱子之推波助澜也。
我们知道,朱子与上蔡之间有着很深的思想渊源。虽然后人多渲染朱子为道南四传,但是朱子对杨时和罗从彦的关注却远远不及对谢的关注。朱子在二十岁之前,曾至少三次精读上蔡的《论语解》,后来又精心编订《上蔡语录》,而他与张栻等湖南学者的往复学术论辩,许多就是围绕上蔡所提出的某些话头来展开的。相对来说,朱子对龟山的关心就少多了,更很少提到罗从彦。为什么朱子最早接触的是上蔡而非龟山的著作①?这个问题目前很难说清楚。不过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朱子在早年对上蔡有着特殊的兴趣,也颇为上蔡学说所吸引,这一点毫无疑义。朱子后来也承认,“熹自少年妄意为学,既赖先生之言以发其趣”②。可以说,上蔡是朱子早年思想发展的重要引路人之一(另外一个是李侗)。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后来对上蔡思想的扬弃,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朱子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正因为如此,在二程的诸弟子中,朱子对上蔡的批评最多,也最深刻。总之,我们不能过度宣扬朱子的所谓“道南之传”,却看不到朱子对前贤思想的广泛吸取。在这一点上,钱穆先生的看法无疑是睿智的。
朱子曾概括谢良佐的思想为:“以生意论仁,以实理论诚,以常惺惺论敬,以求是论穷理,其命理皆精当,而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则于夫子(二程)教人之法又最为得其纲领”③,这表明朱子对上蔡的思想颇多肯定。对此,陈来在《宋明理学》一书中已经有详细的论述,本文则重在考察上蔡与朱子思想之间的“跨带交流”,以对陈来的论述做出补充。
朱子对上蔡总的批评
朱子对上蔡的认识,有一个从早年全力推崇在到中晚年之后批评有加的复杂演变过程,而其中的转折点基本就是标志着朱子思想趋于成熟的“中和乙丑之悟”:朱子的“中和新说”首先是针对湖湘学派而起,而其批判的锋芒自然也会延伸到作为湖湘学派思想源头的谢上蔡身上。
朱子对上蔡的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视其为“禅学”。正如陈来所指出的,朱子所理解的“禅说”,泛指在外部特征上与佛家相类似各种学说和主张。这些外部特征包括:重内遗外、趋于简易、兀然期悟、弃除文字、张狂颠绝,①乃至忽略理而论心,对心理解知觉化、感觉化,言语高妙、不懈卑近等等。我们知道,朱子主张儒学与佛学的本质区别在于虚实之辨,上面所提到的“禅说”的特征,都表现出“虚”的一面。朱子对上蔡“禅说”的指责,也集中在这些方面上。再者,朱子对上蔡的批评,更注意上蔡学术对后世学风的“负面”导向上,而这又主要体现在工夫论的层面。
再者,朱子对上蔡的批评,也明显有突出儒学的德性价值观,反对上蔡主张心之无著、自由、活泼的一面。这与他主张辟佛老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在一定程度上,朱子对上蔡思想的批判,交织着对自己早年思想发展历程的反思,交织着他对于张九成、湖南诸学者、陆九渊及其后学们之间思想互动的反思和批判,也交织着朱子在面对上蔡与明道思想一致性之时的复杂心情,交织着他对于儒学与佛老之学关系问题的警觉。由此,朱子对上蔡思想的扬弃,所面对的就不只是已成为历史的上蔡文本,而是包含有赋予历史性的话题以当下意义的因素在内。我们在注意到朱子对上蔡的批评往往失之太过的同时,也要对朱子的特别用心有同情的理解。
求仁为急
谢良佐的仁说基本上承明道的仁说而来,但是对伊川的说法也有所继承。明道特别强调“体仁”,而上蔡则进一步把明道的说法发挥为要去察识、体会“生意”和“知觉”,以此来体认仁。他的观点又被概括为“只要见得此心,便以为仁”②、“心有所觉谓之仁”③、“有知觉、认痛痒,便唤作仁”①、“活者为仁”②等。对于谢的这一说法,后人或褒或贬,差距很大。赞同者强调其与明道“仁说”的一致性,而攻击者如朱子则直接视之为禅说。其实,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讲,朱子并不是没有看到上蔡与明道在仁说上的关联性,他也承认上蔡“以生意论仁”之说是“命理精当”。但是,他更关注的问题有点:一是认为以知觉论仁很难和佛家的说法相区分,二是这一说法或对后来学者产生负面的导向作用。在当时特定情景下,朱子的担心不能算是多虑。
先来说第一个方面:我们能很容易地在佛教文献中找出以知觉和“作用”为佛性的例子,而单纯地视“知觉”和“生意”为仁,就不足以揭示出儒学仁说的根本特性所在。在上蔡的文献中,他对上述界限并未做出严格的区分(也可以说对此问题未有自觉)。比如,谢上蔡曾提到:“仁是四肢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识痛痒,仁是识痛痒(曾本此下云‘儒之仁、佛之觉’)。”③又如他提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学佛者知此,谓之见性,遂以为了,故终归妄诞。圣门学者见此消息,必加功焉……仁,操则存,舍则亡……”④,这两种说法很容易混淆佛与儒学的界限。朱子尤其是担心,在对仁的理解上只强调个体化的感觉,而忽视理而只谈心,这会影响人们对仁的明晰的、可通约的理解,也会混淆性与情的界限。朱子的态度很明确,只有在心所知觉的对象是理的情况下,才可以称之为仁:“须是分作三截看,那不闻痛痒底是不仁,只觉得痛痒、不觉得理底,虽会于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须是觉这理方是。”①
朱子批评上蔡的“仁说”,就集中在其近“禅”上。如,针对上蔡在对《论语》“孝悌,其为仁之本”节的注释中,认为“夫仁之为道,非惟举之莫能胜、而行之莫能至,而语之亦难。其语愈博,其去仁愈远。古人语此者多矣,然而终非仁也……为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可以论仁者莫如人心,人心之不伪者莫如事亲、从兄……但孝弟可以为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间。盖仁之道,古人犹难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实欲知仁,则在力行,自省察吾事亲从兄时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则知仁矣”②的说法,朱子指出,上蔡“孝悌非仁”的说法是“盖谓别有一物是仁,如此则性外有物也”③“其意不主乎为仁,而主乎知仁”④。不仅如此,朱子还从上蔡的这一说法中读出了禅说的味道:“必如其说,则是方其事亲从兄之际,又以一心察此一心,而求识夫活物,其所重者乃在乎活物而不在乎父兄,其所以事而从之,特以求夫活物,而初非以为吾事之当然也。此盖源于佛学之余习而非圣门之本意。观其论此,而吕进伯以为犹释氏之所谓禅,彼乃欣然受之而不辞,则可见矣。”⑤于朱子,主张“以心察心”就是禅说(其实佛学内部也反对二心之说)。从文本上看,朱子对上蔡的指责未必恰当,但是当我们把考察的范围扩展到上蔡后学对其说法的扩展上时,我们或许能明白朱子的真正用心所指:
顷年张子韶之论,以为当事亲,便当体认取那事亲者是何物,方识所谓仁;当事兄,便当体认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识所谓义。某说若如此,则前面方推这心去事亲,随手又便去背后寻摸取这个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随手又便著一心去寻摸取这个义,是二心矣,禅家便是如此……,某尝举子韶之说以问李先生,曰:“当事亲便要体认取个仁,当事兄便要体认取个义,如此则事亲事兄却是没紧要底事,且姑借此来体认取个仁义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问:“上蔡爱说个觉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张子韶初间便是上蔡之说,只是后来又展上蔡之说,说得来放肆无收煞了。”或曰:“南轩初间也有以觉训仁之病。”曰:“大概都是自上蔡处来。”①
在这里,朱子就明确指出了上蔡仁说的负面影响——张九成对上蔡说法的引申,更像是主张“以心察心”。不只如此,朱子更担心上述说法会导致后人把仁理解为隐藏在背后的、独立的“神秘之物”,进而引申出是内非外、只在心上做工夫的做法。在朱子看来,后者的禅意要更浓,代表者就是陆九渊。
再说第二个方面,谢上蔡明确指出求仁当为学者之急务:“心有所觉谓之仁,仁则心与事为一……此善学者所以急急于求仁也”②,不独如此,他还认为:“世人说仁,只管着爱说,怎生见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关爱甚事?何故却近仁?”③这里,上蔡也明确提到了践履的重要性,但是从朱子上文中的批判来看,他显然认为即使上蔡主张力行,也是建立在主张先去“知仁”之上的,并把“知仁”化约为以“觉知”为根本工夫。朱子所批评上蔡的,不在于其无工夫,而在于其工夫之偏。
需要说明的是,正如陈来所指出的,上蔡在具体的求仁工夫上很明显地吸收了伊川“整齐严肃”以持敬的做法。因此,就谢本人而言,早年确实有张狂的毛病,但是在二程的敲打下,他在随后的二十年中还是保持了对此相当的警觉。他对于在工夫层面上放与守之辩证关系的认识也较恰当。而朱子所担心的,更在于上蔡上述说法对后学的影响:上蔡以求仁为急务,还不废其他的工夫,而湖南学者们主张在心之动念处体仁,却很少提到格物致知,这是对上蔡说法的极端化约。④朱子认为,这样做会失之急迫,乃至轻视下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把“急于求仁”变成了“急迫于求仁”,其流弊显而易见。
对朱子来说,他已经把上述流弊和谢的观点联系起来(甚至还上溯到明道那里),并下大力气来扭转这一风气。如,针对有弟子提问:“世有因谢氏之说而推之者,曰:‘人能自观其过,则知其所以观此者即吾之仁,是说如何?’”朱子就明确回答:
(朱子)曰:“此说最为新奇而可喜,吾亦尝闻而悦之矣。然尝以质之于师(李侗),而曰‘不然’,既又验诸行事之实,而后知其果不然也。盖方其无事之时,不务涵养本原,而必欲求过以为观省之资,及其观之之际,则又不务速改其过,而徒欲藉之以为知仁之地,是既失其所以求仁之方矣。且其观之而欲知观者之为仁也,方寸之地、俄顷之间,有过者焉、有观者焉、有知者焉,更相攫挐,迭相排逐,烦扰猝迫,应接不暇,盖不胜其险薄狂怪,而于仁之意味愈不得其彷佛,原其所以然者,盖亦生于‘以觉为仁,而谓爱非仁’之说耳。夫有是性必有是情,故仁之爱、知之觉,犹水之寒、火之热也。程子谓不可以爱为仁,盖曰不可以情为性,犹不可以寒为水而已,然其所谓以仁为爱,体爱为仁用,则于其血脉之所系,未尝不使之相为流通也。故于有子之言、以及此章之,未尝不以爱为言,至于以觉训仁,则盖尝明斥其非矣。今宗本程氏而不深考于此,乃直谓觉为仁、而深疾夫爱之说,则是谓热为水而恶言水之寒也。溺于新奇而不自知其陷于异端,诚以是说推之,则庶乎其有改矣。”①
显然,朱子对上蔡仁说的批评,更多是基于其对后学之导向的忧虑,而他对“因谢氏之说而推之者”(主要指湖南学者)的批评,也基本落脚在工夫论的层面。这其实正能反映出朱子在经历了长期徘徊于杨时学派(道南学派)与谢良佐学派(湖湘学派)之间,苦苦寻求为学工夫之后的一个基本结论。不过,朱子在指责谢的仁说为禅说之同时,也必须正视谢的说法与明道仁说的关联。事实上,是批评二程后学的同时,如何回护二程与其后学思想的一致性,这个问题始终是朱子需要认真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在为学之序上的纠结
朱子对上蔡的批评,还集中在“为学之序”的问题上。上蔡的为学工夫基本不出二程的范围,却有将其简易、内化、趋高的倾向,这也引起了朱子的极大忧虑。
上蔡主张“学者且须是穷理”①,而对于这个“理”字,又被他进一步限定为“天理”、“是处”。②这是对二程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不过,上蔡之穷理说也有其特殊之点:
(谢曰)学者且须是穷理,物物皆有理。穷理则能知天之所为,知天之所为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无往而非理也。穷理则是寻个是处。有我不能穷理,人谁识真我?何者为我?理便是我。穷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曰:“理必物物而穷之乎?”
(谢)曰:“必穷其大者,理一而已。一处理穷,触处皆通。恕其穷理之本欤(曾本此句为‘物虽细者亦有理也’)?”③
上蔡主张穷理要穷其大者,并认为“一处理穷”则能“触处皆通”。这一点是朱子所最为反对的。④事实上,在上蔡那里,理之“大者”只能是指心上之理,而认为“大者通则触处通”,无疑会导向工夫论层面的“不懈卑近”,甚至只是去穷心上之理、务内遗外(这也正是朱子与陆九渊的重要分歧之点)。朱子认为,必如上蔡所说,只去穷“大”的理,这样所见的理会也失之笼统。他有时也以曾点曾参父子为比,认为前者只是见到了理的大而虚的轮廓,而后者则步步为营,所见皆是实理,最终得以有“一以贯之”之境界。朱子强调,正是由于所见之理虚与实的不同,曾点“终不及他的儿子”。
事实上,朱子早年在阅读上蔡《语录》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疑问:既然“理无大小”,那么在穷理工夫上就不应该有所“拣择”,但是前人或主张要“为学有序”,或主张“穷其大者”,这一矛盾确实让朱子困惑了很久。
在李侗“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在分殊耳”的引导下,朱子经过艰苦的反思,明确反对主张只在一处穷理,并希望由此能触处皆通的说法,而是主张由积累而贯通说,其《格物补传》就是明证。朱子的态度很明确:因为理无大小,所以不能刻意拣择穷理的对象;又因为事上有分别,所以在穷理时又应该以切近者为先,此之谓“为学有序”,①这完全出于自然,而非拣择。
我们再以一个具体的例子对此详加说明。从二程到上蔡再到朱子,他们都关心一个问题:下学与上达或者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之间的关系。于朱子,他则在这个问题中注意到了上蔡的说法有颠倒“为学之序”的弊端:
谢子曰:“道须是下学而上达始得。不见古人就‘洒扫应对’上做起?”
(问)曰:“‘洒扫应对’上学,却似太琐屑,不展拓。”
(谢)曰:“凡事不必须要高远,且从小处看。只如将一金与人,与将天下与人,虽大小不同,其实一也。我若有轻物底心,将天下与人如一金与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将一金与人如天下与人相似。又若行千尺台边心便恐惧,行平地上心却安稳,我若去得恐惧底心,虽履千仞之险亦只与行平地上一般。只如洒扫不著此心,怎洒扫得?应对不著此心,怎应对得?故曾子欲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为此。古人须要就‘洒扫应对’上养取诚意出来。”②
下学而极其道则上达矣,然上达师无与焉。洒扫应对进退,乃动容貌、出辞气之事,必正心诚意而后能,与酬酢祐神之事何以异?孰以为可而先传?孰以为不可而后倦?如草木区以别矣,其为曲直一也。所以圣人克勤小物而必有始卒,盖本末无二道。③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上蔡的上述说法并不存在什么问题,而对于上蔡的上述说法,朱子却在《论语或问》和《语类》中有连篇累牍的抨击。当然,他也不忘突出上蔡此说与二程说法的区别所在:
……且如洒扫应对,子游便忽略了,子夏便只就这上做工夫。又曰:“谢氏说此章甚差。”①
上蔡之学,初见其无碍,甚喜之,然细观之,终不离禅底见解。如洒扫应对处,此只是小子之始学,程先生因发明虽始学,然其终之大者亦不离此。上蔡于此类处,便说的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终,若如此说时(即谢主张在下学上养诚意),便是不安于其小者初者,必知其有所谓大者方安为之……上蔡于小处,说的亦大了……上蔡大率张皇不安贴。②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个“思无邪”便了,便略了那诗三百,圣人须是从诗三百逐一篇理会了,然后理会思无邪,此所谓下学而上达也。今人止务上达,自要免得下学,如说道洒扫应对进退便有天道,③都不去做那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到得洒扫则不安于洒扫,进退则不安于进退,应对则不安于应对,那里面曲折去处都鹘突无理会了。这个须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贯通到这里,方是一贯。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习而但求察。④
“谢说则源于程子之意而失之远矣,夫下学而极其道固上达矣,然此方论下学之始为,未遽及夫极其道而上达之意也。上达固非师之所能与,然此方论为师教人之序,未遽及夫师无与焉之妙也。不吝之心一也,而一金天下则其捐之有难易之殊;不惧之心一也,而平地高台则其习之有先后之序。必如谢氏之说,将使学者先获而后难,不安于下学而妄意于上达,且谓为学之道尽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而无复格物、致知、修身、齐家之事也。其与子夏程子之意正相反矣。”曰:“程子亦常以理无大小,而洒扫应对精义入神者不异,何以异于谢氏之意?而以为相反,何也?”(朱子)曰:“程子所谓必有所以然者,以为同出于理之自然也。谢氏以必正心诚意而后能者,则以为同出于心之使然也。程子所谓慎独者,则不敢忽其小者,以求其理之所当。谢氏独以著心为言,则又如其论颜子克己、曾子贵道之说,初不问理之是非,而唯吾心之所欲为也。然此其失之小者耳。程子虽以理无大小为言,然其意则以明夫小不谨则将害其大,小不尽则不可以进于大,而欲使人谨其小者,以驯致其大者耳。如谢氏之云,则反使人恃其小者以自大,而谓夫大者之真不过如此也。此岂非相反之尤者哉?”曰:“其与子夏相反者,又何也?”(朱子)曰:“子夏正以次序为言,而谢氏以为无次序;子夏以草木为区别,而谢氏乃以为曲直则一;子夏以唯圣人为有始卒,而谢氏则无圣人众人之分,此其相反亦可见矣。”①
二程曾提出“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独”②,甚至主张“后人便将性命别作一般事说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统底事,就孝弟中便可尽性至命。至如洒扫应对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统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却被后来人言性命者别作一般高远说”③,上蔡的说法基本上是对此的“忠实“发挥。
表面上看,主张下学而上达是上蔡与朱子之间的共识,因此朱子对上蔡的批评颇令人感到不知所谓。但是就朱子的立场来说,他对上蔡的批评有以下几点:
其一,下学就是下学,上达就是上达,二者之间的分界不可混淆。因此,试图在“洒扫应对进退”这些下学之事上“著心”,认为只有在正心诚意之后才能做好洒扫应对进退之事的说法,就是“不安下学”、“妄意上达”,就是急于求知、急于求察。
其二,认为“下学而极其道则上达”的说法,也会导出“谓为学之道尽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不去做其他工夫的结论。其实,朱子的上述担心并不为过,上蔡不是提到过“一处理穷”则“触处皆通”吗?依照他的思路,在洒扫应对上做好了,就可以实现精义入神,自然就“无复格物、致知、修身、齐家之事也”了。
其三,上蔡总有把小事说大的毛病,这是其“狂者胸次”的体现。
其四,朱子还刻意强调了上蔡此说与二程说法的区别:二程的意思是强调理无大小,上蔡则强调心之所欲为;二程是在强调谨小以致大,上蔡则“恃其小者以自大”。
总之,朱子对上蔡的三点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其为学无次序(或次序不当),混淆了下学与上达之分。我们则认为,朱子对上蔡的批评,往往是基于他对上蔡学说的前见(事先形成的总体判断)使然。就文本来说,朱子的批评往往是在自说自话,未必都能抓住上蔡的本意。但是若是从同情之理解的角度来看,我们未尝不能从中看出朱子对于上蔡学说对后学潜在的引导作用的担心。事实上,朱子的上述担心又会在和湖南学者陆九渊及其弟子们的接触中一再被放大,并最终激化。
心无所著之“气象”
在上蔡的文献中,与“境界”一词内涵大致相当的“气象”一词频繁出现,而上蔡也比周、张、二程等人更为重视探讨圣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问题。上蔡的“气象论”自然也成为朱子之境界论的形成过程中,大力扬弃的对象。
有趣的是,上蔡的“气象论”也与明道的主张有直接的关联。明道的文献中时常有对“优游”、“心闲”和“无事”的吟咏,甚至有“太山为高矣,然太山顶上已不属太山。虽尧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①的说法,上蔡对此则有进一步的引申:
道以无所倚为至,……曾点之学,虽禹稷之事故可以优为。②
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才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点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然易做,只是无心近乎忘。③
把来作用弄,便是做两般看当了,是将此事横在肚里,一如子路、冉求相似,便被他曾点冷眼看,他只管独对春风吟咏,肚里混没些能解,岂不快活!①
显然,上蔡提倡的“无著”与明道提到的“无事”有内在的关联。但是从明道的《定性说》来看,明道所说的“无事”,是指“物来而顺应”,还是要强调去“应物”,而上蔡这段文字中的“无著”,就变成了“肚里混没些能解”的一味快活,成了真正的无所事事,这一点是朱子难以容忍的。朱子不止针对《论语》中“曾点言志”一段,强调“学固着学,然事亦岂可废也?若都不就事上学,只要便如曾点样快活,将来却恐狂了人去也”②,还就此引出了对上蔡的批评:
圣贤之心所以异于佛老者,正以无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谓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旷然无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则亦何以异于虚无寂灭之学,而岂圣人之事哉?抑观其直以异端无实之妄言(指列子御风)为比,则其得失亦可见矣。③
上蔡“尧舜事业横在胸中”之说,若谓尧舜自将已做了底事业横在胸中,则世间无此等小器量底尧舜,若说学者,则凡圣贤一言一行皆当潜心玩索,要识得他底蕴,自家分上一一要用,岂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丧志”之说,盖是箴上蔡记诵博识而不理会道理之病,渠得此语,遂一向扫荡,直要得胸中旷然、无一毫所能,则可谓矫枉过其正矣。观其论曾点事,遂及列子御风,以为易做,则可见也。大抵明道所谓‘与学者语,如扶醉人’,真是如此。④
这里,朱子对上蔡的批评显然是过了。上蔡所说的不著一事,本意还是要突出顺理之自然:如他又提到“尧舜汤武做底事业,只是与天理合一,几曾做作,横在肚里?见他做出许多掀天动地盖世底功业,如太空中一点浮云相似,他把做甚么……孔子便不然……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为,更不作用”①。就此而言,上蔡的说法仍不出明道“定心”之说的范围,而又点出“不著心”的实质是“与天理合一”,这是对明道说法的合理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再次转换视角,尤其是聚焦朱子晚年时人竞相谈论“与点之乐”的现实,就会明白朱子之指责上蔡此说的现实用心所在。②
以常惺惺论敬
朱子对上蔡的观点并非一味地批评,尤其是对于上蔡借用佛家“主人翁是常惺惺”的说法而提出“敬是常惺惺法”③的做法,朱子却是完全肯定的:“谢良佐之言则曰‘敬是常惺惺法’……此皆切至之言,深得圣经之旨。”④为什么这一次,以辟佛著称的朱子,却对于上蔡化用佛教的词汇不以为意呢?道理很简单,上蔡的这一说法完全是在强调“敬的要义就在于持续不懈的明觉状态”,这也就是朱子自己所说的“静中有个觉处”的意思,这虽在字面上与佛教一致,但是却无碍上蔡表达自己思想的清晰性(上蔡的本意是在强调儒家之敬与庄子心斋的区别:前者是要时时关注,后者则是要事事放下)。同时,上蔡的说法与朱子后来希望以敬来统摄自己心性修养工夫的努力也是一致的。如,朱子在著名的“中和新说”中就提到:“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心主乎一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是以君子之于敬,亦无动静语默而不用其力焉。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艮》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有以主乎静中之动,是以寂而未尝不感;有以察乎动中之静,是以感而未尝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贯彻而无一息之不仁也。”①在这里,“知觉不昧”即是上蔡“常惺惺”之确解,它是贯通动静的,而主敬也恰恰成为朱子在多年探求习性修养工夫之后的最终结论。在此意义上,他对上蔡的说法当然是肯定的。
总论
朱子曾指出,上蔡是张无垢和陆象山的思想源头,但是从陆九渊的立场看,其实上蔡对他的影响甚微(陆九渊的著作中并未提及上蔡)。反之,上蔡对朱子的影响却始终挥之不去:朱子对上蔡思想不只是有批判,更有吸收。在不同的时期,我们都能在朱子的文献中找到他首肯上蔡某观点的文字,虽然越是到了晚年,他批评上蔡的文字也越多起来。可以说,上蔡在后世的最大贡献,就是引起了朱子的积极回应,从而使得上蔡所关注的许多问题一变成为理学的热点问题。当然,《上蔡语录》之所以能在后世广为流传,也是与朱子的整理分不开的。
二杨时之学趋于简易
与上蔡相比,杨时(下文简称龟山)与佛老的关系更近,甚至还注释过庄、列的著作,而朱子对龟山的批评也更为直接。上蔡的所谓“禅说”,还只是与佛学的某些外部特征相类似,而龟山的许多说法,却是真正的禅说,如全祖望(谢山)引宋儒黄震(东发)语即指出:
祖望谨案:慈溪黄氏曰:“龟山气象和平,议论醇正,说经旨极切,论人物极严,可以垂训万世。使不间流于异端,岂不诚醇儒哉?乃不料其晚年竟溺于佛氏。如云:‘总老言经中说十识,第八庵摩罗识,唐言(田按,即汉语称为)白净无垢,第九阿赖邪识,唐言善恶种子。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又云:‘庞居士谓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此即尧舜之道在行止疾徐间。’又云:‘《圆觉经》言作、止、任灭是四病。作即所谓助长,止即所谓不耘苗,任灭即是无事。’又云:‘谓形色为天性,亦犹所谓色即是空。’又云:‘《维摩经》云真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又云:‘庄子《逍遥游》所谓无入不自得,《养生主》所谓行其所无事’,如此数则,可骇可叹。”黄氏之言,真龟山之诤臣也,故附于此(本段文字的点断,以中华书局版为准)。①
全祖望此文颇能揭示龟山晚年溺佛的状况(其实龟山早年也有溺佛的经历),但是查对黄震的原文,谢的引文与东发的原文出入较大(或许是点校者的错误使然,或许是谢山对东发的文字有所总结):
(针对龟山的几条“禅说”)按附合至此,可怪可骇。人心一至溺,是非即成颠倒,前辈尚不能免,后学可不自惧乎?夫龟山本忠门之高第也(田按,下疑有脱文)。
龟山气象平和,议论醇正,说经旨甚切,论人物极严,事必于其正理,而凡挟数用术苟就功名者,决不许之,可以垂训万世。使不间流于异端,岂不诚醇儒哉?横渠思索高深,往往非后学之所宜先,似不若龟山之平直,动可人意。然其精到之语,必前此圣贤之所未发,斥绝异端,一语不流。高明者多自立,浑厚者易迁变,此任道之有贵于刚大哉。②
无论如何,龟山晚年溺佛的程度要远远超过上蔡,其引佛老语以解经的程度也是上蔡所不及的。不过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却认为,“但是无论如何,至少在批判王学的场合,杨时并不在佛教面前丢盔弃甲:‘夫儒佛不两立久矣,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王氏乃不会起是非邪正,尊其人,师其道……’”③,此话或许过重,杨时在涉及儒佛的根本区别之处,还是能坚持儒者立场的。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黎昕先生所言,“据陈荣捷教授统计,《四书集注》共用了32个学者的731条语录,而其中引杨时语录就达73条之多,仅次于二程和尹淳之后(二程为225条,尹焞为90条),位居第三”。①这一事实颇能说明,较之于上蔡的高妙之言,朱子更喜欢龟山对四书的平实解读,认为其立场与二程更为接近。
在很大程度上,龟山是二程的祖述者,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龟山还是有自己特色的。
理与气
二程对理气关系问题讨论的不多,龟山对此问题则有所关注。他对理与气的说明比较微妙:既有“通天下一气”的说法,也有“天下只是一理”的说法,但是却没有明确地对理与气之关系如何予以明确的说明。事实上,似乎理气关系也并不是二程及其弟子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在龟山,对理这一概念的讨论并不多,而引人注意的倒是其对“通天下一气”这一观点的多次强调。龟山并毫不掩饰这一说法与庄子思想的渊源关系(至少在《踵息庵记》一文中,“通天下一气耳”的说法与庄子有莫大的关系,而张载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过类似的说法)——虽然龟山这一说法也是受到孟子和张载影响的产物。关于这个问题,土田健次郎先生即认为,只有在朱熹那里,“气”才是始终与“理”相对置的概念,而理气关系论也才成为贯穿于宇宙论、人性论、道德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在二程及其弟子们那里,情况还不是如此。他以程颐为例,指出,“在程颐的有关文献中,将‘理’字与‘气’字明确对置的例子几乎没有……仅从字面上讲,可以说程颐还没有理气之论”②。我们认为,土田健次郎先生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在二程及其弟子们那里,的确还没有把理气关系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模式,也可以说,他们对理的关注要远远优先于气。
在龟山那里,对作为本体意义的“理”字提到的甚少,更没有将理与气对置的例子。毋宁说,龟山对理和气的认识基本上是因袭前人之论,由此,学界讨论龟山究竟是理一元论者,还是气一元论者,还是理气二元论者的问题虽然很热烈,却始终难有定论。
就《龟山语录》文本而言,龟山论“气”的内容相对固定:较之张载区分气之本然和气之客形、朱子能从气的感性的殊象中提炼出作为一般的“气”之概念这样的新意来说,龟山对气的理解毫无新意可言。与此相对,出现在《龟山语录》中的“理”字的含义却比较复杂,但是主要还是在集中在“规律”的意义上,进而提出“乘理”、“任理”、“循理”等概念,却基本上没有像二程那样在本根、本体的意义上使用过理字。这种情况,以下面的这则材料最具代表性:
语仲素(罗从彦):“《西铭》只是发明一个事天底道理,所谓事天者,循天理而巳。”①
“事天”,就是要循天之理,在这里,“理”还是仅仅是规律的含义。陈来指出,龟山的格物论有摇摆于理学与心学之间的一面,其实龟山在对理气关系的说明上,未尝没有摇摆的因素存在。龟山学说的特色就是杂众说,还并没有凝聚成清晰、有系统的自家理论。
性论
龟山持性善论立场,这一点当无异议。他在对《中庸》首章的诠释中即指出:
“‘天命之谓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谓道’,离性非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则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盖原于此。谓性有不善者,诬天也。性无不善,则不可加损也,无俟乎修焉,率之而已。”②
龟山此文提倡“性不假修”,这难以得到朱子的认同,但是龟山这里所持的性善论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不过,龟山对性的理解也颇受佛家的影响:他曾直接以佛学术语比附性善论来反驳王安石“性无善恶”的性论:
通揔老言:“经中说十识,第八庵摩罗识,唐言白净无垢,第九阿頼耶识,唐言善恶种子。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谓探其本;言善恶混,乃是于善恶巳萌处看。”荆公盖不知此。①
按照揔老的意思,只有就人的善恶念头已经萌生之时说,才能说善恶混,而就性之本(本源、本质、本然)来说,则性为善,龟山所取于他的,也仅仅只是这一点。不过,这一说法在朱子那里显然是无法接受的:这无异于是说“本然之善不与恶对”,也很自然会被引申成为性超善恶的观点,对之的批判尤为严厉。但是我们从这段文字本身来看,龟山还是意在强调“性善是本”,有善有恶是末的观点。
又如,龟山也曾以“具足圆成、本无亏欠”、“性无变坏”等词汇来诠释性,并由此提出“性不假修”的说法。我们认为,类似这样的说法在儒家典籍中是没有先例的,只能是受到佛说影响下的产物。我们知道,在朱子之前,宋儒们对于心与性并未做出过严格的区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张载和明道所讨论的定性问题,其实应该称为“定心”才更为恰当。因此,龟山以性为“具足”、“无亏”云云,其实是在另一意义上提出了本心的提法。此外,龟山明确提出过“性、命、道,一体而异名”②的说法,颇有把“性”上推到天之层面的意思(即认为性在人欲之先),这实际上是开了湖南学者尤其是胡宏将“性”本体化之先河。
虽然龟山的性论受到了“禅说”的影响,但是其根本处并未走出儒家的藩篱,这又有表现为龟山在论性上对孟子道性善的反复强调,也表现在其多次宣扬明道所主张的、以“循天理”来诠释“率性”的观点。同时,针对张载气质之性的说法,龟山则极力将其与孟子的性善说统一起来:
仲素问:“横渠云气质之性,如何?”曰:“人所资禀固有不同者,若论其本,则无不善。盖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无不善,而人则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时而恶矣。犹人之生也,气得其和则为安乐人,及其有疾也,以气不和而然也。然气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则反(天按,当为返字)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说气质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刚柔缓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谓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于湛浊,则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①
龟山上述观点很独特,他是用常态和非常态之分来统合孟子与张载的观点,其立论是基于性气不分的一元思路。对龟山而言,性只有一个(龟山所理解的性,表述为心更合适),其常态、本然是善,恶则只是性之偶然的、非本然的状态。龟山的这一说法和张载以气之未形、已形的两分来论性不同,也与朱子对气质之性的理解不同:对朱子来说,只能以理为善,龟山的说法是混淆了理与气、性与情之别:“阴阳,气也。不能无不善,唯所以阴阳者,则是所谓道,而无不善也。今既以阴阳为无不善,而不能必其无不善,则又曰‘善者其常而亦有时而恶焉’,则非所以语性之善矣。”②再者,朱子显然认为,人作为理与气的合体,必然会受到气禀的影响,气质之性与生俱来,也不可摆脱,朱子认为这才是常。由此,人所能做的,就不是要去根除气质之性,而是要努力变化气质,直到人的行动皆能发于天理之公,直到气质完全听从天理的指挥为止。但是从龟山的这段话来看,他显然认为气质之性是应该“去除”的。正因为龟山不注意区分性与气、性与情的界限,因此他又会主张“口之于味等,性中本来有这个,若不是性中有,怎生发得出来”①之说,这一说法也是朱子难以赞同的。龟山的这一说法与清代学者尤其是戴震的看法颇为类似
龟山对孟子与张载性论的统合,显然尚且处在感性和经验层面,但这却足以保证其儒者的基本立场。
格物说
龟山的格物说也颇具特色:他将格物与明善和诚身联系起来,有明显强调内在优先性的倾向,这一点却遭到了朱子的严厉批评。但是龟山的说法并非没有所本,在很大程度上,龟山的格物说是对明道说法的进一步引申。
明道的格物说特别强调反身、强调学文与进德的不同,而庞万里先生也把这一点作为明道与伊川格物说的显要不同之处。如,明道就很强调:
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所守不约,泛滥无功。②
致知,但知止于至善……不须外面。只务观物理,汎然正如游骑无所归也。③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于至善”,反己守约是也。④
明道强调内(我)之对于外(物理)的优先性。相对而言,伊川则在强调明善的同时,指出明善不能离开明理,尤其是穷物理:
人患事系,思虑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在乎格物穷理。穷至于物理,则渐久后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⑤
伊川与明道不同之处,在于突出“明善在于格物穷理”,因为二者其实“只是一理”,强调了二者同等的重要性。
龟山对于二程的格物说都有所继承,但主要还是以明道说为主,而更趋于“简易直接”,甚至提出“物固不可胜穷,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①的说法。这就和明道主张以我为本来通物我的说法有所偏离。龟山屡屡强调“一”(一气、一理、一身)以及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而对“理一分殊”原则未必有明确的理解,这是导致上述偏离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伊川之强调“理一分殊”,是在先承认分殊的前提下,再去求其贯通之处的“理之一”,此即所谓在积累中以求贯通,由此,对外物之殊性的认识就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在“理一分殊”的模式下,人之善与物之理都是作为“一”之理的体现,其本则同,因此明善与格物就不再是不相关的了。在明道,虽然很强调以我为主的格物观,但也强调“物来顺应”,强调要不系于我而系于物。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容纳了对外物的关注。
而在龟山,则仅仅以“凡形色之具于吾身,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目之于色,耳之于省,口鼻之于美味,接乎外耳不到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②云云以为说明。对此,朱子明确予以反驳:
程子曰:“所谓穷理者,非必尽穷天下之物,又非只穷一物而众理皆通,但要积累多后,脱然有贯通处”。又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不必言因见物而反求诸身也。然语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③
反身而诚者,物格知至而反之于身,则所明之善无不实,有如前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无内外隐显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则反之而不诚者多矣,安得直谓但能反求诸身,则不待求之于外,而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而无不诚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离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尤非大学之本意矣。①
于朱子而言,认为反身而诚就可以穷尽天下之理也属于“禅说”之属,这与陆象山的说法没有区别。朱子也注意到,龟山并没有认为只要“反身而诚”就够了,而同时也强调学习典章的重要性:
(问)曰:“杨氏之说有‘虚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
(答)曰:“固也。是其前段主于诚意,故以为有法度而无诚意则法度为虚器,正言以发之也。其后段主于格物,故以为若但知诚意,而不知治天下国家之道,则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为虚器而不之讲,反语以诘之也。此其不同审矣。”②
朱子意谓,龟山是从一正一反两方面来说明:诚意固然是主导,但是诚意并不能代替格外物,二者不可偏废。这表明,龟山毕竟不同于与后世主张只在心上做工夫者,与伊川的格物说并无根本冲突。但是在总体上,龟山在格物与诚身之间,更重视的是后者。朱子注意龟山的,主要是这一点。
“诚”不仅是龟山格物说的核心,还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意义:
盖惟圣人与天同德者为能诚焉。③
自一身之修推而至于天下,无二道也,本诸诚意而已。④
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⑤
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诚意为主。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也。⑥
大致说来,诚意之于龟山,相当于敬之于二程,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但是,龟山以诚意说来统摄为学工夫,其重内在、重简易的特色也更为明显。
对《中庸》的诠释
在许多学者看来,对《中庸》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未发”问题的关注,是以龟山为代表的道南学派的主要特色所在,这也是推动朱子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从文本上看,这些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如龟山就认为:
《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①
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②
龟山这里对《中庸》的赞叹,足以表明其对《中庸》的推许要远在《论》、《孟》、《大学》之上。龟山的《中庸解》久已遗失,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宋人卫湜在《礼记集说》中对龟山《中庸解》的摘录,以及朱子对龟山中庸说的批评性资料而一窥其大概。③在此方面,复旦大学的郭晓东教授已有《论杨龟山对〈中庸〉的诠释及朱子的批评》④一文有专门的论述。本文则仅结合朱子对龟山“中庸义”的批判,具体来看龟山与二程之观点上的细微差异之处。
总的说来,朱子对龟山的中庸说之批评要大于肯定,并多次明确指其为“禅说”。如,针对龟山对《中庸》中“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矣”、“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段的解释中,提出“无适而非道”的说法,朱子即认为:
杨氏“无适非道”之云则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尽……若便指物以为道,而曰“人不能顷刻而离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则是不惟昧于形而上下之别,而堕于释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学者误谓“道无不在,虽欲离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则虽猖狂妄行,亦无适而不为道”,则其为害将有不可胜言者,不但文义之失而已也。①
朱子的意思,龟山的“无适非道”说,在被理解为“所谓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间不能违物而独立,是以无适而不有义理之准则,不可顷刻去之而不由”的情况下,这是可以成立的。但是,龟山此说也可以被理解为事道不分乃至“作用见性”的“禅说”,朱子更忧虑这一点。从龟山的文本来看,其本意恰恰就是朱子所批评的后一种情况。但是,龟山此一说发显然来自二程:
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一作敬),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分于道也远矣……彼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为隘也。吾道则不然,率性而已。②
……夫道不可须臾离也,以其无适而非道也。故于不闻不睹必恐惧戒慎焉,所以慎其独也。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其充此之谓乎。夫如是,诚之至也,故合乎神天,而卒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盖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天,兹其所以为至也……③
我们认为,龟山的上述说法虽然本于二程,不过二程的说法主要是针对儒释之别而发,所要突出的是“直内与方外”的统一,与朱子的第一种解释意思大致一致;而龟山的说法则引向了慎独说,强调恐惧戒慎,突出的是人的内在性工夫。就这点来说,朱子对龟山的指责非常牵强。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龟山从“无适非道”说中挥进一步推出“率性”说,并进一步导出“寒而衣,饥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视听,手足之举履,无非道也……夫尧舜之道,岂有物可玩而乐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农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乐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谓知之者也”①以及“尧舜之道曰孝弟,不过行止疾徐之间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日出而作,晦而息,无非道者,譬之莫不饮食而知味者鲜类”②的说法,就会明白朱子反感龟山此说的深层原因:朱子既指出龟山的说法混淆了形上形下之别,会导致“认欲为理”、“不问理之是非”之流弊,也与“禅说”无法区分(俱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二)。朱子的此处担忧也不是没有理由。
如果说朱子上面对龟山的指责还显牵强的话,那么他对龟山的“未发”说则给予了不加掩饰的指责:
杨氏所谓“未发之时,以心验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则发必中节矣”,又曰“须于未发之际能礼所谓中”,其曰验之、体之、执之,则亦吕氏之失也。③其曰“其恸其喜,中固自若”,疑与程子所云“言和则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细推之,则程子之意,正谓喜怒哀乐已发之处见得未发之理发见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无偏倚、过不及之差,乃时中之中而非浑然在中之中也。若杨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庄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则是以为圣人方当喜怒哀乐之时,其心漠然同于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为,皆不复出于中心之诚矣。大抵杨氏之言多杂于佛老,故其失类如此。④
朱子所批判龟山文字的原文颇长,其核心部分为:
……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验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发而中节,中固未尝忘也。孔子之恸、孟子之喜,因其可恸可喜也,于孔孟何有哉?其恸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鉴之茹物,因物而异形,而鉴之明未尝异也。庄生所谓“出怒不怒则怒出于不怒,出为无为则为出于不为”,亦此意也。若圣人而无喜怒哀乐,则天下之达道废矣……故于是四者,当论其中节、不中节,不当论其有无也。或问:“正心诚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后世自是无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一念之间毫发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圣人始得。且如吾辈,还敢便道自已心得其正否?此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于喜怒哀乐己发之后,能得所谓和。致中和,则天地可位、万物可育,其于平天下何有?”①
从龟山的这段文字可见,可以说龟山此说与明道的《定性说》颇有类似之处,但也可以说是龟山受到了邵雍乃至佛老的影响,朱子之批评,不可谓无的放矢。此外,二程都不主张去体验未发之中,甚至二程在与弟子们讨论中和问题之时,都不曾涉及如何做工夫论的问题。就这一点说,主张在工夫论层面“体验未发”,的确是所谓龟山“道南旨诀”的特色所在。
朱子之批评龟山的,主要集中在龟山主张去“验之、体之、执之”上,颇有主张去“察识”中或是“求中于未发之先”的嫌疑,难怪土田健次郎会认为,湖湘的胡氏主张“察识”已发之端倪论,也是受到了龟山的影响。②总的看来,龟山并不主张纯粹静的工夫,在这一点上龟山与后来学者罗从彦、李侗的主张还是很有差距的。我们在提到“道南旨诀”之时,也要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两次的“中和之悟”是朱子实现思想飞跃的关键点,而对龟山及李侗所主张的“体验未发”说之扬弃,则是朱子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朱子,一味着意去“体验未发”和一味去“察识心之动处”的弊端都是一样的,二者虽然在表面上截然相反,却都属于“禅说”之属。
又如,针对龟山对《中庸》里“中庸不可能”的解释,朱子更是认为:
游氏以舜为绝学无为,而杨氏亦谓:“有能斯有为之者,其违道远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无事焉,夫何能之有?”则皆老佛之余绪。而杨氏下章所论“不知不能,为道远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学于程氏之门号称高第,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晓也已。①
明道对《中庸》这句话的解释为:“克己最难,故中庸不可能也”②,与龟山强调“无为”和“无事”相对照,显然明道更强调做工夫的说法,更合朱子的口味。
再如,针对龟山对《中庸》二十七章的解释,朱子强调:
杨氏之说亦不可晓,盖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礼者道体之节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后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礼为德,而欲以凝夫道则既误矣,而又曰“道非礼则荡而无止、礼非道则梏于仪章器数之末而有所不行”,则是所谓道者,乃为虚无恍惚元无准则之物,所谓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于道也,其诸老氏之言乎?误益甚矣。③
龟山注释的原文如下:
道之峻极于天,道之至也,无礼以范围之,则荡然无止,而天地之化或过矣。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所以体道而范围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谓至德者,礼其是乎?夫礼,天所秩也。后世或以为忠信之薄,或以为伪,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后行”,盖道非礼不止,礼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资也。苟非其人而梏于仪章、器数之末,则愚不肖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
龟山此段释文与二程的说法也有很大的差距:主要是突出的所谓道与礼的内在关系。但是在朱子看来,龟山的说法有认为“道是离开礼而独立存在的空虚之物”的嫌疑。
比较而言,对《中庸》的诠释是龟山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受到朱子批评最多的部分(朱子对龟山之性论、诚意论的批评都属于对中庸义的批评)。在朱子那里,龟山与二程在诠释《中庸》上的差异被刻意放大了。这又被纳入到了其扬弃二程后学之流弊以实现统一学术的大思路下,成为其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龟山之释《论语》
龟山对《论语》、《孟子》的诠释,影响远不及其对《中庸》的诠释。原因就在于,龟山的论、孟解缺少自身的特色吧。龟山的《论语解》、《孟子解》同样早已遗失,但是在朱子的《论孟精义》和《四书或问》中还保存了一些内容。据《论语或问》,龟山的《论语解》有初本、次本、三本之说,①于此可见龟山在《论语解》上也耗费了不少工夫。
在龟山的《论语解》中,他对仁的诠释最引人注目:虽说基本上是对二程仁说的发挥,但是却融合了理一分殊的思路:
道二,仁与不仁而已,故修道必以仁。仁者,人也,合天下之公,非私于一己者也。盖无公天下之诚心,而任一己之私意,则违道远矣。然仁者人也,爱有差等则亲亲为大;义者行吾敬而已,时措之宜则尊贤为大……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事亲,仁之实也,故修身以事亲为本。仁者人也,非私于一己者也。事亲而不知人,则其锡类不广矣。视天下无一物之非仁也,其知人乎?知人而不知天,则夷子之二本也。盖五品之差,天叙也。先王惇五典而有厚薄隆杀之别焉,明天叙而已。②
龟山从“理一分殊”的模式论仁,可谓发二程之所未发:既强调了公天下之心是仁之本;又突出了次等(天叙)是仁之施,是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只有把公天下之心和具体实施层面的爱有次等贯通起来才谓之仁。龟山进而指出,“视天下无一物非仁”的说法是“不知人(之特殊性)”,而不讲次等的说法是“不知天(秩序)”。龟山这一说法力图贯通天和人,一和殊之的关系,颇有创见,也颇受朱子的肯定。
我们知道,“父子相隐”问题始终是儒学的一大困扰。对此的回答,势必要在情理法之间选取一个优先者,而舍去另一方。但是,如果刻意把情与理的矛盾对立起来,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难说圆满。
龟山对此的回答就是完全突出一个情字:“父子相隐,人之情也,若其情,则直在其中矣。子证其父,岂人情也哉?逆而为之,曲孰甚焉”、“父子之真情,岂欲相暴其恶哉!行其真情,乃所谓直。反情以为直,则失其所以直矣。乞酰之不得为直,亦犹是也”。①龟山的意思,情与直是同一的,任情就能保证直。对此,朱子表示并不赞同:
杨氏之说本乎情,谢侯氏尹氏之说本乎理,皆有所不同也。今试以身处之,则所谓情者可体而易见,所谓理者近于泛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见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则人情之或邪或正,初无准则,若之何其必顺此而皆可以为直也邪?苟顺其情而皆可谓之直,则霍光之夫妇相隐可以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皆咈其情而反陷于曲矣,而可乎哉。②
龟山所说的情,当指真情。但无论如何,情与直是不能直接等同的。在朱子,性无不善,而情则或有不善。真情过当也会流于私,所以在重视真情的同时,也还是要讲到准则,讲到理以为限定。于朱子来说,行动本乎人情固然很重要,但还是要做到依乎天理,虽然在朱子那里,情和理之间的界限未必就十分清楚。
朱子对龟山论、孟注释的肯定颇多,甚至不乏“独得之”、“至矣”这样的赞语,但在一些涉及思想性内容的领域(往往是上文提到的几个方面,朱子对龟山的批评依然尖锐)。抛开龟山对一些细节问题的论述,我们注意到朱子所肯定龟山的,往往是其注释平实之处,而对其近禅、新奇、过高,疏阔之论则持批评立场。
例如,龟山对“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解释为:“会物于一己,而后能公天下之好恶,而不为私焉。”①对此,朱子直言龟山的说法本于僧肇,与儒家的说法不类:
杨氏会物于一已者,僧肇之言也。夫谓无私心而自无物我之间,可也。若有意会物而又必于已焉,则是物我未忘,率彼以合乎此也。且物之与己,又若之何而可会哉?此记佛者之言而较之,犹未得为极至之论,况杨氏以儒者而数称之,则不可晓矣。②
龟山此说是否本于僧肇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龟山这一主张泯除物我痕迹的说法,这显然是朱子不能接受的。类似的例证极多,此不赘述。
龟山著述很多,但是在道学史上留下影响的内容并不多。这多少也是诸二程弟子的宿命:处在北宋五子与朱子之间,学术基本以述为主,自身特色不足(即便稍有己见,也多成为朱子批评的对象)。随着朱子影响的扩大,二程诸弟子只有被朱子的光环所笼罩。在很大意义上,他们的价值就在于一度成为朱子思想发展的引路人乃或批评对象,从而促进了朱子思想的飞跃。
附注
①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龟山学案·序录》,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44页。
①二人的《论语解》都已经遗失,但都部分保存在《论语精义》和《论语或问》当中。
②《朱子全书》,第24册,《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第3793页。
③同上。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402页。
②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载《朱子全书》第十四册,第707页。
③朱熹:《论语精义》卷六下,“司马牛问仁”节引,载《朱子全书》第七册,第419页。
①谢良佐:《上蔡语录》卷上,《诸儒鸣道集》卷四十六,第999页。按,谢的原文为:“自然不可易底,便唤作道体;在我身上便唤作德;有知觉、识痛痒便唤作仁;运用处皆是当,便唤作义,大都只是一事,那里有许多分别?”从此段文意看,上蔡并非简单地认生理意义上的知觉、痛痒就是仁。再者,上蔡所说的“识痛痒”也有其特定的含义:“今人唱一喏,不从心中出来,便是不知痛痒……又如仲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见大宾,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识痛痒。”可以说,上蔡的表述是清楚的,不容易引起歧义。不过,谢上蔡有时表述又是含混的,如他在对《论语》中“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这句话的注解中,就认为“要之,四事皆心不纵恣者能之,故近于有所知觉”,这显然就在把仁直接等同于知觉,上蔡并不刻意强调知觉与仁的区分,于此可见一斑,见《论语精义》卷七下,《朱子全书》第七册,第467页。
②《上蔡语录》卷上,《诸儒鸣道集》卷四十六,第985页。
③《上蔡语录》卷中,《诸儒鸣道集》卷四十七,第1015页。
④《上蔡语录》卷上,《诸儒鸣道集》卷四十六,第985页。
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零一,载《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366页。
②谢良佐:《论语解》,《论语精义》卷一上引,载《朱子全书》第七册,第31页。
③《朱子语类》卷二十,载《朱子全书》第十四册,第707页。
④朱熹:《论语或同》卷六,载《朱子全书》第六册,第614页。
⑤同上。
①《朱子语类》卷三十五,载《朱子全书》第十五册,第1303—1304页。
②《论孟精义》引,见《朱子全书》第7册,《论孟精义》卷六下,“司马牛问仁”条,第419页。
③《上蔡语录》卷上,《诸儒鸣道集》卷四十六,第992页。
④谢本人很强调下学而上达,也很重视居敬和穷理的功夫。但在湖南诸学者,似乎特别关注察识心之发动处的功夫,对谢的其他方面讨论得不多。
①《论语或问》卷四,载《朱子全书》第六册,第683页。
①《上蔡语录》卷中,《诸儒鸣道集》卷四十七,第1017、1018页。按,“曾本”此句作“学者先须穷理”,也即上蔡认为穷理是“入德之门”。
②参见陈来师《宋明理学》,第130—132页。
③《上蔡语录》卷中,《诸儒鸣道集》卷四十七,第1017—1018页。
④朱子对此的批评非常多,此不一一列举。
①朱子曾长期困惑于二程既强调理无大小,又主张进学有序的说法,最终从理事关系的角度给对此问题给出了回答,详见《朱子语类》的相关内容。
②《上蔡语录》卷上,《诸儒鸣道集》卷四十六,第1006页。
③《论语精义》卷十,载《朱子全书》第七册,第621页。
①《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载《朱子全书》第十四册,第824页。
②《朱子语类》卷一零一,载《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362页。
③此处《朱子全书》原点断为“如说道‘洒扫应对进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显误。朱子此处所指,就是上蔡的说法。
④《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载《朱子全书》第十四册,第793页。
①《论语或问》引,载《朱子全书》第六册,第907—908页。
②《二程语录·明道先生语三》,《诸儒鸣道集》卷三十,第619页。
③《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四之一》,《诸儒鸣道集》卷三十五,第718页。
①《二程语录·伊川二程先生语四·谢显道记忆平日语》,《诸儒鸣道集》卷二十四,第481页。
②《论语精义》引,载《朱子全书》第七册,第408页。
③《上蔡语录》卷中,《诸儒鸣道集》卷四十七,第1033页。
①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二引,四库全书本。又见于《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记上蔡语》。
②《朱子语类》卷四十,载《朱子全书》第十五册,第1432页。
③《论语或问》卷十一,载《朱子全书》第六册,第796页。
④《朱子文集》卷三十五,《答吕伯恭别纸·上蔡尧舜事业》,载《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第1526页。
①此内容仅见于通行本《上蔡语录》,“鸣道本”则作“今人学诗,将章句横在肚里,怎生得脱洒去,莫道章句,便将尧舜横在肚里也即不得”。见《诸儒鸣道集》卷四十六,第997页。
②关于这一点,详见拙作《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此不赘述。
③《上蔡语录》卷中,《诸儒鸣道集》卷四十七,第1033页。
④《朱子文集》卷,《经庭讲义·大学》,载《朱子全书》第二十册,第708页。
①《朱子文集》卷三十二,《答张钦夫·诸说例蒙印可》,载《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第1419页。
①黄宗羲、全祖望编:《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51页。
②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一,《读本朝诸儒理学书》,第894页,元后至元刻本,黄山书社,中国基本古籍库。
③土田健次郎:《道学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43页。
①黎昕:《从四书集注看朱熹对杨时理学思想的批评和继承》,《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9年第1期。
②《道学的形成》,第215~216页。
①杨时:《龟山集》卷十二,《龟山语录·语录三·余杭所闻》,四库全书本。
②石〓编、朱熹删订、严佐之点校:《中庸辑略》,第9,载《朱子全书外编》第一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①《龟山集》卷十三,《语录四·毗陵所闻》。田按,这一段,在元释熙仲所集的《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中,则作:“文靖公龟山杨时,为东林总禅师友善。每谓师曰:‘禅学虽高,却于儒学未有所得。’师曰:‘儒学紧要处也,记得些?且道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得个什么?’公默然。总又与公言十识:‘第八庵摩罗识,唐言白净无垢;第九阿赖耶识,唐言善恶种子。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性善则可谓探本言,善恶混,乃是于善恶未(原文如此,当为已字)萠处看。’公然之。于是服膺”,二者文字略有差异。见台湾新文丰公司1995年版,《藏经书院版卍续藏经》,第132册,第0211页。
②《龟山集》卷十四,《答胡德辉问》。
①《龟山集》卷十二,《语录三·余杭所闻》。
②《孟子或问》卷十一,第980、981页。
①《孟子精义》卷十四,第832页。
②《二程语录·二程先生语二之一》,《诸儒鸣道集》卷二十,第393、394页。
③《二程语录·二程先生语九》,《诸儒鸣道集》卷二十七,第547页。
④《二程语录·明道先生语二》,《诸儒鸣道集》卷三十,第614页。
⑤《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一之一》,《诸儒鸣道集》卷三十一,第626页。按,“鸣道本”此段与《遗书》稍有不同,后者作:“人患事系累,思虑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穷理。穷至于物理,则渐久后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比较而言,《遗书》记录为优。
①《龟山集》卷二十六,《题萧欲仁大学篇后》。
②同上。
③《朱子文集》卷七十,《记程门诸子论学同异》,载《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92页。
①《中庸或问》,载《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91页。
②《四书或问》,第589—590页。
③《龟山集》卷二十一,《答吕秀才·辱问以所疑》。
④《龟山集》卷一,《上渊圣皇帝》。
⑤《龟山集》卷十二,《语录三·余杭所闻》。
⑥《龟山集》卷二十一,《答学者其一·孟子曰天》。
①《龟山集》卷四,《中庸义序》。
②《龟山集》卷二十六,《题中庸后示陈知默》。
③龟山的《中庸解》基本保存在宋儒石(石子重)的《中庸集解》一书中,但是该书被朱子后来删减为《中庸辑略》一书(删减七十四条,删除六十条),而《中庸辑略》在明代嘉靖本中再次被删除八十余条。由此,龟山的《中庸解》也损失大半。所幸清人莫友芝有《中庸集解》之辑本。
④收入吴震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489页。
①《中庸或问》,第557页。
②《二程语录》卷四,载《诸儒鸣道集》卷二十五,第505页。
③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三十六引,四库全书本。
①《龟山集》卷二十,《答胡康侯其一》。
②《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五引。
③朱子对吕氏的批评,主要针对其“由空而后见夫中”,认为这是“欲于未发之前求见夫所谓中者而执之”。
④《中庸或问》,第563、564页。
①《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四引。
②《道学的形成》,第449页。
①《中庸或问》,第568页。
②《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六引。
③《中庸或问》,第600、601页。
①《论语或问》卷一,载《朱子全书》第六册,第612页。
②《礼记集说》卷一百三十引。
①《论语精义》卷七上,第459页。
②《论语或问》卷十四,第817、818页。
①《论语精义》卷二下,载《朱子全书》第七册,第137页。
②《论语或问》卷四,载《朱子全书》第六册,第677页。
①(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66册,《刑法》二之第127页,1936年北平图书馆影印本。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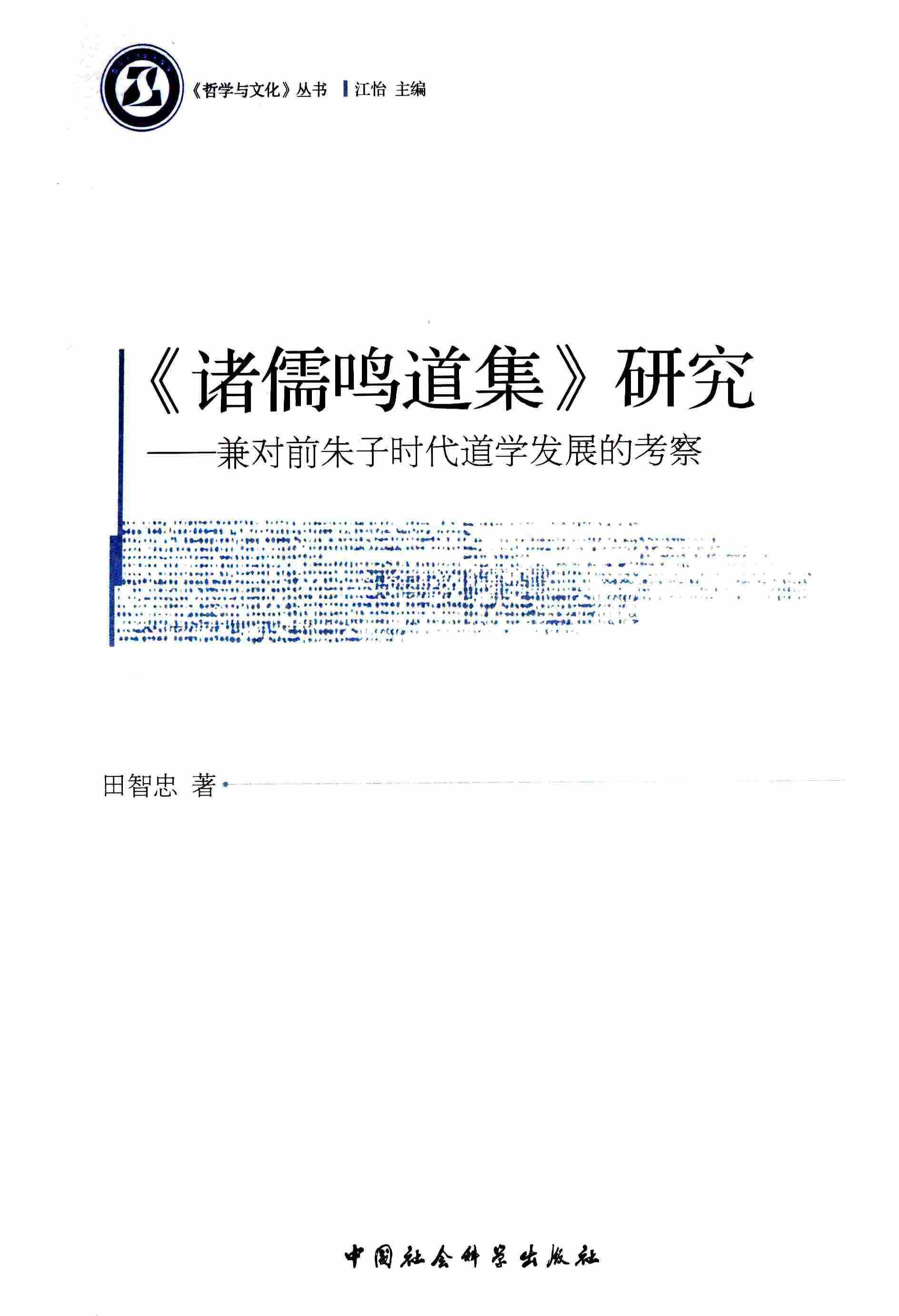
《《诸儒鸣道集》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内容包括:《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考、关于《诸儒鸣道集》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诸儒鸣道集》视野下的宋代儒学多元性研究、周敦颐与张载的道学话语构建、二程对道学话语的构建、谢良佐与杨时对道学话语的构建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