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二程对道学话语的构建
| 内容出处: | 《《诸儒鸣道集》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5191 |
| 颗粒名称: | 第七章 二程对道学话语的构建 |
| 分类号: | B244.4 |
| 页数: | 16 |
| 页码: | 276-291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周敦颐、张载和二程是道学话语建构的重要代表人物。周敦颐强调天道自然无为,张载则以气为本,而二程则以天理观为基础,重新构建了“一天人”的思想体系。二程的天理观强调理是世界的本质,并突出了儒学之道的德性之维,为人的德性修养功夫奠基。 |
| 关键词: | 周敦颐 张载 道学话语建构 |
内容
周敦颐、张载在道学话语建构上虽然也兼顾天与人,其贡献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天道的说明上。但是,无论是周还是张,他们对天的说明更多是强调其自然的一面,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天是自然的,但人却应该是自为的。如何从强调天之自然和无为中引出人之德性和修养德行之积极有为的一面,并能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始终是一个大的问题:
在周敦颐的体系里既然太极是宇宙的本根,人性又源于宇宙本根,因而人性应当就是太极元气的本性的表现,但周敦颐并未明确肯定这一点。①
周敦颐同样没有明确肯定人之仁义这个“极”,就是“太极”之阴阳本性的在人身上的表现,虽然这在周敦颐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
在张载以气为本的思想体系中,此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张载发展了汉唐的元气论,构造了一个气一元论的完整体系。基于这个体系,他把太虚之气作为人性的根源。这一作法在理论上虽可自圆其说,但由太虚(气)之性如何转而为仁义礼智(理),并不是没有困难。②
对于天或者本然之气,张载多强调其自然的一面;对于人,张载则强调其德性和积极有为的一面。但是自然无为的天如何又能成为人之德性的本源与根据,张载在这方面同样缺乏明确的说明。事实上,在周敦颐和张载那里,天人之关系还没有真正得以贯通,尽管他们对此都有所努力。
上述问题在二程①那里有明确的解答:以天理观为基础,他们重新构建起了“一天人”的思想体系,此可谓是二程在道学话语构建上的最大贡献。
较之于周敦颐和张载(甚至还可以上推到汉唐诸儒),二程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则有根本的不同:他们视理为世界的本质,而不再纠缠于对宇宙生成和形而下方面的关注。由此,在二程那里,天的本质就不再只是自然的,而更是理性的、德性的。这样,天与人之间也就彻底实现了本质上的贯通。显然,“理”或“天理”由此便成了二程后数百年间道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而人的尊德性问题也得到了来自天道层面的直接支撑。
再者,从周张到二程,其所关注的话题也逐渐聚焦到人伦这个中心上:庞万里先生就认为,二程思想“人伦是重点,伦理思想处于主导地位,而天道观则是从属的。这是二程之学的根本特点,也是由二程确立起来的宋明理学的一个基本特征”。②庞先生的观点虽然还可以商榷,但是二程确实更多是在关注人道中的问题,《程氏易传》文本就最能说明这一点。③这当然不是说二程就完全不关注天道,相反,天理观④始终是二程整个思想的基础,居于奠基性的地位。只不过,他们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已经由天那边而转向了人这边。
一天理观
二程认为,理或天理是天的本质,而此前大家关注的气,只是理驱动下的表象而已。天与理之间是直接同一的关系:“天者,理也”、“自理言之谓之天”。①从二程这里开始,天不在仅仅是苍苍然的、可见的一物,而是与“理”确立起了内在而本质的关联。这里,二程所提的“天理”不同于此前人们所理解的“理”:理不再居于宾词的地位,而一跃成为主语,成为本根。张岱年先生认为,“在先秦哲学,所谓理,皆以分殊言”,②这是说,“理”在先秦哲学中是纹理、条理的意思,只是个修饰性的宾语。其实,不独先秦哲学是如此,就是汉唐哲学也是如此。与此相对,二程所说的天理“则以总一言”,是气之所以能呈现为万物的究竟根据,也是这个世界的本根。在二程那里,理首先是“独立的”,它自根自本,自是其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而此前被认为是本根的气则变为二程眼中理的附属。这一转变,显然是颠覆性的。
在儒学史上,二程所理解的理是颇有新意的。惟其如此,二程才会自信的声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己体贴出来。”③——他们所体贴出来的,不是这已经给人反复提到的两个字,而是其中包含的新意,是他们对此二字的全新理解。
欲要深入地了解二程天理观在道学话语建构中的意义,我们还需要对二程之天理观与传统道论之异同作出深入的比较。我们知道,在二程之前,人们普遍地视理为殊理,而视道为统名(总一),此外也有视道为世界本根的说法(道家)。那么,二程的天理观与前人的道论相比,其特殊之处又表现在哪里呢?其实,这个问题在韩愈那里已经有所提到:“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儒释道都在谈道德(佛家在格义阶段也大量使用道德、性命一类词汇),但是离开了仁义这一确指,所谓道德的内涵就是空洞的、混乱的,甚至会流于老庄之既尊道德却又在非毁仁义上去。显然,儒释道之间对“道”的理解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儒家之道始终强调其伦理、德性属性,而佛老之道则有突出“非人化”、非德性化的因素。单纯“道德”这一概念已经不足以揭示儒学之为儒学的特质所在。与此相应,二程提出天理观,旧明显突出了儒学之道的德性之维,具有凝定儒学之主题、为人之德性修养功夫奠基的作用。
二程还特别强调以理为前提的,天人之间的一本关系:天理不独是天的本质,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终根据:此即所谓“天人无间”①,所谓“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②。他们不仅从理的普遍性角度提出:“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只心便是天”③的说法,而且还特别强调不但天可以包人,而且人也可以包天:“若如或者别立一天,谓人不可以包天,则有方(限定,拘束的意思)矣,是二本也”、“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④这里,二程无论是说只心便是天,还是说人可以包天,无非是强调人心中所有的理和天理无二罢了,却绝不是像佛家那样主张“心生万法”。显然,二程较之于前贤而论,更为彻底地贯彻了天人一本的观念,而且其立论基点也显有不同。
于二程,天人之“一本”又具体体现为理一分殊的关系:天人之合,先在其有分,笼统的一体之物(抽象的同一)也就无所谓合。⑤只有在强调天人之分的前提下,探讨天人之合、之一本,才有意义。具体来说:理是一、是本,人是殊、是末;理为纯,人为杂(理与气杂)。一方面,作为一的“理”就呈现在“众殊”之上,这是天人之一本的最集中体现;而另一方面,众“殊”则是以相互差异的形式而呈现着理一,这也意味着“殊”之基于“一”的动态的成就、生成和展开的因素。由此,道学中的“天人一本”,是在同一性这个根本上绽放的多样性。毋宁说,主张随才成就是其主张“理一分殊”的合理推论。
多数心学家包括一些当代学者往往质疑程朱之何以通过外向的格物穷理功夫,便能引出人自身内在的明明德实践之结果,进而认为外物之理与人的德性是二本,这是出于对程朱之学的误解,至少是对程朱学所主张的“理一分殊”理念没有足够的自觉。二程对此有明确地说明,如提出“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⑥,这就是告诫人不要隔绝天道和人道、人的性与外物之理。在二程乃至大多数宋明儒者看来,天道之阴阳、地道之刚柔和人道之仁义都是理这个“一”在不同层面的显现(都是殊理,但无不是“理一”的体现),此即所谓“理一分殊”。由此,所谓性理和物理就不是两个理,格物穷理也自然可以成为明明德之助。
较之于传统儒学以天或者以气为核心的天人一体观念,二程提出以理为核心的新的天人一体(或一本)的理念,这是一个真正的创新。
二程之天理观的提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明确了形上与形下、道与器的区分,把人的视域从形而下的现象界提升到了形上的理世界。①这就大大强化了儒学的理想性,也改善了以往认为儒学不关注形而上问题、只限于治世之道的诘难。
自二程之后,理或天理成为道学乃或理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二程也因此被视为道学或理学的创始者。
二性即理
二程在道学话语构建上的第二个贡献,是提出“性即是理”的说法。我们认为,“性即是理”应该被视为是二程心性论的核心,而以往学界却往往忽视这一点。
从先秦直到宋明,心性论、性情论从来都是儒学中的重头戏,而其基本特色就在于以天人之际为视野,展开对人心性问题的讨论,二程的心性论的精义也正在于此。
概言之,在先秦儒家论性中,《中庸》、《孟子》②和《荀子》有着不尽相同的诠释方向,而近年地下出土的《性自命出》(或称《性情论》)则与《中庸》的说法更为类似。总的来说,先秦的心性论是以天为中心的,强调天赋,强调天之于人的优先性:《中庸》和《性自命出》都强调“天命”是人性之本,人性需要由天命来定义——“天命之谓性”和“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基本上是同意的。同时,在孟子之前,天的本质为何①以及天究竟是在把什么命予人,这一点却没有被人说明过。由此,人的“性”更多是与人生而即有的自然属性相联系的(即生之谓性):“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②等观点即是最好的说明。与此相对,《孟子》则更突出强调“性”是人所固有的类本质这一点——孟子继承了《中庸》和《性自命出》的说法,提出人之“大体”(即善性)来自天赋的说法,却已经不重视天之“命”的一面。孟子似乎更强调,并非所有天赋的因素都能被视为是人的“性”,而只有标志着人之所以为人之特质者才可以称为人的性。在此意义上,他并不完全赞同“生之谓性”的观点,也明确反对“食色性也”的论调,认为后一种说法无异于把人之性等同于牛马之性。孟子转而强调,只有天赋的同时又是为人所固有的善端,才是人之为人的特性所在,这也才是人的性。孟子的这一新提法,是开创性的,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
不过,孟子同样没有说明人的性与天的本质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他甚至很少提到天。《荀子》论性,似乎又回到了“生之谓性”的层面:以好利、疾恶、耳目之欲、有好声色这些自然属性为人的性。由于荀子所理解的天是自然之天,因此对他来说人性只是天生、“生而有”的自然属性而已。需要说明的是,荀子并不认为人性即是人的本质,而是认为群或者伪这些后天属性才是标志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性所在。可以说,孟荀在论性上都能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由于二人的立论基础不同,所以其观点也很难调和。
汉唐论性,根本特色是强调气禀,在天人之间,主导权又回到了主宰之天和气质上。但是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本章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上:如何才能建立起自然、气化之天与人之德性本质之间的有效关联呢?在此阶段,基于人这一聚焦点的,对心与性情之内在而精深的分析不见了。这一问题甚至是到了张载那里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张载性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天之性是人之性的底色(即彰显天与人在本质上的贯通),进而提出尽性的目的在于使人“返本”,使天地之性成为现实人性的主导。张载的上述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其以气为本的思想体系和强调天地之性的自然化特色,都使其很难跳出陈来在上文中所提到的困局。
二程之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接着张载讲的,其基本格局同样是在天人、理气的大视野下来论性。不过,与张载合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来论性(其实都是气之性)的思路不同,二程则转而从理与气之合的视角来讨论性,①引入理来论性使二程对心性的讨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主要贡献正在于提出“性即是理”的观点:
性即是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②
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③
(天)理之在物(人)为性,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二程主张“性不可也内外言”④的确切所指,就是指理无内外,故性无内外。这里,二程所说的理,只能是天理,其所说的性,也只能是天命之性。二程此说的突破性就在于,以“无不善”的理——也即是天的本质来充实孟子对人性善的论证说明,为人性善的说法奠定了形上本体层面的基础。我们知道,孟子的性善论自提出之日起就在受到各种各样挑战。在其身后,各种性论也层出不穷,而孟子的说法则基本上没有人正面回应过。二程的这一说法,在延续此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天命之谓性”的说法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天理无不善,而天恰恰是在把“无不善”的理性赋予人,因此在天人一本的前提下,人的本质与天的本质是直接同一的,因此人性之本质也就只能是善的。可以说,二程为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更新的证明(至于理无不善的说法是否能站得住脚,这里暂不讨论)。自此,基于天人一理或者说天人一本的理念,人性的本质与天理便可以直接同一(只是人性的“本”与天理的同一),那么人的道德修养实践就有了来自天的根源性保证。
当然,基于理一分殊①、理气合一的视角,二程乃至后来的朱子都不会认为,现实中的人性都是至善无恶的。在提出理性之后,二程也很关注气质之性,以便对在现实中人性的不齐做出说明:他们认为,从气禀的角度来说,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但是此之“性”已经不是本然、源头意义上的“性”,而只是流了。这里,二程提出了源与流的说法:就源论,头则性无不善,而就其流论,则性或有不善,但是流之不善是因为受到了气禀的影响,是气禀掩盖、杂染了(而非改变)性的本质。二程认为,只有统合源与流、性与气而观之(一定要统而观之),我们对人性的了解才是完备的,此即“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②。当然,无论是张载还是二程,都不是在简单重复汉唐诸儒以气禀而论性的窠臼,而是希望对人的现实与本质、理想与现实之间张力做出说明,在确保对人性本善的前提下,进而使“变化气质”成为其道德践履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二程之论性同样不限于抽象的概念分析,而是强调了动态的生成、生意和生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告子此言是……)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③这里,二程之“部分肯定”告子的观点,其前提是对告子说法的“曲解”——将生解释为生意,生机,然后将“生之谓性”解释为万物在天地之气化流行中所得之性,而二程将生或生意引入对性的说明,使其性论不再局限于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了体验、感受和境界论的成分。
三仁说
二程在道学话语构建上的第三个贡献,是重新诠释了仁及识仁说。“仁”本是先秦汉唐儒学都很重视概念。虽然只有到了朱子和张栻那里,对仁的讨论才达到了高峰,但是二程对仁的讨论无疑为后来的这一热潮的出现,奠定了基调。
我们知道,先秦儒学论仁,多限于就人而论仁之范围。汉唐诸儒在元气论和阴阳五行的模式下,开始将仁义与天之阴阳(之气)、将仁义礼智信与四时五行之间展开比附。他们这样做的长处是开始寻求在天人之际的视野下来论仁,把仁学推进到了一定的高度;其短处,一是这类比附往往会失之牵强,理性的成分不足;而另一个短处是,这种泛自然化、元气化的论仁方式,会远离开人这个中心(即使他们会提到人,也是自然化,甚至气化的、被物化了的人),有把仁自然属性化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在将仁义礼智信与四时五行的比附中,强调以木为春,春主生,其德为仁,这其实了开了以“生”来论仁的先河,只不过董仲舒还并没有刻意要强调这一点。
在北宋,多数学者基于传统的观点而强调从爱人的角度来诠释仁;与此同时,“以生论仁”则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趋势。如,周敦颐即提出“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的说法。①同时,张载也主张“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这些说法在二程那里都得到了发挥。当然,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周张二人都继承了先秦仁学的精神,而突出强调的是以爱说仁。
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二程在论仁上继承时贤“以生论仁”的同时,特别强调从人的角度来论仁。这在二程论仁上是一个共性。②此外,多数学者已经注意到,大程子与小程子在对仁的诠释上略有差别:前者高远,后者平实;前者以体验和感受为基础,后者以理性的分析为基础。我们以为,两人的仁说未尝不是一种良性的互补,而非对立。他们的说法在朱子那里则得到了进一步的综合。
明道论仁,强调的是人的感受性:尤其是动态的、充满生意的感受。其著名的观生意体仁、切脉体仁、观雏体仁、以浑然与物同体之感受为识仁之效验诸说法,都能说明这一点。在这里,以我为主的观字、体字最为至要,明道甚至提出:
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哉?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何尝支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贡以为仁之方也。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①
从上文可知,无论是体字还是观字,都在指示出知觉与仁的内在关联性。但是从这段话文义看,明道所说的“知”,其本意是“体是心”。明道不否认“知”关联着仁(也是仁的表征之一),但他不会笼统地赞同以知觉为仁的观点。
明道论仁之最著名者,则是其“识仁篇”: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②
陈来认为,“所谓学者先须识仁,识并不是认识,识仁实即体仁”③。在这里,“体”仁实即是去感受万物息息相关之生意,去培养物我之间血脉相通的一体感,尤其是要体验个人的生命意识。于明道,“体仁”既是功夫,也是效验。他认为,只要真切体会到了仁之流行发现处,以诚敬存之就可以了,不需要刻意地去做防检和穷索的功夫。当然,在明道那里,可以说仁者会有“浑然与物同体”之境界,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用“与物同体”来界定仁,明道基本不用严格下定义的方式来界定仁,这是明道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再者,明道强调的“与物同体”,又内在包含着“义礼智信皆仁”、“视物如己”的因素。所以,明道此说与道家“万物一体”的说法显有不同,是一种有我之境:陈来即认为,“此种境界指向的是一种慈悯的情怀,即亲亲、仁民、爱物,以此境界实现人的社会义务”①。道家所主张的万物一体说的核心却是要忘我,是一种“负的境界”,而以明道为代表的道学的“与物同体”说则以有我(我的情感、感受,主要是恻隐之心)为前提,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爱有差等”,是一种“正的境界”。与此相对,墨家之主张“兼爱”,惠施之主张是万物一体,更多的是抽象的、逻辑上的同一(不讲差别的同一),其深处则是一个利字。当然,对于许多儒者来说,未必对上述差异有高度的自觉,甚至有的会主张三教合一,他们对仁的理解就很难和道家思想划清界限。事实上,伊川和朱子都很忧虑这一点,也在下大力气辨析这一点。
伊川论仁,则重在辨明义理——公、爱,知觉、万物一体与仁之间的关系,都属于其关注的范围。伊川强调,仁是“性”、是体,而公和爱是用,属于情的范畴,知觉属于智的范畴。仁与它们之间有内在的关联,却不能直接相等同。这些说法,许多显然是针对明道而发,包含有“纠偏”的意味。
伊川也曾提到公与仁之间的关联性: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②
仁者,公也。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喻,可谓仁之方也’。尝谓孔子之语仁,以教人者唯此为尽,要之不出于公也。③
又问:“如何是仁”?曰:“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则常教他将公字思量”。④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仁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①
上文所引,至少有两条出自伊川之口,可知强调公与仁的内在关联是二程的共识。对伊川来说,公与仁最近,最能说明仁之本质,但他明确指出“不可将公公便唤作仁”。同理,在对待爱与仁的关系上,伊川也持相类似的立场:“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②
伊川论仁,还特别强调了理一分殊的原则,这是对张载之《西铭》的进一步发挥,集中体现于著名的《答杨时论〈西铭〉书》③中:
……《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
前已述及,张载的《西铭》含有与天地同体的意思,杨时即质疑张载此说会流于墨家的兼爱说。明道试图从情感立场来区分“与物同体”说与道家的“万物一体”说不同,而伊川则从一本与二本的差异来说明儒家之仁与墨家之兼爱的区别:主张理一分殊是一本,而主张兼爱则是二本。对于一本与二本的根本区别,学界讨论已多,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伊川认为,“分立而推理一”才能防止爱流为私,这才是正确的“仁之方”。“理一分殊”也预示着“广义的”仁又应该是“狭义的”仁与义的统一体。义就是适宜,恰当(应该)。“分立而推理一”则意味着在恰当的差异中体现出统一性,也意味着“老幼及人”需要以“爱由亲始”为圆心,为出发点。有了这个圆心,就是一本,反之就是二本。据孟子说,这个圆心就是不容己而当下呈现出来的真情——首先是亲情,这没有什么道理、理性可讲,就是自然而然的东西。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限制它,不要让它流于私而已,而义就是在起到这一限定作用。伊川和孟子都会认为,强调无差别的兼爱,就是要视自己的亲人为路人,而这正好说明你心中本来就没有爱亲之情(更不要说是爱人了)——那么所谓的兼爱就只能以“利”为基础(墨子的本意绝非如此)。
基于“理一分殊”的一本立场,伊川明确反对当时颇为流行的以“万物一体”为仁的说法。庞万里先生指出,“伊川侧重在人的范围内讲人……认为仁只适合于人道……不能推之及物”①,这就抓住了伊川仁说的精髓:伊川立论,更多聚焦在人这个中心上,既强调了人与万物的界限与区别,也突出了儒学与墨学、与佛老之学(后者的共性是空泛的讨论万物一体)的界限。
四工夫论
二程在道学话语建构上的第四方面的贡献,集中在工夫论领域。我们知道,无论是道学还是广义的理学,都以学以成圣,由内圣以达外王为根本宗旨,并强调所学与道德践履实践相结合,②因此重视践履工夫是理学的特色所在。
学界已经注意到,明道与伊川的工夫论颇有不同:明道重视体认而伊川重视格物。当然,上述差异并不是绝对的。由下文可知,二人在工夫论上相同的主张也很多。
伊川的工夫论,可以概括为涵养与进学并进:具体表述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③。这里,伊川是主张以“主敬”来统摄涵养工夫,并以格物致知来统摄进学工夫的。不过,伊川似乎认为敬与致知之间还是一体的关系:不独在致知中始终需要保持诚确(即敬)的态度,而且主敬工夫也需要得到来自致知方面的支持:“或问进修之术何先,曰‘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④于伊川,正心诚意与主敬其实是一体之两面,而心之正、意之诚(敬)又首先在于有真知、在于明理(他又指出,保持诚敬的状态“则心便一……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由此,主敬与致知之间就不是不相干的两个工夫,而是水乳交融的一体关系。
陈来曾认为,“‘敬’是程颐提倡的主要修养方法……程颐则不遗余力地强调敬”,他所理解的“敬”既包括外在仪表的庄严,也包括内在心境的主一无适。①显然,伊川之主敬工夫实质是强调内与外相贯通。在对敬的强调上,我们可以看到二程工夫论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关系:明道更活,伊川更直。
值得注意的是,二程之强调“主敬”工夫,中心的关注点“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困扰宋明大多数理学家的‘思虑纷扰’的问题”。②明道与伊川对此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很值得我们进行细致的比较。
众所周知,明道对此问题的讨论系承接张载的书信而发,由于张载的来信提到的是“定性”,所以明道也以如何来“定性”作为回复。③其实,正如朱子后来所提到的,此处的“性”字表述为“心”字会更为合适。明道之回复即著名的《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④其要点可概括如下:
其一,心通内外、贯动静,心之定亦贯通动静,心之定指的是安定,而非不动。这里,明道论说的重心放在了破除认为心有内外之分与是内非外的认识上(往往是佛老的说法)。
其二,主张人应该效法天地之“普万物”,进而做到顺万事,具体就是要努力做到“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并批判了通过绝外物、除外诱的方式来定心的手段之无效。
其三,指出人不能定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受蔽而流于自私,自私则会远离自然,无法做到内外两忘。反之,则应该以公心应物而“无事”,明道称此为“明”的境界。
其四,指出定心之理想状态为喜怒发于应物之“适当”,即做到喜怒不出于己,而应该系于物(理)。明道以怒为例,具体说明如何以理(之是非)之怒而定心。
总之,明道定心的方法可以概括为空廓其心,动依于理而心无挂碍。这是其主张“与物同体”说的必然推论。
与明道相应,伊川对于如何定心问题也颇有思索:
吕与叔尝言,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曰:“此正如破屋中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其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①
闲邪存诚。闲邪则诚自存。如人有室,垣墙不修,不能防寇,寇从东来,逐之则复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二②人复至。不如修其垣墙,则寇自不至,故欲闲邪也。③
从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伊川在解决此问题上的不同思路:心要自主,“有主”说的是心的主体性或主导性、主宰性。对伊川而言,心有主是需要通过做工夫来培养实现的,培养的途径不外乎两端:一是主一或主敬,使心集中精神,长期保持一种恭敬、敬畏的状态;二是明理,通过格致工夫提高对天理的自觉性。显然,伊川所强调的心要有所主也是贯通动静的。伊川同样重视在应事之际“心有所主”的重要性:“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④伊川此论,与明道强调因循、强调自然明显不同,更强调有所作为,有所干涉的一面。
明道和伊川的定心说,与孟子的“不动心”,庄子和王弼、邵雍之主张无心以应物面对的是相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明道与庄子和王弼相近,而伊川与孟子相近。不过,明道之“定心”说与庄、王之说还是有根本区别:指导其定心说的,仍然是儒学的核心价值——大公说,天理说。
结语
二程无论是在理学史上的影响,还是在道学话语构建中的作用有目共睹。就近而言,杨时、谢良佐以及湖湘学派和道南学派为学工夫的确立,显然是受到了二程的深刻影响。上述二学派在促进朱子思想的成熟发展中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其在心性论及工夫论上的分歧也曾长期困扰朱子。有趣的是,朱子也正是在精研二程著作之下,才最终突破了上述困境,使自己的思想趋向定型。从长远说,二程之天理说、明道之识仁说、定性说、格致说对理学的影响可谓贯彻始终,并充当着道学与理学话语的主导。从这个意义说,二程是道学与理学当之无愧的建立者。
在周敦颐的体系里既然太极是宇宙的本根,人性又源于宇宙本根,因而人性应当就是太极元气的本性的表现,但周敦颐并未明确肯定这一点。①
周敦颐同样没有明确肯定人之仁义这个“极”,就是“太极”之阴阳本性的在人身上的表现,虽然这在周敦颐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
在张载以气为本的思想体系中,此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张载发展了汉唐的元气论,构造了一个气一元论的完整体系。基于这个体系,他把太虚之气作为人性的根源。这一作法在理论上虽可自圆其说,但由太虚(气)之性如何转而为仁义礼智(理),并不是没有困难。②
对于天或者本然之气,张载多强调其自然的一面;对于人,张载则强调其德性和积极有为的一面。但是自然无为的天如何又能成为人之德性的本源与根据,张载在这方面同样缺乏明确的说明。事实上,在周敦颐和张载那里,天人之关系还没有真正得以贯通,尽管他们对此都有所努力。
上述问题在二程①那里有明确的解答:以天理观为基础,他们重新构建起了“一天人”的思想体系,此可谓是二程在道学话语构建上的最大贡献。
较之于周敦颐和张载(甚至还可以上推到汉唐诸儒),二程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则有根本的不同:他们视理为世界的本质,而不再纠缠于对宇宙生成和形而下方面的关注。由此,在二程那里,天的本质就不再只是自然的,而更是理性的、德性的。这样,天与人之间也就彻底实现了本质上的贯通。显然,“理”或“天理”由此便成了二程后数百年间道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而人的尊德性问题也得到了来自天道层面的直接支撑。
再者,从周张到二程,其所关注的话题也逐渐聚焦到人伦这个中心上:庞万里先生就认为,二程思想“人伦是重点,伦理思想处于主导地位,而天道观则是从属的。这是二程之学的根本特点,也是由二程确立起来的宋明理学的一个基本特征”。②庞先生的观点虽然还可以商榷,但是二程确实更多是在关注人道中的问题,《程氏易传》文本就最能说明这一点。③这当然不是说二程就完全不关注天道,相反,天理观④始终是二程整个思想的基础,居于奠基性的地位。只不过,他们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已经由天那边而转向了人这边。
一天理观
二程认为,理或天理是天的本质,而此前大家关注的气,只是理驱动下的表象而已。天与理之间是直接同一的关系:“天者,理也”、“自理言之谓之天”。①从二程这里开始,天不在仅仅是苍苍然的、可见的一物,而是与“理”确立起了内在而本质的关联。这里,二程所提的“天理”不同于此前人们所理解的“理”:理不再居于宾词的地位,而一跃成为主语,成为本根。张岱年先生认为,“在先秦哲学,所谓理,皆以分殊言”,②这是说,“理”在先秦哲学中是纹理、条理的意思,只是个修饰性的宾语。其实,不独先秦哲学是如此,就是汉唐哲学也是如此。与此相对,二程所说的天理“则以总一言”,是气之所以能呈现为万物的究竟根据,也是这个世界的本根。在二程那里,理首先是“独立的”,它自根自本,自是其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而此前被认为是本根的气则变为二程眼中理的附属。这一转变,显然是颠覆性的。
在儒学史上,二程所理解的理是颇有新意的。惟其如此,二程才会自信的声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己体贴出来。”③——他们所体贴出来的,不是这已经给人反复提到的两个字,而是其中包含的新意,是他们对此二字的全新理解。
欲要深入地了解二程天理观在道学话语建构中的意义,我们还需要对二程之天理观与传统道论之异同作出深入的比较。我们知道,在二程之前,人们普遍地视理为殊理,而视道为统名(总一),此外也有视道为世界本根的说法(道家)。那么,二程的天理观与前人的道论相比,其特殊之处又表现在哪里呢?其实,这个问题在韩愈那里已经有所提到:“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儒释道都在谈道德(佛家在格义阶段也大量使用道德、性命一类词汇),但是离开了仁义这一确指,所谓道德的内涵就是空洞的、混乱的,甚至会流于老庄之既尊道德却又在非毁仁义上去。显然,儒释道之间对“道”的理解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儒家之道始终强调其伦理、德性属性,而佛老之道则有突出“非人化”、非德性化的因素。单纯“道德”这一概念已经不足以揭示儒学之为儒学的特质所在。与此相应,二程提出天理观,旧明显突出了儒学之道的德性之维,具有凝定儒学之主题、为人之德性修养功夫奠基的作用。
二程还特别强调以理为前提的,天人之间的一本关系:天理不独是天的本质,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终根据:此即所谓“天人无间”①,所谓“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②。他们不仅从理的普遍性角度提出:“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只心便是天”③的说法,而且还特别强调不但天可以包人,而且人也可以包天:“若如或者别立一天,谓人不可以包天,则有方(限定,拘束的意思)矣,是二本也”、“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④这里,二程无论是说只心便是天,还是说人可以包天,无非是强调人心中所有的理和天理无二罢了,却绝不是像佛家那样主张“心生万法”。显然,二程较之于前贤而论,更为彻底地贯彻了天人一本的观念,而且其立论基点也显有不同。
于二程,天人之“一本”又具体体现为理一分殊的关系:天人之合,先在其有分,笼统的一体之物(抽象的同一)也就无所谓合。⑤只有在强调天人之分的前提下,探讨天人之合、之一本,才有意义。具体来说:理是一、是本,人是殊、是末;理为纯,人为杂(理与气杂)。一方面,作为一的“理”就呈现在“众殊”之上,这是天人之一本的最集中体现;而另一方面,众“殊”则是以相互差异的形式而呈现着理一,这也意味着“殊”之基于“一”的动态的成就、生成和展开的因素。由此,道学中的“天人一本”,是在同一性这个根本上绽放的多样性。毋宁说,主张随才成就是其主张“理一分殊”的合理推论。
多数心学家包括一些当代学者往往质疑程朱之何以通过外向的格物穷理功夫,便能引出人自身内在的明明德实践之结果,进而认为外物之理与人的德性是二本,这是出于对程朱之学的误解,至少是对程朱学所主张的“理一分殊”理念没有足够的自觉。二程对此有明确地说明,如提出“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⑥,这就是告诫人不要隔绝天道和人道、人的性与外物之理。在二程乃至大多数宋明儒者看来,天道之阴阳、地道之刚柔和人道之仁义都是理这个“一”在不同层面的显现(都是殊理,但无不是“理一”的体现),此即所谓“理一分殊”。由此,所谓性理和物理就不是两个理,格物穷理也自然可以成为明明德之助。
较之于传统儒学以天或者以气为核心的天人一体观念,二程提出以理为核心的新的天人一体(或一本)的理念,这是一个真正的创新。
二程之天理观的提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明确了形上与形下、道与器的区分,把人的视域从形而下的现象界提升到了形上的理世界。①这就大大强化了儒学的理想性,也改善了以往认为儒学不关注形而上问题、只限于治世之道的诘难。
自二程之后,理或天理成为道学乃或理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二程也因此被视为道学或理学的创始者。
二性即理
二程在道学话语构建上的第二个贡献,是提出“性即是理”的说法。我们认为,“性即是理”应该被视为是二程心性论的核心,而以往学界却往往忽视这一点。
从先秦直到宋明,心性论、性情论从来都是儒学中的重头戏,而其基本特色就在于以天人之际为视野,展开对人心性问题的讨论,二程的心性论的精义也正在于此。
概言之,在先秦儒家论性中,《中庸》、《孟子》②和《荀子》有着不尽相同的诠释方向,而近年地下出土的《性自命出》(或称《性情论》)则与《中庸》的说法更为类似。总的来说,先秦的心性论是以天为中心的,强调天赋,强调天之于人的优先性:《中庸》和《性自命出》都强调“天命”是人性之本,人性需要由天命来定义——“天命之谓性”和“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基本上是同意的。同时,在孟子之前,天的本质为何①以及天究竟是在把什么命予人,这一点却没有被人说明过。由此,人的“性”更多是与人生而即有的自然属性相联系的(即生之谓性):“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②等观点即是最好的说明。与此相对,《孟子》则更突出强调“性”是人所固有的类本质这一点——孟子继承了《中庸》和《性自命出》的说法,提出人之“大体”(即善性)来自天赋的说法,却已经不重视天之“命”的一面。孟子似乎更强调,并非所有天赋的因素都能被视为是人的“性”,而只有标志着人之所以为人之特质者才可以称为人的性。在此意义上,他并不完全赞同“生之谓性”的观点,也明确反对“食色性也”的论调,认为后一种说法无异于把人之性等同于牛马之性。孟子转而强调,只有天赋的同时又是为人所固有的善端,才是人之为人的特性所在,这也才是人的性。孟子的这一新提法,是开创性的,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
不过,孟子同样没有说明人的性与天的本质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他甚至很少提到天。《荀子》论性,似乎又回到了“生之谓性”的层面:以好利、疾恶、耳目之欲、有好声色这些自然属性为人的性。由于荀子所理解的天是自然之天,因此对他来说人性只是天生、“生而有”的自然属性而已。需要说明的是,荀子并不认为人性即是人的本质,而是认为群或者伪这些后天属性才是标志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性所在。可以说,孟荀在论性上都能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由于二人的立论基础不同,所以其观点也很难调和。
汉唐论性,根本特色是强调气禀,在天人之间,主导权又回到了主宰之天和气质上。但是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本章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上:如何才能建立起自然、气化之天与人之德性本质之间的有效关联呢?在此阶段,基于人这一聚焦点的,对心与性情之内在而精深的分析不见了。这一问题甚至是到了张载那里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张载性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天之性是人之性的底色(即彰显天与人在本质上的贯通),进而提出尽性的目的在于使人“返本”,使天地之性成为现实人性的主导。张载的上述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其以气为本的思想体系和强调天地之性的自然化特色,都使其很难跳出陈来在上文中所提到的困局。
二程之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接着张载讲的,其基本格局同样是在天人、理气的大视野下来论性。不过,与张载合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来论性(其实都是气之性)的思路不同,二程则转而从理与气之合的视角来讨论性,①引入理来论性使二程对心性的讨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主要贡献正在于提出“性即是理”的观点:
性即是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②
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③
(天)理之在物(人)为性,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二程主张“性不可也内外言”④的确切所指,就是指理无内外,故性无内外。这里,二程所说的理,只能是天理,其所说的性,也只能是天命之性。二程此说的突破性就在于,以“无不善”的理——也即是天的本质来充实孟子对人性善的论证说明,为人性善的说法奠定了形上本体层面的基础。我们知道,孟子的性善论自提出之日起就在受到各种各样挑战。在其身后,各种性论也层出不穷,而孟子的说法则基本上没有人正面回应过。二程的这一说法,在延续此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天命之谓性”的说法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天理无不善,而天恰恰是在把“无不善”的理性赋予人,因此在天人一本的前提下,人的本质与天的本质是直接同一的,因此人性之本质也就只能是善的。可以说,二程为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更新的证明(至于理无不善的说法是否能站得住脚,这里暂不讨论)。自此,基于天人一理或者说天人一本的理念,人性的本质与天理便可以直接同一(只是人性的“本”与天理的同一),那么人的道德修养实践就有了来自天的根源性保证。
当然,基于理一分殊①、理气合一的视角,二程乃至后来的朱子都不会认为,现实中的人性都是至善无恶的。在提出理性之后,二程也很关注气质之性,以便对在现实中人性的不齐做出说明:他们认为,从气禀的角度来说,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但是此之“性”已经不是本然、源头意义上的“性”,而只是流了。这里,二程提出了源与流的说法:就源论,头则性无不善,而就其流论,则性或有不善,但是流之不善是因为受到了气禀的影响,是气禀掩盖、杂染了(而非改变)性的本质。二程认为,只有统合源与流、性与气而观之(一定要统而观之),我们对人性的了解才是完备的,此即“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②。当然,无论是张载还是二程,都不是在简单重复汉唐诸儒以气禀而论性的窠臼,而是希望对人的现实与本质、理想与现实之间张力做出说明,在确保对人性本善的前提下,进而使“变化气质”成为其道德践履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二程之论性同样不限于抽象的概念分析,而是强调了动态的生成、生意和生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告子此言是……)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③这里,二程之“部分肯定”告子的观点,其前提是对告子说法的“曲解”——将生解释为生意,生机,然后将“生之谓性”解释为万物在天地之气化流行中所得之性,而二程将生或生意引入对性的说明,使其性论不再局限于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了体验、感受和境界论的成分。
三仁说
二程在道学话语构建上的第三个贡献,是重新诠释了仁及识仁说。“仁”本是先秦汉唐儒学都很重视概念。虽然只有到了朱子和张栻那里,对仁的讨论才达到了高峰,但是二程对仁的讨论无疑为后来的这一热潮的出现,奠定了基调。
我们知道,先秦儒学论仁,多限于就人而论仁之范围。汉唐诸儒在元气论和阴阳五行的模式下,开始将仁义与天之阴阳(之气)、将仁义礼智信与四时五行之间展开比附。他们这样做的长处是开始寻求在天人之际的视野下来论仁,把仁学推进到了一定的高度;其短处,一是这类比附往往会失之牵强,理性的成分不足;而另一个短处是,这种泛自然化、元气化的论仁方式,会远离开人这个中心(即使他们会提到人,也是自然化,甚至气化的、被物化了的人),有把仁自然属性化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在将仁义礼智信与四时五行的比附中,强调以木为春,春主生,其德为仁,这其实了开了以“生”来论仁的先河,只不过董仲舒还并没有刻意要强调这一点。
在北宋,多数学者基于传统的观点而强调从爱人的角度来诠释仁;与此同时,“以生论仁”则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趋势。如,周敦颐即提出“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的说法。①同时,张载也主张“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这些说法在二程那里都得到了发挥。当然,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周张二人都继承了先秦仁学的精神,而突出强调的是以爱说仁。
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二程在论仁上继承时贤“以生论仁”的同时,特别强调从人的角度来论仁。这在二程论仁上是一个共性。②此外,多数学者已经注意到,大程子与小程子在对仁的诠释上略有差别:前者高远,后者平实;前者以体验和感受为基础,后者以理性的分析为基础。我们以为,两人的仁说未尝不是一种良性的互补,而非对立。他们的说法在朱子那里则得到了进一步的综合。
明道论仁,强调的是人的感受性:尤其是动态的、充满生意的感受。其著名的观生意体仁、切脉体仁、观雏体仁、以浑然与物同体之感受为识仁之效验诸说法,都能说明这一点。在这里,以我为主的观字、体字最为至要,明道甚至提出:
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哉?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何尝支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贡以为仁之方也。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①
从上文可知,无论是体字还是观字,都在指示出知觉与仁的内在关联性。但是从这段话文义看,明道所说的“知”,其本意是“体是心”。明道不否认“知”关联着仁(也是仁的表征之一),但他不会笼统地赞同以知觉为仁的观点。
明道论仁之最著名者,则是其“识仁篇”: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②
陈来认为,“所谓学者先须识仁,识并不是认识,识仁实即体仁”③。在这里,“体”仁实即是去感受万物息息相关之生意,去培养物我之间血脉相通的一体感,尤其是要体验个人的生命意识。于明道,“体仁”既是功夫,也是效验。他认为,只要真切体会到了仁之流行发现处,以诚敬存之就可以了,不需要刻意地去做防检和穷索的功夫。当然,在明道那里,可以说仁者会有“浑然与物同体”之境界,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用“与物同体”来界定仁,明道基本不用严格下定义的方式来界定仁,这是明道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再者,明道强调的“与物同体”,又内在包含着“义礼智信皆仁”、“视物如己”的因素。所以,明道此说与道家“万物一体”的说法显有不同,是一种有我之境:陈来即认为,“此种境界指向的是一种慈悯的情怀,即亲亲、仁民、爱物,以此境界实现人的社会义务”①。道家所主张的万物一体说的核心却是要忘我,是一种“负的境界”,而以明道为代表的道学的“与物同体”说则以有我(我的情感、感受,主要是恻隐之心)为前提,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爱有差等”,是一种“正的境界”。与此相对,墨家之主张“兼爱”,惠施之主张是万物一体,更多的是抽象的、逻辑上的同一(不讲差别的同一),其深处则是一个利字。当然,对于许多儒者来说,未必对上述差异有高度的自觉,甚至有的会主张三教合一,他们对仁的理解就很难和道家思想划清界限。事实上,伊川和朱子都很忧虑这一点,也在下大力气辨析这一点。
伊川论仁,则重在辨明义理——公、爱,知觉、万物一体与仁之间的关系,都属于其关注的范围。伊川强调,仁是“性”、是体,而公和爱是用,属于情的范畴,知觉属于智的范畴。仁与它们之间有内在的关联,却不能直接相等同。这些说法,许多显然是针对明道而发,包含有“纠偏”的意味。
伊川也曾提到公与仁之间的关联性: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②
仁者,公也。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喻,可谓仁之方也’。尝谓孔子之语仁,以教人者唯此为尽,要之不出于公也。③
又问:“如何是仁”?曰:“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则常教他将公字思量”。④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仁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①
上文所引,至少有两条出自伊川之口,可知强调公与仁的内在关联是二程的共识。对伊川来说,公与仁最近,最能说明仁之本质,但他明确指出“不可将公公便唤作仁”。同理,在对待爱与仁的关系上,伊川也持相类似的立场:“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②
伊川论仁,还特别强调了理一分殊的原则,这是对张载之《西铭》的进一步发挥,集中体现于著名的《答杨时论〈西铭〉书》③中:
……《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
前已述及,张载的《西铭》含有与天地同体的意思,杨时即质疑张载此说会流于墨家的兼爱说。明道试图从情感立场来区分“与物同体”说与道家的“万物一体”说不同,而伊川则从一本与二本的差异来说明儒家之仁与墨家之兼爱的区别:主张理一分殊是一本,而主张兼爱则是二本。对于一本与二本的根本区别,学界讨论已多,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伊川认为,“分立而推理一”才能防止爱流为私,这才是正确的“仁之方”。“理一分殊”也预示着“广义的”仁又应该是“狭义的”仁与义的统一体。义就是适宜,恰当(应该)。“分立而推理一”则意味着在恰当的差异中体现出统一性,也意味着“老幼及人”需要以“爱由亲始”为圆心,为出发点。有了这个圆心,就是一本,反之就是二本。据孟子说,这个圆心就是不容己而当下呈现出来的真情——首先是亲情,这没有什么道理、理性可讲,就是自然而然的东西。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限制它,不要让它流于私而已,而义就是在起到这一限定作用。伊川和孟子都会认为,强调无差别的兼爱,就是要视自己的亲人为路人,而这正好说明你心中本来就没有爱亲之情(更不要说是爱人了)——那么所谓的兼爱就只能以“利”为基础(墨子的本意绝非如此)。
基于“理一分殊”的一本立场,伊川明确反对当时颇为流行的以“万物一体”为仁的说法。庞万里先生指出,“伊川侧重在人的范围内讲人……认为仁只适合于人道……不能推之及物”①,这就抓住了伊川仁说的精髓:伊川立论,更多聚焦在人这个中心上,既强调了人与万物的界限与区别,也突出了儒学与墨学、与佛老之学(后者的共性是空泛的讨论万物一体)的界限。
四工夫论
二程在道学话语建构上的第四方面的贡献,集中在工夫论领域。我们知道,无论是道学还是广义的理学,都以学以成圣,由内圣以达外王为根本宗旨,并强调所学与道德践履实践相结合,②因此重视践履工夫是理学的特色所在。
学界已经注意到,明道与伊川的工夫论颇有不同:明道重视体认而伊川重视格物。当然,上述差异并不是绝对的。由下文可知,二人在工夫论上相同的主张也很多。
伊川的工夫论,可以概括为涵养与进学并进:具体表述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③。这里,伊川是主张以“主敬”来统摄涵养工夫,并以格物致知来统摄进学工夫的。不过,伊川似乎认为敬与致知之间还是一体的关系:不独在致知中始终需要保持诚确(即敬)的态度,而且主敬工夫也需要得到来自致知方面的支持:“或问进修之术何先,曰‘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④于伊川,正心诚意与主敬其实是一体之两面,而心之正、意之诚(敬)又首先在于有真知、在于明理(他又指出,保持诚敬的状态“则心便一……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由此,主敬与致知之间就不是不相干的两个工夫,而是水乳交融的一体关系。
陈来曾认为,“‘敬’是程颐提倡的主要修养方法……程颐则不遗余力地强调敬”,他所理解的“敬”既包括外在仪表的庄严,也包括内在心境的主一无适。①显然,伊川之主敬工夫实质是强调内与外相贯通。在对敬的强调上,我们可以看到二程工夫论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关系:明道更活,伊川更直。
值得注意的是,二程之强调“主敬”工夫,中心的关注点“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困扰宋明大多数理学家的‘思虑纷扰’的问题”。②明道与伊川对此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很值得我们进行细致的比较。
众所周知,明道对此问题的讨论系承接张载的书信而发,由于张载的来信提到的是“定性”,所以明道也以如何来“定性”作为回复。③其实,正如朱子后来所提到的,此处的“性”字表述为“心”字会更为合适。明道之回复即著名的《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④其要点可概括如下:
其一,心通内外、贯动静,心之定亦贯通动静,心之定指的是安定,而非不动。这里,明道论说的重心放在了破除认为心有内外之分与是内非外的认识上(往往是佛老的说法)。
其二,主张人应该效法天地之“普万物”,进而做到顺万事,具体就是要努力做到“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并批判了通过绝外物、除外诱的方式来定心的手段之无效。
其三,指出人不能定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受蔽而流于自私,自私则会远离自然,无法做到内外两忘。反之,则应该以公心应物而“无事”,明道称此为“明”的境界。
其四,指出定心之理想状态为喜怒发于应物之“适当”,即做到喜怒不出于己,而应该系于物(理)。明道以怒为例,具体说明如何以理(之是非)之怒而定心。
总之,明道定心的方法可以概括为空廓其心,动依于理而心无挂碍。这是其主张“与物同体”说的必然推论。
与明道相应,伊川对于如何定心问题也颇有思索:
吕与叔尝言,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曰:“此正如破屋中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其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①
闲邪存诚。闲邪则诚自存。如人有室,垣墙不修,不能防寇,寇从东来,逐之则复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二②人复至。不如修其垣墙,则寇自不至,故欲闲邪也。③
从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伊川在解决此问题上的不同思路:心要自主,“有主”说的是心的主体性或主导性、主宰性。对伊川而言,心有主是需要通过做工夫来培养实现的,培养的途径不外乎两端:一是主一或主敬,使心集中精神,长期保持一种恭敬、敬畏的状态;二是明理,通过格致工夫提高对天理的自觉性。显然,伊川所强调的心要有所主也是贯通动静的。伊川同样重视在应事之际“心有所主”的重要性:“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④伊川此论,与明道强调因循、强调自然明显不同,更强调有所作为,有所干涉的一面。
明道和伊川的定心说,与孟子的“不动心”,庄子和王弼、邵雍之主张无心以应物面对的是相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明道与庄子和王弼相近,而伊川与孟子相近。不过,明道之“定心”说与庄、王之说还是有根本区别:指导其定心说的,仍然是儒学的核心价值——大公说,天理说。
结语
二程无论是在理学史上的影响,还是在道学话语构建中的作用有目共睹。就近而言,杨时、谢良佐以及湖湘学派和道南学派为学工夫的确立,显然是受到了二程的深刻影响。上述二学派在促进朱子思想的成熟发展中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其在心性论及工夫论上的分歧也曾长期困扰朱子。有趣的是,朱子也正是在精研二程著作之下,才最终突破了上述困境,使自己的思想趋向定型。从长远说,二程之天理说、明道之识仁说、定性说、格致说对理学的影响可谓贯彻始终,并充当着道学与理学话语的主导。从这个意义说,二程是道学与理学当之无愧的建立者。
附注
①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②《宋明理学》,第69页。
①许多学者注意到了程颢与程颐之间思想的差别,本文对此也有所注意,对二人思想的差异处会有所提及。
②庞万里:《二程哲学体系》,北京航空航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在庞先生之前,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③二程之前的注《易》者,基本以之来阐释天道,而二程注《易》,则重在阐释人伦物理。
④“天理”一词由庄子首先使用,但是在《庄子》一书中,“天”的含义是自然、天然,“天理”即指“天然之理”,在庄子思想中,不存在一个实体化、本体化了的天的概念。在宋代,张载大量使用了这一概念,但气是张载理论体系的根本,天理仍然只是一个从属性的概念。从这个角度说,二程的天理观在具体内涵上有前所未有的原创性。
①分别见《二程语录·明道先生语一》,《诸儒鸣道集》卷二十九,第617页;《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十一》,《诸儒鸣道集》卷四十三,第930页。
②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③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传闻杂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24页。“天理”一词张载也使用过,但还是属于传统的用法。
①《二程语录·二程先生语二之二》,《诸儒鸣道集》卷二十一,第419页。
②《二程语录·二程先生语?(原书标为七,后改为八,当为六)》,《诸儒鸣道集》卷二十四,第517页。
③分别见《二程语录·二程先生语二之一》,《诸儒鸣道集》卷二十,第393、383页。
④《二程语录·明道先生语一》,《诸儒鸣道集》卷二十九,第586页。
⑤有趣的是,当今学者往往能注意到,二程之间,明道强调统体,而伊川强则调分别。
⑥《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十一·伊川杂录》,第914页。
①形上与形下的区分以及“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见于《易传》,但是在二程看来,《易传》所言仍然是形而下者。此外,道教和邵雍都早于二程提出了先天的概念,张载更是有“性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的说法,不过上述说法仍属于元气论、宇宙论范围,此是其与二程天理论的根本不同。
②《中庸》与《孟子》何先何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依照本文的逻辑,我们认为《中庸》中有部分内容是先于《孟子》的,性论即是其中之一。
①前贤曾总结古人对天的理解有主宰、自然、神秘、德性、义理诸方面。在《孟子》之前,人们对天的理解还没有德性和义理的因素。
②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①这一点,已经为张岱年先生所指出,此不赘述。
②《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十一·伊川杂录》,第927页。
③《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十四·畅潜道录》,第963页。
④《二程语录·二程先生语四》,《诸儒鸣道集》卷二十四,第485页。
①笔者曾经指出,“理一分殊”是儒学传统天人关系在宋代的新的表现方式。理是天的本质,而殊则以人为代表。
②《二程语录·二程先生语七》,《诸儒鸣道集》卷二十四,第517页。
③《二程语录·明道先生语一》,《诸儒鸣道集》卷二十九,第585页。
①吴震先生认为,“将‘仁’与‘生’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也许要数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见氏著《泰州学派研究》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此说不确。
②伊川同样强调生与仁的关联,如著名的谷种之喻。
①《二程语录·二程先生语五》,《诸儒鸣道集》卷二十五,第506—507页。
②《二程语录·二程先生语二之一》,《诸儒鸣道集》卷二十,第386页。
③陈来:《宋元明哲学史教程》,三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①《宋元明哲学史教程》,第105页。
②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二,《二程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20页。
③均见《二程语录·二程先生语十》,《诸儒鸣道集》卷二十八,第555页。按,本卷题注显示“不分二先生语”。
④《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十一》,《诸儒鸣道集》卷四十三,第918页。
①《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一之二》,《诸儒鸣道集》卷三十二,第648页。
②《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四之一》,《诸儒鸣道集》卷三十五,第769页。
③《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九》,第609页。
①《二程哲学体系》,第215页。
②陈老师即指出:是否有“践履功夫”是区别传统儒林文士与理学思想家的重要标准,见《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③《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四之二》,《诸儒鸣道集》卷三十六,第751页。
④同上。
①《宋明理学》,第104页。
②同上书,第107页。
③张载主张“心统性情”说,性之于张载来说,相当于心之体,但是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二程的共鸣。后来朱子虽然极力称赞张载的此说,却不会认为性即是心之体,因此才会认为所定的应该是心而非性。
④《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二·明道先生文二·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第460页。
①《二程语录一·二程先生语一》,《诸儒鸣道集》卷十九,第370页。
②通行本为“一”字。
③《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一之三》,《诸儒鸣道集》卷三十三,第682页。
④同上书,第681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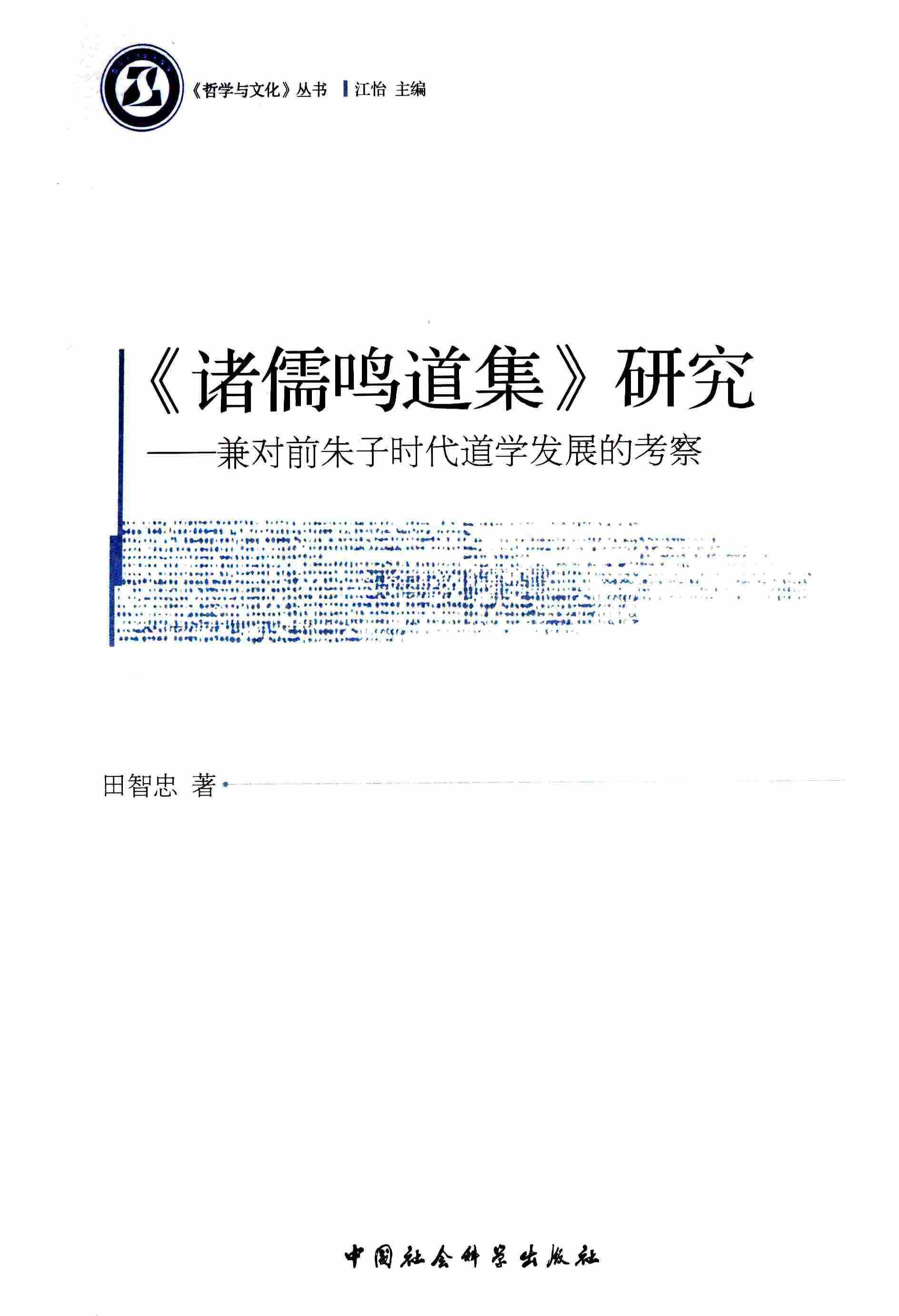
《《诸儒鸣道集》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内容包括:《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考、关于《诸儒鸣道集》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诸儒鸣道集》视野下的宋代儒学多元性研究、周敦颐与张载的道学话语构建、二程对道学话语的构建、谢良佐与杨时对道学话语的构建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