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周敦颐与张载的道学话语构建
| 内容出处: | 《《诸儒鸣道集》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5188 |
| 颗粒名称: | 第六章 周敦颐与张载的道学话语构建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18 |
| 页码: | 258-275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周敦颐与张载都关注天道和人道,构建了道学话语模式,周敦颐提出学以成圣理念,主张主静立人极,重视道德修养;张载则关注气本论和易学,强调实践和功夫。 |
| 关键词: | 周敦颐 张载 道学话语模式 |
内容
周敦颐与张载,其共性是“皆由言天道以及于人道、圣道”①,对天道的关注是二人立学的根基。学界对周、张二人的研究成果很多,本文只是关注他们在构建道学话语模式上所做出的贡献。
一周敦颐对道学话语模式的构建
冯友兰先生指出,周敦颐对于道学的主题,都已经提出来了,②而且是首先提出来的。比如希贤希圣之学、比如孔颜乐处、道德性命之说等等。这也是其后来能被推为“道学宗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认为,周敦颐对于道学话语模式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道学思潮中首先提出学以成圣的理念,并首先对圣人的理想人格予以具体的描画;其次,在整合先秦文献并接续先秦“性与天道”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实现了儒学心性概念的本体化,从而重建了儒学的形上体系;再次,提出主静立人极之修养论,首次提出了对“功夫”的关注,从而也奠定了道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不过,在周敦颐那里,“理”范畴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同时周的思想仍不脱佛老影响的痕迹。这也是后人对其思想的主要诟病之点。
重提学以成圣的理念
周敦颐在道学话语构建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道学思潮中首先提出学以成圣的理念。这颇有扭转风气之功。
本来,在先秦儒学中本有“人人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更有“舍我其谁”的孟子出现。但是随着汉唐儒士对圣人的空前神化以及对儒学典籍的章句化,这一说法就基本上再也无人提及过。在道学思潮中,周敦颐率先提出了“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的口号,并回答了何为圣,如何成圣的问题。这就为道学从汉唐儒学的华丽转身吹响了进军号。这一转身的根本,就是把“自明其德”重新置于中心地位,突出了德性较之于知识的优先性,人较之于书本的优先性。这一转身影响之深远,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从先秦到汉唐,“何为圣”始终是一个不可能被回答的问题——圣人只是存身于常人不可知、不可企及之域,是与“有”相对的另一个世界,普通人成圣更是不可能的。
在《通书》中,周敦颐则对此有明确的回答:“圣,诚而已矣”、“诚、神、几,曰圣人”、“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这就对“何为圣”问题给出了正面的、肯定性的回答。那么,何以周敦颐就敢于回答“何为圣”的问题?他的基本思路就是以天之道来定位人之德,进而认为能够做到继天道而立人极者,就是圣人。既然天之道是可知的,那么圣人之道自然不应该有神秘可言。在他看来,“诚”和“仁义中正”都是人从天继承来的“极”。任何人,只要于此做得纯粹,就是圣人。由此,“圣人”之于常人不再神秘,而成圣之道也不再艰难。①
周敦颐还强调,成圣是人最高的“目的”,一切只能围绕这一目的展开,成为其工具,才有意义: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母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
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②
提到“文以载道”,大家往往强调二者一体的那一面,但是周敦颐此文,其中心则在于强调“道”是“目的”,而“文”只是“载道”的工具。在他看来,如果以“文”本身为追求的根本目的,只能流于奇技淫巧之流。后来道学所强调的圣学与俗学之辨、德性与闻见之辨,小程子强调的学者有三歧、之撰写《颜子所好何学论》,①都是对周敦颐此说的进一步引申。许多人已经指出,儒学发展到汉唐时代,有单纯学术化、对象化的倾向(章句化、训诂化)。道学重新强调了为学与道德修养的一体关系,而把道德修养置于突出的地位,这是从周敦颐开始的。
在对“何为圣”的说明中,周敦颐还特别强调了一个“乐”字——其实就是人内在精神的受用和安立。此后,“孔颜乐处”这一境界论话题就成了道学所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而追问孔颜之乐所乐何事,也成为道学中的一大公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周敦颐自己就有明确的回答:颜子乐的就是“天地间有至贵至爱”者,是与天地为一的胸襟与气象。后来朱子更是明确点出,颜子所乐者道也,是天理也,是见“道”才使得颜子感到其心泰然,因而处富贵贫贱如一。显然,周敦颐通过对“孔颜乐处”的渲染,回答了圣学的理想人格应该如何的问题。自周敦颐之后,“境界论”成为道学的又一主要内容,儒学逐渐突出了作为内圣之学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周敦颐在此指示出了后来道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心性概念的本体化
先秦儒学本来有讲“性与天道”的传统,但是各个文献之间并没有实现统合:“《易传》所关注者,要在‘天道’的系统;《庸》、《孟》所重,显在‘心性’的系统。”②当然,这不是说《易传》就不讲人道,《庸》、《孟》就不讲天道,而是说它们各有侧重:《易传》首重天道,而《庸》、《孟》的心性概念都还没有被提升到本体的层面上。虽然大家也经常提到《庸》、《孟》中的这两章:“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哀公问政章》),“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但是这里“诚”还只是被视为是天的属性,而没有被本体化,被独立化。
《宋元学案》两次提到,“诚”是周敦颐立学之本,更是《通书》的中心。显然,较之于《庸》、《孟》而言,“诚”在《通书》中居于了核心的地位。《通书》以“诚”开篇,而且视之为“圣人之本”。不独如此,周敦颐更是通过《易传》与《中庸》的统合,赋予了“诚”以心之本体的地位,从而拉开了道学将传统儒学心性概念本体化的序幕: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干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①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②
诚之源在天,所谓“诚者天之道也”。但是对周敦颐而言,重点还是在强调这个源自天的诚,是继天之善而又成人之性者,它是人之本,是人的性命之源。同时,“诚”还是沟通天与人的、天之阴阳与人之仁义的枢纽,是人之所以能够继天而立极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诚”就是人的心性本体(前贤有“本体化的普遍心性论”之说),是人的本质。
此外,相对于张载的“心统性情”论,周敦颐则提出了以“诚”为本、“诚、神、几”一体的“心论”体系:此三者之间,“诚”是心之体(本人呢状态),“神”是心之动(用),“几”则通于有无动静之间:
诚无为,几善恶。③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④
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①
“诚神几”的基本结构,显然是从《易传》发展而来的,与后来成为道学核心话题之一的、从《中庸》发展出来的心之“已发未发”论大致相当,却未提到性。但是,与后来主静者往往强调心之“大本”不同,周敦颐特别强调“思”这个“心之用”的重要性:
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②
周敦颐认为“思者,圣功之本”,显然是看到了在“寂然不动”处无法做功夫这一事实。从这一点看,周敦颐与后来所有在功夫论上一味地强调主静者,均有所不同。
主静立人极的修养论
周敦颐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③这里的“人极”,更应该指人的主体性,是人可以与天地参的那个基点。周敦颐强调,人之“主静立人极”在于法天:天之无极而太极,是人之主静立极的根据;天之太极内在包含着阴阳动静,而人之主静之极也内在包含着仁义和“诚”、“几”;天以“静阴”为体,“动阳”为用,④人也以诚之静为体,以几之动为用。天之极也就是人的本,此即《易传》中所强调的天人合德。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周敦颐之主张“主静立人极”,完整的说法是“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这不能被简单化约为“主静立人极”。如果我们看不到周子对“中正仁义”四字的强调,那么对其思想的理解就是片面的。
于周敦颐,主静之静,即相当于立极之极: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水阴根阳,火阳根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①
天之极为太极,混迹于互根互藏的阴阳有无之间,阴阳五行之通体为太极;人之极则为心,也应该静而无静,通于有无(几)之间,并非不动不静。后来二程将周子的主静改为主敬,担心渲染主静会有恶动的流弊,也是担心后人会曲解周的主静思想。
人之主静立极,体现为诚其心,通其神。这又要靠具体的心性修养功夫来实现:那就是“主一”、“无欲”:
“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②
《语录》《濂溪通书》与通行本《通书》相比,少一“曰”字(《通书》作:“曰:‘有要乎?’”)。我们认为,《语录》更接近周敦颐的原本:因为在“圣可学乎”和“请闻焉”之前都没有“曰”字,则在“有要乎”之前没有“曰”字,这是很自然的。
周敦颐强调,“一者无欲也”,又强调“无欲故静”,据此则“一”、“无欲”和“主静”是异名同谓的关系。
对于周敦颐所主张的“无欲”,杨柱才先生结合周敦颐的《养心庭说》,指出周并不主张“寡欲”,而是强调“盖寡焉以至于无”,认为这是比较严厉的禁欲主张(不一定主张彻底的禁欲)。不过,周敦颐之强调“无欲”,并非只是有消极的意义:在强调天人合德的基本思路下,人无私欲才能与天为一,进而顺天之诚而立己极、顺天之阴阳而立己之仁义,此所谓“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显然,周敦颐之主张“无欲”,只是一个起点而非终点。从这方面说,周之主张“无欲”,与佛老之宣扬的“无欲”,是有根本不同的,也与后来道学中纯粹主张静坐者显有不同。
总之,周敦颐较之于此前的儒者而言,其学术有重大的改变,这一改变的方向与道学后来的发展不谋而合。从这一点上来说,周敦颐无疑是道学思潮的重要开创者。
二张载对道学话语模式的构建
较之于周敦颐,张载对于天道的诠释、对于佛老之态度,对于儒学心性论、功夫论、境界论的说明都更为明确。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张载的研究“除了偏重于强调其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外,主要是忽视了张载是一个儒学思想家、道学思想家,忽视或贬低张载在心性论、功夫论、境界论上对新儒家哲学思想所作的贡献”①,一句话,忽视了张载在一些自己所关注的、在道学中真正重要的核心问题上的贡献,此诚为一个大偏失。另外,张载的思想体系较之周敦颐而言更为庞杂,后人对其研究也往往会因为角度的不同而导致“研究经学的不谈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的不讲经学”②。再次,我们之所以忽略张载所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在于我们忽视了张载思想的内在逻辑,把一些外在的尤其是现代人才有的东西强加给张载。从这个方面来说,关注张载在道学话语构建上的贡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上述弊端。
张载在建构道学话语上的贡献体现为:其一,针对佛老的、以气为本的太和观;其二,民胞物与的大心观;其三,性气相合的人性论;其四,诚明两进的修养论;其五,即闻见而趋德性的修养论。
针对佛老的、以气为本的太和观
我们认为,从整体逻辑上看,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之中心点,在于提出了一个根本不同于佛老的,对于这个世界的整体看法,其基本结论就是:“太和”。这也是张载在道学话语构建上非常重要的理念。
张载之提出“太和观”,显然系针对佛老的世界观而发,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当然张载对佛老思想的理解,也包含有一定的曲解成分,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张载认为,老学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徇生执有”,追求人身体的不“化”;二是认为“虚能生气”(实质是主张有生于无),把虚和气当成是完全异质之物。佛学存在的问题也有两个:一是主张寂灭,即认为万物灭后即一无所有(这是张载自己对佛家“寂灭”的理解);二是认为万物为幻化,一切皆空。张载认为,佛家的这两种说法同样会导致物与虚的两不相资。在他看来,佛老二者的具体观点虽然不同,但是其共性都是割裂了虚与气、有与无、体与用之间的联系,而张载特别强调世界恒动的绝对性,主张“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的一体关系。
张载强调,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舞台(或是大流行、大熔炉、大洪流):舞台上的主角只有一个——气(张载明确排除了在此大流行中另有一个主角叫做“无”的可能性),二者的关系就是气布满于虚空(不存在无气的虚空),气在虚空中聚散、运动不息。张载强调,独自聚散于虚空中的气之特性就是“一物两体”:“一”是指气这个主角的整体性和唯一性——自根自本,也无有无、生灭之可言;“两”是说气内在地包含有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属性。在此大“舞台”上,一切的一切都在不得已当中变化着:“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而“万物”也不能不最终“散而为太虚”。这一整体相状张载谓之野马、絪缊,谓之“太和”,此变动不居的历程张载则谓之“道”。张载特别强调“和”,“仇必和而解”是其哲学的整体基调。
张载还特别强调此大流行的“一本”性:现实中万殊之相状虽多,但其本源则一,张载皆以“吾体”视之。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张载提出“虚空即气”、“太虚即气”的本意所在:
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
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隠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
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故圣人语性与天道之极,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诸子浅妄,有有无之分,非穷理之学也。①
学界关于张载的“虚空即气”争论颇多。我们认为,在对张载的含混说法予以解读上,今人应该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既不能把现代人才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加到古人身上,也不能把古人的简单思维复杂化,具体到“虚空即气”,尤其不能对它的解读引向张载本人所批评的观点。有时候,在对古人思想的诠释上,适度地减担子更有助于把问题说清楚。②应该说,把“太虚”理解为一种“微观粒子”或者也是一种形式的“气”的说法,就有以今释古的嫌疑。
仅就概念而论,把太虚与(本然之)气直接等同的说法也难以得到传统文献的支持。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上文中的比喻,把太虚喻为舞台,把气视为主角。那么,张载的本意,无非就是强调主角与舞台的不离这一点:他的“无无”更是点出不存在没有演员的空舞台。换用学术语言说就是:一方面,不存在离气而独立的虚空,虚空之中无处无气;另一方面,也不存在独立于虚空之外的气,离开虚空则气无处顿放。这里,张载明确地否认了虚能生气的可能性,同时也否定了虚无穷、气有限的可能性。相对于把虚能生气理解为时间上有前后关系的生成论的说法,张载的说法属于本体论的说法。
回到这三段文字,其所论说的中心是强调一本之流行:看似有无、隐显、神化、性命,聚散、出入、形不形有不同,看似冰凝水释有不同,但其实都只是气在“大舞台”上的不同形象而已,这就是一本。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载无论是“吾体”的概念,还是其提出“大心”观,还是提出《西铭》,都在明确强调“万物一体”的理念,也强烈释放出张载视整个世界为“一本”的想法。这一想法也是儒学乃至传统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需要认真体会。后来,王阳明曾明确提出,他之所以强调“心外无物”的观点,针对的是那种“析心与理为二”的,将人与世界完全对象化、二分化的观点,进而强调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一体关系,强调自然(对人呈现)的意义化。我们认为,王阳明考虑问题的视角,其实也是张载的视角,甚至是,被阳明视为是“析心与理为二”之代表的朱熹,也在主张“理一分殊”模式下的“天人一本”。
张载又指出,在此大流行中,气这个主角所呈现出的具体形式又颇为不同:有以可见的形式存在者(散殊可象者,张载名之为气,其实称之为客形更为合适),也有以不可见的形式存在者(清通而不可象者,张载名之为神,不妨名之为本然之气),这就像自然界同时有冰又有水一样。可见者即为“显”,而不可见者则为“隐”。“隐者”会因为气之聚而变成“显者”,而“显者”也会因为气之散而变为“隐者”,因为二者是一本的。对于气,只能说其有隐显之转化,而不能说其存在有无之分别:
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①
张载认为,可见者之聚之散,都是短暂的,此谓之客形;不可见者是常态,此谓之气之本体。显然,在此大流行中,任何事物都注定要转变成他者,或明显,或隐微,或剧烈,或潜在:一切都只是这个大流行中气这个主角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罢了,但是这个主角绝对不会谢幕,也不会躲在幕后遥控几个木偶来演出(如佛家所说的,有真际,又有幻化的万物),但他却是又在不停地变换着角色。这里,张载虽然是以客形、糟粕来称谓天地间的法象万形,但是这并没有贬义。张载反对佛家以山河大地为见病的说法,更反对把虚与气视为二物的“体用殊绝”的说法,他会重蹈佛家的覆辙。
民胞物与的大心观
继对天的说明之后,张载提出了作为人之为人所应该持有的态度,这是他在道学话语构建上的第二个贡献:提出民胞物与的大心观。在强调世界一本的前提下,张载进而又提出天人之一本关系:
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①
天从太虚而来,道由气化而显,而太虚之“至静无感”与气之絪缊变化都是性(天地之性)的体现,性与知觉的更进一步结合,就是心。由此,人之本即在于天:“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②此之谓一本。在这个意义上,人只要不自小其心,就能感到可与天地并立,而又息息相通的一体感,进而找到自己在天地视域中的全新定位。这也是张载在《西铭》篇中着力要突出的意思。对张载来说,作天地之民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有与天地一体的胸襟之余,尽到自己做天民所应尽的本分就可以了(在张载看来,天民的本分就是尽其人道):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③
于张载,上述这些看似普通的“不同”行为,在天地视野中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强调天人一体,并不以否定人的特殊性(尽其分)为前提,而恰恰是以人之殊性的充分成就(实现)为前提的。这里,每个人的“分”似有不同,但其做为天命的通性则是一致的,此之谓“一本”基础上的多元。
后来小程子和朱子都很敏锐地注意到,张载所宣扬民胞物与(有次等中的一体),与墨家主张无差别之兼爱(无差别的同一),有根本的不同。当然,后来朱子把张载此处与墨学的不同概括为“理一分殊”,这却未必能契合张载的本意:张载在这里确实有对“一与殊”问题的关照,但是这里作为“一”的应该是“气”而非“理”,作为“殊”的应该是“形”而非“物理”。我们不妨把张载的世界观概括为“气一分殊”论,以区别示。
张载的大心观也决定了其对待生死问题的态度。张载生死观的中心即“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此即儒家传统的安时处顺态度。但是,张载对“此”的说明有自己独特的逻辑性:儒家传统之主张安时处顺,突出的是天命的不可抗拒性,而张载之强调安时处顺,突出的是大化流行的死而不亡和“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的大生命观,有着浓厚的境界论成份。在此大生命观下,肉体的消亡只是“吾大体”之聚之散而已,意味着从一己的客形、寄体形式回复到“吾大体”的本然状态,颇有回家的意味。与此相反,人之“大生命”则与天地神化直接同流,是不息的。在这里,张载通过强调大我和小我之辨,对生死问题提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解决方案。张载尤其强调,顺化代表着一种人生智慧:“天之化也运诸气,人之化也顺夫时。非气非时则化之名何有?化之实何施?《中庸》曰‘至诚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阴阳,与天地同流而无不通也。”①于张载,生时之顺化与面对死亡的顺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张载对生死的态度在二程及朱子那里都得到了回应:二程似乎认为张载的生死观表现为“既屈之气,复为方伸之气”②,即认为张载在抨击佛教的轮回学说之际,仍然不脱“大轮回”的影子:“方伸的‘这个’气”,依然还是“既屈的‘那个’气”,始终只是那一个气的循环。朱子亦承袭二程之说,进一步把张载的说法归纳为“形溃反原”说:“横渠说‘形溃反原’,以为人生得此个物事,既死,此个物事却复归大原去,又别从里面抽出来生人。如一块黄泥,既把来做个弹子了,却依前归一块里面去,又做个弹子出来。伊川便说是‘不必以既屈之气为方伸之气’,若以圣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之语观之,则伊川之说为是。盖人死则气散,其生也,又是从大原里面发出来(叶夔孙录)。”③我们认为,二程与朱子对张载生死观的解读恐怕都不符合张载的本意。对于张载来说,无论是“既屈之气”和“方伸之气”之间,还是新旧客形之间,只是同源而已,并不强调在它们之间有直接的同一联系。其实,朱子“盖人死则气散,其生也,又是从大原里面发出来”的说法,其实也正是张载所要表达的意思。
张载对于人心,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心统性情:
张子曰:心,统性情者也。
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
发于性则见于情,发于情则见于色,以类而应也。①
张载“心统性情”是说法,在朱子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但是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并不特别关注性情的问题,②也没有对此说法予以特别强调。
性气③相合的人性论
杨立华君认为:“张载对人性问题的思考,在道学话语的建构中具有组建性的作用……并以此规定了宋明道学有关人性问题的思考及讨论的基本架构”④,这一说法并不过分。人性论无疑是张载在道学话语建构上非常重要的贡献。
学界多认为,张载人性论是二元的,如张岱年先生指出:“北宋时,关于人性,又有一种新说,与以前的性论都大不相同,即是性两元论……此派的理论,更有一特点,即其人性论皆是从其宇宙论推衍出来的,不仅就性论性,更向宇宙论寻求根据……性两元论,创始于张载,精炼于二程,大成于朱子。”⑤但是,关于张载的人性论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学界目前还存在着争论。我们则认为,在张载那里,就根本性而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地位并不是对等的,毋宁说体现为一种本末的关系,是一本而非二本的。但是就现实的人而论,气质之性则是决定着人的真实人性的直接因素,或者说是决定性因素,需要分别看待。
我们认为,张载是在“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框架下来讨论人“性”问题的:人性虽源自于天①,但是二者却并非直接的同一。现实之人性还要受到形、气的限制。讨论人性问题,必须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
天地之性是张载整个“性论”的起点、是“本”。所谓天地之性,即是气之本体在大化流行中所显现出的性,即是它的自体性:神化、清通,感应、湛一,通有无、兼隐显,参而不偏,本身无所谓变易等等。天地之性先在于人,因此不能被直接称为“人之性”。这也就是张载所说的“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的意思。虽然如此,但是天地之性又构成了人性当中虽然隐而不彰,却又是本质性的内核,可谓是人性的本质。与之相对,气质之性则是因形而后方有之性:表现为攻取、刚柔、缓急、才与不才等,而攻取之性可能导致人的恶行。气质之性因形而后才有,有形则有碍,有形则有偏,乃至出现与天地之性相背反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张载主张:“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②,他甚至有时直接以“气质”或“气”称之。
关于张载的人性论,学界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张载所说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究竟是一个性,还是有两个性。最先挑起这个问题的是朱子。朱子基于其“理一分殊”的一贯性思路,把气质之性视为是天地之性(他认为即是理)在气上的具体呈现形式,就相当于混入了泥土的之后水。总之,朱子认为性只有一个,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不是有两个性。朱子据此展开了对张载之性论的批判,认为张载的性论有二本之嫌。我们认为,这里所反映出的是张载与朱子在思想上的根本区别:较之于朱子的“理一分殊”(一和殊都是理),张载则主张“气一形殊”:本然之气及其性(天地之性)为一(实际表现为一物两体),而万物之形及万物之气质之性为殊。在这个意义上,张载所主张的性论仍然是一元的:形是本然之气的“客”,而气质之性也是天地之性的“客”(暂时的寄体之所)。具体就人性而言,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都只是构成人之现实人性的两大因素,但是张载显然认为,只有天地之性才是人性的本质,才代表着人性之应然和必然。就此而言,我们似乎不能以二元论来看待张载的人性论。
于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张力:人的行为或有可能为天地之性所主导,也有可能受气质之性所支配。虽然说“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①,但是人在性尚未成(实现)之前,他的行为选择完全有被气质之性主导的可能性:“德不能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②如气质之性一旦反客为主,成为人行为的主导,那么人与天相通的类本质也就随之而丧失了。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现实行为就是受气质之性支配的。由此,张载提出了“成性”的概念。这就涉及了张载诚明两进的修养论。
诚明两进的修养论
在一定程度上,张载的“成性”概念是对先秦“尽性”理念的继承:孟子即认为,天赋予人的只是善端,但人为善的可能性却是人之为人的特质,孟子称之为人的性。同时,孟子也强调人还需要做扩充此善端的功夫,此之谓尽性。与此相类似,张载也强调要“成性”。张载所说的“成性”,首先意味着人需要通过心性修养的功夫以变化气质,超越对人行为的现实影响,进而使得人原本与天相通的潜在本性充分呈现,成为支配人的完全主导,这可以谓之“负的功夫”。此外,张载的“成性”的修养功夫还包括正面的穷理致知等。此一正一负的修养功夫相互互补,用张载自己的说法,就是自诚而明与自明而诚之修养功夫的良性互补:
自明诚,由穷理而尽性也;自诚明,由尽性而穷理也。③
释氏……乃诚而恶明者也。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④
自明诚,即由明理而后尽性;自诚明,即由尽性而后明理。张载显然认为,明理与尽性之间不是单向的关系,而是相互蕴涵、交相促进的关系:明可以促进诚,诚也可以助长明。于张载,有诚而无明是佛学的弊端,有明而无诚则是俗儒(沉迷于外在之物,往而不返)的弊端,只有诚明两进才是真儒的本色。在《横渠语录》(即今中华书局本《张载集》中的《张子语录》)中,张载对明与诚、性与气、习的关系又有详细的说明:
明者所学也。明何以谓之学?明者言所见也。大凡宽偏者,是所禀之气也。气者,自万物散殊时各有所得;习者,自包(胞)胎中以至孩婴时,皆是习也。及其长而有所立,自所学者方谓之学。性(田按,指天地之性)则分明在外,故曰:气其一物尔。气(田按,指气质或气质之性)者在性、习之间。性,犹有气之恶者为病,气又有习以害之,此所以要鞭后至于齐,强学以胜其气、习。其间则更有缓急精粗,则是人之性(之天地之性)则[虽]同,气则[有异]……①性则宽偏昏明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于习之异,斯远矣。虽则气之禀偏者,未至于成性时则暂或有暴发,然而所学则却是正,当其如此,则渐宽容。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气与习……
须知自诚明与[自]明诚者有异。自诚明者,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也,谓先自其性理会来,以至行[穷]理;自明诚者,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也,谓先从学问理[会],以推达于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为学而知者,某今亦窃希于明诚,所以勉勉安于不退……
自明诚者,须是要穷理,穷即是学也,所观所求,皆学也。②
张载此文以此前儒学中少见的下定义的方式,将明与诚、性、气、习、学这些概念之关系梳理得清晰明白。对他而言,只有天地之性才能成为人之本性(本质),而气和习两者都会对人之性带来不同的影响(张载更多强调其负面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张载明确强调,明或者学也是“诚”(即变化气质功夫)的重要内容,学(穷理)是为了变化气质,这也点出了诚与明之间的相互蕴涵关系。张载诚与明两进的功夫修养论与后来二程与朱子所主张的涵养与致知两进的功夫论是一致的,较之于后来湖湘学派与杨时一派的功夫论,张载的功夫论更显全面和圆通。
即闻见而趋德性的修养论
张载在构建道学话语上的开创性贡献,还包括对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分: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①
准确地说,“德性之知”不应该算是一种知识,而应该是一种与天同体的视界、意识与是境界,它与儒家的工夫修养论密切相关。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德性之知源自人对天地之性的体认,源自人在本质上与天地参的潜在大我。与之相对,闻见之知则是随人的耳目与外物相接触而后有的知识,是对有形之物的认知。我们不应该把张载对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划分,与当代西方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划分做牵强比附,更不能把张载的这一思想限定在认识论的领域,②更要注意到张载做出这一划分在功夫修养论上的意义。张载认为,人心不应该被束缚在对物的闻见上,这样只会自小其心。心不但要见物,更要见天,要能体物不遗,要知性(天地之性)知天,要与天地参,要突出一种要“有我”的,体验化、感受性的状态,而非认识的,对象化的状态。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张载“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的说法?从张载自己的逻辑看,德性所知是基于气之本然的认识,而闻见之知是对气之“客形”的认识,德性所知先在于闻见之知,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
另一方面,张载同时也强调,虽然耳目在一定条件下是人大其心的障碍,但是耳目的作用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耳目虽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为启之之要也。①
如果心不被闻见之知所束缚的话,反倒可以凭借耳目闻见之穷理致知的功能以实现合内外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讲,张载虽然推崇德性之知,却丝毫不贬损闻见之知(他反对的仅仅是以闻见之知梏其心这一点),而是主张即闻见而跨越闻见,即闻见而趋德性。他主张广泛的格物穷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张载推崇德性之知的理念,是其提倡民胞物与之大心观的必然结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唐儒学流于之“俗学”的反动。在这一点上,他与周敦颐之提出文道之辨、与二程强调颜子之学迥异于“俗儒”之点,是异曲同工的。我们发现,在周、张、二程那里,尊德性以及围绕此而展开的成圣功夫,都被置于了突出的地位,这也成为道学之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关键之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周张二人视为道学的开创者,并不为过。
一周敦颐对道学话语模式的构建
冯友兰先生指出,周敦颐对于道学的主题,都已经提出来了,②而且是首先提出来的。比如希贤希圣之学、比如孔颜乐处、道德性命之说等等。这也是其后来能被推为“道学宗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认为,周敦颐对于道学话语模式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道学思潮中首先提出学以成圣的理念,并首先对圣人的理想人格予以具体的描画;其次,在整合先秦文献并接续先秦“性与天道”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实现了儒学心性概念的本体化,从而重建了儒学的形上体系;再次,提出主静立人极之修养论,首次提出了对“功夫”的关注,从而也奠定了道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不过,在周敦颐那里,“理”范畴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同时周的思想仍不脱佛老影响的痕迹。这也是后人对其思想的主要诟病之点。
重提学以成圣的理念
周敦颐在道学话语构建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道学思潮中首先提出学以成圣的理念。这颇有扭转风气之功。
本来,在先秦儒学中本有“人人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更有“舍我其谁”的孟子出现。但是随着汉唐儒士对圣人的空前神化以及对儒学典籍的章句化,这一说法就基本上再也无人提及过。在道学思潮中,周敦颐率先提出了“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的口号,并回答了何为圣,如何成圣的问题。这就为道学从汉唐儒学的华丽转身吹响了进军号。这一转身的根本,就是把“自明其德”重新置于中心地位,突出了德性较之于知识的优先性,人较之于书本的优先性。这一转身影响之深远,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从先秦到汉唐,“何为圣”始终是一个不可能被回答的问题——圣人只是存身于常人不可知、不可企及之域,是与“有”相对的另一个世界,普通人成圣更是不可能的。
在《通书》中,周敦颐则对此有明确的回答:“圣,诚而已矣”、“诚、神、几,曰圣人”、“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这就对“何为圣”问题给出了正面的、肯定性的回答。那么,何以周敦颐就敢于回答“何为圣”的问题?他的基本思路就是以天之道来定位人之德,进而认为能够做到继天道而立人极者,就是圣人。既然天之道是可知的,那么圣人之道自然不应该有神秘可言。在他看来,“诚”和“仁义中正”都是人从天继承来的“极”。任何人,只要于此做得纯粹,就是圣人。由此,“圣人”之于常人不再神秘,而成圣之道也不再艰难。①
周敦颐还强调,成圣是人最高的“目的”,一切只能围绕这一目的展开,成为其工具,才有意义: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母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
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②
提到“文以载道”,大家往往强调二者一体的那一面,但是周敦颐此文,其中心则在于强调“道”是“目的”,而“文”只是“载道”的工具。在他看来,如果以“文”本身为追求的根本目的,只能流于奇技淫巧之流。后来道学所强调的圣学与俗学之辨、德性与闻见之辨,小程子强调的学者有三歧、之撰写《颜子所好何学论》,①都是对周敦颐此说的进一步引申。许多人已经指出,儒学发展到汉唐时代,有单纯学术化、对象化的倾向(章句化、训诂化)。道学重新强调了为学与道德修养的一体关系,而把道德修养置于突出的地位,这是从周敦颐开始的。
在对“何为圣”的说明中,周敦颐还特别强调了一个“乐”字——其实就是人内在精神的受用和安立。此后,“孔颜乐处”这一境界论话题就成了道学所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而追问孔颜之乐所乐何事,也成为道学中的一大公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周敦颐自己就有明确的回答:颜子乐的就是“天地间有至贵至爱”者,是与天地为一的胸襟与气象。后来朱子更是明确点出,颜子所乐者道也,是天理也,是见“道”才使得颜子感到其心泰然,因而处富贵贫贱如一。显然,周敦颐通过对“孔颜乐处”的渲染,回答了圣学的理想人格应该如何的问题。自周敦颐之后,“境界论”成为道学的又一主要内容,儒学逐渐突出了作为内圣之学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周敦颐在此指示出了后来道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心性概念的本体化
先秦儒学本来有讲“性与天道”的传统,但是各个文献之间并没有实现统合:“《易传》所关注者,要在‘天道’的系统;《庸》、《孟》所重,显在‘心性’的系统。”②当然,这不是说《易传》就不讲人道,《庸》、《孟》就不讲天道,而是说它们各有侧重:《易传》首重天道,而《庸》、《孟》的心性概念都还没有被提升到本体的层面上。虽然大家也经常提到《庸》、《孟》中的这两章:“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哀公问政章》),“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但是这里“诚”还只是被视为是天的属性,而没有被本体化,被独立化。
《宋元学案》两次提到,“诚”是周敦颐立学之本,更是《通书》的中心。显然,较之于《庸》、《孟》而言,“诚”在《通书》中居于了核心的地位。《通书》以“诚”开篇,而且视之为“圣人之本”。不独如此,周敦颐更是通过《易传》与《中庸》的统合,赋予了“诚”以心之本体的地位,从而拉开了道学将传统儒学心性概念本体化的序幕: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干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①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②
诚之源在天,所谓“诚者天之道也”。但是对周敦颐而言,重点还是在强调这个源自天的诚,是继天之善而又成人之性者,它是人之本,是人的性命之源。同时,“诚”还是沟通天与人的、天之阴阳与人之仁义的枢纽,是人之所以能够继天而立极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诚”就是人的心性本体(前贤有“本体化的普遍心性论”之说),是人的本质。
此外,相对于张载的“心统性情”论,周敦颐则提出了以“诚”为本、“诚、神、几”一体的“心论”体系:此三者之间,“诚”是心之体(本人呢状态),“神”是心之动(用),“几”则通于有无动静之间:
诚无为,几善恶。③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④
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①
“诚神几”的基本结构,显然是从《易传》发展而来的,与后来成为道学核心话题之一的、从《中庸》发展出来的心之“已发未发”论大致相当,却未提到性。但是,与后来主静者往往强调心之“大本”不同,周敦颐特别强调“思”这个“心之用”的重要性:
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②
周敦颐认为“思者,圣功之本”,显然是看到了在“寂然不动”处无法做功夫这一事实。从这一点看,周敦颐与后来所有在功夫论上一味地强调主静者,均有所不同。
主静立人极的修养论
周敦颐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③这里的“人极”,更应该指人的主体性,是人可以与天地参的那个基点。周敦颐强调,人之“主静立人极”在于法天:天之无极而太极,是人之主静立极的根据;天之太极内在包含着阴阳动静,而人之主静之极也内在包含着仁义和“诚”、“几”;天以“静阴”为体,“动阳”为用,④人也以诚之静为体,以几之动为用。天之极也就是人的本,此即《易传》中所强调的天人合德。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周敦颐之主张“主静立人极”,完整的说法是“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这不能被简单化约为“主静立人极”。如果我们看不到周子对“中正仁义”四字的强调,那么对其思想的理解就是片面的。
于周敦颐,主静之静,即相当于立极之极: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水阴根阳,火阳根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①
天之极为太极,混迹于互根互藏的阴阳有无之间,阴阳五行之通体为太极;人之极则为心,也应该静而无静,通于有无(几)之间,并非不动不静。后来二程将周子的主静改为主敬,担心渲染主静会有恶动的流弊,也是担心后人会曲解周的主静思想。
人之主静立极,体现为诚其心,通其神。这又要靠具体的心性修养功夫来实现:那就是“主一”、“无欲”:
“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②
《语录》《濂溪通书》与通行本《通书》相比,少一“曰”字(《通书》作:“曰:‘有要乎?’”)。我们认为,《语录》更接近周敦颐的原本:因为在“圣可学乎”和“请闻焉”之前都没有“曰”字,则在“有要乎”之前没有“曰”字,这是很自然的。
周敦颐强调,“一者无欲也”,又强调“无欲故静”,据此则“一”、“无欲”和“主静”是异名同谓的关系。
对于周敦颐所主张的“无欲”,杨柱才先生结合周敦颐的《养心庭说》,指出周并不主张“寡欲”,而是强调“盖寡焉以至于无”,认为这是比较严厉的禁欲主张(不一定主张彻底的禁欲)。不过,周敦颐之强调“无欲”,并非只是有消极的意义:在强调天人合德的基本思路下,人无私欲才能与天为一,进而顺天之诚而立己极、顺天之阴阳而立己之仁义,此所谓“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显然,周敦颐之主张“无欲”,只是一个起点而非终点。从这方面说,周之主张“无欲”,与佛老之宣扬的“无欲”,是有根本不同的,也与后来道学中纯粹主张静坐者显有不同。
总之,周敦颐较之于此前的儒者而言,其学术有重大的改变,这一改变的方向与道学后来的发展不谋而合。从这一点上来说,周敦颐无疑是道学思潮的重要开创者。
二张载对道学话语模式的构建
较之于周敦颐,张载对于天道的诠释、对于佛老之态度,对于儒学心性论、功夫论、境界论的说明都更为明确。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张载的研究“除了偏重于强调其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外,主要是忽视了张载是一个儒学思想家、道学思想家,忽视或贬低张载在心性论、功夫论、境界论上对新儒家哲学思想所作的贡献”①,一句话,忽视了张载在一些自己所关注的、在道学中真正重要的核心问题上的贡献,此诚为一个大偏失。另外,张载的思想体系较之周敦颐而言更为庞杂,后人对其研究也往往会因为角度的不同而导致“研究经学的不谈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的不讲经学”②。再次,我们之所以忽略张载所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在于我们忽视了张载思想的内在逻辑,把一些外在的尤其是现代人才有的东西强加给张载。从这个方面来说,关注张载在道学话语构建上的贡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上述弊端。
张载在建构道学话语上的贡献体现为:其一,针对佛老的、以气为本的太和观;其二,民胞物与的大心观;其三,性气相合的人性论;其四,诚明两进的修养论;其五,即闻见而趋德性的修养论。
针对佛老的、以气为本的太和观
我们认为,从整体逻辑上看,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之中心点,在于提出了一个根本不同于佛老的,对于这个世界的整体看法,其基本结论就是:“太和”。这也是张载在道学话语构建上非常重要的理念。
张载之提出“太和观”,显然系针对佛老的世界观而发,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当然张载对佛老思想的理解,也包含有一定的曲解成分,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张载认为,老学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徇生执有”,追求人身体的不“化”;二是认为“虚能生气”(实质是主张有生于无),把虚和气当成是完全异质之物。佛学存在的问题也有两个:一是主张寂灭,即认为万物灭后即一无所有(这是张载自己对佛家“寂灭”的理解);二是认为万物为幻化,一切皆空。张载认为,佛家的这两种说法同样会导致物与虚的两不相资。在他看来,佛老二者的具体观点虽然不同,但是其共性都是割裂了虚与气、有与无、体与用之间的联系,而张载特别强调世界恒动的绝对性,主张“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的一体关系。
张载强调,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舞台(或是大流行、大熔炉、大洪流):舞台上的主角只有一个——气(张载明确排除了在此大流行中另有一个主角叫做“无”的可能性),二者的关系就是气布满于虚空(不存在无气的虚空),气在虚空中聚散、运动不息。张载强调,独自聚散于虚空中的气之特性就是“一物两体”:“一”是指气这个主角的整体性和唯一性——自根自本,也无有无、生灭之可言;“两”是说气内在地包含有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属性。在此大“舞台”上,一切的一切都在不得已当中变化着:“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而“万物”也不能不最终“散而为太虚”。这一整体相状张载谓之野马、絪缊,谓之“太和”,此变动不居的历程张载则谓之“道”。张载特别强调“和”,“仇必和而解”是其哲学的整体基调。
张载还特别强调此大流行的“一本”性:现实中万殊之相状虽多,但其本源则一,张载皆以“吾体”视之。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张载提出“虚空即气”、“太虚即气”的本意所在:
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
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隠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
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故圣人语性与天道之极,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诸子浅妄,有有无之分,非穷理之学也。①
学界关于张载的“虚空即气”争论颇多。我们认为,在对张载的含混说法予以解读上,今人应该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既不能把现代人才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加到古人身上,也不能把古人的简单思维复杂化,具体到“虚空即气”,尤其不能对它的解读引向张载本人所批评的观点。有时候,在对古人思想的诠释上,适度地减担子更有助于把问题说清楚。②应该说,把“太虚”理解为一种“微观粒子”或者也是一种形式的“气”的说法,就有以今释古的嫌疑。
仅就概念而论,把太虚与(本然之)气直接等同的说法也难以得到传统文献的支持。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上文中的比喻,把太虚喻为舞台,把气视为主角。那么,张载的本意,无非就是强调主角与舞台的不离这一点:他的“无无”更是点出不存在没有演员的空舞台。换用学术语言说就是:一方面,不存在离气而独立的虚空,虚空之中无处无气;另一方面,也不存在独立于虚空之外的气,离开虚空则气无处顿放。这里,张载明确地否认了虚能生气的可能性,同时也否定了虚无穷、气有限的可能性。相对于把虚能生气理解为时间上有前后关系的生成论的说法,张载的说法属于本体论的说法。
回到这三段文字,其所论说的中心是强调一本之流行:看似有无、隐显、神化、性命,聚散、出入、形不形有不同,看似冰凝水释有不同,但其实都只是气在“大舞台”上的不同形象而已,这就是一本。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载无论是“吾体”的概念,还是其提出“大心”观,还是提出《西铭》,都在明确强调“万物一体”的理念,也强烈释放出张载视整个世界为“一本”的想法。这一想法也是儒学乃至传统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需要认真体会。后来,王阳明曾明确提出,他之所以强调“心外无物”的观点,针对的是那种“析心与理为二”的,将人与世界完全对象化、二分化的观点,进而强调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一体关系,强调自然(对人呈现)的意义化。我们认为,王阳明考虑问题的视角,其实也是张载的视角,甚至是,被阳明视为是“析心与理为二”之代表的朱熹,也在主张“理一分殊”模式下的“天人一本”。
张载又指出,在此大流行中,气这个主角所呈现出的具体形式又颇为不同:有以可见的形式存在者(散殊可象者,张载名之为气,其实称之为客形更为合适),也有以不可见的形式存在者(清通而不可象者,张载名之为神,不妨名之为本然之气),这就像自然界同时有冰又有水一样。可见者即为“显”,而不可见者则为“隐”。“隐者”会因为气之聚而变成“显者”,而“显者”也会因为气之散而变为“隐者”,因为二者是一本的。对于气,只能说其有隐显之转化,而不能说其存在有无之分别:
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①
张载认为,可见者之聚之散,都是短暂的,此谓之客形;不可见者是常态,此谓之气之本体。显然,在此大流行中,任何事物都注定要转变成他者,或明显,或隐微,或剧烈,或潜在:一切都只是这个大流行中气这个主角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罢了,但是这个主角绝对不会谢幕,也不会躲在幕后遥控几个木偶来演出(如佛家所说的,有真际,又有幻化的万物),但他却是又在不停地变换着角色。这里,张载虽然是以客形、糟粕来称谓天地间的法象万形,但是这并没有贬义。张载反对佛家以山河大地为见病的说法,更反对把虚与气视为二物的“体用殊绝”的说法,他会重蹈佛家的覆辙。
民胞物与的大心观
继对天的说明之后,张载提出了作为人之为人所应该持有的态度,这是他在道学话语构建上的第二个贡献:提出民胞物与的大心观。在强调世界一本的前提下,张载进而又提出天人之一本关系:
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①
天从太虚而来,道由气化而显,而太虚之“至静无感”与气之絪缊变化都是性(天地之性)的体现,性与知觉的更进一步结合,就是心。由此,人之本即在于天:“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②此之谓一本。在这个意义上,人只要不自小其心,就能感到可与天地并立,而又息息相通的一体感,进而找到自己在天地视域中的全新定位。这也是张载在《西铭》篇中着力要突出的意思。对张载来说,作天地之民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有与天地一体的胸襟之余,尽到自己做天民所应尽的本分就可以了(在张载看来,天民的本分就是尽其人道):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③
于张载,上述这些看似普通的“不同”行为,在天地视野中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强调天人一体,并不以否定人的特殊性(尽其分)为前提,而恰恰是以人之殊性的充分成就(实现)为前提的。这里,每个人的“分”似有不同,但其做为天命的通性则是一致的,此之谓“一本”基础上的多元。
后来小程子和朱子都很敏锐地注意到,张载所宣扬民胞物与(有次等中的一体),与墨家主张无差别之兼爱(无差别的同一),有根本的不同。当然,后来朱子把张载此处与墨学的不同概括为“理一分殊”,这却未必能契合张载的本意:张载在这里确实有对“一与殊”问题的关照,但是这里作为“一”的应该是“气”而非“理”,作为“殊”的应该是“形”而非“物理”。我们不妨把张载的世界观概括为“气一分殊”论,以区别示。
张载的大心观也决定了其对待生死问题的态度。张载生死观的中心即“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此即儒家传统的安时处顺态度。但是,张载对“此”的说明有自己独特的逻辑性:儒家传统之主张安时处顺,突出的是天命的不可抗拒性,而张载之强调安时处顺,突出的是大化流行的死而不亡和“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的大生命观,有着浓厚的境界论成份。在此大生命观下,肉体的消亡只是“吾大体”之聚之散而已,意味着从一己的客形、寄体形式回复到“吾大体”的本然状态,颇有回家的意味。与此相反,人之“大生命”则与天地神化直接同流,是不息的。在这里,张载通过强调大我和小我之辨,对生死问题提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解决方案。张载尤其强调,顺化代表着一种人生智慧:“天之化也运诸气,人之化也顺夫时。非气非时则化之名何有?化之实何施?《中庸》曰‘至诚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阴阳,与天地同流而无不通也。”①于张载,生时之顺化与面对死亡的顺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张载对生死的态度在二程及朱子那里都得到了回应:二程似乎认为张载的生死观表现为“既屈之气,复为方伸之气”②,即认为张载在抨击佛教的轮回学说之际,仍然不脱“大轮回”的影子:“方伸的‘这个’气”,依然还是“既屈的‘那个’气”,始终只是那一个气的循环。朱子亦承袭二程之说,进一步把张载的说法归纳为“形溃反原”说:“横渠说‘形溃反原’,以为人生得此个物事,既死,此个物事却复归大原去,又别从里面抽出来生人。如一块黄泥,既把来做个弹子了,却依前归一块里面去,又做个弹子出来。伊川便说是‘不必以既屈之气为方伸之气’,若以圣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之语观之,则伊川之说为是。盖人死则气散,其生也,又是从大原里面发出来(叶夔孙录)。”③我们认为,二程与朱子对张载生死观的解读恐怕都不符合张载的本意。对于张载来说,无论是“既屈之气”和“方伸之气”之间,还是新旧客形之间,只是同源而已,并不强调在它们之间有直接的同一联系。其实,朱子“盖人死则气散,其生也,又是从大原里面发出来”的说法,其实也正是张载所要表达的意思。
张载对于人心,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心统性情:
张子曰:心,统性情者也。
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
发于性则见于情,发于情则见于色,以类而应也。①
张载“心统性情”是说法,在朱子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但是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并不特别关注性情的问题,②也没有对此说法予以特别强调。
性气③相合的人性论
杨立华君认为:“张载对人性问题的思考,在道学话语的建构中具有组建性的作用……并以此规定了宋明道学有关人性问题的思考及讨论的基本架构”④,这一说法并不过分。人性论无疑是张载在道学话语建构上非常重要的贡献。
学界多认为,张载人性论是二元的,如张岱年先生指出:“北宋时,关于人性,又有一种新说,与以前的性论都大不相同,即是性两元论……此派的理论,更有一特点,即其人性论皆是从其宇宙论推衍出来的,不仅就性论性,更向宇宙论寻求根据……性两元论,创始于张载,精炼于二程,大成于朱子。”⑤但是,关于张载的人性论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学界目前还存在着争论。我们则认为,在张载那里,就根本性而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地位并不是对等的,毋宁说体现为一种本末的关系,是一本而非二本的。但是就现实的人而论,气质之性则是决定着人的真实人性的直接因素,或者说是决定性因素,需要分别看待。
我们认为,张载是在“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框架下来讨论人“性”问题的:人性虽源自于天①,但是二者却并非直接的同一。现实之人性还要受到形、气的限制。讨论人性问题,必须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
天地之性是张载整个“性论”的起点、是“本”。所谓天地之性,即是气之本体在大化流行中所显现出的性,即是它的自体性:神化、清通,感应、湛一,通有无、兼隐显,参而不偏,本身无所谓变易等等。天地之性先在于人,因此不能被直接称为“人之性”。这也就是张载所说的“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的意思。虽然如此,但是天地之性又构成了人性当中虽然隐而不彰,却又是本质性的内核,可谓是人性的本质。与之相对,气质之性则是因形而后方有之性:表现为攻取、刚柔、缓急、才与不才等,而攻取之性可能导致人的恶行。气质之性因形而后才有,有形则有碍,有形则有偏,乃至出现与天地之性相背反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张载主张:“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②,他甚至有时直接以“气质”或“气”称之。
关于张载的人性论,学界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张载所说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究竟是一个性,还是有两个性。最先挑起这个问题的是朱子。朱子基于其“理一分殊”的一贯性思路,把气质之性视为是天地之性(他认为即是理)在气上的具体呈现形式,就相当于混入了泥土的之后水。总之,朱子认为性只有一个,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不是有两个性。朱子据此展开了对张载之性论的批判,认为张载的性论有二本之嫌。我们认为,这里所反映出的是张载与朱子在思想上的根本区别:较之于朱子的“理一分殊”(一和殊都是理),张载则主张“气一形殊”:本然之气及其性(天地之性)为一(实际表现为一物两体),而万物之形及万物之气质之性为殊。在这个意义上,张载所主张的性论仍然是一元的:形是本然之气的“客”,而气质之性也是天地之性的“客”(暂时的寄体之所)。具体就人性而言,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都只是构成人之现实人性的两大因素,但是张载显然认为,只有天地之性才是人性的本质,才代表着人性之应然和必然。就此而言,我们似乎不能以二元论来看待张载的人性论。
于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张力:人的行为或有可能为天地之性所主导,也有可能受气质之性所支配。虽然说“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①,但是人在性尚未成(实现)之前,他的行为选择完全有被气质之性主导的可能性:“德不能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②如气质之性一旦反客为主,成为人行为的主导,那么人与天相通的类本质也就随之而丧失了。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现实行为就是受气质之性支配的。由此,张载提出了“成性”的概念。这就涉及了张载诚明两进的修养论。
诚明两进的修养论
在一定程度上,张载的“成性”概念是对先秦“尽性”理念的继承:孟子即认为,天赋予人的只是善端,但人为善的可能性却是人之为人的特质,孟子称之为人的性。同时,孟子也强调人还需要做扩充此善端的功夫,此之谓尽性。与此相类似,张载也强调要“成性”。张载所说的“成性”,首先意味着人需要通过心性修养的功夫以变化气质,超越对人行为的现实影响,进而使得人原本与天相通的潜在本性充分呈现,成为支配人的完全主导,这可以谓之“负的功夫”。此外,张载的“成性”的修养功夫还包括正面的穷理致知等。此一正一负的修养功夫相互互补,用张载自己的说法,就是自诚而明与自明而诚之修养功夫的良性互补:
自明诚,由穷理而尽性也;自诚明,由尽性而穷理也。③
释氏……乃诚而恶明者也。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④
自明诚,即由明理而后尽性;自诚明,即由尽性而后明理。张载显然认为,明理与尽性之间不是单向的关系,而是相互蕴涵、交相促进的关系:明可以促进诚,诚也可以助长明。于张载,有诚而无明是佛学的弊端,有明而无诚则是俗儒(沉迷于外在之物,往而不返)的弊端,只有诚明两进才是真儒的本色。在《横渠语录》(即今中华书局本《张载集》中的《张子语录》)中,张载对明与诚、性与气、习的关系又有详细的说明:
明者所学也。明何以谓之学?明者言所见也。大凡宽偏者,是所禀之气也。气者,自万物散殊时各有所得;习者,自包(胞)胎中以至孩婴时,皆是习也。及其长而有所立,自所学者方谓之学。性(田按,指天地之性)则分明在外,故曰:气其一物尔。气(田按,指气质或气质之性)者在性、习之间。性,犹有气之恶者为病,气又有习以害之,此所以要鞭后至于齐,强学以胜其气、习。其间则更有缓急精粗,则是人之性(之天地之性)则[虽]同,气则[有异]……①性则宽偏昏明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于习之异,斯远矣。虽则气之禀偏者,未至于成性时则暂或有暴发,然而所学则却是正,当其如此,则渐宽容。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气与习……
须知自诚明与[自]明诚者有异。自诚明者,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也,谓先自其性理会来,以至行[穷]理;自明诚者,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也,谓先从学问理[会],以推达于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为学而知者,某今亦窃希于明诚,所以勉勉安于不退……
自明诚者,须是要穷理,穷即是学也,所观所求,皆学也。②
张载此文以此前儒学中少见的下定义的方式,将明与诚、性、气、习、学这些概念之关系梳理得清晰明白。对他而言,只有天地之性才能成为人之本性(本质),而气和习两者都会对人之性带来不同的影响(张载更多强调其负面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张载明确强调,明或者学也是“诚”(即变化气质功夫)的重要内容,学(穷理)是为了变化气质,这也点出了诚与明之间的相互蕴涵关系。张载诚与明两进的功夫修养论与后来二程与朱子所主张的涵养与致知两进的功夫论是一致的,较之于后来湖湘学派与杨时一派的功夫论,张载的功夫论更显全面和圆通。
即闻见而趋德性的修养论
张载在构建道学话语上的开创性贡献,还包括对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分: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①
准确地说,“德性之知”不应该算是一种知识,而应该是一种与天同体的视界、意识与是境界,它与儒家的工夫修养论密切相关。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德性之知源自人对天地之性的体认,源自人在本质上与天地参的潜在大我。与之相对,闻见之知则是随人的耳目与外物相接触而后有的知识,是对有形之物的认知。我们不应该把张载对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划分,与当代西方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划分做牵强比附,更不能把张载的这一思想限定在认识论的领域,②更要注意到张载做出这一划分在功夫修养论上的意义。张载认为,人心不应该被束缚在对物的闻见上,这样只会自小其心。心不但要见物,更要见天,要能体物不遗,要知性(天地之性)知天,要与天地参,要突出一种要“有我”的,体验化、感受性的状态,而非认识的,对象化的状态。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张载“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的说法?从张载自己的逻辑看,德性所知是基于气之本然的认识,而闻见之知是对气之“客形”的认识,德性所知先在于闻见之知,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
另一方面,张载同时也强调,虽然耳目在一定条件下是人大其心的障碍,但是耳目的作用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耳目虽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为启之之要也。①
如果心不被闻见之知所束缚的话,反倒可以凭借耳目闻见之穷理致知的功能以实现合内外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讲,张载虽然推崇德性之知,却丝毫不贬损闻见之知(他反对的仅仅是以闻见之知梏其心这一点),而是主张即闻见而跨越闻见,即闻见而趋德性。他主张广泛的格物穷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张载推崇德性之知的理念,是其提倡民胞物与之大心观的必然结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唐儒学流于之“俗学”的反动。在这一点上,他与周敦颐之提出文道之辨、与二程强调颜子之学迥异于“俗儒”之点,是异曲同工的。我们发现,在周、张、二程那里,尊德性以及围绕此而展开的成圣功夫,都被置于了突出的地位,这也成为道学之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关键之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周张二人视为道学的开创者,并不为过。
附注
①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①汤用彤先生指出:玄学和佛学在魏晋时期都曾关注圣人是否可学可至的问题,时人(以道生为代表)对此的看法也有一根本的转变。但是在儒学内部对此问题做出回应的,恐怕还是从周敦颐开始的。
②《濂溪通书·文辞》,第53页。
①今之学者岐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见《程氏遗书》卷七。
②李景林:《儒学心性概念的本体化——周濂溪对于宋明理学的开创之功》,载《教化的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2页。
①周敦颐:《濂溪通书·诚》,载《诸儒鸣道集》卷一,《濂溪通书·诚》,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②同上。
③《濂溪通书·诚几德》,第43页。
④《濂溪通书·圣》,第44页。
①《溪通书·思》,第45—46页。
②同上。
③周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页。
④资料显示,周敦颐所画的《太极图》“静阴”在上,“动阳”在下,似乎表明静为体,动为用。
①《濂溪通书·动静》,第48页。
②《濂溪通书·圣学》,第50页。
①杨立华:《气本与神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此为陈来师所作的序言。
②胡元玲:《张载易学及其道学研究——以(横渠易说〉与〈正蒙)为主的探讨》,北京大学20003届博士论文,第16页。此论文已经在台湾文津出版社正式出版。
①张载:《横渠正蒙书·太和篇第一》,载《诸儒鸣道集》卷三,第81、82、84页。
②王夫之对横渠“虚空即气”的注解,仅为“虚空者,气之量;气弥沦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虚空而不见气。凡虚空皆气也”云云。可知,在船山那里,说“虚空皆气”并不是问题。此问题在现当代人变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用现代思维释读横渠的这一观点造成的。
①《横渠正蒙书·太和篇第一》,第82页。
①《横渠正蒙书·太和第一》,第85页。
②《横渠正蒙书·诚明篇第六》,《诸儒鸣道集》卷四,第107页。
③《横渠正蒙书·乾称篇第十七》,《诸儒鸣道集》卷十,第185—186页。
①《横渠正蒙书·神化第四》,第98页。
②《二程遗书》卷十五,四库全书本。
③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四库全书本。
①张载:《张载集》,《性理拾遗》,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74页。
②张岱年先生认为,张载此说可能出于《孟子解》,今已遗。
③这里的性指天地之性,气指气质之性。
④《气本与神化》,第105页。
⑤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①在张载的文献中,“天”的含义并不统一。简言之,张载所说的“天”有“对地之天”和“对人之天”两类:“对地之天”有象而无形,但仍有气的聚散;“对人之天”则强调天道、天理的一面。
②《横渠正蒙书·诚明》,第108页。
①《横渠正蒙书·诚明》,第106页。
②同上书,第109页。
③同上书,第106页。
④《横渠正蒙书·乾称》,第189页。
①此两处据中华书局《张载集》改。
②张载:《横渠语录》卷下,载《诸儒鸣道集》卷十八,第345—346页。
①《横渠正蒙书·大心》,第113页。
②余敦康先生精彩地指出,张载对德性与见闻之知的区分,主要是站在人性论的,讨论应通过何种途径继善成性以实现人的本质,而不是像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站在认识论的立场,讨论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关系。
①《横渠正蒙书·大心》,第114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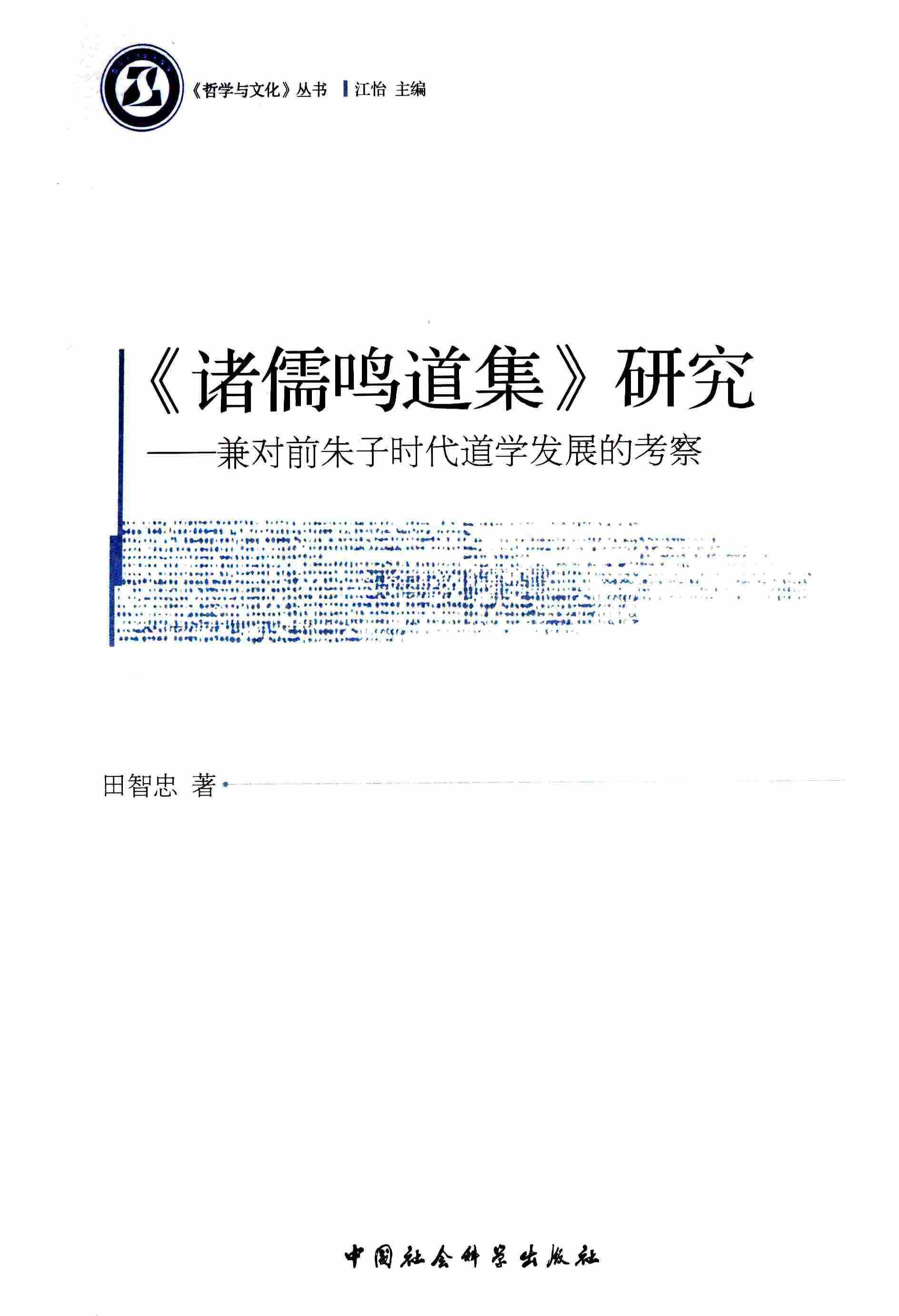
《《诸儒鸣道集》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内容包括:《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考、关于《诸儒鸣道集》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诸儒鸣道集》视野下的宋代儒学多元性研究、周敦颐与张载的道学话语构建、二程对道学话语的构建、谢良佐与杨时对道学话语的构建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