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诸儒鸣道集》选书标准的“去取不可晓”
| 内容出处: | 《《诸儒鸣道集》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5168 |
| 颗粒名称: | 一 关于《诸儒鸣道集》选书标准的“去取不可晓”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2 |
| 页码: | 203-204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陈振孙认为《诸儒鸣道集》选材杂乱,无章法或体例可言,可能编者并非基于学派和道统标准选书。 |
| 关键词: | 陈振孙 诸儒鸣道集 道统标准 |
内容
此说法最初见于陈振孙(约1186—约1262年)的《直斋书录解题》一书,陈这句话的本意和具体背景并不明确。现在看来,作为文献学者的他做出上述判断,未必就是基于以程朱之学为正统的立场:一来,陈与程朱学派并没有直接联系;二来,在《直斋书录解题》刊刻之际,程朱之学还并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正统地位。由此,陈振孙的真正所指,恐怕还是说《诸儒鸣道集》的选材杂乱,没有章法或体例可言吧:即使是基于广义的思想史立场,《诸儒鸣道集》中收录刘安世的三部毫无“思想性”可言的著作,都让人难以理解(假定《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刘安世有较深的渊源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只是选编了刘安世之师司马光的区区一部著作呢)。陈来师指出,“《鸣道集》所收,皆二程师友门人和再传弟子及私淑者”,这是对其所谓“去取不可晓”的一个回应。不过,从这些人的社会关系或政治立场的角度来看,他们大致可以归作一个集团;但是就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十二人的思想并不属于一个系统,至少不应该都算入道学的阵营。①当今学者笼统地把他们都纳入道学的阵营,这很可能会导致对道学理解的空泛化。
我们固然可以说,从地域因素上考量,编刻于杭州附近的《诸儒鸣道集》,其选书标准“去取不可晓”,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浙学“不主一家,不私一说”,尤其经史不分观念的影响。我们知道,虽然浙江学者多与程氏学派有一定的联系,但与二程及其后学的主流思想有很大差距,这也是吕祖谦不被收入《宋史·道学传》的原因之所在。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容忽视——该书的编者本来就不属于儒学阵营,乃至于其身份未必是学者(书商?),他们选书不一定基于学派和道统的标准。我们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很大的,而其之所以会大量选入程门的著作,如果考虑到浙学与二程之间仍有联系,或者当时新学、涑学、蜀学的后继乏人的现实,那么该书的编者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可以理解。这也颇能反映出程学在当时渐成学术主流的历史现实(当然这一现实也自然会反映在商业利益上)。
我们固然可以说,从地域因素上考量,编刻于杭州附近的《诸儒鸣道集》,其选书标准“去取不可晓”,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浙学“不主一家,不私一说”,尤其经史不分观念的影响。我们知道,虽然浙江学者多与程氏学派有一定的联系,但与二程及其后学的主流思想有很大差距,这也是吕祖谦不被收入《宋史·道学传》的原因之所在。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容忽视——该书的编者本来就不属于儒学阵营,乃至于其身份未必是学者(书商?),他们选书不一定基于学派和道统的标准。我们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很大的,而其之所以会大量选入程门的著作,如果考虑到浙学与二程之间仍有联系,或者当时新学、涑学、蜀学的后继乏人的现实,那么该书的编者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可以理解。这也颇能反映出程学在当时渐成学术主流的历史现实(当然这一现实也自然会反映在商业利益上)。
附注
①对于司马光之学的定位,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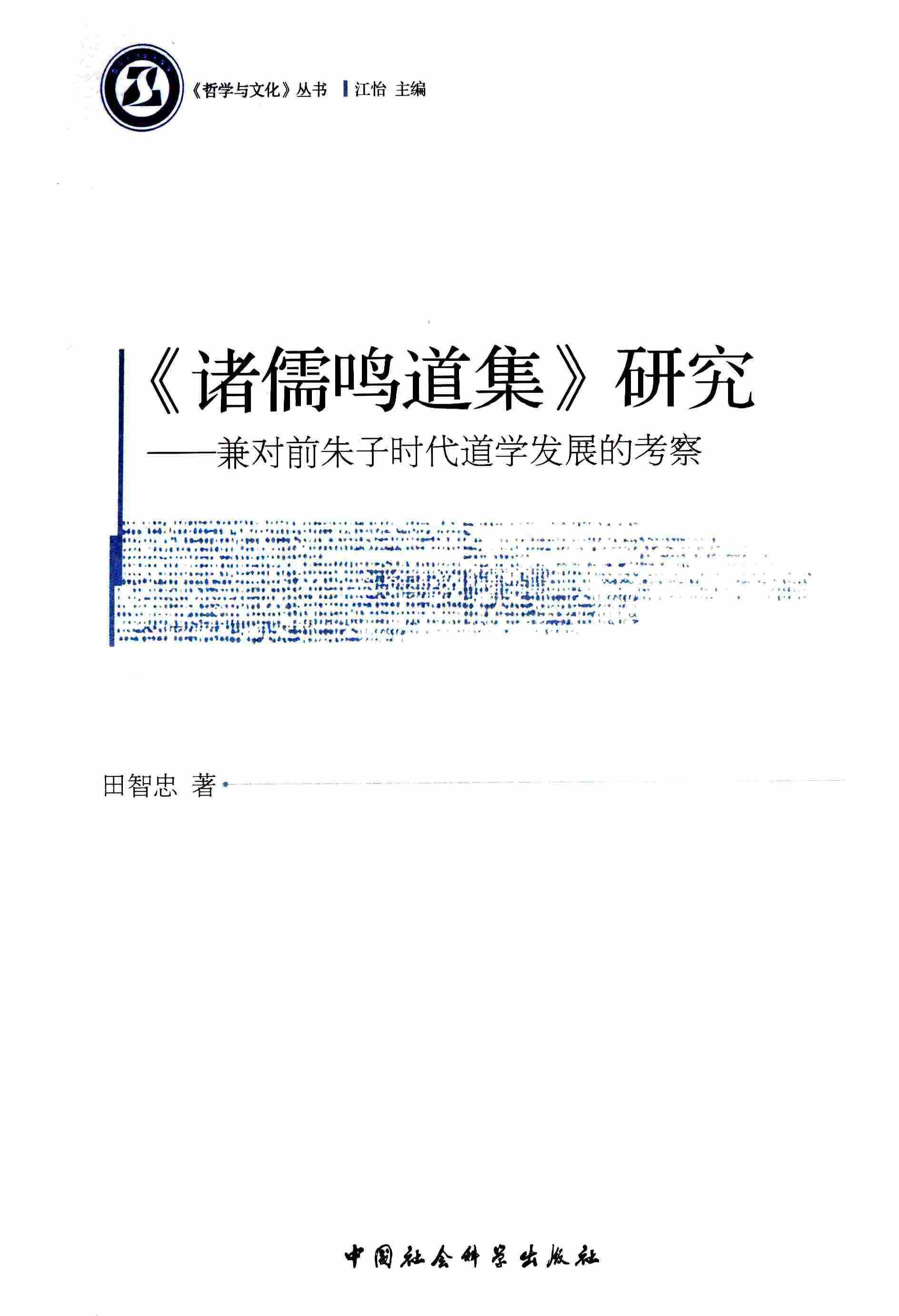
《《诸儒鸣道集》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内容包括:《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考、关于《诸儒鸣道集》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诸儒鸣道集》视野下的宋代儒学多元性研究、周敦颐与张载的道学话语构建、二程对道学话语的构建、谢良佐与杨时对道学话语的构建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