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诸儒鸣道集》的研究现状
| 内容出处: | 《《诸儒鸣道集》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5152 |
| 颗粒名称: | 二《诸儒鸣道集》的研究现状 |
| 分类号: | B244.0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23-33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诸儒鸣道集》在学界受到关注的过程,以及该书的原刻年代与编者身份、与朱熹的关系、与道学及道学谱系、与宋代学术多元化和与周敦颐的著作等方面的热点问题。 |
| 关键词: | 诸儒鸣道集 朱熹 道学 |
内容
关于《诸儒鸣道集》近来受到学界关注的过程,陈来师曾著文有所说明:
在北图找“心统性情”的时候,因看到《张载集》中“张子语录跋”提及“鸣道集本”,便问张先生是否要去看看,张先生说:“其书全名是《诸儒鸣道集》,在北京图书馆,你可以去查查。”于是我就在北图将《诸儒鸣道集》通看一遍,虽然没有查到“心统性情”,但也觉得有收获。由于北图的本子是影宋本,上海图书馆则藏有宋本,我也曾写信到上图询问宋本的序跋情况。情况摸了一遍以后向张先生报告,张先生要我写成文章,经过张先生看过,后来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田按,即《略论〈诸儒鸣道集〉》一文)。我还记得,文中所引黄壮猷的序,原文“时”字是用的讹字,我不认识,也没去查字典,就照抄录下,是张先生将这个字改为通用字,以后我才认得这个字。1986年初,一次在从香山回来的汽车上,杜维明先生说上海图书馆向他介绍《诸儒鸣道集》,他觉得很有价值。张先生即说:“陈来已经写了文章了。”后来杜先生要我把文章影印给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律先生,要燕京图书馆购藏此书。①
后经杜先生推荐,山东友谊出版社于1992年将《诸儒鸣道集》影印出版,此后该书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4年影印线装出版,②其影响也迅速扩大。
在历史上尤其是思想史上,《诸儒鸣道集》长期无人关注,而在陈来师的文章面世之后,《诸儒鸣道集》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并迅速形成了一系列热点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类为:
其一,概括介绍类:以陈来师和顾廷龙先生、方旭东的三篇文章为代表,③旨在对《诸儒鸣道集》的基本情况做出介绍,并对该书的原刻年代、作者身份等问题做出初步的分析判断。
其二,综合研究类:以复旦大学符云辉博士的博士论文《〈诸儒鸣道集〉述评》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邱佳慧博士的博士论文《〈诸儒鸣道〉与道学之再检讨》为代表。这两篇博士论文都对《诸儒鸣道集》有全面的分析研究,其研究思路也大致相同。
其三,围绕《诸儒鸣道集》某一问题的专题性研究,以赵振的一系列论文为代表,单篇文章集中解决一个问题,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如对“鸣道本”《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之渊源关系的分析、对“鸣道本”《二程语录》与张载《横渠经学理窟》之内容重叠的分析等。
其四,借助《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进行拓展性的研究,以杨柱才、林乐昌等人为代表,分别引用该书中的资料来研究周敦颐和张载的著作与思想。
其五,由《诸儒鸣道集》引申的一系列讨论。如田浩、葛兆光等围绕该书所引申出的,关于宋代学术多元化、道学、道学谱系问题的一系列的讨论。
学界目前对《诸儒鸣道集》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热点上:
其一,该书的原刻年代与编者身份。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切材料来确定该书的原刻年代和编者的身份。不过,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判断《诸儒鸣道集》的编订目的、所反映的时代信息等问题的必要前提。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讨论该书所反映的道学谱系、道统观念问题的基础就不可能牢靠——我们凭什么认定该书的编刻者一定属于儒者阵营?凭什么就认为该书反映出的是道学早期对道统的认识?因此,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难题。
其二,该书与朱熹的关系。《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上蔡先生语录》显然出自朱子所编订,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也说明,《诸儒鸣道集》的编刻与朱子或多或少会有关联。而赵振则进一步论证,该书所收录的《二程语录》也出自朱熹所编订。这一说法会在本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确认。据现有资料判断,本报告认为,“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和《二程语录》的刊刻,明显违背了朱子本人的意志。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该书的编者与朱子之联系是很松散的。
其三,该书与道学、道学谱系。田浩先生特别注意《诸儒鸣道集》对所收著作的选取问题:《诸儒鸣道集》收录了司马光及其弟子刘安世的著作。田浩先生据此认为,该书编者对于道学的理解颇不同于朱熹,代表着另一种道学谱系。符云辉邱佳慧均赞同田浩的观点,并都有所发挥。
其四,该书与宋代学术多元化。宋代儒学在总体上有一个由多元到一元的发展趋势。但是自《宋史·道学传》之后,这一历史有明显被化约的趋势。《诸儒鸣道集》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到南宋初期儒学发展多元化的有益资料:司马光、潘殖、江民表,刘安世,这些不属于“正统”道学体系的学者的著作被收录其中。这颇能反映出在朱子的学术定于一尊之前宋代儒学之面貌,也能丰富我们对宋代道学史发展之曲折性的认识。
其五,该书与周敦颐的著作。学界目前对于周敦颐的著作尚有很多的疑问,而“鸣道本”《濂溪通书》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通书》版本:虽然在朱子编订“长沙本”《通书》之前,社会上早已有“舂陵”、“零陵”、“九江”以及侯师圣传本和尹焞传本、胡宏整理本和祁宽整理本等多个《通书》版本在流传,但是这些版本我们今天都已经无法看到了。“长沙本”《通书》编订于乾道二年(后文有详细考证),而《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也与此相当,因此“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长沙本”《通书》,并且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通书》版本。这也为我们研究周敦颐著作的早期流传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总的看来,学界对《诸儒鸣道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完满解决,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该书的精确研究与应用。
首先,关于该书的原刻年代问题。学界对此的讨论仍限于陈来师和顾廷龙先生,别人基本上是在因袭二先生的说法。陈来师据《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上蔡先生语录》和《二程语录》两书判断,“《鸣道集》有可能是在朱熹校定《上蔡语录》至编定《遗书》的十年之间(1158—1168年)编成的。”①陈来师此说跨越了宋高宗绍兴年间到宋孝宗隆兴、乾道年间。但是据该书的避讳情况来看,该书原刻的年代还可以后推至少五年时间。顾先生认为:“此本(指《诸儒鸣道集》)原刻当在孝宗(田按,1163—1189年)时代无疑。”②我们认为,顾先生此说对《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下限的判定有些太晚。事实上,该书所收录的著作有不少在1168年前后出现了更新、更好的版本,如朱子于1166年编订“长沙本”《通书》,此本“视他本最详密”(“长沙本”的编订地点离《诸儒鸣道集》的编刻地点稍远,可能没有被该书的编者及时发现);于1168年重修《上蔡语录》并编订《程氏遗书》;于1173年编订《屏山集》,内含《圣传论》修定本;于1179年编订“南康本”《通书》,是为《通书》定本,《诸儒鸣道集》的编者没有什么理由不采用这些新的版本,而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诸儒鸣道集》编刻之际,这些更新的版本还没有进入该书编者的视野之内,这也意味着,《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要早于这些新版本的面世时间。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判断,我们完全可以把该书的原刻年代限定在乾道初年这个时间段内。对《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问题的解决,也为我们探索该书所反映的时代信息奠定了基础。
其次,该书的编者身份问题。此问题目前只有陈来师有所讨论,此后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沿袭他的结论(或有所修订,如向世陵和方旭东都指出,胡宪不大可能是该书的编者)。问题是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资料能够帮助我们揭开疑问,所以除非有新资料被发现,我们对此只能提出推测而已。不过,大家似乎都默认,《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一定属于道学阵营中人。这一立论前提却是值得商榷的——该书很可能属于坊刻本,其编者与书商的关联或许要比与道学阵营的关联要更紧密。笔者会在后文中对此给出进一步的说明。对我们而言,对该书编者身份的讨论更有价值。试想,如果该书的编者不属于道学阵营,那么我们讨论他们对道学谱系的理解还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其三,关于对道学、道学谱系的理解问题。在其大作《朱熹的思维世界》中,田浩(Tillman,HoytCleveland)先生借助《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提出了自己对道学以及道学谱系的独特理解。他希望道学可以涵盖哲学思辨、文化价值、现实政论三个层面(此为该书余英时先生的序言里的概括)。田浩的提法后来也得到了众多《诸儒鸣道集》研究者们的积极回应:如符云辉和邱佳慧等人。目前学界围绕道学一词的争论颇多,也颇能反映出哲学视角与历史学视角看问题的不同(方旭东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此不赘述。不过,田浩显然认为,《诸儒鸣道集》能反映出道学初期的多元面貌(田浩的本意,应该是指南宋道学初期的面貌),这个所谓的“早期”显然是针对朱子所编的《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而来。但是,《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显然并没有像田浩所认为的那样,要领先朱子编订《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的时间多少。依照陈祖武先生的研究成果,《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与《伊洛渊源录》之大纲所形成的时间基本相当,甚至还要稍晚些①,也仅仅早于《近思录》数年而已,“因此,如果指望从时间领先这一点上为《诸儒鸣道集》更能反映道学面貌进行辩护,其基础不能不说是很薄弱的”①,方旭东君的上述观点颇显中允。事实上,即使是抛开时间问题,田浩的观点也不是没有商榷的余地:在田浩所认为的南宋道学第一时期,他也只能举出张九成和胡宏二人为当时学术多元性的例证(胡宏的著作却没有被《诸儒鸣道集》收录),与之相对,在他所认为的第二阶段,则有朱子与湖湘学派、朱子与吕祖谦等浙学中人的一系列论争;在田浩所认为的南宋道学第三时期,至少还有陈亮、叶适(田浩没有提到)、陆九渊等人与朱子相对,总之,这后两个阶段也未尝不可以“多元”视之。我们认为,《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著作并不限于程朱一系,同时还包含了潘殖、江公望以及司马光、刘安世的著作,我们也可以据此讨论宋代学术的多元化问题(田浩先生的眼界尚不够宽阔)。但是,田浩先生对“道学早期”这一概念的使用颇为随意,《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完全有可能是朱子的同时代人,甚至不一定比朱子年长(在《诸儒鸣道集》原刻之际,朱子已经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并步入中年),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再者,关于道学谱系的问题,田浩等人很希望也把司马光、刘安世等人纳入道学的阵营中,本书对此持相反的观点。在唐宋之际,“道”这个概念相当混乱,至少它是儒释道共同使用的概念,因此才会有“道德为虚位,仁义为定名”的说法。因此,过分扩大“道学”一词的外延,难免会导致此概念内涵的空洞化。事实上,田浩也没有在其著作中贯彻他的想法,他的著作中所收录的人物,基本上不出程门后学的范围。
其四,关于“鸣道本”《二程语录》与《程氏遗书》关系问题。赵振撰长文《〈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集中论证《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都系朱子所编,只不过前者是初稿,而后者是定稿,此观点目前已经基本为学界所接受。不过,细察赵所提出的证据,发现每一条证据都不足以一锤定音。这些证据的组合也还不足以使其观点成为定案。略举其问题明显者如下:
赵的文中提出:
朱熹在编辑《遗书》时曾先编辑了一部初稿,而此初稿编成后即付梓,他在与何叔京的信中谈到过此事,说:“语录倾来收拾数家,各有篇帙首尾,记录姓名,比之近世所行者差为完善。故各仍其旧目而编之,不敢辄有移易。近有欲刻版于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当得其摹本以献,今无别本可以持内也。”[2](p1842)当朱熹拿到刊印的初稿本子时,发现了许多原来没有发现的错误,其《与平父书中杂说》云:“《程氏遗书》细看尚多误字,盖元本如此,今以它本参之,乃觉其误耳。”[2](p1838)于是决定对初稿重新进行校订。但由于自己有许多事务缠身,校订工作时断时续,所以后来他在写给何叔京的另外一封信中说:“语录比因再阅,尚有合整顿处。已略下手,会冗中辍。它时附呈未晚。”[2](p1846)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决定委托许顺之等人对《遗书》初稿进行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校勘,他写信给许顺之说:“向者程舶来求语录本子去刊,因属令送下邑(指同安)中,委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叶学古就城中独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书答之,再送下覆校。千万与二丈三友子细校过。”[2](p1781—1782)并在答复许顺之的信中对校书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曰:“承上巳日书,知尝到城中校书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据旧本为定,若显然谬误,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阙误可疑,无可依据者,宁且存之,以俟后学,切不可以私意辄有更改。盖前贤指意深远,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误后来,其罪将有所归,不可容易。千万千万!”[2](p1782)而这一工作直到乾道四年(1168年)才完成。①(田按,文中的[2],系指《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版;后同)
按照赵在文中的叙述,在时间上应该是先有朱子给何镐(叔京)的第一封信中提到“刊行语录”这件事,然后才会有他在《与平父书中杂说》中提到《程氏遗书》有错误这件事,再后来才有他在给何镐的第二封信中述及“语录”整理工作拖延的情况,最后才是朱子给许顺之的书信,告诫他们要认真校书,其前后顺序应该如此。但是,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从赵的这段文字看,除了《与平父书中杂说》中提到《程氏遗书》外,其前其后的书信提的都只是“语录”,这个《程氏遗书》名称的出现的确让人感到非常突兀;二是赵文中所提到的《与平父书中杂说》这封信的具体写作时间不详,因此这几封信的写作先后顺序是否就是如赵所排列的这样?这一点颇属疑问。陈来师就倾向于认为《与平父书中杂说》作于1168年之后,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是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显然,赵的论证缺乏对此的必要审查,他对朱子书信的排列比较随意。
再如,赵文中又提到:
《遗书》附录中的《伊川先生年谱》多次出现“见《语录》”字样的注文,这里的《语录》当指《二程语录》,因为从《程氏遗书附录后序》中我们得知该序作于乾道四年夏四月,也就是《遗书》修订完稿时,换句话说,《遗书》附录一卷及附录后序编写于《二程语录》刊行之后,故《语录》未载这部分内容。不仅如此,就是《程氏遗书后序》亦作于《遗书》修订完稿时,朱熹在乾道四年写给王近思的信中说:“校书闻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略见编纂之意。”[2](p1798)这里的序当指《程氏遗书后序》,此时王近思正与许顺之等人受朱熹委托在同安城校订《遗书》。并且在该序写成后,朱熹还就此征求过其他人的意见,他在写给林择之的信中说:“《文定祠记》、《知言序》、《遗书》二序并录呈。……三序并告参祥喻及,幸更呈诸同志议之。既欲行远,不厌祥熟也。”[2](p5456)其中《遗书》二序指的就是《程氏遗书后序》和《程氏遗书附录后序》,所以《语录》亦不载《程氏遗书后序》。①
赵认为:《伊川先生年谱》多次出现“见《语录》”字样的注文,这里的《语录》当指《二程语录》”云云,这一说法显然失察。《伊川先生年谱》中“语录”二字凡十见。其中“幼有高识非礼不动”条、“不知者或诮其委曲已甚”条、“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条、“某起于草莱”条、“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条,均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族子至愚不足责”条见于《程氏遗书》卷十九;“范致虚言"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一(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伊川先生病革门人郭忠孝生视之”条见于《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二(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由此可知,至朱子编订《伊川先生年谱》时为止,朱子所提到的“语录”,均包括《程氏遗书》和《程氏外书》的内容在内,是对流传下来的“二程语录”的统称,而非指“统编的程氏语录集”,尤其不能说是指《程氏遗书》或是其初稿或“鸣道本”《二程语录》①。
还如,赵推测:“但令人不解的是,平生治学严谨的朱熹为什么会让这样一个存在诸多问题的《二程语录》本子匆忙面世。笔者推测朱熹之所以这样急于发表自己所编的《二程语录》,很可能是想建立他在二程思想诠释方面的权威地位,并借机削弱其他学派,特别是胡安国家族在这方面所施加的影响,从而使自己在争取道学正统地位的斗争中能处于有利地位……”②此说同样令人生疑。据赵的推测,朱子是主动要发布《二程语录》的,考诸朱子自己的文献记述,此说恐怕不能成立。朱子自己已经反复声明“语录”初稿系被程宪拿走,并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匆匆刊刻的,朱子对此除了去信交涉外,还积极组织对“语录”的重新校对,这怎么能说是朱子主动要发布“初稿”呢?再者,在乾道四年之前,朱子与湖湘学派正处于蜜月期,其思想也正处于“中和旧说”阶段,朱子称赞湖湘学派为学功夫的书信也有很多。无论如何,朱子都不会在此时以争正统为目的主动发布《二程语录》。
一年后,赵振又作《朱熹与二程语录的整理与编辑》一文,对其所提出的观点做出了充实。如,赵又提出:“种种迹象表明,《遗书》初稿(赵认为即“鸣道本”《二程语录》的底本)很可能最初是由张栻刊于严州,朱熹《答吕伯恭》之四云:‘严州《遗书》本子初校未精,而钦夫去郡。今潘叔玠在彼,可以改正,并刻《外书》,以补其遗’”③云云,赵似乎是认为,朱子此信作于1166—1168年之间,此说不确。赵所引的书信为文集卷三十四之《答吕伯恭…前日魏应仲》(田按,实为《答吕伯恭》之五十五)。陈来师判定此书作于淳熙四年(1177年)①,或许有些太晚。但是,这封信却不可能作于1168年朱子正式刊刻《程氏遗书》之前:据杨世文先生考证,张栻于乾道五年(1169年)才由刘珙推荐,“知严州”,而其第二年则被调任回京②。据此,这封信也应该作于此时或稍后。尤其是这段文字中也提到了《外书》,其写作年代更不应该在1168年之前。显然,这封信中所提到的《遗书》,肯定不是指“鸣道本”《二程语录》。赵的观点是错误的。
赵振先生指出《二程语录》出自朱子所编,系《程氏遗书》的初稿,这一点颇有创见,但是其具体的论证过程也有很多的瑕疵。这也值得我们在后文中仔细探讨。
第五,关于《诸儒鸣道集》与周敦颐著作情况考辨的问题。陈来师指出:
据朱熹这些记述(田按,指朱子在“建安本”和“南康本”《通书》后序中的记述),《太极图》及《说》原附于《通书》之末,朱熹初定长沙本时一遵旧例,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后根据潘清逸为周敦颐所作墓志中“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的说法,意识到《太极图说》当是一部独立著作,在建安本才把《太极图说》独立出来并列于《通书》之前,从此《太极图说》便与《通书》分开了。
但是朱熹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井不完全相符。比朱熹更早一些的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说,《通书》一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所传本是也………逮卜居九江,得九江本于其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这就是说《通书》的程门传本有太极图,而九江周敦颐家藏旧本则没有。换言之,《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按照祁氏的说法,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祁氏仅及太极图当系简言之)。今《鸣道集》本亦无《太极图》,因此,如果可以断定鸣道集本早于朱子定本,那就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
这个本子也是今天所见到的《通书》的最早版本。①
现在看来,“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朱子所编订的“长沙本”《通书》当无异议,而综合“鸣道本”与“九江本”《通书》的情况判断,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通书》早期版本的流传分周氏故家藏本和程门传本两个系列,前者未收太极图,而后者则不独收录有太极图,也收录有《太极图说》。但是,“九江本”《通书》中是否如陈来师所推测的那样“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还存在进一步商榷的余地。据笔者判断,“九江本”只是没有《太极图》,却收录有所谓《太极说》,《太极说》具体内容与今天的《太极图说》基本一致。这也足以表明了《通书》早期版本流传情况的复杂性。
杨柱才先生也依据“鸣道本”《濂溪通书》,对《通书》在早期的流传情况有所说明。如他认为:“宋本《诸儒鸣道集》所收《濂溪通书》无《太极图》,当即是祁宽所见九江家藏旧本《通书》”②,此说不确:据朱子所见,“鸣道本”与“九江本”《通书》有很大差距。同时,杨还因袭束景南先生的观点,认为杨方给朱子的九江故家本《通书》系后出者,这一观点也颇值得商榷。
总之,上面提到研究成果和仍存在的问题也是本书立论的前提与基础。我们会在自己材料和视角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给出回应与解答。
在北图找“心统性情”的时候,因看到《张载集》中“张子语录跋”提及“鸣道集本”,便问张先生是否要去看看,张先生说:“其书全名是《诸儒鸣道集》,在北京图书馆,你可以去查查。”于是我就在北图将《诸儒鸣道集》通看一遍,虽然没有查到“心统性情”,但也觉得有收获。由于北图的本子是影宋本,上海图书馆则藏有宋本,我也曾写信到上图询问宋本的序跋情况。情况摸了一遍以后向张先生报告,张先生要我写成文章,经过张先生看过,后来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田按,即《略论〈诸儒鸣道集〉》一文)。我还记得,文中所引黄壮猷的序,原文“时”字是用的讹字,我不认识,也没去查字典,就照抄录下,是张先生将这个字改为通用字,以后我才认得这个字。1986年初,一次在从香山回来的汽车上,杜维明先生说上海图书馆向他介绍《诸儒鸣道集》,他觉得很有价值。张先生即说:“陈来已经写了文章了。”后来杜先生要我把文章影印给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律先生,要燕京图书馆购藏此书。①
后经杜先生推荐,山东友谊出版社于1992年将《诸儒鸣道集》影印出版,此后该书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4年影印线装出版,②其影响也迅速扩大。
在历史上尤其是思想史上,《诸儒鸣道集》长期无人关注,而在陈来师的文章面世之后,《诸儒鸣道集》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并迅速形成了一系列热点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类为:
其一,概括介绍类:以陈来师和顾廷龙先生、方旭东的三篇文章为代表,③旨在对《诸儒鸣道集》的基本情况做出介绍,并对该书的原刻年代、作者身份等问题做出初步的分析判断。
其二,综合研究类:以复旦大学符云辉博士的博士论文《〈诸儒鸣道集〉述评》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邱佳慧博士的博士论文《〈诸儒鸣道〉与道学之再检讨》为代表。这两篇博士论文都对《诸儒鸣道集》有全面的分析研究,其研究思路也大致相同。
其三,围绕《诸儒鸣道集》某一问题的专题性研究,以赵振的一系列论文为代表,单篇文章集中解决一个问题,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如对“鸣道本”《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之渊源关系的分析、对“鸣道本”《二程语录》与张载《横渠经学理窟》之内容重叠的分析等。
其四,借助《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进行拓展性的研究,以杨柱才、林乐昌等人为代表,分别引用该书中的资料来研究周敦颐和张载的著作与思想。
其五,由《诸儒鸣道集》引申的一系列讨论。如田浩、葛兆光等围绕该书所引申出的,关于宋代学术多元化、道学、道学谱系问题的一系列的讨论。
学界目前对《诸儒鸣道集》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热点上:
其一,该书的原刻年代与编者身份。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切材料来确定该书的原刻年代和编者的身份。不过,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判断《诸儒鸣道集》的编订目的、所反映的时代信息等问题的必要前提。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讨论该书所反映的道学谱系、道统观念问题的基础就不可能牢靠——我们凭什么认定该书的编刻者一定属于儒者阵营?凭什么就认为该书反映出的是道学早期对道统的认识?因此,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难题。
其二,该书与朱熹的关系。《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上蔡先生语录》显然出自朱子所编订,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也说明,《诸儒鸣道集》的编刻与朱子或多或少会有关联。而赵振则进一步论证,该书所收录的《二程语录》也出自朱熹所编订。这一说法会在本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确认。据现有资料判断,本报告认为,“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和《二程语录》的刊刻,明显违背了朱子本人的意志。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该书的编者与朱子之联系是很松散的。
其三,该书与道学、道学谱系。田浩先生特别注意《诸儒鸣道集》对所收著作的选取问题:《诸儒鸣道集》收录了司马光及其弟子刘安世的著作。田浩先生据此认为,该书编者对于道学的理解颇不同于朱熹,代表着另一种道学谱系。符云辉邱佳慧均赞同田浩的观点,并都有所发挥。
其四,该书与宋代学术多元化。宋代儒学在总体上有一个由多元到一元的发展趋势。但是自《宋史·道学传》之后,这一历史有明显被化约的趋势。《诸儒鸣道集》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到南宋初期儒学发展多元化的有益资料:司马光、潘殖、江民表,刘安世,这些不属于“正统”道学体系的学者的著作被收录其中。这颇能反映出在朱子的学术定于一尊之前宋代儒学之面貌,也能丰富我们对宋代道学史发展之曲折性的认识。
其五,该书与周敦颐的著作。学界目前对于周敦颐的著作尚有很多的疑问,而“鸣道本”《濂溪通书》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通书》版本:虽然在朱子编订“长沙本”《通书》之前,社会上早已有“舂陵”、“零陵”、“九江”以及侯师圣传本和尹焞传本、胡宏整理本和祁宽整理本等多个《通书》版本在流传,但是这些版本我们今天都已经无法看到了。“长沙本”《通书》编订于乾道二年(后文有详细考证),而《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也与此相当,因此“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长沙本”《通书》,并且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通书》版本。这也为我们研究周敦颐著作的早期流传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总的看来,学界对《诸儒鸣道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完满解决,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该书的精确研究与应用。
首先,关于该书的原刻年代问题。学界对此的讨论仍限于陈来师和顾廷龙先生,别人基本上是在因袭二先生的说法。陈来师据《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上蔡先生语录》和《二程语录》两书判断,“《鸣道集》有可能是在朱熹校定《上蔡语录》至编定《遗书》的十年之间(1158—1168年)编成的。”①陈来师此说跨越了宋高宗绍兴年间到宋孝宗隆兴、乾道年间。但是据该书的避讳情况来看,该书原刻的年代还可以后推至少五年时间。顾先生认为:“此本(指《诸儒鸣道集》)原刻当在孝宗(田按,1163—1189年)时代无疑。”②我们认为,顾先生此说对《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下限的判定有些太晚。事实上,该书所收录的著作有不少在1168年前后出现了更新、更好的版本,如朱子于1166年编订“长沙本”《通书》,此本“视他本最详密”(“长沙本”的编订地点离《诸儒鸣道集》的编刻地点稍远,可能没有被该书的编者及时发现);于1168年重修《上蔡语录》并编订《程氏遗书》;于1173年编订《屏山集》,内含《圣传论》修定本;于1179年编订“南康本”《通书》,是为《通书》定本,《诸儒鸣道集》的编者没有什么理由不采用这些新的版本,而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诸儒鸣道集》编刻之际,这些更新的版本还没有进入该书编者的视野之内,这也意味着,《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要早于这些新版本的面世时间。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判断,我们完全可以把该书的原刻年代限定在乾道初年这个时间段内。对《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问题的解决,也为我们探索该书所反映的时代信息奠定了基础。
其次,该书的编者身份问题。此问题目前只有陈来师有所讨论,此后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沿袭他的结论(或有所修订,如向世陵和方旭东都指出,胡宪不大可能是该书的编者)。问题是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资料能够帮助我们揭开疑问,所以除非有新资料被发现,我们对此只能提出推测而已。不过,大家似乎都默认,《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一定属于道学阵营中人。这一立论前提却是值得商榷的——该书很可能属于坊刻本,其编者与书商的关联或许要比与道学阵营的关联要更紧密。笔者会在后文中对此给出进一步的说明。对我们而言,对该书编者身份的讨论更有价值。试想,如果该书的编者不属于道学阵营,那么我们讨论他们对道学谱系的理解还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其三,关于对道学、道学谱系的理解问题。在其大作《朱熹的思维世界》中,田浩(Tillman,HoytCleveland)先生借助《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提出了自己对道学以及道学谱系的独特理解。他希望道学可以涵盖哲学思辨、文化价值、现实政论三个层面(此为该书余英时先生的序言里的概括)。田浩的提法后来也得到了众多《诸儒鸣道集》研究者们的积极回应:如符云辉和邱佳慧等人。目前学界围绕道学一词的争论颇多,也颇能反映出哲学视角与历史学视角看问题的不同(方旭东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此不赘述。不过,田浩显然认为,《诸儒鸣道集》能反映出道学初期的多元面貌(田浩的本意,应该是指南宋道学初期的面貌),这个所谓的“早期”显然是针对朱子所编的《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而来。但是,《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显然并没有像田浩所认为的那样,要领先朱子编订《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的时间多少。依照陈祖武先生的研究成果,《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与《伊洛渊源录》之大纲所形成的时间基本相当,甚至还要稍晚些①,也仅仅早于《近思录》数年而已,“因此,如果指望从时间领先这一点上为《诸儒鸣道集》更能反映道学面貌进行辩护,其基础不能不说是很薄弱的”①,方旭东君的上述观点颇显中允。事实上,即使是抛开时间问题,田浩的观点也不是没有商榷的余地:在田浩所认为的南宋道学第一时期,他也只能举出张九成和胡宏二人为当时学术多元性的例证(胡宏的著作却没有被《诸儒鸣道集》收录),与之相对,在他所认为的第二阶段,则有朱子与湖湘学派、朱子与吕祖谦等浙学中人的一系列论争;在田浩所认为的南宋道学第三时期,至少还有陈亮、叶适(田浩没有提到)、陆九渊等人与朱子相对,总之,这后两个阶段也未尝不可以“多元”视之。我们认为,《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著作并不限于程朱一系,同时还包含了潘殖、江公望以及司马光、刘安世的著作,我们也可以据此讨论宋代学术的多元化问题(田浩先生的眼界尚不够宽阔)。但是,田浩先生对“道学早期”这一概念的使用颇为随意,《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完全有可能是朱子的同时代人,甚至不一定比朱子年长(在《诸儒鸣道集》原刻之际,朱子已经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并步入中年),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再者,关于道学谱系的问题,田浩等人很希望也把司马光、刘安世等人纳入道学的阵营中,本书对此持相反的观点。在唐宋之际,“道”这个概念相当混乱,至少它是儒释道共同使用的概念,因此才会有“道德为虚位,仁义为定名”的说法。因此,过分扩大“道学”一词的外延,难免会导致此概念内涵的空洞化。事实上,田浩也没有在其著作中贯彻他的想法,他的著作中所收录的人物,基本上不出程门后学的范围。
其四,关于“鸣道本”《二程语录》与《程氏遗书》关系问题。赵振撰长文《〈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集中论证《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都系朱子所编,只不过前者是初稿,而后者是定稿,此观点目前已经基本为学界所接受。不过,细察赵所提出的证据,发现每一条证据都不足以一锤定音。这些证据的组合也还不足以使其观点成为定案。略举其问题明显者如下:
赵的文中提出:
朱熹在编辑《遗书》时曾先编辑了一部初稿,而此初稿编成后即付梓,他在与何叔京的信中谈到过此事,说:“语录倾来收拾数家,各有篇帙首尾,记录姓名,比之近世所行者差为完善。故各仍其旧目而编之,不敢辄有移易。近有欲刻版于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当得其摹本以献,今无别本可以持内也。”[2](p1842)当朱熹拿到刊印的初稿本子时,发现了许多原来没有发现的错误,其《与平父书中杂说》云:“《程氏遗书》细看尚多误字,盖元本如此,今以它本参之,乃觉其误耳。”[2](p1838)于是决定对初稿重新进行校订。但由于自己有许多事务缠身,校订工作时断时续,所以后来他在写给何叔京的另外一封信中说:“语录比因再阅,尚有合整顿处。已略下手,会冗中辍。它时附呈未晚。”[2](p1846)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决定委托许顺之等人对《遗书》初稿进行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校勘,他写信给许顺之说:“向者程舶来求语录本子去刊,因属令送下邑(指同安)中,委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叶学古就城中独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书答之,再送下覆校。千万与二丈三友子细校过。”[2](p1781—1782)并在答复许顺之的信中对校书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曰:“承上巳日书,知尝到城中校书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据旧本为定,若显然谬误,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阙误可疑,无可依据者,宁且存之,以俟后学,切不可以私意辄有更改。盖前贤指意深远,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误后来,其罪将有所归,不可容易。千万千万!”[2](p1782)而这一工作直到乾道四年(1168年)才完成。①(田按,文中的[2],系指《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版;后同)
按照赵在文中的叙述,在时间上应该是先有朱子给何镐(叔京)的第一封信中提到“刊行语录”这件事,然后才会有他在《与平父书中杂说》中提到《程氏遗书》有错误这件事,再后来才有他在给何镐的第二封信中述及“语录”整理工作拖延的情况,最后才是朱子给许顺之的书信,告诫他们要认真校书,其前后顺序应该如此。但是,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从赵的这段文字看,除了《与平父书中杂说》中提到《程氏遗书》外,其前其后的书信提的都只是“语录”,这个《程氏遗书》名称的出现的确让人感到非常突兀;二是赵文中所提到的《与平父书中杂说》这封信的具体写作时间不详,因此这几封信的写作先后顺序是否就是如赵所排列的这样?这一点颇属疑问。陈来师就倾向于认为《与平父书中杂说》作于1168年之后,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是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显然,赵的论证缺乏对此的必要审查,他对朱子书信的排列比较随意。
再如,赵文中又提到:
《遗书》附录中的《伊川先生年谱》多次出现“见《语录》”字样的注文,这里的《语录》当指《二程语录》,因为从《程氏遗书附录后序》中我们得知该序作于乾道四年夏四月,也就是《遗书》修订完稿时,换句话说,《遗书》附录一卷及附录后序编写于《二程语录》刊行之后,故《语录》未载这部分内容。不仅如此,就是《程氏遗书后序》亦作于《遗书》修订完稿时,朱熹在乾道四年写给王近思的信中说:“校书闻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略见编纂之意。”[2](p1798)这里的序当指《程氏遗书后序》,此时王近思正与许顺之等人受朱熹委托在同安城校订《遗书》。并且在该序写成后,朱熹还就此征求过其他人的意见,他在写给林择之的信中说:“《文定祠记》、《知言序》、《遗书》二序并录呈。……三序并告参祥喻及,幸更呈诸同志议之。既欲行远,不厌祥熟也。”[2](p5456)其中《遗书》二序指的就是《程氏遗书后序》和《程氏遗书附录后序》,所以《语录》亦不载《程氏遗书后序》。①
赵认为:《伊川先生年谱》多次出现“见《语录》”字样的注文,这里的《语录》当指《二程语录》”云云,这一说法显然失察。《伊川先生年谱》中“语录”二字凡十见。其中“幼有高识非礼不动”条、“不知者或诮其委曲已甚”条、“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条、“某起于草莱”条、“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条,均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族子至愚不足责”条见于《程氏遗书》卷十九;“范致虚言"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一(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伊川先生病革门人郭忠孝生视之”条见于《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二(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由此可知,至朱子编订《伊川先生年谱》时为止,朱子所提到的“语录”,均包括《程氏遗书》和《程氏外书》的内容在内,是对流传下来的“二程语录”的统称,而非指“统编的程氏语录集”,尤其不能说是指《程氏遗书》或是其初稿或“鸣道本”《二程语录》①。
还如,赵推测:“但令人不解的是,平生治学严谨的朱熹为什么会让这样一个存在诸多问题的《二程语录》本子匆忙面世。笔者推测朱熹之所以这样急于发表自己所编的《二程语录》,很可能是想建立他在二程思想诠释方面的权威地位,并借机削弱其他学派,特别是胡安国家族在这方面所施加的影响,从而使自己在争取道学正统地位的斗争中能处于有利地位……”②此说同样令人生疑。据赵的推测,朱子是主动要发布《二程语录》的,考诸朱子自己的文献记述,此说恐怕不能成立。朱子自己已经反复声明“语录”初稿系被程宪拿走,并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匆匆刊刻的,朱子对此除了去信交涉外,还积极组织对“语录”的重新校对,这怎么能说是朱子主动要发布“初稿”呢?再者,在乾道四年之前,朱子与湖湘学派正处于蜜月期,其思想也正处于“中和旧说”阶段,朱子称赞湖湘学派为学功夫的书信也有很多。无论如何,朱子都不会在此时以争正统为目的主动发布《二程语录》。
一年后,赵振又作《朱熹与二程语录的整理与编辑》一文,对其所提出的观点做出了充实。如,赵又提出:“种种迹象表明,《遗书》初稿(赵认为即“鸣道本”《二程语录》的底本)很可能最初是由张栻刊于严州,朱熹《答吕伯恭》之四云:‘严州《遗书》本子初校未精,而钦夫去郡。今潘叔玠在彼,可以改正,并刻《外书》,以补其遗’”③云云,赵似乎是认为,朱子此信作于1166—1168年之间,此说不确。赵所引的书信为文集卷三十四之《答吕伯恭…前日魏应仲》(田按,实为《答吕伯恭》之五十五)。陈来师判定此书作于淳熙四年(1177年)①,或许有些太晚。但是,这封信却不可能作于1168年朱子正式刊刻《程氏遗书》之前:据杨世文先生考证,张栻于乾道五年(1169年)才由刘珙推荐,“知严州”,而其第二年则被调任回京②。据此,这封信也应该作于此时或稍后。尤其是这段文字中也提到了《外书》,其写作年代更不应该在1168年之前。显然,这封信中所提到的《遗书》,肯定不是指“鸣道本”《二程语录》。赵的观点是错误的。
赵振先生指出《二程语录》出自朱子所编,系《程氏遗书》的初稿,这一点颇有创见,但是其具体的论证过程也有很多的瑕疵。这也值得我们在后文中仔细探讨。
第五,关于《诸儒鸣道集》与周敦颐著作情况考辨的问题。陈来师指出:
据朱熹这些记述(田按,指朱子在“建安本”和“南康本”《通书》后序中的记述),《太极图》及《说》原附于《通书》之末,朱熹初定长沙本时一遵旧例,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后根据潘清逸为周敦颐所作墓志中“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的说法,意识到《太极图说》当是一部独立著作,在建安本才把《太极图说》独立出来并列于《通书》之前,从此《太极图说》便与《通书》分开了。
但是朱熹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井不完全相符。比朱熹更早一些的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说,《通书》一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所传本是也………逮卜居九江,得九江本于其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这就是说《通书》的程门传本有太极图,而九江周敦颐家藏旧本则没有。换言之,《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按照祁氏的说法,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祁氏仅及太极图当系简言之)。今《鸣道集》本亦无《太极图》,因此,如果可以断定鸣道集本早于朱子定本,那就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
这个本子也是今天所见到的《通书》的最早版本。①
现在看来,“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朱子所编订的“长沙本”《通书》当无异议,而综合“鸣道本”与“九江本”《通书》的情况判断,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通书》早期版本的流传分周氏故家藏本和程门传本两个系列,前者未收太极图,而后者则不独收录有太极图,也收录有《太极图说》。但是,“九江本”《通书》中是否如陈来师所推测的那样“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还存在进一步商榷的余地。据笔者判断,“九江本”只是没有《太极图》,却收录有所谓《太极说》,《太极说》具体内容与今天的《太极图说》基本一致。这也足以表明了《通书》早期版本流传情况的复杂性。
杨柱才先生也依据“鸣道本”《濂溪通书》,对《通书》在早期的流传情况有所说明。如他认为:“宋本《诸儒鸣道集》所收《濂溪通书》无《太极图》,当即是祁宽所见九江家藏旧本《通书》”②,此说不确:据朱子所见,“鸣道本”与“九江本”《通书》有很大差距。同时,杨还因袭束景南先生的观点,认为杨方给朱子的九江故家本《通书》系后出者,这一观点也颇值得商榷。
总之,上面提到研究成果和仍存在的问题也是本书立论的前提与基础。我们会在自己材料和视角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给出回应与解答。
附注
①陈来:《岂弟君子,教之诲之——张岱年先生和我的求学时代》,载陈来《燕园问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②该书被收入了中华再造善本丛书。
③方旭东的文章为:《〈诸儒鸣道集〉再议》,载《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十三辑,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编,2010年2月。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4页。
②顾廷龙:《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见《诸儒鸣道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又按,据陈先行先生的《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一书提到:“近见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撰文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山东出版《孔子文化大全》所印此书的底本是来自美国哈佛燕京社,其实不是。上图既向杜维明教授提供了此书的复制件,后闻山东欲影印出版,正合顾廷龙先生的意愿,所以也向山东提供了复制件。当时因顾患病,出版前言由我代笔,但我至今未看到所印之书,再说本人水平有限,故未将这篇前言收入《顾廷龙文集》中”云云,可知此文实际系出自陈先生之手。见陈先行所著:《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此点系由一位台湾朋友指出,特此鸣谢。
①朱子在乾道二年给何镐的信中,已经提到过《渊源录》的编订,据陈祖武先生推测,这一年《渊源录》的大纲已经完成,见其著《中国学案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32页。
①方旭东:《〈诸儒鸣道集〉再议》,在《儒教文化研究》第十三辑,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2010年2月。
①赵振:《〈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43页。
①赵振:《〈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44页。
①朱子后来自己也强调,《年谱》的编订,系“熹尝窃取《实录》所书,《文集》、《内》、《外》书所载,与凡他书之可证者,次其后先,以为《年谱》”。
②《〈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第144页。
③赵振:《朱熹与二程语录的整理与编辑》,《天中学刊》2007年第4期,第120页。
①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4页。
②杨世文、王蓉贵点校:《张栻全集》,前言,第8页,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1—32页。
②杨柱才:《道学宗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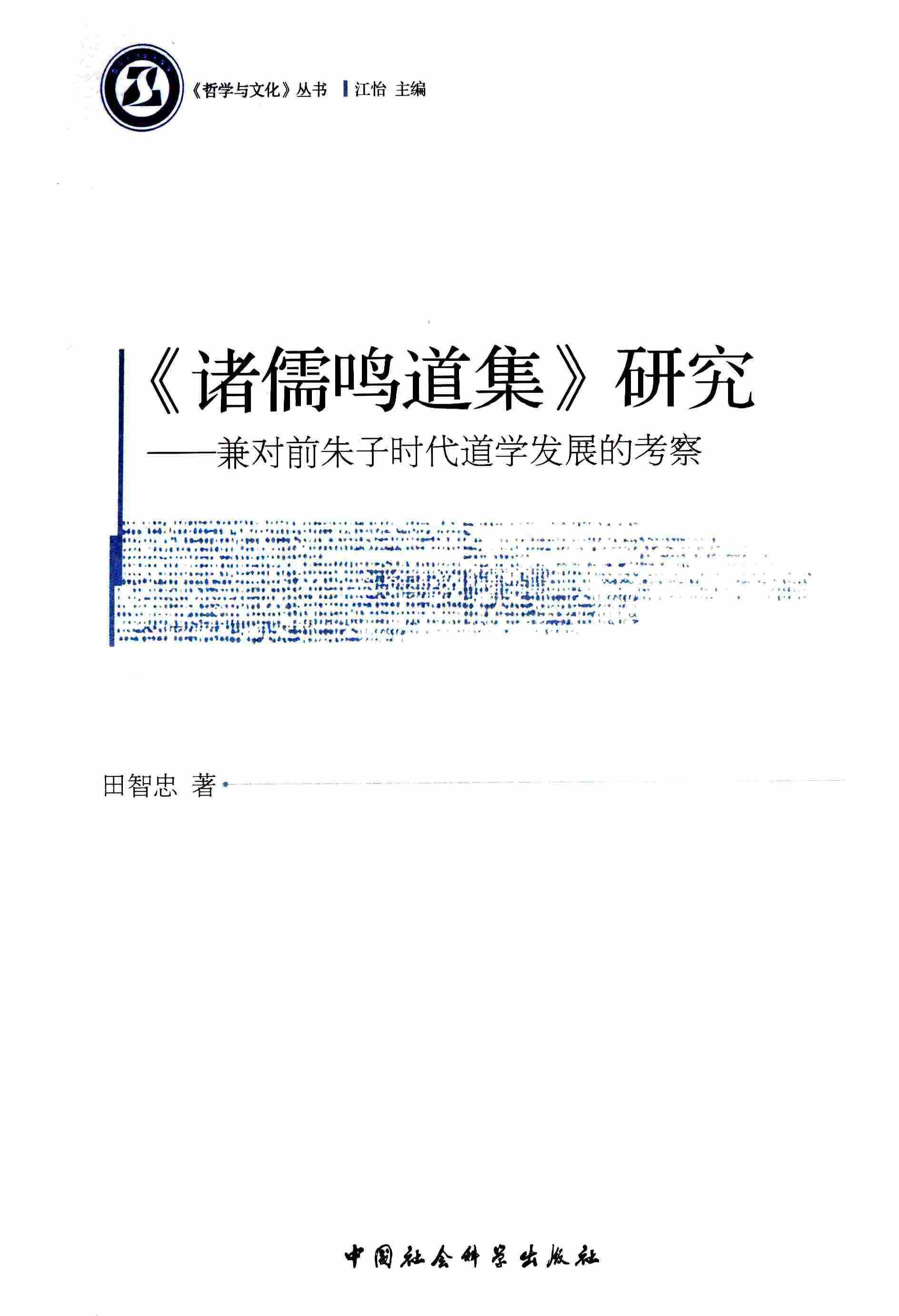
《《诸儒鸣道集》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内容包括:《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考、关于《诸儒鸣道集》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诸儒鸣道集》视野下的宋代儒学多元性研究、周敦颐与张载的道学话语构建、二程对道学话语的构建、谢良佐与杨时对道学话语的构建等。
阅读
相关人物
杜维明
相关人物
顾廷龙
相关人物
刘安世
相关人物
司马光
相关人物
田浩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
符云辉
相关人物
邱佳慧
相关人物
潘殖
相关人物
江民表
相关人物
刘安世
相关人物
周敦颐
相关人物
胡宏
相关人物
向世陵
相关人物
方旭东
相关人物
余英时
相关人物
陈祖武
相关人物
方旭东
相关人物
田浩
相关人物
张九成
相关人物
胡宏
相关人物
朱子
相关人物
吕祖谦
相关人物
陈亮
相关人物
叶适
相关人物
陆九渊
相关人物
司马光
相关人物
刘安世
相关人物
何叔京
相关人物
许顺之
相关人物
叶学古
相关人物
何镐
相关人物
赵文中
相关人物
王近思
相关人物
许顺之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