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 内容出处: | 《《诸儒鸣道集》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5137 |
| 颗粒名称: | 导言 |
| 页数: | 31 |
| 页码: | 3-33 |
内容
一《诸儒鸣道集》简介
《诸儒鸣道集》是唯一由宋人所编纂的一部传世理学丛书,①而且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我国第一部丛书,②该书中所收录的许多著作,也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其版本与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诸儒鸣道集》,系由黄状猷在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修补后印本,而非原刻本。关于此修补印本的基本状况,学界多有介绍:
如,在清人潘祖荫所著的《滂喜斋藏书记》一书中提到《诸儒鸣道集》:“所采诸儒语录,自濂溪、涑水以下凡十三家。《濂溪通书》一卷、《涑水迂书》一卷,横渠《正蒙》八卷、《经学理窟》五卷、《语录》三卷,《二程语录》二十七卷、《上蔡语录》三卷、《元城语录》三卷、《刘先生谭录》一卷、《道护录》一卷、《江民表心性说》一卷、《龟山语录》四卷、《安正忘筌集》十卷、《崇安圣传论》二卷、《横浦日新》二卷。后有楷书题记云:‘越有《诸儒鸣道集》最佳,年久板腐字漫,观者病之,乃命刊工剜蠹填梓,随订旧本,锓足其文,令整楷焉。时端平二禩八月吉日,郡守闽川黄壮猷书。’每半叶十二行,行廿一字,内缺《迂书》一卷、《理窟·第五》一卷、《二程语录》第八至十九卷,皆钞补明文渊阁官书,其书函犹原库装也,至今不蠹不脱,触手如新,昆山徐氏旧藏。”③
顾廷龙先生也提到《诸儒鸣道集》:“此本框高十九点三公分,宽十四公分,半页十二行,行廿一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字仿欧体,皮纸精印”①云云。
《诸儒鸣道集》一书,共收录宋儒周敦颐、张载、二程、司马光、杨时、谢良佐、刘安世、潘殖、刘子翚、江公望、张九成十一位学者的著作共十五种。对于该书所收录的各种著作,前贤多已经有过详细的说明,现择其要并结合本人的校读资料,有选择的说明如下:
周敦颐的《濂溪通书》一卷
“鸣道本”(指《诸儒鸣道集》所收录该书的版本,下同)《濂溪通书》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的《通书》,也要早于朱子所整理的“长沙本”《太极通书》。《濂溪通书》与世传本的《通书》(即朱熹所编订的“南康本”《太极通书》)在内容上也颇有不同。《濂溪通书》最引人注目之点在于,书中并没有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这颇能引起我们对《通书》早期流传问题的关注。
朱子在《太极通书后序》(即朱子所编订的“建安本”《太极通书》的后序)一文中曾指出:“右周子之书一编,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矣,然犹有所未尽也……”②在这里,朱子所说的“未尽”,应该是说在“建安本”《太极通书》之前的《通书》诸版本,都是把《太极图》附于末尾,“此则诸本皆失之”这一点吧。对此,陈来师已经指出,朱子的上述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因为祁宽的《通书后跋》一文已经指明“九江本”《通书》无《太极图》这一事实(据本报告考证,“九江本”中确实收录有《太极说》,即《太极图说》),而“鸣道本”《濂溪通书》则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并表明《通书》早期流传情况极为复杂,即有不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版本(如“鸣道本”),也有只收录《太极图说》却不收录《太极图》的版本(临汀杨方所见“九江本”),还有完整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程门传本。从上述情况看,《通书》早期版本的流传,有一个逐渐被充实、丰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朱子手中最后完成的。
“鸣道本”《濂溪通书》与朱子所编的“南康本”《太极通书》①(下文中简称为“南康本”)之间,在具体文字上也稍有不同,详列如下:
第一,《诚几德》章:“发微不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南康本”作:“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②“鸣道本”似有脱字。
第二,《师》章:“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惟中者,和也……暗者求于明师道立矣”,“南康本”则作:“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惟中也者,和也……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③两相比较,“南康本”为优。
第三,《化》章:“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民,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噫,道岂远乎哉?”“南康本”题为《顺化》章,作:“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道岂远乎哉?”④从此句的排比句式判断,前一处“南康本”作“物”字为优,而后一处“鸣道本”有“噫”字为优。
第四,《礼乐》章:“阴阳理然后和”,“南康本”作:“阴阳理而后和”,⑤二者可并存。
第五,《务实》章:“德业未有著”,“南康本”同,今理学丛书本《周敦颐集》则作“德业有未著”,⑥为优。
第六,《爱敬》章:“孰无过,乌知其不能改”,“南康本”作:“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⑦据下文判断,“鸣道本”为优。
第七,《乐》章:“古圣王制礼法”,“南康本”题为《乐上》章,作:“古者圣王制礼法”,⑧“南康本”为优。
第八,《圣学》章:“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南康本”作:“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①“鸣道本”显有脱字。
第九,《颜子》章:“夫富贵,人所爱者也”,“南康本”作:“夫富贵,人所爱也”,②“南康本”为优。
第十,《圣蕴》章:“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不复也。孔子曰:‘予欲无言……’”,“南康本”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子曰:‘予欲无言……’”③。
第十一,《乾损益动》章:“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非(一本无非字)是过”,“南康本”无双行夹注,也无“非”字④。
第十二,《家人睽复无妄》章:“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无妄则诚焉”,“南康本”作:“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无妄则诚矣”,⑤可两存。
第十三,《刑》章:“既成矣不止即过焉”,“南康本”作:“既成矣不止则过焉”,⑥“南康本”为优。
第十四,《孔子》章:“王祀孔子报德报功无尽焉……实与天地参而四時同者”,“南康本”作:“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实与天地参而四時同”⑦。
第十五,《蒙艮》章:“山下出泉静而止(双行夹注:一作而清也)”,“南康本”无双行夹注,作“山下出泉静而清”⑧。
就二者的刊刻质量而论,“南康本”明显为优,这并不令人奇怪。不过,“南康本”却有两处明显不及《濂溪通书》。由此可知:其一,朱子在编订“南康本”时,并没有参考《濂溪通书》,否则他会据此来改正“南康本”中的错误。其二,与朱子所提到的“九江本”及“胡宏本”《通书》相比较,《濂溪通书》的错误更少。其三,《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不选在当时更为流行(也更容易得到)的程门传本的《通书》,却选择《濂溪通书》,原因待考。但是,这或许说明,其与程门之间未必有直接师承渊源关系。
就二者刊刻的时间而论,“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南康本”《太极通书》,乃至“长沙本”《通书》,这一点当无疑义。例如,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即在《濂溪通书》中,有一处作“孔子曰”、另一处作“孔子”,而在“南康本”中,则分别变成了“子曰”和“夫子”,这些细微的差异其实是有深意的:后者之称谓更为“亲切”,也流露出对儒家道统更为强烈的认同感。我们基本可以判定,称“孔子曰”和“孔子”的《濂溪通书》更接近周敦颐的原稿,原因是假定周敦颐的原稿作“子曰”和“夫子”,其在后来是不大可能会被改作“孔子曰”和“孔子”的(此一点,系受王博老师讲授《论语》时的启发,特表感谢)。
不过,“鸣道本”《濂溪通书》的编订年代也不可能太早,因为该书中三次出现以双行夹注“一本”或“一作”形式出现的校勘痕迹(除上文中给出的例子外,另外一次出现在《濂溪通书》的《理性命》章中)。这足以说明,《濂溪通书》的编者(不一定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在编订《濂溪通书》时,至少是参考了当时流行中的,两个以上版本的《通书》,因此《濂溪通书》本身不可能是《通书》最早的版本,其编订年代很可能要在南宋之后。至于《濂溪通书》中为什么不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原因存疑。当然,《濂溪通书》的编者很可能也认为《太极图》或《太极图说》本身就不属于《通书》,尤其是如果他们见到的《通书》版本是把《太极图》或《太极图说》附在文后的话。
司马光的《涑水迂书》一卷
“鸣道本”《涑水迂书》与世传的四部丛刊影宋本《迂书》(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四)的内容基本相同。此二书与四库全书本《迂书》(收入四库本《传家集》中)比较,则又有一定的差异。如,“四库本”《迂书序》有双行夹注“嘉祐二年作”云云,为“鸣道本”和四部丛刊本所无;“四库本”《知非》条下有双行夹注“嘉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作”,也为“鸣道本”和四部丛刊本所无;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天人·迂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理性》、《事亲》、《事神》、《宽猛》、《无益》、《学要》、《治心》、《文害》、《道大》、《道同》、《绝四》、《求用》、《负恩》、《羡厌》、《老释》、《凿龙门辨》、《无为赞》诸条,“四库本”都有双行夹注注明了其具体写作年代,这都是“鸣道本”和四部丛刊本所无。又如,此二书的《无为赞贻邢和叔》,“四库本”只作《无为赞》,可知“鸣道本”《涑水迂书》更接近司马光的原稿。
另外,“鸣道本”和四部丛刊本《涑水迂书》明显不同于“四库本”《迂书》之处,是缺少《天人·迂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条。“鸣道本”《涑水迂书》本为清人配抄,是否有所遗漏,待考。
张载的《横渠正蒙书》八卷
“鸣道本”《横渠正蒙书》八卷是目前仅见的宋刻全本《正蒙》,也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正蒙》刻本。林乐昌先生以为:“在《正蒙》的两个明本之前,再向前追溯,还有两个宋本,按时间先后看,一是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国朝二百家明贤文粹》书隐斋刻本所收《正蒙书》上下太极图二卷,简称文粹本;二是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诸儒鸣道》浙刻本所收《横渠正蒙书》八卷,简称鸣道本。由于早于鸣道本的文粹本只是节选本,故当以鸣道本为《正蒙》之祖本,而文粹本则仍有重要的对校价值。”①这里,林先生显然是把《诸儒鸣道集》的再刻时间当成了它的原刻时间,其说不确。
陈来师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以及《直斋书录解题》等书指出,宋代流行的《正蒙》基本上为十卷本,而“鸣道本”《横渠正蒙书》则为八卷本,“鸣道本”所缺的是“胡安国所传编为一卷”和“末有行状一卷”,而非缺《正蒙》的正文。②但是,胡安国所传一卷的内容具体究竟是“传”(zhuan),还是“所传(chuan)者”,目前还不确定。
“鸣道本”《横渠正蒙书》与《张子全书》本《正蒙》比较,内容基本相同。今中华书局本《张载集》中的《正蒙》,点校者根据《横渠易说》、《周易系词精义》、《宋元学案》、《张子正蒙注》等书,指出《张子全书》本《正蒙》存在着大量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却又都出现在“鸣道本”《横渠正蒙书》中。由此可知,《正蒙》的初稿很可能已经包含有这些“错误”了。具体原因,应该是张载在撰写《正蒙》时,多是仅凭记忆随意来转述他早年的研究成果所致。
“鸣道本”《横渠正蒙书》在具体内容上与“张载集本”《正蒙》也稍有不同。①如《大易》篇“洁净精微,不累其迹”条,“鸣道本”后有双行夹注:“一本云‘深于易矣’”,此双行夹注为其他诸本所无。②又如,《乐器》篇“亲亲尊尊又曰亲亲尊贤”条,“鸣道本”后有双行夹注:“一本先得作先将”,此双行夹注也为其他诸本所无。同篇“义民安分之良民而已”条,“鸣道本”后有双行夹注:“一本‘准牧’下有‘无’字,併为一节”,为其他诸本所无。③再如,“鸣道本”的《乾称》篇中,则有数条错误:
其一,“凡可状皆有也”条,“鸣道本”作:“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因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舍气有象否?非象有意否?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
此条在“四库本”被分为三条:
“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
“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舍气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
“张载集本”此条也被分为三条:
“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舍气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①
综合比较,只是“张载集本”对于双行夹注的处理才是正确的,“鸣道本”把三条内容放在一段中,最不恰当。
其二,“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条和“大学当先知天德”条,“鸣道本”作:“浮屠明鬼,有识之死,受生循环,厌苦求免,可谓知乎?以人生为妄见,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
“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极论要归,必谓死生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悟则有义、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昼夜、通阴阳,体之不二。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其俗达之天下,致善恶、知愚、男女、臧获,人人著信,使英才间气,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驱,因谓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故未识圣人心,己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自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
“四库本”此两条合为一条,作:“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以人生为妄,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惑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极论要归,必谓死生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悟则有义、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昼夜、通阴阳,体之不二……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
“张载集本”与“四库本”相同,只不过是由点校者依据《宋文鉴》把“四库本”中的双行夹注改为了正文。这样,“鸣道本”中本有两段双行夹注,在“四库本”中变成了一段,而“张载集本”则把“鸣道本”中双行夹注的内容都变成了正文。中华书局点校者指出,“浮屠明鬼”条文字又称《与吕微仲书》,收入《张载集》第350页,作:“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亦出庄生之流。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以人生为妄见,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者,惑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极论要归,必谓生死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悟则有义、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昼夜、道(当为通字)阴阳,体之不二……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①
比较上述四者可知,“鸣道本”、“四库本”、“张载集本”各有失误也各有所长,当以《与吕微仲书》为准(也可能张载在编撰《正蒙》时,未严格对照《与吕微仲书》,故《正蒙》与《与吕微仲书》未必完全一致)。
第三,“益物必诚”条,“鸣道本”后有双行夹注:“铭诸牅以自诏”,此为今本所无。②
第四,“戏言出于思”条,“鸣道本”作:“戏言出于思也……引咎其不出汝者,长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张载集本”作:“戏言出于思也……归咎其不出汝者,长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中华书局点校者指出,在《宋文鑬》中,“归咎”已经误作“因咎”,可知出現的时间应该很早。③
综合判断,虽然“鸣道本”《横渠正蒙书》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宋刻全本《正蒙》,但却不是最好的版本。我们对张载著作的研究也不能完全以此为据。此外,通过对今流行的各《正蒙》版本与“鸣道本”《横渠正蒙》的比较可知,《正蒙》的双行夹注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而是由作者的“原注”和该书的整理者逐渐添加而成的,且各版本之间在双行夹注内容上也不尽一致。
再者,在《横渠正蒙书》的夹注中,屡屡提到的“一本”如何如何,这一事实表明,该书的编订同样参考的两个以上的底本,其编订时间同样不会太早,很可能晚于北宋末年。
张载的《横渠经学理窟》五卷
“鸣道本”《横渠经学理窟》受人关注的是它的卷数问题,以及其与“二程语录”之间的内容重叠问题。在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提到:“《理窟》二卷,右题金华先生,未详何人,为程张之学者”,而在赵希弁的《郡斋读书志附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则都提到《经学理窟》为一卷本,而“鸣道本”《横渠经学理窟》则为五卷,与今通行本同。陈来师怀疑《附志》有误。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在宋代已经有虽卷数不同,但内容基本相同的多种《经学理窟》版本在流传,而目前传世的《经学理窟》本则与“鸣道本”一致,为五卷。
关于《理窟》中的某些内容与《二程语录》重复的问题,张岱年先生指出,这些重复内容“从大部分的题材语气来看,又确像张载的话”,张先生怀疑此书或为张载与二程之“语录”的汇编。今人赵振对此也有较为详细的考证:他详细考辨了二书中二十二条内容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条目,指出其中绝大多数内容当出自张载,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一些程颐的话。他同时指出,两书重复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见于《二程遗书》中由关中学者所记的第二卷(包括上、下两卷)和第十五卷”。①从常理推测,或许是程颐回应或者是转述张载的某些言论,或者是与张载讨论某问题的言论,被后学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上述的重复内容。
与世传通行本《经学理窟》(中华书局《张载集》本)相比,“鸣道本”《横渠经学理窟》也有多处不同:
其一:《学大原上》章“道理今日却见分明”条:“道理今日却见分明……上又见性与天道,他日须胜孟子,门人如子贡子夏等人,必有之乎”。
“张载集本”作:“道理今日却见分明……下面又见性与天道,他日须胜孟子,门人如子贡子夏等人,必有之乎”,两相比较,鸣道本为优。①
其二:《学大原上》章:“人早起未尝交物须意锐精健”条:“张载集本”中“锐”误作“鋧”字,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②
其三:《学大原下》章:“张载集本”之“教之而不受”条:“教之而不受,虽强告之无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纳也。今夫石田,虽水润沃,其干可立待者,以其不纳故也。庄子言‘内无受者不入,外无主者不出’”条,③此条内容不见于“鸣道本”。
其四:《学大原下》章:“鸣道本”之“学者以尧舜之事”条:“学者以尧舜之事,须刻日月要得之,犹恐不至,在可媿而不为,此始学之良术也”。
“张载集本”作:“学者不论天资美恶,亦不专在勤苦,但观其趣向,著心处如何。学者以尧舜之事须刻日月要得之,犹恐不至,有何媿而不为,此始学之良术也。”④“鸣道本”显有脱文。
第五:《学大原下》章:“鸣道本”作:“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自出,若安坐则何尝有疑”。
“张载集本”作:“学行之乃见,至其疑处,始是实疑,于是有学(点校者注明,此四句从《易说》佚文移此)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自出(原文为出自,点校者依照《宋元学案》改正),若安坐则何尝有疑”。
第六:《学大原下》章:“大抵人能洪道”条,“洪”字为因避讳而改字,“弘”为本字,“张载集本”不误。⑤
第七:《学大原下》章:“世儒之学正”条:“世儒之学,正惟洒扫应对,便是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于此不阙文”。
“张载集本”作:“世儒之学,正惟洒扫应对便是,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⑥
两相比较,“鸣道本”为正。
第八:《自道》章:“家中有孔子真尝欲置于左右”条:“则至于不敢拜”,“张载集本”的底本“拜”字误为“伐”字,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①
其九:《自道》章:“上曰慕尧舜者不必”条:“如岂则岂可无其迹”,“如岂”为“如是”之误,“张载集本”不误。②
第十:《自道》章:“某自今日欲正经为事”条:“故不免须责于家人辈”,“责”字,“张载集本”的底本误为“贵”字(四库本却不误),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③
第十一:《祭祀》章:“无后者必祭”条:“干袷及其高祖”,“干”字,“张载集本”的底本误为“子”字(四库本却不误),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④
第十二:《祭祀》章:“七庙之主聚于太祖者”条:“且祧者当易檐”,“檐”字,“张载集本”的底本误为“担”字,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⑤
综上所述,“鸣道本”在总体上错误比今通行本要少,但是本身也有许多错误。“鸣道本”《横渠经学理窟》同为清人配抄,与“鸣道集”原本是否有差异,不详。
张载的《横渠语录》三卷
“张载集本”《张子语录》(底本为南宋吴坚刻本)在刊刻时,已经依照“鸣道本”校订过,二者的详细异同,可参看《张载集》的相关章节,此处从略。
概言之,“鸣道本”中也有一些错误,不可以为准绳。
二程的《二程语录》二十七卷
“鸣道本”《二程语录》与今通行本《程氏遗书》差距最大,受学界的关注也最多。关于二者之间的详细差距,本书拟作为个案详加讨论,这里仅略论其大概。
目前,关于“鸣道本”《二程语录》的突出研究成果,是赵振所指出的,《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大同小异,二者同为朱子所编订,只不过前者是初稿,后者是修订稿,①赵先生的结论可谓是不刊之论,但是其论证过程并非无懈可击。
谢良佐的《上蔡先生语录》三卷
陈来师指出,“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当出自朱子定本。据朱子《谢上蔡语录后序》云,三卷本的《上蔡语录》是他在“括苍吴任写本一篇(题曰《上蔡先生语录》)”、“吴中板本一篇(题曰《逍遥先生语录》)”,以及从胡宪那里得到“胡文定公家写本二篇(题曰《谢子雅言》)”这四篇原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四篇原稿当中:“胡氏上篇”是“胡本”所独有的,专门记录胡安国与谢良佐之间的问答,被朱子编为《上蔡语录》卷上;“胡本”的下篇“与板本、吴氏本略同,然时有小异”,但内容更为精练,朱子综合三本异同,定为《上蔡语录》卷中;“板本”与“吴本”、“胡本”比较,则多出“百余章”,被朱子精简为三十余章,定为《上蔡语录》卷下,是为《上蔡先生语录》三卷定本。“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也正是三卷本,且与朱子定本内容基本一致,必然出自朱子的整理。关于此本与后来诸《上蔡语录》版本之间的异同情况,北大哲学系的韩国留学生李根德君有《谢良佐〈上蔡语录〉研究》之硕士论文,对此有极为详细的比较,此不赘述。
此外,笔者在对“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的分析中发现,此版本与朱子在绍兴二十九年和乾道四年所编订的两个版本的《上蔡语录》相比,均有细微的差别(具体差别见后文),由此判断,“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的底本很可能就是被人在江西盗刻的版本,本文称之为“盗印本”。
刘安世的《元城先生语》三卷
关于刘安世以及“鸣道本”《元城先生语》三卷的情况,台湾的邱佳慧博士在其硕士论文《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②中都有详尽的说明。据《元城先生语录序》①介绍,《元城先生语录》编订于绍兴五年②(1135年)正月。邱文提到:“《元城语录》目前所见者有三,分别为上海图书馆所藏《诸儒鸣道集》中《元城语录》;《丛书集成新编》收马永卿辑、王崇庆注解、崔铣编行录与钱培名补脱文的《元城语录解》;以及《四库全书》的版本”。③经查,《元城语录解》同时也被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中,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④该书的整理者注明,其所参考的版本有惜阴轩丛书本、小万卷楼丛书本和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元城先生语录》所据的底本是惜阴轩丛书本,此外又根据小万卷楼丛书本补充了脱文。
“鸣道本”《元城先生语》与《元城语录解》比较,最明显的不同是未收录见于后者的张九成作于绍兴六年(1136年)的序(应该是节本)。邱文即据此判断:“可见《元城语录》一书语此时(田按,此处“此时”所指不详)分了至少两条路线流传,其一为王崇庆注解本,较广为人知的版本;其二是《诸儒鸣道集》所收的版本,亦应是马永卿所著作的原本”。⑤邱这个判断还缺乏足够证据的支持,因为注解本究竟出现于何时,这目前还是个疑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诸儒鸣道集》刊刻之际,社会上应该有带有张九成序的另一个版本的《元城语录》在流行。这也从侧面说明,《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张九成的关系并不十分亲密,否则他们在编刻《诸儒鸣道集》时,完全应该选择收录此序言之版本的《元城先生语》。
再者,“鸣道本”《元城先生语》与《元城语录解》相比,更为完整、精确。二者“时有一二字不同”,但《元城语录解》脱《元城先生语》中的第二十一条(“先生一日仆闲言语”条⑥)约数百字,便是明证。
刘安世的《刘先生谈录》一卷、《刘先生道护录》一卷
此二书仅依靠《诸儒鸣道集》得以流传至今,此外并无其他版本传世以便比较。但是,正如邱文所指出的,《直斋书录解题》标明《道护录》为一卷十九则,《郡斋读书志附志》则说《道护录》为二卷(田按,疑为“一卷”之误)十九则,①今“鸣道本”《刘先生道护录》却只有十五则,恐有缺文,亦或并非善本。
江公望的《江民表心性说》一卷
江公望字民表,关于他的资料,除了《宋史》中的记载之外,多又见于宋人宗晓所编的《乐邦文类》、明人夏树芳所辑的《名公法喜志》、清人彭际清所述的《居士传》中。据上述资料来看,江公望曾经“作《念佛三昧咏》,大劝于世”②;“……居常与妻俞氏蔬食清斋,修念佛三昧,著《念佛方便文》曰:‘世出世间之法,欲得成办省力,莫若系心一缘,即如称念阿弥陀佛,有巧方便,无用动口,不出音声,微以舌根敲击前齿,心念随应,音声历然,声不越窍,闻性内融,心印舌机,机抽念根,从闻入流,反闻自性,是三融会,念念圆通,久久遂成唯心识观。若是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无所,六根杳寂,诸识消除,法法全真,门门绝待,瞥尔遂成真如实观。初机后学,一心摄念如来,乃至营办家事种种作务,亦自不相妨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过旬月便成三昧。所谓自心作佛,自心是佛,自心见佛’……”③;而夏树芳则提到江:“尝著《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劝道俗。又尝书于家塾曰:‘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无所,六根杳寂,诸识销落,法法全真,门门绝待,瞥尔遂成,真如实观。初机后学,一心摄念如来,即使营办家事,种种作务,亦自不相妨碍。若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过旬日,便成三昧。是故上根大器,一念直超;平展之流,善观方便”。④上述三条文献对江公望文献的说明颇有矛盾,但也说明江公望的数篇文字的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
江公望传世的文献,除了上述《念佛三昧文》和宋史列传中的片段文字之外,就是因《诸儒鸣道集》而得以流传的《心性说》了。江公望还曾有部分文字混入吴中版本的《逍遥先生语录》(实际出自江的《辨道录》)中,但是被朱子在整理《上蔡语录》时删除,今已不传。
江公望《性说》引人注目之点在于注重区分正性和习性之不同。依照江公望的逻辑,“正性”即所谓“空无自性”,这一观念明显来自于佛教,江公望又指“正性”为“全性”;而“习性”即所谓习(江强调,习即是学)得之性,善恶、智愚、凡圣等都被他视为“习性”。江公望认为,“正性”不同于“习性”,亦不离“习性”。孔子所论之性和《尚书》重所强调的,只是“习性”,强调的是“学之不可已也”。总的看来,江公望对“性”的解释显然是受到了“佛性”论的影响,而在宋代士大夫中,江公望当属于溺佛颇深者之列。
杨时的《龟山语录》四卷
《直斋书录解题》云:“《龟山语录》五卷,延平陈渊几叟、罗从彦仲素、建安胡大原伯逢所录,杨时中立之语及其子迥汇稿共四卷,末卷为附录墓志遗事,顺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①这是说,五卷本的《龟山语录》中,前四卷为杨时的女婿陈渊、杨的弟子罗从彦和杨的后学胡大原所编,第五卷则为朱子弟子廖德明所汇集。又,稍后赵希弁的《郡斋读书志附志》,则收录有《龟山先生语录》四卷,可知应该是先有一个四卷本的《龟山语录》流传,随后才有五卷本的《龟山语录》面世,而“鸣道本”《龟山语录》正好是四卷本,当为早期流传的《龟山语录》版本。
胡大原为湖湘学派主将之一,师从胡宏,曾参与四卷本的《龟山语录》的编订工作。据王立新先生为点校本《斐然集崇正辩》撰写的前言称,胡寅于宣和六年(1124年)四月,得子胡大原。据此可知,胡大原年长朱子六岁,小于张九成,四卷本《龟山语录》形成的时间很可能要晚于《横浦日新》面世的时间,而且只是被收录入《郡斋读书志附志》中。
与南宋末年的五卷本《龟山语录》(四部丛刊续编所收南宋末吴坚刻本,简称“吴本”)相比,“鸣道本”与之稍有异同,但是差距并不大。
第一,“问孔子曰中庸之为德”条:“极,犹室之极,所处中则至矣”,“吴本”则脱“中”字。①
第二,“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条:“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役于身体”,“役”字,“吴本”误为“设”字。②
第三,“吕晦叔真大臣其言简而意足”条:“臣”字,“吴本”作“人”字,怀疑为因避讳而改字。③
第四,“朝廷设法卖酒所在官吏”条:“往往民间得钱遂用之”,“吴本”作:“往往民间得钱遂用之有方”二字,“鸣道本”疑为脱文。④
第五,“天生聪明时■所谓天生者”条:“然后可以制人而止其乱。曰:‘夫聪明……”,“夫”字,“吴本”误作“天”字。⑤
第六,“世之事鬼神所以陷于淫谄者”条:“汉儒信祖有功、宗有德”,“信”字,“吴本”作“言”字。⑥
第七,“吕吉甫解孝经义”条:“故孔子以其而尽告之”,“吴本”同:“故孔子以其未晓而尽告之”,“鸣道本”和“吴本”皆有脱文。⑦
第八,“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条:“孟子以恻隠之心為人之端”,“人”字,“吴本”作“仁”字,“鸣道本”当为因避讳而改字。⑧
第九,“因言秦汉以下事”条:“六经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鸣道本”此条以下有大量脱文,⑨约有五百字,据“吴本”,“鸣道本”此处脱“因言秦汉以下事”条部分文字、“盥而不荐初未尝”条全部、“又云无诚意”条全部、“予欲观古人”条全部、“棠棣之言朋友”条全部和“问所解论语犯而不校”条部分,该书的脱文怀疑为脱页所致。
第十,“孟子一部书只是要正人心”条:“孟人遇人便道性善”,“孟人”乃“孟子”之误,“吴本”不误。①
第十一,“曾见志完云上合下”条:“吴本”则作:“谓曾见志完云上合下,。②
第十二,“叔孙通作原庙是不使人主改过”条:此条在“吴本”中被分为两条,即“叔孙通作原庙是不使人主改过”条和“勿意只是去私意,若诚意则不可去也”调,③“勿意只是去私意”条末有夹注标明:“重见”。
第十三,“问易曰乾坤其易之门邪”条:“如某与定夫相会,亦未尝及(抹去四字)定夫学易”,“吴本”则作:“如某与定夫相会,亦未尝及从可,某常疑定夫学易”,④此处当以“吴本”为准。
第十四,“字说所谓大同于物者”条:“若离人而之天,正所谓顽空(抹去一字)总老言经中说十识”,⑤据“吴本”,抹去的应为“通”字。
第十五,“伊川语录云以忠恕为一贯”条:“问中庸发明忠恕之理(抹去一字)有一贯之意”,⑥据“吴本”,抹去的应为“以”字。
综合判断,“鸣道本”《龟山语录》既有抹字的情况,也有脱文的情况,表明其刊刻颇为匆忙,但是与“吴本”相比,仍然能够校订出其不少错误,“鸣道本”显然与原稿更为接近。
潘殖的《安正忘筌集》十卷
目前学界对《安正忘筌集》的讨论不多,也只有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先生曾写过以“忘筌集”为题名的论文。与续修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上下两卷本《安正忘筌集》(明万历刻本,题为潘植作,前有焦竑序)⑦以及该书的清刻本《浦城遗书》本相比,二者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十卷本的“鸣道本”《安正忘筌集》更为完整。如顾廷龙先生就指出:“又如《安正忘筌集》,《浦城遗书》本缺《河图数图》与《洛书数图》……”①,而“鸣道本”则非常完整。
在具体文字上,该书的“鸣道本”与万历本也有所差异。
其一,《宅心》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蕴太极于中,是为天地之心”,“万历本”中“于”字误为“之”字,意思全别。②
其二,“万历本”《图书奥旨》章末“理彰于事可因”之后,有一页文字与《蓍卦》章中“于此用事而洞”后一页文字颠倒③,而“鸣道本”不误。
综合判断,“鸣道本”《安正忘筌集》要明显优于“万历本”。
刘子翚的《崇安圣传论》二卷
刘子翚(1101~1147年),字彦冲,一作彦仲,号屏山,建州崇安人。顾廷龙先生认为,刘的著作“……《崇安圣传论》等著作仅赖此书(田按,指《诸儒鸣道集》)得以传世”④,其实此说法不确。四库本《屏山集》卷一中的《圣传论十首》(简称“屏山集本”),此即《崇安圣传论》也。二者相比,“鸣道本”为二卷,而“屏山集本”则仅为一卷,同时题目也稍有差别:“鸣道本”每章题目为“尧舜(一)、禹(仁)、汤(学)、文王(力)、周公(谦牧)、孔子(死生)、颜子(复)、曹子(孝)、子思(中)、孟子(自得)”,而“屏山集本”的目录仅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颜子、曹子、子思、孟子”。此外,在具体内容上,“鸣道本”与“屏山集本”⑤相比,也出入颇大。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崇安圣传论》为刘子翚的初稿,而《圣传论十首》则为修订稿(形成年代不晚于1147年)。这当中,《圣传论十首》有数篇文章的结尾被完全重写,而十篇的全文均经过较大的改动,兹将二者的详细比较附于书后,以便阅者查考。
关于《屏山集》,胡宪和朱子都曾提到该书整理的过程:
……乃遽哭其丧,是年予盖六十有一而彦冲甫四十七……越十有三年,其嗣子玶始编次其遗文,凡得古赋、古律、诗、记、铭、章奏、议论二十卷,目曰《屏山集》……绍兴三十年六月朔,籍溪胡宪序。①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玶所编次,已定,可缮写(《朱子全书》原文点断如此,当断为“编次已定,可缮写。”)。先生启手足时,玶年甚幼,以故平生遗文多所散逸。后十余年,始复访求,以补家书之缺,则皆传写失真,同异参错而不可读矣。于是反复雠订,又十余年,然后此二十卷者始克成书,无大讹谬。熹以门墙洒扫之旧,幸获与讨论焉。窃以为先生文辞之伟,固足以惊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学,静退之风,形于文墨,有足以发蒙蔽而销鄙吝之萌者,尤览者所宜尽心也。因书其故以告后之君子。乾道癸巳(1173年)七月庚戌门人朱熹谨书。②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二载:“右正言何若言:自赵鼎唱为伊川之学,高亢之徒从而合之,乃有横渠《正蒙书》、《圣传十论》……”③据此可知,《圣传论十首》形成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之前。不过,《屏山集》初编于1160年,晚于刘去世十多年,定编于1173年,晚于刘去世近三十年。这颇能说明刘后继乏人的现实。
此外,在“鸣道本”《崇安圣传论》中多次出现的“钦”字,在“屏山集本”中都被改为“敬”字,笔者怀疑这与避讳宋钦宗的庙号有关。若果真如此,则“鸣道本”的底本当完成于北宋,而“屏山集本”则完成修订于南宋初年。“鸣道本”《崇安圣传论》,也为我们判断《诸儒鸣道集》编者与刘子翚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材料。《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所以会选取《圣传论》早期流传的版本,而不选择“屏山集本”,这从侧面说明他们与刘子翚的关系比较疏远,也更不可能是刘的后学或是弟子。
张九成的《横浦日新》二卷
“鸣道本”《横浦日新》与世传本(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八十三册,收录有《横浦日新》一卷本)略有差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录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明吴惟明刻本,题为张九成的外甥于恕辑。我们则认为,一卷本所标的作者是错误的,于恕只是于淳熙元年(1174年)辑录了《横浦心传录》三卷,而明人则在刊刻该本时,误将《横浦日新》的作者标成了于恕。这是因为,于恕在其本人所作的《无垢先生横浦心传录序》中已经说明:“予学生郎晔,粗得数语,纂为所录,而士大夫已翕然传诵,信知舅氏一话一言为世所重如此”①云云,文中所指的“粗得数语,纂为所录”,显指《日新》,再结合《郡斋读书志附志》中的例证,于恕此处所指,必为《横浦日新》无疑。
在具体文字上,“鸣道本”《横浦日新》与世传本完全相同。
二《诸儒鸣道集》的研究现状
关于《诸儒鸣道集》近来受到学界关注的过程,陈来师曾著文有所说明:
在北图找“心统性情”的时候,因看到《张载集》中“张子语录跋”提及“鸣道集本”,便问张先生是否要去看看,张先生说:“其书全名是《诸儒鸣道集》,在北京图书馆,你可以去查查。”于是我就在北图将《诸儒鸣道集》通看一遍,虽然没有查到“心统性情”,但也觉得有收获。由于北图的本子是影宋本,上海图书馆则藏有宋本,我也曾写信到上图询问宋本的序跋情况。情况摸了一遍以后向张先生报告,张先生要我写成文章,经过张先生看过,后来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田按,即《略论〈诸儒鸣道集〉》一文)。我还记得,文中所引黄壮猷的序,原文“时”字是用的讹字,我不认识,也没去查字典,就照抄录下,是张先生将这个字改为通用字,以后我才认得这个字。1986年初,一次在从香山回来的汽车上,杜维明先生说上海图书馆向他介绍《诸儒鸣道集》,他觉得很有价值。张先生即说:“陈来已经写了文章了。”后来杜先生要我把文章影印给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律先生,要燕京图书馆购藏此书。①
后经杜先生推荐,山东友谊出版社于1992年将《诸儒鸣道集》影印出版,此后该书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4年影印线装出版,②其影响也迅速扩大。
在历史上尤其是思想史上,《诸儒鸣道集》长期无人关注,而在陈来师的文章面世之后,《诸儒鸣道集》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并迅速形成了一系列热点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类为:
其一,概括介绍类:以陈来师和顾廷龙先生、方旭东的三篇文章为代表,③旨在对《诸儒鸣道集》的基本情况做出介绍,并对该书的原刻年代、作者身份等问题做出初步的分析判断。
其二,综合研究类:以复旦大学符云辉博士的博士论文《〈诸儒鸣道集〉述评》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邱佳慧博士的博士论文《〈诸儒鸣道〉与道学之再检讨》为代表。这两篇博士论文都对《诸儒鸣道集》有全面的分析研究,其研究思路也大致相同。
其三,围绕《诸儒鸣道集》某一问题的专题性研究,以赵振的一系列论文为代表,单篇文章集中解决一个问题,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如对“鸣道本”《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之渊源关系的分析、对“鸣道本”《二程语录》与张载《横渠经学理窟》之内容重叠的分析等。
其四,借助《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进行拓展性的研究,以杨柱才、林乐昌等人为代表,分别引用该书中的资料来研究周敦颐和张载的著作与思想。
其五,由《诸儒鸣道集》引申的一系列讨论。如田浩、葛兆光等围绕该书所引申出的,关于宋代学术多元化、道学、道学谱系问题的一系列的讨论。
学界目前对《诸儒鸣道集》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热点上:
其一,该书的原刻年代与编者身份。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切材料来确定该书的原刻年代和编者的身份。不过,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判断《诸儒鸣道集》的编订目的、所反映的时代信息等问题的必要前提。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讨论该书所反映的道学谱系、道统观念问题的基础就不可能牢靠——我们凭什么认定该书的编刻者一定属于儒者阵营?凭什么就认为该书反映出的是道学早期对道统的认识?因此,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难题。
其二,该书与朱熹的关系。《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上蔡先生语录》显然出自朱子所编订,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也说明,《诸儒鸣道集》的编刻与朱子或多或少会有关联。而赵振则进一步论证,该书所收录的《二程语录》也出自朱熹所编订。这一说法会在本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确认。据现有资料判断,本报告认为,“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和《二程语录》的刊刻,明显违背了朱子本人的意志。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该书的编者与朱子之联系是很松散的。
其三,该书与道学、道学谱系。田浩先生特别注意《诸儒鸣道集》对所收著作的选取问题:《诸儒鸣道集》收录了司马光及其弟子刘安世的著作。田浩先生据此认为,该书编者对于道学的理解颇不同于朱熹,代表着另一种道学谱系。符云辉邱佳慧均赞同田浩的观点,并都有所发挥。
其四,该书与宋代学术多元化。宋代儒学在总体上有一个由多元到一元的发展趋势。但是自《宋史·道学传》之后,这一历史有明显被化约的趋势。《诸儒鸣道集》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到南宋初期儒学发展多元化的有益资料:司马光、潘殖、江民表,刘安世,这些不属于“正统”道学体系的学者的著作被收录其中。这颇能反映出在朱子的学术定于一尊之前宋代儒学之面貌,也能丰富我们对宋代道学史发展之曲折性的认识。
其五,该书与周敦颐的著作。学界目前对于周敦颐的著作尚有很多的疑问,而“鸣道本”《濂溪通书》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通书》版本:虽然在朱子编订“长沙本”《通书》之前,社会上早已有“舂陵”、“零陵”、“九江”以及侯师圣传本和尹焞传本、胡宏整理本和祁宽整理本等多个《通书》版本在流传,但是这些版本我们今天都已经无法看到了。“长沙本”《通书》编订于乾道二年(后文有详细考证),而《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也与此相当,因此“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长沙本”《通书》,并且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通书》版本。这也为我们研究周敦颐著作的早期流传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总的看来,学界对《诸儒鸣道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完满解决,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该书的精确研究与应用。
首先,关于该书的原刻年代问题。学界对此的讨论仍限于陈来师和顾廷龙先生,别人基本上是在因袭二先生的说法。陈来师据《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上蔡先生语录》和《二程语录》两书判断,“《鸣道集》有可能是在朱熹校定《上蔡语录》至编定《遗书》的十年之间(1158—1168年)编成的。”①陈来师此说跨越了宋高宗绍兴年间到宋孝宗隆兴、乾道年间。但是据该书的避讳情况来看,该书原刻的年代还可以后推至少五年时间。顾先生认为:“此本(指《诸儒鸣道集》)原刻当在孝宗(田按,1163—1189年)时代无疑。”②我们认为,顾先生此说对《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下限的判定有些太晚。事实上,该书所收录的著作有不少在1168年前后出现了更新、更好的版本,如朱子于1166年编订“长沙本”《通书》,此本“视他本最详密”(“长沙本”的编订地点离《诸儒鸣道集》的编刻地点稍远,可能没有被该书的编者及时发现);于1168年重修《上蔡语录》并编订《程氏遗书》;于1173年编订《屏山集》,内含《圣传论》修定本;于1179年编订“南康本”《通书》,是为《通书》定本,《诸儒鸣道集》的编者没有什么理由不采用这些新的版本,而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诸儒鸣道集》编刻之际,这些更新的版本还没有进入该书编者的视野之内,这也意味着,《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要早于这些新版本的面世时间。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判断,我们完全可以把该书的原刻年代限定在乾道初年这个时间段内。对《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问题的解决,也为我们探索该书所反映的时代信息奠定了基础。
其次,该书的编者身份问题。此问题目前只有陈来师有所讨论,此后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沿袭他的结论(或有所修订,如向世陵和方旭东都指出,胡宪不大可能是该书的编者)。问题是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资料能够帮助我们揭开疑问,所以除非有新资料被发现,我们对此只能提出推测而已。不过,大家似乎都默认,《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一定属于道学阵营中人。这一立论前提却是值得商榷的——该书很可能属于坊刻本,其编者与书商的关联或许要比与道学阵营的关联要更紧密。笔者会在后文中对此给出进一步的说明。对我们而言,对该书编者身份的讨论更有价值。试想,如果该书的编者不属于道学阵营,那么我们讨论他们对道学谱系的理解还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其三,关于对道学、道学谱系的理解问题。在其大作《朱熹的思维世界》中,田浩(Tillman,HoytCleveland)先生借助《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提出了自己对道学以及道学谱系的独特理解。他希望道学可以涵盖哲学思辨、文化价值、现实政论三个层面(此为该书余英时先生的序言里的概括)。田浩的提法后来也得到了众多《诸儒鸣道集》研究者们的积极回应:如符云辉和邱佳慧等人。目前学界围绕道学一词的争论颇多,也颇能反映出哲学视角与历史学视角看问题的不同(方旭东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此不赘述。不过,田浩显然认为,《诸儒鸣道集》能反映出道学初期的多元面貌(田浩的本意,应该是指南宋道学初期的面貌),这个所谓的“早期”显然是针对朱子所编的《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而来。但是,《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显然并没有像田浩所认为的那样,要领先朱子编订《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的时间多少。依照陈祖武先生的研究成果,《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与《伊洛渊源录》之大纲所形成的时间基本相当,甚至还要稍晚些①,也仅仅早于《近思录》数年而已,“因此,如果指望从时间领先这一点上为《诸儒鸣道集》更能反映道学面貌进行辩护,其基础不能不说是很薄弱的”①,方旭东君的上述观点颇显中允。事实上,即使是抛开时间问题,田浩的观点也不是没有商榷的余地:在田浩所认为的南宋道学第一时期,他也只能举出张九成和胡宏二人为当时学术多元性的例证(胡宏的著作却没有被《诸儒鸣道集》收录),与之相对,在他所认为的第二阶段,则有朱子与湖湘学派、朱子与吕祖谦等浙学中人的一系列论争;在田浩所认为的南宋道学第三时期,至少还有陈亮、叶适(田浩没有提到)、陆九渊等人与朱子相对,总之,这后两个阶段也未尝不可以“多元”视之。我们认为,《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著作并不限于程朱一系,同时还包含了潘殖、江公望以及司马光、刘安世的著作,我们也可以据此讨论宋代学术的多元化问题(田浩先生的眼界尚不够宽阔)。但是,田浩先生对“道学早期”这一概念的使用颇为随意,《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完全有可能是朱子的同时代人,甚至不一定比朱子年长(在《诸儒鸣道集》原刻之际,朱子已经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并步入中年),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再者,关于道学谱系的问题,田浩等人很希望也把司马光、刘安世等人纳入道学的阵营中,本书对此持相反的观点。在唐宋之际,“道”这个概念相当混乱,至少它是儒释道共同使用的概念,因此才会有“道德为虚位,仁义为定名”的说法。因此,过分扩大“道学”一词的外延,难免会导致此概念内涵的空洞化。事实上,田浩也没有在其著作中贯彻他的想法,他的著作中所收录的人物,基本上不出程门后学的范围。
其四,关于“鸣道本”《二程语录》与《程氏遗书》关系问题。赵振撰长文《〈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集中论证《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都系朱子所编,只不过前者是初稿,而后者是定稿,此观点目前已经基本为学界所接受。不过,细察赵所提出的证据,发现每一条证据都不足以一锤定音。这些证据的组合也还不足以使其观点成为定案。略举其问题明显者如下:
赵的文中提出:
朱熹在编辑《遗书》时曾先编辑了一部初稿,而此初稿编成后即付梓,他在与何叔京的信中谈到过此事,说:“语录倾来收拾数家,各有篇帙首尾,记录姓名,比之近世所行者差为完善。故各仍其旧目而编之,不敢辄有移易。近有欲刻版于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当得其摹本以献,今无别本可以持内也。”[2](p1842)当朱熹拿到刊印的初稿本子时,发现了许多原来没有发现的错误,其《与平父书中杂说》云:“《程氏遗书》细看尚多误字,盖元本如此,今以它本参之,乃觉其误耳。”[2](p1838)于是决定对初稿重新进行校订。但由于自己有许多事务缠身,校订工作时断时续,所以后来他在写给何叔京的另外一封信中说:“语录比因再阅,尚有合整顿处。已略下手,会冗中辍。它时附呈未晚。”[2](p1846)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决定委托许顺之等人对《遗书》初稿进行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校勘,他写信给许顺之说:“向者程舶来求语录本子去刊,因属令送下邑(指同安)中,委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叶学古就城中独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书答之,再送下覆校。千万与二丈三友子细校过。”[2](p1781—1782)并在答复许顺之的信中对校书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曰:“承上巳日书,知尝到城中校书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据旧本为定,若显然谬误,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阙误可疑,无可依据者,宁且存之,以俟后学,切不可以私意辄有更改。盖前贤指意深远,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误后来,其罪将有所归,不可容易。千万千万!”[2](p1782)而这一工作直到乾道四年(1168年)才完成。①(田按,文中的[2],系指《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版;后同)
按照赵在文中的叙述,在时间上应该是先有朱子给何镐(叔京)的第一封信中提到“刊行语录”这件事,然后才会有他在《与平父书中杂说》中提到《程氏遗书》有错误这件事,再后来才有他在给何镐的第二封信中述及“语录”整理工作拖延的情况,最后才是朱子给许顺之的书信,告诫他们要认真校书,其前后顺序应该如此。但是,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从赵的这段文字看,除了《与平父书中杂说》中提到《程氏遗书》外,其前其后的书信提的都只是“语录”,这个《程氏遗书》名称的出现的确让人感到非常突兀;二是赵文中所提到的《与平父书中杂说》这封信的具体写作时间不详,因此这几封信的写作先后顺序是否就是如赵所排列的这样?这一点颇属疑问。陈来师就倾向于认为《与平父书中杂说》作于1168年之后,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是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显然,赵的论证缺乏对此的必要审查,他对朱子书信的排列比较随意。
再如,赵文中又提到:
《遗书》附录中的《伊川先生年谱》多次出现“见《语录》”字样的注文,这里的《语录》当指《二程语录》,因为从《程氏遗书附录后序》中我们得知该序作于乾道四年夏四月,也就是《遗书》修订完稿时,换句话说,《遗书》附录一卷及附录后序编写于《二程语录》刊行之后,故《语录》未载这部分内容。不仅如此,就是《程氏遗书后序》亦作于《遗书》修订完稿时,朱熹在乾道四年写给王近思的信中说:“校书闻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略见编纂之意。”[2](p1798)这里的序当指《程氏遗书后序》,此时王近思正与许顺之等人受朱熹委托在同安城校订《遗书》。并且在该序写成后,朱熹还就此征求过其他人的意见,他在写给林择之的信中说:“《文定祠记》、《知言序》、《遗书》二序并录呈。……三序并告参祥喻及,幸更呈诸同志议之。既欲行远,不厌祥熟也。”[2](p5456)其中《遗书》二序指的就是《程氏遗书后序》和《程氏遗书附录后序》,所以《语录》亦不载《程氏遗书后序》。①
赵认为:《伊川先生年谱》多次出现“见《语录》”字样的注文,这里的《语录》当指《二程语录》”云云,这一说法显然失察。《伊川先生年谱》中“语录”二字凡十见。其中“幼有高识非礼不动”条、“不知者或诮其委曲已甚”条、“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条、“某起于草莱”条、“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条,均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族子至愚不足责”条见于《程氏遗书》卷十九;“范致虚言"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一(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伊川先生病革门人郭忠孝生视之”条见于《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二(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由此可知,至朱子编订《伊川先生年谱》时为止,朱子所提到的“语录”,均包括《程氏遗书》和《程氏外书》的内容在内,是对流传下来的“二程语录”的统称,而非指“统编的程氏语录集”,尤其不能说是指《程氏遗书》或是其初稿或“鸣道本”《二程语录》①。
还如,赵推测:“但令人不解的是,平生治学严谨的朱熹为什么会让这样一个存在诸多问题的《二程语录》本子匆忙面世。笔者推测朱熹之所以这样急于发表自己所编的《二程语录》,很可能是想建立他在二程思想诠释方面的权威地位,并借机削弱其他学派,特别是胡安国家族在这方面所施加的影响,从而使自己在争取道学正统地位的斗争中能处于有利地位……”②此说同样令人生疑。据赵的推测,朱子是主动要发布《二程语录》的,考诸朱子自己的文献记述,此说恐怕不能成立。朱子自己已经反复声明“语录”初稿系被程宪拿走,并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匆匆刊刻的,朱子对此除了去信交涉外,还积极组织对“语录”的重新校对,这怎么能说是朱子主动要发布“初稿”呢?再者,在乾道四年之前,朱子与湖湘学派正处于蜜月期,其思想也正处于“中和旧说”阶段,朱子称赞湖湘学派为学功夫的书信也有很多。无论如何,朱子都不会在此时以争正统为目的主动发布《二程语录》。
一年后,赵振又作《朱熹与二程语录的整理与编辑》一文,对其所提出的观点做出了充实。如,赵又提出:“种种迹象表明,《遗书》初稿(赵认为即“鸣道本”《二程语录》的底本)很可能最初是由张栻刊于严州,朱熹《答吕伯恭》之四云:‘严州《遗书》本子初校未精,而钦夫去郡。今潘叔玠在彼,可以改正,并刻《外书》,以补其遗’”③云云,赵似乎是认为,朱子此信作于1166—1168年之间,此说不确。赵所引的书信为文集卷三十四之《答吕伯恭…前日魏应仲》(田按,实为《答吕伯恭》之五十五)。陈来师判定此书作于淳熙四年(1177年)①,或许有些太晚。但是,这封信却不可能作于1168年朱子正式刊刻《程氏遗书》之前:据杨世文先生考证,张栻于乾道五年(1169年)才由刘珙推荐,“知严州”,而其第二年则被调任回京②。据此,这封信也应该作于此时或稍后。尤其是这段文字中也提到了《外书》,其写作年代更不应该在1168年之前。显然,这封信中所提到的《遗书》,肯定不是指“鸣道本”《二程语录》。赵的观点是错误的。
赵振先生指出《二程语录》出自朱子所编,系《程氏遗书》的初稿,这一点颇有创见,但是其具体的论证过程也有很多的瑕疵。这也值得我们在后文中仔细探讨。
第五,关于《诸儒鸣道集》与周敦颐著作情况考辨的问题。陈来师指出:
据朱熹这些记述(田按,指朱子在“建安本”和“南康本”《通书》后序中的记述),《太极图》及《说》原附于《通书》之末,朱熹初定长沙本时一遵旧例,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后根据潘清逸为周敦颐所作墓志中“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的说法,意识到《太极图说》当是一部独立著作,在建安本才把《太极图说》独立出来并列于《通书》之前,从此《太极图说》便与《通书》分开了。
但是朱熹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井不完全相符。比朱熹更早一些的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说,《通书》一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所传本是也………逮卜居九江,得九江本于其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这就是说《通书》的程门传本有太极图,而九江周敦颐家藏旧本则没有。换言之,《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按照祁氏的说法,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祁氏仅及太极图当系简言之)。今《鸣道集》本亦无《太极图》,因此,如果可以断定鸣道集本早于朱子定本,那就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
这个本子也是今天所见到的《通书》的最早版本。①
现在看来,“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朱子所编订的“长沙本”《通书》当无异议,而综合“鸣道本”与“九江本”《通书》的情况判断,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通书》早期版本的流传分周氏故家藏本和程门传本两个系列,前者未收太极图,而后者则不独收录有太极图,也收录有《太极图说》。但是,“九江本”《通书》中是否如陈来师所推测的那样“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还存在进一步商榷的余地。据笔者判断,“九江本”只是没有《太极图》,却收录有所谓《太极说》,《太极说》具体内容与今天的《太极图说》基本一致。这也足以表明了《通书》早期版本流传情况的复杂性。
杨柱才先生也依据“鸣道本”《濂溪通书》,对《通书》在早期的流传情况有所说明。如他认为:“宋本《诸儒鸣道集》所收《濂溪通书》无《太极图》,当即是祁宽所见九江家藏旧本《通书》”②,此说不确:据朱子所见,“鸣道本”与“九江本”《通书》有很大差距。同时,杨还因袭束景南先生的观点,认为杨方给朱子的九江故家本《通书》系后出者,这一观点也颇值得商榷。
总之,上面提到研究成果和仍存在的问题也是本书立论的前提与基础。我们会在自己材料和视角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给出回应与解答。
《诸儒鸣道集》是唯一由宋人所编纂的一部传世理学丛书,①而且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我国第一部丛书,②该书中所收录的许多著作,也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其版本与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诸儒鸣道集》,系由黄状猷在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修补后印本,而非原刻本。关于此修补印本的基本状况,学界多有介绍:
如,在清人潘祖荫所著的《滂喜斋藏书记》一书中提到《诸儒鸣道集》:“所采诸儒语录,自濂溪、涑水以下凡十三家。《濂溪通书》一卷、《涑水迂书》一卷,横渠《正蒙》八卷、《经学理窟》五卷、《语录》三卷,《二程语录》二十七卷、《上蔡语录》三卷、《元城语录》三卷、《刘先生谭录》一卷、《道护录》一卷、《江民表心性说》一卷、《龟山语录》四卷、《安正忘筌集》十卷、《崇安圣传论》二卷、《横浦日新》二卷。后有楷书题记云:‘越有《诸儒鸣道集》最佳,年久板腐字漫,观者病之,乃命刊工剜蠹填梓,随订旧本,锓足其文,令整楷焉。时端平二禩八月吉日,郡守闽川黄壮猷书。’每半叶十二行,行廿一字,内缺《迂书》一卷、《理窟·第五》一卷、《二程语录》第八至十九卷,皆钞补明文渊阁官书,其书函犹原库装也,至今不蠹不脱,触手如新,昆山徐氏旧藏。”③
顾廷龙先生也提到《诸儒鸣道集》:“此本框高十九点三公分,宽十四公分,半页十二行,行廿一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字仿欧体,皮纸精印”①云云。
《诸儒鸣道集》一书,共收录宋儒周敦颐、张载、二程、司马光、杨时、谢良佐、刘安世、潘殖、刘子翚、江公望、张九成十一位学者的著作共十五种。对于该书所收录的各种著作,前贤多已经有过详细的说明,现择其要并结合本人的校读资料,有选择的说明如下:
周敦颐的《濂溪通书》一卷
“鸣道本”(指《诸儒鸣道集》所收录该书的版本,下同)《濂溪通书》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的《通书》,也要早于朱子所整理的“长沙本”《太极通书》。《濂溪通书》与世传本的《通书》(即朱熹所编订的“南康本”《太极通书》)在内容上也颇有不同。《濂溪通书》最引人注目之点在于,书中并没有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这颇能引起我们对《通书》早期流传问题的关注。
朱子在《太极通书后序》(即朱子所编订的“建安本”《太极通书》的后序)一文中曾指出:“右周子之书一编,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矣,然犹有所未尽也……”②在这里,朱子所说的“未尽”,应该是说在“建安本”《太极通书》之前的《通书》诸版本,都是把《太极图》附于末尾,“此则诸本皆失之”这一点吧。对此,陈来师已经指出,朱子的上述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因为祁宽的《通书后跋》一文已经指明“九江本”《通书》无《太极图》这一事实(据本报告考证,“九江本”中确实收录有《太极说》,即《太极图说》),而“鸣道本”《濂溪通书》则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并表明《通书》早期流传情况极为复杂,即有不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版本(如“鸣道本”),也有只收录《太极图说》却不收录《太极图》的版本(临汀杨方所见“九江本”),还有完整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程门传本。从上述情况看,《通书》早期版本的流传,有一个逐渐被充实、丰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朱子手中最后完成的。
“鸣道本”《濂溪通书》与朱子所编的“南康本”《太极通书》①(下文中简称为“南康本”)之间,在具体文字上也稍有不同,详列如下:
第一,《诚几德》章:“发微不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南康本”作:“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②“鸣道本”似有脱字。
第二,《师》章:“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惟中者,和也……暗者求于明师道立矣”,“南康本”则作:“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惟中也者,和也……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③两相比较,“南康本”为优。
第三,《化》章:“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民,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噫,道岂远乎哉?”“南康本”题为《顺化》章,作:“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道岂远乎哉?”④从此句的排比句式判断,前一处“南康本”作“物”字为优,而后一处“鸣道本”有“噫”字为优。
第四,《礼乐》章:“阴阳理然后和”,“南康本”作:“阴阳理而后和”,⑤二者可并存。
第五,《务实》章:“德业未有著”,“南康本”同,今理学丛书本《周敦颐集》则作“德业有未著”,⑥为优。
第六,《爱敬》章:“孰无过,乌知其不能改”,“南康本”作:“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⑦据下文判断,“鸣道本”为优。
第七,《乐》章:“古圣王制礼法”,“南康本”题为《乐上》章,作:“古者圣王制礼法”,⑧“南康本”为优。
第八,《圣学》章:“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南康本”作:“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①“鸣道本”显有脱字。
第九,《颜子》章:“夫富贵,人所爱者也”,“南康本”作:“夫富贵,人所爱也”,②“南康本”为优。
第十,《圣蕴》章:“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不复也。孔子曰:‘予欲无言……’”,“南康本”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子曰:‘予欲无言……’”③。
第十一,《乾损益动》章:“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非(一本无非字)是过”,“南康本”无双行夹注,也无“非”字④。
第十二,《家人睽复无妄》章:“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无妄则诚焉”,“南康本”作:“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无妄则诚矣”,⑤可两存。
第十三,《刑》章:“既成矣不止即过焉”,“南康本”作:“既成矣不止则过焉”,⑥“南康本”为优。
第十四,《孔子》章:“王祀孔子报德报功无尽焉……实与天地参而四時同者”,“南康本”作:“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实与天地参而四時同”⑦。
第十五,《蒙艮》章:“山下出泉静而止(双行夹注:一作而清也)”,“南康本”无双行夹注,作“山下出泉静而清”⑧。
就二者的刊刻质量而论,“南康本”明显为优,这并不令人奇怪。不过,“南康本”却有两处明显不及《濂溪通书》。由此可知:其一,朱子在编订“南康本”时,并没有参考《濂溪通书》,否则他会据此来改正“南康本”中的错误。其二,与朱子所提到的“九江本”及“胡宏本”《通书》相比较,《濂溪通书》的错误更少。其三,《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不选在当时更为流行(也更容易得到)的程门传本的《通书》,却选择《濂溪通书》,原因待考。但是,这或许说明,其与程门之间未必有直接师承渊源关系。
就二者刊刻的时间而论,“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南康本”《太极通书》,乃至“长沙本”《通书》,这一点当无疑义。例如,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即在《濂溪通书》中,有一处作“孔子曰”、另一处作“孔子”,而在“南康本”中,则分别变成了“子曰”和“夫子”,这些细微的差异其实是有深意的:后者之称谓更为“亲切”,也流露出对儒家道统更为强烈的认同感。我们基本可以判定,称“孔子曰”和“孔子”的《濂溪通书》更接近周敦颐的原稿,原因是假定周敦颐的原稿作“子曰”和“夫子”,其在后来是不大可能会被改作“孔子曰”和“孔子”的(此一点,系受王博老师讲授《论语》时的启发,特表感谢)。
不过,“鸣道本”《濂溪通书》的编订年代也不可能太早,因为该书中三次出现以双行夹注“一本”或“一作”形式出现的校勘痕迹(除上文中给出的例子外,另外一次出现在《濂溪通书》的《理性命》章中)。这足以说明,《濂溪通书》的编者(不一定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在编订《濂溪通书》时,至少是参考了当时流行中的,两个以上版本的《通书》,因此《濂溪通书》本身不可能是《通书》最早的版本,其编订年代很可能要在南宋之后。至于《濂溪通书》中为什么不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原因存疑。当然,《濂溪通书》的编者很可能也认为《太极图》或《太极图说》本身就不属于《通书》,尤其是如果他们见到的《通书》版本是把《太极图》或《太极图说》附在文后的话。
司马光的《涑水迂书》一卷
“鸣道本”《涑水迂书》与世传的四部丛刊影宋本《迂书》(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四)的内容基本相同。此二书与四库全书本《迂书》(收入四库本《传家集》中)比较,则又有一定的差异。如,“四库本”《迂书序》有双行夹注“嘉祐二年作”云云,为“鸣道本”和四部丛刊本所无;“四库本”《知非》条下有双行夹注“嘉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作”,也为“鸣道本”和四部丛刊本所无;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天人·迂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理性》、《事亲》、《事神》、《宽猛》、《无益》、《学要》、《治心》、《文害》、《道大》、《道同》、《绝四》、《求用》、《负恩》、《羡厌》、《老释》、《凿龙门辨》、《无为赞》诸条,“四库本”都有双行夹注注明了其具体写作年代,这都是“鸣道本”和四部丛刊本所无。又如,此二书的《无为赞贻邢和叔》,“四库本”只作《无为赞》,可知“鸣道本”《涑水迂书》更接近司马光的原稿。
另外,“鸣道本”和四部丛刊本《涑水迂书》明显不同于“四库本”《迂书》之处,是缺少《天人·迂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条。“鸣道本”《涑水迂书》本为清人配抄,是否有所遗漏,待考。
张载的《横渠正蒙书》八卷
“鸣道本”《横渠正蒙书》八卷是目前仅见的宋刻全本《正蒙》,也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正蒙》刻本。林乐昌先生以为:“在《正蒙》的两个明本之前,再向前追溯,还有两个宋本,按时间先后看,一是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国朝二百家明贤文粹》书隐斋刻本所收《正蒙书》上下太极图二卷,简称文粹本;二是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诸儒鸣道》浙刻本所收《横渠正蒙书》八卷,简称鸣道本。由于早于鸣道本的文粹本只是节选本,故当以鸣道本为《正蒙》之祖本,而文粹本则仍有重要的对校价值。”①这里,林先生显然是把《诸儒鸣道集》的再刻时间当成了它的原刻时间,其说不确。
陈来师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以及《直斋书录解题》等书指出,宋代流行的《正蒙》基本上为十卷本,而“鸣道本”《横渠正蒙书》则为八卷本,“鸣道本”所缺的是“胡安国所传编为一卷”和“末有行状一卷”,而非缺《正蒙》的正文。②但是,胡安国所传一卷的内容具体究竟是“传”(zhuan),还是“所传(chuan)者”,目前还不确定。
“鸣道本”《横渠正蒙书》与《张子全书》本《正蒙》比较,内容基本相同。今中华书局本《张载集》中的《正蒙》,点校者根据《横渠易说》、《周易系词精义》、《宋元学案》、《张子正蒙注》等书,指出《张子全书》本《正蒙》存在着大量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却又都出现在“鸣道本”《横渠正蒙书》中。由此可知,《正蒙》的初稿很可能已经包含有这些“错误”了。具体原因,应该是张载在撰写《正蒙》时,多是仅凭记忆随意来转述他早年的研究成果所致。
“鸣道本”《横渠正蒙书》在具体内容上与“张载集本”《正蒙》也稍有不同。①如《大易》篇“洁净精微,不累其迹”条,“鸣道本”后有双行夹注:“一本云‘深于易矣’”,此双行夹注为其他诸本所无。②又如,《乐器》篇“亲亲尊尊又曰亲亲尊贤”条,“鸣道本”后有双行夹注:“一本先得作先将”,此双行夹注也为其他诸本所无。同篇“义民安分之良民而已”条,“鸣道本”后有双行夹注:“一本‘准牧’下有‘无’字,併为一节”,为其他诸本所无。③再如,“鸣道本”的《乾称》篇中,则有数条错误:
其一,“凡可状皆有也”条,“鸣道本”作:“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因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舍气有象否?非象有意否?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
此条在“四库本”被分为三条:
“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
“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舍气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
“张载集本”此条也被分为三条:
“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舍气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①
综合比较,只是“张载集本”对于双行夹注的处理才是正确的,“鸣道本”把三条内容放在一段中,最不恰当。
其二,“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条和“大学当先知天德”条,“鸣道本”作:“浮屠明鬼,有识之死,受生循环,厌苦求免,可谓知乎?以人生为妄见,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
“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极论要归,必谓死生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悟则有义、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昼夜、通阴阳,体之不二。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其俗达之天下,致善恶、知愚、男女、臧获,人人著信,使英才间气,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驱,因谓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故未识圣人心,己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自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
“四库本”此两条合为一条,作:“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以人生为妄,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惑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极论要归,必谓死生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悟则有义、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昼夜、通阴阳,体之不二……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
“张载集本”与“四库本”相同,只不过是由点校者依据《宋文鉴》把“四库本”中的双行夹注改为了正文。这样,“鸣道本”中本有两段双行夹注,在“四库本”中变成了一段,而“张载集本”则把“鸣道本”中双行夹注的内容都变成了正文。中华书局点校者指出,“浮屠明鬼”条文字又称《与吕微仲书》,收入《张载集》第350页,作:“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亦出庄生之流。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以人生为妄见,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者,惑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极论要归,必谓生死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悟则有义、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昼夜、道(当为通字)阴阳,体之不二……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①
比较上述四者可知,“鸣道本”、“四库本”、“张载集本”各有失误也各有所长,当以《与吕微仲书》为准(也可能张载在编撰《正蒙》时,未严格对照《与吕微仲书》,故《正蒙》与《与吕微仲书》未必完全一致)。
第三,“益物必诚”条,“鸣道本”后有双行夹注:“铭诸牅以自诏”,此为今本所无。②
第四,“戏言出于思”条,“鸣道本”作:“戏言出于思也……引咎其不出汝者,长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张载集本”作:“戏言出于思也……归咎其不出汝者,长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中华书局点校者指出,在《宋文鑬》中,“归咎”已经误作“因咎”,可知出現的时间应该很早。③
综合判断,虽然“鸣道本”《横渠正蒙书》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宋刻全本《正蒙》,但却不是最好的版本。我们对张载著作的研究也不能完全以此为据。此外,通过对今流行的各《正蒙》版本与“鸣道本”《横渠正蒙》的比较可知,《正蒙》的双行夹注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而是由作者的“原注”和该书的整理者逐渐添加而成的,且各版本之间在双行夹注内容上也不尽一致。
再者,在《横渠正蒙书》的夹注中,屡屡提到的“一本”如何如何,这一事实表明,该书的编订同样参考的两个以上的底本,其编订时间同样不会太早,很可能晚于北宋末年。
张载的《横渠经学理窟》五卷
“鸣道本”《横渠经学理窟》受人关注的是它的卷数问题,以及其与“二程语录”之间的内容重叠问题。在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提到:“《理窟》二卷,右题金华先生,未详何人,为程张之学者”,而在赵希弁的《郡斋读书志附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则都提到《经学理窟》为一卷本,而“鸣道本”《横渠经学理窟》则为五卷,与今通行本同。陈来师怀疑《附志》有误。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在宋代已经有虽卷数不同,但内容基本相同的多种《经学理窟》版本在流传,而目前传世的《经学理窟》本则与“鸣道本”一致,为五卷。
关于《理窟》中的某些内容与《二程语录》重复的问题,张岱年先生指出,这些重复内容“从大部分的题材语气来看,又确像张载的话”,张先生怀疑此书或为张载与二程之“语录”的汇编。今人赵振对此也有较为详细的考证:他详细考辨了二书中二十二条内容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条目,指出其中绝大多数内容当出自张载,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一些程颐的话。他同时指出,两书重复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见于《二程遗书》中由关中学者所记的第二卷(包括上、下两卷)和第十五卷”。①从常理推测,或许是程颐回应或者是转述张载的某些言论,或者是与张载讨论某问题的言论,被后学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上述的重复内容。
与世传通行本《经学理窟》(中华书局《张载集》本)相比,“鸣道本”《横渠经学理窟》也有多处不同:
其一:《学大原上》章“道理今日却见分明”条:“道理今日却见分明……上又见性与天道,他日须胜孟子,门人如子贡子夏等人,必有之乎”。
“张载集本”作:“道理今日却见分明……下面又见性与天道,他日须胜孟子,门人如子贡子夏等人,必有之乎”,两相比较,鸣道本为优。①
其二:《学大原上》章:“人早起未尝交物须意锐精健”条:“张载集本”中“锐”误作“鋧”字,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②
其三:《学大原下》章:“张载集本”之“教之而不受”条:“教之而不受,虽强告之无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纳也。今夫石田,虽水润沃,其干可立待者,以其不纳故也。庄子言‘内无受者不入,外无主者不出’”条,③此条内容不见于“鸣道本”。
其四:《学大原下》章:“鸣道本”之“学者以尧舜之事”条:“学者以尧舜之事,须刻日月要得之,犹恐不至,在可媿而不为,此始学之良术也”。
“张载集本”作:“学者不论天资美恶,亦不专在勤苦,但观其趣向,著心处如何。学者以尧舜之事须刻日月要得之,犹恐不至,有何媿而不为,此始学之良术也。”④“鸣道本”显有脱文。
第五:《学大原下》章:“鸣道本”作:“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自出,若安坐则何尝有疑”。
“张载集本”作:“学行之乃见,至其疑处,始是实疑,于是有学(点校者注明,此四句从《易说》佚文移此)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自出(原文为出自,点校者依照《宋元学案》改正),若安坐则何尝有疑”。
第六:《学大原下》章:“大抵人能洪道”条,“洪”字为因避讳而改字,“弘”为本字,“张载集本”不误。⑤
第七:《学大原下》章:“世儒之学正”条:“世儒之学,正惟洒扫应对,便是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于此不阙文”。
“张载集本”作:“世儒之学,正惟洒扫应对便是,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⑥
两相比较,“鸣道本”为正。
第八:《自道》章:“家中有孔子真尝欲置于左右”条:“则至于不敢拜”,“张载集本”的底本“拜”字误为“伐”字,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①
其九:《自道》章:“上曰慕尧舜者不必”条:“如岂则岂可无其迹”,“如岂”为“如是”之误,“张载集本”不误。②
第十:《自道》章:“某自今日欲正经为事”条:“故不免须责于家人辈”,“责”字,“张载集本”的底本误为“贵”字(四库本却不误),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③
第十一:《祭祀》章:“无后者必祭”条:“干袷及其高祖”,“干”字,“张载集本”的底本误为“子”字(四库本却不误),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④
第十二:《祭祀》章:“七庙之主聚于太祖者”条:“且祧者当易檐”,“檐”字,“张载集本”的底本误为“担”字,已经被点校者改正。⑤
综上所述,“鸣道本”在总体上错误比今通行本要少,但是本身也有许多错误。“鸣道本”《横渠经学理窟》同为清人配抄,与“鸣道集”原本是否有差异,不详。
张载的《横渠语录》三卷
“张载集本”《张子语录》(底本为南宋吴坚刻本)在刊刻时,已经依照“鸣道本”校订过,二者的详细异同,可参看《张载集》的相关章节,此处从略。
概言之,“鸣道本”中也有一些错误,不可以为准绳。
二程的《二程语录》二十七卷
“鸣道本”《二程语录》与今通行本《程氏遗书》差距最大,受学界的关注也最多。关于二者之间的详细差距,本书拟作为个案详加讨论,这里仅略论其大概。
目前,关于“鸣道本”《二程语录》的突出研究成果,是赵振所指出的,《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大同小异,二者同为朱子所编订,只不过前者是初稿,后者是修订稿,①赵先生的结论可谓是不刊之论,但是其论证过程并非无懈可击。
谢良佐的《上蔡先生语录》三卷
陈来师指出,“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当出自朱子定本。据朱子《谢上蔡语录后序》云,三卷本的《上蔡语录》是他在“括苍吴任写本一篇(题曰《上蔡先生语录》)”、“吴中板本一篇(题曰《逍遥先生语录》)”,以及从胡宪那里得到“胡文定公家写本二篇(题曰《谢子雅言》)”这四篇原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四篇原稿当中:“胡氏上篇”是“胡本”所独有的,专门记录胡安国与谢良佐之间的问答,被朱子编为《上蔡语录》卷上;“胡本”的下篇“与板本、吴氏本略同,然时有小异”,但内容更为精练,朱子综合三本异同,定为《上蔡语录》卷中;“板本”与“吴本”、“胡本”比较,则多出“百余章”,被朱子精简为三十余章,定为《上蔡语录》卷下,是为《上蔡先生语录》三卷定本。“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也正是三卷本,且与朱子定本内容基本一致,必然出自朱子的整理。关于此本与后来诸《上蔡语录》版本之间的异同情况,北大哲学系的韩国留学生李根德君有《谢良佐〈上蔡语录〉研究》之硕士论文,对此有极为详细的比较,此不赘述。
此外,笔者在对“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的分析中发现,此版本与朱子在绍兴二十九年和乾道四年所编订的两个版本的《上蔡语录》相比,均有细微的差别(具体差别见后文),由此判断,“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的底本很可能就是被人在江西盗刻的版本,本文称之为“盗印本”。
刘安世的《元城先生语》三卷
关于刘安世以及“鸣道本”《元城先生语》三卷的情况,台湾的邱佳慧博士在其硕士论文《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②中都有详尽的说明。据《元城先生语录序》①介绍,《元城先生语录》编订于绍兴五年②(1135年)正月。邱文提到:“《元城语录》目前所见者有三,分别为上海图书馆所藏《诸儒鸣道集》中《元城语录》;《丛书集成新编》收马永卿辑、王崇庆注解、崔铣编行录与钱培名补脱文的《元城语录解》;以及《四库全书》的版本”。③经查,《元城语录解》同时也被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中,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④该书的整理者注明,其所参考的版本有惜阴轩丛书本、小万卷楼丛书本和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元城先生语录》所据的底本是惜阴轩丛书本,此外又根据小万卷楼丛书本补充了脱文。
“鸣道本”《元城先生语》与《元城语录解》比较,最明显的不同是未收录见于后者的张九成作于绍兴六年(1136年)的序(应该是节本)。邱文即据此判断:“可见《元城语录》一书语此时(田按,此处“此时”所指不详)分了至少两条路线流传,其一为王崇庆注解本,较广为人知的版本;其二是《诸儒鸣道集》所收的版本,亦应是马永卿所著作的原本”。⑤邱这个判断还缺乏足够证据的支持,因为注解本究竟出现于何时,这目前还是个疑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诸儒鸣道集》刊刻之际,社会上应该有带有张九成序的另一个版本的《元城语录》在流行。这也从侧面说明,《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张九成的关系并不十分亲密,否则他们在编刻《诸儒鸣道集》时,完全应该选择收录此序言之版本的《元城先生语》。
再者,“鸣道本”《元城先生语》与《元城语录解》相比,更为完整、精确。二者“时有一二字不同”,但《元城语录解》脱《元城先生语》中的第二十一条(“先生一日仆闲言语”条⑥)约数百字,便是明证。
刘安世的《刘先生谈录》一卷、《刘先生道护录》一卷
此二书仅依靠《诸儒鸣道集》得以流传至今,此外并无其他版本传世以便比较。但是,正如邱文所指出的,《直斋书录解题》标明《道护录》为一卷十九则,《郡斋读书志附志》则说《道护录》为二卷(田按,疑为“一卷”之误)十九则,①今“鸣道本”《刘先生道护录》却只有十五则,恐有缺文,亦或并非善本。
江公望的《江民表心性说》一卷
江公望字民表,关于他的资料,除了《宋史》中的记载之外,多又见于宋人宗晓所编的《乐邦文类》、明人夏树芳所辑的《名公法喜志》、清人彭际清所述的《居士传》中。据上述资料来看,江公望曾经“作《念佛三昧咏》,大劝于世”②;“……居常与妻俞氏蔬食清斋,修念佛三昧,著《念佛方便文》曰:‘世出世间之法,欲得成办省力,莫若系心一缘,即如称念阿弥陀佛,有巧方便,无用动口,不出音声,微以舌根敲击前齿,心念随应,音声历然,声不越窍,闻性内融,心印舌机,机抽念根,从闻入流,反闻自性,是三融会,念念圆通,久久遂成唯心识观。若是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无所,六根杳寂,诸识消除,法法全真,门门绝待,瞥尔遂成真如实观。初机后学,一心摄念如来,乃至营办家事种种作务,亦自不相妨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过旬月便成三昧。所谓自心作佛,自心是佛,自心见佛’……”③;而夏树芳则提到江:“尝著《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劝道俗。又尝书于家塾曰:‘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无所,六根杳寂,诸识销落,法法全真,门门绝待,瞥尔遂成,真如实观。初机后学,一心摄念如来,即使营办家事,种种作务,亦自不相妨碍。若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过旬日,便成三昧。是故上根大器,一念直超;平展之流,善观方便”。④上述三条文献对江公望文献的说明颇有矛盾,但也说明江公望的数篇文字的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
江公望传世的文献,除了上述《念佛三昧文》和宋史列传中的片段文字之外,就是因《诸儒鸣道集》而得以流传的《心性说》了。江公望还曾有部分文字混入吴中版本的《逍遥先生语录》(实际出自江的《辨道录》)中,但是被朱子在整理《上蔡语录》时删除,今已不传。
江公望《性说》引人注目之点在于注重区分正性和习性之不同。依照江公望的逻辑,“正性”即所谓“空无自性”,这一观念明显来自于佛教,江公望又指“正性”为“全性”;而“习性”即所谓习(江强调,习即是学)得之性,善恶、智愚、凡圣等都被他视为“习性”。江公望认为,“正性”不同于“习性”,亦不离“习性”。孔子所论之性和《尚书》重所强调的,只是“习性”,强调的是“学之不可已也”。总的看来,江公望对“性”的解释显然是受到了“佛性”论的影响,而在宋代士大夫中,江公望当属于溺佛颇深者之列。
杨时的《龟山语录》四卷
《直斋书录解题》云:“《龟山语录》五卷,延平陈渊几叟、罗从彦仲素、建安胡大原伯逢所录,杨时中立之语及其子迥汇稿共四卷,末卷为附录墓志遗事,顺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①这是说,五卷本的《龟山语录》中,前四卷为杨时的女婿陈渊、杨的弟子罗从彦和杨的后学胡大原所编,第五卷则为朱子弟子廖德明所汇集。又,稍后赵希弁的《郡斋读书志附志》,则收录有《龟山先生语录》四卷,可知应该是先有一个四卷本的《龟山语录》流传,随后才有五卷本的《龟山语录》面世,而“鸣道本”《龟山语录》正好是四卷本,当为早期流传的《龟山语录》版本。
胡大原为湖湘学派主将之一,师从胡宏,曾参与四卷本的《龟山语录》的编订工作。据王立新先生为点校本《斐然集崇正辩》撰写的前言称,胡寅于宣和六年(1124年)四月,得子胡大原。据此可知,胡大原年长朱子六岁,小于张九成,四卷本《龟山语录》形成的时间很可能要晚于《横浦日新》面世的时间,而且只是被收录入《郡斋读书志附志》中。
与南宋末年的五卷本《龟山语录》(四部丛刊续编所收南宋末吴坚刻本,简称“吴本”)相比,“鸣道本”与之稍有异同,但是差距并不大。
第一,“问孔子曰中庸之为德”条:“极,犹室之极,所处中则至矣”,“吴本”则脱“中”字。①
第二,“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条:“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役于身体”,“役”字,“吴本”误为“设”字。②
第三,“吕晦叔真大臣其言简而意足”条:“臣”字,“吴本”作“人”字,怀疑为因避讳而改字。③
第四,“朝廷设法卖酒所在官吏”条:“往往民间得钱遂用之”,“吴本”作:“往往民间得钱遂用之有方”二字,“鸣道本”疑为脱文。④
第五,“天生聪明时■所谓天生者”条:“然后可以制人而止其乱。曰:‘夫聪明……”,“夫”字,“吴本”误作“天”字。⑤
第六,“世之事鬼神所以陷于淫谄者”条:“汉儒信祖有功、宗有德”,“信”字,“吴本”作“言”字。⑥
第七,“吕吉甫解孝经义”条:“故孔子以其而尽告之”,“吴本”同:“故孔子以其未晓而尽告之”,“鸣道本”和“吴本”皆有脱文。⑦
第八,“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条:“孟子以恻隠之心為人之端”,“人”字,“吴本”作“仁”字,“鸣道本”当为因避讳而改字。⑧
第九,“因言秦汉以下事”条:“六经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鸣道本”此条以下有大量脱文,⑨约有五百字,据“吴本”,“鸣道本”此处脱“因言秦汉以下事”条部分文字、“盥而不荐初未尝”条全部、“又云无诚意”条全部、“予欲观古人”条全部、“棠棣之言朋友”条全部和“问所解论语犯而不校”条部分,该书的脱文怀疑为脱页所致。
第十,“孟子一部书只是要正人心”条:“孟人遇人便道性善”,“孟人”乃“孟子”之误,“吴本”不误。①
第十一,“曾见志完云上合下”条:“吴本”则作:“谓曾见志完云上合下,。②
第十二,“叔孙通作原庙是不使人主改过”条:此条在“吴本”中被分为两条,即“叔孙通作原庙是不使人主改过”条和“勿意只是去私意,若诚意则不可去也”调,③“勿意只是去私意”条末有夹注标明:“重见”。
第十三,“问易曰乾坤其易之门邪”条:“如某与定夫相会,亦未尝及(抹去四字)定夫学易”,“吴本”则作:“如某与定夫相会,亦未尝及从可,某常疑定夫学易”,④此处当以“吴本”为准。
第十四,“字说所谓大同于物者”条:“若离人而之天,正所谓顽空(抹去一字)总老言经中说十识”,⑤据“吴本”,抹去的应为“通”字。
第十五,“伊川语录云以忠恕为一贯”条:“问中庸发明忠恕之理(抹去一字)有一贯之意”,⑥据“吴本”,抹去的应为“以”字。
综合判断,“鸣道本”《龟山语录》既有抹字的情况,也有脱文的情况,表明其刊刻颇为匆忙,但是与“吴本”相比,仍然能够校订出其不少错误,“鸣道本”显然与原稿更为接近。
潘殖的《安正忘筌集》十卷
目前学界对《安正忘筌集》的讨论不多,也只有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先生曾写过以“忘筌集”为题名的论文。与续修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上下两卷本《安正忘筌集》(明万历刻本,题为潘植作,前有焦竑序)⑦以及该书的清刻本《浦城遗书》本相比,二者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十卷本的“鸣道本”《安正忘筌集》更为完整。如顾廷龙先生就指出:“又如《安正忘筌集》,《浦城遗书》本缺《河图数图》与《洛书数图》……”①,而“鸣道本”则非常完整。
在具体文字上,该书的“鸣道本”与万历本也有所差异。
其一,《宅心》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蕴太极于中,是为天地之心”,“万历本”中“于”字误为“之”字,意思全别。②
其二,“万历本”《图书奥旨》章末“理彰于事可因”之后,有一页文字与《蓍卦》章中“于此用事而洞”后一页文字颠倒③,而“鸣道本”不误。
综合判断,“鸣道本”《安正忘筌集》要明显优于“万历本”。
刘子翚的《崇安圣传论》二卷
刘子翚(1101~1147年),字彦冲,一作彦仲,号屏山,建州崇安人。顾廷龙先生认为,刘的著作“……《崇安圣传论》等著作仅赖此书(田按,指《诸儒鸣道集》)得以传世”④,其实此说法不确。四库本《屏山集》卷一中的《圣传论十首》(简称“屏山集本”),此即《崇安圣传论》也。二者相比,“鸣道本”为二卷,而“屏山集本”则仅为一卷,同时题目也稍有差别:“鸣道本”每章题目为“尧舜(一)、禹(仁)、汤(学)、文王(力)、周公(谦牧)、孔子(死生)、颜子(复)、曹子(孝)、子思(中)、孟子(自得)”,而“屏山集本”的目录仅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颜子、曹子、子思、孟子”。此外,在具体内容上,“鸣道本”与“屏山集本”⑤相比,也出入颇大。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崇安圣传论》为刘子翚的初稿,而《圣传论十首》则为修订稿(形成年代不晚于1147年)。这当中,《圣传论十首》有数篇文章的结尾被完全重写,而十篇的全文均经过较大的改动,兹将二者的详细比较附于书后,以便阅者查考。
关于《屏山集》,胡宪和朱子都曾提到该书整理的过程:
……乃遽哭其丧,是年予盖六十有一而彦冲甫四十七……越十有三年,其嗣子玶始编次其遗文,凡得古赋、古律、诗、记、铭、章奏、议论二十卷,目曰《屏山集》……绍兴三十年六月朔,籍溪胡宪序。①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玶所编次,已定,可缮写(《朱子全书》原文点断如此,当断为“编次已定,可缮写。”)。先生启手足时,玶年甚幼,以故平生遗文多所散逸。后十余年,始复访求,以补家书之缺,则皆传写失真,同异参错而不可读矣。于是反复雠订,又十余年,然后此二十卷者始克成书,无大讹谬。熹以门墙洒扫之旧,幸获与讨论焉。窃以为先生文辞之伟,固足以惊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学,静退之风,形于文墨,有足以发蒙蔽而销鄙吝之萌者,尤览者所宜尽心也。因书其故以告后之君子。乾道癸巳(1173年)七月庚戌门人朱熹谨书。②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二载:“右正言何若言:自赵鼎唱为伊川之学,高亢之徒从而合之,乃有横渠《正蒙书》、《圣传十论》……”③据此可知,《圣传论十首》形成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之前。不过,《屏山集》初编于1160年,晚于刘去世十多年,定编于1173年,晚于刘去世近三十年。这颇能说明刘后继乏人的现实。
此外,在“鸣道本”《崇安圣传论》中多次出现的“钦”字,在“屏山集本”中都被改为“敬”字,笔者怀疑这与避讳宋钦宗的庙号有关。若果真如此,则“鸣道本”的底本当完成于北宋,而“屏山集本”则完成修订于南宋初年。“鸣道本”《崇安圣传论》,也为我们判断《诸儒鸣道集》编者与刘子翚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材料。《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所以会选取《圣传论》早期流传的版本,而不选择“屏山集本”,这从侧面说明他们与刘子翚的关系比较疏远,也更不可能是刘的后学或是弟子。
张九成的《横浦日新》二卷
“鸣道本”《横浦日新》与世传本(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八十三册,收录有《横浦日新》一卷本)略有差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录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明吴惟明刻本,题为张九成的外甥于恕辑。我们则认为,一卷本所标的作者是错误的,于恕只是于淳熙元年(1174年)辑录了《横浦心传录》三卷,而明人则在刊刻该本时,误将《横浦日新》的作者标成了于恕。这是因为,于恕在其本人所作的《无垢先生横浦心传录序》中已经说明:“予学生郎晔,粗得数语,纂为所录,而士大夫已翕然传诵,信知舅氏一话一言为世所重如此”①云云,文中所指的“粗得数语,纂为所录”,显指《日新》,再结合《郡斋读书志附志》中的例证,于恕此处所指,必为《横浦日新》无疑。
在具体文字上,“鸣道本”《横浦日新》与世传本完全相同。
二《诸儒鸣道集》的研究现状
关于《诸儒鸣道集》近来受到学界关注的过程,陈来师曾著文有所说明:
在北图找“心统性情”的时候,因看到《张载集》中“张子语录跋”提及“鸣道集本”,便问张先生是否要去看看,张先生说:“其书全名是《诸儒鸣道集》,在北京图书馆,你可以去查查。”于是我就在北图将《诸儒鸣道集》通看一遍,虽然没有查到“心统性情”,但也觉得有收获。由于北图的本子是影宋本,上海图书馆则藏有宋本,我也曾写信到上图询问宋本的序跋情况。情况摸了一遍以后向张先生报告,张先生要我写成文章,经过张先生看过,后来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田按,即《略论〈诸儒鸣道集〉》一文)。我还记得,文中所引黄壮猷的序,原文“时”字是用的讹字,我不认识,也没去查字典,就照抄录下,是张先生将这个字改为通用字,以后我才认得这个字。1986年初,一次在从香山回来的汽车上,杜维明先生说上海图书馆向他介绍《诸儒鸣道集》,他觉得很有价值。张先生即说:“陈来已经写了文章了。”后来杜先生要我把文章影印给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律先生,要燕京图书馆购藏此书。①
后经杜先生推荐,山东友谊出版社于1992年将《诸儒鸣道集》影印出版,此后该书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4年影印线装出版,②其影响也迅速扩大。
在历史上尤其是思想史上,《诸儒鸣道集》长期无人关注,而在陈来师的文章面世之后,《诸儒鸣道集》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并迅速形成了一系列热点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类为:
其一,概括介绍类:以陈来师和顾廷龙先生、方旭东的三篇文章为代表,③旨在对《诸儒鸣道集》的基本情况做出介绍,并对该书的原刻年代、作者身份等问题做出初步的分析判断。
其二,综合研究类:以复旦大学符云辉博士的博士论文《〈诸儒鸣道集〉述评》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邱佳慧博士的博士论文《〈诸儒鸣道〉与道学之再检讨》为代表。这两篇博士论文都对《诸儒鸣道集》有全面的分析研究,其研究思路也大致相同。
其三,围绕《诸儒鸣道集》某一问题的专题性研究,以赵振的一系列论文为代表,单篇文章集中解决一个问题,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如对“鸣道本”《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之渊源关系的分析、对“鸣道本”《二程语录》与张载《横渠经学理窟》之内容重叠的分析等。
其四,借助《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进行拓展性的研究,以杨柱才、林乐昌等人为代表,分别引用该书中的资料来研究周敦颐和张载的著作与思想。
其五,由《诸儒鸣道集》引申的一系列讨论。如田浩、葛兆光等围绕该书所引申出的,关于宋代学术多元化、道学、道学谱系问题的一系列的讨论。
学界目前对《诸儒鸣道集》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热点上:
其一,该书的原刻年代与编者身份。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切材料来确定该书的原刻年代和编者的身份。不过,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判断《诸儒鸣道集》的编订目的、所反映的时代信息等问题的必要前提。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讨论该书所反映的道学谱系、道统观念问题的基础就不可能牢靠——我们凭什么认定该书的编刻者一定属于儒者阵营?凭什么就认为该书反映出的是道学早期对道统的认识?因此,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难题。
其二,该书与朱熹的关系。《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上蔡先生语录》显然出自朱子所编订,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也说明,《诸儒鸣道集》的编刻与朱子或多或少会有关联。而赵振则进一步论证,该书所收录的《二程语录》也出自朱熹所编订。这一说法会在本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确认。据现有资料判断,本报告认为,“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和《二程语录》的刊刻,明显违背了朱子本人的意志。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该书的编者与朱子之联系是很松散的。
其三,该书与道学、道学谱系。田浩先生特别注意《诸儒鸣道集》对所收著作的选取问题:《诸儒鸣道集》收录了司马光及其弟子刘安世的著作。田浩先生据此认为,该书编者对于道学的理解颇不同于朱熹,代表着另一种道学谱系。符云辉邱佳慧均赞同田浩的观点,并都有所发挥。
其四,该书与宋代学术多元化。宋代儒学在总体上有一个由多元到一元的发展趋势。但是自《宋史·道学传》之后,这一历史有明显被化约的趋势。《诸儒鸣道集》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到南宋初期儒学发展多元化的有益资料:司马光、潘殖、江民表,刘安世,这些不属于“正统”道学体系的学者的著作被收录其中。这颇能反映出在朱子的学术定于一尊之前宋代儒学之面貌,也能丰富我们对宋代道学史发展之曲折性的认识。
其五,该书与周敦颐的著作。学界目前对于周敦颐的著作尚有很多的疑问,而“鸣道本”《濂溪通书》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通书》版本:虽然在朱子编订“长沙本”《通书》之前,社会上早已有“舂陵”、“零陵”、“九江”以及侯师圣传本和尹焞传本、胡宏整理本和祁宽整理本等多个《通书》版本在流传,但是这些版本我们今天都已经无法看到了。“长沙本”《通书》编订于乾道二年(后文有详细考证),而《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也与此相当,因此“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长沙本”《通书》,并且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通书》版本。这也为我们研究周敦颐著作的早期流传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总的看来,学界对《诸儒鸣道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完满解决,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该书的精确研究与应用。
首先,关于该书的原刻年代问题。学界对此的讨论仍限于陈来师和顾廷龙先生,别人基本上是在因袭二先生的说法。陈来师据《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上蔡先生语录》和《二程语录》两书判断,“《鸣道集》有可能是在朱熹校定《上蔡语录》至编定《遗书》的十年之间(1158—1168年)编成的。”①陈来师此说跨越了宋高宗绍兴年间到宋孝宗隆兴、乾道年间。但是据该书的避讳情况来看,该书原刻的年代还可以后推至少五年时间。顾先生认为:“此本(指《诸儒鸣道集》)原刻当在孝宗(田按,1163—1189年)时代无疑。”②我们认为,顾先生此说对《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下限的判定有些太晚。事实上,该书所收录的著作有不少在1168年前后出现了更新、更好的版本,如朱子于1166年编订“长沙本”《通书》,此本“视他本最详密”(“长沙本”的编订地点离《诸儒鸣道集》的编刻地点稍远,可能没有被该书的编者及时发现);于1168年重修《上蔡语录》并编订《程氏遗书》;于1173年编订《屏山集》,内含《圣传论》修定本;于1179年编订“南康本”《通书》,是为《通书》定本,《诸儒鸣道集》的编者没有什么理由不采用这些新的版本,而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诸儒鸣道集》编刻之际,这些更新的版本还没有进入该书编者的视野之内,这也意味着,《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要早于这些新版本的面世时间。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判断,我们完全可以把该书的原刻年代限定在乾道初年这个时间段内。对《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问题的解决,也为我们探索该书所反映的时代信息奠定了基础。
其次,该书的编者身份问题。此问题目前只有陈来师有所讨论,此后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沿袭他的结论(或有所修订,如向世陵和方旭东都指出,胡宪不大可能是该书的编者)。问题是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资料能够帮助我们揭开疑问,所以除非有新资料被发现,我们对此只能提出推测而已。不过,大家似乎都默认,《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一定属于道学阵营中人。这一立论前提却是值得商榷的——该书很可能属于坊刻本,其编者与书商的关联或许要比与道学阵营的关联要更紧密。笔者会在后文中对此给出进一步的说明。对我们而言,对该书编者身份的讨论更有价值。试想,如果该书的编者不属于道学阵营,那么我们讨论他们对道学谱系的理解还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其三,关于对道学、道学谱系的理解问题。在其大作《朱熹的思维世界》中,田浩(Tillman,HoytCleveland)先生借助《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提出了自己对道学以及道学谱系的独特理解。他希望道学可以涵盖哲学思辨、文化价值、现实政论三个层面(此为该书余英时先生的序言里的概括)。田浩的提法后来也得到了众多《诸儒鸣道集》研究者们的积极回应:如符云辉和邱佳慧等人。目前学界围绕道学一词的争论颇多,也颇能反映出哲学视角与历史学视角看问题的不同(方旭东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此不赘述。不过,田浩显然认为,《诸儒鸣道集》能反映出道学初期的多元面貌(田浩的本意,应该是指南宋道学初期的面貌),这个所谓的“早期”显然是针对朱子所编的《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而来。但是,《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显然并没有像田浩所认为的那样,要领先朱子编订《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的时间多少。依照陈祖武先生的研究成果,《诸儒鸣道集》的原刻年代与《伊洛渊源录》之大纲所形成的时间基本相当,甚至还要稍晚些①,也仅仅早于《近思录》数年而已,“因此,如果指望从时间领先这一点上为《诸儒鸣道集》更能反映道学面貌进行辩护,其基础不能不说是很薄弱的”①,方旭东君的上述观点颇显中允。事实上,即使是抛开时间问题,田浩的观点也不是没有商榷的余地:在田浩所认为的南宋道学第一时期,他也只能举出张九成和胡宏二人为当时学术多元性的例证(胡宏的著作却没有被《诸儒鸣道集》收录),与之相对,在他所认为的第二阶段,则有朱子与湖湘学派、朱子与吕祖谦等浙学中人的一系列论争;在田浩所认为的南宋道学第三时期,至少还有陈亮、叶适(田浩没有提到)、陆九渊等人与朱子相对,总之,这后两个阶段也未尝不可以“多元”视之。我们认为,《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著作并不限于程朱一系,同时还包含了潘殖、江公望以及司马光、刘安世的著作,我们也可以据此讨论宋代学术的多元化问题(田浩先生的眼界尚不够宽阔)。但是,田浩先生对“道学早期”这一概念的使用颇为随意,《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完全有可能是朱子的同时代人,甚至不一定比朱子年长(在《诸儒鸣道集》原刻之际,朱子已经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并步入中年),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再者,关于道学谱系的问题,田浩等人很希望也把司马光、刘安世等人纳入道学的阵营中,本书对此持相反的观点。在唐宋之际,“道”这个概念相当混乱,至少它是儒释道共同使用的概念,因此才会有“道德为虚位,仁义为定名”的说法。因此,过分扩大“道学”一词的外延,难免会导致此概念内涵的空洞化。事实上,田浩也没有在其著作中贯彻他的想法,他的著作中所收录的人物,基本上不出程门后学的范围。
其四,关于“鸣道本”《二程语录》与《程氏遗书》关系问题。赵振撰长文《〈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集中论证《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都系朱子所编,只不过前者是初稿,而后者是定稿,此观点目前已经基本为学界所接受。不过,细察赵所提出的证据,发现每一条证据都不足以一锤定音。这些证据的组合也还不足以使其观点成为定案。略举其问题明显者如下:
赵的文中提出:
朱熹在编辑《遗书》时曾先编辑了一部初稿,而此初稿编成后即付梓,他在与何叔京的信中谈到过此事,说:“语录倾来收拾数家,各有篇帙首尾,记录姓名,比之近世所行者差为完善。故各仍其旧目而编之,不敢辄有移易。近有欲刻版于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当得其摹本以献,今无别本可以持内也。”[2](p1842)当朱熹拿到刊印的初稿本子时,发现了许多原来没有发现的错误,其《与平父书中杂说》云:“《程氏遗书》细看尚多误字,盖元本如此,今以它本参之,乃觉其误耳。”[2](p1838)于是决定对初稿重新进行校订。但由于自己有许多事务缠身,校订工作时断时续,所以后来他在写给何叔京的另外一封信中说:“语录比因再阅,尚有合整顿处。已略下手,会冗中辍。它时附呈未晚。”[2](p1846)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决定委托许顺之等人对《遗书》初稿进行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校勘,他写信给许顺之说:“向者程舶来求语录本子去刊,因属令送下邑(指同安)中,委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叶学古就城中独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书答之,再送下覆校。千万与二丈三友子细校过。”[2](p1781—1782)并在答复许顺之的信中对校书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曰:“承上巳日书,知尝到城中校书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据旧本为定,若显然谬误,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阙误可疑,无可依据者,宁且存之,以俟后学,切不可以私意辄有更改。盖前贤指意深远,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误后来,其罪将有所归,不可容易。千万千万!”[2](p1782)而这一工作直到乾道四年(1168年)才完成。①(田按,文中的[2],系指《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版;后同)
按照赵在文中的叙述,在时间上应该是先有朱子给何镐(叔京)的第一封信中提到“刊行语录”这件事,然后才会有他在《与平父书中杂说》中提到《程氏遗书》有错误这件事,再后来才有他在给何镐的第二封信中述及“语录”整理工作拖延的情况,最后才是朱子给许顺之的书信,告诫他们要认真校书,其前后顺序应该如此。但是,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从赵的这段文字看,除了《与平父书中杂说》中提到《程氏遗书》外,其前其后的书信提的都只是“语录”,这个《程氏遗书》名称的出现的确让人感到非常突兀;二是赵文中所提到的《与平父书中杂说》这封信的具体写作时间不详,因此这几封信的写作先后顺序是否就是如赵所排列的这样?这一点颇属疑问。陈来师就倾向于认为《与平父书中杂说》作于1168年之后,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是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显然,赵的论证缺乏对此的必要审查,他对朱子书信的排列比较随意。
再如,赵文中又提到:
《遗书》附录中的《伊川先生年谱》多次出现“见《语录》”字样的注文,这里的《语录》当指《二程语录》,因为从《程氏遗书附录后序》中我们得知该序作于乾道四年夏四月,也就是《遗书》修订完稿时,换句话说,《遗书》附录一卷及附录后序编写于《二程语录》刊行之后,故《语录》未载这部分内容。不仅如此,就是《程氏遗书后序》亦作于《遗书》修订完稿时,朱熹在乾道四年写给王近思的信中说:“校书闻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略见编纂之意。”[2](p1798)这里的序当指《程氏遗书后序》,此时王近思正与许顺之等人受朱熹委托在同安城校订《遗书》。并且在该序写成后,朱熹还就此征求过其他人的意见,他在写给林择之的信中说:“《文定祠记》、《知言序》、《遗书》二序并录呈。……三序并告参祥喻及,幸更呈诸同志议之。既欲行远,不厌祥熟也。”[2](p5456)其中《遗书》二序指的就是《程氏遗书后序》和《程氏遗书附录后序》,所以《语录》亦不载《程氏遗书后序》。①
赵认为:《伊川先生年谱》多次出现“见《语录》”字样的注文,这里的《语录》当指《二程语录》”云云,这一说法显然失察。《伊川先生年谱》中“语录”二字凡十见。其中“幼有高识非礼不动”条、“不知者或诮其委曲已甚”条、“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条、“某起于草莱”条、“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条,均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族子至愚不足责”条见于《程氏遗书》卷十九;“范致虚言"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一(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伊川先生病革门人郭忠孝生视之”条见于《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二(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由此可知,至朱子编订《伊川先生年谱》时为止,朱子所提到的“语录”,均包括《程氏遗书》和《程氏外书》的内容在内,是对流传下来的“二程语录”的统称,而非指“统编的程氏语录集”,尤其不能说是指《程氏遗书》或是其初稿或“鸣道本”《二程语录》①。
还如,赵推测:“但令人不解的是,平生治学严谨的朱熹为什么会让这样一个存在诸多问题的《二程语录》本子匆忙面世。笔者推测朱熹之所以这样急于发表自己所编的《二程语录》,很可能是想建立他在二程思想诠释方面的权威地位,并借机削弱其他学派,特别是胡安国家族在这方面所施加的影响,从而使自己在争取道学正统地位的斗争中能处于有利地位……”②此说同样令人生疑。据赵的推测,朱子是主动要发布《二程语录》的,考诸朱子自己的文献记述,此说恐怕不能成立。朱子自己已经反复声明“语录”初稿系被程宪拿走,并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匆匆刊刻的,朱子对此除了去信交涉外,还积极组织对“语录”的重新校对,这怎么能说是朱子主动要发布“初稿”呢?再者,在乾道四年之前,朱子与湖湘学派正处于蜜月期,其思想也正处于“中和旧说”阶段,朱子称赞湖湘学派为学功夫的书信也有很多。无论如何,朱子都不会在此时以争正统为目的主动发布《二程语录》。
一年后,赵振又作《朱熹与二程语录的整理与编辑》一文,对其所提出的观点做出了充实。如,赵又提出:“种种迹象表明,《遗书》初稿(赵认为即“鸣道本”《二程语录》的底本)很可能最初是由张栻刊于严州,朱熹《答吕伯恭》之四云:‘严州《遗书》本子初校未精,而钦夫去郡。今潘叔玠在彼,可以改正,并刻《外书》,以补其遗’”③云云,赵似乎是认为,朱子此信作于1166—1168年之间,此说不确。赵所引的书信为文集卷三十四之《答吕伯恭…前日魏应仲》(田按,实为《答吕伯恭》之五十五)。陈来师判定此书作于淳熙四年(1177年)①,或许有些太晚。但是,这封信却不可能作于1168年朱子正式刊刻《程氏遗书》之前:据杨世文先生考证,张栻于乾道五年(1169年)才由刘珙推荐,“知严州”,而其第二年则被调任回京②。据此,这封信也应该作于此时或稍后。尤其是这段文字中也提到了《外书》,其写作年代更不应该在1168年之前。显然,这封信中所提到的《遗书》,肯定不是指“鸣道本”《二程语录》。赵的观点是错误的。
赵振先生指出《二程语录》出自朱子所编,系《程氏遗书》的初稿,这一点颇有创见,但是其具体的论证过程也有很多的瑕疵。这也值得我们在后文中仔细探讨。
第五,关于《诸儒鸣道集》与周敦颐著作情况考辨的问题。陈来师指出:
据朱熹这些记述(田按,指朱子在“建安本”和“南康本”《通书》后序中的记述),《太极图》及《说》原附于《通书》之末,朱熹初定长沙本时一遵旧例,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后根据潘清逸为周敦颐所作墓志中“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的说法,意识到《太极图说》当是一部独立著作,在建安本才把《太极图说》独立出来并列于《通书》之前,从此《太极图说》便与《通书》分开了。
但是朱熹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井不完全相符。比朱熹更早一些的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说,《通书》一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所传本是也………逮卜居九江,得九江本于其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这就是说《通书》的程门传本有太极图,而九江周敦颐家藏旧本则没有。换言之,《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按照祁氏的说法,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祁氏仅及太极图当系简言之)。今《鸣道集》本亦无《太极图》,因此,如果可以断定鸣道集本早于朱子定本,那就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
这个本子也是今天所见到的《通书》的最早版本。①
现在看来,“鸣道本”《濂溪通书》要早于朱子所编订的“长沙本”《通书》当无异议,而综合“鸣道本”与“九江本”《通书》的情况判断,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通书》早期版本的流传分周氏故家藏本和程门传本两个系列,前者未收太极图,而后者则不独收录有太极图,也收录有《太极图说》。但是,“九江本”《通书》中是否如陈来师所推测的那样“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还存在进一步商榷的余地。据笔者判断,“九江本”只是没有《太极图》,却收录有所谓《太极说》,《太极说》具体内容与今天的《太极图说》基本一致。这也足以表明了《通书》早期版本流传情况的复杂性。
杨柱才先生也依据“鸣道本”《濂溪通书》,对《通书》在早期的流传情况有所说明。如他认为:“宋本《诸儒鸣道集》所收《濂溪通书》无《太极图》,当即是祁宽所见九江家藏旧本《通书》”②,此说不确:据朱子所见,“鸣道本”与“九江本”《通书》有很大差距。同时,杨还因袭束景南先生的观点,认为杨方给朱子的九江故家本《通书》系后出者,这一观点也颇值得商榷。
总之,上面提到研究成果和仍存在的问题也是本书立论的前提与基础。我们会在自己材料和视角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给出回应与解答。
附注
①顾廷龙:《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载《诸儒鸣道集》,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②陈来:《略论〈诸儒鸣道集〉》,《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③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二,《子部》,“宋刻诸儒鸣道集七十二卷”条,上海:中国历代题跋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9页。
①《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第5页。
②周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页。
①见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八十八册之《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
②《濂溪通书·诚几德》,载《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3页;《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八十八册,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下文中简称《濂溪集》。
③见《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4页;《濂溪集》,第94页。
④《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7页;《濂溪集》,第96页。
⑤同上书,第97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8页;《濂溪集》,第97页;《周敦颐集》,第24页。
②《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8页;《濂溪集》,第97页。
⑧《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9页;《濂溪集》,第99页。
①《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0页;《濂溪集》,第100页。
②《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1页;《濂溪集》,第101页。
③《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3页;《濂溪集》,第103页。
④《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4页;《濂溪集》,第104页。
⑤《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5页;《濂溪集》,第105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6页;《濂溪集》,第106页。
⑦《诸儒鸣道集》卷一,第57页;《濂溪集》,第107页。
⑧同上。
①林乐昌:《通行本〈正蒙〉校勘辨误》,《中国哲学史》2010年4期,第54—58页。
②《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2页。
①林乐昌先生有专文依照“鸣道本”《横渠正蒙》对“张载集本”《正蒙》校勘,指出“张载集本”《正蒙》误校有七十多例,他并列出了其中的十例。见林乐昌:《通行本〈正蒙〉校勘辨误》,《中国哲学史》2010年4期,第54—58页。
②分别见“鸣道本”第161页、《张载集》第50页。
③分别见“鸣道本”第177页、《张载集》第58页。
①分别见《诸儒鸣道集》第186页、《张载集》第63页。
①分别见《诸儒鸣道集》第188页、《张载集》第64、350页。
②分别见《诸儒鸣道集》第191页、《张载集》第66页。
③分别见《诸儒鸣道集》第192页、《张载集》第66页。
①赵振:《二程语录的文献误入问题辨析》,《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6期,第72页。
①分别见“鸣道本”第259页、《张载集》第281页。
②分别见“鸣道本”第260页、《张载集》第281页。
③见《张载集》,第285页。
④分别见“鸣道本”第269页、《张载集》第286页。
⑤分别见“鸣道本”第271页,《张载集》第287页。
⑥分别见“鸣道本”第273页、《张载集》第288页。
①分别见“鸣道本”第275页、《张载集》第289页。
②分别见“鸣道本”第276页、《张载集》第290页。
③分别见“鸣道本”第277页、《张载集》第290页。
④分别见“鸣道本”第281页、《张载集》第292页。
⑤分别见“鸣道本”第286页、《张载集》第295页。
①赵振:《〈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②邱佳慧:《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
①《诸儒鸣道集》,第1053页。
②邱文误为“绍圣五年”,见《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第32页。
③《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第33页。
④钱培名补脱文;崔铣编行录、王崇庆解、马永卿辑:《元城语录解附行录解脱文》,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⑤《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第37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四十九,第1080—1081页。
①《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第41页。
②宗晓编:《乐邦文类》卷三,《宝积莲社画壁记》,《大正藏》,第四十七册,经号1969,第189页。
③彭绍升编:《居士传》卷二十七,《郑介夫邹志完江民表陈莹中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清光绪戊寅年钱塘许氏刊本影印1991年版,第366—367页。
④夏树芳辑:《名公法喜志》卷四,《续藏经》,第150册,中国撰述,史传部,补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05页。
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儒家类》,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版,第271页。
①《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五,第1202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一》,载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年版,四部丛刊续编本,第317—318册,第3页。
②《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五,第1203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一》,第4页。
③《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五,第1228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一》,第12页。
④《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五,第1232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一》,第15页。
⑤《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六,第1240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二》,第2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六,第1244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二》,第4页。
⑦《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六,第1250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二》,第9页;《杨龟山先生全集卷十》,《语录一》,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所据底本为光绪九年知延平府张国正重刊道南杨氏祠堂本,第534页。
⑧《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六,第1251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二》,第10页。
⑨《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六,第1274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二》,第26—28页。
①《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七,第1287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三》,第8页。
②《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七,第1290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三》,第10页。
③《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七,第1295页;《龟山先生语录卷三》,第10页。
④《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八,第1335页;《龟山先生语录卷四》,第14页。
⑤《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八,第1346页;《龟山先生语录卷四》,第22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五十八,第1347页;《龟山先生语录卷四》,第23页。
⑦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第9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①《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载《诸儒鸣道集》,第6页。
②分别见《诸儒鸣道集》卷五十九,第1357页;《续修四库全书》,第934册,第273页。
③分别见《诸儒鸣道集》,第1397、1398页;《续修四库全书》,第934册,第286页。
④《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载《诸儒鸣道集》,第5页。
⑤《屏山集》四库全书本,黄山书社出版的明刻本同。
①刘子翚:《屏山集》,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甫宋建炎至德祐,四库全书本。
②朱熹著、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书屏山先生文集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数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4—3825页。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二,《绍兴十四年甲子》,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53页。
①于恕:《无垢先生横浦心传录三卷横浦日新一卷》,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八十三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66页。
①陈来:《岂弟君子,教之诲之——张岱年先生和我的求学时代》,载陈来《燕园问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②该书被收入了中华再造善本丛书。
③方旭东的文章为:《〈诸儒鸣道集〉再议》,载《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十三辑,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编,2010年2月。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4页。
②顾廷龙:《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见《诸儒鸣道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又按,据陈先行先生的《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一书提到:“近见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撰文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山东出版《孔子文化大全》所印此书的底本是来自美国哈佛燕京社,其实不是。上图既向杜维明教授提供了此书的复制件,后闻山东欲影印出版,正合顾廷龙先生的意愿,所以也向山东提供了复制件。当时因顾患病,出版前言由我代笔,但我至今未看到所印之书,再说本人水平有限,故未将这篇前言收入《顾廷龙文集》中”云云,可知此文实际系出自陈先生之手。见陈先行所著:《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此点系由一位台湾朋友指出,特此鸣谢。
①朱子在乾道二年给何镐的信中,已经提到过《渊源录》的编订,据陈祖武先生推测,这一年《渊源录》的大纲已经完成,见其著《中国学案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32页。
①方旭东:《〈诸儒鸣道集〉再议》,在《儒教文化研究》第十三辑,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2010年2月。
①赵振:《〈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43页。
①赵振:《〈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44页。
①朱子后来自己也强调,《年谱》的编订,系“熹尝窃取《实录》所书,《文集》、《内》、《外》书所载,与凡他书之可证者,次其后先,以为《年谱》”。
②《〈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第144页。
③赵振:《朱熹与二程语录的整理与编辑》,《天中学刊》2007年第4期,第120页。
①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4页。
②杨世文、王蓉贵点校:《张栻全集》,前言,第8页,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1—32页。
②杨柱才:《道学宗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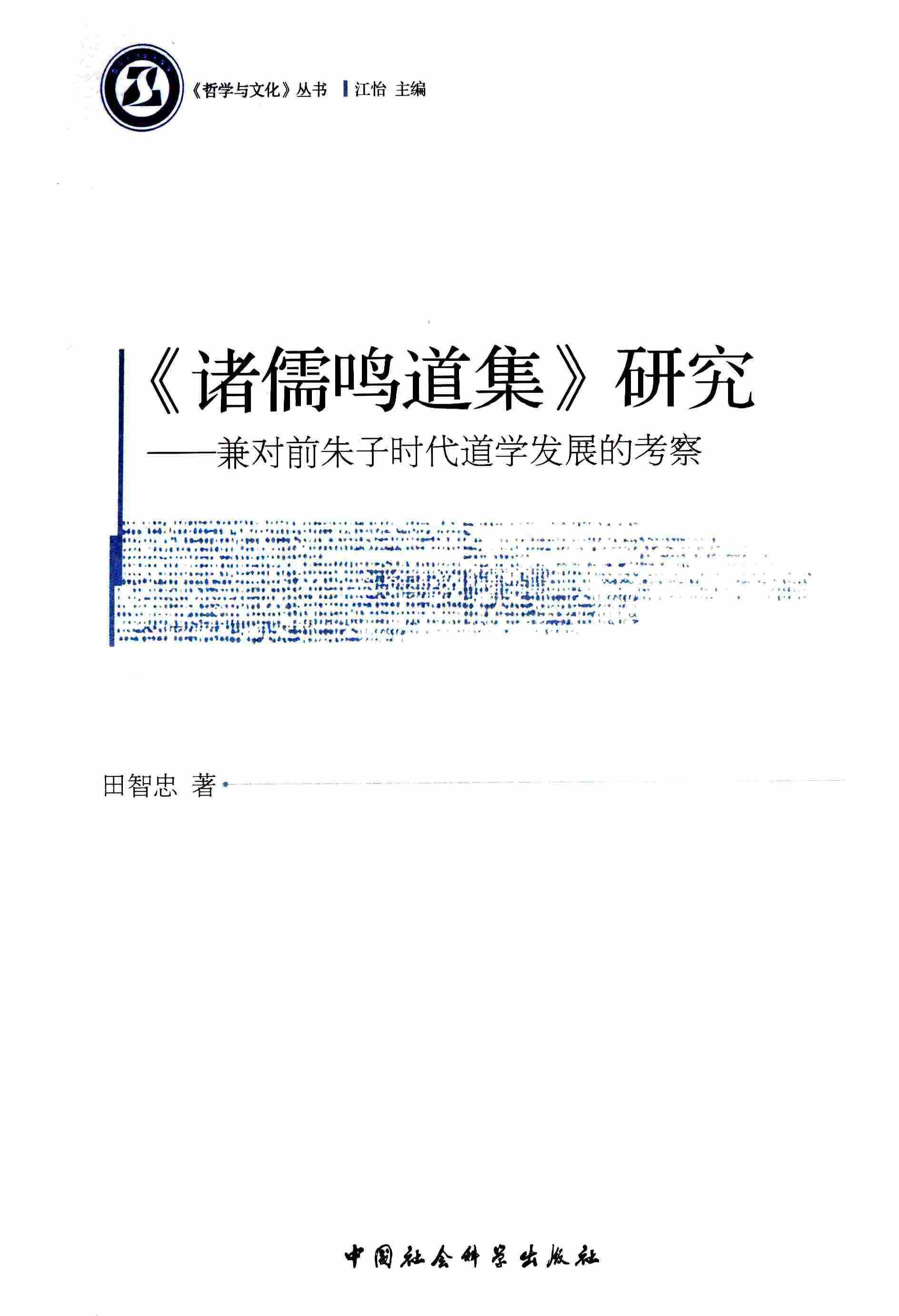
《《诸儒鸣道集》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内容包括:《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考、关于《诸儒鸣道集》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诸儒鸣道集》视野下的宋代儒学多元性研究、周敦颐与张载的道学话语构建、二程对道学话语的构建、谢良佐与杨时对道学话语的构建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