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官能视域中的朱子心论
| 内容出处: | 《从官能、性理到工夫:朱子心论新探》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4834 |
| 颗粒名称: | 第一章 官能视域中的朱子心论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38 |
| 页码: | 11-48 |
| 摘要: | 本章我们主要探讨了朱子心论的“官能”面向。通过三节的探讨,我们发现:在朱子,心的基本义,即是指人这里的“知—觉”之能,而“知—觉”之能能够运用为“思”能、“情”能、“意”能;人类心灵之间在官能构成和自我认同方面是相同的,但同时存在着从“上智”到“下愚”的千差万别,“学习”能够使这种差别不断得到调整,并指向“愚”的最终消除。朱子对于人类心灵基本面的刻画是明晰、确定、全面而细致的。 |
| 关键词: | 朱熹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所谓“官能”,是指朱子常常用以说心的“知觉”“思”乃至“情”“意”等(在朱子,“知觉”“情”“意”都是能力,此待后文详论)。不可否认,这些官能并非朱子心论的根本面向,因为它们就其本身而言,毕竟不够深刻。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官能是朱子心论的重要面向乃至基本面向,不充分探明它们所显示出的“心”之义涵,也会影响我们深入朱子心论的根本面向。职是之故,学界既有的相关研究几乎都从这些话题开始探讨,最典型的当属陈来教授《朱子哲学研究》,其中“心之诸说”部分以“心与知觉”和“心为主宰”两节开头①,而笔者的新探也无以自外于这一路径。
第一节 心等于知觉之能——心与知觉新探
一 心等于知觉
前辈学者无不注意到朱子这里“知觉”和心的密切关系,但一些学者认为在朱子,“知觉”就是心或者说心等于“知觉”,②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在朱子,“知觉”仅仅是心的主要功能而心并不完全等同于“知觉”①,且双方都没有对另一方的观点作出应对,这使得双方的见解都还停留于一种语焉不详的状态。这两种说法表面差之毫厘,但实际上直接冲突,而且涉及整个朱子心论地基的确定性,必须加以辨明、厘定。笔者重新考察朱子所有相关论述后认为,“心等于知觉”说应该才是朱子本意(“心具众理说”不在“心等于知觉说”之外,此待后文详论),“知觉仅仅是心的主要功能”之说应当是出于对朱子一些言论望文生义的误解。
首先,遍检朱子现存著作,可以发现朱子对于心共有四处定义,谨依文献可靠度排列如下:
(一)《尚书·大禹谟解》:“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②
(二)《孟子集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③
(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心”则知觉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④
(四)《朱子语类》:有知觉谓之“心”。⑤
此中“神明”是“知觉”的代名词,而从句法语义上讲,“主于身而应事物”“具众理而应万事”“具此理”分别是对其前面“人之知觉”“人之神明”“知觉之在人”的进一步申说,不是在“人之知觉”“人之神明”“知觉之在人”之外有所增添,所以前三处定义都支持“心等于知觉”之说,只有第四处定义表面支持“心仅仅是有知觉而并不等于知觉”的观点。但一方面,前三处定义所在文献都更为正式,而第四处定义所在文献则没有那么可靠;另一方面,第四处定义实际上也不是要为“知觉”之外的东西保留余地,而只是要提示我们,心之为“知觉”还“具众理”而不可以浅显观而已,朱子在这里、乃至在其他含有“心有知觉”之意的言论中,都没有进一步说“心还有某某”,①可以反证出这一点来。
事实上,就是在《语类》中,也随处可见“心等于知觉”的证据,如朱子在讲论中时而说“心性只是一个物事,离不得”②,时而又说“理不离知觉,知觉不离理”③,时而反对“性中别有一个心”,时而又反对“性外别有一个知觉”(“性中别有一个心”的“中”是“外”的意思),④甚至不加说明地以横渠“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心”之说来佐证自己“有这知觉,方运用得这道理”的看法⑤,此中“心”和“知觉”的同位互换,无疑都蕴含着“心等于知觉”的前提。
不可否认,在正式而可靠的《中庸章句序》中,朱子曾说:“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⑥此中“心之虚灵知觉”一言,表面上好像是在表达“心的虚灵知觉”而支持“心仅仅是有知觉而并不等于知觉”的观点。但实际上,“心之虚灵知觉”并不是“心的虚灵知觉”的意思,而是“心作为虚灵知觉”的意思。因为一方面,“之”字在朱子不但有“的”的意思,而且有“作为”的意思,如“理之所以然”“念虑之微”“事为之著”,都是“理作为所以然”“念虑作为微者”“事为作为著者”,而不可能是“理的所以然”(在朱子,“理”便是“所以然”,不可能更有“理的所以然”)、“念虑的微”“事为的著”的意思(这两种表达都是不合文法的);另一方面,下文直接将“人心、道心之异”归为“所以为知觉者不同”,可以反向确定“心之虚灵知觉”是“心作为虚灵知觉”的意思,而不是“心的虚灵知觉”的意思。在《文集》《语类》中,朱子也曾有“心之知觉”的表达,如《文集》“心之知觉,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①、《语类》“心之知觉,又是那气之虚灵底”②,不难推知,这些话中的“心之知觉”也都是“心作为知觉”的意思,而不是“心的知觉”的意思。这也是我们在朱子这里找不到“心之其他”的原因所在。
总而言之,“心等于知觉”之说应该才是朱子本意,“知觉仅仅是‘心’的主要功能”之说应该是出于对朱子一些言论望文生义的误解。后来阳明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③,也指出了“心”和“知觉”的等同。确定了这一点,朱子心论才能获得稳定而确切的地基,朱子关于心的其他论述才能顺利地获得理解。有学者认为,朱熹对心的讨论是极为多的,他对心的解释就像孔子对仁的解释一样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并没有对其下一个固定而明晰的定义。“多方面、多层次”自然是好的,但“多”到“没有对其下一个固定而明晰的定义”,便无异于说朱子对于心的讨论是一个大杂烩,“分殊”而不“理一”。这种说法的出发点明显是为朱子辩护,但如此辩护,恐适得其反。
二 心(知觉)等于知觉之能
认为心等于“知觉”的学者,又或认为“知觉(心)”有时不仅仅指“知觉之能”,还包括“知觉成果”在内。①但笔者梳理朱子相关文献后发现,在朱子,心(知觉)应该一直都仅仅指“知觉之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包括“知觉成果”在内(在朱子,知觉之能包括思、情、意在内,但思、情、意都不是“知觉成果”,此待后文详论)。因为“知觉成果”就其所是而言,应该纯粹是一些信息,只是因为是知觉带来的而得以有“知觉”作定语,不在任何意义上是一种知觉;就其所在而言,在朱子这里是存储于有别于心的“魄”中,没有任何机会成为“心”的一部分(“知觉成果”因为是“心/知觉”带来的,往往带着关于“心/知觉”的信息,即之可见“心/知觉”的内在条理,如康德所谓感性纯直观、知性范畴、理念之类是也,但即便是这些关于“心/知觉”的信息,也只是信息而存于“魄”,无论从所是还是所在而言,都不在“心/知觉”的所指之内)。这即是说,在朱子这里,存在着一种叫作“魄”的器官,这一器官负责存储心所获得的信息,但并不在心的所指之内。朱子说:
会思量讨度底便是魂,会记当去底便是魄。②
知识处是神,记事处是魄……小儿无记性,亦是魄不足。③
凡能记忆,皆魄之所藏受也,至于运用发出来是魂。这两个物事
本不相离……魄盛,则耳目聪明,能记忆,所以老人多目昏耳聩,记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④
此三条论“魄”甚明,可见朱子承认“魄”的存在并归信息存储功能于“魄”。进一步,朱子又说:
不可以“知”字为“魄”,才说“知”,便是主于“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咸淡,要从舌上过。①
“知”是“心”而不可以为“魄”、“心但能知(而不能存)”,则负责存储的“魄”之不属于“心(知觉)”甚明。②朱子又说:
气曰魂,体曰魄。③
“曰”在这里虽然只是“属于”的意思,不是“等于”的意思,但此已可见在“身心”这组对待之中,“魄”是属于身体而不是属于“心(知觉)”的。总而言之,在朱子,“心(知觉)”仅仅负责获取信息(“心但能知”),存储信息的任务则由“魄”来负责(“凡能记忆,皆魄之所藏受也”);“心(知觉)”才获取信息,信息便即刻存入“魄”中成为“魄之内容”甚至是“身之内容”(“体曰魄”),“心(知觉)”则只有“对象”而始终无所谓“内容”;从身体之外获取信息时是如此,从“魄”中获取信息时或者说对“魄”中信息进行再勘察(即日常所谓反观内省)时也是如此。然则“知觉成果”之为“‘魄’中信息”,而“知觉(心)”之不必越俎代庖,而始终仅仅指“知觉之能”,应当可以无疑。众所周知,朱子对佛教“以心观心”之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果“知觉(心)”真的包括“知觉成果”的话,那么人的正常反思、内观或者说曾子所谓“三省”、《中庸》所谓“内省”便只能解释为“以心观心”,而朱子对“以心观心”之说的批评便会显得不近人情,甚至有悖于自己的儒家立场。但实际上在朱子,人的正常反思、内观或者说曾子所谓“三省”、《中庸》所谓“内省”是“以心观魄”而为一种“以心观物”(“魄”中信息也是一种“物”),并不是“以心观心”,朱子对“以心观心”之说的批评仅仅指向“以知觉之能观知觉之能”,并不伤及人的正常反思、内观和曾子所谓“三省”、《中庸》所谓“内省”。①
不可否认,朱子本人对于“心(知觉)”概念的使用中,有几种表达的字面会对人产生误导,让人误以为其所言“心(知觉)”涵盖“知觉成果”,这些表达有:(1)以“虚”“空”说“心(知觉)”,甚至以“镜”喻“心(知觉)”而曰“如鉴之空”;(2)“心具某某”甚至“心包某某”;(3)“心中(里)”。这些说法从字面上看起来似乎将“存储”这一功能及其连带的“知觉成果”归给了“心(知觉)”,但笔者仔细考察这三种表达的实义后发现实际情况应该并非如此,谨依次辨析如下。
(1.1)朱子所言的“虚”是指“心(知觉)”作为“知觉之能”相对于一般事物乃至其他能力而言趋近无迹的本质特点,而不是“内部存储空间”尚未被填充意义上的初始特点,朱子说:
人心本是湛然虚明,事物之来,随感而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
事过便当依前恁地虚,方得。②
人须通达万变,心常湛然在这里。③
第二句中“湛然”即“虚”。如果朱子所言的“虚”是“内部存储空间”尚未被填充意义上的初始特点的话,那么他“事过”“通达万变”之后仍然“虚”的期待,便似乎是在期待一个人完全失去记忆能力一样。朱子显然不会发出这样的期待。只有当朱子所言的“虚”是作为知觉能力而趋近无迹的本质特点的时候,这两段所表达的期待才能获得合理的理解:期待此心不失其趋近无形无迹的特点,也即不失其作为“知觉之能”的敏锐度、不被钝化。又朱子说:
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耳目之视听,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岂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视听之,则犹有形象也。若心之虚灵,何尝有物!①
心者,气之精爽。②
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③
这里的“本体”是“本来样子”也即“本质特点”的意思④;“非我所能虚”,即不以人的经历为转移;“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应当是插入语,所以第三段后半段的意思当为“耳目之视听岂有形象?然犹有形象,若心之虚灵,何尝有耳目这样的形象呢?”只有作为知觉能力而趋近无迹意义上的“虚”,才可以和“灵”并称、互代(朱子首尾说“虚灵”,中间只说“虚”,即是以“虚”代“虚灵”),⑤才是本质特点而不以人的经历为转移,也才真正说得上“何尝有耳目这样的形象”“气之精爽”“比性则微有迹”。内部存储空间尚未被填充意义上的“虚”,不能和“灵”并称、互代,只是初始特点而必定被人的经历所填充,很难说得上“何尝有耳目这样的形象”尤其是“气之精爽”“比性则微有迹”。(1.2)“空”是“虚”的另一种说法,朱子一方面说“此心虚明,万理具足”⑥,另一方面又说“心虽空而万理咸备”⑦,即显示出这一点,所以所谓“空”也不是内部存储空间尚未被填充意义上的初始特点,而是作为知觉能力趋近无迹的本质特点。(1.3)“如鉴之空”的比喻不能执之太实,因为一方面朱子明确说过“譬喻无十分亲切底”⑧,另一方面“鉴”毕竟说不上“何尝有物”或者说“趋近无迹”。总而言之,朱子以“虚”“空”说“心(知觉)”,甚至以“镜”喻“心(知觉)”而曰“如鉴之空”,看似蕴含着“心(知觉)”涵盖“知觉成果”的意思,但实际上恰恰相反。
(2.1)“心具某某”中的“具”字不是“存储”或者“装载”的意思,因为“某某”无论在《集注》《文集》还是《语类》中,都几乎固定地是“(众/万)理”或者“此性”①,而朱子反复说“此理无形无影”②“理之体该万事万物,又初无形迹之可见”③“(心、意犹有痕迹)如性,则全无兆朕,只是许多道理在这里”④“论性,要须先识得性是个甚么样物事。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道理”⑤,这些话都表明,在朱子,“(众/万)理”或者说“此性”是完全无迹的,⑥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知觉成果”,没有被“存储”被“装载”的可能。因此,“心具某某”这样的表达并不是“心存储、装载着某某”的意思,并不是将存储功能又划给了“心(知觉)”(其实义待后文详论)o(2.2)“心包某某”(包含该载、包蓄)则是“心具某某”的口语化、形象化表达,因为被“包”的“对象”也不出“万理”“性”二说,且这种表达于《集注》《文集》《语类》三种书中,仅见于《语类》,⑦不可执之太过。总而言之,“心具(包)某某”的说法也是看似蕴含着“心(知觉)”涵盖“知觉成果”的意思,但实际上恰恰相反。
(3)在检索《集注》所得全部一处(在所引程子之言中)、检索《文集》所得全部六处、检索《语类》所得一百七十七处“心中(里)”的表达中,①只有《语类》中有一处支持“存储”之属“心(知觉)”,②其他各处则都不支持甚至明显反对这一点(其中“心中/里”可以理解为“心作为中/里”),③所以“心中(里)”的表达至少并不必然出乎“心(知觉)等于知觉之能”、不包含知觉成果这一结论之外。
综上所述,朱子这里“心等于知觉”同时意味着“心等于知觉之能”。后来阳明曾说“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④也指出了“心”之为“能”。这进一步说明,朱子所言的“心”的所指,是清楚、明白而稳定的,不是含混、模糊而游移的,因此“朱子心论”是有明确的基石的,而不是左支右绌的。而朱子以“心”为“知觉之能”,与其说比日常用法“窄”,不如说比日常用法精确,这种精确化的意义,是不可限量的。
三 心(知觉之能)等于“知(认识形下)—觉(领悟形上)”之能
在朱子,所谓“知觉之能”,究竟是怎样的能力?或者说“知觉之能”这四个字表明了“心”是一种怎样的能力?这是确定了“心等于知觉等于知觉之能”之后,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论者多以“知觉(之能)”为“认识”能力,但从笔者所见朱子文献来看,“认识”能力可能只说中了“知觉(之能)”中的“知”字,而遗漏了“知觉(之能)”中的“觉”字,后者足以表达一种比“认识”更深的“领悟”能力。换句话说,从笔者所见朱子文献来看,“知觉(之能)”是一种始于“认识”达于“领悟”的双重能力,而不只是“认识”这样一种单层能力。由此则可以说“知觉之能”四字表明了心是一种“通过认识去领悟”的能力,或者简言之,一种“知—觉”之能。此中“知”字表述浅层的“认识”能力、“觉”字表述深层的“领悟”能力这一点的依据,谨详述如下。
朱子曾明确表示,“知”字可以表述此心认取事物的经验因素(即形下因素)或者说直面对象的浅层能力,这种能力又可以称为“识”;“觉”字可以表述此心洞见事物的生生之理(即形上根据)或者说醒豁自身的深层能力,这种能力又可以称为“悟”。程子因与人论“觉”而提起孟子“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说,且论之曰“‘知’是知此事,‘觉’是觉此理”,朱子承之而曰:
“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觉”者,因理而觉。“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觉”,则是自心中有所觉悟。①
“先觉”“后觉”之“觉”,是自悟之觉。②
又正式注解《孟子》“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大学》“致知”的时候说:
“知”,谓识其事之所当然;“觉”,谓悟其理之所以然。③
“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④
这四条论述中,第一条第一句明确以“知”为一种认取事物的经验因素的能力、以“觉”为一种洞见事物的生生之理的能力;第一条第二句及第二条则又以两个“自”字明白指示出“觉”是醒豁自身的能力,同时反衬出“知”是一种直面对象的能力(“事物”与“自”相对则为对象)。盖经验因素都是在此心之外作为对象的,而生生之理则不但在事物自身,而且在此心自身,所以认取事物形色因素和直面对象、洞见事物生生之理和醒豁自身其实都是一回事,蒙培元论朱子之“觉”说:“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逆向的自我知觉,并不是横向的认知关系”,也已指出“觉”之为醒豁自身的能力这一点;①第三条、第四条则不但含有前两条的意思,而且指明了“知”能和“识”能、“觉”能和“悟”能的等同。张立文教授说:“‘知’是与事物接触,而获得对此一事的了解;‘觉’是在‘知’基础上,心中有所觉悟,即对此一事不仅有所了解,而且有一定的见解,形成了关于此一事物的整个形象,这就是‘知觉’。”延在钦说:“朱熹认为,所谓‘知’是指通过与事物接触而知晓该事物的所当然。而且,所谓‘觉’是指通过一种觉悟而领会其所以然……这样看来,‘觉’是比‘知’更深刻而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也都意识到了朱子这里“知”“觉”二字的区别,但所言还不够精确。
以上所引虽然主要都是朱子对经典特定语句的论述,不是他对作为心的“知觉之能”的直接分析,但以朱子对经典的熟稔和用字之不苟,将他对于“知”“觉”“心”的训释和论述结合起来看,应该至少是一条可行之路,加上朱子心论中处处显示出“心(知觉之能)”确实不止于“认识”而有一种“领悟”道理的能力,所以这条可行之路应该就是真正的道路所在。这即是说,虽然朱子没有明确说过,但如果我们将朱子所言的心理解为一种“通过认识形下去领悟形上”的能力,或者简而言之,一种“知—觉”之能,应该是无悖于朱子本意的。
又,心之为“知—觉”之能,尤其是其中的“觉”能,其实还蕴含着“实践”能力在其中,因为在朱子,道理是“当然而不容已”的,所以“觉于理”之心一定不会停留于“知(认识)”之静观,而必进于循理之实践,去实现道理或者说完成道理的自我实现。心的实践一定是通过驱动身体(包括魄也包括耳目口鼻在内)、支配事物来完成的,所以“觉”能所蕴含着的实践能力也被朱子称为“主宰”能力,或者说在朱子,“觉”能蕴含着“主宰”能力在自身。延在钦认为“依朱熹之看法,因为人类有知觉功能,所以能主宰一身和万事万物”①,也暗含着这个意思。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前文所提到的对于心的定义中,朱子为什么以“主于身而应事物”申说“知觉”二字,也才能理解下面这段对话:
问:“知如何宰物?”曰:“无所知觉,则不足以宰制万物。要宰制他,也须是知觉。”②
这番对话如果不是没有意义的话,弟子漏掉而朱子添加的“觉”字,便是奥秘所在:“觉”能蕴含着主宰能力在自身,所以添加“觉”字能够解答“知如何宰物”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朱子将心等同于“知觉”或者说“知—觉”之能的时候,并没有遗漏心的主宰乃至实践能力。众所周知,阳明后来说知行本体原是合一的,从朱子心论的视角看,则“知”“行”可以说是一心之中通贯的两种能力,故原本合一。
总而言之,通过考察朱子的“知觉”之说,我们发现,在朱子,心是一种蕴含着主宰、实践能力的“知(认识形下)—觉(领悟形上)”之能。可以说,朱子心论的地基不但是明白确定的,而且是丰富而非干瘪的。明确而丰富的地基,预言着一个稳固而庞大的体系。
第二节 从“知—觉”到思、情、意——心与思、情、意新探
一 心(“知—觉”之能)包含“思”能、“情”能、“意”能
上一节提到,在朱子,心或者说“知—觉”之能包括“思”“情”“意”在内,而“思”“情”“意”都是能力。所谓心(“知—觉”之能)包括“思”“情”“意”,是指“思”“情”“意”都是心(“知—觉”之能)在与包括“魄”中信息在内的具体他者接触时的升级版、运用态,具体来说:
此心(“知—觉”之能)最初与具体他者接触的时候,较浅的“知”能或者说认识能力会首先获得对象——即他者的经验因素,并升级为“思”以解析之。《语类》载朱子答弟子“知与思,于人身最紧要”之问时说“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与手相似,思是交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①,即是此意,后来阳明说“思是良知之发用”②,与朱子“思所以用夫知也”义同。随着“思”的深入,较深的“觉”能也会获得对象——即他者或者说此心的生生道理,所谓“思则得之”是也,③并升级为“情”以呈现之,呈现出来,便是此心对于他者表达基本态度(这种呈现是直达于眼神、面色的,所以是可见的,但未必所有人都有眼力见到)。朱子曾说:
性具于心,发而中节,则是性自心中发出来也,是之谓情。④
“情”是“性自心中发出来”,等于说“情”是此心“因理而觉”所生,即显示出“情”是“觉”能在获得对象时的升级版这一点(朱子这句话中所含的仅仅以“中节”者为“情”、不以“不中节”者为“情”的意思,待后文心与善恶处详辨)。需要说明的是,在朱子,心性二者“说着一个,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⑤,所以“性自心中发出来也,是之谓情”这一点,即“情是心灵因性理而觉所生”这一点,又常被朱子简化表述为“性之已发者,情也”⑥“情是性之发”⑦“(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⑧。也就是说,类似“情是性之发”这样的表达里面虽然没有出现“心”字,但实际上都隐含着“心”字在其中。如当朱子说“情根乎性”⑨“情本乎性,故与性为对”“性是根,情是那芽子”①,又以《乐记》“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之说中“性之欲”三字为“即所谓情也”②且又说“及其感物而动,则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则无自而发,故曰‘性之欲’”③的时候,其中“性”字背后都隐含着“心”字,所谓“说着一个,一个随到”是也,这是解读朱子言论时所需特别注意者。④话说回来,上所言“思”,无论面对怎样的他者,也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他者,其面貌永远都是解析,不会有任何异样,但“情”则因为是“性理”的呈现而一物一时一地各有其“理”,所以会随着他者的不同,甚至时地的不同而更有不同的具体面貌,所以《中庸》有“喜怒哀乐”之说,孟子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说,《礼运》有七情之说,而朱子也说“情却多般”。⑤
随着“觉”能升级为“情”,“觉”能中所蕴含的“实践作用”也会浮出水面而首先呈现为“意”,以围绕基本态度为他者谋划,然后“主宰”身体及事物,将谋划的蓝图付诸实施,他者因此得到一定的处置。《语类》载:
李梦先问情、意之别。曰:“情是会做底,意是去百般计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后用。”(夔孙录云:“因是有情而后用其意。”)⑥
问:“意是心之运用处,是发处?”曰:“运用是发了。”问:“情亦是发处,何以别?”曰:“情是性之发,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如爱那物是情,所以去爱那物是意。情如舟车,意如人去使那舟车一般。”①
情又是意底骨子。②
凡营为、谋度、往来,皆意也。③
这些言论,一方面指明了“意”之为“情”的后继、围绕“情”施展这一点;另一方面指明了“意”之为实践性的谋划之能的实质;延在钦说“这就是说,在发生某种情感后,意是要用尽一些方法而做该事情”④,也指出了这一点;柳阳辉说“‘意’是更具备主动性的心理活动”⑤、张立文教授曾说“(在朱子)‘意’是一种意见和主张,它是在‘知觉’积累了有关某一事的丰富感性材料基础上,通过‘心思’,认识了某一事物的本质,而形成了设想和方案”,所言皆近是。有学者认为朱子所言的“意”指意识或观念,接近于现代心字的内涵,恐于朱子营为、谋度、主张之说不合。现代所谓“意识”“观念”“心”其实只能对应上朱子所言的“知”“思”,而在朱子这里,“意”和“思”相近而实不同。相近处在于,二者都是心灵的高度运转状态,且“意”和“思”一样,也是无论面对怎样的他者,也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他者,其面貌永远都是谋划,不会有任何异样;不同之处在于,“思”是一种静观的、分析的、辨别的能力,静观准确、分析清楚、辨别明白,“思”便完成其职分,“意”是一种支配的、综合的、谋划的能力,支配妥当、综合完整、谋划周密,“意”才完成其职分。当然,二者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意”以“思”为基础,朱子认同程子所说“三(思)则私意起而反惑矣”⑥,又自言“如好恶是‘情’,‘好好色,恶恶臭’,便是‘意’”(观察、分辨“好色”“恶臭”,便是“思”),⑦即体现出这一点。
基于“意”给予他者的处置,如果双方都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则他者满足而退,不再需要“意”,“意”也“功成身退”,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如果有另外的具体他者接踵而来,此心自然又会有一番“思”“情”“意”的“运用”,但如果没有另外的具体他者接踵来至,另一番“思”“情”“意”的“运用”自然无从而起,此心不得不回复到纯然“知—觉”之能的面貌中去(这种状态不易理解,但在朱子这里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在后面中和新说部分会有详细论述)。后来阳明说“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①,所言诚是,从朱子心论的视角来看,“思”“情”“意”都不可能“悬空”,都是事物触发因而关联于事物的。
“思”“情”“意”既然是心(“知—觉”之能)在与他者接触时的升级态、运用态,则三者在朱子之为纯然能力而不含任何意义上的信息可知,因为能力的升级态、运用态,一定仍然是能力,不可能质变或掺入其他东西。其中“思”之为能力,毋庸赘言,“情”“意”之为能力,还有以下证据:
心,便是官人;气质,便是官人所习尚,或宽或猛;情,便是当厅处断事,如县尉捉得贼。②
情犹施设,心则其人也。③
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也。④
欲为这事,是意;能为这事,是情。⑤
情是会做底,意是去百般计较做底。⑥
此中第二条中的“施”“设”都是动词。一、二、四、五条皆以动词说“情”“意”,三、四两条复以“能”说“情”,则“情”“意”在朱子为纯粹能力可知。柳阳辉说“‘情’和‘意’都是心理活动”,也以“情”“意”为能力。⑦如前所言,“思”能、“情”能、“意”能的运用会在“魄”中留下信息或者说痕迹,这些信息或者说痕迹中有很多是直接关于“思”能、“情”能、“意”能的样貌的,却并非“思”能、“情”能、“意”能本身,日常以关于“思”能、“情”能、“意”能的信息甚至“思”能、“情”能、“意”能的运用所留下的一切痕迹为“思”能、“情”能、“意”能本身,从朱子的角度看,恐怕是一种张冠李戴。
又,“知”浅“觉”深,而“思”是“知”的升级态,“情”是“觉”的升级态,则“思”自然是“情”的先导,“情”自然是“思”的后继,二者是先后串行关系,而非同时并行的关系,朱子描述心之应事接物时说“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①,也表明了这一点。由此则在朱子,“思”和“情”是不可能冲突的,而日常所谓“思”和“情”或者说理智和情感的冲突,实际上是一路“思”—“情”和另一路“思”—“情”的冲突,只不过前者中作为后继的“情”可能很微弱,后者中作为先导的“思”可能很迅捷,以至于人们不易察觉而已(这种迅捷之思也曾被《中庸》表述为“诚者不思而得”,但至少在朱子看来,所谓“不思而得”本质上仍然是“才思即得”,其中“不思”只是说没有平常人那种“百思不得其解”的迟钝之“思”而已,朱子回答弟子“圣人有思无思”之问说“圣人……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即是此意)。如孟子“孺子将入于井”一章中,“乍见”即有恻隐之心,好像只有“情”没有“思”,但实际上恻隐之心建基于对孺子所处情境迅速而清晰的认知和判断;那些想要“邀誉于乡党朋友”的人,好像只有“思”没有“情”,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对孺子无“情”,对“邀誉”则有执着的喜好,难免有对于能够邀誉的窃喜;还有的人在救与不救之间纠结,“救”的理路可能是“判断孺子将入井—恻隐之心”,也可能是“判断孺子将入井和想到可以邀誉—邀誉之窃喜”或其他,“不救”的理路可能是“救了也不能邀誉——讨厌浪费时间”,也可能是“想到讹诈事件——恐惧”或其他,但都不可能在“思”—“情”这一线路上缺少任何一环;而这种纠结,以及出于邀誉的救或者不救、出于对于讹诈事件的恐惧的不救,显然都是“思”之太多所致,这些坏的结果虽然都表现在“情”上,但无法在任何意义上归罪于“情”,所以对治的方法也不会是加强理智对于情感的控制,而是“思”的自我净化,包括朱子在内的理学家经常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思”上,根源即在于此。另外,关于“知—觉”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其所发出的“思”—“情”会分为两路形成纠结,我们在后文“道心人心”部分会进行讨论。
总而言之,在朱子,心(“知—觉”之能)包含“思”能、“情”能、“意”能这一系列能力在自身,或者说,心之为“知—觉”之能,其实是可以运用为“思”能、“情”能、“意”能的“知—觉”之能。朱子心论地基的丰富性,可以说已经毋庸置疑了。需要说明的是,论者或认为,朱子用以表述心之官能的,还有“志”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在朱子,“志”并非一种独立的官能,而只是一种特殊的“情”,一种由高明广大的事物所触发的强烈而恒久的情感,其言曰:“‘志’与‘意’都属情,情字较大”(这里朱子一反其区分情、意的通常做法,将意也纳入情的范畴中,实际上只是以情指代思、情、意这一系列能力,并非真的取消了意的独立性。后面“心统性情”部分我们还会涉及这一点),①“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②即是此意。
二 基于“知—觉”“思”“情”“意”的体用分析
不难看出,在朱子,“心”在作为自己单独存在的时候,其面貌是“知—觉”之能,在发挥自己的才能的时候,其面貌是“思”能、“情”能、“意”能,在这个意义上朱子以“知—觉”之能为“心本身”,以“思”能、“情”能、“意”能为“心之运用”。朱子说:
然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及其动也,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艮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①
其静时,思虑未萌,知觉不昧,乃复所谓“见天地之心”,静中之动也。其动时,发皆中节,止于其则,乃艮之“不获其身,不见其人”,动中之静也。②
动静、中和问题待后文详论。据第一段后半段及第二段可知,第一段前半段中所谓“事物未至,思虑未萌”其实是“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一性浑然道义全具”是在申说“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并不是在“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之外有所添加,“体”即本身,所以所谓“事物未至,思虑未萌(知觉不昧),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其实就是在说“知—觉”之能是“心本身”。朱子曾说“意则有主向”③,所以“各有攸主”其实是在说“意”能,而所谓“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其实就是在说“思”能、“情”能、“意”能是“心之运用”。又朱子《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说:
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按:此处“性”字,王懋竑《年谱》作“情”)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④
此中“思虑未萌”无疑仍然是“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体”仍然是“本身”的意思,“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也是在申说“体”而不是有所增加,所以所谓“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实质上也是以“知—觉”之能为“心本身”。这里的“情”字代表“思”“情”“意”三能,所以所谓“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也是以“思”能、“情”能、“意”能为“心之运用”。又朱子说:
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说得?①
这里的“体用”也是“本身和运用”的意思。“未发之前”即未与他者接触而“运用”之时,此心的面貌只能是“知—觉”之能,而朱子谓之“心之体”,也是以“知—觉”之能为心本身。“已发之际”即与他者接触而“运用”之时,此心的面貌会是“思”能、“情”能、“意”能,而朱子谓之“心之用”,也是以“思”能、“情”能、“意”能为心之运用。又朱子《大学章句》中说:
经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诚。”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②
这里的“意”代指“思”能、“情”能、“意”能,“知”代指“知—觉”之能,“心体”即心本身,“发”即运用。以“心体之明有所未尽”说“知”之未至,蕴含着以“知—觉”之能为心本身的意思。以“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说“意”之未诚,蕴含着以“思”能、“情”能、“意”为心之运用的意思。③后来阳明说“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①,也以“知觉”为本身,以“意”为运用,与朱子大体相同。
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是不会随他者的来去而存在或不存在的,作为心之运用的“思”能、“情”能、“意”能,则会随他者的来去而出现或消失,在这个意义上朱子说:
因此偶复记忆胡文定公所谓“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则虽一日之问百起百灭,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语。②
“不起不灭心之体”“一日之间百起百灭,而心固自若”即是说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不会随他者的来去而存在或不存在,“方起方灭心之用”则是说作为心之运用的“思”能、“情”能、“意”能则会随他者的来去而出现或消失,所以朱子认为“自是好语”。朱子紧接着又强调说:
但读者当知,所谓“不起不灭”者,非是块然不动、无所知觉也,又非百起百灭之中,别有一物不起不灭也。
此中“无所知觉”是“无知觉之能”的意思,不是“无知觉对象”的意思。一直存在的心本身实际上就是“知—觉”之能,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以说“所谓‘不起不灭’者,非是块然不动、无所知觉也”。他者来至而“思”能、“情”能、“意”能出现,则“知—觉”之能已然升级,不再存在“思”能、“情”能、“意”能之外的“知—觉”之能,他者离去而“思”能、“情”能、“意”能消失,则“知—觉”之能则回复到“知—觉”之能的面貌,所以说“非百起百灭之中,别有一物不起不灭也”;后来阳明说“然谓‘良知常若居于优闲无事之地’,语尚有病。
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①,又说:“未发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②,也是此意。作为运用面貌的“思”能、“情”能、“意”能意味着心与他者的接触,可以说是一种“动”的面貌,相对而言,作为本来面貌而意味着心的独自存在的“知—觉”之能,虽然“非是块然不动”,但终究显示出一种“静”态出来,所以朱子紧接着又说:
但此心莹然,全无私意,是则寂然不动之本体,其顺理而起、顺理而灭,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尔。
“寂然不动”即“静”,“本体”即“本来体段”,也即“本身”或者说“体”,③“感”即“动”。“寂然不动之本体”即以“静”形容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即以“(感)动”形容作为心之运用的“思”能、“情”能、“意”能。在前文所引《答张钦夫》第四十九一段中,朱子在“事物未至”和“事至物来”前面分别冠以“方其静也”“及其动也”字样,也以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为“静”,以作为心之运用的“思”能、“情”能、“意”能为“动”。又朱子曾说: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能觉者,而无所知所觉之事,此于《易》卦为纯坤不为无阳之象”④“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觉而无运用,冬之象也”①、“心如水,情是动处”②,也以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为“静”,以作为心之运用之一的“情”能为“动”。后来阳明说“心之本体原自不动”③,与朱子意同,而他回答弟子“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的问题时说“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用言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④不可谓不精彩,但若说其中“先儒”包括朱子,则未免诬枉,朱子之意也是“静可以见其体(而用在其中),动可以见其用(而体在其中)”,而不是“以动静为体用”。事实上,“动静”二词是形容词而非名词,是虚词而非实词,“体用”则是名词、实词,很少会有思想家犯“以形容词、虚词为体用”的错误,弟子的问题应该只是出于他自己的误解,基本不会有思想家能够真的能够对号入座。
我们上文已经提到,在朱子,“心具此性(众理)”,而“心具此性(众理)”的首要意义,便是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具此性”,在这个意义上,如上面所引《答张钦夫》第四十九及《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所示,朱子主要在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这里说“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天命之性,当体具焉”。又朱子说:
然则仁义礼智信云者,乃所谓未发之蕴、而性之真也欤?⑤
未发之前,万理备具……所以合做此事,实具此理,乃未发也。⑥
“未发”则此心作为其本身也即“知—觉”之能存在,所以这两句也都是在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上说“具此性(众理)”。⑦进一步,我们上文也曾提到,朱子反对“性中(外)别有一个心”“性外别有一个知觉”,而认为“心性只是一个物事,离不得”“理不离知觉,知觉不离理”,甚至“此两个说着一个,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所以朱子经常将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藏在“性”字之中,其言曰:
情之未发者,性也。①
喜怒哀乐未发,无所偏倚,此之谓“中”。“中”,性也;“寂然不动”,言其体则然也。②
其未发,则性也。③
未发是性。④
大概在身则有个心,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⑤
“未发”“心之体”在上文被表述为“知觉不昧”而“一性浑然”,在这些表述中却直接表述为“性”,唯一的合理解释只能是,朱子将作为心本身的“知一觉”之能藏在了“性”字之中,这和他“说着一个一个随到”的说法也是一致的。事实上,朱子是有明确的“藏‘知一觉’之能于性”乃至“藏心于性”的意识的,他论《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之说曰“所谓‘静’者,亦指未感时而言耳。当此之时,心之所存,浑是天理,未有人欲之伪,故曰‘天之性’”⑥,“所引‘人生而静’,不知如何看‘静’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耳。盖当此之时,此心浑然,天理全具”⑦,引入“心”来解释“天之性”之说,即体现出这一点。他又曾回答弟子孔子不说心之问说“孔门虽不曾说心,然答弟子问仁处,非理会心而何。仁即心也,但当时不说个‘心’字耳”⑧,也体现出明显的“藏心于性”的意识。论者多认为朱子特别强调心、性之别,因而对于以上说法难以有确切的理解,但实际上,朱子所言“心、性之别”只是和其他学者对比才显得“特别”,在其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则与“心性之一”平起平坐甚至以“心性之一”为前提,可谓无甚“特别”,所以除了朱子明言心性之别的地方,其他所有论述中的“心”字都蕴含着“性”字在其中,“性”字也都蕴含着“心”字在其中,这也是解读朱子学说所需特别注意的地方。后来刘宗周说“朱子以未发言性,仍是逃空堕幻之见。性者生而有之之理,无处无之”①,一方面是没有看出“性”字之后隐藏的“知—觉”之能,另一方面是不知“未发为性”只是“未发可以见其体”的意思,不是将未发和性完全等同。
“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被藏在“性”字之中,则“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的属“静”常常会被表述为“性”属“静”,“思”能、“情”能、“意”能作为“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的发用,也常常会被表达为“性”的发用,朱子说“人受天地之中,只有个心性安然不动……性静而情动”②“性静,情动”③“性是静,情是动”④,都是以“性”之属“静”表述“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的属“静”,又朱子说“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⑤,则是以“性之用”表述“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的发用,不难看出,上文所引用到的“情是性之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需要说明的是,朱子不但有“心之(本)体”的说法,而且继承了孟子“本心”的说法。由于这两个概念字面相似,且朱子既说过“心之本体本无不善”⑥,又说过“本心元无不善”⑦,所以论者多将二者等同起来,延在钦说:“从朱熹所提的‘未尝不善’‘本无不善’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谓‘心之本体’是相当于孟子所提出的不忍人之心、四端之心、良心、本心等概念”⑧,即是如此,牟宗三亦然。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很不相同的。从字面上讲,二者的结构完全相反:“心之本体”中“心”是定语形容词,“本(体)”是名词;而“本心”中则“本”是定语形容词,“心”是名词。从所指上讲:“心之本体”和“心之发用”相对,是指心本身,属于对“心”的分析;“本心”则和“非本心”或者说“被奴役之心”相对,而有其本身,属于对“心”的评判。朱子说:
夫人心是活物,当动而动,当静而静,动静不失其时,则其道光明,是乃本心全体大用。①
不错底是本心,错底是失其本心。②
第一条即指明“本心”有“体”有“用”,第二条则显示出“本心”属于对心的评判。朱子《论语集注》曾引胡氏之言说“其日用之间,本心莹然,随所意欲,莫非至理。盖心即体,欲即用”云云,③注解《孟子》“本心”之说的时候说“本心,谓羞恶之心”④,又论之曰:“盖本心之发,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为而为之也。”⑤这三处合而观之,也可知在朱子,“本心”有“体”有“用”。事实上,发用意义上的“本心”,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日常所言“本意”,朱子说“盖得时行道者,圣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圣人之不得已”⑥“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为季氏附益,夫岂其本心哉”⑦“而今若教公读易,只看古注,并近世数家注,又非某之本心”⑧“建贼范汝为本无技能,为盗亦非其本心”⑨,这些话里的“本心”都可以换成“本意”而不失其义,盖“意”属于“心”,笼统而言则曰“本心”,精确而言则曰“本意”。“本意”当然不可能在“心之本体”的概念之内。陈来教授《朱子哲学研究》第十章“心说之辨”极具启发意义,但其中有一个基本误解,即将“本心”等同于“心之本体”来看,导致这一论辩的实义没有得到完全的揭示,我们后文讨论朱子敬论的时候会重新梳理“心说之辨”中的关键论述。
第三节 智愚与学习——心灵差异新探
一 气禀差异论本质上是心灵差异论
所谓“心是可以运用为思能、情能、意能的‘知—觉’之能”,当然是说所有人的心“自婴儿至于老死”都是可以运用为“思”能、“情”能、“意”能的“知—觉”之能。从“体”上讲,没有人在任何时候有比“知—觉”之能更多的能力,也没有人在任何时候缺少“知”“觉”二者中任何一重能力,也没有人在任何时候有不同于“知—觉”的其他结构,更没有人的“知—觉”之能不是无间于他者的来去而恒定存在的;从“用”上讲,没有人在任何时候有比“思”能、“情”能、“意”能更多的能力,也没有人在任何时候缺少“思”能、“情”能、“意”能中任何一种,也没有人在任何时候有不同于“思”“情”“意”的其他顺序,更没有人的“思”能、“情”能、“意”能不是随他者的来去而出现或消失的。朱子说“熹尝谓:有是形,则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则谓之性,仁义礼智是也;性之所感于物而动则谓之情,恻隐、羞恶、是非、辞让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圣凡为有无也”①“以某看来,须是别换过天地,方别换一样人情……天地无终穷,人情安得有异”②“有个人在此,决定是有那羞恶、恻隐、是非、辞让之情”③,即表明了上述意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朱子没有看到人类心灵之间在相同基础上显然存在的差异尤其是先天差异,朱子又说:“心本未尝不同,随人生得来便别了。”④即是说人类心灵之间在相同的基础上有差异,且这种差异是与生俱来的。但“心”的“随人生得来便别”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人类心灵之间的先天差异究竟是什么?朱子既没有在这里接着说明,似乎也没有在其他地方有所论述,以至于学界目前对朱子心论的研究都直接绕过了这一问题(延在钦认为“由于人所禀受的气质不同,在心的功能上有一定的差异”①,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并未深究)。但一方面,如果朱子心论在这个问题上薄弱,那么它对于人类心灵的解释力会变得很可疑;另一方面,朱子这里不含“心”“别”字样的言论,未必就一定不是在论述人类心灵差异。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地检查朱子著名的“气禀(气质)论”中在“人”的范围内的论述,便会发现,朱子的“人类气禀(气质)论”,是或者首要地是在论述人类心灵之间的先天差异,或者说是或者首要地是“随人生得来便别”的注脚,这一点在以下言论中最为明白地显示出来。
其一,朱子论“气质”曰:
人性虽同,禀气不能无偏重。有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而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而恻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水火亦然。唯阴阳合德,五性全备,然后中正而为圣人也。②
这一段是就先天而言。在人,所谓“禀气”无非身、心二者。如果所谓“木气”“金气”是指“身体”的话,那么所谓“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便会沦为身体决定论。这显然不可能是朱子本意。只有所谓“木气”“金气”首先乃至完全是指“心”,“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才能够得到合理的理解。如此则至少朱子这一段中的“禀气”指“心”无疑,而所谓“禀气”之“偏重”“木气重”“金气重”“中正”则都是在对比人类心灵之间的先天差异。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木气”“金气”既非身也非心,而是人身上的第三种存在,这样的理解并非朱子之意,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心之形而上下部分辨明。
其二,朱子回答弟子“气禀有清浊不同”之问说:
气禀之殊,其类不一,非但“清浊”二字而已。今人有聪明,事事晓者,其气清矣,而所为未必皆中于理,则是其气不醇也。有谨厚忠信者,其气醇矣,而所知未必皆达于理,则是其气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见。①
这一段也是在先天的意义上说的。其中“聪明事事晓”“谨厚忠信”也显然都是在说“心”,而所谓“气清”而“不醇”“气醇”而“不清”也显然都是在说人类心灵之间的先天差异。又朱子说:
气禀所拘,只通得一路,极多样:或厚于此而薄于彼,或通于彼而塞于此。有人能尽通天下利害而不识义理,或工于百工技艺而不解读书。②
很难想象,“通天下利害而不识义理”和“工于百工技艺而不解读书”不首先是心灵方面的先天差异。
其三,朱子曰:
然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故上知生知之资,是气清明纯粹,而无一毫昏浊,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学而能,如尧舜是也。其次则亚于生知,必学而后知,必行而后至。又其次者,资禀既偏,又有所蔽,须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后方能及亚于生知者。及进而不已,则成功一也。③
这一段也是在先天的意义上说的,其中所谓“昏明清浊之异”可能有身体的因素在其中,但必定首先是指人类心灵之间的先天差异,惟其如此,后文才能一直说“知”云云。又朱子说:
性者万物之原,而气禀则有清浊,是以有圣愚之异。④
惟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天理浑然,无所亏阙。①
这两句也都是在先天的意义上说的。很难想象,朱子所说的“圣愚之异”不是或者不首先是心灵方面的差异,而“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则几乎已经直接说出这一点了。
其四,朱子论人的“气质之性”说:
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以不净之器盛之,则臭;以污泥之器盛之,则浊。②
这一段也是在说先天差异,只要我们没有忘记朱子“心性之别,如以碗盛水”“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这样的表达,便能很容易地发现其中的“器”都是指“心”,而所谓“净器”“不净之器”“污泥之器”,则是在人类心灵之间对比出来的先天差异。
至此已经可以确定,朱子的“人类气禀(气质)论”,就是或者至少首先是一种“心灵先天差异论”,能将所谓“心本未尝不同,随人生得来便别”的实义初步解析出来。
二 从“智”“愚”到“学”
根据上面的引文,朱子所论人类心灵之间的先天差异可以表述为一种先天的“智”“愚”之异。③具体来说,在朱子,有的人的心灵生来便是相对更为“智”的,有的人的心灵则生来便比较“愚”。从“体”上讲,有的人的“知—觉”之能生来便相对更为“智”,其全面认识透彻领悟的机会相对更多,多之至,则无论后天与任何他者接触,都能够全面认识透彻领
悟,没有任何他者能够蒙蔽、诱惑进而奴役它;有的人的“知—觉”之能则生来便比较“愚”,其全面认识透彻领悟的机会则相对较少,少之至,则后天只有与极其简单的他者接触,才能够全面认识透彻领悟,稍微丰富或者复杂一点的他者都能够蒙蔽、诱惑进而奴役它。相应地,从“用”上讲,有的人的“思”能、“情”能、“意”能生来便相对更为“智”,其清楚分析饱满表态周密谋划的机会相对更多,多之至,则后天无论与任何他者接触,都能够清楚分析饱满表态周密谋划,没有任何他者能够使之“正墙面而立”;有的人的“思”能、“情”能、“意”能则生来便比较“愚”,其清楚分析饱满表态周密谋划的机会相对更少,少之至,则后天稍微丰富或者复杂一点的他者,便能够使之捉襟见肘。其中生来便极于“智”的心灵,便是上文所谓“上智生知之资”,生来便非常“愚”的心灵,便是和“上智”相对的“下愚”之资,生来便比较普通的心灵,则介于“上智生知之资”和“下愚”之资之间,而为参差不齐的普通资质。①只有生来便上智的心灵,才会终其一生都不会有丝毫地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朱子说:
如尧舜之时,真个是“宠绥四方”。只是世间不好底人,不定叠底事,才遇尧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谓之“克相上帝”,盖助上帝之不及也。②
在朱子,“尧舜”即是“上智生知之资”的代表,所以这段话即是在说生来便上智的心灵,会终其一生都不会有丝毫的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除此之外的其他心灵,在后天都存在着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的可能,只是越接近“上智生知之资”,这种可能性越小,且一旦发生,程度也越浅,越至于“下愚”之资,这种可能性越大,且一旦发生,程度也越深。
生来便上智的心灵之所以终其一生都不会有丝毫地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也是因为生来便上智的心灵在后天必然彻底地“好学”且极其善于学习。朱子说“质敏不学,乃大不敏。有圣人之资必好学,必下问。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学,更不问,便已是凡下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也只是好学下问。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于帝,无非取诸人以为善。孔子说:‘礼,吾闻诸老聃。’这也是学于老聃,方知得这一事”①,“如孔子所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此有甚紧要?圣人却忧者,何故?惟其忧之,所以为圣人。所谓‘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②,即是说生来便上智的心灵在后天一定会彻底好学,后来王夫之也说“质以忠信为美,德以好学为极”,③认为好学是最高的德性,和朱子正相印证;又朱子说“‘好古敏以求之’,圣人是生知而学者。然其所谓学,岂若常人之学也!‘闻一知十’,不足以尽之”,④则是说生来便上智的心灵在后天一定会极其善于学习。后天彻底“好学”且极其善于学习,既体现出其生来便已然上智的绝佳资质,又保证着它终其一生都不会丝毫丧失其上智的绝佳资质,⑤则其终其一生都不会有丝毫的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自然不在话下。
生来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虽然不会完全没有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但终究难免时或学而不得乃至时或辍学,朱子论孔子“发愤忘食”说:
“‘发愤忘食’,是发愤便能忘食;‘乐以忘忧’,是乐便能忘忧,更无些小系累,无所不用其极,从这头便点到那头,但见义理之无穷,不知身世之可忧,岁月之有变也。众人纵如何发愤,也有些无紧要心在;虽如何乐,终有些系累乎其中。”①此中“众人纵如何发愤,也有些无紧要心在”,即是说生来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难免时或辍学。②辍学或者学而无得的时候,生来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裹足不前,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的可能保持其存在。但学习且有得的时候,生来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得以改变自身的先天资质,向“上智”自我提升,理学认为“学”的本质是“变化气质”“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强”,即是此意,延在钦说“所谓‘变化气质’可以视为要通过学问而把心的功能提高到从‘暗’到‘明’的阶段”,也指出了这一点。③自我提升的过程中,不但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的可能性逐渐降低,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也不断增强,以至于自我提升的效率逐渐提高。到了自我提升的终点,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也达到极强,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的可能性彻底消除,因为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完全改变了自身的先天资质,自我提升到了“上智”之资,所谓“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是也。④不难看出,先天越是接近于“上智生知之资”的心灵,起点越高、效率越高,因而后天自我提升为“上智”之资便越容易,先天越是至于“下愚”之资的心灵,起点越低、效率越低,因而后天自我提升为“上智”之资便越难。朱子在上面“以污泥之器盛之,则浊”后面接着说:“但既臭浊,猝难得便清。故‘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也煞用气力,然后能至。”又说:“人之为学,却是要变化气禀,然极难变化。”①认为先天越是至于“下愚”之资的心灵,后天自我提升为“上智”之资便越难。
话说回来,在朱子,即便是生为“下愚”之资的心灵,在后天也不会完全没有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孔子曾以“下愚”为“不移”,而朱子则认为孔子所谓“不移”是“不肯移”,而不是“不可移”,因此认为“下愚”终究是“可移”的),②所以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向“上智”之资自我提升是必然趋势。这即是说,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同时也是生来便带着向“上智”之资自我提升的倾向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与其称为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不如称为生来便向“上智”之资自我提升的心灵。或者说,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其自我认知可能是“生来较为普通”,其先天自我认同却不会是“生而较为普通”,而一定是“上智生知之资”。正是在先天自我认同的意义上,朱子说“圣人于天下,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③,又认为每一个人的心从本质上讲都是“完具”的④,这些话并不是说普通人有两颗心,只是说其有高于自身之所是的自我认同,上文“心本未尝不同”一言,应该也有这方面的意思。“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而“本未尝不同”,则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向“上智之资”的自我提升,在确实是一种自我改变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回归乃至自我复原,或者说对于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而言,“学”的根本性质,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回归乃至自我复原的工作。朱子说:
今之为学,须是求复其初,求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与我者,便须以圣贤为标准……人之为学,正如说恢复相似:
且如东南亦自有许多财赋,许多兵甲,尽自好了,如何必要恢复?只为祖宗元有之物,须当复得;若不复得,终是不了。今人为学,彼善于此,随分做个好人,亦自足矣,何须必要做圣贤?只为天之所以与我者,不可不复得;若不复得,终是不了,所以须要讲论。学以圣贤为准,故问学须要复性命之本然,求造圣贤之极,方是学问。①
更有一事,如今学者须是莫把做外面事看。人须要学,不学便欠阙了他底,学时便得个恰好。②
这些话即是说,对于“上智生知之资”之外的其他心灵而言,“天之所以与我者”虽然并非“上智”心灵,却是以“上智”心灵为自我认同的心灵,所以后天只要还没有自我提升至于“上智”之资,此心便不会满足、不会善罢甘休,只有自我提升至于“上智”之资,此心才会觉得做回了自己、觉得刚刚好。
由此可见,在朱子,从先天的角度来看,人类心灵有同有异:其同不仅在于具体的功能组成是相同的,而且在于无不以“上智”之资为自我认同,其异则在于其实际所是从已然“上智”到尚是“下愚”的千差万别。从后天的角度来看,人类心灵总体趋同,先天便上智的心灵会保持其“上智”之资,先天较为普通的心灵则无不向“上智”之资自我提升,但因为先天较为普通的心灵自我提升的难度有难有易、效率有高有低,所以在总体趋同的背景下,先天较为普通的心灵之间的差距反而有可能被拉大。又,无论是对于生来便上智的心灵的后天自我保持而言,还是对于生来较为普通的心灵的自我提升而言,又或者对于后天自我提升为“上智”之资的心灵其后的自我保持而言,“学”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①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强调“人之所贵者,惟学而已矣”,又论“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说:“如狂作圣,则有之。既是圣人,决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学。”(假设“圣”不“学”,则“作狂”,假设“狂”能“学”,则“作圣”,这里的因果联系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只有“狂”能“学”的假设可能兑现,“圣”不“学”的假设是不可能兑现的,所以说“如狂作圣,则有之。既是圣人,决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学”)
众所周知,朱子对陆象山的一个著名批评,在于“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②。既然气禀之异本质上是心灵方面先天的“智”“愚”之异,那么朱子这一批评的实义便是在说陆象山不顾人类心灵先天存在的从“上智”到“下愚”的差异。考诸陆象山自己的言论,如其言曰“圣人与我同类,此心此理谁能异之”③,“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④,“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⑤,不得不说,象山确实主要是在说“心本未尝不同”的意思,而较少言及“随人生得来便别”的意思。相形之下,不得不说,朱子对于人类心灵的刻画确实是更为全面、细致的。
小结
本章我们主要探讨了朱子心论的“官能”面向。通过三节的探讨,我们发现:在朱子,心的基本义,即是指人这里的“知—觉”之能,而“知—觉”之能能够运用为“思”能、“情”能、“意”能;人类心灵之间在官能构成和自我认同方面是相同的,但同时存在着从“上智”到“下愚”的千差万别,“学习”能够使这种差别不断得到调整,并指向“愚”的最终消除。朱子对于人类心灵基本面的刻画是明晰、确定、全面而细致的。
第一节 心等于知觉之能——心与知觉新探
一 心等于知觉
前辈学者无不注意到朱子这里“知觉”和心的密切关系,但一些学者认为在朱子,“知觉”就是心或者说心等于“知觉”,②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在朱子,“知觉”仅仅是心的主要功能而心并不完全等同于“知觉”①,且双方都没有对另一方的观点作出应对,这使得双方的见解都还停留于一种语焉不详的状态。这两种说法表面差之毫厘,但实际上直接冲突,而且涉及整个朱子心论地基的确定性,必须加以辨明、厘定。笔者重新考察朱子所有相关论述后认为,“心等于知觉”说应该才是朱子本意(“心具众理说”不在“心等于知觉说”之外,此待后文详论),“知觉仅仅是心的主要功能”之说应当是出于对朱子一些言论望文生义的误解。
首先,遍检朱子现存著作,可以发现朱子对于心共有四处定义,谨依文献可靠度排列如下:
(一)《尚书·大禹谟解》:“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②
(二)《孟子集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③
(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心”则知觉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④
(四)《朱子语类》:有知觉谓之“心”。⑤
此中“神明”是“知觉”的代名词,而从句法语义上讲,“主于身而应事物”“具众理而应万事”“具此理”分别是对其前面“人之知觉”“人之神明”“知觉之在人”的进一步申说,不是在“人之知觉”“人之神明”“知觉之在人”之外有所增添,所以前三处定义都支持“心等于知觉”之说,只有第四处定义表面支持“心仅仅是有知觉而并不等于知觉”的观点。但一方面,前三处定义所在文献都更为正式,而第四处定义所在文献则没有那么可靠;另一方面,第四处定义实际上也不是要为“知觉”之外的东西保留余地,而只是要提示我们,心之为“知觉”还“具众理”而不可以浅显观而已,朱子在这里、乃至在其他含有“心有知觉”之意的言论中,都没有进一步说“心还有某某”,①可以反证出这一点来。
事实上,就是在《语类》中,也随处可见“心等于知觉”的证据,如朱子在讲论中时而说“心性只是一个物事,离不得”②,时而又说“理不离知觉,知觉不离理”③,时而反对“性中别有一个心”,时而又反对“性外别有一个知觉”(“性中别有一个心”的“中”是“外”的意思),④甚至不加说明地以横渠“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心”之说来佐证自己“有这知觉,方运用得这道理”的看法⑤,此中“心”和“知觉”的同位互换,无疑都蕴含着“心等于知觉”的前提。
不可否认,在正式而可靠的《中庸章句序》中,朱子曾说:“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⑥此中“心之虚灵知觉”一言,表面上好像是在表达“心的虚灵知觉”而支持“心仅仅是有知觉而并不等于知觉”的观点。但实际上,“心之虚灵知觉”并不是“心的虚灵知觉”的意思,而是“心作为虚灵知觉”的意思。因为一方面,“之”字在朱子不但有“的”的意思,而且有“作为”的意思,如“理之所以然”“念虑之微”“事为之著”,都是“理作为所以然”“念虑作为微者”“事为作为著者”,而不可能是“理的所以然”(在朱子,“理”便是“所以然”,不可能更有“理的所以然”)、“念虑的微”“事为的著”的意思(这两种表达都是不合文法的);另一方面,下文直接将“人心、道心之异”归为“所以为知觉者不同”,可以反向确定“心之虚灵知觉”是“心作为虚灵知觉”的意思,而不是“心的虚灵知觉”的意思。在《文集》《语类》中,朱子也曾有“心之知觉”的表达,如《文集》“心之知觉,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①、《语类》“心之知觉,又是那气之虚灵底”②,不难推知,这些话中的“心之知觉”也都是“心作为知觉”的意思,而不是“心的知觉”的意思。这也是我们在朱子这里找不到“心之其他”的原因所在。
总而言之,“心等于知觉”之说应该才是朱子本意,“知觉仅仅是‘心’的主要功能”之说应该是出于对朱子一些言论望文生义的误解。后来阳明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③,也指出了“心”和“知觉”的等同。确定了这一点,朱子心论才能获得稳定而确切的地基,朱子关于心的其他论述才能顺利地获得理解。有学者认为,朱熹对心的讨论是极为多的,他对心的解释就像孔子对仁的解释一样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并没有对其下一个固定而明晰的定义。“多方面、多层次”自然是好的,但“多”到“没有对其下一个固定而明晰的定义”,便无异于说朱子对于心的讨论是一个大杂烩,“分殊”而不“理一”。这种说法的出发点明显是为朱子辩护,但如此辩护,恐适得其反。
二 心(知觉)等于知觉之能
认为心等于“知觉”的学者,又或认为“知觉(心)”有时不仅仅指“知觉之能”,还包括“知觉成果”在内。①但笔者梳理朱子相关文献后发现,在朱子,心(知觉)应该一直都仅仅指“知觉之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包括“知觉成果”在内(在朱子,知觉之能包括思、情、意在内,但思、情、意都不是“知觉成果”,此待后文详论)。因为“知觉成果”就其所是而言,应该纯粹是一些信息,只是因为是知觉带来的而得以有“知觉”作定语,不在任何意义上是一种知觉;就其所在而言,在朱子这里是存储于有别于心的“魄”中,没有任何机会成为“心”的一部分(“知觉成果”因为是“心/知觉”带来的,往往带着关于“心/知觉”的信息,即之可见“心/知觉”的内在条理,如康德所谓感性纯直观、知性范畴、理念之类是也,但即便是这些关于“心/知觉”的信息,也只是信息而存于“魄”,无论从所是还是所在而言,都不在“心/知觉”的所指之内)。这即是说,在朱子这里,存在着一种叫作“魄”的器官,这一器官负责存储心所获得的信息,但并不在心的所指之内。朱子说:
会思量讨度底便是魂,会记当去底便是魄。②
知识处是神,记事处是魄……小儿无记性,亦是魄不足。③
凡能记忆,皆魄之所藏受也,至于运用发出来是魂。这两个物事
本不相离……魄盛,则耳目聪明,能记忆,所以老人多目昏耳聩,记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④
此三条论“魄”甚明,可见朱子承认“魄”的存在并归信息存储功能于“魄”。进一步,朱子又说:
不可以“知”字为“魄”,才说“知”,便是主于“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咸淡,要从舌上过。①
“知”是“心”而不可以为“魄”、“心但能知(而不能存)”,则负责存储的“魄”之不属于“心(知觉)”甚明。②朱子又说:
气曰魂,体曰魄。③
“曰”在这里虽然只是“属于”的意思,不是“等于”的意思,但此已可见在“身心”这组对待之中,“魄”是属于身体而不是属于“心(知觉)”的。总而言之,在朱子,“心(知觉)”仅仅负责获取信息(“心但能知”),存储信息的任务则由“魄”来负责(“凡能记忆,皆魄之所藏受也”);“心(知觉)”才获取信息,信息便即刻存入“魄”中成为“魄之内容”甚至是“身之内容”(“体曰魄”),“心(知觉)”则只有“对象”而始终无所谓“内容”;从身体之外获取信息时是如此,从“魄”中获取信息时或者说对“魄”中信息进行再勘察(即日常所谓反观内省)时也是如此。然则“知觉成果”之为“‘魄’中信息”,而“知觉(心)”之不必越俎代庖,而始终仅仅指“知觉之能”,应当可以无疑。众所周知,朱子对佛教“以心观心”之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果“知觉(心)”真的包括“知觉成果”的话,那么人的正常反思、内观或者说曾子所谓“三省”、《中庸》所谓“内省”便只能解释为“以心观心”,而朱子对“以心观心”之说的批评便会显得不近人情,甚至有悖于自己的儒家立场。但实际上在朱子,人的正常反思、内观或者说曾子所谓“三省”、《中庸》所谓“内省”是“以心观魄”而为一种“以心观物”(“魄”中信息也是一种“物”),并不是“以心观心”,朱子对“以心观心”之说的批评仅仅指向“以知觉之能观知觉之能”,并不伤及人的正常反思、内观和曾子所谓“三省”、《中庸》所谓“内省”。①
不可否认,朱子本人对于“心(知觉)”概念的使用中,有几种表达的字面会对人产生误导,让人误以为其所言“心(知觉)”涵盖“知觉成果”,这些表达有:(1)以“虚”“空”说“心(知觉)”,甚至以“镜”喻“心(知觉)”而曰“如鉴之空”;(2)“心具某某”甚至“心包某某”;(3)“心中(里)”。这些说法从字面上看起来似乎将“存储”这一功能及其连带的“知觉成果”归给了“心(知觉)”,但笔者仔细考察这三种表达的实义后发现实际情况应该并非如此,谨依次辨析如下。
(1.1)朱子所言的“虚”是指“心(知觉)”作为“知觉之能”相对于一般事物乃至其他能力而言趋近无迹的本质特点,而不是“内部存储空间”尚未被填充意义上的初始特点,朱子说:
人心本是湛然虚明,事物之来,随感而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
事过便当依前恁地虚,方得。②
人须通达万变,心常湛然在这里。③
第二句中“湛然”即“虚”。如果朱子所言的“虚”是“内部存储空间”尚未被填充意义上的初始特点的话,那么他“事过”“通达万变”之后仍然“虚”的期待,便似乎是在期待一个人完全失去记忆能力一样。朱子显然不会发出这样的期待。只有当朱子所言的“虚”是作为知觉能力而趋近无迹的本质特点的时候,这两段所表达的期待才能获得合理的理解:期待此心不失其趋近无形无迹的特点,也即不失其作为“知觉之能”的敏锐度、不被钝化。又朱子说:
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耳目之视听,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岂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视听之,则犹有形象也。若心之虚灵,何尝有物!①
心者,气之精爽。②
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③
这里的“本体”是“本来样子”也即“本质特点”的意思④;“非我所能虚”,即不以人的经历为转移;“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应当是插入语,所以第三段后半段的意思当为“耳目之视听岂有形象?然犹有形象,若心之虚灵,何尝有耳目这样的形象呢?”只有作为知觉能力而趋近无迹意义上的“虚”,才可以和“灵”并称、互代(朱子首尾说“虚灵”,中间只说“虚”,即是以“虚”代“虚灵”),⑤才是本质特点而不以人的经历为转移,也才真正说得上“何尝有耳目这样的形象”“气之精爽”“比性则微有迹”。内部存储空间尚未被填充意义上的“虚”,不能和“灵”并称、互代,只是初始特点而必定被人的经历所填充,很难说得上“何尝有耳目这样的形象”尤其是“气之精爽”“比性则微有迹”。(1.2)“空”是“虚”的另一种说法,朱子一方面说“此心虚明,万理具足”⑥,另一方面又说“心虽空而万理咸备”⑦,即显示出这一点,所以所谓“空”也不是内部存储空间尚未被填充意义上的初始特点,而是作为知觉能力趋近无迹的本质特点。(1.3)“如鉴之空”的比喻不能执之太实,因为一方面朱子明确说过“譬喻无十分亲切底”⑧,另一方面“鉴”毕竟说不上“何尝有物”或者说“趋近无迹”。总而言之,朱子以“虚”“空”说“心(知觉)”,甚至以“镜”喻“心(知觉)”而曰“如鉴之空”,看似蕴含着“心(知觉)”涵盖“知觉成果”的意思,但实际上恰恰相反。
(2.1)“心具某某”中的“具”字不是“存储”或者“装载”的意思,因为“某某”无论在《集注》《文集》还是《语类》中,都几乎固定地是“(众/万)理”或者“此性”①,而朱子反复说“此理无形无影”②“理之体该万事万物,又初无形迹之可见”③“(心、意犹有痕迹)如性,则全无兆朕,只是许多道理在这里”④“论性,要须先识得性是个甚么样物事。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道理”⑤,这些话都表明,在朱子,“(众/万)理”或者说“此性”是完全无迹的,⑥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知觉成果”,没有被“存储”被“装载”的可能。因此,“心具某某”这样的表达并不是“心存储、装载着某某”的意思,并不是将存储功能又划给了“心(知觉)”(其实义待后文详论)o(2.2)“心包某某”(包含该载、包蓄)则是“心具某某”的口语化、形象化表达,因为被“包”的“对象”也不出“万理”“性”二说,且这种表达于《集注》《文集》《语类》三种书中,仅见于《语类》,⑦不可执之太过。总而言之,“心具(包)某某”的说法也是看似蕴含着“心(知觉)”涵盖“知觉成果”的意思,但实际上恰恰相反。
(3)在检索《集注》所得全部一处(在所引程子之言中)、检索《文集》所得全部六处、检索《语类》所得一百七十七处“心中(里)”的表达中,①只有《语类》中有一处支持“存储”之属“心(知觉)”,②其他各处则都不支持甚至明显反对这一点(其中“心中/里”可以理解为“心作为中/里”),③所以“心中(里)”的表达至少并不必然出乎“心(知觉)等于知觉之能”、不包含知觉成果这一结论之外。
综上所述,朱子这里“心等于知觉”同时意味着“心等于知觉之能”。后来阳明曾说“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④也指出了“心”之为“能”。这进一步说明,朱子所言的“心”的所指,是清楚、明白而稳定的,不是含混、模糊而游移的,因此“朱子心论”是有明确的基石的,而不是左支右绌的。而朱子以“心”为“知觉之能”,与其说比日常用法“窄”,不如说比日常用法精确,这种精确化的意义,是不可限量的。
三 心(知觉之能)等于“知(认识形下)—觉(领悟形上)”之能
在朱子,所谓“知觉之能”,究竟是怎样的能力?或者说“知觉之能”这四个字表明了“心”是一种怎样的能力?这是确定了“心等于知觉等于知觉之能”之后,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论者多以“知觉(之能)”为“认识”能力,但从笔者所见朱子文献来看,“认识”能力可能只说中了“知觉(之能)”中的“知”字,而遗漏了“知觉(之能)”中的“觉”字,后者足以表达一种比“认识”更深的“领悟”能力。换句话说,从笔者所见朱子文献来看,“知觉(之能)”是一种始于“认识”达于“领悟”的双重能力,而不只是“认识”这样一种单层能力。由此则可以说“知觉之能”四字表明了心是一种“通过认识去领悟”的能力,或者简言之,一种“知—觉”之能。此中“知”字表述浅层的“认识”能力、“觉”字表述深层的“领悟”能力这一点的依据,谨详述如下。
朱子曾明确表示,“知”字可以表述此心认取事物的经验因素(即形下因素)或者说直面对象的浅层能力,这种能力又可以称为“识”;“觉”字可以表述此心洞见事物的生生之理(即形上根据)或者说醒豁自身的深层能力,这种能力又可以称为“悟”。程子因与人论“觉”而提起孟子“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说,且论之曰“‘知’是知此事,‘觉’是觉此理”,朱子承之而曰:
“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觉”者,因理而觉。“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觉”,则是自心中有所觉悟。①
“先觉”“后觉”之“觉”,是自悟之觉。②
又正式注解《孟子》“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大学》“致知”的时候说:
“知”,谓识其事之所当然;“觉”,谓悟其理之所以然。③
“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④
这四条论述中,第一条第一句明确以“知”为一种认取事物的经验因素的能力、以“觉”为一种洞见事物的生生之理的能力;第一条第二句及第二条则又以两个“自”字明白指示出“觉”是醒豁自身的能力,同时反衬出“知”是一种直面对象的能力(“事物”与“自”相对则为对象)。盖经验因素都是在此心之外作为对象的,而生生之理则不但在事物自身,而且在此心自身,所以认取事物形色因素和直面对象、洞见事物生生之理和醒豁自身其实都是一回事,蒙培元论朱子之“觉”说:“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逆向的自我知觉,并不是横向的认知关系”,也已指出“觉”之为醒豁自身的能力这一点;①第三条、第四条则不但含有前两条的意思,而且指明了“知”能和“识”能、“觉”能和“悟”能的等同。张立文教授说:“‘知’是与事物接触,而获得对此一事的了解;‘觉’是在‘知’基础上,心中有所觉悟,即对此一事不仅有所了解,而且有一定的见解,形成了关于此一事物的整个形象,这就是‘知觉’。”延在钦说:“朱熹认为,所谓‘知’是指通过与事物接触而知晓该事物的所当然。而且,所谓‘觉’是指通过一种觉悟而领会其所以然……这样看来,‘觉’是比‘知’更深刻而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也都意识到了朱子这里“知”“觉”二字的区别,但所言还不够精确。
以上所引虽然主要都是朱子对经典特定语句的论述,不是他对作为心的“知觉之能”的直接分析,但以朱子对经典的熟稔和用字之不苟,将他对于“知”“觉”“心”的训释和论述结合起来看,应该至少是一条可行之路,加上朱子心论中处处显示出“心(知觉之能)”确实不止于“认识”而有一种“领悟”道理的能力,所以这条可行之路应该就是真正的道路所在。这即是说,虽然朱子没有明确说过,但如果我们将朱子所言的心理解为一种“通过认识形下去领悟形上”的能力,或者简而言之,一种“知—觉”之能,应该是无悖于朱子本意的。
又,心之为“知—觉”之能,尤其是其中的“觉”能,其实还蕴含着“实践”能力在其中,因为在朱子,道理是“当然而不容已”的,所以“觉于理”之心一定不会停留于“知(认识)”之静观,而必进于循理之实践,去实现道理或者说完成道理的自我实现。心的实践一定是通过驱动身体(包括魄也包括耳目口鼻在内)、支配事物来完成的,所以“觉”能所蕴含着的实践能力也被朱子称为“主宰”能力,或者说在朱子,“觉”能蕴含着“主宰”能力在自身。延在钦认为“依朱熹之看法,因为人类有知觉功能,所以能主宰一身和万事万物”①,也暗含着这个意思。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前文所提到的对于心的定义中,朱子为什么以“主于身而应事物”申说“知觉”二字,也才能理解下面这段对话:
问:“知如何宰物?”曰:“无所知觉,则不足以宰制万物。要宰制他,也须是知觉。”②
这番对话如果不是没有意义的话,弟子漏掉而朱子添加的“觉”字,便是奥秘所在:“觉”能蕴含着主宰能力在自身,所以添加“觉”字能够解答“知如何宰物”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朱子将心等同于“知觉”或者说“知—觉”之能的时候,并没有遗漏心的主宰乃至实践能力。众所周知,阳明后来说知行本体原是合一的,从朱子心论的视角看,则“知”“行”可以说是一心之中通贯的两种能力,故原本合一。
总而言之,通过考察朱子的“知觉”之说,我们发现,在朱子,心是一种蕴含着主宰、实践能力的“知(认识形下)—觉(领悟形上)”之能。可以说,朱子心论的地基不但是明白确定的,而且是丰富而非干瘪的。明确而丰富的地基,预言着一个稳固而庞大的体系。
第二节 从“知—觉”到思、情、意——心与思、情、意新探
一 心(“知—觉”之能)包含“思”能、“情”能、“意”能
上一节提到,在朱子,心或者说“知—觉”之能包括“思”“情”“意”在内,而“思”“情”“意”都是能力。所谓心(“知—觉”之能)包括“思”“情”“意”,是指“思”“情”“意”都是心(“知—觉”之能)在与包括“魄”中信息在内的具体他者接触时的升级版、运用态,具体来说:
此心(“知—觉”之能)最初与具体他者接触的时候,较浅的“知”能或者说认识能力会首先获得对象——即他者的经验因素,并升级为“思”以解析之。《语类》载朱子答弟子“知与思,于人身最紧要”之问时说“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与手相似,思是交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①,即是此意,后来阳明说“思是良知之发用”②,与朱子“思所以用夫知也”义同。随着“思”的深入,较深的“觉”能也会获得对象——即他者或者说此心的生生道理,所谓“思则得之”是也,③并升级为“情”以呈现之,呈现出来,便是此心对于他者表达基本态度(这种呈现是直达于眼神、面色的,所以是可见的,但未必所有人都有眼力见到)。朱子曾说:
性具于心,发而中节,则是性自心中发出来也,是之谓情。④
“情”是“性自心中发出来”,等于说“情”是此心“因理而觉”所生,即显示出“情”是“觉”能在获得对象时的升级版这一点(朱子这句话中所含的仅仅以“中节”者为“情”、不以“不中节”者为“情”的意思,待后文心与善恶处详辨)。需要说明的是,在朱子,心性二者“说着一个,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⑤,所以“性自心中发出来也,是之谓情”这一点,即“情是心灵因性理而觉所生”这一点,又常被朱子简化表述为“性之已发者,情也”⑥“情是性之发”⑦“(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⑧。也就是说,类似“情是性之发”这样的表达里面虽然没有出现“心”字,但实际上都隐含着“心”字在其中。如当朱子说“情根乎性”⑨“情本乎性,故与性为对”“性是根,情是那芽子”①,又以《乐记》“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之说中“性之欲”三字为“即所谓情也”②且又说“及其感物而动,则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则无自而发,故曰‘性之欲’”③的时候,其中“性”字背后都隐含着“心”字,所谓“说着一个,一个随到”是也,这是解读朱子言论时所需特别注意者。④话说回来,上所言“思”,无论面对怎样的他者,也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他者,其面貌永远都是解析,不会有任何异样,但“情”则因为是“性理”的呈现而一物一时一地各有其“理”,所以会随着他者的不同,甚至时地的不同而更有不同的具体面貌,所以《中庸》有“喜怒哀乐”之说,孟子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说,《礼运》有七情之说,而朱子也说“情却多般”。⑤
随着“觉”能升级为“情”,“觉”能中所蕴含的“实践作用”也会浮出水面而首先呈现为“意”,以围绕基本态度为他者谋划,然后“主宰”身体及事物,将谋划的蓝图付诸实施,他者因此得到一定的处置。《语类》载:
李梦先问情、意之别。曰:“情是会做底,意是去百般计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后用。”(夔孙录云:“因是有情而后用其意。”)⑥
问:“意是心之运用处,是发处?”曰:“运用是发了。”问:“情亦是发处,何以别?”曰:“情是性之发,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如爱那物是情,所以去爱那物是意。情如舟车,意如人去使那舟车一般。”①
情又是意底骨子。②
凡营为、谋度、往来,皆意也。③
这些言论,一方面指明了“意”之为“情”的后继、围绕“情”施展这一点;另一方面指明了“意”之为实践性的谋划之能的实质;延在钦说“这就是说,在发生某种情感后,意是要用尽一些方法而做该事情”④,也指出了这一点;柳阳辉说“‘意’是更具备主动性的心理活动”⑤、张立文教授曾说“(在朱子)‘意’是一种意见和主张,它是在‘知觉’积累了有关某一事的丰富感性材料基础上,通过‘心思’,认识了某一事物的本质,而形成了设想和方案”,所言皆近是。有学者认为朱子所言的“意”指意识或观念,接近于现代心字的内涵,恐于朱子营为、谋度、主张之说不合。现代所谓“意识”“观念”“心”其实只能对应上朱子所言的“知”“思”,而在朱子这里,“意”和“思”相近而实不同。相近处在于,二者都是心灵的高度运转状态,且“意”和“思”一样,也是无论面对怎样的他者,也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他者,其面貌永远都是谋划,不会有任何异样;不同之处在于,“思”是一种静观的、分析的、辨别的能力,静观准确、分析清楚、辨别明白,“思”便完成其职分,“意”是一种支配的、综合的、谋划的能力,支配妥当、综合完整、谋划周密,“意”才完成其职分。当然,二者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意”以“思”为基础,朱子认同程子所说“三(思)则私意起而反惑矣”⑥,又自言“如好恶是‘情’,‘好好色,恶恶臭’,便是‘意’”(观察、分辨“好色”“恶臭”,便是“思”),⑦即体现出这一点。
基于“意”给予他者的处置,如果双方都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则他者满足而退,不再需要“意”,“意”也“功成身退”,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如果有另外的具体他者接踵而来,此心自然又会有一番“思”“情”“意”的“运用”,但如果没有另外的具体他者接踵来至,另一番“思”“情”“意”的“运用”自然无从而起,此心不得不回复到纯然“知—觉”之能的面貌中去(这种状态不易理解,但在朱子这里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在后面中和新说部分会有详细论述)。后来阳明说“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①,所言诚是,从朱子心论的视角来看,“思”“情”“意”都不可能“悬空”,都是事物触发因而关联于事物的。
“思”“情”“意”既然是心(“知—觉”之能)在与他者接触时的升级态、运用态,则三者在朱子之为纯然能力而不含任何意义上的信息可知,因为能力的升级态、运用态,一定仍然是能力,不可能质变或掺入其他东西。其中“思”之为能力,毋庸赘言,“情”“意”之为能力,还有以下证据:
心,便是官人;气质,便是官人所习尚,或宽或猛;情,便是当厅处断事,如县尉捉得贼。②
情犹施设,心则其人也。③
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也。④
欲为这事,是意;能为这事,是情。⑤
情是会做底,意是去百般计较做底。⑥
此中第二条中的“施”“设”都是动词。一、二、四、五条皆以动词说“情”“意”,三、四两条复以“能”说“情”,则“情”“意”在朱子为纯粹能力可知。柳阳辉说“‘情’和‘意’都是心理活动”,也以“情”“意”为能力。⑦如前所言,“思”能、“情”能、“意”能的运用会在“魄”中留下信息或者说痕迹,这些信息或者说痕迹中有很多是直接关于“思”能、“情”能、“意”能的样貌的,却并非“思”能、“情”能、“意”能本身,日常以关于“思”能、“情”能、“意”能的信息甚至“思”能、“情”能、“意”能的运用所留下的一切痕迹为“思”能、“情”能、“意”能本身,从朱子的角度看,恐怕是一种张冠李戴。
又,“知”浅“觉”深,而“思”是“知”的升级态,“情”是“觉”的升级态,则“思”自然是“情”的先导,“情”自然是“思”的后继,二者是先后串行关系,而非同时并行的关系,朱子描述心之应事接物时说“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①,也表明了这一点。由此则在朱子,“思”和“情”是不可能冲突的,而日常所谓“思”和“情”或者说理智和情感的冲突,实际上是一路“思”—“情”和另一路“思”—“情”的冲突,只不过前者中作为后继的“情”可能很微弱,后者中作为先导的“思”可能很迅捷,以至于人们不易察觉而已(这种迅捷之思也曾被《中庸》表述为“诚者不思而得”,但至少在朱子看来,所谓“不思而得”本质上仍然是“才思即得”,其中“不思”只是说没有平常人那种“百思不得其解”的迟钝之“思”而已,朱子回答弟子“圣人有思无思”之问说“圣人……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即是此意)。如孟子“孺子将入于井”一章中,“乍见”即有恻隐之心,好像只有“情”没有“思”,但实际上恻隐之心建基于对孺子所处情境迅速而清晰的认知和判断;那些想要“邀誉于乡党朋友”的人,好像只有“思”没有“情”,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对孺子无“情”,对“邀誉”则有执着的喜好,难免有对于能够邀誉的窃喜;还有的人在救与不救之间纠结,“救”的理路可能是“判断孺子将入井—恻隐之心”,也可能是“判断孺子将入井和想到可以邀誉—邀誉之窃喜”或其他,“不救”的理路可能是“救了也不能邀誉——讨厌浪费时间”,也可能是“想到讹诈事件——恐惧”或其他,但都不可能在“思”—“情”这一线路上缺少任何一环;而这种纠结,以及出于邀誉的救或者不救、出于对于讹诈事件的恐惧的不救,显然都是“思”之太多所致,这些坏的结果虽然都表现在“情”上,但无法在任何意义上归罪于“情”,所以对治的方法也不会是加强理智对于情感的控制,而是“思”的自我净化,包括朱子在内的理学家经常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思”上,根源即在于此。另外,关于“知—觉”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其所发出的“思”—“情”会分为两路形成纠结,我们在后文“道心人心”部分会进行讨论。
总而言之,在朱子,心(“知—觉”之能)包含“思”能、“情”能、“意”能这一系列能力在自身,或者说,心之为“知—觉”之能,其实是可以运用为“思”能、“情”能、“意”能的“知—觉”之能。朱子心论地基的丰富性,可以说已经毋庸置疑了。需要说明的是,论者或认为,朱子用以表述心之官能的,还有“志”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在朱子,“志”并非一种独立的官能,而只是一种特殊的“情”,一种由高明广大的事物所触发的强烈而恒久的情感,其言曰:“‘志’与‘意’都属情,情字较大”(这里朱子一反其区分情、意的通常做法,将意也纳入情的范畴中,实际上只是以情指代思、情、意这一系列能力,并非真的取消了意的独立性。后面“心统性情”部分我们还会涉及这一点),①“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②即是此意。
二 基于“知—觉”“思”“情”“意”的体用分析
不难看出,在朱子,“心”在作为自己单独存在的时候,其面貌是“知—觉”之能,在发挥自己的才能的时候,其面貌是“思”能、“情”能、“意”能,在这个意义上朱子以“知—觉”之能为“心本身”,以“思”能、“情”能、“意”能为“心之运用”。朱子说:
然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及其动也,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艮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①
其静时,思虑未萌,知觉不昧,乃复所谓“见天地之心”,静中之动也。其动时,发皆中节,止于其则,乃艮之“不获其身,不见其人”,动中之静也。②
动静、中和问题待后文详论。据第一段后半段及第二段可知,第一段前半段中所谓“事物未至,思虑未萌”其实是“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一性浑然道义全具”是在申说“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并不是在“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之外有所添加,“体”即本身,所以所谓“事物未至,思虑未萌(知觉不昧),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其实就是在说“知—觉”之能是“心本身”。朱子曾说“意则有主向”③,所以“各有攸主”其实是在说“意”能,而所谓“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其实就是在说“思”能、“情”能、“意”能是“心之运用”。又朱子《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说:
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按:此处“性”字,王懋竑《年谱》作“情”)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④
此中“思虑未萌”无疑仍然是“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体”仍然是“本身”的意思,“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也是在申说“体”而不是有所增加,所以所谓“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实质上也是以“知—觉”之能为“心本身”。这里的“情”字代表“思”“情”“意”三能,所以所谓“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也是以“思”能、“情”能、“意”能为“心之运用”。又朱子说:
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说得?①
这里的“体用”也是“本身和运用”的意思。“未发之前”即未与他者接触而“运用”之时,此心的面貌只能是“知—觉”之能,而朱子谓之“心之体”,也是以“知—觉”之能为心本身。“已发之际”即与他者接触而“运用”之时,此心的面貌会是“思”能、“情”能、“意”能,而朱子谓之“心之用”,也是以“思”能、“情”能、“意”能为心之运用。又朱子《大学章句》中说:
经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诚。”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②
这里的“意”代指“思”能、“情”能、“意”能,“知”代指“知—觉”之能,“心体”即心本身,“发”即运用。以“心体之明有所未尽”说“知”之未至,蕴含着以“知—觉”之能为心本身的意思。以“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说“意”之未诚,蕴含着以“思”能、“情”能、“意”为心之运用的意思。③后来阳明说“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①,也以“知觉”为本身,以“意”为运用,与朱子大体相同。
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是不会随他者的来去而存在或不存在的,作为心之运用的“思”能、“情”能、“意”能,则会随他者的来去而出现或消失,在这个意义上朱子说:
因此偶复记忆胡文定公所谓“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则虽一日之问百起百灭,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语。②
“不起不灭心之体”“一日之间百起百灭,而心固自若”即是说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不会随他者的来去而存在或不存在,“方起方灭心之用”则是说作为心之运用的“思”能、“情”能、“意”能则会随他者的来去而出现或消失,所以朱子认为“自是好语”。朱子紧接着又强调说:
但读者当知,所谓“不起不灭”者,非是块然不动、无所知觉也,又非百起百灭之中,别有一物不起不灭也。
此中“无所知觉”是“无知觉之能”的意思,不是“无知觉对象”的意思。一直存在的心本身实际上就是“知—觉”之能,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以说“所谓‘不起不灭’者,非是块然不动、无所知觉也”。他者来至而“思”能、“情”能、“意”能出现,则“知—觉”之能已然升级,不再存在“思”能、“情”能、“意”能之外的“知—觉”之能,他者离去而“思”能、“情”能、“意”能消失,则“知—觉”之能则回复到“知—觉”之能的面貌,所以说“非百起百灭之中,别有一物不起不灭也”;后来阳明说“然谓‘良知常若居于优闲无事之地’,语尚有病。
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①,又说:“未发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②,也是此意。作为运用面貌的“思”能、“情”能、“意”能意味着心与他者的接触,可以说是一种“动”的面貌,相对而言,作为本来面貌而意味着心的独自存在的“知—觉”之能,虽然“非是块然不动”,但终究显示出一种“静”态出来,所以朱子紧接着又说:
但此心莹然,全无私意,是则寂然不动之本体,其顺理而起、顺理而灭,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尔。
“寂然不动”即“静”,“本体”即“本来体段”,也即“本身”或者说“体”,③“感”即“动”。“寂然不动之本体”即以“静”形容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即以“(感)动”形容作为心之运用的“思”能、“情”能、“意”能。在前文所引《答张钦夫》第四十九一段中,朱子在“事物未至”和“事至物来”前面分别冠以“方其静也”“及其动也”字样,也以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为“静”,以作为心之运用的“思”能、“情”能、“意”能为“动”。又朱子曾说: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能觉者,而无所知所觉之事,此于《易》卦为纯坤不为无阳之象”④“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觉而无运用,冬之象也”①、“心如水,情是动处”②,也以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为“静”,以作为心之运用之一的“情”能为“动”。后来阳明说“心之本体原自不动”③,与朱子意同,而他回答弟子“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的问题时说“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用言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④不可谓不精彩,但若说其中“先儒”包括朱子,则未免诬枉,朱子之意也是“静可以见其体(而用在其中),动可以见其用(而体在其中)”,而不是“以动静为体用”。事实上,“动静”二词是形容词而非名词,是虚词而非实词,“体用”则是名词、实词,很少会有思想家犯“以形容词、虚词为体用”的错误,弟子的问题应该只是出于他自己的误解,基本不会有思想家能够真的能够对号入座。
我们上文已经提到,在朱子,“心具此性(众理)”,而“心具此性(众理)”的首要意义,便是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具此性”,在这个意义上,如上面所引《答张钦夫》第四十九及《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所示,朱子主要在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这里说“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天命之性,当体具焉”。又朱子说:
然则仁义礼智信云者,乃所谓未发之蕴、而性之真也欤?⑤
未发之前,万理备具……所以合做此事,实具此理,乃未发也。⑥
“未发”则此心作为其本身也即“知—觉”之能存在,所以这两句也都是在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上说“具此性(众理)”。⑦进一步,我们上文也曾提到,朱子反对“性中(外)别有一个心”“性外别有一个知觉”,而认为“心性只是一个物事,离不得”“理不离知觉,知觉不离理”,甚至“此两个说着一个,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所以朱子经常将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藏在“性”字之中,其言曰:
情之未发者,性也。①
喜怒哀乐未发,无所偏倚,此之谓“中”。“中”,性也;“寂然不动”,言其体则然也。②
其未发,则性也。③
未发是性。④
大概在身则有个心,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⑤
“未发”“心之体”在上文被表述为“知觉不昧”而“一性浑然”,在这些表述中却直接表述为“性”,唯一的合理解释只能是,朱子将作为心本身的“知一觉”之能藏在了“性”字之中,这和他“说着一个一个随到”的说法也是一致的。事实上,朱子是有明确的“藏‘知一觉’之能于性”乃至“藏心于性”的意识的,他论《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之说曰“所谓‘静’者,亦指未感时而言耳。当此之时,心之所存,浑是天理,未有人欲之伪,故曰‘天之性’”⑥,“所引‘人生而静’,不知如何看‘静’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耳。盖当此之时,此心浑然,天理全具”⑦,引入“心”来解释“天之性”之说,即体现出这一点。他又曾回答弟子孔子不说心之问说“孔门虽不曾说心,然答弟子问仁处,非理会心而何。仁即心也,但当时不说个‘心’字耳”⑧,也体现出明显的“藏心于性”的意识。论者多认为朱子特别强调心、性之别,因而对于以上说法难以有确切的理解,但实际上,朱子所言“心、性之别”只是和其他学者对比才显得“特别”,在其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则与“心性之一”平起平坐甚至以“心性之一”为前提,可谓无甚“特别”,所以除了朱子明言心性之别的地方,其他所有论述中的“心”字都蕴含着“性”字在其中,“性”字也都蕴含着“心”字在其中,这也是解读朱子学说所需特别注意的地方。后来刘宗周说“朱子以未发言性,仍是逃空堕幻之见。性者生而有之之理,无处无之”①,一方面是没有看出“性”字之后隐藏的“知—觉”之能,另一方面是不知“未发为性”只是“未发可以见其体”的意思,不是将未发和性完全等同。
“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被藏在“性”字之中,则“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的属“静”常常会被表述为“性”属“静”,“思”能、“情”能、“意”能作为“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的发用,也常常会被表达为“性”的发用,朱子说“人受天地之中,只有个心性安然不动……性静而情动”②“性静,情动”③“性是静,情是动”④,都是以“性”之属“静”表述“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的属“静”,又朱子说“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⑤,则是以“性之用”表述“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的发用,不难看出,上文所引用到的“情是性之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需要说明的是,朱子不但有“心之(本)体”的说法,而且继承了孟子“本心”的说法。由于这两个概念字面相似,且朱子既说过“心之本体本无不善”⑥,又说过“本心元无不善”⑦,所以论者多将二者等同起来,延在钦说:“从朱熹所提的‘未尝不善’‘本无不善’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谓‘心之本体’是相当于孟子所提出的不忍人之心、四端之心、良心、本心等概念”⑧,即是如此,牟宗三亦然。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很不相同的。从字面上讲,二者的结构完全相反:“心之本体”中“心”是定语形容词,“本(体)”是名词;而“本心”中则“本”是定语形容词,“心”是名词。从所指上讲:“心之本体”和“心之发用”相对,是指心本身,属于对“心”的分析;“本心”则和“非本心”或者说“被奴役之心”相对,而有其本身,属于对“心”的评判。朱子说:
夫人心是活物,当动而动,当静而静,动静不失其时,则其道光明,是乃本心全体大用。①
不错底是本心,错底是失其本心。②
第一条即指明“本心”有“体”有“用”,第二条则显示出“本心”属于对心的评判。朱子《论语集注》曾引胡氏之言说“其日用之间,本心莹然,随所意欲,莫非至理。盖心即体,欲即用”云云,③注解《孟子》“本心”之说的时候说“本心,谓羞恶之心”④,又论之曰:“盖本心之发,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为而为之也。”⑤这三处合而观之,也可知在朱子,“本心”有“体”有“用”。事实上,发用意义上的“本心”,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日常所言“本意”,朱子说“盖得时行道者,圣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圣人之不得已”⑥“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为季氏附益,夫岂其本心哉”⑦“而今若教公读易,只看古注,并近世数家注,又非某之本心”⑧“建贼范汝为本无技能,为盗亦非其本心”⑨,这些话里的“本心”都可以换成“本意”而不失其义,盖“意”属于“心”,笼统而言则曰“本心”,精确而言则曰“本意”。“本意”当然不可能在“心之本体”的概念之内。陈来教授《朱子哲学研究》第十章“心说之辨”极具启发意义,但其中有一个基本误解,即将“本心”等同于“心之本体”来看,导致这一论辩的实义没有得到完全的揭示,我们后文讨论朱子敬论的时候会重新梳理“心说之辨”中的关键论述。
第三节 智愚与学习——心灵差异新探
一 气禀差异论本质上是心灵差异论
所谓“心是可以运用为思能、情能、意能的‘知—觉’之能”,当然是说所有人的心“自婴儿至于老死”都是可以运用为“思”能、“情”能、“意”能的“知—觉”之能。从“体”上讲,没有人在任何时候有比“知—觉”之能更多的能力,也没有人在任何时候缺少“知”“觉”二者中任何一重能力,也没有人在任何时候有不同于“知—觉”的其他结构,更没有人的“知—觉”之能不是无间于他者的来去而恒定存在的;从“用”上讲,没有人在任何时候有比“思”能、“情”能、“意”能更多的能力,也没有人在任何时候缺少“思”能、“情”能、“意”能中任何一种,也没有人在任何时候有不同于“思”“情”“意”的其他顺序,更没有人的“思”能、“情”能、“意”能不是随他者的来去而出现或消失的。朱子说“熹尝谓:有是形,则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则谓之性,仁义礼智是也;性之所感于物而动则谓之情,恻隐、羞恶、是非、辞让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圣凡为有无也”①“以某看来,须是别换过天地,方别换一样人情……天地无终穷,人情安得有异”②“有个人在此,决定是有那羞恶、恻隐、是非、辞让之情”③,即表明了上述意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朱子没有看到人类心灵之间在相同基础上显然存在的差异尤其是先天差异,朱子又说:“心本未尝不同,随人生得来便别了。”④即是说人类心灵之间在相同的基础上有差异,且这种差异是与生俱来的。但“心”的“随人生得来便别”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人类心灵之间的先天差异究竟是什么?朱子既没有在这里接着说明,似乎也没有在其他地方有所论述,以至于学界目前对朱子心论的研究都直接绕过了这一问题(延在钦认为“由于人所禀受的气质不同,在心的功能上有一定的差异”①,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并未深究)。但一方面,如果朱子心论在这个问题上薄弱,那么它对于人类心灵的解释力会变得很可疑;另一方面,朱子这里不含“心”“别”字样的言论,未必就一定不是在论述人类心灵差异。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地检查朱子著名的“气禀(气质)论”中在“人”的范围内的论述,便会发现,朱子的“人类气禀(气质)论”,是或者首要地是在论述人类心灵之间的先天差异,或者说是或者首要地是“随人生得来便别”的注脚,这一点在以下言论中最为明白地显示出来。
其一,朱子论“气质”曰:
人性虽同,禀气不能无偏重。有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而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而恻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水火亦然。唯阴阳合德,五性全备,然后中正而为圣人也。②
这一段是就先天而言。在人,所谓“禀气”无非身、心二者。如果所谓“木气”“金气”是指“身体”的话,那么所谓“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便会沦为身体决定论。这显然不可能是朱子本意。只有所谓“木气”“金气”首先乃至完全是指“心”,“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才能够得到合理的理解。如此则至少朱子这一段中的“禀气”指“心”无疑,而所谓“禀气”之“偏重”“木气重”“金气重”“中正”则都是在对比人类心灵之间的先天差异。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木气”“金气”既非身也非心,而是人身上的第三种存在,这样的理解并非朱子之意,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心之形而上下部分辨明。
其二,朱子回答弟子“气禀有清浊不同”之问说:
气禀之殊,其类不一,非但“清浊”二字而已。今人有聪明,事事晓者,其气清矣,而所为未必皆中于理,则是其气不醇也。有谨厚忠信者,其气醇矣,而所知未必皆达于理,则是其气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见。①
这一段也是在先天的意义上说的。其中“聪明事事晓”“谨厚忠信”也显然都是在说“心”,而所谓“气清”而“不醇”“气醇”而“不清”也显然都是在说人类心灵之间的先天差异。又朱子说:
气禀所拘,只通得一路,极多样:或厚于此而薄于彼,或通于彼而塞于此。有人能尽通天下利害而不识义理,或工于百工技艺而不解读书。②
很难想象,“通天下利害而不识义理”和“工于百工技艺而不解读书”不首先是心灵方面的先天差异。
其三,朱子曰:
然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故上知生知之资,是气清明纯粹,而无一毫昏浊,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学而能,如尧舜是也。其次则亚于生知,必学而后知,必行而后至。又其次者,资禀既偏,又有所蔽,须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后方能及亚于生知者。及进而不已,则成功一也。③
这一段也是在先天的意义上说的,其中所谓“昏明清浊之异”可能有身体的因素在其中,但必定首先是指人类心灵之间的先天差异,惟其如此,后文才能一直说“知”云云。又朱子说:
性者万物之原,而气禀则有清浊,是以有圣愚之异。④
惟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天理浑然,无所亏阙。①
这两句也都是在先天的意义上说的。很难想象,朱子所说的“圣愚之异”不是或者不首先是心灵方面的差异,而“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则几乎已经直接说出这一点了。
其四,朱子论人的“气质之性”说:
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以不净之器盛之,则臭;以污泥之器盛之,则浊。②
这一段也是在说先天差异,只要我们没有忘记朱子“心性之别,如以碗盛水”“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这样的表达,便能很容易地发现其中的“器”都是指“心”,而所谓“净器”“不净之器”“污泥之器”,则是在人类心灵之间对比出来的先天差异。
至此已经可以确定,朱子的“人类气禀(气质)论”,就是或者至少首先是一种“心灵先天差异论”,能将所谓“心本未尝不同,随人生得来便别”的实义初步解析出来。
二 从“智”“愚”到“学”
根据上面的引文,朱子所论人类心灵之间的先天差异可以表述为一种先天的“智”“愚”之异。③具体来说,在朱子,有的人的心灵生来便是相对更为“智”的,有的人的心灵则生来便比较“愚”。从“体”上讲,有的人的“知—觉”之能生来便相对更为“智”,其全面认识透彻领悟的机会相对更多,多之至,则无论后天与任何他者接触,都能够全面认识透彻领
悟,没有任何他者能够蒙蔽、诱惑进而奴役它;有的人的“知—觉”之能则生来便比较“愚”,其全面认识透彻领悟的机会则相对较少,少之至,则后天只有与极其简单的他者接触,才能够全面认识透彻领悟,稍微丰富或者复杂一点的他者都能够蒙蔽、诱惑进而奴役它。相应地,从“用”上讲,有的人的“思”能、“情”能、“意”能生来便相对更为“智”,其清楚分析饱满表态周密谋划的机会相对更多,多之至,则后天无论与任何他者接触,都能够清楚分析饱满表态周密谋划,没有任何他者能够使之“正墙面而立”;有的人的“思”能、“情”能、“意”能则生来便比较“愚”,其清楚分析饱满表态周密谋划的机会相对更少,少之至,则后天稍微丰富或者复杂一点的他者,便能够使之捉襟见肘。其中生来便极于“智”的心灵,便是上文所谓“上智生知之资”,生来便非常“愚”的心灵,便是和“上智”相对的“下愚”之资,生来便比较普通的心灵,则介于“上智生知之资”和“下愚”之资之间,而为参差不齐的普通资质。①只有生来便上智的心灵,才会终其一生都不会有丝毫地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朱子说:
如尧舜之时,真个是“宠绥四方”。只是世间不好底人,不定叠底事,才遇尧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谓之“克相上帝”,盖助上帝之不及也。②
在朱子,“尧舜”即是“上智生知之资”的代表,所以这段话即是在说生来便上智的心灵,会终其一生都不会有丝毫的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除此之外的其他心灵,在后天都存在着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的可能,只是越接近“上智生知之资”,这种可能性越小,且一旦发生,程度也越浅,越至于“下愚”之资,这种可能性越大,且一旦发生,程度也越深。
生来便上智的心灵之所以终其一生都不会有丝毫地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也是因为生来便上智的心灵在后天必然彻底地“好学”且极其善于学习。朱子说“质敏不学,乃大不敏。有圣人之资必好学,必下问。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学,更不问,便已是凡下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也只是好学下问。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于帝,无非取诸人以为善。孔子说:‘礼,吾闻诸老聃。’这也是学于老聃,方知得这一事”①,“如孔子所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此有甚紧要?圣人却忧者,何故?惟其忧之,所以为圣人。所谓‘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②,即是说生来便上智的心灵在后天一定会彻底好学,后来王夫之也说“质以忠信为美,德以好学为极”,③认为好学是最高的德性,和朱子正相印证;又朱子说“‘好古敏以求之’,圣人是生知而学者。然其所谓学,岂若常人之学也!‘闻一知十’,不足以尽之”,④则是说生来便上智的心灵在后天一定会极其善于学习。后天彻底“好学”且极其善于学习,既体现出其生来便已然上智的绝佳资质,又保证着它终其一生都不会丝毫丧失其上智的绝佳资质,⑤则其终其一生都不会有丝毫的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自然不在话下。
生来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虽然不会完全没有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但终究难免时或学而不得乃至时或辍学,朱子论孔子“发愤忘食”说:
“‘发愤忘食’,是发愤便能忘食;‘乐以忘忧’,是乐便能忘忧,更无些小系累,无所不用其极,从这头便点到那头,但见义理之无穷,不知身世之可忧,岁月之有变也。众人纵如何发愤,也有些无紧要心在;虽如何乐,终有些系累乎其中。”①此中“众人纵如何发愤,也有些无紧要心在”,即是说生来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难免时或辍学。②辍学或者学而无得的时候,生来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裹足不前,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的可能保持其存在。但学习且有得的时候,生来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得以改变自身的先天资质,向“上智”自我提升,理学认为“学”的本质是“变化气质”“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强”,即是此意,延在钦说“所谓‘变化气质’可以视为要通过学问而把心的功能提高到从‘暗’到‘明’的阶段”,也指出了这一点。③自我提升的过程中,不但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的可能性逐渐降低,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也不断增强,以至于自我提升的效率逐渐提高。到了自我提升的终点,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也达到极强,被蒙蔽、诱惑、奴役、难倒的可能性彻底消除,因为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完全改变了自身的先天资质,自我提升到了“上智”之资,所谓“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是也。④不难看出,先天越是接近于“上智生知之资”的心灵,起点越高、效率越高,因而后天自我提升为“上智”之资便越容易,先天越是至于“下愚”之资的心灵,起点越低、效率越低,因而后天自我提升为“上智”之资便越难。朱子在上面“以污泥之器盛之,则浊”后面接着说:“但既臭浊,猝难得便清。故‘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也煞用气力,然后能至。”又说:“人之为学,却是要变化气禀,然极难变化。”①认为先天越是至于“下愚”之资的心灵,后天自我提升为“上智”之资便越难。
话说回来,在朱子,即便是生为“下愚”之资的心灵,在后天也不会完全没有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孔子曾以“下愚”为“不移”,而朱子则认为孔子所谓“不移”是“不肯移”,而不是“不可移”,因此认为“下愚”终究是“可移”的),②所以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向“上智”之资自我提升是必然趋势。这即是说,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同时也是生来便带着向“上智”之资自我提升的倾向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与其称为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不如称为生来便向“上智”之资自我提升的心灵。或者说,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其自我认知可能是“生来较为普通”,其先天自我认同却不会是“生而较为普通”,而一定是“上智生知之资”。正是在先天自我认同的意义上,朱子说“圣人于天下,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③,又认为每一个人的心从本质上讲都是“完具”的④,这些话并不是说普通人有两颗心,只是说其有高于自身之所是的自我认同,上文“心本未尝不同”一言,应该也有这方面的意思。“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而“本未尝不同”,则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在后天向“上智之资”的自我提升,在确实是一种自我改变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回归乃至自我复原,或者说对于生而较为普通的心灵而言,“学”的根本性质,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回归乃至自我复原的工作。朱子说:
今之为学,须是求复其初,求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与我者,便须以圣贤为标准……人之为学,正如说恢复相似:
且如东南亦自有许多财赋,许多兵甲,尽自好了,如何必要恢复?只为祖宗元有之物,须当复得;若不复得,终是不了。今人为学,彼善于此,随分做个好人,亦自足矣,何须必要做圣贤?只为天之所以与我者,不可不复得;若不复得,终是不了,所以须要讲论。学以圣贤为准,故问学须要复性命之本然,求造圣贤之极,方是学问。①
更有一事,如今学者须是莫把做外面事看。人须要学,不学便欠阙了他底,学时便得个恰好。②
这些话即是说,对于“上智生知之资”之外的其他心灵而言,“天之所以与我者”虽然并非“上智”心灵,却是以“上智”心灵为自我认同的心灵,所以后天只要还没有自我提升至于“上智”之资,此心便不会满足、不会善罢甘休,只有自我提升至于“上智”之资,此心才会觉得做回了自己、觉得刚刚好。
由此可见,在朱子,从先天的角度来看,人类心灵有同有异:其同不仅在于具体的功能组成是相同的,而且在于无不以“上智”之资为自我认同,其异则在于其实际所是从已然“上智”到尚是“下愚”的千差万别。从后天的角度来看,人类心灵总体趋同,先天便上智的心灵会保持其“上智”之资,先天较为普通的心灵则无不向“上智”之资自我提升,但因为先天较为普通的心灵自我提升的难度有难有易、效率有高有低,所以在总体趋同的背景下,先天较为普通的心灵之间的差距反而有可能被拉大。又,无论是对于生来便上智的心灵的后天自我保持而言,还是对于生来较为普通的心灵的自我提升而言,又或者对于后天自我提升为“上智”之资的心灵其后的自我保持而言,“学”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①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强调“人之所贵者,惟学而已矣”,又论“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说:“如狂作圣,则有之。既是圣人,决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学。”(假设“圣”不“学”,则“作狂”,假设“狂”能“学”,则“作圣”,这里的因果联系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只有“狂”能“学”的假设可能兑现,“圣”不“学”的假设是不可能兑现的,所以说“如狂作圣,则有之。既是圣人,决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学”)
众所周知,朱子对陆象山的一个著名批评,在于“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②。既然气禀之异本质上是心灵方面先天的“智”“愚”之异,那么朱子这一批评的实义便是在说陆象山不顾人类心灵先天存在的从“上智”到“下愚”的差异。考诸陆象山自己的言论,如其言曰“圣人与我同类,此心此理谁能异之”③,“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④,“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⑤,不得不说,象山确实主要是在说“心本未尝不同”的意思,而较少言及“随人生得来便别”的意思。相形之下,不得不说,朱子对于人类心灵的刻画确实是更为全面、细致的。
小结
本章我们主要探讨了朱子心论的“官能”面向。通过三节的探讨,我们发现:在朱子,心的基本义,即是指人这里的“知—觉”之能,而“知—觉”之能能够运用为“思”能、“情”能、“意”能;人类心灵之间在官能构成和自我认同方面是相同的,但同时存在着从“上智”到“下愚”的千差万别,“学习”能够使这种差别不断得到调整,并指向“愚”的最终消除。朱子对于人类心灵基本面的刻画是明晰、确定、全面而细致的。
附注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213—214页。
②孙利认为,“朱熹哲学中,心的基本意义是指知觉”(《朱熹“心”论》,《江淮论坛》2002年第5期),杜保瑞教授论朱子心论说“人是一气化的存在,人有灵明知觉,以心总说之”(《对朱熹以气说心的当代诠释之反思》,《朱子学刊》2016年第1期),即是此意。陈来教授说:“在朱熹哲学中心的主要意义是指知觉”(《朱子哲学研究》,第213页),应该也是这个意思,但话语间又留下了余地。
①延在钦认为“朱熹认为心本来具有知觉功能”“知觉代表心所具有的认识功能和主宰功能”(《朱熹心论研究》,第116页),杨俊峰认为“朱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些观点,他经常用‘虚灵知觉’或‘虚明知觉’说明心的功能特点”(《心理之间——朱子心性论研究》,第105页),蒋昭阳认为“在朱子看来,心的最主要官能之一就是具有知觉的认识能力”(《辨析朱子心性论中的“心”》,《兰州学刊》2007年第11期),李妍静认为“朱熹所提出的‘心’的主要性质是‘知觉’……‘虚灵不昧’之心是心具有知觉的前提,也是发挥知觉能力的主要条件”(《朱熹修养功夫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5年,第35页),都是这个意思。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80页。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9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67页。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4340页。
①其他含有“心有知觉”之意的言论如《晦庵朱文公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故谓仁者心有知觉则可,谓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不可”(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13页)、《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若指有知觉者为性,只是说得‘心’字”(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192页)、“若曰‘心有知觉之谓仁’,却不得”(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706页)、“告子只说那生来底便是性,手足运行,耳目视听,与夫心有知觉之类”(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1875页)、“横渠之言大率有未莹处。有心则自有知觉,又何合性与知觉之有”(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1944页),这些言论中都没有进一步说“心还有某某”。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762页。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19页。
④原文如下:“今先说一个心,便教人识得个情性底总脑,教人知得个道理存着处。若先说性,却似性中别有一个心。横渠‘心统性情’语极好,又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则恐不能无病,便似性外别有一个知觉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7页)⑤原文如下:“聪明视听,作为运用,皆是有这知觉,方运用得这道理,所以横渠说:“人能弘道”,是心能尽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检心。’”(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1942页)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2590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1942页。
③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
①陈来教授说:“在朱熹哲学中,‘所’常常不是指认识所反应的客观对象,而是指认识的结果,认识的内容。因此,知觉不仅指能知觉,而且指所知觉,这个所知觉是指有内容的具体知觉(观念、思想)。”(《朱子哲学研究》,第214页)其中“认识的结果”“认识的内容”即“知觉成果”。孙利沿用了陈来教授的观点说:“这里的知觉一方面是指人的知觉能力即能觉,一方面是指所思虑的具体内容即所觉。”(《朱熹“心”论》,《江淮论坛》2002年第5期)杨俊峰似乎也沿用了这一观点,其言曰:“道心与人心同为心之知觉,但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心理之间——朱子心性论研究》,第114页)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163页。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90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980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981页。
②张子说“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谓之‘心’,可乎”(《正蒙·大心篇》),也反对将“存象”者称为“心”。在上所引“凡能记忆”一段中朱子曾说“能知觉底是魄,然知觉发出来底又是魂”,这句话表面上将“知觉(心)”归给了“魄”,但实际上只是说“魄”是“知觉”(心)的载体,并不是说“知觉(心)”属“魄”。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158页。
①“魄”中最初的信息一定是来自身体之外的,对这些信息进行再勘察所得的信息,从源头上讲,也可以说都是来自身体之外的,所以阳明后来曾说:“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76页)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538页。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641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1页。
②同上书,第219页。
③同上书,第221页。
④乔清举教授亦认为这里的“本体”“是指心的本来的体段、作用、功能,不是性或者理那样的道德本体。”(乔清举:《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哲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⑤这样的互代不只这一处,如朱子又说:“此心至灵,细入毫芒纤芥之间,便知便觉,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便到那里;下面方来又不知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便也到那里。这个神明不测,至虚至灵,是甚次第!”(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613页)此比段以“至灵”开头,以“至灵”结尾,也说明“虚”可以代“虚灵”。
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620页。
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91页。
⑧原文:“或问‘成之者性’。曰:‘性如宝珠,气质如水。水有清有污,故珠或全见,或半见,或不见。’又问:‘先生尝说性是理,本无是物。若譬之宝珠,则却有是物。’曰:‘譬喻无十分亲切底。”(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525页)①只有一处多出了个“情”字:“心具此性情。”(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8页)其义后文会专门讲到。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494页。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224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1页。
⑤同上书。相同的言论还有:“性无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这理耳。”(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47页)⑥朱子说“理无形,故就气上看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882页),也是同样的意思。又朱子曾说:“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116页)其中“净洁空阔底世界”常常被误认为是在说类似真空一样的空间,但实际上综合朱子对于“理”的论述,不难发现,这里只是强调“无形迹”的意思而已,并没有将“理”说为“真空世界”的意思。
⑦“具是理”“包万理”这样的意思经常跟在“虚”字、“空”字之后,又从侧面确认了上所言“虚”“空”的实义一定是趋近无迹。
①《文集》中“心中”四见,“心里”两见。
②“去了本子,(本子上的内容)都在心中。”(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324页)。
③例子太多,不胜枚举,仅举几例作为代表:如“自家心中具许多道理在这里”(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435页)、“自家心里许多道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818页)是在表达“心具众理”的意思;“居敬则心中无物”(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4页)、“心中若无一事时,便是敬”(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84页)其实是在表达上文趋近无迹之“虚”的意思;“心中欲为善”(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518页)、“他心里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03页)中的“中”“里”字都可以省略。
④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36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1859页。
②同上。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10页。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根据“知,犹识也”四字来看,“知”“识”在朱子这里是两个词,不是一个词,所以后面“吾之知识”应当标点为“吾之知、识”。
①蒙培元:《中国心性论》,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364页。众所周知,阳明批评朱子格物说,认为朱子“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但事实上,朱子是“于事事物物上求启发”的“通内外”之说,而不是“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的“义外”说。
①延在钦:《朱熹心论研究》,第124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584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4页。此言也为另一弟子所录,主要内容相同:“又问:‘知与思,于身最切紧。’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584页)②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72页。
③明清之际儒者陆桴亭说“悟处皆出于思,不思无由得悟”、“悟者思而得通也”(《思辨录辑要》卷3格致类第54条,同治正谊堂本),也指示出“思”—“(觉)悟”这一路径。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37页。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2页。
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74页。
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1页。
⑧同上书,第224页。
⑨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95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51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63页。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99页。
④当然,在“说着一个一个随到”的前提下,究竟是“说着”心还是“说着”性,也是有区别的。延在钦说:“总之,关于情的来源问题,在朱熹那里,虽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它与其说理论上的矛盾和冲突,不如说由所要强调的重点不同而产生的结果。朱熹通过‘情者,心之动’的说法强调作为感应的主体的心的主宰功能。与此不同,朱熹所主张的‘情者,性之动’的见解可以说他要确立如同四端的道德情感所以为‘善’的根据。而且,他通过‘性之动’‘性之发’的说法而主张人类本性应当体现于所有意识活动上。”(《朱熹心论研究》,第150页)所言大体没有问题。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430页。
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1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1页。
②同上书,第232页。
③同上书,第232页。
④延在钦:《朱熹心论研究》,第188页。
⑤柳阳辉:《儒学大师朱熹的心理学思想述略》,《兰台世界》2014年第9期。
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1页。
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2页。
①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91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192页。
③同上书,第215页。
④同上书,第191页。
⑤同上书,第542页。
⑥同上书,第231页。
⑦柳阳辉:《儒学大师朱熹的心理学思想述略》,《兰台世界》2014年第9期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19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2页。
②同上。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19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49页。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2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30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5页。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页。
③任荟婵说:“心的体就是事物未能被人感知时,人的思虑没有萌动,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没有感知的能力,只是没有去感知而已,这种‘静’的状态就叫作‘中’。心的用是事物与人接触而被人感知,人的思虑萌动,各种器官交互作用,各司其职,这种动的状态就是‘和’。这就是说,在事物与人接触之前,人的思绪是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下的,但这种静止并不意味着人没有感知事物的能力,是绝对静止的;而只有事物与人接触时,人的思虑才会萌动,同时感觉器官也会积极地运作,而人的感官运作和不运作,人的心并没有变动过,只是前者表现得被动一些,后者表现得主动活跃一些。也就是说心的体用是一体的,它只是周流贯彻,表象不同而已。总之,作为‘心”的体和用,其实就是心未发和己发时的状况,因为,无论是心与外物接触,感官积极活动时的已发情况,还是心处于未发时的静止状态,它都只是那唯一的心在应物或是未应物时的两种情况,所以心的体用是合一的。”(《论朱熹心的思想》,《安徽文学(下半月)》2014年第10期)也蕴含这一点。
①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47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21页。
①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65页。
②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64页。
③“心之本体”中的“本体”就是“本体”二字的字面意思,并不是“ontology”的意思。延在钦说“至于朱熹所谓‘心之本体’,在这里‘本体’不是指作为万物的生成、存在、变化的根本原因的本体,而是指事物的原来的样子或本然状态”(《朱子心论研究》,第110页),也是这个意思。张岱年先生说“朱熹所说的‘心之本体’是指心的本来固有的内容”(《中国古典哲学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吴冬梅说“朱子的‘体’‘用’是其独特的‘体’‘用’,不可能与现代意义上的‘体’‘用’内涵完全一致”(《“心与理一”与“超凡入圣”之学——朱子心论研究》,第21页),也是在试图强调这一点。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21页。此句《全书》标点有误,此意又见《中庸或问》:“盖当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觉者,而未有所知觉也。”(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562页)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86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1。又“性、情则一。性是不动,情是动处,意则有主向”(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2页)、“心是浑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动处”(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04页),这两处也是相同的意思。
③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4页。
④同上书,第31页。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6页。
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38页。
⑦程子“其未发也五性具焉”(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77页)一言,应当是朱子这些说法的先驱。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74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41页。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790页。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694页。
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99页。
⑦同上书,第1979页。
⑧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647页。
①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04页。
③同上书,第3370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43页。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15页。
⑥同上书,第228页。
⑦同上书,第223页。
⑧延在钦:《朱熹心论研究》,第109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1747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366页。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5页。
④同上书,第333页。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924页。
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787页。
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6页。
⑧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92页。
⑨同上书,第4149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28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56页。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430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3页。
①延在钦:《朱熹心论研究》,第169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05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04页。
②同上书,第205页。
③同上书,第194页。
④同上书,第207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551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02页。又朱子说:“性离气禀不得。有气禀,性方存在里面;无气禀,性便无所寄搭了。禀得气清者,性便在清气之中,这清气不隔蔽那善;禀得气浊者,性在浊气之中,为浊气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这又随物各具去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34页)也是相同的意思。
③这种“智”“愚”之异又被表述为“明”“暗”之异:“天之生物,其理固无差别,但人物所禀形气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异。”(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68页)①在以下这段对话中,“人类气禀(气质)论”之首先为“心灵先天差异论”和“上智生知之资”及其下资质的存在这两点也已经呼之欲出了。或问:“口耳目心皆官也。不知天所赋之气质,不昏明清浊其口耳目,而独昏明清浊其心,何也?然夷惠伊尹非拘于气禀者,处物之义,乃不若夫子之时,岂独是非之心不若圣人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浊之异。如易牙师旷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由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于气质之拘者,所以孟子以为不同,而不愿学也。”(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
1894页)“心亦由是而已”即是说人类心灵之间也存在着像口耳目之间那样的“昏明清浊之异”,有一种人类心灵像“易牙师旷”的口耳一样,是人类心灵之中“最清者也”,其他人类心灵则相对“昏”“浊”。又,生来上智、生来介于“智”“愚”之间、生来非常“愚”的区别经常被朱子表述为“无蔽”“蔽之较薄”“蔽之较厚”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朱子评论横渠“凡物莫不有性。由通蔽开塞,所以有人物之别;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别”说“似欠了生知之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06页)。
其中“无蔽”和“有蔽”的区别又被朱子表述为“无限量”和“有限量”之别,朱子注“天纵之将圣”说“纵,犹肆也,言不为限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0页),又说“天放纵圣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它”,又答弟子“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之问曰“看气象,亦似天限量它一般”(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336页),即是此意。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396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829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591。
③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14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247页。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孔子之圣,也只是好学:‘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82页)。
⑤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以“上智”为“不移”,朱子亦曰:“既是圣人,决不到得作狂。”(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624页)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244页。
②问“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曰:“圣人全体极至,没那半间不界底事。发愤便忘食,乐便忘忧,直恁地极至。大概圣人做事,如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直是恁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243页)问:“‘发愤忘食’,未知圣人发愤是如何?”曰:“要知他发愤也不得。只是圣人做事超越众人,便做到极处,发愤便忘食,乐便忘忧。若他人,发愤未必能忘食,乐处未必能忘忧。圣人直是脱洒,私欲自是惹不着。这两句虽无甚利害,细看来,见得圣人超出乎万物之表!”(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244页)这两条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③延在钦:《朱熹心论研究》,第169页。
④“强”在儒家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价值,除了《中庸》、朱子之外,后世陆桴亭也说:“朱子注‘不动心’云‘心有主则能不动矣’,窃自验之,心无主固动,即心有主之时,亦未必遽能不动,譬如一家之中,卒有盗贼事变,主人虽在,未必皆镇定舒徐,此主人弱故也。要得主人强,须是集义工夫透。”(《思辨录辑要》卷6诚正类第31条)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198页。
②朱子有时也会表达“下愚不可移”的意思,如其言曰:“如这道理,圣人知得尽得,愚不肖要增进一分不得,硬拘定在这里。”(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336页)但综合来看,“可移”应该是朱子的主要意思。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990页。
④“此心此理,虽本完具,却为气质之禀不能无偏。”(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2543页)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22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66页。又朱子说:“学问是自家合做底。
不知学问,则是欠阙了自家底;知学问,则方无所欠阙。今人把学问来做外面添底事看了”(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80页),“圣贤只是做得人当为底事尽。
今做到圣贤,止是恰好,又不是过外。”(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80页)回答“达道、达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则一,何也”之问说:“此气质之异,而性则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灵,不待教而于此无不知也;安而行之,安于义理,不待习而于此无所咈也;此人之禀气清明、赋质纯粹、天理浑然、无所亏丧者也。学而知者,有所不知,则学以知之,虽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虽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无蔽、得粹之多而未能无杂、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学而未达,困心衡虑,而后知之者也;勉强而行者,不获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强矫而行之者也;此则昏蔽驳杂,天理几亡,久而后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气质之禀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则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则其所知、所至无少异焉,亦复其初而已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586页)也都是相同的意思。
①朱子有时仅仅以普通心灵的自我提升为“学”,不以“上智”心灵的自我保持为“学”,如其言曰“生知之圣,不待学而自至。若非生知,须要学问”(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658页),“窃谓人之所以为学者,以吾之心未若圣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圣人之心,是以烛理未明、无所准则,随其所好,高者过、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为过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与天地圣人之心无异矣,则尚何学之为哉”(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20页)。但生知之圣必好学应该才是朱子的正意。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886页。
③《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1页。
④同上书,第444页。
⑤同上书,第196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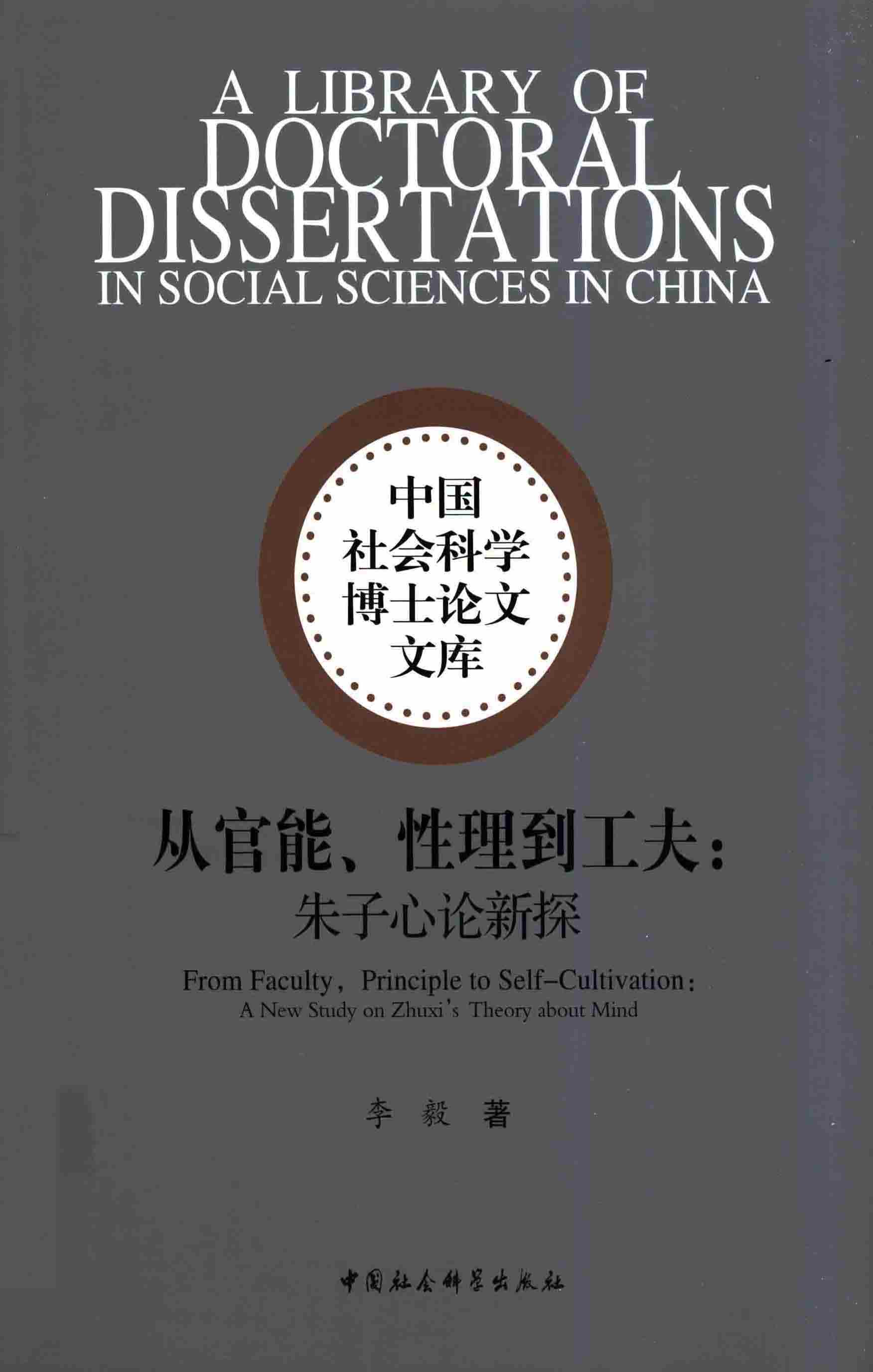
《从官能、性理到工夫:朱子心论新探》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在总结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朱子“心之学说”概括为“官能”“性理”“虚实动静”“身体与善恶”“工夫”五个紧密联系的部分,并对其中十多个子论题如“心与知觉、思、情、意”“心统性情”“中和新说”“道心人心”“知行论”等的内容及脉络,进行了精益求精的哲学探讨和贴切着实的现代诠释,得出了一系列较新颖而透彻的结论。
阅读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