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审辞气“托言”“祝愿之辞”追述对强烈情感表达方式的体认用汉乐府等类比]
朱熹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又以涵泳文本为读诗之原则,所以对《诗经》具体作品的解释每多胜说。朱熹对《诗经》作品之辞气与曲折情感每多贴切之体认,尤其值得关注。研究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体认,不应忽视这一点。
一、审辞气
朱熹说诗,以审辞气而得胜说者,比比皆是。其说《邶风·柏舟》一篇,最为典型。该篇《序》云:“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认定其主题为写仁人不遇。《诗序辨说》云:“不知其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为不遇于君。此则失矣”,则以《序》说为非。《诗集传》径云:“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又云:“《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诗,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作文按:《邶风·绿衣》)相类,岂非庄姜之诗也欤?”朱熹虽援引《列女传》为证,但其判断该篇为妇人之诗的主要依据却是“其辞气卑顺柔弱”。现代阐释者虽然未必认为该篇是庄姜之诗,但大抵认同其抒情主人公是女子。判定该篇为弃妇之诗,显然比“仁而不遇”更合乎情理。《序》者说诗,每为比附政治所误;汉儒又依《序》说诗,以讹传讹,往往越说越离谱。朱熹能不为《序》者误导,求诗意于辞之中,又敏感于其辞气,故往往得其真谛。
审其辞气,察其情理,往往易得《诗》之本来面目。朱熹对“淫诗”的认定亦得益于此。如《王风·丘中有麻》篇,《序》云:“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诗序辨说》则云:“此亦淫奔者之词。其篇上属《大车》,而语意不庄,非望贤之意。序说误矣。”《郑风·风雨》篇,《序》云:“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诗序辨说》则云:“序意甚美,然考其词轻佻狎昵,非思贤之意也。”于此二篇,《序》者以为思贤之作,朱熹不以为然,其理由无非是此二篇轻佻狎昵、语意不庄。朱熹说诗的根本方法是求诗意于辞之中,而其具体手段又往往是审辞气、察情理。“淫诗”说是朱熹对诗经学的大贡献,归根结底,却是得益于对诗之辞气与情感的敏感。
审辞气、察情理,使得朱熹对《诗》之人物关系往往有正确认识。典型例证是《周南·卷耳》与《邶风》有关庄姜诸篇。
《周南·卷耳》篇,《序》云:“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之序,首句得之,余皆傅会之凿说。后妃虽知臣下之勤劳而忧之,然曰嗟我怀人,则其言亲昵,非后妃之所得施于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独为后妃;而后章之我,皆为使臣。首尾衡决,不相承应,亦非文字之体也。”据《序》者之说,该篇是国史一类人写后妃体恤使臣之勤劳。朱熹则完全不同意这种意见。朱熹的依据是该诗辞气亲昵,诗中“嗟我怀人”一句,显示其当事人是夫妻关系,非后妃所能施于使臣。故《诗集传》首章径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而《序》者将之解释为后妃与使臣,显然于情理不合。
《邶风》之《终风》、《日月》二篇,《序》者皆以为庄姜遭州吁之暴,朱熹则不以为然。《邶风·终风》篇,《序》云:“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诗序辨说》云:“详味此诗,有夫妇之情,无母子之意。若是庄姜之诗,则亦当在庄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诗集传》云:“庄公之为人,狂荡暴疾,庄姜盖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终风且暴为比。”《序》者以此篇为庄姜伤己遭州吁之暴;朱熹则以为诗言庄公狂暴,庄姜自伤遇人不淑。朱熹以庄公狂暴易《序》“州吁之暴”,其依据无非是该诗有夫妇之情,而无母子之意。
《邶风·日月》篇,《序》云:“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诗序辨说》云“此诗《序》以为庄姜之作,今未有以见其不然。但谓遭州吁之难而作,则未然耳。盖诗言宁不我顾,犹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无良,亦非所以施于前人者。明是庄公在时所作,其篇次亦当在《燕燕》之前。”诗之作者是庄姜,这一点朱熹对《序》没有不同意见,但朱熹对《序》所云“遭州吁之难”则很不以为然。朱熹的依据是:1、诗云“宁不我顾”,有盼望其回心转意之意;2、诗云“德音无良”,不应该是对已故之人的指责。有了这两条理由,朱熹便认定该篇作于庄公在世之时,《序》云“遭州吁之难”与实际情况不合。审其文意辞气,以断诗之世次,正是朱熹的高明之处。
审辞气以断世次的典型例子,还有《小雅·楚茨》等篇。《诗序辨说》于《小雅·楚茨》一篇云:“自此篇至《车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无讽刺之意。序以为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诗固有如此者,然不必十篇相属,而绝无一言以见其为衰世之意也。窃恐《正雅》之篇有错脱在此耳,序皆失之。”“风雅正变”之说,是汉学诗经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汉学诗经学认为“诗缘政”,有周之世,以成康为界,政局大有不同,故其诗亦相应有正变之分。成康以前之诗为《正风》、《正雅》,成康之后诗为《变风》、《变雅》。具体到《诗经》篇目,则《二南》为《正风》,《邶风》以下十三国风为《变风》;《鹿鸣》至《菁菁者莪》16篇为《正小雅》,以下58篇为《变小雅》;《文王》至《卷阿》18篇为《正大雅》,以下13篇为《变大雅》。(依据:郑玄《诗谱序》)依汉学诗经学体系,凡世次在前的,为《正风》、《正雅》,以颂美为主;凡世次在后的,为《变风》、《变雅》,以讽刺为主。《楚茨》至《车舝》十篇,在《变小雅》之列,当为“刺诗”,故其诗虽无讽刺之言,《序》者一律认为是“陈古刺今”。朱熹则不以为然,以其“词气和平,称述详雅”为依据,认定其为美诗,当为《正雅》错简在此。《诗经》之编次,未必是先秦原貌,汉儒风雅正变之说亦过于牵强傅会。朱熹反对风雅正变说不够彻底是其局限,但根据辞气来判定美刺,远比汉儒仅据编次来判定来得高明。
审辞气,还往往使得朱熹对诗中曲折之情有深切的体会。如《邶风·简兮》篇,《诗集传》首章总括全篇之意云:“贤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轻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誉而实自嘲也。”“若自誉而实自嘲”,非对诗之情感体贴入微者所不能道。该诗第三章“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诗集传》对“公言锡爵”做如下发挥:“‘公言锡爵’,即《仪礼》宴饮而献工之礼也。以硕人而得此,则亦辱矣,乃反以其赉予之亲洽为荣而夸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能看出诗之作者是在说反话,其态度是玩世不恭,非得以对诗之抒情精神有深入体会为前提不可。《诗集传》于该篇篇末引张子之言,曰:“为禄仕而抱关击坼,则犹恭其职也。为伶官,则杂于侏儒俳优之间,不恭甚矣。其得谓之贤者,虽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过人,又能卷而怀之,是亦可以为贤矣。东方朔似之。”朱熹的灵感或者来自张子“东方朔似之”这一句。但张子是从“杂于侏儒俳优之间”而能“卷而怀之”的道德立场,将其人与东方朔作比;朱熹则扣紧“玩世不恭”、“若自誉而实自嘲”,其着眼点是诗的表达方式。
审辞气,对认识文学表达的虚实关系亦大有裨益。《朱子语类》记朱熹论《常棣》之诗,有云:“‘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实以兄弟为不如友生也。犹言丧乱既平之后,乃谓反不如友生乎?盖疑而问之辞也。”(81/2118,潘时举记)注意到这是“疑而问之辞”,说明朱熹对字面背后作者的隐情多有留意。此亦非缺乏文学修养者所能为。
二、“托言”
朱熹读《诗》,以涵泳文本为根本方法,处处体察《诗》之情感、辞气,对《诗》的一些特殊表达方式往往有较深的体认。“托言”义例的发明,尤能说明这一问题。且看《周南·卷耳》与《召南·草虫》两篇例证:
《周南·卷耳》篇首章:“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诗集传》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次章“陟彼崔嵬,我马虺。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诗集传》云:“此又托言欲登崔嵬之山,以望所怀之人而往从之,则马罷病而不能进,于是且酌金〓之酒,而欲其不至于长以为念也。”两个“托言”,说明未必实有此事,而只是诗人的想象之词,是诗歌习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现代阐释者于该篇抒情主人公每多怀疑,理由无非是女子似不应驰马高岗、纵酒消忧。所以现代阐释者往往将此篇看作男女对答之辞,认为首章是女子思念夫君之辞,首章以下则是夫君对答之辞。这种处理方法不无一定道理,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至少朱熹的解释能自圆其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阐释。“托言”确实是诗歌传统中固有的一种表达方式,古诗写思念、忧伤主题,十之八九不离饮酒,大抵不过是借“饮酒”来表达某种情绪而已;实际饮酒与否,则是另外一码事。后世女作家的诗词创作尤能说明这一问题。古代女子生活较为狭隘,诗作中表现的未必是现实生活所能有的,但却可以凭想象来构拟。朱熹能认识到诗歌中存在“托言”这种表达方式,并且用“托言”来解释《诗经》的具体作品,是其高明之处。驰马高岗、纵酒消忧,固不应是女子之常规;但若当作想象之辞,则未尝不可。加上朱熹认定该篇抒情主人公是后妃而非普通女子,“采采卷耳”恐亦不能是实情;但将其处理为“托言”,则合乎情理与文学创作的规律。朱熹于此特地标明“托言”,说明其对《诗经》的文学表现方法多有关注,亦多贴切体会。毛、郑之伦,于此则全无认识。
《召南·草虫》次章“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诗集传》云:“赋也。登山盖托以望君子。”此例亦同。登山采蕨,未必实有此事,不过是借以表达思望君子之“托言”而言。《诗集传》于其首章隐括诗意云:“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该篇既为行役相思主题,妇人以其夫不在,思念之,故有此作,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恐亦为预想之词。以“托言”说诗,往往可得圆融之解释。不明“托言”义例,则难免扦格难通。
《诗集传》点明“托言”者,共有7例。
附录15:《诗集传》指明“托言”例:
01 《周南·卷耳》,《诗集传》首章:“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诗集传》次章:“此又托言欲登崔嵬之山,以望所怀之人而往从之,则马罷病而不能进,于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于长以为念也。”
02 《召南·草虫》,《诗集传》次章:“赋也。登山盖托以望君子。”
03 《召南·行露》,《诗集传》首章:“赋也……盖以女子早夜独行,或有强暴侵凌之患,故托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溽。”
04 《邶风·简兮》,《诗集传》末章:“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离骚》亦以美人目其君也。”
05 《卫风·有狐》,《诗集传》首章:“比也……国乱民散,丧其妃耦,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独行,而忧其无裳也。”
06 《王风·采葛》,《诗集传》首章:“采葛所以为绤,盖淫奔者托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07 《魏风·硕鼠》,《诗集传》首章:“比也……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诗序辨说》:“此亦托于硕鼠以刺其有司之辞,未必直以硕鼠比其君也。”
以上诸例,“托言”者皆未必实有其事,都无非是借以表达某种情感或情绪而已。朱熹于如此众多的篇目特意点明“托言”义例,一者可见“托言”是《诗经》作品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二者可见他对文学作品的表现方法有很深的体认,三者可见他时时以文学眼光来观照《诗经》。故朱熹说《诗》,并非单单是理学角度,而是对文学表达方式有很深的体会和认识。
《朱子语类》中有一条记载,是朱熹与弟子谈论《卷耳》与《葛覃》在表现方法上的差异的:
问:《卷耳》与前篇《葛覃》同是赋体,又似略不同。盖《葛覃》直叙其所经历之事,《卷耳》则是托言也。
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设使不曾经历,而自言我之所怀者如此,则亦是赋体。(81/2097,潘时举记)
朱熹这里强调的是《卷耳》与《葛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表现方法:《葛覃》是写实有之事,《卷耳》则是托言构拟。虽然不是亲身经历的实有之事,但在文学表达里却是允许的。这种表达方式,和写实有之事一样,都是“赋”体的一种类型。后妃未必自采卷耳,但出于文学表达的需要,却是可以这样说的。《朱子语类》记载朱熹与弟子谈论《召南·采蘩》时,亦涉及这一问题:
问:采苹蘩以供祭祀,采枲耳以备酒浆,后妃夫人恐未必亲为之。
曰:诗人且如此说。(81/2100,廖德明记)
《诗三百》言及后妃夫人亲自从事采集等劳作的,不止是采卷耳一事而已。读者或怀疑此等劳作之事与后妃夫人身份不相符合。朱熹则直接道破:这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而已。这样的眼光,实在是朱熹的高明之处。
三、“祝愿之辞”
“托言”之外,朱熹还注意到《诗经》其他的一些文学表现方法,如“祝愿之辞”和“追述”例。
“祝愿之辞”例,以《鲁颂》之《泮水》、《〓宫》最为典型。《朱子语类》有云:“《颂》是告于神明,却《鲁颂》中多是颂当时之君。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岂有此事?曰:是颂愿之辞。”(81/2140,黄㽦记)
《鲁颂·泮水》篇,《诗集传》于其三章章末云:“此章以下,皆颂祷之辞也。”该诗五章曰:“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此后数章皆为演绎“淮夷攸服”之辞。《诗集传》于其五章章末云:“盖古者出兵,受成于学;及其反也,释奠于学,而以讯馘告。故诗人因鲁侯在泮,而愿其有是功也。”既云“愿其有是功”,说明实际情况未必如此,而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理想而已。《鲁颂》诸篇,汉学诗经学以为皆鲁僖公之诗,朱熹对此不以为然。《诗集传》于《鲁颂》解题云:“旧说,皆以为伯禽十九世孙僖公申之诗,今无所考。独《〓宫》一篇,为僖公之诗无疑。”《鲁颂·泮水》篇世次不可考,诗中所云“淮夷攸服”之事更是虚无缥缈。毛、郑释此篇,皆以“淮夷攸服”为实有之事,但却没有任何旁证。朱熹说诗,有考诸书史一法,既无任何书史旁证,自然不肯轻易盲从旧说,故视之为颂祷祝愿之辞。既为颂祷祝愿之辞,自然难免夸大虚美。出于文体自身的需要,表达一下美好的愿望也未尝不可。朱熹对这一套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故在此特地点醒是“颂祷之辞”,是“愿其有是功也”。
比之汉儒,要圆融高明得多。
《鲁颂·〓宫》篇,《诗集传》于其三章章末云:“此章以后,皆言僖公致敬郊庙,而神降之福,国人称愿之如此也。”该诗八章有云:“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常、许究为何地,毛、郑说法不一。《传》云:“常、许,鲁南鄙、西鄙。”《笺》云:“许,许田也,鲁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尝,在薛之旁。《春秋传》鲁庄公三十年筑台于薛,是与周公有常邑。许田,未闻也。六国时,齐有孟尝君食邑于薛。”《孔疏》云:“常为南鄙,许为西鄙,或当有所依据,不知所出何书也……《传》以常、许为鲁之鄙邑,书传无文,故《笺》易之:许,许田也,鲁朝宿之邑……桓公以许与郑,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复周公之宇也。《春秋传》于僖公之世不书得许田,盖经传缺漏,故无其事也。”据《孔疏》,《郑笺》以书传无文,故不从《毛传》“南鄙、西鄙”之说。但“《春秋传》于僖公之世不书得许田”,既然“经传缺漏”,不知《郑笺》、《孔疏》之说根据何在?朱熹正是看到了毛、郑、《孔疏》之说不足取信于人,故《诗集传》云:“常,或作尝,在薛之旁。许,许田也,鲁朝宿之邑也。皆鲁之故地,见侵于诸侯而未复者,故鲁人以是愿僖公也。”僖公究竟收复常、许之地与否,经传无考,《郑笺》、《孔疏》凭空坐实,实属一厢情愿。但若理解成祝愿之辞,则圆融无碍。《鲁颂·〓宫》为《诗经》最长的一篇,以铺叙夸张为能事,格局阔大,气势恢弘,从纯文学角度来看,写得非常成功,对后来的汉大赋的写作风格亦有一定影响。但诗中所述,恐与信史相差甚远。朱熹于此种表达方法有深入认识,故能一针见血指出是国人称愿之辞。此二例说明文学修养于正确理解诗意大有助益。相形之下,毛、郑说诗之弊,正在欠缺文学修养。
四、追述
朱熹不仅注意到祝愿之辞,而且还注意到追述之例。《诗集传》于《大雅·文王之什》作结曰:“《郑谱》此以上为文武时诗,以下为成王周公时诗。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则非文王之诗矣。又曰无念尔祖,则非武王之诗矣。《大明》、《有声》,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为文武之时所作乎?盖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后之诗,但些什皆追述文武之德,故《谱》因此而误耳。”对于《正大雅》的时代,郑玄主张《文王有声》以上为文王、武王时所作,以下为成王、周公时所作;朱熹不赞同这种意见,主张《正大雅》是成康之时及成康以后的作品,诗中言及文王、武王,都是追述其德。《大雅·文王有声》七章“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诗集传》引张子之言,曰:“此举谥者,追述其事之言也。”该篇作于成王之时,言武王落成镐京之事,自是追述之辞。追述本是一种重要的叙述方式,有较高文学修养的朱熹自然对此并不陌生,故能在解说诗文时运用自如。
又《周颂·执竞》篇,《序》云“祀武王也。”《诗序辨说》云:“此诗并及成康,则序说误矣。其说已具于《昊天有成命》之篇。苏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时,因从小序之言,此亦以辞害意之失。《皇矣》之诗于王季章中盖已有此句矣,又岂可以其太蚤而别为之说耶?诗人之言或先或后,要不失为周有天下之意耳。”《执竞》诗云:“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汉学诗经学以之为成王、周公之时祭祀武王之诗,故不以诗中“成康”为成王、康王。《毛传》释“不显成康”一句云:“不显乎成大功而安之也”,是以“成康”为成就安定大业。《郑谱》云: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此即汉学诗经学于《周颂》时代背景的纲领性文件。《诗集传》于《颂》诗解题则云:“《周颂》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后之诗。”是朱熹主张《周颂》大都经周公所定,但也有一些康王以后的作品。其实朱熹这一论断的依据乃在《周颂》中有一些篇章言及成王、康王。《执竞》之外,《昊天有成命》一篇的时代,朱熹亦不赞同毛、郑之说。《昊天有成命》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序》云:“郊祀天地也。”《诗序辨说》云:“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后祀成王之诗无疑。而毛、郑旧说定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故凡《颂》中有成王及康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己意。其迂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古今诸儒,无有觉其谬者。独欧阳公著《时世论》以斥之,其辨明矣。……故今特上据《国语》,旁采欧阳,以定其说,庶几有以不失此诗之本指耳。”故《诗集传》云:“此诗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诗也”,又云:“《国语》叔向引此诗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证之,则其为祀成王之诗无疑矣”,从而断言“此康王以后之诗”。《郑笺》释“成王不敢康”云:“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诗集传》释“成王”则云:“成王,名诵,武王之子。”对“成王”、“成康”解释的不同,显示出朱熹与汉学诗经学的异趣。汉儒囿于成说,未免画地为牢;朱熹则能不盲从汉儒,求诗意于辞之中,往往能得合乎情理之解释。至于苏辙,本亦有独立思考之精神,于《执竞》一篇从《小序》的理由则是因为诗言“奄有四方”,而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时,故以之为祀武王之诗。但朱熹批评苏辙犯了“以辞害意”的错误。朱熹的理由是《皇矣》一诗第三章写王季已有“奄有四方”这一
句。王季的时代,周室仅为一方诸侯,何来“奄有四方”?但诗人也便这样用了。“奄有四方”用于王季,既不嫌其早;用于成王、康王,又何必嫌其晚?“诗人之言或先或后,要不失为周有天下之意耳”,无非是诗歌习用的表达方式而已。故朱熹不取毛、郑之说,而径以该篇为昭王以后之诗。这虽然只是世次的考订,但却包含对文学表达方式的深刻认识。
此外,《周南·汝坟》首章“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诗集传》云:“汝旁之国,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妇人喜其君子行役而归,因记其未归之时,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赋之也。”《诗集传》之所以有“追赋”之说,大约是因为其诗二章云:“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二章既云“既见君子”,则首章之“未见君子”为“追赋”之辞。此不涉及世次问题,但亦属“追述”之例。
五、对强烈情感表达方式的体认
朱熹对诗中强烈的抒情精神往往有较深的体会。对《诗经》作品一些具体字词的解释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将毛、郑与朱熹对这些字词的解释做一番比较,便可发现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邶风·日月》首章:“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郑笺》云:“日月,喻国君与夫人也,当同德齐意以治国者,常道也。”《诗集传》则云:“日居月诸,呼而诉之也”。该篇末章“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郑笺》云:“父兮母兮者,言己尊之如父,又亲之如母,乃反养育我之不终也。”《诗集传》云:“不得于夫,而叹父母养我之不终,盖忧患疾痛之极,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因《小序》云:“《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故《郑笺》处处牵合《小序》所认定庄姜与庄公之关系,以“日月”喻国君与夫人之地位;以“父兮母兮”为庄姜自言待庄公之情如待父母。如此说诗,实牵强傅会,故为朱熹所不取。朱熹则从情理与情感表达方式入手,认为呼父母而告,呼日月而诉,都是因为内心过于悲痛郁结,是强烈的情感喷薄而出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表达方式。朱熹与郑玄对诗中“日月”、“父母”解释的不同,反映了二者说诗方法的不同。以郑玄为代表的汉学诗经学“依《序》说诗”,且以道德等各种比附为能事,并不把《诗》当独立的文学作品看;朱熹则涵泳文本,“求诗意于辞之中”,细致体察诗人的情感与表达方式。尽管朱熹也强调《诗》的教化作用,但首先是当文学作品来看。
《邶风·日月》篇的“日月”之外,对《诗经》部分作品中“天”的解释不同,更具有普遍性,也更为典型。今举数例于下:
《小雅·小明》首章:“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载離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岂不怀归?畏此罪罟。”《郑笺》云:“明明上天,喻王者当光明如日之中也;照临下土,喻王者当察理天下之事。据时幽王不能然,故举以刺之。”《诗集传》云:“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岁末,而未得归,故呼天而诉之。”郑玄以比兴说诗,比附政治、道德品性,故以上天喻王;朱熹则不以上天喻王。
《大雅·板》首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毛传》云:“上帝,以称王者也。”《郑笺》云:“王为政反先王与天之道,天下之民,尽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诗集传》云:“世乱乃人所为,而曰上帝板板者,无所归咎之辞耳。”毛、郑训上帝为王,纯粹从比附政治的角度出发;朱子则以为天,是从情感与表达方式的角度来体察。
《大雅·瞻印》首章:“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毛传》云:“昊天,斥王也。”《郑笺》云:“仰视幽王为政,则不爱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恶以败乱之。”《诗集传》云:“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乱,无所归咎之辞也。”此例亦同。
朱熹对《诗经》部分作品“天”字的解释,总使笔者想起《史记》中的两段著名文字:其一是《项羽本纪》写项羽垓下兵败后对部下的一段告白:“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其二是《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怨而作《离骚》的解释:“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太史公以磊落特出之才,因李陵事遭宫刑横祸,发愤而著《史记》,书中处处流落出悲怆之情。其志也怒,其情也哀,故于笔下人物之情志多同情性之理解,尤其擅长表达那种无处诉说、难以名说的愤怒与悲哀。个体的生命,相对于天地的永恒过于渺小;个人的意志,在命运面前终究是无奈和徒劳。当生命的激情经过跌宕而落于谷底,当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穷途末路的心灵往往会对天地、命运质问。无所归咎,是故归咎于命运;无处诉说,是故呼告于天地。这或许是一切悲剧美最感动人的地方。项羽一世英雄,战无不胜,只到临死,他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败给刘邦。这悲怆的末路英雄,只能发出“天亡我”的呐喊。屈原以高洁正直之身,一心为国谋,竟遭诽谤疏远,内心无法接受这样不公的事实。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差太大,不能不象个委屈的孩子一样呼告控诉于上帝。“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这是个体生命遭遇不幸时本能的反应,是人类情感最激烈的一种表达方式。朱熹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能看出《诗经》中这类文字是“无所归咎之辞”。“忧患疾痛之极,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的概括,与太史公又是何其相似!由此,我们可以见出朱熹的文学修养,他对悲怆的感情与呼告父母、天地的表达方式有太深的体会。此亦非以比附政治为能事的毛、郑之伦所能及。
六、用汉乐府等类比
朱熹重视《诗经》作品文学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以《楚辞》、汉魏乐府、后世民歌来比附《诗经》。前文已论朱熹以“而今闲泼曲子”比况《国风》,除了这种风格类型上的比附之外,在解释具体作品时,朱熹也常常援引后世的文学作品来做比较。兹举数例于下:
《邶风·简兮》篇,《诗集传》于其末章云:“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离骚》亦以美人目其君也。”这是拿《离骚》作比。《郑风·遵大路》篇,《诗集传》于其首章云:“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衣祛而留之曰……宋玉赋有‘遵大路兮揽子祛’之句,亦男女相悦之词。”这是拿宋玉的作品来作比。前者尚只是单个词句的比照解释,后者则是作品性质上的比照说明了,说明朱熹将二者同样看待。
《秦风·晨风》篇,《诗集传》首章云:“妇人以夫不在,而言……此与扊扅之歌同意,盖秦俗也。”“扊扅之歌”是弃妇诗,可见朱熹视《秦风·晨风》为弃妇诗。
《小雅·頍弁》篇,《序》云:“诸公刺幽王也。暴戾无亲,不能宴乐同姓、亲睦九族,孤危将亡,故作是诗也。”《诗序辨说》云:“序见诗言‘死丧无日’,便谓‘孤危将亡’。不知古人劝人宴乐多为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类,且汉魏以来乐府犹多如此,如‘少壮几时’、‘人生几何’之类是也。”汉魏乐府古诗多忧生之嗟,但往往是借以表达某一种情绪,劝人及时行乐而已。朱熹熟知这一现象,所以能看出《小雅·頍弁》一篇中与此相似的情绪。该诗末章:“有頍者弁,实维在首。尔酒既旨,尔肴既阜。岂伊异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郑笺》云:“王政既衰,我无所依怙,死亡无有日数,能复几何与王相见也?且今夕喜乐此酒,此乃王之宴礼也。刺幽王将丧亡,哀之也。”《郑笺》的阐释,完全是依《序》说诗。《诗集传》则云:“言霰集则将雪之候,以比老至则将死之征也。故卒章言死丧无日,不能久相见矣,但当乐饮以尽今夕之欢。”朱熹显然看出了“死丧无日,无几相见”只是一种劝人行乐的表达方式而已。所以《诗集传》对全篇诗旨亦不取《序》者刺幽王孤危将亡之说,而只云“此亦燕兄弟亲戚之诗”。
审辞气、“托言”例、“祝愿之辞”例、“追述”例、对强烈情感表达方式的体认、用汉乐府等类比,是朱熹对《诗三百》文学表现方法有深刻体会和清醒认识的具体表现。这些都说明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很充分的认识,朱熹已经是在很大程度上用文学的眼光来看《诗经》。
朱熹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又以涵泳文本为读诗之原则,所以对《诗经》具体作品的解释每多胜说。朱熹对《诗经》作品之辞气与曲折情感每多贴切之体认,尤其值得关注。研究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体认,不应忽视这一点。
一、审辞气
朱熹说诗,以审辞气而得胜说者,比比皆是。其说《邶风·柏舟》一篇,最为典型。该篇《序》云:“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认定其主题为写仁人不遇。《诗序辨说》云:“不知其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为不遇于君。此则失矣”,则以《序》说为非。《诗集传》径云:“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又云:“《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诗,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作文按:《邶风·绿衣》)相类,岂非庄姜之诗也欤?”朱熹虽援引《列女传》为证,但其判断该篇为妇人之诗的主要依据却是“其辞气卑顺柔弱”。现代阐释者虽然未必认为该篇是庄姜之诗,但大抵认同其抒情主人公是女子。判定该篇为弃妇之诗,显然比“仁而不遇”更合乎情理。《序》者说诗,每为比附政治所误;汉儒又依《序》说诗,以讹传讹,往往越说越离谱。朱熹能不为《序》者误导,求诗意于辞之中,又敏感于其辞气,故往往得其真谛。
审其辞气,察其情理,往往易得《诗》之本来面目。朱熹对“淫诗”的认定亦得益于此。如《王风·丘中有麻》篇,《序》云:“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诗序辨说》则云:“此亦淫奔者之词。其篇上属《大车》,而语意不庄,非望贤之意。序说误矣。”《郑风·风雨》篇,《序》云:“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诗序辨说》则云:“序意甚美,然考其词轻佻狎昵,非思贤之意也。”于此二篇,《序》者以为思贤之作,朱熹不以为然,其理由无非是此二篇轻佻狎昵、语意不庄。朱熹说诗的根本方法是求诗意于辞之中,而其具体手段又往往是审辞气、察情理。“淫诗”说是朱熹对诗经学的大贡献,归根结底,却是得益于对诗之辞气与情感的敏感。
审辞气、察情理,使得朱熹对《诗》之人物关系往往有正确认识。典型例证是《周南·卷耳》与《邶风》有关庄姜诸篇。
《周南·卷耳》篇,《序》云:“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之序,首句得之,余皆傅会之凿说。后妃虽知臣下之勤劳而忧之,然曰嗟我怀人,则其言亲昵,非后妃之所得施于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独为后妃;而后章之我,皆为使臣。首尾衡决,不相承应,亦非文字之体也。”据《序》者之说,该篇是国史一类人写后妃体恤使臣之勤劳。朱熹则完全不同意这种意见。朱熹的依据是该诗辞气亲昵,诗中“嗟我怀人”一句,显示其当事人是夫妻关系,非后妃所能施于使臣。故《诗集传》首章径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而《序》者将之解释为后妃与使臣,显然于情理不合。
《邶风》之《终风》、《日月》二篇,《序》者皆以为庄姜遭州吁之暴,朱熹则不以为然。《邶风·终风》篇,《序》云:“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诗序辨说》云:“详味此诗,有夫妇之情,无母子之意。若是庄姜之诗,则亦当在庄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诗集传》云:“庄公之为人,狂荡暴疾,庄姜盖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终风且暴为比。”《序》者以此篇为庄姜伤己遭州吁之暴;朱熹则以为诗言庄公狂暴,庄姜自伤遇人不淑。朱熹以庄公狂暴易《序》“州吁之暴”,其依据无非是该诗有夫妇之情,而无母子之意。
《邶风·日月》篇,《序》云:“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诗序辨说》云“此诗《序》以为庄姜之作,今未有以见其不然。但谓遭州吁之难而作,则未然耳。盖诗言宁不我顾,犹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无良,亦非所以施于前人者。明是庄公在时所作,其篇次亦当在《燕燕》之前。”诗之作者是庄姜,这一点朱熹对《序》没有不同意见,但朱熹对《序》所云“遭州吁之难”则很不以为然。朱熹的依据是:1、诗云“宁不我顾”,有盼望其回心转意之意;2、诗云“德音无良”,不应该是对已故之人的指责。有了这两条理由,朱熹便认定该篇作于庄公在世之时,《序》云“遭州吁之难”与实际情况不合。审其文意辞气,以断诗之世次,正是朱熹的高明之处。
审辞气以断世次的典型例子,还有《小雅·楚茨》等篇。《诗序辨说》于《小雅·楚茨》一篇云:“自此篇至《车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无讽刺之意。序以为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诗固有如此者,然不必十篇相属,而绝无一言以见其为衰世之意也。窃恐《正雅》之篇有错脱在此耳,序皆失之。”“风雅正变”之说,是汉学诗经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汉学诗经学认为“诗缘政”,有周之世,以成康为界,政局大有不同,故其诗亦相应有正变之分。成康以前之诗为《正风》、《正雅》,成康之后诗为《变风》、《变雅》。具体到《诗经》篇目,则《二南》为《正风》,《邶风》以下十三国风为《变风》;《鹿鸣》至《菁菁者莪》16篇为《正小雅》,以下58篇为《变小雅》;《文王》至《卷阿》18篇为《正大雅》,以下13篇为《变大雅》。(依据:郑玄《诗谱序》)依汉学诗经学体系,凡世次在前的,为《正风》、《正雅》,以颂美为主;凡世次在后的,为《变风》、《变雅》,以讽刺为主。《楚茨》至《车舝》十篇,在《变小雅》之列,当为“刺诗”,故其诗虽无讽刺之言,《序》者一律认为是“陈古刺今”。朱熹则不以为然,以其“词气和平,称述详雅”为依据,认定其为美诗,当为《正雅》错简在此。《诗经》之编次,未必是先秦原貌,汉儒风雅正变之说亦过于牵强傅会。朱熹反对风雅正变说不够彻底是其局限,但根据辞气来判定美刺,远比汉儒仅据编次来判定来得高明。
审辞气,还往往使得朱熹对诗中曲折之情有深切的体会。如《邶风·简兮》篇,《诗集传》首章总括全篇之意云:“贤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轻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誉而实自嘲也。”“若自誉而实自嘲”,非对诗之情感体贴入微者所不能道。该诗第三章“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诗集传》对“公言锡爵”做如下发挥:“‘公言锡爵’,即《仪礼》宴饮而献工之礼也。以硕人而得此,则亦辱矣,乃反以其赉予之亲洽为荣而夸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能看出诗之作者是在说反话,其态度是玩世不恭,非得以对诗之抒情精神有深入体会为前提不可。《诗集传》于该篇篇末引张子之言,曰:“为禄仕而抱关击坼,则犹恭其职也。为伶官,则杂于侏儒俳优之间,不恭甚矣。其得谓之贤者,虽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过人,又能卷而怀之,是亦可以为贤矣。东方朔似之。”朱熹的灵感或者来自张子“东方朔似之”这一句。但张子是从“杂于侏儒俳优之间”而能“卷而怀之”的道德立场,将其人与东方朔作比;朱熹则扣紧“玩世不恭”、“若自誉而实自嘲”,其着眼点是诗的表达方式。
审辞气,对认识文学表达的虚实关系亦大有裨益。《朱子语类》记朱熹论《常棣》之诗,有云:“‘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实以兄弟为不如友生也。犹言丧乱既平之后,乃谓反不如友生乎?盖疑而问之辞也。”(81/2118,潘时举记)注意到这是“疑而问之辞”,说明朱熹对字面背后作者的隐情多有留意。此亦非缺乏文学修养者所能为。
二、“托言”
朱熹读《诗》,以涵泳文本为根本方法,处处体察《诗》之情感、辞气,对《诗》的一些特殊表达方式往往有较深的体认。“托言”义例的发明,尤能说明这一问题。且看《周南·卷耳》与《召南·草虫》两篇例证:
《周南·卷耳》篇首章:“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诗集传》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次章“陟彼崔嵬,我马虺。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诗集传》云:“此又托言欲登崔嵬之山,以望所怀之人而往从之,则马罷病而不能进,于是且酌金〓之酒,而欲其不至于长以为念也。”两个“托言”,说明未必实有此事,而只是诗人的想象之词,是诗歌习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现代阐释者于该篇抒情主人公每多怀疑,理由无非是女子似不应驰马高岗、纵酒消忧。所以现代阐释者往往将此篇看作男女对答之辞,认为首章是女子思念夫君之辞,首章以下则是夫君对答之辞。这种处理方法不无一定道理,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至少朱熹的解释能自圆其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阐释。“托言”确实是诗歌传统中固有的一种表达方式,古诗写思念、忧伤主题,十之八九不离饮酒,大抵不过是借“饮酒”来表达某种情绪而已;实际饮酒与否,则是另外一码事。后世女作家的诗词创作尤能说明这一问题。古代女子生活较为狭隘,诗作中表现的未必是现实生活所能有的,但却可以凭想象来构拟。朱熹能认识到诗歌中存在“托言”这种表达方式,并且用“托言”来解释《诗经》的具体作品,是其高明之处。驰马高岗、纵酒消忧,固不应是女子之常规;但若当作想象之辞,则未尝不可。加上朱熹认定该篇抒情主人公是后妃而非普通女子,“采采卷耳”恐亦不能是实情;但将其处理为“托言”,则合乎情理与文学创作的规律。朱熹于此特地标明“托言”,说明其对《诗经》的文学表现方法多有关注,亦多贴切体会。毛、郑之伦,于此则全无认识。
《召南·草虫》次章“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诗集传》云:“赋也。登山盖托以望君子。”此例亦同。登山采蕨,未必实有此事,不过是借以表达思望君子之“托言”而言。《诗集传》于其首章隐括诗意云:“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该篇既为行役相思主题,妇人以其夫不在,思念之,故有此作,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恐亦为预想之词。以“托言”说诗,往往可得圆融之解释。不明“托言”义例,则难免扦格难通。
《诗集传》点明“托言”者,共有7例。
附录15:《诗集传》指明“托言”例:
01 《周南·卷耳》,《诗集传》首章:“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诗集传》次章:“此又托言欲登崔嵬之山,以望所怀之人而往从之,则马罷病而不能进,于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于长以为念也。”
02 《召南·草虫》,《诗集传》次章:“赋也。登山盖托以望君子。”
03 《召南·行露》,《诗集传》首章:“赋也……盖以女子早夜独行,或有强暴侵凌之患,故托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溽。”
04 《邶风·简兮》,《诗集传》末章:“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离骚》亦以美人目其君也。”
05 《卫风·有狐》,《诗集传》首章:“比也……国乱民散,丧其妃耦,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独行,而忧其无裳也。”
06 《王风·采葛》,《诗集传》首章:“采葛所以为绤,盖淫奔者托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07 《魏风·硕鼠》,《诗集传》首章:“比也……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诗序辨说》:“此亦托于硕鼠以刺其有司之辞,未必直以硕鼠比其君也。”
以上诸例,“托言”者皆未必实有其事,都无非是借以表达某种情感或情绪而已。朱熹于如此众多的篇目特意点明“托言”义例,一者可见“托言”是《诗经》作品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二者可见他对文学作品的表现方法有很深的体认,三者可见他时时以文学眼光来观照《诗经》。故朱熹说《诗》,并非单单是理学角度,而是对文学表达方式有很深的体会和认识。
《朱子语类》中有一条记载,是朱熹与弟子谈论《卷耳》与《葛覃》在表现方法上的差异的:
问:《卷耳》与前篇《葛覃》同是赋体,又似略不同。盖《葛覃》直叙其所经历之事,《卷耳》则是托言也。
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设使不曾经历,而自言我之所怀者如此,则亦是赋体。(81/2097,潘时举记)
朱熹这里强调的是《卷耳》与《葛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表现方法:《葛覃》是写实有之事,《卷耳》则是托言构拟。虽然不是亲身经历的实有之事,但在文学表达里却是允许的。这种表达方式,和写实有之事一样,都是“赋”体的一种类型。后妃未必自采卷耳,但出于文学表达的需要,却是可以这样说的。《朱子语类》记载朱熹与弟子谈论《召南·采蘩》时,亦涉及这一问题:
问:采苹蘩以供祭祀,采枲耳以备酒浆,后妃夫人恐未必亲为之。
曰:诗人且如此说。(81/2100,廖德明记)
《诗三百》言及后妃夫人亲自从事采集等劳作的,不止是采卷耳一事而已。读者或怀疑此等劳作之事与后妃夫人身份不相符合。朱熹则直接道破:这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而已。这样的眼光,实在是朱熹的高明之处。
三、“祝愿之辞”
“托言”之外,朱熹还注意到《诗经》其他的一些文学表现方法,如“祝愿之辞”和“追述”例。
“祝愿之辞”例,以《鲁颂》之《泮水》、《〓宫》最为典型。《朱子语类》有云:“《颂》是告于神明,却《鲁颂》中多是颂当时之君。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岂有此事?曰:是颂愿之辞。”(81/2140,黄㽦记)
《鲁颂·泮水》篇,《诗集传》于其三章章末云:“此章以下,皆颂祷之辞也。”该诗五章曰:“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此后数章皆为演绎“淮夷攸服”之辞。《诗集传》于其五章章末云:“盖古者出兵,受成于学;及其反也,释奠于学,而以讯馘告。故诗人因鲁侯在泮,而愿其有是功也。”既云“愿其有是功”,说明实际情况未必如此,而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理想而已。《鲁颂》诸篇,汉学诗经学以为皆鲁僖公之诗,朱熹对此不以为然。《诗集传》于《鲁颂》解题云:“旧说,皆以为伯禽十九世孙僖公申之诗,今无所考。独《〓宫》一篇,为僖公之诗无疑。”《鲁颂·泮水》篇世次不可考,诗中所云“淮夷攸服”之事更是虚无缥缈。毛、郑释此篇,皆以“淮夷攸服”为实有之事,但却没有任何旁证。朱熹说诗,有考诸书史一法,既无任何书史旁证,自然不肯轻易盲从旧说,故视之为颂祷祝愿之辞。既为颂祷祝愿之辞,自然难免夸大虚美。出于文体自身的需要,表达一下美好的愿望也未尝不可。朱熹对这一套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故在此特地点醒是“颂祷之辞”,是“愿其有是功也”。
比之汉儒,要圆融高明得多。
《鲁颂·〓宫》篇,《诗集传》于其三章章末云:“此章以后,皆言僖公致敬郊庙,而神降之福,国人称愿之如此也。”该诗八章有云:“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常、许究为何地,毛、郑说法不一。《传》云:“常、许,鲁南鄙、西鄙。”《笺》云:“许,许田也,鲁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尝,在薛之旁。《春秋传》鲁庄公三十年筑台于薛,是与周公有常邑。许田,未闻也。六国时,齐有孟尝君食邑于薛。”《孔疏》云:“常为南鄙,许为西鄙,或当有所依据,不知所出何书也……《传》以常、许为鲁之鄙邑,书传无文,故《笺》易之:许,许田也,鲁朝宿之邑……桓公以许与郑,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复周公之宇也。《春秋传》于僖公之世不书得许田,盖经传缺漏,故无其事也。”据《孔疏》,《郑笺》以书传无文,故不从《毛传》“南鄙、西鄙”之说。但“《春秋传》于僖公之世不书得许田”,既然“经传缺漏”,不知《郑笺》、《孔疏》之说根据何在?朱熹正是看到了毛、郑、《孔疏》之说不足取信于人,故《诗集传》云:“常,或作尝,在薛之旁。许,许田也,鲁朝宿之邑也。皆鲁之故地,见侵于诸侯而未复者,故鲁人以是愿僖公也。”僖公究竟收复常、许之地与否,经传无考,《郑笺》、《孔疏》凭空坐实,实属一厢情愿。但若理解成祝愿之辞,则圆融无碍。《鲁颂·〓宫》为《诗经》最长的一篇,以铺叙夸张为能事,格局阔大,气势恢弘,从纯文学角度来看,写得非常成功,对后来的汉大赋的写作风格亦有一定影响。但诗中所述,恐与信史相差甚远。朱熹于此种表达方法有深入认识,故能一针见血指出是国人称愿之辞。此二例说明文学修养于正确理解诗意大有助益。相形之下,毛、郑说诗之弊,正在欠缺文学修养。
四、追述
朱熹不仅注意到祝愿之辞,而且还注意到追述之例。《诗集传》于《大雅·文王之什》作结曰:“《郑谱》此以上为文武时诗,以下为成王周公时诗。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则非文王之诗矣。又曰无念尔祖,则非武王之诗矣。《大明》、《有声》,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为文武之时所作乎?盖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后之诗,但些什皆追述文武之德,故《谱》因此而误耳。”对于《正大雅》的时代,郑玄主张《文王有声》以上为文王、武王时所作,以下为成王、周公时所作;朱熹不赞同这种意见,主张《正大雅》是成康之时及成康以后的作品,诗中言及文王、武王,都是追述其德。《大雅·文王有声》七章“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诗集传》引张子之言,曰:“此举谥者,追述其事之言也。”该篇作于成王之时,言武王落成镐京之事,自是追述之辞。追述本是一种重要的叙述方式,有较高文学修养的朱熹自然对此并不陌生,故能在解说诗文时运用自如。
又《周颂·执竞》篇,《序》云“祀武王也。”《诗序辨说》云:“此诗并及成康,则序说误矣。其说已具于《昊天有成命》之篇。苏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时,因从小序之言,此亦以辞害意之失。《皇矣》之诗于王季章中盖已有此句矣,又岂可以其太蚤而别为之说耶?诗人之言或先或后,要不失为周有天下之意耳。”《执竞》诗云:“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汉学诗经学以之为成王、周公之时祭祀武王之诗,故不以诗中“成康”为成王、康王。《毛传》释“不显成康”一句云:“不显乎成大功而安之也”,是以“成康”为成就安定大业。《郑谱》云: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此即汉学诗经学于《周颂》时代背景的纲领性文件。《诗集传》于《颂》诗解题则云:“《周颂》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后之诗。”是朱熹主张《周颂》大都经周公所定,但也有一些康王以后的作品。其实朱熹这一论断的依据乃在《周颂》中有一些篇章言及成王、康王。《执竞》之外,《昊天有成命》一篇的时代,朱熹亦不赞同毛、郑之说。《昊天有成命》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序》云:“郊祀天地也。”《诗序辨说》云:“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后祀成王之诗无疑。而毛、郑旧说定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故凡《颂》中有成王及康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己意。其迂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古今诸儒,无有觉其谬者。独欧阳公著《时世论》以斥之,其辨明矣。……故今特上据《国语》,旁采欧阳,以定其说,庶几有以不失此诗之本指耳。”故《诗集传》云:“此诗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诗也”,又云:“《国语》叔向引此诗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证之,则其为祀成王之诗无疑矣”,从而断言“此康王以后之诗”。《郑笺》释“成王不敢康”云:“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诗集传》释“成王”则云:“成王,名诵,武王之子。”对“成王”、“成康”解释的不同,显示出朱熹与汉学诗经学的异趣。汉儒囿于成说,未免画地为牢;朱熹则能不盲从汉儒,求诗意于辞之中,往往能得合乎情理之解释。至于苏辙,本亦有独立思考之精神,于《执竞》一篇从《小序》的理由则是因为诗言“奄有四方”,而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时,故以之为祀武王之诗。但朱熹批评苏辙犯了“以辞害意”的错误。朱熹的理由是《皇矣》一诗第三章写王季已有“奄有四方”这一
句。王季的时代,周室仅为一方诸侯,何来“奄有四方”?但诗人也便这样用了。“奄有四方”用于王季,既不嫌其早;用于成王、康王,又何必嫌其晚?“诗人之言或先或后,要不失为周有天下之意耳”,无非是诗歌习用的表达方式而已。故朱熹不取毛、郑之说,而径以该篇为昭王以后之诗。这虽然只是世次的考订,但却包含对文学表达方式的深刻认识。
此外,《周南·汝坟》首章“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诗集传》云:“汝旁之国,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妇人喜其君子行役而归,因记其未归之时,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赋之也。”《诗集传》之所以有“追赋”之说,大约是因为其诗二章云:“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二章既云“既见君子”,则首章之“未见君子”为“追赋”之辞。此不涉及世次问题,但亦属“追述”之例。
五、对强烈情感表达方式的体认
朱熹对诗中强烈的抒情精神往往有较深的体会。对《诗经》作品一些具体字词的解释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将毛、郑与朱熹对这些字词的解释做一番比较,便可发现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邶风·日月》首章:“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郑笺》云:“日月,喻国君与夫人也,当同德齐意以治国者,常道也。”《诗集传》则云:“日居月诸,呼而诉之也”。该篇末章“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郑笺》云:“父兮母兮者,言己尊之如父,又亲之如母,乃反养育我之不终也。”《诗集传》云:“不得于夫,而叹父母养我之不终,盖忧患疾痛之极,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因《小序》云:“《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故《郑笺》处处牵合《小序》所认定庄姜与庄公之关系,以“日月”喻国君与夫人之地位;以“父兮母兮”为庄姜自言待庄公之情如待父母。如此说诗,实牵强傅会,故为朱熹所不取。朱熹则从情理与情感表达方式入手,认为呼父母而告,呼日月而诉,都是因为内心过于悲痛郁结,是强烈的情感喷薄而出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表达方式。朱熹与郑玄对诗中“日月”、“父母”解释的不同,反映了二者说诗方法的不同。以郑玄为代表的汉学诗经学“依《序》说诗”,且以道德等各种比附为能事,并不把《诗》当独立的文学作品看;朱熹则涵泳文本,“求诗意于辞之中”,细致体察诗人的情感与表达方式。尽管朱熹也强调《诗》的教化作用,但首先是当文学作品来看。
《邶风·日月》篇的“日月”之外,对《诗经》部分作品中“天”的解释不同,更具有普遍性,也更为典型。今举数例于下:
《小雅·小明》首章:“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载離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岂不怀归?畏此罪罟。”《郑笺》云:“明明上天,喻王者当光明如日之中也;照临下土,喻王者当察理天下之事。据时幽王不能然,故举以刺之。”《诗集传》云:“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岁末,而未得归,故呼天而诉之。”郑玄以比兴说诗,比附政治、道德品性,故以上天喻王;朱熹则不以上天喻王。
《大雅·板》首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毛传》云:“上帝,以称王者也。”《郑笺》云:“王为政反先王与天之道,天下之民,尽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诗集传》云:“世乱乃人所为,而曰上帝板板者,无所归咎之辞耳。”毛、郑训上帝为王,纯粹从比附政治的角度出发;朱子则以为天,是从情感与表达方式的角度来体察。
《大雅·瞻印》首章:“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毛传》云:“昊天,斥王也。”《郑笺》云:“仰视幽王为政,则不爱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恶以败乱之。”《诗集传》云:“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乱,无所归咎之辞也。”此例亦同。
朱熹对《诗经》部分作品“天”字的解释,总使笔者想起《史记》中的两段著名文字:其一是《项羽本纪》写项羽垓下兵败后对部下的一段告白:“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其二是《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怨而作《离骚》的解释:“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太史公以磊落特出之才,因李陵事遭宫刑横祸,发愤而著《史记》,书中处处流落出悲怆之情。其志也怒,其情也哀,故于笔下人物之情志多同情性之理解,尤其擅长表达那种无处诉说、难以名说的愤怒与悲哀。个体的生命,相对于天地的永恒过于渺小;个人的意志,在命运面前终究是无奈和徒劳。当生命的激情经过跌宕而落于谷底,当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穷途末路的心灵往往会对天地、命运质问。无所归咎,是故归咎于命运;无处诉说,是故呼告于天地。这或许是一切悲剧美最感动人的地方。项羽一世英雄,战无不胜,只到临死,他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败给刘邦。这悲怆的末路英雄,只能发出“天亡我”的呐喊。屈原以高洁正直之身,一心为国谋,竟遭诽谤疏远,内心无法接受这样不公的事实。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差太大,不能不象个委屈的孩子一样呼告控诉于上帝。“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这是个体生命遭遇不幸时本能的反应,是人类情感最激烈的一种表达方式。朱熹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能看出《诗经》中这类文字是“无所归咎之辞”。“忧患疾痛之极,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的概括,与太史公又是何其相似!由此,我们可以见出朱熹的文学修养,他对悲怆的感情与呼告父母、天地的表达方式有太深的体会。此亦非以比附政治为能事的毛、郑之伦所能及。
六、用汉乐府等类比
朱熹重视《诗经》作品文学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以《楚辞》、汉魏乐府、后世民歌来比附《诗经》。前文已论朱熹以“而今闲泼曲子”比况《国风》,除了这种风格类型上的比附之外,在解释具体作品时,朱熹也常常援引后世的文学作品来做比较。兹举数例于下:
《邶风·简兮》篇,《诗集传》于其末章云:“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离骚》亦以美人目其君也。”这是拿《离骚》作比。《郑风·遵大路》篇,《诗集传》于其首章云:“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衣祛而留之曰……宋玉赋有‘遵大路兮揽子祛’之句,亦男女相悦之词。”这是拿宋玉的作品来作比。前者尚只是单个词句的比照解释,后者则是作品性质上的比照说明了,说明朱熹将二者同样看待。
《秦风·晨风》篇,《诗集传》首章云:“妇人以夫不在,而言……此与扊扅之歌同意,盖秦俗也。”“扊扅之歌”是弃妇诗,可见朱熹视《秦风·晨风》为弃妇诗。
《小雅·頍弁》篇,《序》云:“诸公刺幽王也。暴戾无亲,不能宴乐同姓、亲睦九族,孤危将亡,故作是诗也。”《诗序辨说》云:“序见诗言‘死丧无日’,便谓‘孤危将亡’。不知古人劝人宴乐多为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类,且汉魏以来乐府犹多如此,如‘少壮几时’、‘人生几何’之类是也。”汉魏乐府古诗多忧生之嗟,但往往是借以表达某一种情绪,劝人及时行乐而已。朱熹熟知这一现象,所以能看出《小雅·頍弁》一篇中与此相似的情绪。该诗末章:“有頍者弁,实维在首。尔酒既旨,尔肴既阜。岂伊异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郑笺》云:“王政既衰,我无所依怙,死亡无有日数,能复几何与王相见也?且今夕喜乐此酒,此乃王之宴礼也。刺幽王将丧亡,哀之也。”《郑笺》的阐释,完全是依《序》说诗。《诗集传》则云:“言霰集则将雪之候,以比老至则将死之征也。故卒章言死丧无日,不能久相见矣,但当乐饮以尽今夕之欢。”朱熹显然看出了“死丧无日,无几相见”只是一种劝人行乐的表达方式而已。所以《诗集传》对全篇诗旨亦不取《序》者刺幽王孤危将亡之说,而只云“此亦燕兄弟亲戚之诗”。
审辞气、“托言”例、“祝愿之辞”例、“追述”例、对强烈情感表达方式的体认、用汉乐府等类比,是朱熹对《诗三百》文学表现方法有深刻体会和清醒认识的具体表现。这些都说明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很充分的认识,朱熹已经是在很大程度上用文学的眼光来看《诗经》。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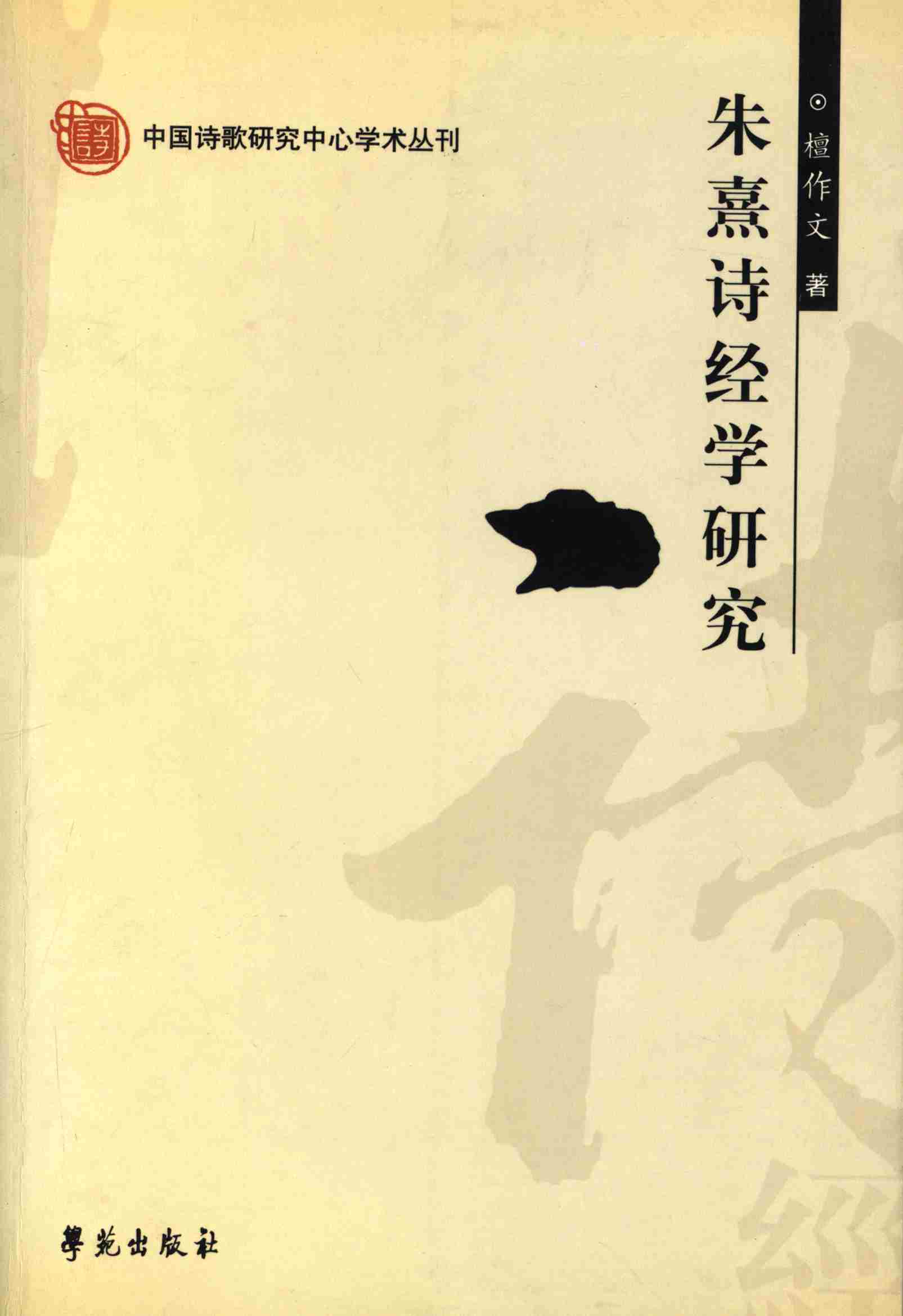
《朱熹诗经学研究》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本书为南宋朱熹诗词作品集,分为感事诗、哲理诗、山水诗、酬对诗、杂咏诗和词赋六大类。其中感事诗90首,主要反映朱熹对天下大事的观感及其在各个时期的基本思想倾向,按其主题又分为爱国恤民与述怀明志两组;哲理诗73首,主要反映朱熹的学术观点,按其主题又分为宇宦观、人生观、道德修养和为学三组;山水诗148首,主要反映朱熹的游踪和各地山川形胜,其中又分为武夷云谷、衡岳、庐山及其他胜地四大块;酬对诗87首,主要反映朱熹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内又分为奉和、题赠、迎送、寿挽四组;杂咏诗99首,为朱熹对各种事物的吟咏与思想寄寓,反映其日常生活情趣,内又分为咏物、咏景、咏居、咏事四组;词赋18首,按体裁分类。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