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学术背景的考察
| 内容出处: | 《朱熹诗经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4498 |
| 颗粒名称: | 第三节 学术背景的考察 |
| 其他题名: | [《周易本义》欧阳修《诗本义》等“本义”溯源] |
| 分类号: | I207.22 |
| 页数: | 21 |
| 页码: | 58-78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治《诗经》学的根本方法是求其本义,这一方法也适用于治其他古籍,尤其是《易》学。他主张《易》本为卜筮而作,经传各自为说,不应据传解经。求《易》本义有两层意义:一是不作义理上的傅会,二是不依传解经。对于《周易》经传的形成,朱熹认为是由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重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传组成的。他认为四圣都是以《周易》为卜筮之书。在《系辞》作者的这一问题上,朱熹虽然认为《系辞》是孔子所作,但却受到欧阳修易说的影响。 |
| 关键词: | 朱熹 诗经 文学研究 |
内容
一、《周易本义》
涵泳文本、求其本义是朱熹治《诗经》学的根本方法。这一方法又不限于《诗经》一门,实际上,朱熹治一切古籍大抵都能坚持这一方法,而以治《易》尤为典型。朱熹著有《周易本义》一书,从书名自身即可看出其旨趣。朱熹治《易》学,有两样基本主张:一是《易》本为卜筮而作。二是《易》之经传各自为说,不必据传解经。所谓《易》本义即指《易》本为卜筮之书,不是为义理而作。求易本义有两层意义:一是不作义理上的傅会;二是不依传解经。
《汉书·艺文志》云:
《易》曰:“宓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所谓《易》之经即指伏羲与文王所作的部分——卦象及卦爻辞,《易》之传指孔子所作十篇(习惯上称为“十翼”)。关于《周易》经传的形成,自《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说后,易学界一直把《周易》经传看成是周孔之道的体现,认为伏羲画卦,周文王作卦爻辞,孔子作传,三圣之业一脉相承,并无差别。因而对《周易》一书的理解,都依传文义解释经文。由于依传解经,将《周易》一书进一步哲理化,《周易》作为占筮的典籍,其本来的面貌则被湮没了。直到北宋欧阳修提出《系辞》非孔子所作,这种传统的观念才发生动摇。
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下)有云:
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
欧阳修对《易》传的判断与批评和朱熹对《诗序》的批评很相似:朱熹认为《序》非圣人作,依《序》说诗有害于后人对《诗经》的理解;欧阳修认为《易》传(大部分)非圣人作,后人依之解经,“至使害经而惑世”。
在《系辞》作者的这一问题上,朱熹并不赞成欧阳修的说法,仍认为《系辞》为孔子所作,但他对《周易》的理解,却受到欧阳修易说的影响。
关于《周易》经传的形成,朱熹取四圣说,即: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重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传;并认为四圣皆以《周易》为卜筮之书。《朱子语类》有云:
《易》本为卜筮之书……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想当初伏羲化卦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66/1622,甘节记)
朱熹易“三圣说”为“四圣说”的理由是“谓《爻辞》为周公者,盖其中有说文王,不应是文王自说”。(67/1846,叶贺孙记)但有些时候,他又往往将文王说与周公说视作一个整体。朱熹屡屡强调伏羲《易》、文王周公《易》与孔子《易》各自为阵,不宜强为牵合。且看《朱子语类》里的言论:
01 学《易》者须将《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做一意看,不得。(66/1622,辅广记)
02 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66/1630,沈僩记)
03 须是将伏羲画底卦做一样看,文王卦做一样看;文王周公说底《彖》、《象》做一样看,孔子说底做一样看,王辅嗣伊川说底各做一样看。(67/1645,渊记)
朱熹强调伏羲《易》、文王周公《易》与孔子《易》牵合不得,乃是因为其间有不吻合之处,《朱子语类》有云:
01 《乾》之“元亨利贞”,本是筮得此卦,则大亨而利于守正,而《彖辞》、《文言》皆以为是四德。某常疑如此等类,皆是别立说以发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马之贞”,则发得不甚相似矣。(67/1645,杨道夫记)
02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书。(67/1645,廖德明记)
文王卦与伏羲卦已自不同,孔子《十翼》与文王周公卦爻辞又有理解上的分歧,离则双美,合者两伤,故不如各自做一样看。汉至唐的易学家将三者当作一个整体,弥缝于其间,自然难免于牵强。《易》之经传既各自为体,自然不必依传解经。
朱熹屡次强调《易》本卜筮之书,至孔子作《十翼》方始
从义理上着眼,《朱子语类》有云:“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话说!文王重卦作《系辞》,周公作《爻辞》,也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66/1622,辅广记)。朱熹还明确指出孔子说《易》不得易本义,请看《朱子语类》中这一段文字:
据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今人说得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说虽粗,然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某一人说,则晓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用,元未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读伏羲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画八卦,那里有许多文字言语,只是说八个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其大要不出于阴阳刚柔、吉凶消长之理。然亦尝说破,只是使人之卜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今人未曾明得《乾》、《坤》之象,便先说《乾》、《坤》之理,所以说得都无情理。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古人占处说,如卜得《乾卦》,则大亨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要说出来。孔子之心,又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只认各人自说一副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说《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样。某所以不敢从,而原《易》之所以为作而为之说,为此也。(66/1630,沈僩记)
朱熹认为当初伏羲画卦,只是为了卜筮,占卦象之阴阳,卜人事之吉凶,而无关于义理。圣贤如孔子,以义理说《易》,尚且被朱熹说作“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至如后人纷纷以义理说《易》,不顾《易》本卜筮之书的事实,朱熹更是给以严厉批评。其《答吕伯恭》书(见《朱熹集》卷33,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458—1459页)云:“窃疑卦爻之词,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以训诫。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诫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容该贯曲畅旁通之妙。”《朱子语类》亦云:“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做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66/1622,辅广记)。
《朱子语类》又云:
《易》以卜筮用,道理便在里面,但只未说到这处。如《楚辞》以神为君,祀之者为臣,以见其敬奉不可忘之义。固是说君臣,但假托事神而说。今也须与他说事神,然后及他事君之意。今解直去解作事君,也未为不是;但须先为他结了事神一重,方及那处,《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说他本意,便将理来衮说了。(66/1635,林学履记)
据此,是朱熹并不反对根据《易》来说道理,但朱熹强调首先要将《易》作卜筮之书看,就卜筮来探讨其本意。在得其本意之后,再借以说明道理是可以的;但如果没有求本义在先,一上来就大谈义理,则不可取。《楚辞·九歌》是祀神之曲,其本意是讲事神的;必须先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意义上解释诗意,然后才可以作事君的发挥。“今也须与他说事神,然后及他事君之意”,这里的先后至关重要,这实际是承认文本的独立地位具有优先原则。作为理学大师的朱熹,义理是其治学的根本。但在注解经典古籍时,他始终将文本放在第一位,尊重文本的独立性地位,然后才是义理上的发挥。朱熹诗经学实极重视“养心劝惩”、“变化气质”,但在说解《诗三百》文意时,他能始终贯彻“求诗意于辞之中”的原则。汉学诗经学正是缺少了这一个环节,拿义理来直接套文本,忽视了文本的独立性地位。朱熹批评后人依《序》说诗,也正是因为后人将第二位的阐释置于了第一位的《诗三百》文本之上。对《易》来说,经的部分实际可视做文本自身,传的部分则是后人阐释。尽管其阐释者是孔子,是儒家的大圣人,但相对于经作为文本自身的第一性来说,它也只能是第二位的。求易本义,当就经解经,而不当依传解经。所以《朱子语类》说:“《易》本为卜筮之书……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系辞》,是犹不看《刑统》,而看《刑统》之《序例》也,安能晓!今人须以卜筮之书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66/1622,甘节记)。
《朱子语类》颇载朱熹教诲弟子读《易》之法:
01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之《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学者且依故《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矣。(66/1648,李方子记)
02 读《易》之法,先读正经。不晓,则将《彖》、《象》、《系辞》来解。(77/1661,甘节记)
03 看《易》,且将《爻辞》看。理会得后,却看《象辞》。(77/1661,胡泳记)
“先读正经”,“先读本爻”,正如先读《诗经》本文,正是尊重文本独立性,求其意于辞之中的方法。
朱伯崑对朱熹在易学上的贡献有一段很好的概括:
朱熹关于《周易》经传的论述,在易学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从汉朝以来,无论是义理学派还是象数学派,其解易都是经传不分,以传解经,并且将经文部分逐渐哲理化。到宋代易学家将《周易》视为讲哲理的教科书,特别是程氏《易传》,由于突出以义理解易,使《周易》丧失了其本来面貌。而朱熹则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研究《周易》经传,以经为占筮的经典,以传为后来讲义理或哲理的著述,认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脱离筮法解释《周易》,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言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还以这种观点研究了易学的历史。认为从汉易京房到程氏易学,各成一家之言,其解易并非就是《周易》经传之本义,但如其说出一番道理,亦应肯定,不应抛弃。①
我们可以说朱熹《周易本义》不依传解经,同于其《诗集传》不依《序》说诗。反对易学史上的过多义理傅会,亦正如反对毛、郑一派一味以美刺说《诗》。这正可以说明朱熹治经典古籍之学的一贯态度。
二、欧阳修《诗本义》等
求本义实乃有宋学术一大思潮,不独朱熹一人而已。如欧阳修《易童子问》以系辞非孔子作,苏轼、苏辙兄弟对《尚书》等古籍的新注,郑樵《诗辨妄》等书的写作,尽管对旧说之扬弃在程度上或有大小之分,但都能独立思考,求经书本来之面目。宋人对《诗经》的研究,尤能见其求本义之学术风气。
在朱熹之前,宋人之中,以欧阳修、苏辙、郑樵三人在求诗本义上贡献最大。这三个人,郑樵大抵是坚决废《序》的,苏辙仅取《序》之首句,欧阳修虽未有废《序》之论,但在求诗本义的理论建设上功不可没。
先说郑樵。郑樵的很多见解都为朱熹所接受,朱熹在诗经学著作中屡次提及郑樵:
01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80/2076,叶贺孙记)
02 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谥,却傅会作《小序》美刺。(80/2079,吴振记)
03 旧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某近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意自见。(80/2068,余大雅记)
04 先生举郑渔仲之说言:出于朝廷者为《雅》,出于民俗者为《风》。文武之时,周、召之民作者谓之周、召之《风》。东迁之后,王畿之民作者谓之《王风》。(80/2067,钱木之记)
05 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诗集传·郑风·将仲子》)
06 莆田郑氏谓此实淫奔之诗,无关于庄公、叔段之事。(《诗序辨说·郑风·将仲子》)
01、03条是朱熹自言废《序》受郑樵影响;05、06条说明郑樵对“淫诗”早有认识;04条说明朱熹“《国风》里巷歌谣说”亦本于郑樵;02条说明郑樵早已指出《小序》是依谥傅会美刺。凡此四端,皆朱熹诗经学之重要组成,而郑樵已发先声,朱熹亦屡屡称道之。我们甚至可以说,朱熹诗经学之义例基本来自郑樵。在讨论宋代诗经学时,郑樵实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只是郑樵对诗经学的研究不及朱熹系统和专门,其书《诗辨妄》①又亡佚,因此郑樵在诗经学上的影响远不如朱熹,他的一些论断也不得不赖朱熹的征引而得以流传,且有待于朱熹来发扬光大。
苏辙亦著有《诗经集传》,于《诗序》仅取首句。朱熹曾云:“子由《诗解》好处多。”(80/2090,钱木之记),《诗集传》征引苏辙之说亦极多,据曹虹统计共43处②,为征引宋人著作之首。《诗序辨说》亦于《大雅·文王》、《大雅·荡》二篇称引苏辙之说(《诗序辨说·大雅·文王》:“称王改元之说,欧阳公、苏氏、游氏辨之已详。”《诗序辨说·大雅·荡》:“苏氏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以为援证。朱熹称道苏辙,一是因为苏辙文学修养高,解诗有高过前人之处③;二是因为苏辙亦有考史之能④。苏辙于《诗序》仅取首句,也是因为看不惯《序》者太多的傅会穿凿。但朱熹还是嫌他废《序》不够彻底,《朱子语类》云“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80/2074,邵浩记),《诗序辨说》亦不乏专门辩驳苏辙取《序》首句之处,共有4例(附录11)。
附录11:《诗序辨说》专门辩驳苏辙取《序》首句之失例:
01 《周南·汉广》,《诗序辨说》:“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苏氏乃例取其首句,而去其下文,则于此类两失之矣。”
02 《周颂·昊天有成命》,《诗序辨说》:“苏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尝见其不可信之实也。愚于《汉广》之篇已尝论之。”
03 《周颂·执竞》,《诗序辨说》:“苏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时,因从小序之言。此亦以辞害意之失。”
04 《鲁颂·〓宫》,《诗序辨说》:“此诗言庄公之子,又言新庙奕奕,则为僖公修庙之诗明矣。但诗所谓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复周公之土宇耳,非谓其已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误如此,而苏氏信之,何哉?”
《诗序辨说》尚于《周南·桃夭》《周南·兔罝》、《鄘风·桑中》、《小雅·南山有台》4篇直接指出《序》之首句有误。《诗序辨说》卷首有云:“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义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
苏辙大抵相信《序》之首句传自圣人,只是“首句”之后的“续句”之引申发挥,多半是后世陋儒所为,不值得信从。朱熹则认为整个《诗序》,包括《序》的“续句”和“首句”在内,都不合诗本义,都应摒弃。
《朱子语类》云:“欧公《诗本义》亦好。”(80/2090,钱木之记)。朱熹推崇欧阳修,也有文学修养①与考史之能②两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欧阳修对求诗本义的理论建设有巨大贡献。《朱子语类》有云:
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本末》篇。又有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得也无妨。”其论甚好。(80/2089,沈僩)
欧阳修“《诗》之本末”论,为朱熹所激赏。欧阳修谓学者当知《诗》学有此四端: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
《诗本义》(卷十四)云:
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颂;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说;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
这四端,又有本末之分:
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
诗人之意是本,太师之职是末。圣人之志是本,经师之业是末。知其本末,则知学《诗》之主次。其又云:“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太师考其义类,于《诗》本身来说只是后人的一种理解与整理而已。诗人作诗时,又没有和太师商量过,太师的理解未必就是作者之意。今人学《诗》,探求诗人之意才是第一要紧的事;至于太师之类人的解释和整理,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孔子治《诗》,无非是“著其善恶以为劝戒”而已。学者读《诗》,无非是为了增进人格、变化气质,历代经师的繁复解说知不知道也并不要紧。
欧阳修虽未有废《序》的言论,但《诗》之本末的划分于求诗本义有重要意义。既然后来太师的理解未必合于诗人之意,且相对来说是第二位的,其本身的地位就变得次要;既然后世经师解《诗》不过是人自为说,未必合诗人之意,亦未必得圣人之志,那对读者来说也是可有可无的了。欧阳修“《诗》之本末”论一下子将诗本义与“著其善恶以为劝戒”的人格教育功能凸显了出来。“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这二者正是朱
熹诗经学之根本精神!“求诗人之意”,是求其本来面目,合乎朱熹格物之学术门径;“达圣人之志”,是救天下世道人心,是朱熹治学之根本目的。明乎此,则无怪乎朱熹对欧阳修“《诗》之本末”论要击节叹赏了。
三、“本义”溯源
《汉书·艺文志》有云: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这大约是最早提及《诗》“本义”的。但是这里的“本义”有其特定的涵义,与宋人求诗本义的“本义”并不是一回事。这涉及到汉人著述的体例问题,大约有此三端:1、“故训”与“传”之异同;2、“内传”与“外传”之异同;3、“正义”与“旁义”之异同。
《汉志》“咸非其本义”究竟指几家,学界意见不一。颜师古注云:“与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者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之。”王先谦《汉书补注》云:“此谓齐韩二传推演之词,皆非本义,不得其真耳。非并鲁诗言之。鲁最为近者,言齐韩训故亦各有取,惟鲁最优。颜谓三家皆不得谬矣。既不得其真,何言最近乎!”按颜师古的理解,是说鲁、齐、韩三家都不得本义。王先谦则认为仅指齐、韩二家不得本义。辨析其间是非,或当从汉人著述体例入手。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杂考各说·毛诗故训传名义考》云:
汉儒说经,莫不先通诂训。《汉书·扬雄传》言“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故通而已”。《儒林传》言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已”。而《后汉书·桓谭传》亦言谭“遍通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则知诂训与章句有辨。章句者,离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语多傅会,繁而不杀,蔡邕所谓“前儒特为章句者,皆用其意传,非其本旨”,刘勰所谓“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也。诂训则博习古文,通其转注、假借,不烦章解句释,而奥义自辟,班固所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史》、《汉》、《儒林传》皆言鲁申公为《诗训诂》,而《汉书·楚元王传》及《鲁国先贤传》皆言申公始为《诗传》,则知《汉志》所载《鲁故》、《鲁说》者,即《鲁传》也。何休《公羊传注》亦言“传谓诂训”,似故训与传初无甚异。而《汉志》既载《齐后氏故》、《孙氏故》、《韩故》,又载《齐后氏传》、《孙氏传》、《韩内外传》,则训诂与传又自不同。盖散言则故训、传俱可通称,对言则故训与传异,连言故训与分言故、训者又异……盖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引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①
马瑞辰指出“散言则故训、传俱可通称,对言则故训与传异”。汉人固然有“故训”与“传”混称的习惯,但是《汉志》所载却有“辨章学术”的意义在,称“故训”与称“传”,有其体例上的区别。称“故”(诂训)者大抵仅“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称“传”则并引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也就是说“故”的通例是注重词义的训释,仅就经文自身解说大义,一般不做过多的题外发挥;而“传”(章句)的通例则是要对经文作引申发挥,要称引经文以外的东西来阐发经义。“故”的特点是简括清通,“传”则容易傅会穿凿。马瑞辰引前后《汉书》所记扬雄、蔡邕之言行,亦足以说明两汉之交及东汉儒者对二者性质的认识。蔡邕明确指出“章句”多非经本旨。《汉志》于“咸非其本义”句前云“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辨析“咸非其本义”,必须考虑到“训诂”和“传”在体例上的不同。从汉人“故”与“传”体例差异入手,《汉志》所云“咸非其本义”似指齐、韩二家而言。
陈澧《东塾读书记》对先秦、秦汉人著述之内传、外传之分有明确辨析①。陈澧云:“韩非有《解老》篇。复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即《外传》之体。其《解老》即内传。”《韩非子》有《喻老》、《解老》二篇,《喻老》的体例是引古事以明《老子》之理,《解老》篇则是直接阐发《老子》思想。《喻老》是外传体,《解老》是内传体。《外传》之体,可引古事,亦可引古人之言(包括古人之诗),陈澧云“今本《韩诗外传》,有元至正十五年钱惟善序云:‘断章取义,有合于孔门商赐言《诗》之旨。’澧案:孟子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亦外传之体。”又云:“西汉经学,惟《诗》有毛氏、韩氏两家之书,传至今日。读者得知古人内传、外传之体,乃天之未丧斯文也。《直斋书录解题》云‘《韩诗外传》,多记杂说,不专解《诗》,果当时本书否?’(卷二)杭堇浦云‘董生《繁露》、韩婴《外传》,偭背经旨,铺列杂说,是谓畔经。’(《古文百篇序》)此则不知内外传之体矣。”陈澧认为《毛传》与《韩诗外传》正好是内传与外传的典型代表。虽然陈澧批评《直斋书录解题》怀疑《韩诗外传》非当时之书、批评杭世骏说《韩诗外传》畔经。但二家对《韩诗外传》特点的认识却不可移易。“多记杂说,不专解《诗》”、“偭背经旨,铺列杂说”,正是《韩诗外传》的特色。陈澧于此亦有深刻认识,他说:“采杂说,非本义,盖专指《外传》而言。”认为《汉志》所云“咸非其本义”专指《外传》,而“非本义”的标志是“采杂说”。
皮锡瑞论《诗》又有“正义”、“旁义”之分,其《经学通论·诗经》①“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义亦未尽可信”条云:“三家所传近古,而孰为正义、孰为旁义,已莫能定。以为诗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又云三家诗“存于世者,惟《韩诗外传》,而外传亦引诗之体,而非作诗之义。”“正义”指作诗之义,“旁义”指后人引申傅会之说。“正义”、“旁义”与“故”、“传”之体有很大关系,与“内传”、“外传”之体亦有很大关系。引申傅会愈多,则离诗人之意愈远。相对于“故”来说,“传”的引申傅会为多;“故”于“正义”为近,“传”多“旁义”。相对于“内传”来说,“外传”的引申傅会为多,“内传”近于“正义”,“外传”多属“旁义”。
汉人著述,于“故”、“传”、“内传”、“外传”之体有自觉认识,《汉志》著录更是于诸体之分有清醒认识。观其著录《诗经》学著述即可明此理。《汉志》载: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
《鲁故》二十五卷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何者为“故”,何者为“传”,何者为“内传”,何者为“外传”,泾渭分明。《汉志》著录鲁诗,有《鲁故》、《鲁说》,而无《鲁传》,《汉书·儒林传》亦云:“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作文按:《史记·儒林传》云:“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上一“疑”字,或为衍文。)我们知道,《韩诗外传》是采杂说的,齐诗喜言“天人之际”,傅会阴阳五行,惟鲁诗较为质朴简括,而少引申傅会之说。故《汉志》有鲁最为近之之论。
三家诗说,今存者惟有《韩诗外传》。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来看看《韩诗外传》的特色。兹引其卷首第一段于下:
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以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怒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桥褐趋时,当务为急。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曰:“夙夜在公,实命不同。”
这一段文字,在结构上包括一个故事和《诗经》的两句(姑且称为“断章”)。但我们很难说这是引事以明《诗》。在这个结构中,《诗》之断章已经脱离原诗,不再是原诗的一个有机组成;它已是新的文本结构的一个部分,为新的文本服务。《韩诗外传》的作者在这里用这两句,是“断章取义”的态度,仅取这断章含有的某一种意思,而非其原诗的意思。在这里,这一断章与这一故事,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断章的义实际受这个要说的道理制约。“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出自《召南·小星》。因文献不存,我们无法知道韩诗对这一篇篇义的确切理解。但无论如何,绝不会理解成是写曾子的。这里的故事,是引事以明义;这里的诗,是引《诗》以明义。《韩诗外传》作者本人所要表达的义才是第一位的,至于诗之原义(作诗之义)已经在新的结构中被消解。《直斋书录解题》云《韩诗外传》“不专解《诗》”,诚为有见。
徐复观对《韩诗外传》的特点与性质有很好的概括:
他(韩婴)在《外传》中,共引用《荀子》凡五十四次,其深受《荀子》的影响,可无疑问。即《外传》表达的形式,除继承《春秋》以事明义的传统外,更将所述之事与《诗》结合起来,而成为事与《诗》的结合,实即史与诗互相证成的特殊形式,亦由《荀子》发展而来。……《韩诗外传》,未引《诗》作结者仅二十八处,而此二十八处,可推定为文字的残缺。其引诗作结时,也多援用《荀子》所用的格式。……《韩诗外传》,乃韩婴以前言往行的故事,发明《诗》的微言大义之书。此时,《诗》与故事的结合,皆是象征层次上的结合。……韩氏乃直承孔门“诗教”,并不否定其本义,但不仅在本义上说《诗》,使《诗》发挥更大的教育意义。①
徐复观指出《韩诗外传》受《荀子》影响,乃是用引古事与引《诗》相结合的方法来说明道理。于《诗》而言,它“不仅在本义上说《诗》”,而且要“发明《诗》的微言大义”。这样看来,《韩诗外传》在性质上同于一般子书,解经只是门面话,阐明自己的义理才是其目的。这样一来,自难逃《汉志》非诗本义之讥。
《汉志》言齐韩二家诗传“咸非其本义”的特定语境是汉人的著述体例,主要是从“故”与“传”、“内传”与“外传”、“正义”与“旁义”的差异性着眼。《汉志》所言的“本义”是与“引申义”相对而言的。齐、韩二家或主于阴阳五行,或受《荀子》等子书影响,多是在“引申义”的层面上说《诗》,故“咸非其本义”。相对来说,鲁诗(《鲁故》)较少在“引申义”的层面上说《诗》,故“最为近之”。从著述体例着眼,根据是否在“引申义”层面上说《诗》,在《汉志》的立场,毛诗恐怕当属得其本义,或者较鲁诗更近本义的。
林叶连云:
班固谓西汉诗经学有齐、鲁、韩、毛四家。但因齐、鲁、韩诗于两汉皆立于学官,宛若诗学正宗,故班氏奉命撰《汉书》,便专就齐、鲁、韩三家,较其优劣,而不评毛诗。只在文末附带提及毛诗。班氏所言“自谓子夏所传”,“自谓”也者,其涵义为“非官方说法”,而非微辞。盖班氏所撰者,官书也,立于官方立场以发言,乃理所当然。总之,《汉志》非但未尝丝毫褒贬、评价毛诗,反而谓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成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此方为贬辞。①
林叶连所言,实不无道理。班固之世,古文经学地位上升,况且《汉志》本于刘歆《七略》,其对古文学派的毛诗给以认同,亦在情理之中。毛诗的著述体例是“但明训诂”,每篇有一极短小的序隐括诗义,很少作“引申义”层面上的发挥。用“故”和“传”的著述体例来区分,毛诗的体例属“故”;用“内传”和“外传”来区分,其性质又属“内传”;用“正义”和“旁义”来区分,其所言属“正义”。
需要特地指出的是:宋人所说的“本义”并不是汉人(《汉志》)说的“本义”,此“本义”非彼“本义”也。《汉志》说的“本义”是从著述体例的角度着眼,朱熹等人说的“本义”则是从辞与意的关系这一角度着眼。《汉志》之所以认为齐、韩二家诗“非其本义”,乃是因为它们属“传”体,而且是偏于“外传”体,多言“旁义”;《汉志》言鲁诗“最为近之”,是因为鲁诗(《鲁故》)属“故”体,多言“正义”。毛诗著述体例为“故”体和“内传”体,所言亦为“正义”。从《汉志》的立场,可以类推出毛诗最近本义之一结论。但是宋人求诗本义的对立面却恰恰正是毛诗(当然也是因为其时三家诗仅存《韩诗外传》,而其内容又不专解《诗》)。在朱熹等人看来,毛诗是不得“本义”的。朱熹所说的“本义”基本等同于“辞意”。尽管汉人(《汉志》)和朱熹所理解的“本义”都指“作者之义”,但他们对“作者之义”的认识实有本质差别。以毛、郑为代表的汉学一派从来不认为自己的阐释是背离“作者之义”的,他们认为“作者之义”即是他们所理解的诗义。他们认为,《诗》“作者之义”必有政治讽喻义,并不就是文本字面上的意思(“辞意”)。但在朱熹的立场,毛、郑一派所理解的诗义多属穿凿傅会,而从“辞意”才能求得真正的“作者之意”。
《汉志》所言之“本义”与宋人所理解的“本义”,在语境和涵义上有很大不同,更不是宋人求诗本义的源头。宋人所求之“本义”或来自禅宗。我们知道,南禅(以六祖惠能《坛经》为标志)的出现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南禅鼓吹“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摆脱历来佛经注疏的束缚,而倡独立思考、自证自悟之大旗。其怀疑精神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对宋明理学在学理建设上实有重大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南禅与宋人求经典本义之间的相似性:南禅所要求的是佛性,历来的佛经注疏都是后人对佛性的一种阐释,惠能主张摆脱后人阐释的束缚,而将思考直接指向佛性自身;朱熹所要求的是诗本义,《序》、《传》、《笺》、《疏》等都只是后人对诗义的一种阐释,朱熹力主废《序》,而于《诗》辞之中求其本义。南禅有“第一义”、“第二义”之分;欧阳修倡“《诗》有本末”论,为朱熹所激赏。南禅重自证自悟;朱熹教人读《诗》贵“涵泳”。这些相似性无不说明宋人求经典本义的思考方法实受南禅之影响。
自中唐南禅兴起以来,怀疑精神与独立思考对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壮大,至宋时已成时代之普遍风气。故宋儒对待经典文献之态度实与前人大异,其精英人物大抵能摆脱汉唐注疏之束缚,而求其本义于经文之中。仅就诗经学而言,朱熹之前,欧阳修、苏辙、郑樵等人已有此种精神。朱熹生逢其时,得风云之际会,总有宋一代诗经学之大成。
涵泳文本、求其本义是朱熹治《诗经》学的根本方法。这一方法又不限于《诗经》一门,实际上,朱熹治一切古籍大抵都能坚持这一方法,而以治《易》尤为典型。朱熹著有《周易本义》一书,从书名自身即可看出其旨趣。朱熹治《易》学,有两样基本主张:一是《易》本为卜筮而作。二是《易》之经传各自为说,不必据传解经。所谓《易》本义即指《易》本为卜筮之书,不是为义理而作。求易本义有两层意义:一是不作义理上的傅会;二是不依传解经。
《汉书·艺文志》云:
《易》曰:“宓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所谓《易》之经即指伏羲与文王所作的部分——卦象及卦爻辞,《易》之传指孔子所作十篇(习惯上称为“十翼”)。关于《周易》经传的形成,自《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说后,易学界一直把《周易》经传看成是周孔之道的体现,认为伏羲画卦,周文王作卦爻辞,孔子作传,三圣之业一脉相承,并无差别。因而对《周易》一书的理解,都依传文义解释经文。由于依传解经,将《周易》一书进一步哲理化,《周易》作为占筮的典籍,其本来的面貌则被湮没了。直到北宋欧阳修提出《系辞》非孔子所作,这种传统的观念才发生动摇。
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下)有云:
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
欧阳修对《易》传的判断与批评和朱熹对《诗序》的批评很相似:朱熹认为《序》非圣人作,依《序》说诗有害于后人对《诗经》的理解;欧阳修认为《易》传(大部分)非圣人作,后人依之解经,“至使害经而惑世”。
在《系辞》作者的这一问题上,朱熹并不赞成欧阳修的说法,仍认为《系辞》为孔子所作,但他对《周易》的理解,却受到欧阳修易说的影响。
关于《周易》经传的形成,朱熹取四圣说,即: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重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传;并认为四圣皆以《周易》为卜筮之书。《朱子语类》有云:
《易》本为卜筮之书……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想当初伏羲化卦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66/1622,甘节记)
朱熹易“三圣说”为“四圣说”的理由是“谓《爻辞》为周公者,盖其中有说文王,不应是文王自说”。(67/1846,叶贺孙记)但有些时候,他又往往将文王说与周公说视作一个整体。朱熹屡屡强调伏羲《易》、文王周公《易》与孔子《易》各自为阵,不宜强为牵合。且看《朱子语类》里的言论:
01 学《易》者须将《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做一意看,不得。(66/1622,辅广记)
02 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66/1630,沈僩记)
03 须是将伏羲画底卦做一样看,文王卦做一样看;文王周公说底《彖》、《象》做一样看,孔子说底做一样看,王辅嗣伊川说底各做一样看。(67/1645,渊记)
朱熹强调伏羲《易》、文王周公《易》与孔子《易》牵合不得,乃是因为其间有不吻合之处,《朱子语类》有云:
01 《乾》之“元亨利贞”,本是筮得此卦,则大亨而利于守正,而《彖辞》、《文言》皆以为是四德。某常疑如此等类,皆是别立说以发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马之贞”,则发得不甚相似矣。(67/1645,杨道夫记)
02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书。(67/1645,廖德明记)
文王卦与伏羲卦已自不同,孔子《十翼》与文王周公卦爻辞又有理解上的分歧,离则双美,合者两伤,故不如各自做一样看。汉至唐的易学家将三者当作一个整体,弥缝于其间,自然难免于牵强。《易》之经传既各自为体,自然不必依传解经。
朱熹屡次强调《易》本卜筮之书,至孔子作《十翼》方始
从义理上着眼,《朱子语类》有云:“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话说!文王重卦作《系辞》,周公作《爻辞》,也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66/1622,辅广记)。朱熹还明确指出孔子说《易》不得易本义,请看《朱子语类》中这一段文字:
据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今人说得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说虽粗,然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某一人说,则晓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用,元未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读伏羲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画八卦,那里有许多文字言语,只是说八个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其大要不出于阴阳刚柔、吉凶消长之理。然亦尝说破,只是使人之卜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今人未曾明得《乾》、《坤》之象,便先说《乾》、《坤》之理,所以说得都无情理。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古人占处说,如卜得《乾卦》,则大亨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要说出来。孔子之心,又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只认各人自说一副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说《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样。某所以不敢从,而原《易》之所以为作而为之说,为此也。(66/1630,沈僩记)
朱熹认为当初伏羲画卦,只是为了卜筮,占卦象之阴阳,卜人事之吉凶,而无关于义理。圣贤如孔子,以义理说《易》,尚且被朱熹说作“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至如后人纷纷以义理说《易》,不顾《易》本卜筮之书的事实,朱熹更是给以严厉批评。其《答吕伯恭》书(见《朱熹集》卷33,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458—1459页)云:“窃疑卦爻之词,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以训诫。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诫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容该贯曲畅旁通之妙。”《朱子语类》亦云:“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做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66/1622,辅广记)。
《朱子语类》又云:
《易》以卜筮用,道理便在里面,但只未说到这处。如《楚辞》以神为君,祀之者为臣,以见其敬奉不可忘之义。固是说君臣,但假托事神而说。今也须与他说事神,然后及他事君之意。今解直去解作事君,也未为不是;但须先为他结了事神一重,方及那处,《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说他本意,便将理来衮说了。(66/1635,林学履记)
据此,是朱熹并不反对根据《易》来说道理,但朱熹强调首先要将《易》作卜筮之书看,就卜筮来探讨其本意。在得其本意之后,再借以说明道理是可以的;但如果没有求本义在先,一上来就大谈义理,则不可取。《楚辞·九歌》是祀神之曲,其本意是讲事神的;必须先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意义上解释诗意,然后才可以作事君的发挥。“今也须与他说事神,然后及他事君之意”,这里的先后至关重要,这实际是承认文本的独立地位具有优先原则。作为理学大师的朱熹,义理是其治学的根本。但在注解经典古籍时,他始终将文本放在第一位,尊重文本的独立性地位,然后才是义理上的发挥。朱熹诗经学实极重视“养心劝惩”、“变化气质”,但在说解《诗三百》文意时,他能始终贯彻“求诗意于辞之中”的原则。汉学诗经学正是缺少了这一个环节,拿义理来直接套文本,忽视了文本的独立性地位。朱熹批评后人依《序》说诗,也正是因为后人将第二位的阐释置于了第一位的《诗三百》文本之上。对《易》来说,经的部分实际可视做文本自身,传的部分则是后人阐释。尽管其阐释者是孔子,是儒家的大圣人,但相对于经作为文本自身的第一性来说,它也只能是第二位的。求易本义,当就经解经,而不当依传解经。所以《朱子语类》说:“《易》本为卜筮之书……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系辞》,是犹不看《刑统》,而看《刑统》之《序例》也,安能晓!今人须以卜筮之书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66/1622,甘节记)。
《朱子语类》颇载朱熹教诲弟子读《易》之法:
01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之《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学者且依故《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矣。(66/1648,李方子记)
02 读《易》之法,先读正经。不晓,则将《彖》、《象》、《系辞》来解。(77/1661,甘节记)
03 看《易》,且将《爻辞》看。理会得后,却看《象辞》。(77/1661,胡泳记)
“先读正经”,“先读本爻”,正如先读《诗经》本文,正是尊重文本独立性,求其意于辞之中的方法。
朱伯崑对朱熹在易学上的贡献有一段很好的概括:
朱熹关于《周易》经传的论述,在易学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从汉朝以来,无论是义理学派还是象数学派,其解易都是经传不分,以传解经,并且将经文部分逐渐哲理化。到宋代易学家将《周易》视为讲哲理的教科书,特别是程氏《易传》,由于突出以义理解易,使《周易》丧失了其本来面貌。而朱熹则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研究《周易》经传,以经为占筮的经典,以传为后来讲义理或哲理的著述,认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脱离筮法解释《周易》,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言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还以这种观点研究了易学的历史。认为从汉易京房到程氏易学,各成一家之言,其解易并非就是《周易》经传之本义,但如其说出一番道理,亦应肯定,不应抛弃。①
我们可以说朱熹《周易本义》不依传解经,同于其《诗集传》不依《序》说诗。反对易学史上的过多义理傅会,亦正如反对毛、郑一派一味以美刺说《诗》。这正可以说明朱熹治经典古籍之学的一贯态度。
二、欧阳修《诗本义》等
求本义实乃有宋学术一大思潮,不独朱熹一人而已。如欧阳修《易童子问》以系辞非孔子作,苏轼、苏辙兄弟对《尚书》等古籍的新注,郑樵《诗辨妄》等书的写作,尽管对旧说之扬弃在程度上或有大小之分,但都能独立思考,求经书本来之面目。宋人对《诗经》的研究,尤能见其求本义之学术风气。
在朱熹之前,宋人之中,以欧阳修、苏辙、郑樵三人在求诗本义上贡献最大。这三个人,郑樵大抵是坚决废《序》的,苏辙仅取《序》之首句,欧阳修虽未有废《序》之论,但在求诗本义的理论建设上功不可没。
先说郑樵。郑樵的很多见解都为朱熹所接受,朱熹在诗经学著作中屡次提及郑樵:
01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80/2076,叶贺孙记)
02 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谥,却傅会作《小序》美刺。(80/2079,吴振记)
03 旧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某近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意自见。(80/2068,余大雅记)
04 先生举郑渔仲之说言:出于朝廷者为《雅》,出于民俗者为《风》。文武之时,周、召之民作者谓之周、召之《风》。东迁之后,王畿之民作者谓之《王风》。(80/2067,钱木之记)
05 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诗集传·郑风·将仲子》)
06 莆田郑氏谓此实淫奔之诗,无关于庄公、叔段之事。(《诗序辨说·郑风·将仲子》)
01、03条是朱熹自言废《序》受郑樵影响;05、06条说明郑樵对“淫诗”早有认识;04条说明朱熹“《国风》里巷歌谣说”亦本于郑樵;02条说明郑樵早已指出《小序》是依谥傅会美刺。凡此四端,皆朱熹诗经学之重要组成,而郑樵已发先声,朱熹亦屡屡称道之。我们甚至可以说,朱熹诗经学之义例基本来自郑樵。在讨论宋代诗经学时,郑樵实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只是郑樵对诗经学的研究不及朱熹系统和专门,其书《诗辨妄》①又亡佚,因此郑樵在诗经学上的影响远不如朱熹,他的一些论断也不得不赖朱熹的征引而得以流传,且有待于朱熹来发扬光大。
苏辙亦著有《诗经集传》,于《诗序》仅取首句。朱熹曾云:“子由《诗解》好处多。”(80/2090,钱木之记),《诗集传》征引苏辙之说亦极多,据曹虹统计共43处②,为征引宋人著作之首。《诗序辨说》亦于《大雅·文王》、《大雅·荡》二篇称引苏辙之说(《诗序辨说·大雅·文王》:“称王改元之说,欧阳公、苏氏、游氏辨之已详。”《诗序辨说·大雅·荡》:“苏氏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以为援证。朱熹称道苏辙,一是因为苏辙文学修养高,解诗有高过前人之处③;二是因为苏辙亦有考史之能④。苏辙于《诗序》仅取首句,也是因为看不惯《序》者太多的傅会穿凿。但朱熹还是嫌他废《序》不够彻底,《朱子语类》云“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80/2074,邵浩记),《诗序辨说》亦不乏专门辩驳苏辙取《序》首句之处,共有4例(附录11)。
附录11:《诗序辨说》专门辩驳苏辙取《序》首句之失例:
01 《周南·汉广》,《诗序辨说》:“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苏氏乃例取其首句,而去其下文,则于此类两失之矣。”
02 《周颂·昊天有成命》,《诗序辨说》:“苏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尝见其不可信之实也。愚于《汉广》之篇已尝论之。”
03 《周颂·执竞》,《诗序辨说》:“苏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时,因从小序之言。此亦以辞害意之失。”
04 《鲁颂·〓宫》,《诗序辨说》:“此诗言庄公之子,又言新庙奕奕,则为僖公修庙之诗明矣。但诗所谓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复周公之土宇耳,非谓其已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误如此,而苏氏信之,何哉?”
《诗序辨说》尚于《周南·桃夭》《周南·兔罝》、《鄘风·桑中》、《小雅·南山有台》4篇直接指出《序》之首句有误。《诗序辨说》卷首有云:“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义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
苏辙大抵相信《序》之首句传自圣人,只是“首句”之后的“续句”之引申发挥,多半是后世陋儒所为,不值得信从。朱熹则认为整个《诗序》,包括《序》的“续句”和“首句”在内,都不合诗本义,都应摒弃。
《朱子语类》云:“欧公《诗本义》亦好。”(80/2090,钱木之记)。朱熹推崇欧阳修,也有文学修养①与考史之能②两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欧阳修对求诗本义的理论建设有巨大贡献。《朱子语类》有云:
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本末》篇。又有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得也无妨。”其论甚好。(80/2089,沈僩)
欧阳修“《诗》之本末”论,为朱熹所激赏。欧阳修谓学者当知《诗》学有此四端: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
《诗本义》(卷十四)云:
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颂;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说;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
这四端,又有本末之分:
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
诗人之意是本,太师之职是末。圣人之志是本,经师之业是末。知其本末,则知学《诗》之主次。其又云:“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太师考其义类,于《诗》本身来说只是后人的一种理解与整理而已。诗人作诗时,又没有和太师商量过,太师的理解未必就是作者之意。今人学《诗》,探求诗人之意才是第一要紧的事;至于太师之类人的解释和整理,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孔子治《诗》,无非是“著其善恶以为劝戒”而已。学者读《诗》,无非是为了增进人格、变化气质,历代经师的繁复解说知不知道也并不要紧。
欧阳修虽未有废《序》的言论,但《诗》之本末的划分于求诗本义有重要意义。既然后来太师的理解未必合于诗人之意,且相对来说是第二位的,其本身的地位就变得次要;既然后世经师解《诗》不过是人自为说,未必合诗人之意,亦未必得圣人之志,那对读者来说也是可有可无的了。欧阳修“《诗》之本末”论一下子将诗本义与“著其善恶以为劝戒”的人格教育功能凸显了出来。“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这二者正是朱
熹诗经学之根本精神!“求诗人之意”,是求其本来面目,合乎朱熹格物之学术门径;“达圣人之志”,是救天下世道人心,是朱熹治学之根本目的。明乎此,则无怪乎朱熹对欧阳修“《诗》之本末”论要击节叹赏了。
三、“本义”溯源
《汉书·艺文志》有云: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这大约是最早提及《诗》“本义”的。但是这里的“本义”有其特定的涵义,与宋人求诗本义的“本义”并不是一回事。这涉及到汉人著述的体例问题,大约有此三端:1、“故训”与“传”之异同;2、“内传”与“外传”之异同;3、“正义”与“旁义”之异同。
《汉志》“咸非其本义”究竟指几家,学界意见不一。颜师古注云:“与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者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之。”王先谦《汉书补注》云:“此谓齐韩二传推演之词,皆非本义,不得其真耳。非并鲁诗言之。鲁最为近者,言齐韩训故亦各有取,惟鲁最优。颜谓三家皆不得谬矣。既不得其真,何言最近乎!”按颜师古的理解,是说鲁、齐、韩三家都不得本义。王先谦则认为仅指齐、韩二家不得本义。辨析其间是非,或当从汉人著述体例入手。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杂考各说·毛诗故训传名义考》云:
汉儒说经,莫不先通诂训。《汉书·扬雄传》言“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故通而已”。《儒林传》言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已”。而《后汉书·桓谭传》亦言谭“遍通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则知诂训与章句有辨。章句者,离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语多傅会,繁而不杀,蔡邕所谓“前儒特为章句者,皆用其意传,非其本旨”,刘勰所谓“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也。诂训则博习古文,通其转注、假借,不烦章解句释,而奥义自辟,班固所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史》、《汉》、《儒林传》皆言鲁申公为《诗训诂》,而《汉书·楚元王传》及《鲁国先贤传》皆言申公始为《诗传》,则知《汉志》所载《鲁故》、《鲁说》者,即《鲁传》也。何休《公羊传注》亦言“传谓诂训”,似故训与传初无甚异。而《汉志》既载《齐后氏故》、《孙氏故》、《韩故》,又载《齐后氏传》、《孙氏传》、《韩内外传》,则训诂与传又自不同。盖散言则故训、传俱可通称,对言则故训与传异,连言故训与分言故、训者又异……盖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引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①
马瑞辰指出“散言则故训、传俱可通称,对言则故训与传异”。汉人固然有“故训”与“传”混称的习惯,但是《汉志》所载却有“辨章学术”的意义在,称“故训”与称“传”,有其体例上的区别。称“故”(诂训)者大抵仅“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称“传”则并引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也就是说“故”的通例是注重词义的训释,仅就经文自身解说大义,一般不做过多的题外发挥;而“传”(章句)的通例则是要对经文作引申发挥,要称引经文以外的东西来阐发经义。“故”的特点是简括清通,“传”则容易傅会穿凿。马瑞辰引前后《汉书》所记扬雄、蔡邕之言行,亦足以说明两汉之交及东汉儒者对二者性质的认识。蔡邕明确指出“章句”多非经本旨。《汉志》于“咸非其本义”句前云“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辨析“咸非其本义”,必须考虑到“训诂”和“传”在体例上的不同。从汉人“故”与“传”体例差异入手,《汉志》所云“咸非其本义”似指齐、韩二家而言。
陈澧《东塾读书记》对先秦、秦汉人著述之内传、外传之分有明确辨析①。陈澧云:“韩非有《解老》篇。复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即《外传》之体。其《解老》即内传。”《韩非子》有《喻老》、《解老》二篇,《喻老》的体例是引古事以明《老子》之理,《解老》篇则是直接阐发《老子》思想。《喻老》是外传体,《解老》是内传体。《外传》之体,可引古事,亦可引古人之言(包括古人之诗),陈澧云“今本《韩诗外传》,有元至正十五年钱惟善序云:‘断章取义,有合于孔门商赐言《诗》之旨。’澧案:孟子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亦外传之体。”又云:“西汉经学,惟《诗》有毛氏、韩氏两家之书,传至今日。读者得知古人内传、外传之体,乃天之未丧斯文也。《直斋书录解题》云‘《韩诗外传》,多记杂说,不专解《诗》,果当时本书否?’(卷二)杭堇浦云‘董生《繁露》、韩婴《外传》,偭背经旨,铺列杂说,是谓畔经。’(《古文百篇序》)此则不知内外传之体矣。”陈澧认为《毛传》与《韩诗外传》正好是内传与外传的典型代表。虽然陈澧批评《直斋书录解题》怀疑《韩诗外传》非当时之书、批评杭世骏说《韩诗外传》畔经。但二家对《韩诗外传》特点的认识却不可移易。“多记杂说,不专解《诗》”、“偭背经旨,铺列杂说”,正是《韩诗外传》的特色。陈澧于此亦有深刻认识,他说:“采杂说,非本义,盖专指《外传》而言。”认为《汉志》所云“咸非其本义”专指《外传》,而“非本义”的标志是“采杂说”。
皮锡瑞论《诗》又有“正义”、“旁义”之分,其《经学通论·诗经》①“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义亦未尽可信”条云:“三家所传近古,而孰为正义、孰为旁义,已莫能定。以为诗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又云三家诗“存于世者,惟《韩诗外传》,而外传亦引诗之体,而非作诗之义。”“正义”指作诗之义,“旁义”指后人引申傅会之说。“正义”、“旁义”与“故”、“传”之体有很大关系,与“内传”、“外传”之体亦有很大关系。引申傅会愈多,则离诗人之意愈远。相对于“故”来说,“传”的引申傅会为多;“故”于“正义”为近,“传”多“旁义”。相对于“内传”来说,“外传”的引申傅会为多,“内传”近于“正义”,“外传”多属“旁义”。
汉人著述,于“故”、“传”、“内传”、“外传”之体有自觉认识,《汉志》著录更是于诸体之分有清醒认识。观其著录《诗经》学著述即可明此理。《汉志》载: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
《鲁故》二十五卷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何者为“故”,何者为“传”,何者为“内传”,何者为“外传”,泾渭分明。《汉志》著录鲁诗,有《鲁故》、《鲁说》,而无《鲁传》,《汉书·儒林传》亦云:“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作文按:《史记·儒林传》云:“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上一“疑”字,或为衍文。)我们知道,《韩诗外传》是采杂说的,齐诗喜言“天人之际”,傅会阴阳五行,惟鲁诗较为质朴简括,而少引申傅会之说。故《汉志》有鲁最为近之之论。
三家诗说,今存者惟有《韩诗外传》。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来看看《韩诗外传》的特色。兹引其卷首第一段于下:
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以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怒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桥褐趋时,当务为急。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曰:“夙夜在公,实命不同。”
这一段文字,在结构上包括一个故事和《诗经》的两句(姑且称为“断章”)。但我们很难说这是引事以明《诗》。在这个结构中,《诗》之断章已经脱离原诗,不再是原诗的一个有机组成;它已是新的文本结构的一个部分,为新的文本服务。《韩诗外传》的作者在这里用这两句,是“断章取义”的态度,仅取这断章含有的某一种意思,而非其原诗的意思。在这里,这一断章与这一故事,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断章的义实际受这个要说的道理制约。“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出自《召南·小星》。因文献不存,我们无法知道韩诗对这一篇篇义的确切理解。但无论如何,绝不会理解成是写曾子的。这里的故事,是引事以明义;这里的诗,是引《诗》以明义。《韩诗外传》作者本人所要表达的义才是第一位的,至于诗之原义(作诗之义)已经在新的结构中被消解。《直斋书录解题》云《韩诗外传》“不专解《诗》”,诚为有见。
徐复观对《韩诗外传》的特点与性质有很好的概括:
他(韩婴)在《外传》中,共引用《荀子》凡五十四次,其深受《荀子》的影响,可无疑问。即《外传》表达的形式,除继承《春秋》以事明义的传统外,更将所述之事与《诗》结合起来,而成为事与《诗》的结合,实即史与诗互相证成的特殊形式,亦由《荀子》发展而来。……《韩诗外传》,未引《诗》作结者仅二十八处,而此二十八处,可推定为文字的残缺。其引诗作结时,也多援用《荀子》所用的格式。……《韩诗外传》,乃韩婴以前言往行的故事,发明《诗》的微言大义之书。此时,《诗》与故事的结合,皆是象征层次上的结合。……韩氏乃直承孔门“诗教”,并不否定其本义,但不仅在本义上说《诗》,使《诗》发挥更大的教育意义。①
徐复观指出《韩诗外传》受《荀子》影响,乃是用引古事与引《诗》相结合的方法来说明道理。于《诗》而言,它“不仅在本义上说《诗》”,而且要“发明《诗》的微言大义”。这样看来,《韩诗外传》在性质上同于一般子书,解经只是门面话,阐明自己的义理才是其目的。这样一来,自难逃《汉志》非诗本义之讥。
《汉志》言齐韩二家诗传“咸非其本义”的特定语境是汉人的著述体例,主要是从“故”与“传”、“内传”与“外传”、“正义”与“旁义”的差异性着眼。《汉志》所言的“本义”是与“引申义”相对而言的。齐、韩二家或主于阴阳五行,或受《荀子》等子书影响,多是在“引申义”的层面上说《诗》,故“咸非其本义”。相对来说,鲁诗(《鲁故》)较少在“引申义”的层面上说《诗》,故“最为近之”。从著述体例着眼,根据是否在“引申义”层面上说《诗》,在《汉志》的立场,毛诗恐怕当属得其本义,或者较鲁诗更近本义的。
林叶连云:
班固谓西汉诗经学有齐、鲁、韩、毛四家。但因齐、鲁、韩诗于两汉皆立于学官,宛若诗学正宗,故班氏奉命撰《汉书》,便专就齐、鲁、韩三家,较其优劣,而不评毛诗。只在文末附带提及毛诗。班氏所言“自谓子夏所传”,“自谓”也者,其涵义为“非官方说法”,而非微辞。盖班氏所撰者,官书也,立于官方立场以发言,乃理所当然。总之,《汉志》非但未尝丝毫褒贬、评价毛诗,反而谓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成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此方为贬辞。①
林叶连所言,实不无道理。班固之世,古文经学地位上升,况且《汉志》本于刘歆《七略》,其对古文学派的毛诗给以认同,亦在情理之中。毛诗的著述体例是“但明训诂”,每篇有一极短小的序隐括诗义,很少作“引申义”层面上的发挥。用“故”和“传”的著述体例来区分,毛诗的体例属“故”;用“内传”和“外传”来区分,其性质又属“内传”;用“正义”和“旁义”来区分,其所言属“正义”。
需要特地指出的是:宋人所说的“本义”并不是汉人(《汉志》)说的“本义”,此“本义”非彼“本义”也。《汉志》说的“本义”是从著述体例的角度着眼,朱熹等人说的“本义”则是从辞与意的关系这一角度着眼。《汉志》之所以认为齐、韩二家诗“非其本义”,乃是因为它们属“传”体,而且是偏于“外传”体,多言“旁义”;《汉志》言鲁诗“最为近之”,是因为鲁诗(《鲁故》)属“故”体,多言“正义”。毛诗著述体例为“故”体和“内传”体,所言亦为“正义”。从《汉志》的立场,可以类推出毛诗最近本义之一结论。但是宋人求诗本义的对立面却恰恰正是毛诗(当然也是因为其时三家诗仅存《韩诗外传》,而其内容又不专解《诗》)。在朱熹等人看来,毛诗是不得“本义”的。朱熹所说的“本义”基本等同于“辞意”。尽管汉人(《汉志》)和朱熹所理解的“本义”都指“作者之义”,但他们对“作者之义”的认识实有本质差别。以毛、郑为代表的汉学一派从来不认为自己的阐释是背离“作者之义”的,他们认为“作者之义”即是他们所理解的诗义。他们认为,《诗》“作者之义”必有政治讽喻义,并不就是文本字面上的意思(“辞意”)。但在朱熹的立场,毛、郑一派所理解的诗义多属穿凿傅会,而从“辞意”才能求得真正的“作者之意”。
《汉志》所言之“本义”与宋人所理解的“本义”,在语境和涵义上有很大不同,更不是宋人求诗本义的源头。宋人所求之“本义”或来自禅宗。我们知道,南禅(以六祖惠能《坛经》为标志)的出现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南禅鼓吹“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摆脱历来佛经注疏的束缚,而倡独立思考、自证自悟之大旗。其怀疑精神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对宋明理学在学理建设上实有重大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南禅与宋人求经典本义之间的相似性:南禅所要求的是佛性,历来的佛经注疏都是后人对佛性的一种阐释,惠能主张摆脱后人阐释的束缚,而将思考直接指向佛性自身;朱熹所要求的是诗本义,《序》、《传》、《笺》、《疏》等都只是后人对诗义的一种阐释,朱熹力主废《序》,而于《诗》辞之中求其本义。南禅有“第一义”、“第二义”之分;欧阳修倡“《诗》有本末”论,为朱熹所激赏。南禅重自证自悟;朱熹教人读《诗》贵“涵泳”。这些相似性无不说明宋人求经典本义的思考方法实受南禅之影响。
自中唐南禅兴起以来,怀疑精神与独立思考对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壮大,至宋时已成时代之普遍风气。故宋儒对待经典文献之态度实与前人大异,其精英人物大抵能摆脱汉唐注疏之束缚,而求其本义于经文之中。仅就诗经学而言,朱熹之前,欧阳修、苏辙、郑樵等人已有此种精神。朱熹生逢其时,得风云之际会,总有宋一代诗经学之大成。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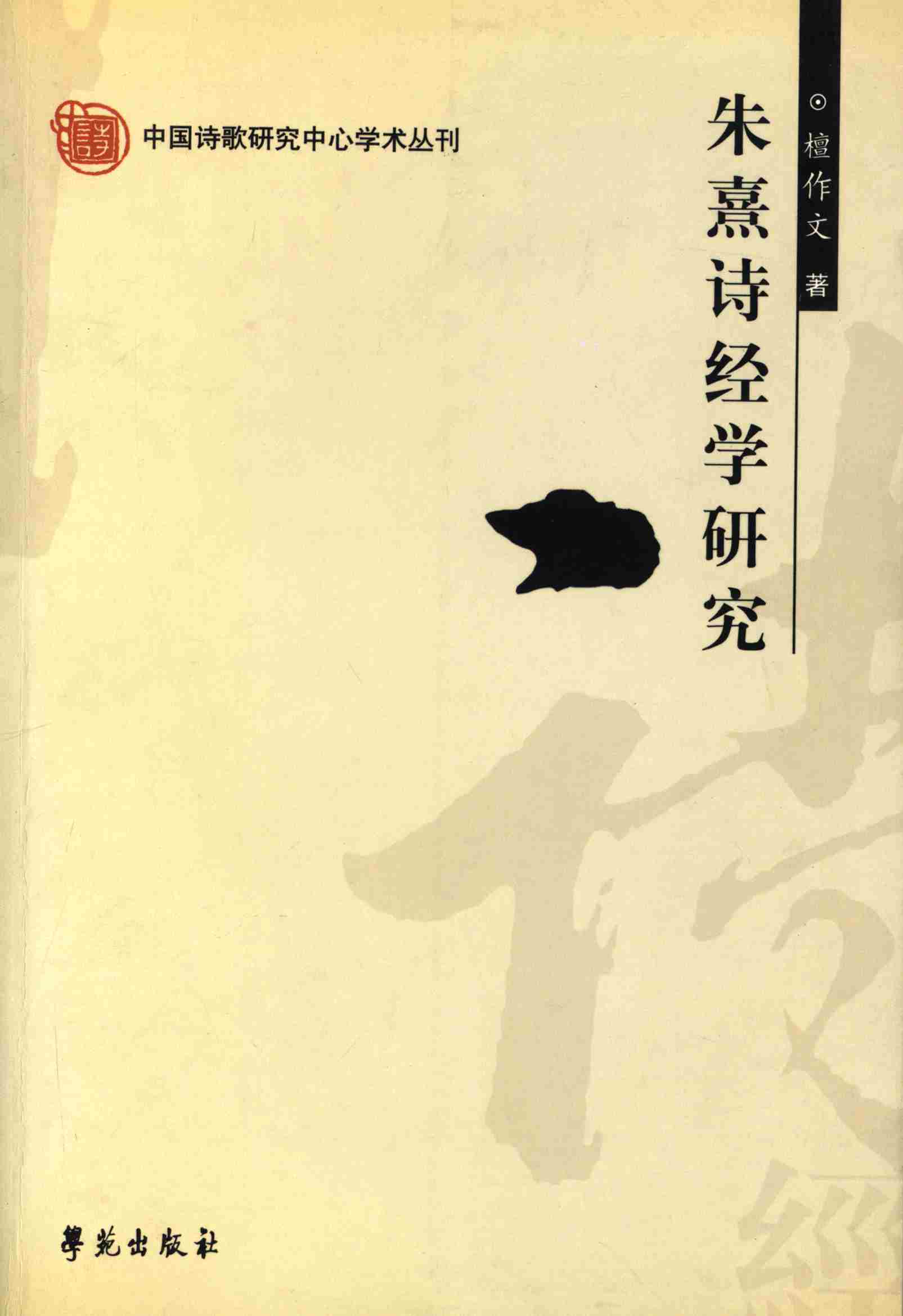
《朱熹诗经学研究》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本书为南宋朱熹诗词作品集,分为感事诗、哲理诗、山水诗、酬对诗、杂咏诗和词赋六大类。其中感事诗90首,主要反映朱熹对天下大事的观感及其在各个时期的基本思想倾向,按其主题又分为爱国恤民与述怀明志两组;哲理诗73首,主要反映朱熹的学术观点,按其主题又分为宇宦观、人生观、道德修养和为学三组;山水诗148首,主要反映朱熹的游踪和各地山川形胜,其中又分为武夷云谷、衡岳、庐山及其他胜地四大块;酬对诗87首,主要反映朱熹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内又分为奉和、题赠、迎送、寿挽四组;杂咏诗99首,为朱熹对各种事物的吟咏与思想寄寓,反映其日常生活情趣,内又分为咏物、咏景、咏居、咏事四组;词赋18首,按体裁分类。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