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熹诗经学释义原则
| 内容出处: | 《朱熹诗经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4495 |
| 颗粒名称: | 第一章 朱熹诗经学释义原则 |
| 分类号: | I207.22 |
| 页数: | 78 |
| 页码: | 1-78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到,汉诗经学共有四家,分今、古文二派。其中,毛氏一家在汉初已传于民间,至东汉时影响超过今文三家,但自郑笺通行后,三家诗更见衰微,甚至不传。魏王肃则作《毛诗义驳》诸书,申毛难郑,导致三家与毛之争变为郑、王之争。至唐修《五经正义》时,采用毛《传》郑《笺》,争议才得以平息。而通行本《十三经注疏》则包含《诗序》、《毛传》、《郑笺》、《诗谱》、《孔疏》五部分,代表了汉诗经学的整体。在宋诗经学中,欧阳修《诗本义》反对了毛、郑之说,断以己义,开启了宋学之新局。其后,郑樵作《诗序辨妄》等书,直接指责《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朱熹则集宋学大成,作《诗集传》及《诗序辨说》,弃序不用,专于文本自身求诗本义,且杂采毛、郑,间录三家,一以己义为取舍。因此,废《序》与求诗本义成为朱熹对汉学诗经学的一场革命。 |
| 关键词: | 朱熹 诗经 文学研究 |
内容
《四库全书总目》云:“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汉诗经学共有四家,分今、古文二派:今文有鲁、齐、韩三家,汉武帝前皆已立于学官;古文有毛氏一家,汉初亦已传于民间。《毛诗》西汉时未能立于学官,但至东汉时影响超过今文三家,当时大儒皆治之。汉末郑玄就《毛传》作《笺》,间采三家之义(主要是《韩诗》,郑玄初治之)。自郑笺通行,三家诗更见衰微,竟至于不传(今存者惟《韩诗外传》,亦不能代表三家诗说)。魏王肃则作《毛诗义驳》诸书,申毛难郑。于是三家与毛之争,一变而为郑、王之争。诸儒或申郑难王,或申王难郑。至唐修《五经正义》,用毛《传》郑《笺》,而其争乃息。今之通行《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则含《诗序》、《毛传》、《郑笺》、《诗谱》、《孔疏》五部分。《诗序》为解诗旨之作,兼及世次;《毛传》以文字训诂为主,兼有对诗义的串讲发挥,然极简略;《郑笺》进一步发挥毛传之说,且对毛传时有驳正;《诗谱》亦郑玄所作,专论三百篇之世次;《孔疏》则对《毛传》、《郑笺》详加疏证,详细串讲章义篇义,且辨析毛郑异同,但以调和为主。从细处着眼,五个部分不尽吻合;但将这五者视为一个代表汉诗经学的整体,亦未尝不可。
自立门户的宋诗经学,则始于欧阳修《诗本义》。《本义》辩诘毛、郑,断以己义,力反东汉以来治《诗》之旧习。苏辙继起,作《诗集传》,始攻击毛序,仅存录首句。南宋时,郑樵作《诗序辨妄》,直斥《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王质《诗总闻》亦同此声气。朱熹则集宋学大成,作《诗集传》及《诗序辨说》,弃序不用,专于文本自身求诗本义,且杂采毛、郑,间录三家,一以己义为取舍。
废《序》与求诗本义实是朱熹对汉学诗经学的一场革命。
第一节 求诗本义
[辞与意的关系 《序》不合《诗》本意 涵泳文本]
一、辞与意的关系
马端临有云:
《诗》、《书》之序,自史传不能明其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解经,则依古、今文析而二之,而备论其得失。而于《诗·国风》诸篇之序,诋斥尤多。以愚观之,《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论之,《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何也?《书》,直陈其事而已,《序》者,后人之作,藉令深得经意,亦不过能发明其所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诗》则异于《书》矣。然《雅》、《颂》之作,其辞易知,其意易明,故读《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七章,则“文王受命作周”之语赘矣。……盖作者之意已明,则《序》者之辞可略。……至于读《国风》诸篇,而后知《诗》之不可无《序》,而《序》之有功于《诗》也。盖《风》之为体,
比兴之辞多于叙述,风喻之意浮于指斥。盖有反复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者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意料当时旨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而文公深诋之,且于《桑中》、《溱洧》诸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于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乌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其说固善矣。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只《郑》、《卫》诸篇哉?若《芣苡》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者,而其语不过形容采掇芣苡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采掇者为何事?而慨叹者为何说乎?……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均一淫佚之词,出于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芣苡》、《黍离》之不言所谓……文公胡不玩索《诗》辞,别自为说,而卒如《序》者旧说,求作诗之意于诗辞之外矣?何独于《郑》、《卫》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而使圣经为录淫辞之具乎?且夫子尝删诗矣。其所取于《关雎》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之《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佚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婚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烦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者何等一篇也!……或曰:《序》者之序诗,与文公之释诗,俱非得于作诗之人亲传面命也。《序》求诗意于辞之外,文公求诗意于辞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说而妄拟先儒也。盖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说《诗》者读《诗》,而后知《序》说之不谬,而文公之说多可疑也。孔子之说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之说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不能无过,故其于男女夫妇之间,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间,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七十五篇(作文按:当为一百六十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复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于无邪之训,而以辞害意之过也。而况《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旷之悲,遇合之喜,虽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辞哀,习其读,而不知其旨,易以动荡人心之邪情泆志,而况以铺张揄扬之词,而序淫佚流荡之行乎?然诗人之意则非以为是而劝之也。盖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言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于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决非淫佚之人所自赋也。①
这大约是辩驳朱熹不依《序》说诗最有系统的一段议论。马端临其意在辩《诗序》不可废,但却对汉学诗经学与朱熹诗经学的释义原则多有讨论。尽管马端临在回护《诗序》方面不足取,但他对汉学诗经学与朱熹诗经学释义方法的总结以及思考该问题的切入点,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意义。马端临抓住《国风》特别是其中的《郑》、《卫》之诗(也即朱熹认定的“淫诗”)来讨论这个问题,正是看出了其间存在“辞”与“意”这一对关系。朱熹与汉学诗经学的分歧正在于处理《诗三百》文本“辞”与“意”的关系上:“《序》求诗意于辞之外,文公求诗意于辞之中。”
在讨论文本的“辞”与“意”关系时,有三个因素需要考虑:1、文本自身(姑且称为“辞”);2、作者之意(姑且称为“作意”);3、阐释者的释义(姑且称为“释义”)。从理论上讲,前二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只要一个文本被创作出来,其“辞”(文本自身)就客观存在,“作意”(创作者自身的意图)也是客观存在的。“作意”与“辞”之间可以有两种模式:1、“作意即辞意”,文本的字面意义就是作者之意;2、“作意非辞意”,作者之意并不就是文本自身,而是隐含于文本中的一种比喻意。其所以存在这两种模式,是因为人类的表达方式存在直接叙述与比喻说明这两种情况。文学作品的表达更是如此。“作意即辞意”,是很容易理解的。至于“作意非辞意”,唐人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诗是很好的例证。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文本自身浅显易懂,其字面意思无非是说一个新嫁娘,刚和新郎入了洞房,正在考虑次日清早见公婆的事情:她很有些担心公婆不喜欢自己的装束,所以问新郎自己的打扮是否入时。但这诗的题目却是《近试上张水部》,而且是代书体,是一个考生写给考官的信——他想探听一下考官大人的口风呢!诗人的作意与诗辞的表面意义并非是一回事,二者之间不过是一种比喻性的关系而已。“释义”是阐释者在阅读文本之后,根据文本所提供的信息,并结合以往的阅读经验,对文本所做出的一种解释。从理论上说,“释义”只能是主观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阐释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感受来对文本加以解释的,他们的意见自然可以很不相同。“释义”可以无限接近于“作意”,但总是存在“误差”。“作意”与“辞意”之间本就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模式,阐释者在对文本进行解释时,也可以有两种不同方法:1、“求诗意于辞之中”;2、“求诗意于辞之外”。前者以“作意即辞意”为认识前提;后者以“作意非辞意”为前提。从方法的角度来说,二者之间未可置以轩轾。但这两种阐释方法都必须以对象的针对性为前提,它们都只适合于自己特定的对象。“求诗意于辞之中”的阐释方法适用于“作意即辞意”这一类型,但却不适用于“作意非辞意”的类型。用“求诗意于辞之中”的方法来阐释“作意即辞意”这一类型,不同的阐释者或许有高下之分,但对于事实真相(“作意”)来说,“释义”只有一个误差大小的问题。但如果是“作意非辞意”这一类型,阐释者却用了“求诗意于辞之中”这种方法,那就不是“误差”的问题,而是“谬误”了。“求诗意于辞之外”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对,它只适用于“作意非辞意”这一类型,却不适用于“作意即辞意”的类型。
判定“释义”是否合于“作意”,首先要对“作意”与“辞意”的关系做出明确判断。“求诗意于辞之中”,是通行的阐释方法;“求诗意于辞之外”,则必须要有“作意非辞意”的前提存在。一般来说,“作意即辞意”是通例,“作意非辞意”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如果要对一个文本做出“作意非辞意”的认定,必须要有足够的背景方面的限制性条件。我们确认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属于“作意非辞意”这种类型,是因为其作者、诗题以及当事人的身份关系提供给我们充分的信息。有这种充分的背景性限制条件,“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才能够让人信服。不具备这种充分的背景性限制条件,“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则只能是莫须有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只对有充分的背景性限制性条件的文本作“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对“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我们判定其“释义”是否合于“作意”,也以其是否有充分的背景性限制条件为根据。诗歌史的实际情况是:文本及其背景材料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足以让我们作出“作意非辞意”的判断的,并不多见。对绝大多数的诗篇,我们一般认为其“作意即辞意”,并用“求诗意于辞之中”的方法来对其进行阐释。
“《序》求诗意于辞之外,文公求诗意于辞之中。”《序》者说《诗》的方法是求文字自身以外的特殊涵义,朱熹则是根据文本自身来说《诗》。《序》者说《诗》,不外乎美、刺二端。汉儒从政治讽喻的角度来理解《诗三百》,认为“《诗》缘政”,《诗三百》所有作品都是美刺当时国君政事的。对国政进行美刺,即是汉学诗经学所理解的“作意”。但是,诚如马端临所指出的,《诗三百》尤其是《国风》部分,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譬如《周南·芣苡》),其文本自身只是“反复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者之意”。对于汉儒来说,由于习惯了比兴说诗(实际是道德政治譬喻)的思维方式,对《序》者的解说很容易接受。但对不采用这一思维方式的阐释者来说,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问题,亦即马端临隐括朱熹之意:“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乌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诗三百》文本自身,尤其是《国风》部分,其辞意并不晦涩,根据文本自身来解说,很容易做到明白晓畅。其文本字面上明明是一种意思,与《序》者所云,并不相干;凭什么要放弃其字面意思而听从《序》的意见呢?汉儒坚持《诗三百》在文本字面意义之外尚有一个非美即刺的作者之意;朱熹则认为作者之意即在《诗三百》文本自身,而汉儒所挖掘的《诗》意并不是诗人本意。所以他要摆脱《序》的束缚,求诗本意。马端临认识到《序》者与朱熹在处理《诗三百》文本“辞”与“意”关系上有根本分歧,他们是用了两种不同的阐释方法。马端临屡言《诗》之意当如《序》说而不当如朱熹所说,是因为他受《序》的影响太深,脑子里有根深蒂固的《诗》不能无为而作(必须有政治讽喻意义)的观念。汉学诗经学一派都有这样的思维前提:《诗经》既然是“经”,它就应该有超乎其文本自身以外的深意在。所以其(《国风》部分)“作意非辞意”,必须要用“求诗意于辞之外”的方法来对其加以阐释。
马端临用“求诗意于辞之外”与“求诗意于辞之中”来概括《序》者与朱熹在说诗方法上的根本差别,是极有见地的。但他回护《诗序》的理由却站不住脚。马端临是史学名家,精于考据辨析,但他这里论证《序》说可靠的理由在逻辑上却有问题。其论《序》说可信的理由无非如下三条:1、《诗》意有必赖《序》而后明者;2、《序》者言《诗》意态度果断,应该是有根据、有传授渊源的;3、孔孟说《诗》与《序》者相合。但这三条理由实不能证明《序》说可信:1、《序》确实给了《诗》一种规定性的解释,但此解释未必得《诗》之本意。以《诗》意有必赖《序》而后明者为理由证明《序》说可信,在逻辑上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2、《序》者态度确实果断,但这与意见正确与否是两码事。3、借助孔孟之言,是诉诸权威的思路。孔孟是文化思想之巨人,但不等于他们的认识一概正确。即使《序》者说诗合于孔孟,亦不能证明其说合于诗人本意。
尽管在今天看来,马端临论证《序》说可靠的三条理由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但马端临自己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他对《序》说是一种坚信的态度。不独马端临,《诗》汉学一派对《序》的权威地位,也是从来坚信不疑的。我们可以说,《诗序》是汉学诗经学的灵魂,依《序》说诗是汉学诗经学的根本特征。
因为对《诗序》作者的争议,《诗序》与《毛传》的先后亦相应成为诗经学的一大公案。笔者个人的意见,则主张《诗序》至少不晚于《毛传》,而且《毛传》分明是依序说诗。这可以从《毛传》与《诗序》在字句上的对应关系得到证明。《毛传》以“但明训诂”为特色,但在具体说诗时,不少地方有超出训诂范围的发挥。这些发挥颇值玩味。如《召南·江有汜》篇,《毛传》于“不我以,其后也悔”句后注曰:“嫡能自悔也。”诗文自身绝不涉于嫡媵之意,注者显然不能在训诂范围内作此断语。《毛传》断言是“嫡”而非他人能自悔,无非是有《诗序》作根据罢了。《诗序》云:“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也。”若无《诗序》的根据,《毛传》是断不可做出这样的解说的。与《召南·江有汜》篇类似,《毛传》说诗有超出训诂范围的发挥,而且是不能直接从诗辞之中得出,但却与《序》有明显对应关系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例子说明《毛传》分明是依《序》说诗。《郑笺》和《孔疏》的依《序》说诗,则是不待说的。几乎每一句的解说,都要迁就《诗序》,绝不敢有什么动摇和怀疑。
二、《序》不合《诗》本意
因为《诗序》自身的说诗方法是“求诗意于辞之外”,所以,凡是尊《序》的一派都主张《诗经》“作意非辞意”,且都关注于文本以外的政治譬喻义。《毛传》也好,《郑笺》也好,其对《诗经》文本的阐释,都是以《序》为核心,来做具体发挥。朱熹对《序》者“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方法以及毛、郑依《序》说诗极为不满,他自己的做法乃是要“求诗意于辞之中”,以文本自身为首要根据。《朱子语类》中颇多这方面的议论:
01 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或每日令人讽读,却从旁听之。其话有未通者,略检注解看,却时时诵其本文,便见其语脉所在。(80/2083,黄㽦记)①
02 某解《诗》,多不依他《序》。纵解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诗上下文意,则得罪于圣贤也。(80/2092,包扬记)
03 大抵今人说《诗》,多去辨他《序》文,要求著落。至其正文“关关雎鸠”之义,却不与理会。(80/2068,余大雅记)
04 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80/2068,余大雅记)
05 伯恭专信《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要出脱回护。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80/2074,邵浩记)
……
朱熹反复强调的是读《诗》、解《诗》需要虚心诵读正文,要根据其本文自身来理解诗意。《序》者说诗,多与这一原则相背离,所以多不得诗之本意。如果一味依《序》说诗,而不仔细考察文本上下文自身,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理解。正因为朱熹与《序》对诗意的解说有一个“求诗意于辞之中”与“求诗意于辞之外”的根本差别,所以朱熹对《序》者的解释多不以为然。《诗序辨说》对《序》的具体批评亦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诗序辨说》指出“诗中未见此意”者共有17例(附录1)。
附录1:《诗序辨说》明言“诗中未见此意”例:
01 《召南·草虫》,《序》:“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诗序辨说》:“未见以礼自防之意。”
02个《召南·江有汜》,《序》:“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也。”《诗序辨说》:“诗中未见勤劳无怨之意。”
03 《邶风·雄雉》,《序》:“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诗序辨说》:“未有以见其为宣公之时、与淫乱不恤国事之意。”
04 《邶风·谷风》,《序》:“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诗序辨说》:“亦未有以见化其上之意。”
05 《卫风·考槃》,《序》:“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诗序辨说》:“诗文未见有见弃于君之意。”
06 《卫风·竹竿》,《序》:“卫女思归也。适异国而不见答,思而能以礼者也。”《诗序辨说》:“未见不见答之意。”
07 《郑风·女曰鸡鸣》,《序》:“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诗序辨说》:“此亦未有以见其陈古刺今之意。”
08 《唐风·羔裘》,《序》:“刺时也。晋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诗序辨说》:“诗中未见此意。”
09 《小雅·绵蛮》,《序》:“微臣刺乱也。大臣不用仁心,遗忘微贱,不肯饮食教载之。故作是诗也。”《诗序辨说》:“此诗未有刺大臣之意。”
10 《周颂·维天之命》,《序》:“大平告文王也。”《诗序辨说》:“诗中未见告太平之意。”
11 《周颂·维清》,《序》:“奏象舞也。”《诗序辨说》:“诗中未见奏象舞之意。”
12 《周颂·烈文》,《序》:“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诗序辨说》:“诗中未见即政之意。”
13 《周颂·雝》,《序》:“谛大祖也。”《诗序辨说》:“诗文亦无此意”。
14 《周颂·酌》,《序》:“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
之道,以养天下也。”《诗序辨说》:“诗中无酌字,未见酌先祖以养天下之意。”
15 《鲁颂·》,《序》:“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诗序辨说》:“诗中亦未见务农重谷之意。”
16 《鲁颂·有〓》,《序》:“颂僖公君臣有道。”《诗序辨说》:“此但宴饮之诗,未见君臣有道之意。”
17 《商颂·烈祖》,《序》:“祀中宗也。”《诗序辨说》:“详此诗,未见其为祀中宗。”
以上17例,都是《序》者对《诗经》作品做出的解释,但其解释有超乎“辞”意的地方;朱熹则以文本为根据,对其超乎文本的随意发挥一一加以指陈。
其实,《诗序辨说》象这样直接说“诗中未见此意”的情况,还只是对《序》的解说进行部分质疑。如《召南·江有汜》篇,《诗集传》云:“是时汜水之旁,媵有待年于国,而嫡不与之偕行者,其后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这样的理解和《序》者的解释实际并无太大的分歧。但因为文本自身看不出“勤劳无怨”的意思而《序》有此一说,《诗序辨说》还是要特意指出来。对一点点的不以文本为根据的随意发挥都不放过,正可以说明朱熹对文本是何等的重视!
《诗序辨说》于一些篇目则干脆说《序》者所说“非诗本意”,共有4例(附录2)。
附录2:《诗序辨说》径云《序》者所说“非诗本意”例:
01 《郑风·狡童》,《序》:“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诗序辨说》:“非诗之本旨,明矣。”
02 《小雅·吉日》,《序》:“美宣王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诗序辨说》:“序慎微以下,非诗本
意。”
03 《小雅·瞻彼洛矣》,《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诸侯,赏善罚恶焉。”《诗序辨说》:“此序以命服为赏善,六师为罚恶,然非诗之本意也。”
04 《大雅·荡》,《序》:“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诗序辨说》:“苏氏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诗之本意也。”
云“非诗本意”,无非是指《序》者的解说与文本的实际情况不相合。至于《诗序辨说》径云“《序》说误矣”(如《邶风·终风》篇等)或“此序全非诗意”(如《唐风·有杕之杜》篇等)的情况,在朱熹的立场,《序》者的解释更是与《诗》之本意相差甚远了!前引马端临所集中讨论的“淫诗”问题,最为典型。朱熹对《序》者解说淫诗,或者以为是诗人“刺淫”,或者别作他解的做法很不满意,干脆根据文本自身把它们都理解为淫者自叙其事。关于“淫诗”的问题,将在论文的第二章具体讨论,这里暂不细说。
《诗序辨说》卷首云:
《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惟《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篇,毛公始分以置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义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又以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词,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燎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
朱熹指出:1、《序》非圣人作;2、《序》有不合诗人之本义处。以此否定《序》的权威性。在这两个理由中,后者更为关键。在今天看来,《序》是否出于圣人之门,与其是否合理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但古代读书人都有这样一个情结,他们习惯于认为圣人之言是真理,并且希望自己的意见能从圣人那里找到根据。马端临辩驳朱熹废《序》,便拿《序》者说《诗》合于孔孟当一个重要依据。汉学诗经学一派坚信《序》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以为《序》出于圣人之门(是孔子入室弟子子夏所传)。《序》既然出于圣人之门,其对诗旨的阐释自可尊崇,故汉学诗经学一派主张依《序》说诗。迷信孔子,断送了他们的独立思考。朱熹却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大儒,所以他能以己意说诗,别开生面。尽管“《序》非圣人作”与“《序》有不合诗人之本义处”,在否定《序》的权威性上是两个并列性的理由,但实际上前者的根据恐怕还在后者。《后汉书·儒林传》云卫宏作《毛诗序》,固然在文献上提供了一个证据,但朱熹认为“《序》非圣人作”,主要还是因为《序》的阐释多与《诗》辞本意不合。朱熹“求诗意于辞之中”,觉《序》不合诗旨之处甚多,因疑其非圣人所作,故不主张依《序》说诗,而于文本自身求诗本义。
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指出“《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序》只是阐释者对《诗》的一种规定性解释,相对于《诗三百》文本自身来说,它只能是第二位的。《诗三百》文本和《序》之间本是主客关系,《诗三百》文本自身是主,《序》是客。后人不明《序》乃汉人之作,误以为是圣人遗说,因此依《序》说诗,穿凿迁就,破碎经文,在所不惜。这样做,则是将《诗三百》文本和《序》之间的主客关系倒置了过来,《序》成了主,《诗三百》文本自身反成了客。这是朱熹所坚决反对和要纠正的。
朱熹有云:“《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且只将四字成句底诗读,却自分晓。见作《诗集传》,待取《诗》令编排放前面,驱逐(作文按:此处似应有一“序”字)过后面,自作一处。”(《朱子语类》,80/2074,陈文蔚记)又云:“《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朱子语类》,80/2074,甘节记)《序》不得《诗》本意,后人依《序》说诗,更是混淆视听,将读者引入歧途。所以朱熹理直气壮地说:“某解《诗》,多不依他《序》。”(《朱子语类》,80/2092,包扬记)朱熹的原则乃是以《诗三百》文本自身为根据,求诗本意。《诗集传》是其“求诗意于辞之中”的实践。《诗集传》不录《序》说,朱熹另著《诗序辨说》,将《诗序》汇为一编,且逐条加以辩驳。朱熹将《诗序》与《诗三百》经文自身剥离,单独汇为一编,其理由即《诗序辨说·序》所云“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朱子语类》云:“敬之问《诗》、《书》序。曰:古本自是别作一处。如《易大传》、班固《叙传》并在后。京师旧本《扬子》注,其序亦总在后。”(80/2074,廖德明记)。先秦、秦汉人著书的通例是《序》在正文之后,朱熹因此坚信《序》是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了。
三、涵泳文本
朱熹求诗本义的根本方法是涵泳文本。《朱子语类》载朱熹教弟子读《诗》之法,不厌其烦地强调涵泳工夫,且看:
01 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候仿佛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如人拾得一个无题目诗,再三熟看,亦须辨得出来。若被旧说一局局定,便看不出。(80/2085,吴必大记)
02 提取摘要;分类号;关键词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仍不可先看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认得此诗是说个甚事。谓如拾得一个无题目诗,说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开,必是梅花诗也。(80/2085,万人杰记)
03 读《诗》正在吟咏讽诵,观察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今公读《诗》,只是将己意去包笼他,如做时文相似。中间委曲周旋之意,尽不曾理会得,济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看尽,何用逐日只捱得数章,而又不曾透彻耶?且如入人城郭,须是逐街坊里巷,屋庐台榭,车马人物,一一看尽,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见城是如此,便说我都知得了。如《郑诗》虽淫乱,然《出其东门》一诗,却如此好。《女曰鸡鸣》一诗,意思亦好。读之,真个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80/2086,钱木之记)
04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直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看来书只是要读,读得熟时,道理自见,切忌先自布置说!(80/2086,沈僩记)
05 须是读熟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取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80/2087,沈僩记)
06 大凡读书,先晓得文义了,只是常常熟读。如看《诗》,不须得着意去里面训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80/2087,林夔孙记)
07 先生问林武子(作文按:当为林子武。林夔孙,字子武):“看《诗》何处?”曰:“至《大雅》。”大声曰:“公前日方看《节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而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开板便晓,但于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时,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强五十遍,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时。“题彼脊鸰,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这个看时,也只是恁地,但里面意思却有说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说不得里面。”(80/2087,黄义刚记)
所谓“涵泳文本”,实际就是要求熟读《诗三百》诗文自身,仔细玩味体察诗中的曲折情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终须是烂熟于心了,才容易对文辞中所体现的作者情感有较贴切的体会,才容易对辞意有一个确解。文字表达相对于图画、戏剧等表达方式来说,其直观性要稍弱一些;诗歌更是一种表达复杂情感的文学样式。所以,诗歌尤其需要“涵泳”。文学感受是一种特殊的感受,需要读者对阅读对象有极细微的了解,并根据个人的情感经验在内心对文本事件作一构拟。文学阅读是一项极细腻与感性的心理活动;文学审美是一种很微妙的境界,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般来说,文学感受力的高下取决于读者的心灵敏感度与以往的情感经验,不同的读者,对作品的感受程度有高下之别。但对同一读者来说,在心灵敏感度与情感经验是一定量的情况下,其对作品的感受程度则取决于对作品的熟悉程度。朱熹说“百遍自是强五十遍,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朱熹强调要熟读文本。不断熟读,徐徐玩味,对作品的体会自然会逐步加深,而且对文学的感受能力也会在此中不断提升。如果不以“涵泳文本”为方法,而只一味看别人的解释,那就很难对作品有深切的体会。《庄子》有轮扁的譬喻,“斫轮”尚且不能父喻于子,何况是文学感受呢?文学感受只能是靠自己体会,阐释者可以给读者以正确的引导,但却无法越俎代庖。阐释者自身在理解辞意时,更是需要细心体会。所以,朱熹一再告诫弟子读《诗》时,最好什么注解都不必先去看,只管将文本熟读,久之自有体会。再高明的阐释都不能替代读者自身的阅读与感受,何况《序》对《诗》的解释还有那么多不尽如人意乃至有歪曲之处呢?朱熹主要是从求诗本义的角度,针对汉学诗经学依《序》说诗来提倡“涵泳文本”的;但对“涵泳”的重视和大力提倡,也说明朱熹对《诗三百》的文学性有深刻认识。
“涵泳文本,求诗本义”是朱熹说诗的根本方法,“揆以情理”和“考诸书史”则是其辩驳《诗序》的具体手段。
朱熹说诗,每求不远于人情物理。《朱子语类》中有这样一条:“问:以《诗》观之,虽千百载之远,人之情伪只此而已,更无两般。曰:以某看来,须是别换过天地,方别换一样人情,
释氏之说固不足据,然其书说尽百千万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况天地无终穷,人情安得有异!”(80/2083—2084,吴必大记)。这是由《诗》说到人情,朱熹说《诗》却往往是据人情以论《诗》。如《唐风·山有枢》篇,《序》云:“刺晋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政荒民散,将以危亡,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国人作诗以刺之。”《诗序辨说》:“此诗盖以答《蟋蟀》之意,而宽其忧。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说大误。”朱熹不取《序》之刺晋昭公一说,乃是因为该篇辞意“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序》者不察于此,是疏于人情物理。至于“淫诗”问题的辩论,更能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先看《朱子语类》中的一条记载:
李茂钦问:“先生曾与东莱辩论淫奔之诗。东莱谓诗人所作,先生谓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晓其说。”曰:“若是诗人所作讥刺淫奔,则婺州人如有淫奔,东莱何不作一诗刺之?”茂钦又引他事问难。先生曰:“未须别说,只为我答此一句来。”茂钦辞穷。先生曰:“若人家有隐僻事,便作诗讦其短讥刺,此乃今之轻薄子,好作谑词嘲乡里之类,为一乡所疾害者。诗人温醇,必不如此。”(80/2093,李杞记)
对于“淫诗”理解有异,是朱熹与吕东莱的一大分歧。吕东莱于“淫诗”是依从《序》者所说,朱熹则认为是“淫者自作”。朱熹在给李茂钦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如此理解“淫诗”时,说:如果婺州有人淫奔,东莱会不会作诗刺之呢?以东莱的身份,绝不会这样做。同样的道理,“诗人”既是贤君子,自然也不会这样做。《诗序辨说·桑中》篇又说:“……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间,犹有宾主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这也是从人情物理的角度来说明问题。
朱熹有云: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80/2076,叶贺孙记)
“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说明“考诸书史”是朱熹辩驳《诗序》的重要手段。《序》者说诗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傅会历史,将《诗三百》的每一篇都落实到具体的国君政事上。我们之所以说《序》者说诗是傅会历史,乃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具体的文献根据。前文在讨论文本的“辞”与“意”关系时,已经指出:“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方法只适用于“作意非辞意”这种类型的文本;而对一文本做出“作意非辞意”的类型判断,必须要有充分的背景性限制条件。如果《序》者有充分的文献材料,足以证明自己对《诗三百》文本“作意非辞意”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它对《诗三百》所作的“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自然无可厚非。但遗憾的是,没有这样的文献材料。朱熹正是看透了这一点,《史记》、《国语》等书中没有《序》者所需要的《诗三百》的背景性材料,因此《序》者的阐释从方法上就失去了立脚之地。
“考诸书史”,发现《序》者的阐释前提存在问题;“揆以情理”,又感觉《序》的若干解释不合于人情物理。《序》还有什么能让朱熹信服呢?所以朱熹干脆另起炉灶,抛开《诗序》,涵泳文本,求诗本义。《诗序辨说·周颂·昊天有成命》篇云:“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后祀成王之诗无疑。”“详考经文”,自然即是以文本为根据;“以《国语》证之”,则是“考诸书史”了。这短短一段话,正吐露了朱熹求诗
本义的方法手段。
第二节 朱熹对《序》的具体批评
[《序》无“理”断章取义傅会历史杨慎、姚际恒等论朱熹废《序》]
诗经学汉、宋之争的关键在于是尊《序》还是废《序》。落实到文本阐释上,实际只是个是否依《序》说诗的问题。尊《序》、废《序》之争的关键,在于论者对《诗序》是否合于诗旨的判断。汉学一派以为《诗序》出于圣人(为其入室弟子所传),其对诗旨的阐释自可尊崇,故主张依《序》说诗;以朱熹为核心的宋学家以怀疑之精神,独立思考,觉《诗序》不合诗旨之处甚多,因疑其非圣人所作,故不主张依《序》说诗。“涵泳文本,求诗本义”是朱熹说诗的根本方法,“考诸书史”和“揆以情理”则是其辩驳《诗序》的具体手段。从涵泳文本自身求《诗》本义,进而发现《诗序》不尽合于《诗》旨,实是朱熹废《序》的根本。
上一节已详论《序》不合《诗》义以及朱熹不主张依《序》说诗,这一节,我们来讨论朱熹对《诗序》的具体批评。
一、《序》无“理”
朱熹是宋明理学第一大师,其为学根本即在“义理”二字。“义理”精神,在朱熹各种著述中均有深刻的体现,其治《诗经》之学亦不例外。关于朱熹诗经学与其理学思想之关系,我们将在论文的第四章给以专门讨论。此处仅就朱熹从“理”的角度批评《诗序》,略作论述。
朱熹义理之学,其根本用意乃在世道人心。其对《诗序》的批评,亦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诗序辨说·邶风·柏舟》篇云:“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是使读者疑于当时之人,绝无善者称君、过者称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则扼腕切齿,嬉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序》以美刺说诗,而刺又多于美,且其矛头多直接指向时君国政。朱熹认为这很容易误导读者,使读者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当时士人全没有“善者称君、过者称己”的美德,稍不得志,就刻薄讽刺君上。这与儒家“忠恕”、“尊卑”等基本伦理观念大相悖离,“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再如《郑风·狡童》篇,《序》云:“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诗序辨说》云:“昭公尝为郑国之君,而不幸失国,非有大恶,使其民疾之如寇仇也。况方刺其不能与圣人图事,权臣擅命,则是公犹在位也,岂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邪?……大抵《序》者之于郑诗,凡不得其说者,则举而归之于忽。文义一失,而其害于义理有不可胜言者。一则使昭公无辜而被谤;二则使诗人脱其淫谑之实罪,而丽于讪上悖礼之虚恶;三则厚诬圣人删述之意。以为实贱昭公之守正,而深与诗人之无礼于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后之说者,犹或主之。其论愈精,其害愈甚。学者不可以不察也。”按照朱熹的理解,《郑风·狡童》是一篇淫者自叙其事的“淫诗”,但《序》者将其说成是刺郑昭公忽的。可是在朱熹看来,昭公为政并无什么过失,不应“无辜而被谤”;何况为臣子的作诗,怎么能用“狡童”来称呼君上呢!?这还有什么君臣尊卑的观念在?这不仅是对诗旨理解有偏差,在义理上也有很大问题。对于以“义理”为根本的朱熹来说,这自然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我们可以这样说:“求诗意于辞之中”,发现《序》每不合于《诗》本意,是朱熹不依《序》说诗的根本原因。但其著《诗序辨说》,孜孜于辩驳、攻讦《诗序》,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序》有害于义理。
朱熹义理之学以世道人心为根本,但其为学根本途径则是“格物致知”。“格物”乃是要“格”出“物”中之“理”,所以朱熹在思考一切问题时尤其重视其内在理路。其治《诗经》亦然。朱熹在批评《序》无“义理”的同时,也对《序》有悖于一般性的“理”多有指陈。这一般性的“理”包括情理、文理等。《诗序辨说》对《序》无理的指陈比比皆是,共有17例(附录3)。
附录3:《诗序辨说》指陈《序》无理例:
01 《周南·关雎》,《序》:“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诗序辨说》:“按《论语》孔子尝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盖淫者乐之过,伤者哀之过,独为是诗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乐中节,而不至于过耳。而序者乃析哀乐淫伤,各为一事,而不相须,则已失其旨矣。至以伤为伤善之心,则又大失其旨,而全无文理。”
02 《卫风·氓》,《诗序辨说》:“……其曰美反正者,尤无理。”
03 《郑风·山有扶苏》,《诗序辨说》:“此下四诗(按:《萚兮》、《狡童》、《褰裳》、《丰》)及《扬之水》,皆男女戏谑之词。序之者不得其说,而例以为刺忽,殊无情理。”
04 《郑风·狡童》,《诗序辨说》:“大抵序者之于郑
诗,凡不得其说者,则举而归之于忽。文义一失,而其害于义理有不可胜言者。一则使昭公无辜而被谤……”
05 《魏风·十亩之间》,《诗序辨说》:“国削则其民随之,序文殊无理。”
06 《唐风·蟋蟀》,《诗序辨说》:“况古今风俗之变,常必由俭以入奢,而其变之渐,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谓君之俭反过于初,而民之俗犹知用礼,则尤恐其无是理也。”
07 《唐风·无衣》,《诗序辨说》:“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颠倒顺逆,乱伦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
08 《秦风·渭阳》,《诗序辨说》:“此序得之。但我见舅氏,如母存焉两句,若为康公之辞者,其情哀矣。然无所系属,不成文理。”
09 《豳风·破斧》,《诗序辨说》:“此归士美周公之词,非大夫恶四国之诗也。且诗所谓四国,犹言斩伐四国耳,序说以为管蔡商奄,尤无理也。”
10 《小雅·白华》,《诗序辨说》:“此序尤无理。”
11 《小雅·雨无正》,《诗序辨说》:“此序尤无义理,欧阳公、刘氏说已见本篇。”
12 《小雅·鸳鸯》,《诗序辨说》:“此序穿凿,尤为无理。”
13 《大雅·旱麓》,《诗序辨说》:“序大误。其曰百福干禄者,尤不成文理。”
14 《大雅·行苇》,《诗序辨说》:“(说者)碎读之,逐句自生意义,不暇寻绎血脉,照管前后……随文生义,无复伦理。”
15 《大雅·韩奕》,《诗序辨说》“其曰能赐命诸侯,则尤浅陋无理矣。既为天子,赐命诸侯,自其常事。春秋
战国之时犹有能行之者,亦何足为美哉?”
16 《大雅·召旻》,《诗序辨说》:“旻闵以下不成文理。”
17 《周颂·昊天有成命》,《诗序辨说》:“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两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己意。其淤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
以上17例都是直接批评《序》无“理”的。有批评《序》无义理的,如例04,例07,例11。有批评《序》的解释不合于情理的,如例03,06,这种情况前文论朱熹说《诗》但求不远于人情物理时已有讨论。更多的例子则是批评《序》无“文理”,也即说《序》不合文章逻辑。
《诗序辨说》还有些地方虽未出现“无理”之类的字样,但实际上也是认为“无理”的。如《周南·卷耳》篇,《诗序辨说》云:“首章之我独为后妃,而后章之我为使臣,首尾衡决不相承应,亦非文字之体也。”虽未出现“无理”字样,实际是说无文理。再如《唐风·山有枢》篇,《诗序辨说》云:“此诗盖以答《蟋蟀》之意,而宽其忧。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说大误。”虽未曾出现“无理”字样,实际是说不合情理、有悖义理。
不管是“义理”、“情理”,还是“文理”,凡是朱熹批评《序》无“理”的,都是说《序》对《诗》的解说没有道理。从有理无理的角度来辨《序》,正是朱熹的特色。《诗序辨说》中也有说到《序》有“理”的地方,如《诗序辨说·大雅·云汉》篇云:“此序有理”,《诗序辨说·大雅·常武》篇云:“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于理亦通”。但说《序》有“理”之处相对来说是极少的。在朱熹看来,不通、无理才是《序》的基本特色。
《小雅·小宛》篇,《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不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乱畏祸而相戒之辞尔。”《诗集传》于其篇末云:“此诗之辞最为明白,而意极恳至。说者必欲为刺王之言,故其说穿凿破碎,无理尤甚。今悉改定,读者详之。”朱熹批评《序》者无“理”,说到底,还是看不惯它的穿凿傅会。
二、断章取义
朱熹还指出《诗序》在说诗时有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断章取义;二是傅会历史。
现代诗经学对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多有专门研究。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①一文,反复强调“赋诗言志”多采取“断章取义”的方法,而不管作诗的本义。朱自清《诗言志辨·诗言志·赋诗言志》②亦指出:“赋诗言志”是从外交方面出发,诗以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与献诗陈己志不同。其特点是颂多而讽少,与献诗相反。“献诗的诗都有定旨,全篇意义明白。赋诗却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断章取义只是借用诗句作自己的话,所取的只是句子的文义,就是字面的意思,而不管全诗用意,就是上下文的意思。”《诗言志辨·比兴·兴义溯源》则指出:“赋诗只取一二章,并且只取一章中一二句,以合己意,叫作‘断章取义’,引诗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借用古诗,加以引申,取其能明己意而止。‘作诗人之意’是不问的。”毛、郑解《诗》是“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以断章之义为全章全篇之义,而说比兴时尤然。”
其实,朱熹对“赋诗言志”多“断章取义”、汉儒说《诗》受“赋诗言志”影响这两个义例早有发明。朱熹有云:“《左传》所载歌诗,多与本意元不相关。”(80/2071,叶贺孙记),这便是说《左传》所载“赋诗言志”多是“断章取义”了。《诗序辨说》中有两处直接说到《序》者说诗受先秦人赋诗、引诗“断章取义”的影响。
其一是《郑风·褰裳》篇,《序》云:“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诗序辨说》云:“此序之失,盖本于子太叔、韩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断章取义之意耳。”朱熹这里说的“盖本于子太叔、韩宣子之言”,是指《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的一次“赋诗言志”。兹录《左传》原文相关章节于下: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怕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子太叔赋的正是《褰裳》这篇诗。顾颉刚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中对此作过很好的演绎,他说:
这一次,因为韩宣子要“知郑志”,所以郑六卿赋的都是郑诗。郑国的诗是情诗最多,所以这一次赋的诗也是情诗特多;如子太叔赋的《褰裳》,就是情思很荡的!“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这正是荡妇骂恶少的口吻,说:“你不要我,难道就没有别人吗?”淫荡的态度真活画出来了!子太叔断章取义,用在这里,比喻他愿意从晋,只恐晋国的拒绝;所以韩宣子就说:“我在这里,怎会使你去寻别人呢!”子太叔拜谢他,他又说:“没有这样的警戒,那能有始有终呢!”可见断章取义的用处,可以不嫌得字句的淫亵,不顾得作诗人的本义。
顾颉刚的演绎,足以很好地说明春秋时“赋诗言志”是可以不顾作诗人的本义。《褰裳》的字面意义自然是一篇情诗,可是子太叔用来表示自己从晋的意愿,韩宣子也很明白他的意思。郑国权臣子产最后拜谢韩宣子,说的是:“吾子靖乱,敢不拜德!”郑国弱小,晋国强大,所以郑需要晋帮助靖乱。《褰裳》《序》云:“国人思大国之正己”,正是由此而来。朱熹是明眼人,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序》不明白“赋诗”是“断章取义”的道理,而上了子太叔、韩宣子的当。故《朱子语类》有云:“《褰裳》诗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岂不是淫奔之辞!只缘《左传》中韩宣子引‘岂无他人’,便将做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不知古人引《诗》,但借其言仪寓己意,初不理会上下文义,偶一时引之耳。”(80/2091,黄㽦记)。
其二是《大雅·既醉》篇,《序》云:“太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诗序辨说》云:“序之失如上篇(作文按:《大雅·行苇》),盖亦为孟子断章所误尔。”按:《孟子·告子(上)》:“《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朱熹亦看出了《序》者对该篇的解说受到了《孟子》的影响。但是《孟子》是引一句诗来说明自己要说的道理,这句诗已经从原诗中割离开来,它不再是原诗的一个有机组成,而要在新的结构中发挥意义上的作用。原诗完整的章节是“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此父兄所以答《行苇》之诗,言享其饮食恩意之厚,而愿其受福如此也。”朱熹的解释明显比《序》要合于情理和文意。《序》者正是被孟子断章所误。
《诗序辨说》于《大雅·行苇》篇,对汉儒断章取义的说诗方法做了尖锐的批评。该篇《序》云:“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考〓,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诗序辨说》云:“此诗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说者不知比兴之体、音韵之节,遂不复得全诗之本意,而碎读之,逐句自生意义,不暇寻绎血脉,照管前后。但见‘勿践行苇’,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但见‘黄〓台背’,便谓‘养老’;但见‘以祈黄〓’,便谓‘乞言’;但见‘介尔景福’,便为‘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伦理。诸序之中,此失尤甚。览者详之。”
《朱子语类》亦云:“看来《诗序》当时只是个山东学究等人做,不是个老师宿儒之言,故所言都无一事是当。如《行苇》之《序》虽皆是诗人之言,但却不得诗人之意。不知而今做诗人到这处将如何做,于理决不顺。”(80/2078,黄卓记)。又云:“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80/2075,周谟记)。
不顾血脉文理,割裂全篇,仅就一句傅会生说,正是汉儒的伎俩。但是文本的有机整体性是在对文本进行阐释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文本局部(单独的一句诗)的含义受整体(完整的一篇诗或一章诗)制约,不能将局部从整体中割裂开来。只有将局部纳入整体之中,将局部当成整体的一个组成,其阐释才是有效的。失去整体制约的局部文本,其阐释的外部限定性条件过于单薄。对于单独的一句诗,阐释者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主观意志,对其进行多种可能性的解释;但这种阐释很难进行文本还原,即与它在文本整体限定条件下的意义很难符合。前引《大雅·既醉》篇的例子,《孟子》将“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解释为饱乎仁义,单从这两句自身来看,这样的解释是可以的。但将它还原为原诗完整章节“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的一个有机组成时,这样的解释就不很妥帖了。单就一句生说的方法,正是忽视了文本的有机整体性。如《行苇》一诗,《序》的解说每一句都是对应于诗辞的,但却没有将其当成一个有机整体来阐释,所以还是与诗人的本意有很大距离。所以朱熹说:“《行苇》之《序》虽皆是诗人之言,但却不得诗人之意。”
《诗序辨说》指明《小序》是“断章取义”、“仅就一句生说”的例子,在《郑风·褰裳》、《大雅·既醉》、《大雅·行苇》之外尚有8例,共11例(附录4)。
附录4:《诗序辨说》指陈《小序》“断章取义”、“仅就一句生说”例:
01《周南·汉广》,《序》:“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诗序辨说》:“此诗以篇内有‘汉之广矣’一句得名,而序
者谬误,乃以德广所及为言,失之远矣。”
02 《郑风·褰裳》,《序》:“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诗序辨说》:“此序之失,盖本于子太叔、韩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断章取义之意耳。”
03 《郑风·野有蔓草》,《序》:“思遇时也。君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诗序辨说》:“东莱吕氏曰:‘君之泽不下流,乃讲师见零露之语从而附益之。’”
04 《小雅·蓼萧》,《序》:“泽及四海也。”《诗序辨说》:“序不知此为燕诸侯之诗,但见零露之云,即以为泽及四海。其失与《野有蔓草》同。臆说浅妄类如此云。”
05 《小雅·甫田》,《序》:“刺幽王也,君子伤今而思古焉。”《诗序辨说》“此序专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说,而不察其下文‘今适南亩’以下,亦未尝不有年也。”
06 《小雅·大田》,《序》:“刺幽王也。言鳏寡不能自存焉。”《诗序辨说》:“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
07 《小雅·裳裳者华》,《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则谗谄并进,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焉。”《诗序辨说》:“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说。”
08 《小雅·桑扈》,《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动无礼文焉。”《诗序辨说》:“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说。”
09 《大雅·行苇》,《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诗序辨说》:“此诗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说者不知比兴之体、音韵之节,遂不复得全诗之本意,而碎读之,逐句自生意义,不暇寻绎血脉,照管前后。但见‘勿践行
苇’,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但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但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但见‘介尔景福’,便为‘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伦理。诸序之中,此失尤甚。”
10 《大雅·既醉》篇,《序》云:“太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诗序辨说》云:“序之失如上篇(作文按:《大雅·行苇》),盖亦为孟子断章所误尔。”
11 《大雅·凫鹥》,《序》:“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祗祖考安乐之也。”《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大雅·既醉》)。”
三、傅会历史
傅会历史主要是因为汉儒过于迷信“风雅正变”之说,依据世次来定诗之美刺。凡是一篇诗,在汉儒看来一定是要对时政有所美刺的。凡是时代在前(周初文武成康时)的,一律是“美”;时代在后的,一般就认定是“刺”,而且往往要派附给恶谥之君。若是世次在后,而文意为美的,便说是“陈古刺今”。《诗序辨说》于《邶风·柏舟》篇对此辩驳尤为有力,朱熹指出:“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而其时世名氏,则不可以强而推。故凡《小序》,惟诗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于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诗序》)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傅会书史,依托名谥,凿空妄语,以误后人……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并对《诗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的傅会方法做了具体剖析,曰:“盖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以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甑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序予之。”朱熹的意思是:《诗三百》作品的文意,可以根据文本推敲而得;但其具体时代及当事人,却不能凭空傅会。《诗三百》作品的具体时代和当事人可分为三种类型:1、诗文自身已经明白指出的,如《陈风·株林》有“从夏南”(作文按:夏南,即夏徵舒,陈灵公时人。)之句;2、历史文献对其创作背景有明确记载的,如《左传·闵公二年》有云“许穆夫人赋《载驰》”;3、诗文自身及历史文献对其时代及当事人皆无具体说明的。相对来说,前两种类型是少数,《诗三百》多数作品属于后一种类型。对于这后一种类型,其时代及当事人实际是不可确考的,但是《诗序》却对其每一篇的时代及当事人都加以强行编派,这自然难免是“强不知以为知”,难逃后人“穿凿傅会”之讥。
朱熹在具体辩驳《诗序》傅会历史时,大抵不外乎以下三端:1、妄断世次;2、美刺不当;3、滥用“陈古刺今”。而这三者之间又往往呈交叉关系。
(1)妄断世次
朱熹对《诗序》在没有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强行编派《诗三百》作品以具体时代与当事人,很不满意。《诗序辨说》专辨此类情况的例子很多。一般来说,《序》对《诗三百》作品时代的认定,已经包含对当事人的认定在内。辩驳其具体时代与辩驳当事人往往是同一件事。有个别情况看上去比较特殊,如《小雅·大东》篇,《序》云:“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诗序辨说》云:“谭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据。”这似乎是专辨当事人的。但既然说当事人不可考,自然隐含时代不可考在其中了。
《正大雅》以及《周颂》的时代,朱熹与汉学诗经学在认识有较大分歧。《诗集传》于《大雅·文王之什》作结云:“《郑谱》此以上为文武时诗,以下为成王周公时诗。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则非文王之诗矣。又曰‘无念尔祖’,则非武王之诗矣。《大明》、《有声》,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为文武之时所作乎?盖《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后之诗,但些什皆追述文武之德,故《谱》因此而误耳。”郑玄《诗谱》认为《大雅》《文王有声》以上皆为文王、武王时诗,朱熹不以为然。对于《周颂》,《郑谱》认为都是周公所定;《诗序辨说》于《昊天有成命》、《执竞》二篇则对此专门辩驳(内容详见附录5),朱熹认为《周颂》亦有康王以后的作品。
朱熹还发现《序》对《诗三百》世次的编派有自相矛盾之处。《小雅·常棣》篇,《序》云:“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诗序辨说》云:“序得之,但与《鱼丽》之序相矛盾。以诗意考之,盖此得而彼失也。”按:《小雅·鱼丽》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常棣》篇目在《天保》之前,很明显,《序》者认为《常棣》的时代是文、武之时。但“管蔡之失道”却发生在武王去世以后。所以《诗集传》次章云:“此诗盖周公既诛管蔡而作……序以为闵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为文武之诗则误矣。大抵旧说诗之时世,皆不足信。举此自相矛盾者,以见其一端,后不能悉辨也。”
今检《诗序辨说》与《诗集传》,知朱熹明确辩驳《序》所编派世次与当事人者,共39处(详见附录5),实际篇目则为60篇,占《诗经》全部作品的20%左右。(计算方法:如《诗序辨说·秦风·车邻》云:“未见其必为秦仲之诗,大率《秦风》惟《黄鸟》、《渭阳》为有据,其他诸诗皆未有考。”按:《秦风》共有10篇作品,《诗序辨说》于《车邻》、《小戎》2篇有辩,又云《黄鸟》、《渭阳》有据,则“皆未有考”的“其他诸诗”包括《驷驖》、《蒹葭》、《终南》、《晨风》、《无衣》、《权舆》6篇。计算具体篇目时,应加入这6篇。余者依此类推,不另说明。)
附录5:朱熹辩驳《诗序》妄断世次例:
01 《召南·何彼襛矣》,《诗序辨说》“此诗世次不可知”。《诗集传》首章:“此乃武王以后之诗,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作文按:《序》以为二南皆文王时诗。)
02 《邶风·柏舟》,《序》:“卫顷公之时。”《诗序辨说》(略)。
03 《邶风·日月》,《序》:“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诗序辨说》:“此诗序以为庄姜之作,今未有以见其不然。但谓遭州吁之难而作,则未然耳。盖诗言宁不我顾,犹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无良,亦非所以施于前人者。明是庄公在时所作,其篇次亦当在《燕燕》之前。”
04 《邶风·终风》,《序》:“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诗序辨说》:“详味此诗,有夫妇之情,无母子之意。若是庄姜之诗,则亦当在庄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
05 《邶风·雄雉》,《序》:“刺卫宣公也。”《诗序辨说》:“未有以见其为宣公之时。”
06 《邶风·匏有苦叶》,《序》:“刺卫宣公也。”《诗序辨说》:“未有以见其为刺宣公、夫人之诗。”
07 《卫风·氓》,《序》:“刺时也。宣公之时,……”《诗序辨说》:“宣公未有考。”
08 《王风·君子于役》,《序》:“刺平王也。”《诗序辨说》:“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09 《郑风·狡童》,《序》:“刺忽也。”《诗序辨说》:“大抵序者之于郑诗,凡不得其说者,则举而归之于忽。”(作文按:《序》将郑诗归之于忽者,尚有《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
10 《齐风·鸡鸣》,《序》:“哀公荒淫怠慢。”《诗序辨说》:“哀公未有所考。”
11 《齐风·还》,《序》:“哀公好田猎。”《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鸡鸣》)。”
12 《齐风·甫田》,《序》:“大夫刺襄公也。”《诗序辨说》:“未见其为襄公之诗。”
13 《齐风·敝笱》,《序》:“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也。”《诗序辨说》:“桓当作庄。”
14 《唐风·采苓》,《序》:“刺晋献公也。”《诗序辨说》:“献公固喜攻战而好谗佞,然未见此二诗之作于其时也。”(作文按:包括前篇《葛生》。)
15 《秦风·车邻》,《序》:“美秦仲也。”《诗序辨说》:“未见其必为秦仲之诗,大率秦风惟《黄鸟》、《渭阳》为有据,其他诸诗皆未有考。”(作文按:包括《驷驖》、《蒹葭》、《终南》、《晨风》、《无衣》、《权舆》。)
16 《秦风·小戎》,《序》:“美襄公也。”《诗序辨说》:“此诗时世未必然。”
17 《陈风·墓门》,《序》:“刺陈佗也。”《诗序辨
说》:“陈国君臣,事无可纪。独陈佗以乱贼被讨,见书于《春秋》,故以无良之诗与之。序之作大抵类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18 《曹风·蜉蝣》,《序》:“昭公国小而迫。”《诗序辨说》:“言昭公未有考。”
19 《曹风·候人》,《序》:“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诗序辨说》:“此诗但以三百赤芾合于《左传》所记晋侯入曹之事,序遂以为共公,未知然否。”
20 《小雅·采薇》,《序》:“文王之时。”《诗序辨说》:“此未必文王之诗,以天子之命者衍说也。”
21 《小雅·出车》,《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采薇》)。诗所谓天子,所谓王命,皆周王耳。”
22 《小雅·杕杜》,《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出车》)。”
23 《小雅·南有嘉鱼》,《诗序辨说》:“又以专指成王,皆失之矣。”
24 《小雅·鸿雁》,《序》:“美宣王也。”《诗序辨说》:“此以下时世多不可考。”《诗集传》首章章末:“未有以见其为宣王之诗。后三篇(作文按:《庭燎》、《沔水》、《鹤鸣》)放次。”
25 《小雅·祈父》,《序》:“刺宣王也。”《诗集传》篇末:“今考之诗文,未有以见其必为宣王耳。”
26 《小雅·黄鸟》,《序》:“刺宣王也。”《诗集传》篇末:“今按诗文,未见其为宣王之世,下篇(作文按:《我行其野》)亦然。”
27 《小雅·斯干》,《序》:“宣王考室也。”《诗集传》篇末:“今亦未有以见其必为是时之诗也。”
28 《小雅·节南山》,《序》:“家父刺幽王。”《诗集传》篇末:“序以此为幽王之诗。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来聘,于周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终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异。大抵序之时世皆不足信,今姑阙焉可也。”
29 《小雅·雨无正》,《序》:“大夫刺幽王也。”《诗集传》篇末:“其为幽王诗,亦未有所考。”
30 《小雅·何人斯》,《序》:“苏公刺暴公也。”《诗序辨说》:“但此诗中只有暴字,而无公字及苏公字,不知序何所据而得此事也。”《诗集传》:“旧说暴公为卿士,而谮苏公,故苏公作诗以绝之……但旧说于诗无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也。”
31 《小雅·大东》,《序》:“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诗序辨说》:“谭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据。”
32 《小雅·鼓钟》,《序》:“刺幽王也。”《诗序辨说》“此诗文不明,故序不敢质其事,但随例为刺幽王耳。实皆未可知也。”
33 《小雅·黍苗》,《序》:“刺幽王也。”《诗序辨说》:“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
34 《小雅·渐渐之石》,《序》:“下国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序得诗意,但不知果为何时耳。”
35 《大雅·文王有声》,《序》:“继伐也。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卒其伐攻也。”《诗序辨说》:“《郑谱》之误,说见本篇。”《诗集传》篇末:“《郑谱》此以上为文武时诗,以下为成王周公时诗。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则非文王之诗矣。又曰无念尔祖,则非武王之诗矣。《大明》、《有声》,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为文武之时所作乎?盖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后之诗,但些什皆为追述文武之德,故《谱》因此而误耳。”
36 《大雅·假乐》,《序》:“嘉成王也。”《诗序辨说》:“假本嘉字,然非为嘉成王也。”
37 《大雅·公刘》,《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诗序辨说》:“然此诗未有以见其为康公之作意,其传授或有自来耳,后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作文按:包括《泂酌》、《卷阿》、《民劳》、《板》、《荡》。)
38 《周颂·昊天有成命》,《诗序辨说》:“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后祀成王之诗无疑。而毛、郑旧说,定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故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两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己意。其淤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
39 《周颂·执竞》,《诗序辨说》“此诗并及成康,则序说误矣。其说已具于《昊天有成命》之篇。”
(2)美刺不当
《序》者以美刺说诗,认为《诗三百》皆是美刺国君时政之作,朱熹于此深为不满。《朱子语类》颇多这方面的意见:
01 “温柔敦厚”,诗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讥刺人,安得“温柔敦厚”!(80/2065,滕璘记)
02 《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80/2074,郑可学记)
03 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如此,亦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雕,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情性之正?(80/2076—2077,叶贺孙记)
04 《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诗虽存,而意不可得。序诗者妄诞其说,但疑见其人如此,便以为是诗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庄姜之诗,却以为刺卫顷公。今观《史记》所述,顷公竟无一事可纪,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无其事。顷公固亦是卫一不美之君。序诗者但见其诗有不美之迹,便指为刺顷公之诗。此类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无其实。至有不能考者,则但言“刺诗也”,“思贤妃也”。然此是泛泛而言。(80/2078,黄卓记)
…………
以上四条材料说明:朱熹认为《诗三百》中应该颇有一些作品与今人作诗是同样的情形,不过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而已,未必都是讥刺他人。如果篇篇都是讥刺国君,又哪里能算“温柔敦厚”呢?但是《诗序》却是以美刺说诗,对每一篇作品都要来一个或“美”或“刺”的解释,这有什么道理呢?在《诗》辞文意与背景条件两方面都不能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序》凭什么断定一篇作品一定是美(或刺)那个人(具体的国君)呢?在朱熹看来,《诗序》“美刺不当”之处实在是太多了。朱熹指陈《诗序》“美刺不当”,大抵分两种类型:一是诗文自身本无关美刺的;二是《序》所认定的“美”“刺”与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的。
“无关美刺”的典型是“淫诗”。如《鄘风·桑中》篇,《序》云:“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诗集传》云:“此人自言将采唐于沫,而与其所思之人,相期会迎送如此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序》者认为该篇是诗人刺淫奔之作;朱熹则认为是淫奔者所自作,是“淫者”自叙其事,自抒其情,与美刺无关。又如《陈风·防有鹊巢》,《序》云:“忧谗也。宣公多信谗,君子忧惧焉。”《诗集传》云:“此男女之有私,而忧或间之之辞。”《诗序辨说》云:“此不得为刺诗。”《序》者认为该篇是刺宣公(信谗)的,朱熹则认为是淫奔男女“忧或间之之辞”,与刺宣公全不相关。(关于“淫诗”的问题,将在论文的第二章专门讨论。朱熹认定《诗三百》中共有“淫诗”28篇。)
“淫诗”之外,朱熹亦指出另外一些篇目本“无关美刺”,但《序》者却以美刺说之。如《邶风·凯风》篇,《序》云:“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诗序辨说》云:“此乃七子自责之辞,非美七子之作也。”既是“自责”,自然无关美刺。这是无关美刺而《序》者以为“美”的例子。
至于无关美刺而《序》者以为“刺”的,有6例(附录6)。
附录6:《诗序辨说》指陈无关美刺而《序》者以为刺例:
01 《郑风·叔于田》,《序》:“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说而归之。”《诗序辨说》:“国人之心贰于叔,而歌其田狩适野之事,初非以刺庄公,亦非说其出于田而后归之也。”
02 《郑风·大叔于田》,《序》:“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诗序辨说》:“此诗与上篇(作文按:《叔于田》)意同,非刺庄公也。”
03 《唐风·绸缪》,《序》:“刺晋乱也。国乱则昏姻不得其时也。”《诗序辨说》:“此但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词,未必为刺晋国之乱也。”
04 《小雅·小宛》,《序》:“大夫刺幽王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不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乱畏祸而相戒之辞尔。”
05 《小雅·绵蛮》,《序》:“微臣刺乱也。大臣不用仁心,遗忘微贱,不肯饮食教载之,故作是诗也。”《诗序辨说》“此诗未有刺大臣之意,盖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则褊狭之甚,无复温柔敦厚之意。”
06 《大雅·抑》,《序》:“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诗序辨说》:“其曰刺厉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
在朱熹看来,例01、例02是国人歌唱叔段的,与刺庄公本无关系。例03是“为昏姻者相得而喜”,例04是兄弟之间自相劝诫,例05是微臣自道其心之所欲,例06是卫武公自警,自然都与美刺无关了。
朱熹认为《序》所认定的“美”“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有两种类型:一是本当为“刺”,而《序》以为“美”;二是本当为“美”,而《序》以为“刺”。前者的典型例证是《唐风·无衣》,该篇《序》云:“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诗序辨说》云:“序以为美之,失其旨矣。”后者有5例(附录7)。
附录7:《诗序辨说》指陈《序》误美为刺例:
01 《卫风·考槃》,《序》:“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诗序辨说》:“此为美贤者穷处而能安其乐之诗,文意甚明。然诗文未有见弃于君之意,则亦不得为刺庄公矣。”
02 《魏风·伐檀》,《序》:“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诗序辨说》:“此诗专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贪,失其旨矣。”
03 《曹风·鸤鸠》,《序》,“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诗序辨说》:“此美诗,非刺诗。”
04 《小雅·隰桑》,《序》:“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诗序辨说》:“此亦非刺诗。疑与上篇(作文按:《黍苗》)脱简在此也。”
朱熹批评《序》者“美刺不当”,“刺”者不当的例子比“美”者不当的要多,这是因为《序》所认定的“刺”诗比“美”诗多。《序》者编派刺诗世次的通例是刺以谥恶而得之。《朱子语类》有云:“问:《诗传》尽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硕人》、《定之方中》等,见于《左传》者,自可无疑。若其他刺诗无所据,多是世儒将他谥号不美者,挨就立名尔。”(80/2078,余大雅记)又云:“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谥,却傅会作《小序》美刺。”(《朱子语类》,80/2079,吴振记)。这与前引《诗序辨说·邶风·柏舟》篇所论,强调的都是“刺以谥恶而得之”这一个通例。《邶风·柏舟》篇之外,《诗序辨说》尚于其他5篇指出《序》所刺国君是因为其谥恶(附录8)。
附录8:《诗序辨说》指陈“刺以谥恶而得之”例:
01 《齐风·鸡鸣》,《序》:“哀公荒淫怠慢。”《诗序辨说》:“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岂亦以谥恶而得之欤?”
02 《齐风·还》,《序》:“哀公好田猎。”《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鸡鸣》)。”
03 《唐风·蟋蟀》,《序》:“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娱乐也。”《诗序辨说》:“所谓刺僖公者,盖特以谥得之。”
04 《陈风·宛丘》,《序》:“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诗序辨说》:“陈国小,无事实。幽公但以谥恶,故得游荡无度之诗。未敢信也。”
05 《陈风·东门之粉》,《序》:“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宛丘》)。”
综上,朱熹直接指出《诗序》“美刺不当”的有46篇,占《诗经》全部作品的15%左右。(其中“无关美刺”的35篇:“淫诗”28篇之外,《序》者误以为“美”的1篇,误以为“刺”的6篇。《序》所认定的“美”、“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5篇:误“美”为“刺”的1篇,误“刺”为“美”的4篇。“刺以谥恶而得之”的6篇。)
(3)滥用“陈古刺今”
前引《诗序辨说·邶风·柏舟》篇云:“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序》者以美刺说诗,又囿于“风雅正变”之说,于《变风》、《变雅》非美谥贤君之时而辞意为美者,便一律说成是“陈古刺今”。《诗序辨说·郑风·羔裘》云:“序以《变风》不应有美,故以此为言古以刺今之诗。今详诗意,恐未必然。且当时郑之大夫,如子皮、子产之徒,岂无可以当此诗者?但今不可考耳。”亦指出《序》以该篇为“陈古刺今”,是基于“《变风》不应有美”这一认识。《诗序辨说·小雅·楚茨》云:“自此篇至《车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无讽刺之意。序以为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诗固有如此者,然不必十篇相属,而绝无一言以见其为衰世之意也。窃恐《正雅》之篇有错脱在此耳,序皆失之。”朱熹以词气为根据,判断《小雅》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
华》、《桑扈》、《鸳鸯》、《頍弁》、《车舝》这十篇作品是“美诗”而非“刺诗”,并指出《序》者以之为“刺诗”的原因是它们在《变雅》之中,被当成了“伤今思古之作”。朱熹对这种“陈古刺今”的理解实不以为然。《朱子语类》云:“《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傅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便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甚多。”(80/2074,郑可学记)。也是批评《序》者说诗滥用“陈古刺今”。
《小序》明言“陈古刺今”的有13处,其篇目如下(附录9)。
附录9:《小序》明言“陈古刺今”例:
01 《王风·大车》,“大车,刺周大夫也。礼义陵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焉。”
02 《郑风·羔裘》,“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诗序辨说》:“序以变风不应有美,故以此为言古以刺今之诗。今详诗意,恐未必然。且当时郑之大夫,如子皮、子产之徒,岂无可以当此诗者?但今不可考耳。”
03 《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诗序辨说》:“此亦未有以见陈古刺今之意。”
04 《齐风·卢令》,《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猎毕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陈古以风焉。”
05 《小雅·楚茨》,《序》:“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谨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诗序辨说》:“自此篇至《车舝》凡十篇(作文按:1、《楚茨》,2、《信南山》,3、《甫田》,4、《大田》,5、《瞻彼洛矣》,6、《裳裳者华》,7、《桑扈》,8、《鸳鸯》,9、《頍弁》,10、《车舝》。),似出一手,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无讽刺之意。序以为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诗固有如此者,然不必十篇相属,而绝无一言以见其为衰世之意也。窃恐《正雅》之篇有错脱在此耳,序皆失之。”
06 《小雅·信南山》,《序》:“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07 《小雅·甫田》,《序》:“刺幽王也。君子伤今而思古焉。”
08 《小雅·瞻彼洛矣》,《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诸侯,赏善罚恶焉。”
09 《小雅·鸳鸯》,《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万物有道,自奉养有节焉。”
10 《小雅·鱼藻》,《序》:“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诗序辨说》:“此诗序与《楚茨》等篇相类。”
11 《小雅·采菽》,《序》:“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诗序辨说》:“同上。”
12 《小雅·都人士》,《序》:“周人刺衣服无常也。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一。伤今不复见古人也。”
13 《小雅·瓠叶》,《序》:“大夫刺幽王也。上弃礼而不能行,虽有牲牢饔饩,不肯用也。故思古人不以微薄废礼焉。”
这13例以外,《小雅·黍苗》篇《序》云:“刺幽王也。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郑笺》云:“陈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群臣废此恩泽事业焉。”《诗序辨说》云:
“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乃指今之卿士不能行周宣王时召穆伯之职,实际上也是“陈古刺今”。另有一些篇目,《诗序》虽未明言是“陈古刺今”,但《郑笺》、《孔疏》却指出其是“陈古刺今”。如《小雅·大田》篇,《序》云:“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也”,并未明言该篇是“陈古刺今”;《郑笺》却云:“幽王之时,政烦赋重而不务农事,虫灾害谷,风雨不时,万民饥馑,矜寡无所取活,故时臣思古以刺之”,明确指出是“陈古刺今”。《孔疏》亦云:“四章皆陈古善反以刺王之辞。”
“陈古刺今”是汉学诗经学说《诗》的一个通例。朱熹对汉学诗经学以“陈古刺今”为由所认定的“刺诗”,大抵都以其辞意为根据,当作美诗来理解。再如《齐风·鸡鸣》一篇,《诗序》云:“《鸡鸣》,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诗集传》首章云:“言古之贤妃御于君所,至于将旦之时,必告君曰:鸡既鸣矣,会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视朝也。……故诗人叙其事而美之也。”是朱熹以为该篇亦是“陈古”,但却不是“刺今”,所以将其视为“美诗”。
《诗序辨说》还对《序》所认定的诗之作者有所辩驳,这以“淫诗”最为典型。我们在论文第二章论朱熹对《诗经》抒情主体性的认识时,将对这个问题作专门讨论。朱熹将“淫诗”处理为“淫者”自作,与《序》者理解为诗人刺淫大异其趣。“淫诗”之外,《诗序辨说》也对一些篇目《序》所认定的作者提出了质疑。如《小雅·小弁》篇,《序》云:“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诗序辨说》云:“此诗明白为放子之作无疑,但未有以见其必为宜臼耳。序又以为宜臼之傅,尤不知所据也。”
四、杨慎、姚际恒等论朱熹废《序》
后人对朱熹废《序》,有两种批评意见影响较大。一是认为朱熹废《序》实乃出于一时偏激;二是认为朱熹废《序》太不彻底。前一种意见以杨慎和《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后一种意见的始作俑者是姚际恒。
《四库全书总目·诗集传提要》云:“杨慎《丹铅录》谓文公因吕成公太尊《小序》,遂尽变其说。虽臆度之词,或亦不无所因欤!”今检杨慎《丹铅余录·总录(卷十八)·诗小序》,有云:朱子作《诗传》,尽去《小序》,盖矫吕东莱之弊。一时气使之偏,非公心也。马端临及姚牧庵诸家辨之悉矣。有一条可发一笑,并记于此。《小序》云“菁莪,乐育人才也”,“子衿,学校废也”,《传》皆以为非。及作《白鹿洞赋》,有曰“广青衿之疑问”,又曰“乐菁莪之长育”。或举以为问,先生曰:“旧说亦不可废。”此何异俗谚所谓“玉波去四点,依旧是王皮”乎!
愚按:杨慎此说颇可商榷。吕东莱是宋代诗经学遵《序》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对其太尊《小序》颇有微词,这是事实。《朱子语类》中颇多议论吕东莱太尊《小序》之处,如:
01 伯恭专信《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要出脱回护。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80/2074,邵浩记)
02 东莱《诗记》却编得子细,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说甚么?向尝与之论此,如《清人》、《载驰》一二诗可信。渠却云:安得许多文字证据?某云:无证而可疑者,只当阙之,不可据《序》作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
也。此是《序》者大害处!(80/2076—2077,叶贺孙记)
03 问:《诗传》多不解《诗序》,何也?曰: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缪戾,有不可胜言。东莱不合只因《序》讲解,便有许多牵强处。某尝与言之,终不肯信。《读诗记》中虽多说《序》,然亦有说不行处,亦废之。某因作《诗传》,遂成《诗序辨说》一册,其他缪戾,辨之颇详。(80/2078,李煇记)
这三条都是批评吕东莱太尊《小序》,其所著《读诗记》亦不得诗人本意。朱熹废《序》,且对吕东莱太尊《小序》有专门批评,确实也可以说是欲矫其弊。但这并不是一种意气之争,而是两个学派、两种不同说诗方法之争。在这里,吕东莱和朱熹是作为两个学派的代表,吕东莱是尊《序》派的代表,朱熹是废《序》派的代表。朱熹对吕东莱的批评实际是对整个尊《序》派的批评,这要远远超过对具体个人的批评。朱熹以“求诗意于辞之中”为根本方法,一切以文本自身为根据,揆以情理,考诸书史,进而发现《序》多不合于《诗》本意,这是他废《序》的根本原因。朱熹废《序》实有深刻的思考与系统的理论根据为基础,而非一时冲动。况朱熹自言“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缪戾,有不可胜言”。朱熹年长于吕东莱七岁,朱熹二十、三十之时,吕东莱尚未著《读诗记》,何可言朱子废《序》是受吕东莱的刺激?!杨慎之说固为臆度之词矣。杨慎“一时气使之偏,非公心也”之说,实厚诬古人。《四库全书总目》引申杨慎之说,云“遂尽变其说”,其意以为此前朱熹解《诗》是依《序》说解,待吕东莱《读诗记》成书之后,出于意气之争,乃废《序》不用,实亦出于汉学一派的立场党同伐异,有失公允。
又杨慎所引《白鹿洞赋》亦不能说明问题。典故的应用大抵是出于一种传统习惯,其本身有一个积淀过程。典故用得久了,其文本背景也就逐渐淡化,可以与其在文本中的本意有距离。这可以从我们今天的情形反过来逆推:譬如一个大学搞校庆,纪念文章里大可以用“子衿”、“菁莪”的典故,这典故自然是本于《序》和《毛传》的解说,是比喻学校教育的,但文章的作者,作为一个现代人,他对“子衿”一诗的理解恐怕自然是当作爱情诗的。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将“子衿”当典故来用,全不妨碍对其诗爱情主题的理解。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做,朱熹又为什么不能呢?杨慎的这条理由实在也没有道理。
尊《序》一派的人批评朱熹不该废《序》,废《序》派中则有人批评朱熹废《序》太不彻底。姚际恒《诗经通论·自序》①批评朱熹:“作为《辨说》,力诋《序》之妄,由是自为《集传》,得以肆然行其说;而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而且违其所是,从其所非焉。武断自用,尤足惑世。”《诗经通论》卷前《诗经论旨》又云:“其从《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不从而阴合之者,又有意实不然之而终不出其范围者,十之二三,故愚谓:遵《序》者莫若《集传》。”
夏传才亦云:
朱熹具有一定进步性的治学方法,和他的根本立场观点产生了矛盾。他一方面力图探求三百篇的本义,一方面又要宣扬封建礼教。他突破传统《传》、《序》、《笺》、《疏》的束缚,考证求实,就本文理解诗义时,能够获得一些正确和接近正确的认识,但他不能越过封建礼教的藩篱;一碰到这个藩篱,他就要缩回来。封建卫道的理学家朱熹,不可能进行彻底的自由研究,为了宣扬圣道王化、三纲五常,他又不能不回到穿凿傅会曲解诗义的老路上去,用新的穿凿傅会来代替旧的穿凿傅会。
正因为如此,朱熹一方面废弃《诗序》,并对《诗序》进行了总的批判;一方面又在对诗篇的具体解释中,自觉不自觉地继承《诗序》的一些说法:在《诗集传》中有些题解公开袭用,说《诗序》“斯言得之”或“庶几近之”;有些则改头换面,偷偷地贩运进来。清代人早看到朱熹的这个毛病,姚际恒就批评他“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朱熹反《诗序》又是不彻底的。①
这种意见有无道理呢?窃以为当析而言之。《诗集传》有些地方沿袭了《诗序》,这是事实。但“遵《序》者莫若《集传》”恐非持平之论。
关于《诗集传》题解与《诗序》的关系,莫砺锋《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②一文,有很具体的统计分析。他将《诗集传》题解与《诗序》的关系分为五种类型:1、《诗集传》采用《小序》说;2、《诗集传》不提《小序》而全袭其说;3、《诗集传》与《小序》大同小异;4、《诗集传》与《小序》说不同;5、《诗集传》认为应存疑。并做了张详细的统计表,其表如下(按:不包括六篇笙诗):
根据这张统计表,他说:
一、二两类共计82首,也即朱熹同意《小序》说的诗共占《诗经》总数的27%。三、四两类共几215首,也即朱熹对《小序》说有异议的诗共占《诗经》总数对70%。这说明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但是改正《小序》说的比较多。这几种情况在全书各部分所占的比重也不一致。比如在《郑风》21篇中,《诗集传》与《小序》说不同的就有14篇,占三分之二。这主要是因为《郑风》中民间情歌特别多,所以受到《小序》的歪曲也特别严重。这说明《诗集传》对《小序》的修正,主要是针对那些受到《小序》严重歪曲的诗篇而发的。相形之下,《诗集传》对诗义的解释要比《小序》正确。……总之,《诗集传》采取《小序》说的大多是确有根据的说法,朱熹对《小序》的取舍态度是比较慎重、正确的,后代的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小序》,对朱熹的“废序”颇有微词,实在是出于偏见。
笔者以为“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但是改正《小序》说的比较多”这一结论是比较中肯的。这里对其略作补充说明:
莫先生将“《诗集传》与《小序》说不同”的情况分为以下两种类型:1、“释义截然不同”;2、“释义无大分歧,但认为其为刺为美则截然相反”。实际上,第一种类型主要是淫诗,第二种类型即笔者所论朱熹批评《序》者滥用“陈古刺今”。莫先生将“《诗集传》与《小序》大同小异”的情况分为以下4个类型:1、“释义稍有不同”;2、“释义基本相同,但《小序》拘于‘美刺’之说,在进一步的阐发时就犯了穿凿傅会的错误”;3、“释义基本相同,但对诗的作者说法不同”;4、“释义基本相同,但对作诗的时代说法不同”。其实,莫先生的第2、3、4三种类型,即笔者所论朱熹辩驳《序》者“妄断美刺”、“误认作者”、“妄断世次”。此三端,皆《诗序辨说》孜孜以驳,于朱熹自身而言,应该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至于第一种类型,莫先生举的例是《周南·桃夭》篇,该篇《序》云:“后妃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昏姻以时,国无鳏民也。”《诗集传》云:“文王之化,自家而国,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故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而叹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莫先生认为二者实无本质差别;但也承认存在两处差异:(1)《小序》是归美后妃,《诗集传》是归美文王;(2)《小序》着眼于男子不作鳏民,《诗集传》着眼于女子能宜室家。笔者以为这两处差异对朱熹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朱子语类》有云:“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桃夭》之诗谓‘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为文王刑家及国,其化固如此,岂专后妃所能致耶?”(80/2075,周谟记)。《诗集传》于《周南》总结亦云:“今言诗者,或乃专美后妃,而不本文王,其亦误矣。”可见在朱熹看来《序》者理解为专美后妃,是“大无义理”的。另外,《序》所云“男子不作鳏民”恐非诗辞本文所有之意,《诗集传》“女子能宜室家”则切合文本自身。这一细微差异实际反映了朱熹说《诗》最重文本的态度。朱熹《诗集传》往往于细微处见精神,莫先生认为是“小异”的地方,从朱熹自身的立场来看,实未必只是“小异”。
朱熹废《序》的初衷是《序》多不合于《诗》本意,且有害于后人对《诗》的理解。朱熹本人解《诗》的原则是“涵泳本文”、“求诗本意”;辩驳《诗序》的手段无外乎文本、情理与文献根据这三端。《诗集传》之题解与《小序》有异有同,大抵是实事求是,根据其本人“涵泳”所得,同于其所当同,异于其所不得不异。
对于《诗集传》沿袭《诗序》之处亦当析而言之:有些是沿袭了其错误,有些则不是。如《召南·野有死麕》篇,《序》云:“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诗序辨说》云:“此序得之”,是朱熹于此篇之意见同于《序》说。但此诗之第三章云:“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哪里是凛然拒绝的口气!?王柏《诗疑》尚且能以之为“淫诗”,分明看出其间真意。朱熹此处沿袭《序》说,自然是“从其所非”了。这种情形,《诗集传》中确有不少,我们也不必为贤者讳。但多数时候,朱熹从《序》则是有正当理由的,大抵是因为《序》有经文、史传之证。《诗序辨说》颇有指出《序》有经文、史传之证,故不误的例证,请看附录10。
附录10:《诗序辨说》明言《序》有经文、史传之证,故不误例:
01 《鄘风·干旄》,《诗序辨说》:“《定之方中》一篇,经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误。”
02 《鄘风·载驰》,《诗序辨说》:“此亦经明白,而序不误者。又有《春秋传》可证。”
03 《卫风·硕人》,《诗序辨说》:“此序据《春秋传》,得之。”
04 《齐风·南山》,《诗序辨说》:“此序据《春秋》经传为文,说见本篇。”
05 《唐风·扬之水》,《诗序辨说》:“诗文明白,序说不误。”
06 《秦风·黄鸟》,《诗序辨说》:“此序最为有据。”
07 《陈风·株林》,《诗序辨说》:“《陈风》独此篇为有据。”
08 《豳风·鸱枭》,《诗序辨说》:“此序以《金滕》为文,最为有据。”
…………
以上诸例,或者经文自身明白,或者《春秋》经传对其创作背景有明确说明,《序》者以此二端为根据,自然不至于有很大偏差。这种情况下,朱熹对诗义的理解自然与《序》者一样。这并不是个沿袭的问题,而是不得不同于其所当同。如果不这样,才是应了姚际恒的批评——“违其所是”呢!
朱熹批评《序》者说诗惯于傅会历史,大抵是针对历史文献对诗之创作背景没有明确记载的情况而言。前文所论《序》者“妄断世次”与依谥编派刺诗是其具体表现。对于《序》者所言有文献根据,但诗文自身未必与之相合的情况,朱熹又常常采取“或然”(有时用“姑从”)的态度。如《邶风·击鼓》篇,《序》云:“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诗集传》次章云:“旧说以为此春秋隐公四年……之事,恐或然也。”《诗序辨说》云:“《春秋》隐公四年,宋、卫、陈、蔡伐郑,正州吁自立之时也。序盖据诗文平陈与宋而引此为说,恐或然也。”按:《序》所云州吁命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春秋》有明文记载;但《击鼓》诗所云,可能指这件事,也可能不指这件事。一定要肯定其是或不是指这件事,都嫌失之武断。朱熹云“恐或然也”正是慎重的态度。此例甚多,兹不枚举。
即使同一篇《诗序》之中,朱熹亦大抵能从其所是,弃其所非。如《诗序辨说·秦风·小戎》云:“此诗时世未必然;而义则得之。”朱熹认为《序》所认定世次靠不住,故不取;但认为所说诗义可取。又如《周南·葛覃》,《序》云:“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恭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之妇道也。”《诗集传》云:“《小序》以为后妃之本,庶几近之。”《诗序辨说》云:“此诗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谓在父母家者一句为未安。盖若未嫁之时,即诗中不应遽已归宁父母为言……”对小序可取之处给以肯定,对其不妥之处亦指出,正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再如《大雅·抑》篇,《序》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之序,有得有失……以诗考之,则其曰刺厉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是这种态度。
可以说,在根本说《诗》方法上,朱熹与《序》者有“求诗意于辞之中”与“求诗意于辞之外”的分歧,而且朱熹认为《序》有害于读者对《诗》义的理解。所以朱熹对《诗序》是从整体上给以否定的。但在《诗集传》具体解诗时,对待《诗序》的态度,大抵是同于其所当同、异于其所不得不异,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姚际恒“遵《序》者莫若《集传》”之论失于偏激;杨慎的批评更嫌武断,近于臆说。
第三节 学术背景的考察
[《周易本义》欧阳修《诗本义》等“本义”溯源]
一、《周易本义》
涵泳文本、求其本义是朱熹治《诗经》学的根本方法。这一方法又不限于《诗经》一门,实际上,朱熹治一切古籍大抵都能坚持这一方法,而以治《易》尤为典型。朱熹著有《周易本义》一书,从书名自身即可看出其旨趣。朱熹治《易》学,有两样基本主张:一是《易》本为卜筮而作。二是《易》之经传各自为说,不必据传解经。所谓《易》本义即指《易》本为卜筮之书,不是为义理而作。求易本义有两层意义:一是不作义理上的傅会;二是不依传解经。
《汉书·艺文志》云:
《易》曰:“宓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所谓《易》之经即指伏羲与文王所作的部分——卦象及卦爻辞,《易》之传指孔子所作十篇(习惯上称为“十翼”)。关于《周易》经传的形成,自《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说后,易学界一直把《周易》经传看成是周孔之道的体现,认为伏羲画卦,周文王作卦爻辞,孔子作传,三圣之业一脉相承,并无差别。因而对《周易》一书的理解,都依传文义解释经文。由于依传解经,将《周易》一书进一步哲理化,《周易》作为占筮的典籍,其本来的面貌则被湮没了。直到北宋欧阳修提出《系辞》非孔子所作,这种传统的观念才发生动摇。
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下)有云:
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
欧阳修对《易》传的判断与批评和朱熹对《诗序》的批评很相似:朱熹认为《序》非圣人作,依《序》说诗有害于后人对《诗经》的理解;欧阳修认为《易》传(大部分)非圣人作,后人依之解经,“至使害经而惑世”。
在《系辞》作者的这一问题上,朱熹并不赞成欧阳修的说法,仍认为《系辞》为孔子所作,但他对《周易》的理解,却受到欧阳修易说的影响。
关于《周易》经传的形成,朱熹取四圣说,即: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重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传;并认为四圣皆以《周易》为卜筮之书。《朱子语类》有云:
《易》本为卜筮之书……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想当初伏羲化卦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66/1622,甘节记)
朱熹易“三圣说”为“四圣说”的理由是“谓《爻辞》为周公者,盖其中有说文王,不应是文王自说”。(67/1846,叶贺孙记)但有些时候,他又往往将文王说与周公说视作一个整体。朱熹屡屡强调伏羲《易》、文王周公《易》与孔子《易》各自为阵,不宜强为牵合。且看《朱子语类》里的言论:
01 学《易》者须将《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做一意看,不得。(66/1622,辅广记)
02 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66/1630,沈僩记)
03 须是将伏羲画底卦做一样看,文王卦做一样看;文王周公说底《彖》、《象》做一样看,孔子说底做一样看,王辅嗣伊川说底各做一样看。(67/1645,渊记)
朱熹强调伏羲《易》、文王周公《易》与孔子《易》牵合不得,乃是因为其间有不吻合之处,《朱子语类》有云:
01 《乾》之“元亨利贞”,本是筮得此卦,则大亨而利于守正,而《彖辞》、《文言》皆以为是四德。某常疑如此等类,皆是别立说以发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马之贞”,则发得不甚相似矣。(67/1645,杨道夫记)
02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书。(67/1645,廖德明记)
文王卦与伏羲卦已自不同,孔子《十翼》与文王周公卦爻辞又有理解上的分歧,离则双美,合者两伤,故不如各自做一样看。汉至唐的易学家将三者当作一个整体,弥缝于其间,自然难免于牵强。《易》之经传既各自为体,自然不必依传解经。
朱熹屡次强调《易》本卜筮之书,至孔子作《十翼》方始
从义理上着眼,《朱子语类》有云:“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话说!文王重卦作《系辞》,周公作《爻辞》,也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66/1622,辅广记)。朱熹还明确指出孔子说《易》不得易本义,请看《朱子语类》中这一段文字:
据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今人说得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说虽粗,然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某一人说,则晓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用,元未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读伏羲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画八卦,那里有许多文字言语,只是说八个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其大要不出于阴阳刚柔、吉凶消长之理。然亦尝说破,只是使人之卜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今人未曾明得《乾》、《坤》之象,便先说《乾》、《坤》之理,所以说得都无情理。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古人占处说,如卜得《乾卦》,则大亨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要说出来。孔子之心,又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只认各人自说一副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说《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样。某所以不敢从,而原《易》之所以为作而为之说,为此也。(66/1630,沈僩记)
朱熹认为当初伏羲画卦,只是为了卜筮,占卦象之阴阳,卜人事之吉凶,而无关于义理。圣贤如孔子,以义理说《易》,尚且被朱熹说作“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至如后人纷纷以义理说《易》,不顾《易》本卜筮之书的事实,朱熹更是给以严厉批评。其《答吕伯恭》书(见《朱熹集》卷33,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458—1459页)云:“窃疑卦爻之词,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以训诫。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诫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容该贯曲畅旁通之妙。”《朱子语类》亦云:“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做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66/1622,辅广记)。
《朱子语类》又云:
《易》以卜筮用,道理便在里面,但只未说到这处。如《楚辞》以神为君,祀之者为臣,以见其敬奉不可忘之义。固是说君臣,但假托事神而说。今也须与他说事神,然后及他事君之意。今解直去解作事君,也未为不是;但须先为他结了事神一重,方及那处,《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说他本意,便将理来衮说了。(66/1635,林学履记)
据此,是朱熹并不反对根据《易》来说道理,但朱熹强调首先要将《易》作卜筮之书看,就卜筮来探讨其本意。在得其本意之后,再借以说明道理是可以的;但如果没有求本义在先,一上来就大谈义理,则不可取。《楚辞·九歌》是祀神之曲,其本意是讲事神的;必须先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意义上解释诗意,然后才可以作事君的发挥。“今也须与他说事神,然后及他事君之意”,这里的先后至关重要,这实际是承认文本的独立地位具有优先原则。作为理学大师的朱熹,义理是其治学的根本。但在注解经典古籍时,他始终将文本放在第一位,尊重文本的独立性地位,然后才是义理上的发挥。朱熹诗经学实极重视“养心劝惩”、“变化气质”,但在说解《诗三百》文意时,他能始终贯彻“求诗意于辞之中”的原则。汉学诗经学正是缺少了这一个环节,拿义理来直接套文本,忽视了文本的独立性地位。朱熹批评后人依《序》说诗,也正是因为后人将第二位的阐释置于了第一位的《诗三百》文本之上。对《易》来说,经的部分实际可视做文本自身,传的部分则是后人阐释。尽管其阐释者是孔子,是儒家的大圣人,但相对于经作为文本自身的第一性来说,它也只能是第二位的。求易本义,当就经解经,而不当依传解经。所以《朱子语类》说:“《易》本为卜筮之书……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系辞》,是犹不看《刑统》,而看《刑统》之《序例》也,安能晓!今人须以卜筮之书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66/1622,甘节记)。
《朱子语类》颇载朱熹教诲弟子读《易》之法:
01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之《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学者且依故《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矣。(66/1648,李方子记)
02 读《易》之法,先读正经。不晓,则将《彖》、《象》、《系辞》来解。(77/1661,甘节记)
03 看《易》,且将《爻辞》看。理会得后,却看《象辞》。(77/1661,胡泳记)
“先读正经”,“先读本爻”,正如先读《诗经》本文,正是尊重文本独立性,求其意于辞之中的方法。
朱伯崑对朱熹在易学上的贡献有一段很好的概括:
朱熹关于《周易》经传的论述,在易学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从汉朝以来,无论是义理学派还是象数学派,其解易都是经传不分,以传解经,并且将经文部分逐渐哲理化。到宋代易学家将《周易》视为讲哲理的教科书,特别是程氏《易传》,由于突出以义理解易,使《周易》丧失了其本来面貌。而朱熹则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研究《周易》经传,以经为占筮的经典,以传为后来讲义理或哲理的著述,认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脱离筮法解释《周易》,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言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还以这种观点研究了易学的历史。认为从汉易京房到程氏易学,各成一家之言,其解易并非就是《周易》经传之本义,但如其说出一番道理,亦应肯定,不应抛弃。①
我们可以说朱熹《周易本义》不依传解经,同于其《诗集传》不依《序》说诗。反对易学史上的过多义理傅会,亦正如反对毛、郑一派一味以美刺说《诗》。这正可以说明朱熹治经典古籍之学的一贯态度。
二、欧阳修《诗本义》等
求本义实乃有宋学术一大思潮,不独朱熹一人而已。如欧阳修《易童子问》以系辞非孔子作,苏轼、苏辙兄弟对《尚书》等古籍的新注,郑樵《诗辨妄》等书的写作,尽管对旧说之扬弃在程度上或有大小之分,但都能独立思考,求经书本来之面目。宋人对《诗经》的研究,尤能见其求本义之学术风气。
在朱熹之前,宋人之中,以欧阳修、苏辙、郑樵三人在求诗本义上贡献最大。这三个人,郑樵大抵是坚决废《序》的,苏辙仅取《序》之首句,欧阳修虽未有废《序》之论,但在求诗本义的理论建设上功不可没。
先说郑樵。郑樵的很多见解都为朱熹所接受,朱熹在诗经学著作中屡次提及郑樵:
01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80/2076,叶贺孙记)
02 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谥,却傅会作《小序》美刺。(80/2079,吴振记)
03 旧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某近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意自见。(80/2068,余大雅记)
04 先生举郑渔仲之说言:出于朝廷者为《雅》,出于民俗者为《风》。文武之时,周、召之民作者谓之周、召之《风》。东迁之后,王畿之民作者谓之《王风》。(80/2067,钱木之记)
05 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诗集传·郑风·将仲子》)
06 莆田郑氏谓此实淫奔之诗,无关于庄公、叔段之事。(《诗序辨说·郑风·将仲子》)
01、03条是朱熹自言废《序》受郑樵影响;05、06条说明郑樵对“淫诗”早有认识;04条说明朱熹“《国风》里巷歌谣说”亦本于郑樵;02条说明郑樵早已指出《小序》是依谥傅会美刺。凡此四端,皆朱熹诗经学之重要组成,而郑樵已发先声,朱熹亦屡屡称道之。我们甚至可以说,朱熹诗经学之义例基本来自郑樵。在讨论宋代诗经学时,郑樵实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只是郑樵对诗经学的研究不及朱熹系统和专门,其书《诗辨妄》①又亡佚,因此郑樵在诗经学上的影响远不如朱熹,他的一些论断也不得不赖朱熹的征引而得以流传,且有待于朱熹来发扬光大。
苏辙亦著有《诗经集传》,于《诗序》仅取首句。朱熹曾云:“子由《诗解》好处多。”(80/2090,钱木之记),《诗集传》征引苏辙之说亦极多,据曹虹统计共43处②,为征引宋人著作之首。《诗序辨说》亦于《大雅·文王》、《大雅·荡》二篇称引苏辙之说(《诗序辨说·大雅·文王》:“称王改元之说,欧阳公、苏氏、游氏辨之已详。”《诗序辨说·大雅·荡》:“苏氏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以为援证。朱熹称道苏辙,一是因为苏辙文学修养高,解诗有高过前人之处③;二是因为苏辙亦有考史之能④。苏辙于《诗序》仅取首句,也是因为看不惯《序》者太多的傅会穿凿。但朱熹还是嫌他废《序》不够彻底,《朱子语类》云“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80/2074,邵浩记),《诗序辨说》亦不乏专门辩驳苏辙取《序》首句之处,共有4例(附录11)。
附录11:《诗序辨说》专门辩驳苏辙取《序》首句之失例:
01 《周南·汉广》,《诗序辨说》:“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苏氏乃例取其首句,而去其下文,则于此类两失之矣。”
02 《周颂·昊天有成命》,《诗序辨说》:“苏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尝见其不可信之实也。愚于《汉广》之篇已尝论之。”
03 《周颂·执竞》,《诗序辨说》:“苏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时,因从小序之言。此亦以辞害意之失。”
04 《鲁颂·〓宫》,《诗序辨说》:“此诗言庄公之子,又言新庙奕奕,则为僖公修庙之诗明矣。但诗所谓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复周公之土宇耳,非谓其已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误如此,而苏氏信之,何哉?”
《诗序辨说》尚于《周南·桃夭》《周南·兔罝》、《鄘风·桑中》、《小雅·南山有台》4篇直接指出《序》之首句有误。《诗序辨说》卷首有云:“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义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
苏辙大抵相信《序》之首句传自圣人,只是“首句”之后的“续句”之引申发挥,多半是后世陋儒所为,不值得信从。朱熹则认为整个《诗序》,包括《序》的“续句”和“首句”在内,都不合诗本义,都应摒弃。
《朱子语类》云:“欧公《诗本义》亦好。”(80/2090,钱木之记)。朱熹推崇欧阳修,也有文学修养①与考史之能②两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欧阳修对求诗本义的理论建设有巨大贡献。《朱子语类》有云:
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本末》篇。又有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得也无妨。”其论甚好。(80/2089,沈僩)
欧阳修“《诗》之本末”论,为朱熹所激赏。欧阳修谓学者当知《诗》学有此四端: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
《诗本义》(卷十四)云:
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颂;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说;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
这四端,又有本末之分:
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
诗人之意是本,太师之职是末。圣人之志是本,经师之业是末。知其本末,则知学《诗》之主次。其又云:“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太师考其义类,于《诗》本身来说只是后人的一种理解与整理而已。诗人作诗时,又没有和太师商量过,太师的理解未必就是作者之意。今人学《诗》,探求诗人之意才是第一要紧的事;至于太师之类人的解释和整理,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孔子治《诗》,无非是“著其善恶以为劝戒”而已。学者读《诗》,无非是为了增进人格、变化气质,历代经师的繁复解说知不知道也并不要紧。
欧阳修虽未有废《序》的言论,但《诗》之本末的划分于求诗本义有重要意义。既然后来太师的理解未必合于诗人之意,且相对来说是第二位的,其本身的地位就变得次要;既然后世经师解《诗》不过是人自为说,未必合诗人之意,亦未必得圣人之志,那对读者来说也是可有可无的了。欧阳修“《诗》之本末”论一下子将诗本义与“著其善恶以为劝戒”的人格教育功能凸显了出来。“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这二者正是朱
熹诗经学之根本精神!“求诗人之意”,是求其本来面目,合乎朱熹格物之学术门径;“达圣人之志”,是救天下世道人心,是朱熹治学之根本目的。明乎此,则无怪乎朱熹对欧阳修“《诗》之本末”论要击节叹赏了。
三、“本义”溯源
《汉书·艺文志》有云: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这大约是最早提及《诗》“本义”的。但是这里的“本义”有其特定的涵义,与宋人求诗本义的“本义”并不是一回事。这涉及到汉人著述的体例问题,大约有此三端:1、“故训”与“传”之异同;2、“内传”与“外传”之异同;3、“正义”与“旁义”之异同。
《汉志》“咸非其本义”究竟指几家,学界意见不一。颜师古注云:“与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者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之。”王先谦《汉书补注》云:“此谓齐韩二传推演之词,皆非本义,不得其真耳。非并鲁诗言之。鲁最为近者,言齐韩训故亦各有取,惟鲁最优。颜谓三家皆不得谬矣。既不得其真,何言最近乎!”按颜师古的理解,是说鲁、齐、韩三家都不得本义。王先谦则认为仅指齐、韩二家不得本义。辨析其间是非,或当从汉人著述体例入手。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杂考各说·毛诗故训传名义考》云:
汉儒说经,莫不先通诂训。《汉书·扬雄传》言“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故通而已”。《儒林传》言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已”。而《后汉书·桓谭传》亦言谭“遍通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则知诂训与章句有辨。章句者,离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语多傅会,繁而不杀,蔡邕所谓“前儒特为章句者,皆用其意传,非其本旨”,刘勰所谓“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也。诂训则博习古文,通其转注、假借,不烦章解句释,而奥义自辟,班固所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史》、《汉》、《儒林传》皆言鲁申公为《诗训诂》,而《汉书·楚元王传》及《鲁国先贤传》皆言申公始为《诗传》,则知《汉志》所载《鲁故》、《鲁说》者,即《鲁传》也。何休《公羊传注》亦言“传谓诂训”,似故训与传初无甚异。而《汉志》既载《齐后氏故》、《孙氏故》、《韩故》,又载《齐后氏传》、《孙氏传》、《韩内外传》,则训诂与传又自不同。盖散言则故训、传俱可通称,对言则故训与传异,连言故训与分言故、训者又异……盖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引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①
马瑞辰指出“散言则故训、传俱可通称,对言则故训与传异”。汉人固然有“故训”与“传”混称的习惯,但是《汉志》所载却有“辨章学术”的意义在,称“故训”与称“传”,有其体例上的区别。称“故”(诂训)者大抵仅“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称“传”则并引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也就是说“故”的通例是注重词义的训释,仅就经文自身解说大义,一般不做过多的题外发挥;而“传”(章句)的通例则是要对经文作引申发挥,要称引经文以外的东西来阐发经义。“故”的特点是简括清通,“传”则容易傅会穿凿。马瑞辰引前后《汉书》所记扬雄、蔡邕之言行,亦足以说明两汉之交及东汉儒者对二者性质的认识。蔡邕明确指出“章句”多非经本旨。《汉志》于“咸非其本义”句前云“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辨析“咸非其本义”,必须考虑到“训诂”和“传”在体例上的不同。从汉人“故”与“传”体例差异入手,《汉志》所云“咸非其本义”似指齐、韩二家而言。
陈澧《东塾读书记》对先秦、秦汉人著述之内传、外传之分有明确辨析①。陈澧云:“韩非有《解老》篇。复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即《外传》之体。其《解老》即内传。”《韩非子》有《喻老》、《解老》二篇,《喻老》的体例是引古事以明《老子》之理,《解老》篇则是直接阐发《老子》思想。《喻老》是外传体,《解老》是内传体。《外传》之体,可引古事,亦可引古人之言(包括古人之诗),陈澧云“今本《韩诗外传》,有元至正十五年钱惟善序云:‘断章取义,有合于孔门商赐言《诗》之旨。’澧案:孟子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亦外传之体。”又云:“西汉经学,惟《诗》有毛氏、韩氏两家之书,传至今日。读者得知古人内传、外传之体,乃天之未丧斯文也。《直斋书录解题》云‘《韩诗外传》,多记杂说,不专解《诗》,果当时本书否?’(卷二)杭堇浦云‘董生《繁露》、韩婴《外传》,偭背经旨,铺列杂说,是谓畔经。’(《古文百篇序》)此则不知内外传之体矣。”陈澧认为《毛传》与《韩诗外传》正好是内传与外传的典型代表。虽然陈澧批评《直斋书录解题》怀疑《韩诗外传》非当时之书、批评杭世骏说《韩诗外传》畔经。但二家对《韩诗外传》特点的认识却不可移易。“多记杂说,不专解《诗》”、“偭背经旨,铺列杂说”,正是《韩诗外传》的特色。陈澧于此亦有深刻认识,他说:“采杂说,非本义,盖专指《外传》而言。”认为《汉志》所云“咸非其本义”专指《外传》,而“非本义”的标志是“采杂说”。
皮锡瑞论《诗》又有“正义”、“旁义”之分,其《经学通论·诗经》①“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义亦未尽可信”条云:“三家所传近古,而孰为正义、孰为旁义,已莫能定。以为诗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又云三家诗“存于世者,惟《韩诗外传》,而外传亦引诗之体,而非作诗之义。”“正义”指作诗之义,“旁义”指后人引申傅会之说。“正义”、“旁义”与“故”、“传”之体有很大关系,与“内传”、“外传”之体亦有很大关系。引申傅会愈多,则离诗人之意愈远。相对于“故”来说,“传”的引申傅会为多;“故”于“正义”为近,“传”多“旁义”。相对于“内传”来说,“外传”的引申傅会为多,“内传”近于“正义”,“外传”多属“旁义”。
汉人著述,于“故”、“传”、“内传”、“外传”之体有自觉认识,《汉志》著录更是于诸体之分有清醒认识。观其著录《诗经》学著述即可明此理。《汉志》载: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
《鲁故》二十五卷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何者为“故”,何者为“传”,何者为“内传”,何者为“外传”,泾渭分明。《汉志》著录鲁诗,有《鲁故》、《鲁说》,而无《鲁传》,《汉书·儒林传》亦云:“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作文按:《史记·儒林传》云:“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上一“疑”字,或为衍文。)我们知道,《韩诗外传》是采杂说的,齐诗喜言“天人之际”,傅会阴阳五行,惟鲁诗较为质朴简括,而少引申傅会之说。故《汉志》有鲁最为近之之论。
三家诗说,今存者惟有《韩诗外传》。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来看看《韩诗外传》的特色。兹引其卷首第一段于下:
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以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怒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桥褐趋时,当务为急。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曰:“夙夜在公,实命不同。”
这一段文字,在结构上包括一个故事和《诗经》的两句(姑且称为“断章”)。但我们很难说这是引事以明《诗》。在这个结构中,《诗》之断章已经脱离原诗,不再是原诗的一个有机组成;它已是新的文本结构的一个部分,为新的文本服务。《韩诗外传》的作者在这里用这两句,是“断章取义”的态度,仅取这断章含有的某一种意思,而非其原诗的意思。在这里,这一断章与这一故事,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断章的义实际受这个要说的道理制约。“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出自《召南·小星》。因文献不存,我们无法知道韩诗对这一篇篇义的确切理解。但无论如何,绝不会理解成是写曾子的。这里的故事,是引事以明义;这里的诗,是引《诗》以明义。《韩诗外传》作者本人所要表达的义才是第一位的,至于诗之原义(作诗之义)已经在新的结构中被消解。《直斋书录解题》云《韩诗外传》“不专解《诗》”,诚为有见。
徐复观对《韩诗外传》的特点与性质有很好的概括:
他(韩婴)在《外传》中,共引用《荀子》凡五十四次,其深受《荀子》的影响,可无疑问。即《外传》表达的形式,除继承《春秋》以事明义的传统外,更将所述之事与《诗》结合起来,而成为事与《诗》的结合,实即史与诗互相证成的特殊形式,亦由《荀子》发展而来。……《韩诗外传》,未引《诗》作结者仅二十八处,而此二十八处,可推定为文字的残缺。其引诗作结时,也多援用《荀子》所用的格式。……《韩诗外传》,乃韩婴以前言往行的故事,发明《诗》的微言大义之书。此时,《诗》与故事的结合,皆是象征层次上的结合。……韩氏乃直承孔门“诗教”,并不否定其本义,但不仅在本义上说《诗》,使《诗》发挥更大的教育意义。①
徐复观指出《韩诗外传》受《荀子》影响,乃是用引古事与引《诗》相结合的方法来说明道理。于《诗》而言,它“不仅在本义上说《诗》”,而且要“发明《诗》的微言大义”。这样看来,《韩诗外传》在性质上同于一般子书,解经只是门面话,阐明自己的义理才是其目的。这样一来,自难逃《汉志》非诗本义之讥。
《汉志》言齐韩二家诗传“咸非其本义”的特定语境是汉人的著述体例,主要是从“故”与“传”、“内传”与“外传”、“正义”与“旁义”的差异性着眼。《汉志》所言的“本义”是与“引申义”相对而言的。齐、韩二家或主于阴阳五行,或受《荀子》等子书影响,多是在“引申义”的层面上说《诗》,故“咸非其本义”。相对来说,鲁诗(《鲁故》)较少在“引申义”的层面上说《诗》,故“最为近之”。从著述体例着眼,根据是否在“引申义”层面上说《诗》,在《汉志》的立场,毛诗恐怕当属得其本义,或者较鲁诗更近本义的。
林叶连云:
班固谓西汉诗经学有齐、鲁、韩、毛四家。但因齐、鲁、韩诗于两汉皆立于学官,宛若诗学正宗,故班氏奉命撰《汉书》,便专就齐、鲁、韩三家,较其优劣,而不评毛诗。只在文末附带提及毛诗。班氏所言“自谓子夏所传”,“自谓”也者,其涵义为“非官方说法”,而非微辞。盖班氏所撰者,官书也,立于官方立场以发言,乃理所当然。总之,《汉志》非但未尝丝毫褒贬、评价毛诗,反而谓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成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此方为贬辞。①
林叶连所言,实不无道理。班固之世,古文经学地位上升,况且《汉志》本于刘歆《七略》,其对古文学派的毛诗给以认同,亦在情理之中。毛诗的著述体例是“但明训诂”,每篇有一极短小的序隐括诗义,很少作“引申义”层面上的发挥。用“故”和“传”的著述体例来区分,毛诗的体例属“故”;用“内传”和“外传”来区分,其性质又属“内传”;用“正义”和“旁义”来区分,其所言属“正义”。
需要特地指出的是:宋人所说的“本义”并不是汉人(《汉志》)说的“本义”,此“本义”非彼“本义”也。《汉志》说的“本义”是从著述体例的角度着眼,朱熹等人说的“本义”则是从辞与意的关系这一角度着眼。《汉志》之所以认为齐、韩二家诗“非其本义”,乃是因为它们属“传”体,而且是偏于“外传”体,多言“旁义”;《汉志》言鲁诗“最为近之”,是因为鲁诗(《鲁故》)属“故”体,多言“正义”。毛诗著述体例为“故”体和“内传”体,所言亦为“正义”。从《汉志》的立场,可以类推出毛诗最近本义之一结论。但是宋人求诗本义的对立面却恰恰正是毛诗(当然也是因为其时三家诗仅存《韩诗外传》,而其内容又不专解《诗》)。在朱熹等人看来,毛诗是不得“本义”的。朱熹所说的“本义”基本等同于“辞意”。尽管汉人(《汉志》)和朱熹所理解的“本义”都指“作者之义”,但他们对“作者之义”的认识实有本质差别。以毛、郑为代表的汉学一派从来不认为自己的阐释是背离“作者之义”的,他们认为“作者之义”即是他们所理解的诗义。他们认为,《诗》“作者之义”必有政治讽喻义,并不就是文本字面上的意思(“辞意”)。但在朱熹的立场,毛、郑一派所理解的诗义多属穿凿傅会,而从“辞意”才能求得真正的“作者之意”。
《汉志》所言之“本义”与宋人所理解的“本义”,在语境和涵义上有很大不同,更不是宋人求诗本义的源头。宋人所求之“本义”或来自禅宗。我们知道,南禅(以六祖惠能《坛经》为标志)的出现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南禅鼓吹“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摆脱历来佛经注疏的束缚,而倡独立思考、自证自悟之大旗。其怀疑精神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对宋明理学在学理建设上实有重大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南禅与宋人求经典本义之间的相似性:南禅所要求的是佛性,历来的佛经注疏都是后人对佛性的一种阐释,惠能主张摆脱后人阐释的束缚,而将思考直接指向佛性自身;朱熹所要求的是诗本义,《序》、《传》、《笺》、《疏》等都只是后人对诗义的一种阐释,朱熹力主废《序》,而于《诗》辞之中求其本义。南禅有“第一义”、“第二义”之分;欧阳修倡“《诗》有本末”论,为朱熹所激赏。南禅重自证自悟;朱熹教人读《诗》贵“涵泳”。这些相似性无不说明宋人求经典本义的思考方法实受南禅之影响。
自中唐南禅兴起以来,怀疑精神与独立思考对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壮大,至宋时已成时代之普遍风气。故宋儒对待经典文献之态度实与前人大异,其精英人物大抵能摆脱汉唐注疏之束缚,而求其本义于经文之中。仅就诗经学而言,朱熹之前,欧阳修、苏辙、郑樵等人已有此种精神。朱熹生逢其时,得风云之际会,总有宋一代诗经学之大成。
自立门户的宋诗经学,则始于欧阳修《诗本义》。《本义》辩诘毛、郑,断以己义,力反东汉以来治《诗》之旧习。苏辙继起,作《诗集传》,始攻击毛序,仅存录首句。南宋时,郑樵作《诗序辨妄》,直斥《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王质《诗总闻》亦同此声气。朱熹则集宋学大成,作《诗集传》及《诗序辨说》,弃序不用,专于文本自身求诗本义,且杂采毛、郑,间录三家,一以己义为取舍。
废《序》与求诗本义实是朱熹对汉学诗经学的一场革命。
第一节 求诗本义
[辞与意的关系 《序》不合《诗》本意 涵泳文本]
一、辞与意的关系
马端临有云:
《诗》、《书》之序,自史传不能明其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解经,则依古、今文析而二之,而备论其得失。而于《诗·国风》诸篇之序,诋斥尤多。以愚观之,《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论之,《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何也?《书》,直陈其事而已,《序》者,后人之作,藉令深得经意,亦不过能发明其所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诗》则异于《书》矣。然《雅》、《颂》之作,其辞易知,其意易明,故读《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七章,则“文王受命作周”之语赘矣。……盖作者之意已明,则《序》者之辞可略。……至于读《国风》诸篇,而后知《诗》之不可无《序》,而《序》之有功于《诗》也。盖《风》之为体,
比兴之辞多于叙述,风喻之意浮于指斥。盖有反复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者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意料当时旨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而文公深诋之,且于《桑中》、《溱洧》诸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于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乌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其说固善矣。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只《郑》、《卫》诸篇哉?若《芣苡》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者,而其语不过形容采掇芣苡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采掇者为何事?而慨叹者为何说乎?……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均一淫佚之词,出于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芣苡》、《黍离》之不言所谓……文公胡不玩索《诗》辞,别自为说,而卒如《序》者旧说,求作诗之意于诗辞之外矣?何独于《郑》、《卫》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而使圣经为录淫辞之具乎?且夫子尝删诗矣。其所取于《关雎》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之《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佚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婚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烦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者何等一篇也!……或曰:《序》者之序诗,与文公之释诗,俱非得于作诗之人亲传面命也。《序》求诗意于辞之外,文公求诗意于辞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说而妄拟先儒也。盖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说《诗》者读《诗》,而后知《序》说之不谬,而文公之说多可疑也。孔子之说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之说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不能无过,故其于男女夫妇之间,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间,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七十五篇(作文按:当为一百六十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复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于无邪之训,而以辞害意之过也。而况《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旷之悲,遇合之喜,虽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辞哀,习其读,而不知其旨,易以动荡人心之邪情泆志,而况以铺张揄扬之词,而序淫佚流荡之行乎?然诗人之意则非以为是而劝之也。盖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言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于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决非淫佚之人所自赋也。①
这大约是辩驳朱熹不依《序》说诗最有系统的一段议论。马端临其意在辩《诗序》不可废,但却对汉学诗经学与朱熹诗经学的释义原则多有讨论。尽管马端临在回护《诗序》方面不足取,但他对汉学诗经学与朱熹诗经学释义方法的总结以及思考该问题的切入点,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意义。马端临抓住《国风》特别是其中的《郑》、《卫》之诗(也即朱熹认定的“淫诗”)来讨论这个问题,正是看出了其间存在“辞”与“意”这一对关系。朱熹与汉学诗经学的分歧正在于处理《诗三百》文本“辞”与“意”的关系上:“《序》求诗意于辞之外,文公求诗意于辞之中。”
在讨论文本的“辞”与“意”关系时,有三个因素需要考虑:1、文本自身(姑且称为“辞”);2、作者之意(姑且称为“作意”);3、阐释者的释义(姑且称为“释义”)。从理论上讲,前二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只要一个文本被创作出来,其“辞”(文本自身)就客观存在,“作意”(创作者自身的意图)也是客观存在的。“作意”与“辞”之间可以有两种模式:1、“作意即辞意”,文本的字面意义就是作者之意;2、“作意非辞意”,作者之意并不就是文本自身,而是隐含于文本中的一种比喻意。其所以存在这两种模式,是因为人类的表达方式存在直接叙述与比喻说明这两种情况。文学作品的表达更是如此。“作意即辞意”,是很容易理解的。至于“作意非辞意”,唐人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诗是很好的例证。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文本自身浅显易懂,其字面意思无非是说一个新嫁娘,刚和新郎入了洞房,正在考虑次日清早见公婆的事情:她很有些担心公婆不喜欢自己的装束,所以问新郎自己的打扮是否入时。但这诗的题目却是《近试上张水部》,而且是代书体,是一个考生写给考官的信——他想探听一下考官大人的口风呢!诗人的作意与诗辞的表面意义并非是一回事,二者之间不过是一种比喻性的关系而已。“释义”是阐释者在阅读文本之后,根据文本所提供的信息,并结合以往的阅读经验,对文本所做出的一种解释。从理论上说,“释义”只能是主观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阐释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感受来对文本加以解释的,他们的意见自然可以很不相同。“释义”可以无限接近于“作意”,但总是存在“误差”。“作意”与“辞意”之间本就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模式,阐释者在对文本进行解释时,也可以有两种不同方法:1、“求诗意于辞之中”;2、“求诗意于辞之外”。前者以“作意即辞意”为认识前提;后者以“作意非辞意”为前提。从方法的角度来说,二者之间未可置以轩轾。但这两种阐释方法都必须以对象的针对性为前提,它们都只适合于自己特定的对象。“求诗意于辞之中”的阐释方法适用于“作意即辞意”这一类型,但却不适用于“作意非辞意”的类型。用“求诗意于辞之中”的方法来阐释“作意即辞意”这一类型,不同的阐释者或许有高下之分,但对于事实真相(“作意”)来说,“释义”只有一个误差大小的问题。但如果是“作意非辞意”这一类型,阐释者却用了“求诗意于辞之中”这种方法,那就不是“误差”的问题,而是“谬误”了。“求诗意于辞之外”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对,它只适用于“作意非辞意”这一类型,却不适用于“作意即辞意”的类型。
判定“释义”是否合于“作意”,首先要对“作意”与“辞意”的关系做出明确判断。“求诗意于辞之中”,是通行的阐释方法;“求诗意于辞之外”,则必须要有“作意非辞意”的前提存在。一般来说,“作意即辞意”是通例,“作意非辞意”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如果要对一个文本做出“作意非辞意”的认定,必须要有足够的背景方面的限制性条件。我们确认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属于“作意非辞意”这种类型,是因为其作者、诗题以及当事人的身份关系提供给我们充分的信息。有这种充分的背景性限制条件,“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才能够让人信服。不具备这种充分的背景性限制条件,“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则只能是莫须有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只对有充分的背景性限制性条件的文本作“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对“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我们判定其“释义”是否合于“作意”,也以其是否有充分的背景性限制条件为根据。诗歌史的实际情况是:文本及其背景材料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足以让我们作出“作意非辞意”的判断的,并不多见。对绝大多数的诗篇,我们一般认为其“作意即辞意”,并用“求诗意于辞之中”的方法来对其进行阐释。
“《序》求诗意于辞之外,文公求诗意于辞之中。”《序》者说《诗》的方法是求文字自身以外的特殊涵义,朱熹则是根据文本自身来说《诗》。《序》者说《诗》,不外乎美、刺二端。汉儒从政治讽喻的角度来理解《诗三百》,认为“《诗》缘政”,《诗三百》所有作品都是美刺当时国君政事的。对国政进行美刺,即是汉学诗经学所理解的“作意”。但是,诚如马端临所指出的,《诗三百》尤其是《国风》部分,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譬如《周南·芣苡》),其文本自身只是“反复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者之意”。对于汉儒来说,由于习惯了比兴说诗(实际是道德政治譬喻)的思维方式,对《序》者的解说很容易接受。但对不采用这一思维方式的阐释者来说,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问题,亦即马端临隐括朱熹之意:“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乌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诗三百》文本自身,尤其是《国风》部分,其辞意并不晦涩,根据文本自身来解说,很容易做到明白晓畅。其文本字面上明明是一种意思,与《序》者所云,并不相干;凭什么要放弃其字面意思而听从《序》的意见呢?汉儒坚持《诗三百》在文本字面意义之外尚有一个非美即刺的作者之意;朱熹则认为作者之意即在《诗三百》文本自身,而汉儒所挖掘的《诗》意并不是诗人本意。所以他要摆脱《序》的束缚,求诗本意。马端临认识到《序》者与朱熹在处理《诗三百》文本“辞”与“意”关系上有根本分歧,他们是用了两种不同的阐释方法。马端临屡言《诗》之意当如《序》说而不当如朱熹所说,是因为他受《序》的影响太深,脑子里有根深蒂固的《诗》不能无为而作(必须有政治讽喻意义)的观念。汉学诗经学一派都有这样的思维前提:《诗经》既然是“经”,它就应该有超乎其文本自身以外的深意在。所以其(《国风》部分)“作意非辞意”,必须要用“求诗意于辞之外”的方法来对其加以阐释。
马端临用“求诗意于辞之外”与“求诗意于辞之中”来概括《序》者与朱熹在说诗方法上的根本差别,是极有见地的。但他回护《诗序》的理由却站不住脚。马端临是史学名家,精于考据辨析,但他这里论证《序》说可靠的理由在逻辑上却有问题。其论《序》说可信的理由无非如下三条:1、《诗》意有必赖《序》而后明者;2、《序》者言《诗》意态度果断,应该是有根据、有传授渊源的;3、孔孟说《诗》与《序》者相合。但这三条理由实不能证明《序》说可信:1、《序》确实给了《诗》一种规定性的解释,但此解释未必得《诗》之本意。以《诗》意有必赖《序》而后明者为理由证明《序》说可信,在逻辑上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2、《序》者态度确实果断,但这与意见正确与否是两码事。3、借助孔孟之言,是诉诸权威的思路。孔孟是文化思想之巨人,但不等于他们的认识一概正确。即使《序》者说诗合于孔孟,亦不能证明其说合于诗人本意。
尽管在今天看来,马端临论证《序》说可靠的三条理由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但马端临自己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他对《序》说是一种坚信的态度。不独马端临,《诗》汉学一派对《序》的权威地位,也是从来坚信不疑的。我们可以说,《诗序》是汉学诗经学的灵魂,依《序》说诗是汉学诗经学的根本特征。
因为对《诗序》作者的争议,《诗序》与《毛传》的先后亦相应成为诗经学的一大公案。笔者个人的意见,则主张《诗序》至少不晚于《毛传》,而且《毛传》分明是依序说诗。这可以从《毛传》与《诗序》在字句上的对应关系得到证明。《毛传》以“但明训诂”为特色,但在具体说诗时,不少地方有超出训诂范围的发挥。这些发挥颇值玩味。如《召南·江有汜》篇,《毛传》于“不我以,其后也悔”句后注曰:“嫡能自悔也。”诗文自身绝不涉于嫡媵之意,注者显然不能在训诂范围内作此断语。《毛传》断言是“嫡”而非他人能自悔,无非是有《诗序》作根据罢了。《诗序》云:“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也。”若无《诗序》的根据,《毛传》是断不可做出这样的解说的。与《召南·江有汜》篇类似,《毛传》说诗有超出训诂范围的发挥,而且是不能直接从诗辞之中得出,但却与《序》有明显对应关系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例子说明《毛传》分明是依《序》说诗。《郑笺》和《孔疏》的依《序》说诗,则是不待说的。几乎每一句的解说,都要迁就《诗序》,绝不敢有什么动摇和怀疑。
二、《序》不合《诗》本意
因为《诗序》自身的说诗方法是“求诗意于辞之外”,所以,凡是尊《序》的一派都主张《诗经》“作意非辞意”,且都关注于文本以外的政治譬喻义。《毛传》也好,《郑笺》也好,其对《诗经》文本的阐释,都是以《序》为核心,来做具体发挥。朱熹对《序》者“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方法以及毛、郑依《序》说诗极为不满,他自己的做法乃是要“求诗意于辞之中”,以文本自身为首要根据。《朱子语类》中颇多这方面的议论:
01 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或每日令人讽读,却从旁听之。其话有未通者,略检注解看,却时时诵其本文,便见其语脉所在。(80/2083,黄㽦记)①
02 某解《诗》,多不依他《序》。纵解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诗上下文意,则得罪于圣贤也。(80/2092,包扬记)
03 大抵今人说《诗》,多去辨他《序》文,要求著落。至其正文“关关雎鸠”之义,却不与理会。(80/2068,余大雅记)
04 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80/2068,余大雅记)
05 伯恭专信《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要出脱回护。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80/2074,邵浩记)
……
朱熹反复强调的是读《诗》、解《诗》需要虚心诵读正文,要根据其本文自身来理解诗意。《序》者说诗,多与这一原则相背离,所以多不得诗之本意。如果一味依《序》说诗,而不仔细考察文本上下文自身,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理解。正因为朱熹与《序》对诗意的解说有一个“求诗意于辞之中”与“求诗意于辞之外”的根本差别,所以朱熹对《序》者的解释多不以为然。《诗序辨说》对《序》的具体批评亦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诗序辨说》指出“诗中未见此意”者共有17例(附录1)。
附录1:《诗序辨说》明言“诗中未见此意”例:
01 《召南·草虫》,《序》:“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诗序辨说》:“未见以礼自防之意。”
02个《召南·江有汜》,《序》:“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也。”《诗序辨说》:“诗中未见勤劳无怨之意。”
03 《邶风·雄雉》,《序》:“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诗序辨说》:“未有以见其为宣公之时、与淫乱不恤国事之意。”
04 《邶风·谷风》,《序》:“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诗序辨说》:“亦未有以见化其上之意。”
05 《卫风·考槃》,《序》:“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诗序辨说》:“诗文未见有见弃于君之意。”
06 《卫风·竹竿》,《序》:“卫女思归也。适异国而不见答,思而能以礼者也。”《诗序辨说》:“未见不见答之意。”
07 《郑风·女曰鸡鸣》,《序》:“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诗序辨说》:“此亦未有以见其陈古刺今之意。”
08 《唐风·羔裘》,《序》:“刺时也。晋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诗序辨说》:“诗中未见此意。”
09 《小雅·绵蛮》,《序》:“微臣刺乱也。大臣不用仁心,遗忘微贱,不肯饮食教载之。故作是诗也。”《诗序辨说》:“此诗未有刺大臣之意。”
10 《周颂·维天之命》,《序》:“大平告文王也。”《诗序辨说》:“诗中未见告太平之意。”
11 《周颂·维清》,《序》:“奏象舞也。”《诗序辨说》:“诗中未见奏象舞之意。”
12 《周颂·烈文》,《序》:“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诗序辨说》:“诗中未见即政之意。”
13 《周颂·雝》,《序》:“谛大祖也。”《诗序辨说》:“诗文亦无此意”。
14 《周颂·酌》,《序》:“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
之道,以养天下也。”《诗序辨说》:“诗中无酌字,未见酌先祖以养天下之意。”
15 《鲁颂·》,《序》:“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诗序辨说》:“诗中亦未见务农重谷之意。”
16 《鲁颂·有〓》,《序》:“颂僖公君臣有道。”《诗序辨说》:“此但宴饮之诗,未见君臣有道之意。”
17 《商颂·烈祖》,《序》:“祀中宗也。”《诗序辨说》:“详此诗,未见其为祀中宗。”
以上17例,都是《序》者对《诗经》作品做出的解释,但其解释有超乎“辞”意的地方;朱熹则以文本为根据,对其超乎文本的随意发挥一一加以指陈。
其实,《诗序辨说》象这样直接说“诗中未见此意”的情况,还只是对《序》的解说进行部分质疑。如《召南·江有汜》篇,《诗集传》云:“是时汜水之旁,媵有待年于国,而嫡不与之偕行者,其后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这样的理解和《序》者的解释实际并无太大的分歧。但因为文本自身看不出“勤劳无怨”的意思而《序》有此一说,《诗序辨说》还是要特意指出来。对一点点的不以文本为根据的随意发挥都不放过,正可以说明朱熹对文本是何等的重视!
《诗序辨说》于一些篇目则干脆说《序》者所说“非诗本意”,共有4例(附录2)。
附录2:《诗序辨说》径云《序》者所说“非诗本意”例:
01 《郑风·狡童》,《序》:“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诗序辨说》:“非诗之本旨,明矣。”
02 《小雅·吉日》,《序》:“美宣王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诗序辨说》:“序慎微以下,非诗本
意。”
03 《小雅·瞻彼洛矣》,《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诸侯,赏善罚恶焉。”《诗序辨说》:“此序以命服为赏善,六师为罚恶,然非诗之本意也。”
04 《大雅·荡》,《序》:“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诗序辨说》:“苏氏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诗之本意也。”
云“非诗本意”,无非是指《序》者的解说与文本的实际情况不相合。至于《诗序辨说》径云“《序》说误矣”(如《邶风·终风》篇等)或“此序全非诗意”(如《唐风·有杕之杜》篇等)的情况,在朱熹的立场,《序》者的解释更是与《诗》之本意相差甚远了!前引马端临所集中讨论的“淫诗”问题,最为典型。朱熹对《序》者解说淫诗,或者以为是诗人“刺淫”,或者别作他解的做法很不满意,干脆根据文本自身把它们都理解为淫者自叙其事。关于“淫诗”的问题,将在论文的第二章具体讨论,这里暂不细说。
《诗序辨说》卷首云:
《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惟《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篇,毛公始分以置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义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又以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词,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燎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
朱熹指出:1、《序》非圣人作;2、《序》有不合诗人之本义处。以此否定《序》的权威性。在这两个理由中,后者更为关键。在今天看来,《序》是否出于圣人之门,与其是否合理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但古代读书人都有这样一个情结,他们习惯于认为圣人之言是真理,并且希望自己的意见能从圣人那里找到根据。马端临辩驳朱熹废《序》,便拿《序》者说《诗》合于孔孟当一个重要依据。汉学诗经学一派坚信《序》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以为《序》出于圣人之门(是孔子入室弟子子夏所传)。《序》既然出于圣人之门,其对诗旨的阐释自可尊崇,故汉学诗经学一派主张依《序》说诗。迷信孔子,断送了他们的独立思考。朱熹却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大儒,所以他能以己意说诗,别开生面。尽管“《序》非圣人作”与“《序》有不合诗人之本义处”,在否定《序》的权威性上是两个并列性的理由,但实际上前者的根据恐怕还在后者。《后汉书·儒林传》云卫宏作《毛诗序》,固然在文献上提供了一个证据,但朱熹认为“《序》非圣人作”,主要还是因为《序》的阐释多与《诗》辞本意不合。朱熹“求诗意于辞之中”,觉《序》不合诗旨之处甚多,因疑其非圣人所作,故不主张依《序》说诗,而于文本自身求诗本义。
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指出“《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序》只是阐释者对《诗》的一种规定性解释,相对于《诗三百》文本自身来说,它只能是第二位的。《诗三百》文本和《序》之间本是主客关系,《诗三百》文本自身是主,《序》是客。后人不明《序》乃汉人之作,误以为是圣人遗说,因此依《序》说诗,穿凿迁就,破碎经文,在所不惜。这样做,则是将《诗三百》文本和《序》之间的主客关系倒置了过来,《序》成了主,《诗三百》文本自身反成了客。这是朱熹所坚决反对和要纠正的。
朱熹有云:“《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且只将四字成句底诗读,却自分晓。见作《诗集传》,待取《诗》令编排放前面,驱逐(作文按:此处似应有一“序”字)过后面,自作一处。”(《朱子语类》,80/2074,陈文蔚记)又云:“《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朱子语类》,80/2074,甘节记)《序》不得《诗》本意,后人依《序》说诗,更是混淆视听,将读者引入歧途。所以朱熹理直气壮地说:“某解《诗》,多不依他《序》。”(《朱子语类》,80/2092,包扬记)朱熹的原则乃是以《诗三百》文本自身为根据,求诗本意。《诗集传》是其“求诗意于辞之中”的实践。《诗集传》不录《序》说,朱熹另著《诗序辨说》,将《诗序》汇为一编,且逐条加以辩驳。朱熹将《诗序》与《诗三百》经文自身剥离,单独汇为一编,其理由即《诗序辨说·序》所云“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朱子语类》云:“敬之问《诗》、《书》序。曰:古本自是别作一处。如《易大传》、班固《叙传》并在后。京师旧本《扬子》注,其序亦总在后。”(80/2074,廖德明记)。先秦、秦汉人著书的通例是《序》在正文之后,朱熹因此坚信《序》是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了。
三、涵泳文本
朱熹求诗本义的根本方法是涵泳文本。《朱子语类》载朱熹教弟子读《诗》之法,不厌其烦地强调涵泳工夫,且看:
01 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候仿佛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如人拾得一个无题目诗,再三熟看,亦须辨得出来。若被旧说一局局定,便看不出。(80/2085,吴必大记)
02 提取摘要;分类号;关键词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仍不可先看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认得此诗是说个甚事。谓如拾得一个无题目诗,说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开,必是梅花诗也。(80/2085,万人杰记)
03 读《诗》正在吟咏讽诵,观察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今公读《诗》,只是将己意去包笼他,如做时文相似。中间委曲周旋之意,尽不曾理会得,济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看尽,何用逐日只捱得数章,而又不曾透彻耶?且如入人城郭,须是逐街坊里巷,屋庐台榭,车马人物,一一看尽,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见城是如此,便说我都知得了。如《郑诗》虽淫乱,然《出其东门》一诗,却如此好。《女曰鸡鸣》一诗,意思亦好。读之,真个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80/2086,钱木之记)
04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直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看来书只是要读,读得熟时,道理自见,切忌先自布置说!(80/2086,沈僩记)
05 须是读熟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取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80/2087,沈僩记)
06 大凡读书,先晓得文义了,只是常常熟读。如看《诗》,不须得着意去里面训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80/2087,林夔孙记)
07 先生问林武子(作文按:当为林子武。林夔孙,字子武):“看《诗》何处?”曰:“至《大雅》。”大声曰:“公前日方看《节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而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开板便晓,但于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时,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强五十遍,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时。“题彼脊鸰,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这个看时,也只是恁地,但里面意思却有说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说不得里面。”(80/2087,黄义刚记)
所谓“涵泳文本”,实际就是要求熟读《诗三百》诗文自身,仔细玩味体察诗中的曲折情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终须是烂熟于心了,才容易对文辞中所体现的作者情感有较贴切的体会,才容易对辞意有一个确解。文字表达相对于图画、戏剧等表达方式来说,其直观性要稍弱一些;诗歌更是一种表达复杂情感的文学样式。所以,诗歌尤其需要“涵泳”。文学感受是一种特殊的感受,需要读者对阅读对象有极细微的了解,并根据个人的情感经验在内心对文本事件作一构拟。文学阅读是一项极细腻与感性的心理活动;文学审美是一种很微妙的境界,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般来说,文学感受力的高下取决于读者的心灵敏感度与以往的情感经验,不同的读者,对作品的感受程度有高下之别。但对同一读者来说,在心灵敏感度与情感经验是一定量的情况下,其对作品的感受程度则取决于对作品的熟悉程度。朱熹说“百遍自是强五十遍,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朱熹强调要熟读文本。不断熟读,徐徐玩味,对作品的体会自然会逐步加深,而且对文学的感受能力也会在此中不断提升。如果不以“涵泳文本”为方法,而只一味看别人的解释,那就很难对作品有深切的体会。《庄子》有轮扁的譬喻,“斫轮”尚且不能父喻于子,何况是文学感受呢?文学感受只能是靠自己体会,阐释者可以给读者以正确的引导,但却无法越俎代庖。阐释者自身在理解辞意时,更是需要细心体会。所以,朱熹一再告诫弟子读《诗》时,最好什么注解都不必先去看,只管将文本熟读,久之自有体会。再高明的阐释都不能替代读者自身的阅读与感受,何况《序》对《诗》的解释还有那么多不尽如人意乃至有歪曲之处呢?朱熹主要是从求诗本义的角度,针对汉学诗经学依《序》说诗来提倡“涵泳文本”的;但对“涵泳”的重视和大力提倡,也说明朱熹对《诗三百》的文学性有深刻认识。
“涵泳文本,求诗本义”是朱熹说诗的根本方法,“揆以情理”和“考诸书史”则是其辩驳《诗序》的具体手段。
朱熹说诗,每求不远于人情物理。《朱子语类》中有这样一条:“问:以《诗》观之,虽千百载之远,人之情伪只此而已,更无两般。曰:以某看来,须是别换过天地,方别换一样人情,
释氏之说固不足据,然其书说尽百千万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况天地无终穷,人情安得有异!”(80/2083—2084,吴必大记)。这是由《诗》说到人情,朱熹说《诗》却往往是据人情以论《诗》。如《唐风·山有枢》篇,《序》云:“刺晋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政荒民散,将以危亡,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国人作诗以刺之。”《诗序辨说》:“此诗盖以答《蟋蟀》之意,而宽其忧。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说大误。”朱熹不取《序》之刺晋昭公一说,乃是因为该篇辞意“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序》者不察于此,是疏于人情物理。至于“淫诗”问题的辩论,更能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先看《朱子语类》中的一条记载:
李茂钦问:“先生曾与东莱辩论淫奔之诗。东莱谓诗人所作,先生谓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晓其说。”曰:“若是诗人所作讥刺淫奔,则婺州人如有淫奔,东莱何不作一诗刺之?”茂钦又引他事问难。先生曰:“未须别说,只为我答此一句来。”茂钦辞穷。先生曰:“若人家有隐僻事,便作诗讦其短讥刺,此乃今之轻薄子,好作谑词嘲乡里之类,为一乡所疾害者。诗人温醇,必不如此。”(80/2093,李杞记)
对于“淫诗”理解有异,是朱熹与吕东莱的一大分歧。吕东莱于“淫诗”是依从《序》者所说,朱熹则认为是“淫者自作”。朱熹在给李茂钦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如此理解“淫诗”时,说:如果婺州有人淫奔,东莱会不会作诗刺之呢?以东莱的身份,绝不会这样做。同样的道理,“诗人”既是贤君子,自然也不会这样做。《诗序辨说·桑中》篇又说:“……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间,犹有宾主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这也是从人情物理的角度来说明问题。
朱熹有云: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80/2076,叶贺孙记)
“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说明“考诸书史”是朱熹辩驳《诗序》的重要手段。《序》者说诗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傅会历史,将《诗三百》的每一篇都落实到具体的国君政事上。我们之所以说《序》者说诗是傅会历史,乃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具体的文献根据。前文在讨论文本的“辞”与“意”关系时,已经指出:“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方法只适用于“作意非辞意”这种类型的文本;而对一文本做出“作意非辞意”的类型判断,必须要有充分的背景性限制条件。如果《序》者有充分的文献材料,足以证明自己对《诗三百》文本“作意非辞意”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它对《诗三百》所作的“求诗意于辞之外”的阐释自然无可厚非。但遗憾的是,没有这样的文献材料。朱熹正是看透了这一点,《史记》、《国语》等书中没有《序》者所需要的《诗三百》的背景性材料,因此《序》者的阐释从方法上就失去了立脚之地。
“考诸书史”,发现《序》者的阐释前提存在问题;“揆以情理”,又感觉《序》的若干解释不合于人情物理。《序》还有什么能让朱熹信服呢?所以朱熹干脆另起炉灶,抛开《诗序》,涵泳文本,求诗本义。《诗序辨说·周颂·昊天有成命》篇云:“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后祀成王之诗无疑。”“详考经文”,自然即是以文本为根据;“以《国语》证之”,则是“考诸书史”了。这短短一段话,正吐露了朱熹求诗
本义的方法手段。
第二节 朱熹对《序》的具体批评
[《序》无“理”断章取义傅会历史杨慎、姚际恒等论朱熹废《序》]
诗经学汉、宋之争的关键在于是尊《序》还是废《序》。落实到文本阐释上,实际只是个是否依《序》说诗的问题。尊《序》、废《序》之争的关键,在于论者对《诗序》是否合于诗旨的判断。汉学一派以为《诗序》出于圣人(为其入室弟子所传),其对诗旨的阐释自可尊崇,故主张依《序》说诗;以朱熹为核心的宋学家以怀疑之精神,独立思考,觉《诗序》不合诗旨之处甚多,因疑其非圣人所作,故不主张依《序》说诗。“涵泳文本,求诗本义”是朱熹说诗的根本方法,“考诸书史”和“揆以情理”则是其辩驳《诗序》的具体手段。从涵泳文本自身求《诗》本义,进而发现《诗序》不尽合于《诗》旨,实是朱熹废《序》的根本。
上一节已详论《序》不合《诗》义以及朱熹不主张依《序》说诗,这一节,我们来讨论朱熹对《诗序》的具体批评。
一、《序》无“理”
朱熹是宋明理学第一大师,其为学根本即在“义理”二字。“义理”精神,在朱熹各种著述中均有深刻的体现,其治《诗经》之学亦不例外。关于朱熹诗经学与其理学思想之关系,我们将在论文的第四章给以专门讨论。此处仅就朱熹从“理”的角度批评《诗序》,略作论述。
朱熹义理之学,其根本用意乃在世道人心。其对《诗序》的批评,亦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诗序辨说·邶风·柏舟》篇云:“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是使读者疑于当时之人,绝无善者称君、过者称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则扼腕切齿,嬉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序》以美刺说诗,而刺又多于美,且其矛头多直接指向时君国政。朱熹认为这很容易误导读者,使读者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当时士人全没有“善者称君、过者称己”的美德,稍不得志,就刻薄讽刺君上。这与儒家“忠恕”、“尊卑”等基本伦理观念大相悖离,“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再如《郑风·狡童》篇,《序》云:“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诗序辨说》云:“昭公尝为郑国之君,而不幸失国,非有大恶,使其民疾之如寇仇也。况方刺其不能与圣人图事,权臣擅命,则是公犹在位也,岂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邪?……大抵《序》者之于郑诗,凡不得其说者,则举而归之于忽。文义一失,而其害于义理有不可胜言者。一则使昭公无辜而被谤;二则使诗人脱其淫谑之实罪,而丽于讪上悖礼之虚恶;三则厚诬圣人删述之意。以为实贱昭公之守正,而深与诗人之无礼于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后之说者,犹或主之。其论愈精,其害愈甚。学者不可以不察也。”按照朱熹的理解,《郑风·狡童》是一篇淫者自叙其事的“淫诗”,但《序》者将其说成是刺郑昭公忽的。可是在朱熹看来,昭公为政并无什么过失,不应“无辜而被谤”;何况为臣子的作诗,怎么能用“狡童”来称呼君上呢!?这还有什么君臣尊卑的观念在?这不仅是对诗旨理解有偏差,在义理上也有很大问题。对于以“义理”为根本的朱熹来说,这自然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我们可以这样说:“求诗意于辞之中”,发现《序》每不合于《诗》本意,是朱熹不依《序》说诗的根本原因。但其著《诗序辨说》,孜孜于辩驳、攻讦《诗序》,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序》有害于义理。
朱熹义理之学以世道人心为根本,但其为学根本途径则是“格物致知”。“格物”乃是要“格”出“物”中之“理”,所以朱熹在思考一切问题时尤其重视其内在理路。其治《诗经》亦然。朱熹在批评《序》无“义理”的同时,也对《序》有悖于一般性的“理”多有指陈。这一般性的“理”包括情理、文理等。《诗序辨说》对《序》无理的指陈比比皆是,共有17例(附录3)。
附录3:《诗序辨说》指陈《序》无理例:
01 《周南·关雎》,《序》:“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诗序辨说》:“按《论语》孔子尝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盖淫者乐之过,伤者哀之过,独为是诗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乐中节,而不至于过耳。而序者乃析哀乐淫伤,各为一事,而不相须,则已失其旨矣。至以伤为伤善之心,则又大失其旨,而全无文理。”
02 《卫风·氓》,《诗序辨说》:“……其曰美反正者,尤无理。”
03 《郑风·山有扶苏》,《诗序辨说》:“此下四诗(按:《萚兮》、《狡童》、《褰裳》、《丰》)及《扬之水》,皆男女戏谑之词。序之者不得其说,而例以为刺忽,殊无情理。”
04 《郑风·狡童》,《诗序辨说》:“大抵序者之于郑
诗,凡不得其说者,则举而归之于忽。文义一失,而其害于义理有不可胜言者。一则使昭公无辜而被谤……”
05 《魏风·十亩之间》,《诗序辨说》:“国削则其民随之,序文殊无理。”
06 《唐风·蟋蟀》,《诗序辨说》:“况古今风俗之变,常必由俭以入奢,而其变之渐,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谓君之俭反过于初,而民之俗犹知用礼,则尤恐其无是理也。”
07 《唐风·无衣》,《诗序辨说》:“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颠倒顺逆,乱伦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
08 《秦风·渭阳》,《诗序辨说》:“此序得之。但我见舅氏,如母存焉两句,若为康公之辞者,其情哀矣。然无所系属,不成文理。”
09 《豳风·破斧》,《诗序辨说》:“此归士美周公之词,非大夫恶四国之诗也。且诗所谓四国,犹言斩伐四国耳,序说以为管蔡商奄,尤无理也。”
10 《小雅·白华》,《诗序辨说》:“此序尤无理。”
11 《小雅·雨无正》,《诗序辨说》:“此序尤无义理,欧阳公、刘氏说已见本篇。”
12 《小雅·鸳鸯》,《诗序辨说》:“此序穿凿,尤为无理。”
13 《大雅·旱麓》,《诗序辨说》:“序大误。其曰百福干禄者,尤不成文理。”
14 《大雅·行苇》,《诗序辨说》:“(说者)碎读之,逐句自生意义,不暇寻绎血脉,照管前后……随文生义,无复伦理。”
15 《大雅·韩奕》,《诗序辨说》“其曰能赐命诸侯,则尤浅陋无理矣。既为天子,赐命诸侯,自其常事。春秋
战国之时犹有能行之者,亦何足为美哉?”
16 《大雅·召旻》,《诗序辨说》:“旻闵以下不成文理。”
17 《周颂·昊天有成命》,《诗序辨说》:“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两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己意。其淤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
以上17例都是直接批评《序》无“理”的。有批评《序》无义理的,如例04,例07,例11。有批评《序》的解释不合于情理的,如例03,06,这种情况前文论朱熹说《诗》但求不远于人情物理时已有讨论。更多的例子则是批评《序》无“文理”,也即说《序》不合文章逻辑。
《诗序辨说》还有些地方虽未出现“无理”之类的字样,但实际上也是认为“无理”的。如《周南·卷耳》篇,《诗序辨说》云:“首章之我独为后妃,而后章之我为使臣,首尾衡决不相承应,亦非文字之体也。”虽未出现“无理”字样,实际是说无文理。再如《唐风·山有枢》篇,《诗序辨说》云:“此诗盖以答《蟋蟀》之意,而宽其忧。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说大误。”虽未曾出现“无理”字样,实际是说不合情理、有悖义理。
不管是“义理”、“情理”,还是“文理”,凡是朱熹批评《序》无“理”的,都是说《序》对《诗》的解说没有道理。从有理无理的角度来辨《序》,正是朱熹的特色。《诗序辨说》中也有说到《序》有“理”的地方,如《诗序辨说·大雅·云汉》篇云:“此序有理”,《诗序辨说·大雅·常武》篇云:“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于理亦通”。但说《序》有“理”之处相对来说是极少的。在朱熹看来,不通、无理才是《序》的基本特色。
《小雅·小宛》篇,《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不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乱畏祸而相戒之辞尔。”《诗集传》于其篇末云:“此诗之辞最为明白,而意极恳至。说者必欲为刺王之言,故其说穿凿破碎,无理尤甚。今悉改定,读者详之。”朱熹批评《序》者无“理”,说到底,还是看不惯它的穿凿傅会。
二、断章取义
朱熹还指出《诗序》在说诗时有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断章取义;二是傅会历史。
现代诗经学对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多有专门研究。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①一文,反复强调“赋诗言志”多采取“断章取义”的方法,而不管作诗的本义。朱自清《诗言志辨·诗言志·赋诗言志》②亦指出:“赋诗言志”是从外交方面出发,诗以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与献诗陈己志不同。其特点是颂多而讽少,与献诗相反。“献诗的诗都有定旨,全篇意义明白。赋诗却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断章取义只是借用诗句作自己的话,所取的只是句子的文义,就是字面的意思,而不管全诗用意,就是上下文的意思。”《诗言志辨·比兴·兴义溯源》则指出:“赋诗只取一二章,并且只取一章中一二句,以合己意,叫作‘断章取义’,引诗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借用古诗,加以引申,取其能明己意而止。‘作诗人之意’是不问的。”毛、郑解《诗》是“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以断章之义为全章全篇之义,而说比兴时尤然。”
其实,朱熹对“赋诗言志”多“断章取义”、汉儒说《诗》受“赋诗言志”影响这两个义例早有发明。朱熹有云:“《左传》所载歌诗,多与本意元不相关。”(80/2071,叶贺孙记),这便是说《左传》所载“赋诗言志”多是“断章取义”了。《诗序辨说》中有两处直接说到《序》者说诗受先秦人赋诗、引诗“断章取义”的影响。
其一是《郑风·褰裳》篇,《序》云:“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诗序辨说》云:“此序之失,盖本于子太叔、韩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断章取义之意耳。”朱熹这里说的“盖本于子太叔、韩宣子之言”,是指《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的一次“赋诗言志”。兹录《左传》原文相关章节于下: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怕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子太叔赋的正是《褰裳》这篇诗。顾颉刚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中对此作过很好的演绎,他说:
这一次,因为韩宣子要“知郑志”,所以郑六卿赋的都是郑诗。郑国的诗是情诗最多,所以这一次赋的诗也是情诗特多;如子太叔赋的《褰裳》,就是情思很荡的!“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这正是荡妇骂恶少的口吻,说:“你不要我,难道就没有别人吗?”淫荡的态度真活画出来了!子太叔断章取义,用在这里,比喻他愿意从晋,只恐晋国的拒绝;所以韩宣子就说:“我在这里,怎会使你去寻别人呢!”子太叔拜谢他,他又说:“没有这样的警戒,那能有始有终呢!”可见断章取义的用处,可以不嫌得字句的淫亵,不顾得作诗人的本义。
顾颉刚的演绎,足以很好地说明春秋时“赋诗言志”是可以不顾作诗人的本义。《褰裳》的字面意义自然是一篇情诗,可是子太叔用来表示自己从晋的意愿,韩宣子也很明白他的意思。郑国权臣子产最后拜谢韩宣子,说的是:“吾子靖乱,敢不拜德!”郑国弱小,晋国强大,所以郑需要晋帮助靖乱。《褰裳》《序》云:“国人思大国之正己”,正是由此而来。朱熹是明眼人,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序》不明白“赋诗”是“断章取义”的道理,而上了子太叔、韩宣子的当。故《朱子语类》有云:“《褰裳》诗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岂不是淫奔之辞!只缘《左传》中韩宣子引‘岂无他人’,便将做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不知古人引《诗》,但借其言仪寓己意,初不理会上下文义,偶一时引之耳。”(80/2091,黄㽦记)。
其二是《大雅·既醉》篇,《序》云:“太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诗序辨说》云:“序之失如上篇(作文按:《大雅·行苇》),盖亦为孟子断章所误尔。”按:《孟子·告子(上)》:“《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朱熹亦看出了《序》者对该篇的解说受到了《孟子》的影响。但是《孟子》是引一句诗来说明自己要说的道理,这句诗已经从原诗中割离开来,它不再是原诗的一个有机组成,而要在新的结构中发挥意义上的作用。原诗完整的章节是“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此父兄所以答《行苇》之诗,言享其饮食恩意之厚,而愿其受福如此也。”朱熹的解释明显比《序》要合于情理和文意。《序》者正是被孟子断章所误。
《诗序辨说》于《大雅·行苇》篇,对汉儒断章取义的说诗方法做了尖锐的批评。该篇《序》云:“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考〓,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诗序辨说》云:“此诗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说者不知比兴之体、音韵之节,遂不复得全诗之本意,而碎读之,逐句自生意义,不暇寻绎血脉,照管前后。但见‘勿践行苇’,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但见‘黄〓台背’,便谓‘养老’;但见‘以祈黄〓’,便谓‘乞言’;但见‘介尔景福’,便为‘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伦理。诸序之中,此失尤甚。览者详之。”
《朱子语类》亦云:“看来《诗序》当时只是个山东学究等人做,不是个老师宿儒之言,故所言都无一事是当。如《行苇》之《序》虽皆是诗人之言,但却不得诗人之意。不知而今做诗人到这处将如何做,于理决不顺。”(80/2078,黄卓记)。又云:“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80/2075,周谟记)。
不顾血脉文理,割裂全篇,仅就一句傅会生说,正是汉儒的伎俩。但是文本的有机整体性是在对文本进行阐释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文本局部(单独的一句诗)的含义受整体(完整的一篇诗或一章诗)制约,不能将局部从整体中割裂开来。只有将局部纳入整体之中,将局部当成整体的一个组成,其阐释才是有效的。失去整体制约的局部文本,其阐释的外部限定性条件过于单薄。对于单独的一句诗,阐释者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主观意志,对其进行多种可能性的解释;但这种阐释很难进行文本还原,即与它在文本整体限定条件下的意义很难符合。前引《大雅·既醉》篇的例子,《孟子》将“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解释为饱乎仁义,单从这两句自身来看,这样的解释是可以的。但将它还原为原诗完整章节“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的一个有机组成时,这样的解释就不很妥帖了。单就一句生说的方法,正是忽视了文本的有机整体性。如《行苇》一诗,《序》的解说每一句都是对应于诗辞的,但却没有将其当成一个有机整体来阐释,所以还是与诗人的本意有很大距离。所以朱熹说:“《行苇》之《序》虽皆是诗人之言,但却不得诗人之意。”
《诗序辨说》指明《小序》是“断章取义”、“仅就一句生说”的例子,在《郑风·褰裳》、《大雅·既醉》、《大雅·行苇》之外尚有8例,共11例(附录4)。
附录4:《诗序辨说》指陈《小序》“断章取义”、“仅就一句生说”例:
01《周南·汉广》,《序》:“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诗序辨说》:“此诗以篇内有‘汉之广矣’一句得名,而序
者谬误,乃以德广所及为言,失之远矣。”
02 《郑风·褰裳》,《序》:“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诗序辨说》:“此序之失,盖本于子太叔、韩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断章取义之意耳。”
03 《郑风·野有蔓草》,《序》:“思遇时也。君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诗序辨说》:“东莱吕氏曰:‘君之泽不下流,乃讲师见零露之语从而附益之。’”
04 《小雅·蓼萧》,《序》:“泽及四海也。”《诗序辨说》:“序不知此为燕诸侯之诗,但见零露之云,即以为泽及四海。其失与《野有蔓草》同。臆说浅妄类如此云。”
05 《小雅·甫田》,《序》:“刺幽王也,君子伤今而思古焉。”《诗序辨说》“此序专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说,而不察其下文‘今适南亩’以下,亦未尝不有年也。”
06 《小雅·大田》,《序》:“刺幽王也。言鳏寡不能自存焉。”《诗序辨说》:“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
07 《小雅·裳裳者华》,《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则谗谄并进,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焉。”《诗序辨说》:“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说。”
08 《小雅·桑扈》,《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动无礼文焉。”《诗序辨说》:“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说。”
09 《大雅·行苇》,《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诗序辨说》:“此诗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说者不知比兴之体、音韵之节,遂不复得全诗之本意,而碎读之,逐句自生意义,不暇寻绎血脉,照管前后。但见‘勿践行
苇’,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但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但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但见‘介尔景福’,便为‘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伦理。诸序之中,此失尤甚。”
10 《大雅·既醉》篇,《序》云:“太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诗序辨说》云:“序之失如上篇(作文按:《大雅·行苇》),盖亦为孟子断章所误尔。”
11 《大雅·凫鹥》,《序》:“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祗祖考安乐之也。”《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大雅·既醉》)。”
三、傅会历史
傅会历史主要是因为汉儒过于迷信“风雅正变”之说,依据世次来定诗之美刺。凡是一篇诗,在汉儒看来一定是要对时政有所美刺的。凡是时代在前(周初文武成康时)的,一律是“美”;时代在后的,一般就认定是“刺”,而且往往要派附给恶谥之君。若是世次在后,而文意为美的,便说是“陈古刺今”。《诗序辨说》于《邶风·柏舟》篇对此辩驳尤为有力,朱熹指出:“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而其时世名氏,则不可以强而推。故凡《小序》,惟诗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于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诗序》)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傅会书史,依托名谥,凿空妄语,以误后人……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并对《诗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的傅会方法做了具体剖析,曰:“盖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以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甑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序予之。”朱熹的意思是:《诗三百》作品的文意,可以根据文本推敲而得;但其具体时代及当事人,却不能凭空傅会。《诗三百》作品的具体时代和当事人可分为三种类型:1、诗文自身已经明白指出的,如《陈风·株林》有“从夏南”(作文按:夏南,即夏徵舒,陈灵公时人。)之句;2、历史文献对其创作背景有明确记载的,如《左传·闵公二年》有云“许穆夫人赋《载驰》”;3、诗文自身及历史文献对其时代及当事人皆无具体说明的。相对来说,前两种类型是少数,《诗三百》多数作品属于后一种类型。对于这后一种类型,其时代及当事人实际是不可确考的,但是《诗序》却对其每一篇的时代及当事人都加以强行编派,这自然难免是“强不知以为知”,难逃后人“穿凿傅会”之讥。
朱熹在具体辩驳《诗序》傅会历史时,大抵不外乎以下三端:1、妄断世次;2、美刺不当;3、滥用“陈古刺今”。而这三者之间又往往呈交叉关系。
(1)妄断世次
朱熹对《诗序》在没有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强行编派《诗三百》作品以具体时代与当事人,很不满意。《诗序辨说》专辨此类情况的例子很多。一般来说,《序》对《诗三百》作品时代的认定,已经包含对当事人的认定在内。辩驳其具体时代与辩驳当事人往往是同一件事。有个别情况看上去比较特殊,如《小雅·大东》篇,《序》云:“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诗序辨说》云:“谭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据。”这似乎是专辨当事人的。但既然说当事人不可考,自然隐含时代不可考在其中了。
《正大雅》以及《周颂》的时代,朱熹与汉学诗经学在认识有较大分歧。《诗集传》于《大雅·文王之什》作结云:“《郑谱》此以上为文武时诗,以下为成王周公时诗。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则非文王之诗矣。又曰‘无念尔祖’,则非武王之诗矣。《大明》、《有声》,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为文武之时所作乎?盖《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后之诗,但些什皆追述文武之德,故《谱》因此而误耳。”郑玄《诗谱》认为《大雅》《文王有声》以上皆为文王、武王时诗,朱熹不以为然。对于《周颂》,《郑谱》认为都是周公所定;《诗序辨说》于《昊天有成命》、《执竞》二篇则对此专门辩驳(内容详见附录5),朱熹认为《周颂》亦有康王以后的作品。
朱熹还发现《序》对《诗三百》世次的编派有自相矛盾之处。《小雅·常棣》篇,《序》云:“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诗序辨说》云:“序得之,但与《鱼丽》之序相矛盾。以诗意考之,盖此得而彼失也。”按:《小雅·鱼丽》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常棣》篇目在《天保》之前,很明显,《序》者认为《常棣》的时代是文、武之时。但“管蔡之失道”却发生在武王去世以后。所以《诗集传》次章云:“此诗盖周公既诛管蔡而作……序以为闵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为文武之诗则误矣。大抵旧说诗之时世,皆不足信。举此自相矛盾者,以见其一端,后不能悉辨也。”
今检《诗序辨说》与《诗集传》,知朱熹明确辩驳《序》所编派世次与当事人者,共39处(详见附录5),实际篇目则为60篇,占《诗经》全部作品的20%左右。(计算方法:如《诗序辨说·秦风·车邻》云:“未见其必为秦仲之诗,大率《秦风》惟《黄鸟》、《渭阳》为有据,其他诸诗皆未有考。”按:《秦风》共有10篇作品,《诗序辨说》于《车邻》、《小戎》2篇有辩,又云《黄鸟》、《渭阳》有据,则“皆未有考”的“其他诸诗”包括《驷驖》、《蒹葭》、《终南》、《晨风》、《无衣》、《权舆》6篇。计算具体篇目时,应加入这6篇。余者依此类推,不另说明。)
附录5:朱熹辩驳《诗序》妄断世次例:
01 《召南·何彼襛矣》,《诗序辨说》“此诗世次不可知”。《诗集传》首章:“此乃武王以后之诗,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作文按:《序》以为二南皆文王时诗。)
02 《邶风·柏舟》,《序》:“卫顷公之时。”《诗序辨说》(略)。
03 《邶风·日月》,《序》:“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诗序辨说》:“此诗序以为庄姜之作,今未有以见其不然。但谓遭州吁之难而作,则未然耳。盖诗言宁不我顾,犹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无良,亦非所以施于前人者。明是庄公在时所作,其篇次亦当在《燕燕》之前。”
04 《邶风·终风》,《序》:“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诗序辨说》:“详味此诗,有夫妇之情,无母子之意。若是庄姜之诗,则亦当在庄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
05 《邶风·雄雉》,《序》:“刺卫宣公也。”《诗序辨说》:“未有以见其为宣公之时。”
06 《邶风·匏有苦叶》,《序》:“刺卫宣公也。”《诗序辨说》:“未有以见其为刺宣公、夫人之诗。”
07 《卫风·氓》,《序》:“刺时也。宣公之时,……”《诗序辨说》:“宣公未有考。”
08 《王风·君子于役》,《序》:“刺平王也。”《诗序辨说》:“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09 《郑风·狡童》,《序》:“刺忽也。”《诗序辨说》:“大抵序者之于郑诗,凡不得其说者,则举而归之于忽。”(作文按:《序》将郑诗归之于忽者,尚有《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
10 《齐风·鸡鸣》,《序》:“哀公荒淫怠慢。”《诗序辨说》:“哀公未有所考。”
11 《齐风·还》,《序》:“哀公好田猎。”《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鸡鸣》)。”
12 《齐风·甫田》,《序》:“大夫刺襄公也。”《诗序辨说》:“未见其为襄公之诗。”
13 《齐风·敝笱》,《序》:“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也。”《诗序辨说》:“桓当作庄。”
14 《唐风·采苓》,《序》:“刺晋献公也。”《诗序辨说》:“献公固喜攻战而好谗佞,然未见此二诗之作于其时也。”(作文按:包括前篇《葛生》。)
15 《秦风·车邻》,《序》:“美秦仲也。”《诗序辨说》:“未见其必为秦仲之诗,大率秦风惟《黄鸟》、《渭阳》为有据,其他诸诗皆未有考。”(作文按:包括《驷驖》、《蒹葭》、《终南》、《晨风》、《无衣》、《权舆》。)
16 《秦风·小戎》,《序》:“美襄公也。”《诗序辨说》:“此诗时世未必然。”
17 《陈风·墓门》,《序》:“刺陈佗也。”《诗序辨
说》:“陈国君臣,事无可纪。独陈佗以乱贼被讨,见书于《春秋》,故以无良之诗与之。序之作大抵类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18 《曹风·蜉蝣》,《序》:“昭公国小而迫。”《诗序辨说》:“言昭公未有考。”
19 《曹风·候人》,《序》:“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诗序辨说》:“此诗但以三百赤芾合于《左传》所记晋侯入曹之事,序遂以为共公,未知然否。”
20 《小雅·采薇》,《序》:“文王之时。”《诗序辨说》:“此未必文王之诗,以天子之命者衍说也。”
21 《小雅·出车》,《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采薇》)。诗所谓天子,所谓王命,皆周王耳。”
22 《小雅·杕杜》,《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出车》)。”
23 《小雅·南有嘉鱼》,《诗序辨说》:“又以专指成王,皆失之矣。”
24 《小雅·鸿雁》,《序》:“美宣王也。”《诗序辨说》:“此以下时世多不可考。”《诗集传》首章章末:“未有以见其为宣王之诗。后三篇(作文按:《庭燎》、《沔水》、《鹤鸣》)放次。”
25 《小雅·祈父》,《序》:“刺宣王也。”《诗集传》篇末:“今考之诗文,未有以见其必为宣王耳。”
26 《小雅·黄鸟》,《序》:“刺宣王也。”《诗集传》篇末:“今按诗文,未见其为宣王之世,下篇(作文按:《我行其野》)亦然。”
27 《小雅·斯干》,《序》:“宣王考室也。”《诗集传》篇末:“今亦未有以见其必为是时之诗也。”
28 《小雅·节南山》,《序》:“家父刺幽王。”《诗集传》篇末:“序以此为幽王之诗。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来聘,于周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终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异。大抵序之时世皆不足信,今姑阙焉可也。”
29 《小雅·雨无正》,《序》:“大夫刺幽王也。”《诗集传》篇末:“其为幽王诗,亦未有所考。”
30 《小雅·何人斯》,《序》:“苏公刺暴公也。”《诗序辨说》:“但此诗中只有暴字,而无公字及苏公字,不知序何所据而得此事也。”《诗集传》:“旧说暴公为卿士,而谮苏公,故苏公作诗以绝之……但旧说于诗无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也。”
31 《小雅·大东》,《序》:“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诗序辨说》:“谭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据。”
32 《小雅·鼓钟》,《序》:“刺幽王也。”《诗序辨说》“此诗文不明,故序不敢质其事,但随例为刺幽王耳。实皆未可知也。”
33 《小雅·黍苗》,《序》:“刺幽王也。”《诗序辨说》:“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
34 《小雅·渐渐之石》,《序》:“下国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序得诗意,但不知果为何时耳。”
35 《大雅·文王有声》,《序》:“继伐也。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卒其伐攻也。”《诗序辨说》:“《郑谱》之误,说见本篇。”《诗集传》篇末:“《郑谱》此以上为文武时诗,以下为成王周公时诗。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则非文王之诗矣。又曰无念尔祖,则非武王之诗矣。《大明》、《有声》,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为文武之时所作乎?盖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后之诗,但些什皆为追述文武之德,故《谱》因此而误耳。”
36 《大雅·假乐》,《序》:“嘉成王也。”《诗序辨说》:“假本嘉字,然非为嘉成王也。”
37 《大雅·公刘》,《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诗序辨说》:“然此诗未有以见其为康公之作意,其传授或有自来耳,后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作文按:包括《泂酌》、《卷阿》、《民劳》、《板》、《荡》。)
38 《周颂·昊天有成命》,《诗序辨说》:“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后祀成王之诗无疑。而毛、郑旧说,定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故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两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己意。其淤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
39 《周颂·执竞》,《诗序辨说》“此诗并及成康,则序说误矣。其说已具于《昊天有成命》之篇。”
(2)美刺不当
《序》者以美刺说诗,认为《诗三百》皆是美刺国君时政之作,朱熹于此深为不满。《朱子语类》颇多这方面的意见:
01 “温柔敦厚”,诗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讥刺人,安得“温柔敦厚”!(80/2065,滕璘记)
02 《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80/2074,郑可学记)
03 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如此,亦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雕,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情性之正?(80/2076—2077,叶贺孙记)
04 《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诗虽存,而意不可得。序诗者妄诞其说,但疑见其人如此,便以为是诗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庄姜之诗,却以为刺卫顷公。今观《史记》所述,顷公竟无一事可纪,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无其事。顷公固亦是卫一不美之君。序诗者但见其诗有不美之迹,便指为刺顷公之诗。此类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无其实。至有不能考者,则但言“刺诗也”,“思贤妃也”。然此是泛泛而言。(80/2078,黄卓记)
…………
以上四条材料说明:朱熹认为《诗三百》中应该颇有一些作品与今人作诗是同样的情形,不过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而已,未必都是讥刺他人。如果篇篇都是讥刺国君,又哪里能算“温柔敦厚”呢?但是《诗序》却是以美刺说诗,对每一篇作品都要来一个或“美”或“刺”的解释,这有什么道理呢?在《诗》辞文意与背景条件两方面都不能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序》凭什么断定一篇作品一定是美(或刺)那个人(具体的国君)呢?在朱熹看来,《诗序》“美刺不当”之处实在是太多了。朱熹指陈《诗序》“美刺不当”,大抵分两种类型:一是诗文自身本无关美刺的;二是《序》所认定的“美”“刺”与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的。
“无关美刺”的典型是“淫诗”。如《鄘风·桑中》篇,《序》云:“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诗集传》云:“此人自言将采唐于沫,而与其所思之人,相期会迎送如此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序》者认为该篇是诗人刺淫奔之作;朱熹则认为是淫奔者所自作,是“淫者”自叙其事,自抒其情,与美刺无关。又如《陈风·防有鹊巢》,《序》云:“忧谗也。宣公多信谗,君子忧惧焉。”《诗集传》云:“此男女之有私,而忧或间之之辞。”《诗序辨说》云:“此不得为刺诗。”《序》者认为该篇是刺宣公(信谗)的,朱熹则认为是淫奔男女“忧或间之之辞”,与刺宣公全不相关。(关于“淫诗”的问题,将在论文的第二章专门讨论。朱熹认定《诗三百》中共有“淫诗”28篇。)
“淫诗”之外,朱熹亦指出另外一些篇目本“无关美刺”,但《序》者却以美刺说之。如《邶风·凯风》篇,《序》云:“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诗序辨说》云:“此乃七子自责之辞,非美七子之作也。”既是“自责”,自然无关美刺。这是无关美刺而《序》者以为“美”的例子。
至于无关美刺而《序》者以为“刺”的,有6例(附录6)。
附录6:《诗序辨说》指陈无关美刺而《序》者以为刺例:
01 《郑风·叔于田》,《序》:“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说而归之。”《诗序辨说》:“国人之心贰于叔,而歌其田狩适野之事,初非以刺庄公,亦非说其出于田而后归之也。”
02 《郑风·大叔于田》,《序》:“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诗序辨说》:“此诗与上篇(作文按:《叔于田》)意同,非刺庄公也。”
03 《唐风·绸缪》,《序》:“刺晋乱也。国乱则昏姻不得其时也。”《诗序辨说》:“此但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词,未必为刺晋国之乱也。”
04 《小雅·小宛》,《序》:“大夫刺幽王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不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乱畏祸而相戒之辞尔。”
05 《小雅·绵蛮》,《序》:“微臣刺乱也。大臣不用仁心,遗忘微贱,不肯饮食教载之,故作是诗也。”《诗序辨说》“此诗未有刺大臣之意,盖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则褊狭之甚,无复温柔敦厚之意。”
06 《大雅·抑》,《序》:“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诗序辨说》:“其曰刺厉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
在朱熹看来,例01、例02是国人歌唱叔段的,与刺庄公本无关系。例03是“为昏姻者相得而喜”,例04是兄弟之间自相劝诫,例05是微臣自道其心之所欲,例06是卫武公自警,自然都与美刺无关了。
朱熹认为《序》所认定的“美”“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有两种类型:一是本当为“刺”,而《序》以为“美”;二是本当为“美”,而《序》以为“刺”。前者的典型例证是《唐风·无衣》,该篇《序》云:“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诗序辨说》云:“序以为美之,失其旨矣。”后者有5例(附录7)。
附录7:《诗序辨说》指陈《序》误美为刺例:
01 《卫风·考槃》,《序》:“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诗序辨说》:“此为美贤者穷处而能安其乐之诗,文意甚明。然诗文未有见弃于君之意,则亦不得为刺庄公矣。”
02 《魏风·伐檀》,《序》:“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诗序辨说》:“此诗专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贪,失其旨矣。”
03 《曹风·鸤鸠》,《序》,“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诗序辨说》:“此美诗,非刺诗。”
04 《小雅·隰桑》,《序》:“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诗序辨说》:“此亦非刺诗。疑与上篇(作文按:《黍苗》)脱简在此也。”
朱熹批评《序》者“美刺不当”,“刺”者不当的例子比“美”者不当的要多,这是因为《序》所认定的“刺”诗比“美”诗多。《序》者编派刺诗世次的通例是刺以谥恶而得之。《朱子语类》有云:“问:《诗传》尽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硕人》、《定之方中》等,见于《左传》者,自可无疑。若其他刺诗无所据,多是世儒将他谥号不美者,挨就立名尔。”(80/2078,余大雅记)又云:“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谥,却傅会作《小序》美刺。”(《朱子语类》,80/2079,吴振记)。这与前引《诗序辨说·邶风·柏舟》篇所论,强调的都是“刺以谥恶而得之”这一个通例。《邶风·柏舟》篇之外,《诗序辨说》尚于其他5篇指出《序》所刺国君是因为其谥恶(附录8)。
附录8:《诗序辨说》指陈“刺以谥恶而得之”例:
01 《齐风·鸡鸣》,《序》:“哀公荒淫怠慢。”《诗序辨说》:“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岂亦以谥恶而得之欤?”
02 《齐风·还》,《序》:“哀公好田猎。”《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鸡鸣》)。”
03 《唐风·蟋蟀》,《序》:“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娱乐也。”《诗序辨说》:“所谓刺僖公者,盖特以谥得之。”
04 《陈风·宛丘》,《序》:“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诗序辨说》:“陈国小,无事实。幽公但以谥恶,故得游荡无度之诗。未敢信也。”
05 《陈风·东门之粉》,《序》:“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宛丘》)。”
综上,朱熹直接指出《诗序》“美刺不当”的有46篇,占《诗经》全部作品的15%左右。(其中“无关美刺”的35篇:“淫诗”28篇之外,《序》者误以为“美”的1篇,误以为“刺”的6篇。《序》所认定的“美”、“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5篇:误“美”为“刺”的1篇,误“刺”为“美”的4篇。“刺以谥恶而得之”的6篇。)
(3)滥用“陈古刺今”
前引《诗序辨说·邶风·柏舟》篇云:“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序》者以美刺说诗,又囿于“风雅正变”之说,于《变风》、《变雅》非美谥贤君之时而辞意为美者,便一律说成是“陈古刺今”。《诗序辨说·郑风·羔裘》云:“序以《变风》不应有美,故以此为言古以刺今之诗。今详诗意,恐未必然。且当时郑之大夫,如子皮、子产之徒,岂无可以当此诗者?但今不可考耳。”亦指出《序》以该篇为“陈古刺今”,是基于“《变风》不应有美”这一认识。《诗序辨说·小雅·楚茨》云:“自此篇至《车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无讽刺之意。序以为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诗固有如此者,然不必十篇相属,而绝无一言以见其为衰世之意也。窃恐《正雅》之篇有错脱在此耳,序皆失之。”朱熹以词气为根据,判断《小雅》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
华》、《桑扈》、《鸳鸯》、《頍弁》、《车舝》这十篇作品是“美诗”而非“刺诗”,并指出《序》者以之为“刺诗”的原因是它们在《变雅》之中,被当成了“伤今思古之作”。朱熹对这种“陈古刺今”的理解实不以为然。《朱子语类》云:“《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傅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便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甚多。”(80/2074,郑可学记)。也是批评《序》者说诗滥用“陈古刺今”。
《小序》明言“陈古刺今”的有13处,其篇目如下(附录9)。
附录9:《小序》明言“陈古刺今”例:
01 《王风·大车》,“大车,刺周大夫也。礼义陵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焉。”
02 《郑风·羔裘》,“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诗序辨说》:“序以变风不应有美,故以此为言古以刺今之诗。今详诗意,恐未必然。且当时郑之大夫,如子皮、子产之徒,岂无可以当此诗者?但今不可考耳。”
03 《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诗序辨说》:“此亦未有以见陈古刺今之意。”
04 《齐风·卢令》,《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猎毕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陈古以风焉。”
05 《小雅·楚茨》,《序》:“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谨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诗序辨说》:“自此篇至《车舝》凡十篇(作文按:1、《楚茨》,2、《信南山》,3、《甫田》,4、《大田》,5、《瞻彼洛矣》,6、《裳裳者华》,7、《桑扈》,8、《鸳鸯》,9、《頍弁》,10、《车舝》。),似出一手,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无讽刺之意。序以为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诗固有如此者,然不必十篇相属,而绝无一言以见其为衰世之意也。窃恐《正雅》之篇有错脱在此耳,序皆失之。”
06 《小雅·信南山》,《序》:“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07 《小雅·甫田》,《序》:“刺幽王也。君子伤今而思古焉。”
08 《小雅·瞻彼洛矣》,《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诸侯,赏善罚恶焉。”
09 《小雅·鸳鸯》,《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万物有道,自奉养有节焉。”
10 《小雅·鱼藻》,《序》:“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诗序辨说》:“此诗序与《楚茨》等篇相类。”
11 《小雅·采菽》,《序》:“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诗序辨说》:“同上。”
12 《小雅·都人士》,《序》:“周人刺衣服无常也。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一。伤今不复见古人也。”
13 《小雅·瓠叶》,《序》:“大夫刺幽王也。上弃礼而不能行,虽有牲牢饔饩,不肯用也。故思古人不以微薄废礼焉。”
这13例以外,《小雅·黍苗》篇《序》云:“刺幽王也。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郑笺》云:“陈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群臣废此恩泽事业焉。”《诗序辨说》云:
“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乃指今之卿士不能行周宣王时召穆伯之职,实际上也是“陈古刺今”。另有一些篇目,《诗序》虽未明言是“陈古刺今”,但《郑笺》、《孔疏》却指出其是“陈古刺今”。如《小雅·大田》篇,《序》云:“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也”,并未明言该篇是“陈古刺今”;《郑笺》却云:“幽王之时,政烦赋重而不务农事,虫灾害谷,风雨不时,万民饥馑,矜寡无所取活,故时臣思古以刺之”,明确指出是“陈古刺今”。《孔疏》亦云:“四章皆陈古善反以刺王之辞。”
“陈古刺今”是汉学诗经学说《诗》的一个通例。朱熹对汉学诗经学以“陈古刺今”为由所认定的“刺诗”,大抵都以其辞意为根据,当作美诗来理解。再如《齐风·鸡鸣》一篇,《诗序》云:“《鸡鸣》,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诗集传》首章云:“言古之贤妃御于君所,至于将旦之时,必告君曰:鸡既鸣矣,会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视朝也。……故诗人叙其事而美之也。”是朱熹以为该篇亦是“陈古”,但却不是“刺今”,所以将其视为“美诗”。
《诗序辨说》还对《序》所认定的诗之作者有所辩驳,这以“淫诗”最为典型。我们在论文第二章论朱熹对《诗经》抒情主体性的认识时,将对这个问题作专门讨论。朱熹将“淫诗”处理为“淫者”自作,与《序》者理解为诗人刺淫大异其趣。“淫诗”之外,《诗序辨说》也对一些篇目《序》所认定的作者提出了质疑。如《小雅·小弁》篇,《序》云:“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诗序辨说》云:“此诗明白为放子之作无疑,但未有以见其必为宜臼耳。序又以为宜臼之傅,尤不知所据也。”
四、杨慎、姚际恒等论朱熹废《序》
后人对朱熹废《序》,有两种批评意见影响较大。一是认为朱熹废《序》实乃出于一时偏激;二是认为朱熹废《序》太不彻底。前一种意见以杨慎和《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后一种意见的始作俑者是姚际恒。
《四库全书总目·诗集传提要》云:“杨慎《丹铅录》谓文公因吕成公太尊《小序》,遂尽变其说。虽臆度之词,或亦不无所因欤!”今检杨慎《丹铅余录·总录(卷十八)·诗小序》,有云:朱子作《诗传》,尽去《小序》,盖矫吕东莱之弊。一时气使之偏,非公心也。马端临及姚牧庵诸家辨之悉矣。有一条可发一笑,并记于此。《小序》云“菁莪,乐育人才也”,“子衿,学校废也”,《传》皆以为非。及作《白鹿洞赋》,有曰“广青衿之疑问”,又曰“乐菁莪之长育”。或举以为问,先生曰:“旧说亦不可废。”此何异俗谚所谓“玉波去四点,依旧是王皮”乎!
愚按:杨慎此说颇可商榷。吕东莱是宋代诗经学遵《序》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对其太尊《小序》颇有微词,这是事实。《朱子语类》中颇多议论吕东莱太尊《小序》之处,如:
01 伯恭专信《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要出脱回护。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80/2074,邵浩记)
02 东莱《诗记》却编得子细,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说甚么?向尝与之论此,如《清人》、《载驰》一二诗可信。渠却云:安得许多文字证据?某云:无证而可疑者,只当阙之,不可据《序》作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
也。此是《序》者大害处!(80/2076—2077,叶贺孙记)
03 问:《诗传》多不解《诗序》,何也?曰: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缪戾,有不可胜言。东莱不合只因《序》讲解,便有许多牵强处。某尝与言之,终不肯信。《读诗记》中虽多说《序》,然亦有说不行处,亦废之。某因作《诗传》,遂成《诗序辨说》一册,其他缪戾,辨之颇详。(80/2078,李煇记)
这三条都是批评吕东莱太尊《小序》,其所著《读诗记》亦不得诗人本意。朱熹废《序》,且对吕东莱太尊《小序》有专门批评,确实也可以说是欲矫其弊。但这并不是一种意气之争,而是两个学派、两种不同说诗方法之争。在这里,吕东莱和朱熹是作为两个学派的代表,吕东莱是尊《序》派的代表,朱熹是废《序》派的代表。朱熹对吕东莱的批评实际是对整个尊《序》派的批评,这要远远超过对具体个人的批评。朱熹以“求诗意于辞之中”为根本方法,一切以文本自身为根据,揆以情理,考诸书史,进而发现《序》多不合于《诗》本意,这是他废《序》的根本原因。朱熹废《序》实有深刻的思考与系统的理论根据为基础,而非一时冲动。况朱熹自言“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缪戾,有不可胜言”。朱熹年长于吕东莱七岁,朱熹二十、三十之时,吕东莱尚未著《读诗记》,何可言朱子废《序》是受吕东莱的刺激?!杨慎之说固为臆度之词矣。杨慎“一时气使之偏,非公心也”之说,实厚诬古人。《四库全书总目》引申杨慎之说,云“遂尽变其说”,其意以为此前朱熹解《诗》是依《序》说解,待吕东莱《读诗记》成书之后,出于意气之争,乃废《序》不用,实亦出于汉学一派的立场党同伐异,有失公允。
又杨慎所引《白鹿洞赋》亦不能说明问题。典故的应用大抵是出于一种传统习惯,其本身有一个积淀过程。典故用得久了,其文本背景也就逐渐淡化,可以与其在文本中的本意有距离。这可以从我们今天的情形反过来逆推:譬如一个大学搞校庆,纪念文章里大可以用“子衿”、“菁莪”的典故,这典故自然是本于《序》和《毛传》的解说,是比喻学校教育的,但文章的作者,作为一个现代人,他对“子衿”一诗的理解恐怕自然是当作爱情诗的。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将“子衿”当典故来用,全不妨碍对其诗爱情主题的理解。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做,朱熹又为什么不能呢?杨慎的这条理由实在也没有道理。
尊《序》一派的人批评朱熹不该废《序》,废《序》派中则有人批评朱熹废《序》太不彻底。姚际恒《诗经通论·自序》①批评朱熹:“作为《辨说》,力诋《序》之妄,由是自为《集传》,得以肆然行其说;而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而且违其所是,从其所非焉。武断自用,尤足惑世。”《诗经通论》卷前《诗经论旨》又云:“其从《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不从而阴合之者,又有意实不然之而终不出其范围者,十之二三,故愚谓:遵《序》者莫若《集传》。”
夏传才亦云:
朱熹具有一定进步性的治学方法,和他的根本立场观点产生了矛盾。他一方面力图探求三百篇的本义,一方面又要宣扬封建礼教。他突破传统《传》、《序》、《笺》、《疏》的束缚,考证求实,就本文理解诗义时,能够获得一些正确和接近正确的认识,但他不能越过封建礼教的藩篱;一碰到这个藩篱,他就要缩回来。封建卫道的理学家朱熹,不可能进行彻底的自由研究,为了宣扬圣道王化、三纲五常,他又不能不回到穿凿傅会曲解诗义的老路上去,用新的穿凿傅会来代替旧的穿凿傅会。
正因为如此,朱熹一方面废弃《诗序》,并对《诗序》进行了总的批判;一方面又在对诗篇的具体解释中,自觉不自觉地继承《诗序》的一些说法:在《诗集传》中有些题解公开袭用,说《诗序》“斯言得之”或“庶几近之”;有些则改头换面,偷偷地贩运进来。清代人早看到朱熹的这个毛病,姚际恒就批评他“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朱熹反《诗序》又是不彻底的。①
这种意见有无道理呢?窃以为当析而言之。《诗集传》有些地方沿袭了《诗序》,这是事实。但“遵《序》者莫若《集传》”恐非持平之论。
关于《诗集传》题解与《诗序》的关系,莫砺锋《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②一文,有很具体的统计分析。他将《诗集传》题解与《诗序》的关系分为五种类型:1、《诗集传》采用《小序》说;2、《诗集传》不提《小序》而全袭其说;3、《诗集传》与《小序》大同小异;4、《诗集传》与《小序》说不同;5、《诗集传》认为应存疑。并做了张详细的统计表,其表如下(按:不包括六篇笙诗):
根据这张统计表,他说:
一、二两类共计82首,也即朱熹同意《小序》说的诗共占《诗经》总数的27%。三、四两类共几215首,也即朱熹对《小序》说有异议的诗共占《诗经》总数对70%。这说明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但是改正《小序》说的比较多。这几种情况在全书各部分所占的比重也不一致。比如在《郑风》21篇中,《诗集传》与《小序》说不同的就有14篇,占三分之二。这主要是因为《郑风》中民间情歌特别多,所以受到《小序》的歪曲也特别严重。这说明《诗集传》对《小序》的修正,主要是针对那些受到《小序》严重歪曲的诗篇而发的。相形之下,《诗集传》对诗义的解释要比《小序》正确。……总之,《诗集传》采取《小序》说的大多是确有根据的说法,朱熹对《小序》的取舍态度是比较慎重、正确的,后代的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小序》,对朱熹的“废序”颇有微词,实在是出于偏见。
笔者以为“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但是改正《小序》说的比较多”这一结论是比较中肯的。这里对其略作补充说明:
莫先生将“《诗集传》与《小序》说不同”的情况分为以下两种类型:1、“释义截然不同”;2、“释义无大分歧,但认为其为刺为美则截然相反”。实际上,第一种类型主要是淫诗,第二种类型即笔者所论朱熹批评《序》者滥用“陈古刺今”。莫先生将“《诗集传》与《小序》大同小异”的情况分为以下4个类型:1、“释义稍有不同”;2、“释义基本相同,但《小序》拘于‘美刺’之说,在进一步的阐发时就犯了穿凿傅会的错误”;3、“释义基本相同,但对诗的作者说法不同”;4、“释义基本相同,但对作诗的时代说法不同”。其实,莫先生的第2、3、4三种类型,即笔者所论朱熹辩驳《序》者“妄断美刺”、“误认作者”、“妄断世次”。此三端,皆《诗序辨说》孜孜以驳,于朱熹自身而言,应该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至于第一种类型,莫先生举的例是《周南·桃夭》篇,该篇《序》云:“后妃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昏姻以时,国无鳏民也。”《诗集传》云:“文王之化,自家而国,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故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而叹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莫先生认为二者实无本质差别;但也承认存在两处差异:(1)《小序》是归美后妃,《诗集传》是归美文王;(2)《小序》着眼于男子不作鳏民,《诗集传》着眼于女子能宜室家。笔者以为这两处差异对朱熹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朱子语类》有云:“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桃夭》之诗谓‘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为文王刑家及国,其化固如此,岂专后妃所能致耶?”(80/2075,周谟记)。《诗集传》于《周南》总结亦云:“今言诗者,或乃专美后妃,而不本文王,其亦误矣。”可见在朱熹看来《序》者理解为专美后妃,是“大无义理”的。另外,《序》所云“男子不作鳏民”恐非诗辞本文所有之意,《诗集传》“女子能宜室家”则切合文本自身。这一细微差异实际反映了朱熹说《诗》最重文本的态度。朱熹《诗集传》往往于细微处见精神,莫先生认为是“小异”的地方,从朱熹自身的立场来看,实未必只是“小异”。
朱熹废《序》的初衷是《序》多不合于《诗》本意,且有害于后人对《诗》的理解。朱熹本人解《诗》的原则是“涵泳本文”、“求诗本意”;辩驳《诗序》的手段无外乎文本、情理与文献根据这三端。《诗集传》之题解与《小序》有异有同,大抵是实事求是,根据其本人“涵泳”所得,同于其所当同,异于其所不得不异。
对于《诗集传》沿袭《诗序》之处亦当析而言之:有些是沿袭了其错误,有些则不是。如《召南·野有死麕》篇,《序》云:“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诗序辨说》云:“此序得之”,是朱熹于此篇之意见同于《序》说。但此诗之第三章云:“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哪里是凛然拒绝的口气!?王柏《诗疑》尚且能以之为“淫诗”,分明看出其间真意。朱熹此处沿袭《序》说,自然是“从其所非”了。这种情形,《诗集传》中确有不少,我们也不必为贤者讳。但多数时候,朱熹从《序》则是有正当理由的,大抵是因为《序》有经文、史传之证。《诗序辨说》颇有指出《序》有经文、史传之证,故不误的例证,请看附录10。
附录10:《诗序辨说》明言《序》有经文、史传之证,故不误例:
01 《鄘风·干旄》,《诗序辨说》:“《定之方中》一篇,经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误。”
02 《鄘风·载驰》,《诗序辨说》:“此亦经明白,而序不误者。又有《春秋传》可证。”
03 《卫风·硕人》,《诗序辨说》:“此序据《春秋传》,得之。”
04 《齐风·南山》,《诗序辨说》:“此序据《春秋》经传为文,说见本篇。”
05 《唐风·扬之水》,《诗序辨说》:“诗文明白,序说不误。”
06 《秦风·黄鸟》,《诗序辨说》:“此序最为有据。”
07 《陈风·株林》,《诗序辨说》:“《陈风》独此篇为有据。”
08 《豳风·鸱枭》,《诗序辨说》:“此序以《金滕》为文,最为有据。”
…………
以上诸例,或者经文自身明白,或者《春秋》经传对其创作背景有明确说明,《序》者以此二端为根据,自然不至于有很大偏差。这种情况下,朱熹对诗义的理解自然与《序》者一样。这并不是个沿袭的问题,而是不得不同于其所当同。如果不这样,才是应了姚际恒的批评——“违其所是”呢!
朱熹批评《序》者说诗惯于傅会历史,大抵是针对历史文献对诗之创作背景没有明确记载的情况而言。前文所论《序》者“妄断世次”与依谥编派刺诗是其具体表现。对于《序》者所言有文献根据,但诗文自身未必与之相合的情况,朱熹又常常采取“或然”(有时用“姑从”)的态度。如《邶风·击鼓》篇,《序》云:“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诗集传》次章云:“旧说以为此春秋隐公四年……之事,恐或然也。”《诗序辨说》云:“《春秋》隐公四年,宋、卫、陈、蔡伐郑,正州吁自立之时也。序盖据诗文平陈与宋而引此为说,恐或然也。”按:《序》所云州吁命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春秋》有明文记载;但《击鼓》诗所云,可能指这件事,也可能不指这件事。一定要肯定其是或不是指这件事,都嫌失之武断。朱熹云“恐或然也”正是慎重的态度。此例甚多,兹不枚举。
即使同一篇《诗序》之中,朱熹亦大抵能从其所是,弃其所非。如《诗序辨说·秦风·小戎》云:“此诗时世未必然;而义则得之。”朱熹认为《序》所认定世次靠不住,故不取;但认为所说诗义可取。又如《周南·葛覃》,《序》云:“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恭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之妇道也。”《诗集传》云:“《小序》以为后妃之本,庶几近之。”《诗序辨说》云:“此诗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谓在父母家者一句为未安。盖若未嫁之时,即诗中不应遽已归宁父母为言……”对小序可取之处给以肯定,对其不妥之处亦指出,正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再如《大雅·抑》篇,《序》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之序,有得有失……以诗考之,则其曰刺厉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是这种态度。
可以说,在根本说《诗》方法上,朱熹与《序》者有“求诗意于辞之中”与“求诗意于辞之外”的分歧,而且朱熹认为《序》有害于读者对《诗》义的理解。所以朱熹对《诗序》是从整体上给以否定的。但在《诗集传》具体解诗时,对待《诗序》的态度,大抵是同于其所当同、异于其所不得不异,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姚际恒“遵《序》者莫若《集传》”之论失于偏激;杨慎的批评更嫌武断,近于臆说。
第三节 学术背景的考察
[《周易本义》欧阳修《诗本义》等“本义”溯源]
一、《周易本义》
涵泳文本、求其本义是朱熹治《诗经》学的根本方法。这一方法又不限于《诗经》一门,实际上,朱熹治一切古籍大抵都能坚持这一方法,而以治《易》尤为典型。朱熹著有《周易本义》一书,从书名自身即可看出其旨趣。朱熹治《易》学,有两样基本主张:一是《易》本为卜筮而作。二是《易》之经传各自为说,不必据传解经。所谓《易》本义即指《易》本为卜筮之书,不是为义理而作。求易本义有两层意义:一是不作义理上的傅会;二是不依传解经。
《汉书·艺文志》云:
《易》曰:“宓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所谓《易》之经即指伏羲与文王所作的部分——卦象及卦爻辞,《易》之传指孔子所作十篇(习惯上称为“十翼”)。关于《周易》经传的形成,自《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说后,易学界一直把《周易》经传看成是周孔之道的体现,认为伏羲画卦,周文王作卦爻辞,孔子作传,三圣之业一脉相承,并无差别。因而对《周易》一书的理解,都依传文义解释经文。由于依传解经,将《周易》一书进一步哲理化,《周易》作为占筮的典籍,其本来的面貌则被湮没了。直到北宋欧阳修提出《系辞》非孔子所作,这种传统的观念才发生动摇。
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下)有云:
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
欧阳修对《易》传的判断与批评和朱熹对《诗序》的批评很相似:朱熹认为《序》非圣人作,依《序》说诗有害于后人对《诗经》的理解;欧阳修认为《易》传(大部分)非圣人作,后人依之解经,“至使害经而惑世”。
在《系辞》作者的这一问题上,朱熹并不赞成欧阳修的说法,仍认为《系辞》为孔子所作,但他对《周易》的理解,却受到欧阳修易说的影响。
关于《周易》经传的形成,朱熹取四圣说,即: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重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传;并认为四圣皆以《周易》为卜筮之书。《朱子语类》有云:
《易》本为卜筮之书……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想当初伏羲化卦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66/1622,甘节记)
朱熹易“三圣说”为“四圣说”的理由是“谓《爻辞》为周公者,盖其中有说文王,不应是文王自说”。(67/1846,叶贺孙记)但有些时候,他又往往将文王说与周公说视作一个整体。朱熹屡屡强调伏羲《易》、文王周公《易》与孔子《易》各自为阵,不宜强为牵合。且看《朱子语类》里的言论:
01 学《易》者须将《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做一意看,不得。(66/1622,辅广记)
02 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66/1630,沈僩记)
03 须是将伏羲画底卦做一样看,文王卦做一样看;文王周公说底《彖》、《象》做一样看,孔子说底做一样看,王辅嗣伊川说底各做一样看。(67/1645,渊记)
朱熹强调伏羲《易》、文王周公《易》与孔子《易》牵合不得,乃是因为其间有不吻合之处,《朱子语类》有云:
01 《乾》之“元亨利贞”,本是筮得此卦,则大亨而利于守正,而《彖辞》、《文言》皆以为是四德。某常疑如此等类,皆是别立说以发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马之贞”,则发得不甚相似矣。(67/1645,杨道夫记)
02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书。(67/1645,廖德明记)
文王卦与伏羲卦已自不同,孔子《十翼》与文王周公卦爻辞又有理解上的分歧,离则双美,合者两伤,故不如各自做一样看。汉至唐的易学家将三者当作一个整体,弥缝于其间,自然难免于牵强。《易》之经传既各自为体,自然不必依传解经。
朱熹屡次强调《易》本卜筮之书,至孔子作《十翼》方始
从义理上着眼,《朱子语类》有云:“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话说!文王重卦作《系辞》,周公作《爻辞》,也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66/1622,辅广记)。朱熹还明确指出孔子说《易》不得易本义,请看《朱子语类》中这一段文字:
据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今人说得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说虽粗,然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某一人说,则晓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用,元未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读伏羲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画八卦,那里有许多文字言语,只是说八个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其大要不出于阴阳刚柔、吉凶消长之理。然亦尝说破,只是使人之卜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今人未曾明得《乾》、《坤》之象,便先说《乾》、《坤》之理,所以说得都无情理。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古人占处说,如卜得《乾卦》,则大亨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要说出来。孔子之心,又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只认各人自说一副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说《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样。某所以不敢从,而原《易》之所以为作而为之说,为此也。(66/1630,沈僩记)
朱熹认为当初伏羲画卦,只是为了卜筮,占卦象之阴阳,卜人事之吉凶,而无关于义理。圣贤如孔子,以义理说《易》,尚且被朱熹说作“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至如后人纷纷以义理说《易》,不顾《易》本卜筮之书的事实,朱熹更是给以严厉批评。其《答吕伯恭》书(见《朱熹集》卷33,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458—1459页)云:“窃疑卦爻之词,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以训诫。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诫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容该贯曲畅旁通之妙。”《朱子语类》亦云:“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做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66/1622,辅广记)。
《朱子语类》又云:
《易》以卜筮用,道理便在里面,但只未说到这处。如《楚辞》以神为君,祀之者为臣,以见其敬奉不可忘之义。固是说君臣,但假托事神而说。今也须与他说事神,然后及他事君之意。今解直去解作事君,也未为不是;但须先为他结了事神一重,方及那处,《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说他本意,便将理来衮说了。(66/1635,林学履记)
据此,是朱熹并不反对根据《易》来说道理,但朱熹强调首先要将《易》作卜筮之书看,就卜筮来探讨其本意。在得其本意之后,再借以说明道理是可以的;但如果没有求本义在先,一上来就大谈义理,则不可取。《楚辞·九歌》是祀神之曲,其本意是讲事神的;必须先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意义上解释诗意,然后才可以作事君的发挥。“今也须与他说事神,然后及他事君之意”,这里的先后至关重要,这实际是承认文本的独立地位具有优先原则。作为理学大师的朱熹,义理是其治学的根本。但在注解经典古籍时,他始终将文本放在第一位,尊重文本的独立性地位,然后才是义理上的发挥。朱熹诗经学实极重视“养心劝惩”、“变化气质”,但在说解《诗三百》文意时,他能始终贯彻“求诗意于辞之中”的原则。汉学诗经学正是缺少了这一个环节,拿义理来直接套文本,忽视了文本的独立性地位。朱熹批评后人依《序》说诗,也正是因为后人将第二位的阐释置于了第一位的《诗三百》文本之上。对《易》来说,经的部分实际可视做文本自身,传的部分则是后人阐释。尽管其阐释者是孔子,是儒家的大圣人,但相对于经作为文本自身的第一性来说,它也只能是第二位的。求易本义,当就经解经,而不当依传解经。所以《朱子语类》说:“《易》本为卜筮之书……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系辞》,是犹不看《刑统》,而看《刑统》之《序例》也,安能晓!今人须以卜筮之书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66/1622,甘节记)。
《朱子语类》颇载朱熹教诲弟子读《易》之法:
01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之《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学者且依故《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矣。(66/1648,李方子记)
02 读《易》之法,先读正经。不晓,则将《彖》、《象》、《系辞》来解。(77/1661,甘节记)
03 看《易》,且将《爻辞》看。理会得后,却看《象辞》。(77/1661,胡泳记)
“先读正经”,“先读本爻”,正如先读《诗经》本文,正是尊重文本独立性,求其意于辞之中的方法。
朱伯崑对朱熹在易学上的贡献有一段很好的概括:
朱熹关于《周易》经传的论述,在易学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从汉朝以来,无论是义理学派还是象数学派,其解易都是经传不分,以传解经,并且将经文部分逐渐哲理化。到宋代易学家将《周易》视为讲哲理的教科书,特别是程氏《易传》,由于突出以义理解易,使《周易》丧失了其本来面貌。而朱熹则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研究《周易》经传,以经为占筮的经典,以传为后来讲义理或哲理的著述,认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脱离筮法解释《周易》,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言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还以这种观点研究了易学的历史。认为从汉易京房到程氏易学,各成一家之言,其解易并非就是《周易》经传之本义,但如其说出一番道理,亦应肯定,不应抛弃。①
我们可以说朱熹《周易本义》不依传解经,同于其《诗集传》不依《序》说诗。反对易学史上的过多义理傅会,亦正如反对毛、郑一派一味以美刺说《诗》。这正可以说明朱熹治经典古籍之学的一贯态度。
二、欧阳修《诗本义》等
求本义实乃有宋学术一大思潮,不独朱熹一人而已。如欧阳修《易童子问》以系辞非孔子作,苏轼、苏辙兄弟对《尚书》等古籍的新注,郑樵《诗辨妄》等书的写作,尽管对旧说之扬弃在程度上或有大小之分,但都能独立思考,求经书本来之面目。宋人对《诗经》的研究,尤能见其求本义之学术风气。
在朱熹之前,宋人之中,以欧阳修、苏辙、郑樵三人在求诗本义上贡献最大。这三个人,郑樵大抵是坚决废《序》的,苏辙仅取《序》之首句,欧阳修虽未有废《序》之论,但在求诗本义的理论建设上功不可没。
先说郑樵。郑樵的很多见解都为朱熹所接受,朱熹在诗经学著作中屡次提及郑樵:
01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80/2076,叶贺孙记)
02 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谥,却傅会作《小序》美刺。(80/2079,吴振记)
03 旧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某近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意自见。(80/2068,余大雅记)
04 先生举郑渔仲之说言:出于朝廷者为《雅》,出于民俗者为《风》。文武之时,周、召之民作者谓之周、召之《风》。东迁之后,王畿之民作者谓之《王风》。(80/2067,钱木之记)
05 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诗集传·郑风·将仲子》)
06 莆田郑氏谓此实淫奔之诗,无关于庄公、叔段之事。(《诗序辨说·郑风·将仲子》)
01、03条是朱熹自言废《序》受郑樵影响;05、06条说明郑樵对“淫诗”早有认识;04条说明朱熹“《国风》里巷歌谣说”亦本于郑樵;02条说明郑樵早已指出《小序》是依谥傅会美刺。凡此四端,皆朱熹诗经学之重要组成,而郑樵已发先声,朱熹亦屡屡称道之。我们甚至可以说,朱熹诗经学之义例基本来自郑樵。在讨论宋代诗经学时,郑樵实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只是郑樵对诗经学的研究不及朱熹系统和专门,其书《诗辨妄》①又亡佚,因此郑樵在诗经学上的影响远不如朱熹,他的一些论断也不得不赖朱熹的征引而得以流传,且有待于朱熹来发扬光大。
苏辙亦著有《诗经集传》,于《诗序》仅取首句。朱熹曾云:“子由《诗解》好处多。”(80/2090,钱木之记),《诗集传》征引苏辙之说亦极多,据曹虹统计共43处②,为征引宋人著作之首。《诗序辨说》亦于《大雅·文王》、《大雅·荡》二篇称引苏辙之说(《诗序辨说·大雅·文王》:“称王改元之说,欧阳公、苏氏、游氏辨之已详。”《诗序辨说·大雅·荡》:“苏氏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以为援证。朱熹称道苏辙,一是因为苏辙文学修养高,解诗有高过前人之处③;二是因为苏辙亦有考史之能④。苏辙于《诗序》仅取首句,也是因为看不惯《序》者太多的傅会穿凿。但朱熹还是嫌他废《序》不够彻底,《朱子语类》云“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80/2074,邵浩记),《诗序辨说》亦不乏专门辩驳苏辙取《序》首句之处,共有4例(附录11)。
附录11:《诗序辨说》专门辩驳苏辙取《序》首句之失例:
01 《周南·汉广》,《诗序辨说》:“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苏氏乃例取其首句,而去其下文,则于此类两失之矣。”
02 《周颂·昊天有成命》,《诗序辨说》:“苏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尝见其不可信之实也。愚于《汉广》之篇已尝论之。”
03 《周颂·执竞》,《诗序辨说》:“苏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时,因从小序之言。此亦以辞害意之失。”
04 《鲁颂·〓宫》,《诗序辨说》:“此诗言庄公之子,又言新庙奕奕,则为僖公修庙之诗明矣。但诗所谓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复周公之土宇耳,非谓其已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误如此,而苏氏信之,何哉?”
《诗序辨说》尚于《周南·桃夭》《周南·兔罝》、《鄘风·桑中》、《小雅·南山有台》4篇直接指出《序》之首句有误。《诗序辨说》卷首有云:“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义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
苏辙大抵相信《序》之首句传自圣人,只是“首句”之后的“续句”之引申发挥,多半是后世陋儒所为,不值得信从。朱熹则认为整个《诗序》,包括《序》的“续句”和“首句”在内,都不合诗本义,都应摒弃。
《朱子语类》云:“欧公《诗本义》亦好。”(80/2090,钱木之记)。朱熹推崇欧阳修,也有文学修养①与考史之能②两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欧阳修对求诗本义的理论建设有巨大贡献。《朱子语类》有云:
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本末》篇。又有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得也无妨。”其论甚好。(80/2089,沈僩)
欧阳修“《诗》之本末”论,为朱熹所激赏。欧阳修谓学者当知《诗》学有此四端: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
《诗本义》(卷十四)云:
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颂;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说;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
这四端,又有本末之分:
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
诗人之意是本,太师之职是末。圣人之志是本,经师之业是末。知其本末,则知学《诗》之主次。其又云:“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太师考其义类,于《诗》本身来说只是后人的一种理解与整理而已。诗人作诗时,又没有和太师商量过,太师的理解未必就是作者之意。今人学《诗》,探求诗人之意才是第一要紧的事;至于太师之类人的解释和整理,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孔子治《诗》,无非是“著其善恶以为劝戒”而已。学者读《诗》,无非是为了增进人格、变化气质,历代经师的繁复解说知不知道也并不要紧。
欧阳修虽未有废《序》的言论,但《诗》之本末的划分于求诗本义有重要意义。既然后来太师的理解未必合于诗人之意,且相对来说是第二位的,其本身的地位就变得次要;既然后世经师解《诗》不过是人自为说,未必合诗人之意,亦未必得圣人之志,那对读者来说也是可有可无的了。欧阳修“《诗》之本末”论一下子将诗本义与“著其善恶以为劝戒”的人格教育功能凸显了出来。“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这二者正是朱
熹诗经学之根本精神!“求诗人之意”,是求其本来面目,合乎朱熹格物之学术门径;“达圣人之志”,是救天下世道人心,是朱熹治学之根本目的。明乎此,则无怪乎朱熹对欧阳修“《诗》之本末”论要击节叹赏了。
三、“本义”溯源
《汉书·艺文志》有云: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这大约是最早提及《诗》“本义”的。但是这里的“本义”有其特定的涵义,与宋人求诗本义的“本义”并不是一回事。这涉及到汉人著述的体例问题,大约有此三端:1、“故训”与“传”之异同;2、“内传”与“外传”之异同;3、“正义”与“旁义”之异同。
《汉志》“咸非其本义”究竟指几家,学界意见不一。颜师古注云:“与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者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之。”王先谦《汉书补注》云:“此谓齐韩二传推演之词,皆非本义,不得其真耳。非并鲁诗言之。鲁最为近者,言齐韩训故亦各有取,惟鲁最优。颜谓三家皆不得谬矣。既不得其真,何言最近乎!”按颜师古的理解,是说鲁、齐、韩三家都不得本义。王先谦则认为仅指齐、韩二家不得本义。辨析其间是非,或当从汉人著述体例入手。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杂考各说·毛诗故训传名义考》云:
汉儒说经,莫不先通诂训。《汉书·扬雄传》言“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故通而已”。《儒林传》言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已”。而《后汉书·桓谭传》亦言谭“遍通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则知诂训与章句有辨。章句者,离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语多傅会,繁而不杀,蔡邕所谓“前儒特为章句者,皆用其意传,非其本旨”,刘勰所谓“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也。诂训则博习古文,通其转注、假借,不烦章解句释,而奥义自辟,班固所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史》、《汉》、《儒林传》皆言鲁申公为《诗训诂》,而《汉书·楚元王传》及《鲁国先贤传》皆言申公始为《诗传》,则知《汉志》所载《鲁故》、《鲁说》者,即《鲁传》也。何休《公羊传注》亦言“传谓诂训”,似故训与传初无甚异。而《汉志》既载《齐后氏故》、《孙氏故》、《韩故》,又载《齐后氏传》、《孙氏传》、《韩内外传》,则训诂与传又自不同。盖散言则故训、传俱可通称,对言则故训与传异,连言故训与分言故、训者又异……盖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引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①
马瑞辰指出“散言则故训、传俱可通称,对言则故训与传异”。汉人固然有“故训”与“传”混称的习惯,但是《汉志》所载却有“辨章学术”的意义在,称“故训”与称“传”,有其体例上的区别。称“故”(诂训)者大抵仅“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称“传”则并引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也就是说“故”的通例是注重词义的训释,仅就经文自身解说大义,一般不做过多的题外发挥;而“传”(章句)的通例则是要对经文作引申发挥,要称引经文以外的东西来阐发经义。“故”的特点是简括清通,“传”则容易傅会穿凿。马瑞辰引前后《汉书》所记扬雄、蔡邕之言行,亦足以说明两汉之交及东汉儒者对二者性质的认识。蔡邕明确指出“章句”多非经本旨。《汉志》于“咸非其本义”句前云“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辨析“咸非其本义”,必须考虑到“训诂”和“传”在体例上的不同。从汉人“故”与“传”体例差异入手,《汉志》所云“咸非其本义”似指齐、韩二家而言。
陈澧《东塾读书记》对先秦、秦汉人著述之内传、外传之分有明确辨析①。陈澧云:“韩非有《解老》篇。复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即《外传》之体。其《解老》即内传。”《韩非子》有《喻老》、《解老》二篇,《喻老》的体例是引古事以明《老子》之理,《解老》篇则是直接阐发《老子》思想。《喻老》是外传体,《解老》是内传体。《外传》之体,可引古事,亦可引古人之言(包括古人之诗),陈澧云“今本《韩诗外传》,有元至正十五年钱惟善序云:‘断章取义,有合于孔门商赐言《诗》之旨。’澧案:孟子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亦外传之体。”又云:“西汉经学,惟《诗》有毛氏、韩氏两家之书,传至今日。读者得知古人内传、外传之体,乃天之未丧斯文也。《直斋书录解题》云‘《韩诗外传》,多记杂说,不专解《诗》,果当时本书否?’(卷二)杭堇浦云‘董生《繁露》、韩婴《外传》,偭背经旨,铺列杂说,是谓畔经。’(《古文百篇序》)此则不知内外传之体矣。”陈澧认为《毛传》与《韩诗外传》正好是内传与外传的典型代表。虽然陈澧批评《直斋书录解题》怀疑《韩诗外传》非当时之书、批评杭世骏说《韩诗外传》畔经。但二家对《韩诗外传》特点的认识却不可移易。“多记杂说,不专解《诗》”、“偭背经旨,铺列杂说”,正是《韩诗外传》的特色。陈澧于此亦有深刻认识,他说:“采杂说,非本义,盖专指《外传》而言。”认为《汉志》所云“咸非其本义”专指《外传》,而“非本义”的标志是“采杂说”。
皮锡瑞论《诗》又有“正义”、“旁义”之分,其《经学通论·诗经》①“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义亦未尽可信”条云:“三家所传近古,而孰为正义、孰为旁义,已莫能定。以为诗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又云三家诗“存于世者,惟《韩诗外传》,而外传亦引诗之体,而非作诗之义。”“正义”指作诗之义,“旁义”指后人引申傅会之说。“正义”、“旁义”与“故”、“传”之体有很大关系,与“内传”、“外传”之体亦有很大关系。引申傅会愈多,则离诗人之意愈远。相对于“故”来说,“传”的引申傅会为多;“故”于“正义”为近,“传”多“旁义”。相对于“内传”来说,“外传”的引申傅会为多,“内传”近于“正义”,“外传”多属“旁义”。
汉人著述,于“故”、“传”、“内传”、“外传”之体有自觉认识,《汉志》著录更是于诸体之分有清醒认识。观其著录《诗经》学著述即可明此理。《汉志》载: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
《鲁故》二十五卷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何者为“故”,何者为“传”,何者为“内传”,何者为“外传”,泾渭分明。《汉志》著录鲁诗,有《鲁故》、《鲁说》,而无《鲁传》,《汉书·儒林传》亦云:“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作文按:《史记·儒林传》云:“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上一“疑”字,或为衍文。)我们知道,《韩诗外传》是采杂说的,齐诗喜言“天人之际”,傅会阴阳五行,惟鲁诗较为质朴简括,而少引申傅会之说。故《汉志》有鲁最为近之之论。
三家诗说,今存者惟有《韩诗外传》。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来看看《韩诗外传》的特色。兹引其卷首第一段于下:
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以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怒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桥褐趋时,当务为急。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曰:“夙夜在公,实命不同。”
这一段文字,在结构上包括一个故事和《诗经》的两句(姑且称为“断章”)。但我们很难说这是引事以明《诗》。在这个结构中,《诗》之断章已经脱离原诗,不再是原诗的一个有机组成;它已是新的文本结构的一个部分,为新的文本服务。《韩诗外传》的作者在这里用这两句,是“断章取义”的态度,仅取这断章含有的某一种意思,而非其原诗的意思。在这里,这一断章与这一故事,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断章的义实际受这个要说的道理制约。“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出自《召南·小星》。因文献不存,我们无法知道韩诗对这一篇篇义的确切理解。但无论如何,绝不会理解成是写曾子的。这里的故事,是引事以明义;这里的诗,是引《诗》以明义。《韩诗外传》作者本人所要表达的义才是第一位的,至于诗之原义(作诗之义)已经在新的结构中被消解。《直斋书录解题》云《韩诗外传》“不专解《诗》”,诚为有见。
徐复观对《韩诗外传》的特点与性质有很好的概括:
他(韩婴)在《外传》中,共引用《荀子》凡五十四次,其深受《荀子》的影响,可无疑问。即《外传》表达的形式,除继承《春秋》以事明义的传统外,更将所述之事与《诗》结合起来,而成为事与《诗》的结合,实即史与诗互相证成的特殊形式,亦由《荀子》发展而来。……《韩诗外传》,未引《诗》作结者仅二十八处,而此二十八处,可推定为文字的残缺。其引诗作结时,也多援用《荀子》所用的格式。……《韩诗外传》,乃韩婴以前言往行的故事,发明《诗》的微言大义之书。此时,《诗》与故事的结合,皆是象征层次上的结合。……韩氏乃直承孔门“诗教”,并不否定其本义,但不仅在本义上说《诗》,使《诗》发挥更大的教育意义。①
徐复观指出《韩诗外传》受《荀子》影响,乃是用引古事与引《诗》相结合的方法来说明道理。于《诗》而言,它“不仅在本义上说《诗》”,而且要“发明《诗》的微言大义”。这样看来,《韩诗外传》在性质上同于一般子书,解经只是门面话,阐明自己的义理才是其目的。这样一来,自难逃《汉志》非诗本义之讥。
《汉志》言齐韩二家诗传“咸非其本义”的特定语境是汉人的著述体例,主要是从“故”与“传”、“内传”与“外传”、“正义”与“旁义”的差异性着眼。《汉志》所言的“本义”是与“引申义”相对而言的。齐、韩二家或主于阴阳五行,或受《荀子》等子书影响,多是在“引申义”的层面上说《诗》,故“咸非其本义”。相对来说,鲁诗(《鲁故》)较少在“引申义”的层面上说《诗》,故“最为近之”。从著述体例着眼,根据是否在“引申义”层面上说《诗》,在《汉志》的立场,毛诗恐怕当属得其本义,或者较鲁诗更近本义的。
林叶连云:
班固谓西汉诗经学有齐、鲁、韩、毛四家。但因齐、鲁、韩诗于两汉皆立于学官,宛若诗学正宗,故班氏奉命撰《汉书》,便专就齐、鲁、韩三家,较其优劣,而不评毛诗。只在文末附带提及毛诗。班氏所言“自谓子夏所传”,“自谓”也者,其涵义为“非官方说法”,而非微辞。盖班氏所撰者,官书也,立于官方立场以发言,乃理所当然。总之,《汉志》非但未尝丝毫褒贬、评价毛诗,反而谓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成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此方为贬辞。①
林叶连所言,实不无道理。班固之世,古文经学地位上升,况且《汉志》本于刘歆《七略》,其对古文学派的毛诗给以认同,亦在情理之中。毛诗的著述体例是“但明训诂”,每篇有一极短小的序隐括诗义,很少作“引申义”层面上的发挥。用“故”和“传”的著述体例来区分,毛诗的体例属“故”;用“内传”和“外传”来区分,其性质又属“内传”;用“正义”和“旁义”来区分,其所言属“正义”。
需要特地指出的是:宋人所说的“本义”并不是汉人(《汉志》)说的“本义”,此“本义”非彼“本义”也。《汉志》说的“本义”是从著述体例的角度着眼,朱熹等人说的“本义”则是从辞与意的关系这一角度着眼。《汉志》之所以认为齐、韩二家诗“非其本义”,乃是因为它们属“传”体,而且是偏于“外传”体,多言“旁义”;《汉志》言鲁诗“最为近之”,是因为鲁诗(《鲁故》)属“故”体,多言“正义”。毛诗著述体例为“故”体和“内传”体,所言亦为“正义”。从《汉志》的立场,可以类推出毛诗最近本义之一结论。但是宋人求诗本义的对立面却恰恰正是毛诗(当然也是因为其时三家诗仅存《韩诗外传》,而其内容又不专解《诗》)。在朱熹等人看来,毛诗是不得“本义”的。朱熹所说的“本义”基本等同于“辞意”。尽管汉人(《汉志》)和朱熹所理解的“本义”都指“作者之义”,但他们对“作者之义”的认识实有本质差别。以毛、郑为代表的汉学一派从来不认为自己的阐释是背离“作者之义”的,他们认为“作者之义”即是他们所理解的诗义。他们认为,《诗》“作者之义”必有政治讽喻义,并不就是文本字面上的意思(“辞意”)。但在朱熹的立场,毛、郑一派所理解的诗义多属穿凿傅会,而从“辞意”才能求得真正的“作者之意”。
《汉志》所言之“本义”与宋人所理解的“本义”,在语境和涵义上有很大不同,更不是宋人求诗本义的源头。宋人所求之“本义”或来自禅宗。我们知道,南禅(以六祖惠能《坛经》为标志)的出现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南禅鼓吹“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摆脱历来佛经注疏的束缚,而倡独立思考、自证自悟之大旗。其怀疑精神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对宋明理学在学理建设上实有重大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南禅与宋人求经典本义之间的相似性:南禅所要求的是佛性,历来的佛经注疏都是后人对佛性的一种阐释,惠能主张摆脱后人阐释的束缚,而将思考直接指向佛性自身;朱熹所要求的是诗本义,《序》、《传》、《笺》、《疏》等都只是后人对诗义的一种阐释,朱熹力主废《序》,而于《诗》辞之中求其本义。南禅有“第一义”、“第二义”之分;欧阳修倡“《诗》有本末”论,为朱熹所激赏。南禅重自证自悟;朱熹教人读《诗》贵“涵泳”。这些相似性无不说明宋人求经典本义的思考方法实受南禅之影响。
自中唐南禅兴起以来,怀疑精神与独立思考对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壮大,至宋时已成时代之普遍风气。故宋儒对待经典文献之态度实与前人大异,其精英人物大抵能摆脱汉唐注疏之束缚,而求其本义于经文之中。仅就诗经学而言,朱熹之前,欧阳修、苏辙、郑樵等人已有此种精神。朱熹生逢其时,得风云之际会,总有宋一代诗经学之大成。
附注
①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5》,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1540页。朱彝尊《经义考·<诗>二·诗序·马端临条》(卷98)所引,与此同。
①此处“/”的数字前指《朱子语类》的卷数,后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的页数。后同。
①文见《古史辨》第3册,北平朴社1931年版;原题《诗经的厄运和幸运》,刊于《小说月报》14卷3—5号。
②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年初版。通行本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① 姚际恒《诗经通论》,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① 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7月版,177—178页。
② 莫砺锋《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见《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140—155页。
①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439—440页。
① 顾颉刚辑有《诗辨妄》,北平朴社1938年版。但顾颉刚所辑,亦有遗漏,如朱熹著作关于郑樵者,仅辑3条(按:即笔者所举01、02、04条)。
② 曹虹《朱熹诗集传新论》,收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朱子语类》云:“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诗》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头者。苏黄门《诗说》疏放,觉得好。”(80/2089,吴振记)
④ 《诗集传》于《魏风》卷首云:“苏氏曰:‘魏地入晋久矣,其诗疑皆为晋而作,故列于唐风之前,犹邶鄘之于卫也。’今按篇中公、公路、公族,皆晋官,疑实晋诗。”
① 《朱子语类》云:“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80/2089,吴振记)
② 《诗序辨说·周颂·昊天有成命》: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后祀成王之诗无疑。而毛、郑旧说,定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故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两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己意。其淤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古今诸儒,无有觉其谬者,独欧阳公著时世论以斥之,其辩明矣。
①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4—5页。
① 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107—108页。
① 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5—6页。
① 林叶连《中国历代诗经学》,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版,88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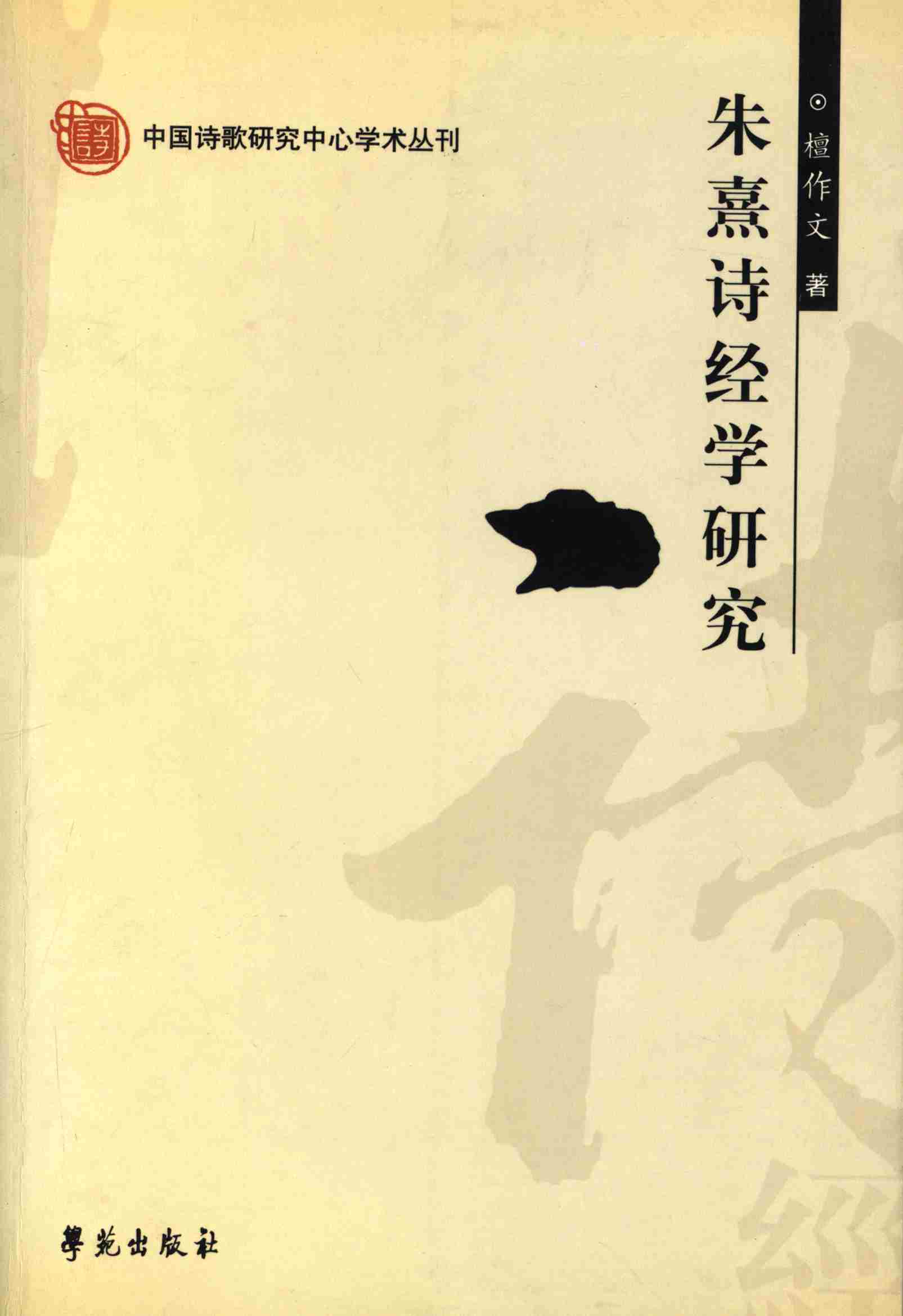
《朱熹诗经学研究》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本书为南宋朱熹诗词作品集,分为感事诗、哲理诗、山水诗、酬对诗、杂咏诗和词赋六大类。其中感事诗90首,主要反映朱熹对天下大事的观感及其在各个时期的基本思想倾向,按其主题又分为爱国恤民与述怀明志两组;哲理诗73首,主要反映朱熹的学术观点,按其主题又分为宇宦观、人生观、道德修养和为学三组;山水诗148首,主要反映朱熹的游踪和各地山川形胜,其中又分为武夷云谷、衡岳、庐山及其他胜地四大块;酬对诗87首,主要反映朱熹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内又分为奉和、题赠、迎送、寿挽四组;杂咏诗99首,为朱熹对各种事物的吟咏与思想寄寓,反映其日常生活情趣,内又分为咏物、咏景、咏居、咏事四组;词赋18首,按体裁分类。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