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纲要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两千年的诗经学史,是一笔陈年烂账。其中分歧尤大者,在汉宋之争。汉代传《诗》者,有齐、鲁、韩、毛四家。宋学诗经学的集大成著作为朱熹的《诗集传》。因今文三家诗已亡(今存者惟《韩诗外传》,不足以代表三家诗),故论汉、宋诗经学之异同,其重点必落实到比较《诗集传》与《毛传》、《郑笺》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汉、宋诗经学(《诗集传》与《毛传》、《郑笺》)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其荦荦大者,约为以下四端:一、在文本阐释方法上的不同;二、对文本性质认识的不同;三、对“赋比兴”之“兴”认识的不同;四、在《诗》之用上的不同。
一 汉、宋诗经学在文本阐释方法上的不同:“依《序》说诗”与“求诗本义”
汉、宋诗经学之争的关键在于是尊《序》还是废《序》。落实到文本阐释上,实际只是个是否依《序》说诗的问题。尊《序》、废《序》之争的关键,在于论者对《诗序》是否合于诗旨的判断。汉学一派以为《诗序》出于圣人(为其入室弟子所传),其对诗旨的阐释自可尊崇,故主张依《序》说诗;宋学一派以怀疑之精神,独立思考,觉《诗序》不合诗旨之处甚多,因疑其非圣人所作,故不主张依序《说》诗,而于文本自身求诗本义。
因为对《诗序》作者的争议,《诗序》与《毛传》的先后亦相应成为诗经学的一大公案。笔者个人的意见主张《诗序》至少不晚于毛传,而且《毛传》分明是依序说诗。《郑笺》和《孔疏》的依序说诗,自不待言:几乎每一句的解说,都要迁就《诗序》,绝不敢有什么动摇和怀疑。我们可以说,《诗序》是汉诗经学的灵魂,依《序》说诗是汉诗经学的根本特征。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诗经学却不如此。朱熹在《诗序辨说》卷首就指出:一、《序》出于汉人之手,非圣人作;二、《序》有不合诗人之本义处。从根本上否定了《诗序》的权威性。朱熹对后人不明《序》乃汉人之作,误以为是圣人遗说,因此依《序》说诗,穿凿迁就的做法,深为不满。朱熹批评汉学诗经学依《序》说诗、迷失本义的同时,提出自己的解诗主张:涵泳本文,求诗本义。从涵泳文本自身求诗本义,进而发现《诗序》不尽合于诗旨,实是宋儒废《序》的根本。
以《诗序》为核心的汉诗经学在说诗上有两个错误倾向:一是断章取义,一是傅会历史。“断章取义”,是将《诗经》作品文本的局部从整体上割裂开来,不顾文本的整体性,随意生说。朱熹对汉学诗经学不顾文理血脉、割裂全篇,仅据一句生说的做法,给予了严厉批评。“傅会历史”,主要是因为汉儒过于迷信“风雅正变”之说,依据世次来定诗之美刺。凡是一篇诗,在汉儒看来一定是要对时政有所美刺的。凡是时代在前(周初文武成康时)的,一律是“美”;时代在后的,一般就认定是“刺”。若是世次在后,而文意为美的,便说是“陈古刺今”。朱熹在《诗集传》和《诗序辨说》中,从妄断世次、美刺不当、滥用“陈古刺今”等三方面,对汉学诗经学傅会历史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具体辩驳。其辩驳的具体手段则是“考诸书史”和“揆以情理”。
不依《序》说诗,而于经文自身求诗本义,实际上是承认《诗经》文本自身的独立性,这为从文学角度认识《诗经》,并使其最终脱离经学的附庸地位,提供了可能,是宋学对汉学的一大突破。否定断章取义,主张说诗要照管前后血脉,则是认同《诗经》文本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局部(单独的一句)的含义受整体(完整的一篇或其中一章)制约,不能将局部从整体中割裂开来。宋学的这一认识也较汉学合理。
二 汉、宋诗经学对文本性质认识的不同:“政治美刺诗”与“一般抒情诗”
对《诗经》文本性质的认识有异,亦是汉、宋诗经学的分歧之处。汉诗经学认定《诗三百》是政治美刺诗,默认其叙述角度为第三人称。宋诗经学则认为《诗三百》中相当一部分是一般抒情诗,而且是以第一人称自抒其情。
《诗集传序》曰:“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变风中相当数量的作品是淫奔者之辞:如《鄘风·桑中》篇,《诗序辨说》云:“此淫奔者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认定国风的一大部分为里巷男女言情之作,并对其抒情主体加以确认,指出其中的一部分(“淫诗”)乃淫奔者所自作,是朱熹对诗经学的一大贡献。
《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异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这一节包含了以下两种认识:一、变风、变雅的作者是国史。二、其创作目的是“讽其上。”我们还可由此推论《诗序》默认整个《诗三百》的作者是国史(只有《鄘风·载驰》等极少篇目例外),从《小序》来看,其具体处理方式,则有时笼统题曰“国人伤之”或“君子刺之”。序者对整个《诗三百》的认识是非美即刺,亦即认定《诗三百》在性质上纯为美刺国事的政治诗,而非一般性的抒情诗。汉诗经学沿袭《诗序》的认识,亦将《诗三百》当作政治诗看,解诗之时,往往傅会政治。
汉诗经学将诗的作者默认为国史一类人,具体到“淫诗”的解说时,将其作者处理为事件的局外人,认为作者只是以第三人称的身份来叙述这事件,他的目的乃是要抨击这淫乱之事,以及造成这风气的政治背景。这样做,实际上是取消了这类诗歌在一般意义上的抒情性,而将其处理成纯粹的政治美刺诗。朱熹对这类诗歌的抒情主体,则做出了合理而有意义的确认。既然是自作,便是“淫奔者”以第一人称自歌其事、自抒其情,这实际上乃是认定其为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诗。尽管朱熹从理学的立场否定了这种男女私情,目之为“淫诗”,但毕竟为后人认识这类诗的抒情性指明了方向。
不独“淫诗”,此外的很多作品,朱熹也明确指出是抒情主人公所自作。如《邶风·雄雉》篇,《诗序》曰:“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诗序辨说》则云:“此亦妇人作,非国人之所为也。”《诗集传》则云:“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故言雄雉之飞,舒缓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从役于外,而自遗阻隔也。”依《诗序》的理解,此诗是刺时之作,不过是国史以旁观者身份叙述人民的苦难而已。朱熹则确认其为思妇之词,是抒情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自歌怨旷之苦,于是这首诗便具有了后世闺怨一类诗的品质,也便有了一唱三叹之致。
有了对抒情主体的确认为基础,朱熹在具体说诗时,往往对其曲折幽深之情有真切体会。如《卫风·氓》篇,《诗集传》曰:“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于其第五章又曰:“盖淫奔之人,不为兄弟所齿,亦不为兄弟所恤,理固有所必然者,亦何所归咎哉!但自痛悼而已。”明确指出是悔恨之作,并能体会到其“但自痛悼而已”的心情,远胜《诗序》“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的理解。
重视其抒情性,使得朱熹对《诗经》文本的文学性有很好的把握,从而对某些作品做出了比汉诗经学更合理的解释。如《邶风·柏舟》篇,《诗集传》云:“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诗,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相类,岂非庄姜之诗也欤?”从辞气的角度确认该篇是妇人自抒其情,要比《诗序》认定为刺诗合理。如《小雅·頍弁》篇,《诗序辨说》批评《诗序》云:“《序》见诗言‘死丧无日’,便谓‘孤危将亡’,不知古人劝人燕乐多为此言,如‘逝者其耋,它人是保’之类。且汉魏以来乐府犹多如此,如‘少壮几时’、‘人生几何’之类是也。”用汉魏乐府来比附《诗三百》,则说明朱熹认识到两者之间有相通处。如《召南·卷耳》篇,《诗集传》于首章末曰:“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于次章末又曰:“此又托言欲登此崔巍之山……”,这两个“托言”说明朱熹认为“采采卷耳”与“陟彼崔巍”皆非写实,而只是为抒情服务的想象之辞,由此可见朱熹对“文学的”表达方法有很深的认识。又如《鲁颂·〓宫》篇,《诗集传》于第三章末云:“此章以后,皆言僖公致敬郊庙,而神降之福,国人称愿之如此。”该篇颂鲁国之盛言过其实,是否信史,值得怀疑。汉诗经学傅会书史以坐实之,不免授人把柄。朱熹则斩截地指出是国人称愿之辞,使人读之如冰涣然。诗歌既然有抒情性质,自然可以抒发一种理想,不必句句写实。由此,朱熹注意到《诗三百》在表现上的“虚”与“实”之关系。汉诗经学将《诗三百》认定为政治美刺诗,是国史一类人以旁观者身份叙述事件,自然不可能象朱熹这样地来解诗。
敏感于诗之辞气,用汉魏乐府作比附,并注意到其在表现上的虚实关系,这已然是从文学角度来认识《诗经》,是宋学高于汉学之处。而这一文学角度,根源于宋学对《诗经》文本性质的认识。因此,对抒情主体性的确认,是宋学对汉学的一场革命。
三 汉、宋诗经学对“赋比兴”之“兴”认识的不同:“取义”与“不甚取义”
对“赋、比、兴”,尤其是对“兴”的认识有很大差别,亦是汉、宋诗经学的一大分歧。汉诗经学基本上是从取义的角度来认识“兴”,比附道德与政治;宋诗经学则从艺术修辞的角度来认识“赋、比、兴”,无比附之色彩。
关于“兴”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朱熹给“赋、比、兴”下过定义,对于宋诗经学所用之“兴”,后人无歧解。《毛传》虽“独标兴体”,但未对其内涵做明确界定,后人的界定亦未必合于《毛传》本义。但我们可以从《毛传》自身总结出“兴”之义例。
《毛传》与《诗集传》在“兴”之义例上的差别,首先表现在标“兴”的位置不同。
《毛传》一般于首章的某句(多数是二句)之下标兴,而不是在章末(有个别地方标在章末,乃是因为在意义上整章为一个句群。亦有个别地方不是标在首章,如《小雅·南有嘉鱼》篇,标在第三章,算是特例)。而《诗集传》,无论“赋”、“比”、“兴”,都标在各章章末。标“兴”位置的差别反映了《毛传》与《诗集传》对“兴”的性质认识不同。《毛传》认定一个句群(一般是两句)自身具有“兴”义,其“兴”义并不依赖于上下文的关系而存在,故标“兴”于句群之末。《诗集传》的“兴”,则指上下文在修辞上的一种关系,所以标“兴”于各章章末。
我们再看《毛传》与《诗集传》在“兴”的具体用法上的区别。《毛传》标“兴”,有时不加任何解说,有时则对“兴”义加以申说。如《关雎》篇,《毛传》在“兴也”之后,有这样一节:“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鸠之有别焉。”这是单就此二句取义,认为“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上是写“关雎”,实际上是喻“后妃之德”。因为在“挚而有别”这一点有相似性,所以《毛传》可以用“关雎”之性来比附“后妃”之德。凡是《毛传》“兴”的取义,无不基于这种对“本体”(若“雎鸠”)和“兴体”(若“后妃”)之间的相似性的认定。而这种相似性的认定,又往往要落实到道德或政治的比附上。《诗集传》三章章末皆标“兴”,于首章章末亦有一节解说,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彼关关然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乃是从句群之间的关系着眼,“兴”指的是“他物”(上个句群)与“所咏之辞”(下个句群)之间“先言”与“引起”的关系。朱熹所理解的“兴”实不能脱离这种关系而存在。同是一个“兴”字,对于《毛传》来说,“本体”一定是经文中的一个句群;“兴体”则是“本体”隐含的某种类比性喻义,而决不是经文中的另一个句群。对于《诗集传》来说,“本体”和“兴体”一定都是经文中的一个句群,而且通常是同一章中的上下文。(其实,对《诗集传》来说,称之为“本句”和“兴句”更加合适。)
《孔疏》云“比显而兴隐”,“兴”义既然很深隐,自然要用特殊的眼光来发掘,于是汉儒便充分发挥其穿凿的特长,用心发掘经文字面以外的“深意”。朱熹向来厌恶汉儒的穿凿,自然对这种“深意”持怀疑的态度。
前文所举《周南·关雎》篇的例子,似乎《诗集传》之“兴”也是取义的,它们的“本体”与“兴体”之间也有某种类似性。但这种取义明显不同于《毛传》的“兴”之取义,亦不是其本质性特征。朱熹不甚看重“本体”与“兴体”之间有无意义上的关联,他所认定为“兴”的诗,颇有一些“全不取义”。如《召南·小星》篇,《诗集传》于二章章末皆标“兴也”,并云:“盖众妾进御于君,不敢当夕,见星而往,见星而还,故因所见以起兴。其于义无所取,特取在东、在公两字之相应耳。”可以因所见起兴,可以因声韵相近起兴,于《小雅·南有嘉鱼》篇末章则径直说:“此兴之全不取义者也。”“兴”可以“于义无所取”,是朱熹对汉诗经学的一大突破。
取义是毛、郑之“兴”的本质性特征,以类比取喻的方法,赋予《诗三百》道德或政治的意义,与汉儒将《诗三百》看作“政治美刺诗”的这一认识是相一致的。朱熹则主张“兴诗不甚取义”,而将“兴”视为一种修辞手法。宋学完全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认识“赋、比、兴”的,这亦是对汉学的一大突破。对比附道德以说诗的扬弃,使得《诗经》文本作为独立体而存在的价值进一步凸现出来。
四 汉、宋诗经学在《诗》之用上的不同:“‘礼’的规范”与“‘养心劝惩’说”
在对《诗经》文本做具体阐释之外,汉、宋诗经学也都重视其教化作用,但着眼点有所不同。汉儒“以礼说诗”,重视其对个人行为的外在规范性作用;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倡“养心劝惩”之说。
汉诗经学中,今文经学家更重《诗》之用。西汉今文经学讲究通经致用,他们具体的做法是以《诗三百》当谏书。《汉书·昌邑王传》载昌邑王郎中令龚遂事,《汉书·儒林传》载昌邑王师王式事,都说明习《诗》是当时王室的日课,而且时人认同以《诗三百》作谏书这一观念。《汉书·匡衡传》亦载匡衡好引《诗》以谏。汉成帝即位,匡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曰:“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源。’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所论颇似《关雎》篇小序,并要求时君以此为择偶标准。
“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一句,显示出汉儒以“礼”说诗的本色。“礼”的内涵,可以通俗地说成是时人认同并遵守的“行为规范”。儒家重“礼”,“礼”又涉及人伦规范的各方面,不独婚姻而已,所以汉儒能在很广阔的范围内以礼说诗。汉儒认定《诗三百》是美刺之作,所及又皆王侯宫室之事,因此以礼说诗,从《诗》中演绎出贵族的行为标准,并反过来要求当时的统治者遵从此规范。这是汉儒“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的理论依据。
以礼说诗乃是《诗序》的法宝,凡是合于礼的,它便定为“美”;不合于礼的,它便说是“刺”。《诗序》又是毛、郑一派的灵魂,所以我们说毛、郑一派诗经学亦是“以礼说诗”。但是,毛、郑古文经学家一派在《诗》之用上却远不如今文家。史传无毛公以《诗三百》作谏书的美谈。至于东汉一朝,这一风气竟似绝迹。古文经学家的成就似仅在学术自身,与时政的关系则远不及今文经学家密切。东汉以后的诗经学遂流为纯粹的章句训诂之学。
这一点令朱熹很不满意。既不满于章句之末学,自不得不留心于《诗》之用,于是朱熹提出“养心劝惩”说。《诗集传》于《关雎》篇云:“学者姑即其辞而玩其理以养心焉,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诗集传·序》论《诗》之教,曰:“因有以劝惩之……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朱熹于《读吕氏诗记桑中高》篇论“劝惩”最为充分,曰:“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则雅人庄士有难言之者矣。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悯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以“劝善惩恶”来解说“思无邪”,并将“无邪”认定为“读者之思”,是一大创见。朱熹不外是教人以《诗》为鉴,
“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读“淫诗”要心知其丑而自为警戒。
朱熹论《诗》之用,尤重感发意志之“兴”。《诗传遗说》卷一《纲领》载其论《诗》之兴数条,如:“兴,起也……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兴于诗,兴此心也”,“有以兴起其善心,惩创其恶志,便是兴于诗之功也”,“问诗如何可以兴,曰:‘读诗,见其不美者,令人羞恶,见其美者,令人兴起’”,无不说明朱熹对《诗》之“兴”感发意志的认识,依旧落实于劝善惩恶之上。尤其值注意的是,朱熹劝惩的对象是“善心”和“恶志”,属于内在的心性范畴。朱熹倡“劝惩养心”之说,与他对心性的认识有关。朱熹认为性有“天理之性”(亦称“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别。天理之性,纯粹至善,气质之性,则因所禀有昏明清浊之异,善恶不齐。但是,可以通过“学以反之”,变化气质,使其向“天理之性”看齐。读《诗》以感发意志是“学以反之”的重要途径。
与以礼说诗、重外在约束的汉诗经学不同,宋儒的诗教说重内在的修养。“劝惩”即“养心”,纯粹是一种内省的功夫。通过学《诗》来感发善心,重人格的培养,类似于今日提倡的美育。此外,汉儒诗教的规范对象直接指向最高统治层,宋学诗教的对象则要广阔得多。
两千年的诗经学史,是一笔陈年烂账。其中分歧尤大者,在汉宋之争。汉代传《诗》者,有齐、鲁、韩、毛四家。宋学诗经学的集大成著作为朱熹的《诗集传》。因今文三家诗已亡(今存者惟《韩诗外传》,不足以代表三家诗),故论汉、宋诗经学之异同,其重点必落实到比较《诗集传》与《毛传》、《郑笺》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汉、宋诗经学(《诗集传》与《毛传》、《郑笺》)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其荦荦大者,约为以下四端:一、在文本阐释方法上的不同;二、对文本性质认识的不同;三、对“赋比兴”之“兴”认识的不同;四、在《诗》之用上的不同。
一 汉、宋诗经学在文本阐释方法上的不同:“依《序》说诗”与“求诗本义”
汉、宋诗经学之争的关键在于是尊《序》还是废《序》。落实到文本阐释上,实际只是个是否依《序》说诗的问题。尊《序》、废《序》之争的关键,在于论者对《诗序》是否合于诗旨的判断。汉学一派以为《诗序》出于圣人(为其入室弟子所传),其对诗旨的阐释自可尊崇,故主张依《序》说诗;宋学一派以怀疑之精神,独立思考,觉《诗序》不合诗旨之处甚多,因疑其非圣人所作,故不主张依序《说》诗,而于文本自身求诗本义。
因为对《诗序》作者的争议,《诗序》与《毛传》的先后亦相应成为诗经学的一大公案。笔者个人的意见主张《诗序》至少不晚于毛传,而且《毛传》分明是依序说诗。《郑笺》和《孔疏》的依序说诗,自不待言:几乎每一句的解说,都要迁就《诗序》,绝不敢有什么动摇和怀疑。我们可以说,《诗序》是汉诗经学的灵魂,依《序》说诗是汉诗经学的根本特征。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诗经学却不如此。朱熹在《诗序辨说》卷首就指出:一、《序》出于汉人之手,非圣人作;二、《序》有不合诗人之本义处。从根本上否定了《诗序》的权威性。朱熹对后人不明《序》乃汉人之作,误以为是圣人遗说,因此依《序》说诗,穿凿迁就的做法,深为不满。朱熹批评汉学诗经学依《序》说诗、迷失本义的同时,提出自己的解诗主张:涵泳本文,求诗本义。从涵泳文本自身求诗本义,进而发现《诗序》不尽合于诗旨,实是宋儒废《序》的根本。
以《诗序》为核心的汉诗经学在说诗上有两个错误倾向:一是断章取义,一是傅会历史。“断章取义”,是将《诗经》作品文本的局部从整体上割裂开来,不顾文本的整体性,随意生说。朱熹对汉学诗经学不顾文理血脉、割裂全篇,仅据一句生说的做法,给予了严厉批评。“傅会历史”,主要是因为汉儒过于迷信“风雅正变”之说,依据世次来定诗之美刺。凡是一篇诗,在汉儒看来一定是要对时政有所美刺的。凡是时代在前(周初文武成康时)的,一律是“美”;时代在后的,一般就认定是“刺”。若是世次在后,而文意为美的,便说是“陈古刺今”。朱熹在《诗集传》和《诗序辨说》中,从妄断世次、美刺不当、滥用“陈古刺今”等三方面,对汉学诗经学傅会历史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具体辩驳。其辩驳的具体手段则是“考诸书史”和“揆以情理”。
不依《序》说诗,而于经文自身求诗本义,实际上是承认《诗经》文本自身的独立性,这为从文学角度认识《诗经》,并使其最终脱离经学的附庸地位,提供了可能,是宋学对汉学的一大突破。否定断章取义,主张说诗要照管前后血脉,则是认同《诗经》文本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局部(单独的一句)的含义受整体(完整的一篇或其中一章)制约,不能将局部从整体中割裂开来。宋学的这一认识也较汉学合理。
二 汉、宋诗经学对文本性质认识的不同:“政治美刺诗”与“一般抒情诗”
对《诗经》文本性质的认识有异,亦是汉、宋诗经学的分歧之处。汉诗经学认定《诗三百》是政治美刺诗,默认其叙述角度为第三人称。宋诗经学则认为《诗三百》中相当一部分是一般抒情诗,而且是以第一人称自抒其情。
《诗集传序》曰:“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变风中相当数量的作品是淫奔者之辞:如《鄘风·桑中》篇,《诗序辨说》云:“此淫奔者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认定国风的一大部分为里巷男女言情之作,并对其抒情主体加以确认,指出其中的一部分(“淫诗”)乃淫奔者所自作,是朱熹对诗经学的一大贡献。
《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异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这一节包含了以下两种认识:一、变风、变雅的作者是国史。二、其创作目的是“讽其上。”我们还可由此推论《诗序》默认整个《诗三百》的作者是国史(只有《鄘风·载驰》等极少篇目例外),从《小序》来看,其具体处理方式,则有时笼统题曰“国人伤之”或“君子刺之”。序者对整个《诗三百》的认识是非美即刺,亦即认定《诗三百》在性质上纯为美刺国事的政治诗,而非一般性的抒情诗。汉诗经学沿袭《诗序》的认识,亦将《诗三百》当作政治诗看,解诗之时,往往傅会政治。
汉诗经学将诗的作者默认为国史一类人,具体到“淫诗”的解说时,将其作者处理为事件的局外人,认为作者只是以第三人称的身份来叙述这事件,他的目的乃是要抨击这淫乱之事,以及造成这风气的政治背景。这样做,实际上是取消了这类诗歌在一般意义上的抒情性,而将其处理成纯粹的政治美刺诗。朱熹对这类诗歌的抒情主体,则做出了合理而有意义的确认。既然是自作,便是“淫奔者”以第一人称自歌其事、自抒其情,这实际上乃是认定其为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诗。尽管朱熹从理学的立场否定了这种男女私情,目之为“淫诗”,但毕竟为后人认识这类诗的抒情性指明了方向。
不独“淫诗”,此外的很多作品,朱熹也明确指出是抒情主人公所自作。如《邶风·雄雉》篇,《诗序》曰:“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诗序辨说》则云:“此亦妇人作,非国人之所为也。”《诗集传》则云:“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故言雄雉之飞,舒缓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从役于外,而自遗阻隔也。”依《诗序》的理解,此诗是刺时之作,不过是国史以旁观者身份叙述人民的苦难而已。朱熹则确认其为思妇之词,是抒情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自歌怨旷之苦,于是这首诗便具有了后世闺怨一类诗的品质,也便有了一唱三叹之致。
有了对抒情主体的确认为基础,朱熹在具体说诗时,往往对其曲折幽深之情有真切体会。如《卫风·氓》篇,《诗集传》曰:“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于其第五章又曰:“盖淫奔之人,不为兄弟所齿,亦不为兄弟所恤,理固有所必然者,亦何所归咎哉!但自痛悼而已。”明确指出是悔恨之作,并能体会到其“但自痛悼而已”的心情,远胜《诗序》“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的理解。
重视其抒情性,使得朱熹对《诗经》文本的文学性有很好的把握,从而对某些作品做出了比汉诗经学更合理的解释。如《邶风·柏舟》篇,《诗集传》云:“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诗,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相类,岂非庄姜之诗也欤?”从辞气的角度确认该篇是妇人自抒其情,要比《诗序》认定为刺诗合理。如《小雅·頍弁》篇,《诗序辨说》批评《诗序》云:“《序》见诗言‘死丧无日’,便谓‘孤危将亡’,不知古人劝人燕乐多为此言,如‘逝者其耋,它人是保’之类。且汉魏以来乐府犹多如此,如‘少壮几时’、‘人生几何’之类是也。”用汉魏乐府来比附《诗三百》,则说明朱熹认识到两者之间有相通处。如《召南·卷耳》篇,《诗集传》于首章末曰:“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于次章末又曰:“此又托言欲登此崔巍之山……”,这两个“托言”说明朱熹认为“采采卷耳”与“陟彼崔巍”皆非写实,而只是为抒情服务的想象之辞,由此可见朱熹对“文学的”表达方法有很深的认识。又如《鲁颂·〓宫》篇,《诗集传》于第三章末云:“此章以后,皆言僖公致敬郊庙,而神降之福,国人称愿之如此。”该篇颂鲁国之盛言过其实,是否信史,值得怀疑。汉诗经学傅会书史以坐实之,不免授人把柄。朱熹则斩截地指出是国人称愿之辞,使人读之如冰涣然。诗歌既然有抒情性质,自然可以抒发一种理想,不必句句写实。由此,朱熹注意到《诗三百》在表现上的“虚”与“实”之关系。汉诗经学将《诗三百》认定为政治美刺诗,是国史一类人以旁观者身份叙述事件,自然不可能象朱熹这样地来解诗。
敏感于诗之辞气,用汉魏乐府作比附,并注意到其在表现上的虚实关系,这已然是从文学角度来认识《诗经》,是宋学高于汉学之处。而这一文学角度,根源于宋学对《诗经》文本性质的认识。因此,对抒情主体性的确认,是宋学对汉学的一场革命。
三 汉、宋诗经学对“赋比兴”之“兴”认识的不同:“取义”与“不甚取义”
对“赋、比、兴”,尤其是对“兴”的认识有很大差别,亦是汉、宋诗经学的一大分歧。汉诗经学基本上是从取义的角度来认识“兴”,比附道德与政治;宋诗经学则从艺术修辞的角度来认识“赋、比、兴”,无比附之色彩。
关于“兴”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朱熹给“赋、比、兴”下过定义,对于宋诗经学所用之“兴”,后人无歧解。《毛传》虽“独标兴体”,但未对其内涵做明确界定,后人的界定亦未必合于《毛传》本义。但我们可以从《毛传》自身总结出“兴”之义例。
《毛传》与《诗集传》在“兴”之义例上的差别,首先表现在标“兴”的位置不同。
《毛传》一般于首章的某句(多数是二句)之下标兴,而不是在章末(有个别地方标在章末,乃是因为在意义上整章为一个句群。亦有个别地方不是标在首章,如《小雅·南有嘉鱼》篇,标在第三章,算是特例)。而《诗集传》,无论“赋”、“比”、“兴”,都标在各章章末。标“兴”位置的差别反映了《毛传》与《诗集传》对“兴”的性质认识不同。《毛传》认定一个句群(一般是两句)自身具有“兴”义,其“兴”义并不依赖于上下文的关系而存在,故标“兴”于句群之末。《诗集传》的“兴”,则指上下文在修辞上的一种关系,所以标“兴”于各章章末。
我们再看《毛传》与《诗集传》在“兴”的具体用法上的区别。《毛传》标“兴”,有时不加任何解说,有时则对“兴”义加以申说。如《关雎》篇,《毛传》在“兴也”之后,有这样一节:“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鸠之有别焉。”这是单就此二句取义,认为“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上是写“关雎”,实际上是喻“后妃之德”。因为在“挚而有别”这一点有相似性,所以《毛传》可以用“关雎”之性来比附“后妃”之德。凡是《毛传》“兴”的取义,无不基于这种对“本体”(若“雎鸠”)和“兴体”(若“后妃”)之间的相似性的认定。而这种相似性的认定,又往往要落实到道德或政治的比附上。《诗集传》三章章末皆标“兴”,于首章章末亦有一节解说,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彼关关然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乃是从句群之间的关系着眼,“兴”指的是“他物”(上个句群)与“所咏之辞”(下个句群)之间“先言”与“引起”的关系。朱熹所理解的“兴”实不能脱离这种关系而存在。同是一个“兴”字,对于《毛传》来说,“本体”一定是经文中的一个句群;“兴体”则是“本体”隐含的某种类比性喻义,而决不是经文中的另一个句群。对于《诗集传》来说,“本体”和“兴体”一定都是经文中的一个句群,而且通常是同一章中的上下文。(其实,对《诗集传》来说,称之为“本句”和“兴句”更加合适。)
《孔疏》云“比显而兴隐”,“兴”义既然很深隐,自然要用特殊的眼光来发掘,于是汉儒便充分发挥其穿凿的特长,用心发掘经文字面以外的“深意”。朱熹向来厌恶汉儒的穿凿,自然对这种“深意”持怀疑的态度。
前文所举《周南·关雎》篇的例子,似乎《诗集传》之“兴”也是取义的,它们的“本体”与“兴体”之间也有某种类似性。但这种取义明显不同于《毛传》的“兴”之取义,亦不是其本质性特征。朱熹不甚看重“本体”与“兴体”之间有无意义上的关联,他所认定为“兴”的诗,颇有一些“全不取义”。如《召南·小星》篇,《诗集传》于二章章末皆标“兴也”,并云:“盖众妾进御于君,不敢当夕,见星而往,见星而还,故因所见以起兴。其于义无所取,特取在东、在公两字之相应耳。”可以因所见起兴,可以因声韵相近起兴,于《小雅·南有嘉鱼》篇末章则径直说:“此兴之全不取义者也。”“兴”可以“于义无所取”,是朱熹对汉诗经学的一大突破。
取义是毛、郑之“兴”的本质性特征,以类比取喻的方法,赋予《诗三百》道德或政治的意义,与汉儒将《诗三百》看作“政治美刺诗”的这一认识是相一致的。朱熹则主张“兴诗不甚取义”,而将“兴”视为一种修辞手法。宋学完全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认识“赋、比、兴”的,这亦是对汉学的一大突破。对比附道德以说诗的扬弃,使得《诗经》文本作为独立体而存在的价值进一步凸现出来。
四 汉、宋诗经学在《诗》之用上的不同:“‘礼’的规范”与“‘养心劝惩’说”
在对《诗经》文本做具体阐释之外,汉、宋诗经学也都重视其教化作用,但着眼点有所不同。汉儒“以礼说诗”,重视其对个人行为的外在规范性作用;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倡“养心劝惩”之说。
汉诗经学中,今文经学家更重《诗》之用。西汉今文经学讲究通经致用,他们具体的做法是以《诗三百》当谏书。《汉书·昌邑王传》载昌邑王郎中令龚遂事,《汉书·儒林传》载昌邑王师王式事,都说明习《诗》是当时王室的日课,而且时人认同以《诗三百》作谏书这一观念。《汉书·匡衡传》亦载匡衡好引《诗》以谏。汉成帝即位,匡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曰:“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源。’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所论颇似《关雎》篇小序,并要求时君以此为择偶标准。
“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一句,显示出汉儒以“礼”说诗的本色。“礼”的内涵,可以通俗地说成是时人认同并遵守的“行为规范”。儒家重“礼”,“礼”又涉及人伦规范的各方面,不独婚姻而已,所以汉儒能在很广阔的范围内以礼说诗。汉儒认定《诗三百》是美刺之作,所及又皆王侯宫室之事,因此以礼说诗,从《诗》中演绎出贵族的行为标准,并反过来要求当时的统治者遵从此规范。这是汉儒“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的理论依据。
以礼说诗乃是《诗序》的法宝,凡是合于礼的,它便定为“美”;不合于礼的,它便说是“刺”。《诗序》又是毛、郑一派的灵魂,所以我们说毛、郑一派诗经学亦是“以礼说诗”。但是,毛、郑古文经学家一派在《诗》之用上却远不如今文家。史传无毛公以《诗三百》作谏书的美谈。至于东汉一朝,这一风气竟似绝迹。古文经学家的成就似仅在学术自身,与时政的关系则远不及今文经学家密切。东汉以后的诗经学遂流为纯粹的章句训诂之学。
这一点令朱熹很不满意。既不满于章句之末学,自不得不留心于《诗》之用,于是朱熹提出“养心劝惩”说。《诗集传》于《关雎》篇云:“学者姑即其辞而玩其理以养心焉,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诗集传·序》论《诗》之教,曰:“因有以劝惩之……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朱熹于《读吕氏诗记桑中高》篇论“劝惩”最为充分,曰:“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则雅人庄士有难言之者矣。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悯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以“劝善惩恶”来解说“思无邪”,并将“无邪”认定为“读者之思”,是一大创见。朱熹不外是教人以《诗》为鉴,
“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读“淫诗”要心知其丑而自为警戒。
朱熹论《诗》之用,尤重感发意志之“兴”。《诗传遗说》卷一《纲领》载其论《诗》之兴数条,如:“兴,起也……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兴于诗,兴此心也”,“有以兴起其善心,惩创其恶志,便是兴于诗之功也”,“问诗如何可以兴,曰:‘读诗,见其不美者,令人羞恶,见其美者,令人兴起’”,无不说明朱熹对《诗》之“兴”感发意志的认识,依旧落实于劝善惩恶之上。尤其值注意的是,朱熹劝惩的对象是“善心”和“恶志”,属于内在的心性范畴。朱熹倡“劝惩养心”之说,与他对心性的认识有关。朱熹认为性有“天理之性”(亦称“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别。天理之性,纯粹至善,气质之性,则因所禀有昏明清浊之异,善恶不齐。但是,可以通过“学以反之”,变化气质,使其向“天理之性”看齐。读《诗》以感发意志是“学以反之”的重要途径。
与以礼说诗、重外在约束的汉诗经学不同,宋儒的诗教说重内在的修养。“劝惩”即“养心”,纯粹是一种内省的功夫。通过学《诗》来感发善心,重人格的培养,类似于今日提倡的美育。此外,汉儒诗教的规范对象直接指向最高统治层,宋学诗教的对象则要广阔得多。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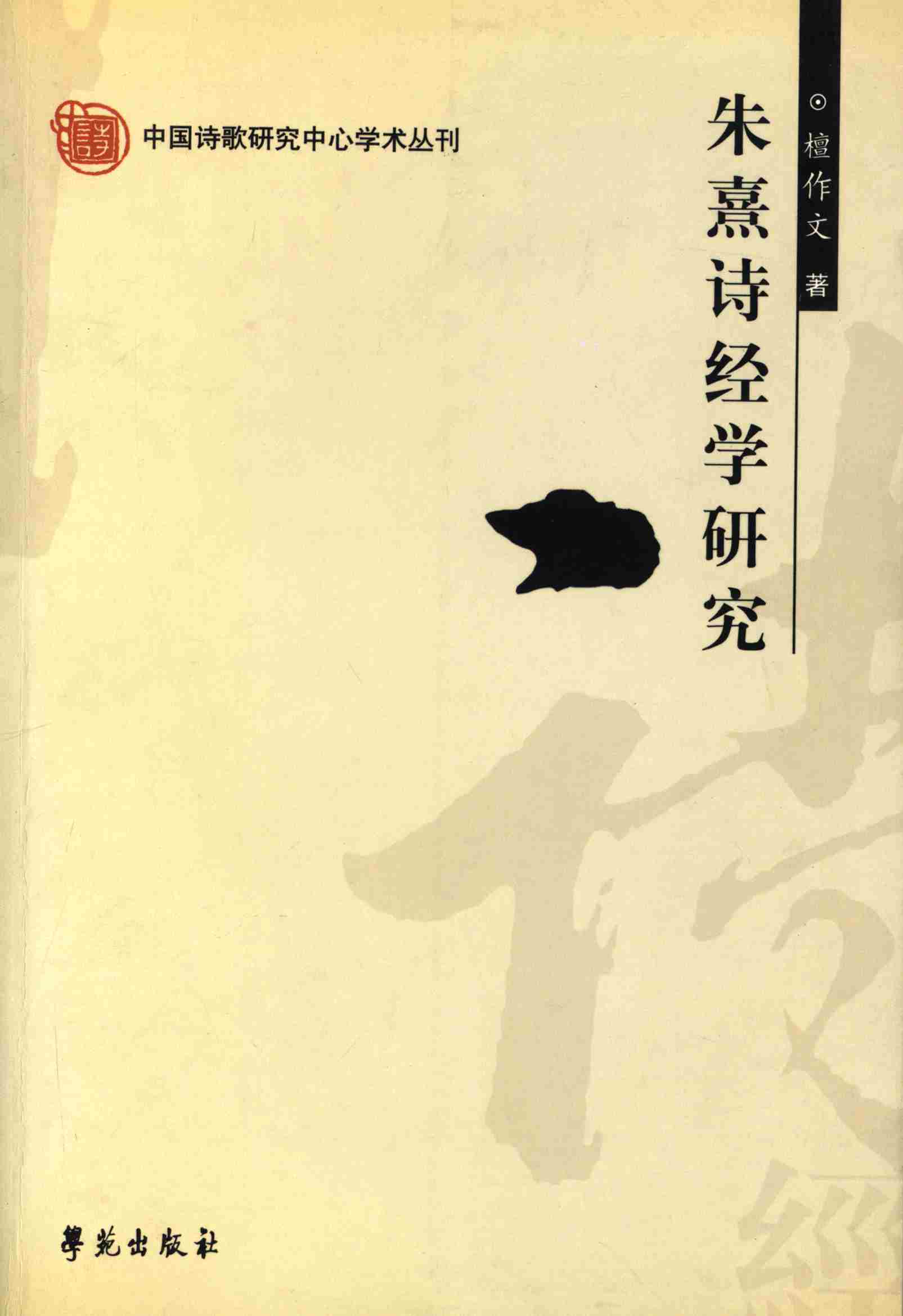
《朱熹诗经学研究》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本书为南宋朱熹诗词作品集,分为感事诗、哲理诗、山水诗、酬对诗、杂咏诗和词赋六大类。其中感事诗90首,主要反映朱熹对天下大事的观感及其在各个时期的基本思想倾向,按其主题又分为爱国恤民与述怀明志两组;哲理诗73首,主要反映朱熹的学术观点,按其主题又分为宇宦观、人生观、道德修养和为学三组;山水诗148首,主要反映朱熹的游踪和各地山川形胜,其中又分为武夷云谷、衡岳、庐山及其他胜地四大块;酬对诗87首,主要反映朱熹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内又分为奉和、题赠、迎送、寿挽四组;杂咏诗99首,为朱熹对各种事物的吟咏与思想寄寓,反映其日常生活情趣,内又分为咏物、咏景、咏居、咏事四组;词赋18首,按体裁分类。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