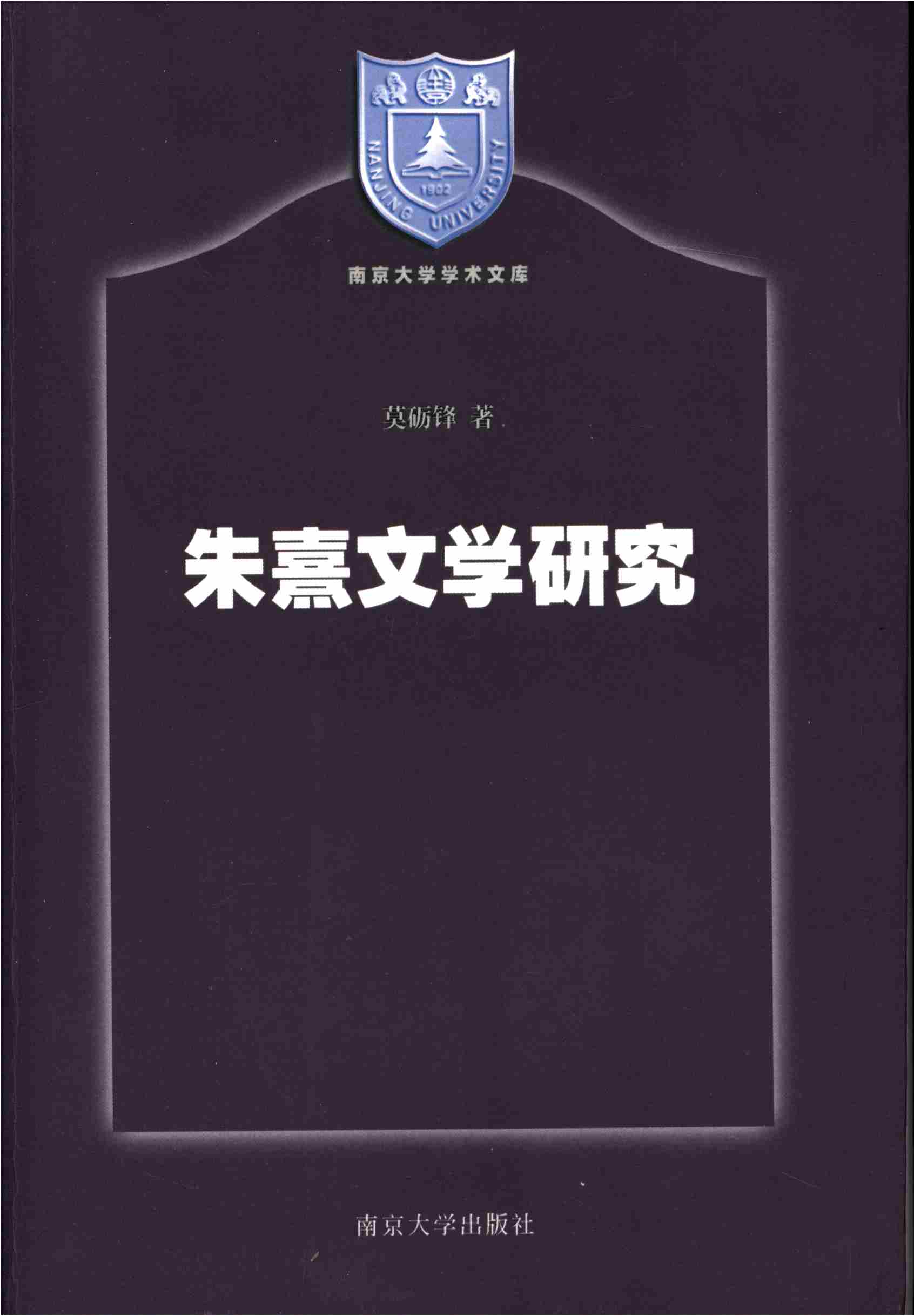四、朱熹重要文学著作考释
| 内容出处: | 《朱熹文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4451 |
| 颗粒名称: | 四、朱熹重要文学著作考释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23 |
| 页码: | 14-3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是中国宋代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他在文学著作考释方面留下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他最著名的考释著作包括《四书集注》和《周易集注》。《四书集注》是对四部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进行详细的注解和解释,深入阐发其中的思想与道理,对后世研究儒家经典的影响深远。《周易集注》是对古代文化经典《周易》的考释,涵盖了哲学、象数学等多个层面的解读,对后世的易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 关键词: | 朱熹 文学 著作考释 |
内容
毫无疑问,朱熹最重要的文学著作是《诗集传》、《楚辞集注》和《韩文考异》三种。对于这三种著作的内容和意义,我们将另辟专章予以论述,本节中先对三书的成书过程进行考释。
(一)《诗集传》
朱熹对于《诗经》用力最勤,《诗集传》便是他研究《诗经》的成果之结晶。但是关于此书的成书时间,却历来说法不一。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三系此书于淳熙四年(1177),是年朱熹四十八岁,今人多从此说。③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今本《诗集传》卷首的《序》署曰“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但是其实朱熹的孙子朱鉴在《诗传遗说》卷二中早已指出这篇序不是为《诗集传》而作:“《诗传》旧序,此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经时所作,后乃尽去《小序》。”清人《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此序写于《诗集传》成书之前:“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无一语斥《小序》,盖犹初稿。序末称‘时方辑诗传’,是其证也。”①今揆此序语意,确实尚无显斥《小序》之处,可见它原来并不是为尽去《小序》的《诗集传》而作,当然不能据它来确定《诗集传》的成书年代。
此外,近人吴其昌在《朱子著述考》中认为《诗集传》成书于淳熙四年(1177)之后,淳熙七年(1180)之前,然未有确证。②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则说“《诗集传》在丁酉亦尚未动稿”,又说“乙未前,《诗集传》似已大体成书”。③今按丁酉是淳熙四年(1177),乙未是淳熙二年(1175),钱氏所言分明是自相龃龉。
事实上朱熹治《诗》是一件旷日持久的工作,《诗集传》的撰写大约始于淳熙四年,而其修订则一直持续到庆元五年(1199),即朱熹去世前的一年。④
朱熹早年说《诗》,基本上遵从《小序》之说,当时也曾成书,此书朱熹称之为《集解》,⑤或称《诗解》。⑥原书已佚,但在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中保存了若干片断,束景南据之辑成《诗集解辑存》。⑦关于这部《诗解》,吴其昌认为与《诗集传》是两部书,⑧钱穆则认为是《诗集传》的初稿。⑨我们认为两种说法不妨并存,因为第一,两书都曾单独刊行,主要的观点又不同,当然可以看作两部著作。第二,两书异中有同,我们以《郑风》为例,把《吕氏家塾读诗记》中所引的《诗解》与《诗集传》进行对比,发现前者对《将仲子》、《狡童》、《褰裳》、《风雨》等篇的解释是遵从《小序》的,没有像后者那样称之为“淫奔者之诗”。但是关于《野有蔓草》、《溱洧》两篇,前者的解释基本上包括在《诗集传》中,文字上仅有一二字之差异。由此可见,《诗集传》对《诗解》作了相当大的改动,但也有所保留,所以可以把《诗解》视为《诗集传》的基础或初稿。
毫无疑问,《诗集传》代表着朱熹的晚年定论,我们应该根据它而不是《诗解》来评判朱熹的《诗经》学。但是,朱熹在《诗集传》中的体现的重要文学思想,即不盲从汉儒注疏而直接依据《诗经》的文本来体会其旨意的观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朱熹曾对门人说:“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①对这段话,王懋竑认为“其为记者之误无疑也。”②钱穆也认为“所云‘后到三十岁’,恐是‘五十岁’之误。否则是二十岁后又三十岁,在朱子五十岁左右,始断然知《小序》之出汉儒。”③的确,说朱熹三十岁时便已断然不信《小序》,是有些不太准确。但是他那时已经对《小序》产生怀疑,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朱熹还说过一些类似的话,不会都是出于门人误记,例如:“郑渔仲《诗辨》:‘《将仲子》只是淫奔之诗,非刺仲子之诗也。’某自幼便知其说之是。”④又如:“熹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荡旧说,诗意方活。”⑤前一则告诉我们,朱熹疑《小序》并非是毫无来由忽生圣解,而是受到了其他宋儒的启发。郑樵比朱熹年长二十六岁,他在《诗辨妄》中已经指出《诗序》是汉人所作,而且是“村野妄人所作”,朱熹自幼便已读到《诗辨妄》,当然有助于疑序观点的形成。①后一则告诉我们,朱熹作《诗解》时虽然尚未弃去《小序》,但心中早已多有怀疑,不过是“曲为之说”而已。所以朱熹晚年回忆自己青年时代便已疑《序》,是与事实并不矛盾的。
那么,既然朱熹早年已经怀疑《小序》,为什么在《诗解》中又并不斥责《小序》呢?原来朱熹治学十分谨慎,虽然善于怀疑,但未经深思熟虑是不肯轻易创立新说的。从上面所引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他从怀疑《小序》到公然抛弃《小序》,是经历了一个颇长的过程的。在淳熙四年(1177),朱熹虽然早已对《小序》有所怀疑,但尚未形诸文字。淳熙四年他为《诗解》作序,也还没有明言《小序》之非。但次年也即淳熙五年(1178),他写信给吕祖谦说:“大抵《小序》尽出后人臆度,若不脱此窠臼,终无缘得正当也。去年略修旧说,订正为多,尚恨未能尽去,得失相半,不成完书耳。”②可见他已公开声明废弃《小序》,并准备以此为指导思想改写《诗解》。其后朱熹又多次与吕祖谦书信往来,争辩《小序》之是非。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卒。次年,朱熹作《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深为感慨地说:“此书所谓朱氏者,实熹少时浅陋之说,而伯恭父误有取焉。其后历时既久,自知其说有所未安,如‘雅郑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则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熹窃惑之。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矣。”③由此可知,朱熹对于废弃《小序》的态度十分认真,他决心要把《小序》的是非弄个水落石出。甚至在他反复修改后终于定稿的、以废弃《小序》为说诗主旨的《诗集传》于淳熙十四年(1187)付梓之后,他仍然不停地对之进行修订。淳熙十六年(1189),年已六十的朱熹写信对蔡季通说:“《诗传》中欲改数行,乃马庄父来说,当时看得不仔细,只见一字不同,便为此说。今详看乃知误也,幸付匠者正之。”①同年他又写信给吴伯丰说:“《诗传》中有音未备者,有训未备者,有以经统传、舛其次者,此类皆失之不详,今当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减矣。不免别作《补脱》一卷,附之《辨说》之后。……其例如后……”②他在此信中所说到的应予补订之处,有的在今本《诗集传》中没有照改,例如《周南·樛木》篇,此信中指出:“乐只音止二字,合附本字下。”今本《诗集传》未从。但也有几处已经改正,例如《鄘风·载驰》篇,此信中指出:“‘无以我为有过,虽尔’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下。”今本《诗集传》已据之改正。可见朱熹对于《诗集传》一书确是倾注了一番心血的,他早年怀疑《小序》,经长时间的酝酿、修订,终于写成尽废《小序》的《诗集传》,付梓后还继续修补,力求精益求精。所以到了暮年,朱熹对《诗集传》“自以为无复遗恨,曰:‘后世若有扬子云,必好之矣!’”③
《诗集传》于淳熙十四年(1187)首次刊行后,在朱熹生前又曾数次翻刻,据朱鉴《诗传遗说后跋》所记,当时计有建安本、豫章本、长沙本、后山本、江西本等几种刊本,但大多没有留存至今。现在的通行本《诗集传》二十卷是从曾经朱鉴藏过的后山本而出,当即朱熹的晚年定本。另有八卷本乃后代坊刻所并,不足据。
(二)《楚辞集注》
朱熹自幼喜爱《楚辞》,但与《诗集传》的编写不同,他关于《楚辞》的著作却是到晚年才动笔的。关于《楚辞集注》的成书年代,南宋的赵希弁说:“公之加意此书,则作牧于楚之后也。或曰:有感于赵忠定之变而然。”①周密《齐东野语》卷三“绍熙内禅”条也认为此书是朱熹因赵汝愚被谪并暴卒一事而作。今按朱熹“作牧于楚”事在绍熙五年(1194),②而赵汝愚贬永州事在庆元元年(1195),赵暴卒于衡阳道中事在庆元二年(1196),故赵希弁、周密所言意即《楚辞集注》作于庆元二年以后。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下则将《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楚辞辨证》一起系于庆元五年(1199)。今考《楚辞集注》一书未题编写年月,唯朱熹门人杨楫尝跋此书曰:“庆元乙卯,楫侍先生于考亭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永。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③此跋中“乙卯”是指庆元元年(1195),杨楫于此年初来考亭。而杨楫得见朱熹出示“所释《楚辞》一篇”则是在其后,也即赵汝愚“谪死于永”的丙辰(庆元二年)或更后。赵汝愚其人虽然并非朱熹心目中的大贤,但他与朱熹一起受到韩侂胄的打击,且同被目为“伪党”。赵以宋宗室的身份被贬谪到湖南的永州,情形类似于屈原之流放沅湘。庆元元年冬,朱熹仿屈原《橘颂》作《梅花赋》,赋末乱辞云:“王孙兮归来,无使哀江南兮。”①即针对赵汝愚被贬一事而言。而当赵汝愚因遭韩侂胄的爪牙窘辱而暴卒后,太学生敖陶孙即哭之曰:“狼胡无地归姬旦,鱼腹终天痛屈原!”②所以朱熹在庆元年间动手注释《楚辞》,确有深意存焉。他在《楚辞集注》的序中说:“(旧注)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予于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櫽括,定为《集注》八卷。庶几读者得以见古人于千载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载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于后者之不闻也。呜呼悕矣,是岂易与俗人言哉!”这种抑塞历落、慨乎言之的语气,确实与他当时的悲愤心情相吻合。
杨楫在庆元二年看到的“所释《楚辞》一篇”,当是《楚辞集注》的一部分。其后,朱熹注释《楚辞》的工作陆续进行。庆元三年(1197),朱熹写信给方士繇说:“近又看《楚辞》,抄得数卷。大抵世间文字,无不错误,可叹也!”③庆元四年(1198),他又写信给郑子上说:“病中不敢劳心看经书,闲取《楚辞》遮眼,亦便有无限合整理处,但恐犯忌,不敢形纸墨耳。”④此期内朱熹还常与门人谈论《楚辞》,例如谈到《天问》中“启棘宾商”一句说:“某以为‘棘’字是‘梦’字,‘商’字是古文篆‘天’字。”⑤又说:“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①今考前一则为林夔孙所记,乃庆元三年(1197)后所闻,而今本《楚辞集注》卷三中对该句也注曰:“窃疑‘棘’当作‘梦’,‘商’当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误也。”与林生所录者非常接近。后一则为沈僴所记,乃庆元四年(1198)后所闻,语意也与《楚辞集注》序意相合。由此可见朱熹在庆元三、四年间一直在从事《楚辞集注》的撰写。到了庆元五年(1199)三月,朱熹在《楚辞辨证》的题记中说:“余既集王、洪《骚》注,顾其训故文义之外,犹有不可不知者,然虑文字之太繁,览者或没溺而失其要也。别记于后,以备参考。”揆其语意,此时《楚辞集注》已经完成。综上所述,《楚辞集注》成书当在庆元四年或庆元五年初。
在完成《楚辞集注》与《楚辞辨证》以后,朱熹整理《楚辞》的工作仍在继续:第一,他动手编写《楚辞后语》,对晁补之的《续楚辞》、《变离骚》二书所录的作品进行增删,此书在他生前未及完稿,朱熹之子朱在跋此书说:“先君晚岁草定此编,盖本诸晁氏《续》、《变》二书,其去取之义精矣。然未尝以示人也。每章之首,皆略叙其述作之由,而因以著其是非得失之迹。独《思玄》、《悲愤》及《复志赋》以下,至于《幽怀》,则仅存其目,而未及有所论述。”直到嘉定五年(1212),也即朱熹去世十二年后,才由朱在将此书遗稿整理誊写,并于嘉定十年(1217)与《楚辞集注》一并刊行。第二,朱熹又动手编撰《楚辞音考》。庆元五年(1199),朱熹写信给巩仲至说:“《楚辞》板既漫灭,虽修得亦不济事。然欲重刊,又不可整理。使其可以就加雠校,若修得了,可就彼中先校一番,却以一净本见示。当为参订、改定、商量。若别刊得一本,亦佳事也。近得古田一士人所著《补音》一卷,亦甚有功,异时当并以奉寄也。”②庆元六年(1200),也即朱熹去世的那年,他又写信给巩仲至说:“《楚辞》修未?旋了旋寄数板,节次发来为幸。古田《补音》,此间无人写得,今寄一书与苏君,幸能托县官,差人赍去乡下寻之,就其传录尤便。亦闻渠写本颇经删节,已嘱令为全录去矣。然此尝编得《音考》一卷,‘音’谓集古今正音、协韵,通而为一。‘考’谓考诸本同异,并附其间。只欲别为一卷,附之书后,不必搀入正文之下,碍人眼目,妨人吟讽。但亦未甚详密,正文有异同,但择一稳者为定可也。”①此书作于庆元六年春,是年三月九日朱熹逝世,可见《楚辞音考》一书在他生前未及完成。
前文提到的朱熹易箦之前尚“修《楚辞》一段”,现已无法断定是指《楚辞后语》还是《楚辞音考》,但可以肯定他临终之前仍在从事关于《楚辞》的著作。
对于朱熹在垂暮之际孜孜不倦地从事《楚辞》研究一事,他的一些门人颇为不解。杨楫在《楚辞集注》的跋中说:“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楫辈亦不敢窃而请焉。”②的确,如果纯从理学的角度来看,像朱熹那样的理学宗师何必要耗费心力在《楚辞》上呢?然而事实上朱熹对文学的态度是与二程等人相去甚远的,他在晚年动手注释《楚辞》,固然有如上所述的受赵汝愚贬死一事的激发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一向喜好《楚辞》,他对屈原的忠君爱国之心有强烈的共鸣,他对《楚辞》的精彩绝艳也极为倾倒。朱熹注释《楚辞》始于庆元二年(1196),但他对《楚辞》的研究早就开始了。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书楚辞协韵后》中说:“始予得黄叔垕父所定《楚辞协韵》而爱之,以寄漳守傅景仁,景仁为刻板,置公帑。未几予来代景仁,……于是即其板本,复刊正之,使览者无疑也。”①又作《再跋楚辞协韵》说:“《楚辞协韵》九章,所谓‘将寓未详’者,当时黄君盖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读之,故于此不得其说而阙焉。近见閤皁道士甘梦叔说,‘寓’乃‘当’字之误,因亟考之,则黄长睿、洪庆善本果皆作‘当’。……以文义音韵言之,二家之本为是。”②同年他还写信给吴斗南说:“《楚辞协韵》一本纳上,其间尚多谬误,幸略为订之。复以见喻,尚可修改也。”③可见朱熹早就对《楚辞》研究十分留意,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一气呵成《楚辞集注》等一系列著作,正是长期研究、厚积薄发的结果。
《楚辞集注》在朱熹生前未及刊行,现存最早的本子刊于嘉定六年(1213),《楚辞辨证》附录于后。《楚辞后语》六卷则于嘉定十年(1217)由朱在刊刻单行本,今已失传。端平二年(1235),朱鉴始把《楚辞集注》、《楚辞辨证》和《楚辞后语》合刻成一书,并把《楚辞集注》和《楚辞后语》中重复的三篇删去,成为《楚辞集注》的定本。这个本子一直流传至今,曾经山东聊城海源阁收藏,现藏于北京图书馆。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将此本影印出版,成为今日的通行本。由于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宋刊本均已不存,晁补之的《续楚辞》、《变离骚》更是已经失传,所以宋端平本《楚辞集注》已成为今日尚存的最古老、最完整的《楚辞》刻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朱熹地下有知,对此当感欣慰!
(三)《韩文考异》
对于宋人来说,韩愈具有两方面的先导意义。一方面,他是一位以弘扬儒道、排斥异端为己任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他是一位倡导古文、反对骈俪之风的文学家。所以北宋的理学家和古文家对韩愈其人都相当重视,不过重视的角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宋代理学家中文学素养最高的人,他对韩愈的态度也就格外的复杂。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有褒有贬,总的说来则是贬多于褒。朱熹认为韩愈虽然弘扬儒道,但是“只于治国平天下处用功,而未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①又认为韩愈“于道见其大体规模极分明,但未能究其所从来。而体察操履处,皆不细密。”②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也是有褒有贬,但总的说来是赞扬多于讥评。虽然朱熹不满于韩愈的重视文学更甚于儒道:“韩文公第一义是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③“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④然而朱熹对韩文自身是极为赞赏的,他自称:“余少时喜读韩文。”⑤他晚年聚徒讲学时,仍不时对弟子赞扬韩文:“退之文字尽好,末年尤好。”⑥甚至指点弟子学好古文的途径是:“看得韩文熟!”⑦正由于朱熹对韩文持有很高的评价,他才会在晚年耗费心血撰成《韩文考异》一书。
从表面上看,朱熹《韩文考异》是针对方崧卿《韩集举正》而作的。方崧卿(1135—1194),字季申,福建莆田人。其《韩集举正》成书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三年之后,朱熹作《跋方季申所校韩文》,指出方书未能尽善。更数年而《韩文考异》成。但事实上朱熹早就有校勘韩文之念了。他在《跋方季申所校韩文》中说:“余自少喜读韩文,常病世无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广流布,而未暇也。”可见他是因为无暇才迟迟没有动手,但这件事是时时在他心头的。上引跋文中还说到了他注意韩文的一个事例:
又季申所谓谢本,则绍兴甲戌、乙亥之间,余官温陵,谢公弟如晦之子景莫为舶司属官,尝于其几间见之。盖用天台印本,剪裂粘缀,依陈后山本别为次序,而卷首款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读其《送陈秀才序》一篇,“则何不信之有”句内辄用丹笔围去“不”字。初甚骇之,再加寻绎,乃知必去此字,然后一篇首尾始复贯通。盖传袭之误久矣,读者虽亦微觉其硋而未暇深究也。常窃识之,以验他本,皆不其然。此本虽精,亦复不见。岂季申读时,便文纵口,尚不免小有遗脱,将所见者非其真本,先传校者已失此字也耶?(《文集》卷八三,第4页)
钱穆对此极为注意,并据此而认为“朱子为《韩文考异》,其发心积意,远自四十年以前,亦岂一旦乘兴之所能遽成乎?”①从绍兴甲戌(1154)到《韩文考异》成书的庆元年间,确有四十多年的时间跨度。然而朱熹对韩文产生兴趣其实还在绍兴甲戌之前。因为《韩文考异》卷六《送陈秀才彤》下云:“旧读此序,尝怪‘则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断绝,不相承应,每窃疑之。后见谢氏手校真本……”可见朱熹对韩文的“发兴积意”早在见到谢本之前就已开始了。绍兴甲戌那年朱熹二十五岁,也即朱熹对韩文的兴趣始于青年时代,这与他自称“自少喜读韩文”是互相印证的。
《韩文考异》成书于何年?清人王懋竑纂订《朱子年谱》卷四下系之于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是年朱熹六十八岁。近代学者对此均无异词,如牛继昌《朱熹著述分类考略》、①金云铭《朱子著述考》、②钱穆《朱子新学案》、束景南《朱子大传》都持此说。然而王谱的系年其实是根据不足的,因为朱熹文集中涉及《韩文考异》的文章如《韩文考异序》、《书韩文考异前》及《修韩文举正例》③都没有署年月,而今存各本《韩文考异》也大多未署年月,④王谱不过是沿袭旧谱之说而已。所以王懋竑又在《朱子年谱考异》卷四中说:“或《考异》之成在戊午。”戊午即庆元四年(1198)。我认为王懋竑的两种说法都欠准确,现论证如下:
方崧卿《韩集举正》成书于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见到方书后感到不满意,并曾与方商榷。《韩文考异》卷六中据谢本删去《送陈秀才彤》内一字,且云:“方据谢本为多,而亦独遗此字,岂亦未尝见其真本邪?尝以告之,又不见信。故今特删‘不’字,而复详著其说云。”可见朱熹曾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方崧卿,冀其修改,后来才决定另作《考异》。
朱熹晚年著书大多有弟子充当助手,帮助他编撰《韩文考异》的重要助手是方士繇。方士繇(1148—1199),一名伯休,字伯谟,莆田人。他二十多岁即往建安师从朱熹,后徙家至崇安籍溪,遂废举业,专心讲学,并时时往朱熹处问学。陆游说方在朱门“称高弟”,⑤但由于方颇能独立思考,不像其他朱门弟子那样把朱熹的每一句话都奉为金科玉律。比如他曾劝朱熹少著书,①且以朱熹教人读《四书集注》为不然。②朱熹则认为方治学不纯,曾在方去世后说他:“未去时亦安静明了,但可惜后来一向废学,身后但有诗数篇耳。”③也许正是由于方士繇较喜文学,朱熹才把协助编撰《韩文考异》的重任托付给他。《朱文公文集》卷四四中保存了他写给方的书信二十四通,其中有九通谈及《韩文考异》。据此我们不但可以明白方士繇助编《韩文考异》的过程,而且可以推测成书的时间。《与方伯谟》之十七云:“《韩考》烦早为并手写来,便付此人。尤幸。闻冰玉皆入伪党,为之奈何!”《与方伯谟》之十八云:“《韩考》已领。今早遣去者,更烦详阅签示。适有人自三衢来,云琐闼以论陈源故,补外。”束景南认为前书中“冰玉皆入伪党”指庆元二年(1196)刘德秀、何澹、胡紘等沦为伪党,后书中“琐闼以论陈源”是指是年汪义端论陈源而补外,故二书皆作于庆元二年,④可信。由此可知,《韩文考异》的编撰至迟在庆元二年就已开始了。
值得重视的是下面这两通书,《与方伯谟》之二三云:
昨辱惠书,为慰。但见元兴及小儿,皆说伯谟颇觉衰悴,何为如此?今想已强健矣。更宜节适自爱,但强其志,则气自随之。些小外邪,不能为害也。熹病躯粗遣,诸证亦时往外。但亦随事损益,终是多服补药不得。令子闻已归,《韩文外集考异》曾带得归否?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写了,更得此补足,须更送去评定。庄仲为点勘,已颇详细矣。近又看《楚辞》,抄得数卷,大抵世间文字,无不错误,可叹也。
《与方伯谟》之二四云:
比想侍奉佳庆。令子程试,必甚如意,闻将以望前一日揭榜,冀闻吉语也。……《韩考》后卷如何得早检示,幸甚。熹衰病百变,支吾不暇。近又得一奇证,若寒疝者,间或腹中气刺而痛,未知竟如何,姑复任之耳。陈来和束景南都将这两通书系于庆元三年,他们的理由都是据王谱所载,《韩文考异》成书于此年。①但是如果我们不把《韩文考异》成于庆元三年当作毋需证明的前提,则二书的系年尚需重新考索。首先,书中说到的方士繇“颇觉衰悴”,朱熹也“得一奇证”。我们知道,朱熹在庆元三年没有得大病,到了次年则疾病不断。朱熹《答林井伯》之八云:“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几不能起……然明年便七十矣。”②此书作于庆元四年(1198),时朱熹年六十九岁。而方士繇也是从庆元四年秋天开始病重的,朱熹《答黄直卿》之六七云:“伯谟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间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起。”③此书作于庆元五年(1199),方即卒于是年。所以从二书中所述朱、方二人的病情来看,把二书系于庆元四年或五年比较合理。
其次,第二十三书中说到“近又看到《楚辞》”云云。虽然朱熹注释《楚辞》的工作早从庆元二年(1196)就已开始了,但他全面地整理《楚辞》却是在庆元四年以后。《答郑子上》之十七云:“病中不敢劳心看经书,闲取《楚辞》遮眼,亦便有无限合整理处。”①陈来、束景南俱系此书于庆元四年,可信。②又《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云:“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③此乃沈僴所录,时在庆元四年以后。所以《与方伯谟》之二三中所说的“近又看《楚辞》,抄得数卷”,很可能是指庆元四年以后的事。
第三,《与方伯谟》之二四问及:“令子程试,必甚如意,闻将以望前一日揭榜,冀闻吉语也。”据《文献通考》卷三二所载《宋登科记总目》,庆元年间有两个大比之年,前者在庆元二年,后者在庆元五年。据《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五,庆元五年五月(方士繇即卒于是月),“赐礼部进士曾从龙以下四百十一人及第出身”。所以《与方伯谟》之二四很可能是作于庆元五年。如果上述推论能成立的话,那么《韩文考导》就不可能成于庆元三年,而是成于庆元五年。
此外,《朱子语类》中也有一些旁证。《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载:“先生方修《韩文考异》,而学者至。因曰:‘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如《辨鹖冠子》及说列子在庄子前、及《非国语》之类,辨得皆是。’黄达才言:‘柳文较古。’曰:‘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不似韩文规模阔。学柳文也得,但会衰了人文字。’”④这段话是黄义刚所录,下面又附有夔孙所录的大意相同的一段。据《朱子语类》卷首所附姓氏,可知黄义刚录在癸丑(1193)以后,朱熹“方修《韩文考异》”,也即尚未成书。此下有好几语录都是谈韩文的,其中“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一则乃郭友仁所录,⑤时在戊午(1198),这也与上面的推论相合。
又《朱子语类》卷一三七载:“先生考订韩文公《与大颠书》”,下面记录了尧卿、义刚、安卿诸弟子与朱熹讨论《与大颠书》的问答。①这则语录乃黄义刚所录,中间夹有两处异文,皆标“淳录”。按陈淳字安卿,录在庚戌(1190)和己未(1199)两年。因黄义刚录在癸丑(1197)以后,故此则语录必在己未年。文中的“安卿”则指陈淳,“尧卿”乃李唐咨。《语类》卷一一七陈淳录云:“诸友问疾,请退。先生曰:‘尧卿、安卿且坐,相别十年,有甚大头项工夫,大头项疑难,可商量处?”②据《宋史》卷四三〇《陈淳传》,陈淳从朱熹问学共两次:“及熹来守其乡,淳请受教……后十年淳复往见熹,陈其所得,时熹已寝疾……凡三月而熹卒。”今按朱熹卒于庆元六年(1200)三月九日,则陈淳第二次问学当在庆元五年冬。因此,尧卿(李唐咨)、安卿(陈淳)同在朱熹面前讨论韩愈《与大颠书》之事也必定发生于此时,即庆元五年之冬。朱熹考订韩愈《与大颠书》,就是修《韩文考异》工作的一个部分。《朱文公文集》卷七一有《考韩文公<与大颠书>》一文,共563字,与《韩文考异》卷九《与大颠书》题下自“今按”至“则其决为韩公之文,而非他人之所能作无疑矣”一段只字不异。这就证明《韩文考异》的编撰直到庆元五年冬尚未结束,全书的定稿当然在此后,也即在朱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
综上所述,我认为《韩文考异》的编撰过程长达四年以上,直到庆元五年(1199)乃至六年才最后完成的,以往的学界认为《韩文考异》成书于庆元三年(1197)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最后考察一下《韩文考异》的编撰中朱、方二人分工的情况。
朱熹《与方伯谟》诸书中最早谈到《韩文考异》的第十五书其实就是一份编撰条例:
《韩文考异》大字以国子监版本为主,而注其同异,如云:“某本某作某。”辨其是非,如云:“今按云云。”断其取舍,从监本者已定,则云:“某本非是。”诸别本各异,则云:“皆非是。”未定,则各加“疑”字。别本者已定,则云:“当阙。”或云:“未详。”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不必辨而断也。熹不及奉书,《考异》须如此作,方有条理,幸更详之。
可见最初步的工作即校勘文字之异同是委托方士繇作的,但朱熹事先已制定了条例。第十六书、第十七书中都催促方将《考异》写成送来,至第十八书则云:“《韩考》已领。今早遣去者,更烦详阅签示。”这是朱熹审阅了方的初稿后,又送回方处修改。所谓“签示”,应是朱熹本人的意见。第十九书中说:“《韩考》所订皆甚善,比亦别修得一例,稍分明。”今检《朱文公文集》卷七四中有《修韩文举正例》一则,云:
大书本文定本。上下文无同者,即只出一字。有同字者,即并出上一字。疑似多者,即出全句。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作某,某本作某。”二字及全句,下即注首加本字,后放此。今按云云,当从某本。本同者即前云某某本,后云某某本,后放此。字有多少,即注云“某本有,某本无。”字有颠倒,即注云:“某某字,某本作某某。”今按,以下并同。
我颇怀疑这就是所谓的“别修得一例”。因为从《韩文考异》的实际情况来看,全书并没有像《与方伯谟》之十五中所云,“以国子监版本为主”,而是以方崧卿《韩集举正》为校勘底本的。所谓《修韩文举正例》,似应解作“修订《韩集举正》之条例”。而且《韩文考异》的实际行文方式(包括引原文及校勘记)基本上与上述条例是一致的。《与方伯谟》之二十云:“《韩考》已从头整顿一过,今且附去十卷,更烦为看签出疑误处。附来换下卷。但鄙意更欲俟审定所当从之正字后,却修过。以今定本为主,而注诸本之得失于下,则方本自在其间。亦不妨有所辨论,而体面正当,不见排抵显然之迹,但今未暇尔。缘其间有未定处,须更子细,为难也。”此书更清楚地显示了朱熹对《韩文考异》郑重其事的态度,他对方士繇的初稿“从头整顿一过”,且“签出疑误处”,再付方氏写定,而且对条例作了修改。至第二十二书,朱熹又提出“韩文欲并外集及《顺录》作《考异》”,并认为只有将《韩集举正》未收的《顺宗实录》等补入,才算是“员满此功德”。由此可见,方士繇参加了《韩文考异》的大部分编撰工作,功不可没。但是整部书的指导思想出于朱熹,全书体例是朱熹制定的,最后的定稿也是朱熹完成的。从上文所述的考订《与大颠书》等情况来看,书中重要问题的考辨审订也是朱熹亲自进行的。所以《韩文考异》在总体上应被视作朱熹的著作。
《韩文考异》最早是于何时刊行的?束景南说:“就在这一年(砺锋按:指庆元三年)《韩文考异》全部完成,先由他的弟子郑文振印刻于潮州,到庆元六年正月又由魏仲举二刻于建安。”①言之凿凿,然而与事实不符。首先,如上所述,《韩文考异》的完成不会早于庆元五年,所以绝不可能刊于庆元三年。今考《朱文公文集》卷四五《答廖子晦》之十五云:“《韩文考异》,袁子质、郑文振欲写本就彼刻版。恐其间颇有伪气,引惹生事,然当一面录付之。但开版事须更斟酌,若欲开版,须依此本别刊一本韩文方得,又恐枉复劳费工力耳。”陈来将此书系于庆元五年(1199),证据充足。②可见在庆元五年,朱熹对于袁、郑二人刊刻《韩文考异》的建议尚在犹豫不决,其主要的顾虑是“恐其间颇有伪气”,也即担心刻书会引来新的政治迫害。然而后来袁、郑二人还是将《韩文考异》带往潮州刊刻,但未敢署朱熹之名。《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四《答刘晦伯》云:“所喻南安韩文,久已得之,舛讹殊甚……昨为《考异》一书,专为此本发也。近日潮州取去,隐其名以镂板,异时自当见之。”但后来此书到底刻成没有,朱熹生前有没有看到刻成之书,因文献不足,现已无法断定。
其次,所谓“魏仲举二刻于建安”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魏仲举,名怀忠,曾于庆元六年刊行《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①据清人朱彝尊《跋五百家昌黎集注》云:“《昌黎集训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别集》一卷,附《论语笔解》十卷。庆元六年春,建安魏仲举刻于家塾……是书向藏长洲文伯仁家,归吾乡李太仆君实,盖宋椠之最精者。惜中间阙三卷,后人补钞。”②这部魏本韩集至清乾隆时收藏于内府,《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著录为:“《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前载《昌黎先生序传碑记》一卷、《看韩文纲目》一卷、《引用书目》一卷、《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后有《别集》一卷、《论语笔解》十卷、许渤《序》、《昌黎文集后序》五篇。”同时入藏内府的还有另一部魏本韩集,《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著录为:“《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宋魏仲举集注,前载《引用书目》一卷、《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韩文类谱》七卷。”并指出:“《正集》目录后有木记曰:‘庆元六禩孟春建安魏仲举刻梓于家塾。”由此可见,魏仲举在庆元六年曾刊刻韩集是可信的,但此部韩集中根本不包括《韩文考异》。
可是后人却将魏本韩集与《韩文考异》混为一谈了。清末丁丙善本书室中收藏了一部魏本韩集,著录为“《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附《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昌黎先生序记碑铭》一卷、《韩文类谱》十卷。”①并将此书定为宋庆元刊本。与此同时,丁丙还收藏有一部《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十卷,他因为两部书都钤有祁氏澹生堂、朱彝尊和惠栋的藏书印,就遽然断定两书必是同时所刻,所以在《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四中著录《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说:“此魏仲举与《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同时刊本。”可是丁丙的这个判断根据是不足的,因为他所收藏的魏本韩集与《韩文考异》分明是两部互相独立的书,虽然它们曾经同一批藏书家之手,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乃同时所刻。据商务印书馆1912年的影印本来看,这两部书首先是在惠栋手中合在一起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中有三册是补钞的,每册首叶都钤有“惠栋之印”、“定宇”二印。而《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的首二卷也是补钞的,字迹与前书所补系出一手,而且首叶也钤有同样的二印。这说明当时惠栋曾以同样的方式钞补二书,可能即视它们为同一书的两个部分。丁丙收得二书后,也把它们装于一函。二书卷末都有光绪二十二年王棻的跋,后跋中云:“松生先生以此书与《五百家注》共装一匣,间以示余。”又云:“其书当与《五百家注》同时所刊。”丁丙著录这本《韩文考异》为魏仲举刊本,当即承王棻之误。其实连丁丙所藏的魏本韩集是否宋庆元刊本,都很可疑。因为《天禄琳琅书目》著录有两本魏本韩集,其一有“庆元六禩”云云的木记,另一本有明代文氏“玉兰堂”的藏书印,而丁丙的藏本既无此木记,也不见此印,所以根本没有根据说它就是朱彝尊和《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之本。而且丁丙藏本卷首的《诸儒名氏》中有“新安朱氏,名熹,字元晦,议论见《韩文考异》、《晦庵文集》。”可是细检注文,却不见朱熹之语。即使如《外集》卷二《召大颠和尚书》,注文也仅引及韩醇等人,一字未及《韩文考异》对此文的详细考订。可证此书根本没有包括《韩文考异》,《诸儒名氏》所云,或为后代翻刻时增入。而且从影印本来看,丁丙所藏的魏本韩集和《韩文考异》的版式、行格完全不同,揆诸情理,也不可能是出于一人之手的“同时刊本”。①自从1912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将丁丙所藏的上述二书影印合并为一书以后,它们就流传较广了。②商务印书馆的卷末有孙毓修跋云:“此宋刻《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据《曝书亭集》及《天禄琳琅志》,则宋庆元六年建安魏仲安刊本也。……《考异》犹是朱子原本,未为王伯大所乱,更是罕见秘籍。”于是《韩文考异》曾由魏仲举在庆元六年刊行的说法就广为人知了。究其原委,这实在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宋本《昌黎先生集考异》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涵芬楼影印的底本,是庆元六年以后的翻刻本,而《考异》则更是后来翻刻时补配在一起的。”甚确。其实以情理揆之,魏仲举在庆元六年刊行《韩文考异》且题作《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党禁正严,就在前一年的十二月,韩侂胄的党羽还气势汹汹地上疏要求对“伪党”继续进行打击:“其长恶弗悛者,必重置典宪,投之荒远。”③当庆元六年三月朱熹去世后,还有人上疏要求对朱门弟子的会葬严加防范,以致于“门生故旧不敢送葬”。④魏仲举何人也,竟能在如此严酷阴森的政治气候下公然刊刻《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
从现存材料来看,《韩文考异》的版本有两个系统,现简述如下:
第一个系统是王伯大刊本,刊刻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商务印书馆1926年影印元刊本《朱文公校韩昌黎先生集》卷首有王伯大的序言,即署为宝庆三年。关于王本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言之甚详:“伯大以朱子《韩文考异》于本集之外别为卷帙,不便寻览,乃重为编次。离析《考异》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刻于南剑州。又采洪兴祖《年谱辨证》、樊汝霖《年谱注》、孙汝听《解》、韩醇《解》、祝充《解》,为之音释,附于各篇之末。厥后麻沙书坊以注释缀于篇末,仍不便检阅,亦取而散诸句下。盖王伯大改朱子之本,实一误且再误也。”①王本虽然改变了朱熹原本的形式而且多误,但它便于阅读,所以历代翻刻不绝,流传极广。
第二个系统是张洽刊本,初刊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与王本不同,张洽本是完全遵照朱熹的原本刊刻的,虽然张洽在跋中自称“间有愚见一二,亦各系卷末。”但通检全书,其实只有三则,分别附于卷一、卷四、卷七之末。张洽本在后代流传不广,明正统间曾有翻刻,但传本也甚罕见。清康熙年间,编修《朱子全书》的理学名臣李光地曾翻刻此书,后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有著录,题作《原本韩文考异》。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山西祁县图书馆所藏张洽本影印出版,此本曾经毛晋、季振宜等著名藏书家之手,除卷七末四页系钞配外,居然宋刻全帙,弥足珍贵。本书征引《韩文考异》,皆依此本。
王伯大本和张洽本都初刻于宋理宗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身败名裂后,党禁即渐告解弛。宁宗嘉定二年(1209),朱熹被赐谥曰“文”。嘉定五年(1212),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被立于国学。至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朱熹被追赠太师,封信国公。《韩文考异》在此时刊行问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一)《诗集传》
朱熹对于《诗经》用力最勤,《诗集传》便是他研究《诗经》的成果之结晶。但是关于此书的成书时间,却历来说法不一。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三系此书于淳熙四年(1177),是年朱熹四十八岁,今人多从此说。③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今本《诗集传》卷首的《序》署曰“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但是其实朱熹的孙子朱鉴在《诗传遗说》卷二中早已指出这篇序不是为《诗集传》而作:“《诗传》旧序,此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经时所作,后乃尽去《小序》。”清人《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此序写于《诗集传》成书之前:“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无一语斥《小序》,盖犹初稿。序末称‘时方辑诗传’,是其证也。”①今揆此序语意,确实尚无显斥《小序》之处,可见它原来并不是为尽去《小序》的《诗集传》而作,当然不能据它来确定《诗集传》的成书年代。
此外,近人吴其昌在《朱子著述考》中认为《诗集传》成书于淳熙四年(1177)之后,淳熙七年(1180)之前,然未有确证。②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则说“《诗集传》在丁酉亦尚未动稿”,又说“乙未前,《诗集传》似已大体成书”。③今按丁酉是淳熙四年(1177),乙未是淳熙二年(1175),钱氏所言分明是自相龃龉。
事实上朱熹治《诗》是一件旷日持久的工作,《诗集传》的撰写大约始于淳熙四年,而其修订则一直持续到庆元五年(1199),即朱熹去世前的一年。④
朱熹早年说《诗》,基本上遵从《小序》之说,当时也曾成书,此书朱熹称之为《集解》,⑤或称《诗解》。⑥原书已佚,但在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中保存了若干片断,束景南据之辑成《诗集解辑存》。⑦关于这部《诗解》,吴其昌认为与《诗集传》是两部书,⑧钱穆则认为是《诗集传》的初稿。⑨我们认为两种说法不妨并存,因为第一,两书都曾单独刊行,主要的观点又不同,当然可以看作两部著作。第二,两书异中有同,我们以《郑风》为例,把《吕氏家塾读诗记》中所引的《诗解》与《诗集传》进行对比,发现前者对《将仲子》、《狡童》、《褰裳》、《风雨》等篇的解释是遵从《小序》的,没有像后者那样称之为“淫奔者之诗”。但是关于《野有蔓草》、《溱洧》两篇,前者的解释基本上包括在《诗集传》中,文字上仅有一二字之差异。由此可见,《诗集传》对《诗解》作了相当大的改动,但也有所保留,所以可以把《诗解》视为《诗集传》的基础或初稿。
毫无疑问,《诗集传》代表着朱熹的晚年定论,我们应该根据它而不是《诗解》来评判朱熹的《诗经》学。但是,朱熹在《诗集传》中的体现的重要文学思想,即不盲从汉儒注疏而直接依据《诗经》的文本来体会其旨意的观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朱熹曾对门人说:“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①对这段话,王懋竑认为“其为记者之误无疑也。”②钱穆也认为“所云‘后到三十岁’,恐是‘五十岁’之误。否则是二十岁后又三十岁,在朱子五十岁左右,始断然知《小序》之出汉儒。”③的确,说朱熹三十岁时便已断然不信《小序》,是有些不太准确。但是他那时已经对《小序》产生怀疑,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朱熹还说过一些类似的话,不会都是出于门人误记,例如:“郑渔仲《诗辨》:‘《将仲子》只是淫奔之诗,非刺仲子之诗也。’某自幼便知其说之是。”④又如:“熹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荡旧说,诗意方活。”⑤前一则告诉我们,朱熹疑《小序》并非是毫无来由忽生圣解,而是受到了其他宋儒的启发。郑樵比朱熹年长二十六岁,他在《诗辨妄》中已经指出《诗序》是汉人所作,而且是“村野妄人所作”,朱熹自幼便已读到《诗辨妄》,当然有助于疑序观点的形成。①后一则告诉我们,朱熹作《诗解》时虽然尚未弃去《小序》,但心中早已多有怀疑,不过是“曲为之说”而已。所以朱熹晚年回忆自己青年时代便已疑《序》,是与事实并不矛盾的。
那么,既然朱熹早年已经怀疑《小序》,为什么在《诗解》中又并不斥责《小序》呢?原来朱熹治学十分谨慎,虽然善于怀疑,但未经深思熟虑是不肯轻易创立新说的。从上面所引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他从怀疑《小序》到公然抛弃《小序》,是经历了一个颇长的过程的。在淳熙四年(1177),朱熹虽然早已对《小序》有所怀疑,但尚未形诸文字。淳熙四年他为《诗解》作序,也还没有明言《小序》之非。但次年也即淳熙五年(1178),他写信给吕祖谦说:“大抵《小序》尽出后人臆度,若不脱此窠臼,终无缘得正当也。去年略修旧说,订正为多,尚恨未能尽去,得失相半,不成完书耳。”②可见他已公开声明废弃《小序》,并准备以此为指导思想改写《诗解》。其后朱熹又多次与吕祖谦书信往来,争辩《小序》之是非。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卒。次年,朱熹作《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深为感慨地说:“此书所谓朱氏者,实熹少时浅陋之说,而伯恭父误有取焉。其后历时既久,自知其说有所未安,如‘雅郑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则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熹窃惑之。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矣。”③由此可知,朱熹对于废弃《小序》的态度十分认真,他决心要把《小序》的是非弄个水落石出。甚至在他反复修改后终于定稿的、以废弃《小序》为说诗主旨的《诗集传》于淳熙十四年(1187)付梓之后,他仍然不停地对之进行修订。淳熙十六年(1189),年已六十的朱熹写信对蔡季通说:“《诗传》中欲改数行,乃马庄父来说,当时看得不仔细,只见一字不同,便为此说。今详看乃知误也,幸付匠者正之。”①同年他又写信给吴伯丰说:“《诗传》中有音未备者,有训未备者,有以经统传、舛其次者,此类皆失之不详,今当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减矣。不免别作《补脱》一卷,附之《辨说》之后。……其例如后……”②他在此信中所说到的应予补订之处,有的在今本《诗集传》中没有照改,例如《周南·樛木》篇,此信中指出:“乐只音止二字,合附本字下。”今本《诗集传》未从。但也有几处已经改正,例如《鄘风·载驰》篇,此信中指出:“‘无以我为有过,虽尔’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下。”今本《诗集传》已据之改正。可见朱熹对于《诗集传》一书确是倾注了一番心血的,他早年怀疑《小序》,经长时间的酝酿、修订,终于写成尽废《小序》的《诗集传》,付梓后还继续修补,力求精益求精。所以到了暮年,朱熹对《诗集传》“自以为无复遗恨,曰:‘后世若有扬子云,必好之矣!’”③
《诗集传》于淳熙十四年(1187)首次刊行后,在朱熹生前又曾数次翻刻,据朱鉴《诗传遗说后跋》所记,当时计有建安本、豫章本、长沙本、后山本、江西本等几种刊本,但大多没有留存至今。现在的通行本《诗集传》二十卷是从曾经朱鉴藏过的后山本而出,当即朱熹的晚年定本。另有八卷本乃后代坊刻所并,不足据。
(二)《楚辞集注》
朱熹自幼喜爱《楚辞》,但与《诗集传》的编写不同,他关于《楚辞》的著作却是到晚年才动笔的。关于《楚辞集注》的成书年代,南宋的赵希弁说:“公之加意此书,则作牧于楚之后也。或曰:有感于赵忠定之变而然。”①周密《齐东野语》卷三“绍熙内禅”条也认为此书是朱熹因赵汝愚被谪并暴卒一事而作。今按朱熹“作牧于楚”事在绍熙五年(1194),②而赵汝愚贬永州事在庆元元年(1195),赵暴卒于衡阳道中事在庆元二年(1196),故赵希弁、周密所言意即《楚辞集注》作于庆元二年以后。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下则将《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楚辞辨证》一起系于庆元五年(1199)。今考《楚辞集注》一书未题编写年月,唯朱熹门人杨楫尝跋此书曰:“庆元乙卯,楫侍先生于考亭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永。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③此跋中“乙卯”是指庆元元年(1195),杨楫于此年初来考亭。而杨楫得见朱熹出示“所释《楚辞》一篇”则是在其后,也即赵汝愚“谪死于永”的丙辰(庆元二年)或更后。赵汝愚其人虽然并非朱熹心目中的大贤,但他与朱熹一起受到韩侂胄的打击,且同被目为“伪党”。赵以宋宗室的身份被贬谪到湖南的永州,情形类似于屈原之流放沅湘。庆元元年冬,朱熹仿屈原《橘颂》作《梅花赋》,赋末乱辞云:“王孙兮归来,无使哀江南兮。”①即针对赵汝愚被贬一事而言。而当赵汝愚因遭韩侂胄的爪牙窘辱而暴卒后,太学生敖陶孙即哭之曰:“狼胡无地归姬旦,鱼腹终天痛屈原!”②所以朱熹在庆元年间动手注释《楚辞》,确有深意存焉。他在《楚辞集注》的序中说:“(旧注)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予于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櫽括,定为《集注》八卷。庶几读者得以见古人于千载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载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于后者之不闻也。呜呼悕矣,是岂易与俗人言哉!”这种抑塞历落、慨乎言之的语气,确实与他当时的悲愤心情相吻合。
杨楫在庆元二年看到的“所释《楚辞》一篇”,当是《楚辞集注》的一部分。其后,朱熹注释《楚辞》的工作陆续进行。庆元三年(1197),朱熹写信给方士繇说:“近又看《楚辞》,抄得数卷。大抵世间文字,无不错误,可叹也!”③庆元四年(1198),他又写信给郑子上说:“病中不敢劳心看经书,闲取《楚辞》遮眼,亦便有无限合整理处,但恐犯忌,不敢形纸墨耳。”④此期内朱熹还常与门人谈论《楚辞》,例如谈到《天问》中“启棘宾商”一句说:“某以为‘棘’字是‘梦’字,‘商’字是古文篆‘天’字。”⑤又说:“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①今考前一则为林夔孙所记,乃庆元三年(1197)后所闻,而今本《楚辞集注》卷三中对该句也注曰:“窃疑‘棘’当作‘梦’,‘商’当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误也。”与林生所录者非常接近。后一则为沈僴所记,乃庆元四年(1198)后所闻,语意也与《楚辞集注》序意相合。由此可见朱熹在庆元三、四年间一直在从事《楚辞集注》的撰写。到了庆元五年(1199)三月,朱熹在《楚辞辨证》的题记中说:“余既集王、洪《骚》注,顾其训故文义之外,犹有不可不知者,然虑文字之太繁,览者或没溺而失其要也。别记于后,以备参考。”揆其语意,此时《楚辞集注》已经完成。综上所述,《楚辞集注》成书当在庆元四年或庆元五年初。
在完成《楚辞集注》与《楚辞辨证》以后,朱熹整理《楚辞》的工作仍在继续:第一,他动手编写《楚辞后语》,对晁补之的《续楚辞》、《变离骚》二书所录的作品进行增删,此书在他生前未及完稿,朱熹之子朱在跋此书说:“先君晚岁草定此编,盖本诸晁氏《续》、《变》二书,其去取之义精矣。然未尝以示人也。每章之首,皆略叙其述作之由,而因以著其是非得失之迹。独《思玄》、《悲愤》及《复志赋》以下,至于《幽怀》,则仅存其目,而未及有所论述。”直到嘉定五年(1212),也即朱熹去世十二年后,才由朱在将此书遗稿整理誊写,并于嘉定十年(1217)与《楚辞集注》一并刊行。第二,朱熹又动手编撰《楚辞音考》。庆元五年(1199),朱熹写信给巩仲至说:“《楚辞》板既漫灭,虽修得亦不济事。然欲重刊,又不可整理。使其可以就加雠校,若修得了,可就彼中先校一番,却以一净本见示。当为参订、改定、商量。若别刊得一本,亦佳事也。近得古田一士人所著《补音》一卷,亦甚有功,异时当并以奉寄也。”②庆元六年(1200),也即朱熹去世的那年,他又写信给巩仲至说:“《楚辞》修未?旋了旋寄数板,节次发来为幸。古田《补音》,此间无人写得,今寄一书与苏君,幸能托县官,差人赍去乡下寻之,就其传录尤便。亦闻渠写本颇经删节,已嘱令为全录去矣。然此尝编得《音考》一卷,‘音’谓集古今正音、协韵,通而为一。‘考’谓考诸本同异,并附其间。只欲别为一卷,附之书后,不必搀入正文之下,碍人眼目,妨人吟讽。但亦未甚详密,正文有异同,但择一稳者为定可也。”①此书作于庆元六年春,是年三月九日朱熹逝世,可见《楚辞音考》一书在他生前未及完成。
前文提到的朱熹易箦之前尚“修《楚辞》一段”,现已无法断定是指《楚辞后语》还是《楚辞音考》,但可以肯定他临终之前仍在从事关于《楚辞》的著作。
对于朱熹在垂暮之际孜孜不倦地从事《楚辞》研究一事,他的一些门人颇为不解。杨楫在《楚辞集注》的跋中说:“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楫辈亦不敢窃而请焉。”②的确,如果纯从理学的角度来看,像朱熹那样的理学宗师何必要耗费心力在《楚辞》上呢?然而事实上朱熹对文学的态度是与二程等人相去甚远的,他在晚年动手注释《楚辞》,固然有如上所述的受赵汝愚贬死一事的激发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一向喜好《楚辞》,他对屈原的忠君爱国之心有强烈的共鸣,他对《楚辞》的精彩绝艳也极为倾倒。朱熹注释《楚辞》始于庆元二年(1196),但他对《楚辞》的研究早就开始了。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书楚辞协韵后》中说:“始予得黄叔垕父所定《楚辞协韵》而爱之,以寄漳守傅景仁,景仁为刻板,置公帑。未几予来代景仁,……于是即其板本,复刊正之,使览者无疑也。”①又作《再跋楚辞协韵》说:“《楚辞协韵》九章,所谓‘将寓未详’者,当时黄君盖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读之,故于此不得其说而阙焉。近见閤皁道士甘梦叔说,‘寓’乃‘当’字之误,因亟考之,则黄长睿、洪庆善本果皆作‘当’。……以文义音韵言之,二家之本为是。”②同年他还写信给吴斗南说:“《楚辞协韵》一本纳上,其间尚多谬误,幸略为订之。复以见喻,尚可修改也。”③可见朱熹早就对《楚辞》研究十分留意,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一气呵成《楚辞集注》等一系列著作,正是长期研究、厚积薄发的结果。
《楚辞集注》在朱熹生前未及刊行,现存最早的本子刊于嘉定六年(1213),《楚辞辨证》附录于后。《楚辞后语》六卷则于嘉定十年(1217)由朱在刊刻单行本,今已失传。端平二年(1235),朱鉴始把《楚辞集注》、《楚辞辨证》和《楚辞后语》合刻成一书,并把《楚辞集注》和《楚辞后语》中重复的三篇删去,成为《楚辞集注》的定本。这个本子一直流传至今,曾经山东聊城海源阁收藏,现藏于北京图书馆。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将此本影印出版,成为今日的通行本。由于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宋刊本均已不存,晁补之的《续楚辞》、《变离骚》更是已经失传,所以宋端平本《楚辞集注》已成为今日尚存的最古老、最完整的《楚辞》刻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朱熹地下有知,对此当感欣慰!
(三)《韩文考异》
对于宋人来说,韩愈具有两方面的先导意义。一方面,他是一位以弘扬儒道、排斥异端为己任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他是一位倡导古文、反对骈俪之风的文学家。所以北宋的理学家和古文家对韩愈其人都相当重视,不过重视的角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宋代理学家中文学素养最高的人,他对韩愈的态度也就格外的复杂。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有褒有贬,总的说来则是贬多于褒。朱熹认为韩愈虽然弘扬儒道,但是“只于治国平天下处用功,而未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①又认为韩愈“于道见其大体规模极分明,但未能究其所从来。而体察操履处,皆不细密。”②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也是有褒有贬,但总的说来是赞扬多于讥评。虽然朱熹不满于韩愈的重视文学更甚于儒道:“韩文公第一义是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③“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④然而朱熹对韩文自身是极为赞赏的,他自称:“余少时喜读韩文。”⑤他晚年聚徒讲学时,仍不时对弟子赞扬韩文:“退之文字尽好,末年尤好。”⑥甚至指点弟子学好古文的途径是:“看得韩文熟!”⑦正由于朱熹对韩文持有很高的评价,他才会在晚年耗费心血撰成《韩文考异》一书。
从表面上看,朱熹《韩文考异》是针对方崧卿《韩集举正》而作的。方崧卿(1135—1194),字季申,福建莆田人。其《韩集举正》成书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三年之后,朱熹作《跋方季申所校韩文》,指出方书未能尽善。更数年而《韩文考异》成。但事实上朱熹早就有校勘韩文之念了。他在《跋方季申所校韩文》中说:“余自少喜读韩文,常病世无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广流布,而未暇也。”可见他是因为无暇才迟迟没有动手,但这件事是时时在他心头的。上引跋文中还说到了他注意韩文的一个事例:
又季申所谓谢本,则绍兴甲戌、乙亥之间,余官温陵,谢公弟如晦之子景莫为舶司属官,尝于其几间见之。盖用天台印本,剪裂粘缀,依陈后山本别为次序,而卷首款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读其《送陈秀才序》一篇,“则何不信之有”句内辄用丹笔围去“不”字。初甚骇之,再加寻绎,乃知必去此字,然后一篇首尾始复贯通。盖传袭之误久矣,读者虽亦微觉其硋而未暇深究也。常窃识之,以验他本,皆不其然。此本虽精,亦复不见。岂季申读时,便文纵口,尚不免小有遗脱,将所见者非其真本,先传校者已失此字也耶?(《文集》卷八三,第4页)
钱穆对此极为注意,并据此而认为“朱子为《韩文考异》,其发心积意,远自四十年以前,亦岂一旦乘兴之所能遽成乎?”①从绍兴甲戌(1154)到《韩文考异》成书的庆元年间,确有四十多年的时间跨度。然而朱熹对韩文产生兴趣其实还在绍兴甲戌之前。因为《韩文考异》卷六《送陈秀才彤》下云:“旧读此序,尝怪‘则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断绝,不相承应,每窃疑之。后见谢氏手校真本……”可见朱熹对韩文的“发兴积意”早在见到谢本之前就已开始了。绍兴甲戌那年朱熹二十五岁,也即朱熹对韩文的兴趣始于青年时代,这与他自称“自少喜读韩文”是互相印证的。
《韩文考异》成书于何年?清人王懋竑纂订《朱子年谱》卷四下系之于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是年朱熹六十八岁。近代学者对此均无异词,如牛继昌《朱熹著述分类考略》、①金云铭《朱子著述考》、②钱穆《朱子新学案》、束景南《朱子大传》都持此说。然而王谱的系年其实是根据不足的,因为朱熹文集中涉及《韩文考异》的文章如《韩文考异序》、《书韩文考异前》及《修韩文举正例》③都没有署年月,而今存各本《韩文考异》也大多未署年月,④王谱不过是沿袭旧谱之说而已。所以王懋竑又在《朱子年谱考异》卷四中说:“或《考异》之成在戊午。”戊午即庆元四年(1198)。我认为王懋竑的两种说法都欠准确,现论证如下:
方崧卿《韩集举正》成书于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见到方书后感到不满意,并曾与方商榷。《韩文考异》卷六中据谢本删去《送陈秀才彤》内一字,且云:“方据谢本为多,而亦独遗此字,岂亦未尝见其真本邪?尝以告之,又不见信。故今特删‘不’字,而复详著其说云。”可见朱熹曾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方崧卿,冀其修改,后来才决定另作《考异》。
朱熹晚年著书大多有弟子充当助手,帮助他编撰《韩文考异》的重要助手是方士繇。方士繇(1148—1199),一名伯休,字伯谟,莆田人。他二十多岁即往建安师从朱熹,后徙家至崇安籍溪,遂废举业,专心讲学,并时时往朱熹处问学。陆游说方在朱门“称高弟”,⑤但由于方颇能独立思考,不像其他朱门弟子那样把朱熹的每一句话都奉为金科玉律。比如他曾劝朱熹少著书,①且以朱熹教人读《四书集注》为不然。②朱熹则认为方治学不纯,曾在方去世后说他:“未去时亦安静明了,但可惜后来一向废学,身后但有诗数篇耳。”③也许正是由于方士繇较喜文学,朱熹才把协助编撰《韩文考异》的重任托付给他。《朱文公文集》卷四四中保存了他写给方的书信二十四通,其中有九通谈及《韩文考异》。据此我们不但可以明白方士繇助编《韩文考异》的过程,而且可以推测成书的时间。《与方伯谟》之十七云:“《韩考》烦早为并手写来,便付此人。尤幸。闻冰玉皆入伪党,为之奈何!”《与方伯谟》之十八云:“《韩考》已领。今早遣去者,更烦详阅签示。适有人自三衢来,云琐闼以论陈源故,补外。”束景南认为前书中“冰玉皆入伪党”指庆元二年(1196)刘德秀、何澹、胡紘等沦为伪党,后书中“琐闼以论陈源”是指是年汪义端论陈源而补外,故二书皆作于庆元二年,④可信。由此可知,《韩文考异》的编撰至迟在庆元二年就已开始了。
值得重视的是下面这两通书,《与方伯谟》之二三云:
昨辱惠书,为慰。但见元兴及小儿,皆说伯谟颇觉衰悴,何为如此?今想已强健矣。更宜节适自爱,但强其志,则气自随之。些小外邪,不能为害也。熹病躯粗遣,诸证亦时往外。但亦随事损益,终是多服补药不得。令子闻已归,《韩文外集考异》曾带得归否?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写了,更得此补足,须更送去评定。庄仲为点勘,已颇详细矣。近又看《楚辞》,抄得数卷,大抵世间文字,无不错误,可叹也。
《与方伯谟》之二四云:
比想侍奉佳庆。令子程试,必甚如意,闻将以望前一日揭榜,冀闻吉语也。……《韩考》后卷如何得早检示,幸甚。熹衰病百变,支吾不暇。近又得一奇证,若寒疝者,间或腹中气刺而痛,未知竟如何,姑复任之耳。陈来和束景南都将这两通书系于庆元三年,他们的理由都是据王谱所载,《韩文考异》成书于此年。①但是如果我们不把《韩文考异》成于庆元三年当作毋需证明的前提,则二书的系年尚需重新考索。首先,书中说到的方士繇“颇觉衰悴”,朱熹也“得一奇证”。我们知道,朱熹在庆元三年没有得大病,到了次年则疾病不断。朱熹《答林井伯》之八云:“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几不能起……然明年便七十矣。”②此书作于庆元四年(1198),时朱熹年六十九岁。而方士繇也是从庆元四年秋天开始病重的,朱熹《答黄直卿》之六七云:“伯谟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间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起。”③此书作于庆元五年(1199),方即卒于是年。所以从二书中所述朱、方二人的病情来看,把二书系于庆元四年或五年比较合理。
其次,第二十三书中说到“近又看到《楚辞》”云云。虽然朱熹注释《楚辞》的工作早从庆元二年(1196)就已开始了,但他全面地整理《楚辞》却是在庆元四年以后。《答郑子上》之十七云:“病中不敢劳心看经书,闲取《楚辞》遮眼,亦便有无限合整理处。”①陈来、束景南俱系此书于庆元四年,可信。②又《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云:“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③此乃沈僴所录,时在庆元四年以后。所以《与方伯谟》之二三中所说的“近又看《楚辞》,抄得数卷”,很可能是指庆元四年以后的事。
第三,《与方伯谟》之二四问及:“令子程试,必甚如意,闻将以望前一日揭榜,冀闻吉语也。”据《文献通考》卷三二所载《宋登科记总目》,庆元年间有两个大比之年,前者在庆元二年,后者在庆元五年。据《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五,庆元五年五月(方士繇即卒于是月),“赐礼部进士曾从龙以下四百十一人及第出身”。所以《与方伯谟》之二四很可能是作于庆元五年。如果上述推论能成立的话,那么《韩文考导》就不可能成于庆元三年,而是成于庆元五年。
此外,《朱子语类》中也有一些旁证。《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载:“先生方修《韩文考异》,而学者至。因曰:‘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如《辨鹖冠子》及说列子在庄子前、及《非国语》之类,辨得皆是。’黄达才言:‘柳文较古。’曰:‘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不似韩文规模阔。学柳文也得,但会衰了人文字。’”④这段话是黄义刚所录,下面又附有夔孙所录的大意相同的一段。据《朱子语类》卷首所附姓氏,可知黄义刚录在癸丑(1193)以后,朱熹“方修《韩文考异》”,也即尚未成书。此下有好几语录都是谈韩文的,其中“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一则乃郭友仁所录,⑤时在戊午(1198),这也与上面的推论相合。
又《朱子语类》卷一三七载:“先生考订韩文公《与大颠书》”,下面记录了尧卿、义刚、安卿诸弟子与朱熹讨论《与大颠书》的问答。①这则语录乃黄义刚所录,中间夹有两处异文,皆标“淳录”。按陈淳字安卿,录在庚戌(1190)和己未(1199)两年。因黄义刚录在癸丑(1197)以后,故此则语录必在己未年。文中的“安卿”则指陈淳,“尧卿”乃李唐咨。《语类》卷一一七陈淳录云:“诸友问疾,请退。先生曰:‘尧卿、安卿且坐,相别十年,有甚大头项工夫,大头项疑难,可商量处?”②据《宋史》卷四三〇《陈淳传》,陈淳从朱熹问学共两次:“及熹来守其乡,淳请受教……后十年淳复往见熹,陈其所得,时熹已寝疾……凡三月而熹卒。”今按朱熹卒于庆元六年(1200)三月九日,则陈淳第二次问学当在庆元五年冬。因此,尧卿(李唐咨)、安卿(陈淳)同在朱熹面前讨论韩愈《与大颠书》之事也必定发生于此时,即庆元五年之冬。朱熹考订韩愈《与大颠书》,就是修《韩文考异》工作的一个部分。《朱文公文集》卷七一有《考韩文公<与大颠书>》一文,共563字,与《韩文考异》卷九《与大颠书》题下自“今按”至“则其决为韩公之文,而非他人之所能作无疑矣”一段只字不异。这就证明《韩文考异》的编撰直到庆元五年冬尚未结束,全书的定稿当然在此后,也即在朱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
综上所述,我认为《韩文考异》的编撰过程长达四年以上,直到庆元五年(1199)乃至六年才最后完成的,以往的学界认为《韩文考异》成书于庆元三年(1197)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最后考察一下《韩文考异》的编撰中朱、方二人分工的情况。
朱熹《与方伯谟》诸书中最早谈到《韩文考异》的第十五书其实就是一份编撰条例:
《韩文考异》大字以国子监版本为主,而注其同异,如云:“某本某作某。”辨其是非,如云:“今按云云。”断其取舍,从监本者已定,则云:“某本非是。”诸别本各异,则云:“皆非是。”未定,则各加“疑”字。别本者已定,则云:“当阙。”或云:“未详。”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不必辨而断也。熹不及奉书,《考异》须如此作,方有条理,幸更详之。
可见最初步的工作即校勘文字之异同是委托方士繇作的,但朱熹事先已制定了条例。第十六书、第十七书中都催促方将《考异》写成送来,至第十八书则云:“《韩考》已领。今早遣去者,更烦详阅签示。”这是朱熹审阅了方的初稿后,又送回方处修改。所谓“签示”,应是朱熹本人的意见。第十九书中说:“《韩考》所订皆甚善,比亦别修得一例,稍分明。”今检《朱文公文集》卷七四中有《修韩文举正例》一则,云:
大书本文定本。上下文无同者,即只出一字。有同字者,即并出上一字。疑似多者,即出全句。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作某,某本作某。”二字及全句,下即注首加本字,后放此。今按云云,当从某本。本同者即前云某某本,后云某某本,后放此。字有多少,即注云“某本有,某本无。”字有颠倒,即注云:“某某字,某本作某某。”今按,以下并同。
我颇怀疑这就是所谓的“别修得一例”。因为从《韩文考异》的实际情况来看,全书并没有像《与方伯谟》之十五中所云,“以国子监版本为主”,而是以方崧卿《韩集举正》为校勘底本的。所谓《修韩文举正例》,似应解作“修订《韩集举正》之条例”。而且《韩文考异》的实际行文方式(包括引原文及校勘记)基本上与上述条例是一致的。《与方伯谟》之二十云:“《韩考》已从头整顿一过,今且附去十卷,更烦为看签出疑误处。附来换下卷。但鄙意更欲俟审定所当从之正字后,却修过。以今定本为主,而注诸本之得失于下,则方本自在其间。亦不妨有所辨论,而体面正当,不见排抵显然之迹,但今未暇尔。缘其间有未定处,须更子细,为难也。”此书更清楚地显示了朱熹对《韩文考异》郑重其事的态度,他对方士繇的初稿“从头整顿一过”,且“签出疑误处”,再付方氏写定,而且对条例作了修改。至第二十二书,朱熹又提出“韩文欲并外集及《顺录》作《考异》”,并认为只有将《韩集举正》未收的《顺宗实录》等补入,才算是“员满此功德”。由此可见,方士繇参加了《韩文考异》的大部分编撰工作,功不可没。但是整部书的指导思想出于朱熹,全书体例是朱熹制定的,最后的定稿也是朱熹完成的。从上文所述的考订《与大颠书》等情况来看,书中重要问题的考辨审订也是朱熹亲自进行的。所以《韩文考异》在总体上应被视作朱熹的著作。
《韩文考异》最早是于何时刊行的?束景南说:“就在这一年(砺锋按:指庆元三年)《韩文考异》全部完成,先由他的弟子郑文振印刻于潮州,到庆元六年正月又由魏仲举二刻于建安。”①言之凿凿,然而与事实不符。首先,如上所述,《韩文考异》的完成不会早于庆元五年,所以绝不可能刊于庆元三年。今考《朱文公文集》卷四五《答廖子晦》之十五云:“《韩文考异》,袁子质、郑文振欲写本就彼刻版。恐其间颇有伪气,引惹生事,然当一面录付之。但开版事须更斟酌,若欲开版,须依此本别刊一本韩文方得,又恐枉复劳费工力耳。”陈来将此书系于庆元五年(1199),证据充足。②可见在庆元五年,朱熹对于袁、郑二人刊刻《韩文考异》的建议尚在犹豫不决,其主要的顾虑是“恐其间颇有伪气”,也即担心刻书会引来新的政治迫害。然而后来袁、郑二人还是将《韩文考异》带往潮州刊刻,但未敢署朱熹之名。《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四《答刘晦伯》云:“所喻南安韩文,久已得之,舛讹殊甚……昨为《考异》一书,专为此本发也。近日潮州取去,隐其名以镂板,异时自当见之。”但后来此书到底刻成没有,朱熹生前有没有看到刻成之书,因文献不足,现已无法断定。
其次,所谓“魏仲举二刻于建安”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魏仲举,名怀忠,曾于庆元六年刊行《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①据清人朱彝尊《跋五百家昌黎集注》云:“《昌黎集训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别集》一卷,附《论语笔解》十卷。庆元六年春,建安魏仲举刻于家塾……是书向藏长洲文伯仁家,归吾乡李太仆君实,盖宋椠之最精者。惜中间阙三卷,后人补钞。”②这部魏本韩集至清乾隆时收藏于内府,《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著录为:“《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前载《昌黎先生序传碑记》一卷、《看韩文纲目》一卷、《引用书目》一卷、《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后有《别集》一卷、《论语笔解》十卷、许渤《序》、《昌黎文集后序》五篇。”同时入藏内府的还有另一部魏本韩集,《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著录为:“《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宋魏仲举集注,前载《引用书目》一卷、《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韩文类谱》七卷。”并指出:“《正集》目录后有木记曰:‘庆元六禩孟春建安魏仲举刻梓于家塾。”由此可见,魏仲举在庆元六年曾刊刻韩集是可信的,但此部韩集中根本不包括《韩文考异》。
可是后人却将魏本韩集与《韩文考异》混为一谈了。清末丁丙善本书室中收藏了一部魏本韩集,著录为“《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附《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昌黎先生序记碑铭》一卷、《韩文类谱》十卷。”①并将此书定为宋庆元刊本。与此同时,丁丙还收藏有一部《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十卷,他因为两部书都钤有祁氏澹生堂、朱彝尊和惠栋的藏书印,就遽然断定两书必是同时所刻,所以在《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四中著录《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说:“此魏仲举与《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同时刊本。”可是丁丙的这个判断根据是不足的,因为他所收藏的魏本韩集与《韩文考异》分明是两部互相独立的书,虽然它们曾经同一批藏书家之手,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乃同时所刻。据商务印书馆1912年的影印本来看,这两部书首先是在惠栋手中合在一起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中有三册是补钞的,每册首叶都钤有“惠栋之印”、“定宇”二印。而《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的首二卷也是补钞的,字迹与前书所补系出一手,而且首叶也钤有同样的二印。这说明当时惠栋曾以同样的方式钞补二书,可能即视它们为同一书的两个部分。丁丙收得二书后,也把它们装于一函。二书卷末都有光绪二十二年王棻的跋,后跋中云:“松生先生以此书与《五百家注》共装一匣,间以示余。”又云:“其书当与《五百家注》同时所刊。”丁丙著录这本《韩文考异》为魏仲举刊本,当即承王棻之误。其实连丁丙所藏的魏本韩集是否宋庆元刊本,都很可疑。因为《天禄琳琅书目》著录有两本魏本韩集,其一有“庆元六禩”云云的木记,另一本有明代文氏“玉兰堂”的藏书印,而丁丙的藏本既无此木记,也不见此印,所以根本没有根据说它就是朱彝尊和《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之本。而且丁丙藏本卷首的《诸儒名氏》中有“新安朱氏,名熹,字元晦,议论见《韩文考异》、《晦庵文集》。”可是细检注文,却不见朱熹之语。即使如《外集》卷二《召大颠和尚书》,注文也仅引及韩醇等人,一字未及《韩文考异》对此文的详细考订。可证此书根本没有包括《韩文考异》,《诸儒名氏》所云,或为后代翻刻时增入。而且从影印本来看,丁丙所藏的魏本韩集和《韩文考异》的版式、行格完全不同,揆诸情理,也不可能是出于一人之手的“同时刊本”。①自从1912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将丁丙所藏的上述二书影印合并为一书以后,它们就流传较广了。②商务印书馆的卷末有孙毓修跋云:“此宋刻《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据《曝书亭集》及《天禄琳琅志》,则宋庆元六年建安魏仲安刊本也。……《考异》犹是朱子原本,未为王伯大所乱,更是罕见秘籍。”于是《韩文考异》曾由魏仲举在庆元六年刊行的说法就广为人知了。究其原委,这实在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宋本《昌黎先生集考异》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涵芬楼影印的底本,是庆元六年以后的翻刻本,而《考异》则更是后来翻刻时补配在一起的。”甚确。其实以情理揆之,魏仲举在庆元六年刊行《韩文考异》且题作《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党禁正严,就在前一年的十二月,韩侂胄的党羽还气势汹汹地上疏要求对“伪党”继续进行打击:“其长恶弗悛者,必重置典宪,投之荒远。”③当庆元六年三月朱熹去世后,还有人上疏要求对朱门弟子的会葬严加防范,以致于“门生故旧不敢送葬”。④魏仲举何人也,竟能在如此严酷阴森的政治气候下公然刊刻《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
从现存材料来看,《韩文考异》的版本有两个系统,现简述如下:
第一个系统是王伯大刊本,刊刻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商务印书馆1926年影印元刊本《朱文公校韩昌黎先生集》卷首有王伯大的序言,即署为宝庆三年。关于王本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言之甚详:“伯大以朱子《韩文考异》于本集之外别为卷帙,不便寻览,乃重为编次。离析《考异》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刻于南剑州。又采洪兴祖《年谱辨证》、樊汝霖《年谱注》、孙汝听《解》、韩醇《解》、祝充《解》,为之音释,附于各篇之末。厥后麻沙书坊以注释缀于篇末,仍不便检阅,亦取而散诸句下。盖王伯大改朱子之本,实一误且再误也。”①王本虽然改变了朱熹原本的形式而且多误,但它便于阅读,所以历代翻刻不绝,流传极广。
第二个系统是张洽刊本,初刊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与王本不同,张洽本是完全遵照朱熹的原本刊刻的,虽然张洽在跋中自称“间有愚见一二,亦各系卷末。”但通检全书,其实只有三则,分别附于卷一、卷四、卷七之末。张洽本在后代流传不广,明正统间曾有翻刻,但传本也甚罕见。清康熙年间,编修《朱子全书》的理学名臣李光地曾翻刻此书,后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有著录,题作《原本韩文考异》。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山西祁县图书馆所藏张洽本影印出版,此本曾经毛晋、季振宜等著名藏书家之手,除卷七末四页系钞配外,居然宋刻全帙,弥足珍贵。本书征引《韩文考异》,皆依此本。
王伯大本和张洽本都初刻于宋理宗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身败名裂后,党禁即渐告解弛。宁宗嘉定二年(1209),朱熹被赐谥曰“文”。嘉定五年(1212),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被立于国学。至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朱熹被追赠太师,封信国公。《韩文考异》在此时刊行问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