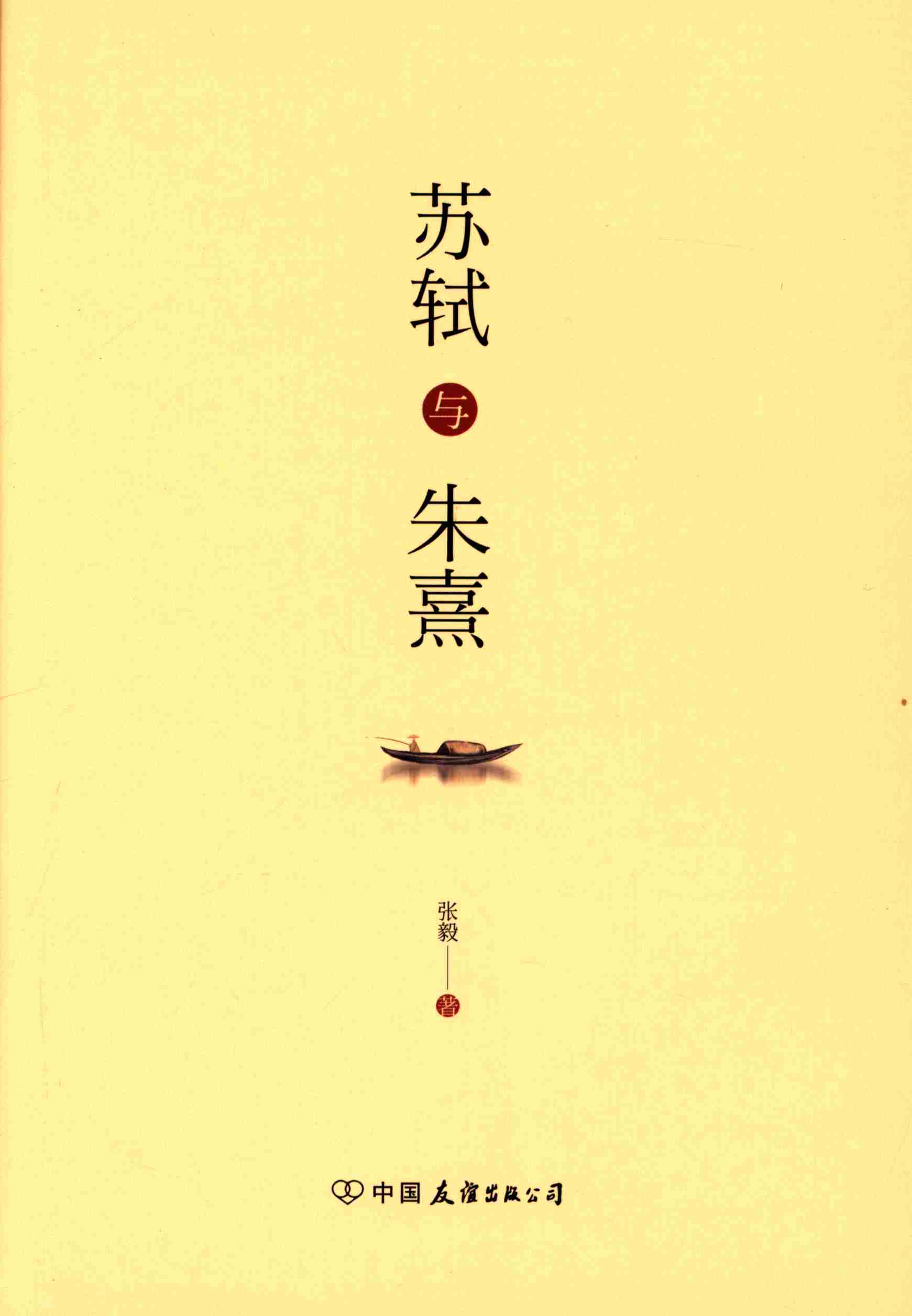文士风流与儒者气象
| 内容出处: | 《苏轼与朱熹》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4260 |
| 颗粒名称: | 文士风流与儒者气象 |
| 分类号: | K825.6 |
| 页数: | 13 |
| 页码: | 229-24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在中国,人们经常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归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如苏轼和朱熹就对人生意义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做相同的事情,却有不同的意义和人生境界。意义取决于对事物的理解和方式。风流的本质并非表面上的男欢女爱,而是一种深刻的情感和超越感,超越感是风流精神的本质。王戎说过,圣人忘情而最下之人只沉溺于感官肉欲中,只有名士所钟之情才能与宇宙人生相关,并具有超越的审美意味。名士重情的事例体现了风流精神,表现了率性任真、潇洒飘逸的超越意味。这与当时社会追求个性解放、贵自然越名教的思潮有关。 |
| 关键词: | 苏轼 朱熹 儒者 气象 |
内容
人生的意义何在,生命归宿在哪里?这是中国士人常思考的问题,而问题的答案就存在于各自的人生追求之中。由苏轼的乐于作文和朱熹的苦于读书,不难看出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尽管他们也可能做相同的事情,但由于各人的理解不同,所做的事对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从而构成了不同的人生境界。意义不同,境界不同,表现于外的举止风度也不一样,如苏轼的放达、潇洒和一往情深,就不同于朱熹严肃、庄重的理性精神。前者可称为文士风流,后者则属儒者气象。
一件事的意义,决定于人们对它的了解程度和方式。谈到文士风流,人们很容易想到男欢女爱,想到历史上流传的许多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如司马相如引卓文君私奔,曹植有感于甄后而作《洛神赋》等。但这只是风流的表象,而非风流的本质。风流与情相关,可以是真情流露,也可以是好色贪欢。情之最深莫如男女交感的缠绵悱恻,故在文人的情感生活里爱情占了显著地位,但真正的情感绝非纯感官的情欲满足。宋代的文士风流是从魏晋的名士风流发展而来的,是一种深于情而又能超越之的审美态度,超越感才是风流精神的本质。
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圣人能以理化情,无情感之累,故曰“忘情”;最下之人则只沉溺于感官肉欲中,所以也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感情;唯名士所钟之情,虽出于个人的感触,但又与宇宙人生的全体相关,有一种超越的审美意味。如桓子野一往有深情,听到别人唱歌就不能自已,辄唤“奈何”。卫玠过江时,见江水茫茫而百感交集,以至形神惨悴。桓温北伐时,见树已十围而感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世说新语》里所讲的些名士重情的事例,是风流精神的体现,含有率性任真而潇洒飘逸的超越意味,与当时追求个性解放、贵自然而越名教的社会思潮相关。
在宋代文人里,苏轼以其旷达潇洒的气度和情怀,可以说是最具超越感的风流人物了。他是个很重情感的人,故其感情生活丰富多彩;同时,由于受老庄思想和禅学的影响,他又是一个能超越生死、物我之上而洞悉宇宙人生底蕴的人。他具有极敏锐的感觉能力,对于生活,有一种超乎有限的具体事物之上的妙赏能力,具有物我无别、物我为一的感觉,这是其重情感的风流精神的真髓。对于诗人来说,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苏轼为悼念亡妻王弗而作的词,属于写男女之情的作品。情可以使人死,也可以使人生,尽管妻子已去世十年了,苏轼犹能在梦中与她相会。时光的流逝使诗人感觉到自己的衰老,担心相逢时妻子会不认识自己,此乃情痴之语。如此一往情深,使诗人入于如梦如幻之境,其感觉已突破了生与死的界限,似乎在梦中还能去与妻子相会,两人相对潸然泪下,无言诉说彼此的思念。写情至此,可谓至真至美至纯,道出了人间男女倾心相爱、至死不渝的真实感受和内心秘密,足以引发普遍的共鸣。可诗人把这种由夫妻之情触发的感觉,置于生死两茫茫的人生空漠的叹喟之中,其超越的意味就很深远,一直坠入宇宙人生变化迷离的无穷境地,令人体味不尽。
苏轼是在自己的人生体验和至性真情里发掘生命意义的。一般说来,情感丰富的人,对痛苦的感觉就更深微,要求解脱的愿望也就更强烈一些。只有把自己个人的感觉从私欲和实用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进入“忘我”的心与物冥的审美体验中,纵身大化,与物推移,方能感觉到生命精神的自由和快乐。苏轼主要是在能充分体现其真情实感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展示生命流行的价值,把人生意义问题转化为生命存在本身的问题。生命存在的体验依赖于人的感觉,没有感觉的存在,是虚幻的存在,但只有在审美感觉中,生命存在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才能自由充分地表现出来。
花草的飘零,水月的晃动,四时节序的变化,一般人并不会为之感动的事,苏轼往往为之感动,并通过想象丰富的文学创作,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如《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一般说来,秋士易感,春女善怀,苏轼因其性格的开朗,很少有无端的伤感。但此词写伤春之情,微词婉转,排遣多情反被无情恼的无奈,表明诗人除了大江东去的豪放外,也有极细腻的儿女柔情,足见其情感世界的丰富。在宋代,词是可以合乐演唱的,流放惠州时,苏轼因见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叫侍妾朝云唱这首词解闷。没想到朝云未展歌喉便泪流满面,苏轼问其原因,朝云说:“奴所不能歌者,‘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苏轼幡然大笑道:“是吾政悲秋,而汝又伤春矣。”可不久朝云就抱病而亡,苏轼方深切地体会到了她唱不下去的心情,于是“终身不复听此词”(《林下偶谈》)。
由于重感情,而且对人间存在的真情有切身的体验,苏轼往往能推己及人,无论对物对人都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心。没有同情心的人,成不了艺术家,也成不了诗人。同情能使人平等地接人待物。如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体验到死亡的恐惧之后,就信守佛家的戒杀生之说,不仅常斋居吃素,还常花钱买鱼来放生。他能以平等的身份与下层老百姓交往,与渔民、樵夫、野老们一起饮酒聊天,谈鬼说神,感受山村淳朴生活的快乐。他曾对弟弟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村夫和乞丐,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这使他胸无城府,极易轻信别人,在政治上吃了不少苦头。可在日常生活里,他仍我行我素,如他在杭州做太守时,常参加有名妓陪伴的酒宴,甚至与朋友一道携妓出游,并应歌妓之邀为她们题诗作词,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态度十分随和。他对堕入风尘的歌妓是抱有同情之心的,无丝毫歧视之念,在为歌妓所作的词里,也只是描写她们的美,没有任何色情的成分。
诗人的同情起于物我一体的感觉,终于移情于物的艺术创作,艺术化了的生活就是充满悲天悯人的同情心的生活。如果说这是苏轼随缘自适、热爱生命的处世态度的反映的话,那么就显然与儒家所讲的“名教”形成了对立。名教要求人们在生活中严格遵守高下尊卑的等级原则,用封建礼仪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严男女之大防,可苏轼在生活中的通达潇洒,已完全把非礼勿视、非礼勿言之类的道德训教搁在了一边。他那种普遍的同情态度,近于释氏所说的我佛慈悲、普度众生,超越是非善恶之上,没有用“义理”来分别好坏。苏轼的文士风流,在某些方面与魏晋名士一样,有任情纵性、越名教而贵自然的倾向,是一种偏于审美解脱的无差别的人生境界。
无差别是建立在诗人物我为一的感觉经验之上的,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差别却是普遍存在的,各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经历不同,人生的意义也就不一样。地位高的人,成就大的人,似乎其人生的意义也就伟大一些。但若就生命存在本身来看,心情愉快地健康地活着才是重要的,不朽的功名乃身外之物。人的生和死都是一样的偶然,生命短暂,人生如梦,是任何道德说教和功名利禄都无法掩盖的事实。一切都将过去,人只要存在过了,生活过了,本身就是意义,其他的都是虚无。故只有艺术和审美才是出路,因为它能使人在有限的生命中体验到永恒,体验到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
艺术使生命沉醉,生命使艺术完满。尽管审美不能解决人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任何现实问题,可生命的存在毕竟被牢牢地感受到和把握到了,这就是苏轼风流精神的意义所在。可这种只注意生命本身,而不考虑人生的意义和信念的处世态度,极易使人产生齐物我、了生死的超然出世之心,追求顺应自然生命的超道德、超社会、超现实的逍遥之游。若不只限于审美生活,而要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去的话,就会使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的纲常伦理趋于瓦解,因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以承认差别为先决条件的。
对与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力密切相关的人类两性情爱关系,苏轼持非常人性化的开明态度。在黄州与朋友谈及养生之事时,他认为要叫人完全除去男女之欲是很困难的。一位朋友赞成这种观点,并举“苏武牧羊”为例。说汉代的苏武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域,被匈奴扣在那里,在冰天雪地的北海边牧羊十九年,可谓了生死之际的人杰了。然而他在那里却免不了爱上当地匈奴女人,与之生儿育女,何况一般人于洞房绮疏之下乎?苏轼闻言大笑,认为讲得非常有道理,便把这段谈话记录了下来。他以为男女之间的性爱乃人类延续生命的一种自然本能,没有除去的必要。所谓人性,既包含情感,也包含欲望,可宋代理学家却把情欲视为天理之大敌,往往闻人谈性爱而色变,必去之而后快。甚至有的理学家认为行洞房之事也要注意男尊女卑,严守道德规范,不能溺于情欲而伤害了义理,真是匪夷所思。
如果说文士风流缘于情的话,那么儒者气象则主于理。
一般说来,理只可思而不可感,超越于经验之上,儒者以读书穷理的方式去探索人生意义时,多做冥思苦想的一脸严肃相。但也不能尽是这样子,整天板着脸也受不了。理学家中亦有较为洒脱与和气之人,如黄庭坚言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朱熹说“延平先生每诵此言,以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周敦颐是朱熹推崇的北宋理学大家,延平先生即朱熹的老师李侗。朱熹在为周敦颐所作的《濂溪象赞》中说:
书不尽言,图不尽意。
风月无边,庭草交翠。
书指《通书》,图指《太极图说》,是周敦颐讲宇宙生成、万物化生和人性修养的理学著作,故朱熹把他视为能洞悉天地万物本体的得道之人,有胸中洒落而风月无边的天人合一的圣贤气象。这种圣贤气象是圣人贤者得道而知天命之后的精神境界,非一般还须读书穷理的儒者所能具备,朱熹生前就从来没有敢以圣贤自居。
即使是可称为圣贤的儒者,气象也有所不同。朱熹在《答孙季和》书里谈到二程时说:“明道(程颢)、伊川(程颐)论性疏密固不同,按其气象,亦各有极至处。明道直是浑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细平实。”程颢的浑然天成,近于周敦颐的胸次洒落,为仁者与物同体时一团和气的气象,由注重反身而诚的内心体验而来。宋代新儒家里陆九渊的心学派即循此路径,以分别濂溪、明道与伊川、朱熹的不同。在为学待物方面,程颢善于发明极致而通透洒落,程颐是即事明理而耐咀嚼。朱熹认为向程颢学习易于开发,但不如学程颐更易有所成就,所以他倾向于程颐那种辨明事理的精细平实,气象也偏于随事检点的严肃整齐。
儒者气象虽主于理,却有专于“理一”上体验和于“分殊”上穷理的区别,大程属于前者,小程倾向于后者。于静坐体验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属于专在心中体会理一,虽然能造就出喜怒不形于色的醇儒,但也有流于专就里面体认的禅学的危险。程门后学里就不乏身带禅气之人,朱熹早年也不例外。但他后来着重强调即事明理,因为“若未发时,自著不得工夫。未发之时,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语类》卷二六),很难分辨出高下来。儒者气象应于“已发”中见,于穷理工夫中见。朱熹在谈到看圣贤气象时说:“须是子细体认他工夫是如何,然后看他气象是如何,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语类》卷三〇)认为只有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
朱熹所讲的穷理功夫,于内指道德人格的涵养,要在内心始终保持道德自律的主一无适,以理辨明是非善恶;于外指事事都要符合义理和礼教规范,绝不姑息养奸。其举止态度不仅有不苟言笑、严于律己的严肃,也有疾恶如仇、正义凛然的庄重。由于理学家所讲的理或天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要贯彻高下尊卑的“义”的原则,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和有情有义,所以在富于同情心的文人看来,这种正人君子的儒者气象难免有失公允和不近人情处。
如朱熹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时,奏劾前台州郡守唐仲友贪污淫虐,前后六上奏章。又令人将天台营妓严蕊收捕入狱拷打逼供,要她交代勾结唐仲友为虎作伥的犯罪事实。不论朱熹此举的用心如何,其处理方式是有失公允的。严蕊作为色艺俱全的营妓,是朝廷专门设置的供当地官员享乐的泄欲工具,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对象,不管她愿不愿意,与台州的最高长官唐仲友发生两性关系都是必然的,并不能作为她勾结官府的证据,更不能把唐仲友的腐化堕落、徇私受贿也归罪于她。即使是出于要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大公无私之心,朱熹弹劾赃官而拿妓女开刀,也暴露了儒家那种唯女子与小人难养、视女人为祸水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对妇女的歧视。
朱熹痛恨以色艺招引男人的妓女,认为她们诱发人欲而灭绝天理,可如他所说,这种本来是有助于扶持社会风化的疾恶如仇,如用之不当,便至于残忍了。当然,根据儒家所讲的义理,残忍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说法。朱熹说:“如人之残忍,便是翻了恻隐。如放火杀人可谓至恶,若把那去炊饭,杀其人之所当杀,岂不是天理。”(《语类》卷九七)如此说,朱熹等人对妓女的残忍,倒是出于义理之正的恻隐之心了,是一种正当的疾恶如仇的感情。可当时真正所当杀的是赃官唐仲友,却因他与丞相王淮为姻家,朝中有人而未受处罚,真正坐牢的是无辜的弱女子严蕊。难怪宋代的野史和文人笔记要对此大加渲染,对严蕊一掬同情之泪,而把朱熹描绘成性格乖戾、气象狰狞的道学人物。这当然是对守道循理的正人君子形象的丑化,有夸饰过当之处。
对儒者来说,守道循理的刚毅正直,不仅体现在接人应事方面,也体现在自身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上。儒学是“为己”之学,朱熹奏劾唐仲友失败后,辞官回到武夷山中,继续自己读书穷理的儒者生涯。武夷山苍翠可玩和九溪八曲的秀丽山水胜景,触动了他的诗情,他写下了《武夷精舍杂咏》十二首等一批融情于景的作品。诗是写得不错的,只因其中有“居然我泉石”的句子,一些看不惯朱熹正人君子面孔的反道学人士,抓住其中的“我”字大做文章,说朱熹有独占武夷山的野心。这无疑是别有用心的诽谤,可朱熹反躬自省,觉得自己言情之作中确有私心作怪。他在《答林择之》书里说:“昨关目思量,许多纷纷,都从《十二咏》首篇中一‘我’字生出。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触处作灾怪也。”这促使他更加戒慎恐惧,随时检点自己的言行,以理抑情,奉行克己之道,连朋友想出资为他在武夷山中盖房子都拒绝了。将刚毅正直的傲骨隐于低眉木讷、睟面盎背的严肃气象中。
朱熹于“分殊”上穷理的修养功夫很到家,甚至连写字这样的细事末节都注意到了。他认为字能反映出人的德性,书品连着人品,如同为拜相之人,韩琦的书法端庄谨重,反映出其心胸的安静详密与雍容和豫,不同于王安石那种有跨越古今、开阖宇宙的躁扰急迫气象(《跋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帖》)。以被公认为宋代书法四大家的苏、黄、米、蔡而言,苏轼的字学晋人,端庄杂流利,刚健含阿娜,虽有肩耸肉多之病,但具魏晋名士风味,极萧散自得之趣,足以映衬其文士风流;黄庭坚的字劲瘦锐利,米芾的字带豪狂之气,皆能表现其性格;蔡襄的字笔画端直严谨,无一处败笔,但缺乏个性特色。朱熹在评宋人的书法时,最推崇蔡襄而否定苏、黄等人,他认为“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即蔡襄)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语类》卷一四○)。他在《跋朱喻二公法帖》里说:“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朱熹论书法,强调的是要能体现端人正士品行的儒者气象,而不是表现艺术个性的文人风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儒者的穷理修养带有否定自我、压抑个性的倾向,一切都要符合理的法度和规范。
可这样一来,不仅具有艺术气质的文人不会买账,就是儒者内部也难以完全认同。因为理是死的,天理只有一个,据说此理万古不变,而人心却是活的。心不止能思,亦能感。思是理智的反省,易流于艰奥深沉;感是情感体验,活泼而实在。情感体验是人之生命存在的最基本方式,所谓性理,所谓本体,如果完全脱离了人的情感知觉,便都会落空。而且道德实践行为是由情感意向决定的,宋代新儒家里的心学派,喜言“曾点气象”,注重主体的内心体验而求洒落,以“自得”于心的情感体验和直觉为心性存养工夫的根本。这容易导致对个人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意识的强调,而忽略了所谓“天理”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意义,流于禅家的运水搬柴莫非妙道的“作用是性”之说。若以类于参禅的方式去悟理,易使人以为自己的心灵就是真理的主宰,顿悟时的净洁快活仅止于自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不负有责任,甚至不相信儒家经典的思想权威,难免有离经叛道之嫌。
对此,朱熹早有警惕,尽力想加以纠正,可也有力不从心的无可奈何之感。因为心学派束书不观的“简易工夫”,对于追求“孔颜乐处”和盼望早日成圣成贤的儒者来说,其吸引力远远大于长年累月读书穷理的格物致知。如陆九渊所说: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这是何等气魄!在朱、陆鹅湖之辩后不久,当陆九龄到铅山负荆请罪,表示愿意把自己的立场从心学派转到理学派上来时,朱熹并没有感到特别欣喜。
他在追和陆九龄的《鹅湖寺和陆子寿》里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仍对心学派所说的发明本心的“无言”顿悟方法的“将久大”表示担心,而后来宋明理学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一件事的意义,决定于人们对它的了解程度和方式。谈到文士风流,人们很容易想到男欢女爱,想到历史上流传的许多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如司马相如引卓文君私奔,曹植有感于甄后而作《洛神赋》等。但这只是风流的表象,而非风流的本质。风流与情相关,可以是真情流露,也可以是好色贪欢。情之最深莫如男女交感的缠绵悱恻,故在文人的情感生活里爱情占了显著地位,但真正的情感绝非纯感官的情欲满足。宋代的文士风流是从魏晋的名士风流发展而来的,是一种深于情而又能超越之的审美态度,超越感才是风流精神的本质。
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圣人能以理化情,无情感之累,故曰“忘情”;最下之人则只沉溺于感官肉欲中,所以也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感情;唯名士所钟之情,虽出于个人的感触,但又与宇宙人生的全体相关,有一种超越的审美意味。如桓子野一往有深情,听到别人唱歌就不能自已,辄唤“奈何”。卫玠过江时,见江水茫茫而百感交集,以至形神惨悴。桓温北伐时,见树已十围而感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世说新语》里所讲的些名士重情的事例,是风流精神的体现,含有率性任真而潇洒飘逸的超越意味,与当时追求个性解放、贵自然而越名教的社会思潮相关。
在宋代文人里,苏轼以其旷达潇洒的气度和情怀,可以说是最具超越感的风流人物了。他是个很重情感的人,故其感情生活丰富多彩;同时,由于受老庄思想和禅学的影响,他又是一个能超越生死、物我之上而洞悉宇宙人生底蕴的人。他具有极敏锐的感觉能力,对于生活,有一种超乎有限的具体事物之上的妙赏能力,具有物我无别、物我为一的感觉,这是其重情感的风流精神的真髓。对于诗人来说,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苏轼为悼念亡妻王弗而作的词,属于写男女之情的作品。情可以使人死,也可以使人生,尽管妻子已去世十年了,苏轼犹能在梦中与她相会。时光的流逝使诗人感觉到自己的衰老,担心相逢时妻子会不认识自己,此乃情痴之语。如此一往情深,使诗人入于如梦如幻之境,其感觉已突破了生与死的界限,似乎在梦中还能去与妻子相会,两人相对潸然泪下,无言诉说彼此的思念。写情至此,可谓至真至美至纯,道出了人间男女倾心相爱、至死不渝的真实感受和内心秘密,足以引发普遍的共鸣。可诗人把这种由夫妻之情触发的感觉,置于生死两茫茫的人生空漠的叹喟之中,其超越的意味就很深远,一直坠入宇宙人生变化迷离的无穷境地,令人体味不尽。
苏轼是在自己的人生体验和至性真情里发掘生命意义的。一般说来,情感丰富的人,对痛苦的感觉就更深微,要求解脱的愿望也就更强烈一些。只有把自己个人的感觉从私欲和实用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进入“忘我”的心与物冥的审美体验中,纵身大化,与物推移,方能感觉到生命精神的自由和快乐。苏轼主要是在能充分体现其真情实感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展示生命流行的价值,把人生意义问题转化为生命存在本身的问题。生命存在的体验依赖于人的感觉,没有感觉的存在,是虚幻的存在,但只有在审美感觉中,生命存在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才能自由充分地表现出来。
花草的飘零,水月的晃动,四时节序的变化,一般人并不会为之感动的事,苏轼往往为之感动,并通过想象丰富的文学创作,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如《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一般说来,秋士易感,春女善怀,苏轼因其性格的开朗,很少有无端的伤感。但此词写伤春之情,微词婉转,排遣多情反被无情恼的无奈,表明诗人除了大江东去的豪放外,也有极细腻的儿女柔情,足见其情感世界的丰富。在宋代,词是可以合乐演唱的,流放惠州时,苏轼因见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叫侍妾朝云唱这首词解闷。没想到朝云未展歌喉便泪流满面,苏轼问其原因,朝云说:“奴所不能歌者,‘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苏轼幡然大笑道:“是吾政悲秋,而汝又伤春矣。”可不久朝云就抱病而亡,苏轼方深切地体会到了她唱不下去的心情,于是“终身不复听此词”(《林下偶谈》)。
由于重感情,而且对人间存在的真情有切身的体验,苏轼往往能推己及人,无论对物对人都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心。没有同情心的人,成不了艺术家,也成不了诗人。同情能使人平等地接人待物。如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体验到死亡的恐惧之后,就信守佛家的戒杀生之说,不仅常斋居吃素,还常花钱买鱼来放生。他能以平等的身份与下层老百姓交往,与渔民、樵夫、野老们一起饮酒聊天,谈鬼说神,感受山村淳朴生活的快乐。他曾对弟弟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村夫和乞丐,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这使他胸无城府,极易轻信别人,在政治上吃了不少苦头。可在日常生活里,他仍我行我素,如他在杭州做太守时,常参加有名妓陪伴的酒宴,甚至与朋友一道携妓出游,并应歌妓之邀为她们题诗作词,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态度十分随和。他对堕入风尘的歌妓是抱有同情之心的,无丝毫歧视之念,在为歌妓所作的词里,也只是描写她们的美,没有任何色情的成分。
诗人的同情起于物我一体的感觉,终于移情于物的艺术创作,艺术化了的生活就是充满悲天悯人的同情心的生活。如果说这是苏轼随缘自适、热爱生命的处世态度的反映的话,那么就显然与儒家所讲的“名教”形成了对立。名教要求人们在生活中严格遵守高下尊卑的等级原则,用封建礼仪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严男女之大防,可苏轼在生活中的通达潇洒,已完全把非礼勿视、非礼勿言之类的道德训教搁在了一边。他那种普遍的同情态度,近于释氏所说的我佛慈悲、普度众生,超越是非善恶之上,没有用“义理”来分别好坏。苏轼的文士风流,在某些方面与魏晋名士一样,有任情纵性、越名教而贵自然的倾向,是一种偏于审美解脱的无差别的人生境界。
无差别是建立在诗人物我为一的感觉经验之上的,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差别却是普遍存在的,各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经历不同,人生的意义也就不一样。地位高的人,成就大的人,似乎其人生的意义也就伟大一些。但若就生命存在本身来看,心情愉快地健康地活着才是重要的,不朽的功名乃身外之物。人的生和死都是一样的偶然,生命短暂,人生如梦,是任何道德说教和功名利禄都无法掩盖的事实。一切都将过去,人只要存在过了,生活过了,本身就是意义,其他的都是虚无。故只有艺术和审美才是出路,因为它能使人在有限的生命中体验到永恒,体验到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
艺术使生命沉醉,生命使艺术完满。尽管审美不能解决人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任何现实问题,可生命的存在毕竟被牢牢地感受到和把握到了,这就是苏轼风流精神的意义所在。可这种只注意生命本身,而不考虑人生的意义和信念的处世态度,极易使人产生齐物我、了生死的超然出世之心,追求顺应自然生命的超道德、超社会、超现实的逍遥之游。若不只限于审美生活,而要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去的话,就会使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的纲常伦理趋于瓦解,因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以承认差别为先决条件的。
对与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力密切相关的人类两性情爱关系,苏轼持非常人性化的开明态度。在黄州与朋友谈及养生之事时,他认为要叫人完全除去男女之欲是很困难的。一位朋友赞成这种观点,并举“苏武牧羊”为例。说汉代的苏武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域,被匈奴扣在那里,在冰天雪地的北海边牧羊十九年,可谓了生死之际的人杰了。然而他在那里却免不了爱上当地匈奴女人,与之生儿育女,何况一般人于洞房绮疏之下乎?苏轼闻言大笑,认为讲得非常有道理,便把这段谈话记录了下来。他以为男女之间的性爱乃人类延续生命的一种自然本能,没有除去的必要。所谓人性,既包含情感,也包含欲望,可宋代理学家却把情欲视为天理之大敌,往往闻人谈性爱而色变,必去之而后快。甚至有的理学家认为行洞房之事也要注意男尊女卑,严守道德规范,不能溺于情欲而伤害了义理,真是匪夷所思。
如果说文士风流缘于情的话,那么儒者气象则主于理。
一般说来,理只可思而不可感,超越于经验之上,儒者以读书穷理的方式去探索人生意义时,多做冥思苦想的一脸严肃相。但也不能尽是这样子,整天板着脸也受不了。理学家中亦有较为洒脱与和气之人,如黄庭坚言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朱熹说“延平先生每诵此言,以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周敦颐是朱熹推崇的北宋理学大家,延平先生即朱熹的老师李侗。朱熹在为周敦颐所作的《濂溪象赞》中说:
书不尽言,图不尽意。
风月无边,庭草交翠。
书指《通书》,图指《太极图说》,是周敦颐讲宇宙生成、万物化生和人性修养的理学著作,故朱熹把他视为能洞悉天地万物本体的得道之人,有胸中洒落而风月无边的天人合一的圣贤气象。这种圣贤气象是圣人贤者得道而知天命之后的精神境界,非一般还须读书穷理的儒者所能具备,朱熹生前就从来没有敢以圣贤自居。
即使是可称为圣贤的儒者,气象也有所不同。朱熹在《答孙季和》书里谈到二程时说:“明道(程颢)、伊川(程颐)论性疏密固不同,按其气象,亦各有极至处。明道直是浑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细平实。”程颢的浑然天成,近于周敦颐的胸次洒落,为仁者与物同体时一团和气的气象,由注重反身而诚的内心体验而来。宋代新儒家里陆九渊的心学派即循此路径,以分别濂溪、明道与伊川、朱熹的不同。在为学待物方面,程颢善于发明极致而通透洒落,程颐是即事明理而耐咀嚼。朱熹认为向程颢学习易于开发,但不如学程颐更易有所成就,所以他倾向于程颐那种辨明事理的精细平实,气象也偏于随事检点的严肃整齐。
儒者气象虽主于理,却有专于“理一”上体验和于“分殊”上穷理的区别,大程属于前者,小程倾向于后者。于静坐体验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属于专在心中体会理一,虽然能造就出喜怒不形于色的醇儒,但也有流于专就里面体认的禅学的危险。程门后学里就不乏身带禅气之人,朱熹早年也不例外。但他后来着重强调即事明理,因为“若未发时,自著不得工夫。未发之时,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语类》卷二六),很难分辨出高下来。儒者气象应于“已发”中见,于穷理工夫中见。朱熹在谈到看圣贤气象时说:“须是子细体认他工夫是如何,然后看他气象是如何,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语类》卷三〇)认为只有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
朱熹所讲的穷理功夫,于内指道德人格的涵养,要在内心始终保持道德自律的主一无适,以理辨明是非善恶;于外指事事都要符合义理和礼教规范,绝不姑息养奸。其举止态度不仅有不苟言笑、严于律己的严肃,也有疾恶如仇、正义凛然的庄重。由于理学家所讲的理或天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要贯彻高下尊卑的“义”的原则,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和有情有义,所以在富于同情心的文人看来,这种正人君子的儒者气象难免有失公允和不近人情处。
如朱熹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时,奏劾前台州郡守唐仲友贪污淫虐,前后六上奏章。又令人将天台营妓严蕊收捕入狱拷打逼供,要她交代勾结唐仲友为虎作伥的犯罪事实。不论朱熹此举的用心如何,其处理方式是有失公允的。严蕊作为色艺俱全的营妓,是朝廷专门设置的供当地官员享乐的泄欲工具,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对象,不管她愿不愿意,与台州的最高长官唐仲友发生两性关系都是必然的,并不能作为她勾结官府的证据,更不能把唐仲友的腐化堕落、徇私受贿也归罪于她。即使是出于要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大公无私之心,朱熹弹劾赃官而拿妓女开刀,也暴露了儒家那种唯女子与小人难养、视女人为祸水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对妇女的歧视。
朱熹痛恨以色艺招引男人的妓女,认为她们诱发人欲而灭绝天理,可如他所说,这种本来是有助于扶持社会风化的疾恶如仇,如用之不当,便至于残忍了。当然,根据儒家所讲的义理,残忍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说法。朱熹说:“如人之残忍,便是翻了恻隐。如放火杀人可谓至恶,若把那去炊饭,杀其人之所当杀,岂不是天理。”(《语类》卷九七)如此说,朱熹等人对妓女的残忍,倒是出于义理之正的恻隐之心了,是一种正当的疾恶如仇的感情。可当时真正所当杀的是赃官唐仲友,却因他与丞相王淮为姻家,朝中有人而未受处罚,真正坐牢的是无辜的弱女子严蕊。难怪宋代的野史和文人笔记要对此大加渲染,对严蕊一掬同情之泪,而把朱熹描绘成性格乖戾、气象狰狞的道学人物。这当然是对守道循理的正人君子形象的丑化,有夸饰过当之处。
对儒者来说,守道循理的刚毅正直,不仅体现在接人应事方面,也体现在自身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上。儒学是“为己”之学,朱熹奏劾唐仲友失败后,辞官回到武夷山中,继续自己读书穷理的儒者生涯。武夷山苍翠可玩和九溪八曲的秀丽山水胜景,触动了他的诗情,他写下了《武夷精舍杂咏》十二首等一批融情于景的作品。诗是写得不错的,只因其中有“居然我泉石”的句子,一些看不惯朱熹正人君子面孔的反道学人士,抓住其中的“我”字大做文章,说朱熹有独占武夷山的野心。这无疑是别有用心的诽谤,可朱熹反躬自省,觉得自己言情之作中确有私心作怪。他在《答林择之》书里说:“昨关目思量,许多纷纷,都从《十二咏》首篇中一‘我’字生出。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触处作灾怪也。”这促使他更加戒慎恐惧,随时检点自己的言行,以理抑情,奉行克己之道,连朋友想出资为他在武夷山中盖房子都拒绝了。将刚毅正直的傲骨隐于低眉木讷、睟面盎背的严肃气象中。
朱熹于“分殊”上穷理的修养功夫很到家,甚至连写字这样的细事末节都注意到了。他认为字能反映出人的德性,书品连着人品,如同为拜相之人,韩琦的书法端庄谨重,反映出其心胸的安静详密与雍容和豫,不同于王安石那种有跨越古今、开阖宇宙的躁扰急迫气象(《跋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帖》)。以被公认为宋代书法四大家的苏、黄、米、蔡而言,苏轼的字学晋人,端庄杂流利,刚健含阿娜,虽有肩耸肉多之病,但具魏晋名士风味,极萧散自得之趣,足以映衬其文士风流;黄庭坚的字劲瘦锐利,米芾的字带豪狂之气,皆能表现其性格;蔡襄的字笔画端直严谨,无一处败笔,但缺乏个性特色。朱熹在评宋人的书法时,最推崇蔡襄而否定苏、黄等人,他认为“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即蔡襄)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语类》卷一四○)。他在《跋朱喻二公法帖》里说:“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朱熹论书法,强调的是要能体现端人正士品行的儒者气象,而不是表现艺术个性的文人风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儒者的穷理修养带有否定自我、压抑个性的倾向,一切都要符合理的法度和规范。
可这样一来,不仅具有艺术气质的文人不会买账,就是儒者内部也难以完全认同。因为理是死的,天理只有一个,据说此理万古不变,而人心却是活的。心不止能思,亦能感。思是理智的反省,易流于艰奥深沉;感是情感体验,活泼而实在。情感体验是人之生命存在的最基本方式,所谓性理,所谓本体,如果完全脱离了人的情感知觉,便都会落空。而且道德实践行为是由情感意向决定的,宋代新儒家里的心学派,喜言“曾点气象”,注重主体的内心体验而求洒落,以“自得”于心的情感体验和直觉为心性存养工夫的根本。这容易导致对个人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意识的强调,而忽略了所谓“天理”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意义,流于禅家的运水搬柴莫非妙道的“作用是性”之说。若以类于参禅的方式去悟理,易使人以为自己的心灵就是真理的主宰,顿悟时的净洁快活仅止于自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不负有责任,甚至不相信儒家经典的思想权威,难免有离经叛道之嫌。
对此,朱熹早有警惕,尽力想加以纠正,可也有力不从心的无可奈何之感。因为心学派束书不观的“简易工夫”,对于追求“孔颜乐处”和盼望早日成圣成贤的儒者来说,其吸引力远远大于长年累月读书穷理的格物致知。如陆九渊所说: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这是何等气魄!在朱、陆鹅湖之辩后不久,当陆九龄到铅山负荆请罪,表示愿意把自己的立场从心学派转到理学派上来时,朱熹并没有感到特别欣喜。
他在追和陆九龄的《鹅湖寺和陆子寿》里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仍对心学派所说的发明本心的“无言”顿悟方法的“将久大”表示担心,而后来宋明理学的发展也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