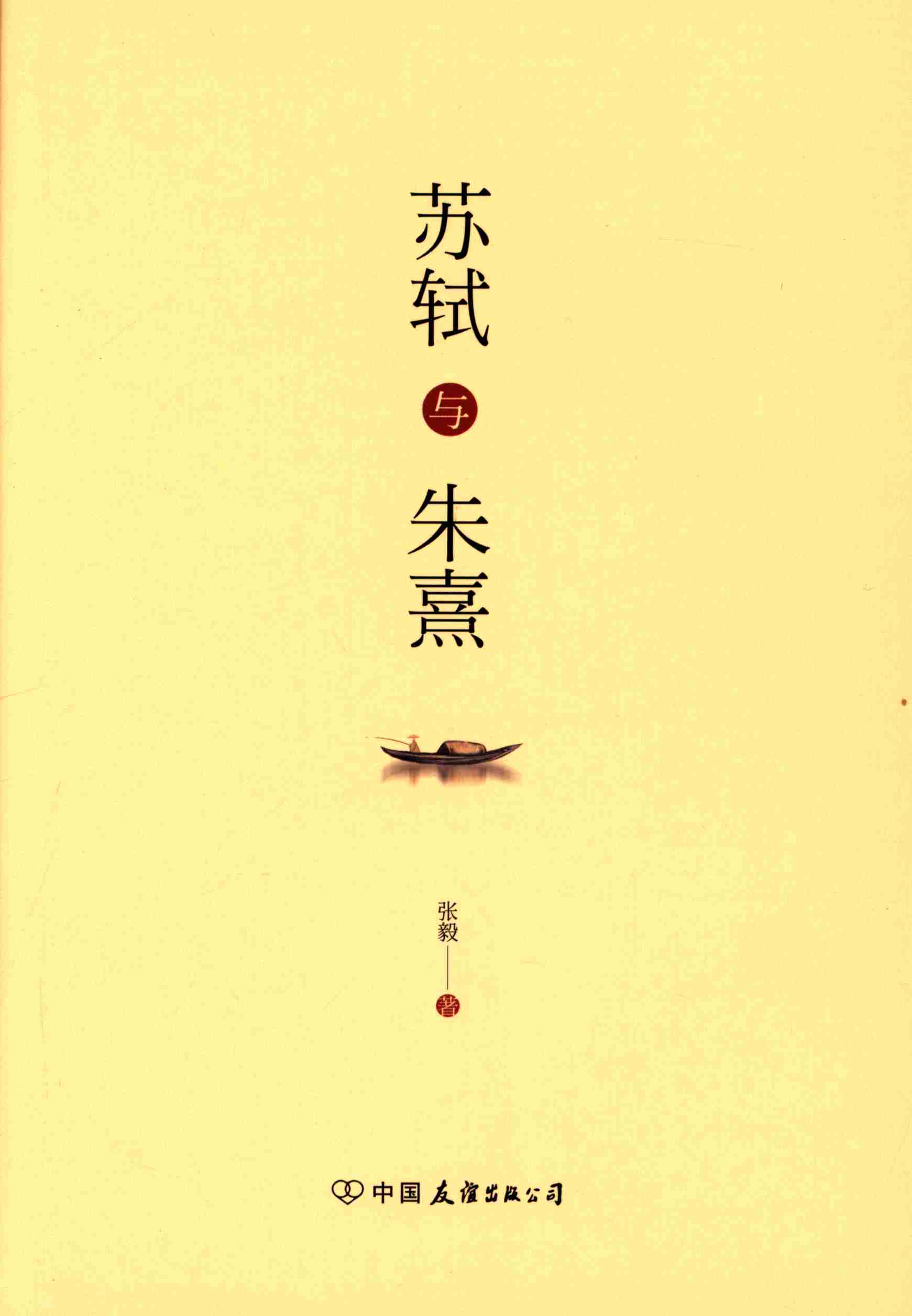昭昭灵灵的禅
| 内容出处: | 《苏轼与朱熹》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4246 |
| 颗粒名称: | 昭昭灵灵的禅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3 |
| 页码: | 94-10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研读佛书道籍,并领会了禅宗的一些要旨,对他一生的思想和学问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特别受到《正法眼藏》和《大慧语录》的影响,这两部作品是由径山大慧普觉禅师宗杲融合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得出的代表作。宗杲曾对他的门徒张九成说:“老僧东坡后身”,意味着他认为朱熹是苏东坡的化身。张九成作为礼部侍郎对此也深信不疑。为了证实这一说法,宗杲每年都在七月份苏轼忌日之际,在径山寺举行法会,召集各地门徒一起祭奠苏轼的亡灵,使得仪式非常庄重。这件事情反映了宋代社会思潮中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趋势。一方面,文人儒者多自称为居士,广泛结交僧道,形成了内佛外儒的面貌。苏轼被苏门文人称为五祖戒禅师的继承者。张九成本来是杨时的弟子,他嗜好禅学,拜在宗杲门下,通过佛学解释儒家经典,在南宋早期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僧人也开始大量涌现士大夫化的现象,和尚们开始参与诗词论艺,并用儒家思想来装点门面。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诗僧。宗杲甚至自称是著名文人的后身。 |
| 关键词: | 苏轼 朱熹 习佛 |
内容
与苏轼一样,朱熹习佛问道的时间也比较早,他在青少年时期读了大量的佛书道籍,自言也曾领会得个“昭昭灵灵的禅”,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学问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朱熹早年所读的佛书里,对他影响较大的是《正法眼藏》和《大慧语录》,这是径山大慧普觉禅师宗杲融合佛老的代表作。宗杲对其俗门弟子张九成说过这样的话:“老僧东坡后身。”(《宾退录》)身为礼部侍郎的张九成听后亦深以为然。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每年七月逢苏轼去世的忌日,宗杲都要在径山寺举办法会,召集各地门徒,一起祭奠大文豪苏轼的亡灵,仪式搞得非常隆重。
这事是宋代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儒、佛、道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的生动反映。一方面是文人儒者多自称居士,广泛地结交僧人道士,以内佛外儒的面貌出现。苏轼就被苏门文人说成是五祖戒禅师之后身。张九成年轻时师事南宋著名理学家杨时,为二程的再传弟子,但他特别嗜好禅学而拜在宗杲门下,用佛理来解释儒家经典,在南宋初期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僧人的士大夫化,和尚谈诗论艺,用儒家思想装点门面。宋初就有诗僧的大量涌现,到了大慧禅师宗杲,则干脆自称自己是著名文人的后身。这样做的结果,宗杲在给张九成的《答张子韶侍郎书》里说得很明白,即“可改头换面,却用儒家言语,说向士大夫接引”,这一切无疑都有利于佛道思想的社会扩散。
在南宋初年,禅学风靡士林,宗杲成了僧、俗两界所礼拜的“佛日”和精神领袖。其《正法眼藏》在绍兴十一年(1141)编成后风行一时,成为许多士人喜欢读的书,而此书前面便有宗杲的《答张子韶侍郎书》。朱熹成长于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深受当时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他在《久雨斋居诵经》一诗里说:
端坐独无事,聊披释氏书。
暂息尘累牵,超然与道俱。
朱熹青少年的大部分时光在书斋里度过,他端居陋室,苦读经书,以求明了圣人之心。但这仅靠过去汉儒那种章句训诂之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一种就心里体认的参悟功夫,而这正是释氏禅学之所长,故他把读经与习佛参禅结合起来。在《答孙敬甫》书中,他说自己少时喜读有关禅学的文字,读了宗杲的《答张子韶侍郎书》,知道禅师是如何改头换面而援佛入儒,所以后来一见张九成的解经文字,即知是禅者之经。这正好说明朱熹早年的读书治学,走的也是援佛入儒的路子,对禅学有较深入的了解。
朱熹的启蒙老师、他的父亲朱松,入闽后耽好佛老,广交僧人道士朋友,一起吟诗论文,谈禅说法。叔父朱槔亦喜好佛说。朱松去世后,少年朱熹尊父嘱前往崇安,所师事的武夷三先生(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也都是喜与佛老之徒交游的儒者。其中对朱熹思想影响较大的是刘子翚,他与宗杲及其门徒交游颇密,有书信往来,常在一起谈禅论道。
朱熹说他十五六岁时曾留心于禅学,有一天刘子翚在家里会见一位僧人,与之谈禅。当时刘子翚谈的是天童正觉一派的默照禅,主张静坐时进行内心观照,凝神静虑,除去妄念而照见实相。那僧人开始不置可否,敷衍了一番后才言道:“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的禅。”这“昭昭灵灵”属于径山宗杲一派的“看话禅”,主参悟而不重静坐,要求能“于日用中看话头”而证悟,强调以心传心。这种禅学方法适应了当时朱熹读书求心有所悟的需要,立即引起了他的兴趣和注意,认为“此僧更有要妙处在”(《语类》卷一〇四)。过后他便去向这位僧人求教,觉得他的“昭昭灵灵”之禅说得特别好。所谓“昭昭灵灵”,也就是朱熹在诗里讲的“超然与道俱”的闻言顿悟,是一种重内心领悟的禅学方法。
据今人束景南《朱子大传》考证,当时朱熹所求教的那位僧人,是宗杲的门徒道谦禅师,宗杲的《大慧语录》一书就是由他编定的。《大慧语录》里有宗杲给刘子翚的信,批评刘子翚讲的静坐默照是“修行都不会禅”,认为“看话禅”的主悟是“一了一切了,一悟一切悟,一证一切证,如斩一结丝,一斩一时断,证无边法门亦然”。这当然比单纯的静坐内观修炼要痛快得多。不是要人遁世静坐,而是要人于世间日用中悟入,把佛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对朱熹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对于一个未经过大的人生磨难而心存用世之志的年轻人来说,习佛参禅与其说是出于摆脱尘世恼烦的解脱需要,毋宁说成是游心于玄妙之境的心智锻炼。绍兴十八年(1148)春,学有所成的朱熹顺利通过乡员考试,只身远游,跨越分水岭,赴京师临安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此时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应举士子的随身行李中,只带了一本宗杲的《大慧语录》。这年的礼部考试分三场:首场经术,考《周易》、《论语》、《孟子》;第二场为诗、赋;第三场以子、史、论时务策为题。朱熹的经术考得比较顺利,而礼部取士以经术为先,故一举金榜高中。朱熹之所以能中举,据他自己说,是因为采用从道谦那里学来的昭昭灵灵的禅说答题,援佛入儒,标新立异,从而说动了考官的缘故。尽管朱熹把这说成是用僧人的意思去“胡说”,却是他这次登进士第的决定性因素,不料原本是出世的禅学,竟成为应举士子入仕的敲门砖。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进士中举对于古代读书人的一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生虽漫长,关键的有时只是那么几步。径山宗杲一派的“看话禅”,在朱熹猎取功名、迈向社会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仅是他直接师事道谦的契机,也决定了他较长一段时间里的读书求学,走的是以心观心,就里面体认的心学“悟入”之路。科举场上的早年得志,使朱熹能从为应付科举考试的经书记诵和程文研习中解脱出来,根据自己的兴趣,广泛地阅读经史文章、佛书道籍,以至兵书术数等百家之书,几乎已到无所不读的地步,从而奠定了他成为知识广博、思想丰富的一代大儒和文化伟人所需的学养基础。
在儒者看来,做人须明理,而明理必读书。朱熹二十岁左右是一个全面读书的时期,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语类》卷一〇四)他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好读书而求甚解,每一类都记有两厚册的读书心得。就佛书而言,他所涉猎的自然不止当代僧人编撰的著作,佛教的一些重要典籍,如《心经》、《楞严经》、《圆觉经》、《严华经》、《金刚经》、《坛经》等,他都做过认真的研读,而且有极精辟的见解。如他认为《心经》是由卷帙庞大的《大般若经》节缩而成,《楞严经》前后只是说咒,中间部分是中土的好佛者所增添进去的。《圆觉经》只有前两三卷好,后面强说部分为文章之士所添。《金刚经》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只是教人“无心了方是”,要之只是说个无。在常见的佛典里,《华严经》的论说比较精密。
正是这种对佛书的潜心研读,把朱熹引向了直接习佛参禅路。他在《答汪尚书》里谈到师事李侗之前的求学经历时说:“熹于释氏之说,盖当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所谓“未能有得”当然不只是谦虚之语,原因容当后说,先讲“盖当师其人”的人是谁?由于朱熹成为大儒后,讳言自己在求学过程中曾师事过禅师的事,以致此事显得有些扑朔迷离。但李侗在《与罗博文书》里谈到朱熹时,说他“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这“谦开善”指的是开善寺出身的禅师道谦,一位得“佛日”宗杲真传的高僧。道谦是武夷三先生的禅友兼诗友,曾结密庵于建宁的清湍亭附近,朱熹的《游密庵》和《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分韵赋诗得竹字》等诗作,就透露出了他师事道谦的情况。在后一首诗中,有“再拜仰高山,悚然心神肃。我生虽已后,久此寄斋粥”之语,对道谦的崇敬溢于言表。
那么,朱熹究竟从禅师道谦处学到了什么呢?
道谦与宗杲一样,都是善于用禅宗公案里玄妙的“话头”或“机锋语”启示信徒的禅师。在《罗湖野录》里,有一封道谦论禅的信,他认为禅悟别无功夫,只是将心识上所有的东西一时放下即可,故“行住坐卧决定不是,见闻觉知决定不是,思量分别决定不是,语言问答决定不是”,要人言语断道,豁然顿悟。也就是说,要摒弃一切外在的言行见闻,也不能有觉知思量,全凭自己内心直觉就里面体认。既不能用闻见知觉,又不能用语言思维,那禅师将如何启人顿悟,以印证心底里“昭昭灵灵的禅”呢?他说:“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云‘无’;‘如何是佛’,云门道‘干屎橛’。管取呵呵大笑。”这与佛教传说中的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有异曲同工之妙。
狗子有佛性无、佛在干屎橛以及佛法麻三斤等,本来都是唐代禅师在回答僧徒提出的关于佛性、佛和佛法等问题时的答非所问之语。按照禅宗“明心见性”之说,不能自悟本心而还要向人求教,就是骑驴找驴,永远难成正果。佛性、佛与佛法就在自性之中,所以禅悟只能是自悟,是一种具有神秘内心体验的直觉,不可言说,更不可思议。一言说、一思议即非禅,故高明的禅师往往用些答非所问之语将求教者的言说和思议堵回去。这些答非所问之语原只是禅师破口说出的不言之言,本身毫无意义,但却有如对请教者的当头棒喝,使其惊骇,以为藏有玄门机锋,颇费参寻。到后来,此等语就成为一种禅宗公案里的“话头”,所谓“看话禅”,就是要人能由这些“话头”悟入,故狗子佛性、干屎橛、麻三斤等,也就成为道谦用来印证“昭昭灵灵的禅”的平常话头了。
在《归元直指集》里,有朱熹向道谦问禅的记载。朱熹态度很虔诚地问:“狗子佛性话头未有悟入,愿授一言,警所不逮。”但道谦终于没有回答。若要回答,也不过是麻三斤或干屎橛一类的话头,与狗子佛性的话头乃大同小异。本来禅宗的“话头”就是不可思议的,而朱熹偏要思议,问个究竟,未能管取呵呵大笑,有会于心,而是想要求甚解,把握其能言说的道理,路头一差,越走离禅越远,其结果只能是“未能有得”了。
朱熹是以儒者读书做学问的态度来习佛参禅的,想心空悟理,弄个明白,而禅悟多少带有宗教信仰的神秘色彩。凡有关信仰的事,有时并无多少道理可讲,理必无者,事或有之,信之则有,不信则无。若对禅宗“话头”真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它也就失去了玄妙的机锋,变得很简单、很平常了。正如后来朱熹所说:
禅只是一个呆守法,如麻三斤、干屎橛,他道理初不在这上,只是叫他麻了心,只思量这一路,专一积久,忽有见处,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会散乱,久后光明自发。(《语类》卷一二六)
这是朱熹逃禅归儒后,对“昭昭灵灵”的“看话禅”所做的剖析和说明。他认为禅门中的参话头,只是教人心系一处,呆守着有如麻了心一般,心思集中在一处,有如系重石于一发之上,久之,发断石坠地,一时心无所系,空荡荡的,若因此而豁然开朗,如有所见,便可称之为“悟”。其要只是把定一心,令精神镇定,注意力集中,久之忽然自有开悟,如光明自发一般。朱熹认为禅的这种心理直觉体验,与庄子所说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是相同的,本无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宗杲、道谦等人会说,吹嘘得大,所以能鼓动一世人心,吸引众多士人。
毫无疑问,朱熹对看话禅的清晰解剖,实已把握到了当时禅门里的最高秘密,证明他对禅有极真切的了解。只是这种“识庐山真面目”的了解,属于清醒的理性认识,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僧人那种不可思议的直觉体验,是不可同日语的。水至清则无鱼,理至明则无禅。朱熹之所以能由识禅而走向后来的逃禅之路,皆由于好求甚解所至。
这并不意味着习佛参禅的经历对朱熹没起多大的作用。朱熹在道谦那里虽没有获得某种神秘的直觉悟入而成为佛门弟子,但看话禅那种注重专一积久的内心体验的参悟方法,却对其读书生活有重大的影响,成为他融贯儒佛道三家的心学功夫。他认为读书要先定其心,致一而不懈,久之自然会有悟解和心得。他说:“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少间体验得熟,自家之心便是圣人之心。某自二十岁时看道理,便要看那里面。”(《语类》卷一二〇)这一时期,朱熹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牧斋”,牧指牧心。刘子翚《圣传论》说:“善牧心者,摄思虑于未崩之时,……此君子平居自牧,常持以谦之功也。”所以“牧”与“谦”同义,朱熹以“牧”名其书斋,与他师事禅师道谦是有直接联系的。牧心的目的是为了“明心见性”,所谓“摄思虑”,与朱熹论禅悟时所说的“把定一心”意思相同,指的是就里面体认的心学工夫。
收在朱熹《牧斋净稿》中的四十多首诗,有一半是咏叹佛老的,而且都有某种禅悟的味道。如他在《夏日二首》其一里说:“抱疴守穷庐,释志趣幽禅。即此穷日夕,宁为外务牵?”表明自己参禅时用志不分、心不为外务所乱的趣向。朱熹主悟的心学方法和修养功夫,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是他师事道谦的结果。宗杲《正法眼藏》宣扬的那种直指本心、教外别传的心印思想和顿悟方法,通过道谦而传给了朱熹。
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当年轻的朱熹结束泛观博览的读书生活,以朝廷任命的左迪功郎的身份,南下泉州任同安县主簿时,身上还隐约带着一股禅气。到泉州不久,他前往当地最大的名刹开元寺游观礼拜,并用大字书写了一副对联,让人悬挂在寺院门口。对联云:“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将“佛国”与“圣人”并称,反映的正是他以心学融佛老入儒的立场和观点。因为只有从禅宗“以心传心”的立场来谈圣学心传,认为古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心即圣人之心,才有可能得出“满街都是圣人”的结论。而且这里面还含有人人皆有佛性,都可顿悟成佛的佛性论思想。心想圣人而身在佛国,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也可以看作是当时朱熹出入于儒、佛之间的夫子自道。
泉州是禅风炽盛之地,凡山水名胜皆有佛寺,处处香烟缭绕,禅师出没,自唐代以来便有“泉南佛国”之称。处于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会触动朱熹昭昭灵灵的禅心,有了访禅的雅兴。他有一次奉檄往泉州的安溪县按事三日,时间很短,但也要专门抽出一天时间登临安溪县北的凤山,游观建在山上的凭虚阁和通玄庵。在通玄庵,朱熹想到了天台德韶国师于通玄峰顶悟道的禅门故事,于是在庵壁上题写道: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通玄峰顶,不是人间。
这是依照德韶国师的偈颂改写的,只调整了一下句子先后。据说德韶国师曾先后十七次问法于龙牙,一无所获,后来在通玄峰顶洗澡时忽然大悟,写下了这样一首偈颂:“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此偈是德韶国师悟道的标志,所谓“不是人间”,指心外无境,世间一切不过是心的幻影,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唯有心能含识万法,圆成自足,故又云“心外无法”。这种对心空一切的真如佛性的悟解,与法眼宗所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一样的。法眼赞叹说:“即此一偈,可起吾宗。”(《五灯会元》)法眼宗是唐末五代受华严思想影响的禅宗学派,朱熹对华严禅事理圆融的无碍法界之说十分欣赏,所以把德韶国师的这首偈颂熟记在心。当他登上通玄峰顶时,似乎对释氏唯明一心的禅悟有了更深的体会,于是把德韶国师的偈颂巧妙地加以改编,突出了“心外无法”的地位和作用。
这表明朱熹对“昭昭灵灵的禅”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心的作用和精神境界方面。他信奉宋儒效法禅宗“以心传心”而提出的道统心传之说,读书常能以己心体验圣人之心,从以往圣贤著作的字缝中悟出许多义理来,这使他的解经著作带有“昭昭灵灵”的新儒家特色,有别于汉唐旧儒的死守章句。直至晚年,朱熹于酒酣兴逸之际,还用大字书写德韶国师的偈颂赠门徒,再次透露出此中的消息。佛说的迷人处,正在此心方寸之间。
朱熹讲“心外无法”,当然不是要像释氏那样,在把人间万象和客观世界当作心的幻影加以否定的同时,把人的主观世界的心意活动也视为虚妄而加以否定。释氏心空无物,亦无义理,故心也是空,与万象同归于空寂。如“看话禅”的顿悟,指“话头”忽然从心中失去,像打一个失落,一时心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只是空寂。如此讲悟,就连心体也否定掉了,一切都是毕竟空。朱熹在《答张敬夫》书里说:“释氏虽自惟明一心,然实不识心体。”他认为所谓“心外无法”,应当是指天序、天命、恻隐、羞恶、是非一类的义理,莫不该备于心,这实际是在讲天理具于一心,而心外无理了。
如此说,则释氏“明心见性”的禅悟功夫,亦可作为儒者正心诚意的穷理方法。在任同安县主簿期间,朱熹已开始逐步认识到释氏的归心于空寂是不对的,只有以“义理”养心,才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所以他积极整顿县学,在为县学作的《四斋铭》里,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教导学子,后来又把四斋更名为正心、诚意二斋。其思想的变化在斋名上也体现了出来。
当朱熹从“牧斋”里走出来,开始浮沉官场的同安主簿生涯时,过去那种读书养心或参禅悟道而独善其身的生活态度,就被儒者读书明理以求经世治邦的入世精神所代替。这时他听从李侗的劝告,暂且将禅学放在一边,从“面前事”上做起,“于日用处下工夫”,把注意力由空心悟理转到格物穷理方面来,以应事接物的“致知”代替麻了心的“悟入”。后来他正式拜李侗为师后,又一心只读圣贤之书,“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语类》卷一〇四)他认为释氏专一积久的修养功夫,只是让心地空豁豁的,更无一物,不能方外。而儒者的正心诚意功夫,讲究集义养气,心虽虚而理则实,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可施于人伦日用之间,与释氏的一向归于空寂是完全不同的。这促使朱熹从对心空境无的禅悟的迷恋中摆脱出来,返回到儒家修身养性的名教乐园,开始了他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
由此可以看出,儒者的习佛参禅与文人是不同的。宋代文人如苏轼的习佛,是为了求得心灵的平衡与解脱,他们真正醉心于佛说,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坎坷的中晚年,是在看破红尘之后,或者说是在有所觉悟之后。所以他们并不在意于能于佛理中悟到什么,而更乐意描述无所住的清净心境和意态,在想象中进入无差别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但是宋儒如朱熹的出入佛老,多是在年轻时的读书求学期间,他们在习佛参禅过程中总是存有入世之念,总是想于道理方面有所得。当他们明白释氏绝圣弃智的空寂之说,安放不下儒家有益于世用的“实理”时,只好走向弃佛崇儒之路,但他们的内心已非一张白纸,佛禅的心性之说已在他们的心灵和思想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澄心静虑、专一积久的禅学,成为他们虚心悟理的心学工夫和提高精神境界的方法。
在朱熹早年所读的佛书里,对他影响较大的是《正法眼藏》和《大慧语录》,这是径山大慧普觉禅师宗杲融合佛老的代表作。宗杲对其俗门弟子张九成说过这样的话:“老僧东坡后身。”(《宾退录》)身为礼部侍郎的张九成听后亦深以为然。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每年七月逢苏轼去世的忌日,宗杲都要在径山寺举办法会,召集各地门徒,一起祭奠大文豪苏轼的亡灵,仪式搞得非常隆重。
这事是宋代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儒、佛、道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的生动反映。一方面是文人儒者多自称居士,广泛地结交僧人道士,以内佛外儒的面貌出现。苏轼就被苏门文人说成是五祖戒禅师之后身。张九成年轻时师事南宋著名理学家杨时,为二程的再传弟子,但他特别嗜好禅学而拜在宗杲门下,用佛理来解释儒家经典,在南宋初期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僧人的士大夫化,和尚谈诗论艺,用儒家思想装点门面。宋初就有诗僧的大量涌现,到了大慧禅师宗杲,则干脆自称自己是著名文人的后身。这样做的结果,宗杲在给张九成的《答张子韶侍郎书》里说得很明白,即“可改头换面,却用儒家言语,说向士大夫接引”,这一切无疑都有利于佛道思想的社会扩散。
在南宋初年,禅学风靡士林,宗杲成了僧、俗两界所礼拜的“佛日”和精神领袖。其《正法眼藏》在绍兴十一年(1141)编成后风行一时,成为许多士人喜欢读的书,而此书前面便有宗杲的《答张子韶侍郎书》。朱熹成长于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深受当时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他在《久雨斋居诵经》一诗里说:
端坐独无事,聊披释氏书。
暂息尘累牵,超然与道俱。
朱熹青少年的大部分时光在书斋里度过,他端居陋室,苦读经书,以求明了圣人之心。但这仅靠过去汉儒那种章句训诂之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一种就心里体认的参悟功夫,而这正是释氏禅学之所长,故他把读经与习佛参禅结合起来。在《答孙敬甫》书中,他说自己少时喜读有关禅学的文字,读了宗杲的《答张子韶侍郎书》,知道禅师是如何改头换面而援佛入儒,所以后来一见张九成的解经文字,即知是禅者之经。这正好说明朱熹早年的读书治学,走的也是援佛入儒的路子,对禅学有较深入的了解。
朱熹的启蒙老师、他的父亲朱松,入闽后耽好佛老,广交僧人道士朋友,一起吟诗论文,谈禅说法。叔父朱槔亦喜好佛说。朱松去世后,少年朱熹尊父嘱前往崇安,所师事的武夷三先生(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也都是喜与佛老之徒交游的儒者。其中对朱熹思想影响较大的是刘子翚,他与宗杲及其门徒交游颇密,有书信往来,常在一起谈禅论道。
朱熹说他十五六岁时曾留心于禅学,有一天刘子翚在家里会见一位僧人,与之谈禅。当时刘子翚谈的是天童正觉一派的默照禅,主张静坐时进行内心观照,凝神静虑,除去妄念而照见实相。那僧人开始不置可否,敷衍了一番后才言道:“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的禅。”这“昭昭灵灵”属于径山宗杲一派的“看话禅”,主参悟而不重静坐,要求能“于日用中看话头”而证悟,强调以心传心。这种禅学方法适应了当时朱熹读书求心有所悟的需要,立即引起了他的兴趣和注意,认为“此僧更有要妙处在”(《语类》卷一〇四)。过后他便去向这位僧人求教,觉得他的“昭昭灵灵”之禅说得特别好。所谓“昭昭灵灵”,也就是朱熹在诗里讲的“超然与道俱”的闻言顿悟,是一种重内心领悟的禅学方法。
据今人束景南《朱子大传》考证,当时朱熹所求教的那位僧人,是宗杲的门徒道谦禅师,宗杲的《大慧语录》一书就是由他编定的。《大慧语录》里有宗杲给刘子翚的信,批评刘子翚讲的静坐默照是“修行都不会禅”,认为“看话禅”的主悟是“一了一切了,一悟一切悟,一证一切证,如斩一结丝,一斩一时断,证无边法门亦然”。这当然比单纯的静坐内观修炼要痛快得多。不是要人遁世静坐,而是要人于世间日用中悟入,把佛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对朱熹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对于一个未经过大的人生磨难而心存用世之志的年轻人来说,习佛参禅与其说是出于摆脱尘世恼烦的解脱需要,毋宁说成是游心于玄妙之境的心智锻炼。绍兴十八年(1148)春,学有所成的朱熹顺利通过乡员考试,只身远游,跨越分水岭,赴京师临安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此时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应举士子的随身行李中,只带了一本宗杲的《大慧语录》。这年的礼部考试分三场:首场经术,考《周易》、《论语》、《孟子》;第二场为诗、赋;第三场以子、史、论时务策为题。朱熹的经术考得比较顺利,而礼部取士以经术为先,故一举金榜高中。朱熹之所以能中举,据他自己说,是因为采用从道谦那里学来的昭昭灵灵的禅说答题,援佛入儒,标新立异,从而说动了考官的缘故。尽管朱熹把这说成是用僧人的意思去“胡说”,却是他这次登进士第的决定性因素,不料原本是出世的禅学,竟成为应举士子入仕的敲门砖。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进士中举对于古代读书人的一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生虽漫长,关键的有时只是那么几步。径山宗杲一派的“看话禅”,在朱熹猎取功名、迈向社会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仅是他直接师事道谦的契机,也决定了他较长一段时间里的读书求学,走的是以心观心,就里面体认的心学“悟入”之路。科举场上的早年得志,使朱熹能从为应付科举考试的经书记诵和程文研习中解脱出来,根据自己的兴趣,广泛地阅读经史文章、佛书道籍,以至兵书术数等百家之书,几乎已到无所不读的地步,从而奠定了他成为知识广博、思想丰富的一代大儒和文化伟人所需的学养基础。
在儒者看来,做人须明理,而明理必读书。朱熹二十岁左右是一个全面读书的时期,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语类》卷一〇四)他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好读书而求甚解,每一类都记有两厚册的读书心得。就佛书而言,他所涉猎的自然不止当代僧人编撰的著作,佛教的一些重要典籍,如《心经》、《楞严经》、《圆觉经》、《严华经》、《金刚经》、《坛经》等,他都做过认真的研读,而且有极精辟的见解。如他认为《心经》是由卷帙庞大的《大般若经》节缩而成,《楞严经》前后只是说咒,中间部分是中土的好佛者所增添进去的。《圆觉经》只有前两三卷好,后面强说部分为文章之士所添。《金刚经》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只是教人“无心了方是”,要之只是说个无。在常见的佛典里,《华严经》的论说比较精密。
正是这种对佛书的潜心研读,把朱熹引向了直接习佛参禅路。他在《答汪尚书》里谈到师事李侗之前的求学经历时说:“熹于释氏之说,盖当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所谓“未能有得”当然不只是谦虚之语,原因容当后说,先讲“盖当师其人”的人是谁?由于朱熹成为大儒后,讳言自己在求学过程中曾师事过禅师的事,以致此事显得有些扑朔迷离。但李侗在《与罗博文书》里谈到朱熹时,说他“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这“谦开善”指的是开善寺出身的禅师道谦,一位得“佛日”宗杲真传的高僧。道谦是武夷三先生的禅友兼诗友,曾结密庵于建宁的清湍亭附近,朱熹的《游密庵》和《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分韵赋诗得竹字》等诗作,就透露出了他师事道谦的情况。在后一首诗中,有“再拜仰高山,悚然心神肃。我生虽已后,久此寄斋粥”之语,对道谦的崇敬溢于言表。
那么,朱熹究竟从禅师道谦处学到了什么呢?
道谦与宗杲一样,都是善于用禅宗公案里玄妙的“话头”或“机锋语”启示信徒的禅师。在《罗湖野录》里,有一封道谦论禅的信,他认为禅悟别无功夫,只是将心识上所有的东西一时放下即可,故“行住坐卧决定不是,见闻觉知决定不是,思量分别决定不是,语言问答决定不是”,要人言语断道,豁然顿悟。也就是说,要摒弃一切外在的言行见闻,也不能有觉知思量,全凭自己内心直觉就里面体认。既不能用闻见知觉,又不能用语言思维,那禅师将如何启人顿悟,以印证心底里“昭昭灵灵的禅”呢?他说:“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云‘无’;‘如何是佛’,云门道‘干屎橛’。管取呵呵大笑。”这与佛教传说中的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有异曲同工之妙。
狗子有佛性无、佛在干屎橛以及佛法麻三斤等,本来都是唐代禅师在回答僧徒提出的关于佛性、佛和佛法等问题时的答非所问之语。按照禅宗“明心见性”之说,不能自悟本心而还要向人求教,就是骑驴找驴,永远难成正果。佛性、佛与佛法就在自性之中,所以禅悟只能是自悟,是一种具有神秘内心体验的直觉,不可言说,更不可思议。一言说、一思议即非禅,故高明的禅师往往用些答非所问之语将求教者的言说和思议堵回去。这些答非所问之语原只是禅师破口说出的不言之言,本身毫无意义,但却有如对请教者的当头棒喝,使其惊骇,以为藏有玄门机锋,颇费参寻。到后来,此等语就成为一种禅宗公案里的“话头”,所谓“看话禅”,就是要人能由这些“话头”悟入,故狗子佛性、干屎橛、麻三斤等,也就成为道谦用来印证“昭昭灵灵的禅”的平常话头了。
在《归元直指集》里,有朱熹向道谦问禅的记载。朱熹态度很虔诚地问:“狗子佛性话头未有悟入,愿授一言,警所不逮。”但道谦终于没有回答。若要回答,也不过是麻三斤或干屎橛一类的话头,与狗子佛性的话头乃大同小异。本来禅宗的“话头”就是不可思议的,而朱熹偏要思议,问个究竟,未能管取呵呵大笑,有会于心,而是想要求甚解,把握其能言说的道理,路头一差,越走离禅越远,其结果只能是“未能有得”了。
朱熹是以儒者读书做学问的态度来习佛参禅的,想心空悟理,弄个明白,而禅悟多少带有宗教信仰的神秘色彩。凡有关信仰的事,有时并无多少道理可讲,理必无者,事或有之,信之则有,不信则无。若对禅宗“话头”真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它也就失去了玄妙的机锋,变得很简单、很平常了。正如后来朱熹所说:
禅只是一个呆守法,如麻三斤、干屎橛,他道理初不在这上,只是叫他麻了心,只思量这一路,专一积久,忽有见处,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会散乱,久后光明自发。(《语类》卷一二六)
这是朱熹逃禅归儒后,对“昭昭灵灵”的“看话禅”所做的剖析和说明。他认为禅门中的参话头,只是教人心系一处,呆守着有如麻了心一般,心思集中在一处,有如系重石于一发之上,久之,发断石坠地,一时心无所系,空荡荡的,若因此而豁然开朗,如有所见,便可称之为“悟”。其要只是把定一心,令精神镇定,注意力集中,久之忽然自有开悟,如光明自发一般。朱熹认为禅的这种心理直觉体验,与庄子所说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是相同的,本无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宗杲、道谦等人会说,吹嘘得大,所以能鼓动一世人心,吸引众多士人。
毫无疑问,朱熹对看话禅的清晰解剖,实已把握到了当时禅门里的最高秘密,证明他对禅有极真切的了解。只是这种“识庐山真面目”的了解,属于清醒的理性认识,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僧人那种不可思议的直觉体验,是不可同日语的。水至清则无鱼,理至明则无禅。朱熹之所以能由识禅而走向后来的逃禅之路,皆由于好求甚解所至。
这并不意味着习佛参禅的经历对朱熹没起多大的作用。朱熹在道谦那里虽没有获得某种神秘的直觉悟入而成为佛门弟子,但看话禅那种注重专一积久的内心体验的参悟方法,却对其读书生活有重大的影响,成为他融贯儒佛道三家的心学功夫。他认为读书要先定其心,致一而不懈,久之自然会有悟解和心得。他说:“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少间体验得熟,自家之心便是圣人之心。某自二十岁时看道理,便要看那里面。”(《语类》卷一二〇)这一时期,朱熹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牧斋”,牧指牧心。刘子翚《圣传论》说:“善牧心者,摄思虑于未崩之时,……此君子平居自牧,常持以谦之功也。”所以“牧”与“谦”同义,朱熹以“牧”名其书斋,与他师事禅师道谦是有直接联系的。牧心的目的是为了“明心见性”,所谓“摄思虑”,与朱熹论禅悟时所说的“把定一心”意思相同,指的是就里面体认的心学工夫。
收在朱熹《牧斋净稿》中的四十多首诗,有一半是咏叹佛老的,而且都有某种禅悟的味道。如他在《夏日二首》其一里说:“抱疴守穷庐,释志趣幽禅。即此穷日夕,宁为外务牵?”表明自己参禅时用志不分、心不为外务所乱的趣向。朱熹主悟的心学方法和修养功夫,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是他师事道谦的结果。宗杲《正法眼藏》宣扬的那种直指本心、教外别传的心印思想和顿悟方法,通过道谦而传给了朱熹。
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当年轻的朱熹结束泛观博览的读书生活,以朝廷任命的左迪功郎的身份,南下泉州任同安县主簿时,身上还隐约带着一股禅气。到泉州不久,他前往当地最大的名刹开元寺游观礼拜,并用大字书写了一副对联,让人悬挂在寺院门口。对联云:“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将“佛国”与“圣人”并称,反映的正是他以心学融佛老入儒的立场和观点。因为只有从禅宗“以心传心”的立场来谈圣学心传,认为古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心即圣人之心,才有可能得出“满街都是圣人”的结论。而且这里面还含有人人皆有佛性,都可顿悟成佛的佛性论思想。心想圣人而身在佛国,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也可以看作是当时朱熹出入于儒、佛之间的夫子自道。
泉州是禅风炽盛之地,凡山水名胜皆有佛寺,处处香烟缭绕,禅师出没,自唐代以来便有“泉南佛国”之称。处于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会触动朱熹昭昭灵灵的禅心,有了访禅的雅兴。他有一次奉檄往泉州的安溪县按事三日,时间很短,但也要专门抽出一天时间登临安溪县北的凤山,游观建在山上的凭虚阁和通玄庵。在通玄庵,朱熹想到了天台德韶国师于通玄峰顶悟道的禅门故事,于是在庵壁上题写道: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通玄峰顶,不是人间。
这是依照德韶国师的偈颂改写的,只调整了一下句子先后。据说德韶国师曾先后十七次问法于龙牙,一无所获,后来在通玄峰顶洗澡时忽然大悟,写下了这样一首偈颂:“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此偈是德韶国师悟道的标志,所谓“不是人间”,指心外无境,世间一切不过是心的幻影,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唯有心能含识万法,圆成自足,故又云“心外无法”。这种对心空一切的真如佛性的悟解,与法眼宗所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一样的。法眼赞叹说:“即此一偈,可起吾宗。”(《五灯会元》)法眼宗是唐末五代受华严思想影响的禅宗学派,朱熹对华严禅事理圆融的无碍法界之说十分欣赏,所以把德韶国师的这首偈颂熟记在心。当他登上通玄峰顶时,似乎对释氏唯明一心的禅悟有了更深的体会,于是把德韶国师的偈颂巧妙地加以改编,突出了“心外无法”的地位和作用。
这表明朱熹对“昭昭灵灵的禅”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心的作用和精神境界方面。他信奉宋儒效法禅宗“以心传心”而提出的道统心传之说,读书常能以己心体验圣人之心,从以往圣贤著作的字缝中悟出许多义理来,这使他的解经著作带有“昭昭灵灵”的新儒家特色,有别于汉唐旧儒的死守章句。直至晚年,朱熹于酒酣兴逸之际,还用大字书写德韶国师的偈颂赠门徒,再次透露出此中的消息。佛说的迷人处,正在此心方寸之间。
朱熹讲“心外无法”,当然不是要像释氏那样,在把人间万象和客观世界当作心的幻影加以否定的同时,把人的主观世界的心意活动也视为虚妄而加以否定。释氏心空无物,亦无义理,故心也是空,与万象同归于空寂。如“看话禅”的顿悟,指“话头”忽然从心中失去,像打一个失落,一时心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只是空寂。如此讲悟,就连心体也否定掉了,一切都是毕竟空。朱熹在《答张敬夫》书里说:“释氏虽自惟明一心,然实不识心体。”他认为所谓“心外无法”,应当是指天序、天命、恻隐、羞恶、是非一类的义理,莫不该备于心,这实际是在讲天理具于一心,而心外无理了。
如此说,则释氏“明心见性”的禅悟功夫,亦可作为儒者正心诚意的穷理方法。在任同安县主簿期间,朱熹已开始逐步认识到释氏的归心于空寂是不对的,只有以“义理”养心,才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所以他积极整顿县学,在为县学作的《四斋铭》里,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教导学子,后来又把四斋更名为正心、诚意二斋。其思想的变化在斋名上也体现了出来。
当朱熹从“牧斋”里走出来,开始浮沉官场的同安主簿生涯时,过去那种读书养心或参禅悟道而独善其身的生活态度,就被儒者读书明理以求经世治邦的入世精神所代替。这时他听从李侗的劝告,暂且将禅学放在一边,从“面前事”上做起,“于日用处下工夫”,把注意力由空心悟理转到格物穷理方面来,以应事接物的“致知”代替麻了心的“悟入”。后来他正式拜李侗为师后,又一心只读圣贤之书,“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语类》卷一〇四)他认为释氏专一积久的修养功夫,只是让心地空豁豁的,更无一物,不能方外。而儒者的正心诚意功夫,讲究集义养气,心虽虚而理则实,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可施于人伦日用之间,与释氏的一向归于空寂是完全不同的。这促使朱熹从对心空境无的禅悟的迷恋中摆脱出来,返回到儒家修身养性的名教乐园,开始了他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
由此可以看出,儒者的习佛参禅与文人是不同的。宋代文人如苏轼的习佛,是为了求得心灵的平衡与解脱,他们真正醉心于佛说,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坎坷的中晚年,是在看破红尘之后,或者说是在有所觉悟之后。所以他们并不在意于能于佛理中悟到什么,而更乐意描述无所住的清净心境和意态,在想象中进入无差别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但是宋儒如朱熹的出入佛老,多是在年轻时的读书求学期间,他们在习佛参禅过程中总是存有入世之念,总是想于道理方面有所得。当他们明白释氏绝圣弃智的空寂之说,安放不下儒家有益于世用的“实理”时,只好走向弃佛崇儒之路,但他们的内心已非一张白纸,佛禅的心性之说已在他们的心灵和思想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澄心静虑、专一积久的禅学,成为他们虚心悟理的心学工夫和提高精神境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