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性从夫及其变通
| 内容出处: |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887 |
| 颗粒名称: | (三)女性从夫及其变通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 |
| 页码: | 358-363 |
| 摘要: | 这段文字指出了过去对于宋代儒者的女性观念进行批评的态度,即女性在婚前依从父亲,婚后依从丈夫,丈夫去世后依从子女。同时也提到了中国传统礼制对女性的束缚,这种束缚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女性与丈夫、翁姑、子女之间的关系常常非常复杂,各种形式各异。因此,在司法过程中,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官员往往需要在具体问题上采取相对灵活的处理方式,以维护社会的相对公平。 |
| 关键词: | 黄榦 女性 变通 |
内容
以往的论者对于宋代儒者的女性观念颇有指责,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①。其实,中国传统礼制对于女性的约束,由来已久。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女性与丈夫、女性与翁姑、女性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往往相当复杂,形态各异。而当司法过程中遇到许多不同的案件时,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官员,就不能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采取相对变通的处理方式,以维护社会的相对公平。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中有《徐家论陈家取去媳妇及田产》一案,说的是陈氏妇人嫁往徐氏为妻,并有陪嫁田产。陈氏妇人与徐氏丈夫生活多年,育有子女四人,后来不幸夫亡,其陈氏娘家怂恿陈氏妇人回居娘家,索回当初陪嫁的田产。陈氏娘家此举,纯为陪嫁的田产,因此,黄榦在判词中这样写道:
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是以夫之家为其家也。妇人谓嫁曰归,是以得嫁为得所归也。莫重于夫、莫尊于姑、莫亲于子,一齐而不可变,岂可以生死易其心哉?陈氏之为徐孟彝之妻,则以徐孟彝之家为其家,而得所归矣。不幸而夫死,必当体其夫之意,事其姑终身焉。假使无子,犹不可归,况有女三人、有男一人,携之以归其父之家犹不可,况弃之而去?既不以身奉其姑,而反以其子累其姑,此岂复有人道乎?父给田而予之嫁,是为徐氏之田矣。夫置田而以装奁为名,是亦徐氏之田也,陈氏岂得而有之?使徐氏无子,则陈氏取其田以为己有可也,况有子四人,则自当以田分其诸子,岂得取其田而弃诸子乎?使陈氏果有此志,陈文明为之父、陈伯洪为之兄,尚当力戒之,岂得容之使归,反助之为不义乎?察其事情,未必出于陈氏之本意,乃陈文明、陈伯洪实为此举也。陈文明独无儿妇乎?使伯洪死其妻亦弃其子以累其父母,取其田而自归,陈文明岂得无词乎?陈氏一妇人,陈文明亦老矣,其实则陈伯洪之罪也。知军吴寺簿不察此义,反将徐孟彝之弟徐善英勘断以为不应教其母争讼,是纵陈氏为不义也。欲将陈伯洪从杖六十,勘断押陈氏归徐家。仍监将两项田听从徐氏收管,花利教其子、嫁其女,庶得允当。申提刑使衙取旨挥一行人召保。①
在这个案件中,黄榦根据“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礼制原则,判定陈氏夫人既为徐孟彝之妻,“则以徐孟彝之家为其家,而得所归矣”。虽然丈夫已去世,但是作为徐家之人,其所有财产自然应该归属于徐家。即使陈氏最终去世,这些财产也应该由徐氏儿子继承。因此,其娘家是没有权力收回陪嫁的妆奁田产的。而其娘家妄行取回陈氏及田产,实为不义,故应予以惩处,“将陈伯洪从杖六十,勘断押陈氏归徐家”。
陈氏与徐氏两家的关系相对简单,虽然因为陈氏娘家贪图取回妆奁田产而产生诉讼,但是毕竟事由仅涉两家,官司易判。而下面这件关于《京宣义诉曾嵓叟取妻归葬》的案件,关系就相当复杂了。该案件事由如下:
京宣义经使军陈词,取妻周氏归葬。使军行下本县详状照条施行,本县遂追周氏之兄周司户及周氏前夫之子曾嵓叟供对。今据两家干人赍出周司户之才及曾嵓叟状词前来出官,今看详周氏初嫁曾氏,再嫁赵副将,又再嫁京宣义,则周氏于曾家之义绝矣。既为京宣义之妻,则其死也,当归葬于京氏。然考其岁月,京宣义以开禧二年十一月娶周氏为妻,次年八月取归隆兴府,经及两月,周氏以京宣义溺于嬖妾,遂逃归曾家。自后京宣义赴池阳丞,周氏不复随往。至去年八月间,周氏身死,京宣义与周氏为夫妇,仅及一年,则已反目不相顾矣。既溺于嬖妾,无复伉俪之情;又携其妾之官,而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凡四年,又岂复有夫妇之义乎?周氏于曾家固为义绝,而京宣义之于周氏,亦不复有夫妇之义矣。使京宣义于周氏果有夫妇之义,则不应溺嬖妾而弃正室,又不应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数年,而挈其妾以之官。生而弃之而不顾,死则欲夺以归葬,此岂出于死则同穴之至情乎?特欲骚扰曾嵓叟之家,以装奁诬赖,因以为利耳。此岂士大夫之所当为哉?其说以为始乃娶赵副将之妻,不应曾嵓叟占留以葬,独不思周氏之嫁京宣义,乃自曾家出嫁,其避京宣义之妾而归也,亦归于曾家,岂得以为与曾家无干涉乎?周氏于曾固为义绝,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听改嫁。今京宣义弃周氏而去,亦绝矣。以义断之,则两家皆为义绝,以恩处之,则京宣义于周氏绝无夫妇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则未尝替也。京宣义公相之子孙,名在仕版,不应为此闾巷之态,妄生词诉周氏之丧。乞行下听从曾嵓叟安葬,仍乞告示京宣义,不得更有词诉。申使军取旨挥干人留领断由讫放。①
这个案件的事由甚为特殊,周氏夫人曾经嫁给三夫,“初嫁曾氏,再嫁赵副将,又再嫁京宣义”。初嫁曾氏时,生有儿子。三嫁京宣义之后,虽然名义上为京家之妻,但是京宣义沉溺于嬖妾之欢,于周氏毫无感情,“京宣义与周氏为夫妇,仅及一年,则已反目不相顾矣。既溺于嬖妾,无复伉俪之情”。周氏在京家既无女主人的地位,只好回到曾家,与自己的儿子相依过日子。而当周氏去世后,京宣义却经使军陈词,诉求取妻周氏归葬。对于这个案件,黄榦认为,周氏一再改嫁,与出嫁的曾家之义已绝;但是现嫁给京宣义为妻,二者没有真正的夫妻感情,京宣义“携其妾之官,而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凡四年,又岂复有夫妇之义乎?”,因此从家庭夫妻之义而言,周氏与曾家、京家均已不存在“夫妻之义”,故京宣义诉求取妻周氏归葬,于义无据。“生而弃之而不顾,死则欲夺以归葬,此岂出于死则同穴之至情乎?”然而周氏于曾家,虽然从夫妻之义的角度讲,“固为义绝”,但是宋代的法律规定:“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听改嫁。”以恩情度之,“则京宣义于周氏绝无夫妇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则未尝替也”。因此黄榦判定,周氏归于曾家安葬拜祭,京家不得妄行争执归葬。“乞行下听从曾嵓叟安葬,仍乞告示京宣义,不得更有词诉。”在这个案件的审理中,黄榦既不是根据所谓的妇女贞洁的原则,也不是根据犹如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既嫁从夫的现实原则,而是以夫妻的真实感情作为判案的原则。夫妻既无感情,恩与义并绝,周氏就只能判给义绝而恩存的曾家了。这一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黄榦作为一名关心社会现实的儒者,在坚持义理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情理变通的经世原则。①
从黄榦在司法实践中对妇女地位的认知这一事实,我们又可以从中看出最为后世所诟病的妇女“贞节观”在宋代实施的某些侧面。在上举的许多案例中,妇女改嫁的事情屡有发生,黄榦对于改嫁女性的案件判决,一般都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就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看,一般皆以为,中国社会对妇女守节方面的态度,存在一个演进的过程,虽然“从一而终”的妇女贞节一直受到高度认同,但是在明代以前,对礼教最具敏感度的士人,在其文集中,一般也不忌讳记载再嫁的妇女。同时,无论是宗室贵族还是士大夫官员,对于家族中的妇女再嫁,或娶再嫁的妇女,也不介意,或者说,即使介意,也不是最优先的考量。与之相比,门第或经济等因素显然更为重要。宋代之前,妇女仍然拥有选择再嫁的自由与空间,自周迄宋,妇女皆不讳再嫁。②我们从黄榦的判词中,再一次印证了宋代妇女贞节问题的这一事实。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以及社会上的认知,往往把中国妇女贞节的非人道化归咎于宋儒特别是宋代的理学家们。诚然,一部分宋儒确实把妇女的贞节观念提高到泛道德化的高度。特别是理学家程颐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言论,在中国妇女贞节观的历史演变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把妇女的贞节纳入到“天理”的范畴,使原本特出的道德行为开始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而就理学系统而言,天理是内于人心的,这就将原本是随机发生的道德实践赋予了普遍化的意涵。”③后世对于妇女贞节问题的认知,往往以宋儒程颐的这一极端言论而加以叙述。但是,同样作为儒者、理学家,又是程颐的晚辈的黄榦,却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对妇女的贞节问题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则我们今天对于宋儒们在妇女观上的评价,似不宜一概而论。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中有《徐家论陈家取去媳妇及田产》一案,说的是陈氏妇人嫁往徐氏为妻,并有陪嫁田产。陈氏妇人与徐氏丈夫生活多年,育有子女四人,后来不幸夫亡,其陈氏娘家怂恿陈氏妇人回居娘家,索回当初陪嫁的田产。陈氏娘家此举,纯为陪嫁的田产,因此,黄榦在判词中这样写道:
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是以夫之家为其家也。妇人谓嫁曰归,是以得嫁为得所归也。莫重于夫、莫尊于姑、莫亲于子,一齐而不可变,岂可以生死易其心哉?陈氏之为徐孟彝之妻,则以徐孟彝之家为其家,而得所归矣。不幸而夫死,必当体其夫之意,事其姑终身焉。假使无子,犹不可归,况有女三人、有男一人,携之以归其父之家犹不可,况弃之而去?既不以身奉其姑,而反以其子累其姑,此岂复有人道乎?父给田而予之嫁,是为徐氏之田矣。夫置田而以装奁为名,是亦徐氏之田也,陈氏岂得而有之?使徐氏无子,则陈氏取其田以为己有可也,况有子四人,则自当以田分其诸子,岂得取其田而弃诸子乎?使陈氏果有此志,陈文明为之父、陈伯洪为之兄,尚当力戒之,岂得容之使归,反助之为不义乎?察其事情,未必出于陈氏之本意,乃陈文明、陈伯洪实为此举也。陈文明独无儿妇乎?使伯洪死其妻亦弃其子以累其父母,取其田而自归,陈文明岂得无词乎?陈氏一妇人,陈文明亦老矣,其实则陈伯洪之罪也。知军吴寺簿不察此义,反将徐孟彝之弟徐善英勘断以为不应教其母争讼,是纵陈氏为不义也。欲将陈伯洪从杖六十,勘断押陈氏归徐家。仍监将两项田听从徐氏收管,花利教其子、嫁其女,庶得允当。申提刑使衙取旨挥一行人召保。①
在这个案件中,黄榦根据“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礼制原则,判定陈氏夫人既为徐孟彝之妻,“则以徐孟彝之家为其家,而得所归矣”。虽然丈夫已去世,但是作为徐家之人,其所有财产自然应该归属于徐家。即使陈氏最终去世,这些财产也应该由徐氏儿子继承。因此,其娘家是没有权力收回陪嫁的妆奁田产的。而其娘家妄行取回陈氏及田产,实为不义,故应予以惩处,“将陈伯洪从杖六十,勘断押陈氏归徐家”。
陈氏与徐氏两家的关系相对简单,虽然因为陈氏娘家贪图取回妆奁田产而产生诉讼,但是毕竟事由仅涉两家,官司易判。而下面这件关于《京宣义诉曾嵓叟取妻归葬》的案件,关系就相当复杂了。该案件事由如下:
京宣义经使军陈词,取妻周氏归葬。使军行下本县详状照条施行,本县遂追周氏之兄周司户及周氏前夫之子曾嵓叟供对。今据两家干人赍出周司户之才及曾嵓叟状词前来出官,今看详周氏初嫁曾氏,再嫁赵副将,又再嫁京宣义,则周氏于曾家之义绝矣。既为京宣义之妻,则其死也,当归葬于京氏。然考其岁月,京宣义以开禧二年十一月娶周氏为妻,次年八月取归隆兴府,经及两月,周氏以京宣义溺于嬖妾,遂逃归曾家。自后京宣义赴池阳丞,周氏不复随往。至去年八月间,周氏身死,京宣义与周氏为夫妇,仅及一年,则已反目不相顾矣。既溺于嬖妾,无复伉俪之情;又携其妾之官,而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凡四年,又岂复有夫妇之义乎?周氏于曾家固为义绝,而京宣义之于周氏,亦不复有夫妇之义矣。使京宣义于周氏果有夫妇之义,则不应溺嬖妾而弃正室,又不应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数年,而挈其妾以之官。生而弃之而不顾,死则欲夺以归葬,此岂出于死则同穴之至情乎?特欲骚扰曾嵓叟之家,以装奁诬赖,因以为利耳。此岂士大夫之所当为哉?其说以为始乃娶赵副将之妻,不应曾嵓叟占留以葬,独不思周氏之嫁京宣义,乃自曾家出嫁,其避京宣义之妾而归也,亦归于曾家,岂得以为与曾家无干涉乎?周氏于曾固为义绝,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听改嫁。今京宣义弃周氏而去,亦绝矣。以义断之,则两家皆为义绝,以恩处之,则京宣义于周氏绝无夫妇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则未尝替也。京宣义公相之子孙,名在仕版,不应为此闾巷之态,妄生词诉周氏之丧。乞行下听从曾嵓叟安葬,仍乞告示京宣义,不得更有词诉。申使军取旨挥干人留领断由讫放。①
这个案件的事由甚为特殊,周氏夫人曾经嫁给三夫,“初嫁曾氏,再嫁赵副将,又再嫁京宣义”。初嫁曾氏时,生有儿子。三嫁京宣义之后,虽然名义上为京家之妻,但是京宣义沉溺于嬖妾之欢,于周氏毫无感情,“京宣义与周氏为夫妇,仅及一年,则已反目不相顾矣。既溺于嬖妾,无复伉俪之情”。周氏在京家既无女主人的地位,只好回到曾家,与自己的儿子相依过日子。而当周氏去世后,京宣义却经使军陈词,诉求取妻周氏归葬。对于这个案件,黄榦认为,周氏一再改嫁,与出嫁的曾家之义已绝;但是现嫁给京宣义为妻,二者没有真正的夫妻感情,京宣义“携其妾之官,而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凡四年,又岂复有夫妇之义乎?”,因此从家庭夫妻之义而言,周氏与曾家、京家均已不存在“夫妻之义”,故京宣义诉求取妻周氏归葬,于义无据。“生而弃之而不顾,死则欲夺以归葬,此岂出于死则同穴之至情乎?”然而周氏于曾家,虽然从夫妻之义的角度讲,“固为义绝”,但是宋代的法律规定:“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听改嫁。”以恩情度之,“则京宣义于周氏绝无夫妇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则未尝替也”。因此黄榦判定,周氏归于曾家安葬拜祭,京家不得妄行争执归葬。“乞行下听从曾嵓叟安葬,仍乞告示京宣义,不得更有词诉。”在这个案件的审理中,黄榦既不是根据所谓的妇女贞洁的原则,也不是根据犹如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既嫁从夫的现实原则,而是以夫妻的真实感情作为判案的原则。夫妻既无感情,恩与义并绝,周氏就只能判给义绝而恩存的曾家了。这一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黄榦作为一名关心社会现实的儒者,在坚持义理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情理变通的经世原则。①
从黄榦在司法实践中对妇女地位的认知这一事实,我们又可以从中看出最为后世所诟病的妇女“贞节观”在宋代实施的某些侧面。在上举的许多案例中,妇女改嫁的事情屡有发生,黄榦对于改嫁女性的案件判决,一般都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就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看,一般皆以为,中国社会对妇女守节方面的态度,存在一个演进的过程,虽然“从一而终”的妇女贞节一直受到高度认同,但是在明代以前,对礼教最具敏感度的士人,在其文集中,一般也不忌讳记载再嫁的妇女。同时,无论是宗室贵族还是士大夫官员,对于家族中的妇女再嫁,或娶再嫁的妇女,也不介意,或者说,即使介意,也不是最优先的考量。与之相比,门第或经济等因素显然更为重要。宋代之前,妇女仍然拥有选择再嫁的自由与空间,自周迄宋,妇女皆不讳再嫁。②我们从黄榦的判词中,再一次印证了宋代妇女贞节问题的这一事实。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以及社会上的认知,往往把中国妇女贞节的非人道化归咎于宋儒特别是宋代的理学家们。诚然,一部分宋儒确实把妇女的贞节观念提高到泛道德化的高度。特别是理学家程颐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言论,在中国妇女贞节观的历史演变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把妇女的贞节纳入到“天理”的范畴,使原本特出的道德行为开始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而就理学系统而言,天理是内于人心的,这就将原本是随机发生的道德实践赋予了普遍化的意涵。”③后世对于妇女贞节问题的认知,往往以宋儒程颐的这一极端言论而加以叙述。但是,同样作为儒者、理学家,又是程颐的晚辈的黄榦,却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对妇女的贞节问题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则我们今天对于宋儒们在妇女观上的评价,似不宜一概而论。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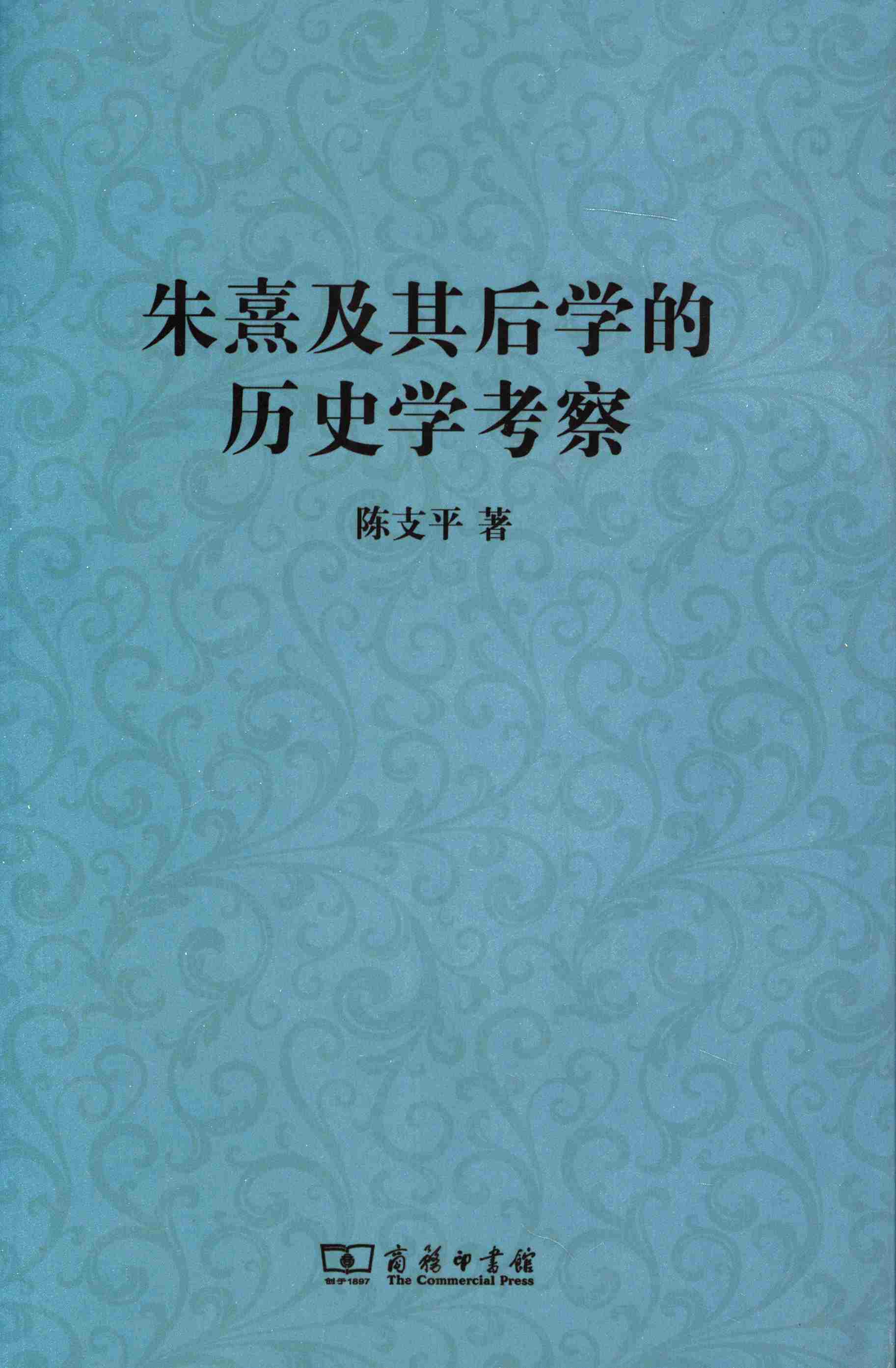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本书主要考察朱熹及其后学们究竟为当时的社会做了些什么,以及这些事情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朱熹和他的学生们,有从政的经历,也有当平民的经历,他们在所谓的“行”的实践上,表现更多。鉴于此,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朱子学,突破了从哲学视角研究朱子学的传统。与从哲学视角注重“想什么”不同,历史学更注重“做什么”。作者以自己所擅长的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对朱熹及其后学在这两个领域的所作所为,做出了尝试性的分析。
阅读
相关人物
黄榦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