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族、家庭血缘关系的异化
| 内容出处: |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885 |
| 颗粒名称: | (一)家族、家庭血缘关系的异化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1 |
| 页码: | 343-353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古代的宗法制度基于血缘关系,血缘纯正是宗法制度传承的前提。在中国历史上,宗法制在三代先秦时期延续,北宋时期的儒者对宗子的要求也是基于纯正血缘的传承。周代实行的宗法制度强调嫡长子继承,注重宗嗣的延续。形成于周代的大宗制度和置后制度反映了中国宗族建构和世系延续的重要性。 |
| 关键词: | 家族 家庭 血缘关系 |
内容
古代“宗法制”的基础,是宗法继承的血缘关系,血缘关系的纯正是宗法制度得以传承的最基本的前提。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三代先秦的“宗法制”延续,还是北宋时期儒者们对于“宗子”的要求与设立,纯正血缘的传承都是家族与家庭得以延续的重中之重。周代的宗法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侧重宗嗣,强调的是“大宗不可以绝”。周代世系的延续,就是指“宗”的延续。形成于周代的“百世不迁”的大宗制度、宗子无后而另行“置后”制度等,反映了中国宗族的核心是建构并维持“世系”的完整和延续的重要性。两汉时期,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也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重视宗嗣。继承帝祚的儿子为大宗,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的儿子为小宗,这些小宗在本侯国内又是大宗。《汉书·文帝纪》:“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列侯始受国者亦皆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不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汉代仍有“大宗不可以绝”的观念。《汉书》卷八《宣帝纪》载霍光奏议曰:“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这种情况在《汉书》传记中也有类似记载。两汉时期,无论是皇帝还是诸侯王、人臣,在大宗无后的情况下,常常以同宗之支子为大宗后,这是重视宗嗣的体现。
与此同时,爵位继承的实子制原则。实子制即亲生之子,汉代王、列侯封爵传袭,采取嫡长子继承制,不允许嗣子和隔代的孙子继承。无嫡子袭爵,则削除封国,这就是所谓的“无子国除”。汉代爵位继承中,诸侯有罪或无子,除有天子特恩外,一般是应“国除”绝嗣的。汉代有“非子”之罪,即对非亲生或奸乱生之子的制裁。“非子”之罪,是针对秦汉之际非婚生子事多而定,是为了强调父亲血缘的纯正。综观两汉史,汉代诸侯王因无子嗣而国除的不乏其例。但是到了西汉中后期,这种“无子国除”的情况开始有所松动。《汉书·宣帝纪》载宣帝诏书:“封(张)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追赐贺谥曰阳都哀侯。”师古曰:“所子者,言养弟子以为子。”这是张贺以侄为嗣,后为朝廷承认为嗣子承爵。应该指出的是,西汉中后期这种非实子嗣子的承爵只是特例。在此之前,“亡子而有孙”和“子同产子”是不能承爵的,实子继承限制在“亲子”的范围内。在此之后,承爵由实子扩大到侄、孙的范围,无子但有孙和养侄为嗣的承爵,是国家允许的,不再是皇恩的“殊数”了。东汉中后期,以同产子为嗣和承爵,则习以为常了。①
从先秦以迄汉代的父系继嗣制度演变历程看,虽然早先的诸侯世家十分强调嫡子的承继,但是实际上,家族的传承,甚至包括皇室家族、诸侯家族的传承,要百分百地确保血缘的纯正性,都是有些难于预料的。就皇室、诸侯这些高贵的血统家族而言,万一出现直系血缘中断的情况,他们也不得不进行一些变通,采取在同宗别子之内寻找继承人,其血缘关系虽然比起直系传承要疏远一些,但多少还是保证了同一祖先血缘的联系性与传承性。但是从一般的民间家族、家庭来看,由于其家族、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远不能与皇室、诸侯等高贵家族相比,民间家族、家庭血缘关系得以中断的情景,一定要比皇室、诸侯家族血缘关系中断的概率高得多。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秦汉以来中国民间家族、家庭对于血缘关系中断的处理方式,我们现在固然不甚了解,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推测的是,当民间家族、家庭遇到血缘关系中断的时候,一定也会参照皇室、诸侯等高贵家族的做法,采取在同宗别子之内寻找血缘继承人的办法。而在本宗之内寻求血缘继承人,一般的原则是先在血缘最亲密的近支血亲中寻求,近支血亲中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才不得不从血亲较为疏远的旁支子弟中寻求血缘继承人。《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中有一份《谢文学诉嫂黎氏立继》的判词,说的是血缘继承的近亲与远亲之争:
谢文学名骏,讼其嫂黎氏不立其子五六冬郎为嗣,而立堂兄谢鹏之子五八孜为嗣,自嘉定三年论诉至今,经隔五年。宁都杨知县、柯知县、赣州佥厅及本州赵司法皆以为立嗣当从黎氏,谢文学不应争立,援法据理,极为明白。宁都县曾追到黎氏出官供责,称是其夫谢骖在日,与弟谢骏时常争闹,有同冤家。又称其夫病重,称欲立谢鹏之子五八孜。又追到族长数人,并称谢骖不愿立谢骏之子,而愿立谢鹏之子。在法夫亡妻在,从其妻便。使谢骖元无意立谢鹏之子,尚听黎氏所立,况又出于谢骖之本意乎?今谢文学骏健讼不已,复经转运使台,必欲争立。且法令以为不当立,两知县以为不当立,本州佥厅以为不当立,提刑司委送赵司法亦以为不当立,其族长以为不当立,其嫂黎氏亦以为不当立,谢骏何人,乃敢蔑视官府、违慢条法、欺凌孤幼、斥责族长?显是豪横,难以轻恕。照得提刑李吏部恶其健讼,尝将谢骏枷禁州院,今来尚不唆改。今据谢骏复遣干人谢卓前来本县投词,锢身解转运使衙,欲乞并追谢骏痛赐惩治,以为豪猾健讼者之戒。①从古代宗法礼制上说,家族血缘继承应该先亲后疏,兄长谢骖既然无嗣,本应立其亲弟谢骏之子为后嗣。但是由于谢骖生前与弟弟谢骏关系不和,“谢骖在日,与弟谢骏时常争闹,有同冤家”,谢骖不愿立谢骏之子为嗣,而是另外在同宗堂兄之中寻求立嗣的对象,遂立堂兄谢鹏之子五八孜为嗣。由此谢骏不服,向衙门告诉其嫂立堂兄谢鹏之子五八孜为嗣不当,应予改正。但是从各级衙门审理的结果看,无论是宁都杨知县、柯知县、赣州佥厅及本州赵司法,甚至陈氏家族内的族长们,皆以为立嗣当从黎氏,谢骏不应争立,“援法据理,极为明白”。这也就是说,到了南宋时期,家庭的血缘继嗣,并不是首先依照血缘先近后疏的继承原则,而是更多地尊重立嗣者的意愿。并且,“在法夫亡妻在,从其妻便。使谢骖元无意立谢鹏之子,尚听黎氏所立,况又出于谢骖之本意乎?”。夫亡妻在,未亡之妻在本家立嗣上具有重要的决定权,其小叔谢骏,不得以近亲而阻挡其兄嫂立堂侄子为嗣。居于以上法理及社会人情,故黄榦在判词中对谢骏的无理诉讼,予以斥责:“谢骏何人,乃敢蔑视官府、违慢条法、欺凌孤幼、斥责族长?显是豪横,难以轻恕。……今据谢骏复遣干人谢卓前来本县投词,锢身解转运使衙,欲乞并追谢骏痛赐惩治,以为豪猾健讼者之戒。”根据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南宋时期的家族、家庭血缘继承,所谓血亲先近后疏的原则已经得到较大的改变。
那么,在同宗血亲之内寻求血缘继承人之外,有没有可能在血缘关系之外的人群当中寻找家族、家庭继承人呢?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中有一份《判词》,很值得我们注意。《李良佐诉李师膺取唐氏归李家》中云:
在礼为之后、为之子,师膺既归李氏,则以世英为父,以孔氏
为母。今复取唐氏归李家,则是二母也。况李良佐所陈,因唐氏之弟所讼。而世英死,此尤人子之至痛,唐氏决不可往来李家,李师膺决不可再收养唐氏。李师膺为李世英之子,已经历年深,亦尝为世英持斩衰之服,善事孔氏,母子无间言,友爱师勉兄弟无异意。李良佐乃辄生异姓不可收养之论,以离其心。在法祖父母所立之子,苟无显过,虽其母亦不应遣逐。今其母尚能容之,良佐何人,乃欲遣逐之乎?李师膺断然当为李世英之子,李良佐断然不可妄兴异议。唐氏当去师膺,当立李良佐,又欲榜示徐、罗二解元,使不得往来李师膺之家,此亦遣逐师膺之意,盖欲使师膺失所依也。良佐之处心不臧情态已见,徐、罗二解元则未见有侵欺之实,岂可预行榜示?况李师膺年已二十二,亦非全然不辨菽麦,而为外人所侵者。徐、罗二解元果有侵欺,李良佐旋行陈告亦未为晚。世间亦真有可托孤之人,亦安知徐、罗二解元非念其孤幼而为之经纪其家?难以预行给榜,并行下保晓谕李师膺兄弟并徐、罗二解元,各照本县所行取知委申。①
这个案件讲的是李师膺以异姓入继离家为嗣,“为李世英之子,已经历年深,亦尝为世英持斩衰之服,善事孔氏,母子无间言,友爱师勉兄弟无异意”。但是父亲李世英去世后,李良佐妄兴诉讼,要求奉回李世英的前妻唐氏回归李家,而遣逐李师膺出家门,另立李良佐为嗣。黄榦经过调查之后,判定“李师膺断然当为李世英之子,李良佐断然不可妄兴异议”。在这一判词中,黄榦肯定了异姓子李师膺继承李家的正当合法性。
在另一份名曰《陈如椿论房弟妇不应立异姓子为嗣》的判词中,黄榦同样也是遵循了父母自主选择异姓子为嗣的正当合法性原则。该判词全文如下:
使府送下陈如椿论房弟妇刘氏不应立异姓子为嗣,委本县照条看定申本县参考案牍,又有见任辰溪知县陈敏学申州公状,亦与陈如椿之辞一同。刘氏以为其夫宁乡知县陈邵于甲寅年在潭州抱养同官遗弃之子立名志学,经今十六年,即非今方立为嗣。辰溪知县陈敏学及陈如椿却称知县不曾立外人为嗣。今考陈如椿之辞,以为知县癸丑年离任,志学甲寅年始生,则是在潭州时犹未生。此收养之子,据刘氏赍出印纸,陈知县乃是癸丑年冬十一月方满,亦安知其尚留潭州两月间收养志学以为子乎?又考陈如椿之辞,以为知县但有庶生子六三哥,即无收养之子。据刘氏却称六三哥亦是收养之子。及再令陈如椿供对,却是收养吴博士之子。其言词又自反复,则其所告志学非收养之子,亦是虚妄可知。又据刘氏赍到自童蒙以来读书学字十数卷,皆积年陈旧文字,问其所从之师,则在抚州者见有先生姓饶。及请到饶先生供对,则又称去年陈知县已送志学相从读书,岂得以为身死之后旋立十五六岁异姓之子乎?陈知县年五十有七而亡,其妻刘氏亦年五六十岁,其相处不为不久,何其夫身死之后,乃信干仆之言立十五六岁素不相识之子以为嗣乎?则陈如椿之虚妄无可疑者。陈如椿自称挟术为生,则其为人乃破落把持起倒刘氏钱物而不得,遂扶陈敏学论诉,意欲立敏学之子为陈知县之嗣,异日并有刘氏物业。此市井破落之常,不足深责。辰溪知县陈敏学身为士夫,不顾义理,不念刘氏乃其叔母,亦敢移文本州,与破落陈如椿挟同妄诉,欲以吞并叔父之业,廉耻道丧,莫此为甚。今据刘氏所供,辰溪知县陈敏学之父一机宜,亦是陈安抚收养遗弃之子。今乃罪刘氏不合收养为不当,是责其祖、辱其父也。为人子者责其祖、辱其父、诬其零丁孤寡之叔母,罪莫大焉。合将陈如椿重行勘断,念其于刘氏之子有族伯之亲,申解使府乞将陈如椿责戒励放,仍牒辰溪知县知委,庶其少知改悔,以全士大夫之名节,余人放。①
在这份判词中,讲的是有陈如椿者,上诉认为其房弟妇刘氏立异姓子为嗣,所为不当,有乱宗之嫌,应予撤销,更立同宗辰溪知县陈敏学之子为嗣。黄榦经过周密访查之后,认为刘氏立异姓子为嗣,原是十几年前先夫宁乡知县陈邵在世时所收养,并非刘氏现在起意。其先夫宁乡知县陈邵是本宗血缘继承人,既然认定异姓子陈志学为嗣,夫为妻纲,刘氏继承先夫的遗愿,指定异姓子陈志学为嗣,并无不当,应予肯定。黄榦还进一步在判词中指出,辰溪知县陈敏学及陈如椿妄兴诉讼,指责刘氏立异姓子为嗣,实际上是贪图刘氏及其先夫陈邵的物业,因此,黄榦还特别在判词中对原告辰溪知县陈敏学及陈如椿提出处分意见:“合将陈如椿重行勘断,念其于刘氏之子有族伯之亲,申解使府乞将陈如椿责戒励放,仍牒辰溪知县知委,庶其少知改悔,以全士大夫之名节。”
很明显,黄榦的判词,对于刘氏立异姓子为嗣,并没有从血缘乱宗的角度来进行思考,而是从刘氏先夫在世时已经确定立异姓子为嗣,即为正当,因此必须从司法的角度予以确认。另一方面,黄榦认为家族内部屡有此类诉讼,根本原因不在于“血缘乱宗”,而是在于贪图别人物业,“其为人乃破落把持起倒刘氏钱物而不得,遂扶陈敏学论诉,意欲立敏学之子为陈知县之嗣,异日并有刘氏物业。此市井破落之常”。更有意思的是,在以上诉讼案件中,陈氏家族的三代人之中,立异姓子为嗣的情况远不止刘氏一家,其他至少还有“六三哥亦是收养之子……却是收养吴博士之子”。甚至参与告诉刘氏立异姓子为嗣的辰溪知县陈敏学,其父亲“一机宜,亦是陈安抚收养遗弃之子”。陈氏家族的告诉各方,均为仕宦人家,本应更加重视家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但实际情况却是屡屡收养异姓子为嗣,则南宋时期民间社会在血缘关系传承上的异化现象,还是时常发生的。
宋代以来新的家族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使得民间社会特别是个体家庭对于家族组织的依赖性大大增强。个体家庭的发展有赖于整个家族的庇护,家族的衰亡也就意味着个体家庭的流落无依,难于立足乡里。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缺乏长久稳定性,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一般家庭生老病死、丧偶夭子所发生的概率相当高,许多家族、家庭往往因天灾人祸而处于濒临绝嗣的边缘。因此,到了明清时期,民间社会中以外姓子弟继承家庭、家族血缘关系的情况就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了。我曾经对明清时期福建家族社会的血缘继承问题进行过资料的搜集,发现所谓的家族血缘继承,仅仅是一种传承的文化观念而已,在民间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血缘关系的混杂、异姓承宗基本上不为一般的家族和家庭所排斥。如闽南漳州诏安一带,买女赘婿、孀妇赘男等现象,导致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发生混杂。《问俗录》云:“买女赘婿,孀妇赘男,以承禋祀,守丘墓,分守家业,仰事俯畜,无异所生。族中人亦不以乱宗为嫌。于是有约定初生之男从妻族,再生之男从夫族者;有生从妻姓,没从夫姓者。”①闽西的明溪县亦然,“邑人乏子嗣,恒买他人子女继续。子未大,买女入门,长成婚室,生儿为嗣。女大则赘男为婿,立约夫从女姓,恃为半子,生子儿则女妇两有”①。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纯粹成了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只要家族的嗣系得以延继,婚姻关系以及血缘的正统与否都是次要的。
家族重视男子系统,固有血缘继嗣的原因,同时对于壮大家族势力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相互割据、对抗的乡族社会里,家族男丁的兴旺与否,直接关系到家族势力的强弱,家族拥有众多的男丁,就意味着在社会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优势。因此,福建各家族为了壮大自己的男丁队伍,不仅不以借妻生子为嫌,甚至还盛行各种“养子”“义男”“螟蛉子”等习俗。《厦门志·风俗志》云:“闽人多养子,即有子者亦必抱养数子……或藉多子以为强房。积习相沿,恬不为怪。”②《同安县志·风俗志》亦云:“同俗向喜乞养他人子,及子复生子,遂混含不可究诘。始但出于巨乡大族强房者为之,嘉道前械斗盛行,乡人恃丁多为强之流弊,后则竞相仿效。”③明代何乔远《闽书》记载明代沿海各地的情景时云:“有番舶之饶,行者入海附赀,或得窭子弃儿,抚如己出,长使通番,其存亡无所患苦。”④
从原则上讲,福建民间家族的婚姻混乱和养子制度,是与家族强调的纯洁血缘关系和道德标准相抵触的,但实际上,家族所提倡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都是具有两重性的,它既是传统道德的,又是现实功利的,而归根到底,传统道德的倡导是为现实功利服务的。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动荡纷乱的社会变迁和家族割据、对抗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强调传统的家族道德和血缘关系,并不能使所有的家族都得到顺利的发展。
相反地,在这机械相争的社会里,强凌弱、众暴寡,再加上外部战乱的破坏,有的家族壮大发展,有的家族却衰败没落,强盛的家族更加强盛,而弱小的家族更加弱小,甚至完全消亡。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家族利用各种变通权宜办法来壮大家族的男丁队伍,完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就客观条件而言,也具有现实之可能。那些衰败的家族、贫困的家庭,无力娶妻成家,为社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窭儿弃子”,而强宗大姓,为了巩固家族的地位,则竞相收养义子、义男,“夫随嫁儿得以承宗,鬻义子得以入祠,吕嬴牛马,诏安氏族之实已不可考矣”①。于是,为了使这种变通的继嗣关系与家族的道德原则相适应,福建许多家族不得不重新制定血缘的继嗣标准和族谱的记载条例,以承认养子、义男、螟蛉子、赘婿等在家族续嗣上的合法性。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侯官县林氏家族的林允昌在一份《遗书》中告诫后人:“昌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承父命,抱各口董家有一新添幼童……尚在血下,方才三日,名为午使。痛母无乳,日夜食哺,百般抚养,犹胜亲生。今幸年已二十有五,娶媳黄氏,复蒙天庇佑,得产男孙一丁、女孙二口。纵谓螟蛉之子,亦不得复言螟蛉之孙。今昌病体临危,理合诸亲面前,将昌分下所有一切产业尽付与男午使掌管,家下弟侄不得妄相争执,藉称立嗣等情。”晋江县《虹山彭氏族谱》的《新订谱例》也对血缘嗣系的记载做出适应性规定:“螟蛉异姓,旧谱所戒,然近乡巨室,所在多有,即以吾族而论,亦相习成风,而生长子孙者实繁有徒。若概削即不书,势必有窒碍难行之处,且不慎于始,而慎之于后,亦非折衷办法也。兹特变文起例,凡螟蛉异姓为嗣者,书曰‘养子’。”这种强调“纵谓螟蛉之子,亦不得复言螟蛉之孙”,“若概削即不书,势必有窒碍难行之处”的意识,体现了明清时期民间家族在血缘继承观念上的重大改变。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家族而言,运用各种手段,包括承继异姓子,来维持世系的完整和延续,显然比重视和坚守血缘的纯正性更为重要。家族对于婚姻和继嗣的变通权宜办法,并没有改变福建乃至整个中国家族血缘的整体关系,相反,养子、螟蛉子不断消融于家族的血缘关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家族的男子嗣系,巩固和发展了家族的社会地位。①而我们从黄榦的判词中可以了解到,这种观念的改变,在南宋时期已经从法律上得到了体现,随着宋以后社会的不断变迁,到了明清时期以至近代,家族制度中的所谓重视血缘嗣系,与北宋时期儒者们的最初设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与此同时,爵位继承的实子制原则。实子制即亲生之子,汉代王、列侯封爵传袭,采取嫡长子继承制,不允许嗣子和隔代的孙子继承。无嫡子袭爵,则削除封国,这就是所谓的“无子国除”。汉代爵位继承中,诸侯有罪或无子,除有天子特恩外,一般是应“国除”绝嗣的。汉代有“非子”之罪,即对非亲生或奸乱生之子的制裁。“非子”之罪,是针对秦汉之际非婚生子事多而定,是为了强调父亲血缘的纯正。综观两汉史,汉代诸侯王因无子嗣而国除的不乏其例。但是到了西汉中后期,这种“无子国除”的情况开始有所松动。《汉书·宣帝纪》载宣帝诏书:“封(张)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追赐贺谥曰阳都哀侯。”师古曰:“所子者,言养弟子以为子。”这是张贺以侄为嗣,后为朝廷承认为嗣子承爵。应该指出的是,西汉中后期这种非实子嗣子的承爵只是特例。在此之前,“亡子而有孙”和“子同产子”是不能承爵的,实子继承限制在“亲子”的范围内。在此之后,承爵由实子扩大到侄、孙的范围,无子但有孙和养侄为嗣的承爵,是国家允许的,不再是皇恩的“殊数”了。东汉中后期,以同产子为嗣和承爵,则习以为常了。①
从先秦以迄汉代的父系继嗣制度演变历程看,虽然早先的诸侯世家十分强调嫡子的承继,但是实际上,家族的传承,甚至包括皇室家族、诸侯家族的传承,要百分百地确保血缘的纯正性,都是有些难于预料的。就皇室、诸侯这些高贵的血统家族而言,万一出现直系血缘中断的情况,他们也不得不进行一些变通,采取在同宗别子之内寻找继承人,其血缘关系虽然比起直系传承要疏远一些,但多少还是保证了同一祖先血缘的联系性与传承性。但是从一般的民间家族、家庭来看,由于其家族、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远不能与皇室、诸侯等高贵家族相比,民间家族、家庭血缘关系得以中断的情景,一定要比皇室、诸侯家族血缘关系中断的概率高得多。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秦汉以来中国民间家族、家庭对于血缘关系中断的处理方式,我们现在固然不甚了解,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推测的是,当民间家族、家庭遇到血缘关系中断的时候,一定也会参照皇室、诸侯等高贵家族的做法,采取在同宗别子之内寻找血缘继承人的办法。而在本宗之内寻求血缘继承人,一般的原则是先在血缘最亲密的近支血亲中寻求,近支血亲中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才不得不从血亲较为疏远的旁支子弟中寻求血缘继承人。《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中有一份《谢文学诉嫂黎氏立继》的判词,说的是血缘继承的近亲与远亲之争:
谢文学名骏,讼其嫂黎氏不立其子五六冬郎为嗣,而立堂兄谢鹏之子五八孜为嗣,自嘉定三年论诉至今,经隔五年。宁都杨知县、柯知县、赣州佥厅及本州赵司法皆以为立嗣当从黎氏,谢文学不应争立,援法据理,极为明白。宁都县曾追到黎氏出官供责,称是其夫谢骖在日,与弟谢骏时常争闹,有同冤家。又称其夫病重,称欲立谢鹏之子五八孜。又追到族长数人,并称谢骖不愿立谢骏之子,而愿立谢鹏之子。在法夫亡妻在,从其妻便。使谢骖元无意立谢鹏之子,尚听黎氏所立,况又出于谢骖之本意乎?今谢文学骏健讼不已,复经转运使台,必欲争立。且法令以为不当立,两知县以为不当立,本州佥厅以为不当立,提刑司委送赵司法亦以为不当立,其族长以为不当立,其嫂黎氏亦以为不当立,谢骏何人,乃敢蔑视官府、违慢条法、欺凌孤幼、斥责族长?显是豪横,难以轻恕。照得提刑李吏部恶其健讼,尝将谢骏枷禁州院,今来尚不唆改。今据谢骏复遣干人谢卓前来本县投词,锢身解转运使衙,欲乞并追谢骏痛赐惩治,以为豪猾健讼者之戒。①从古代宗法礼制上说,家族血缘继承应该先亲后疏,兄长谢骖既然无嗣,本应立其亲弟谢骏之子为后嗣。但是由于谢骖生前与弟弟谢骏关系不和,“谢骖在日,与弟谢骏时常争闹,有同冤家”,谢骖不愿立谢骏之子为嗣,而是另外在同宗堂兄之中寻求立嗣的对象,遂立堂兄谢鹏之子五八孜为嗣。由此谢骏不服,向衙门告诉其嫂立堂兄谢鹏之子五八孜为嗣不当,应予改正。但是从各级衙门审理的结果看,无论是宁都杨知县、柯知县、赣州佥厅及本州赵司法,甚至陈氏家族内的族长们,皆以为立嗣当从黎氏,谢骏不应争立,“援法据理,极为明白”。这也就是说,到了南宋时期,家庭的血缘继嗣,并不是首先依照血缘先近后疏的继承原则,而是更多地尊重立嗣者的意愿。并且,“在法夫亡妻在,从其妻便。使谢骖元无意立谢鹏之子,尚听黎氏所立,况又出于谢骖之本意乎?”。夫亡妻在,未亡之妻在本家立嗣上具有重要的决定权,其小叔谢骏,不得以近亲而阻挡其兄嫂立堂侄子为嗣。居于以上法理及社会人情,故黄榦在判词中对谢骏的无理诉讼,予以斥责:“谢骏何人,乃敢蔑视官府、违慢条法、欺凌孤幼、斥责族长?显是豪横,难以轻恕。……今据谢骏复遣干人谢卓前来本县投词,锢身解转运使衙,欲乞并追谢骏痛赐惩治,以为豪猾健讼者之戒。”根据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南宋时期的家族、家庭血缘继承,所谓血亲先近后疏的原则已经得到较大的改变。
那么,在同宗血亲之内寻求血缘继承人之外,有没有可能在血缘关系之外的人群当中寻找家族、家庭继承人呢?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中有一份《判词》,很值得我们注意。《李良佐诉李师膺取唐氏归李家》中云:
在礼为之后、为之子,师膺既归李氏,则以世英为父,以孔氏
为母。今复取唐氏归李家,则是二母也。况李良佐所陈,因唐氏之弟所讼。而世英死,此尤人子之至痛,唐氏决不可往来李家,李师膺决不可再收养唐氏。李师膺为李世英之子,已经历年深,亦尝为世英持斩衰之服,善事孔氏,母子无间言,友爱师勉兄弟无异意。李良佐乃辄生异姓不可收养之论,以离其心。在法祖父母所立之子,苟无显过,虽其母亦不应遣逐。今其母尚能容之,良佐何人,乃欲遣逐之乎?李师膺断然当为李世英之子,李良佐断然不可妄兴异议。唐氏当去师膺,当立李良佐,又欲榜示徐、罗二解元,使不得往来李师膺之家,此亦遣逐师膺之意,盖欲使师膺失所依也。良佐之处心不臧情态已见,徐、罗二解元则未见有侵欺之实,岂可预行榜示?况李师膺年已二十二,亦非全然不辨菽麦,而为外人所侵者。徐、罗二解元果有侵欺,李良佐旋行陈告亦未为晚。世间亦真有可托孤之人,亦安知徐、罗二解元非念其孤幼而为之经纪其家?难以预行给榜,并行下保晓谕李师膺兄弟并徐、罗二解元,各照本县所行取知委申。①
这个案件讲的是李师膺以异姓入继离家为嗣,“为李世英之子,已经历年深,亦尝为世英持斩衰之服,善事孔氏,母子无间言,友爱师勉兄弟无异意”。但是父亲李世英去世后,李良佐妄兴诉讼,要求奉回李世英的前妻唐氏回归李家,而遣逐李师膺出家门,另立李良佐为嗣。黄榦经过调查之后,判定“李师膺断然当为李世英之子,李良佐断然不可妄兴异议”。在这一判词中,黄榦肯定了异姓子李师膺继承李家的正当合法性。
在另一份名曰《陈如椿论房弟妇不应立异姓子为嗣》的判词中,黄榦同样也是遵循了父母自主选择异姓子为嗣的正当合法性原则。该判词全文如下:
使府送下陈如椿论房弟妇刘氏不应立异姓子为嗣,委本县照条看定申本县参考案牍,又有见任辰溪知县陈敏学申州公状,亦与陈如椿之辞一同。刘氏以为其夫宁乡知县陈邵于甲寅年在潭州抱养同官遗弃之子立名志学,经今十六年,即非今方立为嗣。辰溪知县陈敏学及陈如椿却称知县不曾立外人为嗣。今考陈如椿之辞,以为知县癸丑年离任,志学甲寅年始生,则是在潭州时犹未生。此收养之子,据刘氏赍出印纸,陈知县乃是癸丑年冬十一月方满,亦安知其尚留潭州两月间收养志学以为子乎?又考陈如椿之辞,以为知县但有庶生子六三哥,即无收养之子。据刘氏却称六三哥亦是收养之子。及再令陈如椿供对,却是收养吴博士之子。其言词又自反复,则其所告志学非收养之子,亦是虚妄可知。又据刘氏赍到自童蒙以来读书学字十数卷,皆积年陈旧文字,问其所从之师,则在抚州者见有先生姓饶。及请到饶先生供对,则又称去年陈知县已送志学相从读书,岂得以为身死之后旋立十五六岁异姓之子乎?陈知县年五十有七而亡,其妻刘氏亦年五六十岁,其相处不为不久,何其夫身死之后,乃信干仆之言立十五六岁素不相识之子以为嗣乎?则陈如椿之虚妄无可疑者。陈如椿自称挟术为生,则其为人乃破落把持起倒刘氏钱物而不得,遂扶陈敏学论诉,意欲立敏学之子为陈知县之嗣,异日并有刘氏物业。此市井破落之常,不足深责。辰溪知县陈敏学身为士夫,不顾义理,不念刘氏乃其叔母,亦敢移文本州,与破落陈如椿挟同妄诉,欲以吞并叔父之业,廉耻道丧,莫此为甚。今据刘氏所供,辰溪知县陈敏学之父一机宜,亦是陈安抚收养遗弃之子。今乃罪刘氏不合收养为不当,是责其祖、辱其父也。为人子者责其祖、辱其父、诬其零丁孤寡之叔母,罪莫大焉。合将陈如椿重行勘断,念其于刘氏之子有族伯之亲,申解使府乞将陈如椿责戒励放,仍牒辰溪知县知委,庶其少知改悔,以全士大夫之名节,余人放。①
在这份判词中,讲的是有陈如椿者,上诉认为其房弟妇刘氏立异姓子为嗣,所为不当,有乱宗之嫌,应予撤销,更立同宗辰溪知县陈敏学之子为嗣。黄榦经过周密访查之后,认为刘氏立异姓子为嗣,原是十几年前先夫宁乡知县陈邵在世时所收养,并非刘氏现在起意。其先夫宁乡知县陈邵是本宗血缘继承人,既然认定异姓子陈志学为嗣,夫为妻纲,刘氏继承先夫的遗愿,指定异姓子陈志学为嗣,并无不当,应予肯定。黄榦还进一步在判词中指出,辰溪知县陈敏学及陈如椿妄兴诉讼,指责刘氏立异姓子为嗣,实际上是贪图刘氏及其先夫陈邵的物业,因此,黄榦还特别在判词中对原告辰溪知县陈敏学及陈如椿提出处分意见:“合将陈如椿重行勘断,念其于刘氏之子有族伯之亲,申解使府乞将陈如椿责戒励放,仍牒辰溪知县知委,庶其少知改悔,以全士大夫之名节。”
很明显,黄榦的判词,对于刘氏立异姓子为嗣,并没有从血缘乱宗的角度来进行思考,而是从刘氏先夫在世时已经确定立异姓子为嗣,即为正当,因此必须从司法的角度予以确认。另一方面,黄榦认为家族内部屡有此类诉讼,根本原因不在于“血缘乱宗”,而是在于贪图别人物业,“其为人乃破落把持起倒刘氏钱物而不得,遂扶陈敏学论诉,意欲立敏学之子为陈知县之嗣,异日并有刘氏物业。此市井破落之常”。更有意思的是,在以上诉讼案件中,陈氏家族的三代人之中,立异姓子为嗣的情况远不止刘氏一家,其他至少还有“六三哥亦是收养之子……却是收养吴博士之子”。甚至参与告诉刘氏立异姓子为嗣的辰溪知县陈敏学,其父亲“一机宜,亦是陈安抚收养遗弃之子”。陈氏家族的告诉各方,均为仕宦人家,本应更加重视家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但实际情况却是屡屡收养异姓子为嗣,则南宋时期民间社会在血缘关系传承上的异化现象,还是时常发生的。
宋代以来新的家族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使得民间社会特别是个体家庭对于家族组织的依赖性大大增强。个体家庭的发展有赖于整个家族的庇护,家族的衰亡也就意味着个体家庭的流落无依,难于立足乡里。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缺乏长久稳定性,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一般家庭生老病死、丧偶夭子所发生的概率相当高,许多家族、家庭往往因天灾人祸而处于濒临绝嗣的边缘。因此,到了明清时期,民间社会中以外姓子弟继承家庭、家族血缘关系的情况就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了。我曾经对明清时期福建家族社会的血缘继承问题进行过资料的搜集,发现所谓的家族血缘继承,仅仅是一种传承的文化观念而已,在民间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血缘关系的混杂、异姓承宗基本上不为一般的家族和家庭所排斥。如闽南漳州诏安一带,买女赘婿、孀妇赘男等现象,导致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发生混杂。《问俗录》云:“买女赘婿,孀妇赘男,以承禋祀,守丘墓,分守家业,仰事俯畜,无异所生。族中人亦不以乱宗为嫌。于是有约定初生之男从妻族,再生之男从夫族者;有生从妻姓,没从夫姓者。”①闽西的明溪县亦然,“邑人乏子嗣,恒买他人子女继续。子未大,买女入门,长成婚室,生儿为嗣。女大则赘男为婿,立约夫从女姓,恃为半子,生子儿则女妇两有”①。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纯粹成了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只要家族的嗣系得以延继,婚姻关系以及血缘的正统与否都是次要的。
家族重视男子系统,固有血缘继嗣的原因,同时对于壮大家族势力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相互割据、对抗的乡族社会里,家族男丁的兴旺与否,直接关系到家族势力的强弱,家族拥有众多的男丁,就意味着在社会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优势。因此,福建各家族为了壮大自己的男丁队伍,不仅不以借妻生子为嫌,甚至还盛行各种“养子”“义男”“螟蛉子”等习俗。《厦门志·风俗志》云:“闽人多养子,即有子者亦必抱养数子……或藉多子以为强房。积习相沿,恬不为怪。”②《同安县志·风俗志》亦云:“同俗向喜乞养他人子,及子复生子,遂混含不可究诘。始但出于巨乡大族强房者为之,嘉道前械斗盛行,乡人恃丁多为强之流弊,后则竞相仿效。”③明代何乔远《闽书》记载明代沿海各地的情景时云:“有番舶之饶,行者入海附赀,或得窭子弃儿,抚如己出,长使通番,其存亡无所患苦。”④
从原则上讲,福建民间家族的婚姻混乱和养子制度,是与家族强调的纯洁血缘关系和道德标准相抵触的,但实际上,家族所提倡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都是具有两重性的,它既是传统道德的,又是现实功利的,而归根到底,传统道德的倡导是为现实功利服务的。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动荡纷乱的社会变迁和家族割据、对抗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强调传统的家族道德和血缘关系,并不能使所有的家族都得到顺利的发展。
相反地,在这机械相争的社会里,强凌弱、众暴寡,再加上外部战乱的破坏,有的家族壮大发展,有的家族却衰败没落,强盛的家族更加强盛,而弱小的家族更加弱小,甚至完全消亡。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家族利用各种变通权宜办法来壮大家族的男丁队伍,完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就客观条件而言,也具有现实之可能。那些衰败的家族、贫困的家庭,无力娶妻成家,为社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窭儿弃子”,而强宗大姓,为了巩固家族的地位,则竞相收养义子、义男,“夫随嫁儿得以承宗,鬻义子得以入祠,吕嬴牛马,诏安氏族之实已不可考矣”①。于是,为了使这种变通的继嗣关系与家族的道德原则相适应,福建许多家族不得不重新制定血缘的继嗣标准和族谱的记载条例,以承认养子、义男、螟蛉子、赘婿等在家族续嗣上的合法性。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侯官县林氏家族的林允昌在一份《遗书》中告诫后人:“昌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承父命,抱各口董家有一新添幼童……尚在血下,方才三日,名为午使。痛母无乳,日夜食哺,百般抚养,犹胜亲生。今幸年已二十有五,娶媳黄氏,复蒙天庇佑,得产男孙一丁、女孙二口。纵谓螟蛉之子,亦不得复言螟蛉之孙。今昌病体临危,理合诸亲面前,将昌分下所有一切产业尽付与男午使掌管,家下弟侄不得妄相争执,藉称立嗣等情。”晋江县《虹山彭氏族谱》的《新订谱例》也对血缘嗣系的记载做出适应性规定:“螟蛉异姓,旧谱所戒,然近乡巨室,所在多有,即以吾族而论,亦相习成风,而生长子孙者实繁有徒。若概削即不书,势必有窒碍难行之处,且不慎于始,而慎之于后,亦非折衷办法也。兹特变文起例,凡螟蛉异姓为嗣者,书曰‘养子’。”这种强调“纵谓螟蛉之子,亦不得复言螟蛉之孙”,“若概削即不书,势必有窒碍难行之处”的意识,体现了明清时期民间家族在血缘继承观念上的重大改变。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家族而言,运用各种手段,包括承继异姓子,来维持世系的完整和延续,显然比重视和坚守血缘的纯正性更为重要。家族对于婚姻和继嗣的变通权宜办法,并没有改变福建乃至整个中国家族血缘的整体关系,相反,养子、螟蛉子不断消融于家族的血缘关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家族的男子嗣系,巩固和发展了家族的社会地位。①而我们从黄榦的判词中可以了解到,这种观念的改变,在南宋时期已经从法律上得到了体现,随着宋以后社会的不断变迁,到了明清时期以至近代,家族制度中的所谓重视血缘嗣系,与北宋时期儒者们的最初设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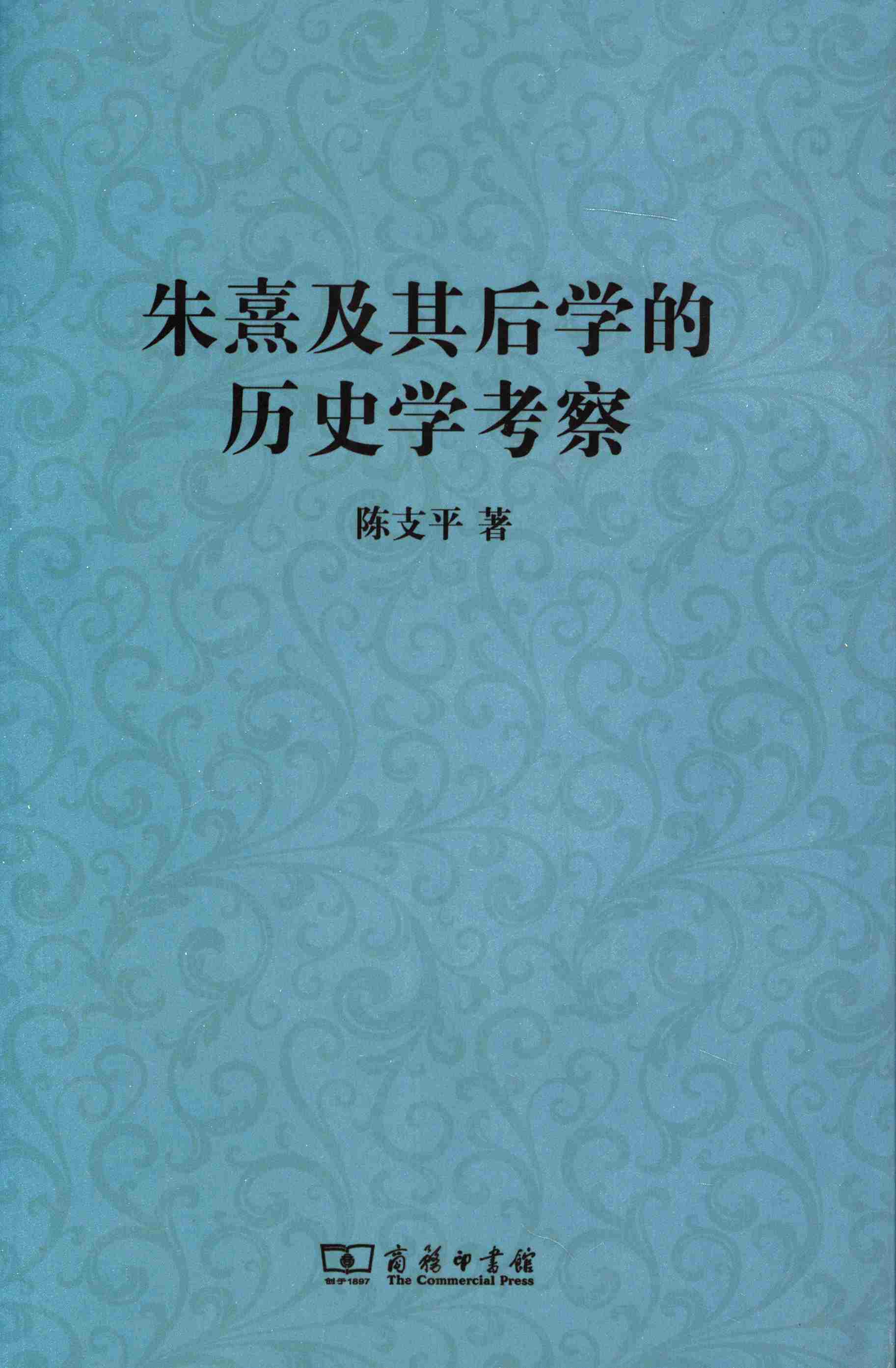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本书主要考察朱熹及其后学们究竟为当时的社会做了些什么,以及这些事情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朱熹和他的学生们,有从政的经历,也有当平民的经历,他们在所谓的“行”的实践上,表现更多。鉴于此,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朱子学,突破了从哲学视角研究朱子学的传统。与从哲学视角注重“想什么”不同,历史学更注重“做什么”。作者以自己所擅长的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对朱熹及其后学在这两个领域的所作所为,做出了尝试性的分析。
阅读
相关人物
黄榦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