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横行乡里、无视法纪
| 内容出处: |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881 |
| 颗粒名称: | (二)横行乡里、无视法纪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 |
| 页码: | 324-329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从黄榦的《判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类有权有势的豪强,他们横行乡里,欺压平民,却能屡屡运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网络,规避法律的惩罚。如在《判词》中出现多次的“谢知府”,就是一个相当突出的无视法律的恶劣士绅。 |
| 关键词: | 黄榦 无视法纪 横行乡里 |
内容
从黄榦的《判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类有权有势的豪强,他们横行乡里,欺压平民,却能屡屡运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网络,规避法律的惩罚。如在《判词》中出现多次的“谢知府”,就是一个相当突出的无视法律的恶劣士绅。
《判词·窑户杨三十四等论谢知府宅强买砖瓦》记载谢知府的不法行为云:
窑户十七人,经县陈词论谢知府宅非理吊缚抑勒白要砖瓦事,本县追到干人邹彦、王明供对,两词各不从实供招,遂各散禁。今以两词供答参详,据干人赍到文约,并称所买砖瓦皆是大砖大瓦,则所供价例乃窑户之说,为是干人初供,以为小砖小瓦,则与元立文约不同,此乃是低价抑勒之验。窑户所以不得已而哀号于县庭也,小民以烧砖瓦为业,不过日求升合,以活其妻孥,惟恐人之不售也。所售愈多,则得利愈厚,岂有甘心饥饿而不求售者哉?寄居之家所还价直与民户等,彼亦何苦而不求售?今至于合为朋曹经官论诉,必是有甚不能平而后至此也。今观其所议收买砖瓦窑户不肯卖,便至于经官陈词,差弓手邹全、保正温彦追出。寄居之与民户初无统属,交关市易当取其情愿,岂有挟官司之号令逼勒,而使之中卖之理?至于立约,又不与之较物之厚薄小大与价之多寡,则异日结算以何为据?是不复照平常人户交易之例,而自有一种门庭,庶几支还多寡惟吾之命是听也。又先支每人钱米共约八贯,而欲使之入纳砖瓦万三千片。所纳未足,更不支钱。一万三千砖瓦所直十七千,今乃只得钱八贯,而欲其纳足,窑户安得余钱,可以先为烧造砖瓦纳足,而后请钱耶?小民之贫,朝不谋夕,今其立约乃如此是。但知吾之形势可以抑勒,而不知理有不可,则必不能免人户之论诉也。今又以为元约一万三千,今只入五六千便作了足,即是现买现卖。本宅何不前期将钱借与各人?世间交易,未有不前期借钱以为定者。况所烧砖瓦非一人之力所能办,非一日之期所能成,必须作泥造坯,必须候干燥,必须入窑烧变,必经隔旬月而后成。今六月半得钱,七月半之后逐旋交纳。所入之价反多于所借之钱,岂得尚归罪于窑户耶?干人之词尚欲惩治窑户之背约。所谓文约,岂窑户之所情愿?追之以弓手、保正抑勒,而使之着押耳。官司二税,朝廷立为省限。形势之家,尚有出违省限不肯输纳者,况于私家非理之文约而可以责人之必不背约耶?寄居百姓,贵贱不同。张官置吏难以偏徇……谢知府宅干人赍到文约四纸,并称大砖大瓦;今状中却称是小样,显是诬赖。六月十三日交去定钱,七月半逐旋入去砖瓦,今却称是经隔三月。形势之家,欺凌乡民,率皆类此。……取索赖人砖瓦、欠人钱物,岂得以为无罪?不应收禁私家,却得将人打缚,官司不得禁人豪强之状,即此可见。①
在这个案件里,黄榦经过审理,看清了豪强谢知府倚仗权势,强行要窑户的一万三千片砖瓦,仅支付窑户“每人钱米共约八贯”。窑户向其索取砖瓦价钱,谢知府反而恶人先告状,把窑户们告上衙门,诉窑户违约。更有甚者,谢知府为了达到强夺窑户砖瓦的目的,还利用其在官府中的关系,擅自动用官差弓手,下乡恐吓拘押贫民,黄榦在《邹宗逸诉谢八官人违法刑害》的判词中说:“昨窑户并邹宗逸陈词,并是弓手骚扰。在法弓手官司尚不得差出下乡,私家辄行差使,是以引惹人户词诉。况佐官不得受状,近降旨挥甚严。今遣人出屋,辄以停藏为名,妄经尉司。县尉亦不契勘便行受理,此皆受制大家,深属未便。据词人所论专指谢八官人,乞行追究。今以两魁漕贡见该奏荐不伏出官,若事属利害,则虽命官亦合追逮。但今所陈以为干人,则难便令主仆供对,且唤上词人并最紧合干人邹季文、戴祥、张仲三名对。”①县衙尉司的庇护,是势豪谢知府一家得逞不法的重要原因。
势豪谢知府横行乡里,在黄榦所经手的判词中屡有提到。如在《彭念七论谢知府宅追扰》中,谢知府肆意役使乡民,稍不如意,即私自冒造官府文引,差使衙门中人拘押追索,该判词写道:“普天之下,莫非王民。虽有贵贱贫富之不同,其为国家之赤子则一而已。张官置吏,务以安存百姓,而形势之家,专欲骚扰细民。所谓寄居者,既叨冒朝廷官职,寄寓州县,尤当仰体国家矜百姓之意。今乃国家之官职,害国家之百姓。此岂士大夫所当为哉?近据彭念七状称,有次弟彭念九充谢知府宅甲头,……忽睹谢知府宅干人郭胜同胡甲头赍引前来,称是谢知府宅文字追唤彭念七、彭三一赴本宅根究,委实惧怕,不敢前去。……乃辄追扰其兄弟彭念七之不伏,勾追与其亲戚曾少四,尤不相干涉。又辄论诉其亲戚,如此支蔓,害及无辜,使细民何自而得安其生业耶?使谢知府宅存心平恕、不务刻削,为甲头何苦逃窜?至于逃窜,亦只得经官追其正身,岂得私出文引,追扰其兄弟,妄兴词诉,残害其亲戚?则是但知官职形势可以欺压细民,而略不体朝廷张官置吏存恤百姓之意,委实切害。”②
在《宋有论谢知府宅侵占坟地》案件中,谢知府竟然伪造交易文书、强迫宋氏家人画押,从而霸占宋氏园地。宋氏家人虽然屡屡上诉,但谢知府倚仗权势,勾结官府,案件拖延十年之久,不得理清,宋氏家人亦遭到谢知府私下关锁抑逼。黄榦到任之后,再次审理,他在《判词》中写道:“谢知府宅干人索干照理断,干人录白到契字,称宋有已曾作知见交钱着押。……宋有称宋朝英被谢知府宅关锁抑逼,一家恐畏,只得着押。……及索出宋有关书,乃是宋有、宋辅两户均分产业,内有众户尅留产业甲龙、甲师字两号,有祖父母墓共四所,兄弟商议不得典卖,关约分明。今谢知府宅乃于嘉定元年立契买置,只作宋朝英立契。岂有宋辅、宋有两名尅留物业,内有坟墓四所,乃径与宋辅之孙宋朝英交易之理?又岂有绍兴年间兄弟立约不得典卖,乃可以违约交易之理?以宋有共分物业乃能使之作知见人着押?则是以形势抑逼可知。交易之时,宋朝英年未及丁,则其畏惧听从亦无可疑者。宋有又曾经县经军经转运司论诉,竟不获伸,则其恃形势尤可见也。人家坟墓乃子孙百年醮祭之地,谢知府宅乃欲白夺以为园囿饮宴之所,谢知府杜无祖先父母乎?其不仁不义、恃豪强乃敢如此!”①
势豪谢知府强占他人田产物业之事,并不止以上二例。在《张凯夫诉谢知府宅贪并田产》的案件中,谢知府乘人之危贪并田产:“先欲遣逐其子,而后夺其产也。夫所立之子,妻不应遣逐;夫所有之产,寡妇不应出卖,二者皆是违法。绝人之嗣而夺其产,挟其妻以害其侄婿,此有人心者所不为也。……此两事并是违法。谢知府虽已移徙,其家尚留旧居。今乃倚恃豪撗,不肯赍出干照,使词诉无由结绝案。先给据将所管违法典卖田产监张凯夫具出号段,书填给付张凯夫管业收花利,仍再申安抚使司。”①在《王显论谢知府占庙》一案中,谢知府竟然连神灵的庙产也不放过。“西岳云滕庙,元是王显家舍地造庙以为邑民祈求之所。已而家贫,遂托神以自活,神依显之地以居,显依神之灵以食。谢知府既架屋其侧,遂占庙之路以为圃,又种竹于庙之四围,以芘荫其花圃宅场。民畏谢知府之形势,所谓邀福乞灵者,皆不敢过其门,而神之血食者,遂失其所依矣。王显本依神以活其家,谢知府又从而逐之,使其族人专庙祝之利,而王显又失其所依矣。谢知府但知形势之可以肆其欲,而不思神人共愤,则谢知府亦不能自安也。……士大夫欲创造屋庐以为子孙无穷之计,亦须顾理义、畏条法,然后心安而子孙可保也。今至于夷丘陇毁祠庙以广第宅,侈燕游携持孥累日居其中,果能下筦上簟而安斯寝乎?使官司不为之理直,而冥冥之间所谓福善祸淫者,亦岂无可畏者乎?所有庙地合给还王显照祖管业。”②
不仅如此,势豪谢知府一家作恶多端。在黄榦的判词中,还有一例是徐少十控告谢知府宅九官人及人力胡先强奸的案件。该判词书云:“胡先供去年曾与阿张通奸,又称今年系是和奸。据阿张供通去年不曾有通奸来历,今来系是强奸。两名所供异同。权官即不曾勘对着实,便欲将胡先、阿张同断。若是强奸,则阿张不应同断,胡先亦不应止从杖罪决遣。又阿张所供曾被谢九官人强奸,如此则是主仆通同强奸阿张,情理难恕。今亦不曾追问谢九官人,此是案吏怕惧谢知府形势,使贫弱之家受此屈抑。再引监阿张唤上胡先,仍追谢九官人对限。只今如追不到,备申诸司,仍先监词人起离外处居止,徐十元住谢家房屋。”③
势豪谢知府一家之所以可以横行乡里而肆无忌惮,关键就在于谢知府一家与当地官府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地方官吏或是畏惧谢家的权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蒙眬过事;或是受到谢家的贿赂赠惠,相互包庇。当黄榦审理谢九官人强奸一案时,谢家竟然可以指使一班士人替其喊冤叫屈。为此,黄榦不畏要挟,写出告示予以严正警告:“人为告罪,县道理断公事,自有条法。若事属小可,尚可从恕。至于身为士人,强奸人妻。在法合该徒配,岂容轻恕!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况又为人告不可恕之罪!则决非士类可知。榜县门,今后有士人辄入县庭为人告罪者,先勘断门子及本案人吏。”①
南宋晚年诸如谢知府这样的“士人”之所以敢于横行乡里、无视法纪,正是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当地的上层社会及官府中建立了相互为利而又相互袒护的关系网。在这种关系网的笼罩之下,许多受屈的一般民众,就很难得到国家法律真正的保护。即使有一部分敢于为民请命、坚持法纪的地方官员如黄榦等,在审理、执行法纪的过程中,也是阻力不断、困难重重。
《判词·窑户杨三十四等论谢知府宅强买砖瓦》记载谢知府的不法行为云:
窑户十七人,经县陈词论谢知府宅非理吊缚抑勒白要砖瓦事,本县追到干人邹彦、王明供对,两词各不从实供招,遂各散禁。今以两词供答参详,据干人赍到文约,并称所买砖瓦皆是大砖大瓦,则所供价例乃窑户之说,为是干人初供,以为小砖小瓦,则与元立文约不同,此乃是低价抑勒之验。窑户所以不得已而哀号于县庭也,小民以烧砖瓦为业,不过日求升合,以活其妻孥,惟恐人之不售也。所售愈多,则得利愈厚,岂有甘心饥饿而不求售者哉?寄居之家所还价直与民户等,彼亦何苦而不求售?今至于合为朋曹经官论诉,必是有甚不能平而后至此也。今观其所议收买砖瓦窑户不肯卖,便至于经官陈词,差弓手邹全、保正温彦追出。寄居之与民户初无统属,交关市易当取其情愿,岂有挟官司之号令逼勒,而使之中卖之理?至于立约,又不与之较物之厚薄小大与价之多寡,则异日结算以何为据?是不复照平常人户交易之例,而自有一种门庭,庶几支还多寡惟吾之命是听也。又先支每人钱米共约八贯,而欲使之入纳砖瓦万三千片。所纳未足,更不支钱。一万三千砖瓦所直十七千,今乃只得钱八贯,而欲其纳足,窑户安得余钱,可以先为烧造砖瓦纳足,而后请钱耶?小民之贫,朝不谋夕,今其立约乃如此是。但知吾之形势可以抑勒,而不知理有不可,则必不能免人户之论诉也。今又以为元约一万三千,今只入五六千便作了足,即是现买现卖。本宅何不前期将钱借与各人?世间交易,未有不前期借钱以为定者。况所烧砖瓦非一人之力所能办,非一日之期所能成,必须作泥造坯,必须候干燥,必须入窑烧变,必经隔旬月而后成。今六月半得钱,七月半之后逐旋交纳。所入之价反多于所借之钱,岂得尚归罪于窑户耶?干人之词尚欲惩治窑户之背约。所谓文约,岂窑户之所情愿?追之以弓手、保正抑勒,而使之着押耳。官司二税,朝廷立为省限。形势之家,尚有出违省限不肯输纳者,况于私家非理之文约而可以责人之必不背约耶?寄居百姓,贵贱不同。张官置吏难以偏徇……谢知府宅干人赍到文约四纸,并称大砖大瓦;今状中却称是小样,显是诬赖。六月十三日交去定钱,七月半逐旋入去砖瓦,今却称是经隔三月。形势之家,欺凌乡民,率皆类此。……取索赖人砖瓦、欠人钱物,岂得以为无罪?不应收禁私家,却得将人打缚,官司不得禁人豪强之状,即此可见。①
在这个案件里,黄榦经过审理,看清了豪强谢知府倚仗权势,强行要窑户的一万三千片砖瓦,仅支付窑户“每人钱米共约八贯”。窑户向其索取砖瓦价钱,谢知府反而恶人先告状,把窑户们告上衙门,诉窑户违约。更有甚者,谢知府为了达到强夺窑户砖瓦的目的,还利用其在官府中的关系,擅自动用官差弓手,下乡恐吓拘押贫民,黄榦在《邹宗逸诉谢八官人违法刑害》的判词中说:“昨窑户并邹宗逸陈词,并是弓手骚扰。在法弓手官司尚不得差出下乡,私家辄行差使,是以引惹人户词诉。况佐官不得受状,近降旨挥甚严。今遣人出屋,辄以停藏为名,妄经尉司。县尉亦不契勘便行受理,此皆受制大家,深属未便。据词人所论专指谢八官人,乞行追究。今以两魁漕贡见该奏荐不伏出官,若事属利害,则虽命官亦合追逮。但今所陈以为干人,则难便令主仆供对,且唤上词人并最紧合干人邹季文、戴祥、张仲三名对。”①县衙尉司的庇护,是势豪谢知府一家得逞不法的重要原因。
势豪谢知府横行乡里,在黄榦所经手的判词中屡有提到。如在《彭念七论谢知府宅追扰》中,谢知府肆意役使乡民,稍不如意,即私自冒造官府文引,差使衙门中人拘押追索,该判词写道:“普天之下,莫非王民。虽有贵贱贫富之不同,其为国家之赤子则一而已。张官置吏,务以安存百姓,而形势之家,专欲骚扰细民。所谓寄居者,既叨冒朝廷官职,寄寓州县,尤当仰体国家矜百姓之意。今乃国家之官职,害国家之百姓。此岂士大夫所当为哉?近据彭念七状称,有次弟彭念九充谢知府宅甲头,……忽睹谢知府宅干人郭胜同胡甲头赍引前来,称是谢知府宅文字追唤彭念七、彭三一赴本宅根究,委实惧怕,不敢前去。……乃辄追扰其兄弟彭念七之不伏,勾追与其亲戚曾少四,尤不相干涉。又辄论诉其亲戚,如此支蔓,害及无辜,使细民何自而得安其生业耶?使谢知府宅存心平恕、不务刻削,为甲头何苦逃窜?至于逃窜,亦只得经官追其正身,岂得私出文引,追扰其兄弟,妄兴词诉,残害其亲戚?则是但知官职形势可以欺压细民,而略不体朝廷张官置吏存恤百姓之意,委实切害。”②
在《宋有论谢知府宅侵占坟地》案件中,谢知府竟然伪造交易文书、强迫宋氏家人画押,从而霸占宋氏园地。宋氏家人虽然屡屡上诉,但谢知府倚仗权势,勾结官府,案件拖延十年之久,不得理清,宋氏家人亦遭到谢知府私下关锁抑逼。黄榦到任之后,再次审理,他在《判词》中写道:“谢知府宅干人索干照理断,干人录白到契字,称宋有已曾作知见交钱着押。……宋有称宋朝英被谢知府宅关锁抑逼,一家恐畏,只得着押。……及索出宋有关书,乃是宋有、宋辅两户均分产业,内有众户尅留产业甲龙、甲师字两号,有祖父母墓共四所,兄弟商议不得典卖,关约分明。今谢知府宅乃于嘉定元年立契买置,只作宋朝英立契。岂有宋辅、宋有两名尅留物业,内有坟墓四所,乃径与宋辅之孙宋朝英交易之理?又岂有绍兴年间兄弟立约不得典卖,乃可以违约交易之理?以宋有共分物业乃能使之作知见人着押?则是以形势抑逼可知。交易之时,宋朝英年未及丁,则其畏惧听从亦无可疑者。宋有又曾经县经军经转运司论诉,竟不获伸,则其恃形势尤可见也。人家坟墓乃子孙百年醮祭之地,谢知府宅乃欲白夺以为园囿饮宴之所,谢知府杜无祖先父母乎?其不仁不义、恃豪强乃敢如此!”①
势豪谢知府强占他人田产物业之事,并不止以上二例。在《张凯夫诉谢知府宅贪并田产》的案件中,谢知府乘人之危贪并田产:“先欲遣逐其子,而后夺其产也。夫所立之子,妻不应遣逐;夫所有之产,寡妇不应出卖,二者皆是违法。绝人之嗣而夺其产,挟其妻以害其侄婿,此有人心者所不为也。……此两事并是违法。谢知府虽已移徙,其家尚留旧居。今乃倚恃豪撗,不肯赍出干照,使词诉无由结绝案。先给据将所管违法典卖田产监张凯夫具出号段,书填给付张凯夫管业收花利,仍再申安抚使司。”①在《王显论谢知府占庙》一案中,谢知府竟然连神灵的庙产也不放过。“西岳云滕庙,元是王显家舍地造庙以为邑民祈求之所。已而家贫,遂托神以自活,神依显之地以居,显依神之灵以食。谢知府既架屋其侧,遂占庙之路以为圃,又种竹于庙之四围,以芘荫其花圃宅场。民畏谢知府之形势,所谓邀福乞灵者,皆不敢过其门,而神之血食者,遂失其所依矣。王显本依神以活其家,谢知府又从而逐之,使其族人专庙祝之利,而王显又失其所依矣。谢知府但知形势之可以肆其欲,而不思神人共愤,则谢知府亦不能自安也。……士大夫欲创造屋庐以为子孙无穷之计,亦须顾理义、畏条法,然后心安而子孙可保也。今至于夷丘陇毁祠庙以广第宅,侈燕游携持孥累日居其中,果能下筦上簟而安斯寝乎?使官司不为之理直,而冥冥之间所谓福善祸淫者,亦岂无可畏者乎?所有庙地合给还王显照祖管业。”②
不仅如此,势豪谢知府一家作恶多端。在黄榦的判词中,还有一例是徐少十控告谢知府宅九官人及人力胡先强奸的案件。该判词书云:“胡先供去年曾与阿张通奸,又称今年系是和奸。据阿张供通去年不曾有通奸来历,今来系是强奸。两名所供异同。权官即不曾勘对着实,便欲将胡先、阿张同断。若是强奸,则阿张不应同断,胡先亦不应止从杖罪决遣。又阿张所供曾被谢九官人强奸,如此则是主仆通同强奸阿张,情理难恕。今亦不曾追问谢九官人,此是案吏怕惧谢知府形势,使贫弱之家受此屈抑。再引监阿张唤上胡先,仍追谢九官人对限。只今如追不到,备申诸司,仍先监词人起离外处居止,徐十元住谢家房屋。”③
势豪谢知府一家之所以可以横行乡里而肆无忌惮,关键就在于谢知府一家与当地官府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地方官吏或是畏惧谢家的权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蒙眬过事;或是受到谢家的贿赂赠惠,相互包庇。当黄榦审理谢九官人强奸一案时,谢家竟然可以指使一班士人替其喊冤叫屈。为此,黄榦不畏要挟,写出告示予以严正警告:“人为告罪,县道理断公事,自有条法。若事属小可,尚可从恕。至于身为士人,强奸人妻。在法合该徒配,岂容轻恕!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况又为人告不可恕之罪!则决非士类可知。榜县门,今后有士人辄入县庭为人告罪者,先勘断门子及本案人吏。”①
南宋晚年诸如谢知府这样的“士人”之所以敢于横行乡里、无视法纪,正是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当地的上层社会及官府中建立了相互为利而又相互袒护的关系网。在这种关系网的笼罩之下,许多受屈的一般民众,就很难得到国家法律真正的保护。即使有一部分敢于为民请命、坚持法纪的地方官员如黄榦等,在审理、执行法纪的过程中,也是阻力不断、困难重重。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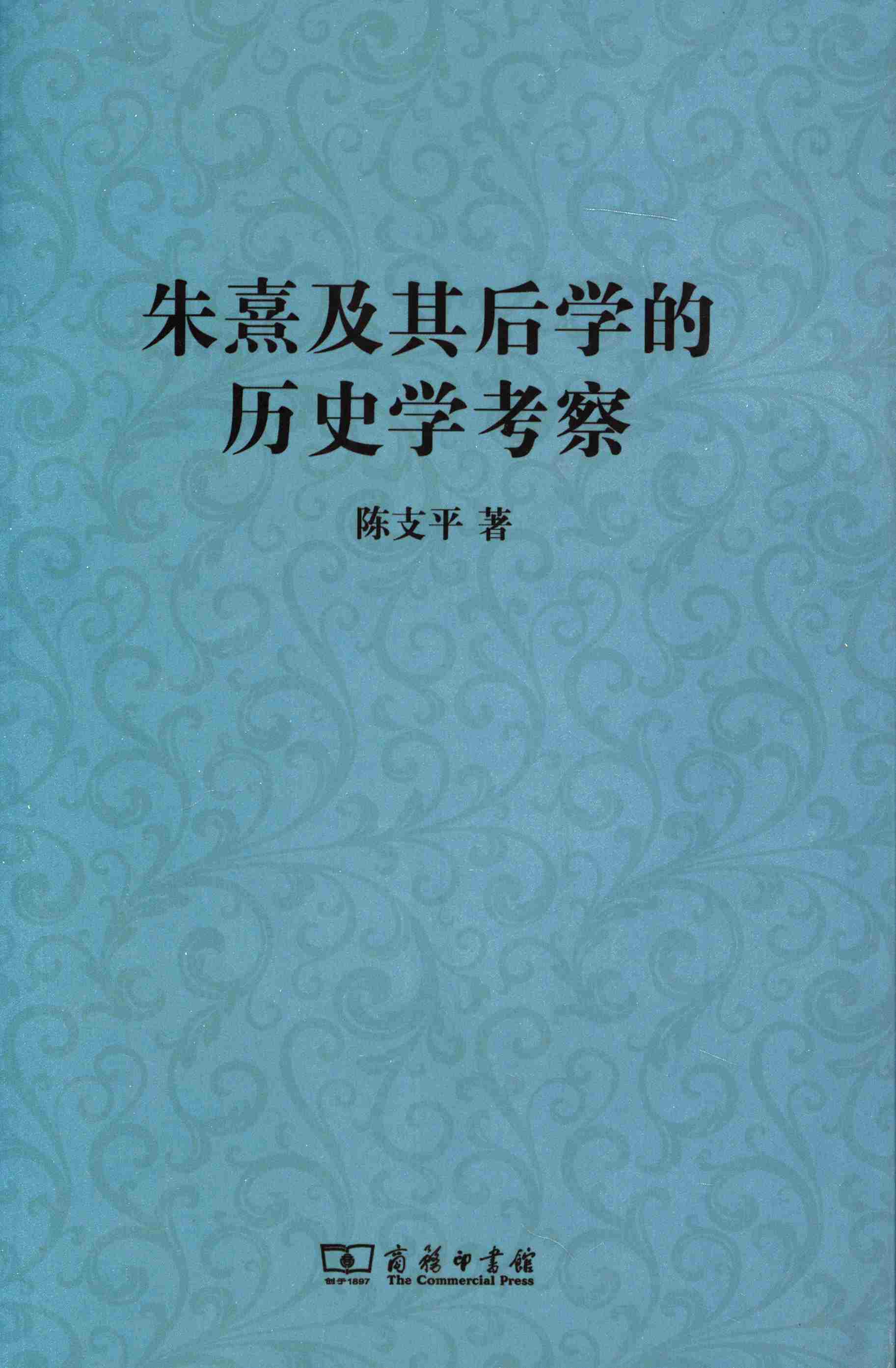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本书主要考察朱熹及其后学们究竟为当时的社会做了些什么,以及这些事情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朱熹和他的学生们,有从政的经历,也有当平民的经历,他们在所谓的“行”的实践上,表现更多。鉴于此,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朱子学,突破了从哲学视角研究朱子学的传统。与从哲学视角注重“想什么”不同,历史学更注重“做什么”。作者以自己所擅长的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对朱熹及其后学在这两个领域的所作所为,做出了尝试性的分析。
阅读
相关人物
黄榦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