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时期儒者的代表性家族设计
| 内容出处: |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822 |
| 颗粒名称: | (一)北宋时期儒者的代表性家族设计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2 |
| 页码: | 16-2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北宋时期,理学家张载和二程兄弟在重建家族制度的设计上非常有名。张载在《正蒙》和《经学理窟》中提出了自己的设计理念,尤其在《经学理窟·宗法》中详细阐述了重建宋代家族制度的基本构想。他强调重要性,包括管理人心、弘扬宗族风俗和确立宗子法。他认为如果不立宗法,人们就无法知道自己的族系来源,家族及国家的统一都会受到影响。他还提到宗子法的重要性,认为如果不确立宗子法,后世将无法知道某个家族的来源,家族的传承也会中断。他认为宗子法的确立对朝廷有益处,可以保障家族的延续并给予朝廷忠诚的支持。此外,他还强调了家族庙宇、祭祀和祭田等要素的重要性,其中关于家庙和祭祀的规定受到先秦宗法制度的影响。他通过确立宗子的领导地位,模仿了先秦时期诸侯的嫡长继承制度,强调宗子在家族中的权威地位,并将其提升到与大君相仿佛的崇高地位。张载认为宗子应该承担起保护家族中贫弱孤独的责任,并强调宗子纯孝的重要性。总的来说,张载的构想中涉及家族庙宇、谱牒、祭祀以及宗子等多个方面,他认为通过重建家族制度可以推动家族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
| 关键词: | 北宋时期 儒者 家族设计 |
内容
北宋时期儒者对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最著名的莫过于理学家张载和二程兄弟。张载在其著作《正蒙》和《经学理窟》中都对重建新的家族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设计理念。特别是在《经学理窟·宗法》中,比较集中地提出了重建宋代家族制度的基本构想。《宗法》篇略云: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夫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来宗己,非己宗于人也。所以继祢则谓之继祢之宗;继祖则谓之继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独宗子之为士,为庶人亦然。……后来朝廷有制,曾任两府则宅舍不许分,意欲后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尝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则此亦不济事。……其所以旌别之意甚善,然亦处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绝嗣。不若各就坟冢给与田五七顷,与一闲名目,使之世守其禄,不惟可以为天下忠义之劝,亦是为忠义者实受其报。……
王制言“大夫之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若诸侯则以有国,指始封之君为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宗子既庙其祖祢,支子不得别祭,所以严宗庙,合族属。故曰“庶子不祭祖祢,明其宗也”。①
张载在这一关于家族重建的构想中,除了论述重建家族制度对于“国”与“家”的重要性之外,已经基本触及宋代以来中国家族的三大要素,即家庙(祠堂)、谱牒、祭祀与祭田等。对于谱牒,张载语焉不详,但是对于家庙与祭祀,则有着比较严格的规定。而这种比较严格的规定,显然是从先秦时期的“宗法”制中仿制下来的。尤其是对于新建家族中的领导者——宗子,基本上是模仿先秦时期诸侯继承的嫡长体制。
为了确立“宗子”的领导权威,张载首先对“宗”予以“人来宗己”的绝对地位,即所谓“夫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来宗己,非己宗于人也”。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则把“宗子”提高到与“大君”相仿佛的崇高地位,“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②。家族的“宗子”,就应该跟“大君”一样,统属家族内部的尊贵贫贱、茕独鳏寡,“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
作为家族的当然领导者,张载赋予“宗子”主持家族祭祀的权利。“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独宗子之为士,为庶人亦然。”这就是说,宗子是家族中主持祭祀的人。即使宗子身份是士,庶子的地位在大夫以上,家族的祭祀也必须在宗子的家中举行。社会地位的变化,不能改变家族内部宗子的地位。即使宗子连士的身份都没有,只是个庶人或者平民,家族中的祭祀活动依然由宗子主持。
当然,对于三代先秦的宗子制,张载也做了一些变通之法,如对于古代的“支子不祭”,张载认为:“古所谓‘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庙主之而已。支子虽不得祭,至于斋戒致其诚意,则与祭者不异;与则以身执事,不可与则以物助之。但不别立庙,为位行事而已。后世如欲立宗子,当从此义。虽不与祭,情亦可安。”这就是说,支子虽然没有资格主持祭祀,但是他们的态度和情感必须和主持祭祀的宗子一样真诚,那么是可以参与祭祀活动的。只不过支子们只能依附在宗子之后参与祭祀,是绝对不能自己立庙,自己主持祭祀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张载继续论说云:“宗子既庙其祖祢,支子不得别祭,所以严宗庙,合族属,故曰‘庶子不祭祖祢,明其宗也’。”①
在三代先秦时期,祭祀是国家及诸侯事务中的头等大事之一,如果严格按照古代礼制,祭祀活动将是一项非常烦琐沉重的负担,这势必会让一般官宦人家的祭祀活动无法长久坚持下去。更不要说下层的普通民众了。对此,张载又设计出祭祀的变通方法。他说:
今之士大夫,主既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则无义。天子七庙,一日而行则力不给。故礼有一特一祫之说。仲特则祭一,祫则遍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群庙;秋祭曾,冬又祫;来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祢,冬又祫。铺筵设同几,只设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凡人家正厅,似所谓庙也,犹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为祭祀、吉凶、冠婚之事,于此行之。厅后谓之寝,又有适寝,是下室,所居之室也。①
张载认为烦琐的祭祀之礼,可能不是一般民众所能承受,因此设计在普通人居家的正厅,可以当作祭祀祖先的场所,正好如天子所居的大殿一样。这个地方不能住人,专门作为家族内部举行祭祀、占卜吉凶、成人礼、婚礼等重大活动的场所。如此降低家庙的规格和礼数要求,就为家族重建的普遍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前提。
从以上张载对于宋代家族制度的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仿三代先秦诸侯祭祀及其承继的“宗子”法是这个制度的核心内容。而这个新的“宗子”法,在更多的场合是适应于宋代的新兴官僚阶层的,而不适应于一般的贫民家庭与家族。这正如我们上面在引述张载的《宗法》篇中所云:“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宗子法的重建,就可以比较稳妥地维系新兴官僚阶层的长远地位。正因为如此,在宗子的继承方面,张载又设定了官僚身份为先的原则。他举周代周武王非长子而得继的故事云:“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则须是却为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闻有罪,只为武王之圣,顾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绪,故须立武王。……至如人有数子,长者至微贱不立,其间一子仕宦,则更不问长少,须是士人承祭祀。”①
为了确保宗子的地位与权力,不仅家族内部必须予以重点培植,张载同时还建议朝廷也应该以立法等方式,保护宗子的优先地位,特别是在政治仕途上的权力。他说:“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数子,且以适长为大宗,须据所有家计厚给以养宗子。宗子势重,即愿得之。供宗子外乃将所有均给族人。宗子须专立教授,宗子之得失,责在教授。其他族人,别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条,族人须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许族人将已合转官恩泽乞回授宗子,不理选限官,及许将奏荐子弟恩泽与宗子,且要主张门户。宗子不善,则别择其次贤者立之。”②
张载对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先秦时期的“宗法”制进行了变通,但是从整体而言,基本上是把先秦诸侯体制下的宗子法仿制于宋代的官僚体制之上。因而这种以宗子为核心的新的家族制度的建构,并不十分适用于一般的贫民社会。尽管如此,张载关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还是为后世的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兴起,理清了一个可供继续模仿和改进的样式,因此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与张载同时代的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同样也对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建构多有思考与论述。程颢、程颐兄弟同样认为要建构新的家族制度,三代先秦时期的“宗子法”是一种值得效法的形式。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上古时代的“宗子法”败坏,才导致了唐宋以来社会的混乱无序与道德沦丧,“宗子法坏,则人不自知来处,以至流转四方,往往亲未绝,不相识”③。要使纷乱的社会重新走上有序的轨道,就需要恢复上古的“宗子法”,“今无宗子法,故朝廷无世臣。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古者子弟从父兄,今父兄从子弟,子弟为强。由不知本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从根直上一干,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虽远,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处,自然之势也。然又有旁枝达而为干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国,诸侯夺宗云。’”①“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②
上古的宗法制度既然已经败坏,宋代与周代的社会状态已经完全不同,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恢复周代的宗法制度不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是,既然是重建家族,就必须具有家族制度最基本的内容——宗子之法。那么如何重建宗子之法?程颐认为不妨先从若干仕宦大家开始试行:“宗子法坏,……今且试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术要得拘守得须是。且如唐时立庙院,仍不得分割了祖业,使一人主之。”③“宗法须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则人人各知来处。宗子者,谓宗主祭祀也。”④
在一般的情况下,宗子是以嫡长兄为之。宗子具有统率本家族其他成员的权利,特别是负有家族祭祀的权利。对于以宗子为核心的家族祭祀,二程兄弟的设想与张载几乎相同:“古所谓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庙,主之而已。支子虽不得祭,至于斋戒,致其诚意,则与主祭者不异。可与,则以身执事;不可与,则以物助,但不别立庙为位行事而已。后世如欲立宗子,当从此义。虽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废祭,适足长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犹愈于已也。”⑤一个家族的其他儿子即支子,没有主持祭祀的权利,只有宗子有这个权利,因此宗子必须建立家庙,以主持祭祀活动。支子虽然不主持祭祀,但必须诚心诚意地参加斋戒活动,态度必须与主持祭祀的宗子完全一样。如果有条件,最好能够亲身参与;如果不能亲身参与,必须提供物资帮助。但是,支子不能自己立庙主持祭祀。所以,重建家族,再立宗子,必须遵守这个规矩。
二程兄弟对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构建,与张载的设计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以“宗子法”为家族权利核心,家族其他成员依附于宗子之下的一种社会凝聚模式。“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于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于人也。”①而这种“宗子法”,同样比较适用于官僚士大夫家族与家庭,因此,他特别强调说:“士大夫必建家庙。”②
二程兄弟在设计这种家族结构模式的同时,还对家族内部及家庭内部的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进行了思考。程颐对于自己撰写的《六礼》颇为自负,他说:“冠昏丧祭,礼之大者,今人都不以为事。某旧曾修《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将就后,被召遂罢,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间多恋河北旧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渐使知义理,一二年书成,可皆如法。礼从宜,事从俗,有大故害义理者,须当去。”③从现存的文献看,程颐的《六礼》,可能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存留下来的条文相当简略。但是从这些简略的条文中,还是看出二程兄弟对于重建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的重视。如他对父母兄弟之间关系的叙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爱,且如闾阎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于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体重于己之体也。至于犬马亦然。待父母之犬马,必异乎己之犬马也。……或曰:‘事兄尽礼,不得兄之欢心,奈何?’曰:‘但当起敬起孝,尽至诚,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尽友爱之道而已。’”①从这些简略的条文叙述中,已经可以反映出程颐所强调的以孝道为中心的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的基本指向。
对宋代新建家族制度之下的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进行比较详细设计的儒者,是当时的著名士人司马光。他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还编写了《家范》《书仪》两本关于重建家族的著作。《家范》《书仪》的要旨在于协调家族内部及家庭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家族内部各色人等的行为规范,重新建立一种适应于宋代社会的家族伦理和家庭伦理。司马光在这两部著作中所体现出来“家范”“书仪”的主要来源依据,仍然是先秦时期的礼制。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总纂官纪昀等在《家范》的提要中即明确指出这一点:“《家范》十卷,宋司马光撰。……首载《周易·家人》卦辞、及节录《大学》《孝经》《尧典》《诗·思齐篇》语,以为全书之序。其后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杂采史事可为法则者。……朱子尝论《周礼·师氏》云:‘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程颢)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观于是编,犹可见一代伟人修己型家之梗概也。”②我们再来看看司马光在《家范》的开篇序言中所引述的内容:
《周易》:离下巽上。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爱者所以使众也。《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孝经》曰: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昔四岳荐舜于尧,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诗》称文王之德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降及后世,爰自卿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为人法者,今采集以为《家范》。①
司马光在《家范》序言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思维方式,正体现了北宋时期一般儒者对于重建家族制度与家庭伦理的基本理念,即既然要重建家族,就必须有所依傍,而所依傍者的基本来源,只能是古代的宗法体制和上古的所谓“周礼”。虽然说三代先秦时期的这种制度早已成为历史遗迹,但是在司马光等宋儒的采集张扬之下,上古的这些礼制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家族伦理与家庭伦理,依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司马光等所宣扬的“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以及男尊女卑的家族与家庭伦理,就基本上被宋之后的中国社会所承继。司马光在《家范》《书仪》中所体现出来的家族内部伦理和家庭内部伦理,正与张载的家族制度构建框架设计,形成宋代以来新的家族制度的两个基本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谈到北宋时期儒者对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时,我们还不能忽视欧阳修、苏洵等人对于家族谱牒的撰写与推广。重建家族没有家谱是不行的,正如上述张载在《宗法》篇中所指出的“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把修族谱与立宗子法提高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唐宋以前门阀制的谱牒已经废绝,魏晋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对谱牒的垄断必须予以打破,使之适应于宋代社会的一般家族与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士大夫和儒者进行了重新撰写家谱的尝试与实践。宋仁宗皇祐、至和年间(1049~1056)欧阳修编的《欧阳氏族谱》和苏洵编的《苏氏族谱》,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被后世视为宋儒重写新家谱的开端,从此之后,许多士大夫家族,乃至一般的民众家族,也都纷纷以欧阳氏、苏氏族谱为典范,为自己的宗族编修族谱,“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①。欧阳修和苏洵二人,也对自己撰写的族谱相当自负,希望能够由此而推广于天下,使天下所有家族在撰修族谱时有所依据。所谓“是不可使独吾二人为之,将天下举不可无也”①。于是,在欧阳修、苏洵及其他士大夫和儒者的推动下,宋代及其后来就逐渐形成“私谱盛行”的局面。
欧阳修与苏洵对于宋代家族族谱修撰尝试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宋代以前门阀士族谱牒官府编修的性质,改变为私家编修的性质。唐代以前的谱牒,是为了明确诸侯、门阀士族的出身和血统,是世袭制及朝廷提拔官员的依据,也是家族之间联姻的依据。而苏洵、欧阳修等人所创建的宋代族谱,纯粹就是为了维系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它成了凝聚家族以使之长久生存的历史记载与精神力量。虽然亲情联系势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行渐远,但是有了私家族谱的存在,多少有所凭借,有所维系。苏洵在自己撰写的族谱《谱例》中说:
古者诸侯世国,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庙,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独贤士大夫尊祖而贵宗,盖其昭穆存乎其庙,迁毁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与为服,死丧嫁娶相告而不绝,则其势将自至于不忘也。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②
苏洵根据上溯六世祖先的原则,编写了自家的族谱,不由得感慨道:
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见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缌麻,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涂人也。吾之所与相视如涂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
人之身分,而至于涂(途)人,此吾谱之所以作也。①
欧阳修在自己修撰的族谱中也指出,新修的族谱必须“断自可见之世”,从而使得真正的血缘联系“各详其亲,各系其所出”,达到亲疏有伦的目的:
姓氏之出,其来也远,故其上世多亡不见。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如此世久,子孙多则官爵功行载于谱者,不胜其繁。宜以远近亲疏为别,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孙既别自为世,则各详其亲,各系其所出。是详者不繁而略者不遗也。凡诸房子孙,各纪其当纪者,使谱谍互见,亲疏有伦。②
北宋时期张载、二程兄弟、司马光、欧阳修、苏洵等著名儒者关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与建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三代先秦时期的“宗法制”与礼制作为蓝本而推衍出来的带有一定复古性质的模式,但是这些设计毕竟完成了宋代及其后世中国家族制度的基本框架与家族、家庭伦理的价值取向,因而这些设计与实践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而这些设计更侧重于士大夫官僚家族而不适用于一般民众家族的缺陷,就有待于南宋及其后世的不断改进与推行了。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夫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来宗己,非己宗于人也。所以继祢则谓之继祢之宗;继祖则谓之继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独宗子之为士,为庶人亦然。……后来朝廷有制,曾任两府则宅舍不许分,意欲后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尝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则此亦不济事。……其所以旌别之意甚善,然亦处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绝嗣。不若各就坟冢给与田五七顷,与一闲名目,使之世守其禄,不惟可以为天下忠义之劝,亦是为忠义者实受其报。……
王制言“大夫之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若诸侯则以有国,指始封之君为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宗子既庙其祖祢,支子不得别祭,所以严宗庙,合族属。故曰“庶子不祭祖祢,明其宗也”。①
张载在这一关于家族重建的构想中,除了论述重建家族制度对于“国”与“家”的重要性之外,已经基本触及宋代以来中国家族的三大要素,即家庙(祠堂)、谱牒、祭祀与祭田等。对于谱牒,张载语焉不详,但是对于家庙与祭祀,则有着比较严格的规定。而这种比较严格的规定,显然是从先秦时期的“宗法”制中仿制下来的。尤其是对于新建家族中的领导者——宗子,基本上是模仿先秦时期诸侯继承的嫡长体制。
为了确立“宗子”的领导权威,张载首先对“宗”予以“人来宗己”的绝对地位,即所谓“夫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来宗己,非己宗于人也”。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则把“宗子”提高到与“大君”相仿佛的崇高地位,“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②。家族的“宗子”,就应该跟“大君”一样,统属家族内部的尊贵贫贱、茕独鳏寡,“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
作为家族的当然领导者,张载赋予“宗子”主持家族祭祀的权利。“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独宗子之为士,为庶人亦然。”这就是说,宗子是家族中主持祭祀的人。即使宗子身份是士,庶子的地位在大夫以上,家族的祭祀也必须在宗子的家中举行。社会地位的变化,不能改变家族内部宗子的地位。即使宗子连士的身份都没有,只是个庶人或者平民,家族中的祭祀活动依然由宗子主持。
当然,对于三代先秦的宗子制,张载也做了一些变通之法,如对于古代的“支子不祭”,张载认为:“古所谓‘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庙主之而已。支子虽不得祭,至于斋戒致其诚意,则与祭者不异;与则以身执事,不可与则以物助之。但不别立庙,为位行事而已。后世如欲立宗子,当从此义。虽不与祭,情亦可安。”这就是说,支子虽然没有资格主持祭祀,但是他们的态度和情感必须和主持祭祀的宗子一样真诚,那么是可以参与祭祀活动的。只不过支子们只能依附在宗子之后参与祭祀,是绝对不能自己立庙,自己主持祭祀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张载继续论说云:“宗子既庙其祖祢,支子不得别祭,所以严宗庙,合族属,故曰‘庶子不祭祖祢,明其宗也’。”①
在三代先秦时期,祭祀是国家及诸侯事务中的头等大事之一,如果严格按照古代礼制,祭祀活动将是一项非常烦琐沉重的负担,这势必会让一般官宦人家的祭祀活动无法长久坚持下去。更不要说下层的普通民众了。对此,张载又设计出祭祀的变通方法。他说:
今之士大夫,主既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则无义。天子七庙,一日而行则力不给。故礼有一特一祫之说。仲特则祭一,祫则遍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群庙;秋祭曾,冬又祫;来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祢,冬又祫。铺筵设同几,只设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凡人家正厅,似所谓庙也,犹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为祭祀、吉凶、冠婚之事,于此行之。厅后谓之寝,又有适寝,是下室,所居之室也。①
张载认为烦琐的祭祀之礼,可能不是一般民众所能承受,因此设计在普通人居家的正厅,可以当作祭祀祖先的场所,正好如天子所居的大殿一样。这个地方不能住人,专门作为家族内部举行祭祀、占卜吉凶、成人礼、婚礼等重大活动的场所。如此降低家庙的规格和礼数要求,就为家族重建的普遍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前提。
从以上张载对于宋代家族制度的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仿三代先秦诸侯祭祀及其承继的“宗子”法是这个制度的核心内容。而这个新的“宗子”法,在更多的场合是适应于宋代的新兴官僚阶层的,而不适应于一般的贫民家庭与家族。这正如我们上面在引述张载的《宗法》篇中所云:“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宗子法的重建,就可以比较稳妥地维系新兴官僚阶层的长远地位。正因为如此,在宗子的继承方面,张载又设定了官僚身份为先的原则。他举周代周武王非长子而得继的故事云:“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则须是却为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闻有罪,只为武王之圣,顾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绪,故须立武王。……至如人有数子,长者至微贱不立,其间一子仕宦,则更不问长少,须是士人承祭祀。”①
为了确保宗子的地位与权力,不仅家族内部必须予以重点培植,张载同时还建议朝廷也应该以立法等方式,保护宗子的优先地位,特别是在政治仕途上的权力。他说:“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数子,且以适长为大宗,须据所有家计厚给以养宗子。宗子势重,即愿得之。供宗子外乃将所有均给族人。宗子须专立教授,宗子之得失,责在教授。其他族人,别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条,族人须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许族人将已合转官恩泽乞回授宗子,不理选限官,及许将奏荐子弟恩泽与宗子,且要主张门户。宗子不善,则别择其次贤者立之。”②
张载对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先秦时期的“宗法”制进行了变通,但是从整体而言,基本上是把先秦诸侯体制下的宗子法仿制于宋代的官僚体制之上。因而这种以宗子为核心的新的家族制度的建构,并不十分适用于一般的贫民社会。尽管如此,张载关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还是为后世的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兴起,理清了一个可供继续模仿和改进的样式,因此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与张载同时代的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同样也对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建构多有思考与论述。程颢、程颐兄弟同样认为要建构新的家族制度,三代先秦时期的“宗子法”是一种值得效法的形式。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上古时代的“宗子法”败坏,才导致了唐宋以来社会的混乱无序与道德沦丧,“宗子法坏,则人不自知来处,以至流转四方,往往亲未绝,不相识”③。要使纷乱的社会重新走上有序的轨道,就需要恢复上古的“宗子法”,“今无宗子法,故朝廷无世臣。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古者子弟从父兄,今父兄从子弟,子弟为强。由不知本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从根直上一干,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虽远,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处,自然之势也。然又有旁枝达而为干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国,诸侯夺宗云。’”①“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②
上古的宗法制度既然已经败坏,宋代与周代的社会状态已经完全不同,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恢复周代的宗法制度不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是,既然是重建家族,就必须具有家族制度最基本的内容——宗子之法。那么如何重建宗子之法?程颐认为不妨先从若干仕宦大家开始试行:“宗子法坏,……今且试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术要得拘守得须是。且如唐时立庙院,仍不得分割了祖业,使一人主之。”③“宗法须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则人人各知来处。宗子者,谓宗主祭祀也。”④
在一般的情况下,宗子是以嫡长兄为之。宗子具有统率本家族其他成员的权利,特别是负有家族祭祀的权利。对于以宗子为核心的家族祭祀,二程兄弟的设想与张载几乎相同:“古所谓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庙,主之而已。支子虽不得祭,至于斋戒,致其诚意,则与主祭者不异。可与,则以身执事;不可与,则以物助,但不别立庙为位行事而已。后世如欲立宗子,当从此义。虽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废祭,适足长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犹愈于已也。”⑤一个家族的其他儿子即支子,没有主持祭祀的权利,只有宗子有这个权利,因此宗子必须建立家庙,以主持祭祀活动。支子虽然不主持祭祀,但必须诚心诚意地参加斋戒活动,态度必须与主持祭祀的宗子完全一样。如果有条件,最好能够亲身参与;如果不能亲身参与,必须提供物资帮助。但是,支子不能自己立庙主持祭祀。所以,重建家族,再立宗子,必须遵守这个规矩。
二程兄弟对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构建,与张载的设计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以“宗子法”为家族权利核心,家族其他成员依附于宗子之下的一种社会凝聚模式。“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于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于人也。”①而这种“宗子法”,同样比较适用于官僚士大夫家族与家庭,因此,他特别强调说:“士大夫必建家庙。”②
二程兄弟在设计这种家族结构模式的同时,还对家族内部及家庭内部的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进行了思考。程颐对于自己撰写的《六礼》颇为自负,他说:“冠昏丧祭,礼之大者,今人都不以为事。某旧曾修《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将就后,被召遂罢,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间多恋河北旧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渐使知义理,一二年书成,可皆如法。礼从宜,事从俗,有大故害义理者,须当去。”③从现存的文献看,程颐的《六礼》,可能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存留下来的条文相当简略。但是从这些简略的条文中,还是看出二程兄弟对于重建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的重视。如他对父母兄弟之间关系的叙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爱,且如闾阎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于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体重于己之体也。至于犬马亦然。待父母之犬马,必异乎己之犬马也。……或曰:‘事兄尽礼,不得兄之欢心,奈何?’曰:‘但当起敬起孝,尽至诚,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尽友爱之道而已。’”①从这些简略的条文叙述中,已经可以反映出程颐所强调的以孝道为中心的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的基本指向。
对宋代新建家族制度之下的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进行比较详细设计的儒者,是当时的著名士人司马光。他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还编写了《家范》《书仪》两本关于重建家族的著作。《家范》《书仪》的要旨在于协调家族内部及家庭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家族内部各色人等的行为规范,重新建立一种适应于宋代社会的家族伦理和家庭伦理。司马光在这两部著作中所体现出来“家范”“书仪”的主要来源依据,仍然是先秦时期的礼制。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总纂官纪昀等在《家范》的提要中即明确指出这一点:“《家范》十卷,宋司马光撰。……首载《周易·家人》卦辞、及节录《大学》《孝经》《尧典》《诗·思齐篇》语,以为全书之序。其后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杂采史事可为法则者。……朱子尝论《周礼·师氏》云:‘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程颢)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观于是编,犹可见一代伟人修己型家之梗概也。”②我们再来看看司马光在《家范》的开篇序言中所引述的内容:
《周易》:离下巽上。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爱者所以使众也。《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孝经》曰: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昔四岳荐舜于尧,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诗》称文王之德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降及后世,爰自卿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为人法者,今采集以为《家范》。①
司马光在《家范》序言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思维方式,正体现了北宋时期一般儒者对于重建家族制度与家庭伦理的基本理念,即既然要重建家族,就必须有所依傍,而所依傍者的基本来源,只能是古代的宗法体制和上古的所谓“周礼”。虽然说三代先秦时期的这种制度早已成为历史遗迹,但是在司马光等宋儒的采集张扬之下,上古的这些礼制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家族伦理与家庭伦理,依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司马光等所宣扬的“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以及男尊女卑的家族与家庭伦理,就基本上被宋之后的中国社会所承继。司马光在《家范》《书仪》中所体现出来的家族内部伦理和家庭内部伦理,正与张载的家族制度构建框架设计,形成宋代以来新的家族制度的两个基本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谈到北宋时期儒者对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时,我们还不能忽视欧阳修、苏洵等人对于家族谱牒的撰写与推广。重建家族没有家谱是不行的,正如上述张载在《宗法》篇中所指出的“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把修族谱与立宗子法提高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唐宋以前门阀制的谱牒已经废绝,魏晋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对谱牒的垄断必须予以打破,使之适应于宋代社会的一般家族与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士大夫和儒者进行了重新撰写家谱的尝试与实践。宋仁宗皇祐、至和年间(1049~1056)欧阳修编的《欧阳氏族谱》和苏洵编的《苏氏族谱》,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被后世视为宋儒重写新家谱的开端,从此之后,许多士大夫家族,乃至一般的民众家族,也都纷纷以欧阳氏、苏氏族谱为典范,为自己的宗族编修族谱,“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①。欧阳修和苏洵二人,也对自己撰写的族谱相当自负,希望能够由此而推广于天下,使天下所有家族在撰修族谱时有所依据。所谓“是不可使独吾二人为之,将天下举不可无也”①。于是,在欧阳修、苏洵及其他士大夫和儒者的推动下,宋代及其后来就逐渐形成“私谱盛行”的局面。
欧阳修与苏洵对于宋代家族族谱修撰尝试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宋代以前门阀士族谱牒官府编修的性质,改变为私家编修的性质。唐代以前的谱牒,是为了明确诸侯、门阀士族的出身和血统,是世袭制及朝廷提拔官员的依据,也是家族之间联姻的依据。而苏洵、欧阳修等人所创建的宋代族谱,纯粹就是为了维系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它成了凝聚家族以使之长久生存的历史记载与精神力量。虽然亲情联系势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行渐远,但是有了私家族谱的存在,多少有所凭借,有所维系。苏洵在自己撰写的族谱《谱例》中说:
古者诸侯世国,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庙,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独贤士大夫尊祖而贵宗,盖其昭穆存乎其庙,迁毁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与为服,死丧嫁娶相告而不绝,则其势将自至于不忘也。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②
苏洵根据上溯六世祖先的原则,编写了自家的族谱,不由得感慨道:
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见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缌麻,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涂人也。吾之所与相视如涂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
人之身分,而至于涂(途)人,此吾谱之所以作也。①
欧阳修在自己修撰的族谱中也指出,新修的族谱必须“断自可见之世”,从而使得真正的血缘联系“各详其亲,各系其所出”,达到亲疏有伦的目的:
姓氏之出,其来也远,故其上世多亡不见。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如此世久,子孙多则官爵功行载于谱者,不胜其繁。宜以远近亲疏为别,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孙既别自为世,则各详其亲,各系其所出。是详者不繁而略者不遗也。凡诸房子孙,各纪其当纪者,使谱谍互见,亲疏有伦。②
北宋时期张载、二程兄弟、司马光、欧阳修、苏洵等著名儒者关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与建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三代先秦时期的“宗法制”与礼制作为蓝本而推衍出来的带有一定复古性质的模式,但是这些设计毕竟完成了宋代及其后世中国家族制度的基本框架与家族、家庭伦理的价值取向,因而这些设计与实践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而这些设计更侧重于士大夫官僚家族而不适用于一般民众家族的缺陷,就有待于南宋及其后世的不断改进与推行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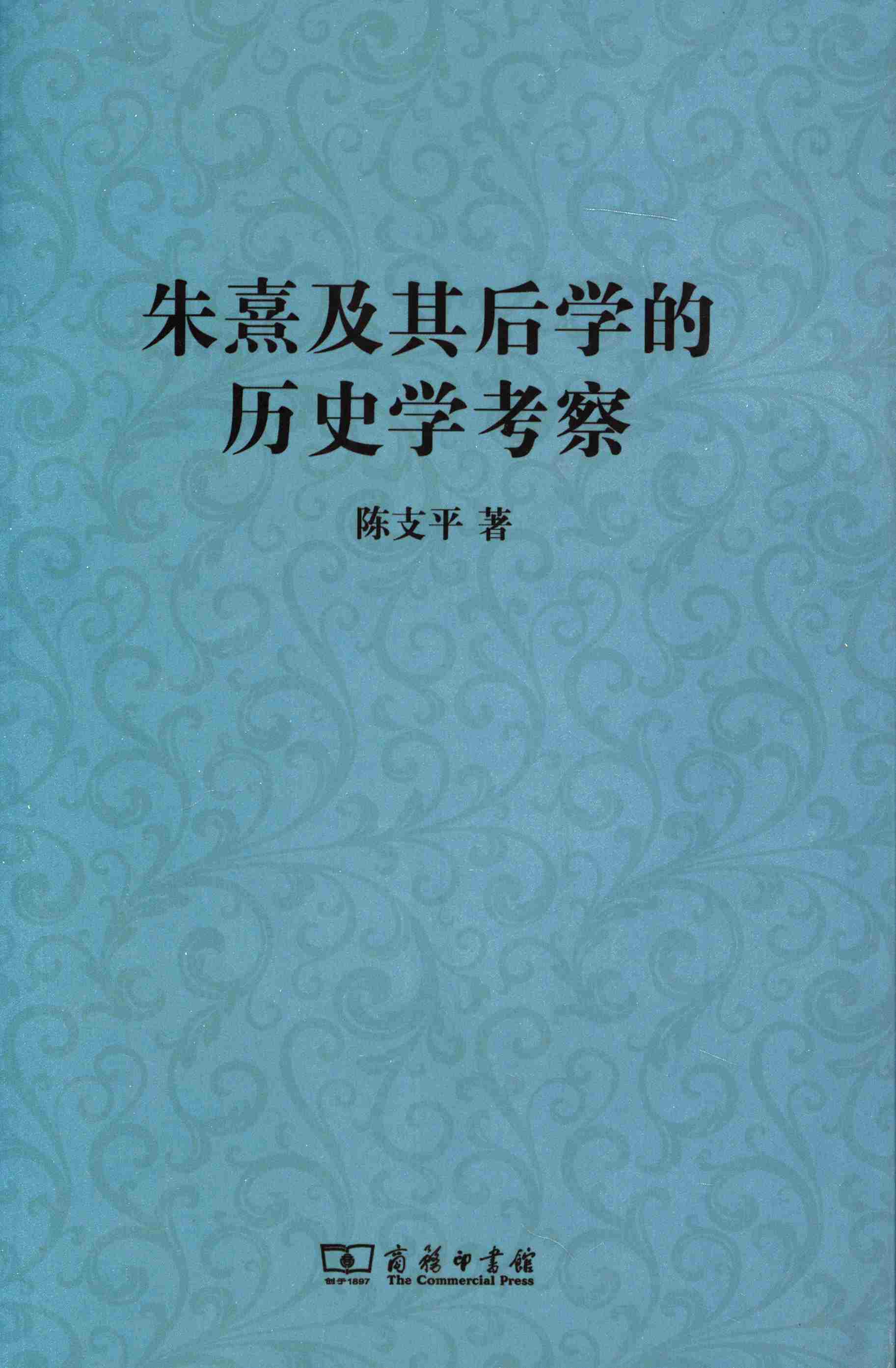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本书主要考察朱熹及其后学们究竟为当时的社会做了些什么,以及这些事情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朱熹和他的学生们,有从政的经历,也有当平民的经历,他们在所谓的“行”的实践上,表现更多。鉴于此,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朱子学,突破了从哲学视角研究朱子学的传统。与从哲学视角注重“想什么”不同,历史学更注重“做什么”。作者以自己所擅长的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对朱熹及其后学在这两个领域的所作所为,做出了尝试性的分析。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