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试论宋儒对于家族制度的设计及其变迁
| 内容出处: |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821 |
| 颗粒名称: | 二、试论宋儒对于家族制度的设计及其变迁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43 |
| 页码: | 15-5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试论宋儒对于家族制度的设计及其变迁的情况。其中包括北宋时期儒者的代表性家族设计、南宋朱熹等理学家对家族制度的改进、宋代儒者及士大夫对同居共财大家庭的宣扬与实践、宋代之后家族制度的变迁及对宋儒设计的若干修正等。 |
| 关键词: | 朱熹 家族制度 设计 |
内容
中国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到了隋唐时期,已经基本消亡。为了适应宋代新的社会体制与社会秩序,许多著名的宋代儒者都试图重新建立一种适应于科举制度之下的官僚体系与平民社会的新的家族制度或宗族制度(以下合称之为家族制度),以维系国家与社会的正常运行。然而,在北宋时期儒者所向往与设计的新的家族制度的范本中,更多的是模仿先秦时期的“宗法”体制,与宋代的民间社会实际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于是,自南宋以降,儒者们不断地对民间家族制度的设计进行修正,使之更为切合民间社会的实际情况,从而成为南宋以来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基本社会体制。下面,我们就对宋代儒者对于家族制度的设计及其变迁历程,进行一个概述性的分析。
(一)北宋时期儒者的代表性家族设计
北宋时期儒者对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最著名的莫过于理学家张载和二程兄弟。张载在其著作《正蒙》和《经学理窟》中都对重建新的家族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设计理念。特别是在《经学理窟·宗法》中,比较集中地提出了重建宋代家族制度的基本构想。《宗法》篇略云: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夫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来宗己,非己宗于人也。所以继祢则谓之继祢之宗;继祖则谓之继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独宗子之为士,为庶人亦然。……后来朝廷有制,曾任两府则宅舍不许分,意欲后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尝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则此亦不济事。……其所以旌别之意甚善,然亦处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绝嗣。不若各就坟冢给与田五七顷,与一闲名目,使之世守其禄,不惟可以为天下忠义之劝,亦是为忠义者实受其报。……
王制言“大夫之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若诸侯则以有国,指始封之君为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宗子既庙其祖祢,支子不得别祭,所以严宗庙,合族属。故曰“庶子不祭祖祢,明其宗也”。①
张载在这一关于家族重建的构想中,除了论述重建家族制度对于“国”与“家”的重要性之外,已经基本触及宋代以来中国家族的三大要素,即家庙(祠堂)、谱牒、祭祀与祭田等。对于谱牒,张载语焉不详,但是对于家庙与祭祀,则有着比较严格的规定。而这种比较严格的规定,显然是从先秦时期的“宗法”制中仿制下来的。尤其是对于新建家族中的领导者——宗子,基本上是模仿先秦时期诸侯继承的嫡长体制。
为了确立“宗子”的领导权威,张载首先对“宗”予以“人来宗己”的绝对地位,即所谓“夫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来宗己,非己宗于人也”。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则把“宗子”提高到与“大君”相仿佛的崇高地位,“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
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②。家族的“宗子”,就应该跟“大君”一样,统属家族内部的尊贵贫贱、茕独鳏寡,“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
作为家族的当然领导者,张载赋予“宗子”主持家族祭祀的权利。“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独宗子之为士,为庶人亦然。”这就是说,宗子是家族中主持祭祀的人。即使宗子身份是士,庶子的地位在大夫以上,家族的祭祀也必须在宗子的家中举行。社会地位的变化,不能改变家族内部宗子的地位。即使宗子连士的身份都没有,只是个庶人或者平民,家族中的祭祀活动依然由宗子主持。
当然,对于三代先秦的宗子制,张载也做了一些变通之法,如对于古代的“支子不祭”,张载认为:“古所谓‘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庙主之而已。支子虽不得祭,至于斋戒致其诚意,则与祭者不异;与则以身执事,不可与则以物助之。但不别立庙,为位行事而已。后世如欲立宗子,当从此义。虽不与祭,情亦可安。”这就是说,支子虽然没有资格主持祭祀,但是他们的态度和情感必须和主持祭祀的宗子一样真诚,那么是可以参与祭祀活动的。只不过支子们只能依附在宗子之后参与祭祀,是绝对不能自己立庙,自己主持祭祀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张载继续论说云:“宗子既庙其祖祢,支子不得别祭,所以严宗庙,合族属,故曰‘庶子不祭祖祢,明其宗也’。”①
在三代先秦时期,祭祀是国家及诸侯事务中的头等大事之一,如果严格按照古代礼制,祭祀活动将是一项非常烦琐沉重的负担,这势必会让一般官宦人家的祭祀活动无法长久坚持下去。更不要说下层的普通民众了。对此,张载又设计出祭祀的变通方法。他说:
今之士大夫,主既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则无义。天子七庙,一日而行则力不给。故礼有一特一祫之说。仲特则祭一,祫则遍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群庙;秋祭曾,冬又祫;来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祢,冬又祫。铺筵设同几,只设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凡人家正厅,似所谓庙也,犹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为祭祀、吉凶、冠婚之事,于此行之。厅后谓之寝,又有适寝,是下室,所居之室也。①
张载认为烦琐的祭祀之礼,可能不是一般民众所能承受,因此设计在普通人居家的正厅,可以当作祭祀祖先的场所,正好如天子所居的大殿一样。这个地方不能住人,专门作为家族内部举行祭祀、占卜吉凶、成人礼、婚礼等重大活动的场所。如此降低家庙的规格和礼数要求,就为家族重建的普遍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前提。
从以上张载对于宋代家族制度的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仿三代先秦诸侯祭祀及其承继的“宗子”法是这个制度的核心内容。而这个新的“宗子”法,在更多的场合是适应于宋代的新兴官僚阶层的,而不适应于一般的贫民家庭与家族。这正如我们上面在引述张载的《宗法》篇中所云:“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宗子法的重建,就可以比较稳妥地维系新兴官僚阶层的长远地位。正因为如此,在宗子的继承方面,张载又设定了官僚身份为先的原则。他举周代周武王非长子而得继的故事云:“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则须是却为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闻有罪,只为武王之圣,顾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绪,故须立武王。……至如人有数子,长者至微贱不立,其间一子仕宦,则更不问长少,须是士人承祭祀。”①
为了确保宗子的地位与权力,不仅家族内部必须予以重点培植,张载同时还建议朝廷也应该以立法等方式,保护宗子的优先地位,特别是在政治仕途上的权力。他说:“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数子,且以适长为大宗,须据所有家计厚给以养宗子。宗子势重,即愿得之。供宗子外乃将所有均给族人。宗子须专立教授,宗子之得失,责在教授。其他族人,别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条,族人须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许族人将已合转官恩泽乞回授宗子,不理选限官,及许将奏荐子弟恩泽与宗子,且要主张门户。宗子不善,则别择其次贤者立之。”②
张载对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先秦时期的“宗法”制进行了变通,但是从整体而言,基本上是把先秦诸侯体制下的宗子法仿制于宋代的官僚体制之上。因而这种以宗子为核心的新的家族制度的建构,并不十分适用于一般的贫民社会。尽管如此,张载关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还是为后世的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兴起,理清了一个可供继续模仿和改进的样式,因此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与张载同时代的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同样也对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建构多有思考与论述。程颢、程颐兄弟同样认为要建构新的家族制度,三代先秦时期的“宗子法”是一种值得效法的形式。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上古时代的“宗子法”败坏,才导致了唐宋以来社会的混乱无序与道德沦丧,“宗子法坏,则人不自知来处,以至流转四方,往往亲未绝,不相识”③。要使纷乱的社会重新走上有序的轨道,就需要恢复上古的“宗子法”,“今无宗子法,故朝廷无世臣。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古者子弟从父兄,今父兄从子弟,子弟为强。由不知本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从根直上一干,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虽远,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处,自然之势也。然又有旁枝达而为干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国,诸侯夺宗云。’”①“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②
上古的宗法制度既然已经败坏,宋代与周代的社会状态已经完全不同,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恢复周代的宗法制度不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是,既然是重建家族,就必须具有家族制度最基本的内容——宗子之法。那么如何重建宗子之法?程颐认为不妨先从若干仕宦大家开始试行:“宗子法坏,……今且试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术要得拘守得须是。且如唐时立庙院,仍不得分割了祖业,使一人主之。”③“宗法须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则人人各知来处。宗子者,谓宗主祭祀也。”④
在一般的情况下,宗子是以嫡长兄为之。宗子具有统率本家族其他成员的权利,特别是负有家族祭祀的权利。对于以宗子为核心的家族祭祀,二程兄弟的设想与张载几乎相同:“古所谓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庙,主之而已。支子虽不得祭,至于斋戒,致其诚意,则与主祭者不异。可与,则以身执事;不可与,则以物助,但不别立庙为位行事而已。后世如欲立宗子,当从此义。虽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废祭,适足长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犹愈于已也。”⑤一个家族的其他儿子即支子,没有主持祭祀的权利,只有宗子有这个权利,因此宗子必须建立家庙,以主持祭祀活动。支子虽然不主持祭祀,但必须诚心诚意地参加斋戒活动,态度必须与主持祭祀的宗子完全一样。如果有条件,最好能够亲身参与;如果不能亲身参与,必须提供物资帮助。但是,支子不能自己立庙主持祭祀。所以,重建家族,再立宗子,必须遵守这个规矩。
二程兄弟对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构建,与张载的设计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以“宗子法”为家族权利核心,家族其他成员依附于宗子之下的一种社会凝聚模式。“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于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于人也。”①而这种“宗子法”,同样比较适用于官僚士大夫家族与家庭,因此,他特别强调说:“士大夫必建家庙。”②
二程兄弟在设计这种家族结构模式的同时,还对家族内部及家庭内部的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进行了思考。程颐对于自己撰写的《六礼》颇为自负,他说:“冠昏丧祭,礼之大者,今人都不以为事。某旧曾修《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将就后,被召遂罢,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间多恋河北旧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渐使知义理,一二年书成,可皆如法。礼从宜,事从俗,有大故害义理者,须当去。”③从现存的文献看,程颐的《六礼》,可能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存留下来的条文相当简略。但是从这些简略的条文中,还是看出二程兄弟对于重建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的重视。如他对父母兄弟之间关系的叙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爱,且如闾阎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于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体重于己之体也。至于犬马亦然。待父母之犬马,必异乎己之犬马也。……或曰:‘事兄尽礼,不得兄之欢心,奈何?’曰:‘但当起敬起孝,尽至诚,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尽友爱之道而已。’”①从这些简略的条文叙述中,已经可以反映出程颐所强调的以孝道为中心的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的基本指向。
对宋代新建家族制度之下的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进行比较详细设计的儒者,是当时的著名士人司马光。他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还编写了《家范》《书仪》两本关于重建家族的著作。《家范》《书仪》的要旨在于协调家族内部及家庭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家族内部各色人等的行为规范,重新建立一种适应于宋代社会的家族伦理和家庭伦理。司马光在这两部著作中所体现出来“家范”“书仪”的主要来源依据,仍然是先秦时期的礼制。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总纂官纪昀等在《家范》的提要中即明确指出这一点:“《家范》十卷,宋司马光撰。……首载《周易·家人》卦辞、及节录《大学》《孝经》《尧典》《诗·思齐篇》语,以为全书之序。其后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杂采史事可为法则者。……朱子尝论《周礼·师氏》云:‘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程颢)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观于是编,犹可见一代伟人修己型家之梗概也。”②我们再来看看司马光在《家范》的开篇序言中所引述的内容:
《周易》:离下巽上。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爱者所以使众也。《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孝经》曰: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昔四岳荐舜于尧,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诗》称文王之德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降及后世,爰自卿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为人法者,今采集以为《家范》。①
司马光在《家范》序言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思维方式,正体现了北宋时期一般儒者对于重建家族制度与家庭伦理的基本理念,即既然要重建家族,就必须有所依傍,而所依傍者的基本来源,只能是古代的宗法体制和上古的所谓“周礼”。虽然说三代先秦时期的这种制度早已成为历史遗迹,但是在司马光等宋儒的采集张扬之下,上古的这些礼制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家族伦理与家庭伦理,依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司马光等所宣扬的“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以及男尊女卑的家族与家庭伦理,就基本上被宋之后的中国社会所承继。司马光在《家范》《书仪》中所体现出来的家族内部伦理和家庭内部伦理,正与张载的家族制度构建框架设计,形成宋代以来新的家族制度的两个基本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谈到北宋时期儒者对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时,我们还不能忽视欧阳修、苏洵等人对于家族谱牒的撰写与推广。重建家族没有家谱是不行的,正如上述张载在《宗法》篇中所指出的“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把修族谱与立宗子法提高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唐宋以前门阀制的谱牒已经废绝,魏晋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对谱牒的垄断必须予以打破,使之适应于宋代社会的一般家族与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士大夫和儒者进行了重新撰写家谱的尝试与实践。宋仁宗皇祐、至和年间(1049~1056)欧阳修编的《欧阳氏族谱》和苏洵编的《苏氏族谱》,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被后世视为宋儒重写新家谱的开端,从此之后,许多士大夫家族,乃至一般的民众家族,也都纷纷以欧阳氏、苏氏族谱为典范,为自己的宗族编修族谱,“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①。欧阳修和苏洵二人,也对自己撰写的族谱相当自负,希望能够由此而推广于天下,使天下所有家族在撰修族谱时有所依据。所谓“是不可使独吾二人为之,将天下举不可无也”①。于是,在欧阳修、苏洵及其他士大夫和儒者的推动下,宋代及其后来就逐渐形成“私谱盛行”的局面。
欧阳修与苏洵对于宋代家族族谱修撰尝试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宋代以前门阀士族谱牒官府编修的性质,改变为私家编修的性质。唐代以前的谱牒,是为了明确诸侯、门阀士族的出身和血统,是世袭制及朝廷提拔官员的依据,也是家族之间联姻的依据。而苏洵、欧阳修等人所创建的宋代族谱,纯粹就是为了维系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它成了凝聚家族以使之长久生存的历史记载与精神力量。虽然亲情联系势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行渐远,但是有了私家族谱的存在,多少有所凭借,有所维系。苏洵在自己撰写的族谱《谱例》中说:
古者诸侯世国,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庙,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独贤士大夫尊祖而贵宗,盖其昭穆存乎其庙,迁毁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与为服,死丧嫁娶相告而不绝,则其势将自至于不忘也。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②
苏洵根据上溯六世祖先的原则,编写了自家的族谱,不由得感慨道:
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见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缌麻,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涂人也。吾之所与相视如涂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
人之身分,而至于涂(途)人,此吾谱之所以作也。①
欧阳修在自己修撰的族谱中也指出,新修的族谱必须“断自可见之世”,从而使得真正的血缘联系“各详其亲,各系其所出”,达到亲疏有伦的目的:
姓氏之出,其来也远,故其上世多亡不见。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如此世久,子孙多则官爵功行载于谱者,不胜其繁。宜以远近亲疏为别,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孙既别自为世,则各详其亲,各系其所出。是详者不繁而略者不遗也。凡诸房子孙,各纪其当纪者,使谱谍互见,亲疏有伦。②
北宋时期张载、二程兄弟、司马光、欧阳修、苏洵等著名儒者关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与建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三代先秦时期的“宗法制”与礼制作为蓝本而推衍出来的带有一定复古性质的模式,但是这些设计毕竟完成了宋代及其后世中国家族制度的基本框架与家族、家庭伦理的价值取向,因而这些设计与实践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而这些设计更侧重于士大夫官僚家族而不适用于一般民众家族的缺陷,就有待于南宋及其后世的不断改进与推行了。
(二)南宋朱熹等理学家对家族制度的改进
北宋时期张载、二程兄弟等儒者对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在当时已经得到了一些实践。但是张载、二程兄弟的这些设计,一方面是比较注重于官僚阶层家族、家庭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又过于依赖三代先秦的宗法制和礼制。因此,这些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族制度在民间社会的普遍推广。于是,到了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人物的理学家们,试图对北宋儒者所建构的家族制度进行改造,使之更加适应于民间社会,特别是通过家规、家礼的制定和践行,转变成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
我们在上面论述张载试图恢复重塑先秦“宗子”制的时候,曾把“宗子”提高到与“大君”相仿的崇高地位,“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①。而对于同样的这一则源自上古的论说,朱熹在其著名的《西铭解》中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说: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则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继承天地,统理人物,则大君而已,故为父母之宗子;辅佐大君、纲纪众事,则大臣而已,故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长吾之长,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贤者才德过于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则凡天下之疲癃残疾、孤独鳏寡,非吾兄弟无告者而何哉!②
朱熹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即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地之子。贤者以及那些可以居高位的士人,只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这种强调表明了朱熹的平民意识。因而他所主张重建的家族,并不是周代的贵族宗法制,而是稍微倾向于平民化的、普通百姓都有权利和能力建立的家族。
从这种平民化的思想出发,朱熹意识到北宋诸儒关于新的家族的设计,存在着某些不切合民间社会实际的弊端,从而影响到新的家族制度的普及。于是,他立志参酌古今、权衡诸儒之说,重新著述,试图建立一种能够适用于民间社会的家族、家庭伦理规范与家族组织。而他的这一理想,集中体现在《家礼》一书之中。
朱熹的《家礼》,据说撰写于南宋乾道五年(1169)。朱熹在自己母亲去世丁忧期间,“居丧尽礼,参酌古今,因成丧、葬、祭礼,又推之于冠、昏,共为一编,命曰《家礼》”①。除《家礼》之外,朱熹在丁忧期间还编写了《祭仪》,在编此书的过程中,将《通典》《会要》中诸家祭礼编为《古今家祭礼》一书,于淳熙元年(1174)印行。朱熹在《家礼》的序言中写道:
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用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①
朱熹在这篇序言中着重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上古的礼制,很多已经不太适用于当前的社会,“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二是近古的一些好礼之士,虽然对上古的礼制进行承继改进,希望推行于当今的社会,但是这些近古之士,在许多方面还是未能切中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也还是不能很好地适用于一般的民众社会,“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用于贫窭者”。基于这样的理念,朱熹对民间家族、家庭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进行了更为详细而又比较切合南宋社会实际的“家礼”改造,撰写了《家礼》一书。
朱熹对于宋代重建新的家族制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祭祖祠堂与祭田的设计。朱熹《家礼》的开篇就是“祠堂”。他写道:
祠堂,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①
“祠堂”一词,可能最早出现于汉代,是建立在坟墓旁祭祀祖先的场所。不过,在祖先坟墓旁边建立庙祠,是王公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的特权,一般的民众则只能在自己家中的厅堂上举行祭祖活动。周礼对天子、诸侯、大夫、士等贵族祠庙祭祖制度有严格的规定,天子可有七庙,侯王可有五庙,大夫可有三庙,士可有一庙,而庶人则不可有庙,只能祭于“寝”,就是家宅中的正屋。到了宋代,除了皇室再也没有什么门阀贵族。皇室有他们专设的太庙中祭祀祖先。一般的官僚即通称的士大夫家族、家庭,则已经没有这种依据门阀体制所相应设立的祭祖“家庙”场所。而一般的民众家族、家庭,也因为科举制度的盛行,都有希望进入到官僚阶层中去。官僚士大夫阶层与一般民众阶层的社会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可能在不断的转换之中。这样一来,家族、家庭的祭祖礼仪,不单单是官僚士大夫阶层的需求,同时也是广大民众的需求,建立新的祭祖礼仪及其场所,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需求。民间社会既然要重建家族制度,必须首先确立祭祀祖先的场所。既然祠庙已经无可考证,朱熹就创造性地将汉代用来墓祭的场所与家居住宅结合在一起,称之为“祠堂”,这样就可以让天下所有的民众,不论官僚士大夫,还是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有了祭祀祖先的正式场所。朱熹关于祠堂的具体设计有如下述:
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正寝谓前堂也。地狭,则以厅事之东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制,不问何向背。但以前为南、后为北,左为东、右为西,后皆放此。
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一卓,大宗及继高祖之小宗,则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继曾祖之小宗,则不敢祭高祖,而虚其西龛一;继祖之小宗,则不敢祭曾祖,而虚其西龛二;继祢之小宗,则不敢祭祖,而虚其西龛三。若大宗世数未满,则亦虚其西龛,如小宗之制。
神主皆藏于椟中,置于卓上,南向。龛外各垂小帘,帘外设香卓于堂中,置香炉香合于其上。两阶之间,又设香卓亦如之。非嫡长子,则不敢祭其父。若与嫡长同居,则死而后其子孙为立祠堂于私室,且随所继世数为龛,俟其出而异居乃备其制。若生而异居,则预于其地立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则因以为祠堂。……旁亲之无后者,以其班祔。伯叔祖父、母,祔于高祖。伯叔父、母,祔于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于祖。子侄祔于父。皆西向。主椟并如正位。侄之父自立祠堂,则迁而从之。①
朱熹的祠堂设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以往儒者的“宗子”主祭的礼仪传统,“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非嫡长子,则不敢祭其父”。但是朱熹关于祠堂设计的最大突破,是允许所有的族人都可以建立祠堂,从而打破了以往“宗子”对于家庙与祭祀的垄断地位。非嫡长子们,得以“预于其地立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则因以为祠堂”,或“死而后其子孙为立祠堂于私室,且随所继世数为龛,俟其出而异居乃备其制”。如此一来,祠堂的建立便成了天下百姓所有子孙的共同权利。南宋以及其后中国民间家族的普遍设置祠堂,就在朱熹《家礼》的倡导之下,得到了切实的施行与推广。
祠堂的设置与祭祀的平民化,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予以支撑的。在三代先秦的“宗法制”下,建立家庙和主持祭祀的“宗子”,得到世袭家国的全力支撑,“宗子”往往就是世袭家国的执掌者。北宋时期张载、二程兄弟等设计的家族“宗子”法,宗子设立家庙和主持家族、家庭的祭祀,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那样,也是得到其家族、家庭包括在经济上的种种条件的优先支持和培植。而朱熹设计的祠堂制度,是试图适用于全社会的一般民众家族与家庭的。社会地位比较崇高和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官僚士大夫家族、家庭,固然可以承担起家族、家庭祭祀的应有负担,但是一般的贫民家族与家庭,就必然面临着建立祠堂和祭祀费用等经济上的困窘局面。再者,所有的官僚士大夫家族、家庭,也无法保障自己家族、家庭的长盛不衰和世泽永续,一旦沦为一般民众,同样也要面临建立、维护祠堂及维系祭祀等所需开支的种种经济负担。
对此,朱熹在设计祠堂的同时,又设计了为祠堂及祭祀提供经济保障的“祭田”以及置备必要的祭祀礼器等。他在《家礼》中写道:
置祭田。初立祠堂,则计见田,每龛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后凡正位、祔者皆放此。宗子主之,以给祭用。上世初未置田,则合墓下子孙之田,计数而割之。皆立约闻官,不得典卖。
具祭器。床、席、倚、卓、盥盆、火炉、酒食之器,随其合用之数,皆具贮于库中而封锁之,不得它用。无库则贮于柜中,不可贮者,列于外门之内。……
或有水火盗贼,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财。易世则改题主而递迁之。改题递迁,礼见《丧礼·大祥》章。大宗之家,始祖亲尽则藏其主于墓所,而大宗犹主其墓田,以奉其墓祭,岁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其第二世以下祖亲尽,及小宗之家高祖亲尽,则迁其主而埋之,其墓田则诸位迭掌,而岁率其子孙一祭之,亦百世不改也。①
在朱熹所设计的“祭田”中,始祖之下的“宗子”依然执掌着大宗的祭祀,故大宗的祭田,由“宗子主之,以给祭用”,而“宗子”之外的子孙们,既然可以各自另立祠堂,那么他们的祭田,也就不属于“宗子”执掌的范围,各归各属,“其墓田则诸位迭掌,而岁率其子孙一祭之”。这实际上使得家族内部的所有成员,都拥有了参与祭祀祖先的权利,“宗子”掌控家族祭祀事务的权利大大弱化。特别是随着世系的延续,从祭祀所亲的人情原则推移,一般族人对于远祖的认知概念逐渐疏远,对于高、曾、祖、祢等近祖的孝思较为强烈,对于高、曾、祖、祢等近祖的祭祀活动自然更为用心。而“宗子”所主持的远祖之祭,反而逐渐成为一种观念上的较为模糊的家族行为,其重要性大大下降。
朱熹对于宋代家族制度之下的礼仪的设计,是多方面的。除了祠堂、祭田之外,还包含了子孙冠礼、婚礼,先人丧礼,祖先祭礼以及家族、家庭内部的居家杂仪规范等等。由于朱熹所涉及的家族、家庭礼仪,比起北宋时期张载、二程兄弟以及司马光等儒者的设计更为切近一般的民众家族与家庭,因此他的《家礼》及相关的家族、家庭礼仪设计,被南宋以及其后的明清时代广泛依循与承继。可以说,就民间社会管理制度与家族、家庭道德伦理的构建,促使儒家文化走向民间社会化而言,朱熹的贡献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儒者,甚至超越了孔子。一直到当今社会,我们依然可以不时地发现朱熹《家礼》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蕴隐的文化因素。
(三)宋代儒者及士大夫对同居共财大家庭的宣扬与实践
宋代儒者们不仅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来设计新的家族制度与家族、家庭伦理规范,而且有不少儒者和士大夫家庭,还身体力行,亲自实践这种新的家族制度,试图以自身的经验,使宋代的家族制度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推行。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到,宋代的许多儒者对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更多的是依仿于三代先秦时期的礼制,特别是周代的礼制。“宗子法”成了大部分宋代儒者最为关键的家族追求与模仿对象。
“宗子法”的核心是在家族内部建立一种祭祀和控制管理家族事务的权威,家族必须在“宗子”的领导下得以延续和发展,家族内部的所有族人,都必须围绕在“宗子”的周围,从而形成一种以“宗子”为主轴,不断向外围扩大的家族体制。而形成这样一种从核心向外围扩大的家族体制,其最理想的实践方式,无过于累世同堂、同爨共食了。这正如司马光在《家范》中所推崇的那样:“国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孙数世二百余口,犹同居共爨。田园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禄,皆聚之一库,计口日给饼饭,婚姻丧葬所费皆有常数,分命子弟掌其事。”①
在宋儒们的倡导、推动和实践之下,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等形式的同爨共食大家庭样板,在宋代得到较多的涌现。这种风气,还对元明清时代的家族制度产生了某些直接的影响。根据今人王善军所搜集到的资料,宋代同居共财的著名大家庭有142家。其累世共居及其家族人口规模情景有如下表。②
根据王善军的研究分析,宋代同居共财大家庭最为集中的地区是陕州湖城县、池州铜陵县、徽州婺源县,分别为一县三家。如果依次计算它们的比例状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陕州共有七县,宋初户数为17443户,平均每县2492户。湖城县的同居共财大家庭比例为万分之十二。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可知,铜陵县的同居共财大家庭比例为万分之五点四,婺源县的同居共财大家庭比例则为万分之三点五。其他地区的比例,自然比这要小得多。而且,这些同居共财大家庭也处在不断产生和不断消亡的过程中,表中所列的数字未必都同时存在,再加上宋初的户口数在宋代应该是较少的时期,所以,以上的推论比例很可能是偏高的。①
就宋代整个民间社会的家族、家庭结构而言,以父母、子女以及祖父母为家庭成员的小家庭结构是普遍现象。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只能是少数的范本。而这种范本,正是宋代儒者重建新的家族制度的理想中的典型。正因为如此,在宋代儒者以及士大夫的大力倡导和宣扬之下,这种累世同居大家庭就特别地突显出来。不仅许多儒者、士大夫热衷于为其树碑立传,广为宣扬,而且政府也在不同的场合予以旌表鼓励。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儒者和士大夫也参与到这种累世同居大家庭的实践中去,这就使得宋代累世同居大家庭的范本更加具有社会影响力。这其中,南宋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家族,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
陆九渊是与朱熹同时代的一位儒学复兴的代表性人物、心学创始人。陆氏兄弟将重建家族的理想付诸实践,使得该家族连绵十世,数代同堂,千人共居,这在宋代是比较罕见的,不仅得到了当时朝廷的多次表彰,而且成为宋代家族制度重建的楷模。《宋史·儒林传》中分别记载了陆九渊兄弟的事迹云:
陆九龄字子寿。……九龄尝继其父志,益修礼学,治家有法。阖门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职,闺门之内严若朝廷,而忠敬乐易,乡人化之,皆逊弟焉。与弟九渊相为师友,和而不同,学者号“二陆”。……
九韶字子美。其学渊粹,隐居山中,昼之言行,夜必书之。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迁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训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①
陆九渊曾经为自己的三位兄弟撰写过墓志铭,也都提到本家族同爨共食的经历。如仲兄陆九叙的墓志云:
公姓陆氏,名九叙,字子仪。抚州金溪人。曾大父演,大父戬,父贺,赠承事郎。母饶氏,赠孺人;继母邓氏,封太孺人。……公气禀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群居族谈,公在其间初若无与,至有疑议,或正色而断之以一言,或谈笑而解之以一说,往往为之涣然。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从事场屋,公独总药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此。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公未尝屑屑于稽检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来,咸得其欢心。不任权诡计数,而人各献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无匮乏。后虽稍有田亩,至今计所收,仅能供数月之粮。食指日众,其仰给药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间,如一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顺出于天性,娣姒皆以为莫及。当穷约时,公之子女,衣服敝败特甚,余氏或时及之,公即正色呵止,必伯叔氏为之处,乃始得衣。虽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虽至窘急,裹囊无不立具。①陆九皋的墓表云:
陆氏徙金溪,年余二百,嗣见九世。公居五世,讳九皋,字子昭。……先君子居约时,门户艰难之事,公所当,每以条理精密,济登平易。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千计,仰药寮以生。伯兄总家务,仲兄治药寮,公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馈补其不足。先君晚岁,用是得与族党宾客,优游觞咏,从容琴弈,裕然无穷匮之忧。当时是,公于妻子裘葛未尝问也。②
综合以上所记述,我们大体可以知道陆九渊家族,从其先祖高、曾之时,就有共居同财的传统。家族中的事务,“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其他兄弟辈,各有所职,共同支撑家族的延续,“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就陆九渊兄弟而言,“伯兄总家务,仲兄治药寮,公授徒家塾”,此外的三个兄弟,则可专心于读书仕进或做学问。家族内的日常生活供给分配,一由家长或主事者主张,没有私心。“合族而食,每轮差子弟掌库三年。”③如主持家族生计主要来源即药业生意的陆九叙,手中掌握的钱财最多,但是“公之子女,衣服敝败特甚,余氏或时及之,公即正色呵止,必伯叔氏为之处,乃始得衣。虽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虽至窘急,裹囊无不立具”。为了加强家族内的团结认同,更好地达到敬宗收族的效果,每天“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
陆九韶撰写有《居家正本制用篇》,对自己家族的实践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在这篇文章中,他反复强调教训家族子弟知书识礼的重要性:“古者民生八岁,入小学,学礼乐射御书数。至十五岁,则各因其材而归之四民。故为农工商贾者,亦得入小学。七年而后就其业。其秀异者,入大学而为士,教之德行。凡小学大学之教,俱不在言语文字。故民皆有实行,而无诈伪。愚谓人之爱子,但当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读须先六经论孟,通晓大义。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节。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党,以交朋友,以接邻里。使不得罪于尊卑上下之际。次读史,以知历代兴衰。究观皇帝王霸,与秦汉以来为国者,规模措置之方。功效逐日可见,惟患不为耳。”“夫事有本末,知愚贤不肖者本,贫富贵贱者末也。得其本,则末随。趋其末,则本末俱废。此理之必然也。今行孝悌,本仁义,则为贤为知。贤知之人,众所尊仰。箪瓢为奉,陋巷为居,己固有以自乐,而人不敢以贫贱而轻之。岂非得其本,而末自随之。夫慕爵位,贪财利,则非贤非知。非贤非知之人,人所鄙贱。虽纡青紫,怀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晓义理。己无以自乐,而人亦莫不鄙贱之。岂非趋其末,而本末俱废乎。”而遵行孝道,更是家族兴盛与永续的根本之道,“至如奉亲最急也。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祭祀最严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方不是因贫乏而废礼义。凡事皆然。则人固不我责。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则礼不废而财不匮矣”。“一家之事。贵于安宁和睦悠久也,其道在于孝悌谦逊。”①
响着后世。因此,清代陈宏谋在编撰《训俗遗规》收录陆九韶的《居家正本制用篇》时,在按语中说:“门内之地,至性所关。虽极愚顽之人,岂无天良之动。而有时视门内如路人,非礼犯分之事,悍然不顾者,名利之心夺之耳。于名利上看得重一分,即于天伦轻一分矣。梭山先生论居家而先之以正本。其言正本也,以孝弟忠信,读书明理为要,而以时俗名利之积习为戒,其警世也良切。至于制用之道,不过费以耗财,亦不因贫而废礼。随时撙节,称家有无,尤理之不可易也,陆氏十世同居,家法严肃,高风笃行,可仰可师。读此,亦足以知其所由来矣。”①显然,以理学著称的江西抚州金溪陆氏家族,很好地实践了宋代儒者所设计的新的家族制度的理想范本。
(四)宋代之后家族制度的变迁及对宋儒设计的若干修正
宋代儒者们对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与实践,已经基本构建起来并且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的中国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整体框架。然而,宋儒们所设计与实践的新的家族制度所存在的两大特征,即“宗子法”和同居共财大家庭体制,其社会适用性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宋儒们设计的“宗子法”,主要在于确保“宗子”在家族内部的领导地位,希望通过“宗子”权威的设立,使家族的其他成员,团结或是被约束在以“宗子”为核心的家族组织之内。因此,“宗子”不仅掌握着家族的祖先祭祀权利,而且还拥有占有或使用家族各种资源的某些特别权利。但是,这种设计忽视了两种社会变迁的必然因素。其一,宋代已经进入以官僚士大夫与一般民众社会地位时有轮换的士人平民时代,不复存在先秦时期诸侯、世家得以继承的“世爵”“世禄”体制,“宗子”的社会地位势必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迁,时在变动之中。一旦“宗子”沦为一般的贫民身份,他们就很难支撑起领导家族的尊崇地位。而一位身份低微的“宗子”,显然不是家族其他成员所期待的,整个家族的社会与政治地位必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其二,一个家族的人丁如果不甚兴旺,数代繁衍下来,族人寥寥可数,则作为先祖嫡系的“宗子”,似乎还可以承负起率领阖族族人归宗祭祀以及从事家族其他活动的重担。但是如果这个家族经过数代繁衍之后,子而孙,孙而曾孙,族人的数量不断扩展,兄弟的分支也越来越多,那么,原先的“宗子”对领导家族的祭祀以及从事其他家族活动的控制能力也就日益下降。而随着家族繁衍代数的增加,这种控制能力就愈加下降。从被“宗子”所领导的其他族众的立场思考,既然“宗子”对于家族的事务越来越力不从心,“宗子”对于族人的利害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淡薄,“宗子”也就逐渐地变成可有可无的角色。于是,随着时间与世代的推移,家族内的血缘近亲之间的关系,逐渐跨越了“宗子”的地位,成为各个家族成员之间最不可或缺的联系。“宗子”日益转化为一种象征性的家族符号,而不是原先实质性的家族内部的领导人物以及对外发生联系的标志性人物。
在这种情形之下,宋代以来中国的家族制度及其组织,不能不对宋儒们所设计的“宗子法”进行某些方面的变通与修正,使之更加切近宋代以来的臣民社会,特别是切近大部分的平民社会。清代康熙年间的大学士李光地,号称“理学名臣”,对于宋儒们的学问多有论述,特别是对于朱子学,更是情有独钟,论著甚多。我们从李光地的论著中,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明清时期士大夫及一般民众家族对于宋儒们宣扬的“宗子”法的变通与修正。
李光地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古代以及宋儒们的一些关于家族制度的主张,并不一定适用于当前的社会,“有古所无,而今时势不同者,须想得到,不然后人亦难行”①。即使对于朱熹《家礼》中的规范,李光地也认为必须有所改变,否则很难施行,“《家礼》要存古法,故段段有宗子行礼,到底人不能行,如今须考定,令眼前可行方好”②。因此,李光地主张家族祭祀等事务,不可拘泥于“宗子”主祭而“支子”不祭的传统,应该予以变通。他在《家庙祭享礼略》中如此写道:
古礼之坏久矣,其渐有因,其本有根,虽有贤人君子讨论而服行之,然所谓不尊不信则久而莫之从也固宜,况乎复古之难,而变今之不易,则凡所讨论,而仅存者亦多贤人君子区区饩羊之意。自其身不能尽行,而望人之从而行之,尤不可得也。
礼莫重于祭,而大宗、小宗之法不讲者且数千年。夫无大宗小宗之法,则源远末离无所统摄。分不定而情不属,虽有仪节之详,将安用之?是以乡异俗、家异法,有身列荐绅士类而迷妄苟简至于犯分悖本而不自知。呜呼!其随俗而安之乎?抑区区讲论,行其宜于今者,而不甚远于圣人之意,庶几存古道之什一于千百也!
岁乙巳,家庙始成,先君子将率族人修岁事焉,于是讲其礼。曰此古所谓大宗者也,当有明时族中先辈长者,尝考古而立宗子矣,然而有数难者。古者无禄则不祭,故庶人荐而已,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其时卿大夫家非世官、则世禄,皆朝廷赐也,而宗子主之,故得以其禄祭。今皆无之,则宗子无禄也,奈何犹备大夫士之礼以祭?父为大夫、子为士,其祭犹不敢以大夫,况庶人乎?难者一也。古者宗子为朝廷所立,故其人为一家之宗,而必口于礼法。今则有樵采负贩使之拜俯兴伏,茫然不省知者矣,而奈何备盛礼以将之?难者二也。凡为宗子者,以其为族人之所尊重,冠昏丧祭必主焉,故祖宗之神于焉凭依。今则轻而贱之者已素,一旦被以衣冠,对越祖宗,人情不属,而鬼神不附。难者三也。是故世变风移,礼以义起。今人家子孙贵者不定,其为宗支也,则不得拘支子不祭之文,而惟断以无禄不祭之法。且近世褒赠祖先,固不择宗支授之,褒赠之所加则祭祀之所及,揆以王法、人情,无可疑者。①
李光地在这里指出了仿行先世“宗子”法的三大难处:第一,古代的“宗子”,“卿大夫家非世官、则世禄,皆朝廷赐也,而宗子主之,故得以其禄祭。今皆无之,则宗子无禄也”。没有世禄支撑的“宗子”,显然无法承担领导家族的重任。第二,古代的“宗子”,“为朝廷所立”,地位崇高,足以表率家族;而如今许多家族的所谓“宗子”,多不知礼数,“则有樵采负贩使之拜俯兴伏,茫然不省知者矣”。家族祭祀有失尊严隆重。第三,贫寒的“宗子”主持家族的祭祀及其他事务,不仅族人不服,鬼神亦不服,完全失去了祭祀的目的。为今之计,只有“世变风移”,“今人家子孙贵者不定,其为宗支也,则不得拘支子不祭之文”。家族的祭祀等大事,不能拘泥于“宗子”主祭、“支子”不祭的古代礼制,应该选择适合这种尊严而又重要任务的其他族人来承担。
“宗子”既不可拘泥于大宗嫡子,那么从整体而言,李光地认为,只要是血亲的族人,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其他族人同样可以担任,“周制有大宗之礼,乃有立适之义。今大宗之礼废,无立适之法,而子各得以为后,则长子、少子当为不异”①。古代规定大宗才能立庙,而今则其他族人只要传继数代,同样可以立庙。“所谓庙者,大宗乎、小宗乎?如大宗也,则惟伊川生存,乃得主祭,若其子孙为无禄人,则亦不得世其祭矣。以理揆之,必也其小宗也。盖四亲之庙,自己立之,则子孙尤可以世其祭以终于已。此亦所谓古未之有,而可以义起者也。故于今而斟酌二贤(程伊川、朱晦庵)之意,则始祖之庙如愚前所云者,盖庶几焉。……则其庙固始祖有也,有之则不可废,故其子孙得更迭以其禄祭无所嫌也。若四亲则亲尽迭祧,而庙非一人之庙,高祖之祭及其元孙以下则废之矣,故祭不常,则庙亦不常,必使法应立庙者立焉,而使其子孙犹得以主其祭,迄于己之祧。而止如伊川之说,固亦变中之正也,犹以为疑,则亦参以愚大宗之说。立庙者主祭,而仍设小宗宗子之位,奠献祝告同之,其亦可矣。若乃五世之中无应立庙之人,而其势不可聚,则各备士庶之礼以奉其四亲,而亦当于高曾祖之忌日,各就其宗子之家而先展拜焉。庶几古人之意未尽湮没。”②
李光地不仅主张大宗之下的近祖可以立庙,而且因为大宗所奉之始祖,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子孙不免感到有些疏远,而对于高、曾、祖、祢的近祖,时代相近,血缘关系更为亲密,因此李光地认为,祭祀祖先的重点,还是要以近祖为主。祭祀近祖的礼仪,也不必拘泥于春秋二祭,而是应该入乡随俗,参照土风民情,时时缅怀拜祭。他在《小宗家祭礼略》中云:古者宗法之行,宗子祭其亲,庙自天子而下降杀以两。……伊川程氏祭礼欲令上下通得祭,其高、曾、祖、祢为四亲庙。……然祭四亲者,亦止于宗子而已,五服以内之支庶,则固有事于宗子之家,非家立庙而人为祭也。然古者无田则不祭,祭用生者之禄,是祭祀必大夫士而后具明矣。古所谓宗子者,皆世官、世禄者也。今贵达者未必宗子,而宗子或夷于氓隶。宗子之分与禄既不足以配其四亲,而支子有爵俸者反绌于不祭之文,而不得伸其追远之爱。如此则程、朱之礼又穷。故曰三王殊世,不相袭礼。今之礼僣乱极矣……吾家大宗之礼又当别论。以四亲言之,我于先人为宗子,而祖以上则非揆之于法得奉祢祀而已。然小宗之法今世亦不行,吾家旧所通行又皆不论宗支,轮年直祀。……今所奉祀并立四亲,幸今聚族祖里伯叔,每岁直祀高曾祖者,吾咸与焉然。退而修四时之事,亦必并设高曾祖考之位而申祝献焉,非僭且渎,实则准以情分而有所不容已也。
吾家大宗时祭,旧止春秋。其奉祀祖考者,则否止于清明、七月等俗祭而已。吾思古人合诸天道,春禘秋尝,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盖春秋之义大矣。惕恻怆之心,自近者始。不当于远祖独行之也。若欲以清明、七月俗节当之,则清明为春暮,七月为秋始,迎来太迟,送往太骤,亦失礼经之意。今欲定于二分之月别卜日为春秋祭,而清明、七月则循俗荐馔焚楮如《家礼》俗节之祭而已。况《家礼》尚有四时之祭,皆用仲月。今春秋而外,有冬节荐鲜,可当冬夏二祭,其礼稍杀于春秋可也。又记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故祭为吉礼,而忌则丧之。余也今俗,废春秋吉祭而反于忌日饮酒食肉,谓之受胙,吉凶溷杂,非人情,殆不可用。今逢忌日,亦当稽朱子《家礼》及语类所载,变冠服、不饮酒食肉,终日不宴亲宾,志有所至,乃近于正生。忌则不然,礼稍杀而情稍舒可也。墓祭原起于奠后土之神,为祖考托体于此,岁祭焉,所以报也。今祭墓者丰于所亲,于土神辄如食其臧获而已,简嫚之极,必干神怒。故今定墓祭牲馔,祖考与土神同奠献,则依《家礼》先祖考而后土神,自内而外,非尊卑之等也。此数者,皆大节目,苟失礼意,不可不正。其余如元旦、五月节、中秋、重阳节,此等皆可不拘丰俭、循俗行之所谓,事死如事生,节序变迁,皆寓不忍忘亲之意。①
李光地在这里认为,不论是古代礼制还是宋儒程颐、朱熹等所提倡的家族祭祀之礼,都不能较好地适应清代的社会现实。“宗子”之制到了清代,“贵达者未必宗子,而宗子或夷于氓隶。宗子之分与禄既不足以配其四亲,而支子有爵俸者反绌于不祭之文,而不得伸其追远之爱”。因此,民间乃至李光地自己的家族,在祭祀祖先方面,都已经是“不论宗支,轮年直祀”。李光地本人也积极参与到这种变通的祭祀祖先仪式中,“今所奉祀并立(高、曾、祖、祢)四亲,幸今聚族祖里伯叔,每岁直祀高曾祖者,吾咸与焉然。退而修四时之事,亦必并设高曾祖考之位而申祝献焉,非僭且渎,实则准以情分而有所不容已也”。对于当时民间社会所盛行的“不论宗支,轮年直祀”的祭祀形式,李光地还在其他的论述中予以肯定:“直祭,非古礼也。然欲均劳逸,且使祖考诸子孙妇皆知蘩之义,而皆于宗子之家行之,亦未为失。”②
当然,李光地所主张的不论大宗、小宗,只要是四世之上均可立庙(祠堂);大宗、小宗都可以设“宗子”;祠堂祭祀的主祭人可以是“宗子”,也可以不是“宗子”,但存在着明显的倾向性,即家族的管理事务,应该偏重于选择家族中具有一定政治、社会地位的族人来承担。如在支子设置祠堂方面,如果各分支中有功名的族人存在,那么就可以优先设置祠堂。他说:
小宗如及身贵,便应立四亲庙,子孙以世代而祧,下至本身元孙,都该用贵者之宗子、宗孙主祭。盖五世之泽未斩也。如五世内支子有贵者,亦不得于此祠中主祭,当自别立四亲庙可也。大宗不容有二,小宗不妨其多。①
小宗立庙“不妨其多”,这就基本扫清了支子各自设置近亲祠堂的礼制障碍。明清以来中国家族内部普遍设立祠堂的现象,与这种观念的转变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家族祭祀方面,李光地更是主张必须由有政治、社会地位的族人来担任主祭人,没有功名的“宗子”,只能是作为“陪祭”参与。他在《治道》中说:
宗法是大事,大宗固宜复,然其子孙贵者不必宗子,宗子不必贵,祭用贵者之禄,岂反使宗子之贱加其上?万一宗子竟是农夫,如之何其加于朝官也?只得贵者主祭,宗子及直祭同祭。主祭者居中,宗子居左,直祭居右,长一辈者稍前,同班者齐排,卑幼者稍后。祝文竟写主祭孙某、宗孙某,直祭孙某。至小宗亦宜仿此意。如某于法得立高、曾、祖考之庙,然某即非高祖之宗子也,某为主祭孙,而宗孙即用高祖之长房、长孙为之。直祭者每年换人,至五世而祧,则用曾孙之长房长孙为宗孙,以次而下。倘有德有爵不可祧者,则仿古礼祖功宗德之意,将此主移向始祖之庙,合族公祭。不然贵者之子孙倘竟降为皂隶,又安可以祖之爵而隆祭之礼?与所
谓葬以大夫祭以士者大不侔矣。祭以本身之爵非以祖考之爵也。①
李光地在《家礼要存》中谈及自己家族的祭祀仪式时说:
宗子行礼,到底人不能行。如今须考定,令眼前可行方好。卿大夫家古有世禄,故子孙虽无位,行事尚得与大夫同。今卿大夫既无世禄,设数传之后,支子显达,而宗子却无禄,则宗子分止宜荐,而支子又不得祭,是使有禄者身享鼎烹,而祖宗仅受菲薄,于心安乎?寒家宗祠在山中,先世士大夫多居郡,祭时不躬不亲,惟使直祭者经理其事,故时序岁腊潦草献享而已。及先君定议,以为宗子有禄,自当主祭。即宗子举人,而支子进士;宗子侍郎,而庶子尚书。爵秩相彷,亦仍当宗子主祭。若宗子无禄,而庶子显贵,则贵者以其禄主祭,居中;宗子居左,直祭者居右,一同奠献。如此斟酌,既不背古意,而于今可行,方不为空言。②
雍正三年(乙巳1725)李氏家族祠堂修葺一新,举行隆重祭祀活动,李光地描述此次祭祀的仪式云:
乙巳元日,聚族于斯……循之宗子法废,爱羊存朔,直年均劳,奠献以爵,三人居中,跪闻嘏祝。为此礼者,非曰贵贵。载稽古义,无禄不祭。左宗、右直,以昭穆位。余家主祭一人,有爵者中立,左宗子、右直年。盖有爵则得以其禄祭,宗子以存古,直年以均劳也。其序立则以昭穆尊卑为前。却若宗子贵,而又直年,则主祭,只用一位。大宗之祭,长至春元始祖、先祖,论取伊川,尚有春秋,沿旧以禋。有明时,宗中先达率于大宗祠祭春秋。先君增以长至元旦,实与伊川论合。然春秋如旧,有其举之未敢废也。此外小宗,各遵其格法得立庙。自厚于昵五世则迁,自统于嫡。今达官封赠及高曾,则法得立四亲之庙,然五世之中须以达者之宗子、宗孙主祭,虽旁支又有贵显,自复立庙为宗,则可不得于小宗庙主祭。盖先者之泽未斩也。①
从以上所引述的清代李光地关于家族“宗子”、祠堂设置及祭祀礼仪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对古代的礼制多有更革,即使是对宋儒程颐、朱熹等人的家族制度设计,也有许多变通之处。而这种更革、变通,正体现了明清时期中国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一般情景。李光地位居高官,精通理学礼制,因此,他自己家族的礼制实践以及他的诸多论述,可能还比较保守一些,对于先人的礼制,尚不至于过多的离经叛道。至于一般民间社会的家族、家庭,“宗子”的概念已经相当淡薄。繁衍至十世以上的家族,“宗子”及先祖、始祖之祭,大多流于形式,无足轻重。近祖之亲,建造祠堂与否主要是视子孙的经济条件而定,不复以贵者为标准。家庭的析居分爨,也基本实行平均分配制度,家族祭祀,由于族田、祭田的设立,也大都采用轮值的办法。这一系列家族制度组织及其礼仪的变迁,正反映了宋代以来社会士人、平民化的整体趋势,先秦时期以世家门阀为基础的“宗法”礼制,必然要转型适应明清时期社会变迁的整体需求。这也正是宋儒们所设计的新的家族制度到了明清时期不断被修正的根本原因。
宋儒们作为新的家族制度组织样板的累世同堂、同爨共食的大家庭形式,同样也是不太符合宋以后中国民间社会的实际情况的。许多研究者把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和累世同居共财、同爨合食的大家庭组织,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家族制度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其实,这是不确切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和道理学家们大力提倡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制度,实际上是有违人性,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违背的。这种大家庭组织几乎都是由某个权威家长(主要是官宦)的惨淡经营、硬撑门面才得到勉强维持的。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时间的推移,大家庭内部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以后辈夫妻形成的小圈子,相互嫉恨,计长论短,争一己之利,与大家庭组织发生频繁的冲突。再者,在同居共财大家庭中,由于森严的等级和烦琐的礼节,成员之间的思想和感情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交流,而只能用一个“忍”字代替。唐朝张公艺九世同居,唐高宗问他何以至此,他大书百余“忍”字以对。无独有偶,宋代“潞州有一农夫,五世同居。太宗讨并州,过其舍,召其长讯之曰:‘若何道而至此邪?’其长对曰:‘臣无他,惟能忍耳!’”。所以宋人常说:“居家久和者,本于能忍。”但怎样一个忍法,其中也是大有学问的。因而,家庭成员之间不但要忍,而且要讲求“处忍之道”。这个“处忍之道”,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是这样描述的:“盖忍成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发,不过一再而已。积之既多,其发也,如洪流之决,不可遇矣。不若随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尔!’曰:‘此其无知尔!’曰:‘此其失误尔!’曰:‘此其所见者小尔!’曰:‘此其利害宁几何!’不使之入于吾心,虽日犯我者十数,亦不至形于言而见于色。然后,见忍之功效为甚大,此所谓善处忍者。”①这种有违人性的隐忍之道,当然不是大多数人所能实践的。因此,这种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最终没有不土崩瓦解、裂变为许多个小家庭的。可以说,这种理想化、模式化的大家庭制度,只能是个别的、临时性的,而不可能是常规的、永久性的。
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之所以是个别的、临时性的,是因为这种大家庭制度严重地束缚了家庭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抑制了私有欲望的生长。一般来说,由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家庭成员都有着共同发家的愿望,因此能够发挥比较充分的生产积极性。一旦儿女辈婚嫁成家,并且生出孙辈,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家庭成员最为关心的,不是这个由数对夫妻组成的大家庭的利益,而是以每对新夫妻及其子女所组成的小家庭的利益。但是在共同生产、集体分配的家庭体制下,每个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小家庭之间,难免会由于劳动、分配、福利以及性格、意气诸方面的差异,产生种种矛盾。随着大家庭内辈分的增加和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小家庭的日益增多,其内部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亦日益激化。但是以聚族而居为形式的家族制度,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这种内部矛盾的发生。就整个家族而言,由众多族人家庭组成的强大的家族势力,可以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从而有效地庇护各个小家庭的安定发展。而就各个小家庭而言,虽然家族组织拥有一定数量的公有财产,但同时也允许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小家庭经济的独自发展。与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制度相比,家族制度下的小家庭有着较多的经营独立性,族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从而为家族内部每一个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小家庭所乐意接受。这是中国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之所以能够永久性存在并且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事实上,自宋代以来,如前面所引述的唐代张公艺和宋代袁采等,许多家族甚至士大夫阶层对于同居共财大家庭的弊端是相当清楚的。一些家族为了防止和杜绝这种内部矛盾的发生,在族规中正式规定族人应及时分家,不得硬撑门面而导致兄弟反目、叔侄不和。如安溪谢氏家族就在《族训》中指出:“示后世子孙有财产当分者,即便请族长立阄书均分给予,不可姑息迟延岁月,一旦无常,不免后患,破家荡产皆此然也。”①又如福州某一陈氏官僚在给子孙的分家文书中写道:“盖闻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余岂以多财遗子孙哉!……与其合之任听虚糜,曷若分之俾知撙节,爰将原承祖遗及余续置产业,除提充公业外,为尔曹匀配阄分。”②
我接触过不少民间家庭的分家析产文书,其中的一些文字也十分值得玩味。如清代乾隆二十三年(1758)泉州张氏家族的分家阄书写道:“仝立阄书,长房方高、二房方升、三房方远长男源、四房方大。父在台时,舌耕粒积,置有泉、台各业。及父司漳铎,唤高兄弟等面命曰:吾没后,尔兄弟分爨……兹孙曾浩繁,而方远不年,诚恐日久未能恪守前规,不得不为善后之计,公议分爨。虽律以九世同居,仅及其半,而较诸世俗浇习,已迥不同。因遵父母遗命,将泉、台产业……焚香敬告祖父之前,公同拈阄,按股登载。……各执阄书一纸、应分细册一本,以垂永久。自今以往,惟愿孙曾追念祖父辛苦,勿弃前基,水木情敦,勿践行苇,则虽分犹合,先人含笑,永昌厥后矣。”③道光三年(1823)漳州府龙溪县林氏家庭的分家阄书记云:“同亲立阄书人兄弟林泉、林果、林辉、胞侄陵南等,窃谓九世同居,此风足效,但家事浩繁,人心不一,难以合理敬遵。母亲之命聊为分爨之计,邀请家长房亲,各将承祖父产业物项会同……凭母亲家长拈阄为定。”①咸丰四年(1854),泉州晋江县何氏家庭的分家文书云:“古者九世同居惟有张公,彼幸一堂聚首,故历世远无异言。今晋江县十五都福全乡何家廷弼、廷奏,系胞兄弟;堂兄廷福,各居一方,安保后日子侄之无异言乎?……各份俱以阄书为证。日后各房丁财贵三多具庆,不得造言生事。今欲有凭,仝立阄书壹样叁纸,各执为照。”②台湾新竹地区的一份分家文书云:“立分阄字人兆清、其旺、其盛兄弟等,窃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者情关手足,宜深聚首之思,谊属孔怀协奏埙箎之雅,岂可别房分门,致叹雁行之折翼?然而夷齐之高风已渺,虽伯仲之笃谊难期。……一旦而思远适况瘁,其何以堪?不得已兄弟相商,请得房族到场,将父遗下水田银项作三股均分,对祖拈阄永远,子孙人等不得争长较短,异言反悔。今欲有凭,特立分阄字式纸各执为照。”③
这些分家文书都体现了一个理想与现实相互矛盾的问题,即对于孝悌观念所提倡的累世共居,心存仰慕,但是在现实社会里,不分家势必引发家族内部的诸多矛盾,“恐有阋墙之患”④。所谓“窃谓九世同居,此风足效,但家事浩繁,人心不一,难以合理敬遵”。“古者九世同居惟有张公,彼幸一堂聚首,故历世远无异言。今晋江县十五都福全乡何家廷弼、廷奏,系胞兄弟;堂兄廷福,各居一方,安保后日子侄之无异言乎?”
以上这些言论和族规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宣告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制度是行不通的。因此,从家族和家庭的发展趋势看,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制度必然为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所融化。我们不能否认,在孝悌等传统观念以及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下,每一个家族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偶尔有一些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出现,但不论是三世同居,四世同居,甚至五世以上同居,最终都不能不裂变为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小家庭,为家族所消化。这种非理性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只是家族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小插曲而已,并不具有制度上的普及性。
人们一致认为,中国这种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制度比较盛行于宋代。两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动荡不定日益加剧,阶级关系日趋复杂与多样化,于是,坚持义理的儒者与士大夫们力图把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局限在大家庭制度之中,使它成为一种既顺应社会变化,又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理想化的家庭模式。我们从历代正史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经过朝廷旌表的这种模式化的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唐代有18家,五代有两家,宋代多达50家,元代近20家,明代亦有20余家①。从宋代到明清时期,这种经过朝廷旌表的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的递减趋势是很明显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受到朝廷旌表的20余家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中,明初至正德年间(1506~1521)竟然多达22家,而嘉靖至明亡,仅有数家而已。②众所周知,明代中期以后,即明代嘉靖、万历之后,是中国家族制度及其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家族祠堂的普遍设置,祭田、族田的日益累积,族谱家乘的修撰与流行,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兴盛起来的。③明代中后期由朝廷旌表的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的锐减,正体现了由众多族人家庭聚族而居为形式的家族制度,在明代中后期得到迅猛的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由朝廷旌表的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的锐减,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因此到了清代,根据《清史稿》的记载,由朝廷旌表的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仅有聊聊五家。①并且,明清时期受朝廷旌表的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也已经很少有如唐宋时期那种诸如张公艺、陆九渊、袁采等以名臣、名儒为核心的典范,而大多是以中下层的民众偶然所形成。
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家族制度及其组织形成的较为正常的途径应当是这样的:当某一个迁居始祖带领妻子儿女在某一个地点定居下来之后,垦荒耕耘,取娶婚嫁,繁衍后代。儿子们长大成人后,便开始分家,儿子辈另成单独家庭,成为长房、二房、三房及更多房。孙儿辈成长婚嫁后,家庭再次分析。家庭分析的最佳时间是在二世同堂和三世同堂之间,三世同堂以上尚未分析即属非正常情况。如此世世相衍,代代分析,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个体小家庭日益增多,原先由某一迁居始祖开创的家庭,便逐渐扩展为家族。在经济社会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族人开始建造祠堂,设置祭田、族田,修撰族谱家乘,敬宗收族,繁衍世系。随着人口的繁殖、家庭的不断分析以及家族规模的不断扩大,家族内部的分支、分房也不断增多,如果不遭受天灾人祸等外部因素的干扰,由某一个迁居始祖开创的家庭,就这样不断地演变成雄踞一方的巨姓大族,或者分析为若干个有着某种相互联系的新的家族。
宋儒们所倡导和实践民间家族制度,无论是宗子制的建立、祠堂祭祀等礼仪的规范,还是累世同居大家庭,等等,更多的是仿袭三代先秦的礼制所形成的。宋儒们虽然极力企望仿袭古代的礼制来重建宋代新的家族制度,但是时代的不同,使得宋儒们的许多设计与日益变迁的社会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他们的有些设计,就不得不在后世的实践中予以不同程度地变更和修正。因此,我们在看到宋儒们为重建宋代以来新的家族制度所做出的贡献及其深远影响的同时,对于中国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这一系列变迁,也是不可不认真予以探究的。
近一个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宋明以来中国民间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形成,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明以来的家族制度,是先秦时期奴隶制与宗法制(或村社制)的残余;二是认为宋明以来的家族制度,基本上是由宋代士人与理学家们重新建构起来的。我们通过对宋儒们所倡导和实践的民间家族制度的过程分析,可以看到以上的两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都是值得重新思考的。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对于宋明以来民间家族制度及其组织所产生的长远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一种文化以至文明的传承,绝不是什么必然消亡的“残余”。而宋儒们对民间家族的重新设计与建构,却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复古性质的承继过程,并非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正是这种具有复古性质的承继过程,又使得宋儒们的最初设计,并不十分适用于宋明以来的民间社会实际。于是,经过其后儒者、士人以至民间的不断改进调试,到了明代中后期,中国民间的家族制度,才最终基本定型并且沿袭了下来。当然,随着近现代特别是当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这种家族制度还将有所变化、有所演进,这是一种必然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是中华文化以至文明的传承趋势,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一)北宋时期儒者的代表性家族设计
北宋时期儒者对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最著名的莫过于理学家张载和二程兄弟。张载在其著作《正蒙》和《经学理窟》中都对重建新的家族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设计理念。特别是在《经学理窟·宗法》中,比较集中地提出了重建宋代家族制度的基本构想。《宗法》篇略云: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夫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来宗己,非己宗于人也。所以继祢则谓之继祢之宗;继祖则谓之继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独宗子之为士,为庶人亦然。……后来朝廷有制,曾任两府则宅舍不许分,意欲后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尝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则此亦不济事。……其所以旌别之意甚善,然亦处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绝嗣。不若各就坟冢给与田五七顷,与一闲名目,使之世守其禄,不惟可以为天下忠义之劝,亦是为忠义者实受其报。……
王制言“大夫之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若诸侯则以有国,指始封之君为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宗子既庙其祖祢,支子不得别祭,所以严宗庙,合族属。故曰“庶子不祭祖祢,明其宗也”。①
张载在这一关于家族重建的构想中,除了论述重建家族制度对于“国”与“家”的重要性之外,已经基本触及宋代以来中国家族的三大要素,即家庙(祠堂)、谱牒、祭祀与祭田等。对于谱牒,张载语焉不详,但是对于家庙与祭祀,则有着比较严格的规定。而这种比较严格的规定,显然是从先秦时期的“宗法”制中仿制下来的。尤其是对于新建家族中的领导者——宗子,基本上是模仿先秦时期诸侯继承的嫡长体制。
为了确立“宗子”的领导权威,张载首先对“宗”予以“人来宗己”的绝对地位,即所谓“夫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来宗己,非己宗于人也”。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则把“宗子”提高到与“大君”相仿佛的崇高地位,“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
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②。家族的“宗子”,就应该跟“大君”一样,统属家族内部的尊贵贫贱、茕独鳏寡,“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
作为家族的当然领导者,张载赋予“宗子”主持家族祭祀的权利。“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独宗子之为士,为庶人亦然。”这就是说,宗子是家族中主持祭祀的人。即使宗子身份是士,庶子的地位在大夫以上,家族的祭祀也必须在宗子的家中举行。社会地位的变化,不能改变家族内部宗子的地位。即使宗子连士的身份都没有,只是个庶人或者平民,家族中的祭祀活动依然由宗子主持。
当然,对于三代先秦的宗子制,张载也做了一些变通之法,如对于古代的“支子不祭”,张载认为:“古所谓‘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庙主之而已。支子虽不得祭,至于斋戒致其诚意,则与祭者不异;与则以身执事,不可与则以物助之。但不别立庙,为位行事而已。后世如欲立宗子,当从此义。虽不与祭,情亦可安。”这就是说,支子虽然没有资格主持祭祀,但是他们的态度和情感必须和主持祭祀的宗子一样真诚,那么是可以参与祭祀活动的。只不过支子们只能依附在宗子之后参与祭祀,是绝对不能自己立庙,自己主持祭祀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张载继续论说云:“宗子既庙其祖祢,支子不得别祭,所以严宗庙,合族属,故曰‘庶子不祭祖祢,明其宗也’。”①
在三代先秦时期,祭祀是国家及诸侯事务中的头等大事之一,如果严格按照古代礼制,祭祀活动将是一项非常烦琐沉重的负担,这势必会让一般官宦人家的祭祀活动无法长久坚持下去。更不要说下层的普通民众了。对此,张载又设计出祭祀的变通方法。他说:
今之士大夫,主既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则无义。天子七庙,一日而行则力不给。故礼有一特一祫之说。仲特则祭一,祫则遍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群庙;秋祭曾,冬又祫;来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祢,冬又祫。铺筵设同几,只设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凡人家正厅,似所谓庙也,犹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为祭祀、吉凶、冠婚之事,于此行之。厅后谓之寝,又有适寝,是下室,所居之室也。①
张载认为烦琐的祭祀之礼,可能不是一般民众所能承受,因此设计在普通人居家的正厅,可以当作祭祀祖先的场所,正好如天子所居的大殿一样。这个地方不能住人,专门作为家族内部举行祭祀、占卜吉凶、成人礼、婚礼等重大活动的场所。如此降低家庙的规格和礼数要求,就为家族重建的普遍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前提。
从以上张载对于宋代家族制度的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仿三代先秦诸侯祭祀及其承继的“宗子”法是这个制度的核心内容。而这个新的“宗子”法,在更多的场合是适应于宋代的新兴官僚阶层的,而不适应于一般的贫民家庭与家族。这正如我们上面在引述张载的《宗法》篇中所云:“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宗子法的重建,就可以比较稳妥地维系新兴官僚阶层的长远地位。正因为如此,在宗子的继承方面,张载又设定了官僚身份为先的原则。他举周代周武王非长子而得继的故事云:“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则须是却为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闻有罪,只为武王之圣,顾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绪,故须立武王。……至如人有数子,长者至微贱不立,其间一子仕宦,则更不问长少,须是士人承祭祀。”①
为了确保宗子的地位与权力,不仅家族内部必须予以重点培植,张载同时还建议朝廷也应该以立法等方式,保护宗子的优先地位,特别是在政治仕途上的权力。他说:“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数子,且以适长为大宗,须据所有家计厚给以养宗子。宗子势重,即愿得之。供宗子外乃将所有均给族人。宗子须专立教授,宗子之得失,责在教授。其他族人,别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条,族人须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许族人将已合转官恩泽乞回授宗子,不理选限官,及许将奏荐子弟恩泽与宗子,且要主张门户。宗子不善,则别择其次贤者立之。”②
张载对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先秦时期的“宗法”制进行了变通,但是从整体而言,基本上是把先秦诸侯体制下的宗子法仿制于宋代的官僚体制之上。因而这种以宗子为核心的新的家族制度的建构,并不十分适用于一般的贫民社会。尽管如此,张载关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还是为后世的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兴起,理清了一个可供继续模仿和改进的样式,因此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与张载同时代的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同样也对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建构多有思考与论述。程颢、程颐兄弟同样认为要建构新的家族制度,三代先秦时期的“宗子法”是一种值得效法的形式。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上古时代的“宗子法”败坏,才导致了唐宋以来社会的混乱无序与道德沦丧,“宗子法坏,则人不自知来处,以至流转四方,往往亲未绝,不相识”③。要使纷乱的社会重新走上有序的轨道,就需要恢复上古的“宗子法”,“今无宗子法,故朝廷无世臣。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古者子弟从父兄,今父兄从子弟,子弟为强。由不知本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从根直上一干,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虽远,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处,自然之势也。然又有旁枝达而为干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国,诸侯夺宗云。’”①“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②
上古的宗法制度既然已经败坏,宋代与周代的社会状态已经完全不同,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恢复周代的宗法制度不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是,既然是重建家族,就必须具有家族制度最基本的内容——宗子之法。那么如何重建宗子之法?程颐认为不妨先从若干仕宦大家开始试行:“宗子法坏,……今且试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术要得拘守得须是。且如唐时立庙院,仍不得分割了祖业,使一人主之。”③“宗法须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则人人各知来处。宗子者,谓宗主祭祀也。”④
在一般的情况下,宗子是以嫡长兄为之。宗子具有统率本家族其他成员的权利,特别是负有家族祭祀的权利。对于以宗子为核心的家族祭祀,二程兄弟的设想与张载几乎相同:“古所谓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庙,主之而已。支子虽不得祭,至于斋戒,致其诚意,则与主祭者不异。可与,则以身执事;不可与,则以物助,但不别立庙为位行事而已。后世如欲立宗子,当从此义。虽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废祭,适足长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犹愈于已也。”⑤一个家族的其他儿子即支子,没有主持祭祀的权利,只有宗子有这个权利,因此宗子必须建立家庙,以主持祭祀活动。支子虽然不主持祭祀,但必须诚心诚意地参加斋戒活动,态度必须与主持祭祀的宗子完全一样。如果有条件,最好能够亲身参与;如果不能亲身参与,必须提供物资帮助。但是,支子不能自己立庙主持祭祀。所以,重建家族,再立宗子,必须遵守这个规矩。
二程兄弟对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构建,与张载的设计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以“宗子法”为家族权利核心,家族其他成员依附于宗子之下的一种社会凝聚模式。“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于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于人也。”①而这种“宗子法”,同样比较适用于官僚士大夫家族与家庭,因此,他特别强调说:“士大夫必建家庙。”②
二程兄弟在设计这种家族结构模式的同时,还对家族内部及家庭内部的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进行了思考。程颐对于自己撰写的《六礼》颇为自负,他说:“冠昏丧祭,礼之大者,今人都不以为事。某旧曾修《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将就后,被召遂罢,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间多恋河北旧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渐使知义理,一二年书成,可皆如法。礼从宜,事从俗,有大故害义理者,须当去。”③从现存的文献看,程颐的《六礼》,可能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存留下来的条文相当简略。但是从这些简略的条文中,还是看出二程兄弟对于重建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的重视。如他对父母兄弟之间关系的叙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爱,且如闾阎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于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体重于己之体也。至于犬马亦然。待父母之犬马,必异乎己之犬马也。……或曰:‘事兄尽礼,不得兄之欢心,奈何?’曰:‘但当起敬起孝,尽至诚,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尽友爱之道而已。’”①从这些简略的条文叙述中,已经可以反映出程颐所强调的以孝道为中心的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的基本指向。
对宋代新建家族制度之下的家族、家庭内部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进行比较详细设计的儒者,是当时的著名士人司马光。他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还编写了《家范》《书仪》两本关于重建家族的著作。《家范》《书仪》的要旨在于协调家族内部及家庭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家族内部各色人等的行为规范,重新建立一种适应于宋代社会的家族伦理和家庭伦理。司马光在这两部著作中所体现出来“家范”“书仪”的主要来源依据,仍然是先秦时期的礼制。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总纂官纪昀等在《家范》的提要中即明确指出这一点:“《家范》十卷,宋司马光撰。……首载《周易·家人》卦辞、及节录《大学》《孝经》《尧典》《诗·思齐篇》语,以为全书之序。其后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杂采史事可为法则者。……朱子尝论《周礼·师氏》云:‘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程颢)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观于是编,犹可见一代伟人修己型家之梗概也。”②我们再来看看司马光在《家范》的开篇序言中所引述的内容:
《周易》:离下巽上。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爱者所以使众也。《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孝经》曰: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昔四岳荐舜于尧,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诗》称文王之德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降及后世,爰自卿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为人法者,今采集以为《家范》。①
司马光在《家范》序言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思维方式,正体现了北宋时期一般儒者对于重建家族制度与家庭伦理的基本理念,即既然要重建家族,就必须有所依傍,而所依傍者的基本来源,只能是古代的宗法体制和上古的所谓“周礼”。虽然说三代先秦时期的这种制度早已成为历史遗迹,但是在司马光等宋儒的采集张扬之下,上古的这些礼制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家族伦理与家庭伦理,依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司马光等所宣扬的“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以及男尊女卑的家族与家庭伦理,就基本上被宋之后的中国社会所承继。司马光在《家范》《书仪》中所体现出来的家族内部伦理和家庭内部伦理,正与张载的家族制度构建框架设计,形成宋代以来新的家族制度的两个基本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谈到北宋时期儒者对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时,我们还不能忽视欧阳修、苏洵等人对于家族谱牒的撰写与推广。重建家族没有家谱是不行的,正如上述张载在《宗法》篇中所指出的“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把修族谱与立宗子法提高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唐宋以前门阀制的谱牒已经废绝,魏晋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对谱牒的垄断必须予以打破,使之适应于宋代社会的一般家族与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士大夫和儒者进行了重新撰写家谱的尝试与实践。宋仁宗皇祐、至和年间(1049~1056)欧阳修编的《欧阳氏族谱》和苏洵编的《苏氏族谱》,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被后世视为宋儒重写新家谱的开端,从此之后,许多士大夫家族,乃至一般的民众家族,也都纷纷以欧阳氏、苏氏族谱为典范,为自己的宗族编修族谱,“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①。欧阳修和苏洵二人,也对自己撰写的族谱相当自负,希望能够由此而推广于天下,使天下所有家族在撰修族谱时有所依据。所谓“是不可使独吾二人为之,将天下举不可无也”①。于是,在欧阳修、苏洵及其他士大夫和儒者的推动下,宋代及其后来就逐渐形成“私谱盛行”的局面。
欧阳修与苏洵对于宋代家族族谱修撰尝试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宋代以前门阀士族谱牒官府编修的性质,改变为私家编修的性质。唐代以前的谱牒,是为了明确诸侯、门阀士族的出身和血统,是世袭制及朝廷提拔官员的依据,也是家族之间联姻的依据。而苏洵、欧阳修等人所创建的宋代族谱,纯粹就是为了维系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它成了凝聚家族以使之长久生存的历史记载与精神力量。虽然亲情联系势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行渐远,但是有了私家族谱的存在,多少有所凭借,有所维系。苏洵在自己撰写的族谱《谱例》中说:
古者诸侯世国,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庙,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独贤士大夫尊祖而贵宗,盖其昭穆存乎其庙,迁毁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与为服,死丧嫁娶相告而不绝,则其势将自至于不忘也。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②
苏洵根据上溯六世祖先的原则,编写了自家的族谱,不由得感慨道:
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见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缌麻,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涂人也。吾之所与相视如涂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
人之身分,而至于涂(途)人,此吾谱之所以作也。①
欧阳修在自己修撰的族谱中也指出,新修的族谱必须“断自可见之世”,从而使得真正的血缘联系“各详其亲,各系其所出”,达到亲疏有伦的目的:
姓氏之出,其来也远,故其上世多亡不见。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如此世久,子孙多则官爵功行载于谱者,不胜其繁。宜以远近亲疏为别,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孙既别自为世,则各详其亲,各系其所出。是详者不繁而略者不遗也。凡诸房子孙,各纪其当纪者,使谱谍互见,亲疏有伦。②
北宋时期张载、二程兄弟、司马光、欧阳修、苏洵等著名儒者关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与建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三代先秦时期的“宗法制”与礼制作为蓝本而推衍出来的带有一定复古性质的模式,但是这些设计毕竟完成了宋代及其后世中国家族制度的基本框架与家族、家庭伦理的价值取向,因而这些设计与实践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而这些设计更侧重于士大夫官僚家族而不适用于一般民众家族的缺陷,就有待于南宋及其后世的不断改进与推行了。
(二)南宋朱熹等理学家对家族制度的改进
北宋时期张载、二程兄弟等儒者对于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在当时已经得到了一些实践。但是张载、二程兄弟的这些设计,一方面是比较注重于官僚阶层家族、家庭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又过于依赖三代先秦的宗法制和礼制。因此,这些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族制度在民间社会的普遍推广。于是,到了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人物的理学家们,试图对北宋儒者所建构的家族制度进行改造,使之更加适应于民间社会,特别是通过家规、家礼的制定和践行,转变成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
我们在上面论述张载试图恢复重塑先秦“宗子”制的时候,曾把“宗子”提高到与“大君”相仿的崇高地位,“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①。而对于同样的这一则源自上古的论说,朱熹在其著名的《西铭解》中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说: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则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继承天地,统理人物,则大君而已,故为父母之宗子;辅佐大君、纲纪众事,则大臣而已,故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长吾之长,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贤者才德过于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则凡天下之疲癃残疾、孤独鳏寡,非吾兄弟无告者而何哉!②
朱熹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即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地之子。贤者以及那些可以居高位的士人,只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这种强调表明了朱熹的平民意识。因而他所主张重建的家族,并不是周代的贵族宗法制,而是稍微倾向于平民化的、普通百姓都有权利和能力建立的家族。
从这种平民化的思想出发,朱熹意识到北宋诸儒关于新的家族的设计,存在着某些不切合民间社会实际的弊端,从而影响到新的家族制度的普及。于是,他立志参酌古今、权衡诸儒之说,重新著述,试图建立一种能够适用于民间社会的家族、家庭伦理规范与家族组织。而他的这一理想,集中体现在《家礼》一书之中。
朱熹的《家礼》,据说撰写于南宋乾道五年(1169)。朱熹在自己母亲去世丁忧期间,“居丧尽礼,参酌古今,因成丧、葬、祭礼,又推之于冠、昏,共为一编,命曰《家礼》”①。除《家礼》之外,朱熹在丁忧期间还编写了《祭仪》,在编此书的过程中,将《通典》《会要》中诸家祭礼编为《古今家祭礼》一书,于淳熙元年(1174)印行。朱熹在《家礼》的序言中写道:
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用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①
朱熹在这篇序言中着重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上古的礼制,很多已经不太适用于当前的社会,“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二是近古的一些好礼之士,虽然对上古的礼制进行承继改进,希望推行于当今的社会,但是这些近古之士,在许多方面还是未能切中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也还是不能很好地适用于一般的民众社会,“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用于贫窭者”。基于这样的理念,朱熹对民间家族、家庭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进行了更为详细而又比较切合南宋社会实际的“家礼”改造,撰写了《家礼》一书。
朱熹对于宋代重建新的家族制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祭祖祠堂与祭田的设计。朱熹《家礼》的开篇就是“祠堂”。他写道:
祠堂,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①
“祠堂”一词,可能最早出现于汉代,是建立在坟墓旁祭祀祖先的场所。不过,在祖先坟墓旁边建立庙祠,是王公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的特权,一般的民众则只能在自己家中的厅堂上举行祭祖活动。周礼对天子、诸侯、大夫、士等贵族祠庙祭祖制度有严格的规定,天子可有七庙,侯王可有五庙,大夫可有三庙,士可有一庙,而庶人则不可有庙,只能祭于“寝”,就是家宅中的正屋。到了宋代,除了皇室再也没有什么门阀贵族。皇室有他们专设的太庙中祭祀祖先。一般的官僚即通称的士大夫家族、家庭,则已经没有这种依据门阀体制所相应设立的祭祖“家庙”场所。而一般的民众家族、家庭,也因为科举制度的盛行,都有希望进入到官僚阶层中去。官僚士大夫阶层与一般民众阶层的社会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可能在不断的转换之中。这样一来,家族、家庭的祭祖礼仪,不单单是官僚士大夫阶层的需求,同时也是广大民众的需求,建立新的祭祖礼仪及其场所,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需求。民间社会既然要重建家族制度,必须首先确立祭祀祖先的场所。既然祠庙已经无可考证,朱熹就创造性地将汉代用来墓祭的场所与家居住宅结合在一起,称之为“祠堂”,这样就可以让天下所有的民众,不论官僚士大夫,还是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有了祭祀祖先的正式场所。朱熹关于祠堂的具体设计有如下述:
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正寝谓前堂也。地狭,则以厅事之东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制,不问何向背。但以前为南、后为北,左为东、右为西,后皆放此。
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一卓,大宗及继高祖之小宗,则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继曾祖之小宗,则不敢祭高祖,而虚其西龛一;继祖之小宗,则不敢祭曾祖,而虚其西龛二;继祢之小宗,则不敢祭祖,而虚其西龛三。若大宗世数未满,则亦虚其西龛,如小宗之制。
神主皆藏于椟中,置于卓上,南向。龛外各垂小帘,帘外设香卓于堂中,置香炉香合于其上。两阶之间,又设香卓亦如之。非嫡长子,则不敢祭其父。若与嫡长同居,则死而后其子孙为立祠堂于私室,且随所继世数为龛,俟其出而异居乃备其制。若生而异居,则预于其地立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则因以为祠堂。……旁亲之无后者,以其班祔。伯叔祖父、母,祔于高祖。伯叔父、母,祔于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于祖。子侄祔于父。皆西向。主椟并如正位。侄之父自立祠堂,则迁而从之。①
朱熹的祠堂设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以往儒者的“宗子”主祭的礼仪传统,“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非嫡长子,则不敢祭其父”。但是朱熹关于祠堂设计的最大突破,是允许所有的族人都可以建立祠堂,从而打破了以往“宗子”对于家庙与祭祀的垄断地位。非嫡长子们,得以“预于其地立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则因以为祠堂”,或“死而后其子孙为立祠堂于私室,且随所继世数为龛,俟其出而异居乃备其制”。如此一来,祠堂的建立便成了天下百姓所有子孙的共同权利。南宋以及其后中国民间家族的普遍设置祠堂,就在朱熹《家礼》的倡导之下,得到了切实的施行与推广。
祠堂的设置与祭祀的平民化,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予以支撑的。在三代先秦的“宗法制”下,建立家庙和主持祭祀的“宗子”,得到世袭家国的全力支撑,“宗子”往往就是世袭家国的执掌者。北宋时期张载、二程兄弟等设计的家族“宗子”法,宗子设立家庙和主持家族、家庭的祭祀,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那样,也是得到其家族、家庭包括在经济上的种种条件的优先支持和培植。而朱熹设计的祠堂制度,是试图适用于全社会的一般民众家族与家庭的。社会地位比较崇高和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官僚士大夫家族、家庭,固然可以承担起家族、家庭祭祀的应有负担,但是一般的贫民家族与家庭,就必然面临着建立祠堂和祭祀费用等经济上的困窘局面。再者,所有的官僚士大夫家族、家庭,也无法保障自己家族、家庭的长盛不衰和世泽永续,一旦沦为一般民众,同样也要面临建立、维护祠堂及维系祭祀等所需开支的种种经济负担。
对此,朱熹在设计祠堂的同时,又设计了为祠堂及祭祀提供经济保障的“祭田”以及置备必要的祭祀礼器等。他在《家礼》中写道:
置祭田。初立祠堂,则计见田,每龛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后凡正位、祔者皆放此。宗子主之,以给祭用。上世初未置田,则合墓下子孙之田,计数而割之。皆立约闻官,不得典卖。
具祭器。床、席、倚、卓、盥盆、火炉、酒食之器,随其合用之数,皆具贮于库中而封锁之,不得它用。无库则贮于柜中,不可贮者,列于外门之内。……
或有水火盗贼,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财。易世则改题主而递迁之。改题递迁,礼见《丧礼·大祥》章。大宗之家,始祖亲尽则藏其主于墓所,而大宗犹主其墓田,以奉其墓祭,岁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其第二世以下祖亲尽,及小宗之家高祖亲尽,则迁其主而埋之,其墓田则诸位迭掌,而岁率其子孙一祭之,亦百世不改也。①
在朱熹所设计的“祭田”中,始祖之下的“宗子”依然执掌着大宗的祭祀,故大宗的祭田,由“宗子主之,以给祭用”,而“宗子”之外的子孙们,既然可以各自另立祠堂,那么他们的祭田,也就不属于“宗子”执掌的范围,各归各属,“其墓田则诸位迭掌,而岁率其子孙一祭之”。这实际上使得家族内部的所有成员,都拥有了参与祭祀祖先的权利,“宗子”掌控家族祭祀事务的权利大大弱化。特别是随着世系的延续,从祭祀所亲的人情原则推移,一般族人对于远祖的认知概念逐渐疏远,对于高、曾、祖、祢等近祖的孝思较为强烈,对于高、曾、祖、祢等近祖的祭祀活动自然更为用心。而“宗子”所主持的远祖之祭,反而逐渐成为一种观念上的较为模糊的家族行为,其重要性大大下降。
朱熹对于宋代家族制度之下的礼仪的设计,是多方面的。除了祠堂、祭田之外,还包含了子孙冠礼、婚礼,先人丧礼,祖先祭礼以及家族、家庭内部的居家杂仪规范等等。由于朱熹所涉及的家族、家庭礼仪,比起北宋时期张载、二程兄弟以及司马光等儒者的设计更为切近一般的民众家族与家庭,因此他的《家礼》及相关的家族、家庭礼仪设计,被南宋以及其后的明清时代广泛依循与承继。可以说,就民间社会管理制度与家族、家庭道德伦理的构建,促使儒家文化走向民间社会化而言,朱熹的贡献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儒者,甚至超越了孔子。一直到当今社会,我们依然可以不时地发现朱熹《家礼》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蕴隐的文化因素。
(三)宋代儒者及士大夫对同居共财大家庭的宣扬与实践
宋代儒者们不仅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来设计新的家族制度与家族、家庭伦理规范,而且有不少儒者和士大夫家庭,还身体力行,亲自实践这种新的家族制度,试图以自身的经验,使宋代的家族制度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推行。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到,宋代的许多儒者对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更多的是依仿于三代先秦时期的礼制,特别是周代的礼制。“宗子法”成了大部分宋代儒者最为关键的家族追求与模仿对象。
“宗子法”的核心是在家族内部建立一种祭祀和控制管理家族事务的权威,家族必须在“宗子”的领导下得以延续和发展,家族内部的所有族人,都必须围绕在“宗子”的周围,从而形成一种以“宗子”为主轴,不断向外围扩大的家族体制。而形成这样一种从核心向外围扩大的家族体制,其最理想的实践方式,无过于累世同堂、同爨共食了。这正如司马光在《家范》中所推崇的那样:“国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孙数世二百余口,犹同居共爨。田园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禄,皆聚之一库,计口日给饼饭,婚姻丧葬所费皆有常数,分命子弟掌其事。”①
在宋儒们的倡导、推动和实践之下,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等形式的同爨共食大家庭样板,在宋代得到较多的涌现。这种风气,还对元明清时代的家族制度产生了某些直接的影响。根据今人王善军所搜集到的资料,宋代同居共财的著名大家庭有142家。其累世共居及其家族人口规模情景有如下表。②
根据王善军的研究分析,宋代同居共财大家庭最为集中的地区是陕州湖城县、池州铜陵县、徽州婺源县,分别为一县三家。如果依次计算它们的比例状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陕州共有七县,宋初户数为17443户,平均每县2492户。湖城县的同居共财大家庭比例为万分之十二。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可知,铜陵县的同居共财大家庭比例为万分之五点四,婺源县的同居共财大家庭比例则为万分之三点五。其他地区的比例,自然比这要小得多。而且,这些同居共财大家庭也处在不断产生和不断消亡的过程中,表中所列的数字未必都同时存在,再加上宋初的户口数在宋代应该是较少的时期,所以,以上的推论比例很可能是偏高的。①
就宋代整个民间社会的家族、家庭结构而言,以父母、子女以及祖父母为家庭成员的小家庭结构是普遍现象。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只能是少数的范本。而这种范本,正是宋代儒者重建新的家族制度的理想中的典型。正因为如此,在宋代儒者以及士大夫的大力倡导和宣扬之下,这种累世同居大家庭就特别地突显出来。不仅许多儒者、士大夫热衷于为其树碑立传,广为宣扬,而且政府也在不同的场合予以旌表鼓励。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儒者和士大夫也参与到这种累世同居大家庭的实践中去,这就使得宋代累世同居大家庭的范本更加具有社会影响力。这其中,南宋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家族,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
陆九渊是与朱熹同时代的一位儒学复兴的代表性人物、心学创始人。陆氏兄弟将重建家族的理想付诸实践,使得该家族连绵十世,数代同堂,千人共居,这在宋代是比较罕见的,不仅得到了当时朝廷的多次表彰,而且成为宋代家族制度重建的楷模。《宋史·儒林传》中分别记载了陆九渊兄弟的事迹云:
陆九龄字子寿。……九龄尝继其父志,益修礼学,治家有法。阖门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职,闺门之内严若朝廷,而忠敬乐易,乡人化之,皆逊弟焉。与弟九渊相为师友,和而不同,学者号“二陆”。……
九韶字子美。其学渊粹,隐居山中,昼之言行,夜必书之。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迁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训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①
陆九渊曾经为自己的三位兄弟撰写过墓志铭,也都提到本家族同爨共食的经历。如仲兄陆九叙的墓志云:
公姓陆氏,名九叙,字子仪。抚州金溪人。曾大父演,大父戬,父贺,赠承事郎。母饶氏,赠孺人;继母邓氏,封太孺人。……公气禀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群居族谈,公在其间初若无与,至有疑议,或正色而断之以一言,或谈笑而解之以一说,往往为之涣然。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从事场屋,公独总药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此。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公未尝屑屑于稽检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来,咸得其欢心。不任权诡计数,而人各献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无匮乏。后虽稍有田亩,至今计所收,仅能供数月之粮。食指日众,其仰给药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间,如一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顺出于天性,娣姒皆以为莫及。当穷约时,公之子女,衣服敝败特甚,余氏或时及之,公即正色呵止,必伯叔氏为之处,乃始得衣。虽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虽至窘急,裹囊无不立具。①陆九皋的墓表云:
陆氏徙金溪,年余二百,嗣见九世。公居五世,讳九皋,字子昭。……先君子居约时,门户艰难之事,公所当,每以条理精密,济登平易。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千计,仰药寮以生。伯兄总家务,仲兄治药寮,公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馈补其不足。先君晚岁,用是得与族党宾客,优游觞咏,从容琴弈,裕然无穷匮之忧。当时是,公于妻子裘葛未尝问也。②
综合以上所记述,我们大体可以知道陆九渊家族,从其先祖高、曾之时,就有共居同财的传统。家族中的事务,“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其他兄弟辈,各有所职,共同支撑家族的延续,“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就陆九渊兄弟而言,“伯兄总家务,仲兄治药寮,公授徒家塾”,此外的三个兄弟,则可专心于读书仕进或做学问。家族内的日常生活供给分配,一由家长或主事者主张,没有私心。“合族而食,每轮差子弟掌库三年。”③如主持家族生计主要来源即药业生意的陆九叙,手中掌握的钱财最多,但是“公之子女,衣服敝败特甚,余氏或时及之,公即正色呵止,必伯叔氏为之处,乃始得衣。虽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虽至窘急,裹囊无不立具”。为了加强家族内的团结认同,更好地达到敬宗收族的效果,每天“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
陆九韶撰写有《居家正本制用篇》,对自己家族的实践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在这篇文章中,他反复强调教训家族子弟知书识礼的重要性:“古者民生八岁,入小学,学礼乐射御书数。至十五岁,则各因其材而归之四民。故为农工商贾者,亦得入小学。七年而后就其业。其秀异者,入大学而为士,教之德行。凡小学大学之教,俱不在言语文字。故民皆有实行,而无诈伪。愚谓人之爱子,但当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读须先六经论孟,通晓大义。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节。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党,以交朋友,以接邻里。使不得罪于尊卑上下之际。次读史,以知历代兴衰。究观皇帝王霸,与秦汉以来为国者,规模措置之方。功效逐日可见,惟患不为耳。”“夫事有本末,知愚贤不肖者本,贫富贵贱者末也。得其本,则末随。趋其末,则本末俱废。此理之必然也。今行孝悌,本仁义,则为贤为知。贤知之人,众所尊仰。箪瓢为奉,陋巷为居,己固有以自乐,而人不敢以贫贱而轻之。岂非得其本,而末自随之。夫慕爵位,贪财利,则非贤非知。非贤非知之人,人所鄙贱。虽纡青紫,怀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晓义理。己无以自乐,而人亦莫不鄙贱之。岂非趋其末,而本末俱废乎。”而遵行孝道,更是家族兴盛与永续的根本之道,“至如奉亲最急也。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祭祀最严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方不是因贫乏而废礼义。凡事皆然。则人固不我责。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则礼不废而财不匮矣”。“一家之事。贵于安宁和睦悠久也,其道在于孝悌谦逊。”①
响着后世。因此,清代陈宏谋在编撰《训俗遗规》收录陆九韶的《居家正本制用篇》时,在按语中说:“门内之地,至性所关。虽极愚顽之人,岂无天良之动。而有时视门内如路人,非礼犯分之事,悍然不顾者,名利之心夺之耳。于名利上看得重一分,即于天伦轻一分矣。梭山先生论居家而先之以正本。其言正本也,以孝弟忠信,读书明理为要,而以时俗名利之积习为戒,其警世也良切。至于制用之道,不过费以耗财,亦不因贫而废礼。随时撙节,称家有无,尤理之不可易也,陆氏十世同居,家法严肃,高风笃行,可仰可师。读此,亦足以知其所由来矣。”①显然,以理学著称的江西抚州金溪陆氏家族,很好地实践了宋代儒者所设计的新的家族制度的理想范本。
(四)宋代之后家族制度的变迁及对宋儒设计的若干修正
宋代儒者们对于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与实践,已经基本构建起来并且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的中国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整体框架。然而,宋儒们所设计与实践的新的家族制度所存在的两大特征,即“宗子法”和同居共财大家庭体制,其社会适用性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宋儒们设计的“宗子法”,主要在于确保“宗子”在家族内部的领导地位,希望通过“宗子”权威的设立,使家族的其他成员,团结或是被约束在以“宗子”为核心的家族组织之内。因此,“宗子”不仅掌握着家族的祖先祭祀权利,而且还拥有占有或使用家族各种资源的某些特别权利。但是,这种设计忽视了两种社会变迁的必然因素。其一,宋代已经进入以官僚士大夫与一般民众社会地位时有轮换的士人平民时代,不复存在先秦时期诸侯、世家得以继承的“世爵”“世禄”体制,“宗子”的社会地位势必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迁,时在变动之中。一旦“宗子”沦为一般的贫民身份,他们就很难支撑起领导家族的尊崇地位。而一位身份低微的“宗子”,显然不是家族其他成员所期待的,整个家族的社会与政治地位必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其二,一个家族的人丁如果不甚兴旺,数代繁衍下来,族人寥寥可数,则作为先祖嫡系的“宗子”,似乎还可以承负起率领阖族族人归宗祭祀以及从事家族其他活动的重担。但是如果这个家族经过数代繁衍之后,子而孙,孙而曾孙,族人的数量不断扩展,兄弟的分支也越来越多,那么,原先的“宗子”对领导家族的祭祀以及从事其他家族活动的控制能力也就日益下降。而随着家族繁衍代数的增加,这种控制能力就愈加下降。从被“宗子”所领导的其他族众的立场思考,既然“宗子”对于家族的事务越来越力不从心,“宗子”对于族人的利害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淡薄,“宗子”也就逐渐地变成可有可无的角色。于是,随着时间与世代的推移,家族内的血缘近亲之间的关系,逐渐跨越了“宗子”的地位,成为各个家族成员之间最不可或缺的联系。“宗子”日益转化为一种象征性的家族符号,而不是原先实质性的家族内部的领导人物以及对外发生联系的标志性人物。
在这种情形之下,宋代以来中国的家族制度及其组织,不能不对宋儒们所设计的“宗子法”进行某些方面的变通与修正,使之更加切近宋代以来的臣民社会,特别是切近大部分的平民社会。清代康熙年间的大学士李光地,号称“理学名臣”,对于宋儒们的学问多有论述,特别是对于朱子学,更是情有独钟,论著甚多。我们从李光地的论著中,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明清时期士大夫及一般民众家族对于宋儒们宣扬的“宗子”法的变通与修正。
李光地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古代以及宋儒们的一些关于家族制度的主张,并不一定适用于当前的社会,“有古所无,而今时势不同者,须想得到,不然后人亦难行”①。即使对于朱熹《家礼》中的规范,李光地也认为必须有所改变,否则很难施行,“《家礼》要存古法,故段段有宗子行礼,到底人不能行,如今须考定,令眼前可行方好”②。因此,李光地主张家族祭祀等事务,不可拘泥于“宗子”主祭而“支子”不祭的传统,应该予以变通。他在《家庙祭享礼略》中如此写道:
古礼之坏久矣,其渐有因,其本有根,虽有贤人君子讨论而服行之,然所谓不尊不信则久而莫之从也固宜,况乎复古之难,而变今之不易,则凡所讨论,而仅存者亦多贤人君子区区饩羊之意。自其身不能尽行,而望人之从而行之,尤不可得也。
礼莫重于祭,而大宗、小宗之法不讲者且数千年。夫无大宗小宗之法,则源远末离无所统摄。分不定而情不属,虽有仪节之详,将安用之?是以乡异俗、家异法,有身列荐绅士类而迷妄苟简至于犯分悖本而不自知。呜呼!其随俗而安之乎?抑区区讲论,行其宜于今者,而不甚远于圣人之意,庶几存古道之什一于千百也!
岁乙巳,家庙始成,先君子将率族人修岁事焉,于是讲其礼。曰此古所谓大宗者也,当有明时族中先辈长者,尝考古而立宗子矣,然而有数难者。古者无禄则不祭,故庶人荐而已,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其时卿大夫家非世官、则世禄,皆朝廷赐也,而宗子主之,故得以其禄祭。今皆无之,则宗子无禄也,奈何犹备大夫士之礼以祭?父为大夫、子为士,其祭犹不敢以大夫,况庶人乎?难者一也。古者宗子为朝廷所立,故其人为一家之宗,而必口于礼法。今则有樵采负贩使之拜俯兴伏,茫然不省知者矣,而奈何备盛礼以将之?难者二也。凡为宗子者,以其为族人之所尊重,冠昏丧祭必主焉,故祖宗之神于焉凭依。今则轻而贱之者已素,一旦被以衣冠,对越祖宗,人情不属,而鬼神不附。难者三也。是故世变风移,礼以义起。今人家子孙贵者不定,其为宗支也,则不得拘支子不祭之文,而惟断以无禄不祭之法。且近世褒赠祖先,固不择宗支授之,褒赠之所加则祭祀之所及,揆以王法、人情,无可疑者。①
李光地在这里指出了仿行先世“宗子”法的三大难处:第一,古代的“宗子”,“卿大夫家非世官、则世禄,皆朝廷赐也,而宗子主之,故得以其禄祭。今皆无之,则宗子无禄也”。没有世禄支撑的“宗子”,显然无法承担领导家族的重任。第二,古代的“宗子”,“为朝廷所立”,地位崇高,足以表率家族;而如今许多家族的所谓“宗子”,多不知礼数,“则有樵采负贩使之拜俯兴伏,茫然不省知者矣”。家族祭祀有失尊严隆重。第三,贫寒的“宗子”主持家族的祭祀及其他事务,不仅族人不服,鬼神亦不服,完全失去了祭祀的目的。为今之计,只有“世变风移”,“今人家子孙贵者不定,其为宗支也,则不得拘支子不祭之文”。家族的祭祀等大事,不能拘泥于“宗子”主祭、“支子”不祭的古代礼制,应该选择适合这种尊严而又重要任务的其他族人来承担。
“宗子”既不可拘泥于大宗嫡子,那么从整体而言,李光地认为,只要是血亲的族人,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其他族人同样可以担任,“周制有大宗之礼,乃有立适之义。今大宗之礼废,无立适之法,而子各得以为后,则长子、少子当为不异”①。古代规定大宗才能立庙,而今则其他族人只要传继数代,同样可以立庙。“所谓庙者,大宗乎、小宗乎?如大宗也,则惟伊川生存,乃得主祭,若其子孙为无禄人,则亦不得世其祭矣。以理揆之,必也其小宗也。盖四亲之庙,自己立之,则子孙尤可以世其祭以终于已。此亦所谓古未之有,而可以义起者也。故于今而斟酌二贤(程伊川、朱晦庵)之意,则始祖之庙如愚前所云者,盖庶几焉。……则其庙固始祖有也,有之则不可废,故其子孙得更迭以其禄祭无所嫌也。若四亲则亲尽迭祧,而庙非一人之庙,高祖之祭及其元孙以下则废之矣,故祭不常,则庙亦不常,必使法应立庙者立焉,而使其子孙犹得以主其祭,迄于己之祧。而止如伊川之说,固亦变中之正也,犹以为疑,则亦参以愚大宗之说。立庙者主祭,而仍设小宗宗子之位,奠献祝告同之,其亦可矣。若乃五世之中无应立庙之人,而其势不可聚,则各备士庶之礼以奉其四亲,而亦当于高曾祖之忌日,各就其宗子之家而先展拜焉。庶几古人之意未尽湮没。”②
李光地不仅主张大宗之下的近祖可以立庙,而且因为大宗所奉之始祖,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子孙不免感到有些疏远,而对于高、曾、祖、祢的近祖,时代相近,血缘关系更为亲密,因此李光地认为,祭祀祖先的重点,还是要以近祖为主。祭祀近祖的礼仪,也不必拘泥于春秋二祭,而是应该入乡随俗,参照土风民情,时时缅怀拜祭。他在《小宗家祭礼略》中云:古者宗法之行,宗子祭其亲,庙自天子而下降杀以两。……伊川程氏祭礼欲令上下通得祭,其高、曾、祖、祢为四亲庙。……然祭四亲者,亦止于宗子而已,五服以内之支庶,则固有事于宗子之家,非家立庙而人为祭也。然古者无田则不祭,祭用生者之禄,是祭祀必大夫士而后具明矣。古所谓宗子者,皆世官、世禄者也。今贵达者未必宗子,而宗子或夷于氓隶。宗子之分与禄既不足以配其四亲,而支子有爵俸者反绌于不祭之文,而不得伸其追远之爱。如此则程、朱之礼又穷。故曰三王殊世,不相袭礼。今之礼僣乱极矣……吾家大宗之礼又当别论。以四亲言之,我于先人为宗子,而祖以上则非揆之于法得奉祢祀而已。然小宗之法今世亦不行,吾家旧所通行又皆不论宗支,轮年直祀。……今所奉祀并立四亲,幸今聚族祖里伯叔,每岁直祀高曾祖者,吾咸与焉然。退而修四时之事,亦必并设高曾祖考之位而申祝献焉,非僭且渎,实则准以情分而有所不容已也。
吾家大宗时祭,旧止春秋。其奉祀祖考者,则否止于清明、七月等俗祭而已。吾思古人合诸天道,春禘秋尝,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盖春秋之义大矣。惕恻怆之心,自近者始。不当于远祖独行之也。若欲以清明、七月俗节当之,则清明为春暮,七月为秋始,迎来太迟,送往太骤,亦失礼经之意。今欲定于二分之月别卜日为春秋祭,而清明、七月则循俗荐馔焚楮如《家礼》俗节之祭而已。况《家礼》尚有四时之祭,皆用仲月。今春秋而外,有冬节荐鲜,可当冬夏二祭,其礼稍杀于春秋可也。又记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故祭为吉礼,而忌则丧之。余也今俗,废春秋吉祭而反于忌日饮酒食肉,谓之受胙,吉凶溷杂,非人情,殆不可用。今逢忌日,亦当稽朱子《家礼》及语类所载,变冠服、不饮酒食肉,终日不宴亲宾,志有所至,乃近于正生。忌则不然,礼稍杀而情稍舒可也。墓祭原起于奠后土之神,为祖考托体于此,岁祭焉,所以报也。今祭墓者丰于所亲,于土神辄如食其臧获而已,简嫚之极,必干神怒。故今定墓祭牲馔,祖考与土神同奠献,则依《家礼》先祖考而后土神,自内而外,非尊卑之等也。此数者,皆大节目,苟失礼意,不可不正。其余如元旦、五月节、中秋、重阳节,此等皆可不拘丰俭、循俗行之所谓,事死如事生,节序变迁,皆寓不忍忘亲之意。①
李光地在这里认为,不论是古代礼制还是宋儒程颐、朱熹等所提倡的家族祭祀之礼,都不能较好地适应清代的社会现实。“宗子”之制到了清代,“贵达者未必宗子,而宗子或夷于氓隶。宗子之分与禄既不足以配其四亲,而支子有爵俸者反绌于不祭之文,而不得伸其追远之爱”。因此,民间乃至李光地自己的家族,在祭祀祖先方面,都已经是“不论宗支,轮年直祀”。李光地本人也积极参与到这种变通的祭祀祖先仪式中,“今所奉祀并立(高、曾、祖、祢)四亲,幸今聚族祖里伯叔,每岁直祀高曾祖者,吾咸与焉然。退而修四时之事,亦必并设高曾祖考之位而申祝献焉,非僭且渎,实则准以情分而有所不容已也”。对于当时民间社会所盛行的“不论宗支,轮年直祀”的祭祀形式,李光地还在其他的论述中予以肯定:“直祭,非古礼也。然欲均劳逸,且使祖考诸子孙妇皆知蘩之义,而皆于宗子之家行之,亦未为失。”②
当然,李光地所主张的不论大宗、小宗,只要是四世之上均可立庙(祠堂);大宗、小宗都可以设“宗子”;祠堂祭祀的主祭人可以是“宗子”,也可以不是“宗子”,但存在着明显的倾向性,即家族的管理事务,应该偏重于选择家族中具有一定政治、社会地位的族人来承担。如在支子设置祠堂方面,如果各分支中有功名的族人存在,那么就可以优先设置祠堂。他说:
小宗如及身贵,便应立四亲庙,子孙以世代而祧,下至本身元孙,都该用贵者之宗子、宗孙主祭。盖五世之泽未斩也。如五世内支子有贵者,亦不得于此祠中主祭,当自别立四亲庙可也。大宗不容有二,小宗不妨其多。①
小宗立庙“不妨其多”,这就基本扫清了支子各自设置近亲祠堂的礼制障碍。明清以来中国家族内部普遍设立祠堂的现象,与这种观念的转变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家族祭祀方面,李光地更是主张必须由有政治、社会地位的族人来担任主祭人,没有功名的“宗子”,只能是作为“陪祭”参与。他在《治道》中说:
宗法是大事,大宗固宜复,然其子孙贵者不必宗子,宗子不必贵,祭用贵者之禄,岂反使宗子之贱加其上?万一宗子竟是农夫,如之何其加于朝官也?只得贵者主祭,宗子及直祭同祭。主祭者居中,宗子居左,直祭居右,长一辈者稍前,同班者齐排,卑幼者稍后。祝文竟写主祭孙某、宗孙某,直祭孙某。至小宗亦宜仿此意。如某于法得立高、曾、祖考之庙,然某即非高祖之宗子也,某为主祭孙,而宗孙即用高祖之长房、长孙为之。直祭者每年换人,至五世而祧,则用曾孙之长房长孙为宗孙,以次而下。倘有德有爵不可祧者,则仿古礼祖功宗德之意,将此主移向始祖之庙,合族公祭。不然贵者之子孙倘竟降为皂隶,又安可以祖之爵而隆祭之礼?与所
谓葬以大夫祭以士者大不侔矣。祭以本身之爵非以祖考之爵也。①
李光地在《家礼要存》中谈及自己家族的祭祀仪式时说:
宗子行礼,到底人不能行。如今须考定,令眼前可行方好。卿大夫家古有世禄,故子孙虽无位,行事尚得与大夫同。今卿大夫既无世禄,设数传之后,支子显达,而宗子却无禄,则宗子分止宜荐,而支子又不得祭,是使有禄者身享鼎烹,而祖宗仅受菲薄,于心安乎?寒家宗祠在山中,先世士大夫多居郡,祭时不躬不亲,惟使直祭者经理其事,故时序岁腊潦草献享而已。及先君定议,以为宗子有禄,自当主祭。即宗子举人,而支子进士;宗子侍郎,而庶子尚书。爵秩相彷,亦仍当宗子主祭。若宗子无禄,而庶子显贵,则贵者以其禄主祭,居中;宗子居左,直祭者居右,一同奠献。如此斟酌,既不背古意,而于今可行,方不为空言。②
雍正三年(乙巳1725)李氏家族祠堂修葺一新,举行隆重祭祀活动,李光地描述此次祭祀的仪式云:
乙巳元日,聚族于斯……循之宗子法废,爱羊存朔,直年均劳,奠献以爵,三人居中,跪闻嘏祝。为此礼者,非曰贵贵。载稽古义,无禄不祭。左宗、右直,以昭穆位。余家主祭一人,有爵者中立,左宗子、右直年。盖有爵则得以其禄祭,宗子以存古,直年以均劳也。其序立则以昭穆尊卑为前。却若宗子贵,而又直年,则主祭,只用一位。大宗之祭,长至春元始祖、先祖,论取伊川,尚有春秋,沿旧以禋。有明时,宗中先达率于大宗祠祭春秋。先君增以长至元旦,实与伊川论合。然春秋如旧,有其举之未敢废也。此外小宗,各遵其格法得立庙。自厚于昵五世则迁,自统于嫡。今达官封赠及高曾,则法得立四亲之庙,然五世之中须以达者之宗子、宗孙主祭,虽旁支又有贵显,自复立庙为宗,则可不得于小宗庙主祭。盖先者之泽未斩也。①
从以上所引述的清代李光地关于家族“宗子”、祠堂设置及祭祀礼仪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对古代的礼制多有更革,即使是对宋儒程颐、朱熹等人的家族制度设计,也有许多变通之处。而这种更革、变通,正体现了明清时期中国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一般情景。李光地位居高官,精通理学礼制,因此,他自己家族的礼制实践以及他的诸多论述,可能还比较保守一些,对于先人的礼制,尚不至于过多的离经叛道。至于一般民间社会的家族、家庭,“宗子”的概念已经相当淡薄。繁衍至十世以上的家族,“宗子”及先祖、始祖之祭,大多流于形式,无足轻重。近祖之亲,建造祠堂与否主要是视子孙的经济条件而定,不复以贵者为标准。家庭的析居分爨,也基本实行平均分配制度,家族祭祀,由于族田、祭田的设立,也大都采用轮值的办法。这一系列家族制度组织及其礼仪的变迁,正反映了宋代以来社会士人、平民化的整体趋势,先秦时期以世家门阀为基础的“宗法”礼制,必然要转型适应明清时期社会变迁的整体需求。这也正是宋儒们所设计的新的家族制度到了明清时期不断被修正的根本原因。
宋儒们作为新的家族制度组织样板的累世同堂、同爨共食的大家庭形式,同样也是不太符合宋以后中国民间社会的实际情况的。许多研究者把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和累世同居共财、同爨合食的大家庭组织,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家族制度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其实,这是不确切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和道理学家们大力提倡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制度,实际上是有违人性,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违背的。这种大家庭组织几乎都是由某个权威家长(主要是官宦)的惨淡经营、硬撑门面才得到勉强维持的。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时间的推移,大家庭内部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以后辈夫妻形成的小圈子,相互嫉恨,计长论短,争一己之利,与大家庭组织发生频繁的冲突。再者,在同居共财大家庭中,由于森严的等级和烦琐的礼节,成员之间的思想和感情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交流,而只能用一个“忍”字代替。唐朝张公艺九世同居,唐高宗问他何以至此,他大书百余“忍”字以对。无独有偶,宋代“潞州有一农夫,五世同居。太宗讨并州,过其舍,召其长讯之曰:‘若何道而至此邪?’其长对曰:‘臣无他,惟能忍耳!’”。所以宋人常说:“居家久和者,本于能忍。”但怎样一个忍法,其中也是大有学问的。因而,家庭成员之间不但要忍,而且要讲求“处忍之道”。这个“处忍之道”,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是这样描述的:“盖忍成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发,不过一再而已。积之既多,其发也,如洪流之决,不可遇矣。不若随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尔!’曰:‘此其无知尔!’曰:‘此其失误尔!’曰:‘此其所见者小尔!’曰:‘此其利害宁几何!’不使之入于吾心,虽日犯我者十数,亦不至形于言而见于色。然后,见忍之功效为甚大,此所谓善处忍者。”①这种有违人性的隐忍之道,当然不是大多数人所能实践的。因此,这种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最终没有不土崩瓦解、裂变为许多个小家庭的。可以说,这种理想化、模式化的大家庭制度,只能是个别的、临时性的,而不可能是常规的、永久性的。
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之所以是个别的、临时性的,是因为这种大家庭制度严重地束缚了家庭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抑制了私有欲望的生长。一般来说,由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家庭成员都有着共同发家的愿望,因此能够发挥比较充分的生产积极性。一旦儿女辈婚嫁成家,并且生出孙辈,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家庭成员最为关心的,不是这个由数对夫妻组成的大家庭的利益,而是以每对新夫妻及其子女所组成的小家庭的利益。但是在共同生产、集体分配的家庭体制下,每个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小家庭之间,难免会由于劳动、分配、福利以及性格、意气诸方面的差异,产生种种矛盾。随着大家庭内辈分的增加和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小家庭的日益增多,其内部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亦日益激化。但是以聚族而居为形式的家族制度,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这种内部矛盾的发生。就整个家族而言,由众多族人家庭组成的强大的家族势力,可以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从而有效地庇护各个小家庭的安定发展。而就各个小家庭而言,虽然家族组织拥有一定数量的公有财产,但同时也允许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小家庭经济的独自发展。与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制度相比,家族制度下的小家庭有着较多的经营独立性,族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从而为家族内部每一个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小家庭所乐意接受。这是中国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之所以能够永久性存在并且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事实上,自宋代以来,如前面所引述的唐代张公艺和宋代袁采等,许多家族甚至士大夫阶层对于同居共财大家庭的弊端是相当清楚的。一些家族为了防止和杜绝这种内部矛盾的发生,在族规中正式规定族人应及时分家,不得硬撑门面而导致兄弟反目、叔侄不和。如安溪谢氏家族就在《族训》中指出:“示后世子孙有财产当分者,即便请族长立阄书均分给予,不可姑息迟延岁月,一旦无常,不免后患,破家荡产皆此然也。”①又如福州某一陈氏官僚在给子孙的分家文书中写道:“盖闻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余岂以多财遗子孙哉!……与其合之任听虚糜,曷若分之俾知撙节,爰将原承祖遗及余续置产业,除提充公业外,为尔曹匀配阄分。”②
我接触过不少民间家庭的分家析产文书,其中的一些文字也十分值得玩味。如清代乾隆二十三年(1758)泉州张氏家族的分家阄书写道:“仝立阄书,长房方高、二房方升、三房方远长男源、四房方大。父在台时,舌耕粒积,置有泉、台各业。及父司漳铎,唤高兄弟等面命曰:吾没后,尔兄弟分爨……兹孙曾浩繁,而方远不年,诚恐日久未能恪守前规,不得不为善后之计,公议分爨。虽律以九世同居,仅及其半,而较诸世俗浇习,已迥不同。因遵父母遗命,将泉、台产业……焚香敬告祖父之前,公同拈阄,按股登载。……各执阄书一纸、应分细册一本,以垂永久。自今以往,惟愿孙曾追念祖父辛苦,勿弃前基,水木情敦,勿践行苇,则虽分犹合,先人含笑,永昌厥后矣。”③道光三年(1823)漳州府龙溪县林氏家庭的分家阄书记云:“同亲立阄书人兄弟林泉、林果、林辉、胞侄陵南等,窃谓九世同居,此风足效,但家事浩繁,人心不一,难以合理敬遵。母亲之命聊为分爨之计,邀请家长房亲,各将承祖父产业物项会同……凭母亲家长拈阄为定。”①咸丰四年(1854),泉州晋江县何氏家庭的分家文书云:“古者九世同居惟有张公,彼幸一堂聚首,故历世远无异言。今晋江县十五都福全乡何家廷弼、廷奏,系胞兄弟;堂兄廷福,各居一方,安保后日子侄之无异言乎?……各份俱以阄书为证。日后各房丁财贵三多具庆,不得造言生事。今欲有凭,仝立阄书壹样叁纸,各执为照。”②台湾新竹地区的一份分家文书云:“立分阄字人兆清、其旺、其盛兄弟等,窃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者情关手足,宜深聚首之思,谊属孔怀协奏埙箎之雅,岂可别房分门,致叹雁行之折翼?然而夷齐之高风已渺,虽伯仲之笃谊难期。……一旦而思远适况瘁,其何以堪?不得已兄弟相商,请得房族到场,将父遗下水田银项作三股均分,对祖拈阄永远,子孙人等不得争长较短,异言反悔。今欲有凭,特立分阄字式纸各执为照。”③
这些分家文书都体现了一个理想与现实相互矛盾的问题,即对于孝悌观念所提倡的累世共居,心存仰慕,但是在现实社会里,不分家势必引发家族内部的诸多矛盾,“恐有阋墙之患”④。所谓“窃谓九世同居,此风足效,但家事浩繁,人心不一,难以合理敬遵”。“古者九世同居惟有张公,彼幸一堂聚首,故历世远无异言。今晋江县十五都福全乡何家廷弼、廷奏,系胞兄弟;堂兄廷福,各居一方,安保后日子侄之无异言乎?”
以上这些言论和族规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宣告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制度是行不通的。因此,从家族和家庭的发展趋势看,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制度必然为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所融化。我们不能否认,在孝悌等传统观念以及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下,每一个家族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偶尔有一些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出现,但不论是三世同居,四世同居,甚至五世以上同居,最终都不能不裂变为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小家庭,为家族所消化。这种非理性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只是家族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小插曲而已,并不具有制度上的普及性。
人们一致认为,中国这种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制度比较盛行于宋代。两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动荡不定日益加剧,阶级关系日趋复杂与多样化,于是,坚持义理的儒者与士大夫们力图把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局限在大家庭制度之中,使它成为一种既顺应社会变化,又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理想化的家庭模式。我们从历代正史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经过朝廷旌表的这种模式化的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唐代有18家,五代有两家,宋代多达50家,元代近20家,明代亦有20余家①。从宋代到明清时期,这种经过朝廷旌表的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的递减趋势是很明显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受到朝廷旌表的20余家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中,明初至正德年间(1506~1521)竟然多达22家,而嘉靖至明亡,仅有数家而已。②众所周知,明代中期以后,即明代嘉靖、万历之后,是中国家族制度及其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家族祠堂的普遍设置,祭田、族田的日益累积,族谱家乘的修撰与流行,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兴盛起来的。③明代中后期由朝廷旌表的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的锐减,正体现了由众多族人家庭聚族而居为形式的家族制度,在明代中后期得到迅猛的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由朝廷旌表的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的锐减,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因此到了清代,根据《清史稿》的记载,由朝廷旌表的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仅有聊聊五家。①并且,明清时期受朝廷旌表的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也已经很少有如唐宋时期那种诸如张公艺、陆九渊、袁采等以名臣、名儒为核心的典范,而大多是以中下层的民众偶然所形成。
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家族制度及其组织形成的较为正常的途径应当是这样的:当某一个迁居始祖带领妻子儿女在某一个地点定居下来之后,垦荒耕耘,取娶婚嫁,繁衍后代。儿子们长大成人后,便开始分家,儿子辈另成单独家庭,成为长房、二房、三房及更多房。孙儿辈成长婚嫁后,家庭再次分析。家庭分析的最佳时间是在二世同堂和三世同堂之间,三世同堂以上尚未分析即属非正常情况。如此世世相衍,代代分析,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个体小家庭日益增多,原先由某一迁居始祖开创的家庭,便逐渐扩展为家族。在经济社会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族人开始建造祠堂,设置祭田、族田,修撰族谱家乘,敬宗收族,繁衍世系。随着人口的繁殖、家庭的不断分析以及家族规模的不断扩大,家族内部的分支、分房也不断增多,如果不遭受天灾人祸等外部因素的干扰,由某一个迁居始祖开创的家庭,就这样不断地演变成雄踞一方的巨姓大族,或者分析为若干个有着某种相互联系的新的家族。
宋儒们所倡导和实践民间家族制度,无论是宗子制的建立、祠堂祭祀等礼仪的规范,还是累世同居大家庭,等等,更多的是仿袭三代先秦的礼制所形成的。宋儒们虽然极力企望仿袭古代的礼制来重建宋代新的家族制度,但是时代的不同,使得宋儒们的许多设计与日益变迁的社会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他们的有些设计,就不得不在后世的实践中予以不同程度地变更和修正。因此,我们在看到宋儒们为重建宋代以来新的家族制度所做出的贡献及其深远影响的同时,对于中国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这一系列变迁,也是不可不认真予以探究的。
近一个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宋明以来中国民间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形成,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明以来的家族制度,是先秦时期奴隶制与宗法制(或村社制)的残余;二是认为宋明以来的家族制度,基本上是由宋代士人与理学家们重新建构起来的。我们通过对宋儒们所倡导和实践的民间家族制度的过程分析,可以看到以上的两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都是值得重新思考的。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对于宋明以来民间家族制度及其组织所产生的长远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一种文化以至文明的传承,绝不是什么必然消亡的“残余”。而宋儒们对民间家族的重新设计与建构,却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复古性质的承继过程,并非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正是这种具有复古性质的承继过程,又使得宋儒们的最初设计,并不十分适用于宋明以来的民间社会实际。于是,经过其后儒者、士人以至民间的不断改进调试,到了明代中后期,中国民间的家族制度,才最终基本定型并且沿袭了下来。当然,随着近现代特别是当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这种家族制度还将有所变化、有所演进,这是一种必然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是中华文化以至文明的传承趋势,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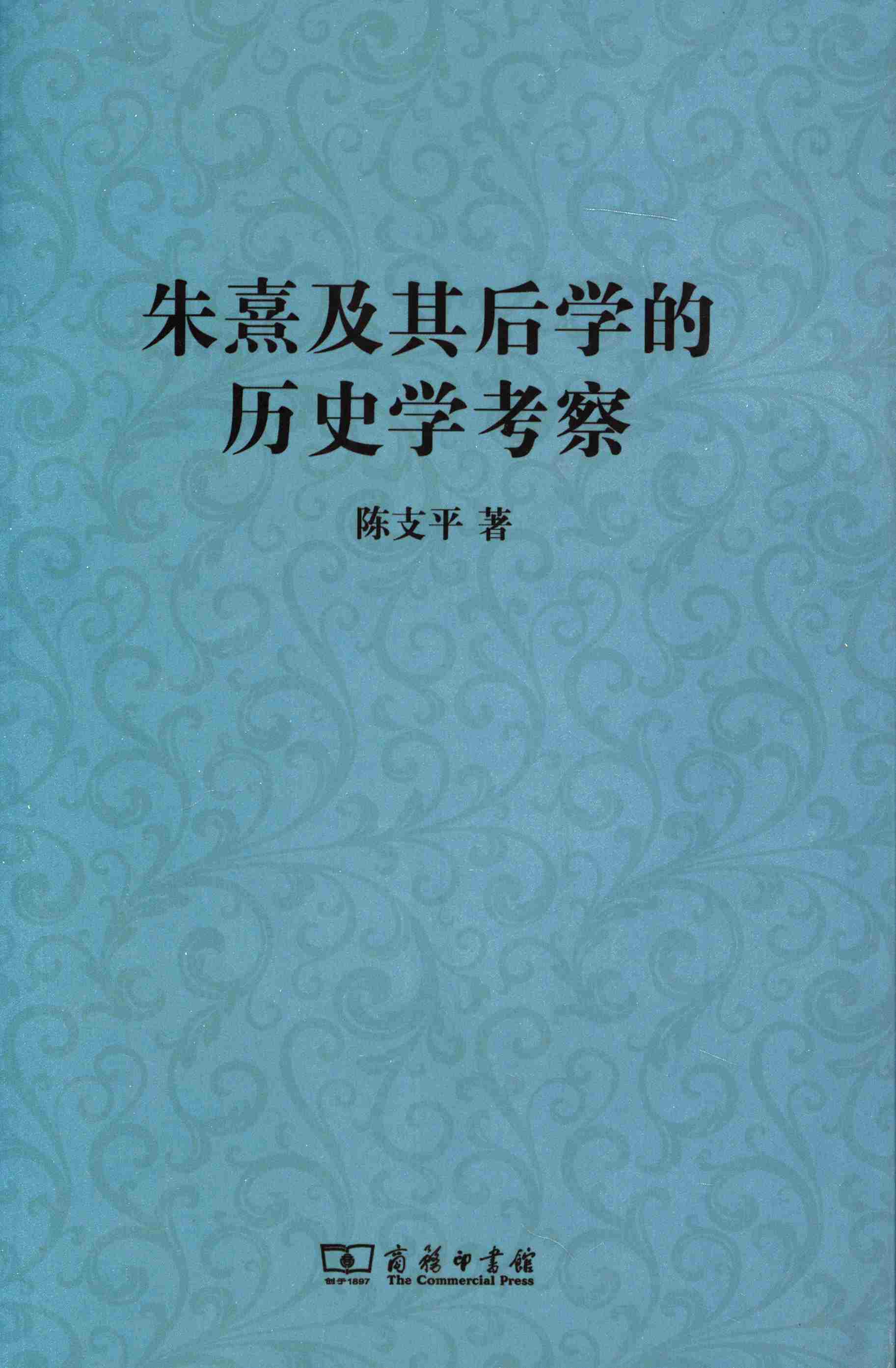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本书主要考察朱熹及其后学们究竟为当时的社会做了些什么,以及这些事情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朱熹和他的学生们,有从政的经历,也有当平民的经历,他们在所谓的“行”的实践上,表现更多。鉴于此,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朱子学,突破了从哲学视角研究朱子学的传统。与从哲学视角注重“想什么”不同,历史学更注重“做什么”。作者以自己所擅长的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对朱熹及其后学在这两个领域的所作所为,做出了尝试性的分析。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