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鹅湖之会与朱熹、陆九渊的异同
| 内容出处: | 《朱熹:孔子之后第一儒》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753 |
| 颗粒名称: | 第九章 鹅湖之会与朱熹、陆九渊的异同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0 |
| 页码: | 104-113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鹅湖之会与朱熹、陆九渊的异同包括互不相下的激辩、“性即理”与“心即理”、不尽余波情况。 |
| 关键词: | 朱熹 陆九渊 鹅湖之会 |
内容
一、互不相下的激辩
鹅湖之会前,陆九龄对陆九渊说:这次集会,为的是讨论学术异同,我们兄弟二人先自不同,怎么能期望鹅湖时大家相同呢?于是,二人反复辩论,至晚才罢,陆九龄表示赞成九渊的观点。第二天早晨,九龄在九渊面前朗读刚写好的诗: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在诗中,陆九龄认为儿童天生地知道爱,长大了天生地知道敬,历代圣贤相传的就是这种爱敬之心,可以不学而知,没有必要到儒家著作的注解中去寻求所谓“精微”之处,那条路走不通。陆九渊认为诗写得很好,但第二句微有不妥。到鹅湖后,陆九龄首先朗诵他的诗,才读了四句,朱熹就完全明白,对吕祖谦说:九龄上了九渊的船了!接着,便和九龄辩论起来。陆九渊说:我在路上写了一首和家兄的诗: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陆九渊集·鹅湖和教授兄韵》)
陆九渊同样认为,人天赋地具有伦理观念,到了墟墓之间会自然产生悲哀之感,进了宗庙会自然产生钦敬之情,那是人人具有,永不消磨的。因此,自己的一套“易简工夫”必将长久光大,而朱熹的“支离事业”只能沉浮一时。听到这里,朱熹的脸色突然变了,但陆九渊不管,继续往下读:“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自然,朱熹老大不高兴。紧接着,又辩论了几天。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氏兄弟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并大谈了一通收敛精神,使之在内而不在外的重要,还想了一个“尧舜之前何书可读”的问题准备难倒朱熹,为陆九龄劝阻。最后,双方互不相下,终于不合而散。
二、“性即理”与“心即理”
鹅湖之会上,朱陆争论主要集中在认识论上,但也表现了他们在世界本原论、人性论、伦理观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
朱熹把独立于人的知觉之外的理(客观精神)作为世界本原,陆九渊则把人的知觉(心)作为世界本原。基于此,朱熹主张“性即理”,陆九渊主张“心即理”。
“性即理”,意即人性是从天上降到人心里来的理。从这里出发,朱熹严格地区别了心和性两个概念,认为心指人的感觉、欲望和动作,性指人的伦理观念,两者不是一回事。他说:“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朱子语类》卷五)他曾将二者比喻为饺子皮和饺子馅的关系,说是“心将性做馅子模样”,因此,只能说“心具众理”,而不能说“心即理”。例如人的视、听、言、动,这是心的作用,但是视、听、言、动必须合于礼才是理。他说:“心只是该得这理,佛氏原不曾识得这理一节,便认知觉运动做性。”(《朱子语类》卷一二六)
禅宗认为佛性就体现在人体各器官的“作用”(功能)上。《菩提达摩传》载,南天竺国王曾向波罗提询问:“性在何处?”波罗提答曰:“性在作用。”并说一偈:“在胎为身,处世为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偏现具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朱熹上文所指斥的“认知觉、运动为性”,即指禅宗的有关思想。朱熹认为必须将人的知觉、动作和关于知觉、动作的伦理规范,即心与性二者严格区分开来。如果混为一谈,必将承认人的活动无时不是理、无处不是理,这就要导致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放松和废弃。他说:“若便以日用之间,举止动作便是道,则无所适而非道,无时而非道。然则君子何用戒慎恐惧,何用更学道为?”(《朱子语类》卷六二)
人具有视、听、言、动的能力,同时,人又为自己制订了关于视、听、言、动的种种伦理规范。前者是人的生理本能,后者是一定阶层、集团或派别的社会利益的反映。朱熹区分二者是正确的,但是他把后者看作是从天上降到人心里来的,这就错了。
“心即理”,说的是人的知觉、动作就是理。陆九渊认为,人的知觉和人的伦理观念本质上是相同的。他说:“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悌,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朱子语录》,《陆九渊集》卷三四)。耳聪目明,属于听觉和视觉,孝与悌则属于伦理观念。在他看来,听觉和视觉是人所固有的,孝悌等伦理观念也是人所固有的。
前文指出,朱熹主张区分人的生理本能和人的伦理规范,陆九渊却将二者混淆起来,从理论思维的发展看,这是一种退步;从实际的社会作用看,这种混淆有时倒有一点积极意义。这就是易于流为“认欲为理”,从而放松和废弃儒学道德修养,为异端思想的滋生提供条件。虽然陆九渊并不是一个不重视儒学道德修养的人,只是对“存诚持敬”的修养方法不满,但是他的学说流行的结果,确实出现过“猖狂妄行”的情况。这一点,到明末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是陆九渊始料所未及的。
由于对儒学伦理的认识不一,体认的途径和方法也就因之而异。朱熹认为在和气的结合过程中,作为世界本原的理分化为在物之理和在心之理。因此,既可以向外通过物去体认,也可以向内在自身探求,这就产生了向外用功和向内用功两条途径。陆九渊则认为既然理是人心所固有的,充塞宇宙之理不过是人心之理的扩张,因此,自然“不必他求”,没有必要去向外体认什么在物之理,直接向自己的心中去寻找就是了。他认为,朱熹的向外用功完全多余。通过穷万物之理以发扬天赋于人心之理,在陆九渊看来,这是绕圈子,走贫道,叫作“支”。而且,天下万物不胜其烦,如何一一研究得?即使研究得了,又怎能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在陆九渊看来,这就叫作“离”。他说:“勤学之士,反为之迷惑,自为支离之说以自禁缠。……岂不重可怜哉!”(《与曾宅之书》,《陆九渊集》卷一)
在体认儒学伦理的方法上,朱熹主张“零零碎碎凑合将来”,即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从体认分殊在万事万物上的理做起,铢积寸累,一步一步,最后,“一旦豁然贯通”,体认出派生万事万物的总的最高的理,完成个人的道德修养。陆九渊则主张“先立乎其大者”(《朱子语录》,《陆九渊集》卷三四),即首先体认人心固有之理,明确地在思想上确立儒学伦理的基本原则,不必在细微之处零零碎碎下工夫。他说:“有本自然有末”,只要“本”树立起来了,那就会“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不然的话,舍本逐末,舍大就小,问题就大了(《朱子语录》卷四,《陆九渊集》卷三五)。
朱熹认为圣贤们的著作乃是理的完备体现,所以他强调“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且主张读书时要在“求其义”狠下工夫。例如穷究孝之理时就要去研讨《论语》中许多论孝的地方,要在文字和注解上“格”。所以,他主张“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朱子语类》卷一八),即多读、多讨论,谨慎地思考,细致地分辨,经过广泛的观览之后达到在思想上确立儒学伦理基本原则的目的。陆九渊则不那么强调读书,不赞成“苦思力索”,孜孜于章句、传注之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先发明人之本心”,当人心固有之理被体认到了的时候,“六经皆我注脚”(《朱子语录》,《陆九渊集》卷三四),不过是对人心固有之理的注解罢了。在陆九渊看来,如果思想上还没有确立儒学伦理的基本原则,就去“泛观博览”,什么书都读,那就会读出毛病来。他说:“田地不清洁,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假寇兵,资盗粮。”(《朱子语录》,《陆九渊集》卷三五)等于给了贼寇以兵力和粮食的援助。
陆九渊强调“六经皆我注脚”,目的在抬高“我”心固有的儒学伦理的地位,以之作为审察一切的最高标准。他说:“使书而皆合于理,虽非圣人之经,尽取之可也。”“如皆不合于理,则虽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而取之也,又可必信之乎?”(《取二三策而已矣》,《陆九渊集》卷三二)这就是说:只要合于理,即使不是圣人之书,也可以全盘吸收;如果不合于理,即使是圣人之书,也不能相信。他反对“师古”,主张“择其当于理者而师之”“惟理之是从”(《策问》,《陆九渊集》卷二四)。这些地方,“理”的地位是抬高了,但是“六经”等儒学经典的地位却相对降低了。
陆九渊主张“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又主张“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陆九渊集》卷三五),即强调的是自己,儒学经典和圣贤权威的地位就更低了。所以朱熹批评他“如今都教坏了后生,个个不肯去读书”,又批评他“好为呵佛骂祖之说”“个个学得不逊”(《朱子语类》卷一〇四、一二四)。其实,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心学在强调“我”心固有之“理”的同时,也就强调了“我”;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理”的内涵就有可能发生变化,“我”的个人之见就可能代替儒学规范,这样,异端思想就可能脱颖而出。这不是陆九渊所愿意看到的,却是他的理论有可能产生的后果。
朱熹主张克人欲,存天理,通过省、察、克、治、主敬等办法扑灭思想中一切违背儒学伦理的念头,陆九渊则反对天理、人欲的区分,主张从正面去发扬人心固有之理。他说:“主于道,则欲消。”(《朱子语录》,《陆九渊集》卷三五)陆九渊的这一思想在晚明时发展为泰州学派的“制欲非体仁论”。这一派认为只要体认到了天赋于人心之“仁”,一切欲念就无从产生。
朱熹反对陆九渊的上述修养方法,认为这是“禅家之说”;陆九渊则自称他的方法简便易行,连愚夫愚妇们也能掌握。
三、不尽余波
朱熹没有能说服陆九渊,但是,却说服了陆九龄。后来,九龄曾致函朱熹,自悔在鹅湖时所持的见解。淳熙五年(1178),朱熹在江西铅山待命,九龄亲到当地探访。二人谈得颇为投机。朱熹对九龄说:“本人旧时持论亦好高,近来渐渐移近下,渐渐着实也。”朱熹并作诗赠九龄,题为《和鹅湖子寿韵》,诗云:“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陆九龄去世后,陆九渊于淳熙八年(1181)到南康,请朱熹为九龄写墓志铭。朱熹邀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他的讲题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两句。他慷慨激昂地说:“今人读书便是为利。如考中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据说听众中有感动得流泪的。朱熹对陆九渊的演说非常满意,认为“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特别请他笔录下来。这次见面,朱熹觉得陆九渊不像鹅湖之会时那样盛气凌人了,但是在许多见解上,二人仍然不合。
淳熙十四年(1 187)至淳熙十六年(1 189)期间,朱熹和陆九渊及其兄陆九韶(子美)之间还曾以通信方式展开过关于“无极”“太极”问题的辩论。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有“无极而太极”一语。无极表示最高、最根本的范畴,它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太极表示阴阳未分之前的混沌元气。“无极而太极”,是说从无极中产生太极。这一思想,实际上是《老子》一书中“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翻版。
陆九渊、陆九韶反对无极这一范畴。陆九渊说:“‘极’字就是‘理’字,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岂可言无?”他认为讲太极就够了,太极上面再加上无极,乃是“牀上之牀”,这是“老氏之学”,“老氏之学不正”,是要不得的。朱熹则认为:“无极而太极”,说的是无形而有理。无极就是无形,说明太极的特征。他并说:无极是周敦颐的真知灼见,他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
这次辩论还涉及了对于“阴阳”的认识等问题。陆九渊认为阴阳是道,是形而上的;朱熹则认为阴阳是器,是形而下的,只有支配阴阳的理才是形而上的。
辩论得很热烈,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陆九渊揭露朱熹哲学的一些常用语,如“太极真体”“不传之秘”“无物之前”“阴阳之外”“不属有无”“不落方体”等都来源于禅宗。他问朱熹:“莫是曾学禅宗,所得如此?”(《与朱元晦书》二,《陆九渊集》卷二)朱熹则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揭露陆九渊“心即理”的说法来源于禅宗的“作用见性”说,说是:“往往只是于禅学中认得个昭昭灵灵能作用底便谓此是太极。”(《答陆子静》,《朱子文集》卷三六)其实,心学也罢,理学也罢,都和佛教的禅宗有不解之缘。
明末的黄宗羲(1610—1695)说:“(朱、陆)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八)因此,尽管二人有时攻讦得很激烈,但实际上,他们的思想却是彼此渗透、互相吸收的。鹅湖之会后,陆九渊就表示,人必须读书、讲学、讨论,朱熹也承认自己确有“支离之病”,花在讨论、讲学上精力多,而在最紧要的道德修养上却“多不得力”。
淳熙十一年(1184)至淳熙十三年(1186)之间,正当朱熹和陈亮展开“义利、王霸”之辩时,朱熹在《答陈肤仲书》中说:陆学固然有的地方似禅,但比“婺州朋友”们专事耳闻目见,不在自己身心上用功要好得多。朱熹这里所指的“婺州朋友”,就是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他要学者们暂时放下朱陆异同之争,尽量吸收陆学的长处。
什么是陆九渊学派的长处呢?据朱熹说,这就是“尊德性”“多持守可观”。他说:“比来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可轻相诋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姑勉力于吾之所急”(《答诸葛诚之书》,《朱子文集》卷五四)。意思很清楚,为了反对事功学派,他要和陆九渊站在同一阵线。
鹅湖之会前,陆九龄对陆九渊说:这次集会,为的是讨论学术异同,我们兄弟二人先自不同,怎么能期望鹅湖时大家相同呢?于是,二人反复辩论,至晚才罢,陆九龄表示赞成九渊的观点。第二天早晨,九龄在九渊面前朗读刚写好的诗: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在诗中,陆九龄认为儿童天生地知道爱,长大了天生地知道敬,历代圣贤相传的就是这种爱敬之心,可以不学而知,没有必要到儒家著作的注解中去寻求所谓“精微”之处,那条路走不通。陆九渊认为诗写得很好,但第二句微有不妥。到鹅湖后,陆九龄首先朗诵他的诗,才读了四句,朱熹就完全明白,对吕祖谦说:九龄上了九渊的船了!接着,便和九龄辩论起来。陆九渊说:我在路上写了一首和家兄的诗: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陆九渊集·鹅湖和教授兄韵》)
陆九渊同样认为,人天赋地具有伦理观念,到了墟墓之间会自然产生悲哀之感,进了宗庙会自然产生钦敬之情,那是人人具有,永不消磨的。因此,自己的一套“易简工夫”必将长久光大,而朱熹的“支离事业”只能沉浮一时。听到这里,朱熹的脸色突然变了,但陆九渊不管,继续往下读:“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自然,朱熹老大不高兴。紧接着,又辩论了几天。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氏兄弟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并大谈了一通收敛精神,使之在内而不在外的重要,还想了一个“尧舜之前何书可读”的问题准备难倒朱熹,为陆九龄劝阻。最后,双方互不相下,终于不合而散。
二、“性即理”与“心即理”
鹅湖之会上,朱陆争论主要集中在认识论上,但也表现了他们在世界本原论、人性论、伦理观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
朱熹把独立于人的知觉之外的理(客观精神)作为世界本原,陆九渊则把人的知觉(心)作为世界本原。基于此,朱熹主张“性即理”,陆九渊主张“心即理”。
“性即理”,意即人性是从天上降到人心里来的理。从这里出发,朱熹严格地区别了心和性两个概念,认为心指人的感觉、欲望和动作,性指人的伦理观念,两者不是一回事。他说:“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朱子语类》卷五)他曾将二者比喻为饺子皮和饺子馅的关系,说是“心将性做馅子模样”,因此,只能说“心具众理”,而不能说“心即理”。例如人的视、听、言、动,这是心的作用,但是视、听、言、动必须合于礼才是理。他说:“心只是该得这理,佛氏原不曾识得这理一节,便认知觉运动做性。”(《朱子语类》卷一二六)
禅宗认为佛性就体现在人体各器官的“作用”(功能)上。《菩提达摩传》载,南天竺国王曾向波罗提询问:“性在何处?”波罗提答曰:“性在作用。”并说一偈:“在胎为身,处世为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偏现具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朱熹上文所指斥的“认知觉、运动为性”,即指禅宗的有关思想。朱熹认为必须将人的知觉、动作和关于知觉、动作的伦理规范,即心与性二者严格区分开来。如果混为一谈,必将承认人的活动无时不是理、无处不是理,这就要导致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放松和废弃。他说:“若便以日用之间,举止动作便是道,则无所适而非道,无时而非道。然则君子何用戒慎恐惧,何用更学道为?”(《朱子语类》卷六二)
人具有视、听、言、动的能力,同时,人又为自己制订了关于视、听、言、动的种种伦理规范。前者是人的生理本能,后者是一定阶层、集团或派别的社会利益的反映。朱熹区分二者是正确的,但是他把后者看作是从天上降到人心里来的,这就错了。
“心即理”,说的是人的知觉、动作就是理。陆九渊认为,人的知觉和人的伦理观念本质上是相同的。他说:“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悌,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朱子语录》,《陆九渊集》卷三四)。耳聪目明,属于听觉和视觉,孝与悌则属于伦理观念。在他看来,听觉和视觉是人所固有的,孝悌等伦理观念也是人所固有的。
前文指出,朱熹主张区分人的生理本能和人的伦理规范,陆九渊却将二者混淆起来,从理论思维的发展看,这是一种退步;从实际的社会作用看,这种混淆有时倒有一点积极意义。这就是易于流为“认欲为理”,从而放松和废弃儒学道德修养,为异端思想的滋生提供条件。虽然陆九渊并不是一个不重视儒学道德修养的人,只是对“存诚持敬”的修养方法不满,但是他的学说流行的结果,确实出现过“猖狂妄行”的情况。这一点,到明末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是陆九渊始料所未及的。
由于对儒学伦理的认识不一,体认的途径和方法也就因之而异。朱熹认为在和气的结合过程中,作为世界本原的理分化为在物之理和在心之理。因此,既可以向外通过物去体认,也可以向内在自身探求,这就产生了向外用功和向内用功两条途径。陆九渊则认为既然理是人心所固有的,充塞宇宙之理不过是人心之理的扩张,因此,自然“不必他求”,没有必要去向外体认什么在物之理,直接向自己的心中去寻找就是了。他认为,朱熹的向外用功完全多余。通过穷万物之理以发扬天赋于人心之理,在陆九渊看来,这是绕圈子,走贫道,叫作“支”。而且,天下万物不胜其烦,如何一一研究得?即使研究得了,又怎能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在陆九渊看来,这就叫作“离”。他说:“勤学之士,反为之迷惑,自为支离之说以自禁缠。……岂不重可怜哉!”(《与曾宅之书》,《陆九渊集》卷一)
在体认儒学伦理的方法上,朱熹主张“零零碎碎凑合将来”,即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从体认分殊在万事万物上的理做起,铢积寸累,一步一步,最后,“一旦豁然贯通”,体认出派生万事万物的总的最高的理,完成个人的道德修养。陆九渊则主张“先立乎其大者”(《朱子语录》,《陆九渊集》卷三四),即首先体认人心固有之理,明确地在思想上确立儒学伦理的基本原则,不必在细微之处零零碎碎下工夫。他说:“有本自然有末”,只要“本”树立起来了,那就会“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不然的话,舍本逐末,舍大就小,问题就大了(《朱子语录》卷四,《陆九渊集》卷三五)。
朱熹认为圣贤们的著作乃是理的完备体现,所以他强调“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且主张读书时要在“求其义”狠下工夫。例如穷究孝之理时就要去研讨《论语》中许多论孝的地方,要在文字和注解上“格”。所以,他主张“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朱子语类》卷一八),即多读、多讨论,谨慎地思考,细致地分辨,经过广泛的观览之后达到在思想上确立儒学伦理基本原则的目的。陆九渊则不那么强调读书,不赞成“苦思力索”,孜孜于章句、传注之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先发明人之本心”,当人心固有之理被体认到了的时候,“六经皆我注脚”(《朱子语录》,《陆九渊集》卷三四),不过是对人心固有之理的注解罢了。在陆九渊看来,如果思想上还没有确立儒学伦理的基本原则,就去“泛观博览”,什么书都读,那就会读出毛病来。他说:“田地不清洁,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假寇兵,资盗粮。”(《朱子语录》,《陆九渊集》卷三五)等于给了贼寇以兵力和粮食的援助。
陆九渊强调“六经皆我注脚”,目的在抬高“我”心固有的儒学伦理的地位,以之作为审察一切的最高标准。他说:“使书而皆合于理,虽非圣人之经,尽取之可也。”“如皆不合于理,则虽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而取之也,又可必信之乎?”(《取二三策而已矣》,《陆九渊集》卷三二)这就是说:只要合于理,即使不是圣人之书,也可以全盘吸收;如果不合于理,即使是圣人之书,也不能相信。他反对“师古”,主张“择其当于理者而师之”“惟理之是从”(《策问》,《陆九渊集》卷二四)。这些地方,“理”的地位是抬高了,但是“六经”等儒学经典的地位却相对降低了。
陆九渊主张“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又主张“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陆九渊集》卷三五),即强调的是自己,儒学经典和圣贤权威的地位就更低了。所以朱熹批评他“如今都教坏了后生,个个不肯去读书”,又批评他“好为呵佛骂祖之说”“个个学得不逊”(《朱子语类》卷一〇四、一二四)。其实,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心学在强调“我”心固有之“理”的同时,也就强调了“我”;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理”的内涵就有可能发生变化,“我”的个人之见就可能代替儒学规范,这样,异端思想就可能脱颖而出。这不是陆九渊所愿意看到的,却是他的理论有可能产生的后果。
朱熹主张克人欲,存天理,通过省、察、克、治、主敬等办法扑灭思想中一切违背儒学伦理的念头,陆九渊则反对天理、人欲的区分,主张从正面去发扬人心固有之理。他说:“主于道,则欲消。”(《朱子语录》,《陆九渊集》卷三五)陆九渊的这一思想在晚明时发展为泰州学派的“制欲非体仁论”。这一派认为只要体认到了天赋于人心之“仁”,一切欲念就无从产生。
朱熹反对陆九渊的上述修养方法,认为这是“禅家之说”;陆九渊则自称他的方法简便易行,连愚夫愚妇们也能掌握。
三、不尽余波
朱熹没有能说服陆九渊,但是,却说服了陆九龄。后来,九龄曾致函朱熹,自悔在鹅湖时所持的见解。淳熙五年(1178),朱熹在江西铅山待命,九龄亲到当地探访。二人谈得颇为投机。朱熹对九龄说:“本人旧时持论亦好高,近来渐渐移近下,渐渐着实也。”朱熹并作诗赠九龄,题为《和鹅湖子寿韵》,诗云:“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陆九龄去世后,陆九渊于淳熙八年(1181)到南康,请朱熹为九龄写墓志铭。朱熹邀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他的讲题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两句。他慷慨激昂地说:“今人读书便是为利。如考中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据说听众中有感动得流泪的。朱熹对陆九渊的演说非常满意,认为“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特别请他笔录下来。这次见面,朱熹觉得陆九渊不像鹅湖之会时那样盛气凌人了,但是在许多见解上,二人仍然不合。
淳熙十四年(1 187)至淳熙十六年(1 189)期间,朱熹和陆九渊及其兄陆九韶(子美)之间还曾以通信方式展开过关于“无极”“太极”问题的辩论。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有“无极而太极”一语。无极表示最高、最根本的范畴,它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太极表示阴阳未分之前的混沌元气。“无极而太极”,是说从无极中产生太极。这一思想,实际上是《老子》一书中“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翻版。
陆九渊、陆九韶反对无极这一范畴。陆九渊说:“‘极’字就是‘理’字,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岂可言无?”他认为讲太极就够了,太极上面再加上无极,乃是“牀上之牀”,这是“老氏之学”,“老氏之学不正”,是要不得的。朱熹则认为:“无极而太极”,说的是无形而有理。无极就是无形,说明太极的特征。他并说:无极是周敦颐的真知灼见,他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
这次辩论还涉及了对于“阴阳”的认识等问题。陆九渊认为阴阳是道,是形而上的;朱熹则认为阴阳是器,是形而下的,只有支配阴阳的理才是形而上的。
辩论得很热烈,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陆九渊揭露朱熹哲学的一些常用语,如“太极真体”“不传之秘”“无物之前”“阴阳之外”“不属有无”“不落方体”等都来源于禅宗。他问朱熹:“莫是曾学禅宗,所得如此?”(《与朱元晦书》二,《陆九渊集》卷二)朱熹则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揭露陆九渊“心即理”的说法来源于禅宗的“作用见性”说,说是:“往往只是于禅学中认得个昭昭灵灵能作用底便谓此是太极。”(《答陆子静》,《朱子文集》卷三六)其实,心学也罢,理学也罢,都和佛教的禅宗有不解之缘。
明末的黄宗羲(1610—1695)说:“(朱、陆)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八)因此,尽管二人有时攻讦得很激烈,但实际上,他们的思想却是彼此渗透、互相吸收的。鹅湖之会后,陆九渊就表示,人必须读书、讲学、讨论,朱熹也承认自己确有“支离之病”,花在讨论、讲学上精力多,而在最紧要的道德修养上却“多不得力”。
淳熙十一年(1184)至淳熙十三年(1186)之间,正当朱熹和陈亮展开“义利、王霸”之辩时,朱熹在《答陈肤仲书》中说:陆学固然有的地方似禅,但比“婺州朋友”们专事耳闻目见,不在自己身心上用功要好得多。朱熹这里所指的“婺州朋友”,就是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他要学者们暂时放下朱陆异同之争,尽量吸收陆学的长处。
什么是陆九渊学派的长处呢?据朱熹说,这就是“尊德性”“多持守可观”。他说:“比来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可轻相诋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姑勉力于吾之所急”(《答诸葛诚之书》,《朱子文集》卷五四)。意思很清楚,为了反对事功学派,他要和陆九渊站在同一阵线。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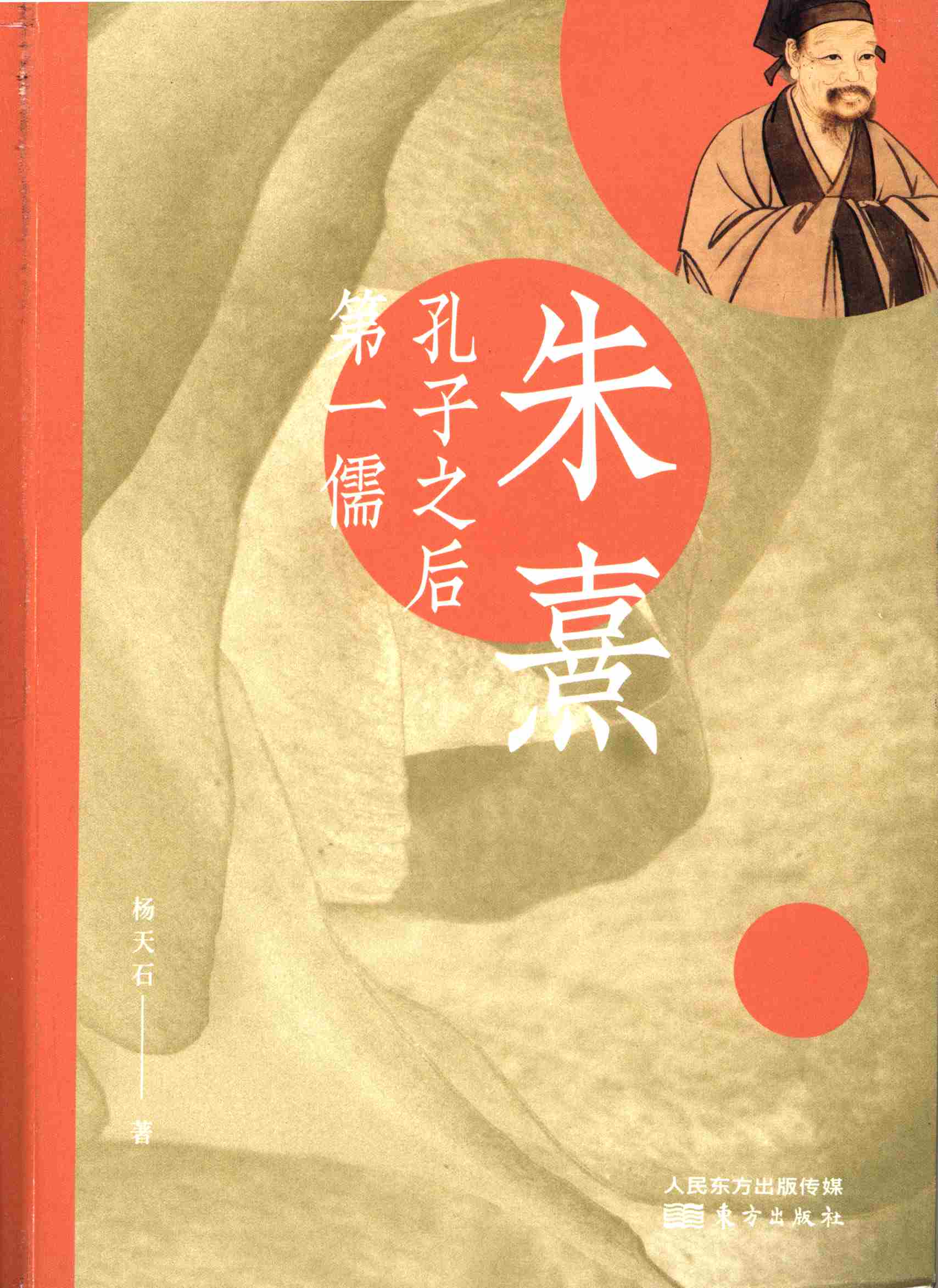
《朱熹:孔子之后第一儒》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本文讲述了以理制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道德要求——宋明儒学关于“理”“欲”关系论述的现代启示、改铸儒学的新需要、生于忧患,长于坎坷的大思想家、社会政治思想、理为“天地万物之根”的世界本原论、“天命”与“气质”相结合的双重人性论、唤醒天赋观念的“格物致知”论、克人欲、存天理 、“一中又自有对”的辩证法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