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荣辱观刍议
| 内容出处: | 《朱子与朱门后学丛论》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611 |
| 颗粒名称: | 朱熹荣辱观刍议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2 |
| 页码: | 63-74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中国思想史中儒家荣辱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强调了教育在传播儒家荣辱观中的重要作用。 |
| 关键词: | 儒家 荣辱观 教育理念 |
内容
一、从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儒家的荣辱观
在我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儒学思想家均无不重视荣辱问题,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荣辱观。而在儒家荣辱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荣辱观的教育理念问题。
春秋时期,管子把知耻列为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四大支柱之一,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维,形声字。从糸(mì),隹(zhuī)声,“糸”指绳索、绳线。本义就是:作为锥形空间架构的绳线组。引申义为:骨干绳线;主绳。再引申义:拴系。说明:古代的车舆的圆盖是对北极天空的模拟。车盖是依靠四根绳索与车舆四角相牵挂的,这四根绳索叫做“四维”。古代的车是对天地的模拟。即车舆的伞形盖象征天,方形的车舆象征大地,车盖的中心柱子象征“天地柱”,马儿象征天地旋转的驱动力。在这样的认识下,古人想象大地的四角也有四根无形的大绳被系在北极点上,这四根无形的大绳也叫作“四维”。
也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于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在这里是引导的意思,“礼”是人际交往的行为准则,社会和谐安定与否,道德理念的引导和行为准则的规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这整段话的意思是,如果仅仅用行政命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约束百姓,他们虽然可以因惧怕惩罚而避免犯罪,但却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从其效果来说,这是被动的;而用道德教化来治理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就能使他们懂得耻辱而不会触犯刑律,从其效果来说,这是主动的。因此,孔子进而提出了“行己有耻”(《论语·子路》)、“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等一系列道德自律的主张,其用意在于使每一个人都能明白,行事立身要有是非观念和羞耻之心,要远离耻辱,不要去做那些让人感到耻辱的事。也就是说,要使人不犯罪、不做坏事,仅仅停留在惧怕法律的惩罚上而不敢为之是不够的。所以,要努力追求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具备做人应有的知耻明辱的良知而耻于为之,远离犯罪,这是孔子荣辱观的主要目标。但是,这种知耻明辱的良知不可能与生俱来,“有耻且格”的效果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必须通过统治者的推行教育,通过教育理念和舆论的引导(道之以德)来实现。这既是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也是孔子作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其所建构的荣辱观中,蕴藏在其中的通过推行教育来传播儒家荣辱观的思想。
继孔子之后,孟子最早提出“荣”“辱”这一对应概念。他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他不仅从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识荣辱的重要性,而且对孔子的识荣辱必须与道德教育紧密结合的思想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公孙丑上》)朱熹指出,所谓善政,是指以法度禁令“制其外”;善教,是以道德齐礼“格其心”。不难看出,孟子已将孔子思想中所深藏不露的通过教育来传播儒家的荣辱观的思想加以进一步的提取和明确,并分别从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和改善道德教育两个致思向度上加以引申和发挥。在《孟子》一书中,“耻”这一概念往往又与“辱”“羞”等交替使用。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不知羞耻之人,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在儒家学者所主张的诸多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中,与荣辱观教育关系比较密切的有孔子所说的“内省”。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见到别人好的行为和品质,就要虚心向他学习;见到不好的品行,就要联系自己,加以反省,并以此为戒,以期努力做到“内省”而不疚,即无道德缺陷。曾子将此方法发展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
内省的方法,是儒家学者极为重视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其含义是内心的自我反省和对自己日常行为的道德审视。这种自我反省与审视,与儒家的荣辱观有着天然的联系。如孟子主张以仁为荣,以不仁为辱,既是对孔子的仁学思想的一种发展,又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儒家荣辱观。而在《孟子》一书中,“耻”这一概念往往又与“辱”“羞”等交替使用。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耻辱羞恶之心,是孟子仁之四端之一,朱熹将其与内省、审察联系到了一起。他说:“要知天之与我,只如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辞逊之心,非人也。’今人非无恻隐、羞恶、是非、辞逊发见处,只是不省察罢了。……只为从前不省察了,此端才见,又被物欲汩没了,所以秉彝不可磨灭处虽在,更终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①这种羞恶之心,孟子称为是“义之端”,也就是人在采取某一行动前,选择使用道德而避免非道德行为的一种发自人之本能良知的萌芽状态;但这种“萌芽”,只是一种最初的“本然”,故往往容易被外界的物欲所“汩没”;而内省或省察,则是对这种被物欲所汩没的一种警醒和提防。由于社会上物欲无所不在,故这种内省就须不间断地时刻进行。如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朱熹所说的“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②。
在道德教育阶段论中,儒家学者主张荣辱观的教育应从幼儿开始。从理论上说,实施教育者最好是从事教育的专门人才,但由于人类现实的家庭婚姻制度,使家长不可避免地成为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的传说,是儒家学者重视童蒙教育,坚持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应该从儿童抓起,应从家庭起步的理念的一种体现。
在理论上提出德育应从“能食能言”的婴幼儿开始实施的,是北宋理学家程颐。他说:“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说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私意偏好生于内,众口辨言铄于外,欲其纯完,不可得也。”①意思是说,婴幼儿时期,知识和思想都是一片空白,谈不上有何主见。这时,就应当以儒家先圣的格言来时时影响和教育他们,即便他们此时尚未领会其意,但只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熏陶,久而久之,就会接受这些思想,就会成为好像是其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此时,即便有错误的东西来诱惑他们,也会不受影响。如果在童蒙时不对小孩进行道德启蒙,等到他们长大后,那些私欲偏好就会在内心滋长,就会受到外界各种错误言行的误导,此时,再要求他们按照纯正完美的道德标准来行事,那就很难了。程颐又进一步将这种童蒙教育方法概括为:“教人者,养其善心,则恶自消。”②“养正于蒙,学之至善也。”③用良好的、健康的教育方法和道德理念,使儿童从小就能构筑起一道知耻明辱、存善去恶的道德防线,来抵御外界各种不良思想的负面影响。否则,“任其自为,听其不为,则中人以下,自弃自暴者众矣。圣人所以贵于立教也。”④“圣人所以立教”,指的是儒学先师的教育目的,这就又将知耻明辱、养善去恶的童蒙教育与儒家的教育目的论联系到了一起。
二、朱熹的荣辱观
朱熹作为我国传统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荣辱观则集中了儒家先圣先贤的精粹。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律人律己,不辱其身
朱熹的荣辱观,不仅限于理论层面上,更重要的是落实在道德践履之中。他认为,这不仅是历代儒家学者用以律己,同时也是用以律人的主要道德标准。他继承了孔子“行己有耻”(《论语·子路》)的思想,进一步提出“行已有耻,则不辱其身”①的观点。行己有耻,这是针对个体而言,是律己;“士人要先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有何用?”②这是律人。且在行文中,所表达的以道德论人品,即德与才(能文)相比,德在才先的涵义十分明确。
朱熹认为,人有了知耻之心,就会远离耻辱,就不会去做那些为人所不齿的事,就能“不辱其身”。为何有了知耻之心,就会远离耻辱呢?朱熹解释说:“知耻是由内心以生,闻过是得之于外。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故耻为重。”③知耻是发自内心的道德理念,是抵御外界各种恶行的道德防线;正因为内心知耻,即使有了过失而不觉,也能闻过而改。故朱熹认为,与“得之于外”的“闻过”相比,知耻更重要。他在建阳考亭书院讲学之时,对他的学生辅广等人强调说:“人须是有廉耻。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④漳州府学教授张某颇具文才,但却品行不端,朱熹将其开除,并训斥为之说情者曰:“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责任不为不重,合当自行规矩。而今却容许多无行之人、争讼职事人在学,枉请官钱,都不成学校!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①为了给士子树立好的榜样,朱熹延请了郡士黄樵、陈淳、徐寓等八人入郡学教授诸生,并发布《漳州延郡士入学牒》。牒文对此八人的学问和操守一一作出评价,以有别于无“廉退之节”的败类,并希望凡学之子弟,从此有“良师畏友之益,庶几理义开明,德业成就”②。
所谓廉退,是廉介与恬退之意。与朱熹同时的著名诗人、学者尤袤驳斥当时朝中有人攻击朱熹的学说为“道学”时,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高度评价为,是将“临财不苟得”视为廉介,“安贫守分”视为恬退,“择言顾行”视为践履,“行己有耻”视为名节③的“贤人君子”。朱熹在外地担任地方官时,针对其时的一些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腐败现象,颇有感触地说:“富贵易得,名节难保,此虽浅近之言,然岂亦可忽哉!”④这就将孔子的行己有耻的荣辱观发展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数百年的气节观。这种气节观的主要表现就是“仰不愧,俯不祚”“常以‘志士不忘在沟壑’为念,则是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⑤他在漳州等地学校所推行的“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表明朱熹是把明荣辱、识廉退作为学校人格和道德教育的首要目标;而为诸生树立可以效仿的明荣辱、识廉退的正人端士形象,则是朱熹将其荣辱观具体落实到学校教学中的典型事例之一。
(二)全善去恶,求荣去辱
在解释孟子提出的“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时,朱熹认为“好荣恶辱,人之常情。然徒恶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⑥。意思是说,仅停留在好荣恶辱这一人之常情的水平上,是远远不够的。“徒恶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就仍然不能免于耻辱。因为知荣辱仅仅是一种初步的道德认知,是孟子所说的“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端是端倪,认知的萌芽状态;义是“宜”之意,行为的当然之则,即人所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羞者,羞己之非;恶者,恶人之恶”①,羞恶也就是知耻之心,是“义”的萌芽;一个人有了知耻之心,也就初步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也就有了初步的、基本的,当然也是可贵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
朱熹说:“人贵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恶念去之。若义利,若善恶,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别于其心。辟如处一家之事,取善舍恶;又如处一国之事,取得舍失,处天下之事,进贤退不肖。蓄疑而不决者,其终不成。”②这就进一步将明荣辱、识善恶提升到如何正确处理家事、国事、天下事来认识。同时,朱熹又进一步认为,仅仅有这一价值判断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将此“义之端”扩而充之,将此价值判断转化为道德践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道德认知、道德评判的层面上。否则,就会落入孟子所说的“恶辱而居不仁”,道德认知与道德践履相脱节,明知其辱却身陷其中。朱熹在此用了一个“去”字。此“去”字,与孔子提出的“远耻辱也”的“远”字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远”字略微有一点被动避开的意思,而“去”字则是积极主动地舍弃,如上文所引的“取善舍恶”“恶念去之”等。通过以上对孟子和朱熹言论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一个“求荣去辱”的儒家荣辱观来。
朱熹认为,“求荣去辱”的关键在于“行”。他说:“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③“《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功夫全在行上。”他批评当时的一种社会不良风气,说:“专做时文的人,他说的都是圣贤说话。且如说廉,他且会说得好;说义,他也会说得好。待他身做处,只自不廉,只自不义,缘他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说。廉,是题目上合说廉;义,是题目上合说义,都不关自家身己些子事。”①知荣辱,行仁义的关键在于“行之之实”,而不是停留在只知作口头或书面文章上,这是朱熹一再强调的“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②的道德实践意义。
在道德实践中,首先要遇到的问题是,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二者在理论上的区分标准是什么?朱熹继承了孟子的“仁则荣,不仁则辱”的观点,即以合于仁义者为荣,以不合于仁义者为辱的同时,对此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在阐释孟子“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一观点时,引用程颐的话说:“‘有不为’,知所择也。惟能有不为,是以可以有为。无所不为者,安能有所为耶?”③他所坚持的择善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准则,就是以合于仁义者为荣,凡合于仁义者,则为之行之;以违背仁义者为耻,凡违背仁义者,则不欲不为。“学者工夫只求一个是。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两端而已。从其是则为善,徇其非则为恶。”④因择善而行,又引发出朱熹的去恶存善,即以善恶来区分荣辱的道德观。他在解释《大学》“存其意者,毋自欺也”时说:“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⑤又说:“天下只是一个善恶,不善即恶,不恶即善。……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远其道,非道远人也。”⑥“若以善恶之象而言,则人之性本独有善而无恶。其为学亦欲去恶而全善。”⑦“若善恶,则有真妄之分,人当克彼以复此,然后可耳。”⑧所谓克彼复此,也就是去恶全善、存善去恶。
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中,荣与辱、善与恶的观念贯穿其道德观的各个层面。这一方面的事例很多,以下仅举几例。
如儒家提倡孝道,朱熹则坚持“孝者,百行之源”的观点。其内容,不仅限于“孝敬父母,慈爱骨肉”,扩而充之,则要“和睦乡邻,救恤灾患,输纳苗税,畏惧公法”①。他在漳州发布的《劝农文》,在强调“生民之本,足食为先”的基础上,将其与敦厉民风的为政措施相结合,以此传播先儒“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②的思想。其原因就在于孝道不仅仅只是做子女的在家里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如果在社会上做了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受耻辱,这同样被视为不孝。
又如淳熙十五年(1188)十一月,朱熹上《戊申封事》,批评当时官风不正,“纲纪不振于上,是以风俗颓弊于下。”朝野上下,“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只知“经营计较”一己之私。“宰相可谄则谄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而“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反遭“群讥众排”③。同时,还批评当政者不知爱养民力,百姓负担越来越沉重,官场“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为贤。于是中外承风,兢为苟急”④。在行文中,朱熹以刚毅正直为荣,以阿谀奉承为耻,以爱养民力为荣,以盘剥百姓为耻的立场十分鲜明。
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首次应诏上《封事》,针对其时“祖宗之境土未复,宗庙之仇耻未除,戎虏之奸谲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极”的现实,提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误疑之也。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①。他谴责卖国贼“秦桧倡和议以误国,挟虏势以邀君,终使彝伦斁坏,遗亲(祸)后君,此其罪之大者”②。他教导学生说:“国家遭汴都之祸,国于东南,所谓大体者,正在于复中原,雪仇耻。”朱熹的这些言论,体现了以爱国为荣,以卖国为耻的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
在坚持正确的荣辱观,在行善去恶的实践中,往往会受到社会不良习气的干扰和误解。比如见义勇为的行为,有时会被人们视为犯傻,以至受到不公不正的待遇和非议,这不仅在当代,在古代同样也有。朱熹对此的观点是,“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也;虽乐于及人,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③意思是,以自己的善行推及他人,使信从善的人越来越多,这固然值得高兴,但如果从善一时得不到他人的赞同或仿效,也毫无烦闷之感,这才是“君子”的境界。体现了朱熹提倡以善及人、助人为乐的思想,坚持的是一种以帮助别人为目的,而不是以帮助别人求得众人赞赏为目的的原则。他还说:“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报,祀而不祈其福,盖以善为当然。”④把帮助别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好事,是一种奉献而不求回报。
(三)培根固本,童蒙养正
作为一个教育家,朱熹非常重视童蒙教育。他认为,童蒙教育阶段是“作圣之基”,也是人的一生中知荣辱、养良知、培其根、固其本的最重要的阶段,其核心内容就是道德教育。
朱熹说:“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①他强调,所谓“学,大抵只是分别个善恶而去就之尔”②。“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③“故学圣人之道,必自小学始,否则虽欲勉焉而进于大学,犹作室而无基也,成亦难矣。”幼儿时期,知识和思想都是一片空白,谈不上有何主见。这时,就应当以儒家先圣的格言来时时影响和教育他们,即便他们此时尚未领会其意,但只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熏陶,久而久之,就会接受这些思想,就会成为好像是其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此时,即便有错误的东西来诱惑他们,也会不受影响。如果在童蒙时不对小孩进行道德启蒙,等到他们长大后,那些私欲偏好就会在内心滋长,就会受到外界各种错误言行的误导,此时,再来要求他们按照纯正完美的道德标准来行事,那就很难了。
有鉴于此,朱熹先后编纂了《小学》《童蒙须知》《训蒙绝句》《弟子职》等童蒙教材。《小学》成书于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他在武夷精舍讲学之时。这是一部以德育教育为主的启蒙读物,贯穿其“童蒙养正”的教育思想,其目的在于“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将此“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为的是能达到“习与知长,化与心成”④的效果。该书共六卷,分为内篇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嘉言、善行。其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的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方面的格言和故事,涵括了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思想,以及传统的荣辱观教育等诸多方面。此书刊行之后,数百年来,一直是儒家实行启蒙教育的重要教材。
总之,朱熹的“行己有耻,不辱其身,全善去恶,求荣去辱”的荣辱观,以及“培根固本,童蒙养正”的一系列观点,则为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本文系2007年9月15日至1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和武夷山市政府主办的“海峡两岸暨全球华人国学研讨会”参会论文,原题为《朱熹荣辱观的当代价值》,刊于《朱子文化》2007年第6期时改今名)
在我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儒学思想家均无不重视荣辱问题,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荣辱观。而在儒家荣辱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荣辱观的教育理念问题。
春秋时期,管子把知耻列为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四大支柱之一,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维,形声字。从糸(mì),隹(zhuī)声,“糸”指绳索、绳线。本义就是:作为锥形空间架构的绳线组。引申义为:骨干绳线;主绳。再引申义:拴系。说明:古代的车舆的圆盖是对北极天空的模拟。车盖是依靠四根绳索与车舆四角相牵挂的,这四根绳索叫做“四维”。古代的车是对天地的模拟。即车舆的伞形盖象征天,方形的车舆象征大地,车盖的中心柱子象征“天地柱”,马儿象征天地旋转的驱动力。在这样的认识下,古人想象大地的四角也有四根无形的大绳被系在北极点上,这四根无形的大绳也叫作“四维”。
也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于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在这里是引导的意思,“礼”是人际交往的行为准则,社会和谐安定与否,道德理念的引导和行为准则的规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这整段话的意思是,如果仅仅用行政命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约束百姓,他们虽然可以因惧怕惩罚而避免犯罪,但却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从其效果来说,这是被动的;而用道德教化来治理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就能使他们懂得耻辱而不会触犯刑律,从其效果来说,这是主动的。因此,孔子进而提出了“行己有耻”(《论语·子路》)、“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等一系列道德自律的主张,其用意在于使每一个人都能明白,行事立身要有是非观念和羞耻之心,要远离耻辱,不要去做那些让人感到耻辱的事。也就是说,要使人不犯罪、不做坏事,仅仅停留在惧怕法律的惩罚上而不敢为之是不够的。所以,要努力追求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具备做人应有的知耻明辱的良知而耻于为之,远离犯罪,这是孔子荣辱观的主要目标。但是,这种知耻明辱的良知不可能与生俱来,“有耻且格”的效果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必须通过统治者的推行教育,通过教育理念和舆论的引导(道之以德)来实现。这既是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也是孔子作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其所建构的荣辱观中,蕴藏在其中的通过推行教育来传播儒家荣辱观的思想。
继孔子之后,孟子最早提出“荣”“辱”这一对应概念。他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他不仅从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识荣辱的重要性,而且对孔子的识荣辱必须与道德教育紧密结合的思想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公孙丑上》)朱熹指出,所谓善政,是指以法度禁令“制其外”;善教,是以道德齐礼“格其心”。不难看出,孟子已将孔子思想中所深藏不露的通过教育来传播儒家的荣辱观的思想加以进一步的提取和明确,并分别从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和改善道德教育两个致思向度上加以引申和发挥。在《孟子》一书中,“耻”这一概念往往又与“辱”“羞”等交替使用。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不知羞耻之人,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在儒家学者所主张的诸多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中,与荣辱观教育关系比较密切的有孔子所说的“内省”。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见到别人好的行为和品质,就要虚心向他学习;见到不好的品行,就要联系自己,加以反省,并以此为戒,以期努力做到“内省”而不疚,即无道德缺陷。曾子将此方法发展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
内省的方法,是儒家学者极为重视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其含义是内心的自我反省和对自己日常行为的道德审视。这种自我反省与审视,与儒家的荣辱观有着天然的联系。如孟子主张以仁为荣,以不仁为辱,既是对孔子的仁学思想的一种发展,又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儒家荣辱观。而在《孟子》一书中,“耻”这一概念往往又与“辱”“羞”等交替使用。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耻辱羞恶之心,是孟子仁之四端之一,朱熹将其与内省、审察联系到了一起。他说:“要知天之与我,只如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辞逊之心,非人也。’今人非无恻隐、羞恶、是非、辞逊发见处,只是不省察罢了。……只为从前不省察了,此端才见,又被物欲汩没了,所以秉彝不可磨灭处虽在,更终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①这种羞恶之心,孟子称为是“义之端”,也就是人在采取某一行动前,选择使用道德而避免非道德行为的一种发自人之本能良知的萌芽状态;但这种“萌芽”,只是一种最初的“本然”,故往往容易被外界的物欲所“汩没”;而内省或省察,则是对这种被物欲所汩没的一种警醒和提防。由于社会上物欲无所不在,故这种内省就须不间断地时刻进行。如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朱熹所说的“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②。
在道德教育阶段论中,儒家学者主张荣辱观的教育应从幼儿开始。从理论上说,实施教育者最好是从事教育的专门人才,但由于人类现实的家庭婚姻制度,使家长不可避免地成为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的传说,是儒家学者重视童蒙教育,坚持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应该从儿童抓起,应从家庭起步的理念的一种体现。
在理论上提出德育应从“能食能言”的婴幼儿开始实施的,是北宋理学家程颐。他说:“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说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私意偏好生于内,众口辨言铄于外,欲其纯完,不可得也。”①意思是说,婴幼儿时期,知识和思想都是一片空白,谈不上有何主见。这时,就应当以儒家先圣的格言来时时影响和教育他们,即便他们此时尚未领会其意,但只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熏陶,久而久之,就会接受这些思想,就会成为好像是其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此时,即便有错误的东西来诱惑他们,也会不受影响。如果在童蒙时不对小孩进行道德启蒙,等到他们长大后,那些私欲偏好就会在内心滋长,就会受到外界各种错误言行的误导,此时,再要求他们按照纯正完美的道德标准来行事,那就很难了。程颐又进一步将这种童蒙教育方法概括为:“教人者,养其善心,则恶自消。”②“养正于蒙,学之至善也。”③用良好的、健康的教育方法和道德理念,使儿童从小就能构筑起一道知耻明辱、存善去恶的道德防线,来抵御外界各种不良思想的负面影响。否则,“任其自为,听其不为,则中人以下,自弃自暴者众矣。圣人所以贵于立教也。”④“圣人所以立教”,指的是儒学先师的教育目的,这就又将知耻明辱、养善去恶的童蒙教育与儒家的教育目的论联系到了一起。
二、朱熹的荣辱观
朱熹作为我国传统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荣辱观则集中了儒家先圣先贤的精粹。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律人律己,不辱其身
朱熹的荣辱观,不仅限于理论层面上,更重要的是落实在道德践履之中。他认为,这不仅是历代儒家学者用以律己,同时也是用以律人的主要道德标准。他继承了孔子“行己有耻”(《论语·子路》)的思想,进一步提出“行已有耻,则不辱其身”①的观点。行己有耻,这是针对个体而言,是律己;“士人要先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有何用?”②这是律人。且在行文中,所表达的以道德论人品,即德与才(能文)相比,德在才先的涵义十分明确。
朱熹认为,人有了知耻之心,就会远离耻辱,就不会去做那些为人所不齿的事,就能“不辱其身”。为何有了知耻之心,就会远离耻辱呢?朱熹解释说:“知耻是由内心以生,闻过是得之于外。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故耻为重。”③知耻是发自内心的道德理念,是抵御外界各种恶行的道德防线;正因为内心知耻,即使有了过失而不觉,也能闻过而改。故朱熹认为,与“得之于外”的“闻过”相比,知耻更重要。他在建阳考亭书院讲学之时,对他的学生辅广等人强调说:“人须是有廉耻。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④漳州府学教授张某颇具文才,但却品行不端,朱熹将其开除,并训斥为之说情者曰:“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责任不为不重,合当自行规矩。而今却容许多无行之人、争讼职事人在学,枉请官钱,都不成学校!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①为了给士子树立好的榜样,朱熹延请了郡士黄樵、陈淳、徐寓等八人入郡学教授诸生,并发布《漳州延郡士入学牒》。牒文对此八人的学问和操守一一作出评价,以有别于无“廉退之节”的败类,并希望凡学之子弟,从此有“良师畏友之益,庶几理义开明,德业成就”②。
所谓廉退,是廉介与恬退之意。与朱熹同时的著名诗人、学者尤袤驳斥当时朝中有人攻击朱熹的学说为“道学”时,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高度评价为,是将“临财不苟得”视为廉介,“安贫守分”视为恬退,“择言顾行”视为践履,“行己有耻”视为名节③的“贤人君子”。朱熹在外地担任地方官时,针对其时的一些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腐败现象,颇有感触地说:“富贵易得,名节难保,此虽浅近之言,然岂亦可忽哉!”④这就将孔子的行己有耻的荣辱观发展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数百年的气节观。这种气节观的主要表现就是“仰不愧,俯不祚”“常以‘志士不忘在沟壑’为念,则是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⑤他在漳州等地学校所推行的“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表明朱熹是把明荣辱、识廉退作为学校人格和道德教育的首要目标;而为诸生树立可以效仿的明荣辱、识廉退的正人端士形象,则是朱熹将其荣辱观具体落实到学校教学中的典型事例之一。
(二)全善去恶,求荣去辱
在解释孟子提出的“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时,朱熹认为“好荣恶辱,人之常情。然徒恶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⑥。意思是说,仅停留在好荣恶辱这一人之常情的水平上,是远远不够的。“徒恶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就仍然不能免于耻辱。因为知荣辱仅仅是一种初步的道德认知,是孟子所说的“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端是端倪,认知的萌芽状态;义是“宜”之意,行为的当然之则,即人所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羞者,羞己之非;恶者,恶人之恶”①,羞恶也就是知耻之心,是“义”的萌芽;一个人有了知耻之心,也就初步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也就有了初步的、基本的,当然也是可贵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
朱熹说:“人贵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恶念去之。若义利,若善恶,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别于其心。辟如处一家之事,取善舍恶;又如处一国之事,取得舍失,处天下之事,进贤退不肖。蓄疑而不决者,其终不成。”②这就进一步将明荣辱、识善恶提升到如何正确处理家事、国事、天下事来认识。同时,朱熹又进一步认为,仅仅有这一价值判断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将此“义之端”扩而充之,将此价值判断转化为道德践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道德认知、道德评判的层面上。否则,就会落入孟子所说的“恶辱而居不仁”,道德认知与道德践履相脱节,明知其辱却身陷其中。朱熹在此用了一个“去”字。此“去”字,与孔子提出的“远耻辱也”的“远”字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远”字略微有一点被动避开的意思,而“去”字则是积极主动地舍弃,如上文所引的“取善舍恶”“恶念去之”等。通过以上对孟子和朱熹言论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一个“求荣去辱”的儒家荣辱观来。
朱熹认为,“求荣去辱”的关键在于“行”。他说:“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③“《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功夫全在行上。”他批评当时的一种社会不良风气,说:“专做时文的人,他说的都是圣贤说话。且如说廉,他且会说得好;说义,他也会说得好。待他身做处,只自不廉,只自不义,缘他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说。廉,是题目上合说廉;义,是题目上合说义,都不关自家身己些子事。”①知荣辱,行仁义的关键在于“行之之实”,而不是停留在只知作口头或书面文章上,这是朱熹一再强调的“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②的道德实践意义。
在道德实践中,首先要遇到的问题是,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二者在理论上的区分标准是什么?朱熹继承了孟子的“仁则荣,不仁则辱”的观点,即以合于仁义者为荣,以不合于仁义者为辱的同时,对此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在阐释孟子“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一观点时,引用程颐的话说:“‘有不为’,知所择也。惟能有不为,是以可以有为。无所不为者,安能有所为耶?”③他所坚持的择善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准则,就是以合于仁义者为荣,凡合于仁义者,则为之行之;以违背仁义者为耻,凡违背仁义者,则不欲不为。“学者工夫只求一个是。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两端而已。从其是则为善,徇其非则为恶。”④因择善而行,又引发出朱熹的去恶存善,即以善恶来区分荣辱的道德观。他在解释《大学》“存其意者,毋自欺也”时说:“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⑤又说:“天下只是一个善恶,不善即恶,不恶即善。……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远其道,非道远人也。”⑥“若以善恶之象而言,则人之性本独有善而无恶。其为学亦欲去恶而全善。”⑦“若善恶,则有真妄之分,人当克彼以复此,然后可耳。”⑧所谓克彼复此,也就是去恶全善、存善去恶。
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中,荣与辱、善与恶的观念贯穿其道德观的各个层面。这一方面的事例很多,以下仅举几例。
如儒家提倡孝道,朱熹则坚持“孝者,百行之源”的观点。其内容,不仅限于“孝敬父母,慈爱骨肉”,扩而充之,则要“和睦乡邻,救恤灾患,输纳苗税,畏惧公法”①。他在漳州发布的《劝农文》,在强调“生民之本,足食为先”的基础上,将其与敦厉民风的为政措施相结合,以此传播先儒“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②的思想。其原因就在于孝道不仅仅只是做子女的在家里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如果在社会上做了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受耻辱,这同样被视为不孝。
又如淳熙十五年(1188)十一月,朱熹上《戊申封事》,批评当时官风不正,“纲纪不振于上,是以风俗颓弊于下。”朝野上下,“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只知“经营计较”一己之私。“宰相可谄则谄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而“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反遭“群讥众排”③。同时,还批评当政者不知爱养民力,百姓负担越来越沉重,官场“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为贤。于是中外承风,兢为苟急”④。在行文中,朱熹以刚毅正直为荣,以阿谀奉承为耻,以爱养民力为荣,以盘剥百姓为耻的立场十分鲜明。
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首次应诏上《封事》,针对其时“祖宗之境土未复,宗庙之仇耻未除,戎虏之奸谲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极”的现实,提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误疑之也。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①。他谴责卖国贼“秦桧倡和议以误国,挟虏势以邀君,终使彝伦斁坏,遗亲(祸)后君,此其罪之大者”②。他教导学生说:“国家遭汴都之祸,国于东南,所谓大体者,正在于复中原,雪仇耻。”朱熹的这些言论,体现了以爱国为荣,以卖国为耻的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
在坚持正确的荣辱观,在行善去恶的实践中,往往会受到社会不良习气的干扰和误解。比如见义勇为的行为,有时会被人们视为犯傻,以至受到不公不正的待遇和非议,这不仅在当代,在古代同样也有。朱熹对此的观点是,“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也;虽乐于及人,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③意思是,以自己的善行推及他人,使信从善的人越来越多,这固然值得高兴,但如果从善一时得不到他人的赞同或仿效,也毫无烦闷之感,这才是“君子”的境界。体现了朱熹提倡以善及人、助人为乐的思想,坚持的是一种以帮助别人为目的,而不是以帮助别人求得众人赞赏为目的的原则。他还说:“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报,祀而不祈其福,盖以善为当然。”④把帮助别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好事,是一种奉献而不求回报。
(三)培根固本,童蒙养正
作为一个教育家,朱熹非常重视童蒙教育。他认为,童蒙教育阶段是“作圣之基”,也是人的一生中知荣辱、养良知、培其根、固其本的最重要的阶段,其核心内容就是道德教育。
朱熹说:“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①他强调,所谓“学,大抵只是分别个善恶而去就之尔”②。“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③“故学圣人之道,必自小学始,否则虽欲勉焉而进于大学,犹作室而无基也,成亦难矣。”幼儿时期,知识和思想都是一片空白,谈不上有何主见。这时,就应当以儒家先圣的格言来时时影响和教育他们,即便他们此时尚未领会其意,但只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熏陶,久而久之,就会接受这些思想,就会成为好像是其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此时,即便有错误的东西来诱惑他们,也会不受影响。如果在童蒙时不对小孩进行道德启蒙,等到他们长大后,那些私欲偏好就会在内心滋长,就会受到外界各种错误言行的误导,此时,再来要求他们按照纯正完美的道德标准来行事,那就很难了。
有鉴于此,朱熹先后编纂了《小学》《童蒙须知》《训蒙绝句》《弟子职》等童蒙教材。《小学》成书于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他在武夷精舍讲学之时。这是一部以德育教育为主的启蒙读物,贯穿其“童蒙养正”的教育思想,其目的在于“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将此“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为的是能达到“习与知长,化与心成”④的效果。该书共六卷,分为内篇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嘉言、善行。其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的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方面的格言和故事,涵括了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思想,以及传统的荣辱观教育等诸多方面。此书刊行之后,数百年来,一直是儒家实行启蒙教育的重要教材。
总之,朱熹的“行己有耻,不辱其身,全善去恶,求荣去辱”的荣辱观,以及“培根固本,童蒙养正”的一系列观点,则为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本文系2007年9月15日至1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和武夷山市政府主办的“海峡两岸暨全球华人国学研讨会”参会论文,原题为《朱熹荣辱观的当代价值》,刊于《朱子文化》2007年第6期时改今名)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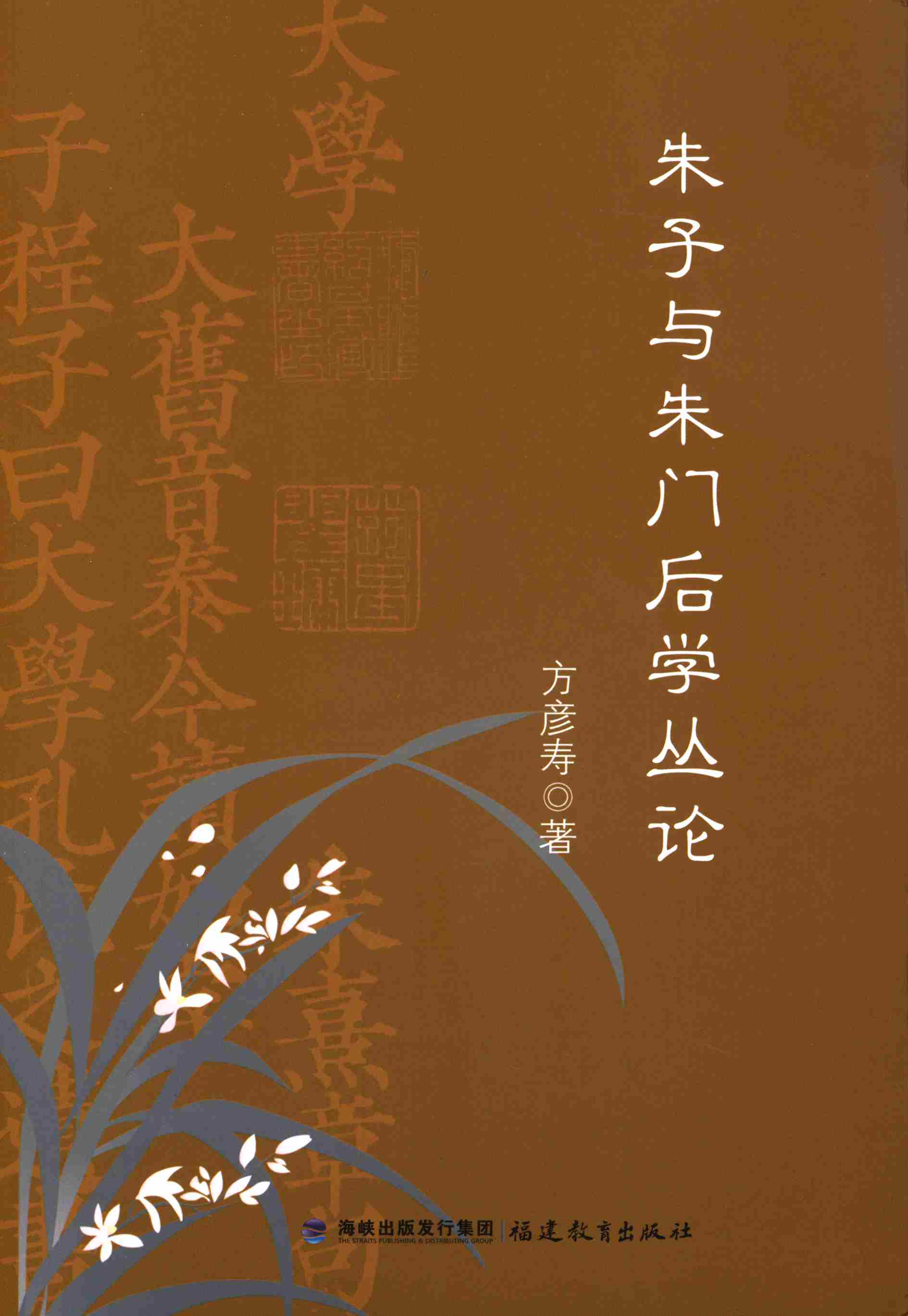
《朱子与朱门后学丛论》
本书分为朱子论、后学论、书院论和前贤论四个专题。“朱子论”内容涉及朱子的理学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道统观、道德观、孝道观、社会治理与社会教化等方面。“后学论”主要论述宋明时期的朱门后学,如黄榦、陈淳、陈宓等理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在继承和弘扬朱子学方面的贡献。“书院论”主要探讨朱熹及其后学所创建的书院在推动朱子学、推动闽台书院文化建设及其发展中的作用。“前贤论”主要探讨有关朱子的前辈学者,如杨时、游酢、李侗等人相关文献的考证。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