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子建立道统的理据
| 内容出处: | 《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573 |
| 颗粒名称: | 三、朱子建立道统的理据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4 |
| 页码: | 396-409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根据陈荣捷先生的观察,道统的概念最早源于孟子,之后韩愈、李翱等继续强调这一概念,宋代程伊川更是撰写了明道先生行状,认为道统已然确立。朱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并追溯到伏羲黄帝时期,确立了道统的地位。朱子在立道统时,排除了汉唐时期的儒者,特别推崇二程,并将周子作为首要标志,其次才是张子,但并未涉及邵子。陈荣捷先生指出,朱子之所以立道统,是出于哲学上的理由,将汉唐儒者排除在外。朱子的立场也得到了宋代史学引用,并且后来的学者也宗承了这一观点。 |
| 关键词: | 朱子 道统 理据 |
内容
据陈荣捷先生的观察,道统之说乃源于孟子,以后韩愈、李翱重述斯旨,至宋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状,谓其兄:“求道之志未至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斯文为己任”,朱子继之,而后道统得以确立。(注二)
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有云:
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子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又再传以得孟氏。……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
由是而由尧舜而二程,道统一贯。朱子且上溯伏羲黄帝,(注三)道统于以确立。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则曰:
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
于此可见朱子显然有担承道统之意。及后黄〓书朱子行状,乃曰:
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
以后宋史引其说,列代学者宗之不乏其人。陈荣捷先生指出,朱子之立道统,是以哲学性的理由排除汉唐诸儒,特尊二程,首标周子,旁置张子,而不及邵子,其言是也。(注四)
我们查考宋儒的基本观念,与先秦儒比较,差别当不在小。随便举几个例: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宋儒则最爱谈论性与天道的问题;子在川上之叹,宋儒说是在谈道体;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宋儒说此澈上澈下语也;从纯考据的观点看来,实在找不出这些说法与原典有什么确定的关联。而宋儒与先秦儒之间的主要差别,好像在宋儒大幅地引入了许多佛老的观念。再随便举几个例来说:宋儒最基本的观念是“理”,但在孔孟,理并不是十分重要的观念,反而是华严才昌言理事无碍的境界;又如太极在先秦也不是重要的观念,在宋儒之中,濂溪首倡之于太极图说,到朱子才变成了一个中心的观念,但朱子并未否认太极图的来源是出于道家的陈搏。其实朱子从不否认宋儒曾受到佛老的影响,语类曰:
近看石林过庭录载上蔡说,伊川参某僧后有得,遂反之。偷其说来做己使,是为洛学。某也尝疑,如石林之说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说,是怎生地?向见光老示及某僧与伊川居士帖,后见此帖乃载山谷集中,后又见有跋此帖者,乃僧与潘子真帖,其差谬类如此。但当初佛学只是说,无存养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养工夫。当初学者亦只是说,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谓伊川偷佛说为己使。(一二六)
据钱穆先生考据,此条某僧指灵源,其与潘淳子真一帖,人误谓之与伊川,朱子辨之。(注五)但奇怪的是,朱子于伊洛偷佛学为己使一语,却似不甚反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势必被逼得要问以下的两个问题:
(一)宋儒是否大段都是佛老之说?而且宋儒往往互相攻讦异己为佛说,此处究竟是否确有阳儒阴释之嫌?
(二)宋儒与先秦儒之关联究竟如何?究竟彼此之间是否有本质性的一脉相传的线索如道统说之所宣称者?抑或宋儒只是借古籍做幌子,骨子里是在说一套与先秦儒十分不同的新东西?
这样的问题根本涉及道统的观念究竟是否可以成立的问题,所以值得我们仔细来考虑。
先就第一个问题来说,由上节的解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宋儒与佛老之间确有一定的分疏。宋儒无疑是受到佛老的刺激而不能满足于传统的窠臼之内,此所以程朱诸儒多必须出入老佛有年而后返归六经,始知吾道自足。儒学要扩大,要应付佛老方面来的强大的冲击,就必须直捣虎穴,在不违背自己的基本精神的前提之下,汲取佛老的灵泉,来恢复自己的活力,这不是一件可羞愧、要隐瞒的事实。其实朱子对于当时儒学之不振感怀极深,批评不遗余力。语类有曰:
或问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体。(中略)。问明道云,自汉以来,诸儒皆不识此,如何?曰:是他不识如何却要道他识?此事除了孔孟,犹是佛老见得些形象。譬如画人一般,佛老画得些模样,后来儒者于此全无相着,如何教他两个不做大。祖道曰:只为佛老从心上起工夫,其学虽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从言语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会者亦只做一场话说过了,所以输与他。曰:彼所谓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胜似儒者多,公此说却是。(三六)
正淳云:某虽不曾理会禅,然看得来圣人之说皆是实理,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皆是实理流行,释氏则所见偏,只管向上去,只是空理流行尔。曰:他虽是说空理,然真个见得那空理流行。自家虽是说实理,然却只是说耳,初不曾真个见得那实理流行也。释氏空底却做得实,自家实底却做得空,紧要处只争这些子。(六三)
问:老子之言似有可取处。曰:它做许多言语,如何无可取?如佛氏亦尽有可取,但归宿门户都错了。(一二六)
由此可见,宋代程朱等大儒都是心胸开扩、不拘门户的豪杰之士,绝非抱残守缺之辈可比。佛老有长处,何不取之于佛老,只要儒者自己的基本精神不流失即可。其实朱子自受学延平以来,儒佛之分疏对他而言即为一重要问题。延平所指点的理一分殊固然是一大关键,但问题所牵涉的决非止此而已!朱子用心反省这一个问题,孝宗隆兴二年甲申三十五岁时有答李伯谏书,既辨儒释之相异,而又申伊洛与孔孟之相同。书中所论所包极广,兹摘录数节如下:
详观所论大抵以释氏为主,而于吾儒之说,近于释者取之,异于释者,在孔孟则多方迁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则无所忌惮而且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识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窃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语意之间不免走作。(中略)。
来书谓圣门以仁为要,而释氏亦言正觉,亦号能仁,又引程氏之说为证,熹窃谓程氏之说以释氏穷幽极微之论观之,似未肯以为极至之论,但老兄与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为重耳。然儒者言仁之体则然,至语其用则毫厘必察,故曰:仁之实、事亲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体用一源而显微所以无间也。释氏之云正觉、能仁者,其论则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来书引天下归仁以证灭度众生之说。熹窃谓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复礼则事事皆仁,故曰天下归仁。试用此意思之毫发不可差,差则入于异学矣。
来书云:夫子语仁以克己为要,佛氏论性以无心为宗,而以龟山心不可无之说为非。熹谓所谓己者,对物之称,乃是私认为己而就此起计较、生爱欲,故当克之。克之而自复于理,则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虚明纯一,贯彻感通,所以尽性体道,皆由于此,今以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则又是有心矣。如此则无心之说何必全是,而不言无心之说何必全非乎?若以无心为是,则克己乃是有心,无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为是,则请从事于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于此,而无心于彼,为此二本而枝其辞也。(中略)。
来书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谓性无伪冒,不必言真。未尝不在,不必言在。盖所谓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者也,曷尝不在,而岂有我之所能私乎?释氏所云真性,不知其与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则古人尽心以知性知天,其学固有所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异乎此,而欲空妄心,见真性,唯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犹所谓廉贾五之,不可不谓之货殖也。伊川之论、未易遽非,亦未易晓。他日于儒学见得一个规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来书谓伊川先生所云内外不备者为不然,盖无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者。此论甚当。据此正是熹所疑处。若使释氏果能敬以直内,则便能义以方外,便须有父子、有君臣,三纲五常,阙一不可。今曰能直内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岂数者之外,别有所谓义乎?以此而观,伊川之语可谓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谓有直内者,亦谓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处,故其发有差,他却全不管着此,所以无方外之一节也。固是有根株则必有枝叶,然五谷之根株则生五谷之枝叶华实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则生稊稗之枝叶华实而不可食,此则不同耳。参术以根株而愈疾,钧吻以根株而杀人,其所以杀人岂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故明道先生又云:释氏惟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元不相连属,但有间断,非道也。此可以见内外不备之意矣。(中略)。
来书云:儒佛见处既无二理,其设教何异也?盖儒教本人事,释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缓于见性,本死生故急于见性。熹谓既谓之本,则此上无复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谓儒本人事缓见性者,亦殊无理。三圣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谓性,孔子言性与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为本于人事乎,本于天道乎?缓于性乎,急于性乎?(原注:然着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为异说所迷,反谓圣学知人事而不知死生,岂不误哉!圣贤教人尽心以知性,躬行以尽性,终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诸天理,缓也缓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尽性至命方是极则,非如见性之说,一见之而遂已也。(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三书之第一书)
此书虽朱子思想尚未完全成熟时作品,然论儒佛分疏处,则与晚语类中言,并无二致。朱子拒绝和会之论是有很强的理据的。依儒者言,则人伦日用不可废,仁义礼智根于心,性理之实即本之于生生而容已之天道。其体用本末,皆与佛氏迥异,焉能以名言之相类而遂讳彼此之间有本质性之差别。
我们再看儒者之借佛老之说,取舍之间,极有分寸,绝非自弃立场者。而运用之妙,存乎其人。如濂溪之借用太极图,道家之本是做修养工夫的引导,以归于无极,而濂溪却将之倒转过来,讲出一符合生生之旨的形上学、宇宙论,肯定人伦日用,这在基本上是儒家精神,绝非道家的精神。又如二程吸纳佛家做修养的工夫,然所涵养证为儒家的性理,决非佛家的空理。而周张程朱由佛老吸取灵泉的果,则为儒家打开了一些全新的视域,增辟了一些重要的层面,复苏儒学的生命,岂云少补。同时儒佛之分疏并不因此而泯灭,且正因为儒家做出了可以和佛家匹敌的心性论、宇宙论,遂使得儒释之对比分清明,让后来的学者可以在其间作自觉的抉择,或者尝试一种更高综合。
如此,我们对于上面所提的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新儒家的确是家思想,决非老佛思想。儒释的分界线是不能不加以确定地维持的。实上程朱等大儒确自觉地把握住儒佛之间根本的分疏,不容和会混淆由此而阳儒阴释之论不攻自破,不值得我们重视。
其次,我们要查究宋儒与先秦儒究竟有怎样的关联,以及道统的念究竟能否成立的问题。
从纯考据的观点看,道统的观念显然是难以成立的。譬如朱子中庸句序追溯道统的根源引危微精一的十六字心传,经清儒考证,乃出于伪古文尚书,诗经原典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根本未必包含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的意思;子思是否中庸的作者也有疑问,近世学者更多以中庸成书乃在孟子之后者。再由考古的观点看,中国的信史断自商代起,则伏羲、黄帝、尧、舜还是属于神话传说的时代,未能确证实有其人。由此看来,道统之说是根据许多未证实的传说所构筑成的一种主观信念,未足采信。
但有趣的是,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儒与先秦儒的连贯性。把时间推回到远古正是先秦儒的一贯作风,所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也。其实孔子本人已经知道得清楚,谈过去的事有文献不足征的问题,所谓夏礼吾能言之,〓不能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三代尚且如此,更何况尧舜!但孔子却相信这里有一条一脉相承的线索,所以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这样推下去,虽十世可知也。孟子更演绎出一套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哲学观。宋儒所继承的正是这一类的观念。所以针对戴震的问题:朱子生于孔子之后一千多年,他怎么能够知道孔子的想法是什么?尊信宋学的人的回答是,千圣相传,只是此心,以心印心,自然不难了解圣人的命意所在。就论语所显露的孔子的性格看来,孔子不会是像今文学家所说,故意虚构出一套古代的理想的图画来托古改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是在真心向往尧舜的盛世,所继承的是文武周公的理想。而这是把道德融贯入现实政治的理想;朱子所崇信的也还是同样的理想,朱子自也不免过分理想化远古的历史,但当时疑古之风未盛,朱子所接受的只不过是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古史的图象而已!而朱子的坚强的信念的真正根源是在千圣相传之心,以及此心所把握之实理,这些是用切问而近思的方式,当下即可以体证的道理,不是时代淹远不可追索的上古遗迹。由此可见,道统成立的真正基础在于此心此理之体认。我们之所以尊崇伏羲、黄帝,只是因为大家一般共认,道曾经具现于伏羲、黄帝而已!其实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之中已经点穿;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由此可见,师道之尊犹有甚于君道,在教育文化上的开拓还更重要于现实政治上的建树。如此则伏羲、黄帝、尧、舜之功自可给人一种源远流长的感觉,同时也说明了创新自有传承为基础,然而即使退一步承认伏羲、黄帝、尧、舜不属于信史范围,也不能因此就完全推翻了道统的观念。因为道统说真正的枢纽点实在是在孔子。从宋儒的观点看,孔子比先王更亲切更明白地表现了道,在孟子则直接继承了孔子,故此我们不能不进一步考虑宋儒与孔孟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只许以一言来概括宋儒的中心理念,或者我们可以说,在宋儒的理解中是以生生之仁为天道与人道的根本。问题在我们能否在孔孟找到这样的思想的根据。
就表面来说,以生生言仁始于程子,不见于先秦之典籍,自可以说是宋儒之创见。但就此而言,则孟子道性善,也是孟子之创见,不见于孔子的论语。故问题的症结在,后儒之创发,是否与先儒在精神上一贯,这才是真正最中心的关键所在。
孔子之所以在儒家占有一最特殊之地位,是在于他首先提出仁为全德,为儒家思想指点了一个确定的方向。孔子虽不曾为仁下一个定义。但君子不可于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显然是孔子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故孔子虽未明言他的一贯之道究竟是什么,仁显然就是他的一贯之道,曾子以忠恕释之,朱子解释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二者显然为仁的表现之一体的两面,似乎不失曾子原意。而尽己可以与明明德配合,推己可以与亲民配合,大学显然也是发扬孔子的儒家思想的一项重要的典籍。孔子本人虽也未明言性善,但他指点出礼后乎,显然肯定礼仪在人性之中有一自然之基础。孔子一生学不厌,教不倦,就是相信人性之中有极大的潜能以向善。从孔子的思想看来,仁义不能是外铄的,到孟子乃明言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则宋儒之归本于孔子,奉孟子为正统,决不能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其次再谈生生的体证。论语虽绝少有关性与天道的讨论,但子贡不可得而闻也的证词并不表示孔子一定没有关于性与天道的思想。孔子描写自己学修的经过就曾明言五十而知天命,又曾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法。宋儒以子在川上叹曰的一段是形容道体,固不免想象力过分丰富。但孔子本人确曾倡导无言之教,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显然孔子的确相信天壤间有一无穷生力在作用,这样的思想与大易生生的思想是互相呼应的。在今日,我们自不可能再相信十翼皆孔子所作,但我们却不能够排除十翼之中有孔子思想的可能性,至少十翼之中大部分是儒门后学发挥孔子这一线索所传承的思想。在今天我们研究孔子,自必以论语为最主要的资料,但不能以论语为唯一的资料。最可靠的方法是我们用论语为间架去网罗其他相关的资料。而论语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一条践仁以知天的线索。孔子的教诲虽把重点放在前者,却不能完全排除了后者的可能性。孟子更明言尽心知性知天而指点了一条更为确定的进路。宋儒顺着这一个方向去推进,不能不说的确是孔孟的苗裔。
再讲到学庸。礼记之中当然大部分是儒门后学的作品。或曰,大学之中讲定静安虑得,不见得纯是儒家的思想。但这样的说法所犯的错误是把儒家思想当作一个静止的常体,事实上儒家的思想不断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没有理由不受其他的思想的影响,也没有理由不向别的思想汲取新的灵泉。问题是这些文献的中心究竟是发挥儒家的思想,还是别派的思想。大学讲三纲领八条目,这明显地是儒家的思想,增加了定静安虑得的修养工夫的次第,一点不显得突兀,也不使之变质成为了非儒家的思想。同理,中庸讲天命之谓性,诚的天道观,都是在本质上属于儒家的思想,与孔孟有着一脉相承的线索。易传之中成分当然更芜杂。但天地之大德曰生;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些都是显明地与儒家的天道观完全符合的思想。宋儒再更进一步发挥出理、太极的崭新的概念,有什么不可以?
事实上,朱子把学庸与论孟放在一起,组成四书,实在是深具卓识。四书之说自不始于朱子,但基于哲学性的理由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并化了那些大的力气为之作集注,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这却是朱子的功劳。朱子之立道统,显然是以内圣之学为规模。故于孔门特重颜曾,并谓孟子没后而遂失其传焉。汉魏以来,只得传经之儒而已!历代大儒如董仲舒、扬雄、文中子、韩愈辈,均于内圣之学并无贡献,故不包括在道统之内。一直要到明道,“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伊川赞其兄之学贵自得,始为宋儒尊为道之正统。但朱子在二程之前又推尊濂溪,此则其煞费苦心处。盖二程缺乏宇宙论的兴趣,中心虽牢固,而缺少集大成的意味。濂溪则别立蹊径,其通书与太极图说打通了易庸之间的通道,而归本于孔颜。这是儒学可以开展的一条新途径。横渠之西铭,二程极推尊,对于正蒙乃不无微词。横渠分别德性之知、见闻之知;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固无乖于正道。但他所销融的清、虚、一、大等观念乃不免歧出,思想表达也不完全圆熟,故只能放在辅翼的地位。至于康节则重象数,其思想的道家意味太重,故既未采入近思录,也不见于伊洛渊源录。钱穆先生谓朱子并非不看重邵子,(注六)此则固然,然朱子也非不看重司马温公,但温公为史家,故也不包括在道统之中。文集卷八十五,有六先生画像赞,即将康节、涑水与濂溪、二程、横渠平列。由此可见,朱子的容量大,架局广,但取舍之间层次分明,法度极为谨严。朱子一生基本用心究竟何在,于此可以思过半矣。
讨论至此而我们也可以对前面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作一个答复。宋儒的思想与先秦儒的思想之间的确有一种本质性的关联。我们至少可以说,宋儒是在不违背孔孟的基本精神之下,受到佛老的冲击,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新儒家的思想。
但我们这样立论,并不是说,儒家就不可以发展出另外的不同思想。事实上,孔子的后学也可以发展出荀子的性恶论,由荀子的思想再推进一步乃可以发展出韩非的法家的思想。但这样的思想却已经脱离了儒家的基本的规模。
其次,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儒家都要同意朱子这种儒家正统的意见。孔子之后,早就有儒分为八的说法。秦火之后,则有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的对立。嗣后又有汉宋的差别;清儒即有以反宋明儒为职志者,好像颜元即以之为丧失了原始儒家的精神。儒家的思想本可以有不同发展的可能性,我在这里只是说明,宋儒是有一条线索可以声言他们是由孔孟以来一脉相承的发展。他们也提出了一定的标准,把某一些思想包含在道统的范围之内,或排拒在道统之外。这一个标准即宋儒体证得最真切的内圣之学的规模。以此而汉唐号称盛世,在思想的层面上却于儒者内圣之学无所增益而被弃置在一旁。同样,宋明儒的慧识到了清朝既已经无以为继,则由宋明儒的标准看乃不能不谓之为一种堕落,一直要到当代熊十力先生出来,才致力于重新恢复这一个传统的思想。
如果以宋学为标准,则内在中心的体证是最重要一件事,章句的解释其余事耳,学问的目的是在见道,其目的本不在词章记诵,更不在客观的饾饤考据的工作。对于文字的解释,一以主观的体验为基础,故此对于文义的引伸,不只不当作一种错误或过失,反而被当作一种慧解的印证看待。只有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宋儒对于“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子在川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一类的新释。这样的新释可能是越出了古典的原义,(正如海德格所谓的doing violence to the text)但却不一定违反原典的精神。而慧识的传递,比章句的传递,对宋儒来说,显然是具有远更重要的价值。
我并不是说,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不会产生一些问题,或者构成一些缺点。在这样的精神的主导之下,客观的学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然而我们必须了解,道统与学统本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若纯由道统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够问,生生之仁的体证是不是反映了生命的真理,其余有关考古、历史、考据的问题都不是十分相干的问题。
当代西方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在“耶稣的研究”(Jesuso-logy)与“基督的信仰”(Christology)之间所作的区分,(注七)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依田立克的说法,有关耶稣生平的研究,譬如耶稣是否生在一个木匠之家,他的许多事迹是否真实的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范围,所得到的结论至多只有较低或较高的盖然性。但是基督道成肉身,十字架的象征所宣泄启示的是,一个生命(现实)的终结是另一个生命(精神)的开始,这里所传达的消息却是绝对的真实,它根本不是知识的对象,只是信仰的对象。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伏羲、黄帝的传说的真实性只有较低或较高的盖然性,这些是历史、考古可以研究的对象。但肯定仁道遍满,建立道统之说所牵涉的却根本是儒家终极信仰的问题,非知识所行境。
我们的经验知识,用宋儒的术语来说,也就是我们的见闻之知,只能够用来发现现象世界内部的关联,而不能够处理有关我们的终极托付的问题。要真正安心立命,却只能够仰赖于我们的德性之知。在这一个层次的体识乃必须存乎其人,的确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用田立克的话来说,人追问生命的意义的问题时,可谓一无凭依,只有倚赖生存的勇气(Couragetobe),跳进他所谓的“神学之环”(Thetheologicalcircle)以内,基督所提供的信息才有一种实存的意义。同样,超越性理之内在于人的生命,这在一般人来说,好像是十分玄妙而不可解。只有在阅历万般之后,终于体会到吾道自足,而进入儒家内圣之学的“解释之环”(Thehermeneuticalcircle),宋儒所讲的那些道理,才好像赤日当空,织毫毕露,无所遁形。在这样的有关生命的终极意义的追求之中,所牵涉的是根本的慧识,吾人所积累的经验知识于此至多只不过有一种参考的价值而已,最后乃必须作一实存性的抉择,究竟是为无神、为基督、为佛老,为儒家,此间必涉及一异质的跳跃。道统之说正是这一个超越信仰层次的问题,故所以对于圈内的人来说,却自有一确定的义理规模,尽可以还出它的理据来,层次分明,秩序井然,步骤深浅,有一定的理路线索可以遵循,绝非武断随意编织的结果。
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有云:
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子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又再传以得孟氏。……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
由是而由尧舜而二程,道统一贯。朱子且上溯伏羲黄帝,(注三)道统于以确立。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则曰:
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
于此可见朱子显然有担承道统之意。及后黄〓书朱子行状,乃曰:
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
以后宋史引其说,列代学者宗之不乏其人。陈荣捷先生指出,朱子之立道统,是以哲学性的理由排除汉唐诸儒,特尊二程,首标周子,旁置张子,而不及邵子,其言是也。(注四)
我们查考宋儒的基本观念,与先秦儒比较,差别当不在小。随便举几个例: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宋儒则最爱谈论性与天道的问题;子在川上之叹,宋儒说是在谈道体;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宋儒说此澈上澈下语也;从纯考据的观点看来,实在找不出这些说法与原典有什么确定的关联。而宋儒与先秦儒之间的主要差别,好像在宋儒大幅地引入了许多佛老的观念。再随便举几个例来说:宋儒最基本的观念是“理”,但在孔孟,理并不是十分重要的观念,反而是华严才昌言理事无碍的境界;又如太极在先秦也不是重要的观念,在宋儒之中,濂溪首倡之于太极图说,到朱子才变成了一个中心的观念,但朱子并未否认太极图的来源是出于道家的陈搏。其实朱子从不否认宋儒曾受到佛老的影响,语类曰:
近看石林过庭录载上蔡说,伊川参某僧后有得,遂反之。偷其说来做己使,是为洛学。某也尝疑,如石林之说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说,是怎生地?向见光老示及某僧与伊川居士帖,后见此帖乃载山谷集中,后又见有跋此帖者,乃僧与潘子真帖,其差谬类如此。但当初佛学只是说,无存养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养工夫。当初学者亦只是说,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谓伊川偷佛说为己使。(一二六)
据钱穆先生考据,此条某僧指灵源,其与潘淳子真一帖,人误谓之与伊川,朱子辨之。(注五)但奇怪的是,朱子于伊洛偷佛学为己使一语,却似不甚反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势必被逼得要问以下的两个问题:
(一)宋儒是否大段都是佛老之说?而且宋儒往往互相攻讦异己为佛说,此处究竟是否确有阳儒阴释之嫌?
(二)宋儒与先秦儒之关联究竟如何?究竟彼此之间是否有本质性的一脉相传的线索如道统说之所宣称者?抑或宋儒只是借古籍做幌子,骨子里是在说一套与先秦儒十分不同的新东西?
这样的问题根本涉及道统的观念究竟是否可以成立的问题,所以值得我们仔细来考虑。
先就第一个问题来说,由上节的解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宋儒与佛老之间确有一定的分疏。宋儒无疑是受到佛老的刺激而不能满足于传统的窠臼之内,此所以程朱诸儒多必须出入老佛有年而后返归六经,始知吾道自足。儒学要扩大,要应付佛老方面来的强大的冲击,就必须直捣虎穴,在不违背自己的基本精神的前提之下,汲取佛老的灵泉,来恢复自己的活力,这不是一件可羞愧、要隐瞒的事实。其实朱子对于当时儒学之不振感怀极深,批评不遗余力。语类有曰:
或问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体。(中略)。问明道云,自汉以来,诸儒皆不识此,如何?曰:是他不识如何却要道他识?此事除了孔孟,犹是佛老见得些形象。譬如画人一般,佛老画得些模样,后来儒者于此全无相着,如何教他两个不做大。祖道曰:只为佛老从心上起工夫,其学虽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从言语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会者亦只做一场话说过了,所以输与他。曰:彼所谓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胜似儒者多,公此说却是。(三六)
正淳云:某虽不曾理会禅,然看得来圣人之说皆是实理,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皆是实理流行,释氏则所见偏,只管向上去,只是空理流行尔。曰:他虽是说空理,然真个见得那空理流行。自家虽是说实理,然却只是说耳,初不曾真个见得那实理流行也。释氏空底却做得实,自家实底却做得空,紧要处只争这些子。(六三)
问:老子之言似有可取处。曰:它做许多言语,如何无可取?如佛氏亦尽有可取,但归宿门户都错了。(一二六)
由此可见,宋代程朱等大儒都是心胸开扩、不拘门户的豪杰之士,绝非抱残守缺之辈可比。佛老有长处,何不取之于佛老,只要儒者自己的基本精神不流失即可。其实朱子自受学延平以来,儒佛之分疏对他而言即为一重要问题。延平所指点的理一分殊固然是一大关键,但问题所牵涉的决非止此而已!朱子用心反省这一个问题,孝宗隆兴二年甲申三十五岁时有答李伯谏书,既辨儒释之相异,而又申伊洛与孔孟之相同。书中所论所包极广,兹摘录数节如下:
详观所论大抵以释氏为主,而于吾儒之说,近于释者取之,异于释者,在孔孟则多方迁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则无所忌惮而且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识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窃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语意之间不免走作。(中略)。
来书谓圣门以仁为要,而释氏亦言正觉,亦号能仁,又引程氏之说为证,熹窃谓程氏之说以释氏穷幽极微之论观之,似未肯以为极至之论,但老兄与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为重耳。然儒者言仁之体则然,至语其用则毫厘必察,故曰:仁之实、事亲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体用一源而显微所以无间也。释氏之云正觉、能仁者,其论则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来书引天下归仁以证灭度众生之说。熹窃谓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复礼则事事皆仁,故曰天下归仁。试用此意思之毫发不可差,差则入于异学矣。
来书云:夫子语仁以克己为要,佛氏论性以无心为宗,而以龟山心不可无之说为非。熹谓所谓己者,对物之称,乃是私认为己而就此起计较、生爱欲,故当克之。克之而自复于理,则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虚明纯一,贯彻感通,所以尽性体道,皆由于此,今以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则又是有心矣。如此则无心之说何必全是,而不言无心之说何必全非乎?若以无心为是,则克己乃是有心,无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为是,则请从事于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于此,而无心于彼,为此二本而枝其辞也。(中略)。
来书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谓性无伪冒,不必言真。未尝不在,不必言在。盖所谓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者也,曷尝不在,而岂有我之所能私乎?释氏所云真性,不知其与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则古人尽心以知性知天,其学固有所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异乎此,而欲空妄心,见真性,唯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犹所谓廉贾五之,不可不谓之货殖也。伊川之论、未易遽非,亦未易晓。他日于儒学见得一个规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来书谓伊川先生所云内外不备者为不然,盖无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者。此论甚当。据此正是熹所疑处。若使释氏果能敬以直内,则便能义以方外,便须有父子、有君臣,三纲五常,阙一不可。今曰能直内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岂数者之外,别有所谓义乎?以此而观,伊川之语可谓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谓有直内者,亦谓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处,故其发有差,他却全不管着此,所以无方外之一节也。固是有根株则必有枝叶,然五谷之根株则生五谷之枝叶华实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则生稊稗之枝叶华实而不可食,此则不同耳。参术以根株而愈疾,钧吻以根株而杀人,其所以杀人岂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故明道先生又云:释氏惟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元不相连属,但有间断,非道也。此可以见内外不备之意矣。(中略)。
来书云:儒佛见处既无二理,其设教何异也?盖儒教本人事,释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缓于见性,本死生故急于见性。熹谓既谓之本,则此上无复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谓儒本人事缓见性者,亦殊无理。三圣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谓性,孔子言性与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为本于人事乎,本于天道乎?缓于性乎,急于性乎?(原注:然着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为异说所迷,反谓圣学知人事而不知死生,岂不误哉!圣贤教人尽心以知性,躬行以尽性,终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诸天理,缓也缓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尽性至命方是极则,非如见性之说,一见之而遂已也。(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三书之第一书)
此书虽朱子思想尚未完全成熟时作品,然论儒佛分疏处,则与晚语类中言,并无二致。朱子拒绝和会之论是有很强的理据的。依儒者言,则人伦日用不可废,仁义礼智根于心,性理之实即本之于生生而容已之天道。其体用本末,皆与佛氏迥异,焉能以名言之相类而遂讳彼此之间有本质性之差别。
我们再看儒者之借佛老之说,取舍之间,极有分寸,绝非自弃立场者。而运用之妙,存乎其人。如濂溪之借用太极图,道家之本是做修养工夫的引导,以归于无极,而濂溪却将之倒转过来,讲出一符合生生之旨的形上学、宇宙论,肯定人伦日用,这在基本上是儒家精神,绝非道家的精神。又如二程吸纳佛家做修养的工夫,然所涵养证为儒家的性理,决非佛家的空理。而周张程朱由佛老吸取灵泉的果,则为儒家打开了一些全新的视域,增辟了一些重要的层面,复苏儒学的生命,岂云少补。同时儒佛之分疏并不因此而泯灭,且正因为儒家做出了可以和佛家匹敌的心性论、宇宙论,遂使得儒释之对比分清明,让后来的学者可以在其间作自觉的抉择,或者尝试一种更高综合。
如此,我们对于上面所提的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新儒家的确是家思想,决非老佛思想。儒释的分界线是不能不加以确定地维持的。实上程朱等大儒确自觉地把握住儒佛之间根本的分疏,不容和会混淆由此而阳儒阴释之论不攻自破,不值得我们重视。
其次,我们要查究宋儒与先秦儒究竟有怎样的关联,以及道统的念究竟能否成立的问题。
从纯考据的观点看,道统的观念显然是难以成立的。譬如朱子中庸句序追溯道统的根源引危微精一的十六字心传,经清儒考证,乃出于伪古文尚书,诗经原典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根本未必包含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的意思;子思是否中庸的作者也有疑问,近世学者更多以中庸成书乃在孟子之后者。再由考古的观点看,中国的信史断自商代起,则伏羲、黄帝、尧、舜还是属于神话传说的时代,未能确证实有其人。由此看来,道统之说是根据许多未证实的传说所构筑成的一种主观信念,未足采信。
但有趣的是,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儒与先秦儒的连贯性。把时间推回到远古正是先秦儒的一贯作风,所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也。其实孔子本人已经知道得清楚,谈过去的事有文献不足征的问题,所谓夏礼吾能言之,〓不能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三代尚且如此,更何况尧舜!但孔子却相信这里有一条一脉相承的线索,所以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这样推下去,虽十世可知也。孟子更演绎出一套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哲学观。宋儒所继承的正是这一类的观念。所以针对戴震的问题:朱子生于孔子之后一千多年,他怎么能够知道孔子的想法是什么?尊信宋学的人的回答是,千圣相传,只是此心,以心印心,自然不难了解圣人的命意所在。就论语所显露的孔子的性格看来,孔子不会是像今文学家所说,故意虚构出一套古代的理想的图画来托古改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是在真心向往尧舜的盛世,所继承的是文武周公的理想。而这是把道德融贯入现实政治的理想;朱子所崇信的也还是同样的理想,朱子自也不免过分理想化远古的历史,但当时疑古之风未盛,朱子所接受的只不过是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古史的图象而已!而朱子的坚强的信念的真正根源是在千圣相传之心,以及此心所把握之实理,这些是用切问而近思的方式,当下即可以体证的道理,不是时代淹远不可追索的上古遗迹。由此可见,道统成立的真正基础在于此心此理之体认。我们之所以尊崇伏羲、黄帝,只是因为大家一般共认,道曾经具现于伏羲、黄帝而已!其实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之中已经点穿;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由此可见,师道之尊犹有甚于君道,在教育文化上的开拓还更重要于现实政治上的建树。如此则伏羲、黄帝、尧、舜之功自可给人一种源远流长的感觉,同时也说明了创新自有传承为基础,然而即使退一步承认伏羲、黄帝、尧、舜不属于信史范围,也不能因此就完全推翻了道统的观念。因为道统说真正的枢纽点实在是在孔子。从宋儒的观点看,孔子比先王更亲切更明白地表现了道,在孟子则直接继承了孔子,故此我们不能不进一步考虑宋儒与孔孟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只许以一言来概括宋儒的中心理念,或者我们可以说,在宋儒的理解中是以生生之仁为天道与人道的根本。问题在我们能否在孔孟找到这样的思想的根据。
就表面来说,以生生言仁始于程子,不见于先秦之典籍,自可以说是宋儒之创见。但就此而言,则孟子道性善,也是孟子之创见,不见于孔子的论语。故问题的症结在,后儒之创发,是否与先儒在精神上一贯,这才是真正最中心的关键所在。
孔子之所以在儒家占有一最特殊之地位,是在于他首先提出仁为全德,为儒家思想指点了一个确定的方向。孔子虽不曾为仁下一个定义。但君子不可于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显然是孔子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故孔子虽未明言他的一贯之道究竟是什么,仁显然就是他的一贯之道,曾子以忠恕释之,朱子解释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二者显然为仁的表现之一体的两面,似乎不失曾子原意。而尽己可以与明明德配合,推己可以与亲民配合,大学显然也是发扬孔子的儒家思想的一项重要的典籍。孔子本人虽也未明言性善,但他指点出礼后乎,显然肯定礼仪在人性之中有一自然之基础。孔子一生学不厌,教不倦,就是相信人性之中有极大的潜能以向善。从孔子的思想看来,仁义不能是外铄的,到孟子乃明言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则宋儒之归本于孔子,奉孟子为正统,决不能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其次再谈生生的体证。论语虽绝少有关性与天道的讨论,但子贡不可得而闻也的证词并不表示孔子一定没有关于性与天道的思想。孔子描写自己学修的经过就曾明言五十而知天命,又曾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法。宋儒以子在川上叹曰的一段是形容道体,固不免想象力过分丰富。但孔子本人确曾倡导无言之教,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显然孔子的确相信天壤间有一无穷生力在作用,这样的思想与大易生生的思想是互相呼应的。在今日,我们自不可能再相信十翼皆孔子所作,但我们却不能够排除十翼之中有孔子思想的可能性,至少十翼之中大部分是儒门后学发挥孔子这一线索所传承的思想。在今天我们研究孔子,自必以论语为最主要的资料,但不能以论语为唯一的资料。最可靠的方法是我们用论语为间架去网罗其他相关的资料。而论语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一条践仁以知天的线索。孔子的教诲虽把重点放在前者,却不能完全排除了后者的可能性。孟子更明言尽心知性知天而指点了一条更为确定的进路。宋儒顺着这一个方向去推进,不能不说的确是孔孟的苗裔。
再讲到学庸。礼记之中当然大部分是儒门后学的作品。或曰,大学之中讲定静安虑得,不见得纯是儒家的思想。但这样的说法所犯的错误是把儒家思想当作一个静止的常体,事实上儒家的思想不断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没有理由不受其他的思想的影响,也没有理由不向别的思想汲取新的灵泉。问题是这些文献的中心究竟是发挥儒家的思想,还是别派的思想。大学讲三纲领八条目,这明显地是儒家的思想,增加了定静安虑得的修养工夫的次第,一点不显得突兀,也不使之变质成为了非儒家的思想。同理,中庸讲天命之谓性,诚的天道观,都是在本质上属于儒家的思想,与孔孟有着一脉相承的线索。易传之中成分当然更芜杂。但天地之大德曰生;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些都是显明地与儒家的天道观完全符合的思想。宋儒再更进一步发挥出理、太极的崭新的概念,有什么不可以?
事实上,朱子把学庸与论孟放在一起,组成四书,实在是深具卓识。四书之说自不始于朱子,但基于哲学性的理由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并化了那些大的力气为之作集注,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这却是朱子的功劳。朱子之立道统,显然是以内圣之学为规模。故于孔门特重颜曾,并谓孟子没后而遂失其传焉。汉魏以来,只得传经之儒而已!历代大儒如董仲舒、扬雄、文中子、韩愈辈,均于内圣之学并无贡献,故不包括在道统之内。一直要到明道,“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伊川赞其兄之学贵自得,始为宋儒尊为道之正统。但朱子在二程之前又推尊濂溪,此则其煞费苦心处。盖二程缺乏宇宙论的兴趣,中心虽牢固,而缺少集大成的意味。濂溪则别立蹊径,其通书与太极图说打通了易庸之间的通道,而归本于孔颜。这是儒学可以开展的一条新途径。横渠之西铭,二程极推尊,对于正蒙乃不无微词。横渠分别德性之知、见闻之知;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固无乖于正道。但他所销融的清、虚、一、大等观念乃不免歧出,思想表达也不完全圆熟,故只能放在辅翼的地位。至于康节则重象数,其思想的道家意味太重,故既未采入近思录,也不见于伊洛渊源录。钱穆先生谓朱子并非不看重邵子,(注六)此则固然,然朱子也非不看重司马温公,但温公为史家,故也不包括在道统之中。文集卷八十五,有六先生画像赞,即将康节、涑水与濂溪、二程、横渠平列。由此可见,朱子的容量大,架局广,但取舍之间层次分明,法度极为谨严。朱子一生基本用心究竟何在,于此可以思过半矣。
讨论至此而我们也可以对前面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作一个答复。宋儒的思想与先秦儒的思想之间的确有一种本质性的关联。我们至少可以说,宋儒是在不违背孔孟的基本精神之下,受到佛老的冲击,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新儒家的思想。
但我们这样立论,并不是说,儒家就不可以发展出另外的不同思想。事实上,孔子的后学也可以发展出荀子的性恶论,由荀子的思想再推进一步乃可以发展出韩非的法家的思想。但这样的思想却已经脱离了儒家的基本的规模。
其次,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儒家都要同意朱子这种儒家正统的意见。孔子之后,早就有儒分为八的说法。秦火之后,则有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的对立。嗣后又有汉宋的差别;清儒即有以反宋明儒为职志者,好像颜元即以之为丧失了原始儒家的精神。儒家的思想本可以有不同发展的可能性,我在这里只是说明,宋儒是有一条线索可以声言他们是由孔孟以来一脉相承的发展。他们也提出了一定的标准,把某一些思想包含在道统的范围之内,或排拒在道统之外。这一个标准即宋儒体证得最真切的内圣之学的规模。以此而汉唐号称盛世,在思想的层面上却于儒者内圣之学无所增益而被弃置在一旁。同样,宋明儒的慧识到了清朝既已经无以为继,则由宋明儒的标准看乃不能不谓之为一种堕落,一直要到当代熊十力先生出来,才致力于重新恢复这一个传统的思想。
如果以宋学为标准,则内在中心的体证是最重要一件事,章句的解释其余事耳,学问的目的是在见道,其目的本不在词章记诵,更不在客观的饾饤考据的工作。对于文字的解释,一以主观的体验为基础,故此对于文义的引伸,不只不当作一种错误或过失,反而被当作一种慧解的印证看待。只有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宋儒对于“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子在川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一类的新释。这样的新释可能是越出了古典的原义,(正如海德格所谓的doing violence to the text)但却不一定违反原典的精神。而慧识的传递,比章句的传递,对宋儒来说,显然是具有远更重要的价值。
我并不是说,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不会产生一些问题,或者构成一些缺点。在这样的精神的主导之下,客观的学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然而我们必须了解,道统与学统本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若纯由道统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够问,生生之仁的体证是不是反映了生命的真理,其余有关考古、历史、考据的问题都不是十分相干的问题。
当代西方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在“耶稣的研究”(Jesuso-logy)与“基督的信仰”(Christology)之间所作的区分,(注七)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依田立克的说法,有关耶稣生平的研究,譬如耶稣是否生在一个木匠之家,他的许多事迹是否真实的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范围,所得到的结论至多只有较低或较高的盖然性。但是基督道成肉身,十字架的象征所宣泄启示的是,一个生命(现实)的终结是另一个生命(精神)的开始,这里所传达的消息却是绝对的真实,它根本不是知识的对象,只是信仰的对象。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伏羲、黄帝的传说的真实性只有较低或较高的盖然性,这些是历史、考古可以研究的对象。但肯定仁道遍满,建立道统之说所牵涉的却根本是儒家终极信仰的问题,非知识所行境。
我们的经验知识,用宋儒的术语来说,也就是我们的见闻之知,只能够用来发现现象世界内部的关联,而不能够处理有关我们的终极托付的问题。要真正安心立命,却只能够仰赖于我们的德性之知。在这一个层次的体识乃必须存乎其人,的确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用田立克的话来说,人追问生命的意义的问题时,可谓一无凭依,只有倚赖生存的勇气(Couragetobe),跳进他所谓的“神学之环”(Thetheologicalcircle)以内,基督所提供的信息才有一种实存的意义。同样,超越性理之内在于人的生命,这在一般人来说,好像是十分玄妙而不可解。只有在阅历万般之后,终于体会到吾道自足,而进入儒家内圣之学的“解释之环”(Thehermeneuticalcircle),宋儒所讲的那些道理,才好像赤日当空,织毫毕露,无所遁形。在这样的有关生命的终极意义的追求之中,所牵涉的是根本的慧识,吾人所积累的经验知识于此至多只不过有一种参考的价值而已,最后乃必须作一实存性的抉择,究竟是为无神、为基督、为佛老,为儒家,此间必涉及一异质的跳跃。道统之说正是这一个超越信仰层次的问题,故所以对于圈内的人来说,却自有一确定的义理规模,尽可以还出它的理据来,层次分明,秩序井然,步骤深浅,有一定的理路线索可以遵循,绝非武断随意编织的结果。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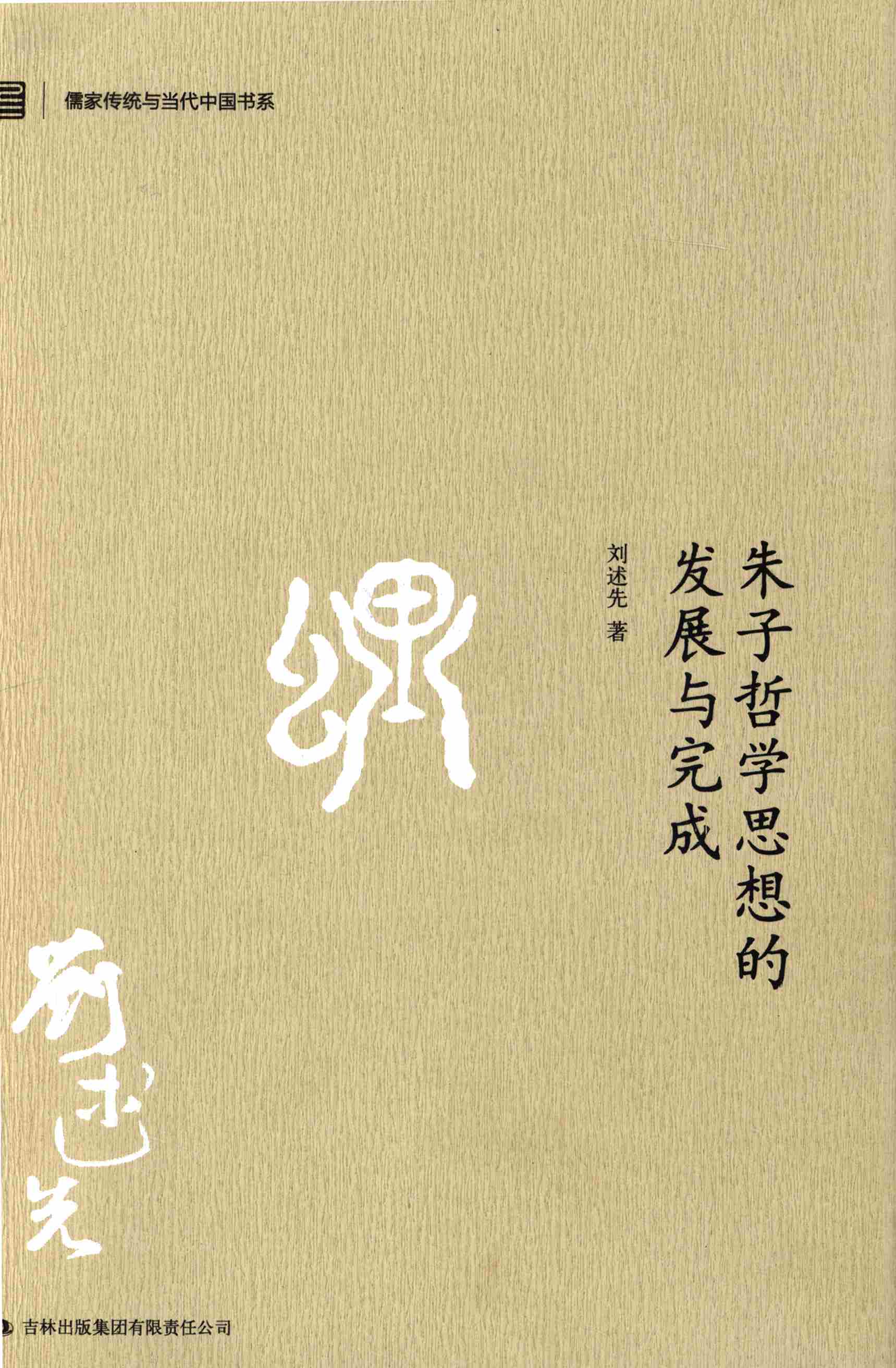
《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
出版者: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剖析了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的学思内涵,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刘述先先生关于宋明儒学研究的成就及其学术思想观点。全书正文分为“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朱子哲学思想的完成”“朱子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之现代意义”三部凡十章。部四章论述朱熹的家学师承、性格志趣、为学进路及其参悟中和与论辩仁说的学思经历,勾勒出朱熹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第二部两章呈现朱熹的心性情三分架局的人性论及其理气二元不离不杂的形上学,厘定了朱熹哲学思想的完成形态。第三部四章梳理朱熹哲学思想自南宋以降与皇权政治、功利取向、陆王心学以及佛道诸家的摩荡,并基于现代观点评论了朱熹本体论、宇宙论、践履论、政治论的得失。附录七篇以专题形式对朱熹生平思想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阅读
相关人物
陈荣捷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