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朱子“曾点气象论”的影响
| 内容出处: | 《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393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朱子“曾点气象论”的影响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41 |
| 页码: | 347-387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这段讨论主要涉及到朱子与王阳明在“曾点气象”的观点上的差异以及对儒学发展的影响。朱子以其影响力统一了人们对“曾点气象”的认识,成为权威看法,直到陈白沙、王阳明出现才有所改变。人们对“曾点气象”的看法反映了对儒学的理想境界与工夫的不同看法,被视为儒学与佛老之争的具体体现。此外,朱子后学与阳明后学围绕“曾点气象”展开了另一方面的争论,朱学注重从“天理”的角度解释,而阳明心学更注重从“良知”、从率真、从容的角度解释。朱子与王阳明的不同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反映了理学体系中不同流派的异同。朱子后学大多被朱子的光环掩盖,几乎没有能在其思想基础上开创新领域的人物。黄震是个例外,他强调朱子思想中“与点”的深远意义,并与三子的答问之正进行对比。东发则进一步强调三子为国之事的正当性,将“曾点气象”完全排除在儒学之外,对朱子和明道的观点进行颠覆。 |
| 关键词: | 朱子 曾点气象论 影响 |
内容
在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中,朱子的出现绝对是一个分水岭。他以其强大的影响力统一了此前人们对此问题的不同认识。他的“曾点气象论”也长期成为对此问题的惟一权威看法。这种情况直到明代中期陈白沙、王阳明出现后才有所改变。总的看来,朱子之后人们对“曾点气象”的看法,仍然较为集中地折射出了其对儒学的理想境界与所用工夫的不同看法,也仍然可以被归纳为敬畏与洒落之争,被看成是儒学与佛老之辨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此之外,人们围绕“曾点气象”还展开了另一个方面的争论:那就是朱子后学大多从“天理”的角度诠释“曾点气象”,极力渲染其中的理性因素;相对而言,以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系则更注重从“良知”、从率真、从容的角度来诠释之,把它理解为一种心境,一种感情。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朱子与王阳明对“曾点气象”的不同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他们及其后学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体现出了理学体系中不同发展流派之间的深刻异同。在明代及以后,朱学与王学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制约推动了儒学的整体发展,我们也能通过二人及其后学对待“曾点气象”的态度,窥探到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大势。
我们说,朱子后学与阳明后学的最大不同是,虽然朱子的直系后学人数众多,但他们都被掩盖在了朱子的巨大光环下。真正能在朱子思想的基础上开出新天地的人几乎没有。“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局面直到明初才有所扭转。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了其弟子们对曾点了讨论上,无论是陈北溪、黄直卿、金履祥,还是真德秀(字景元,后更希元,学者称西山先生,1178——1235)等人都只是坚守着朱子思想的一隅而无所发挥。与上述诸人相比,黄震似乎是个特例,其论“曾点言志”一节,则曰:
四子侍坐,而夫子启以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盖试言其用于世当何如也。三子皆言为国之事,皆答问之正也。曾皙孔门之狂者也,无意于世者也,故自言其潇洒之趣,此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予,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皙浴沂咏而归之言,若有触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继答曾皙之问,则力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三子者哉?①
东发为朱学后劲,黄宗羲称其“《日钞》之作,折中诸儒,即于考亭(即朱子)亦不能苟同”②。东发此论,就被钱穆先生指为“甚得论语‘与点’一欢之深旨,较之《集注》似更允惬”③。我们说,东发此论的核心,是强调三子之答志在为国为正,而曾点无意于世之答为非正。同时,东发也划清了孔子之志与曾点之志的界限:认为前者为适人之适者,后者为自适其适者。这无疑把“曾点气象”彻底逐出了儒学的阵营,也是对朱子和明道之“曾点说”的彻底颠覆。
东发论“曾点气象”的最大特色,还在于对于世人之论该问题之种种玄虚的猛烈抨击:
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甚至谢上蔡以曾皙想象之言为实,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为曾皙独对春风,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于谈禅,是盖学于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华言志,自是实事。”此正论也。又曰:“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此语微过于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曾皙岂能与尧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谓曾皙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咏归之乐,指为老安少怀之志,曾皙与夫子又岂若是其班哉?窃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尔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此专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怀之志,天覆地载之心也,适人之适者也;浴沂咏归之乐,吟风弄月之趣也,自适其适者也。曾皙固未得与尧舜比。岂得与夫子比,而形容之过如此。亦合于其分量而审之矣。①
我们知道,小程子在论“曾点言志”一节时,曾针对时人一味渲染“曾点气象”的流弊,突出强调“子路、冉有、公西华言志,自是实事”。但是,或许是为了回护孔子,或许是为了维护“曾点气象”的正面价值,总之小程子并没有指责曾点,而只是批评时人的一味好高。这里,东发于时人包括朱子盛谈曾点的正面价值没有丝毫的共鸣,而对之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他这样做虽然突出了儒学传统中强调经世致用的优先性,却也使得朱子等人维护“曾点气象”之正面价值的努力与苦心失去了意义。当然,东发强调虚实之辨,其实正是对小程子和朱子一贯精神的继承。只不过,朱子并没有因为是人竞谈与点的流弊而取消“曾点气象”本身之价值,而是既要力图避免此弊端,一面又要大力挖掘“曾点气象”在教化社会中的正面价值。
东发还对谢上蔡的一味好高而陷于佛老,展开了批判。从《黄氏日抄》可见,东发每每指出谢上蔡是杨慈湖(杨简,字敬仲,世称慈湖先生,1141—1226)的思想源头,而其批判谢上蔡者,未尝不是在批判他的同乡杨慈湖辈。今天看来,东发此论颇为平常。但是,理学自濂溪起既有好高之弊,这一风气虽然受到了朱子的暂时抑制,却并没有被完全扭转,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由此,东发此论乃属不得不发之列,更不能以老生常谈视之。
在元初,经常吟咏曾点的是刘因(初名骃,字梦骥,后改名因,字梦吉,后人称静修先生,1249—1293)。我们很容易从他的诗作中读出那种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隐士心态,能看到其所理解的“曾点气象”与理学一系的不同:
巧隐林旁无四邻,背山向水得天真。风光正及二三月,童子同来六七人。十日得闲须小醉,一年最好是深春。鸟声似向花枝说,曾见无怀有此民。①
晋楚英雄管晏才,当时真眼尚谁开。狂生携着鲁儿子,独向舞雩风下来。②
独向舞雩风下来,坐忘门外欲生苔。归时过着颜家巷,说与城南华正开。①
青天仰面,卧看浮云卷。苍狗白衣千万变,都被幽人窥见。偶然梦见华胥,觉来花影扶疏,窗下鲁论谁诵,呼来共咏舞雩。②
于时吾与子,咏春风于舞雩,濯尘缨于沧浪,来登斯楼,终日徜徉,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觞,渺天地于一粒,随造化而翱翔,期万代于咫尺,顺四时而行藏,下视万物杳焉,如千里毫芒,然后嚣嚣然,洋洋然,庶乎可以与天下俱忘者矣。③
刘的这些诗作中,颇有隐者的恬淡情绪和老庄气息。应该说,隐藏在诗人刘因背后的,一定会有那种无法明言的失意感与幻灭感。于刘因,早年的激进与中晚年后的恬淡。其进其隐,背后都包含有许多无人知晓的故事。《元史·刘因传》在论及刘因时就提到:
欧阳元尝赞因画像曰: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论者以为知言。④
同样,《宋元学案》中虽然提到刘因与康节和曾点相近①,但却还是认为静修有功于圣门,并视之为与许衡并列为“元之所藉以立国者”②。应该说,若论其事,则刘因之隐毕竟是事实,而若论其志,则其怀有济世之志也是真实的。是无情的现实浇灭了刘因矢志报国的雄心,使他不得不在出处去就上煞费苦心,最终还是成为了事实上的隐者。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静修用文字和自己的生活诠释出了“曾点气象”所无法彻底摆脱的一面——与遗世思想难以彻底划清的干系,而这也正是朱子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有明一代,学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学虽然在明初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但随着程朱思想被官方化,其自身也在走向僵化,此诚如《明史》所言:
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字正夫,号月川,1376—1434)、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③
可见,明初诸儒的一个明显特色是株守,用容肇祖先生的话说,就是他们“简陋了,腐化了、退化了”④,也丧失了思想的原创性。如薛瑄(字德温,号敬轩,1389—1464,陈来先生的《宋明理学》认为薛瑄死于1465年,不确)竟然喊出了“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云云,其整个思想界的沉闷气氛可想而知。明初诸儒的另一个特色是,宣扬敬畏和清苦严毅的个人作风有余,讲和乐自得之境不足①。这更加剧了理学内部所固有的个体意义上的心(重自由自在)与具有形上意味的性之间的紧张②。此后,以陈白沙、王阳明为代表,学界再次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追求自由、自主、活泼泼的精神也一跃成为时代的主流,而讨论“曾点气象”的真正高峰,也适时地出现在了陈宪章、王阳明之际。
总的来说,与宋儒尤其是朱子相较,明儒不再追求思想上的全面,而是更强调其言说的个性化,注重发挥本人思想中的独特之处。由此,明儒多有一偏之论,也多有惊世骇俗之论,而其在隐微细节的辨析上则远远超越了宋儒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时人围绕“曾点气象”的争论也进一步明朗化了。大致形成了以王学与反王学(朱学)或是王学修正派之间的两军对垒。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近。”④黄梨洲此论,指出了陈黄二人思想的一致性一面。就本文而言,他们的共性又表现为其对“曾点气象”的特别推崇上。
前人在论及明代心学的兴起时,未有不首提陈献章(字公免,别号石斋,后人称白沙先生,1423—1500)者,盖白沙先生为扭转一时风气的人物。陈白沙论学以自然为宗,论境界以曾点、邵康节、周濂溪为的,其基本思想被梨洲概括为:
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远之则为曾点,近之则为尧夫,此可无疑者也。①
在梨洲眼中,白沙之学既以虚静为根本,又能兼顾到日用常行的分殊,既强调未尝致力,又能做到应用而不遗,其“气象”与“曾点气象”相当。而白沙之论曾点,则明显体现出了对程朱理学长期发展之日趋沉闷,日渐僵化的反动:
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思想,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时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若无孟子工夫,骤而语之以曾点见趣,一似说梦。会得,虽尧舜事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②
白沙此论,既推崇曾点之见趣,又不忘强调孟子之工夫,表明上看也颇为圆融,也在强调不能空说气象。但我们还是能够看的出,白沙的理想之境是曾点襟怀,而不是庄敬严毅的状态。而且,他还有意地在强调这一对立。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则在薛瑄、曹端、胡居仁诸人大力强调敬畏有些过头的时候,白沙能起而宣扬曾点襟怀,不能不说具有明显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容肇祖先生认为:“陈献章的思想,他的重要的贡献,是要将个人的思想由书本的束缚及古人的奴隶之下解放出来。”①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宣扬主静和自然,毕竟更容易走向佛老的一边。黄宗羲对此就很中肯的评论到:“然而此处最难理会,稍差,便入狂荡一路。”②在白沙那里,虽然他也有说梦之戒的自觉,但是儒学本有的那种强烈的担当精神还没有发露出来。他更缺少像阳明那样对良知这类观念的正面强调,终给人以“失却最上一层”的感觉③。他也和刘因一样,徘徊在隐士与非隐士之间④。
相对于陈白沙而言,王阳明的思想则更为圆通,也更能凸现儒学的真精神。王守仁(字伯安,1472—1529,世称阳明先生)的思想,就其直接意义来说,是对朱子学的反动;而就时代论,阳明倡导的“心学”是在程朱理学逐渐僵化的情况下出现的思想运动,因而具有全新的气象,也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新解放。由于前贤们对阳明学的精神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此不赘言。
概括而言,论及“曾点气象”,阳明不再遵循朱子以“天理浑然”来注解“曾点气象”的理路——而是转而认为“曾点气象”妙在其狂、其乐,妙在无入而不自得,妙在其是良知的自然发露。这就是说,朱子论“曾点气象”,是围绕理字展开,而阳明论“曾点气象”,则围绕良知(心)展开,这也大致是他们思想异同的一个集中体现。
王阳明曾经以“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做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①的诗句相标榜,把狂者胸次作为其个人为学精神的核心。当然,其本人的气象也与后人心目中的“曾点气象”多有吻合。王自己也曾说过:
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②
在阳明看来,曾点“狂”的前提是他“无意必”、“不愿乎其外”,是以我为主的气概,是自信本心的表现。而他自己也正是因为能做到以我为主,才能使“良知”自然流露:
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③
于他来说,“行不掩言”正与乡愿态度相反对,其所体现出的,是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精神,也正是良知的本然呈现。既然良知时时知是知非,故行动一依良知而行,自然就能做到从容中道,他又有云:
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干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①
阳明认为狂者离圣人只有一克念的距离,因为狂者其志高,其心未坏,这是乡愿者所无法企及的,其对曾点之推许远高于朱子。
在阳明心中,理想人格本来就是多元的——人之才气不同,因此要随才成就,狂者就要成就其狂,而不要去强行改变其本性:
圣贤之学不是这等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以此章(即‘曾点言志’章)观之,圣人何等宽宏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者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的?①
阳明论曾点,最强调他的狂的一面,这也与他提出道学革新的激情与勇气是分不开的。恰如陈来先生所言,曾点式的狂者胸次是构成阳明思想“无”之境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另一方面,阳明也注意到了时人虚说本体,玩弄光景的弊端。他无论是论气象还是论良知,都始终注意强调在工夫上见本体,着力凸现儒学的精神:
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诸生入谢,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敎,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③
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①
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②
阳明很清楚,狂者虽然高于世俗之人,但离真正的圣道还很远,而若只有曾点之狂,而无下学工夫之实,其流弊是危险的。阳明自述对于“良知”的体认过程,则有“千死百难”之语,确实不可以简易空疏、玩弄光景者视之。
此后,王门后学中的泰州一派更是凸显了“曾点气象”中的“乐”、“狂”的一面,他们以狂者自任,高扬儒学的担当精神,倡导“乐学”境界,时时以济世为己任,以一腔热诚积极为实现理想而奔走,“无有放下时节”③。在他们看来,“曾点气象”大体代表着以下的特点:它是人本真心体的自然发露、不假事为、天然、率真、和乐、独立自得、自由自在等,这些都是与其主张要高扬个人主体精神的宗旨是紧紧相连的。不过,他们似乎都有自信太过的嫌疑,不但高唱“现在良知”者有之,就是高唱“良知当下现成”、以解缆放船为工夫者亦然,有的甚至公然宣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是床上之床也。”①虽然以乐为道是其自信本心的表现,但是这种说法毕竟离冲开儒家纲常的束缚不远了。
我们说,尽管许多学者认为,晚明近乎放荡和享乐的风气与阳明后学有关,但我们还没有发现真正的阳明弟子中有所谓“鱼馁肉烂”的现象。即使就是被目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笃吾,又号温陵居士,1527—1602)、颜钧(号山农,1504—1596)、何心隐(原姓梁,名汝元,字夫山,1517—1579)之辈,其文字中也没有特别出格的东西②。相反,我们多能发现泰州学派人的古道热肠,发现他们对于儒学近似于宗教徒式的痴狂。
在当时,从白沙、阳明首推“曾点气象”开始,同样也就出现了反对过分宣扬曾点之乐的声音。随着人人竞相讨论“曾点气象”,反对“曾点气象”的声音也同时强大了起来。这一个案也是明代中期儒学敬畏与洒落之争的典型体现。
早在阳明之前,胡居仁就曾提出:“‘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虽也形容有道气象,终带了些清高意思。”③胡为朱学后劲,自然不便对延平的上述观点多有微辞,但是他还是从道德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宣扬洒落者泼了冷水,认为他们清高有余而担当精神不足。在阳明同时,与阳明直接形成对立的是夏尚朴(字敦夫,号东岩,1466—1538),他指出:
寻常读“与点”一章,只说胸次脱洒是尧舜气象,近读《二典》、《三谟》,方知兢兢业业是尧舜气象。尝以此语双门詹困夫(不详),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复斋(不详)有诗云:“便如曾点象尧舜,怕有余风入老庄。”乃知先辈聪明,亦尝看到此。①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夏氏和詹氏兄弟对当时人人竞言“与点之乐”的反感之情,也能看到其对时人竞言“曾点气象”之流弊的警觉。对他们来说,敬畏与洒落正好对立,过分宣扬了洒落的一面,也就抑制了敬畏的一面,片面地宣扬“曾点气象”,无异于失掉了儒学的基本价值观,而流于佛老。夏还撰写了《浴沂亭记》重申上述思想,其中亦云:
旧尝游太学,得逮事章枫山先生(章懋,字德懋,号暗然子,1437——1522。章讲学于枫木庵中,学者因曰枫山先生,《明儒学案》有传),先生一日谓予云:陈白沙应聘来京师,予在大理往候而问学焉。白沙云:我无以教人,但令学者看‘与点’一章。予(章)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谓专理会与点意思,恐入于禅。白沙云: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朱子时人多流于异学,故以此救之;今人溺于利禄之学深矣,必知此意,然后有进步处耳。予(夏)闻其言恍若有悟,信以洒落为尧舜气象。后读《二典》、《三谟》,乃知兢兢业业方是尧舜气象,孔颜之乐端不外于此矣。故周子有礼先乐后之训,而程子亦云敬则自然和乐,和乐只是心中无事,是皆吾心之固有,非有待于外求者,必从事于敬,庶可知其意味之真耳。岂必放浪形骸之外,留连山水之间,然后为乐其乐耶?因以告夫同游二三君子,且着诸篇以自警焉。①
“我无以教人,但令学者看‘与点’一章”。白沙此论,在明初朱学依然强盛之际提出,其冲击力与解放性可想而知。固然,明初思想之僵化需要通过讲“曾点气象”来予以破除,这也有救时之弊,因病施药的意味。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只要一讲“与点”就会流于禅学。但是,夏氏、章氏的忧虑毕竟不是空穴来风。其后来历史的发展反倒正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二程就提到过救人为学之弊端如扶醉人,需要两面扶持,但主一偏,其为害就不可避免。我们也能在胡居仁等人的文献中发现相同的忧虑。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明代思想风气的转换。
同时,《明儒学案》中还载有:王文成赠诗有“舍瑟春风”之句,(夏)先生答曰:孔门沂水春风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可见,夏与王一个侧重宣扬洒落,一个重在强调敬畏,态度恰好相对。从以上引文中可知,夏氏的这一主张绝非他一人的孤声先发,而是代表了一批人的共同观点①。当然,若细考之,则王门后学内部关于“良知异见”的种种争论,也未尝不包含敬畏与洒落之争的因素。只是对此一点,前贤已经多有论及,这里不再多言②。
以提倡敬畏情来对抗曾点之乐,显然是出于对时人一味寻乐所可能带来的流弊的警觉,也深刻地反映出了理学内部在敬畏与洒落问题上的冲突。在思想史上强调敬畏与洒落的冲突自古已然,但这一矛盾只是到了此时才被人自觉地意识到了,也更被有意地凸显了。
必须指出,上述资料只是反映出了夏东岩思想的一个侧面,而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六十七册所收的《夏东岩先生诗集六卷》中,我们却能看到一个推尊白沙,提倡洒落的东岩形象。仅举四库馆臣对《东岩诗集八卷》的提要③,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多涉理语,近白沙、定山(庄泉,字孔旸,号定山,1413—1475)①流派,集中《读<击壤集>》绝句云:“闲中风月吟边见,始信尧夫是我师。”其宗法可知也。②
东岩的诗集中,宣扬吟风弄月的诗作非常多,文中提到陶潜,东坡,尧夫,白沙的地方也屡屡皆是。如其《题白沙集后》云:岭海谁希贤圣踪,白沙真有古人风③。这表明东岩也没有把敬畏和洒落绝对对立起来,并不主张完全用敬畏来代替洒落。
客观的说,以上心学一脉对“曾点气象”的推许,对于解放人们深受理学教条的束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人对此也都有极高的评价。不过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虽然晚明时期对“曾点气象”的过分渲染,直接导致了时人道德意识的淡化,也确实与被喻为“王学末流之弊”的时代精神危机不无干系,以上所引诸人对这一倾向的警觉与批判自然不无道理,但是反过来说,若只讲敬畏,不讲洒落,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会再次使人们的思想走向僵化,甚至会扼杀人们的主体性。事实上,如何处理敬畏与洒落之间的关系,最大可能的实现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同时又能保证人的个体自由的充分实现,又尽可能的避免包括极端个人主义、玄虚思想、功利主义在内的各种一偏之论对社会的不良影响,这始终是朱子在论“曾点气象”中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哲学史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直到今天,展开对此问题的深入探究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说,单就这两种思潮本身而言,它们都各有利弊,若片面强调其中的任何一方而无所限定,都会出现偏差。相反,只有出现这两种思想交相争辉,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局面,才能够有效的消解与抑制片面宣扬其中的一方所可能出现的弊端。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解决该问题的一个思路吧。
在明代理学内部围绕“曾点气象”展开论争之时,开始有学者要根本取消这一问题,这个人就是杨慎。杨慎(字用修,号升庵,1488—1559)对“曾点气象”的理解颇为另类,颇能开清人学风的先声。我们只有把他的言论放在明清之际思想转变的大背景下,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他的观点的价值。由于前贤已对此有过很多的论述,这里只是简单地提示一下①。总的来说,在杨慎的时代,社会及学术领域正在酝酿着全方位的变革,而由理学向经学进而是礼学的转变,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这一浪潮中,提倡怀疑和走出宋明儒者,提倡实学者渐成潮流。杨慎就是这一潮流中的先驱人物。论及“曾点言志”一节,杨慎强调:
四子侍坐,而夫子启以“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盖试言其用于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为国之事,答问之正也。子路乃率尔以对,先蹈于不辞让,而对之非礼矣。夫子哂之盖哂其不逊,非哂为国也。曾皙是时手方鼓瑟而心口相与,曰:夫子其不悦于为国乎?又见赤与求之答,夫子无言,窃意夫子必不以仕为悦矣。故一承“点,尔何如”之问,从容舍瑟而试问曰:异乎三子者之撰!盖逆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点乃为浴沂咏归之说,盖迎合之言,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与,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漠之滨,而忽闻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独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饮水之乐,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至于三子出而曾点后,盖亦自知答问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独与,故历问之。而夫子历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二三子哉?①
对于杨慎,造伪和以出名为目的的各种翻案是他被人经常提到的话题。这段文字就是一个翻案的典型。我们甚至可以用标新立异来定位杨在说这段话时的内心世界。他不惜设身处地的带曾点立言,为其设计了一段充满机心的内心独白,于是就草草把曾点的言说定性为“迎合之言,非答问之正也”。如果说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朱子等人的曾点论固然难以站得住脚,那么杨慎的观点同样也是想当然的产物——这一添字解经的做法比宋儒之好出己意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杨慎所注意的也正是很多人会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孔子不与“皆言为国之事”的三子,却要与颇有些自得其乐的曾点呢?事实上,只要我们越是把注意力转向《论语》的文本本身,就越会感到宋儒种种解说的不可信,也就越会激发人去探讨孔子与点的真正原因①。杨慎接着指出:
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但欲推之过高,而不知陷于谈禅,其失岂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华言志,自是实事,此正论也。又曰:夫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②。又曰:上下与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尧舜可以当之。曾点何如人,而与天地同流,有尧舜气象乎?且圣人之志,老安少怀,安老必有养老之政,怀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隐居放言亦为政之事也。点之志与圣人岂若是班乎?此言或出于谢上蔡之所录,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纵真程子之言,吾亦辟之矣。程子之贤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也。点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论,且与琴张、牧皮为伍,琴张、牧皮又可与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学者循声吠影,徒知圣人之所与,而不知圣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陈归鲁,欲裁正之者,正为皙辈。惜乎不知所以裁点之事,而徒传与点之语,使实学不明于千载,而虚谈大误于后人也。朱子晚年有门人问与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话,《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工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吕与叔……又因程子吟风美月之言,而演为心斋之说。心斋乃庄子之寓言,此诗不惟厚诬曾点,又嫁非于颜子矣。其去竹林七贤、南朝八达者几希。审如是,何不径学庄列而学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历聘卒老,于行荷蒉、晨门、长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讥讽,而夫子之辙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岂以不仕为高者耶?充点之志而不知圣人之裁,则与桀溺之忘世,庄列之虚无,晋人之清谈,宋人之禅学,皆声应气求,响合影附,不至于猖狂自恣,放浪无检不止也。鼓之舞之流于异端而不觉者,岂非尧舜气象一言为之厉阶哉?①
宋人尧舜气象、天地同流之说又过矣。曾皙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为此言以销壮心而耗余年。此风一降则为庄列,再降则为嵇阮矣。岂可鼓之舞之推波助澜哉?②
这里,杨慎重在抨击时人的各种“曾点论”是“谈虚好高之习”,进而认为曾点之志“与桀溺之忘世,庄列之虚无,晋人之清谈,宋人之禅学”,乃至与佛老之学了无分别。他的这一观点以及“纵真程子之言,吾亦辟之矣”的精神,我们会在更多明清之际学者们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精神也可以概括为崇实二字,体现出了鲜明的批判精神。当然,我们也大可不必如钱穆先生那样,一定要把这种精神和王学联系起来①,试图在理学中为它寻找渊源。另外,有一点也需要我们注意,那就是为杨慎所指出的,朱子晚年不喜人空言曾点,空言气象,这一点概括得还是很准确的。
至于杨慎文中所提到的观点,几乎是黄震观点的翻版,只是增添了一些更具煽动性的文字罢了,不必详做评论。
晚明之际,有感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学者纷纷转而强调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强调儒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之维,其代表当属东林学者和刘宗周。在一定意义上,这也表明,朱子学在当时重新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东林学者基本上站在了王学的对立面(他们又都对王学有所继承),大力批判王学末流的种种流弊。要言之,他们把批判的中心,指向了当时甚嚣尘上的“无善无恶”说和空谈性命、一味寻乐等诸时弊,呼唤大家关心国计民生,呼唤儒学向经世致用复归。这种救世的见解,是东林学派的真精神。正是出于这一缘故,东林学派都对“追求独乐”之属,持一种极为严厉的批判态度:
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②
部中甚安闲,尽可静养,但学者以天下为任,不以一部为职,念至此,无处著一乐字矣。①
问高忠宪(高攀龙):“明道许康节内圣外王之学,何以后儒论学只说程朱?”忠宪曰:“伊川言之矣。康节如空中楼阁。他天资高,胸中无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②
此前已经有很多人认为“曾点气象”有玩世意,但是这些话出自东林党人的口中,却具有格外的震撼力。在他们看来,贞定人道德本心的有效手段就是扎实的工夫,他们呼吁:“不患本体不明,只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处不合,惟患分殊处有差。必做处十分酸涩,得处方能十分通透。”③这也是朱子学精神的体现。
已有许多学者指出,晚明之际在社会领域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士人之心态及生活理念都和前代大相径庭——更注重人的感性一面,更注重人的个体之维,更注重享乐。在此大背景下,东林诸贤所呼吁者,对于维系时代的凝聚力,对于保持社会的基本道德导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也许是时代使然,东林学者基本上都缺乏对朱子宣扬“曾点气象”的苦心的同情之理解,其立论也较朱子为浅。
继东林诸贤之后,能进一步从理论上集有明学术之大成,而自觉以救王学末流之流弊为己任者,则曰刘宗周先生。刘宗周(初名宪章,字启东,一作起东,号念台,学者称其为蕺山先生,1578—1645)是晚明的最后一个大理学家,他的去世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思想深刻地反映着时代跳动的脉搏,近来已经成为了学界研究的热点①。
蕺山为学之绝大精力,在于修正王门后学之流弊:针对其讲无是无非而大讲意根独体之良;针对其刊落工夫、虚说本体而力倡绵密细致的心地工夫:
学者只有工夫可说,其本体处直是着不得一语,才着一语便是工夫边事,然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大抵学者肯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若工夫之外别有本体可以两相凑泊,则亦外物而非道矣。②
上述观点和朱子高度一致,而他的“曾点气象论”,也透露出了独有的消息:
圣人之志,以老安少怀为极致。事即宇宙事,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此洙泗学术之宗也。群居讲求,莫非用世之道。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矣,如不用我,守此以藏矣。故由之有勇知方,求之足民,赤之礼乐,其施为气象不凡矣。
曾点狂者也,胸次洒脱,志趣超远,舍瑟一对,悠然独见性分之全,素位而行,浮云富贵,莫(暮)春即景,若曰吾何以人之知不知为哉?吾有吾时,吾有吾地,吾有吾群,吾有吾乐而已。盖忧则违之之志也。故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子不云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点也见及此,进于道矣,能无与乎?然其如夫子惓惓用世之心,何喟然之叹岂能已哉?及曾点请问辨三子之异同,而夫子一则曰为国,一则曰为邦,又曰诸侯,倦惓用世之心见乎辞矣。虽然,其言不让,未闻道也。安论二子乎?使三子而知所以为国,则夫子不必与点矣。夫子既与点之见道,而又终与三子之为邦,意盖曰不吾知也,则亦为曾点而已;如或知尔,曾点不难为三子,即三子岂可少哉?呜呼,此夫子之志也。点即景容与,便是为国以礼手段。夫子初发问,商个用世之业,觉眉宇间有津津喜色,子路率尔之对,不觉一哂,亦志喜也。及至曾点,乃舍却知尔公案,别寻个丘壑意味出来,将夫子一片热肠顿然灰冷,然其道则是,故叹息而与之云,三子皆以圣贤之学术,奏拯溺、亨屯之略,欲为天下拨乱世而开太平也。兵凶干济,自是宏远之才,康阜生民亦非小康之术,宗庙会同,达乎朝廷,行乎邦国,有礼陶乐淑之化,合而观之,三子事业岂小补云乎哉?使夫子而得邦家,则诸子亦皋夔稷契之俦也。①
蕺山的思想,颇有集有明思想之大成的意味,其为学过程历经数变,基本已将当时的各家思想融和为一处,进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黄宗羲就提出:“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②这里,通过对慎独和对“意”的贞定作用的强调,蕺山着力批判了当时道德理想严重失落的现状,高扬了儒家传统的担当意识和以救世为己任的精神。
蕺山的曾点论,其中心是在强调以人文关怀为中心的“洙泗学术之宗”,强调其核心是“老安少怀”、“民胞物与”的精神。他认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一体之两面,无所谓高低之分,只是取决于现实的条件,此所谓异地皆然,关键是要保持人的性分之全,不愿乎外。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社会人人竞相讨论曾点、轻视三子的流弊,①强调孔子的“惓惓用世之心”,强调“使三子而知所以为国,则夫子不必与点矣”、“三子事业岂小补云乎哉”。这与当时社会黜虚崇实的整体精神是一致的。事实上,我们更能从蕺山的文字中,看出他努力把“夫子既与点之见道,而又终与三子之为邦”合为一体的努力。于蕺山,如果一味肯定曾点之“气象”,其流弊只能是以忘世为高,而一味肯定三子的答问之正,其流弊则是重事为轻进道,抑或是要流于申韩了。
我们说,在明清鼎革之际诸贤中,真正能在“曾点气象”的问题上接续朱子的,实只有王船山一人而已。王船山曾详细论及过朱子的论“曾点气象”。在其大作《读四书大全说》中,船山针对朱子观点提出他在志功之辨、理欲之辨、儒与佛老异同之辨上的思想。
首先,船山借“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这一公案,对朱子以“理”来阐释“曾点气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除孔子是上下千万年语,自孟子以下,莫不是因时以立言。程子曰“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自程子从儒学治道晦蒙否塞后作此一语,后人不可苦向上面讨滋味,致堕疑网。盖自秦以后,所谓儒学者,止于记诵词章,所谓治道者,不过权谋术数。而身心之学,反以付之释老。故程子于此说,吾道中原有此不从事迹上立功名、文字上讨血脉、端居无为而可以立万事万物之本者,为天德、王道大意之存,而二子为能见之也。及乎朱子之时,虽有浙学,而高明者已羞为之,以奔骛于鹅湖(陆学),则直须显漆雕开之本旨,以闲程子之言,使不为淫辞之所托,故实指之曰“斯”,指此理而言。恐其不然,则将有以“斯”为此心者,抑将此“斯”为眼前境物,翠竹黄花,灯笼露柱者。以故,朱子于此,有功于程子甚大。①
船山以为,二程提出以上的公案,很有针对时弊的意味,而二程后人并没有理解他们的苦衷,而是一味“向上面讨滋味”,好高务巧,再次使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偏差(船山认为这一偏差的代表就是象山之学)。有鉴于此,朱子才郑重地指出曾点和漆雕开所见的“大意”,是指此“理”而言。由此,船山认为朱子之论“曾点气象”,既继承了二程论曾点的正面价值,也很有效的规避了二程后学空谈“与点”的流弊。
船山又指出:
朱子谓“三子(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不如曾点之细”,又云“曾点所见乃是大根大本”,只此可思,岂兵农礼乐反是末,是枝叶,春游沂咏反为根本哉?又岂随事致功之为粗,而一概笼罩去之为细耶?看此一段语录,需寻入处。身心无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读语录者,须知“清明在躬”时有“志气如神”事,方解朱子实落见地。①
这里,困扰船山的同样是本文多次提到的难题:为什么“兵农礼乐反是末,是枝叶,春游沂咏反为根本”?他反弹琵琶,一改朱子对严时亨观点的批评态度,认为人只有体会到“清明在躬”的好处,才能真切地体会到朱子的心境,这是把朱子针对严氏的话题转成了辨析理欲之辨的话题。船山从理欲之辨和本末之辨的角度对此做出了回答。他认为,“兵农礼乐”、“随事致功”当然重要,但是辨析理欲之分更为重要:
《论语集注》云“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朱子又云“须先教心直得无欲”,此字却推勘地精严。②
他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人是在“春游沂咏”,还是他已经投身于“兵农礼乐”,而是要看他的一举一动是从天理的当然与必然处出发,还是从个人之私和“己之所欲为”的一己动机出发。若是后者,那么无论他干什么都会怀有“拟议”与“偏据”之心,会因为“儳落机”而生出人欲之伪,进而偏离大本。这样,纵然是他“便成也不足以致主安民,只为他将天理边事以人欲行之耳”。反之,只要他能以无私之本心去去顺理而行,即使是“春游沂咏”也不影响他的天理流行,乃至于此心此理一旦发于事业就会无事不成。在这里,船山继承了朱子认为人一切行为动机必须立足于天理这一大本,必须以公心行公事的一贯立场,在对欲之辨、志功之辨的讨论上坚持了儒家的基本立场。基于对理欲关系的不同理解,船山认为天理和人欲同体而异用的意味。
船山还对理欲之辨展开了进一步的分疏:
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谓之欲。乃以三子反证,则彼之“有勇”、“知方”、“足民”、“相礼”者,岂声色货利之先系其心哉?只缘他预立一愿欲要得如此,得如此而为之,则其欲遂;不得如此而为之,则长似怀挟著一腔子悒怏歆羡在,即此便是人欲,而天理之或当如此、或且不当如此、或虽如此而不尽如此者,则先为愿欲所窒碍而不能通……怀挟著一件,便只是一件,又只在者(这)一件案上作把柄。天理既该夫万事万物,而又只一以贯之。不是且令教民有勇知方,且令足民,且令相礼,揽载著千伶百俐,与他焜燿。故朱子发明根本枝叶之论,而曰“一”、曰“忠”、曰“大本”。凡若此者,岂可先拟而偏据之乎?故三子作“愿”说,作“撰”,便是人欲,便不是天理。
欲者,己之所欲为,非必理之所必为也。①
王汎森先生曾指出,“治晚明清初思想史的人,多已注意到当时思想家反对禁欲主义,发展出自然人性论,尤其是有一种‘情欲大解放’之倾向……在主张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家的作品中,常能见到极为深刻的道德严格主义。这种现象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为特别突出”②。他还把这种现象称作“两极并陈”。王先生指出的这一现象很具有普遍性。我们在王门后学乃至于颜李学派中都能看到这种现象,而船山先生也是其中的典型。事实上船山对理欲之辨,同样也持着道德严格主义的立场。他对人欲的界定就非常严格,也与朱子以不当来界定人欲的说法相通。船山同样把理欲之辨延伸到了人的内心世界:
徒立一志以必欲如此,即此是人欲未净而天理不能流行。三代以下,忠节之士,功名之流,摩拳擦掌,在灯阁下要如何与国家出力,十九不成,便成也不足以致主安民,只为他将天理边事,以人欲行之耳。③
我们在读船山的作品时,常常能感到其深厚的历史批判精神。虽然以“必欲如此”为人欲,这在船山之前已经早有人提及,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他的文字中,感受到他对晚明时那种人潮汹涌,纷纷以承道者自认的状态的反思,感受到其对王门后学流弊的深刻反思。我们也能从《宋论》和《读通鉴论》中,感受到他的这种批判意识①。在这里,对理或是礼的强调,是与船山自觉清算王学以己代理之流弊的巨大努力是相关的。
第二,船山还进而提出了“存养”与“省察”必须并进的观点,并由此突出了儒学与佛老之辨。他不同意“须是人欲净尽,然后天理自然流行”的看法,认为“此语大有病在”。在他看来,“但净人欲”是儒学与佛老共同的一面,净人欲不会自动导致人的天理充周,因为这是两个不可相互替代的过程。相反,人只有自觉去做细致的格致工夫才能真正体会到天理流行之境界。他指出:
须是人欲尽净,然后天理自然流行,此语大有病在……倘须净尽人欲而后天理流行,则但带兵农礼乐一切功利事,便与天理窒碍,叩其实际,岂非“空诸所有”之邪说也?②
他强调,如果抛开了正面的体认天理,而一味强调“净人欲”,就会流于佛老。其实,这正是为朱子晚年所一再强调的“克己”与“复礼”的区别,也是二程所强调的主敬与集义的区别。论到曾点,船山认为,曾点是偏于做净人欲的工夫,“而所以其行不掩者,亦正在此”。他还从体用两方面对此做出了说明:从体上说,“苟天理不充实于中,则何所为主以拒人欲之发”?而从用上说,人必须要时时接触人事,而如果心中无理为之主宰,一接触就会有人欲产生。相反,如果人能做到明礼与净欲两工夫并进(礼,船山指为是“天理之节文”),那么“则兵农礼乐无非天理流行处”。在这里,船山强调“明礼”对于辟佛老的重要性,正是在强调朱子所谓的格物之工夫。这是他对朱熹在该问题上所持观点,诸如力主“涵养”与“致知”并进和强调儒学与佛老虚实之辨等思想的积极回应。在这一点上,陈来先生也有较为明确的说明:
只讲去欲、无语、净欲,就与释氏断烦恼之说无法区别,释氏只讲去欲,不讲存理,不讲有其德,而儒家“仁”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存天理、有其德。因此船山认为,儒家圣学“大要在存天理”,而佛老之学可谓“大要在净尽人欲”。这包括两点,一是儒家在存理遏欲之间主张存理为主,二是儒家的“遏私欲”与佛老的“净人欲”有所不同。①
船山在这里所辨析的,核心精神是儒释之辨,同时也是虚实之辨。这也正是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基本精神。
第三,王夫之还通过对曾点与庄周的比较,强调了所谓的儒道之别。这也是紧承朱子而发的。船山认为,一言以蔽之,庄子思想就是一个“机”字:“看着有难处便躲闪”、“则兵农礼乐、春风沂水了无著手处,谓之不滞于物”,这种态度与儒家的基本宗旨是截然对立的。相反,他自己认为曾点是“然其言春风沂水者,亦无异于言兵农礼乐,则在在有实境”。这不是出于“机心”的选择,而是处处皆然的实境。在这一点上,船山认为“曾点气象”完全不同于老庄之学。我们说,表面上看,“机心”正是庄学所反对的,船山以此来定位庄学似乎有点不相应。但是,船山这里所批判的是庄学“不滞于物”的所谓“机心”,即是在批判它的独善其身,自私用智。另外,船山还针对老庄之学而强调“诚明同德”的重要性,指出一味求乐、不讲事为,“翻(反)以有所明而丧其诚”是老庄之学的本质,这又是他对朱子在辟佛老方面的发展。
显然,以上王夫之所讨论的问题包括理欲之辨和儒学与佛老之别,都是朱子一直想要通过对“曾点气象”的讨论来重点阐述的问题。我们说,明清之际人们对“曾点气象”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中我们分明可以体会到思想转换的先声。
自清代以降,随着明清诸思想家们对理学反思的深入,随着他们为学兴趣的转变,他们开始立足于元典本身探讨是否存在“曾点气象”的问题。总体来看,虽然在清代程朱之学仍然被悬为功令,但是无论是述朱者还是述王者,其思想的原创性都大不如前①。清代汉学之重光乃一大势,儒者特色鲜明如颜习斋者,一传而为李塨,已经离训诂之学不远,此后虽有戴震提出抬轿人与轿中人之喻,但毕竟不足以改变学术发展之大局。仅以曾点问题而论,此后如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近人程树德的《论语集释》都在综合前人论述成果的基础上,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论语》中“曾点言志”一节的本意问题,而程朱对此的论述已经无法再进入他们的视野①。此后,近人杨树达、杨伯峻以及当代编辑的《孔子大全》等等也都只是对“曾点言志”问题本身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却都再没有把它当作理学的基本问题来看待。一叶知秋,至少是仅就清代学术而言,为什么对宋明思想的反思同时也意味着理学整体在走向衰亡?这是个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②。但是,此时“曾点气象”早已成为了指代一种极高个人修养境界的同义词,而为曾点所憧憬的理想生活,也已成为了人们指代理想大同社会的代名词。“曾点气象”无论是在对理学的发展贡献上,还是在促进中国传统哲学境界论的形成上都已经深入人心,其内涵也远远超越了它的原始含义。
在近代学人中,钱穆先生对朱子与“曾点气象”关系问题的考辨颇见工力,也基本上是在照着理学在讲。在其大作《朱子新学案》中,钱先生对朱子在其《文集》与《朱子语类》中对“曾点气象”的种种不同评论做了详尽的梳理,意在通过挖掘朱子与二程在对该问题上的不同评价来辨析他们之间的思想异同。钱穆先生对此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朱子论“曾点气象”的所有内容,也大致勾勒出了朱子在修订《论语集注》中对“曾点气象”的评价过程中的详细变化情况。同时,他也点出了朱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复杂心态与矛盾之情,并且指出了朱子晚年对该问题的晚年定论。不过,钱穆先生似乎对朱子之所以特别关注该问题的背景和深层原因挖掘的不够。尤其他对朱子论“曾点气象”在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没有做更多的介绍。这不能不说是大淳之小疵。另外,钱穆先生对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的年代考证上较之陈来先生而言,稍欠严谨。如其在《朱子新学案》中将《答方伯谟2》一信误作为《答陈明仲15》便是较明显的一例。
相对而言,冯友兰先生也很重视讨论“气象”和“曾点气象”。冯先生自己曾说到:“总起来说,‘境界说’是新理学的中心思想。”①我们说,虽然传统儒学包括宋明理学都有很浓厚的境界论因素,却很难说它是以境界论为中心的。把境界论提高到中心思想的地位,这是冯先生的开新所在。如早在写《贞元六书》之际,冯先生就提出了以四境界说和知天、事天、乐天、同天为代表的人生境界论,而他在晚年编成的《哲学史新编》中,也着重强调了所谓境界和“气象”的问题。由于受新实在论的影响,冯先生早年间过于强调真际、共相、大全之无规定性的一面,给人以游离于儒学核心思想之外的感觉。不过,在编写《哲学史新编》之际,冯先生一改其早年境界论思想中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②,转而强调“与点”和“气象”与道学核心思想的内在联系,并把这作为道学的基本问题来看待。冯先生后来所提出和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文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自近代以来,新儒学一直以复兴儒学者自任,其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但是,新儒家尤其是港台新儒家既强调对传统儒学的继承,更强调对其的开新,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走出了传统儒学乃至宋明理学。世易时移,他们也有了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而其眼界之高,往往要汇中西文化为一,区区“曾点气象”已经很难再激起他们的问题意识了。
例如,熊十力先生认为:
宋儒于事功方面,自是无足称者。《论语》于曾点诸子言志一章,夫子于由、求、赤等,一一以为邦许之,可见孔门师弟精神,非如后儒忽略事功,而朱子《集注》释此章,乃独许曾点,而谓“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朱子此种意思,完全代表宋明理家,非特为其一人之见而已。孔子内圣外王的精神,庄子犹能识之,至宋明诸师,而外王之学遂废。自此,民族愈益式微,此非我辈今日之殷鉴耶?①
《论语》原文中,孔子是在与点还是在与三子,原文俱在,似乎不必再讨论。但熊先生认为“至宋明诸师,而外王之学遂废”之观点,实不足以概括宋明先贤之真精神。事实上,包括朱子本人在内的一大批宋明士大夫绝不轻视事为,但却强调在事为之初,先要求大本以为约束,使外王不至于流于霸道,这又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这一点余英时先生辨之已详,我们也不必再展开论述了。
再如,牟宗三先生针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王襞(字东崖,1512—1588)的评论而说到:
曾点所说即表示一种轻松的乐趣,其志不在作什么事业。此是一时独出彩头。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亦不过是一时的幽默。他们师弟二人都不是在此想表示道体流行之境界。此由子路、冉有、公西华三子离开后,曾皙复与孔子正式讨论三子之所说,即可知之。及至宋儒才把这种乐趣与道体流行之境界打并一起说。①
牟先生认定《论语》“曾点言志”一节的本意不过是“轻松的乐趣”,而孔子的喟然之叹是一时幽默,这只是他自己幽默的体现。其实《论语》本文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幽默可言,毋宁说倒是很庄重的。不过,牟先生指出所谓道体流行云云只是出于宋儒的演绎,这一点却是正确的。牟先生还认为:
宋儒既这样联想在一起,我们即作一体道之境界看。这种境界可以说是儒家内圣之学中所共同承认的,亦是应有的一种义理,亦可以说是儒释道所共同的,禅家尤喜欢这样表示。(若云喜欢多说此,便流于禅,则非是。)宋儒周濂溪亦有这种风格……但既是一种共同的境界,又须看个人的造诣,便不是关键的所在,多说亦无意义……因此朱夫子很不喜欢这一套。所以他说“曾点不可学”。其不可学倒不在那一时的“风乎舞雩”,根本是在不可把学问(实践的工夫)当作四时景致来玩弄……因此,历来言学重点都不在此义上多加宣扬。因此,若专亦此为宗旨(此既是一共同境界,实不可作宗旨),成了此派底特殊风格,人家便说这只是玩弄光景。①
牟先生基本上是把“曾点气象”归结为一种乐趣,因此才会把它看成是儒释道所共同的境界。其实在宋明之际尤其是在朱子的著作里,“曾点气象”还是被赋予了相当多的内容,人们对它也有不同的定位与理解。因此泛泛的说它是儒释道的共同境界,还是说它完全体现了儒学自己的境界,都没有注意到它本身所包含的复杂性。我们既要看到“曾点气象”与佛老相通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所包含的与佛老相异的一面,这样才能体会到前人在辨析“曾点气象”上的苦心。至少以朱子晚年成熟的思想为标准来看,“曾点气象”正是“天理流行”(朱子以此取代了“道体流行”)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曾点气象”与佛老的道体流行境界还是不同的。今天来看,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此中微妙的异同上,这更有利于我们把握理学的基本精神。仅就这点而言,“曾点气象”恰恰是理学中的关键所在。当然,若学者一味地渲染“曾点气象”,并且仅仅把它定位为一种和乐的心境,就会流于玩弄光景,这必然是朱子所批判的。
颇为可惜的是,建国后大陆方面对曾点问题只有零星的关注,尤其对朱熹论“曾点气象”问题论述更少,偶有所及也只是集中在审美与文学领域,没有对该问题从理学视角出发的专题性论述。当然,到本文截稿时为止,仍然没有关于朱熹论“曾点气象”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性论文面世。
在此之外,人们围绕“曾点气象”还展开了另一个方面的争论:那就是朱子后学大多从“天理”的角度诠释“曾点气象”,极力渲染其中的理性因素;相对而言,以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系则更注重从“良知”、从率真、从容的角度来诠释之,把它理解为一种心境,一种感情。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朱子与王阳明对“曾点气象”的不同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他们及其后学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体现出了理学体系中不同发展流派之间的深刻异同。在明代及以后,朱学与王学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制约推动了儒学的整体发展,我们也能通过二人及其后学对待“曾点气象”的态度,窥探到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大势。
我们说,朱子后学与阳明后学的最大不同是,虽然朱子的直系后学人数众多,但他们都被掩盖在了朱子的巨大光环下。真正能在朱子思想的基础上开出新天地的人几乎没有。“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局面直到明初才有所扭转。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了其弟子们对曾点了讨论上,无论是陈北溪、黄直卿、金履祥,还是真德秀(字景元,后更希元,学者称西山先生,1178——1235)等人都只是坚守着朱子思想的一隅而无所发挥。与上述诸人相比,黄震似乎是个特例,其论“曾点言志”一节,则曰:
四子侍坐,而夫子启以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盖试言其用于世当何如也。三子皆言为国之事,皆答问之正也。曾皙孔门之狂者也,无意于世者也,故自言其潇洒之趣,此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予,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皙浴沂咏而归之言,若有触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继答曾皙之问,则力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三子者哉?①
东发为朱学后劲,黄宗羲称其“《日钞》之作,折中诸儒,即于考亭(即朱子)亦不能苟同”②。东发此论,就被钱穆先生指为“甚得论语‘与点’一欢之深旨,较之《集注》似更允惬”③。我们说,东发此论的核心,是强调三子之答志在为国为正,而曾点无意于世之答为非正。同时,东发也划清了孔子之志与曾点之志的界限:认为前者为适人之适者,后者为自适其适者。这无疑把“曾点气象”彻底逐出了儒学的阵营,也是对朱子和明道之“曾点说”的彻底颠覆。
东发论“曾点气象”的最大特色,还在于对于世人之论该问题之种种玄虚的猛烈抨击:
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甚至谢上蔡以曾皙想象之言为实,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为曾皙独对春风,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于谈禅,是盖学于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华言志,自是实事。”此正论也。又曰:“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此语微过于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曾皙岂能与尧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谓曾皙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咏归之乐,指为老安少怀之志,曾皙与夫子又岂若是其班哉?窃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尔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此专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怀之志,天覆地载之心也,适人之适者也;浴沂咏归之乐,吟风弄月之趣也,自适其适者也。曾皙固未得与尧舜比。岂得与夫子比,而形容之过如此。亦合于其分量而审之矣。①
我们知道,小程子在论“曾点言志”一节时,曾针对时人一味渲染“曾点气象”的流弊,突出强调“子路、冉有、公西华言志,自是实事”。但是,或许是为了回护孔子,或许是为了维护“曾点气象”的正面价值,总之小程子并没有指责曾点,而只是批评时人的一味好高。这里,东发于时人包括朱子盛谈曾点的正面价值没有丝毫的共鸣,而对之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他这样做虽然突出了儒学传统中强调经世致用的优先性,却也使得朱子等人维护“曾点气象”之正面价值的努力与苦心失去了意义。当然,东发强调虚实之辨,其实正是对小程子和朱子一贯精神的继承。只不过,朱子并没有因为是人竞谈与点的流弊而取消“曾点气象”本身之价值,而是既要力图避免此弊端,一面又要大力挖掘“曾点气象”在教化社会中的正面价值。
东发还对谢上蔡的一味好高而陷于佛老,展开了批判。从《黄氏日抄》可见,东发每每指出谢上蔡是杨慈湖(杨简,字敬仲,世称慈湖先生,1141—1226)的思想源头,而其批判谢上蔡者,未尝不是在批判他的同乡杨慈湖辈。今天看来,东发此论颇为平常。但是,理学自濂溪起既有好高之弊,这一风气虽然受到了朱子的暂时抑制,却并没有被完全扭转,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由此,东发此论乃属不得不发之列,更不能以老生常谈视之。
在元初,经常吟咏曾点的是刘因(初名骃,字梦骥,后改名因,字梦吉,后人称静修先生,1249—1293)。我们很容易从他的诗作中读出那种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隐士心态,能看到其所理解的“曾点气象”与理学一系的不同:
巧隐林旁无四邻,背山向水得天真。风光正及二三月,童子同来六七人。十日得闲须小醉,一年最好是深春。鸟声似向花枝说,曾见无怀有此民。①
晋楚英雄管晏才,当时真眼尚谁开。狂生携着鲁儿子,独向舞雩风下来。②
独向舞雩风下来,坐忘门外欲生苔。归时过着颜家巷,说与城南华正开。①
青天仰面,卧看浮云卷。苍狗白衣千万变,都被幽人窥见。偶然梦见华胥,觉来花影扶疏,窗下鲁论谁诵,呼来共咏舞雩。②
于时吾与子,咏春风于舞雩,濯尘缨于沧浪,来登斯楼,终日徜徉,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觞,渺天地于一粒,随造化而翱翔,期万代于咫尺,顺四时而行藏,下视万物杳焉,如千里毫芒,然后嚣嚣然,洋洋然,庶乎可以与天下俱忘者矣。③
刘的这些诗作中,颇有隐者的恬淡情绪和老庄气息。应该说,隐藏在诗人刘因背后的,一定会有那种无法明言的失意感与幻灭感。于刘因,早年的激进与中晚年后的恬淡。其进其隐,背后都包含有许多无人知晓的故事。《元史·刘因传》在论及刘因时就提到:
欧阳元尝赞因画像曰: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论者以为知言。④
同样,《宋元学案》中虽然提到刘因与康节和曾点相近①,但却还是认为静修有功于圣门,并视之为与许衡并列为“元之所藉以立国者”②。应该说,若论其事,则刘因之隐毕竟是事实,而若论其志,则其怀有济世之志也是真实的。是无情的现实浇灭了刘因矢志报国的雄心,使他不得不在出处去就上煞费苦心,最终还是成为了事实上的隐者。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静修用文字和自己的生活诠释出了“曾点气象”所无法彻底摆脱的一面——与遗世思想难以彻底划清的干系,而这也正是朱子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有明一代,学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学虽然在明初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但随着程朱思想被官方化,其自身也在走向僵化,此诚如《明史》所言:
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字正夫,号月川,1376—1434)、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③
可见,明初诸儒的一个明显特色是株守,用容肇祖先生的话说,就是他们“简陋了,腐化了、退化了”④,也丧失了思想的原创性。如薛瑄(字德温,号敬轩,1389—1464,陈来先生的《宋明理学》认为薛瑄死于1465年,不确)竟然喊出了“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云云,其整个思想界的沉闷气氛可想而知。明初诸儒的另一个特色是,宣扬敬畏和清苦严毅的个人作风有余,讲和乐自得之境不足①。这更加剧了理学内部所固有的个体意义上的心(重自由自在)与具有形上意味的性之间的紧张②。此后,以陈白沙、王阳明为代表,学界再次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追求自由、自主、活泼泼的精神也一跃成为时代的主流,而讨论“曾点气象”的真正高峰,也适时地出现在了陈宪章、王阳明之际。
总的来说,与宋儒尤其是朱子相较,明儒不再追求思想上的全面,而是更强调其言说的个性化,注重发挥本人思想中的独特之处。由此,明儒多有一偏之论,也多有惊世骇俗之论,而其在隐微细节的辨析上则远远超越了宋儒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时人围绕“曾点气象”的争论也进一步明朗化了。大致形成了以王学与反王学(朱学)或是王学修正派之间的两军对垒。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近。”④黄梨洲此论,指出了陈黄二人思想的一致性一面。就本文而言,他们的共性又表现为其对“曾点气象”的特别推崇上。
前人在论及明代心学的兴起时,未有不首提陈献章(字公免,别号石斋,后人称白沙先生,1423—1500)者,盖白沙先生为扭转一时风气的人物。陈白沙论学以自然为宗,论境界以曾点、邵康节、周濂溪为的,其基本思想被梨洲概括为:
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远之则为曾点,近之则为尧夫,此可无疑者也。①
在梨洲眼中,白沙之学既以虚静为根本,又能兼顾到日用常行的分殊,既强调未尝致力,又能做到应用而不遗,其“气象”与“曾点气象”相当。而白沙之论曾点,则明显体现出了对程朱理学长期发展之日趋沉闷,日渐僵化的反动:
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思想,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时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若无孟子工夫,骤而语之以曾点见趣,一似说梦。会得,虽尧舜事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②
白沙此论,既推崇曾点之见趣,又不忘强调孟子之工夫,表明上看也颇为圆融,也在强调不能空说气象。但我们还是能够看的出,白沙的理想之境是曾点襟怀,而不是庄敬严毅的状态。而且,他还有意地在强调这一对立。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则在薛瑄、曹端、胡居仁诸人大力强调敬畏有些过头的时候,白沙能起而宣扬曾点襟怀,不能不说具有明显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容肇祖先生认为:“陈献章的思想,他的重要的贡献,是要将个人的思想由书本的束缚及古人的奴隶之下解放出来。”①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宣扬主静和自然,毕竟更容易走向佛老的一边。黄宗羲对此就很中肯的评论到:“然而此处最难理会,稍差,便入狂荡一路。”②在白沙那里,虽然他也有说梦之戒的自觉,但是儒学本有的那种强烈的担当精神还没有发露出来。他更缺少像阳明那样对良知这类观念的正面强调,终给人以“失却最上一层”的感觉③。他也和刘因一样,徘徊在隐士与非隐士之间④。
相对于陈白沙而言,王阳明的思想则更为圆通,也更能凸现儒学的真精神。王守仁(字伯安,1472—1529,世称阳明先生)的思想,就其直接意义来说,是对朱子学的反动;而就时代论,阳明倡导的“心学”是在程朱理学逐渐僵化的情况下出现的思想运动,因而具有全新的气象,也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新解放。由于前贤们对阳明学的精神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此不赘言。
概括而言,论及“曾点气象”,阳明不再遵循朱子以“天理浑然”来注解“曾点气象”的理路——而是转而认为“曾点气象”妙在其狂、其乐,妙在无入而不自得,妙在其是良知的自然发露。这就是说,朱子论“曾点气象”,是围绕理字展开,而阳明论“曾点气象”,则围绕良知(心)展开,这也大致是他们思想异同的一个集中体现。
王阳明曾经以“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做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①的诗句相标榜,把狂者胸次作为其个人为学精神的核心。当然,其本人的气象也与后人心目中的“曾点气象”多有吻合。王自己也曾说过:
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②
在阳明看来,曾点“狂”的前提是他“无意必”、“不愿乎其外”,是以我为主的气概,是自信本心的表现。而他自己也正是因为能做到以我为主,才能使“良知”自然流露:
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③
于他来说,“行不掩言”正与乡愿态度相反对,其所体现出的,是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精神,也正是良知的本然呈现。既然良知时时知是知非,故行动一依良知而行,自然就能做到从容中道,他又有云:
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干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①
阳明认为狂者离圣人只有一克念的距离,因为狂者其志高,其心未坏,这是乡愿者所无法企及的,其对曾点之推许远高于朱子。
在阳明心中,理想人格本来就是多元的——人之才气不同,因此要随才成就,狂者就要成就其狂,而不要去强行改变其本性:
圣贤之学不是这等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以此章(即‘曾点言志’章)观之,圣人何等宽宏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者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的?①
阳明论曾点,最强调他的狂的一面,这也与他提出道学革新的激情与勇气是分不开的。恰如陈来先生所言,曾点式的狂者胸次是构成阳明思想“无”之境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另一方面,阳明也注意到了时人虚说本体,玩弄光景的弊端。他无论是论气象还是论良知,都始终注意强调在工夫上见本体,着力凸现儒学的精神:
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诸生入谢,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敎,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③
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①
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②
阳明很清楚,狂者虽然高于世俗之人,但离真正的圣道还很远,而若只有曾点之狂,而无下学工夫之实,其流弊是危险的。阳明自述对于“良知”的体认过程,则有“千死百难”之语,确实不可以简易空疏、玩弄光景者视之。
此后,王门后学中的泰州一派更是凸显了“曾点气象”中的“乐”、“狂”的一面,他们以狂者自任,高扬儒学的担当精神,倡导“乐学”境界,时时以济世为己任,以一腔热诚积极为实现理想而奔走,“无有放下时节”③。在他们看来,“曾点气象”大体代表着以下的特点:它是人本真心体的自然发露、不假事为、天然、率真、和乐、独立自得、自由自在等,这些都是与其主张要高扬个人主体精神的宗旨是紧紧相连的。不过,他们似乎都有自信太过的嫌疑,不但高唱“现在良知”者有之,就是高唱“良知当下现成”、以解缆放船为工夫者亦然,有的甚至公然宣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是床上之床也。”①虽然以乐为道是其自信本心的表现,但是这种说法毕竟离冲开儒家纲常的束缚不远了。
我们说,尽管许多学者认为,晚明近乎放荡和享乐的风气与阳明后学有关,但我们还没有发现真正的阳明弟子中有所谓“鱼馁肉烂”的现象。即使就是被目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笃吾,又号温陵居士,1527—1602)、颜钧(号山农,1504—1596)、何心隐(原姓梁,名汝元,字夫山,1517—1579)之辈,其文字中也没有特别出格的东西②。相反,我们多能发现泰州学派人的古道热肠,发现他们对于儒学近似于宗教徒式的痴狂。
在当时,从白沙、阳明首推“曾点气象”开始,同样也就出现了反对过分宣扬曾点之乐的声音。随着人人竞相讨论“曾点气象”,反对“曾点气象”的声音也同时强大了起来。这一个案也是明代中期儒学敬畏与洒落之争的典型体现。
早在阳明之前,胡居仁就曾提出:“‘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虽也形容有道气象,终带了些清高意思。”③胡为朱学后劲,自然不便对延平的上述观点多有微辞,但是他还是从道德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宣扬洒落者泼了冷水,认为他们清高有余而担当精神不足。在阳明同时,与阳明直接形成对立的是夏尚朴(字敦夫,号东岩,1466—1538),他指出:
寻常读“与点”一章,只说胸次脱洒是尧舜气象,近读《二典》、《三谟》,方知兢兢业业是尧舜气象。尝以此语双门詹困夫(不详),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复斋(不详)有诗云:“便如曾点象尧舜,怕有余风入老庄。”乃知先辈聪明,亦尝看到此。①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夏氏和詹氏兄弟对当时人人竞言“与点之乐”的反感之情,也能看到其对时人竞言“曾点气象”之流弊的警觉。对他们来说,敬畏与洒落正好对立,过分宣扬了洒落的一面,也就抑制了敬畏的一面,片面地宣扬“曾点气象”,无异于失掉了儒学的基本价值观,而流于佛老。夏还撰写了《浴沂亭记》重申上述思想,其中亦云:
旧尝游太学,得逮事章枫山先生(章懋,字德懋,号暗然子,1437——1522。章讲学于枫木庵中,学者因曰枫山先生,《明儒学案》有传),先生一日谓予云:陈白沙应聘来京师,予在大理往候而问学焉。白沙云:我无以教人,但令学者看‘与点’一章。予(章)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谓专理会与点意思,恐入于禅。白沙云: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朱子时人多流于异学,故以此救之;今人溺于利禄之学深矣,必知此意,然后有进步处耳。予(夏)闻其言恍若有悟,信以洒落为尧舜气象。后读《二典》、《三谟》,乃知兢兢业业方是尧舜气象,孔颜之乐端不外于此矣。故周子有礼先乐后之训,而程子亦云敬则自然和乐,和乐只是心中无事,是皆吾心之固有,非有待于外求者,必从事于敬,庶可知其意味之真耳。岂必放浪形骸之外,留连山水之间,然后为乐其乐耶?因以告夫同游二三君子,且着诸篇以自警焉。①
“我无以教人,但令学者看‘与点’一章”。白沙此论,在明初朱学依然强盛之际提出,其冲击力与解放性可想而知。固然,明初思想之僵化需要通过讲“曾点气象”来予以破除,这也有救时之弊,因病施药的意味。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只要一讲“与点”就会流于禅学。但是,夏氏、章氏的忧虑毕竟不是空穴来风。其后来历史的发展反倒正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二程就提到过救人为学之弊端如扶醉人,需要两面扶持,但主一偏,其为害就不可避免。我们也能在胡居仁等人的文献中发现相同的忧虑。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明代思想风气的转换。
同时,《明儒学案》中还载有:王文成赠诗有“舍瑟春风”之句,(夏)先生答曰:孔门沂水春风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可见,夏与王一个侧重宣扬洒落,一个重在强调敬畏,态度恰好相对。从以上引文中可知,夏氏的这一主张绝非他一人的孤声先发,而是代表了一批人的共同观点①。当然,若细考之,则王门后学内部关于“良知异见”的种种争论,也未尝不包含敬畏与洒落之争的因素。只是对此一点,前贤已经多有论及,这里不再多言②。
以提倡敬畏情来对抗曾点之乐,显然是出于对时人一味寻乐所可能带来的流弊的警觉,也深刻地反映出了理学内部在敬畏与洒落问题上的冲突。在思想史上强调敬畏与洒落的冲突自古已然,但这一矛盾只是到了此时才被人自觉地意识到了,也更被有意地凸显了。
必须指出,上述资料只是反映出了夏东岩思想的一个侧面,而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六十七册所收的《夏东岩先生诗集六卷》中,我们却能看到一个推尊白沙,提倡洒落的东岩形象。仅举四库馆臣对《东岩诗集八卷》的提要③,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多涉理语,近白沙、定山(庄泉,字孔旸,号定山,1413—1475)①流派,集中《读<击壤集>》绝句云:“闲中风月吟边见,始信尧夫是我师。”其宗法可知也。②
东岩的诗集中,宣扬吟风弄月的诗作非常多,文中提到陶潜,东坡,尧夫,白沙的地方也屡屡皆是。如其《题白沙集后》云:岭海谁希贤圣踪,白沙真有古人风③。这表明东岩也没有把敬畏和洒落绝对对立起来,并不主张完全用敬畏来代替洒落。
客观的说,以上心学一脉对“曾点气象”的推许,对于解放人们深受理学教条的束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人对此也都有极高的评价。不过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虽然晚明时期对“曾点气象”的过分渲染,直接导致了时人道德意识的淡化,也确实与被喻为“王学末流之弊”的时代精神危机不无干系,以上所引诸人对这一倾向的警觉与批判自然不无道理,但是反过来说,若只讲敬畏,不讲洒落,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会再次使人们的思想走向僵化,甚至会扼杀人们的主体性。事实上,如何处理敬畏与洒落之间的关系,最大可能的实现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同时又能保证人的个体自由的充分实现,又尽可能的避免包括极端个人主义、玄虚思想、功利主义在内的各种一偏之论对社会的不良影响,这始终是朱子在论“曾点气象”中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哲学史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直到今天,展开对此问题的深入探究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说,单就这两种思潮本身而言,它们都各有利弊,若片面强调其中的任何一方而无所限定,都会出现偏差。相反,只有出现这两种思想交相争辉,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局面,才能够有效的消解与抑制片面宣扬其中的一方所可能出现的弊端。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解决该问题的一个思路吧。
在明代理学内部围绕“曾点气象”展开论争之时,开始有学者要根本取消这一问题,这个人就是杨慎。杨慎(字用修,号升庵,1488—1559)对“曾点气象”的理解颇为另类,颇能开清人学风的先声。我们只有把他的言论放在明清之际思想转变的大背景下,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他的观点的价值。由于前贤已对此有过很多的论述,这里只是简单地提示一下①。总的来说,在杨慎的时代,社会及学术领域正在酝酿着全方位的变革,而由理学向经学进而是礼学的转变,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这一浪潮中,提倡怀疑和走出宋明儒者,提倡实学者渐成潮流。杨慎就是这一潮流中的先驱人物。论及“曾点言志”一节,杨慎强调:
四子侍坐,而夫子启以“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盖试言其用于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为国之事,答问之正也。子路乃率尔以对,先蹈于不辞让,而对之非礼矣。夫子哂之盖哂其不逊,非哂为国也。曾皙是时手方鼓瑟而心口相与,曰:夫子其不悦于为国乎?又见赤与求之答,夫子无言,窃意夫子必不以仕为悦矣。故一承“点,尔何如”之问,从容舍瑟而试问曰:异乎三子者之撰!盖逆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点乃为浴沂咏归之说,盖迎合之言,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与,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漠之滨,而忽闻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独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饮水之乐,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至于三子出而曾点后,盖亦自知答问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独与,故历问之。而夫子历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二三子哉?①
对于杨慎,造伪和以出名为目的的各种翻案是他被人经常提到的话题。这段文字就是一个翻案的典型。我们甚至可以用标新立异来定位杨在说这段话时的内心世界。他不惜设身处地的带曾点立言,为其设计了一段充满机心的内心独白,于是就草草把曾点的言说定性为“迎合之言,非答问之正也”。如果说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朱子等人的曾点论固然难以站得住脚,那么杨慎的观点同样也是想当然的产物——这一添字解经的做法比宋儒之好出己意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杨慎所注意的也正是很多人会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孔子不与“皆言为国之事”的三子,却要与颇有些自得其乐的曾点呢?事实上,只要我们越是把注意力转向《论语》的文本本身,就越会感到宋儒种种解说的不可信,也就越会激发人去探讨孔子与点的真正原因①。杨慎接着指出:
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但欲推之过高,而不知陷于谈禅,其失岂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华言志,自是实事,此正论也。又曰:夫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②。又曰:上下与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尧舜可以当之。曾点何如人,而与天地同流,有尧舜气象乎?且圣人之志,老安少怀,安老必有养老之政,怀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隐居放言亦为政之事也。点之志与圣人岂若是班乎?此言或出于谢上蔡之所录,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纵真程子之言,吾亦辟之矣。程子之贤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也。点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论,且与琴张、牧皮为伍,琴张、牧皮又可与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学者循声吠影,徒知圣人之所与,而不知圣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陈归鲁,欲裁正之者,正为皙辈。惜乎不知所以裁点之事,而徒传与点之语,使实学不明于千载,而虚谈大误于后人也。朱子晚年有门人问与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话,《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工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吕与叔……又因程子吟风美月之言,而演为心斋之说。心斋乃庄子之寓言,此诗不惟厚诬曾点,又嫁非于颜子矣。其去竹林七贤、南朝八达者几希。审如是,何不径学庄列而学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历聘卒老,于行荷蒉、晨门、长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讥讽,而夫子之辙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岂以不仕为高者耶?充点之志而不知圣人之裁,则与桀溺之忘世,庄列之虚无,晋人之清谈,宋人之禅学,皆声应气求,响合影附,不至于猖狂自恣,放浪无检不止也。鼓之舞之流于异端而不觉者,岂非尧舜气象一言为之厉阶哉?①
宋人尧舜气象、天地同流之说又过矣。曾皙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为此言以销壮心而耗余年。此风一降则为庄列,再降则为嵇阮矣。岂可鼓之舞之推波助澜哉?②
这里,杨慎重在抨击时人的各种“曾点论”是“谈虚好高之习”,进而认为曾点之志“与桀溺之忘世,庄列之虚无,晋人之清谈,宋人之禅学”,乃至与佛老之学了无分别。他的这一观点以及“纵真程子之言,吾亦辟之矣”的精神,我们会在更多明清之际学者们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精神也可以概括为崇实二字,体现出了鲜明的批判精神。当然,我们也大可不必如钱穆先生那样,一定要把这种精神和王学联系起来①,试图在理学中为它寻找渊源。另外,有一点也需要我们注意,那就是为杨慎所指出的,朱子晚年不喜人空言曾点,空言气象,这一点概括得还是很准确的。
至于杨慎文中所提到的观点,几乎是黄震观点的翻版,只是增添了一些更具煽动性的文字罢了,不必详做评论。
晚明之际,有感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学者纷纷转而强调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强调儒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之维,其代表当属东林学者和刘宗周。在一定意义上,这也表明,朱子学在当时重新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东林学者基本上站在了王学的对立面(他们又都对王学有所继承),大力批判王学末流的种种流弊。要言之,他们把批判的中心,指向了当时甚嚣尘上的“无善无恶”说和空谈性命、一味寻乐等诸时弊,呼唤大家关心国计民生,呼唤儒学向经世致用复归。这种救世的见解,是东林学派的真精神。正是出于这一缘故,东林学派都对“追求独乐”之属,持一种极为严厉的批判态度:
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②
部中甚安闲,尽可静养,但学者以天下为任,不以一部为职,念至此,无处著一乐字矣。①
问高忠宪(高攀龙):“明道许康节内圣外王之学,何以后儒论学只说程朱?”忠宪曰:“伊川言之矣。康节如空中楼阁。他天资高,胸中无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②
此前已经有很多人认为“曾点气象”有玩世意,但是这些话出自东林党人的口中,却具有格外的震撼力。在他们看来,贞定人道德本心的有效手段就是扎实的工夫,他们呼吁:“不患本体不明,只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处不合,惟患分殊处有差。必做处十分酸涩,得处方能十分通透。”③这也是朱子学精神的体现。
已有许多学者指出,晚明之际在社会领域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士人之心态及生活理念都和前代大相径庭——更注重人的感性一面,更注重人的个体之维,更注重享乐。在此大背景下,东林诸贤所呼吁者,对于维系时代的凝聚力,对于保持社会的基本道德导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也许是时代使然,东林学者基本上都缺乏对朱子宣扬“曾点气象”的苦心的同情之理解,其立论也较朱子为浅。
继东林诸贤之后,能进一步从理论上集有明学术之大成,而自觉以救王学末流之流弊为己任者,则曰刘宗周先生。刘宗周(初名宪章,字启东,一作起东,号念台,学者称其为蕺山先生,1578—1645)是晚明的最后一个大理学家,他的去世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思想深刻地反映着时代跳动的脉搏,近来已经成为了学界研究的热点①。
蕺山为学之绝大精力,在于修正王门后学之流弊:针对其讲无是无非而大讲意根独体之良;针对其刊落工夫、虚说本体而力倡绵密细致的心地工夫:
学者只有工夫可说,其本体处直是着不得一语,才着一语便是工夫边事,然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大抵学者肯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若工夫之外别有本体可以两相凑泊,则亦外物而非道矣。②
上述观点和朱子高度一致,而他的“曾点气象论”,也透露出了独有的消息:
圣人之志,以老安少怀为极致。事即宇宙事,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此洙泗学术之宗也。群居讲求,莫非用世之道。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矣,如不用我,守此以藏矣。故由之有勇知方,求之足民,赤之礼乐,其施为气象不凡矣。
曾点狂者也,胸次洒脱,志趣超远,舍瑟一对,悠然独见性分之全,素位而行,浮云富贵,莫(暮)春即景,若曰吾何以人之知不知为哉?吾有吾时,吾有吾地,吾有吾群,吾有吾乐而已。盖忧则违之之志也。故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子不云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点也见及此,进于道矣,能无与乎?然其如夫子惓惓用世之心,何喟然之叹岂能已哉?及曾点请问辨三子之异同,而夫子一则曰为国,一则曰为邦,又曰诸侯,倦惓用世之心见乎辞矣。虽然,其言不让,未闻道也。安论二子乎?使三子而知所以为国,则夫子不必与点矣。夫子既与点之见道,而又终与三子之为邦,意盖曰不吾知也,则亦为曾点而已;如或知尔,曾点不难为三子,即三子岂可少哉?呜呼,此夫子之志也。点即景容与,便是为国以礼手段。夫子初发问,商个用世之业,觉眉宇间有津津喜色,子路率尔之对,不觉一哂,亦志喜也。及至曾点,乃舍却知尔公案,别寻个丘壑意味出来,将夫子一片热肠顿然灰冷,然其道则是,故叹息而与之云,三子皆以圣贤之学术,奏拯溺、亨屯之略,欲为天下拨乱世而开太平也。兵凶干济,自是宏远之才,康阜生民亦非小康之术,宗庙会同,达乎朝廷,行乎邦国,有礼陶乐淑之化,合而观之,三子事业岂小补云乎哉?使夫子而得邦家,则诸子亦皋夔稷契之俦也。①
蕺山的思想,颇有集有明思想之大成的意味,其为学过程历经数变,基本已将当时的各家思想融和为一处,进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黄宗羲就提出:“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②这里,通过对慎独和对“意”的贞定作用的强调,蕺山着力批判了当时道德理想严重失落的现状,高扬了儒家传统的担当意识和以救世为己任的精神。
蕺山的曾点论,其中心是在强调以人文关怀为中心的“洙泗学术之宗”,强调其核心是“老安少怀”、“民胞物与”的精神。他认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一体之两面,无所谓高低之分,只是取决于现实的条件,此所谓异地皆然,关键是要保持人的性分之全,不愿乎外。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社会人人竞相讨论曾点、轻视三子的流弊,①强调孔子的“惓惓用世之心”,强调“使三子而知所以为国,则夫子不必与点矣”、“三子事业岂小补云乎哉”。这与当时社会黜虚崇实的整体精神是一致的。事实上,我们更能从蕺山的文字中,看出他努力把“夫子既与点之见道,而又终与三子之为邦”合为一体的努力。于蕺山,如果一味肯定曾点之“气象”,其流弊只能是以忘世为高,而一味肯定三子的答问之正,其流弊则是重事为轻进道,抑或是要流于申韩了。
我们说,在明清鼎革之际诸贤中,真正能在“曾点气象”的问题上接续朱子的,实只有王船山一人而已。王船山曾详细论及过朱子的论“曾点气象”。在其大作《读四书大全说》中,船山针对朱子观点提出他在志功之辨、理欲之辨、儒与佛老异同之辨上的思想。
首先,船山借“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这一公案,对朱子以“理”来阐释“曾点气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除孔子是上下千万年语,自孟子以下,莫不是因时以立言。程子曰“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自程子从儒学治道晦蒙否塞后作此一语,后人不可苦向上面讨滋味,致堕疑网。盖自秦以后,所谓儒学者,止于记诵词章,所谓治道者,不过权谋术数。而身心之学,反以付之释老。故程子于此说,吾道中原有此不从事迹上立功名、文字上讨血脉、端居无为而可以立万事万物之本者,为天德、王道大意之存,而二子为能见之也。及乎朱子之时,虽有浙学,而高明者已羞为之,以奔骛于鹅湖(陆学),则直须显漆雕开之本旨,以闲程子之言,使不为淫辞之所托,故实指之曰“斯”,指此理而言。恐其不然,则将有以“斯”为此心者,抑将此“斯”为眼前境物,翠竹黄花,灯笼露柱者。以故,朱子于此,有功于程子甚大。①
船山以为,二程提出以上的公案,很有针对时弊的意味,而二程后人并没有理解他们的苦衷,而是一味“向上面讨滋味”,好高务巧,再次使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偏差(船山认为这一偏差的代表就是象山之学)。有鉴于此,朱子才郑重地指出曾点和漆雕开所见的“大意”,是指此“理”而言。由此,船山认为朱子之论“曾点气象”,既继承了二程论曾点的正面价值,也很有效的规避了二程后学空谈“与点”的流弊。
船山又指出:
朱子谓“三子(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不如曾点之细”,又云“曾点所见乃是大根大本”,只此可思,岂兵农礼乐反是末,是枝叶,春游沂咏反为根本哉?又岂随事致功之为粗,而一概笼罩去之为细耶?看此一段语录,需寻入处。身心无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读语录者,须知“清明在躬”时有“志气如神”事,方解朱子实落见地。①
这里,困扰船山的同样是本文多次提到的难题:为什么“兵农礼乐反是末,是枝叶,春游沂咏反为根本”?他反弹琵琶,一改朱子对严时亨观点的批评态度,认为人只有体会到“清明在躬”的好处,才能真切地体会到朱子的心境,这是把朱子针对严氏的话题转成了辨析理欲之辨的话题。船山从理欲之辨和本末之辨的角度对此做出了回答。他认为,“兵农礼乐”、“随事致功”当然重要,但是辨析理欲之分更为重要:
《论语集注》云“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朱子又云“须先教心直得无欲”,此字却推勘地精严。②
他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人是在“春游沂咏”,还是他已经投身于“兵农礼乐”,而是要看他的一举一动是从天理的当然与必然处出发,还是从个人之私和“己之所欲为”的一己动机出发。若是后者,那么无论他干什么都会怀有“拟议”与“偏据”之心,会因为“儳落机”而生出人欲之伪,进而偏离大本。这样,纵然是他“便成也不足以致主安民,只为他将天理边事以人欲行之耳”。反之,只要他能以无私之本心去去顺理而行,即使是“春游沂咏”也不影响他的天理流行,乃至于此心此理一旦发于事业就会无事不成。在这里,船山继承了朱子认为人一切行为动机必须立足于天理这一大本,必须以公心行公事的一贯立场,在对欲之辨、志功之辨的讨论上坚持了儒家的基本立场。基于对理欲关系的不同理解,船山认为天理和人欲同体而异用的意味。
船山还对理欲之辨展开了进一步的分疏:
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谓之欲。乃以三子反证,则彼之“有勇”、“知方”、“足民”、“相礼”者,岂声色货利之先系其心哉?只缘他预立一愿欲要得如此,得如此而为之,则其欲遂;不得如此而为之,则长似怀挟著一腔子悒怏歆羡在,即此便是人欲,而天理之或当如此、或且不当如此、或虽如此而不尽如此者,则先为愿欲所窒碍而不能通……怀挟著一件,便只是一件,又只在者(这)一件案上作把柄。天理既该夫万事万物,而又只一以贯之。不是且令教民有勇知方,且令足民,且令相礼,揽载著千伶百俐,与他焜燿。故朱子发明根本枝叶之论,而曰“一”、曰“忠”、曰“大本”。凡若此者,岂可先拟而偏据之乎?故三子作“愿”说,作“撰”,便是人欲,便不是天理。
欲者,己之所欲为,非必理之所必为也。①
王汎森先生曾指出,“治晚明清初思想史的人,多已注意到当时思想家反对禁欲主义,发展出自然人性论,尤其是有一种‘情欲大解放’之倾向……在主张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家的作品中,常能见到极为深刻的道德严格主义。这种现象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为特别突出”②。他还把这种现象称作“两极并陈”。王先生指出的这一现象很具有普遍性。我们在王门后学乃至于颜李学派中都能看到这种现象,而船山先生也是其中的典型。事实上船山对理欲之辨,同样也持着道德严格主义的立场。他对人欲的界定就非常严格,也与朱子以不当来界定人欲的说法相通。船山同样把理欲之辨延伸到了人的内心世界:
徒立一志以必欲如此,即此是人欲未净而天理不能流行。三代以下,忠节之士,功名之流,摩拳擦掌,在灯阁下要如何与国家出力,十九不成,便成也不足以致主安民,只为他将天理边事,以人欲行之耳。③
我们在读船山的作品时,常常能感到其深厚的历史批判精神。虽然以“必欲如此”为人欲,这在船山之前已经早有人提及,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他的文字中,感受到他对晚明时那种人潮汹涌,纷纷以承道者自认的状态的反思,感受到其对王门后学流弊的深刻反思。我们也能从《宋论》和《读通鉴论》中,感受到他的这种批判意识①。在这里,对理或是礼的强调,是与船山自觉清算王学以己代理之流弊的巨大努力是相关的。
第二,船山还进而提出了“存养”与“省察”必须并进的观点,并由此突出了儒学与佛老之辨。他不同意“须是人欲净尽,然后天理自然流行”的看法,认为“此语大有病在”。在他看来,“但净人欲”是儒学与佛老共同的一面,净人欲不会自动导致人的天理充周,因为这是两个不可相互替代的过程。相反,人只有自觉去做细致的格致工夫才能真正体会到天理流行之境界。他指出:
须是人欲尽净,然后天理自然流行,此语大有病在……倘须净尽人欲而后天理流行,则但带兵农礼乐一切功利事,便与天理窒碍,叩其实际,岂非“空诸所有”之邪说也?②
他强调,如果抛开了正面的体认天理,而一味强调“净人欲”,就会流于佛老。其实,这正是为朱子晚年所一再强调的“克己”与“复礼”的区别,也是二程所强调的主敬与集义的区别。论到曾点,船山认为,曾点是偏于做净人欲的工夫,“而所以其行不掩者,亦正在此”。他还从体用两方面对此做出了说明:从体上说,“苟天理不充实于中,则何所为主以拒人欲之发”?而从用上说,人必须要时时接触人事,而如果心中无理为之主宰,一接触就会有人欲产生。相反,如果人能做到明礼与净欲两工夫并进(礼,船山指为是“天理之节文”),那么“则兵农礼乐无非天理流行处”。在这里,船山强调“明礼”对于辟佛老的重要性,正是在强调朱子所谓的格物之工夫。这是他对朱熹在该问题上所持观点,诸如力主“涵养”与“致知”并进和强调儒学与佛老虚实之辨等思想的积极回应。在这一点上,陈来先生也有较为明确的说明:
只讲去欲、无语、净欲,就与释氏断烦恼之说无法区别,释氏只讲去欲,不讲存理,不讲有其德,而儒家“仁”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存天理、有其德。因此船山认为,儒家圣学“大要在存天理”,而佛老之学可谓“大要在净尽人欲”。这包括两点,一是儒家在存理遏欲之间主张存理为主,二是儒家的“遏私欲”与佛老的“净人欲”有所不同。①
船山在这里所辨析的,核心精神是儒释之辨,同时也是虚实之辨。这也正是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基本精神。
第三,王夫之还通过对曾点与庄周的比较,强调了所谓的儒道之别。这也是紧承朱子而发的。船山认为,一言以蔽之,庄子思想就是一个“机”字:“看着有难处便躲闪”、“则兵农礼乐、春风沂水了无著手处,谓之不滞于物”,这种态度与儒家的基本宗旨是截然对立的。相反,他自己认为曾点是“然其言春风沂水者,亦无异于言兵农礼乐,则在在有实境”。这不是出于“机心”的选择,而是处处皆然的实境。在这一点上,船山认为“曾点气象”完全不同于老庄之学。我们说,表面上看,“机心”正是庄学所反对的,船山以此来定位庄学似乎有点不相应。但是,船山这里所批判的是庄学“不滞于物”的所谓“机心”,即是在批判它的独善其身,自私用智。另外,船山还针对老庄之学而强调“诚明同德”的重要性,指出一味求乐、不讲事为,“翻(反)以有所明而丧其诚”是老庄之学的本质,这又是他对朱子在辟佛老方面的发展。
显然,以上王夫之所讨论的问题包括理欲之辨和儒学与佛老之别,都是朱子一直想要通过对“曾点气象”的讨论来重点阐述的问题。我们说,明清之际人们对“曾点气象”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中我们分明可以体会到思想转换的先声。
自清代以降,随着明清诸思想家们对理学反思的深入,随着他们为学兴趣的转变,他们开始立足于元典本身探讨是否存在“曾点气象”的问题。总体来看,虽然在清代程朱之学仍然被悬为功令,但是无论是述朱者还是述王者,其思想的原创性都大不如前①。清代汉学之重光乃一大势,儒者特色鲜明如颜习斋者,一传而为李塨,已经离训诂之学不远,此后虽有戴震提出抬轿人与轿中人之喻,但毕竟不足以改变学术发展之大局。仅以曾点问题而论,此后如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近人程树德的《论语集释》都在综合前人论述成果的基础上,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论语》中“曾点言志”一节的本意问题,而程朱对此的论述已经无法再进入他们的视野①。此后,近人杨树达、杨伯峻以及当代编辑的《孔子大全》等等也都只是对“曾点言志”问题本身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却都再没有把它当作理学的基本问题来看待。一叶知秋,至少是仅就清代学术而言,为什么对宋明思想的反思同时也意味着理学整体在走向衰亡?这是个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②。但是,此时“曾点气象”早已成为了指代一种极高个人修养境界的同义词,而为曾点所憧憬的理想生活,也已成为了人们指代理想大同社会的代名词。“曾点气象”无论是在对理学的发展贡献上,还是在促进中国传统哲学境界论的形成上都已经深入人心,其内涵也远远超越了它的原始含义。
在近代学人中,钱穆先生对朱子与“曾点气象”关系问题的考辨颇见工力,也基本上是在照着理学在讲。在其大作《朱子新学案》中,钱先生对朱子在其《文集》与《朱子语类》中对“曾点气象”的种种不同评论做了详尽的梳理,意在通过挖掘朱子与二程在对该问题上的不同评价来辨析他们之间的思想异同。钱穆先生对此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朱子论“曾点气象”的所有内容,也大致勾勒出了朱子在修订《论语集注》中对“曾点气象”的评价过程中的详细变化情况。同时,他也点出了朱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复杂心态与矛盾之情,并且指出了朱子晚年对该问题的晚年定论。不过,钱穆先生似乎对朱子之所以特别关注该问题的背景和深层原因挖掘的不够。尤其他对朱子论“曾点气象”在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没有做更多的介绍。这不能不说是大淳之小疵。另外,钱穆先生对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的年代考证上较之陈来先生而言,稍欠严谨。如其在《朱子新学案》中将《答方伯谟2》一信误作为《答陈明仲15》便是较明显的一例。
相对而言,冯友兰先生也很重视讨论“气象”和“曾点气象”。冯先生自己曾说到:“总起来说,‘境界说’是新理学的中心思想。”①我们说,虽然传统儒学包括宋明理学都有很浓厚的境界论因素,却很难说它是以境界论为中心的。把境界论提高到中心思想的地位,这是冯先生的开新所在。如早在写《贞元六书》之际,冯先生就提出了以四境界说和知天、事天、乐天、同天为代表的人生境界论,而他在晚年编成的《哲学史新编》中,也着重强调了所谓境界和“气象”的问题。由于受新实在论的影响,冯先生早年间过于强调真际、共相、大全之无规定性的一面,给人以游离于儒学核心思想之外的感觉。不过,在编写《哲学史新编》之际,冯先生一改其早年境界论思想中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②,转而强调“与点”和“气象”与道学核心思想的内在联系,并把这作为道学的基本问题来看待。冯先生后来所提出和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文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自近代以来,新儒学一直以复兴儒学者自任,其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但是,新儒家尤其是港台新儒家既强调对传统儒学的继承,更强调对其的开新,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走出了传统儒学乃至宋明理学。世易时移,他们也有了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而其眼界之高,往往要汇中西文化为一,区区“曾点气象”已经很难再激起他们的问题意识了。
例如,熊十力先生认为:
宋儒于事功方面,自是无足称者。《论语》于曾点诸子言志一章,夫子于由、求、赤等,一一以为邦许之,可见孔门师弟精神,非如后儒忽略事功,而朱子《集注》释此章,乃独许曾点,而谓“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朱子此种意思,完全代表宋明理家,非特为其一人之见而已。孔子内圣外王的精神,庄子犹能识之,至宋明诸师,而外王之学遂废。自此,民族愈益式微,此非我辈今日之殷鉴耶?①
《论语》原文中,孔子是在与点还是在与三子,原文俱在,似乎不必再讨论。但熊先生认为“至宋明诸师,而外王之学遂废”之观点,实不足以概括宋明先贤之真精神。事实上,包括朱子本人在内的一大批宋明士大夫绝不轻视事为,但却强调在事为之初,先要求大本以为约束,使外王不至于流于霸道,这又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这一点余英时先生辨之已详,我们也不必再展开论述了。
再如,牟宗三先生针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王襞(字东崖,1512—1588)的评论而说到:
曾点所说即表示一种轻松的乐趣,其志不在作什么事业。此是一时独出彩头。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亦不过是一时的幽默。他们师弟二人都不是在此想表示道体流行之境界。此由子路、冉有、公西华三子离开后,曾皙复与孔子正式讨论三子之所说,即可知之。及至宋儒才把这种乐趣与道体流行之境界打并一起说。①
牟先生认定《论语》“曾点言志”一节的本意不过是“轻松的乐趣”,而孔子的喟然之叹是一时幽默,这只是他自己幽默的体现。其实《论语》本文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幽默可言,毋宁说倒是很庄重的。不过,牟先生指出所谓道体流行云云只是出于宋儒的演绎,这一点却是正确的。牟先生还认为:
宋儒既这样联想在一起,我们即作一体道之境界看。这种境界可以说是儒家内圣之学中所共同承认的,亦是应有的一种义理,亦可以说是儒释道所共同的,禅家尤喜欢这样表示。(若云喜欢多说此,便流于禅,则非是。)宋儒周濂溪亦有这种风格……但既是一种共同的境界,又须看个人的造诣,便不是关键的所在,多说亦无意义……因此朱夫子很不喜欢这一套。所以他说“曾点不可学”。其不可学倒不在那一时的“风乎舞雩”,根本是在不可把学问(实践的工夫)当作四时景致来玩弄……因此,历来言学重点都不在此义上多加宣扬。因此,若专亦此为宗旨(此既是一共同境界,实不可作宗旨),成了此派底特殊风格,人家便说这只是玩弄光景。①
牟先生基本上是把“曾点气象”归结为一种乐趣,因此才会把它看成是儒释道所共同的境界。其实在宋明之际尤其是在朱子的著作里,“曾点气象”还是被赋予了相当多的内容,人们对它也有不同的定位与理解。因此泛泛的说它是儒释道的共同境界,还是说它完全体现了儒学自己的境界,都没有注意到它本身所包含的复杂性。我们既要看到“曾点气象”与佛老相通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所包含的与佛老相异的一面,这样才能体会到前人在辨析“曾点气象”上的苦心。至少以朱子晚年成熟的思想为标准来看,“曾点气象”正是“天理流行”(朱子以此取代了“道体流行”)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曾点气象”与佛老的道体流行境界还是不同的。今天来看,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此中微妙的异同上,这更有利于我们把握理学的基本精神。仅就这点而言,“曾点气象”恰恰是理学中的关键所在。当然,若学者一味地渲染“曾点气象”,并且仅仅把它定位为一种和乐的心境,就会流于玩弄光景,这必然是朱子所批判的。
颇为可惜的是,建国后大陆方面对曾点问题只有零星的关注,尤其对朱熹论“曾点气象”问题论述更少,偶有所及也只是集中在审美与文学领域,没有对该问题从理学视角出发的专题性论述。当然,到本文截稿时为止,仍然没有关于朱熹论“曾点气象”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性论文面世。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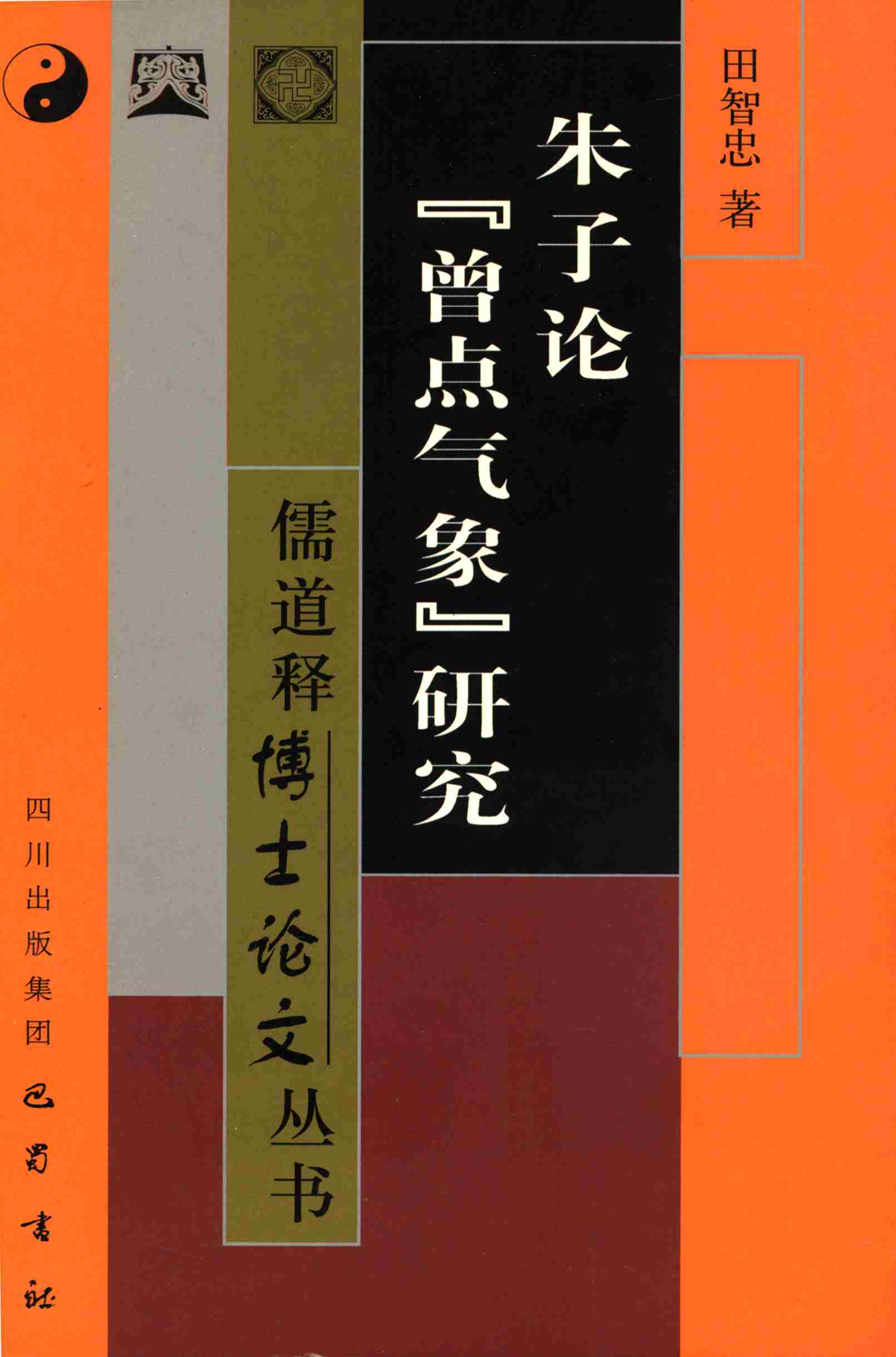
《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出版者:四川出版集团
本书从朱熹关于“曾点气象”话题的讨论契入,直探朱子思想中的有无虚实之辨和儒学与佛老之辨等关键问题,旁及历史上相关“曾点气象”的评论,进而引出中国哲学中关于精神境界、本体与功夫的讨论。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