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成书之际的“曾点气象论”
| 内容出处: | 《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355 |
| 颗粒名称: | 二 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成书之际的“曾点气象论”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1 |
| 页码: | 154-174 |
| 摘要: |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成书之际的“曾点气象论”。在编订《论语集注》初稿时,朱子与张栻讨论了如何评价谢良佐的“曾点说”,并通过数度交流,南轩完全接受了朱子的观点,并对自己的《论语说》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可以说,《论语集注》初稿是朱子讨论“曾点气象”问题的重要起点。张南轩对“曾点气象”有着格外的兴趣,而其在个人“气象”上也颇与曾点相近。他曾与朱子以曾点之乐为题有过数次的诗歌应答。 |
| 关键词: | 曾点气象 朱熹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完成编订《论语集注》是朱子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关节点。正是在此书中,朱子首次提出了他对于一系列理学问题的正式看法,也确定了他诠释前人经典的基本模式和立场。此后,虽然朱子对《论语集注》做过多次调整,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其在编订《论语集注》初稿时所确立的大方向。可以说,《论语集注》初稿是朱子讨论“曾点气象”问题的重要起点。
在朱子编订《论语集注》初稿之际,他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主要是与张栻之间展开的。他们讨论的焦点问题,则是如何评价谢良佐的“曾点说”。通过数度交流,南轩完全接受了朱子的观点,并对自己的《论语说》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张南轩对“曾点气象”有着格外的兴趣,而其在个人“气象”上也颇与曾点相近①。他曾与朱子以曾点之乐为题有过数次的诗歌应答,也曾在刘珙复建(1165年)岳麓书院之初,作《风雩亭词》以吟咏曾点之乐:
……予揆名而诹义,爰远取于舞雩之风。昔洙泗之诸子,侍函丈以从容。因圣师之有问,各跽陈其所衷。独点也之操志,与二三子兮不同。方舍瑟而铿然,谅其乐之素充。味所陈之纡余,夫何有于事功。盖不忘而不助,示何始而何终。于鸢飞而鱼跃,寔天理之中庸。觉唐虞遗烈,俨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与,岂虚言之是崇。嗟学乎兮念,此溯千载以希踪。希踪兮奈何?盖务勉乎敬恭。审操舍兮斯须,凛戒惧乎冥蒙。防物变之外诱,遏起习之内讧。浸私意之脱落,自本心之昭融。斯若人之妙旨,可实得于予躬。循点也之所造,极颜乐之深工。登斯亭而有感,期用力于无穷。②
南轩的这篇词,是我们了解他关于“曾点气象”早期态度的绝佳材料。在这篇词中,他认为“曾点气象”的要点,是“何有于事功”、“不忘而不助”、“寔天理之中庸”。他还认为,曾点言志,不是虚言。论及后人如何学习“曾点气象”,南轩更强调通过“敬恭”、“操舍”、“戒惧”等下学工夫来实得这一“气象”。从下文朱子对南轩《论语说》的批评来看,南轩此时在“曾点气象”上的观点,几乎是他后来《癸巳论语说》的雏形。
次年,朱子致信南轩,就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尹)和靖曰:“脱(疑为若字)使穷其根源,谨其辞说,苟不践行,等为虚语。”石子重云:“愚以为人之所以不能践行者,以其从口耳中得来,未尝穷其根源,无着落故耳。纵谨其辞说,终有疎谬。若诚穷其根源,则其所得非浅,自然欲罢不能,岂有不践行者哉?”范伯崇云:“知之行之,此二者学者始终之事,阙一不可。然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也。”知而不行,岂特今日之患,虽圣门之徒,未免病此。如曾点舞雩之对,其所见非不高明,而言之非不善也,使其能践履,实有诸己而发挥之,则岂让于颜、雍(也)哉?惟其于践履处未能纯熟,此所以为狂者也(约作于乾道二年,1166年)。①
朱子此信,针对的是那些徒务口耳、知而不行的人,是在探寻世人知行脱节的原因。朱子的态度也与数年后他答邓卫老一样,强调若离开实地工夫,纵使“谨其辞说”,也只是虚说。其实,这也是儒学的一贯立场。朱子进而强调:曾点只是所见高明,但其有知少行,因此毕竟还只是狂者之列。朱子的这一观点与其晚年答廖德明“曾点实未行得”的观点是一致的。张南轩答曰:
……知者,凡圣之分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之意,亦曰:“虽已知之,此非艰也,贵于身亲实履之”,此为知之者言也……自孟子而下,大学不明,只为无知之者耳……曾点非若今之自谓有见而直不践履者也。正以见得开扩,便谓圣人境界不下颜曾“请事”、“战兢”之功耳。颜曾“请事”、“战兢”之功,盖无须臾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①
南轩认为,在知行关系上,知先行后,知是行的先导,也更为关键。若有人空说而不贱履,那只是因为他的知还不是真知(至于如何才能有真知,南轩没有说明)。论及曾点,南轩认为曾点所见甚高,因此才会有不下于颜曾“请事”、“战兢”的圣人境界②。但是,南轩此说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他回避了曾点“行不掩言”的一面。应该说,朱张二人所讨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他们显然是在自说自话。
以上是朱子与南轩就“曾点气象”的早期交锋。我们知道,当时朱子正在艰苦探索为学之道,他自己的为学基本宗旨也还不成熟。但其知行并重,行重于知的思想已经初显端倪。这次交锋的结果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在《论语集注》初稿的编订前后之际,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讨论。
一年后,朱子在与南轩讨论“洒落”话题的时候,也提到了“曾点气象”:
示喻黄公洒落之语,旧见李先生称之,以为不易窥测到此。今以为知言,语诚太重,但所改语又似太轻,只云识者亦有取焉,故备列之如何?所谓洒落,只是形容一个不疑所行、清明高远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则何处更有此等气象邪?只如此看有道者胸怀表里亦自可见,若更讨落着,则非言语所及,在人自见得如何?如曾点舍瑟之对,亦何尝说破,落着在甚处邪(约作于乾道六年,1167年)?①
南轩给朱子的信今本《南轩集》未收,也可能是被朱子在整理编订时删除了,因此我们对二人所讨论的细节不得而知。我们知道,李延平非常推崇“洒落”,还把它归结为形容有道者气象。此后“洒落”遂成为当时人人竞相讨论的话题。在此信中,朱子认为“洒落”只是“识者亦有取焉”者,只是“形容一个不疑所行、清明高远之意”,并不主张对其进行过度的渲染与诠释。朱子认为,对于“洒落”最好是去“自见得”,若“更讨落着”,反为不美。自乾道三年秋朱子长沙之行后,朱子已经对南轩有了“见处卓然不可及……但其天姿明敏,初从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太高”的总体印象。朱子在此信中的语气极为委婉,但我们也能体会到他有反对虚说“气象”的意味。不过,此时朱子仍然视“洒落”为一种值得称许的境界。
1177年,朱子在他编定的《论语集注》初稿中首次提出了对“曾点气象”的正式看法。相对于此前在书信和《语类》中对此的讨论而言,这一材料无疑更有价值。《论语集注》的初稿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见到,我们只能据《论语或问》中的资料来分析它的大致内容:
曰:何以言曾点之“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高远”也?曰:方三子之竞言所志也,点独鼓瑟于其间,漠然若无所闻,及夫子问之,然后瑟音少间,乃徐舍瑟而起对焉,而悠然逊避,若终不肯见所为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后不得已而发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尝少出其位,盖澹然若将终身焉者,此其气象之雍容闲暇,志尚之清明高远为何如?而非其见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则亦何以至于此耶?
曰:何以言其“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也?曰:夫暮春之日,万物畅茂之时也;春服既成,人体和适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长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鲁国之胜处也;既浴而风,又咏而归,乐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乐虽若止于一身,然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程子以为“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谓此耳。
或曰:谢氏以为:“曾皙胸中无一毫事,列子驭风之事近之”,其说然乎?曰:圣贤之心所以异于佛老者,正以无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谓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旷然无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则亦何以异于虚无寂灭之学,而岂圣人之事哉?抑观其直以异端无实之妄言为比,则其得失亦可见矣。曰:何以言“夫子之许三子”也?曰:此无贬辞固已可见,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见其平日之与之也……①
这一段资料非常重要。它使我们得以窥见《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初稿的基本内容。这也是我们研究朱子论“曾点气象”之发展脉络的重要线索。
由这则材料可知,《论语集注》的“曾点言志”节的初稿必然包涵以下内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高远……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夫子之许三子……
这些内容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从二程继承来的内容,如“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和“夫子之许三子”;二是朱子自己的思想。当然,朱子自己的思想更值得研究。
在这里,朱子说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明显是承谢上蔡的“曾点说”而来,意在突出曾点之洒落和从容。但是,或许是出于对谢上蔡的“曾点说”流于空疏和佛老化的敏感,朱子在此文中努力试图把“曾点气象”引向淳乎淳的理学境界。
首先,朱子一改谢的“曾点说”对“道”的空疏理解,而赋予“道”以更为儒学化的内涵:“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其次,提到“心不累事”,朱子则明确强调其涵义是“无意必固我之累”。他同时说明,这又是保证圣人能够做到“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的先决条件。用他后来成熟的思想说,“心不累事”强调的是曾点没有刻意为国之心、不规规于事为之末,所强调的是心不为物所役,不为物所滞。朱子认为,做到这样才能突破小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其三,朱子也强调所说的“心不累事”,是圣贤之所以异于佛老者,与谢所渲染的曾点“心中不着一事”截然不同。以此为基础,朱子也公开对谢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后者只强调“旷然无所倚着”的一面,这无异于佛老的虚无寂灭之学。不过,朱子虽然对“心不累事”进行了明确的限定,却在此文的开头花了大量的笔墨大谈曾点的“终不肯见所为”、“澹然若将终身焉”云云,这固然意在突出曾点的“洒落”与“从容”,却也难免给人以曾点“以独善其身为高,蔑视事为,摒弃外物”的嫌疑。后文中甘节等人对朱子此说的疑问,正是由此而发。而朱子此后不久就把这一句改掉,当与他对这句话可能带来的流弊有所警觉有关。
再者,朱子说曾点“志尚高远”、“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就是要突出曾点所怀的志,是儒家化的志,是心怀天地万物、以苍生为怀的志,而非佛老出世间的志,同样也是意在强化“曾点气象”的儒家属性,防止其流于佛老一端。而文中评价曾点“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与时对物之时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程子以为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谓此耳”,正是对此问题的澄清。
由于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只能是《论语集注》初稿“曾点言志”一节的部分,因此我们也不清楚朱子是否对曾点的“行不掩言”有所评价。不过,在这一时期的《朱子语类》中,也载有朱子认为“至于曾点,诚狂者也,只争一撮地,便流为庄周之徒”的慨叹①,这也比程明道认为曾点只是“行有不掩”的评价走得更远了。这表明朱子此时已经很清醒“曾点气象”有“先天不足”——无论如何,“有知无行”的曾点都离儒学的理想人格相差甚远。他对“曾点气象”的评价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边倒的。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中对“曾点言志”一节的评价与其作于同时的《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中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在朱子编订《论语集注》的同一年,张南轩将他在数年前写成的《癸巳论语说》寄给朱子,朱子针对该文提出了一百多条质疑,其中就重点批评了其对“曾点言志”一节的评论。这一材料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朱子此时对于“曾点气象”的基本态度②:
此论甚高,然反复玩之,则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且其间文意首尾自相背戾处极多。且如所谓“曾子非有乐乎此也,盖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两重病痛。夫谓曾子非有乐乎此,此本于明道先生箪瓢陋巷非有可乐之说也。然颜曾之乐虽同,而所从言之则异,不可不察也。盖箪瓢陋巷实非可乐之事,颜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忧改其乐耳。若其所乐,则固在夫箪瓢陋巷之外也。故学者欲求颜子之乐而即其事以求之,则有没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说所以为有功也。若夫曾皙言志,乃其中心之所愿而可乐之事也。盖其见道分明,无所系累,从容和乐,欲与万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霭然见于词气之间,明道所谓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学者欲求曾皙之胸怀气象而舍此以求之,则亦有没世而不可得者矣。夫二子之乐虽同,而所从言则其异有如此者,今乃以彼之意为此之说,岂不误哉?且夫子之问欲知四子之所志也,四子之对皆以其平日所志而言也。今于曾皙之言,独谓其特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之意,则是曾皙于夫子之问,独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临时信口撰成数句无当之大言,以夸其无所不乐之高也,如此则与禅家拈槌竖拂、指东画西者何以异哉?其不得罪于圣人幸矣,又何喟然见与之可望乎?
至于此下虽名为推说曾皙之意者,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已见,则愚恐其自信太重,视圣贤太轻,立说太高而卒归于无实也。且所谓无(所?)不得其乐者,固以人而言之矣,而其下文乃以“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者释之,则未知其以理而言耶,抑以人言之耶?以理而言,则与上文得其所乐之云似不相应;以人而言,则曾皙之心艰危恐迫,倾侧动摇,亦已甚矣,又何以得其所乐,而为天理之自然耶?其以为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者,则求诸曾皙之言,殊未见此曲折。且此既许之以圣人之事矣,又以为圣门实学存养之地,则是方以为学者之事也;若曰姑以为学者之事而已,而又以为行有所不掩焉,则是又并所谓有养者而夺之也。凡此数节殊不相应,皆熹之所不能晓者。
窃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发明的当。若上蔡之说,徒赞其无所系着之意,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风之事为比,则其杂于老庄之见而不近圣贤气象,尤显然矣。凡此说中诸可疑处,恐皆原于此说,窃谓高明更当留意,必如横渠先生所谓“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者,庶有以得圣贤之本心耳。《论语》中大节目似此者不过数章,不可草草如此说过也(作于淳熙四年,1177年)。①
束景南先生指出,“朱熹作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在八月前后(指1177年),其讨论所得,均写入《论语集注》中”②。可见,这篇文章也代表着朱子在编辑《论语集注》初稿时的基本观点。
南轩《癸巳论语说》的初稿今已不可见,但据此信所引,张的来信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曾子非有乐乎此也,盖以见夫无不得其乐之意耳……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者……圣门实学存养之地……故行有不掩焉也。
南轩所主的正是谢良佐的观点(故朱子指出“凡此说中诸可疑处,恐皆原于此说”)。因而,朱子的此信表面上是在批评张拭,其更深一层却是在指出张的文稿中的所有可疑之处,都是来自于对谢良佐“曾点说”的发挥,实际上也是在曲折地批判谢。在此文中,朱子明确点出谢说的弊端是“徒赞其无所系着之意,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这也就是说,谢上蔡过于强调了“曾点气象”虚无的一面,却没有强调其属于儒学之“有”的一面。朱子认为张南轩对曾点的解说犯了同样的毛病:立论太高而无实,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
具体而论,朱子指出,颜子之乐、曾点之乐的本质都是乐道。于颜子,他是不因“箪瓢陋巷”而易其乐道之心;而在曾点,乐道就体现为他的“乐乎此(此这里的此指道)”。因此,把曾点的“非有乐乎此(指“道”)”和颜回的“非乐乎此”(朱子指出,这一“此”,指的是箪瓢陋巷的生活境遇)相混同,就会抹杀曾点之乐是以道为乐的核心精神,无形中把“曾点气象”推到虚无缥缈的佛老阵营中,这是谢的“曾点说”的最大流弊。
其次,朱子认为:说曾点的“无(所?)不得其乐”,会淡化曾点在“言志”这一事实,以及其中所包涵的儒的成分,使人认为曾点单纯是在炫耀“高”和“乐”,这是在把“曾点气象”等同于禅家的“拈槌竖拂、指东画西”。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朱子才肯定,对于“曾点气象”而言,只有极力强调曾点“与圣人之志同”的程明道的观点最为的当,而张南轩的说法有“名为推说曾皙之意者,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己见”的弊端,并指出南轩忽而把“曾点气象”等同于“尧舜所以无为而治”,忽而又说曾点“行有不掩”,忽而从曾点乐的一面说,忽而又从“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的一面说,对“曾点气象”的定位有些飘摇不定。
最后,朱子还特别说明:“《论语》中大节目似此者不过数章,不可草草如此说过也。”他显然认为此节是学者探询为学之方之大关键所在。
另外,文中说曾点“盖其见道分明,无所系累,从容和乐,欲与万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霭然见于词气之间”云云,几乎就是《论语集注》初稿和《论语或问》相关内容的翻版。这也显示出了朱子此时思想的一致性。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癸巳论语解》,就是南轩针对朱子的批评而做出改订的本子。对比此文和朱子的上述评论不难发现,张南轩基本上接受了朱子的批评,并对自己的“曾点说”进行了全面地修正:
……至于曾皙则又异乎是,其鼓瑟舍瑟之间,门人记之如此之详者,盖已可见从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暮)春之时,与数子者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吟咏而归。盖其中心和乐,无所系累,油然欲与万物俱得其所,玩味辞气,温乎如春阳之无不被也,故程子以为此即是尧舜气象,而亦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之意也。皙之志若此,自非其见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于行有不掩焉,则以其于颜氏工夫,有所未能尽耳。夫子以三子之言之实也,故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礼者为国之理也,言之不让则为废礼,而失所以为国之理矣。如求与赤则庶几乎能让者,故复因以称之。①
此文删去了转述谢良佐的文字和“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等把曾点直接等同于尧舜的内容,同时较多采取了程明道和朱子的观点,强调曾点“从容不迫”、“中心和乐,无所系累,油然欲与万物俱得其所”、“见道之明,涵泳有素”云云,这都是显现出了张南轩对于朱子的折节相从之处,表明张南轩在朱子的影响下,在逐渐展开对谢良佐思想的反思。
朱子与南轩围绕“曾点气象”的讨论并没有自此结束。1186年,时任广西安抚使的詹仪之(字体仁,?—1189,《儒林宗派》将其列为吕氏门人①)在桂林刻印了朱子新修订的《四书集注》,与此同时,他致信朱子讨论张南轩的“曾点说”,朱子答曰:
蒙喻钦夫说曾点处,鄙意所疑,近已于《中庸或问》“鸢鱼章”内说破。盖明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语发明己意,说不到处,后人却作实语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约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②关于这件事的背景,程明道曾对谢良佐说: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底。③
明道认为,“鸢飞鱼跃”与“勿忘勿助”所表达的意思可以相互促进:即要强调自由活泼的精神境界,也要注意做工夫。谢良佐在引述程的这句话时,加上了一些自己的补充:“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他是把程的“与点说”与此联系起来,强调了它们可以相通。谢还指出,“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非是极其上下而言,盖真个见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吃紧道与人处,若从此解悟,便可入尧舜气象”、“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犹孟子所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见天理不用私意也”①。上文已经指出,张南轩的“曾点说”是对谢“曾点说”的进一步发挥,而朱子对张南轩的批判也正是对对谢的批判。
由于《中庸或问》自初稿后几乎就几乎没有被修改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朱子对此更为详细的论述:
问:程子所谓“鸢飞鱼跃,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者,何也?(朱子)曰:道之流行,发见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其流行发见于上下之间者,可谓著矣。子思于此指而言之,惟欲学者于此默而识之,则为有以洞见道体之妙而无疑,而程子以为子思吃紧为人处者,正以示人之意为莫切于此也。其曰“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则又以明道之体用流行发见,充塞天地,亘古亘今,虽未尝有一毫之空阙,一息之间断。然其在人而见诸日用之间者,则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后有以自觉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泼泼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体呈露,妙用显行,无所滞碍云尔。非必仰而视乎鸢之飞,俯而观乎鱼之跃,然后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为精密,然但为学者集义、养气而发耳。至于程子借以为言,则又以发明学者洞见道体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盖此一言虽若二事,然其实则必有事焉半词之间已尽其意,善用力者苟能于此超然默会,则道体之妙已跃如矣,何待下句而后足于言耶?圣贤特恐学者用力之过而反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虽有所事而不为所累耳,非谓必有事焉之外,又当别设此念以为正心之防也。①
从这段文字来看,朱子想要在这一段中说破的,是他与张南轩在为学工夫上的根本不同。他认为,程颢提到《中庸》和《孟子》的这两句话,其核心是强调:道体流行,无所不在,但其落实于人,则不外乎人的心。故根本下学工夫在于存心以默识道体,使之全体呈露,无所滞碍,其重心落在自然涵养上。朱子认为这是大本,而“察”只是“但为学者集义、养气而发耳”。而谢说的重点却在强调“察识”,朱子认为这有以心察心的流弊,会使人失之拘束②。这正是朱子所说的“后人(即指谢)却作实语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的意思。一句话,朱与张在曾点说上的分歧,其关键点还落在谢良佐身上。
1195年,吴伯丰(字必大,?—1198,江西人,早师事张南轩、吕东莱,晚师文公,深究理学,议论操守为儒林所重①,吴1180年从朱子学,吴与万人杰都曾先到陆九渊处问学,后又乃师从朱子)②来信,就明道的一句话发生疑问,并就曾点和颜回的异同问题向朱子提出质疑:
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后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必大观颜子之学具体而微矣,然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开之说抑何谓耶?上蔡亦曰: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必大窃谓:固滞狭隘固不足以适道,然不勉学者以存养践行之实,而遽以此为务,此曾点之学非颜子之学也。③
伯丰针对明道与谢上蔡的“放开说”发问,他认为颜子之学的核心就是谨守,这也是学者所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由此,他对明道的放开说感到难以理解,认为曾点的弊端就体现在无存养践行之实,而只有放开,这是曾点不及颜回之处。伯丰担心明道和谢的说法会导致人忽略存养工夫,而刻意去追求胸怀开阔的心境。其实,这正暗含着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洒落与敬畏之辨的问题。其中也包含着对虚实之辨问题的关注。为此,朱子答到:
明道之语亦上蔡所记,或恐须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则自有此验,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谓须要放开也。曾点之胸怀洒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摆脱使开也。有意摆脱则亦不能得开,而非所以为曾点矣。上蔡说恐不缜密,生病痛也(作于庆元元年,1195年)。①
朱子指出,明道所言,是登高自然望远的意思,决不是要“有意放开”。他还强调,曾点的“洒落”也是如此,而非出于有意强求。由此也可见其对曾点的评价尚高,其对“洒落”的理解至此也是正面,至少是中性的。
朱子此段还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理学中“既得后须放开”一段著名公案的基本态度。谢上蔡所记录的明道语录中曾提到:既得后,便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②
上文已指出,明道之学、之气象都强调活泼泼或是洒落,尤其是以著名的《识仁篇》为代表。明道强调“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①,都表明了这一点。明道意味,为学不能一味苦苦株守拘泥。既有所收获,就没有必要再去刻意的“防检”和“穷索”。这一点,明道的表述非常清楚。应该说,明道的这句话和谢对此的记录都没有问题。包括谢氏本人也没有“有意使开”的嫌疑,如谢就曾强调:
问太虚无尽,心有止,安得合一?(谢)曰:心有止,只为用他,若不用,则何止?(问)吾丈莫己不用否?(谢)曰:未到此地,除是圣人便不用。当初曾发此口,被伊川一句坏了二十年。曾往见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贤却发得太早在。②
问:当初发此语时如何?(谢)曰:见得这个事,经时无他念,接物亦应副得去。问: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转却?(谢)曰:当了终须有不透处。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禅家去矣。伊川直是会煅炼得人,说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问:闻此语后,如何?(谢)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始初进时速,后来迟,十数年过,却如梦。问:何故迟?(谢)曰:如射弓,到满时便难开。然此二十年闻见知识却煞长。明道曰:贤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见理后须放开,不放开只是守。开又近于放倒,故有礼以节之,守几于不自在。故有乐以乐之,乐即是放开也。①
“天下何思何率”,代表了一种由必然进到自然的较高境界,对于某些人来说,也确实是有此理,对此伊川并不否认。但他却不认为这句话对任何人都适用。相反,他认为,若没有必要的工夫来支撑,大多数人说这句话都会落空。我们说,对于这些人来说,说“天下何思何虑”,就当属“有意使开”之列,其流弊自然很大。
上蔡在二十年后非常明白:“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禅家去矣。”他强调“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始初进时速,后来迟”、“如射弓,到满时便难开”云云,都体现出了他不敢轻易放开的心情。我们说,朱子多次批评谢上蔡言论高妙,担心其所说太快是一回事,而谢上蔡本人是否对此有所注意是又一回事②。在明道和上蔡,见理后只是守是一失,因此需要乐以乐之;一味放倒又是一失,因此需要礼以节之。二者的恰当结合才会臻于中道。
其实,朱子对放开太早者的担心,更多是担心谢的这一说法对后世的影响,担心的是,后人在谢的说法上再向前卖出一步。准确的说,是和他对谢氏后学——尤其是湖湘学派学风的担心直接相关。对于这一点,上文中已经多次提到,这里不再赘述。这正如明代人们对阳明的批评,未尝不是感于阳明后学的泛滥一样。对这一点,明儒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1434—1484)的观点可兹借鉴:
上蔡记明道语,言“既得后,须放开”。朱子疑之,以为“既得后心胸自然开泰,若有意放开,反成病痛”。愚以为,得后放开虽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故流于庄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所以卒至狂。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寻颜子之乐处,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便要做颜子工夫,求至乎其地。岂有便求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流于异端。①
胡对朱子观点的把握与发挥都很到位。大概明道的这句话,委实可以成为那些本无所得,却想要放开者的借口。在朱子看来,时人的一味求乐,一味好高恶卑,好简易而恶苦涩,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于朱子,在工夫与境界、下学与上达之间,他更愿意把目光放在下学的工夫上。
本文视朱子与吴伯丰的这封信为其论“曾点气象”第一部分的结束。自此以后,朱子与湖湘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基本结束(此后朱子对谢上蔡思想的批判终其一身都在继续,只不过随着朱陆二人交往的开始,朱子也逐渐在把批判的重心转到陆子上。其实,朱子之批陆者,也未尝不是在批谢)。而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中心,转向了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评论的修改上。
在朱子编订《论语集注》初稿之际,他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主要是与张栻之间展开的。他们讨论的焦点问题,则是如何评价谢良佐的“曾点说”。通过数度交流,南轩完全接受了朱子的观点,并对自己的《论语说》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张南轩对“曾点气象”有着格外的兴趣,而其在个人“气象”上也颇与曾点相近①。他曾与朱子以曾点之乐为题有过数次的诗歌应答,也曾在刘珙复建(1165年)岳麓书院之初,作《风雩亭词》以吟咏曾点之乐:
……予揆名而诹义,爰远取于舞雩之风。昔洙泗之诸子,侍函丈以从容。因圣师之有问,各跽陈其所衷。独点也之操志,与二三子兮不同。方舍瑟而铿然,谅其乐之素充。味所陈之纡余,夫何有于事功。盖不忘而不助,示何始而何终。于鸢飞而鱼跃,寔天理之中庸。觉唐虞遗烈,俨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与,岂虚言之是崇。嗟学乎兮念,此溯千载以希踪。希踪兮奈何?盖务勉乎敬恭。审操舍兮斯须,凛戒惧乎冥蒙。防物变之外诱,遏起习之内讧。浸私意之脱落,自本心之昭融。斯若人之妙旨,可实得于予躬。循点也之所造,极颜乐之深工。登斯亭而有感,期用力于无穷。②
南轩的这篇词,是我们了解他关于“曾点气象”早期态度的绝佳材料。在这篇词中,他认为“曾点气象”的要点,是“何有于事功”、“不忘而不助”、“寔天理之中庸”。他还认为,曾点言志,不是虚言。论及后人如何学习“曾点气象”,南轩更强调通过“敬恭”、“操舍”、“戒惧”等下学工夫来实得这一“气象”。从下文朱子对南轩《论语说》的批评来看,南轩此时在“曾点气象”上的观点,几乎是他后来《癸巳论语说》的雏形。
次年,朱子致信南轩,就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尹)和靖曰:“脱(疑为若字)使穷其根源,谨其辞说,苟不践行,等为虚语。”石子重云:“愚以为人之所以不能践行者,以其从口耳中得来,未尝穷其根源,无着落故耳。纵谨其辞说,终有疎谬。若诚穷其根源,则其所得非浅,自然欲罢不能,岂有不践行者哉?”范伯崇云:“知之行之,此二者学者始终之事,阙一不可。然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也。”知而不行,岂特今日之患,虽圣门之徒,未免病此。如曾点舞雩之对,其所见非不高明,而言之非不善也,使其能践履,实有诸己而发挥之,则岂让于颜、雍(也)哉?惟其于践履处未能纯熟,此所以为狂者也(约作于乾道二年,1166年)。①
朱子此信,针对的是那些徒务口耳、知而不行的人,是在探寻世人知行脱节的原因。朱子的态度也与数年后他答邓卫老一样,强调若离开实地工夫,纵使“谨其辞说”,也只是虚说。其实,这也是儒学的一贯立场。朱子进而强调:曾点只是所见高明,但其有知少行,因此毕竟还只是狂者之列。朱子的这一观点与其晚年答廖德明“曾点实未行得”的观点是一致的。张南轩答曰:
……知者,凡圣之分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之意,亦曰:“虽已知之,此非艰也,贵于身亲实履之”,此为知之者言也……自孟子而下,大学不明,只为无知之者耳……曾点非若今之自谓有见而直不践履者也。正以见得开扩,便谓圣人境界不下颜曾“请事”、“战兢”之功耳。颜曾“请事”、“战兢”之功,盖无须臾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①
南轩认为,在知行关系上,知先行后,知是行的先导,也更为关键。若有人空说而不贱履,那只是因为他的知还不是真知(至于如何才能有真知,南轩没有说明)。论及曾点,南轩认为曾点所见甚高,因此才会有不下于颜曾“请事”、“战兢”的圣人境界②。但是,南轩此说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他回避了曾点“行不掩言”的一面。应该说,朱张二人所讨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他们显然是在自说自话。
以上是朱子与南轩就“曾点气象”的早期交锋。我们知道,当时朱子正在艰苦探索为学之道,他自己的为学基本宗旨也还不成熟。但其知行并重,行重于知的思想已经初显端倪。这次交锋的结果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在《论语集注》初稿的编订前后之际,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讨论。
一年后,朱子在与南轩讨论“洒落”话题的时候,也提到了“曾点气象”:
示喻黄公洒落之语,旧见李先生称之,以为不易窥测到此。今以为知言,语诚太重,但所改语又似太轻,只云识者亦有取焉,故备列之如何?所谓洒落,只是形容一个不疑所行、清明高远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则何处更有此等气象邪?只如此看有道者胸怀表里亦自可见,若更讨落着,则非言语所及,在人自见得如何?如曾点舍瑟之对,亦何尝说破,落着在甚处邪(约作于乾道六年,1167年)?①
南轩给朱子的信今本《南轩集》未收,也可能是被朱子在整理编订时删除了,因此我们对二人所讨论的细节不得而知。我们知道,李延平非常推崇“洒落”,还把它归结为形容有道者气象。此后“洒落”遂成为当时人人竞相讨论的话题。在此信中,朱子认为“洒落”只是“识者亦有取焉”者,只是“形容一个不疑所行、清明高远之意”,并不主张对其进行过度的渲染与诠释。朱子认为,对于“洒落”最好是去“自见得”,若“更讨落着”,反为不美。自乾道三年秋朱子长沙之行后,朱子已经对南轩有了“见处卓然不可及……但其天姿明敏,初从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太高”的总体印象。朱子在此信中的语气极为委婉,但我们也能体会到他有反对虚说“气象”的意味。不过,此时朱子仍然视“洒落”为一种值得称许的境界。
1177年,朱子在他编定的《论语集注》初稿中首次提出了对“曾点气象”的正式看法。相对于此前在书信和《语类》中对此的讨论而言,这一材料无疑更有价值。《论语集注》的初稿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见到,我们只能据《论语或问》中的资料来分析它的大致内容:
曰:何以言曾点之“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高远”也?曰:方三子之竞言所志也,点独鼓瑟于其间,漠然若无所闻,及夫子问之,然后瑟音少间,乃徐舍瑟而起对焉,而悠然逊避,若终不肯见所为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后不得已而发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尝少出其位,盖澹然若将终身焉者,此其气象之雍容闲暇,志尚之清明高远为何如?而非其见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则亦何以至于此耶?
曰:何以言其“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也?曰:夫暮春之日,万物畅茂之时也;春服既成,人体和适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长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鲁国之胜处也;既浴而风,又咏而归,乐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乐虽若止于一身,然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程子以为“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谓此耳。
或曰:谢氏以为:“曾皙胸中无一毫事,列子驭风之事近之”,其说然乎?曰:圣贤之心所以异于佛老者,正以无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谓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旷然无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则亦何以异于虚无寂灭之学,而岂圣人之事哉?抑观其直以异端无实之妄言为比,则其得失亦可见矣。曰:何以言“夫子之许三子”也?曰:此无贬辞固已可见,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见其平日之与之也……①
这一段资料非常重要。它使我们得以窥见《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初稿的基本内容。这也是我们研究朱子论“曾点气象”之发展脉络的重要线索。
由这则材料可知,《论语集注》的“曾点言志”节的初稿必然包涵以下内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高远……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夫子之许三子……
这些内容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从二程继承来的内容,如“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和“夫子之许三子”;二是朱子自己的思想。当然,朱子自己的思想更值得研究。
在这里,朱子说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明显是承谢上蔡的“曾点说”而来,意在突出曾点之洒落和从容。但是,或许是出于对谢上蔡的“曾点说”流于空疏和佛老化的敏感,朱子在此文中努力试图把“曾点气象”引向淳乎淳的理学境界。
首先,朱子一改谢的“曾点说”对“道”的空疏理解,而赋予“道”以更为儒学化的内涵:“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其次,提到“心不累事”,朱子则明确强调其涵义是“无意必固我之累”。他同时说明,这又是保证圣人能够做到“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的先决条件。用他后来成熟的思想说,“心不累事”强调的是曾点没有刻意为国之心、不规规于事为之末,所强调的是心不为物所役,不为物所滞。朱子认为,做到这样才能突破小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其三,朱子也强调所说的“心不累事”,是圣贤之所以异于佛老者,与谢所渲染的曾点“心中不着一事”截然不同。以此为基础,朱子也公开对谢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后者只强调“旷然无所倚着”的一面,这无异于佛老的虚无寂灭之学。不过,朱子虽然对“心不累事”进行了明确的限定,却在此文的开头花了大量的笔墨大谈曾点的“终不肯见所为”、“澹然若将终身焉”云云,这固然意在突出曾点的“洒落”与“从容”,却也难免给人以曾点“以独善其身为高,蔑视事为,摒弃外物”的嫌疑。后文中甘节等人对朱子此说的疑问,正是由此而发。而朱子此后不久就把这一句改掉,当与他对这句话可能带来的流弊有所警觉有关。
再者,朱子说曾点“志尚高远”、“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就是要突出曾点所怀的志,是儒家化的志,是心怀天地万物、以苍生为怀的志,而非佛老出世间的志,同样也是意在强化“曾点气象”的儒家属性,防止其流于佛老一端。而文中评价曾点“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与时对物之时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程子以为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谓此耳”,正是对此问题的澄清。
由于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只能是《论语集注》初稿“曾点言志”一节的部分,因此我们也不清楚朱子是否对曾点的“行不掩言”有所评价。不过,在这一时期的《朱子语类》中,也载有朱子认为“至于曾点,诚狂者也,只争一撮地,便流为庄周之徒”的慨叹①,这也比程明道认为曾点只是“行有不掩”的评价走得更远了。这表明朱子此时已经很清醒“曾点气象”有“先天不足”——无论如何,“有知无行”的曾点都离儒学的理想人格相差甚远。他对“曾点气象”的评价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边倒的。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中对“曾点言志”一节的评价与其作于同时的《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中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在朱子编订《论语集注》的同一年,张南轩将他在数年前写成的《癸巳论语说》寄给朱子,朱子针对该文提出了一百多条质疑,其中就重点批评了其对“曾点言志”一节的评论。这一材料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朱子此时对于“曾点气象”的基本态度②:
此论甚高,然反复玩之,则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且其间文意首尾自相背戾处极多。且如所谓“曾子非有乐乎此也,盖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两重病痛。夫谓曾子非有乐乎此,此本于明道先生箪瓢陋巷非有可乐之说也。然颜曾之乐虽同,而所从言之则异,不可不察也。盖箪瓢陋巷实非可乐之事,颜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忧改其乐耳。若其所乐,则固在夫箪瓢陋巷之外也。故学者欲求颜子之乐而即其事以求之,则有没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说所以为有功也。若夫曾皙言志,乃其中心之所愿而可乐之事也。盖其见道分明,无所系累,从容和乐,欲与万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霭然见于词气之间,明道所谓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学者欲求曾皙之胸怀气象而舍此以求之,则亦有没世而不可得者矣。夫二子之乐虽同,而所从言则其异有如此者,今乃以彼之意为此之说,岂不误哉?且夫子之问欲知四子之所志也,四子之对皆以其平日所志而言也。今于曾皙之言,独谓其特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之意,则是曾皙于夫子之问,独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临时信口撰成数句无当之大言,以夸其无所不乐之高也,如此则与禅家拈槌竖拂、指东画西者何以异哉?其不得罪于圣人幸矣,又何喟然见与之可望乎?
至于此下虽名为推说曾皙之意者,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已见,则愚恐其自信太重,视圣贤太轻,立说太高而卒归于无实也。且所谓无(所?)不得其乐者,固以人而言之矣,而其下文乃以“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者释之,则未知其以理而言耶,抑以人言之耶?以理而言,则与上文得其所乐之云似不相应;以人而言,则曾皙之心艰危恐迫,倾侧动摇,亦已甚矣,又何以得其所乐,而为天理之自然耶?其以为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者,则求诸曾皙之言,殊未见此曲折。且此既许之以圣人之事矣,又以为圣门实学存养之地,则是方以为学者之事也;若曰姑以为学者之事而已,而又以为行有所不掩焉,则是又并所谓有养者而夺之也。凡此数节殊不相应,皆熹之所不能晓者。
窃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发明的当。若上蔡之说,徒赞其无所系着之意,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风之事为比,则其杂于老庄之见而不近圣贤气象,尤显然矣。凡此说中诸可疑处,恐皆原于此说,窃谓高明更当留意,必如横渠先生所谓“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者,庶有以得圣贤之本心耳。《论语》中大节目似此者不过数章,不可草草如此说过也(作于淳熙四年,1177年)。①
束景南先生指出,“朱熹作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在八月前后(指1177年),其讨论所得,均写入《论语集注》中”②。可见,这篇文章也代表着朱子在编辑《论语集注》初稿时的基本观点。
南轩《癸巳论语说》的初稿今已不可见,但据此信所引,张的来信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曾子非有乐乎此也,盖以见夫无不得其乐之意耳……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者……圣门实学存养之地……故行有不掩焉也。
南轩所主的正是谢良佐的观点(故朱子指出“凡此说中诸可疑处,恐皆原于此说”)。因而,朱子的此信表面上是在批评张拭,其更深一层却是在指出张的文稿中的所有可疑之处,都是来自于对谢良佐“曾点说”的发挥,实际上也是在曲折地批判谢。在此文中,朱子明确点出谢说的弊端是“徒赞其无所系着之意,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这也就是说,谢上蔡过于强调了“曾点气象”虚无的一面,却没有强调其属于儒学之“有”的一面。朱子认为张南轩对曾点的解说犯了同样的毛病:立论太高而无实,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
具体而论,朱子指出,颜子之乐、曾点之乐的本质都是乐道。于颜子,他是不因“箪瓢陋巷”而易其乐道之心;而在曾点,乐道就体现为他的“乐乎此(此这里的此指道)”。因此,把曾点的“非有乐乎此(指“道”)”和颜回的“非乐乎此”(朱子指出,这一“此”,指的是箪瓢陋巷的生活境遇)相混同,就会抹杀曾点之乐是以道为乐的核心精神,无形中把“曾点气象”推到虚无缥缈的佛老阵营中,这是谢的“曾点说”的最大流弊。
其次,朱子认为:说曾点的“无(所?)不得其乐”,会淡化曾点在“言志”这一事实,以及其中所包涵的儒的成分,使人认为曾点单纯是在炫耀“高”和“乐”,这是在把“曾点气象”等同于禅家的“拈槌竖拂、指东画西”。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朱子才肯定,对于“曾点气象”而言,只有极力强调曾点“与圣人之志同”的程明道的观点最为的当,而张南轩的说法有“名为推说曾皙之意者,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己见”的弊端,并指出南轩忽而把“曾点气象”等同于“尧舜所以无为而治”,忽而又说曾点“行有不掩”,忽而从曾点乐的一面说,忽而又从“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的一面说,对“曾点气象”的定位有些飘摇不定。
最后,朱子还特别说明:“《论语》中大节目似此者不过数章,不可草草如此说过也。”他显然认为此节是学者探询为学之方之大关键所在。
另外,文中说曾点“盖其见道分明,无所系累,从容和乐,欲与万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霭然见于词气之间”云云,几乎就是《论语集注》初稿和《论语或问》相关内容的翻版。这也显示出了朱子此时思想的一致性。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癸巳论语解》,就是南轩针对朱子的批评而做出改订的本子。对比此文和朱子的上述评论不难发现,张南轩基本上接受了朱子的批评,并对自己的“曾点说”进行了全面地修正:
……至于曾皙则又异乎是,其鼓瑟舍瑟之间,门人记之如此之详者,盖已可见从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暮)春之时,与数子者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吟咏而归。盖其中心和乐,无所系累,油然欲与万物俱得其所,玩味辞气,温乎如春阳之无不被也,故程子以为此即是尧舜气象,而亦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之意也。皙之志若此,自非其见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于行有不掩焉,则以其于颜氏工夫,有所未能尽耳。夫子以三子之言之实也,故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礼者为国之理也,言之不让则为废礼,而失所以为国之理矣。如求与赤则庶几乎能让者,故复因以称之。①
此文删去了转述谢良佐的文字和“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等把曾点直接等同于尧舜的内容,同时较多采取了程明道和朱子的观点,强调曾点“从容不迫”、“中心和乐,无所系累,油然欲与万物俱得其所”、“见道之明,涵泳有素”云云,这都是显现出了张南轩对于朱子的折节相从之处,表明张南轩在朱子的影响下,在逐渐展开对谢良佐思想的反思。
朱子与南轩围绕“曾点气象”的讨论并没有自此结束。1186年,时任广西安抚使的詹仪之(字体仁,?—1189,《儒林宗派》将其列为吕氏门人①)在桂林刻印了朱子新修订的《四书集注》,与此同时,他致信朱子讨论张南轩的“曾点说”,朱子答曰:
蒙喻钦夫说曾点处,鄙意所疑,近已于《中庸或问》“鸢鱼章”内说破。盖明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语发明己意,说不到处,后人却作实语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约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②关于这件事的背景,程明道曾对谢良佐说: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底。③
明道认为,“鸢飞鱼跃”与“勿忘勿助”所表达的意思可以相互促进:即要强调自由活泼的精神境界,也要注意做工夫。谢良佐在引述程的这句话时,加上了一些自己的补充:“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他是把程的“与点说”与此联系起来,强调了它们可以相通。谢还指出,“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非是极其上下而言,盖真个见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吃紧道与人处,若从此解悟,便可入尧舜气象”、“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犹孟子所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见天理不用私意也”①。上文已经指出,张南轩的“曾点说”是对谢“曾点说”的进一步发挥,而朱子对张南轩的批判也正是对对谢的批判。
由于《中庸或问》自初稿后几乎就几乎没有被修改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朱子对此更为详细的论述:
问:程子所谓“鸢飞鱼跃,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者,何也?(朱子)曰:道之流行,发见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其流行发见于上下之间者,可谓著矣。子思于此指而言之,惟欲学者于此默而识之,则为有以洞见道体之妙而无疑,而程子以为子思吃紧为人处者,正以示人之意为莫切于此也。其曰“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则又以明道之体用流行发见,充塞天地,亘古亘今,虽未尝有一毫之空阙,一息之间断。然其在人而见诸日用之间者,则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后有以自觉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泼泼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体呈露,妙用显行,无所滞碍云尔。非必仰而视乎鸢之飞,俯而观乎鱼之跃,然后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为精密,然但为学者集义、养气而发耳。至于程子借以为言,则又以发明学者洞见道体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盖此一言虽若二事,然其实则必有事焉半词之间已尽其意,善用力者苟能于此超然默会,则道体之妙已跃如矣,何待下句而后足于言耶?圣贤特恐学者用力之过而反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虽有所事而不为所累耳,非谓必有事焉之外,又当别设此念以为正心之防也。①
从这段文字来看,朱子想要在这一段中说破的,是他与张南轩在为学工夫上的根本不同。他认为,程颢提到《中庸》和《孟子》的这两句话,其核心是强调:道体流行,无所不在,但其落实于人,则不外乎人的心。故根本下学工夫在于存心以默识道体,使之全体呈露,无所滞碍,其重心落在自然涵养上。朱子认为这是大本,而“察”只是“但为学者集义、养气而发耳”。而谢说的重点却在强调“察识”,朱子认为这有以心察心的流弊,会使人失之拘束②。这正是朱子所说的“后人(即指谢)却作实语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的意思。一句话,朱与张在曾点说上的分歧,其关键点还落在谢良佐身上。
1195年,吴伯丰(字必大,?—1198,江西人,早师事张南轩、吕东莱,晚师文公,深究理学,议论操守为儒林所重①,吴1180年从朱子学,吴与万人杰都曾先到陆九渊处问学,后又乃师从朱子)②来信,就明道的一句话发生疑问,并就曾点和颜回的异同问题向朱子提出质疑:
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后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必大观颜子之学具体而微矣,然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开之说抑何谓耶?上蔡亦曰: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必大窃谓:固滞狭隘固不足以适道,然不勉学者以存养践行之实,而遽以此为务,此曾点之学非颜子之学也。③
伯丰针对明道与谢上蔡的“放开说”发问,他认为颜子之学的核心就是谨守,这也是学者所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由此,他对明道的放开说感到难以理解,认为曾点的弊端就体现在无存养践行之实,而只有放开,这是曾点不及颜回之处。伯丰担心明道和谢的说法会导致人忽略存养工夫,而刻意去追求胸怀开阔的心境。其实,这正暗含着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洒落与敬畏之辨的问题。其中也包含着对虚实之辨问题的关注。为此,朱子答到:
明道之语亦上蔡所记,或恐须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则自有此验,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谓须要放开也。曾点之胸怀洒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摆脱使开也。有意摆脱则亦不能得开,而非所以为曾点矣。上蔡说恐不缜密,生病痛也(作于庆元元年,1195年)。①
朱子指出,明道所言,是登高自然望远的意思,决不是要“有意放开”。他还强调,曾点的“洒落”也是如此,而非出于有意强求。由此也可见其对曾点的评价尚高,其对“洒落”的理解至此也是正面,至少是中性的。
朱子此段还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理学中“既得后须放开”一段著名公案的基本态度。谢上蔡所记录的明道语录中曾提到:既得后,便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②
上文已指出,明道之学、之气象都强调活泼泼或是洒落,尤其是以著名的《识仁篇》为代表。明道强调“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①,都表明了这一点。明道意味,为学不能一味苦苦株守拘泥。既有所收获,就没有必要再去刻意的“防检”和“穷索”。这一点,明道的表述非常清楚。应该说,明道的这句话和谢对此的记录都没有问题。包括谢氏本人也没有“有意使开”的嫌疑,如谢就曾强调:
问太虚无尽,心有止,安得合一?(谢)曰:心有止,只为用他,若不用,则何止?(问)吾丈莫己不用否?(谢)曰:未到此地,除是圣人便不用。当初曾发此口,被伊川一句坏了二十年。曾往见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贤却发得太早在。②
问:当初发此语时如何?(谢)曰:见得这个事,经时无他念,接物亦应副得去。问: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转却?(谢)曰:当了终须有不透处。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禅家去矣。伊川直是会煅炼得人,说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问:闻此语后,如何?(谢)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始初进时速,后来迟,十数年过,却如梦。问:何故迟?(谢)曰:如射弓,到满时便难开。然此二十年闻见知识却煞长。明道曰:贤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见理后须放开,不放开只是守。开又近于放倒,故有礼以节之,守几于不自在。故有乐以乐之,乐即是放开也。①
“天下何思何率”,代表了一种由必然进到自然的较高境界,对于某些人来说,也确实是有此理,对此伊川并不否认。但他却不认为这句话对任何人都适用。相反,他认为,若没有必要的工夫来支撑,大多数人说这句话都会落空。我们说,对于这些人来说,说“天下何思何虑”,就当属“有意使开”之列,其流弊自然很大。
上蔡在二十年后非常明白:“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禅家去矣。”他强调“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始初进时速,后来迟”、“如射弓,到满时便难开”云云,都体现出了他不敢轻易放开的心情。我们说,朱子多次批评谢上蔡言论高妙,担心其所说太快是一回事,而谢上蔡本人是否对此有所注意是又一回事②。在明道和上蔡,见理后只是守是一失,因此需要乐以乐之;一味放倒又是一失,因此需要礼以节之。二者的恰当结合才会臻于中道。
其实,朱子对放开太早者的担心,更多是担心谢的这一说法对后世的影响,担心的是,后人在谢的说法上再向前卖出一步。准确的说,是和他对谢氏后学——尤其是湖湘学派学风的担心直接相关。对于这一点,上文中已经多次提到,这里不再赘述。这正如明代人们对阳明的批评,未尝不是感于阳明后学的泛滥一样。对这一点,明儒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1434—1484)的观点可兹借鉴:
上蔡记明道语,言“既得后,须放开”。朱子疑之,以为“既得后心胸自然开泰,若有意放开,反成病痛”。愚以为,得后放开虽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故流于庄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所以卒至狂。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寻颜子之乐处,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便要做颜子工夫,求至乎其地。岂有便求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流于异端。①
胡对朱子观点的把握与发挥都很到位。大概明道的这句话,委实可以成为那些本无所得,却想要放开者的借口。在朱子看来,时人的一味求乐,一味好高恶卑,好简易而恶苦涩,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于朱子,在工夫与境界、下学与上达之间,他更愿意把目光放在下学的工夫上。
本文视朱子与吴伯丰的这封信为其论“曾点气象”第一部分的结束。自此以后,朱子与湖湘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基本结束(此后朱子对谢上蔡思想的批判终其一身都在继续,只不过随着朱陆二人交往的开始,朱子也逐渐在把批判的重心转到陆子上。其实,朱子之批陆者,也未尝不是在批谢)。而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中心,转向了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评论的修改上。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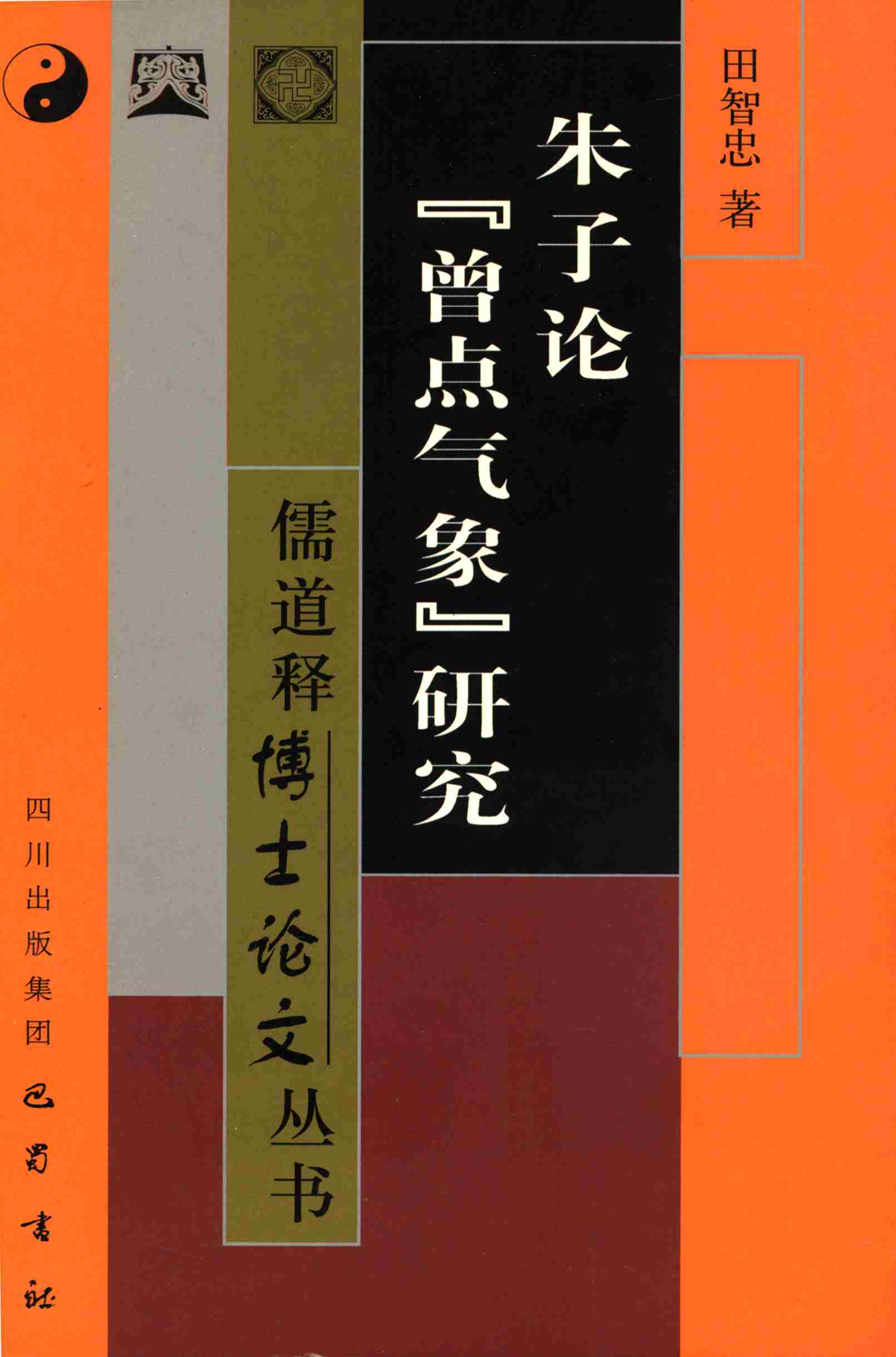
《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出版者:四川出版集团
本书从朱熹关于“曾点气象”话题的讨论契入,直探朱子思想中的有无虚实之辨和儒学与佛老之辨等关键问题,旁及历史上相关“曾点气象”的评论,进而引出中国哲学中关于精神境界、本体与功夫的讨论。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