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约在《论语集注》成书前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研究
| 内容出处: | 《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354 |
| 颗粒名称: | 一 约在《论语集注》成书前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研究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144-154 |
| 摘要: |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朱子在《论语集注》成书前,关于“曾点气象”的书信研究。在“中和新悟”之后,朱子开始将精力放在对各种时弊的批判上,其中主要批判对象是以谢良佐为代表的好高之学。朱子在《记谢上蔡论语疑义》中对谢良佐的“论语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指出其存在说的太高、太快,流于佛老的毛病。这封信表明,朱子已经认识到谢良佐的“论语说”存在问题。此后,他在批驳谢的“曾点说”中,强调了“曾点气象”的重要性。 |
| 关键词: | 曾点气象 朱熹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中和新悟”在朱子的思想发展历程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如果说此前朱子把主要精力放在自我批判上,那么此后他更多是以上述教训为基础,展开了对各种时弊的批判。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从“中和新悟”起,直到朱子编订《论语集注》和《四书或问》阶段为止,朱子所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以谢良佐为代表的好高之学。在“中和新悟”两年后,朱子即作《记谢上蔡论语疑义》,对谢良佐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其中既有对谢氏引《老子》来解《论语》的批驳,又有对其“不觉乗快一向说开……只见旷荡无可捞摸”、“大抵上蔡气象宏阔,所见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①的批判。朱子直言:“上蔡语中诸如此类甚多……几于段段有可疑处……大概亦只是一种病,即此亦可以见其余也。”①这封信表明,朱子至此已经认识到谢良佐的“论语说”在总体上有说的太高、太快,流于佛老的毛病。这也是他日后在批驳谢的“曾点说”时所持的基本立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朱子往往以“洒落”来诠释“曾点气象”,并且显示出了对作为境界之“洒落”的特殊偏爱。不过,此时朱子已经对虚说“气象”的流弊有所警觉,并开始告诫人多做工夫,少谈境界。这也是他对李延平之谆谆告诫的自觉回应。
但是,朱子之对谢上蔡思想的批判,在更深层次上遇到了一个麻烦:如何对待谢上蔡与程明道之间思想上的一致性。上文已经提到,谢上蔡的许多观点都是对程明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其最显著者,上蔡的“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即是明道的“浮云过目”说和“放开说”的发挥。而朱子在对待二人的态度上,则一面“必为明道回护”,一面则“专以归咎上蔡”②,这不能不产生诸多矛盾。事实上,诚如后文所指出的,朱子在具有类似“气象”的曾点、程明道、陆象山之间,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完全回护程明道,同时极力为曾点辩护,却大力的批判陆学。朱子的这一做法同样引发了诸多的矛盾,而深入地分析朱子之所以这样做的隐衷,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朱陆异同,也会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精神。本书在下文中会对此进一步的说明。
随着朱子思想的日渐成熟,朱子也开始与人讨论《论语》“曾点言志”一节,如他针对陈焞(字明仲,生卒不详)的来信就强调说:
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故虽夫子有如或知尔之问,而其所对亦未尝少出其位焉。盖若将终身于此者,而其语言气象,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但其下学工夫实未至此,故夫子虽喟然与之,而终以为狂也(约作于乾道四年,1168年)。①
陈焞为湖湘派著名学者,也是朱子的重要讲友之一。朱子的《文集》收入了朱子答陈明仲的书信共计十六封,黄震曾指出:“答陈明仲书,多辨佛学。”②可见,陈也算是一位溺佛者。而这是引导我们解读以上文字的一个重要线索。
陈来先生疑这封信当作于朱熹39岁前后,但无确证③。考《文集》的同一卷中有“喻及《论语》诸说以此,久不修报,然观大概贪慕高远、说得过当处多,却不是言下正意”云云,则这封信正是朱子对陈明仲之“《论语》诸说”的回复无疑。陈明仲“曾点说”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其极可能失之高远和空泛,因此朱子才会强调曾点的所对是“未尝少出其位”,其用意,显然是在敲打陈。
本文值得我们注意之处是,在此信中朱子首次提出了自己对“曾点气象”的评价。这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会在后文中对朱子的这些评价进行繁琐的比较,以发现其中细微的异同。
具体到这封信的内容,朱子说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与《论语集注》“曾点言志”一节的初稿一致,这完全是对谢良佐的“曾点说”中“见道”和“不累”说的继承;而其说曾点“其语言气象,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但其下学工夫实未至此……而终以为狂也”云云,则显然是来自明道的“曾点说”。由此可见,此时朱子对“曾点言志”一节的看法基本上是以上述二人为准,对谢良佐也还没有贬词。再者,朱子认为曾点“胸次洒落,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则从侧面反映出他当时正在把“洒落”当成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朱子对陈焞强调曾点的“见道无疑”,“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正是在强调“曾点气象”的儒家特色,这也是朱子对“曾点气象”进行儒家化诠释的一个体现。另一方面,朱子此时已经很注意曾点的欠缺工夫的狂的一面,并对此做出了批评,其言外之意正是要明确儒释异同之辨和虚实之辨。陈明仲属于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而谢良佐又是湖湘学派的思想源头。朱子在这封信中对陈明仲的批判,其实也包含着对湖湘学派的整体批判,并预示着他批判谢良佐思想的开始。果然,在朱子作《记谢上蔡论语疑义》的同一年,在回复方士繇就“曾点言志”一节的提问时,就开始公开批判谢的“曾点说”:
夫子梦寐周公,正是圣人至诚不息处,然时止时行无所凝滞,亦未尝不洒落也。故及其衰则不复梦亦可见矣。若是合做底事,则岂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为高,乃老庄之偏说。上蔡所论曾点事似好,然其说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约作于乾道七年,1171年)。①
方士繇(字伯谟,一字伯休,号远庵,1148—1199),1172年前后从朱子学。②陆游《方伯谟墓志铭》记其情况颇详:
……六经皆通,尤长于《易》,亦颇好《老子》……又曰:“释氏固夷也,至于立志坚决,吾亦有取焉”。其博学兼取,不以百家之驳掩所长……工于书……好方技,治疾有奇验,能逆决生死……③
陈荣捷先生曾指出,方伯谟“淡于义理,浓于文词”④,方伯谟所学之驳杂于上文可见一斑。陆游认为上述杂学对于方来说,“然在伯谟甫皆不足言”,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这里,方伯谟给朱子之信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大概是他在解说《论语·而中》的“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节时,在把孔子的这一心境和为谢良佐所渲染的“忘物”境界相比附。对此,朱子一方面认为孔子“时止时行、无所凝滞”,因此他虽然因衰老而不梦周公与此前有所不同,但其洒落则始终未变。另一方面,朱子转而强调,学者尤其不能“以忘物为高”,否则必定会流于佛老,这显然是针对方伯谟的好佛老方外之学而发的。其三,朱子则重点指出谢良佐的“曾点说”虽有其好的一面,但是其过度渲染“忘”有流于老庄的嫌疑。朱子的这一说法与他作于同时期的《记谢上蔡论语疑义》中认为谢良佐“论语说”是“旷荡无可捞摸,便更向别处走,此其立言之病也”①的总体认识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了他对于谢的思想由偏爱到反思的过渡心态。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文中发现朱子对“洒落”境界的欣赏态度。
一年后,石墪(字子重,号克斋,?—1182)②把自己研读《论语》此节的心得寄给朱子以求印证,其中就包括他对“曾点言志”一节的看法: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天机自动,不知其所以然(约作于乾道八年,1172年)。③对此,朱子指出:
门人详记曾皙舍瑟之事,但欲见其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石的说法)则流于庄列之徒矣。且人之举动,孰非天机之自动耶?然亦只此便见曾皙狂处,盖所见高而涵养未至也。④
朱子意味,《论语》本文是要突出曾点的“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但是石子重却在把曾点的这一“气象”归结为“不知其所以然”,就有虚说“气象”,把“气象”无化的意味。故钱穆先生即认为“子重之说,即谢上蔡以列子御风而行相比之说也”①,这在朱子看来正是禅老之说。对于这个意思,朱子在《文集》的同一卷中有更为详细的说明,其点出石子重的病处也更为明显:
按,孔子言“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四句,而以“惟心之谓欤”一句结之,正是直指心之体用,而言其周流变化、神明不测之妙也。若谓“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则是孔子所以言心体者,乃只说得心之病矣。圣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两字有善有恶,不可皆谓“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谓“心之本体,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盖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体,则不知所存者果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为哉(作于淳熙元年,1174年)?②
朱子指出,孔子以操存舍亡、变化不测论心,只是要强调心的周流变化,变动不居,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把它归结为“无”,乃至于进而摒弃“操而存者”,更不是要让人去一味追求“不可以存亡言者”的神秘心体(如中和旧说者)。朱子暗示,石子重之论心、之论“曾点气象”,都犯有这个毛病。另外,朱子还强调,“天机自动”只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的自然状态,根本不值得渲染,而学者更需要从自然发展到应然,要历阶而上,实下工夫。曾点之狂,就在于他只有见处,而涵养未至,因此有流为庄老的倾向。总之,朱子这封信的精神还是儒释之辨和有无之辨。
一年后,吕祖谦在与朱子的通信中提到:
将尧舜事业横在胸中,此《(易)传》说所谓有其善者也。①
上文已经提到,吕祖谦对曾点评价甚高。他并不认为曾点有“言不副行”的毛病。他也对谢良佐的“曾点说”做了正面的解读,认为其含义是要强调心存善念,并以此和《易传》比附。朱子在答信中,再次对谢的“曾点说”提出了批评:
上蔡“尧舜事业横在胸中”之说,若谓尧舜自将已做了底事业横在胸中,则世间无此等小器量底尧舜;若说学者,则凡圣贤一言一行皆当潜心玩索,要识得他底蕴,自家分上一一要用,岂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丧志之说,盖是箴上蔡记诵博识而不理会道理之病,渠得此语,遂一向扫荡,直要得胸中旷然无一毫所能,则可谓矫枉过其正矣。观其论曾点事,遂及列子御风,以为易做,则可见也。大抵明道所谓与学者语,如扶醉人,真是如此。来喻有惩创太过之说,亦正谓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约作于乾道九年,1173年)。①
于朱子,谢的“曾点说”的核心是强调要胸中无事,扫荡一切,这是他对程明道针砭其“玩物丧志”的矫枉过正。朱子强调,于学者而言,正应当着实去做下学工夫,必须要胸中有事才可。当然,朱子也在强调,若学者把“必有事焉”理解为“博识而不理会道理”,或者是为道理所缚却不得“洒落”,这同样也是偏失。
两年以后,朱子与吕祖谦编成《近思录》一书。大约在同时②,邓䌹致信朱子,就此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一条为:
䌹谓“大意”者,得非天理流行之妙,圣贤作用之气象欤?二子胸中洒落,无一毫亏欠,安行天理之至,盖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但二子已能窥测乎此,未必身造乎此也,故曰已见大意。③
邓䌹(字卫老,福建将乐人,生卒不详,与其兄邓邦老同游于朱子之门,著有《近思录问答》)④,认为曾点和漆雕开所见的“大意”,是“天理流行”和“圣贤气象”,因此二人能“胸中洒落,无一毫亏欠”。但他们只是窥测到此,却没有“身造于实地”,这都是朱子论“曾点气象”上的一贯态度。对此,朱子答曰:
且如此说,亦未有病,然须实下功夫,真有见处,方有意味耳(约作于淳熙二年后,1175年后)。①
朱子告诫邓不是能只是空头讨论此问题,而要有在做工夫中增进对此问题的了解。不久,邓再次致信朱子,就此问题再次提出个人的见解。邓的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而朱子的复信则直截了当地指出:
曾点之说,乃不真实之尤者,今亦未须便论见处,且当理会如何是实下功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当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摸笼罩将去,即人人会说,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济事,反害事耳(约作于淳熙二年后,1175年后)。②
诚如朱子所言,邓䌹的说法本身并没有明显的毛病。而朱子重在告诫他注意反身于己,实下工夫去体会,不能空说道理。于朱子,真实不仅意味着说法不错,而且意味着我对它们实有诸己。而这也是《文集》所收书信中朱子所反复告诫邓卫老的核心内容。如:针对邓卫老对“孔颜乐处”的评论,朱子指出“此等处未易一言断,且宜虚心玩味,兼考圣贤为学用力处实下功夫,方自见得。如此硬说无益于事也”;针对邓卫老对“视听思虑动作皆天理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的评论,朱子则强调“识字是紧要处,要识得时,须是学始得”;针对邓卫老对张横渠“横渠先生谓范巽之曰:吾辈不及古人病源何在”的评论,朱子则指出“横渠先生之意,正要学者将此题目时时省察,使之积久贯熟而自得之耳。非谓只要如此说杀也”;针对邓卫老对周敦颐和张载的评论,则指出“不可只如此说了便休,须是常切玩味涵养也”。可见,大概邓有虚说“气象”的毛病,因此朱子才会这样反复告诫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回复邓卫老的第二封信,是他所有论“曾点气象”中最严厉的一例,而《近思录》的成书时间与鹅湖之会相距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由此可以推测,大概朱子的复信也是有激之言吧。朱子此后反复告诫学人要注意真正的“为己”,否则纵然说的道理不差也于事于己无补,这些都应该导源于此。
但是,朱子之对谢上蔡思想的批判,在更深层次上遇到了一个麻烦:如何对待谢上蔡与程明道之间思想上的一致性。上文已经提到,谢上蔡的许多观点都是对程明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其最显著者,上蔡的“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即是明道的“浮云过目”说和“放开说”的发挥。而朱子在对待二人的态度上,则一面“必为明道回护”,一面则“专以归咎上蔡”②,这不能不产生诸多矛盾。事实上,诚如后文所指出的,朱子在具有类似“气象”的曾点、程明道、陆象山之间,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完全回护程明道,同时极力为曾点辩护,却大力的批判陆学。朱子的这一做法同样引发了诸多的矛盾,而深入地分析朱子之所以这样做的隐衷,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朱陆异同,也会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精神。本书在下文中会对此进一步的说明。
随着朱子思想的日渐成熟,朱子也开始与人讨论《论语》“曾点言志”一节,如他针对陈焞(字明仲,生卒不详)的来信就强调说:
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故虽夫子有如或知尔之问,而其所对亦未尝少出其位焉。盖若将终身于此者,而其语言气象,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但其下学工夫实未至此,故夫子虽喟然与之,而终以为狂也(约作于乾道四年,1168年)。①
陈焞为湖湘派著名学者,也是朱子的重要讲友之一。朱子的《文集》收入了朱子答陈明仲的书信共计十六封,黄震曾指出:“答陈明仲书,多辨佛学。”②可见,陈也算是一位溺佛者。而这是引导我们解读以上文字的一个重要线索。
陈来先生疑这封信当作于朱熹39岁前后,但无确证③。考《文集》的同一卷中有“喻及《论语》诸说以此,久不修报,然观大概贪慕高远、说得过当处多,却不是言下正意”云云,则这封信正是朱子对陈明仲之“《论语》诸说”的回复无疑。陈明仲“曾点说”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其极可能失之高远和空泛,因此朱子才会强调曾点的所对是“未尝少出其位”,其用意,显然是在敲打陈。
本文值得我们注意之处是,在此信中朱子首次提出了自己对“曾点气象”的评价。这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会在后文中对朱子的这些评价进行繁琐的比较,以发现其中细微的异同。
具体到这封信的内容,朱子说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与《论语集注》“曾点言志”一节的初稿一致,这完全是对谢良佐的“曾点说”中“见道”和“不累”说的继承;而其说曾点“其语言气象,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但其下学工夫实未至此……而终以为狂也”云云,则显然是来自明道的“曾点说”。由此可见,此时朱子对“曾点言志”一节的看法基本上是以上述二人为准,对谢良佐也还没有贬词。再者,朱子认为曾点“胸次洒落,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则从侧面反映出他当时正在把“洒落”当成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朱子对陈焞强调曾点的“见道无疑”,“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正是在强调“曾点气象”的儒家特色,这也是朱子对“曾点气象”进行儒家化诠释的一个体现。另一方面,朱子此时已经很注意曾点的欠缺工夫的狂的一面,并对此做出了批评,其言外之意正是要明确儒释异同之辨和虚实之辨。陈明仲属于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而谢良佐又是湖湘学派的思想源头。朱子在这封信中对陈明仲的批判,其实也包含着对湖湘学派的整体批判,并预示着他批判谢良佐思想的开始。果然,在朱子作《记谢上蔡论语疑义》的同一年,在回复方士繇就“曾点言志”一节的提问时,就开始公开批判谢的“曾点说”:
夫子梦寐周公,正是圣人至诚不息处,然时止时行无所凝滞,亦未尝不洒落也。故及其衰则不复梦亦可见矣。若是合做底事,则岂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为高,乃老庄之偏说。上蔡所论曾点事似好,然其说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约作于乾道七年,1171年)。①
方士繇(字伯谟,一字伯休,号远庵,1148—1199),1172年前后从朱子学。②陆游《方伯谟墓志铭》记其情况颇详:
……六经皆通,尤长于《易》,亦颇好《老子》……又曰:“释氏固夷也,至于立志坚决,吾亦有取焉”。其博学兼取,不以百家之驳掩所长……工于书……好方技,治疾有奇验,能逆决生死……③
陈荣捷先生曾指出,方伯谟“淡于义理,浓于文词”④,方伯谟所学之驳杂于上文可见一斑。陆游认为上述杂学对于方来说,“然在伯谟甫皆不足言”,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这里,方伯谟给朱子之信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大概是他在解说《论语·而中》的“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节时,在把孔子的这一心境和为谢良佐所渲染的“忘物”境界相比附。对此,朱子一方面认为孔子“时止时行、无所凝滞”,因此他虽然因衰老而不梦周公与此前有所不同,但其洒落则始终未变。另一方面,朱子转而强调,学者尤其不能“以忘物为高”,否则必定会流于佛老,这显然是针对方伯谟的好佛老方外之学而发的。其三,朱子则重点指出谢良佐的“曾点说”虽有其好的一面,但是其过度渲染“忘”有流于老庄的嫌疑。朱子的这一说法与他作于同时期的《记谢上蔡论语疑义》中认为谢良佐“论语说”是“旷荡无可捞摸,便更向别处走,此其立言之病也”①的总体认识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了他对于谢的思想由偏爱到反思的过渡心态。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文中发现朱子对“洒落”境界的欣赏态度。
一年后,石墪(字子重,号克斋,?—1182)②把自己研读《论语》此节的心得寄给朱子以求印证,其中就包括他对“曾点言志”一节的看法: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天机自动,不知其所以然(约作于乾道八年,1172年)。③对此,朱子指出:
门人详记曾皙舍瑟之事,但欲见其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石的说法)则流于庄列之徒矣。且人之举动,孰非天机之自动耶?然亦只此便见曾皙狂处,盖所见高而涵养未至也。④
朱子意味,《论语》本文是要突出曾点的“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但是石子重却在把曾点的这一“气象”归结为“不知其所以然”,就有虚说“气象”,把“气象”无化的意味。故钱穆先生即认为“子重之说,即谢上蔡以列子御风而行相比之说也”①,这在朱子看来正是禅老之说。对于这个意思,朱子在《文集》的同一卷中有更为详细的说明,其点出石子重的病处也更为明显:
按,孔子言“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四句,而以“惟心之谓欤”一句结之,正是直指心之体用,而言其周流变化、神明不测之妙也。若谓“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则是孔子所以言心体者,乃只说得心之病矣。圣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两字有善有恶,不可皆谓“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谓“心之本体,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盖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体,则不知所存者果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为哉(作于淳熙元年,1174年)?②
朱子指出,孔子以操存舍亡、变化不测论心,只是要强调心的周流变化,变动不居,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把它归结为“无”,乃至于进而摒弃“操而存者”,更不是要让人去一味追求“不可以存亡言者”的神秘心体(如中和旧说者)。朱子暗示,石子重之论心、之论“曾点气象”,都犯有这个毛病。另外,朱子还强调,“天机自动”只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的自然状态,根本不值得渲染,而学者更需要从自然发展到应然,要历阶而上,实下工夫。曾点之狂,就在于他只有见处,而涵养未至,因此有流为庄老的倾向。总之,朱子这封信的精神还是儒释之辨和有无之辨。
一年后,吕祖谦在与朱子的通信中提到:
将尧舜事业横在胸中,此《(易)传》说所谓有其善者也。①
上文已经提到,吕祖谦对曾点评价甚高。他并不认为曾点有“言不副行”的毛病。他也对谢良佐的“曾点说”做了正面的解读,认为其含义是要强调心存善念,并以此和《易传》比附。朱子在答信中,再次对谢的“曾点说”提出了批评:
上蔡“尧舜事业横在胸中”之说,若谓尧舜自将已做了底事业横在胸中,则世间无此等小器量底尧舜;若说学者,则凡圣贤一言一行皆当潜心玩索,要识得他底蕴,自家分上一一要用,岂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丧志之说,盖是箴上蔡记诵博识而不理会道理之病,渠得此语,遂一向扫荡,直要得胸中旷然无一毫所能,则可谓矫枉过其正矣。观其论曾点事,遂及列子御风,以为易做,则可见也。大抵明道所谓与学者语,如扶醉人,真是如此。来喻有惩创太过之说,亦正谓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约作于乾道九年,1173年)。①
于朱子,谢的“曾点说”的核心是强调要胸中无事,扫荡一切,这是他对程明道针砭其“玩物丧志”的矫枉过正。朱子强调,于学者而言,正应当着实去做下学工夫,必须要胸中有事才可。当然,朱子也在强调,若学者把“必有事焉”理解为“博识而不理会道理”,或者是为道理所缚却不得“洒落”,这同样也是偏失。
两年以后,朱子与吕祖谦编成《近思录》一书。大约在同时②,邓䌹致信朱子,就此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一条为:
䌹谓“大意”者,得非天理流行之妙,圣贤作用之气象欤?二子胸中洒落,无一毫亏欠,安行天理之至,盖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但二子已能窥测乎此,未必身造乎此也,故曰已见大意。③
邓䌹(字卫老,福建将乐人,生卒不详,与其兄邓邦老同游于朱子之门,著有《近思录问答》)④,认为曾点和漆雕开所见的“大意”,是“天理流行”和“圣贤气象”,因此二人能“胸中洒落,无一毫亏欠”。但他们只是窥测到此,却没有“身造于实地”,这都是朱子论“曾点气象”上的一贯态度。对此,朱子答曰:
且如此说,亦未有病,然须实下功夫,真有见处,方有意味耳(约作于淳熙二年后,1175年后)。①
朱子告诫邓不是能只是空头讨论此问题,而要有在做工夫中增进对此问题的了解。不久,邓再次致信朱子,就此问题再次提出个人的见解。邓的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而朱子的复信则直截了当地指出:
曾点之说,乃不真实之尤者,今亦未须便论见处,且当理会如何是实下功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当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摸笼罩将去,即人人会说,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济事,反害事耳(约作于淳熙二年后,1175年后)。②
诚如朱子所言,邓䌹的说法本身并没有明显的毛病。而朱子重在告诫他注意反身于己,实下工夫去体会,不能空说道理。于朱子,真实不仅意味着说法不错,而且意味着我对它们实有诸己。而这也是《文集》所收书信中朱子所反复告诫邓卫老的核心内容。如:针对邓卫老对“孔颜乐处”的评论,朱子指出“此等处未易一言断,且宜虚心玩味,兼考圣贤为学用力处实下功夫,方自见得。如此硬说无益于事也”;针对邓卫老对“视听思虑动作皆天理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的评论,朱子则强调“识字是紧要处,要识得时,须是学始得”;针对邓卫老对张横渠“横渠先生谓范巽之曰:吾辈不及古人病源何在”的评论,朱子则指出“横渠先生之意,正要学者将此题目时时省察,使之积久贯熟而自得之耳。非谓只要如此说杀也”;针对邓卫老对周敦颐和张载的评论,则指出“不可只如此说了便休,须是常切玩味涵养也”。可见,大概邓有虚说“气象”的毛病,因此朱子才会这样反复告诫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回复邓卫老的第二封信,是他所有论“曾点气象”中最严厉的一例,而《近思录》的成书时间与鹅湖之会相距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由此可以推测,大概朱子的复信也是有激之言吧。朱子此后反复告诫学人要注意真正的“为己”,否则纵然说的道理不差也于事于己无补,这些都应该导源于此。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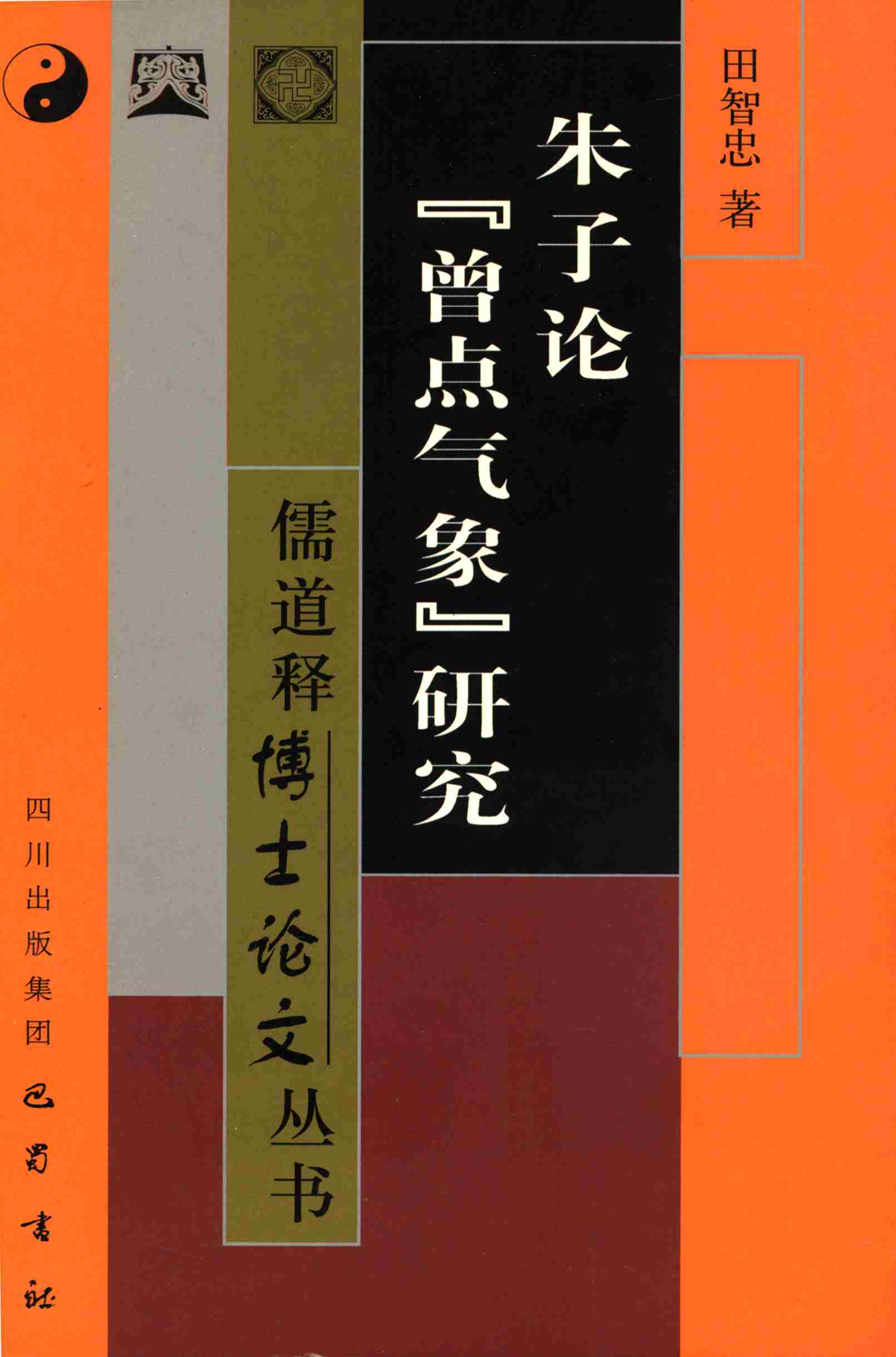
《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出版者:四川出版集团
本书从朱熹关于“曾点气象”话题的讨论契入,直探朱子思想中的有无虚实之辨和儒学与佛老之辨等关键问题,旁及历史上相关“曾点气象”的评论,进而引出中国哲学中关于精神境界、本体与功夫的讨论。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