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学延平阶段
| 内容出处: | 《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350 |
| 颗粒名称: | 二 从学延平阶段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6 |
| 页码: | 102-117 |
| 摘要: |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朱子学习儒学的第二个阶段,即从师于李延平的时期。在这一阶段,朱子实现了从泛滥佛老向二程之学的转变,从“泥书册”向吾身而求之的转变,以及确立了理一分殊、强调虚实之辩的为学宗旨。这些变化都与李延平对他的影响有关。文章还提到了朱子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拜访李延平和与其他人的交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这一阶段,朱子还开始写作《四书集注》,并在其中体现了他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阐释。 |
| 关键词: | 朱熹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朱子寻求为学之方的第二个阶段,指其从学于李延平的时期。由于朱子对延平有一个从“父执”到“师事”的发展过程①,因此这一阶段与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必然会有些重叠。在这一阶段,朱子在寻求为学工夫上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一是从泛滥佛老向一意归本二程之学的转变;二是从“泥书册”,“为道理所缚”向开始即吾身而求之的转变;其三是确立了理一分殊、强调虚实之辩的为学宗旨。这都与李延平对他的影响有关。当然,李侗也曾向朱子介绍过他的主静涵养、求洒落的为学工夫,但朱子对此没有契合。
绍兴二十三年,朱子时年二十四岁,在赴任同安途中,顺路拜访李延平。学界对于这次访问都非常重视,朱子日后回忆到:
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时年十九)。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辅广录)①
朱子初见延平,向他提到了自己宣扬“儒佛一理”的“禅说”,但是他的这些“侗宏阔之言”,并没有得到延平的首肯。延平所批评朱子的焦点,是认为他的这一说法“疑似乱真”,“不是”儒家的正理。因此,延平才会让他看“圣贤言语”来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若延平认为朱子所说的禅法“不是”正宗禅法,却让他去看圣贤言语,这显然有些不合情理)。但是,朱子对此并不服气。他认为李侗没有理会“儒释彼此两不相妨、可以并进”,(而不是怀疑李侗不懂禅学)的道理,疑心延平主张辨析儒佛之异同,是“多事”之举。李延平才告诉他,儒学的真精神不在于其语佛老相通之处,而在于其和佛老相异的一面,在日常之殊理上,而不是在悬空的一理上②。并且,李延平还基于虚实之辨的立场,告诫朱子要真正在儒学本身上用力,在“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③。对于这一点,赵师夏(字致道,号远庵,为朱熹长孙女婿)也有清楚的说明:
文公先生尝谓师夏曰:“余之始学,亦务为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①
刘承相先生已经指出:“延平所言,‘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一语,朱子称为‘此其要也’,则可知该语乃朱子后来对延平所教之总体的概括性提法。”②刘的这一说法还是恰当的。上述这句话的确不是李延平当时所说的原话。而到了金履祥(初名祥,更名开祥,后以开祥非学者名,又改,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1232—1303)那里,李延平训导朱子的话就变成了:
李侗云:天下理一而分殊,今君于何处腾空处理会得一个大道理,更不去分殊上体认?③
这段话显然是杂糅赵师夏的《延平答问跋》和朱子后来所作的《延平先生李公行状》而成,完全是老师训导学生的口气。这就更是以讹传讹了,不足置信。
不过,这次会面还是对朱子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使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天下理一而已”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不过,朱子当时对佛老的迷恋并没有马上被扭转。他对李延平的说法由疑到信,大致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而其产生转变的内因正是李延平劝导他的“读圣贤言语”——典型者就是朱子之彻悟《论语》中的“子夏之门人小子章”。对于这个问题,朱子后来有详细的说明,学者们也有细致的考察。①综合上述资料,朱子此前认为此章在强调“理无大小”,“本末无二道”。但他对此看法又始终心存疑问,认为这似乎与《论语》原文不符。在知同安时,他受李延平的教导,以及明道“君子教人有序”说法的引导,经反复思考,认识到“理无大小”指的是“(理)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坐起,不可拣择,此所以为教人有序也”②。这也就是说,朱子认为“理无大小”强调的是本末大小都是理的体现,因此必须“从头做起,不可拣择”。应该说,朱子此刻的所悟还只是在为“理无大小”一句做注解,至于朱子在此后进一步推导出“事有大小,而理无大小”,那已经不是同安时的观点了。不过,“从头做起”实际就是李侗所说的“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这也透露出了他对儒学与佛老思想异同的最初觉醒。
随着朱子在阅读儒学经典中逐渐感到“渐渐有味”,他对李延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通书问讯逐渐发展到了师事延平。朱子的正式师事延平,也是他结束泛滥佛老阶段而一意归本儒学的标志。
朱子师事延平后的思想交流情况,在他亲手编辑的《延平答问》中有详细的记录。当代学者也有所总结。本文则从其对朱子探求为学之方的影响这一角度,略做归纳。
其一,由泥书册到既重书册,同时也做涵养身心、体验天理之工夫的转变。上文已经指出,苦读是朱子此前阶段为学的基本宗旨。在师事李延平之后,朱子一开始主要是在就儒学的章句训诂问题向他求教:《论语》是朱子问讯的主要话题①,其他则广泛涉及到了以下书籍:
胡文定,(胡安国,字康候,谥文定,1074—1138)《春秋解》,伊川《春秋传》,《横渠语解》,《二程语解》,上蔡《论语说》,《二程语录》,《遗书》,《二苏语孟》,《濂溪遗文》(作者注:濂溪遗文不应该是书名),《颍滨语孟》,吕与叔,(吕大临,字与叔,1044—1091)《中庸解》,《龟山语解》,《和靖语解》,胡明仲,(胡宏,字仁仲,1106—1161,作者注:明仲实为胡寅的字②)《论语解》,《太极图说》,《上蔡语录》,《通书》以及《二程文集》等。③
朱子在苦读儒学经典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泥于章句训诂、悬空说理、颇为道理所缚、内外离绝不相赅贯等诸弊端。而李延平从一开始就希望扭转朱子的这一弊端,让他把用力的重点转移到反身而求,涵养本源上。《延平答问》首载李延平于绍兴二十七年给朱子的复信中,就指出:
于涵养用力处,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①
这里,延平显然是在把涵养和为己之学联系了起来。朱子此前已与李侗有过书信往来,而他之所以选择此信作为《延平答问》一书的开篇,也是要有意突出这一精神的意思。其实,类似的文字在李延平给朱子的复信中比比皆是,如:
尝爱黄鲁直(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1045—1105)作濂溪诗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胸中洒落即作为尽洒落矣。学者至此,虽甚远,亦不可不常存此体段在胸中,庶几遇事廓然,于道理方少进,愿更存养如此。②
对于李延平的上述教诲,朱子很快就有所领悟:
讲学近见延平李先生,始略窥门户……大概此事以涵养本原为先,讲论经旨特以辅此而已。向来泛滥出入无所适从,名为学问,而实何有?亦可笑耳……(作于绍兴三十年十二月间,1160年)。③
我们从《延平答问》所收录的信件中发现,朱李二人答问的内容也在逐渐从章句训诂为主,向逐渐讨论涵养心性为主转变:二人六年间的通信共计二十四封信。就篇幅而论,其中后三年的十六封信在篇幅上反而不如前三年的八封信。就内容而论,朱子后三年书信中,李延平告诫朱子注意在日用间做工夫的话语,则明显在增多。在朱子后来所做的《延平行状》中,他再次把这一点概括为:
(李侗)盖尝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①
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见其为一物而不违乎心目之间也。②
李延平这里所强调的,是要让人明确读书与其个人道德修养的关系,注意用尊德性这个本来统摄道问学,实现二者之间的贯通。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外在的知识转化为“己物”,进而展开为主体自觉的道德贱履工夫,最终臻至洒落、融释之境。而从朱子后来在《文集》和《朱子语类》中对此反复强调,以及他在李延平末后随即对已发未发问题刻苦参究的这一事实来看,朱子确实已经认定《中庸》的已发未发问题是探求为学之方上的关键,并把李延平的这一教导视为自己的基本人生信条。那种认为朱子偏于“道问学”的指责,实不足以服朱子之心。
不过,前贤多已指出,李延平非常希望朱子能在做涵养本源的工夫中实现“洒落”。其所说的“涵养”,指的就是“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的“龟山门下相传指诀”①;而其所说的“洒落”,实指一种“有道者气象”。正如后文中所指出的,在李侗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子都在把“洒落”当成为一个正面的词汇,其对“洒落”的理解也不仅仅限于“对义理的玩味至融会贯通、无所滞碍”②的层面,而是包涵了相当程度的境界论成分。
但是,朱子毕生对“洒落”的理解,始终带有浓厚的理性色彩,而与李延平对“洒落”颇具神秘色彩的理解不尽相同。同时,正是由于“洒落”具有多义性,这也使得朱子对于“洒落”的态度也非常复杂:既有对于世人所宣扬的那种流于放荡的“洒落”的严词批判,也有对他所理解那种正面的“洒落”的高度赞扬。朱子对于“洒落”的微妙态度也集中地反映在了他对于“曾点气象”的评论上。
我们知道,自宋代理学兴起之初,是否有“贱履工夫”,已经成为区别传统的儒生(文章、训诂)与理学人士的重要标准,而朱子从儒学角度对“贱履工夫”的自觉追求与实践,也标志着他此时已经完全归本于理学系统。
这里需要指出,朱子此时还只是在笼统意义上接受了李延平的教导。但是,至于如何具体去做涵养本源的工夫,朱子却始终没有头绪。他对李延平时时教导的“道南旨诀”,也并不相契。对于此中的原因,本文以为,此中原因固然有朱子“贪听讲论,窃好章句”的原因,也有其受根深蒂固的知性思维限定的原因。不过本文认为,对于当时刚刚走出佛老影响的朱子来说,很难把李延平的“静中观未发气象”与佛老之学中的禅定划清界限,这才是他拒绝李侗为学工夫的根本原因。此后的理学发展史也多次证明,强调在静坐中严格划清与佛老之学的界限,是很难成功的。不管习静者多么的在反复暗示他要时时保持一种道德心之警觉,他都会很快进入那种超越善恶的空灵心境,得到一种类似于禅乐的忘我或是与天地一体的神秘体验。这是出于人的生理反应的必然。静坐者若对此不加警觉,就会流向佛老的阵营中①。至少在当时的朱子看来,李侗所谓在静中涵养出的“景象”,与他曾在禅宗静修中出现过的“湛然虚明”、“昭昭灵灵”的景象并无根本上的区别。尽管后来朱子不便对李侗有太多之微词,但他还是通过对杨时等人的批判,隐约指出“道南指诀”在总体上有偏静和逃禅的倾向,而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在李侗死后不久,便对湖湘学派的为学工夫心有所属的原因所在。事实上,从朱子走出佛老的影响开始,他也就很难再与具有神秘、直觉主义特色的道南之学合拍了。
朱子自师从李延平后,逐渐接受了李“不能悬空追逐‘理一’,而要在‘分殊’处踏实做工夫”的训导,并且把这一训导理解为“下学上达、即物穷理”的理性活动。而静坐体验未发正是在“大本”处直接用力,难怪朱子会对此心存疑义。再者,朱子一向认为“心莫非已发”(见《中和旧说三》),而二程又强调“未发之前不可寻觅”的意思,这些因素都使当时仍然泥于书册的朱子无法寻觅到所谓的“未发之大本”。朱子最终选择小程子的理性主义思想是势所必然。
其二,李延平促进了朱子“理一分殊”思想体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方法论、工夫论的形成,也促进朱子逐渐把虚实之辨作为其个人的基本为学宗旨。
“理一分殊”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即物穷理、下学上达,重视辨析虚实之辨,这是朱子思想体系的立论基础,也是朱子确立为学工夫的根本。而李延平对于朱子“理一分殊”观念的形成,功莫大焉。
李延平在朱子二十四岁来拜访时,已经在用类似于“理一分殊”的话头来引导朱子走出佛老的影响。此后,李延平也在有意时时提醒朱子不能玄虚说高妙的一理,而是要注意在“分殊”上做工夫。也正是在李延平的引导下,朱子才会在荒山寒夜时,听杜鹃啼叫苦读《论语》中,顿悟“子夏之门人小子”章的意指,而其所悟,实际上也接近于“理一分殊”的道理。不过,就目前资料看来,朱子对“理一分殊”思想的真正自觉也有一个过程,而在此问题上,“李侗所欲以教授朱熹者和朱熹本人思想之取向”,也有所不同①。
以下资料表明,至少在朱子二十九岁时,他还缺乏对“理一分殊”的完全自觉:
胡丈书中复主前日一贯之说甚力,但云若理会得向上一著,则无有内外上下远近边际,廓然四通八达矣。熹窃谓此语深符鄙意。盖既无有内外边际,则何往而非一贯哉?(作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①
朱子此书的本意是在讨论一贯与忠恕的关系问题,此不详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书中所称许的胡宪的观点,正是所谓的“侗宏阔之言”,而朱子的所谓“既无有内外边际,则何往而非一贯”,其眼光还只落在“向上一著”上,显然离“理一分殊”甚远。因此,朱子后来才会一再强调“与范直阁说‘忠恕’是三十岁时书(实际上是二十九岁),大概也是,然说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较别”云云②。但是,李延平在本年末回答朱子就“一贯、忠恕”问题的问讯时,却并没有提示他用“理一分殊”的思路来处理这一问题。这似乎表明,在此之前,“理一分殊”还没有进入他们的问题域③。而直到两年后,李延平再次致书朱子时,才开始用“理一分殊”的话头来提醒他:
所云见《语录》(二程之语录,当时还尚未成书,)中有“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一句,即认得《西铭》意旨,所见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广求之。然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④
这里,李延平明确告诫朱子“理会分殊”更能代表儒学的基本精神。这也促使朱子把用力的重心从注意“理一”转移到了“分殊”上,转到去关注儒学不同于佛老的地方上。朱子自言:“自见李先生,为学始就平实”①,所指的就是这一转向。事实上,甚至是在朱子三十三岁之际,李延平还在就此话题点拨朱子:
又云“须体认到此纯一不杂处,方见浑然与物同体气象”一段,语却无病。又云“从此推出分殊合宜处,便是义。以下数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贯之,盖五常百行无往而非仁也”,此说大概是。然细推之,却似不曾体认得伊川所谓“理一分殊”、龟山云“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之意,盖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②
这里,李延平还是在就朱子重“理一”有余,而重分殊不足的弊端而提醒他。正是在李延平此信的引导下,朱子才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理一分殊”思想:
问:熹昨妄谓“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乎禽兽者”,先生不以为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说,敢复求正于左右。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体之中即无丝毫欠剩,其一气之运亦无顷刻停息,所谓仁也。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然则仁之为仁,人与物不得不同。知人之为人而存之,人与物不得不异。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说,而先生以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详伊川之语推测之,窃谓“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内本体未发时看。合而言之,则莫非此理。然其中无一物之不该(赅),便自有许多差别,虽散殊错糅不可名状,而纤微之间同异毕显,所谓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此二句乃是于发用处该(赅)摄本体而言,因此端绪而下工夫以推寻之处也。盖“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处。而下文两句,即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谓也。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动之机,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谓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体处,便是义,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尽。义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离乎义之内也。然则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义,前此乃以从此推出分殊合宜处为义,失之远矣。又不知如此上,则推测又还是否?①
朱子此说与前说的最大不同,乃是否定了“从此(指“理一”)推出分殊合宜处为义”的说法,转而认为“义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离乎义之内也。然则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义”。朱子此前视“理一”与“分殊”为本末关系,其潜在的思想是厚本薄末,好同恶异,喜大耻小;而现在则开始把它们看成是体用关系,其潜在的思想是“理一”必须要落实和实现于分殊上,二者是一体之两面。这也标志着朱子“理一分殊”思想的初步形成。当然,李延平在给朱子的复信中针对朱子一味注重单纯的理论辨析的弊端,提醒他不能“只是说话”,而要注意把这一认识转化为自己在日用上做反身贱履的工夫,这又属于李延平教导朱子的一贯立场①。
朱子“理一分殊”思想体系的初步确立,对其日后强调即物穷理、重视下学上达,反对虚说玄妙之境界以及其浓厚批判意识的形成,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仅以虚实之辨为例,李延平从一开始就告诫朱子不能空说无限道理,而在对“仁”的讨论中,他再次告诫朱子要注意“即用见体”:
某尝以谓仁字极难讲说,只看天理统体便是。更心字亦难指说,唯认取发用处是心。二字须要体认得极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难说,《论语》一部,只是说与门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几私欲沈、天理见、则知仁矣。如颜子仲弓之问,圣人所以答之之语,皆其要切用力处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体通有无,贯幽明,无不包括,与人指示于发用处求之也。①
这一精神,正是日后朱子论学的根本宗旨。我们在后文中可见,朱子在晚年就“曾点气象”问题训导陈淳的话语中,所强调的最根本一点,正在于此。
总之,通过与李侗的接触,朱子在辩明儒佛之辨上、在对个人为学工夫的选择上都基本上确定下了其一生的基调。朱子于李延平所强调的体验未发的为学之方不契,这大大影响了其后来对“曾点气象”的基本态度。
绍兴二十三年,朱子时年二十四岁,在赴任同安途中,顺路拜访李延平。学界对于这次访问都非常重视,朱子日后回忆到:
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时年十九)。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辅广录)①
朱子初见延平,向他提到了自己宣扬“儒佛一理”的“禅说”,但是他的这些“侗宏阔之言”,并没有得到延平的首肯。延平所批评朱子的焦点,是认为他的这一说法“疑似乱真”,“不是”儒家的正理。因此,延平才会让他看“圣贤言语”来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若延平认为朱子所说的禅法“不是”正宗禅法,却让他去看圣贤言语,这显然有些不合情理)。但是,朱子对此并不服气。他认为李侗没有理会“儒释彼此两不相妨、可以并进”,(而不是怀疑李侗不懂禅学)的道理,疑心延平主张辨析儒佛之异同,是“多事”之举。李延平才告诉他,儒学的真精神不在于其语佛老相通之处,而在于其和佛老相异的一面,在日常之殊理上,而不是在悬空的一理上②。并且,李延平还基于虚实之辨的立场,告诫朱子要真正在儒学本身上用力,在“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③。对于这一点,赵师夏(字致道,号远庵,为朱熹长孙女婿)也有清楚的说明:
文公先生尝谓师夏曰:“余之始学,亦务为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①
刘承相先生已经指出:“延平所言,‘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一语,朱子称为‘此其要也’,则可知该语乃朱子后来对延平所教之总体的概括性提法。”②刘的这一说法还是恰当的。上述这句话的确不是李延平当时所说的原话。而到了金履祥(初名祥,更名开祥,后以开祥非学者名,又改,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1232—1303)那里,李延平训导朱子的话就变成了:
李侗云:天下理一而分殊,今君于何处腾空处理会得一个大道理,更不去分殊上体认?③
这段话显然是杂糅赵师夏的《延平答问跋》和朱子后来所作的《延平先生李公行状》而成,完全是老师训导学生的口气。这就更是以讹传讹了,不足置信。
不过,这次会面还是对朱子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使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天下理一而已”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不过,朱子当时对佛老的迷恋并没有马上被扭转。他对李延平的说法由疑到信,大致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而其产生转变的内因正是李延平劝导他的“读圣贤言语”——典型者就是朱子之彻悟《论语》中的“子夏之门人小子章”。对于这个问题,朱子后来有详细的说明,学者们也有细致的考察。①综合上述资料,朱子此前认为此章在强调“理无大小”,“本末无二道”。但他对此看法又始终心存疑问,认为这似乎与《论语》原文不符。在知同安时,他受李延平的教导,以及明道“君子教人有序”说法的引导,经反复思考,认识到“理无大小”指的是“(理)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坐起,不可拣择,此所以为教人有序也”②。这也就是说,朱子认为“理无大小”强调的是本末大小都是理的体现,因此必须“从头做起,不可拣择”。应该说,朱子此刻的所悟还只是在为“理无大小”一句做注解,至于朱子在此后进一步推导出“事有大小,而理无大小”,那已经不是同安时的观点了。不过,“从头做起”实际就是李侗所说的“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这也透露出了他对儒学与佛老思想异同的最初觉醒。
随着朱子在阅读儒学经典中逐渐感到“渐渐有味”,他对李延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通书问讯逐渐发展到了师事延平。朱子的正式师事延平,也是他结束泛滥佛老阶段而一意归本儒学的标志。
朱子师事延平后的思想交流情况,在他亲手编辑的《延平答问》中有详细的记录。当代学者也有所总结。本文则从其对朱子探求为学之方的影响这一角度,略做归纳。
其一,由泥书册到既重书册,同时也做涵养身心、体验天理之工夫的转变。上文已经指出,苦读是朱子此前阶段为学的基本宗旨。在师事李延平之后,朱子一开始主要是在就儒学的章句训诂问题向他求教:《论语》是朱子问讯的主要话题①,其他则广泛涉及到了以下书籍:
胡文定,(胡安国,字康候,谥文定,1074—1138)《春秋解》,伊川《春秋传》,《横渠语解》,《二程语解》,上蔡《论语说》,《二程语录》,《遗书》,《二苏语孟》,《濂溪遗文》(作者注:濂溪遗文不应该是书名),《颍滨语孟》,吕与叔,(吕大临,字与叔,1044—1091)《中庸解》,《龟山语解》,《和靖语解》,胡明仲,(胡宏,字仁仲,1106—1161,作者注:明仲实为胡寅的字②)《论语解》,《太极图说》,《上蔡语录》,《通书》以及《二程文集》等。③
朱子在苦读儒学经典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泥于章句训诂、悬空说理、颇为道理所缚、内外离绝不相赅贯等诸弊端。而李延平从一开始就希望扭转朱子的这一弊端,让他把用力的重点转移到反身而求,涵养本源上。《延平答问》首载李延平于绍兴二十七年给朱子的复信中,就指出:
于涵养用力处,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①
这里,延平显然是在把涵养和为己之学联系了起来。朱子此前已与李侗有过书信往来,而他之所以选择此信作为《延平答问》一书的开篇,也是要有意突出这一精神的意思。其实,类似的文字在李延平给朱子的复信中比比皆是,如:
尝爱黄鲁直(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1045—1105)作濂溪诗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胸中洒落即作为尽洒落矣。学者至此,虽甚远,亦不可不常存此体段在胸中,庶几遇事廓然,于道理方少进,愿更存养如此。②
对于李延平的上述教诲,朱子很快就有所领悟:
讲学近见延平李先生,始略窥门户……大概此事以涵养本原为先,讲论经旨特以辅此而已。向来泛滥出入无所适从,名为学问,而实何有?亦可笑耳……(作于绍兴三十年十二月间,1160年)。③
我们从《延平答问》所收录的信件中发现,朱李二人答问的内容也在逐渐从章句训诂为主,向逐渐讨论涵养心性为主转变:二人六年间的通信共计二十四封信。就篇幅而论,其中后三年的十六封信在篇幅上反而不如前三年的八封信。就内容而论,朱子后三年书信中,李延平告诫朱子注意在日用间做工夫的话语,则明显在增多。在朱子后来所做的《延平行状》中,他再次把这一点概括为:
(李侗)盖尝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①
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见其为一物而不违乎心目之间也。②
李延平这里所强调的,是要让人明确读书与其个人道德修养的关系,注意用尊德性这个本来统摄道问学,实现二者之间的贯通。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外在的知识转化为“己物”,进而展开为主体自觉的道德贱履工夫,最终臻至洒落、融释之境。而从朱子后来在《文集》和《朱子语类》中对此反复强调,以及他在李延平末后随即对已发未发问题刻苦参究的这一事实来看,朱子确实已经认定《中庸》的已发未发问题是探求为学之方上的关键,并把李延平的这一教导视为自己的基本人生信条。那种认为朱子偏于“道问学”的指责,实不足以服朱子之心。
不过,前贤多已指出,李延平非常希望朱子能在做涵养本源的工夫中实现“洒落”。其所说的“涵养”,指的就是“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的“龟山门下相传指诀”①;而其所说的“洒落”,实指一种“有道者气象”。正如后文中所指出的,在李侗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子都在把“洒落”当成为一个正面的词汇,其对“洒落”的理解也不仅仅限于“对义理的玩味至融会贯通、无所滞碍”②的层面,而是包涵了相当程度的境界论成分。
但是,朱子毕生对“洒落”的理解,始终带有浓厚的理性色彩,而与李延平对“洒落”颇具神秘色彩的理解不尽相同。同时,正是由于“洒落”具有多义性,这也使得朱子对于“洒落”的态度也非常复杂:既有对于世人所宣扬的那种流于放荡的“洒落”的严词批判,也有对他所理解那种正面的“洒落”的高度赞扬。朱子对于“洒落”的微妙态度也集中地反映在了他对于“曾点气象”的评论上。
我们知道,自宋代理学兴起之初,是否有“贱履工夫”,已经成为区别传统的儒生(文章、训诂)与理学人士的重要标准,而朱子从儒学角度对“贱履工夫”的自觉追求与实践,也标志着他此时已经完全归本于理学系统。
这里需要指出,朱子此时还只是在笼统意义上接受了李延平的教导。但是,至于如何具体去做涵养本源的工夫,朱子却始终没有头绪。他对李延平时时教导的“道南旨诀”,也并不相契。对于此中的原因,本文以为,此中原因固然有朱子“贪听讲论,窃好章句”的原因,也有其受根深蒂固的知性思维限定的原因。不过本文认为,对于当时刚刚走出佛老影响的朱子来说,很难把李延平的“静中观未发气象”与佛老之学中的禅定划清界限,这才是他拒绝李侗为学工夫的根本原因。此后的理学发展史也多次证明,强调在静坐中严格划清与佛老之学的界限,是很难成功的。不管习静者多么的在反复暗示他要时时保持一种道德心之警觉,他都会很快进入那种超越善恶的空灵心境,得到一种类似于禅乐的忘我或是与天地一体的神秘体验。这是出于人的生理反应的必然。静坐者若对此不加警觉,就会流向佛老的阵营中①。至少在当时的朱子看来,李侗所谓在静中涵养出的“景象”,与他曾在禅宗静修中出现过的“湛然虚明”、“昭昭灵灵”的景象并无根本上的区别。尽管后来朱子不便对李侗有太多之微词,但他还是通过对杨时等人的批判,隐约指出“道南指诀”在总体上有偏静和逃禅的倾向,而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在李侗死后不久,便对湖湘学派的为学工夫心有所属的原因所在。事实上,从朱子走出佛老的影响开始,他也就很难再与具有神秘、直觉主义特色的道南之学合拍了。
朱子自师从李延平后,逐渐接受了李“不能悬空追逐‘理一’,而要在‘分殊’处踏实做工夫”的训导,并且把这一训导理解为“下学上达、即物穷理”的理性活动。而静坐体验未发正是在“大本”处直接用力,难怪朱子会对此心存疑义。再者,朱子一向认为“心莫非已发”(见《中和旧说三》),而二程又强调“未发之前不可寻觅”的意思,这些因素都使当时仍然泥于书册的朱子无法寻觅到所谓的“未发之大本”。朱子最终选择小程子的理性主义思想是势所必然。
其二,李延平促进了朱子“理一分殊”思想体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方法论、工夫论的形成,也促进朱子逐渐把虚实之辨作为其个人的基本为学宗旨。
“理一分殊”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即物穷理、下学上达,重视辨析虚实之辨,这是朱子思想体系的立论基础,也是朱子确立为学工夫的根本。而李延平对于朱子“理一分殊”观念的形成,功莫大焉。
李延平在朱子二十四岁来拜访时,已经在用类似于“理一分殊”的话头来引导朱子走出佛老的影响。此后,李延平也在有意时时提醒朱子不能玄虚说高妙的一理,而是要注意在“分殊”上做工夫。也正是在李延平的引导下,朱子才会在荒山寒夜时,听杜鹃啼叫苦读《论语》中,顿悟“子夏之门人小子”章的意指,而其所悟,实际上也接近于“理一分殊”的道理。不过,就目前资料看来,朱子对“理一分殊”思想的真正自觉也有一个过程,而在此问题上,“李侗所欲以教授朱熹者和朱熹本人思想之取向”,也有所不同①。
以下资料表明,至少在朱子二十九岁时,他还缺乏对“理一分殊”的完全自觉:
胡丈书中复主前日一贯之说甚力,但云若理会得向上一著,则无有内外上下远近边际,廓然四通八达矣。熹窃谓此语深符鄙意。盖既无有内外边际,则何往而非一贯哉?(作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①
朱子此书的本意是在讨论一贯与忠恕的关系问题,此不详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书中所称许的胡宪的观点,正是所谓的“侗宏阔之言”,而朱子的所谓“既无有内外边际,则何往而非一贯”,其眼光还只落在“向上一著”上,显然离“理一分殊”甚远。因此,朱子后来才会一再强调“与范直阁说‘忠恕’是三十岁时书(实际上是二十九岁),大概也是,然说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较别”云云②。但是,李延平在本年末回答朱子就“一贯、忠恕”问题的问讯时,却并没有提示他用“理一分殊”的思路来处理这一问题。这似乎表明,在此之前,“理一分殊”还没有进入他们的问题域③。而直到两年后,李延平再次致书朱子时,才开始用“理一分殊”的话头来提醒他:
所云见《语录》(二程之语录,当时还尚未成书,)中有“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一句,即认得《西铭》意旨,所见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广求之。然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④
这里,李延平明确告诫朱子“理会分殊”更能代表儒学的基本精神。这也促使朱子把用力的重心从注意“理一”转移到了“分殊”上,转到去关注儒学不同于佛老的地方上。朱子自言:“自见李先生,为学始就平实”①,所指的就是这一转向。事实上,甚至是在朱子三十三岁之际,李延平还在就此话题点拨朱子:
又云“须体认到此纯一不杂处,方见浑然与物同体气象”一段,语却无病。又云“从此推出分殊合宜处,便是义。以下数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贯之,盖五常百行无往而非仁也”,此说大概是。然细推之,却似不曾体认得伊川所谓“理一分殊”、龟山云“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之意,盖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②
这里,李延平还是在就朱子重“理一”有余,而重分殊不足的弊端而提醒他。正是在李延平此信的引导下,朱子才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理一分殊”思想:
问:熹昨妄谓“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乎禽兽者”,先生不以为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说,敢复求正于左右。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体之中即无丝毫欠剩,其一气之运亦无顷刻停息,所谓仁也。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然则仁之为仁,人与物不得不同。知人之为人而存之,人与物不得不异。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说,而先生以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详伊川之语推测之,窃谓“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内本体未发时看。合而言之,则莫非此理。然其中无一物之不该(赅),便自有许多差别,虽散殊错糅不可名状,而纤微之间同异毕显,所谓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此二句乃是于发用处该(赅)摄本体而言,因此端绪而下工夫以推寻之处也。盖“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处。而下文两句,即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谓也。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动之机,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谓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体处,便是义,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尽。义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离乎义之内也。然则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义,前此乃以从此推出分殊合宜处为义,失之远矣。又不知如此上,则推测又还是否?①
朱子此说与前说的最大不同,乃是否定了“从此(指“理一”)推出分殊合宜处为义”的说法,转而认为“义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离乎义之内也。然则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义”。朱子此前视“理一”与“分殊”为本末关系,其潜在的思想是厚本薄末,好同恶异,喜大耻小;而现在则开始把它们看成是体用关系,其潜在的思想是“理一”必须要落实和实现于分殊上,二者是一体之两面。这也标志着朱子“理一分殊”思想的初步形成。当然,李延平在给朱子的复信中针对朱子一味注重单纯的理论辨析的弊端,提醒他不能“只是说话”,而要注意把这一认识转化为自己在日用上做反身贱履的工夫,这又属于李延平教导朱子的一贯立场①。
朱子“理一分殊”思想体系的初步确立,对其日后强调即物穷理、重视下学上达,反对虚说玄妙之境界以及其浓厚批判意识的形成,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仅以虚实之辨为例,李延平从一开始就告诫朱子不能空说无限道理,而在对“仁”的讨论中,他再次告诫朱子要注意“即用见体”:
某尝以谓仁字极难讲说,只看天理统体便是。更心字亦难指说,唯认取发用处是心。二字须要体认得极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难说,《论语》一部,只是说与门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几私欲沈、天理见、则知仁矣。如颜子仲弓之问,圣人所以答之之语,皆其要切用力处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体通有无,贯幽明,无不包括,与人指示于发用处求之也。①
这一精神,正是日后朱子论学的根本宗旨。我们在后文中可见,朱子在晚年就“曾点气象”问题训导陈淳的话语中,所强调的最根本一点,正在于此。
总之,通过与李侗的接触,朱子在辩明儒佛之辨上、在对个人为学工夫的选择上都基本上确定下了其一生的基调。朱子于李延平所强调的体验未发的为学之方不契,这大大影响了其后来对“曾点气象”的基本态度。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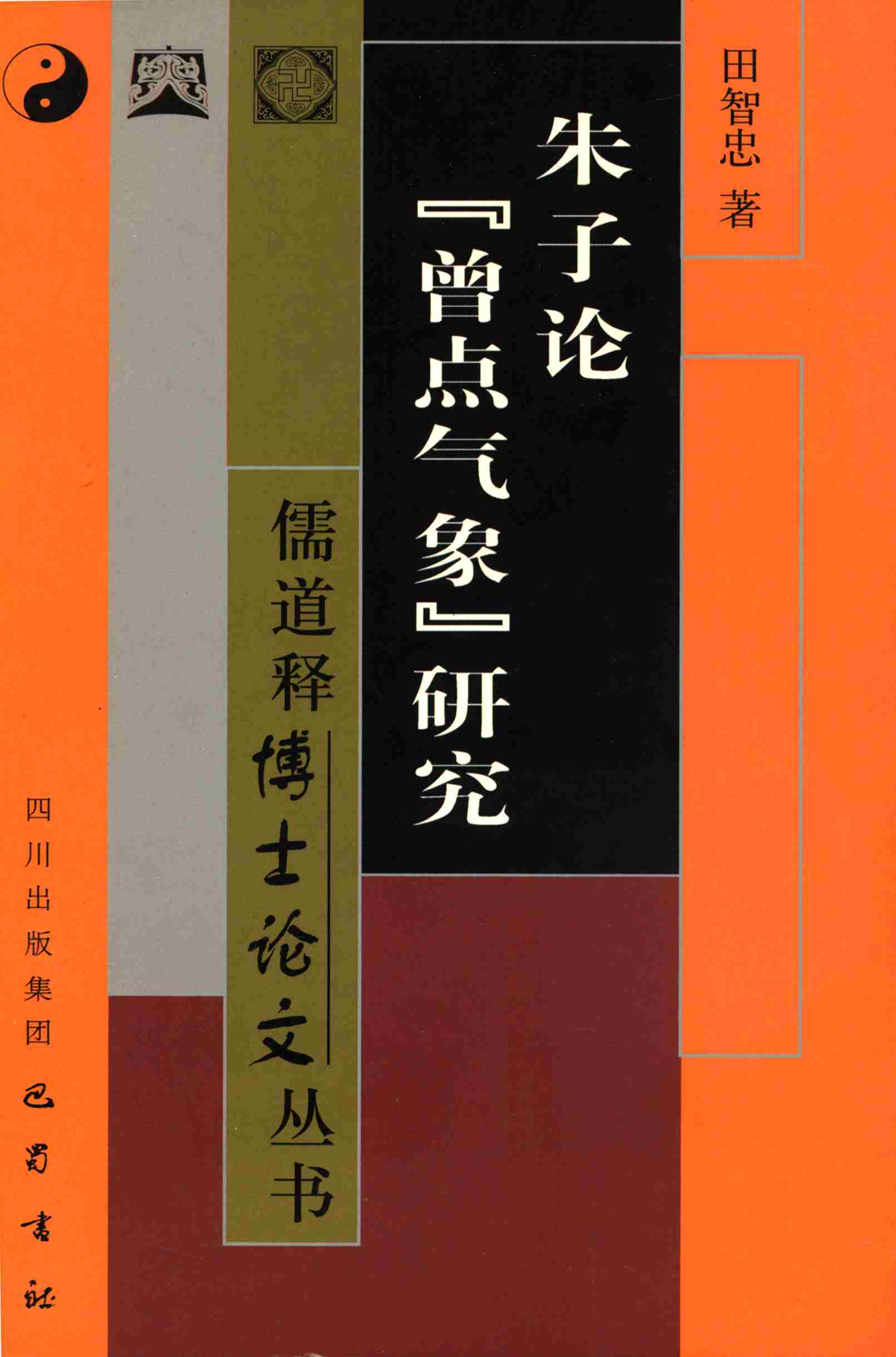
《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出版者:四川出版集团
本书从朱熹关于“曾点气象”话题的讨论契入,直探朱子思想中的有无虚实之辨和儒学与佛老之辨等关键问题,旁及历史上相关“曾点气象”的评论,进而引出中国哲学中关于精神境界、本体与功夫的讨论。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