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延伸的思考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0》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895 |
| 颗粒名称: | 五、延伸的思考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4 |
| 页码: | 110-113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对禅宗进行了消极面的解析与批评,揭示了禅宗语言的特征以及其对学术表达的伤害。他对禅宗的“作用见性”以及伦理进行了分析和批评,警示了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和风险。虽然朱熹在吸收禅宗工夫方面有所肯定,但他也意识到其潜在的危险性。朱熹的禅宗批评对佛教、儒学和中国哲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可以促进它们的传播、发展和完善。 |
| 关键词: | 朱熹 禅宗 解析 |
内容
如上四个维度的考察表明,朱熹对禅宗语言、义理、伦理和工夫都是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的。而朱熹对禅宗的批评和否定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以儒学为绝对参照。朱熹批评禅宗语言,因为禅宗语言既不规范,也不严肃,这与儒家对言说的要求完全相悖。孔子提倡言说要做到:“以义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必须遵循规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孟子好辩,但讲究遵守规则:“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娄上》)与此比较,禅宗语言似乎就不那么在乎规矩了。朱熹批评禅宗“作用见性”,因为儒家的“性”是“理”,是仁、义、礼、智、信诸般道德,而“作用见性”意味着视、听、言、动是“性”,意味着嬉、笑、怒、骂是“性”,如此必然导致对儒家“理”的否定。朱熹批评禅宗伦理,因为儒家伦理重视纲常、推崇血亲、讲究秩序,而禅宗伦理将这些全都否弃了。朱熹批评“坐禅”,乃是因为与儒家的“静坐”比较,不仅没有“天地正学”,而且缺失了“敬”的工夫;朱熹批评“顿悟”,乃是因为与儒家求学问道方式完全相悖,儒学为学秩序是格物致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强调对知识把握的渐进性。可见,朱熹对禅宗的批评与否定完全是以儒学为参照的。二是以禅宗的“极端表现”为批评对象。朱熹批评禅宗语言,抓住其玄妙性、突兀性、模糊性等“缺点”,从而否定整个禅宗语言的作用和意义;朱熹批评禅宗义理,抓住“作用见性”之“作用”二字大做文章,将其实体化、广泛化,再将“由用显性”理解为由形下取代形上、由庸常取代神圣,进而导致对“性”“理”至上性的否定;朱熹批评禅宗伦理,则是盯住禅宗伦理中的“偏激现象”方面,所谓“伤害父母而不顾”,所谓“坐立无常”,并将这些“偏激现象”的负面效应加以放大,危言耸听地宣告禅宗已将一切伦理扫荡无遗,从而否定禅宗伦理存在的价值;朱熹批评禅宗工夫,将“坐禅”的空寂特性加以放大,指其为“呆守法”,又将“顿悟”的神秘特性加以放大,指其不能成为获得知识的正确方法。可见,朱熹批评禅宗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即都是针对语言、义理、伦理、工夫等方面的“极端现象”而开火的。以儒学为参照,那些被认定与儒学相悖的内容,自然被挡在朱熹理学之外;以禅宗“极端现象”为批评对象,以偏概全,且夸大消极面的危害,从而不能全面、正确认识禅宗、学习禅宗。二程曾说:“使其道不合于先王,固不愿学也;如其合于先王,则求之‘六经’足矣,奚必佛?”①这样就从认知坐标和方法两个方面构筑起阻碍禅宗进入朱熹理学的藩篱。因而就这个角度言,禅宗与朱子理学的关系呈现的是“离相”。
但对致力建构博大精深体系的朱熹而言,完全对禅宗视而不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事实上,对于能为其所用的元素,朱熹都是来者不拒的。在禅宗语言方面,朱熹不仅明确指出禅宗语言出自老庄:“老子先唱说,后来佛氏又做得脱洒广阔,然考其语多本庄列。”②是在老庄语言基础上改造而来:“凡彼言之精者,皆窃取庄列之说以为之。”③而且对心、太极、理、性等范畴的论述,也常常不自觉地表现为禅宗语言的形式,比如朱熹说:“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如饮食中鸡心、猪心之属,切开可见,人心亦然。只这些虚处便包藏许多道理,弥纶天地,赅括古今,推广得来,盖天盖地,莫不由此,此所以为人心之妙欤!”④不过,这种论述在禅宗那里似曾相识——“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即若无际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⑤而禅宗“语录体”普遍为宋代儒者所效仿,朱子自然不能例外,《朱子语类》即是杰出代表。因此,虽然朱熹对禅宗语言的理解存在片面之处,而且基本上持批评态度,但并没有完全排斥禅宗的语言形式。在禅宗义理方面,朱熹也有吸收。就心物关系言,朱熹说:“盖天下万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谓也。”①即认为世界万物无不在心中。但禅宗已有同样的观念:“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②朱熹说:“心虽是一物,却虚,故能包含万理。”③禅宗则有:“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④可见,朱熹对禅宗心物关系观念也是有吸收的。概言之,在朱熹,无物不在心中,在禅宗,心外无一物;在朱熹,心包万理,在禅宗,万法尽在心中。就“性悟性迷”言,朱熹说:“人性本善,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⑤禅宗则有:“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复真如,离妄念,本性净。”⑥可见,朱熹在“性悟性迷”观念上与禅宗也是基本一致的。朱熹在禅宗工夫面前表现得更为热情开放。朱熹说:“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养数十年。及其出来,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伟!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自动。”⑦又说:“重处不在怒与过上,只在不迁、不贰上。今不必问过之大小,怒之深浅。只不迁、不贰,是甚力量!便见工夫。佛家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过能不贰,直是难。”⑧可见,朱熹对禅宗工夫的确是发自内心的钦佩。从这个意义上看,禅宗与朱熹理学的关系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亲近性,所呈现的是一种“合相”。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朱熹对禅宗消极面解析与批评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朱熹揭示了禅宗语言的反逻辑、反定义特征,指出其含糊性、无规定性对学术表达造成的伤害,从而提示学者警惕禅宗语言的陷阱。⑨朱熹对“作用见性”的解析和批评,深刻觉悟到这一命题内含的张力,认识到“形上”因为过度依赖“形下”而走向瓦解的可能性,从而警示佛教界正确处理体用关系的必要性。朱熹对禅宗伦理的解析和批评,敏锐地意识到禅宗伦理的消极偏向,将基本人伦物理完全悬置,视伦理为累赘、为约束,言行举止正滑向不可控的状态,伦理被颠覆的风险越来越大。朱熹对禅宗工夫虽然有所肯定,并做了选择性吸收,但他显然意识到禅宗工夫潜在的危险性,除去“空寂无理”之外,更令他忧虑的是演变为目无章法、肆无忌惮之放荡,“无工夫便是工夫”成为时尚,直至走向虚妄。因此,就朱熹理学而言,朱熹对禅宗的吸收是经过认真思考和过滤的(尽管这种思考与过滤为认识水平所限),那些能进入并在朱熹理学中存活下去的元素,是因为朱熹颁发了“通行许可证”。而朱熹理解和批评禅宗的实践之特殊而重大的学术意义在于:对佛教、禅宗而言,应该以朱熹的批评为训,理性地传播、发展佛教;对儒学而言,应该以朱熹的批评为参照,对禅宗必须择优汰劣;对中国哲学而言,则需要在语言、义理、伦理、工夫等方面以禅宗为镜子,取长补短,有效地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完善。因此说,朱熹对禅宗理解和批评的实践,无论是对佛教还是对儒学,抑或对中国哲学,都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但对致力建构博大精深体系的朱熹而言,完全对禅宗视而不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事实上,对于能为其所用的元素,朱熹都是来者不拒的。在禅宗语言方面,朱熹不仅明确指出禅宗语言出自老庄:“老子先唱说,后来佛氏又做得脱洒广阔,然考其语多本庄列。”②是在老庄语言基础上改造而来:“凡彼言之精者,皆窃取庄列之说以为之。”③而且对心、太极、理、性等范畴的论述,也常常不自觉地表现为禅宗语言的形式,比如朱熹说:“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如饮食中鸡心、猪心之属,切开可见,人心亦然。只这些虚处便包藏许多道理,弥纶天地,赅括古今,推广得来,盖天盖地,莫不由此,此所以为人心之妙欤!”④不过,这种论述在禅宗那里似曾相识——“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即若无际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⑤而禅宗“语录体”普遍为宋代儒者所效仿,朱子自然不能例外,《朱子语类》即是杰出代表。因此,虽然朱熹对禅宗语言的理解存在片面之处,而且基本上持批评态度,但并没有完全排斥禅宗的语言形式。在禅宗义理方面,朱熹也有吸收。就心物关系言,朱熹说:“盖天下万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谓也。”①即认为世界万物无不在心中。但禅宗已有同样的观念:“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②朱熹说:“心虽是一物,却虚,故能包含万理。”③禅宗则有:“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④可见,朱熹对禅宗心物关系观念也是有吸收的。概言之,在朱熹,无物不在心中,在禅宗,心外无一物;在朱熹,心包万理,在禅宗,万法尽在心中。就“性悟性迷”言,朱熹说:“人性本善,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⑤禅宗则有:“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复真如,离妄念,本性净。”⑥可见,朱熹在“性悟性迷”观念上与禅宗也是基本一致的。朱熹在禅宗工夫面前表现得更为热情开放。朱熹说:“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养数十年。及其出来,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伟!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自动。”⑦又说:“重处不在怒与过上,只在不迁、不贰上。今不必问过之大小,怒之深浅。只不迁、不贰,是甚力量!便见工夫。佛家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过能不贰,直是难。”⑧可见,朱熹对禅宗工夫的确是发自内心的钦佩。从这个意义上看,禅宗与朱熹理学的关系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亲近性,所呈现的是一种“合相”。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朱熹对禅宗消极面解析与批评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朱熹揭示了禅宗语言的反逻辑、反定义特征,指出其含糊性、无规定性对学术表达造成的伤害,从而提示学者警惕禅宗语言的陷阱。⑨朱熹对“作用见性”的解析和批评,深刻觉悟到这一命题内含的张力,认识到“形上”因为过度依赖“形下”而走向瓦解的可能性,从而警示佛教界正确处理体用关系的必要性。朱熹对禅宗伦理的解析和批评,敏锐地意识到禅宗伦理的消极偏向,将基本人伦物理完全悬置,视伦理为累赘、为约束,言行举止正滑向不可控的状态,伦理被颠覆的风险越来越大。朱熹对禅宗工夫虽然有所肯定,并做了选择性吸收,但他显然意识到禅宗工夫潜在的危险性,除去“空寂无理”之外,更令他忧虑的是演变为目无章法、肆无忌惮之放荡,“无工夫便是工夫”成为时尚,直至走向虚妄。因此,就朱熹理学而言,朱熹对禅宗的吸收是经过认真思考和过滤的(尽管这种思考与过滤为认识水平所限),那些能进入并在朱熹理学中存活下去的元素,是因为朱熹颁发了“通行许可证”。而朱熹理解和批评禅宗的实践之特殊而重大的学术意义在于:对佛教、禅宗而言,应该以朱熹的批评为训,理性地传播、发展佛教;对儒学而言,应该以朱熹的批评为参照,对禅宗必须择优汰劣;对中国哲学而言,则需要在语言、义理、伦理、工夫等方面以禅宗为镜子,取长补短,有效地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完善。因此说,朱熹对禅宗理解和批评的实践,无论是对佛教还是对儒学,抑或对中国哲学,都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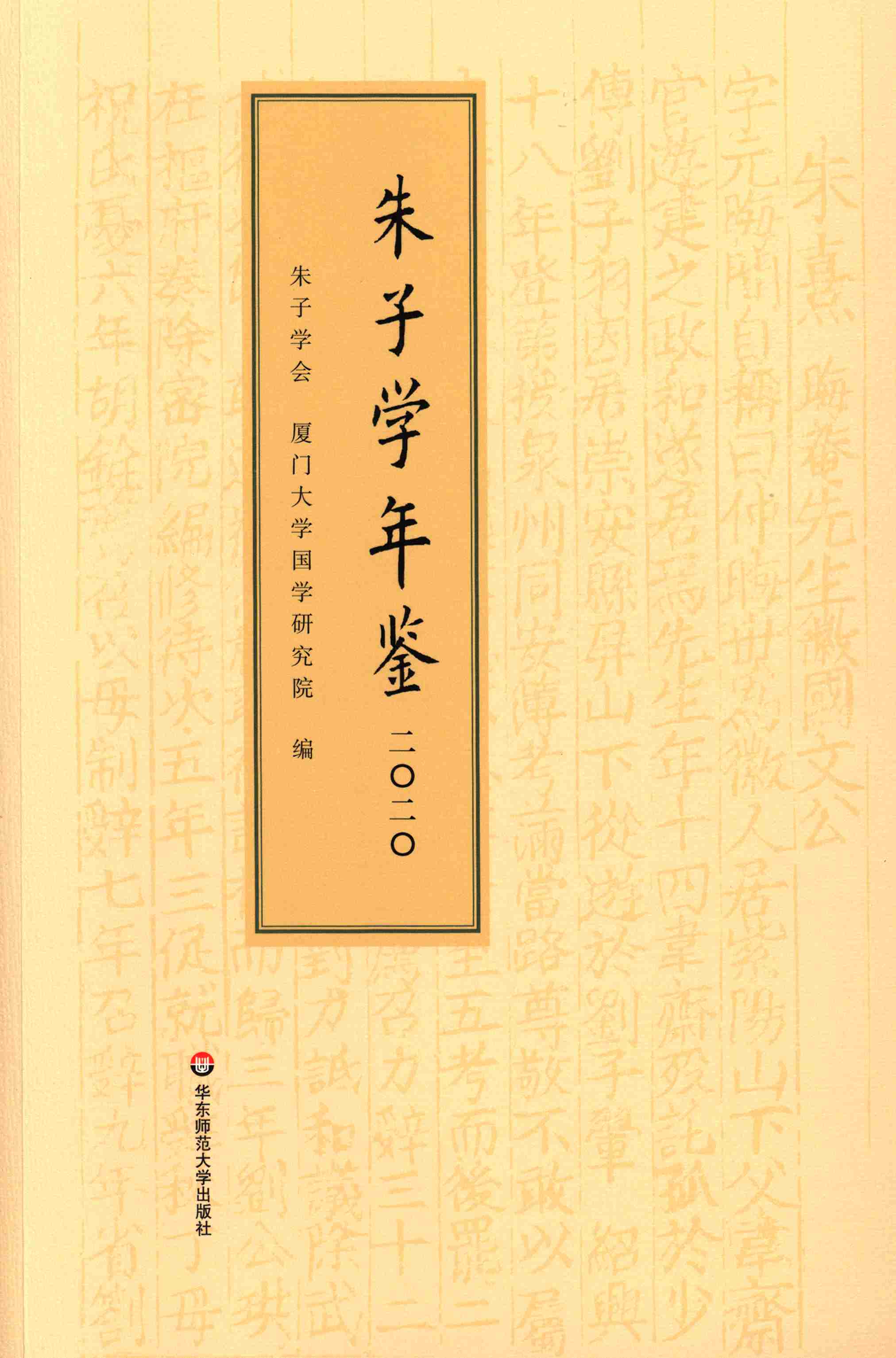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0》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以礼释仁的路径和意义》《2020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