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辩学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0》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888 |
| 颗粒名称: | 六、辩学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 |
| 页码: | 095-100 |
| 摘要: | 本文比较了孟子的好辩与孔子的温良恭俭让之间的不同,并探讨了程朱理学对于辩论的态度。文章指出程颢和朱熹都具有好辩的特点,但表现形式不同。辩论是基于人的性体中智之端的要求,表达了明辨是非的需要。朱熹强调知言在养气之前,是更为重要的前提。 |
| 关键词: | 孟子 好辩 程颢 |
内容
孟子“好辩”③,似与孔子“温良恭俭让”④大不同。前文尝引程颢比较孔孟之气象,可为表证。其实,二程兄弟亦有相似处,只是别具形态。程颢尝对程颐曰:
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⑤
程颢能够“随人材而成就之”,必浑厚附就,否则门人不敢亲近;但太亲近了,往往失其敬意,自然更难“尊严师道”,故有程颐门人立雪之严厉,这是以行代言。朱熹以孟子自任,好辩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不待细言举证,只需看《四书或问》自设问答,便足以为表证。
好辩与否,虽与性格不无关系,但更有不得已处。这不只是像韩愈所讲的“物不得其平则鸣”⑥,而更是因为人的性体所具四端的智之端,就是要明辨是非的。言是认知的表证,言有不明不清,或有分歧,自然要作分辨。换言之,辩是深具于人之性体的要求。因此,朱熹强调孟子虽然是知言与养气并举,但知言在先,是更具重要性的前提。《朱子语类》载:
知言,知理也。
知言,然后能养气。
孟子说养气,先说知言。先知得许多说话,是非邪正都无疑处,方能养此气也。
知言养气,虽是两事,其实相关,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之类。若知言,便见得是非邪正。义理昭然,则浩然之气自生。⑦
这几则语录,可谓层层推进,甚至推到极处,以为“义理昭然,则浩然之气自生”,颇有弱化养气,视之为知言的自然衍生。可见好辩决不是简单的个性问题。
此外,依孟子的自辩,“好辩”还有另一种“不得已也”。他从尧、舜讲起,经文、武、周公而至孔子,指出各时代都是不同的挑战,圣人们回应各自的挑战,任务与方式各不相同,而自己所处的当下,又是新的挑战,必须面对,这是他的“不得已”。孟子曰: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换言之,好辩除了性格、认知外,还具有担当之义。程朱对此是完全认同的。程颐曰:
仲尼圣人,其道大,当定、哀之时,人莫不尊之。后弟子各以其所学行,异端遂起,至孟子时,不得不辨也。①
而朱熹编撰《论孟精义》,除了自己“以备观省”外,诚如《自序》所言,也是因为二程以后,程门离散,所述相异,更有“自讬于程氏,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甚而“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颇已乡之”,故须“明圣传之统,成众说之长,折流俗之谬”。
当然,辩学重在知言,如何知言是辩学的关键。孟子曰: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②
程颢以为,孟子对这四种存在问题的言语有清楚的认识,而且知其所以然,故“孟子知言,即知道也”。程颢进而解释:
诐辞偏蔽,淫辞陷溺深,邪辞信其说至于耽惑,遁辞生于不正,穷著便遁,……此四者杨墨兼有。③
诐是片面,淫是过头,邪是不正,遁是躲闪,这样的言语现象分别表证着言说者对理的认识存在着片面、夸大、陷于歧路,以及理的亏欠。请举杨墨例具体见之。程颐曰:
孟子言墨子爱其兄之子犹邻之子,《墨子》书中何尝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大凡儒者学道,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杨子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④
杨时对此又有更具体的阐释,其曰:
每读《孟子》,观其论墨子苟利天下虽摩顶放踵为之,未尝不悯其为人也。原其心,岂有它哉?盖亦施不欲狭济不欲寡而已。此与世之横目自营者,固不可同日议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兽,孟子岂责人已甚乎?盖君子所以施诸身措之天下,各欲当其可而已。①
概言之,诐淫邪遁的言语之病,实质是对义理的认识发生偏差,而这种偏差的共同问题未当其可,即不能恰如其分。因此尽管墨子兼爱,“苟利天下虽摩顶放踵为之”,看似崇高,却偏离人的心性之正,在墨子还未必显其危害,但由源而流,势必成灾。这里,也佐证了程朱理学的持论必基于个体生存的主体性。
只是,“各欲当其可”,决不是容易的事。注意到了偏差或过分,自然是好事,但着意于求中,中也足以成为一种执念,最终成为障碍。程颐曰:
子莫见杨墨过不及,遂于过不及二者之间执之,却不知有当摩顶放踵利天下时,有当拔一毛利天下不为时,执中而不通变,与执一无异。总之,知言以辩学,言语只有恰如其分,才不流于诐淫邪遁;而这四种毛病虽提醒了认识与言语的主体,但并不是透导人为执中而执中,以至执中而不通变,否则实与诐淫邪遁一样流于弊病。
相对于孟子指出的诐淫邪遁,在知言的问题上,二程以为理学所面临的辩学更为困难。程颢曰:
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只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杨墨之害,亦经孟子辟之,所以廓如也。②
“杨子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都是儒者同道,只是各执一偏,而成毛病。佛老完全不同,他们在哲学的根本观念上与儒家就不同,而言语反而相近,似是而非,更容易迷惑人,为害尤甚。
比如心性问题。佛家自然也讲心性,而且稍不细究,确实与儒家很近似。程颢曰:
告子云生之谓性则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须是谓之性。皆谓之性则可,于中却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释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如此则不可。③
告子与孟子在性上的争辩是告子以生为性,而否定孟子主张的性善。性善与否,这当然是一种哲学预设,自可另当别论,但告子与孟子的分歧是显见的。佛家从言语上看,却是主张性善的,即所谓“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似乎与孟子性善论一样,但其实“蠢动含灵”大大溢出人的范围,这便与孟子性善论有着巨大的区别。
由于佛家把佛性落于整个“蠢动含灵”,因此对于“蠢动含灵”的大多数,便以生死的恐怖以利诱之,而又期望最终能识心见性,其实是上下间断,中间没有儒家讲的存养。佛家有出家的路径,但这根本上无法成为大多数人的道路。可以说,佛与儒在路径上的分歧也是泾渭分明的,但“尽心知性”的话却很相似。程颢曰:
释氏本怖死生为利,岂是公道?惟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元不相连属,但有间断,非道也。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谓识心见性是也,若存心养性一段事则无矣。彼固曰出家独善,便于道体自不足。质夫曰:“尽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养性,佛本不至此。”明道曰:“尽心知性,不假存养,其唯圣人乎?”①
除了心性问题,“觉”也是一个显见的例子。佛家与儒家都讲觉,若不分辩,就很容易混同。程颢曰: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释氏之云觉,甚底是觉斯道?甚底是觉斯民?②
这是就“觉”的内涵作分辩。佛家的“觉”在勘破、在超离凡尘,而儒家的“觉”在觉民、觉道,这个道是存于人世的道。此外,在方法上,佛家的“觉”与儒家的“觉”也截然不同。
或问伊川:“释氏有一宿觉、言下觉之说,如何?”曰:“何必浮图,孟子尝言觉字矣。曰:‘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知是知此事,觉是觉于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若于言下即悟,何啻读十年书。”又曰:“君子之学,则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而老子以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亦自贼其性与!”③
佛家的“觉”是极具神秘性的,而儒家的“觉”是基于读书明事理的。至于道家,则完全是走向反智的方向了。依孟子四端说,智是性体之一,故反智无异于“自贼其性”。
当然,朱熹在型塑程朱理学话语的过程中,更迫切的辩学任务还不在佛老,而更是同时代的“贵显名誉之士”④,其中也包括了前引《论孟精义自序》中所提到的“自讬于程氏,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在编撰《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与《论孟精义》之间,即1166年(37岁)时,朱熹就专门针对苏轼《易传》、苏辙《老子解》、张九成《中庸解》,以及吕大临《大学解》①撰《杂学辨》,进行辩驳;后十年,又针对一册不知何人所编的杂书,“意其或出于吾党,而于鄙意不能无所疑也,惧其流传久远,上累师门”,又撰《记疑》,以作辩正。朱熹的具体辩驳这里不作引述,仅据其诸辨小序,撮其指要而言之。
苏氏兄弟自是高才,苏轼“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②,但朱熹以为他对于《易》中没有弄明白处,却每欲臆言之,而又恐人指出毛病,就总是先讲不可解,又进而解之,“务为闪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读者茫然,虽欲攻之而无所措其辨”。③究其实,还是对性命之理有所不明。苏辙尤其“自许甚高”,以为当世无一人能合儒释道而言之,朱熹以为“其可谓无忌惮者与”,他的病不在于对佛的误解,而在于“学儒之失而流于异端”④。至于张九成与吕大临,张九成是杨时弟子,但逃儒归释,而自以为“世出、世间,两无遗恨矣”⑤,其实是阳儒阴释;“吕氏之先与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学最为近正,然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说,故其末流不能无出入之弊”⑥。朱熹的具体辨析都围绕着上揭各问题而进行。如果细读《杂学辨》《记疑》,不出前述知言中所示诸病,以及认识上的失中与失正之病,而言语之病的根源在于认识之病。
因此,程朱理学之辩学,最终指向在于识中与明白正意。对识中问题,二程几无异语。
明道曰:“学问,闻之知之者,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⑦
伊川曰:“中字最难识,须是默识心通。”⑧如何做到“默识心通”,二程也是持论无异。
明道曰:“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其间,然后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
伊川曰:“解义理,若一向靠书册,何由得?居之安,资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误人。”⑨
二程于此似更强调体会,但不可据此以为二程主张不读书。程颐所谓“若一向靠书册”,正表明他是针对着拘执于书册的毛病而作此强调。不过,由此也足以表证理学终究以个体生命的主体性为基础,并以此生命的自觉与充扩为目标。至于如何在辩学中明白正意,朱熹有一个非常亲切的说法:
某旧时看文字极难,诸家说尽用记。且如《毛诗》,那时未似如今说得如此条畅。古今诸家说,盖用记取,闲时将起思量。这一家说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说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说得全是,那家说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量,少间这正当道理,自然光明灿烂在心目间,如指诸掌。①
至此,辩学由对他者的辩驳而返归自身,从而使得他者构成了程朱理学话语形态的相关环节。他者理论虽然是后现代哲学的重要主题,但它的由来却也可以溯源于近代早期哲学。②这里自然无意于转移主题,由辩学的讨论转向存于其中的他者问题,而仅限于指出,当以他者问题的哲学视角来审视程朱理学的型塑过程,无可置疑地看到,程朱理学在接续孔孟传统的同时,也非常自觉地接续了孟子在辟杨墨的辩学中所呈现的他者问题。对于整个理学来说,完全异端化的佛道是他者,而对于朱熹来说,他者却呈现出多样性,至《论孟精义》的完成时是如此,此后也是如此。多样性的他者事实上构成了程朱理学话语构型中的重要区块,这不仅见诸程朱本人,而且已完全成为理学群体共有的普遍意识。何镐(1128—1175)的《杂学辨跋》从孟子辟杨墨讲起,将理学处理他者问题的历史原因、现实关系,以及为什么要专门针对“贵显名誉之士”而辩学,阐述得很清楚,并最终揭明了针对他者的辩学对于理学自身的意义。何镐曰:
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为心,大惧吾道之不明也,弗顾流俗之讥议,尝即其书破其疵缪,针其膏肓,使读者晓然知异端为非而圣言之为正也。学者苟能因其说而求至当之归,则诸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间,非特足以悟疑辨惑,亦由是可以造道焉。③
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⑤
程颢能够“随人材而成就之”,必浑厚附就,否则门人不敢亲近;但太亲近了,往往失其敬意,自然更难“尊严师道”,故有程颐门人立雪之严厉,这是以行代言。朱熹以孟子自任,好辩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不待细言举证,只需看《四书或问》自设问答,便足以为表证。
好辩与否,虽与性格不无关系,但更有不得已处。这不只是像韩愈所讲的“物不得其平则鸣”⑥,而更是因为人的性体所具四端的智之端,就是要明辨是非的。言是认知的表证,言有不明不清,或有分歧,自然要作分辨。换言之,辩是深具于人之性体的要求。因此,朱熹强调孟子虽然是知言与养气并举,但知言在先,是更具重要性的前提。《朱子语类》载:
知言,知理也。
知言,然后能养气。
孟子说养气,先说知言。先知得许多说话,是非邪正都无疑处,方能养此气也。
知言养气,虽是两事,其实相关,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之类。若知言,便见得是非邪正。义理昭然,则浩然之气自生。⑦
这几则语录,可谓层层推进,甚至推到极处,以为“义理昭然,则浩然之气自生”,颇有弱化养气,视之为知言的自然衍生。可见好辩决不是简单的个性问题。
此外,依孟子的自辩,“好辩”还有另一种“不得已也”。他从尧、舜讲起,经文、武、周公而至孔子,指出各时代都是不同的挑战,圣人们回应各自的挑战,任务与方式各不相同,而自己所处的当下,又是新的挑战,必须面对,这是他的“不得已”。孟子曰: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换言之,好辩除了性格、认知外,还具有担当之义。程朱对此是完全认同的。程颐曰:
仲尼圣人,其道大,当定、哀之时,人莫不尊之。后弟子各以其所学行,异端遂起,至孟子时,不得不辨也。①
而朱熹编撰《论孟精义》,除了自己“以备观省”外,诚如《自序》所言,也是因为二程以后,程门离散,所述相异,更有“自讬于程氏,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甚而“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颇已乡之”,故须“明圣传之统,成众说之长,折流俗之谬”。
当然,辩学重在知言,如何知言是辩学的关键。孟子曰: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②
程颢以为,孟子对这四种存在问题的言语有清楚的认识,而且知其所以然,故“孟子知言,即知道也”。程颢进而解释:
诐辞偏蔽,淫辞陷溺深,邪辞信其说至于耽惑,遁辞生于不正,穷著便遁,……此四者杨墨兼有。③
诐是片面,淫是过头,邪是不正,遁是躲闪,这样的言语现象分别表证着言说者对理的认识存在着片面、夸大、陷于歧路,以及理的亏欠。请举杨墨例具体见之。程颐曰:
孟子言墨子爱其兄之子犹邻之子,《墨子》书中何尝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大凡儒者学道,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杨子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④
杨时对此又有更具体的阐释,其曰:
每读《孟子》,观其论墨子苟利天下虽摩顶放踵为之,未尝不悯其为人也。原其心,岂有它哉?盖亦施不欲狭济不欲寡而已。此与世之横目自营者,固不可同日议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兽,孟子岂责人已甚乎?盖君子所以施诸身措之天下,各欲当其可而已。①
概言之,诐淫邪遁的言语之病,实质是对义理的认识发生偏差,而这种偏差的共同问题未当其可,即不能恰如其分。因此尽管墨子兼爱,“苟利天下虽摩顶放踵为之”,看似崇高,却偏离人的心性之正,在墨子还未必显其危害,但由源而流,势必成灾。这里,也佐证了程朱理学的持论必基于个体生存的主体性。
只是,“各欲当其可”,决不是容易的事。注意到了偏差或过分,自然是好事,但着意于求中,中也足以成为一种执念,最终成为障碍。程颐曰:
子莫见杨墨过不及,遂于过不及二者之间执之,却不知有当摩顶放踵利天下时,有当拔一毛利天下不为时,执中而不通变,与执一无异。总之,知言以辩学,言语只有恰如其分,才不流于诐淫邪遁;而这四种毛病虽提醒了认识与言语的主体,但并不是透导人为执中而执中,以至执中而不通变,否则实与诐淫邪遁一样流于弊病。
相对于孟子指出的诐淫邪遁,在知言的问题上,二程以为理学所面临的辩学更为困难。程颢曰:
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只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杨墨之害,亦经孟子辟之,所以廓如也。②
“杨子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都是儒者同道,只是各执一偏,而成毛病。佛老完全不同,他们在哲学的根本观念上与儒家就不同,而言语反而相近,似是而非,更容易迷惑人,为害尤甚。
比如心性问题。佛家自然也讲心性,而且稍不细究,确实与儒家很近似。程颢曰:
告子云生之谓性则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须是谓之性。皆谓之性则可,于中却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释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如此则不可。③
告子与孟子在性上的争辩是告子以生为性,而否定孟子主张的性善。性善与否,这当然是一种哲学预设,自可另当别论,但告子与孟子的分歧是显见的。佛家从言语上看,却是主张性善的,即所谓“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似乎与孟子性善论一样,但其实“蠢动含灵”大大溢出人的范围,这便与孟子性善论有着巨大的区别。
由于佛家把佛性落于整个“蠢动含灵”,因此对于“蠢动含灵”的大多数,便以生死的恐怖以利诱之,而又期望最终能识心见性,其实是上下间断,中间没有儒家讲的存养。佛家有出家的路径,但这根本上无法成为大多数人的道路。可以说,佛与儒在路径上的分歧也是泾渭分明的,但“尽心知性”的话却很相似。程颢曰:
释氏本怖死生为利,岂是公道?惟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元不相连属,但有间断,非道也。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谓识心见性是也,若存心养性一段事则无矣。彼固曰出家独善,便于道体自不足。质夫曰:“尽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养性,佛本不至此。”明道曰:“尽心知性,不假存养,其唯圣人乎?”①
除了心性问题,“觉”也是一个显见的例子。佛家与儒家都讲觉,若不分辩,就很容易混同。程颢曰: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释氏之云觉,甚底是觉斯道?甚底是觉斯民?②
这是就“觉”的内涵作分辩。佛家的“觉”在勘破、在超离凡尘,而儒家的“觉”在觉民、觉道,这个道是存于人世的道。此外,在方法上,佛家的“觉”与儒家的“觉”也截然不同。
或问伊川:“释氏有一宿觉、言下觉之说,如何?”曰:“何必浮图,孟子尝言觉字矣。曰:‘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知是知此事,觉是觉于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若于言下即悟,何啻读十年书。”又曰:“君子之学,则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而老子以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亦自贼其性与!”③
佛家的“觉”是极具神秘性的,而儒家的“觉”是基于读书明事理的。至于道家,则完全是走向反智的方向了。依孟子四端说,智是性体之一,故反智无异于“自贼其性”。
当然,朱熹在型塑程朱理学话语的过程中,更迫切的辩学任务还不在佛老,而更是同时代的“贵显名誉之士”④,其中也包括了前引《论孟精义自序》中所提到的“自讬于程氏,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在编撰《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与《论孟精义》之间,即1166年(37岁)时,朱熹就专门针对苏轼《易传》、苏辙《老子解》、张九成《中庸解》,以及吕大临《大学解》①撰《杂学辨》,进行辩驳;后十年,又针对一册不知何人所编的杂书,“意其或出于吾党,而于鄙意不能无所疑也,惧其流传久远,上累师门”,又撰《记疑》,以作辩正。朱熹的具体辩驳这里不作引述,仅据其诸辨小序,撮其指要而言之。
苏氏兄弟自是高才,苏轼“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②,但朱熹以为他对于《易》中没有弄明白处,却每欲臆言之,而又恐人指出毛病,就总是先讲不可解,又进而解之,“务为闪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读者茫然,虽欲攻之而无所措其辨”。③究其实,还是对性命之理有所不明。苏辙尤其“自许甚高”,以为当世无一人能合儒释道而言之,朱熹以为“其可谓无忌惮者与”,他的病不在于对佛的误解,而在于“学儒之失而流于异端”④。至于张九成与吕大临,张九成是杨时弟子,但逃儒归释,而自以为“世出、世间,两无遗恨矣”⑤,其实是阳儒阴释;“吕氏之先与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学最为近正,然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说,故其末流不能无出入之弊”⑥。朱熹的具体辨析都围绕着上揭各问题而进行。如果细读《杂学辨》《记疑》,不出前述知言中所示诸病,以及认识上的失中与失正之病,而言语之病的根源在于认识之病。
因此,程朱理学之辩学,最终指向在于识中与明白正意。对识中问题,二程几无异语。
明道曰:“学问,闻之知之者,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⑦
伊川曰:“中字最难识,须是默识心通。”⑧如何做到“默识心通”,二程也是持论无异。
明道曰:“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其间,然后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
伊川曰:“解义理,若一向靠书册,何由得?居之安,资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误人。”⑨
二程于此似更强调体会,但不可据此以为二程主张不读书。程颐所谓“若一向靠书册”,正表明他是针对着拘执于书册的毛病而作此强调。不过,由此也足以表证理学终究以个体生命的主体性为基础,并以此生命的自觉与充扩为目标。至于如何在辩学中明白正意,朱熹有一个非常亲切的说法:
某旧时看文字极难,诸家说尽用记。且如《毛诗》,那时未似如今说得如此条畅。古今诸家说,盖用记取,闲时将起思量。这一家说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说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说得全是,那家说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量,少间这正当道理,自然光明灿烂在心目间,如指诸掌。①
至此,辩学由对他者的辩驳而返归自身,从而使得他者构成了程朱理学话语形态的相关环节。他者理论虽然是后现代哲学的重要主题,但它的由来却也可以溯源于近代早期哲学。②这里自然无意于转移主题,由辩学的讨论转向存于其中的他者问题,而仅限于指出,当以他者问题的哲学视角来审视程朱理学的型塑过程,无可置疑地看到,程朱理学在接续孔孟传统的同时,也非常自觉地接续了孟子在辟杨墨的辩学中所呈现的他者问题。对于整个理学来说,完全异端化的佛道是他者,而对于朱熹来说,他者却呈现出多样性,至《论孟精义》的完成时是如此,此后也是如此。多样性的他者事实上构成了程朱理学话语构型中的重要区块,这不仅见诸程朱本人,而且已完全成为理学群体共有的普遍意识。何镐(1128—1175)的《杂学辨跋》从孟子辟杨墨讲起,将理学处理他者问题的历史原因、现实关系,以及为什么要专门针对“贵显名誉之士”而辩学,阐述得很清楚,并最终揭明了针对他者的辩学对于理学自身的意义。何镐曰:
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为心,大惧吾道之不明也,弗顾流俗之讥议,尝即其书破其疵缪,针其膏肓,使读者晓然知异端为非而圣言之为正也。学者苟能因其说而求至当之归,则诸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间,非特足以悟疑辨惑,亦由是可以造道焉。③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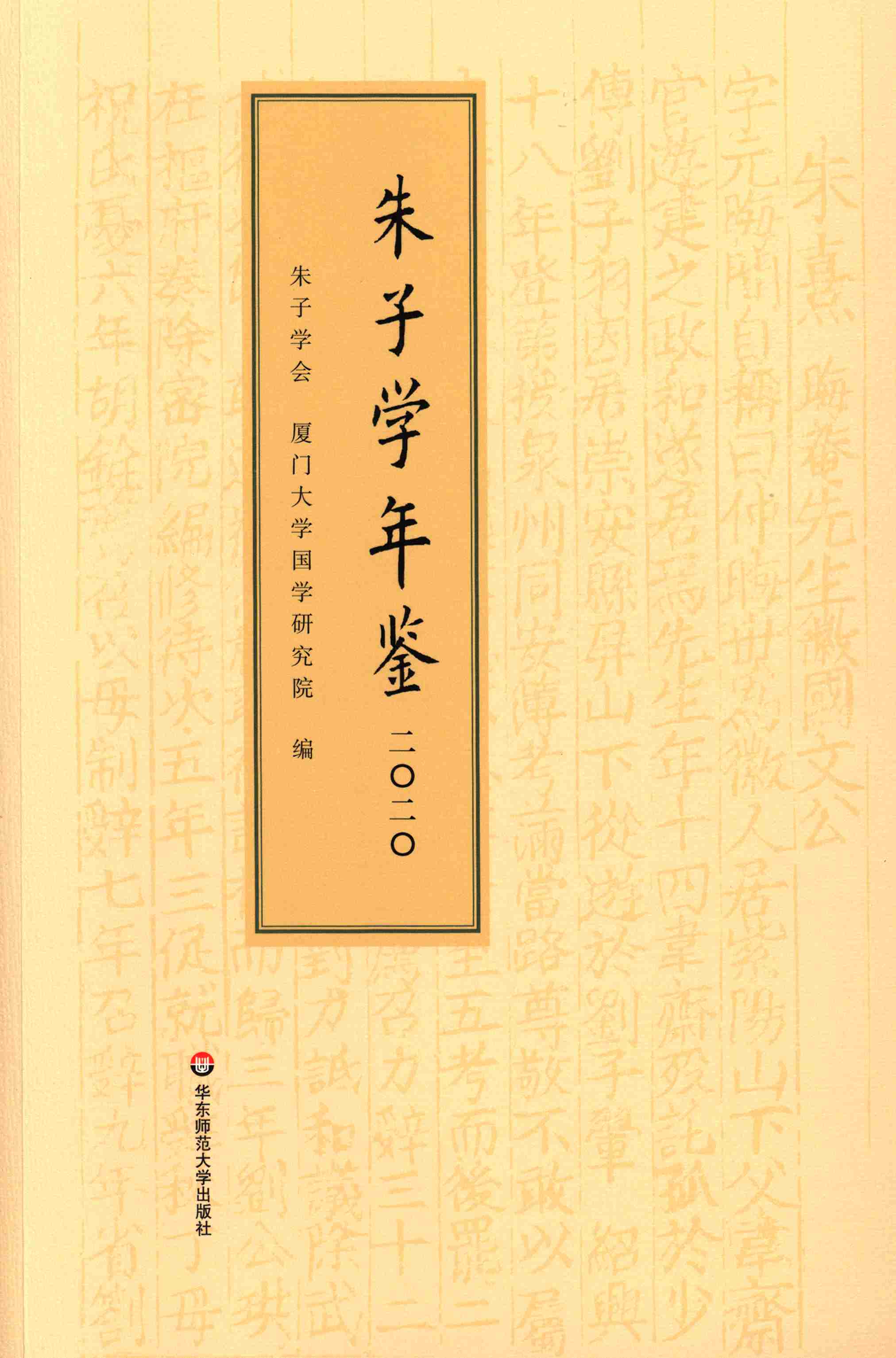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0》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以礼释仁的路径和意义》《2020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何俊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