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存养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0》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887 |
| 颗粒名称: | 五、存养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7 |
| 页码: | 089-095 |
| 摘要: | 本文讨论了仁义礼智四德和性体的关系,将其比喻为花蕾的绽放。仁义礼智是性体的展开,而情感与行为则是性体的发用。存养个人的心与性是程朱理学的核心议题。朱熹在《论孟精义自序》中强调操持存养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孔孟儒学的根本。文章还提到《论语》与《孟子》的区别,以及程朱理学至朱熹的构型彰显。 |
| 关键词: | 仁义礼智 性体 存养 |
内容
恻隐之心内具仁义礼智四德,仁统包之而为性体。由仁而义而礼而智,此为性体的展开,犹如花蕾之绽放,仁义礼智各为其花瓣,信在其中。至于人的情感与行为,则是性体的发用。只是性体的展开,须随心的感发,只有正心而发,性体才能充实而光辉;而作为个体生存着的人,无时无刻不感受着色、香、味、名、利、生、死的挑战,故在仁义揭明以后,“存其心,养其性”①的存养便是程朱理学接续着的核心议题。朱熹在《论孟精义自序》中也说得很清楚,存养就是孔孟儒学的根本,“《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指无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类多体验充扩之功”。所谓“操存涵养”与“体验充扩”,则是“仲尼无迹”与“孟子其迹著”的区别,无迹难见,迹著易踪,故《论语》实比《孟子》难读;程朱理学至朱熹而构型彰显,也是这个道理。
存心与养性是一事之两面,密切关联,但又不可错误理解两者的关系。
问:“仁与心何异?”伊川曰:“心是所生,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则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说仁者心之用则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心所用,只可谓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于心,然亦未可便谓之心之用。”②
心动,则仁起,就此而言,可说仁是心之用;但心与性都是独立的存在,其实是心体与性体。程颐着意区分“心是所生,仁是就事言”,意在强调心是内的,仁则须见之于人的行为,正如“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在内心,而复礼便见之于外。不过,这只是为了区别心与性,性根本是心内具之德,虽见之于外,却实无内外。程颢曰:
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③
要言之,程颐的分别或足以提醒,心体与性体在发用时,会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与感发上的隐显,存心的工夫便显得更为紧要,近乎可以理解成养性的前提。
存心,最形象的描述莫过于孟子讲的“不动心”。④心体原本是感应性的生物存在,本身没有取向,只是感于外物。朱熹曰:
人心本是湛然虚明,事物之来,随感而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事过便
当依前恁地虚,方得。⑤
因此,不动心似乎没有那么难,所以孟子又讲,“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但这其实又是理想的状态,在实际的境遇中,人心的发用总不免或多或少受某种意向性的影响,故朱熹又曰:
心是大底,意是小底。心要恁地做,却被意从后牵将去。且如心爱做个好事,又被一个意道不须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不孝底意思牵了。①
而且不动心的原因也有所不同,需要区别。程颐曰:
不动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动者,有以义制心而不动者。此义也,此不义也,义吾所当取,不义吾所当舍,此以义制心者也。义在我,由而行之,从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动之异。②
以义制心而不动是基于义,造道而不动是基于信,义是四德之一,信虽不属四德,却随四德而在,故可知存心与养性的关系,即心体的觉发虽似先于性体的自觉,但存心又依赖于养性。换言之,存心与养性其实是互为前提。
程颐上述的区分,当然在孟子那里也已指出。孟子分别举北宫黝与孟施舍为例,说明两种不同的不动心,并进而以为北宫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而“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但二程的分析显然更进一层,彰显了理学的特征。
北宫黝要之以必为,孟施舍推之以不惧,北宫黝或未能无惧,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约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北宫黝之勇,气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气而不知守约也。曾子之所谓勇乃守约,守约乃义也,与孟子之勇同。以上是程颢语。程颐又曰: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于气者,有勇于义者。君子勇于义,小人勇于气。③
孟子的举例虽已指出“守气”与“守约”,但终还是在经验的层面,而二程却追至“信道”与“明理”,守气与守约的核心区别在于背后是否有理据,而这个存于事的理据又是与性体之义贯通的。这样的阐明,一方面使不动气的现象之所以有了清楚的说明,另一方面据于这样的说明作出的两种不动气的高下之分,表明理学视理性的判识高于信仰的执守,只有基于明理守约的笃志力行才是理学需追求的,是真正的“勇于义”,否则终究是“勇于气”而已。
有了义与气这一区分,存心之要无疑就在仁义的把握,使仁义之性体充塞于心体,亦可谓“得于心”,或心得于正,存心与养性在这里已完全是合二为一的事情。在如何“得于心”的问题上,孟子提到了比自己更早达到“不动心”境界的告子的一个路径,即“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对此作了分辩,曰: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这段论述提出的“言”与“气”,直接引发了孟子后续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自我论定,加之这里提到的“志”,知言、养气、持志便成为存养的重要方法,从而引发了程门广泛的议论。《孟子精义》于此条作了大量引录,①这里姑且引《朱子语类》中的一段,因其清晰简明,足以呈现朱熹对理学精神的精微阐释。朱熹曰: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犹曰失也,谓言有所不知者则不可求之于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则不可求之于气。孟子谓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其不得于心者,固当求之心。然气不得所养,亦反能动其心,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虽可而未尽也。盖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务知言,亦不务养气,但只硬把定中间个心,要他不动。孟子则是能知言,又能养气,自然心不动。盖“知言”本也,“养气”助也。三者恰如行军,知言则其先锋,知虚识实者。心恰如主帅,气则卒徒也。孟子则前有引导,后有推动,自然无恐惧纷扰,而有以自胜。告子则前后无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与孟子不动心异也。②
据此而知,告子的不动心只是“硬把定中间个心,要他不动”,既不是基于对理的认识上,又得不到气的支持,这样的“不动心”如孟子所言,“未尝知义”,故决非孟子的不动心,自然也不是程朱理学所要的。
如果仔细比较,知言与养气在孟子那里近乎同等权重,但在程朱这里,知言要比养气更显得重要。程颐曰:
心通乎道,故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则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后见也。学者当以道为本,心不通于道,而较古人之是非,犹不持权衡而较轻重,竭其目力,劳其心智,虽使时中,亦古人所谓亿则屡中,君子不贵也。
孟子养气一言,诸君宜潜心玩索,须是实识得方可。勿忘勿助长,只是养气之法,如不识,怎生养?有物始言养,无物又养个什么?浩然之气,须见得一个物。③
朱熹在前引话后,也接着强调了这点:
“不得于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则此一章血脉贯通,而于知言养气,蔽淫邪遁之辞方为有下落也。至于集义工夫,乃在知言之后。不能知言,则亦不能集义。
强调知言先于并重于养气,可以充分反映程朱理学虽然把存养作为求仁的重要工夫,而且非常强调个体的努力,但并没有将这个工夫限于不可通约的个体经验,而是基于义理的认识上,从而使得存养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基础。概言之,明理知言,辨别是非,是存养的根本。这一确认也正是程朱理学之为理学的精神所在。
知言,在辨学中更能说明,故下节再述。这里讨论养气与持志。所谓志,便是心有所向,亦即孟子讲的“得于心”。朱熹曰:
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养心,不是持志外别有个养心。①
有得于心,心有所向,气随之而动,才进而得养浩然之气。程颐曰:
志,气之帅。若论浩然之气,则何者为志?志为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气。志至焉,气次焉,自有先后。
从气随志动,到浩然之气,当然是一个过程,既非自然而必然的进程,更非轻易能实现,这便需要养气。故程颐又曰:
持其志,无暴其气,内外交相养也。②
持志为养心,在内;养气见于形,在外。志虽然是气之帅,但程颐讲“内外交相养”,养气不完全是被动的,它能反过来影响到养心,因此从气随志动到浩然之气的过程,“无暴其气”实为养气的一个技术关键。朱熹曰:
志最紧要,气亦不可缓,故曰“志至焉,气次焉”,“持其志,毋暴其气”,是两边做工夫。③
当然,除了反作用以外,养气的意义还在于两点:其一,由于气形于身,见于外,只有养气才足以最终使个体的生命存在由精神的自善成为实践的主体。《孟子精义》中录程颐答问:
“或曰养心,或曰养气,何也?”曰:“养心则勿害而已,养气则志有所帅也。”④
其二,个体的生命存在原本就是一团血气,只有养气才足以使之获得提炼,成为浩然之气。《朱子语类》载:
问“血气”之“气”与“浩然之气”不同。曰:“气便只是这个气,所谓‘体之充也’便是。
然而,浩然之气与血气虽同为气,但体状与性质却有大不同。程颢曰:
浩然之气,天地之正气,大则无所不在,刚则无所屈,以直顺理而养,则充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气皆主于义而无不在道,一置私意,则馁矣。
是集义所生,事事有理而在义也,非自外袭而取之也。①
这不仅明确描述了浩然之气的体状与性质,而且也阐明了养浩然之气的根本方法,即“配义与道”。程颐曰:
配义与道,谓以义理养成此气合义与道。方其未养,则气自是气,义自是义,及其养成浩然之气,气与义合矣。②
这个“配义与道”,最为关键的“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③,即是由内心之义德的自觉,从而明白循理而行,不是为了迎合外在的种种标准而去做所谓合乎义的事情。
最后再回头略说持志,亦即养心。程颢曰: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④
程颐更进一步解释了“放”字,并以轻重而申说之:
放心谓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
心至重,鸡犬至轻,鸡犬放则知求之,心放则不知求,岂爱其至轻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乐其所不当乐,不乐其所当乐,慕其所
不当慕,不慕其所当慕,皆由不思轻重之分也。⑤
个体的生命为血气所充,心感于外,易流而不返,故持志养心之要在“收放心”。只是,心之所以放流而不返,自然是外物不断在刺激与满足人的欲望,故孟子有“养心莫善于寡欲”说。⑥然如何能够做到呢?程颐曰:
养心莫善于寡欲,欲皆自外来,公,欲亦寡矣。
这是要以公心节私欲,只是人的许多欲望最初尚不到公与私的地步。故朱熹曰:
且如秀才要读书,要读这一件,又要读那一件,又要学写字,又要学作诗,这心一齐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处用其心,也不要人学写字,也不要人学作文章。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个心,如何分做许多去?若只管去闲处用了心,到得合用处,于这本来底都不得力。⑦
由此便知,“寡欲”不可望文生义地等同为节欲,甚而禁欲,它其实还是持志的方法问题。志为心之所向,寡欲是为了志一,这是存心的关键。因此,程颐更主张正面地树立起目标,而不是从反面来寡欲,因为他有切身的体会,心之所向终究是要存于心之所乐的。谢良佐曰:
尝问伊川先生:“养心莫善于寡欲,此一句如何?”先生曰:“此一句浅近,不如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最亲切有滋味。”①
存心与养性是一事之两面,密切关联,但又不可错误理解两者的关系。
问:“仁与心何异?”伊川曰:“心是所生,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则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说仁者心之用则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心所用,只可谓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于心,然亦未可便谓之心之用。”②
心动,则仁起,就此而言,可说仁是心之用;但心与性都是独立的存在,其实是心体与性体。程颐着意区分“心是所生,仁是就事言”,意在强调心是内的,仁则须见之于人的行为,正如“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在内心,而复礼便见之于外。不过,这只是为了区别心与性,性根本是心内具之德,虽见之于外,却实无内外。程颢曰:
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③
要言之,程颐的分别或足以提醒,心体与性体在发用时,会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与感发上的隐显,存心的工夫便显得更为紧要,近乎可以理解成养性的前提。
存心,最形象的描述莫过于孟子讲的“不动心”。④心体原本是感应性的生物存在,本身没有取向,只是感于外物。朱熹曰:
人心本是湛然虚明,事物之来,随感而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事过便
当依前恁地虚,方得。⑤
因此,不动心似乎没有那么难,所以孟子又讲,“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但这其实又是理想的状态,在实际的境遇中,人心的发用总不免或多或少受某种意向性的影响,故朱熹又曰:
心是大底,意是小底。心要恁地做,却被意从后牵将去。且如心爱做个好事,又被一个意道不须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不孝底意思牵了。①
而且不动心的原因也有所不同,需要区别。程颐曰:
不动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动者,有以义制心而不动者。此义也,此不义也,义吾所当取,不义吾所当舍,此以义制心者也。义在我,由而行之,从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动之异。②
以义制心而不动是基于义,造道而不动是基于信,义是四德之一,信虽不属四德,却随四德而在,故可知存心与养性的关系,即心体的觉发虽似先于性体的自觉,但存心又依赖于养性。换言之,存心与养性其实是互为前提。
程颐上述的区分,当然在孟子那里也已指出。孟子分别举北宫黝与孟施舍为例,说明两种不同的不动心,并进而以为北宫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而“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但二程的分析显然更进一层,彰显了理学的特征。
北宫黝要之以必为,孟施舍推之以不惧,北宫黝或未能无惧,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约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北宫黝之勇,气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气而不知守约也。曾子之所谓勇乃守约,守约乃义也,与孟子之勇同。以上是程颢语。程颐又曰: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于气者,有勇于义者。君子勇于义,小人勇于气。③
孟子的举例虽已指出“守气”与“守约”,但终还是在经验的层面,而二程却追至“信道”与“明理”,守气与守约的核心区别在于背后是否有理据,而这个存于事的理据又是与性体之义贯通的。这样的阐明,一方面使不动气的现象之所以有了清楚的说明,另一方面据于这样的说明作出的两种不动气的高下之分,表明理学视理性的判识高于信仰的执守,只有基于明理守约的笃志力行才是理学需追求的,是真正的“勇于义”,否则终究是“勇于气”而已。
有了义与气这一区分,存心之要无疑就在仁义的把握,使仁义之性体充塞于心体,亦可谓“得于心”,或心得于正,存心与养性在这里已完全是合二为一的事情。在如何“得于心”的问题上,孟子提到了比自己更早达到“不动心”境界的告子的一个路径,即“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对此作了分辩,曰: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这段论述提出的“言”与“气”,直接引发了孟子后续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自我论定,加之这里提到的“志”,知言、养气、持志便成为存养的重要方法,从而引发了程门广泛的议论。《孟子精义》于此条作了大量引录,①这里姑且引《朱子语类》中的一段,因其清晰简明,足以呈现朱熹对理学精神的精微阐释。朱熹曰: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犹曰失也,谓言有所不知者则不可求之于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则不可求之于气。孟子谓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其不得于心者,固当求之心。然气不得所养,亦反能动其心,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虽可而未尽也。盖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务知言,亦不务养气,但只硬把定中间个心,要他不动。孟子则是能知言,又能养气,自然心不动。盖“知言”本也,“养气”助也。三者恰如行军,知言则其先锋,知虚识实者。心恰如主帅,气则卒徒也。孟子则前有引导,后有推动,自然无恐惧纷扰,而有以自胜。告子则前后无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与孟子不动心异也。②
据此而知,告子的不动心只是“硬把定中间个心,要他不动”,既不是基于对理的认识上,又得不到气的支持,这样的“不动心”如孟子所言,“未尝知义”,故决非孟子的不动心,自然也不是程朱理学所要的。
如果仔细比较,知言与养气在孟子那里近乎同等权重,但在程朱这里,知言要比养气更显得重要。程颐曰:
心通乎道,故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则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后见也。学者当以道为本,心不通于道,而较古人之是非,犹不持权衡而较轻重,竭其目力,劳其心智,虽使时中,亦古人所谓亿则屡中,君子不贵也。
孟子养气一言,诸君宜潜心玩索,须是实识得方可。勿忘勿助长,只是养气之法,如不识,怎生养?有物始言养,无物又养个什么?浩然之气,须见得一个物。③
朱熹在前引话后,也接着强调了这点:
“不得于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则此一章血脉贯通,而于知言养气,蔽淫邪遁之辞方为有下落也。至于集义工夫,乃在知言之后。不能知言,则亦不能集义。
强调知言先于并重于养气,可以充分反映程朱理学虽然把存养作为求仁的重要工夫,而且非常强调个体的努力,但并没有将这个工夫限于不可通约的个体经验,而是基于义理的认识上,从而使得存养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基础。概言之,明理知言,辨别是非,是存养的根本。这一确认也正是程朱理学之为理学的精神所在。
知言,在辨学中更能说明,故下节再述。这里讨论养气与持志。所谓志,便是心有所向,亦即孟子讲的“得于心”。朱熹曰:
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养心,不是持志外别有个养心。①
有得于心,心有所向,气随之而动,才进而得养浩然之气。程颐曰:
志,气之帅。若论浩然之气,则何者为志?志为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气。志至焉,气次焉,自有先后。
从气随志动,到浩然之气,当然是一个过程,既非自然而必然的进程,更非轻易能实现,这便需要养气。故程颐又曰:
持其志,无暴其气,内外交相养也。②
持志为养心,在内;养气见于形,在外。志虽然是气之帅,但程颐讲“内外交相养”,养气不完全是被动的,它能反过来影响到养心,因此从气随志动到浩然之气的过程,“无暴其气”实为养气的一个技术关键。朱熹曰:
志最紧要,气亦不可缓,故曰“志至焉,气次焉”,“持其志,毋暴其气”,是两边做工夫。③
当然,除了反作用以外,养气的意义还在于两点:其一,由于气形于身,见于外,只有养气才足以最终使个体的生命存在由精神的自善成为实践的主体。《孟子精义》中录程颐答问:
“或曰养心,或曰养气,何也?”曰:“养心则勿害而已,养气则志有所帅也。”④
其二,个体的生命存在原本就是一团血气,只有养气才足以使之获得提炼,成为浩然之气。《朱子语类》载:
问“血气”之“气”与“浩然之气”不同。曰:“气便只是这个气,所谓‘体之充也’便是。
然而,浩然之气与血气虽同为气,但体状与性质却有大不同。程颢曰:
浩然之气,天地之正气,大则无所不在,刚则无所屈,以直顺理而养,则充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气皆主于义而无不在道,一置私意,则馁矣。
是集义所生,事事有理而在义也,非自外袭而取之也。①
这不仅明确描述了浩然之气的体状与性质,而且也阐明了养浩然之气的根本方法,即“配义与道”。程颐曰:
配义与道,谓以义理养成此气合义与道。方其未养,则气自是气,义自是义,及其养成浩然之气,气与义合矣。②
这个“配义与道”,最为关键的“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③,即是由内心之义德的自觉,从而明白循理而行,不是为了迎合外在的种种标准而去做所谓合乎义的事情。
最后再回头略说持志,亦即养心。程颢曰: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④
程颐更进一步解释了“放”字,并以轻重而申说之:
放心谓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
心至重,鸡犬至轻,鸡犬放则知求之,心放则不知求,岂爱其至轻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乐其所不当乐,不乐其所当乐,慕其所
不当慕,不慕其所当慕,皆由不思轻重之分也。⑤
个体的生命为血气所充,心感于外,易流而不返,故持志养心之要在“收放心”。只是,心之所以放流而不返,自然是外物不断在刺激与满足人的欲望,故孟子有“养心莫善于寡欲”说。⑥然如何能够做到呢?程颐曰:
养心莫善于寡欲,欲皆自外来,公,欲亦寡矣。
这是要以公心节私欲,只是人的许多欲望最初尚不到公与私的地步。故朱熹曰:
且如秀才要读书,要读这一件,又要读那一件,又要学写字,又要学作诗,这心一齐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处用其心,也不要人学写字,也不要人学作文章。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个心,如何分做许多去?若只管去闲处用了心,到得合用处,于这本来底都不得力。⑦
由此便知,“寡欲”不可望文生义地等同为节欲,甚而禁欲,它其实还是持志的方法问题。志为心之所向,寡欲是为了志一,这是存心的关键。因此,程颐更主张正面地树立起目标,而不是从反面来寡欲,因为他有切身的体会,心之所向终究是要存于心之所乐的。谢良佐曰:
尝问伊川先生:“养心莫善于寡欲,此一句如何?”先生曰:“此一句浅近,不如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最亲切有滋味。”①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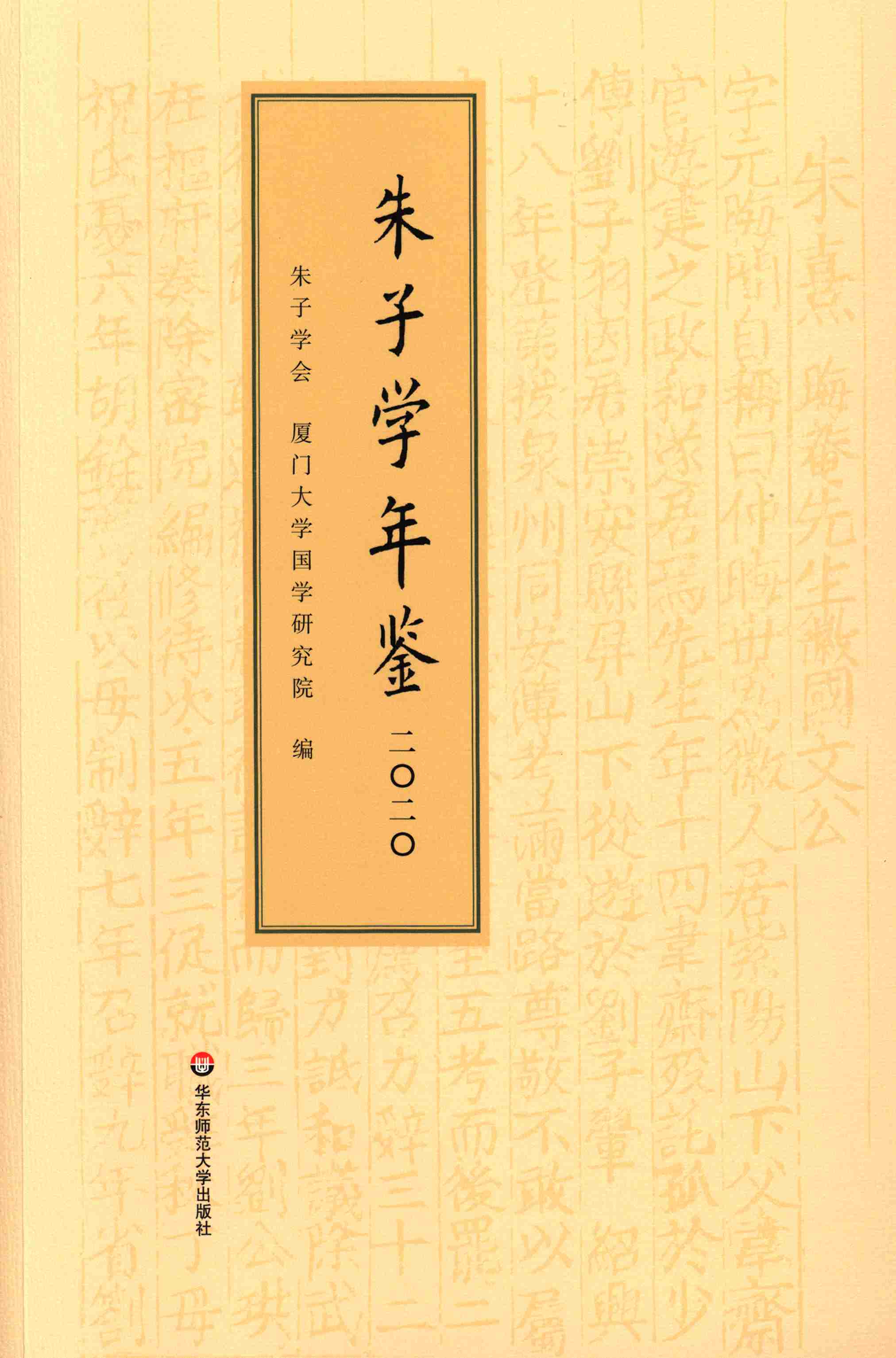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0》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以礼释仁的路径和意义》《2020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何俊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