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仁义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0》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886 |
| 颗粒名称: | 四、仁义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 |
| 页码: | 084-089 |
| 摘要: | 本文讨论了从二程到朱熹的仁说,并提到陈来在这方面的研究。陈来采用了二程、谢良佐、杨时、吕大临、游酢以及胡宏等人的说法,将他们与湖湘学进行分析,从而确立朱熹为核心的程朱理学。文中还提到朱熹的仁说主要体现在《洙泗言仁录》、《克斋记》和《仁说》这三个文本中,并指出这些文本的思想基础都在《论孟精义》中。《论孟精义》在程朱理学的型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展现了程朱理学对于人的确认。 |
| 关键词: | 二程 朱熹 仁说 |
内容
上节述及,二程“本乎人情,出乎礼义”的理,存在着抽空个体生存主体性的危险,而理学致力于排除这一危险的核心工作,就是对人的认定,亦即理学的仁说。关于二程到朱熹的仁说,前贤多有论述,近则以陈来最为重要。①其中,据分析朱熹以前的,陈来采二程、谢良佐、杨时、吕大临与游酢,以及胡宏诸家说,以说明朱熹据二程的立场,统合与整理程门诸子,尤其是谢、杨,以及湖湘学,从而确立朱熹为核心的程朱理学;而分析朱熹仁说的文本主要是三个,即1171年因张栻完成《洙泗言仁录》后的彼此讨论书信,次年(即《论孟精义》成书这年)朱熹为出自自己出生成长地尤溪的友人石子重写的《克斋记》,以及同年稍后写的更重要的《仁说》,以观朱熹在与湖湘学的思想论辩中走向确立。从三个文本与《论孟精义》的编撰时间,便可断言,三个文本的思想基础都在《论孟精义》,而程门统合的工作更在其中,故就程朱理学的型塑而言,这里以《论孟精义》再作补充,或更足以彰显,同时亦可进一步看到程朱理学对人的确认。
朱熹于《仁说》开篇曰: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②
这段话从本体论的高度阐述了人心及其性质与特征,可以认为是朱熹关于仁说的总论。首先,人之为心的自然基础在天地。其次,天地之心的根本是生物,具体为四德,统之于元;人心之德亦有四,统之于仁。这里,仁作了狭义(四德之一)与广义(统包四德)之分。最后,人心之四德显现为具体的感情,即爱恭宜别。但在这段概述中,“天地以生物为心”很明确,而人“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故也应该是“生物”,而不是仁,正如天地之心不是元一样。末尾一句“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则似乎明示天地之生物心,在人即是恻隐心。
论恻隐之心的经典文本是《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且摘录数则朱熹所蒐辑的程门议论以为比较。
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虽桀、跖不能无是以生,但戕贼之以灭天耳。始则不知爱物,俄而至于忍,安之以至于杀,充之以至于好杀,岂人理也哉!”又曰:“恻,恻然。隐,如物之隐应也。此仁之端绪。”
明道先生见谢显道记闻甚博,谓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显道不觉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恻隐之心。”
明道曰:“惟四者有端,而信无端,只有不信,更无信。如东西南北,已有定体,更不可言信。”
程颐的论说首讲心为生道,此心具是形以生,又以恻隐为仁之端绪。程颢与谢良佐的对话,则以切身体会以喻恻隐之心正是身心对外在刺激的一种反映;后一段是解释有四端而不可言信。二程的论说,除了元包天地生物心之四德、仁包人心四德没有明确论及外,其余皆为上引朱熹《仁说》所概括。
游曰:“恻者心之感于物也,隐者心之痛于中也。物之体伤于彼,而吾之心感应于此,仁之体显矣。”
游酢的议论更进一步明确,恻隐是人对外物的感觉所引起的痛觉,这种痛觉自然不完全是生理,而是包括了痛惜等心理在内的反应;前引程颐所述的不知爱物、忍、安之、杀、好杀,便是指人的这种感受性的丧失及其延伸的不同层次的结果。朱熹的“恻隐之心无所不贯”,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程、游师徒议论的综合。
谢曰:“格物穷理,须是识得天理始得。所谓天理者,自然底道理,无毫发杜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方乍见时,其心怵惕,所谓天理也。要誉于乡党朋友,内交于孺子父母兄弟,恶其声而然,即人欲也。天理与人欲相对,有一分人欲,即灭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胜得一分人欲,人欲才肆,天理灭矣。”①
这里明确指出,理学的天理就是人的恻隐心的自然展开,而恻隐心的丧失,即程颐指出的反向展开也是存在于人的自然性中的,此即为人欲。如此,程朱理学核心理论的型塑过程已看得极为清楚。与此同时,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标示,其本义也得其正解。
基于上述的仁说总论,有两个具体的分论,它们既是总论的延伸问题,也可以认为是总论的支撑问题。第一个分论就是如何知仁。依总论,人心就是恻隐心,发用是爱恭宜别之情,在两者之间是仁义礼智;仁包四德,故关键是仁,而仁对应的是爱;仁抽象,爱具体,因此仁与爱便产生互相界定的问题。程门论仁,至朱熹时,已产生许多分歧,在《答张敬夫》信中,朱熹曰:
大抵二先生之前,学者全不知有仁字,凡圣贤说仁处,不过只作爱字看了。自二先生以来,学者始知理会仁字,不敢只作爱说。②
程颢的原话是: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谓之仁。
恻隐则属爱,乃情也,非性也。③
仁是性,爱是情,恻隐也是情。由此,似又可推知,情与心又是相关联的概念,心为体,情为心之发用。仁作为性,实质上是对心之发用的一种价值规定,即善。故在二程看来,孟子言人性善是极为重要的。
或问:“人性本明,因何得有蔽?”伊川先生曰:“此须索理会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虽荀、扬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①只是性及其善的规定被标举出来后,仁之性反过来与发为恻隐、爱之情的心形成对应,仁性为体,而心为发用。谢良佐曰:
性,本体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见于作用者,心也。②
既如此,作为理论的探究,自然要专心于讨论本体的仁性了。然而其结果,则如朱熹指出,撇开情来论性,弊病丛生。朱熹曰:
然其流复不免有弊者,盖专务说仁,而于操存涵养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无复优柔厌饫之味、克己复礼之实,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离了爱字悬空揣摸,既无真实见处,故其为说,恍惚惊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爱字看却之为愈也。从大的方面讲,弊病有两类,一是专务说仁,务虚不务实,全不落在个体生
命的践行上;二是务虚流于悬空揣摸,议论恍惚惊怪。因此,朱熹强调,与其如此,不如回过头来,依旧从情之发用上来体会仁之性。朱熹曰:
若且欲晓得其仁之名义,则又不若且将爱字推求;若见得仁之所以爱,而爱之所以不能尽仁,则仁之名义意思了然在目矣。可以说,朱熹“将爱字推求”仁,正是坚持了二程门下道南一脉的路径。
或问:“何以知仁?”杨(时)氏曰: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体究,久之自见。且孺子将入于井,而人见之者必有恻隐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为之疾痛何耶?曰: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体究此理,知其所从来,则仁之道不远矣。
杨时不仅只是这样就着经典解释来阐述,而且在现实中也能据事作出这样的阐述。在引了上面这段问答后,朱熹接着更引述了下面这则杨时的故事:
薛宗博请诸职事会茶,曰:“礼岂出于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礼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礼起圣人之伪。’真个是。”因问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谓?”薛曰:“前后例如此,近日以事多,与此等稍疏阔,心中打不过,须一请之。”曰:“只为前后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过,岂自外来?如云辞逊之心礼之端,亦只心有所不安,故当辞逊,只此是礼,非伪为也。”③
此外,朱熹的以爱推仁是在答张栻书信中提出,盖回应张栻主张谢良佐的以觉言仁,张栻后来又针对朱熹的以爱推仁,主张程颐的以公论仁。①其实,谢良佐的以觉言仁虽直接来自程颢,但强调感应也是程颐的根本思想,而且他赋予感应以亨通的价值判定。程颐释《咸》卦:
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义,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复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万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则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则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则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妇、亲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则和顺而亨通。事物皆然,故感有亨之理也。②
朱熹当然很知道程颐的观点,而且他还引过程颐讲的“天地间只是个感应”。③至于以公论仁,同样是二程共同的观点,程颢曰:
仁者,公也,人此者也。④而程颐则曰:
仁道难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为仁。⑤
很明确,公实与觉、爱一样,只是理解仁,或践行仁的路径,本身不是仁。相比较而言,朱熹的以爱推仁既得二程本意,也最能说明仁。⑥
第二个分论是如何求仁。前引朱熹《答张敬夫》指出程门后学流为悬空虚说,无复克己复礼之实,故在朱熹看来,知仁固然重要,但最终须落在求仁上。在为石子重写的《克斋记》中,朱熹曰:
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己。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⑦程颐曰:
礼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则义也。⑧
故论仁,必须接着义讲。孟子的一大贡献,在二程看来,就是将仁义合在一起讲。程颢曰: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①
由于义与克己复礼相关联,形之以外在的践行,因此在认识上往往容易忘记义是心的四德之一,内属于仁之性体。程颢曰:
仲尼言仁,未尝兼义,独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孟子言仁必以义配,盖仁者体也,义者用也,知义之为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语道矣。世之所论于义者多外之,不然,则混而无别,非知仁义之说者也。②程颐又将义与敬、理、养气结合着说:
或问:“必有事焉当用敬否?”曰:“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当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又问:“义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义在心内,苟不主义,浩然之气从何而生?理只是发而见于外者。”③
与敬的关系,义是敬的主脑,离开义的敬其实是无所事事。与理的关系,义是存于人之心内的原则,理只是这种原则形之于事。与养气的关系,浩然之气因义而生。故诚如孟子所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④只是克己复礼与内心之义的把握都很难,常常于不自觉中破坏与沦陷,初似无害,久则成患。《论语·八佾》载:
三家者以《雍》辟。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伊川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当为,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袭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彻,故仲尼于此著之。⑤
明道曰:介甫说鲁用天子礼乐,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礼乐”。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岂有过分之事,凡有所为,皆是臣职所当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亲最孝,观其言如此,其事亲之际想亦洋洋自得以为孝有余也。在程朱看来,这个“义”字,“惟是孟子知之”。⑥
朱熹于《仁说》开篇曰: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②
这段话从本体论的高度阐述了人心及其性质与特征,可以认为是朱熹关于仁说的总论。首先,人之为心的自然基础在天地。其次,天地之心的根本是生物,具体为四德,统之于元;人心之德亦有四,统之于仁。这里,仁作了狭义(四德之一)与广义(统包四德)之分。最后,人心之四德显现为具体的感情,即爱恭宜别。但在这段概述中,“天地以生物为心”很明确,而人“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故也应该是“生物”,而不是仁,正如天地之心不是元一样。末尾一句“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则似乎明示天地之生物心,在人即是恻隐心。
论恻隐之心的经典文本是《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且摘录数则朱熹所蒐辑的程门议论以为比较。
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虽桀、跖不能无是以生,但戕贼之以灭天耳。始则不知爱物,俄而至于忍,安之以至于杀,充之以至于好杀,岂人理也哉!”又曰:“恻,恻然。隐,如物之隐应也。此仁之端绪。”
明道先生见谢显道记闻甚博,谓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显道不觉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恻隐之心。”
明道曰:“惟四者有端,而信无端,只有不信,更无信。如东西南北,已有定体,更不可言信。”
程颐的论说首讲心为生道,此心具是形以生,又以恻隐为仁之端绪。程颢与谢良佐的对话,则以切身体会以喻恻隐之心正是身心对外在刺激的一种反映;后一段是解释有四端而不可言信。二程的论说,除了元包天地生物心之四德、仁包人心四德没有明确论及外,其余皆为上引朱熹《仁说》所概括。
游曰:“恻者心之感于物也,隐者心之痛于中也。物之体伤于彼,而吾之心感应于此,仁之体显矣。”
游酢的议论更进一步明确,恻隐是人对外物的感觉所引起的痛觉,这种痛觉自然不完全是生理,而是包括了痛惜等心理在内的反应;前引程颐所述的不知爱物、忍、安之、杀、好杀,便是指人的这种感受性的丧失及其延伸的不同层次的结果。朱熹的“恻隐之心无所不贯”,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程、游师徒议论的综合。
谢曰:“格物穷理,须是识得天理始得。所谓天理者,自然底道理,无毫发杜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方乍见时,其心怵惕,所谓天理也。要誉于乡党朋友,内交于孺子父母兄弟,恶其声而然,即人欲也。天理与人欲相对,有一分人欲,即灭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胜得一分人欲,人欲才肆,天理灭矣。”①
这里明确指出,理学的天理就是人的恻隐心的自然展开,而恻隐心的丧失,即程颐指出的反向展开也是存在于人的自然性中的,此即为人欲。如此,程朱理学核心理论的型塑过程已看得极为清楚。与此同时,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标示,其本义也得其正解。
基于上述的仁说总论,有两个具体的分论,它们既是总论的延伸问题,也可以认为是总论的支撑问题。第一个分论就是如何知仁。依总论,人心就是恻隐心,发用是爱恭宜别之情,在两者之间是仁义礼智;仁包四德,故关键是仁,而仁对应的是爱;仁抽象,爱具体,因此仁与爱便产生互相界定的问题。程门论仁,至朱熹时,已产生许多分歧,在《答张敬夫》信中,朱熹曰:
大抵二先生之前,学者全不知有仁字,凡圣贤说仁处,不过只作爱字看了。自二先生以来,学者始知理会仁字,不敢只作爱说。②
程颢的原话是: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谓之仁。
恻隐则属爱,乃情也,非性也。③
仁是性,爱是情,恻隐也是情。由此,似又可推知,情与心又是相关联的概念,心为体,情为心之发用。仁作为性,实质上是对心之发用的一种价值规定,即善。故在二程看来,孟子言人性善是极为重要的。
或问:“人性本明,因何得有蔽?”伊川先生曰:“此须索理会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虽荀、扬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①只是性及其善的规定被标举出来后,仁之性反过来与发为恻隐、爱之情的心形成对应,仁性为体,而心为发用。谢良佐曰:
性,本体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见于作用者,心也。②
既如此,作为理论的探究,自然要专心于讨论本体的仁性了。然而其结果,则如朱熹指出,撇开情来论性,弊病丛生。朱熹曰:
然其流复不免有弊者,盖专务说仁,而于操存涵养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无复优柔厌饫之味、克己复礼之实,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离了爱字悬空揣摸,既无真实见处,故其为说,恍惚惊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爱字看却之为愈也。从大的方面讲,弊病有两类,一是专务说仁,务虚不务实,全不落在个体生
命的践行上;二是务虚流于悬空揣摸,议论恍惚惊怪。因此,朱熹强调,与其如此,不如回过头来,依旧从情之发用上来体会仁之性。朱熹曰:
若且欲晓得其仁之名义,则又不若且将爱字推求;若见得仁之所以爱,而爱之所以不能尽仁,则仁之名义意思了然在目矣。可以说,朱熹“将爱字推求”仁,正是坚持了二程门下道南一脉的路径。
或问:“何以知仁?”杨(时)氏曰: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体究,久之自见。且孺子将入于井,而人见之者必有恻隐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为之疾痛何耶?曰: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体究此理,知其所从来,则仁之道不远矣。
杨时不仅只是这样就着经典解释来阐述,而且在现实中也能据事作出这样的阐述。在引了上面这段问答后,朱熹接着更引述了下面这则杨时的故事:
薛宗博请诸职事会茶,曰:“礼岂出于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礼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礼起圣人之伪。’真个是。”因问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谓?”薛曰:“前后例如此,近日以事多,与此等稍疏阔,心中打不过,须一请之。”曰:“只为前后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过,岂自外来?如云辞逊之心礼之端,亦只心有所不安,故当辞逊,只此是礼,非伪为也。”③
此外,朱熹的以爱推仁是在答张栻书信中提出,盖回应张栻主张谢良佐的以觉言仁,张栻后来又针对朱熹的以爱推仁,主张程颐的以公论仁。①其实,谢良佐的以觉言仁虽直接来自程颢,但强调感应也是程颐的根本思想,而且他赋予感应以亨通的价值判定。程颐释《咸》卦:
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义,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复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万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则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则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则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妇、亲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则和顺而亨通。事物皆然,故感有亨之理也。②
朱熹当然很知道程颐的观点,而且他还引过程颐讲的“天地间只是个感应”。③至于以公论仁,同样是二程共同的观点,程颢曰:
仁者,公也,人此者也。④而程颐则曰:
仁道难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为仁。⑤
很明确,公实与觉、爱一样,只是理解仁,或践行仁的路径,本身不是仁。相比较而言,朱熹的以爱推仁既得二程本意,也最能说明仁。⑥
第二个分论是如何求仁。前引朱熹《答张敬夫》指出程门后学流为悬空虚说,无复克己复礼之实,故在朱熹看来,知仁固然重要,但最终须落在求仁上。在为石子重写的《克斋记》中,朱熹曰:
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己。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⑦程颐曰:
礼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则义也。⑧
故论仁,必须接着义讲。孟子的一大贡献,在二程看来,就是将仁义合在一起讲。程颢曰: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①
由于义与克己复礼相关联,形之以外在的践行,因此在认识上往往容易忘记义是心的四德之一,内属于仁之性体。程颢曰:
仲尼言仁,未尝兼义,独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孟子言仁必以义配,盖仁者体也,义者用也,知义之为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语道矣。世之所论于义者多外之,不然,则混而无别,非知仁义之说者也。②程颐又将义与敬、理、养气结合着说:
或问:“必有事焉当用敬否?”曰:“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当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又问:“义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义在心内,苟不主义,浩然之气从何而生?理只是发而见于外者。”③
与敬的关系,义是敬的主脑,离开义的敬其实是无所事事。与理的关系,义是存于人之心内的原则,理只是这种原则形之于事。与养气的关系,浩然之气因义而生。故诚如孟子所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④只是克己复礼与内心之义的把握都很难,常常于不自觉中破坏与沦陷,初似无害,久则成患。《论语·八佾》载:
三家者以《雍》辟。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伊川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当为,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袭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彻,故仲尼于此著之。⑤
明道曰:介甫说鲁用天子礼乐,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礼乐”。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岂有过分之事,凡有所为,皆是臣职所当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亲最孝,观其言如此,其事亲之际想亦洋洋自得以为孝有余也。在程朱看来,这个“义”字,“惟是孟子知之”。⑥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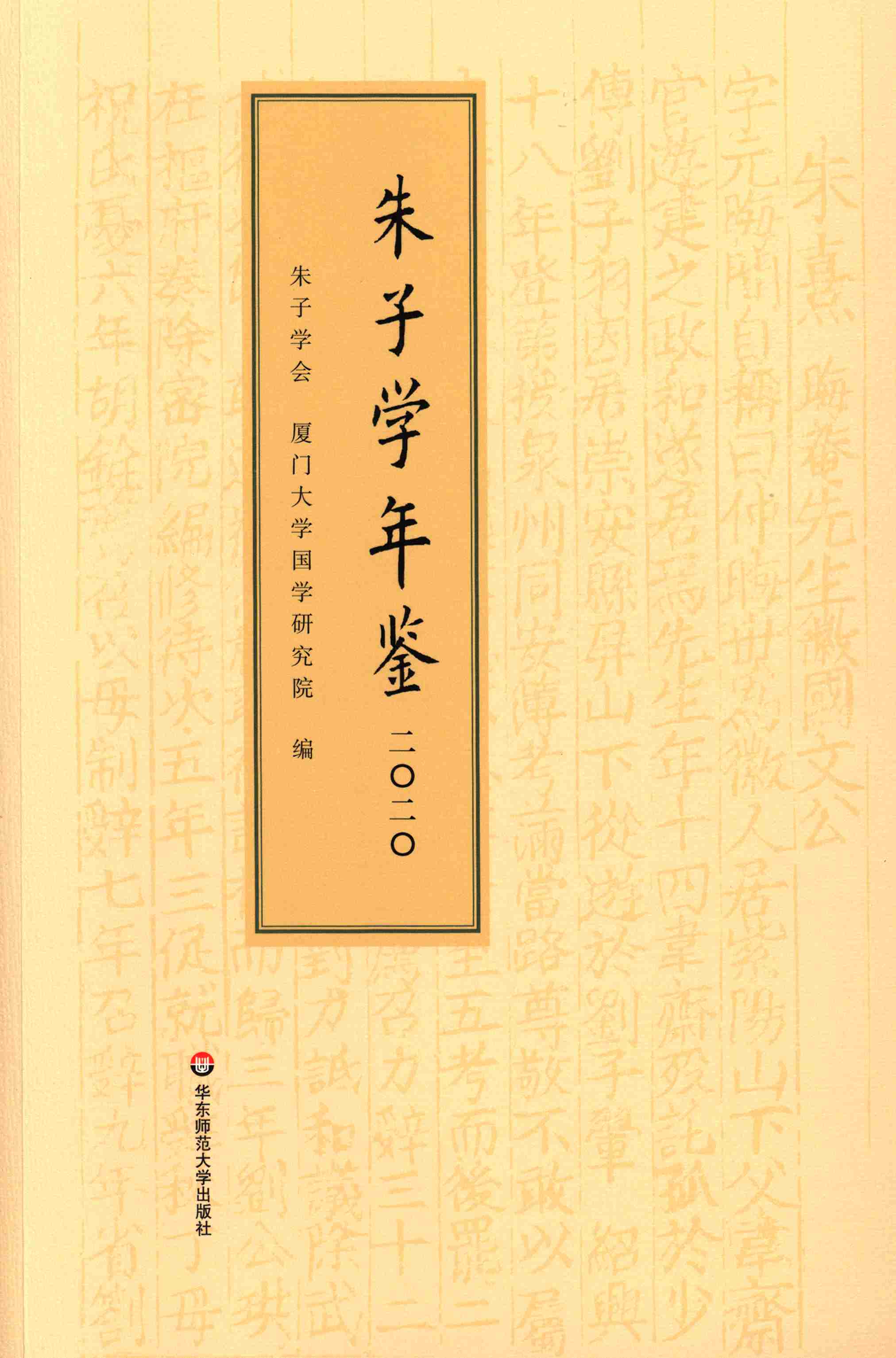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0》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以礼释仁的路径和意义》《2020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