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身体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0》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885 |
| 颗粒名称: | 三、身体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 |
| 页码: | 079-084 |
| 摘要: | 本文讨论了《论孟精义》中人的形象。虽然这是一个言语编织成的文本,但其中充满了真实的人的形象。整个文本将活生生的人的形象置于首位,并强调通过言语来认识人。这些人的形象可以概括为圣贤或渴望成为圣贤的人。 |
| 关键词: | 《论孟精义》 人的形象 圣贤 |
内容
《论孟精义》虽然是一个言语编织成(woven)的文本,但却充满着人的形象。这不仅是因为全部言语客观上都具有着真实的言语主体,更是因为整个文本自始就把鲜活的人的形象放在了首位,即《论孟精义纲领》首论“孔孟气象”,进而强调要由知言而见人,程颢曰:
读其言便可以知其人,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并且最终落在自己的身上,即程颐所谓“切己”:
凡看《论》《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语言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此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②
然则,《论孟精义》中所呈现的人,又究竟是怎样的人呢?笼统地讲,他们自然是圣贤,或是希望成圣成贤的人。但圣贤又是怎样的人呢?请先看程颢几段描述:
1.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
2.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3.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辩。
4.孔子为宰则为宰,为陪臣则为陪臣,皆能发明大道。孟子必得宾师之位,然后能明其道,犹之有许大形象,然后为泰山,有许多水,然后为海,以此未及孔子。
5.子厚(张载)谨严,才谨严便有迫切气象,无宽舒之气。孟子却宽舒,只是中间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之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
6.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①
上引六条,1、2比诸自然,3、4、5似见性格,6可谓涵养,虽然难以进一步概括,但有一点却是断然可言的,他们都是明显具有感性特征的人。
然而众所周知,程朱理学之为“理学”,正在于“理”的高标,以及理性精神的培植与主导,前节见之于语言分析所揭明的论辩精神亦是表证之一,而“穷天理灭人欲”的宣称更给人以理学完全荡去感性的印象,因此《论孟精义》所呈现的充满感性特征的圣贤形象便不得不“深求玩味”了。
为了便于分析的展开,这里同样不妨借镜于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在由近代向现代,以及后现代的演化中,主体问题经历了从普遍理性主体观向个体生存主体观,再到主体终结论的演变。其中,与主体问题密切相关的身体问题成为引导这一演变的重要主题。在笛卡尔主导下的近代哲学中,“我思故我在”所表证的普遍理性主体观使得身心二元结构中“心”获得高扬,理性支配着主体;而身体问题的突出,使得感性得以恢复与张扬,从而促使形而上学的普遍理性主体观解体,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个体生存主体观取而代之;沿着这一方向,感性的张扬进一步实现身体对心灵的造反,走向欲望主体的确立。②
以此参照,似乎可以看到中国哲学自始便处于个体生存主体观,只是儒家时时警惕其向欲望主体的下坠,而致力于建构起普遍理性主体观,使之融入个体生存主体观中,最后达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儒家的这种努力同时受到左右的挑战,墨子倡导兼爱,近乎超越个体生存主体观,杨朱誓言为我,追求固化个体生存主体观,故孟子以辟杨墨为己任。至程朱理学,则是将孔孟的事业由经验的层面提升到理性的层面,理学始成为其思想形态,而杨墨亦转由佛老呈以更为精致的思想。
这样的概述看似简单直白,但虽不中亦不远。《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有著名论乐的“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章,《论孟精义》引录杨时曰:
梁王顾鸿雁麋鹿以问孟子,孟子因以为贤者而后乐此,至其论文王、夏桀之所以异,则独乐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贤者乎,则必语王以忧民而勿为台沼苑囿之观,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则必语王以自乐而广其侈心,是纵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当道。①
追求感官之乐并不是问题,实为正常,只是“独乐不可”。所谓的“贤者”“佞者”,都是失却正常,偏执一端。
感官之乐如此,广义的利益追求也是如此。程颐曰:
君子未尝不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者,盖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便是利。仁义未尝不利。
义利之辩是儒学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孟子见梁惠王,王问“将有以利吾国”,孟子直截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引起后人以为儒学耻以言利,或根本上是拒绝言利的。程颐这段释传则将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君子未尝不欲利”,只是深知“以利为心”的弊病,故而强调仁义,因为言仁义而利自在其中,“仁义未尝不利”。程颐更引《易》与孔子的话予以申说: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盖利者众人之所同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极,则侵夺而致怨仇。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谓先利则不夺不厌,诚哉是言也。大凡人之存心,不可专利。上九以刚而求益之极,众人之所共恶,于是莫有益之,而或攻击之矣。故圣人戒之曰:立心勿恒,乃凶之道也。谓当速改也。②
“利者众人之所同欲也”,因此,虽圣贤与人同。这便从根本上确立了作为个体生存的主体性。
事实上,程朱理学对于这种个体生存主体性的确认,有着非常感性的表达,即孟子所讲的“守身”。孟子曰: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③
此条下,《论孟精义》辑录了二程各自的长段阐发,这里取其简明,仅引程颐的阐释:
或问:“守身如何?”伊川先生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说甚道义。”曰:“人说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岩墙之下。’”或曰:“不说命者又不敢有为。”曰:“非特不敢为,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④
因为问题的涉及,致使程颐将“守身”从具体的准则提到了与“知命”相关联的理论高度。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①命象征着天道对人的规定性,即《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程颢阐发得更清楚:
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②
知命即等同于与性、教、神、道、易相贯通;而以杨时的话,则更体现程朱理学的精神,“天理即所谓命”③。依上引程颐的阐述,不守身就等于不知命,故身体在理学中的重要性便非常清楚了。可以说,身体的存在是程朱理学一切思想观念的前提。
既然如此,那么以天理为最高准则的理学究竟又是如何处理天理与身体感受性之间的紧张的呢?杨时曰:
圣人作处惟求一个是底道理,若果是,虽纣之政有所不革,果非,虽文、武之政有所不因,圣人何所容心,因时乘理,天下安利而已。④
细加体味,程朱理学所高悬的理,并非是形而上的普遍抽象原理,也不是圣人的玄想发明,而只是因时利导,能使“天下安利”的“一个是底道理”。理终究基于感性的生命存在,理并不与感性生命发生紧张,而只是与追求一己之私的感性生命相冲突。
这里,理学的确存在着抽空个体存在主体性的理论危险,因为一己之私的欲望如何界定具有弹性。但理学也从三方面致力排除这种危险。其一,理学所抽去的个体存在主体性,在理论上确切地讲,即是上述呈现为欲望的一己之私,并不是个体存在主体性的全部。当然,这在理论上存在着如何界定的问题。这在理学来说,实是一个核心问题,与对人的认定相关,此待下节专门讨论,这里暂时不论。
其二就是本节所论,个体存在主体性是理学整个论述的前提,也是最后的诉求,更贯彻于身体存在的整个过程中,理学家津津乐道于“活泼泼地”就是最显著的表证。因此,无论如何悬示天理对于个体感性生命的超越性与约束性,天理最终要分殊在个体感性生命中,并呈现出来。孟子曰: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度哉?⑤《论孟精义》于此条分别辑录:
伊川曰:“心有所存,眸子先发见。”尹讲:“存乎中必形于外,不可匿也。”①
故可以断言,理学根本上是否定将个体感性生命空洞化的,理始终不离且基于感性的生命存在。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理学高标天理,作为一个普遍性的理念,以此来剔除个体存在主体性中的一己之私,对于每个人都是有规范性的,但必须看到,正如在孔、孟那里的义利之辩一样,在理学这里,这更是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指向的是权力主体的一己之私,此由前引孟子答梁惠王问已足以知;而当明白这一点时,又足以反过来彰显理学对身体的理解与态度。
孟子与梁惠王论政治,首论义利之辩,再论众独之乐,三论王道之始。前二论已见上述,这里续观理学对孟子王道之始的阐述。孟子的王道之始由孔子先富后教之论而来,《论语·子路》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孟精义》此条辑程门五弟子言,节录如下:
范曰:“此治民之序,自尧舜以来,未有不由之者也。禹平水土以居民,所以庶之也;稷播百谷,所以富之也;契敷五教,所以教之也。”
谢曰:“庶而不富,则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杨曰:“既庶矣,当使之养生送死无憾,然后可驱而之善,此不易之道也。”
侯曰:“既庶既富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尹曰:“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故富而后教之。”②而关于孟子的王道之始,程颐曰:
孟子论王道便实,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便先从养生上说将去,既庶既富,然后以饱食暖衣而无教为不可,故教之也。③
可见,人的生命的现实存在是理学坚不动摇的前提,“饱食暖衣”既为正当,“富而后教”才足以成立。天理王道,决非是与个体感性生命相对立的东西,而恰恰是基于个体感性生命的。程颢曰:
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诚然,“本乎人情”,基于个体感性生命,在经过“出乎礼义”后,个体生存的主体性会被公共化,但不能据此就轻易认为个体生存的主体性就被完全抽空了。从“本乎人情”到“出乎礼义”之间,既有程颐所讲的“礼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即义也”的理论认定①,现实过程中也还存在着进行公与私鉴别的阀门,即程颢所谓“察见天理,不用私意也”。②上引程颢“王道如砥,本乎人情”之语,便是在与下引的话作比较时讲的:
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霸者崎岖反侧于曲迳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③
统观孟子与梁惠王论政治的前三项,义利之辩、众独之乐、王道之始,也都可以看到,其中贯彻着公与私的鉴定。事实上,这也是能否真正解释经典的关键。《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章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名言,可谓对个体生命最高的礼赞,但并不能据此而迂腐地以为凡仁者便不为杀伐之事。《论孟精义》此条下载:
(程颐)先生在经筵日,有二同列论武侯事业,以为武侯战伐所丧亦多,非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事。先生谓:“二公语过矣,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谓杀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讨天下之贼,则何害?”④
如果考虑到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这一不可改变的前置因素,个体生命的存在需要获得公共安全的保障,那么,程朱理学“本乎人情,出乎礼义”的天理,与其说是对个体生存主体性的抹杀,毋宁说更是对个体生存主体性的维护。
最后请再举程颐被贬放涪州编管途中一事,以见理学家对人,乃至对人的形象所抱持的敬意。杨时曰:
翟霖送伊川先生西迁,道宿僧舍,坐处背塑像,先生令转椅勿背。霖问曰:“岂不以其徒敬之,故亦当敬耶?”伊川曰:“但具人形貌,便不当慢。”因赏此语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者也。’盖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无所不用其敬,见似人者不忽,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于轻忽人。”⑤
读其言便可以知其人,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并且最终落在自己的身上,即程颐所谓“切己”:
凡看《论》《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语言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此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②
然则,《论孟精义》中所呈现的人,又究竟是怎样的人呢?笼统地讲,他们自然是圣贤,或是希望成圣成贤的人。但圣贤又是怎样的人呢?请先看程颢几段描述:
1.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
2.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3.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辩。
4.孔子为宰则为宰,为陪臣则为陪臣,皆能发明大道。孟子必得宾师之位,然后能明其道,犹之有许大形象,然后为泰山,有许多水,然后为海,以此未及孔子。
5.子厚(张载)谨严,才谨严便有迫切气象,无宽舒之气。孟子却宽舒,只是中间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之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
6.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①
上引六条,1、2比诸自然,3、4、5似见性格,6可谓涵养,虽然难以进一步概括,但有一点却是断然可言的,他们都是明显具有感性特征的人。
然而众所周知,程朱理学之为“理学”,正在于“理”的高标,以及理性精神的培植与主导,前节见之于语言分析所揭明的论辩精神亦是表证之一,而“穷天理灭人欲”的宣称更给人以理学完全荡去感性的印象,因此《论孟精义》所呈现的充满感性特征的圣贤形象便不得不“深求玩味”了。
为了便于分析的展开,这里同样不妨借镜于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在由近代向现代,以及后现代的演化中,主体问题经历了从普遍理性主体观向个体生存主体观,再到主体终结论的演变。其中,与主体问题密切相关的身体问题成为引导这一演变的重要主题。在笛卡尔主导下的近代哲学中,“我思故我在”所表证的普遍理性主体观使得身心二元结构中“心”获得高扬,理性支配着主体;而身体问题的突出,使得感性得以恢复与张扬,从而促使形而上学的普遍理性主体观解体,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个体生存主体观取而代之;沿着这一方向,感性的张扬进一步实现身体对心灵的造反,走向欲望主体的确立。②
以此参照,似乎可以看到中国哲学自始便处于个体生存主体观,只是儒家时时警惕其向欲望主体的下坠,而致力于建构起普遍理性主体观,使之融入个体生存主体观中,最后达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儒家的这种努力同时受到左右的挑战,墨子倡导兼爱,近乎超越个体生存主体观,杨朱誓言为我,追求固化个体生存主体观,故孟子以辟杨墨为己任。至程朱理学,则是将孔孟的事业由经验的层面提升到理性的层面,理学始成为其思想形态,而杨墨亦转由佛老呈以更为精致的思想。
这样的概述看似简单直白,但虽不中亦不远。《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有著名论乐的“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章,《论孟精义》引录杨时曰:
梁王顾鸿雁麋鹿以问孟子,孟子因以为贤者而后乐此,至其论文王、夏桀之所以异,则独乐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贤者乎,则必语王以忧民而勿为台沼苑囿之观,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则必语王以自乐而广其侈心,是纵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当道。①
追求感官之乐并不是问题,实为正常,只是“独乐不可”。所谓的“贤者”“佞者”,都是失却正常,偏执一端。
感官之乐如此,广义的利益追求也是如此。程颐曰:
君子未尝不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者,盖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便是利。仁义未尝不利。
义利之辩是儒学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孟子见梁惠王,王问“将有以利吾国”,孟子直截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引起后人以为儒学耻以言利,或根本上是拒绝言利的。程颐这段释传则将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君子未尝不欲利”,只是深知“以利为心”的弊病,故而强调仁义,因为言仁义而利自在其中,“仁义未尝不利”。程颐更引《易》与孔子的话予以申说: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盖利者众人之所同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极,则侵夺而致怨仇。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谓先利则不夺不厌,诚哉是言也。大凡人之存心,不可专利。上九以刚而求益之极,众人之所共恶,于是莫有益之,而或攻击之矣。故圣人戒之曰:立心勿恒,乃凶之道也。谓当速改也。②
“利者众人之所同欲也”,因此,虽圣贤与人同。这便从根本上确立了作为个体生存的主体性。
事实上,程朱理学对于这种个体生存主体性的确认,有着非常感性的表达,即孟子所讲的“守身”。孟子曰: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③
此条下,《论孟精义》辑录了二程各自的长段阐发,这里取其简明,仅引程颐的阐释:
或问:“守身如何?”伊川先生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说甚道义。”曰:“人说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岩墙之下。’”或曰:“不说命者又不敢有为。”曰:“非特不敢为,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④
因为问题的涉及,致使程颐将“守身”从具体的准则提到了与“知命”相关联的理论高度。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①命象征着天道对人的规定性,即《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程颢阐发得更清楚:
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②
知命即等同于与性、教、神、道、易相贯通;而以杨时的话,则更体现程朱理学的精神,“天理即所谓命”③。依上引程颐的阐述,不守身就等于不知命,故身体在理学中的重要性便非常清楚了。可以说,身体的存在是程朱理学一切思想观念的前提。
既然如此,那么以天理为最高准则的理学究竟又是如何处理天理与身体感受性之间的紧张的呢?杨时曰:
圣人作处惟求一个是底道理,若果是,虽纣之政有所不革,果非,虽文、武之政有所不因,圣人何所容心,因时乘理,天下安利而已。④
细加体味,程朱理学所高悬的理,并非是形而上的普遍抽象原理,也不是圣人的玄想发明,而只是因时利导,能使“天下安利”的“一个是底道理”。理终究基于感性的生命存在,理并不与感性生命发生紧张,而只是与追求一己之私的感性生命相冲突。
这里,理学的确存在着抽空个体存在主体性的理论危险,因为一己之私的欲望如何界定具有弹性。但理学也从三方面致力排除这种危险。其一,理学所抽去的个体存在主体性,在理论上确切地讲,即是上述呈现为欲望的一己之私,并不是个体存在主体性的全部。当然,这在理论上存在着如何界定的问题。这在理学来说,实是一个核心问题,与对人的认定相关,此待下节专门讨论,这里暂时不论。
其二就是本节所论,个体存在主体性是理学整个论述的前提,也是最后的诉求,更贯彻于身体存在的整个过程中,理学家津津乐道于“活泼泼地”就是最显著的表证。因此,无论如何悬示天理对于个体感性生命的超越性与约束性,天理最终要分殊在个体感性生命中,并呈现出来。孟子曰: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度哉?⑤《论孟精义》于此条分别辑录:
伊川曰:“心有所存,眸子先发见。”尹讲:“存乎中必形于外,不可匿也。”①
故可以断言,理学根本上是否定将个体感性生命空洞化的,理始终不离且基于感性的生命存在。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理学高标天理,作为一个普遍性的理念,以此来剔除个体存在主体性中的一己之私,对于每个人都是有规范性的,但必须看到,正如在孔、孟那里的义利之辩一样,在理学这里,这更是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指向的是权力主体的一己之私,此由前引孟子答梁惠王问已足以知;而当明白这一点时,又足以反过来彰显理学对身体的理解与态度。
孟子与梁惠王论政治,首论义利之辩,再论众独之乐,三论王道之始。前二论已见上述,这里续观理学对孟子王道之始的阐述。孟子的王道之始由孔子先富后教之论而来,《论语·子路》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孟精义》此条辑程门五弟子言,节录如下:
范曰:“此治民之序,自尧舜以来,未有不由之者也。禹平水土以居民,所以庶之也;稷播百谷,所以富之也;契敷五教,所以教之也。”
谢曰:“庶而不富,则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杨曰:“既庶矣,当使之养生送死无憾,然后可驱而之善,此不易之道也。”
侯曰:“既庶既富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尹曰:“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故富而后教之。”②而关于孟子的王道之始,程颐曰:
孟子论王道便实,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便先从养生上说将去,既庶既富,然后以饱食暖衣而无教为不可,故教之也。③
可见,人的生命的现实存在是理学坚不动摇的前提,“饱食暖衣”既为正当,“富而后教”才足以成立。天理王道,决非是与个体感性生命相对立的东西,而恰恰是基于个体感性生命的。程颢曰:
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诚然,“本乎人情”,基于个体感性生命,在经过“出乎礼义”后,个体生存的主体性会被公共化,但不能据此就轻易认为个体生存的主体性就被完全抽空了。从“本乎人情”到“出乎礼义”之间,既有程颐所讲的“礼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即义也”的理论认定①,现实过程中也还存在着进行公与私鉴别的阀门,即程颢所谓“察见天理,不用私意也”。②上引程颢“王道如砥,本乎人情”之语,便是在与下引的话作比较时讲的:
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霸者崎岖反侧于曲迳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③
统观孟子与梁惠王论政治的前三项,义利之辩、众独之乐、王道之始,也都可以看到,其中贯彻着公与私的鉴定。事实上,这也是能否真正解释经典的关键。《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章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名言,可谓对个体生命最高的礼赞,但并不能据此而迂腐地以为凡仁者便不为杀伐之事。《论孟精义》此条下载:
(程颐)先生在经筵日,有二同列论武侯事业,以为武侯战伐所丧亦多,非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事。先生谓:“二公语过矣,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谓杀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讨天下之贼,则何害?”④
如果考虑到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这一不可改变的前置因素,个体生命的存在需要获得公共安全的保障,那么,程朱理学“本乎人情,出乎礼义”的天理,与其说是对个体生存主体性的抹杀,毋宁说更是对个体生存主体性的维护。
最后请再举程颐被贬放涪州编管途中一事,以见理学家对人,乃至对人的形象所抱持的敬意。杨时曰:
翟霖送伊川先生西迁,道宿僧舍,坐处背塑像,先生令转椅勿背。霖问曰:“岂不以其徒敬之,故亦当敬耶?”伊川曰:“但具人形貌,便不当慢。”因赏此语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者也。’盖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无所不用其敬,见似人者不忽,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于轻忽人。”⑤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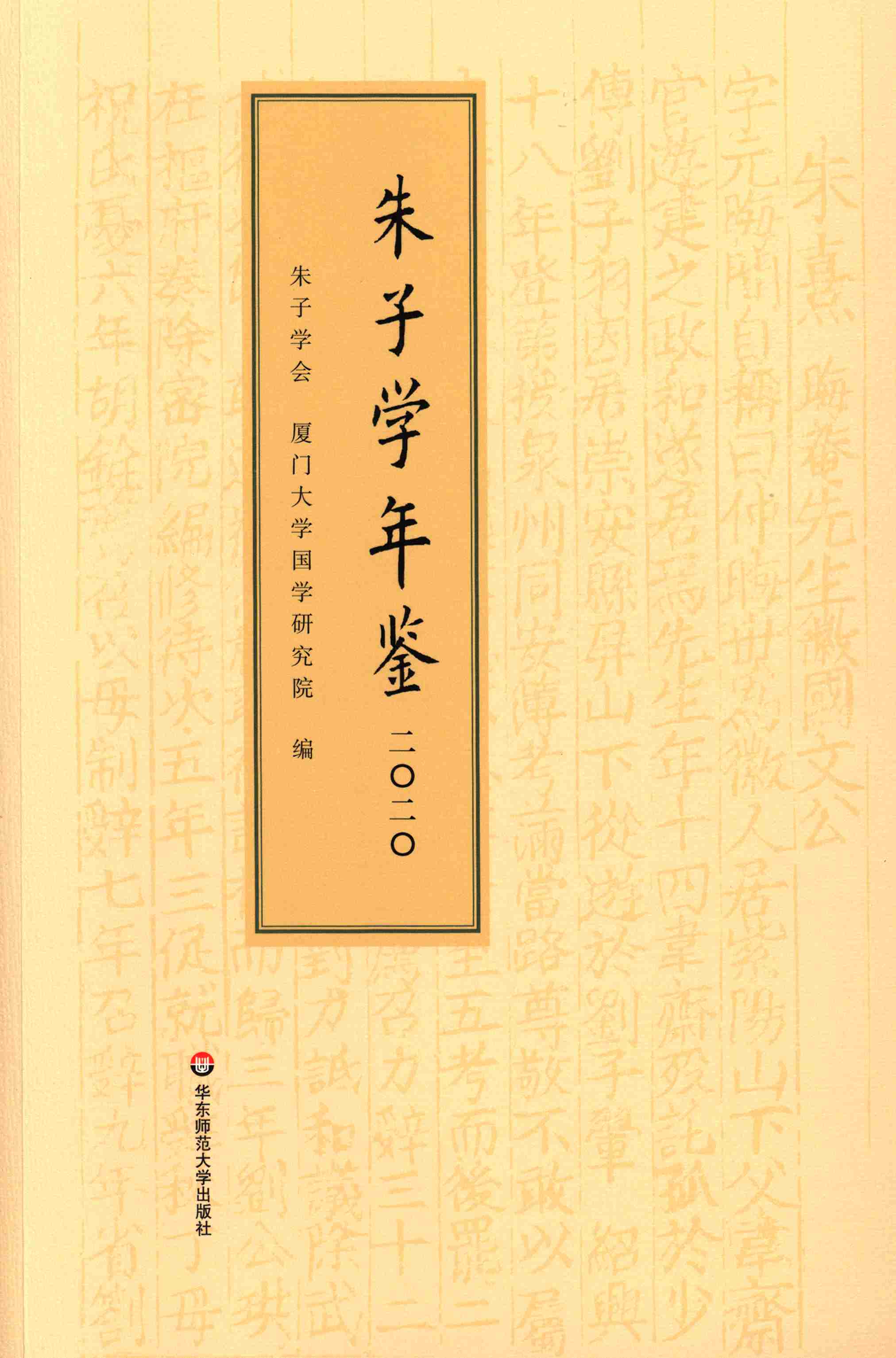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0》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以礼释仁的路径和意义》《2020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何俊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