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言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0》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884 |
| 颗粒名称: | 二、语言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 |
| 页码: | 074-079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朱熹对于《论孟精义》的重视程度。尽管朱熹将其视为思想整顿的初级版本,但在后来的学术发展中仍对其持重要态度。尽管《集注》被视为《论孟精义》的升级版,但朱熹在《语录》中仍强调《论孟精义》的重要性。这表明朱熹对于初级版本仍抱有重要看法。 |
| 关键词: | 朱熹 《论孟精义》 学术发展 |
内容
对于一个话语构型来说,文本是显像,语言则是微像。上一节曾指出,朱熹将“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在《论孟集注》的《读论语孟子法》中提升到第2条,并且贯彻在《论孟集注》中,使之成为《论孟精义》的升级版。照理说,有了升级版,而且朱熹也确实以升级版为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事业,作为初级版的《论孟精义》就不必在乎了;况且正如前引《论孟精义自序》中所言,此书原本是朱熹整顿自己思想时“以备观省”,只是“同志之士有欲从事于此者,亦不隐焉”。那么,为什么朱熹后来对《论孟精义》仍然很看重呢?四库馆臣曰:
朱子初集是书(《论孟精义》),盖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其后采摄菁华,撰成《集注》。中间异同、疑似,当加剖析者,又别著之于《或问》。似此书乃已弃之糟粕。然考诸《语录》,乃谓:“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又谓:“《语孟集义》中所载诸先生语,须是熟读。一一记于心下,时时将来玩味,久久自然理会得。”又似不以《集注》废此书者。①
前引朱熹自称“以备观省”,虽然是自谦之语,但也是部分事实。《论孟精义》(1172年)原是在《论语要义》(1163年)基础上完成的,前后近十年。《要义》是朱熹由禅返儒的标志,而《精义》是他整合二程理学的标志,换言之,从《论语要义》到《论孟精义》确实是朱熹自己思想型塑时期“以备观省”的真实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成《论语要义》后,朱熹马上又补撰了《论语训蒙口义》。在《论语训蒙口义序》中,朱熹曰:
予既叙次《论语要义》,以备览观,暇日又为儿辈读之。大抵诸老先生之为说,本非为童子设也,故其训诂略而义理详。初学者读之,经之文句未能自通,又当遍诵诸说,问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启蒙之要。因为删录,以成此编。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②
虽然朱熹以此通训诂、正音读“便于童子之习而已,故名之曰《训蒙口义》”,但他深知这又是基础,故在《论孟精义纲领》中才会强调,“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然而,颇有意趣的是,尽管朱熹高度意识到训诂是义理的前提,彼此存在高低层级,似乎没有冲突,而且后来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合训诂与义理为一体,为什么他在《论语要义》与《论语训蒙口义》成书后的近十年思想型塑过程中,只致力于单纯的《论孟精义》撰写呢?而且,即便后来撰写《四书章句集注》,他还要将“其余议论,别为《四书或问》一篇”③,为什么朱熹很在乎这些“议论”?
朱熹在《论孟精义自序》中就他限定程门及其同志(实仅张载一人)“蒐辑条疏”的问题,自设问答作了一个详尽的说明:
或曰:然则凡说之行于世而不列于此者,皆无取已乎?曰:不然也。(1)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2)而近世二三名家,与夫所谓学于先生之门人者,其考证推说亦或时有补于文义之间。学者有得于此而后观焉,则亦何适而无得哉?特所以求夫圣贤之意者,则在此而不在彼尔。(3)若夫外自讬于程氏,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则诚不可以入于学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颇已乡之矣,其为害岂浅浅哉?顾其语言气象之间,则实有不难辩者。学者诚用力于此书而有得焉,则于其言虽欲读之,亦且有所不暇矣。①
笔者所标示的三条说明,(3)所涉及的异端杂学辩析问题,且待最后一节讨论,这里专论前两条。
先看第一条说明。“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其功博矣”,因此朱熹声明学者必先弄明白这些,才足以用力于义理。不过,又必须记得,这虽是前提,但毕竟是“童子之习”,为“启蒙之要”,而《论孟精义》则是专以义理为务的。《论孟精义纲领》辑录程颐语曰:
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
读《论》《孟》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传录言语,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②
“晓其文义”“得其言”固然是前提,但“求其意”“得其心”终是根本,“知道”才是研读经典的目的。这就明确表明,在朱熹看来,经典传释实际上存在着两套语言系统,汉魏诸儒使用的是“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的语言系统,即清儒所谓的经学之汉学的语言,程门使用的是义理条疏的语言系统,即清儒所谓的经学之宋学的语言;而且从朱熹自设问答的(2)(3),可知朱熹以为这套宋学的语言系统是宋儒通用的,并非程门独有,只是彼此在思想内容的阐发上存在分歧。对于思想型塑中的朱熹来说,毫无疑问,宋学的语言系统是重中之重;而且即便是两者并用了,经由宋学的语言系统所展开的“议论”也仍然是不可轻弃的。《论孟精义》的体例之所以单方向强化《论语要义》,没有合《论语要义》与《论语训蒙口义》为一体;在升级精华版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书以后,《论孟精义》仍需重视,而且“其余议论别为《或问》”,原因尽在此。
然则,接踵而至的问题是,为什么汉学的语言系统只具有“晓其文义”“得其言”的语义学功能,而只有宋学的语言系统才拥有“求其意”“得其心”“知道”的意义学功能呢?西方哲学在由近代认识论向现代存在论的发展中,存在着重要的“语言学转向”,虽然汉宋学的转移不必强作类比,但却不妨借镜于彼,以解开上述的困惑。在西方近代认识论的语境中,语言被单纯认为是表象的工具,关注语言的静态结构就可以把握语言所要传达的观念与思想。但在转向现代时,静态的语言结构让位于实际生活的发生,语言与实际动态的生活相联系,这一语言学转向直接催生出现代存在论,虽然语言学转向有现象学意义上与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区别①。在朱熹看来,汉学的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正是类同于近代认识论中的语义学,只足以对经典作静态解读,“晓其文义”“得其言”,虽重要却是童蒙之学,而只有宋学的义理条疏则近于现代现象学的意义理论,能够实现“求其意”“得其心”“知道”的追求。
何以见得呢?朱熹辑录程颐所谓“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可以说是一个总的表达,而他具体的释传举例则将这样的认识彰显得极为清楚。程颐曰:
传录言语,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虽孔门亦有是患。(1)如言昭公知礼,巫马期告时,孔子正可不答其问,必更有语言,具巫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过,人必知之”。盖孔子答,巫马期亦知之,陈司败亦知之矣。(2)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圣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为圣人,岂不有害?(3)又如孟子言“放勋曰”,只当言“尧曰”,传者乘放勋为尧号,乃称“放勋曰”。(4)又如言“闻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问,及仲由为比,便信此一句,岂不有害?(5)又如孟子,齐王欲“养弟子以万钟”,此事欲国人矜式。孟子何不可处?但时子以利诱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若观其文,只似孟子不肯为国人矜式,须知不可以利诱之意。(6)“舜不告而娶”,须识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顽,过时不为娶,尧去治之,尧命瞽使舜娶,舜虽不告,尧固告之矣。尧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7)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杀舜为事,尧奚为不治?盖象之杀舜无可见之迹,发人隐慝而治之,非尧也。②
笔者不嫌其烦,照引这段长文,并加以标示,实因朱熹在悬为示范引导的《论孟精义纲领》中辑录这段文字,表明很重要。事实上,程颐这样举例,朱熹这样照引,当时人熟读经典,自然能知晓其所指,今人对经典并不熟知,仅看这段文字,仍不免一头雾水,不明所以。此处限于篇幅,也不宜逐一说明,只能概而言之。程颐所举七例,旨在表明,如果就文本文义进行解读,即便音读、字义、制度、名物都确定无误,仍然只能“得其言未得其心”,甚至作出“必有害”的误读。这些举例不仅彰显了宋学与汉学两种解经语言在功能上的区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实际上也示范了程颐应用宋学的解经语言实现“求其意”“得其心”“知道”的基本方法与路径,即必须将经典文本与历史中的生存实际相结合,切身体会甚至不免想象重构经典文本中没有记录下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当时人而言是不言而喻的,而对后人理解时却变得至关重要。
现在再看第二条说明。“近世二三名家,与夫所谓学于先生之门人者,其考证推说亦或时有补于文义之间”;事实上,五年以后的《论孟集注》就呈现出了极大的开放性,除《论孟精义》所辑录者外,自汉魏以降至当时,直接间接征引者达几十家,虽荆公新学、三苏蜀学也不排斥①,那么《论孟精义》为什么只限于二程以及张载与程门诸弟子呢?朱熹的回答是:
学者有得于此而后观焉,则亦何适而无得哉?特所以求夫圣贤之意者,则在此而不在彼尔。换言之,《论孟精义》的选择范围限定于二程理学,实乃朱熹思想上的认定。
不过,这只是上一节讨论文本所揭示的问题,可作上节的一个补充。而与本节主题有直接关系的是,由朱熹的说明,似乎可以追问,二程对《论》《孟》的解读已充分而精准,与孔、孟之心契合无间,为什么不将范围仅限于二程呢?
前引程颐所举七例表明,在二程理学的经典解读中,客观地对待经典给定的文本是不够的,必须要结合文本的人物及其实际的活动,如此才能使得文本所呈现的死的“语言”,转换成文本中讲话的那个人的活的“言语”。经过了这样的转换以后,对经典的理解就变成了读者与作者跨越时空的对话,经典文本的意义就延伸到解读者的当下生活之中,从而影响当下的生活。可以设想,这个过程自然是艰难的,故“自秦汉以来,儒者类皆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直到宋兴百年才有二程出,与孔、孟心契。唯其不易,故虽孔、孟弟子未必完全理解孔、孟,二程门人也未必完全理解二程,更难完全理解二程对孔、孟的理解。对此,朱熹显然有真切认识,故曰:
读书考义理,似是而非者难辨。且如《精义》中,惟程先生说得确当。至其门人,非惟不尽得夫子之意,虽程子之意,亦多失之。既如此,不是更应限于二程的解说吗?朱熹的看法却又不然,他接着讲:
今读《语》《孟》,不可便道《精义》都不是,都废了。须借它做阶梯去寻求,将来自见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②至此似乎终于明白,《论孟精义》为什么既要排斥程门外的,又不能限于二
程。在朱熹看来,把握经典的义理,既不能太宽泛,以免陷于支蔓,甚至迷于歧路,又不能专限于权威,以免自我逼仄,丧失独立思考。对经典的义理探求,需要二程这样的圣人来接绪前圣,开悟后学,同时又需要圣人门下的贤人参与到对经典的共同研读讨论中,甚至不惜形成某种争辩(argument)。事实上,就朱熹而言,正与孟子一样,终其一生的思想历程,便是充满争辩的。也许这是思想巨子们的共同特征。《孟子精义》卷五《滕文公章句上》“滕文公问为国”章条录张载与人对话:
或谓:“井议不可轻示人,恐致笑及有议论。”先生谓:“有笑有议论,则方有益也。”①
这一对话不仅是其思想开放性的生动显现,而且也充分表证“有笑有议论”的语言或言语本身就构成了理学的存在。
要言之,朱熹建构程朱理学的话语构型,在语言上虽最终呈现为《四书章句集注》的汉学与宋学两套语言的整合,但更视宋学语言的彰显为重要与必要,《论孟精义》充分表证了这一点,《四书或问》也是如此。《论孟精义》中理学传释经典的语言替代了或补充了经学汉学的风格,它使得经典由死的文本转换成活的言语,从而与理学家发生沟通,并且通过共同议论而促成思想的生成。语言或言语在程朱理学这里,已然不再只是反映思想的工具,而毋宁就是理学乃至理学家的生活本身。在此意义上,朱熹对《论孟精义》的看重、对《四书或问》的不弃,并不在于其所表达的思想的正确,而在于它们是思想探求过程的记录,也是理学家追步圣贤生活过程的记录,人们可以“借它做阶梯去寻求,将来自见道理”。
朱子初集是书(《论孟精义》),盖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其后采摄菁华,撰成《集注》。中间异同、疑似,当加剖析者,又别著之于《或问》。似此书乃已弃之糟粕。然考诸《语录》,乃谓:“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又谓:“《语孟集义》中所载诸先生语,须是熟读。一一记于心下,时时将来玩味,久久自然理会得。”又似不以《集注》废此书者。①
前引朱熹自称“以备观省”,虽然是自谦之语,但也是部分事实。《论孟精义》(1172年)原是在《论语要义》(1163年)基础上完成的,前后近十年。《要义》是朱熹由禅返儒的标志,而《精义》是他整合二程理学的标志,换言之,从《论语要义》到《论孟精义》确实是朱熹自己思想型塑时期“以备观省”的真实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成《论语要义》后,朱熹马上又补撰了《论语训蒙口义》。在《论语训蒙口义序》中,朱熹曰:
予既叙次《论语要义》,以备览观,暇日又为儿辈读之。大抵诸老先生之为说,本非为童子设也,故其训诂略而义理详。初学者读之,经之文句未能自通,又当遍诵诸说,问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启蒙之要。因为删录,以成此编。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②
虽然朱熹以此通训诂、正音读“便于童子之习而已,故名之曰《训蒙口义》”,但他深知这又是基础,故在《论孟精义纲领》中才会强调,“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然而,颇有意趣的是,尽管朱熹高度意识到训诂是义理的前提,彼此存在高低层级,似乎没有冲突,而且后来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合训诂与义理为一体,为什么他在《论语要义》与《论语训蒙口义》成书后的近十年思想型塑过程中,只致力于单纯的《论孟精义》撰写呢?而且,即便后来撰写《四书章句集注》,他还要将“其余议论,别为《四书或问》一篇”③,为什么朱熹很在乎这些“议论”?
朱熹在《论孟精义自序》中就他限定程门及其同志(实仅张载一人)“蒐辑条疏”的问题,自设问答作了一个详尽的说明:
或曰:然则凡说之行于世而不列于此者,皆无取已乎?曰:不然也。(1)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2)而近世二三名家,与夫所谓学于先生之门人者,其考证推说亦或时有补于文义之间。学者有得于此而后观焉,则亦何适而无得哉?特所以求夫圣贤之意者,则在此而不在彼尔。(3)若夫外自讬于程氏,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则诚不可以入于学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颇已乡之矣,其为害岂浅浅哉?顾其语言气象之间,则实有不难辩者。学者诚用力于此书而有得焉,则于其言虽欲读之,亦且有所不暇矣。①
笔者所标示的三条说明,(3)所涉及的异端杂学辩析问题,且待最后一节讨论,这里专论前两条。
先看第一条说明。“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其功博矣”,因此朱熹声明学者必先弄明白这些,才足以用力于义理。不过,又必须记得,这虽是前提,但毕竟是“童子之习”,为“启蒙之要”,而《论孟精义》则是专以义理为务的。《论孟精义纲领》辑录程颐语曰:
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
读《论》《孟》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传录言语,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②
“晓其文义”“得其言”固然是前提,但“求其意”“得其心”终是根本,“知道”才是研读经典的目的。这就明确表明,在朱熹看来,经典传释实际上存在着两套语言系统,汉魏诸儒使用的是“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的语言系统,即清儒所谓的经学之汉学的语言,程门使用的是义理条疏的语言系统,即清儒所谓的经学之宋学的语言;而且从朱熹自设问答的(2)(3),可知朱熹以为这套宋学的语言系统是宋儒通用的,并非程门独有,只是彼此在思想内容的阐发上存在分歧。对于思想型塑中的朱熹来说,毫无疑问,宋学的语言系统是重中之重;而且即便是两者并用了,经由宋学的语言系统所展开的“议论”也仍然是不可轻弃的。《论孟精义》的体例之所以单方向强化《论语要义》,没有合《论语要义》与《论语训蒙口义》为一体;在升级精华版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书以后,《论孟精义》仍需重视,而且“其余议论别为《或问》”,原因尽在此。
然则,接踵而至的问题是,为什么汉学的语言系统只具有“晓其文义”“得其言”的语义学功能,而只有宋学的语言系统才拥有“求其意”“得其心”“知道”的意义学功能呢?西方哲学在由近代认识论向现代存在论的发展中,存在着重要的“语言学转向”,虽然汉宋学的转移不必强作类比,但却不妨借镜于彼,以解开上述的困惑。在西方近代认识论的语境中,语言被单纯认为是表象的工具,关注语言的静态结构就可以把握语言所要传达的观念与思想。但在转向现代时,静态的语言结构让位于实际生活的发生,语言与实际动态的生活相联系,这一语言学转向直接催生出现代存在论,虽然语言学转向有现象学意义上与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区别①。在朱熹看来,汉学的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正是类同于近代认识论中的语义学,只足以对经典作静态解读,“晓其文义”“得其言”,虽重要却是童蒙之学,而只有宋学的义理条疏则近于现代现象学的意义理论,能够实现“求其意”“得其心”“知道”的追求。
何以见得呢?朱熹辑录程颐所谓“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可以说是一个总的表达,而他具体的释传举例则将这样的认识彰显得极为清楚。程颐曰:
传录言语,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虽孔门亦有是患。(1)如言昭公知礼,巫马期告时,孔子正可不答其问,必更有语言,具巫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过,人必知之”。盖孔子答,巫马期亦知之,陈司败亦知之矣。(2)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圣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为圣人,岂不有害?(3)又如孟子言“放勋曰”,只当言“尧曰”,传者乘放勋为尧号,乃称“放勋曰”。(4)又如言“闻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问,及仲由为比,便信此一句,岂不有害?(5)又如孟子,齐王欲“养弟子以万钟”,此事欲国人矜式。孟子何不可处?但时子以利诱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若观其文,只似孟子不肯为国人矜式,须知不可以利诱之意。(6)“舜不告而娶”,须识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顽,过时不为娶,尧去治之,尧命瞽使舜娶,舜虽不告,尧固告之矣。尧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7)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杀舜为事,尧奚为不治?盖象之杀舜无可见之迹,发人隐慝而治之,非尧也。②
笔者不嫌其烦,照引这段长文,并加以标示,实因朱熹在悬为示范引导的《论孟精义纲领》中辑录这段文字,表明很重要。事实上,程颐这样举例,朱熹这样照引,当时人熟读经典,自然能知晓其所指,今人对经典并不熟知,仅看这段文字,仍不免一头雾水,不明所以。此处限于篇幅,也不宜逐一说明,只能概而言之。程颐所举七例,旨在表明,如果就文本文义进行解读,即便音读、字义、制度、名物都确定无误,仍然只能“得其言未得其心”,甚至作出“必有害”的误读。这些举例不仅彰显了宋学与汉学两种解经语言在功能上的区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实际上也示范了程颐应用宋学的解经语言实现“求其意”“得其心”“知道”的基本方法与路径,即必须将经典文本与历史中的生存实际相结合,切身体会甚至不免想象重构经典文本中没有记录下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当时人而言是不言而喻的,而对后人理解时却变得至关重要。
现在再看第二条说明。“近世二三名家,与夫所谓学于先生之门人者,其考证推说亦或时有补于文义之间”;事实上,五年以后的《论孟集注》就呈现出了极大的开放性,除《论孟精义》所辑录者外,自汉魏以降至当时,直接间接征引者达几十家,虽荆公新学、三苏蜀学也不排斥①,那么《论孟精义》为什么只限于二程以及张载与程门诸弟子呢?朱熹的回答是:
学者有得于此而后观焉,则亦何适而无得哉?特所以求夫圣贤之意者,则在此而不在彼尔。换言之,《论孟精义》的选择范围限定于二程理学,实乃朱熹思想上的认定。
不过,这只是上一节讨论文本所揭示的问题,可作上节的一个补充。而与本节主题有直接关系的是,由朱熹的说明,似乎可以追问,二程对《论》《孟》的解读已充分而精准,与孔、孟之心契合无间,为什么不将范围仅限于二程呢?
前引程颐所举七例表明,在二程理学的经典解读中,客观地对待经典给定的文本是不够的,必须要结合文本的人物及其实际的活动,如此才能使得文本所呈现的死的“语言”,转换成文本中讲话的那个人的活的“言语”。经过了这样的转换以后,对经典的理解就变成了读者与作者跨越时空的对话,经典文本的意义就延伸到解读者的当下生活之中,从而影响当下的生活。可以设想,这个过程自然是艰难的,故“自秦汉以来,儒者类皆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直到宋兴百年才有二程出,与孔、孟心契。唯其不易,故虽孔、孟弟子未必完全理解孔、孟,二程门人也未必完全理解二程,更难完全理解二程对孔、孟的理解。对此,朱熹显然有真切认识,故曰:
读书考义理,似是而非者难辨。且如《精义》中,惟程先生说得确当。至其门人,非惟不尽得夫子之意,虽程子之意,亦多失之。既如此,不是更应限于二程的解说吗?朱熹的看法却又不然,他接着讲:
今读《语》《孟》,不可便道《精义》都不是,都废了。须借它做阶梯去寻求,将来自见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②至此似乎终于明白,《论孟精义》为什么既要排斥程门外的,又不能限于二
程。在朱熹看来,把握经典的义理,既不能太宽泛,以免陷于支蔓,甚至迷于歧路,又不能专限于权威,以免自我逼仄,丧失独立思考。对经典的义理探求,需要二程这样的圣人来接绪前圣,开悟后学,同时又需要圣人门下的贤人参与到对经典的共同研读讨论中,甚至不惜形成某种争辩(argument)。事实上,就朱熹而言,正与孟子一样,终其一生的思想历程,便是充满争辩的。也许这是思想巨子们的共同特征。《孟子精义》卷五《滕文公章句上》“滕文公问为国”章条录张载与人对话:
或谓:“井议不可轻示人,恐致笑及有议论。”先生谓:“有笑有议论,则方有益也。”①
这一对话不仅是其思想开放性的生动显现,而且也充分表证“有笑有议论”的语言或言语本身就构成了理学的存在。
要言之,朱熹建构程朱理学的话语构型,在语言上虽最终呈现为《四书章句集注》的汉学与宋学两套语言的整合,但更视宋学语言的彰显为重要与必要,《论孟精义》充分表证了这一点,《四书或问》也是如此。《论孟精义》中理学传释经典的语言替代了或补充了经学汉学的风格,它使得经典由死的文本转换成活的言语,从而与理学家发生沟通,并且通过共同议论而促成思想的生成。语言或言语在程朱理学这里,已然不再只是反映思想的工具,而毋宁就是理学乃至理学家的生活本身。在此意义上,朱熹对《论孟精义》的看重、对《四书或问》的不弃,并不在于其所表达的思想的正确,而在于它们是思想探求过程的记录,也是理学家追步圣贤生活过程的记录,人们可以“借它做阶梯去寻求,将来自见道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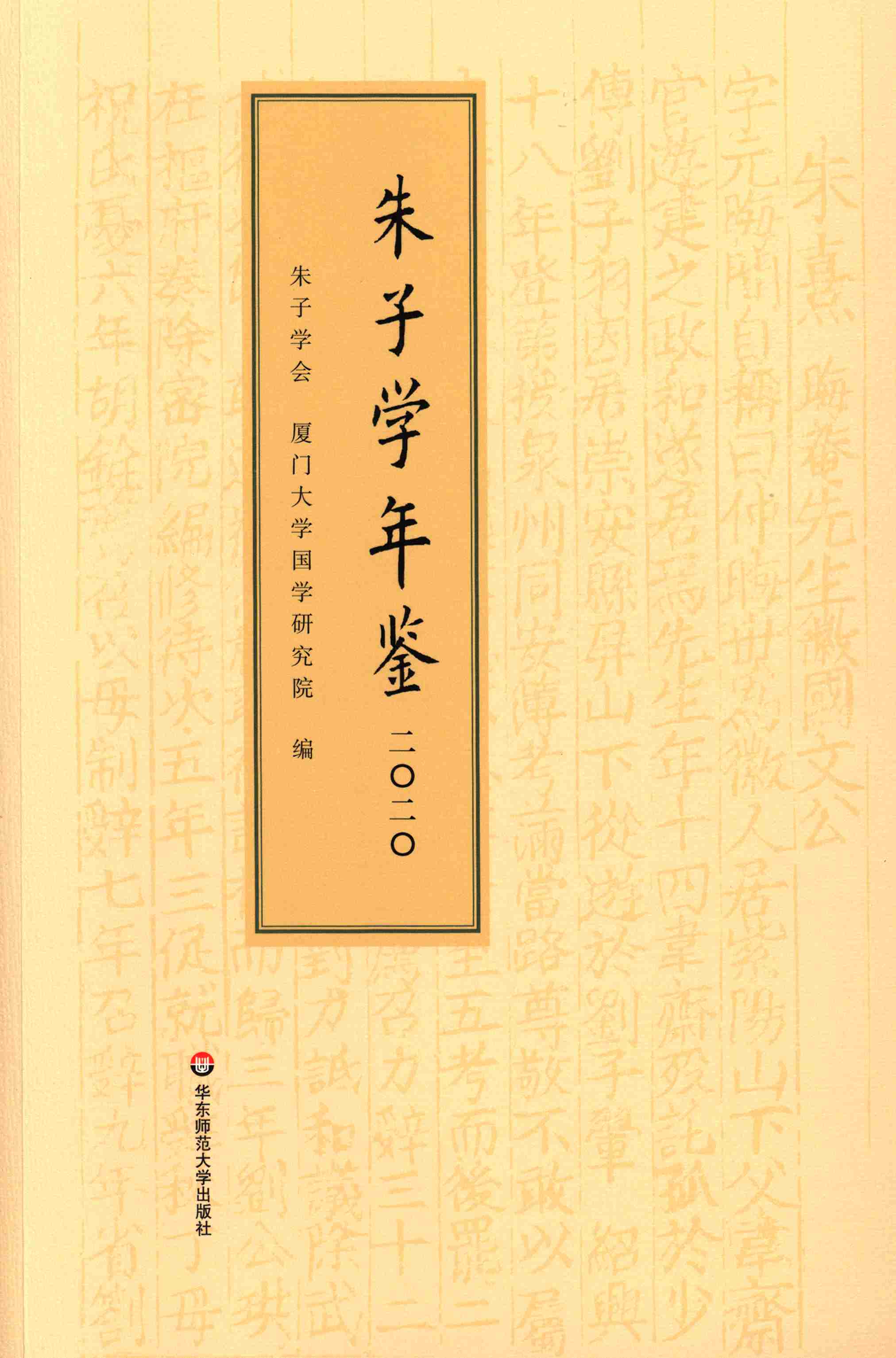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0》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以礼释仁的路径和意义》《2020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何俊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