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以理释仁的路径和意义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0》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872 |
| 颗粒名称: | 朱熹以理释仁的路径和意义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8 |
| 页码: | 048-055 |
| 摘要: | 本篇文章记述了朱熹以理释仁的路径和意义的情况。其中包括儒家经典诠释中的“礼—仁—理”、以理释仁的本体诠释路径、天理论仁学的思想史意义等。 |
| 关键词: | 朱子学 朱熹 以理释仁 |
内容
仁学是儒家的核心思想,故而也成为宋儒建构理学的核心范畴。在当代学者对儒家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论著中,仁学一直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如陈来先生的近著《仁学本体论》,就是一部希望以仁学本体论的建构,响应当代哲学家李泽厚提出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的重大期盼。可见,仁学问题在中国哲学领域的重要性。
作者本人正在从事《四书》学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自然关注《四书》学核心思想的仁学在中国思想历史过程中的演变和发展,特别关注宋儒如何通过对《四书》的经典诠释,完成了“仁”本体化的哲学建构。本文重点探讨朱子的理释仁,考察他如何通过合经典诠释和本体诠释为一体的哲学路径,推动儒家仁学创造性发展的思想历程。
一、儒家经典诠释中的“礼—仁—理”
儒学的形成演变过程漫长,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将中国古代儒学发展过程做一个大的概括,将其简缩为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礼(周公)—仁(孔子)—理(朱熹)。三代先王及周公完成的礼乐制度是中国儒教文明的基础,孔子及其早期儒学创建的仁道精神则是儒学的成型,而宋儒及朱熹完成的天理论却是古典儒学的最高形态。
殷周之际,历史发生巨大变迁,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而创造了礼乐制度文明,《六经》就是礼乐文明的经典文献。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孔子以礼归仁而创造了仁义道德的精神文明,早期儒家诸子著作则是仁义道德的经典文献。从春秋战国到汉晋隋唐时期,记载上古典章制度的《六经》之学一直是经典体系的主体,而早期儒家的著作则只是诠释《六经》的传记之学。所以,汉唐时期儒学、儒教的思想文化被合称为“周孔之道”。“周公”创造的典章制度之“礼”才是主体,是能够设置“博士”的专门之学,而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学术的著作均只是诠释《六经》的传记之学。这样,在汉唐经学体系中,“仁”其实是依附“礼”的。“周孔之道”中“周”是主,“孔”是从。
唐宋之际,历史再次发生巨大变迁,表达“封建贵族”“士族门第”精神的礼教秩序不断受到冲击,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学体系和学术教育制度受到普遍怀疑。代之而起的是“白衣秀才”身份的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崛起,他们追求、突显一种文化主体性的仁义精神及其相关的义理之学,以早期儒家诸子之学为主体而创造了《四书》的新经学体系。两宋以后的儒学被合称为“孔孟之道”。“孔孟之道”的儒学核心思想已经从“礼仪”“文章”转移到“仁义”“心性”。“孔孟之道”其实是肯定儒家诸子之学已经成为儒家学术的主体,同时也是强调儒家诸子之学已经逐渐成为儒家文明的主体。
历史上的儒学先后曾被称为“周孔之教”“孔孟之道”,这两个不同称呼其实源于儒学在经历“礼—仁—理”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思想重心的转移。早期儒家的“礼—仁”建构的结果,到汉唐时期形成了以建构国家礼乐制度为重心的“周孔之教”;而宋儒建构、完成的《四书》学思想体系,确立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脉络,才形成了以仁义精神为重心的“孔孟之道”。而且,宋儒建构的《四书》学,不仅仅确立了仁义道德的“孔孟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学术重心,更加重要的是,朱熹将《四书》学纳入到天理论的哲学体系与信仰体系中去,从而将儒学史上“礼—仁—理”的历史演变与时间过程,化为一种以“天理”统摄“礼—仁”的逻辑体系与空间结构。
所以,宋学兴起是儒学史的一个重大演变和发展,在原典的《论语》《子思子》《孟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其中的核心价值与学术重心;而在宋儒建构的《四书》学思想体系中,“理”终于成为整个新经典体系的核心价值与学术重心。本来,在早期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礼”与“仁”均是十分重要的核心范畴,而且两者又是相互规定和诠释的关系。但是,宋儒在诠释《四书》时,将孔孟著作中的礼、仁均以一个“理”来概括,最终以“理”来统摄礼、仁。我们发现,先秦诸子只是偶然讲到的“理”,宋儒则将其提升、发展为一个普遍的、形而上意义的核心范畴。早期儒家倡导仁、礼是作为人伦关系中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宋儒进一步将其抽象化、普遍化为“理”。一方面,宋儒将周公之礼抽象化、普遍化为“理”,朱熹在注解《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一章时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①宋儒反复强调,他们所说的“理”,其实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体现为“制度品节之可见”“人事之仪则”的“礼”。另一方面,宋儒也将孔子之“仁”抽象化、普遍化为“理”,朱熹解《论语·颜渊》时说:“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②其实,宋儒诠释的《四书》伦理道德规范不仅仅是礼与仁,他们认为孔子提出的所有伦理道德均是“理”。朱熹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之规范和准则,均看作是人伦日用不得不遵循的“理”。他在诠释《孟子》性善论时说:“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①可见,早期儒家提出来的仁、义、礼、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宋儒统统归之于“理”。
在宋儒那里,“理”不仅仅是人文之理,同时还是自然之理,意义已经拓展到自然天地,成为既有普遍性又具必然性的形而上意义的范畴。朱熹在《大学或问》中提出,“理”不仅仅是人类社会,还是天地自然的普遍性、必然性法则,他说:“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②这样,“理”也因此成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君臣父子、人伦日用等一切自然的、社会中事物的普遍本质与法则。为了说明统一的“理”和社会、自然中具体之理的关系,朱熹还提出“理一分殊”的思想。这样,他不仅将礼、仁的人文之理统一到“一理”之中,还将自然之理也统一到“一理”之中。朱熹在解《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③根据朱熹的“理一分殊”原理,主宰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的均是同一个“理”,所以称之为“理一”,而早期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却是“万殊”之理。同时,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还可以进一步分为更细致的“万殊”之理,如“礼”就包含着无数细致的具体节目。
由此可见,宋儒通过诠释《四书》而建构的新仁学,完成了以“理”为中心的知识、价值与信仰的重建。他们通过一系列哲学化的思辨,将“仁”作了形而上的提升,使原典儒学中作为人格精神的仁,重新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永恒的宇宙意义,纳入到一个更加具有哲学性、系统性的天理论体系之中。所以,宋儒的《四书》学,已经大大不同于早期儒家诸子学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如果说早期儒家的《四书》还是以“仁”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话,宋儒的《四书》学则已经建构了以“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和信仰体系。
二、以理释仁的本体诠释路径
宋儒《四书》学的建立,是儒学史的一个重大转型,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型。宋儒将“仁”纳入到以“理”为中心的思想系统,并将其提升为一种普遍、永恒的宇宙精神,确实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事实:孔子提出的仁爱思想已经被宋儒理学化。如果说“礼”“仁”是原典儒学的核心范畴的话,那么,理学化仁学的建立,则代表了新儒学的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和思想体系。
在早期儒学那里,“仁”主要是一种爱人情感和道德情操,而到了理学体系中,“仁”的意义逐渐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仁的意义变化,主要是通过以理释仁的本体论诠释路径而实现的。
其一,仁爱情感的理性化。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仁”明显是一种“情”与“理”相结合的道德观念,也就是李泽厚先生经常讲到的“情理结构”①。早期儒家反复强调:一方面“仁”是一种“爱人”“恻隐”的情感,这一种情感是先天的、自然的;另一方面“仁”又是做人必须遵循的道理和原则,体现为人与人之间能够具有推己及人的情感推理,即一种推己及人的理性。在《四书》体系中,这一推己及人的情感推理的叫法不太一样。《论语》强调这一种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是“忠恕之道”,《大学》称之为“絜矩之道”,而《孟子》则将其看作是直觉性的“恻隐之心”和推己及人。早期儒家主张以人人都有的情感来推导出自己做人的道德选择,在《四书》原典中,“仁”作为一种“情理结构”,往往是以“情”为本,“情”是“仁”的存在基础和主导因素。人为什么会有仁爱?仁爱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早期儒家肯定仁爱主要是一种人与人相爱的自然情感,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孔子为什么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因为孝悌之爱的情感源于自己的血缘关系,这是一种最自然、最强烈、最真实的爱。可见,在早期儒家的仁爱“情理结构”中,作为仁爱的本源、主导因素是“情”而不是“理”。
但是,宋儒一旦将仁爱纳入到天理论的理学体系之中,“天理”就成为统摄仁义礼智的最高存在,从而改造了“仁”的“情理结构”,不是“情”而是“理”已经成为这一“情理结构”的存在基础和主导因素。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这样解释仁:“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②既然仁是“爱之理”,“理”已经成为定义仁的主词,“情理结构”的存在基础和主导因素就是理而不是情。那么,一个人遵循仁道原则,其道德源泉、精神动力就是来自于对“天理”必须遵循的道德理性,而不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情感、自然本性等因素。所以,朱熹强调:“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③一个人之所以服从仁道不是由于自己的内心情感、自然天性,而是因为他不得不遵循天理的理性原则,即所谓“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他不得不以“天理”作为自己的道德意志去战胜自己的感情欲望。所以,在朱熹新“仁学”的“情理结构”中,“理”作为依据和主导,贯穿、主宰了“情”。这是新仁学的一个重大变化。
其二,仁义之爱的普遍化。
在早期儒学中,“仁”完全是一种为人之道,而且首先是孝悌的爱亲之道。孔子及其早期儒家学者反复强调“仁者,人也”①,建立了一个人道论的仁学思想。儒家贵仁,“仁”一方面涉及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相亲相爱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一种亲密关系的建立依赖于个体人格的独立和自觉。所以,儒家人道论的仁学,体现出人之为人的三个主体人格的精神要素,即仁的情感、仁的理性、仁的意志。可见,“仁”完全是以父子兄弟的爱亲为出发点,通过主体人格精神的开展,进而广泛地建立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
宋儒虽然也强调主体人格精神的开展,但是他们并不把仁的情感、仁的理性、仁的意志局限于建立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而是将主体仁心作了极大的拓展,从仁民拓展到爱物,从人道推广到天道。所以,宋儒心目中的“仁”,不仅仅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还体现为人与天地自然的一体不分,特别还体现为宇宙自然的生生不息。正如二程所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②程颢特别表彰张载《西铭》“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③,张载《西铭》表达的恰恰是仁道原则的普遍化,即所谓:“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④这是一种以亲情为基础、但是又完全超越了亲情的仁爱,已经从仁民拓展到爱物,从人道推广到天道。宋儒统合人道与天道,提升人道仁学的天道意义,将《四书》“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与《周易》的“天地之大德”的天道统一起来。这样,在宋儒的仁学体系中,仁爱精神已经超越人道,获得了一种普遍化的天道意义。
其三,仁道原则的形上化。
在先秦儒家那里,仁爱是一种生活日用的道德情感,仁义是一种人伦日用的道德要求,它们均是形而下的现象存在。《易传·系辞》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是早期儒家只是将“天道”看作是“形而上者”,而将“仁”纳入到对“天地之大德”的仿效、追随,“仁爱”只不过是伟大天道的显现与功用(“显诸仁,藏诸用”),是“与天地相似”“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一种具体表现。
但是,宋儒大大提升了“仁道”的形上意义,他们不仅将仁爱情感理性化、仁义原则普遍化,而且进一步将仁道观念形上化。这样,宋儒强调作为“爱之理”的仁,不仅是从爱人的情感转化为爱人的理性,同时开始超越世俗而进入到形上意义的追求。特别是宋儒强调仁是“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仁已经从一般的道德意义转化为形上意义的“仁之体”。程颢在一篇专门讨论仁学的文章中说道:“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①程颢所讲的“识仁”,就是指“仁之道”“仁之理”,在宋儒的思想体系中,此“仁之道”“仁之理”均是形而上者。
由此可见,宋儒强调仁是“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仁已经从一般的道德意义转化为形上意义的“仁之体”。特别是朱熹的仁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体用之辨诠释仁学。这一个作为统一天道和人道的形而上之“体”是什么?就是“理”,仁之理。他认为只有仁之理才可以体现为“天地生物之心”,因为只有“理”才是一种无形无象的形而上之体。作为一个宇宙间最普遍的“理”,它总是充盈于宇宙天地、万事万物、人生日用之中的。可见,以理释仁,使仁的理性提升为形而上的天理,最终完成了仁的本体论诠释。
三、天理论仁学的思想史意义
宋儒将原始儒学的“礼—仁”纳入到天理论体系,导致儒学的学术体系、思想体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应该如何理解、评价这一思想改变?这里,我们主要是从儒学史演变发展的评价尺度,对宋儒的天理化仁学作一粗略探讨。
从总体而言,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宋儒的天理化仁学在儒学史上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表达了儒学演变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升与哲学建构。宋儒天理化仁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强化、提升了儒家仁学的哲学意义。当然,儒学本来就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全面涉及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文明体系,它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全体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信仰、道德、审美、政治、法律、经济、教育、习俗等各个方面。因此,儒学是涉及不同学科领域的全体大用之学,是集中代表中华文明、东亚文明知识体系的综合性学科。②虽然儒学并不能够等同于哲学,但是哲学确是儒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知识维度、精神维度。因为儒学是一门全体大用之学,而深入探讨形而上之体与形而下之用关系的哲学化儒学,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综合性思想维度。宋儒
推动了仁学的重要发展,使仁爱情感理性化、仁义原则普遍化、仁道观念形上化,最终推动了仁学的哲学化。从价值体系来说,仁、仁义并没有发生重要变化,但是宋儒已经将这一套价值体系奠定在坚实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宋儒建构的新儒学,是一种包括理气论、道器论、理一分殊论、心统性情论、格物致知论的哲学体系。应该说,宋儒将原始儒学的礼、仁,统统纳入到理学体系之中,大大提升了儒家的哲学意义。
其次,宋儒天理化仁学的重要贡献,就是强化、提升了儒家仁学的信仰功能。周公制礼作乐而创造礼乐文明,但是礼乐制度必须依据于天神、祖宗的宗教信仰;孔子以礼归仁而创造了道德文明,从而淡化了三代的宗教信仰,而强化了道德主体意识。但是,儒家礼乐文明不能够仅仅建立在这一道德主体意识的基础上,还必须依托在终极实体的信仰基础上。所以,两汉儒家通过回归上古三代的方式,建立一种对天道、天神信仰的文化体系,但是这一神秘化信仰逐渐受到具有理性精神的儒家士大夫的怀疑。所以,宋儒需要重建一种理性化的道德信仰,他们不仅将仁义与天理连接起来,而且将仁、理归结为一种最高意志、最终目的的“天理”“天地之心”,以强化仁学的信仰功能,解决仁义道德的终极意义问题。所以,宋儒强调仁义不仅仅是一种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道德原则,而是具有更加神圣的信仰意义。宋儒将“仁”看作是“天地之心”,他们论说天理、仁的目的性,如《朱子语类》载: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近思之,切谓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天地曷尝有思虑来。然其所以‘四时行,百物生’者,盖以其会当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为天地之道。”……“如此则《易》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又如何?如公所说,只说得他无心处尔。若果无心,则须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他又却自定。”①
朱熹认为“仁”“天心”既是无心的,没有人格神的那种思虑营为;又是有心的,体现着宇宙精神“自定”的目的。此即如朱熹所说:“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灵,但不如人恁地思虑。”②仁道经过这一种“天理”“天地之心”的超验化提升,就具有更加神圣性的信仰意义。朱熹要求个人由外到内均要保持对“仁义”等天理的虔敬态度和信仰精神,保存“对越上帝”敬畏心理,即所谓“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信仰的要求,这一种要求其实是强化了儒家仁学的信仰功能。
可见,宋儒以理释仁,使早期儒家仁学的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宋儒不仅使儒家的价值意义能够奠定在坚实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同时还使得原来的道德之仁具有了更加神圣的信仰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15AZD032)
(原载《中国文化》2020年第1期,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作者本人正在从事《四书》学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自然关注《四书》学核心思想的仁学在中国思想历史过程中的演变和发展,特别关注宋儒如何通过对《四书》的经典诠释,完成了“仁”本体化的哲学建构。本文重点探讨朱子的理释仁,考察他如何通过合经典诠释和本体诠释为一体的哲学路径,推动儒家仁学创造性发展的思想历程。
一、儒家经典诠释中的“礼—仁—理”
儒学的形成演变过程漫长,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将中国古代儒学发展过程做一个大的概括,将其简缩为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礼(周公)—仁(孔子)—理(朱熹)。三代先王及周公完成的礼乐制度是中国儒教文明的基础,孔子及其早期儒学创建的仁道精神则是儒学的成型,而宋儒及朱熹完成的天理论却是古典儒学的最高形态。
殷周之际,历史发生巨大变迁,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而创造了礼乐制度文明,《六经》就是礼乐文明的经典文献。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孔子以礼归仁而创造了仁义道德的精神文明,早期儒家诸子著作则是仁义道德的经典文献。从春秋战国到汉晋隋唐时期,记载上古典章制度的《六经》之学一直是经典体系的主体,而早期儒家的著作则只是诠释《六经》的传记之学。所以,汉唐时期儒学、儒教的思想文化被合称为“周孔之道”。“周公”创造的典章制度之“礼”才是主体,是能够设置“博士”的专门之学,而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学术的著作均只是诠释《六经》的传记之学。这样,在汉唐经学体系中,“仁”其实是依附“礼”的。“周孔之道”中“周”是主,“孔”是从。
唐宋之际,历史再次发生巨大变迁,表达“封建贵族”“士族门第”精神的礼教秩序不断受到冲击,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学体系和学术教育制度受到普遍怀疑。代之而起的是“白衣秀才”身份的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崛起,他们追求、突显一种文化主体性的仁义精神及其相关的义理之学,以早期儒家诸子之学为主体而创造了《四书》的新经学体系。两宋以后的儒学被合称为“孔孟之道”。“孔孟之道”的儒学核心思想已经从“礼仪”“文章”转移到“仁义”“心性”。“孔孟之道”其实是肯定儒家诸子之学已经成为儒家学术的主体,同时也是强调儒家诸子之学已经逐渐成为儒家文明的主体。
历史上的儒学先后曾被称为“周孔之教”“孔孟之道”,这两个不同称呼其实源于儒学在经历“礼—仁—理”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思想重心的转移。早期儒家的“礼—仁”建构的结果,到汉唐时期形成了以建构国家礼乐制度为重心的“周孔之教”;而宋儒建构、完成的《四书》学思想体系,确立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脉络,才形成了以仁义精神为重心的“孔孟之道”。而且,宋儒建构的《四书》学,不仅仅确立了仁义道德的“孔孟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学术重心,更加重要的是,朱熹将《四书》学纳入到天理论的哲学体系与信仰体系中去,从而将儒学史上“礼—仁—理”的历史演变与时间过程,化为一种以“天理”统摄“礼—仁”的逻辑体系与空间结构。
所以,宋学兴起是儒学史的一个重大演变和发展,在原典的《论语》《子思子》《孟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其中的核心价值与学术重心;而在宋儒建构的《四书》学思想体系中,“理”终于成为整个新经典体系的核心价值与学术重心。本来,在早期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礼”与“仁”均是十分重要的核心范畴,而且两者又是相互规定和诠释的关系。但是,宋儒在诠释《四书》时,将孔孟著作中的礼、仁均以一个“理”来概括,最终以“理”来统摄礼、仁。我们发现,先秦诸子只是偶然讲到的“理”,宋儒则将其提升、发展为一个普遍的、形而上意义的核心范畴。早期儒家倡导仁、礼是作为人伦关系中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宋儒进一步将其抽象化、普遍化为“理”。一方面,宋儒将周公之礼抽象化、普遍化为“理”,朱熹在注解《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一章时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①宋儒反复强调,他们所说的“理”,其实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体现为“制度品节之可见”“人事之仪则”的“礼”。另一方面,宋儒也将孔子之“仁”抽象化、普遍化为“理”,朱熹解《论语·颜渊》时说:“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②其实,宋儒诠释的《四书》伦理道德规范不仅仅是礼与仁,他们认为孔子提出的所有伦理道德均是“理”。朱熹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之规范和准则,均看作是人伦日用不得不遵循的“理”。他在诠释《孟子》性善论时说:“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①可见,早期儒家提出来的仁、义、礼、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宋儒统统归之于“理”。
在宋儒那里,“理”不仅仅是人文之理,同时还是自然之理,意义已经拓展到自然天地,成为既有普遍性又具必然性的形而上意义的范畴。朱熹在《大学或问》中提出,“理”不仅仅是人类社会,还是天地自然的普遍性、必然性法则,他说:“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②这样,“理”也因此成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君臣父子、人伦日用等一切自然的、社会中事物的普遍本质与法则。为了说明统一的“理”和社会、自然中具体之理的关系,朱熹还提出“理一分殊”的思想。这样,他不仅将礼、仁的人文之理统一到“一理”之中,还将自然之理也统一到“一理”之中。朱熹在解《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③根据朱熹的“理一分殊”原理,主宰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的均是同一个“理”,所以称之为“理一”,而早期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却是“万殊”之理。同时,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还可以进一步分为更细致的“万殊”之理,如“礼”就包含着无数细致的具体节目。
由此可见,宋儒通过诠释《四书》而建构的新仁学,完成了以“理”为中心的知识、价值与信仰的重建。他们通过一系列哲学化的思辨,将“仁”作了形而上的提升,使原典儒学中作为人格精神的仁,重新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永恒的宇宙意义,纳入到一个更加具有哲学性、系统性的天理论体系之中。所以,宋儒的《四书》学,已经大大不同于早期儒家诸子学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如果说早期儒家的《四书》还是以“仁”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话,宋儒的《四书》学则已经建构了以“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和信仰体系。
二、以理释仁的本体诠释路径
宋儒《四书》学的建立,是儒学史的一个重大转型,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型。宋儒将“仁”纳入到以“理”为中心的思想系统,并将其提升为一种普遍、永恒的宇宙精神,确实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事实:孔子提出的仁爱思想已经被宋儒理学化。如果说“礼”“仁”是原典儒学的核心范畴的话,那么,理学化仁学的建立,则代表了新儒学的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和思想体系。
在早期儒学那里,“仁”主要是一种爱人情感和道德情操,而到了理学体系中,“仁”的意义逐渐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仁的意义变化,主要是通过以理释仁的本体论诠释路径而实现的。
其一,仁爱情感的理性化。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仁”明显是一种“情”与“理”相结合的道德观念,也就是李泽厚先生经常讲到的“情理结构”①。早期儒家反复强调:一方面“仁”是一种“爱人”“恻隐”的情感,这一种情感是先天的、自然的;另一方面“仁”又是做人必须遵循的道理和原则,体现为人与人之间能够具有推己及人的情感推理,即一种推己及人的理性。在《四书》体系中,这一推己及人的情感推理的叫法不太一样。《论语》强调这一种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是“忠恕之道”,《大学》称之为“絜矩之道”,而《孟子》则将其看作是直觉性的“恻隐之心”和推己及人。早期儒家主张以人人都有的情感来推导出自己做人的道德选择,在《四书》原典中,“仁”作为一种“情理结构”,往往是以“情”为本,“情”是“仁”的存在基础和主导因素。人为什么会有仁爱?仁爱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早期儒家肯定仁爱主要是一种人与人相爱的自然情感,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孔子为什么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因为孝悌之爱的情感源于自己的血缘关系,这是一种最自然、最强烈、最真实的爱。可见,在早期儒家的仁爱“情理结构”中,作为仁爱的本源、主导因素是“情”而不是“理”。
但是,宋儒一旦将仁爱纳入到天理论的理学体系之中,“天理”就成为统摄仁义礼智的最高存在,从而改造了“仁”的“情理结构”,不是“情”而是“理”已经成为这一“情理结构”的存在基础和主导因素。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这样解释仁:“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②既然仁是“爱之理”,“理”已经成为定义仁的主词,“情理结构”的存在基础和主导因素就是理而不是情。那么,一个人遵循仁道原则,其道德源泉、精神动力就是来自于对“天理”必须遵循的道德理性,而不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情感、自然本性等因素。所以,朱熹强调:“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③一个人之所以服从仁道不是由于自己的内心情感、自然天性,而是因为他不得不遵循天理的理性原则,即所谓“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他不得不以“天理”作为自己的道德意志去战胜自己的感情欲望。所以,在朱熹新“仁学”的“情理结构”中,“理”作为依据和主导,贯穿、主宰了“情”。这是新仁学的一个重大变化。
其二,仁义之爱的普遍化。
在早期儒学中,“仁”完全是一种为人之道,而且首先是孝悌的爱亲之道。孔子及其早期儒家学者反复强调“仁者,人也”①,建立了一个人道论的仁学思想。儒家贵仁,“仁”一方面涉及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相亲相爱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一种亲密关系的建立依赖于个体人格的独立和自觉。所以,儒家人道论的仁学,体现出人之为人的三个主体人格的精神要素,即仁的情感、仁的理性、仁的意志。可见,“仁”完全是以父子兄弟的爱亲为出发点,通过主体人格精神的开展,进而广泛地建立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
宋儒虽然也强调主体人格精神的开展,但是他们并不把仁的情感、仁的理性、仁的意志局限于建立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而是将主体仁心作了极大的拓展,从仁民拓展到爱物,从人道推广到天道。所以,宋儒心目中的“仁”,不仅仅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还体现为人与天地自然的一体不分,特别还体现为宇宙自然的生生不息。正如二程所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②程颢特别表彰张载《西铭》“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③,张载《西铭》表达的恰恰是仁道原则的普遍化,即所谓:“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④这是一种以亲情为基础、但是又完全超越了亲情的仁爱,已经从仁民拓展到爱物,从人道推广到天道。宋儒统合人道与天道,提升人道仁学的天道意义,将《四书》“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与《周易》的“天地之大德”的天道统一起来。这样,在宋儒的仁学体系中,仁爱精神已经超越人道,获得了一种普遍化的天道意义。
其三,仁道原则的形上化。
在先秦儒家那里,仁爱是一种生活日用的道德情感,仁义是一种人伦日用的道德要求,它们均是形而下的现象存在。《易传·系辞》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是早期儒家只是将“天道”看作是“形而上者”,而将“仁”纳入到对“天地之大德”的仿效、追随,“仁爱”只不过是伟大天道的显现与功用(“显诸仁,藏诸用”),是“与天地相似”“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一种具体表现。
但是,宋儒大大提升了“仁道”的形上意义,他们不仅将仁爱情感理性化、仁义原则普遍化,而且进一步将仁道观念形上化。这样,宋儒强调作为“爱之理”的仁,不仅是从爱人的情感转化为爱人的理性,同时开始超越世俗而进入到形上意义的追求。特别是宋儒强调仁是“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仁已经从一般的道德意义转化为形上意义的“仁之体”。程颢在一篇专门讨论仁学的文章中说道:“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①程颢所讲的“识仁”,就是指“仁之道”“仁之理”,在宋儒的思想体系中,此“仁之道”“仁之理”均是形而上者。
由此可见,宋儒强调仁是“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仁已经从一般的道德意义转化为形上意义的“仁之体”。特别是朱熹的仁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体用之辨诠释仁学。这一个作为统一天道和人道的形而上之“体”是什么?就是“理”,仁之理。他认为只有仁之理才可以体现为“天地生物之心”,因为只有“理”才是一种无形无象的形而上之体。作为一个宇宙间最普遍的“理”,它总是充盈于宇宙天地、万事万物、人生日用之中的。可见,以理释仁,使仁的理性提升为形而上的天理,最终完成了仁的本体论诠释。
三、天理论仁学的思想史意义
宋儒将原始儒学的“礼—仁”纳入到天理论体系,导致儒学的学术体系、思想体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应该如何理解、评价这一思想改变?这里,我们主要是从儒学史演变发展的评价尺度,对宋儒的天理化仁学作一粗略探讨。
从总体而言,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宋儒的天理化仁学在儒学史上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表达了儒学演变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升与哲学建构。宋儒天理化仁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强化、提升了儒家仁学的哲学意义。当然,儒学本来就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全面涉及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文明体系,它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全体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信仰、道德、审美、政治、法律、经济、教育、习俗等各个方面。因此,儒学是涉及不同学科领域的全体大用之学,是集中代表中华文明、东亚文明知识体系的综合性学科。②虽然儒学并不能够等同于哲学,但是哲学确是儒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知识维度、精神维度。因为儒学是一门全体大用之学,而深入探讨形而上之体与形而下之用关系的哲学化儒学,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综合性思想维度。宋儒
推动了仁学的重要发展,使仁爱情感理性化、仁义原则普遍化、仁道观念形上化,最终推动了仁学的哲学化。从价值体系来说,仁、仁义并没有发生重要变化,但是宋儒已经将这一套价值体系奠定在坚实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宋儒建构的新儒学,是一种包括理气论、道器论、理一分殊论、心统性情论、格物致知论的哲学体系。应该说,宋儒将原始儒学的礼、仁,统统纳入到理学体系之中,大大提升了儒家的哲学意义。
其次,宋儒天理化仁学的重要贡献,就是强化、提升了儒家仁学的信仰功能。周公制礼作乐而创造礼乐文明,但是礼乐制度必须依据于天神、祖宗的宗教信仰;孔子以礼归仁而创造了道德文明,从而淡化了三代的宗教信仰,而强化了道德主体意识。但是,儒家礼乐文明不能够仅仅建立在这一道德主体意识的基础上,还必须依托在终极实体的信仰基础上。所以,两汉儒家通过回归上古三代的方式,建立一种对天道、天神信仰的文化体系,但是这一神秘化信仰逐渐受到具有理性精神的儒家士大夫的怀疑。所以,宋儒需要重建一种理性化的道德信仰,他们不仅将仁义与天理连接起来,而且将仁、理归结为一种最高意志、最终目的的“天理”“天地之心”,以强化仁学的信仰功能,解决仁义道德的终极意义问题。所以,宋儒强调仁义不仅仅是一种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道德原则,而是具有更加神圣的信仰意义。宋儒将“仁”看作是“天地之心”,他们论说天理、仁的目的性,如《朱子语类》载: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近思之,切谓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天地曷尝有思虑来。然其所以‘四时行,百物生’者,盖以其会当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为天地之道。”……“如此则《易》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又如何?如公所说,只说得他无心处尔。若果无心,则须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他又却自定。”①
朱熹认为“仁”“天心”既是无心的,没有人格神的那种思虑营为;又是有心的,体现着宇宙精神“自定”的目的。此即如朱熹所说:“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灵,但不如人恁地思虑。”②仁道经过这一种“天理”“天地之心”的超验化提升,就具有更加神圣性的信仰意义。朱熹要求个人由外到内均要保持对“仁义”等天理的虔敬态度和信仰精神,保存“对越上帝”敬畏心理,即所谓“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信仰的要求,这一种要求其实是强化了儒家仁学的信仰功能。
可见,宋儒以理释仁,使早期儒家仁学的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宋儒不仅使儒家的价值意义能够奠定在坚实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同时还使得原来的道德之仁具有了更加神圣的信仰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15AZD032)
(原载《中国文化》2020年第1期,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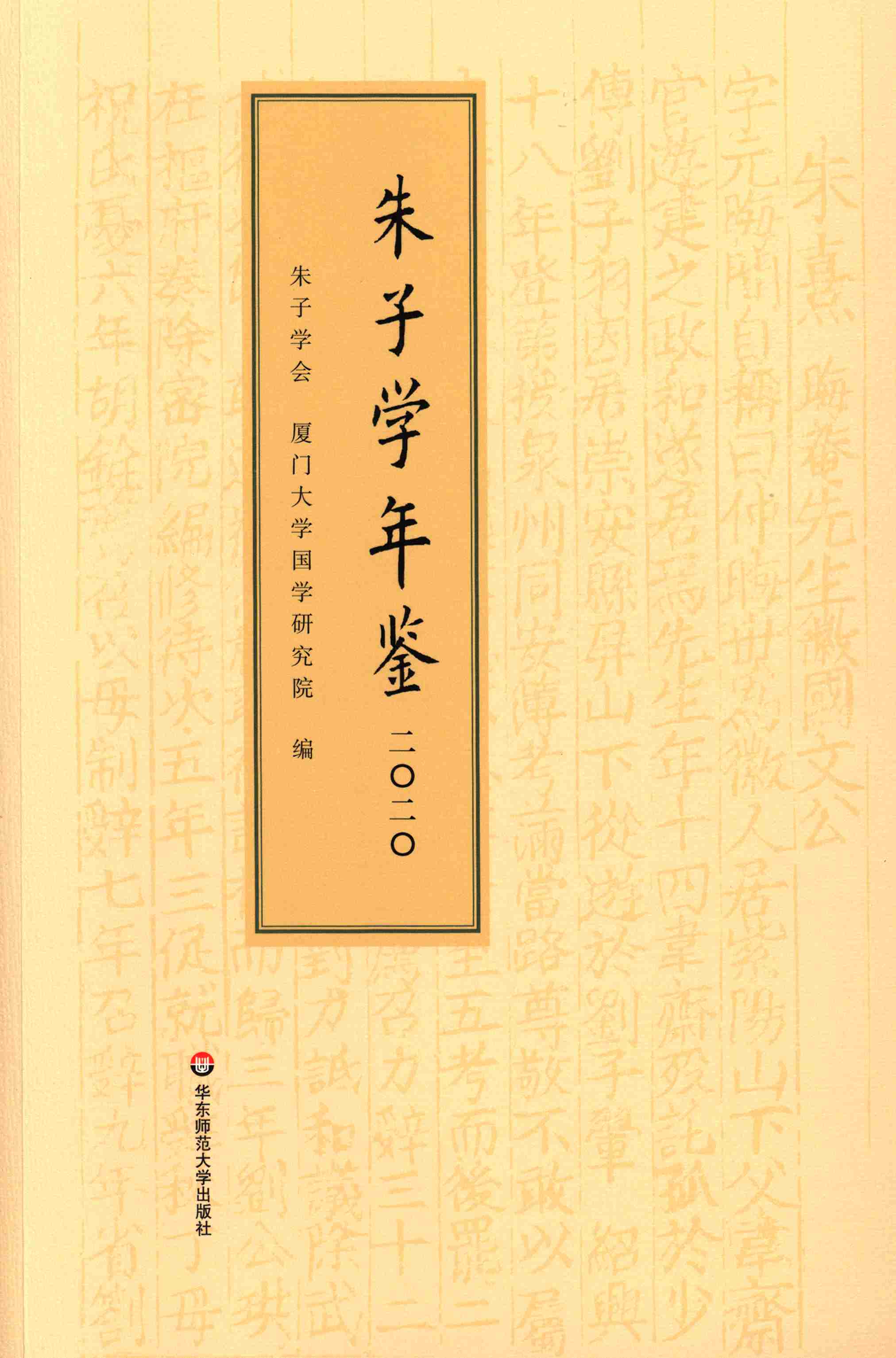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0》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以礼释仁的路径和意义》《2020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