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朱子以“断制”论义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0》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869 |
| 颗粒名称: | 五、朱子以“断制”论义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 |
| 页码: | 033-038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更多地使用“断制”来解释义的价值特性。断制指的是断决裁制的简化表达,强调在面对恶的时候要采取果断坚决的态度,对恶行进行坚决的制止。朱子经常将断制与慈惠相对来讨论,这显示了他对于义的理解。这种对义的指示可以称之为价值特性或价值意向。 |
| 关键词: | 朱子 断制 裁制 |
内容
朱子更多用“断制”来解释义的价值特性。按北宋儒学已有此种解释的例子。如李觏:
温厚而广爱者命之曰仁,断决而从宜者命之曰义。⑤现在来看《朱子语类》:
如慈爱底人少断制,断制之人多残忍。盖仁多,便遮了义;义多,便遮了那仁。⑥
李问:“世间有一种人,慈惠温厚,而于义不足,作事无断制,是如何?”
曰:“人生得多般样,这个便全是气禀。……”①
断制二字应该是断决裁制的简化表达,强调面对恶要态度决然,除恶要断然施行。朱子每以断制与慈惠对言,可见其意。这种对义的指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价值特性或价值意向。
朱子认为,能不能有断制,与人的性格性情有关,而性格来自气禀。如能断制来自金气禀受较多而致。
性有偏者。如得木气多者,仁较多;金气多者,义较多。②
却是汉儒解“天命之谓性”,云“木神仁,金神义”等语,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学者要体会亲切。③
朱子论义之断制:
程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道则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义则吾心之能断制者,所用以处此理者也。④
义未有羞恶之心,只是个断制底心。惟是先有这物事在里面,但随所感触,便自是发出来。⑤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朱子是从心上来讲断制之义,所以强调义是“吾心之能断制者”,“只是个断制底心”。又如:
问:“孟子以恻隐为仁之端,羞恶为义之端。周子曰:‘爱曰仁,宜曰义。’然以其存于心者而言,则恻隐与爱固为仁心之发。然羞恶乃就耻不义上反说,而非直指义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说。不知义在心上,其体段如何。”曰:“义之在心,乃是决裂果断者也。”⑥
这里也可以看出,义在心上,义之在心,都重在从心上说义,这与宜在事上说不同。
朱子论义另一个特点,正如其论仁一样,是把义的讨论置于宇宙论框架之中,使义具有大化流行论的意义。如:
“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冬则生意之藏也。自四而两,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又曰:“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而成终;犹元为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
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故不贞则无以为元也。”又“贞而不固,则非贞。贞,如板筑之有干,不贞则无以为元”。①
于是,朱子论义,常常不能脱开对《文言》“利者义之和”的讨论: “利者义之和。”义是个有界分断制底物事,疑于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为和也。②
问“利物足以和义”。曰:“义断是非,别曲直,近于不和。然是非曲直辨,则便是利,此乃是和处也。”③
义自是个断制底气象,有凛然不可犯处,似不和矣,其实却和。若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义;不义则不和矣。④
义是其间物来能应,事至能断者是。⑤
因为义有判分、断割之意,故一般认为义与和无关,而是与和相反的。但朱子坚持,义表面上似乎不和,其实是和。因为使事物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各得其分,正是为和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问《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长’以下四句,说天德之自然。‘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以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元只是善之长,万物生理皆始于此,众善百行皆统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为仁。亨是嘉之会。此句自来说者多不明。嘉,美也;会,犹齐也。嘉会,众美之会,犹言齐好也。春天发生万物,未大故齐。到夏时,洪纤高下,各各畅茂。盖春方生育,至此乃无一物不畅茂。其在人,则‘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齐到恰好处,所谓动容周旋皆中礼,故于时为夏,于人为礼。利者,为义之和。万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无不得宜,故于时为秋,于人为义。贞者乃事之干。万物至此,收敛成实,事理至此,无不的正,故于时为冬,于人为智。此天德之自然。”⑥
这里对“利者义之和”的解释主要也是从得宜立论,认为各遂其性即是各个得宜,故可谓义之和。
朱子接着说:
“其在君子所当从事于此者,则必‘体仁乃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个字,极有力。体者,以仁为体,仁为我之骨,我以之为体。仁皆从我发出,故无物不在所爱,所以能长人。‘嘉会足以合礼’者,言须是美其所会也。欲其所会之美,当美其所会。盖其厚薄亲疏、尊卑小大相接之体,各有节文,无不中节,即所会皆美,所以能合于礼也。‘利物足以和义’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则义无不和。盖义是断制裁割底物,若似不和。然惟义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无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为义之和也。苏氏说‘利者义之和’,却说义惨杀而不和,不可徒义,须着些利则和。如此,则义是一物,利又是一物;义是苦物,恐人嫌,须着些利令甜,此不知义之言也。义中自有利,使人而皆义,则不遗其亲,不后其君,自无不利,非和而何?‘贞固足以干事。’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为事之干。干事,言事之所依以立,盖正而能固,万事依此而立。在人则是智,至灵至明,是是非非,确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瞒,所以能立事也。干,如板筑之有桢干。今人筑墙,必立一木于土中为骨,俗谓之‘夜叉木’,无此则不可筑。横曰桢,直曰干。无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紧固确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则谓之‘正’也。”①
这是说,物物各得其利便是义,便是义之和。义的价值特性是断制截割,但其作用能使事物各得其所宜。这就把义的特性和其作用作了区分。
朱子晚年的《玉山讲义》:
且道如何说个“仁义”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只“仁义礼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于此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若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①
本文第二节已经显示出,自战国秦汉以来,便常常把仁和义对举,标示出它们各自的价值特性与价值意向。朱子亦然,“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便是他代表性的说法②,并把四德的价值特性与价值意向归为性之本体,即性理。把义的分析用本体与其发用来展开,用已发未发的分析来说,义是断制截割的未发,断制截割是义的已发。所谓“××底道理”,就是××的理,在心性论上,就是指作为未发的本性的理。义是裁制断割的理,仁是温和慈爱的理,仁之发是温和慈爱,义之发是裁制断割。这是朱子哲学性情已发未发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以仁义礼智为性理包含了以四德为德性的思想。不过就论义而言,朱子更关注的似乎是义在由德性展开为德行过程中,义心的特点,即“义在心上”的特点。关于《玉山讲义》这里所涉及的四德说的宇宙论面向,我们会在最后一节一并论及。
朱子关于仁义价值特性的此类说法,也曾受到张九成子韶“仁义说”的影响:
某旧见张子韶有个文字论仁义之实云:“当其事亲之时,有以见其温然如春之意,便是仁;当其从兄之际,有以见其肃然如秋之意,便是义。”某尝对其说,“古人固有习而不察,如今却是略略地习,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略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见某说,忽然曰:‘公适间说得好,可更说一徧看。’”③
义是个毅然说话,如利刀着物。④
义如利刀相似,都割断了许多牵绊。⑤
义如利刀相似,胸中许多劳劳攘攘,到此一齐割断了。圣贤虽千言万语,千头万项,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义,伊川言敬,都彻上彻下。⑥
“义”字如一横剑相似,凡事物到前,便两分去。“君子义以为质”,“义以为上”,“义不食也”,“义弗乘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是此义十分精熟,用便见也。①
这些说法,无论利刀、利刃、横剑,都是形容义字的割断义。都是从义的发用来讲的。
朱子甚至说:
生底意思是仁,杀底意思是义,发见会通是礼,收藏不测是智。②
按庞朴曾以杀论义,合乎朱子之说,而其论证方法是论述“宜”字本指一种祭祀之礼,此种祭祀礼是杀戮宰杀,以此证明义的原初意义与杀有关③。其实,先秦文献的以宜解义,其宜字都不是作为祭祀的宜祭。而且,从朱子的例子可以看出,“杀底意思”不是义字的字源意义,而是从东汉后起的解说中引申出来的思想义。正如生并不是仁字的原初义。所以我们并不能用后起的意义去推原字源的意义。
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再回到第一节最后提及的竹简《五行》篇中论义的思想:
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13章)④
中心辩然而正行之,直也。直而遂之,肆也。肆而不畏强圉,果也。不以小道害大道,简也。有大罪而大诛之,行也。贵贵其等尊贤,义也。(20章)⑤
不仅如此,又另用整整三章的篇幅申明简作为义的意义:“不简不行,不匿不辩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22章)“简之为言,犹练也,大而晏者也。匿之为言,犹匿匿也,小而轸者也。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强,义之方也;柔,仁之方也。……”(23章)“大而晏者,能有取焉。小而轸者,能有取焉。……”(24章)⑥
《五行》篇论义的讲法,比起先秦诸家用宜论义,在思想上更接近于汉以后对义的理解。其思想是,义是对善恶的清楚明辨(这就是辩然而直);对恶要果敢断然去除(这就是果而不畏);对罪的处置要坚持原则(这就是简行)。可见,从先秦以宜训义到汉代以裁断训义,中间有一个过渡的阶段,这就是竹简帛书《五行》篇所代表的对义的理解。可惜我们对这一点研究得还很不够。
温厚而广爱者命之曰仁,断决而从宜者命之曰义。⑤现在来看《朱子语类》:
如慈爱底人少断制,断制之人多残忍。盖仁多,便遮了义;义多,便遮了那仁。⑥
李问:“世间有一种人,慈惠温厚,而于义不足,作事无断制,是如何?”
曰:“人生得多般样,这个便全是气禀。……”①
断制二字应该是断决裁制的简化表达,强调面对恶要态度决然,除恶要断然施行。朱子每以断制与慈惠对言,可见其意。这种对义的指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价值特性或价值意向。
朱子认为,能不能有断制,与人的性格性情有关,而性格来自气禀。如能断制来自金气禀受较多而致。
性有偏者。如得木气多者,仁较多;金气多者,义较多。②
却是汉儒解“天命之谓性”,云“木神仁,金神义”等语,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学者要体会亲切。③
朱子论义之断制:
程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道则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义则吾心之能断制者,所用以处此理者也。④
义未有羞恶之心,只是个断制底心。惟是先有这物事在里面,但随所感触,便自是发出来。⑤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朱子是从心上来讲断制之义,所以强调义是“吾心之能断制者”,“只是个断制底心”。又如:
问:“孟子以恻隐为仁之端,羞恶为义之端。周子曰:‘爱曰仁,宜曰义。’然以其存于心者而言,则恻隐与爱固为仁心之发。然羞恶乃就耻不义上反说,而非直指义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说。不知义在心上,其体段如何。”曰:“义之在心,乃是决裂果断者也。”⑥
这里也可以看出,义在心上,义之在心,都重在从心上说义,这与宜在事上说不同。
朱子论义另一个特点,正如其论仁一样,是把义的讨论置于宇宙论框架之中,使义具有大化流行论的意义。如:
“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冬则生意之藏也。自四而两,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又曰:“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而成终;犹元为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
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故不贞则无以为元也。”又“贞而不固,则非贞。贞,如板筑之有干,不贞则无以为元”。①
于是,朱子论义,常常不能脱开对《文言》“利者义之和”的讨论: “利者义之和。”义是个有界分断制底物事,疑于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为和也。②
问“利物足以和义”。曰:“义断是非,别曲直,近于不和。然是非曲直辨,则便是利,此乃是和处也。”③
义自是个断制底气象,有凛然不可犯处,似不和矣,其实却和。若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义;不义则不和矣。④
义是其间物来能应,事至能断者是。⑤
因为义有判分、断割之意,故一般认为义与和无关,而是与和相反的。但朱子坚持,义表面上似乎不和,其实是和。因为使事物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各得其分,正是为和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问《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长’以下四句,说天德之自然。‘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以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元只是善之长,万物生理皆始于此,众善百行皆统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为仁。亨是嘉之会。此句自来说者多不明。嘉,美也;会,犹齐也。嘉会,众美之会,犹言齐好也。春天发生万物,未大故齐。到夏时,洪纤高下,各各畅茂。盖春方生育,至此乃无一物不畅茂。其在人,则‘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齐到恰好处,所谓动容周旋皆中礼,故于时为夏,于人为礼。利者,为义之和。万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无不得宜,故于时为秋,于人为义。贞者乃事之干。万物至此,收敛成实,事理至此,无不的正,故于时为冬,于人为智。此天德之自然。”⑥
这里对“利者义之和”的解释主要也是从得宜立论,认为各遂其性即是各个得宜,故可谓义之和。
朱子接着说:
“其在君子所当从事于此者,则必‘体仁乃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个字,极有力。体者,以仁为体,仁为我之骨,我以之为体。仁皆从我发出,故无物不在所爱,所以能长人。‘嘉会足以合礼’者,言须是美其所会也。欲其所会之美,当美其所会。盖其厚薄亲疏、尊卑小大相接之体,各有节文,无不中节,即所会皆美,所以能合于礼也。‘利物足以和义’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则义无不和。盖义是断制裁割底物,若似不和。然惟义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无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为义之和也。苏氏说‘利者义之和’,却说义惨杀而不和,不可徒义,须着些利则和。如此,则义是一物,利又是一物;义是苦物,恐人嫌,须着些利令甜,此不知义之言也。义中自有利,使人而皆义,则不遗其亲,不后其君,自无不利,非和而何?‘贞固足以干事。’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为事之干。干事,言事之所依以立,盖正而能固,万事依此而立。在人则是智,至灵至明,是是非非,确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瞒,所以能立事也。干,如板筑之有桢干。今人筑墙,必立一木于土中为骨,俗谓之‘夜叉木’,无此则不可筑。横曰桢,直曰干。无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紧固确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则谓之‘正’也。”①
这是说,物物各得其利便是义,便是义之和。义的价值特性是断制截割,但其作用能使事物各得其所宜。这就把义的特性和其作用作了区分。
朱子晚年的《玉山讲义》:
且道如何说个“仁义”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只“仁义礼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于此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若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①
本文第二节已经显示出,自战国秦汉以来,便常常把仁和义对举,标示出它们各自的价值特性与价值意向。朱子亦然,“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便是他代表性的说法②,并把四德的价值特性与价值意向归为性之本体,即性理。把义的分析用本体与其发用来展开,用已发未发的分析来说,义是断制截割的未发,断制截割是义的已发。所谓“××底道理”,就是××的理,在心性论上,就是指作为未发的本性的理。义是裁制断割的理,仁是温和慈爱的理,仁之发是温和慈爱,义之发是裁制断割。这是朱子哲学性情已发未发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以仁义礼智为性理包含了以四德为德性的思想。不过就论义而言,朱子更关注的似乎是义在由德性展开为德行过程中,义心的特点,即“义在心上”的特点。关于《玉山讲义》这里所涉及的四德说的宇宙论面向,我们会在最后一节一并论及。
朱子关于仁义价值特性的此类说法,也曾受到张九成子韶“仁义说”的影响:
某旧见张子韶有个文字论仁义之实云:“当其事亲之时,有以见其温然如春之意,便是仁;当其从兄之际,有以见其肃然如秋之意,便是义。”某尝对其说,“古人固有习而不察,如今却是略略地习,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略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见某说,忽然曰:‘公适间说得好,可更说一徧看。’”③
义是个毅然说话,如利刀着物。④
义如利刀相似,都割断了许多牵绊。⑤
义如利刀相似,胸中许多劳劳攘攘,到此一齐割断了。圣贤虽千言万语,千头万项,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义,伊川言敬,都彻上彻下。⑥
“义”字如一横剑相似,凡事物到前,便两分去。“君子义以为质”,“义以为上”,“义不食也”,“义弗乘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是此义十分精熟,用便见也。①
这些说法,无论利刀、利刃、横剑,都是形容义字的割断义。都是从义的发用来讲的。
朱子甚至说:
生底意思是仁,杀底意思是义,发见会通是礼,收藏不测是智。②
按庞朴曾以杀论义,合乎朱子之说,而其论证方法是论述“宜”字本指一种祭祀之礼,此种祭祀礼是杀戮宰杀,以此证明义的原初意义与杀有关③。其实,先秦文献的以宜解义,其宜字都不是作为祭祀的宜祭。而且,从朱子的例子可以看出,“杀底意思”不是义字的字源意义,而是从东汉后起的解说中引申出来的思想义。正如生并不是仁字的原初义。所以我们并不能用后起的意义去推原字源的意义。
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再回到第一节最后提及的竹简《五行》篇中论义的思想:
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13章)④
中心辩然而正行之,直也。直而遂之,肆也。肆而不畏强圉,果也。不以小道害大道,简也。有大罪而大诛之,行也。贵贵其等尊贤,义也。(20章)⑤
不仅如此,又另用整整三章的篇幅申明简作为义的意义:“不简不行,不匿不辩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22章)“简之为言,犹练也,大而晏者也。匿之为言,犹匿匿也,小而轸者也。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强,义之方也;柔,仁之方也。……”(23章)“大而晏者,能有取焉。小而轸者,能有取焉。……”(24章)⑥
《五行》篇论义的讲法,比起先秦诸家用宜论义,在思想上更接近于汉以后对义的理解。其思想是,义是对善恶的清楚明辨(这就是辩然而直);对恶要果敢断然去除(这就是果而不畏);对罪的处置要坚持原则(这就是简行)。可见,从先秦以宜训义到汉代以裁断训义,中间有一个过渡的阶段,这就是竹简帛书《五行》篇所代表的对义的理解。可惜我们对这一点研究得还很不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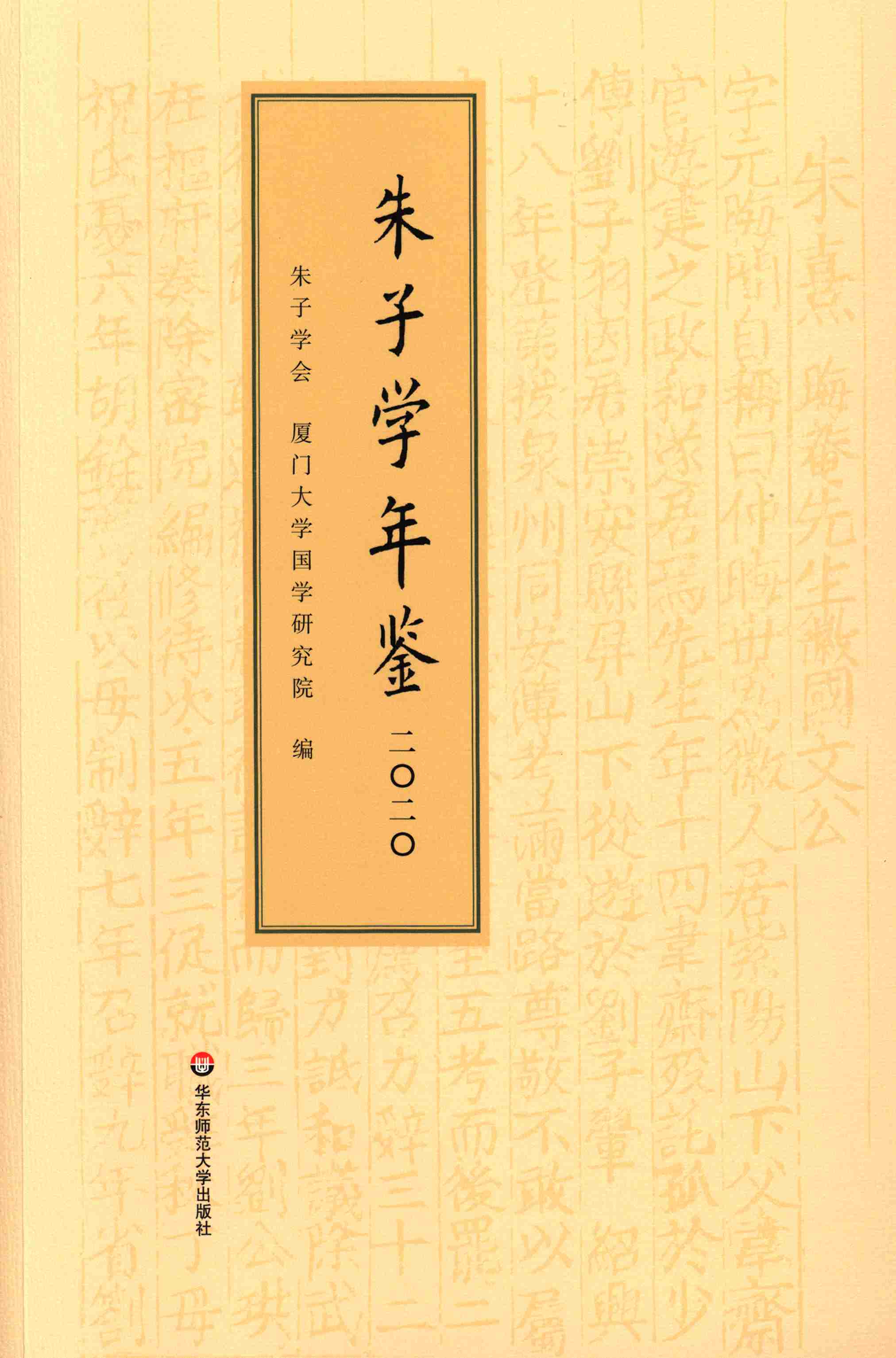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0》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以礼释仁的路径和意义》《2020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陈来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