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朱子以“裁制”解义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0》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868 |
| 颗粒名称: | 四、朱子以“裁制”解义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4 |
| 页码: | 030-033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主要以“义者宜也”的故训解释义字,但在《朱子语类》中,他在界定和把握义字的哲学思想时,主要使用汉儒的裁制和断决来阐发义的思想。这表明朱子在经典解释中对先秦和汉唐时期的训诂义进行了基本区分。同时,汉唐注疏对朱子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尤其是刚柔论仁义的思想对宋儒有一定的影响。这些事实表明汉儒学对宋儒学有一定的影响,朱子以裁制和断决来解释义并非仅仅是从汉唐儒者那里承袭而来,而是经过他的哲学反思和不断体悟后形成的观点。 |
| 关键词: | 朱子 裁制 汉儒 |
内容
虽然朱子在《四书集注》中主要以“义者宜也”的故训作为义字的训诂义,但在《朱子语类》中,朱子对义字作哲学思想的界定、把握时,则主要不是用宜来说明义字之义,而是用汉儒裁制、断决之说来阐发义之思想义。显示出朱子经典诠释中对先秦和汉唐的训诂义作了基本区分。同时可见,汉唐注疏中的训释为朱子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换言之,对朱子义理之学产生了影响。此外,汉儒以刚柔论仁义的思想也对宋儒颇有影响。这些都显示了汉儒之学对宋儒的影响。自然,朱子以裁制断决说义,并非仅仅是对汉唐儒者的说法的沿袭,也是他经过哲学的反思、反复的体会而得以形成的。
上面提到朱子《孟子集注》中说“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其中“事之宜”,是以宜训义。那么何谓“心之制”呢?此“制”即是“裁制”之意。事实上,《四书集注》在主要以宜训义之外,也用裁制释义,如解《孟子》“配义与道”:
义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①
这两句话在后世《孟子》的诠释中影响甚大,也是《孟子集注》中朱子训释义字的代表性说法之一。也由此可见,“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其中的“心之制”,便是心之裁制。在这里,宜字完全未出现。这就指出,义的解释不能只顺着先秦汉唐以宜解义的主流,只从事上去讲,还必须要从心上去讲。“事之宜”是从事上讲的,而“心之制”是从心上讲的。当然,这两句注是顺和原文配义之说而来,但也要看到,这两句也是比照仁字的解释“心之德,爱之理”而来,所以对于义字,朱子解释义字的真正特色不在事之宜,而在与仁字一样,都要从心上界定。仁义也好,其他德行也好,都要从心上去定义。与汉儒不同处在于,朱子强调义之裁制是“人心之裁制”。
朱子《周易本义》解释《坤·文言》“直其正也,方其义也”:此以学而言之也。“正”,谓本体。“义”,谓裁制。敬则本体之守也。②
此处也明确训义为裁制。又如:耳之德聪,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将这意去思量体认。O将爱之理在自家心上自体认思量,便见得仁。O仁是个温和柔软底物事。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见得自是。看石头上如何种物事出!“蔼乎若春阳之温,泛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O当来得于天者只是个仁,所以为心之全体。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义,一界子是仁之礼,一界子是仁之智。一个物事,四脚撑在里面,唯仁兼统之。心里只有此四物,万物万事皆自此出。O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虽分四时,然生意未尝不贯;纵雪霜之惨,亦是生意。O以“生”字说仁,生自是上一节事。当来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须要自体认得。O试自看一个物坚硬如顽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O试自看温和柔软时如何,此所以“孝悌为仁之本”。若如顽石,更下种不得。俗说“硬心肠”,可以见。硬心肠,如何可以与他说话!〇恻隐、羞恶、辞逊、是非,都是两意:恻是初头子,隐是痛;羞是羞己之恶,恶是恶人之恶;辞在我,逊在彼;是、非自分明。O才仁,便生出礼,所以仁配春,礼配夏;义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①这是说,义的本性是裁制,以四季而言,仁为春,礼为夏,义为秋,智为冬。根据朱子的解释,羞恶之心根于义,其中羞是羞自己的恶,恶是恶他人之恶。朱子还说过:“其恻隐,便是仁之善;羞恶,便是义之善。”②朱子《孟子集注》中已经明确提出:“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③据此,义是一个面对恶的德性。义的属性就是面对恶时,要清楚判别善恶、憎恶不善,然后果断去恶。这就是裁制之意。朱子说过:“‘克己复礼为仁’,善善恶恶为义。”④仁是善善,义是恶恶,此意最为重要,可惜朱子对此发挥强调不多。应该说,对义的这种认识在根本上是源于孟子把羞恶与义连接思想的影响。
问:“‘君子喻于义。’义者,天理之所宜,凡事只看道理之所宜为,不顾己私。利者,人情之所欲得,凡事只任私意,但取其便于己则为之,不复顾道理如何。”曰:“义利也未消说得如此重。义利犹头尾然。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小人只管计较利,虽丝毫底利,也自理会得。”⑤
学生的理解,从义利之别而言,义是天理之所宜,即遇事只看道理之所宜为,这里的宜为便是当为、应为。利是遇事只取便利自己。朱子认为,义者宜也,是说见得这事合当如此。朱子这里也是把宜解释为合当、应然。下一截就是结果,上一截是动机,小人只管结果是否有利。君子则在心上看道理如何,要见得义分明。以上是就义利之别的讨论,来看朱子对宜的理解,但朱子论义的思想未止于此。君子要见得义,还要“裁处其宜而为之”。这就把以宜解义,和裁制的解释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义不仅是见事之当然之则,还是以此当然之则去裁处得当合宜,要如此去做。
朱子解释义字时,也常常把裁制和断决二义一并说出,可见汉唐注疏对他的影响:
问“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曰:“中正仁义皆谓发用处。正者,中之质;义者,仁之断。中则无过不及,随时以取中;正则当然之定理。仁则是恻隐慈爱之处,义是裁制断决之事。主静者,主正与义也。正义便是利贞,中是亨,仁是元。”①
或问:“‘配义与道’,盖人之能养是气,本无形声可验。惟于事物当然之理上有所裁制,方始得见其行之勇,断之决。缘这道义与那气厮合出来,所以‘无是,馁也’。”曰:“更须仔细。是如此,其间但有一两字转换费力,便说意不出。”②
可见在朱子,裁制与断决的意义是相通的,都是与“行之勇、断之决”相关的。
朱子也会把断和割联系在一起使用论义:
问:“义者仁之质?”曰:“义有裁制割断意,是把定处,便发出许多仁来。如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把定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便是流行处。”③
把定与流行成为一对宇宙论概念,以前很少受到注意。这里则主要关注其中把裁制与割断联结使用,来解说义的意义。义的宇宙论意义,我们在最后一节再做讨论。
义本是个割截裁制之物,惟施得宜则和,此所以为利。从前人说这一句都错。如东坡说道:“利所以为义之和。”他把义自做个惨杀之物看了,却道得利方和。利是《乾卦》一德,如何这一句却去说义!兼他全不识义,如他处说亦然。④
割截和割断意近,至于和与利的关系,下节还会讨论。值得指出,若把义仅仅理解为裁制的形式功能,用《河上公章句》的说法,这更多地是讲“为义”,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义”的价值引导的作用。
上面提到朱子《孟子集注》中说“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其中“事之宜”,是以宜训义。那么何谓“心之制”呢?此“制”即是“裁制”之意。事实上,《四书集注》在主要以宜训义之外,也用裁制释义,如解《孟子》“配义与道”:
义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①
这两句话在后世《孟子》的诠释中影响甚大,也是《孟子集注》中朱子训释义字的代表性说法之一。也由此可见,“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其中的“心之制”,便是心之裁制。在这里,宜字完全未出现。这就指出,义的解释不能只顺着先秦汉唐以宜解义的主流,只从事上去讲,还必须要从心上去讲。“事之宜”是从事上讲的,而“心之制”是从心上讲的。当然,这两句注是顺和原文配义之说而来,但也要看到,这两句也是比照仁字的解释“心之德,爱之理”而来,所以对于义字,朱子解释义字的真正特色不在事之宜,而在与仁字一样,都要从心上界定。仁义也好,其他德行也好,都要从心上去定义。与汉儒不同处在于,朱子强调义之裁制是“人心之裁制”。
朱子《周易本义》解释《坤·文言》“直其正也,方其义也”:此以学而言之也。“正”,谓本体。“义”,谓裁制。敬则本体之守也。②
此处也明确训义为裁制。又如:耳之德聪,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将这意去思量体认。O将爱之理在自家心上自体认思量,便见得仁。O仁是个温和柔软底物事。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见得自是。看石头上如何种物事出!“蔼乎若春阳之温,泛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O当来得于天者只是个仁,所以为心之全体。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义,一界子是仁之礼,一界子是仁之智。一个物事,四脚撑在里面,唯仁兼统之。心里只有此四物,万物万事皆自此出。O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虽分四时,然生意未尝不贯;纵雪霜之惨,亦是生意。O以“生”字说仁,生自是上一节事。当来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须要自体认得。O试自看一个物坚硬如顽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O试自看温和柔软时如何,此所以“孝悌为仁之本”。若如顽石,更下种不得。俗说“硬心肠”,可以见。硬心肠,如何可以与他说话!〇恻隐、羞恶、辞逊、是非,都是两意:恻是初头子,隐是痛;羞是羞己之恶,恶是恶人之恶;辞在我,逊在彼;是、非自分明。O才仁,便生出礼,所以仁配春,礼配夏;义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①这是说,义的本性是裁制,以四季而言,仁为春,礼为夏,义为秋,智为冬。根据朱子的解释,羞恶之心根于义,其中羞是羞自己的恶,恶是恶他人之恶。朱子还说过:“其恻隐,便是仁之善;羞恶,便是义之善。”②朱子《孟子集注》中已经明确提出:“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③据此,义是一个面对恶的德性。义的属性就是面对恶时,要清楚判别善恶、憎恶不善,然后果断去恶。这就是裁制之意。朱子说过:“‘克己复礼为仁’,善善恶恶为义。”④仁是善善,义是恶恶,此意最为重要,可惜朱子对此发挥强调不多。应该说,对义的这种认识在根本上是源于孟子把羞恶与义连接思想的影响。
问:“‘君子喻于义。’义者,天理之所宜,凡事只看道理之所宜为,不顾己私。利者,人情之所欲得,凡事只任私意,但取其便于己则为之,不复顾道理如何。”曰:“义利也未消说得如此重。义利犹头尾然。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小人只管计较利,虽丝毫底利,也自理会得。”⑤
学生的理解,从义利之别而言,义是天理之所宜,即遇事只看道理之所宜为,这里的宜为便是当为、应为。利是遇事只取便利自己。朱子认为,义者宜也,是说见得这事合当如此。朱子这里也是把宜解释为合当、应然。下一截就是结果,上一截是动机,小人只管结果是否有利。君子则在心上看道理如何,要见得义分明。以上是就义利之别的讨论,来看朱子对宜的理解,但朱子论义的思想未止于此。君子要见得义,还要“裁处其宜而为之”。这就把以宜解义,和裁制的解释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义不仅是见事之当然之则,还是以此当然之则去裁处得当合宜,要如此去做。
朱子解释义字时,也常常把裁制和断决二义一并说出,可见汉唐注疏对他的影响:
问“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曰:“中正仁义皆谓发用处。正者,中之质;义者,仁之断。中则无过不及,随时以取中;正则当然之定理。仁则是恻隐慈爱之处,义是裁制断决之事。主静者,主正与义也。正义便是利贞,中是亨,仁是元。”①
或问:“‘配义与道’,盖人之能养是气,本无形声可验。惟于事物当然之理上有所裁制,方始得见其行之勇,断之决。缘这道义与那气厮合出来,所以‘无是,馁也’。”曰:“更须仔细。是如此,其间但有一两字转换费力,便说意不出。”②
可见在朱子,裁制与断决的意义是相通的,都是与“行之勇、断之决”相关的。
朱子也会把断和割联系在一起使用论义:
问:“义者仁之质?”曰:“义有裁制割断意,是把定处,便发出许多仁来。如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把定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便是流行处。”③
把定与流行成为一对宇宙论概念,以前很少受到注意。这里则主要关注其中把裁制与割断联结使用,来解说义的意义。义的宇宙论意义,我们在最后一节再做讨论。
义本是个割截裁制之物,惟施得宜则和,此所以为利。从前人说这一句都错。如东坡说道:“利所以为义之和。”他把义自做个惨杀之物看了,却道得利方和。利是《乾卦》一德,如何这一句却去说义!兼他全不识义,如他处说亦然。④
割截和割断意近,至于和与利的关系,下节还会讨论。值得指出,若把义仅仅理解为裁制的形式功能,用《河上公章句》的说法,这更多地是讲“为义”,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义”的价值引导的作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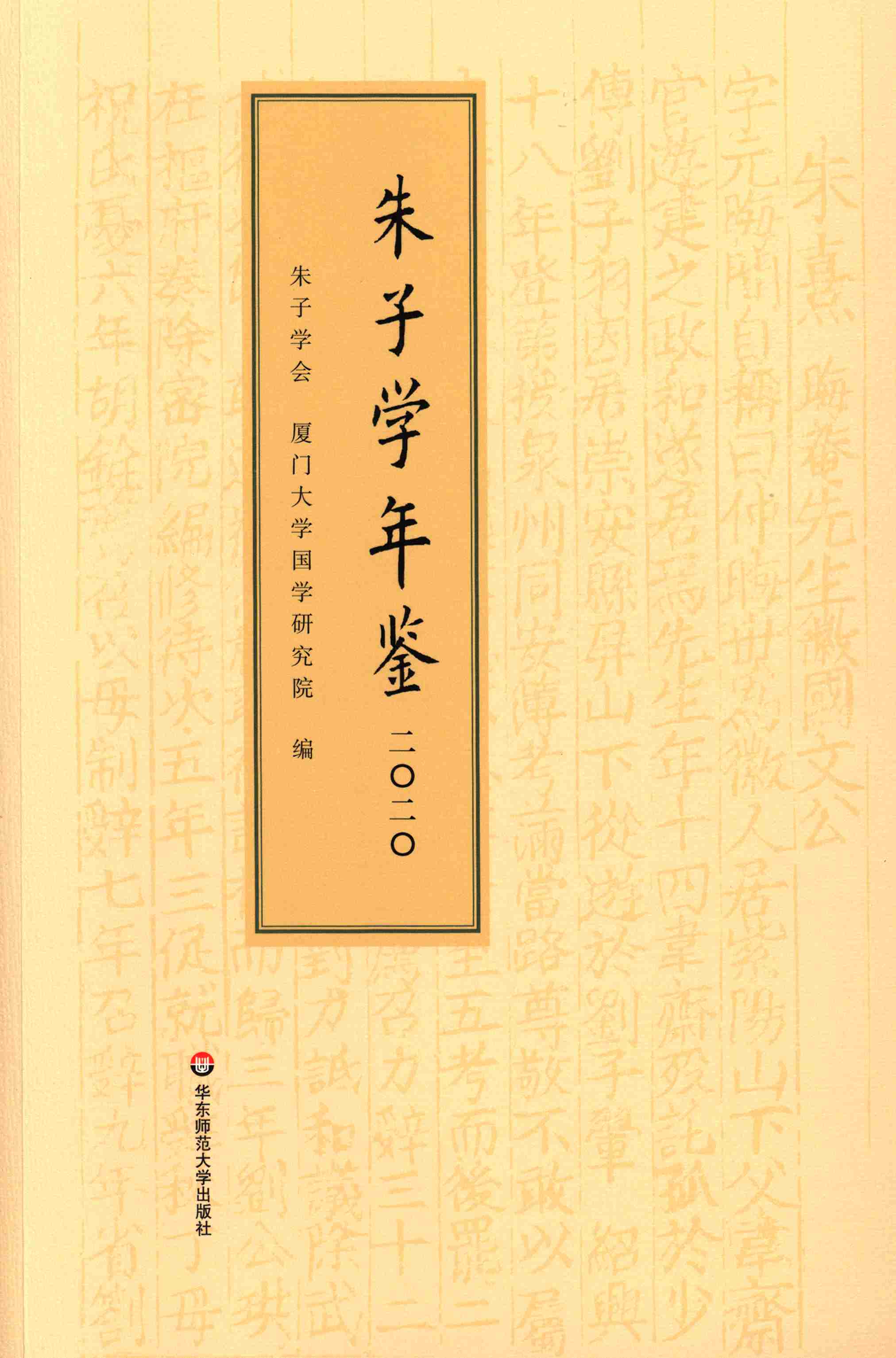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0》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以礼释仁的路径和意义》《2020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陈来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