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礼》与宋代家礼的庶民化倾向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817 |
| 颗粒名称: | 《朱子家礼》与宋代家礼的庶民化倾向 |
| 分类号: | B244.75;G127 |
| 页数: | 18 |
| 页码: | 240-257 |
| 摘要: | 《朱子家礼》是宋代最著名的家礼著作,亦是朱熹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的经典著述之一。明清时代《朱子家礼》更是成为民间通用礼仪文本。学界对《朱子家礼》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将《朱子家礼》与宋代家礼发展趋势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显然并不充分。需要指出的是,《家礼》并不仅仅是朱熹个人的修撰著述,更是宋代家礼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成果,将《家礼》置于宋代家礼修撰的潮流趋势中进行考察,有助于把握《家礼》的庶民化倾向。 |
| 关键词: | 朱子家礼 宋代家礼 庶民化 |
内容
《朱子家礼》是宋代最著名的家礼著作,亦是朱熹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的经典著述之一,明清时代《朱子家礼》更是成为民间通用礼仪文本。学界对《朱子家礼》(以下亦简称《家礼》)的研究成果颇多,基本集中在《家礼》的真伪、版本源流、思想特色、文本传布等方面,②但将《朱子家礼》与宋代家礼发展趋势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显然并无充分。需要指出的是,《家礼》并不仅仅是朱熹个人的修撰著述,更是宋代家礼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成果,将《家礼》置于宋代家礼修撰的潮流趋势之中,从宋代家礼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和考察《家礼》的修撰及其特征,对于今人更趋全面而深入地探究《家礼》的内涵特征、时代特性以及朱熹的礼仪观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倾向:《朱子家礼》编撰的
时代背景
欲解析《家礼》,首先要了解其编撰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宽泛而言是宋代社会的发展变革,狭义一点来说就是宋代官僚士大夫层面以及宋代官方所呈现出来的推行礼制、教化社会的明确思想意图。而这种思想意图直接的表达即为宋代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倾向。
中国古代礼制的奠基时代是在周代,然周时已有礼不下庶人之说,且这种说法在秦汉以后诸代官方礼制中皆有明确体现。唐时颁布的《大唐开元礼》堪称中古礼仪典范,其中明确是以君主、宗亲、官僚为对象制定礼仪制度,具体分为皇帝、皇室成员、三品以上、四品五品、六品以下五个档次,庶人礼仪只是在“六品以下”档次之中略有涉及。①可以说,庶人相关礼仪杂录其中,更大意义是为了强调等级差异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庶民礼仪的修订和规范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北宋建立之后,曾专门颁行针对“士庶”或“民家”抑或“民庶”相关仪制的诏令。与此相对应,在皇帝、宗亲、品官诸礼仪等级之外,庶民百姓的礼仪规范正式成为一个详备而独立的部分存现在官方礼制中。今可看到,《宋史·礼志十八·嘉礼六》“婚礼”有:“亲王纳妃”、“诸王以下婚”、“品官婚礼”、“士庶人婚礼”几项内容。尽管其中以“士庶”为名,包括“三舍生及品官子孙”和庶人,并非单纯为针对庶民的礼仪,但是,这种分类的出现无疑已经是标志着庶民礼仪等级的发展。此外,《宋史·礼志二十八·凶礼四》中有“士庶人丧礼”与“诸臣丧礼等仪”相对应;《宋史·舆服志五》中专门列有“士庶人车服”条目,与“诸臣服”相对。士庶礼仪成为关注点,正是由宋代官方礼制中庶民礼仪的发展演进而来的。宋代庶民礼仪的发展,最明确的标志是宋徽宗颁行的官方礼典《政和五礼新仪》,其中针对庶民层面的礼仪规定已经明确而详备。例如,其书“序例·丧葬之制”中,详细规定了庶人丧葬仪制,再如,五礼仪制中列出了“庶人婚仪”、“庶人冠仪”、“庶人丧仪”等专门针对庶民百姓阶层制定的礼仪条文。这是中国古代官方礼典中第一次明确出现的专门针对庶民的礼仪条文。《政和五礼新仪》中庶民礼仪的专门规定,正是宋代官方礼制“庶民化”趋势的反映。
庶民礼仪被注重,反映的不仅是朝廷礼制内容的日趋完善,更是官僚士大夫群体以及官方推行礼制于庶民、实现社会教化的政策导向。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对推行礼制于庶民、实现礼仪教化的关注就没有庶民礼仪的修订。宋代士大夫对礼制不能下及民间、教民化俗的认识,明显比唐人更为深刻。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乐志》中曰:“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焦点正集中在礼制不为民间所知,天下之人不能被其教化。宋人不仅对推行礼制、实现教化的认识比唐代更进一步,其对官方礼典中存在的针对庶民礼仪的缺憾亦有清晰认知。宋初《开宝通礼》“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开元礼》的不及庶民的缺点,《开宝通礼》亦不能避免。宋神宗时,吕大防上奏请定婚嫁
丧祭之礼,即云:“今之公卿大夫,下逮士民,其婚丧葬祭皆无法度,唯听其为而莫之禁。”“乞诏谕礼官,先择《开宝通礼》论定而明着之,以示天下,违者有禁,断以必行。”①并云其士以上“当专用礼”,“虽未能下逮黎庶,而小人所视,足以成化”。其中已经明确官方礼典中存在的未能“下逮黎庶”缺陷。
正是以这种认知为基础,至宋哲宗元祐时,朝臣奏请中已经明确提出要修订“教民”之礼仪。右司谏朱光庭《上哲宗乞详议五礼以教民》疏中,即奏请举礼官参议“上自朝廷所行之制度,下至民庶所守之规矩”,著为一代之典,颁诸四海,以正人伦变礼俗。②太常博士颜复在上奏哲宗《乞详议五礼以教民》疏中更是直接指出:“士民之礼,踵历代之咎,未降彝制,下无矜式,使有志之士动虚名失实之叹。此甚可为治朝惜也。”认为民需教,“不教则失中,失中则流。祭享之礼不教,则流于祝襘佛齐。婚姻之礼不教,则流于委巷俚习。宾客之礼不教,则流于游衍嬉乐。师田之礼不教,则流于夷风暴俗。丧纪之礼不教,则流于道释数术”③。颜复不仅指出了制礼教民的急迫性,更对修订士民礼仪提出具体建议,亦即“会萃经史古今仪式至诸家祭法,岁荐时享、家范书仪之类可取者,高而不难,近而不迫,成士民五礼”。不必讲究古礼之冕服、礼器,不必要求古礼之币车、筵席,“就其便安”以为主。④换而言之,就是根据现世的实际情况制定“教民”的礼仪。值得注意的是,颜复对“教民”之礼的推行亦有建议,那就是颁布州县,“缓驱以令,使乐而不骇”,促使民众慢慢知晓其义,遵行其仪。总的来看,至于北宋后期,官僚士大夫层面无疑对修订和推行庶民礼仪、实现社会教化已经形成了清晰而稳妥的思路。《政和五礼新仪》专门庶民礼文的出现,显然也是这种思路和意图的体现。
对庶民礼仪的关注在南宋时期继续发展。绍熙中,礼官黄灏奏请于《政和五礼新仪》之内掇取品官、庶人冠昏丧祭礼仪,“摹印颁之郡县”,朝廷允从其奏,此即《政和冠昏丧祭礼》十五卷书。①将品官、士庶冠婚丧祭礼文专门摘录、刊印并颁发各州县地方,正是推行礼仪教化于庶民层面的重要举措。官僚士大夫们在任职地方之际,亦重视推行礼仪的实践。朱熹在泉州就曾提交《申严婚礼状》,其中有云:“仍乞备申使州,检会《政和五礼》士庶婚娶仪式行下,以凭遵守,约束施行。”②正是意在将政和礼典中个关于士庶的礼文规定专门录出颁行于地方之中,以促进庶民百姓的礼仪教化。
尽管庶民礼文的制定并不能说明礼制已经在实际上真正达于庶民生活之中,但是由开始关注修订庶民礼仪到“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遇民庶之家,有冠昏丧葬之礼,即令指受新仪”,官方礼制明确推行于庶民层面的倾向无疑是清晰的。也正是通过对庶民礼仪的修订和推行,官僚士大夫群体所主张的推行礼制、教化民众的意图才有可能更大意义上实现。需要指出的是,就宋代社会而言,官僚士大夫们对推行礼制于庶民层面的教化意图不仅表现在其敦促朝廷修订庶民礼文仪制,更表现在其自身积极修撰和遵行日趋“庶民化”的家礼的行为。二按循礼经、顺应世俗:
北宋家礼庶民化的迹象
唐宋时期,家礼的发展明确呈现出了独特的阶段性特征。唐代家礼修撰始终与世家旧族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家礼文本的著述者主要出身于世家旧族。其次,家礼修撰的事例亦主要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再次,承续礼经旧文而来的家礼修撰,与世家旧族的家学渊源和传承有着直接关系。唐代家礼的世家旧族色彩始终凸显,因此唐代家礼的行用始终有很大局限,并不具有广泛意义。与此相比,宋代家礼则呈现出了别样的面貌。北宋时代局限于世家旧族之中的全面承袭古礼仪制的家礼已基本上不复存在,由普通的科举官僚士大夫修撰并遵行的家礼,表现出了明显的远离经典旧文、参以时宜、遵从民俗的特征,其内容仪制所呈现出来了的庶民化亦日趋明显起来。换而言之,北宋家礼已经表现出了明确的下延及庶民层面的迹象。
北宋家礼的庶民化迹象,首先表现在其修撰者大多是普通的科举官僚士大夫,而其生活已经接近庶民生活层面。北宋家礼修撰和遵行引起士人的广泛关注,家礼影响日渐扩大,与社会变迁家族观念的淡化促成敬宗收族意识的兴起直接相关。然北宋家礼的影响能够超过前代,还有一点无疑不可忽视,北宋家礼修撰者多当朝之名人。据《宋史·艺文志》记载诸家礼文本撰作者,有名相贤相如杜衍、韩琦、司马光、吕大防;又有学古力行之士人宗师,如程颐、张载;其他几人虽不及杜、韩、司马之闻名于世,亦是一时翘楚、宋史有传之名臣,如吕大临、吕大钧,又如范祖禹。这些时代风标性人物修撰和积极遵行家礼,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家礼的影响。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名垂青史,但是不
能否认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科举入仕的普通官僚士大夫。宋代官学发展迅速,家学衰微,类似前代世家大族的家学渊源、礼学传承早已不再。因此,这些普通科举官僚修撰和遵行家礼,其顺应世俗、参以时宜的特点就尤为明显。
北宋家礼的庶民化迹象,还可以从具体礼文仪制规定的顺应世俗表现出来。细观北宋家礼仪制,可以发现,虽然仍有如杜衍家祭“守其家法,不迁于世俗”①这样的例子,但是“独杜氏守其家法,不迁于世俗”②的评语却恰恰表明北宋家礼整体而言与杜氏家礼明显有异,事实上诸家家礼清晰可见的正是“迁于世俗”,正是顺应世俗、参以时宜。例如,韩琦参合前代七家祭礼,撰述韩氏家祭礼十三篇,名曰《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其序中云:“采前说之可行,酌今俗之难废者,以人情断之”③,即采用前人家祭礼可行之于今者,并吸纳世俗之难以轻易废除者。正是由此,韩氏家祭式明确顺应世俗,在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废”。因其“虽出于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忘亲也”。④这种“迁于世俗”“参以时宜”的做法,在张载家礼中也有明显表露。《宋史·张载传》载“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朱熹更是明确指出张载制礼多不本诸《仪礼》,自有“独撰”。亦可知其对“世俗”“时宜”的考量和参用。⑤
司马光在家礼修撰方面卓有成就,其著述包括《书仪》《涑水祭仪》以及《居家杂仪》在内,详细规定了家族冠婚丧祭诸仪,尤其强调祭仪和居家杂仪。①今仅据《书仪》,②其沿用古礼而参以时宜、顺应今俗的特点清晰可见。《书仪》对冠婚丧祭等礼文仪式的规范,屡屡可见的是其行文之中“今从俗”、“且须从俗”、“今从便”之语。例如,“冠”中有礼宾之仪,注云:“今虑贫家不能办,故务从简易”。其实已经考虑到了士庶人家的财力有限,不能按循烦琐古礼行事。又如,“婚仪”中亲迎前一日,有“女氏使人张陈其婿之室”之仪,注云:“俗谓之铺房,古虽无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废也。”亦是顾及到了世俗民情。后人或以为司马光家礼“从俗”最显著者,在于新妇入门拜先灵(祖祢)于影堂而废“三月庙见”的古礼。司马光在此注文中云:“古无此礼,今谓之拜先灵,亦不可废也。”设影堂以祭祖是北宋官僚士大夫家族时俗,《书仪》设有专门影堂祭祀以及影堂杂仪的条目,正是顺从这一世俗而来。但是恰恰这一设置,说明《书仪》家礼规范对象主要是仍是官僚士大夫群体,而非是普通庶民百姓。由此我们在理解韩琦、张载等人家礼中的顺应世情民俗的时候,也就不能将其对普通民俗的参酌估计过甚,因为其同样是主要针对官僚士大夫家族的仪制规定。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的是,北宋家礼是在按袭古礼旧文的基础上,比唐代家礼更为明确地加入了世俗、时宜的因素,更趋从俗、从众、从简易,亦更趋接近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
北宋家礼的庶民化迹象,亦可以从居家杂仪的关注上表现出来。《宋史·艺文志》列北宋时期的10部家礼,家祭礼有8部,家礼修撰主要集中于祭礼,显然承继了唐代家礼修撰的传统,这与自古以来的祭祖为家族重事有关。韩琦、司马光等人亦正是出于对士人之家祭祀“多苟且不经”、官僚之家祭如同闾巷庶民有着清晰的认知,才关注和强调家祭礼仪的规范,但顺应世俗、不违孝子之情的做法使其家祭礼中依然表现出了接近闾巷庶民的迹象。与此8部家祭礼不同,另外两部亦即司马光所著的《书仪》和《居家杂仪》,除了规范冠婚丧祭礼诸仪之外,却表现出了对日常居家杂仪的特别强调。司马光专门撰写了单行本的《居家杂仪》,又在《书仪》一书中专列“居家杂仪”篇。《书仪》卷四“婚仪下”中列有“居家杂仪”,其名目包括凡家长御群子弟及家众、凡诸卑幼事家长、凡为子妇者事父母舅姑、凡为人子弟者事父兄宗族、凡为人子者事父母、凡子妇侍父母舅姑疾、凡为宫室、凡卑幼于尊长、凡节序及非时家宴、凡子始生即教育、凡内外仆妾事主人等等内容,涉及家族内各成员的礼仪规范、日常居家的各个方面。居家杂仪的单独提出、专门规定,是对日常居家生活礼仪的规范和特别强调,这是唐代家礼中关注尚少的内容,无疑是对家礼修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和扩充。居家杂仪的突出规定,表明了北宋家礼日趋接近普通士庶生活层面的现实。
检视家礼的发展历程可见,依据礼经旧文编撰家礼是南北朝世家大族的风习,唐代家礼修撰正是南北朝世家大族撰制家
礼风习的延续。也正是在此传承礼经旧文的趋势特征中,关注冠婚丧祭诸仪而忽视日常居家礼仪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局面,根源在于无论是南北朝的门阀士族还是唐代的世家旧族,其家学渊源、礼学传承都是非常明显的,所谓风教“整密”,垂髫换齿之时“便蒙诱诲”,习得“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①,因此居家日常行为规范并无需要特别关注。然至于宋代,世家旧族早已沦丧,不为人知,家学渊源、礼学传承更不见于私家,兴起于普通士庶层面的科举官僚士大夫们按循礼经、参以时宜、顺从世俗编撰家礼仪制之际,不仅要关注冠婚丧祭诸仪,更要专门关注家族成员的日常行为规范、居家生活的日常礼仪约束。因此,对这种居家杂仪的关注,正反映了北宋家礼日趋接近士庶民众生活层面的趋势特征。
总的来看,以《书仪》为代表的北宋家礼,在按循礼经旧文的基础上,参以时宜、顺应民俗的主旨明确,日趋接近士庶百姓的生活实际,表现出了一定的庶民化的迹象。尽管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家礼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针对自家修订的礼仪规范,因此这种“接近”依然有限,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并未能有更大程度上直白地显露和进展。然这种庶民化迹象的影响依然不可低估,作为宋代家礼庶民化的标志性成果的《朱子家礼》的修撰,正是以北宋家礼的发展演进为基础的。三变古适今、简而易行:《朱子家礼》
庶民化倾向的标识
北宋时期,由于前代世家旧族沦胥不再,崔卢李郑之流为世人所不闻,在家学渊源中断,官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古礼传承无疑已经在事实上为世人所忽视。由此科举官僚家族的家礼修撰和遵行,表露出了鲜明的参以时宜、顺应世情民俗的特点,日趋接近庶民生活实际的趋势。至于南宋时代,家礼则更进一步演化为凸显变古适今原则的普及于士庶之间的明确庶民化的仪制规范。
《宋史·艺文志三》记载南宋家礼文本有朱熹《二十家古今祭礼》二卷①、《四家礼范》五卷②、《家礼》一卷③,赵希苍《赵氏祭录》二卷、李宗思《礼范》一卷、周端朝《冠婚丧祭礼》二卷(集司马氏、程氏、吕氏礼),高闶《送终礼》一卷④等。上述家礼著述者5人,可考身世者4人。与北宋家礼修撰者类似,基本都是官僚士大夫。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宗思曾“从朱子学”①,周端朝亦曾“从朱晦庵武夷读书”②,二者作为朱熹门生,其家礼修撰显然是受到朱熹的影响。从上面所列家礼名目亦可看出,与北宋家礼修撰不同,一是家祭礼虽然依然得到关注,但不再是家礼修撰的绝对重点和主要方向,南宋家礼修撰中关注冠婚丧祭诸项礼仪规范的著述比重增大;二是重视对以往朝代家礼著述的汇总和总结,而此正表明了南宋家礼修撰中直接审视和总结前代家礼著述的倾向。正是在充分审视和总结前代家礼著述的基础上,南宋官僚士大夫们对家礼修撰顺应世俗人情的认知更加明确,徐度评价韩琦家祭礼顺应世俗民情时曾云:“其说多近人情,最为可行。”③朱熹评价司马光《书仪》亦曾云:“读者见其节文度数之详,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见习行,而已有望风退怯之意。又或见其堂室之广,给使之多,仪物之盛,而窃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书虽布,而传者徒为笥箧之藏,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④在此番评述中,朱熹指出司马光家礼对古礼仪节仪物的削减幅度还有局限,幅度还不够大,不能更大意义上接近普通士庶的生活实际,因此传布者虽众但往往不见习行,影响了推广行用。显然朱熹关注的已经是家礼能否接近普通士庶的生活实际,能够真正传布推广的问题了。因此,朱熹撰制《家礼》,与北宋家礼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是由削减古礼烦琐之仪节到直接变易、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其为普通士人、庶民修礼的意图和主张。
首先,朱熹明确阐释其修撰《家礼》的目的,欲推行礼仪规范于士人与庶民之中,既面向好礼之士人,亦针对“贫窭”的庶民层面。朱熹在《家礼·序》文中云:
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用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
按此,朱熹撰制《家礼》的出发点正是基于此前君子所撰家礼的不能行用,自己要撰制家礼欲使好礼之士能遵礼仪、贫窭庶民之家亦能及于礼。与北宋家礼修撰更多是用于自家族内相比,朱熹在修撰《家礼》之初,就明确了将《家礼》推行开来的目的,欲推行的范围从好礼之士到贫窭之家,换而言之,其不仅是欲推行于士人层面,更是要推行于庶民层面。所谓“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正彰显了朱熹意欲为士庶广泛层面制定家礼规范的主张和宗旨。而此欲广泛推行于庶民层面的做法,无疑比北宋家礼修撰有了更进一步的推进和发展。
也正是由此目的出发,朱熹在《家礼·序》中还阐释了修撰家礼的原则,亦即变古适今,所谓变古适今就是在遵行古礼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更大程度上的改变古礼以适应今世,朱熹的具体做法就是略去浮文缛节,强调礼之名分本实。谨名分、崇敬爱以为之本,略浮文而务本实。所以,有学者明确指出,《家礼》“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专用的‘贵族之礼’,而是通用于整个
社会的、更多地考虑到社会普通家庭的‘庶民’之礼”①。显然,《家礼》的庶民化倾向已经在其修撰目的、修撰原则上清晰地表露出来。
其次,《家礼》的“通礼”设置充分体现了其庶民化的倾向。朱熹在《家礼·序》文中明确提出了礼之本的观点,认为:“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者,其本也。”又言到,“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因此,《家礼》开篇第一卷即是“通礼”,“此篇所著,皆所谓有家日用之常礼,不可一日而不修者。”强调的正是日常所行之礼仪,所谓务本实也。而此篇之首要内容“祠堂”,正是其所强调的务本实的关键。朱熹曰:
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
显然,朱熹针对庙制不行而士庶层面又财力有限,提出了祠堂的建制,且祠堂相关仪制体系所用亦多为俗礼,亦正是顺应民情的做法。祠堂具体规制明确考虑士人以及庶民之行用需要,财力限制,力求符合士人及庶民的生活实际。例如,“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按其规定: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若按此规制,则祠堂之建制亦可谓繁杂,非普通庶民之力可以达到。朱熹遂又有曰:
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正寝谓前堂也。地狭,则于厅事之东亦可。
按此记述可见,朱熹在针对官僚士大夫之家或者说财力相当之家规定了较为繁复的三间式祠堂建制的同时,又考虑到了财力贫窭的庶民之家的实际情况,而阐释了一间式祠堂的建制,更甚至提出了“厅事之东”式的祠堂建制。由此言之,朱熹在撰制祠堂规制之时,具体考虑到了普通士庶层面的各种情况,使祠堂规制能够符合士人乃至庶民层面的需求。
此外,祠堂相关仪制内容,朱熹也明显考量了士庶的生活实际、风俗人情。例如,祠堂祭礼时日规定,沿承古代祭祖“正至、朔望则参”的同时,又规定了“俗节”的祭献,曰:“俗节则献以时食。”注文云:“节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阳之类。凡乡俗所尚者,食如角黍;凡节之所尚者,荐以大盘,问以蔬果。礼如正至、朔日之仪。”这一规定顺应乡俗人情,明显是迎合士庶社会层面的风俗习惯的一种举措。而祠堂“有事则告”诸仪亦同样体现了对庶民的考虑,所谓有事则告之“事”,既包括了告授官、告贬降、告追赠等官僚士人家族官品升降之事,还包括了生嫡长子、冠、婚等普通士人、庶民之家皆有的家族重事。对先祖的称呼,亦着意于既可适合官僚士人之家,亦可行用普通庶民之家,其规定“有官封谥则皆称之;无则以生时行第称号,加以府君之上。妣曰‘某氏夫人’”。除了祠堂诸制明显表露对普通庶民的考量外,“居家杂仪”列入“通礼”卷,也充分体现了其对士人、庶民之家的日常家居礼仪规范的重视和强调。
再次,《家礼》中冠婚丧祭诸仪的内容规定,也充分表露出其
庶民化的倾向。朱熹《家礼》五卷,观其篇目,与司马光《书仪》大体类同,甚至一半以上的文字语句援引了《书仪》的内容。①然细读其中冠婚丧祭诸礼之程序步骤、仪式仪物,其与《书仪》的差异明显可见,《家礼》冠婚丧祭诸礼仪式程序显然更趋简单易行。如冠礼仅存告于祠堂、戒宾、宿宾、陈冠服、三加、醮、字冠者、见尊长、礼宾等大仪节。如婚礼程序简化,将古礼之婚六礼削去其三。《书仪》婚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妇见舅姑、婿见妇之父母八项内容,前六项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是为古礼之婚礼“六礼”。《家礼》婚礼仪节包括纳采、纳币、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婿见妇之父母六项内容,明显改易了传统婚礼“六礼”为“三礼”即“纳采、纳币、亲迎”。而即使是此“纳采、纳币、亲迎”三项,其仪式记述亦非拘泥于繁文缛节、厅事仪物,只着重简述仪式过程而已。“庙见”是将古制“三月而庙见”简化为三日“以妇见于祠堂”。再如丧礼,则将《书仪》的三十七节削至二十一节。古礼丧葬甚为烦琐,《书仪》丧仪即包括从初终、复以至祔、小祥、大祥、禫祭等共计37项内容,而《家礼》丧仪却只有初终、沐浴、袭以至祔、小祥、大祥、禫等21个仪式,其对丧礼仪节步骤的变易无疑是十分明显的。较之《书仪》,《家礼》丧仪的叙述文字更趋简洁明了,“节次也更为分明”②。
《家礼》中冠婚丧祭诸仪不仅程序明显简略,行文清晰简明,更重要的是具体仪式规定也力求简单易行,注意考虑庶民之家的财力状况。例如“昏礼”中“纳币”仪节,即曰:“币用色缯,贫富随宜,少不过两,多不逾十,今人更用钗钏、羊酒、果实之属,亦可。”宋时婚礼多重烦琐,纳币聘财亦以多为尚,官僚士大夫层面更是崇尚聘财嫁资,而普通庶民之家往往不行礼仪,更无论婚礼诸节。朱熹意欲推行礼仪于庶民层面,其在尽力简化、省略婚礼仪节程序之同时,明确减少聘财之数量,以使普通庶民之家亦可能遵行简化之后的婚礼仪节。又如,“祭礼”中即明确说明:“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筋力而行之,财力可及者,自当如仪。”所谓称家之有无,实际上是对应礼器、祭品诸事而言,所谓量筋力而行之,实际上是针对施行祭礼时斋戒、省牲、涤器、具馔以及三献诸仪节而言的。此番特别说明,实质是对普通庶民而言,宣扬了一种祭祖贵诚心爱敬而非执着于礼器、祭品以及周备仪节,在能力不及的情况之下,量力而行亦是对祖宗的爱敬呈现,并非是不敬祖先。显然,朱熹的这种有力则如仪、无力则量力即可的主张,对于祭祖之礼能够为更为广泛的庶民层面接受和遵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朱子家礼》不仅彻底改变了儒家礼经旧文仪节繁缛的贵族面孔,甚至也脱离了北宋时代家礼离古不远的状态,成为充分考量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庶民婚丧嫁娶、日常居家生活的一部“庶民之礼”①。当然,庶民化的《家礼》的出现并非偶然,其与宋初以来官僚士大夫们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倾向直接联系在一起,更与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的紧密关联。换句话说,南宋时期庶民化的《家礼》的出现和推行,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
始终贯穿着重本实、轻浮文而量力行礼的主张的《朱子家礼》,正顺应了宋代官僚士大夫传布礼制以教民化俗的追求,因此其书一旦面世即引发关注,加以朱门弟子的大力刊印和注释,故很快便在社会上广泛传布开来。元代《朱子家礼》影响渐及南北,至于明代成为朝廷明确要求士庶之家遵行的礼文范本,其书更传布于日本和朝鲜,在朝鲜半岛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局面的出现,恰恰与《朱子家礼》的鲜明的庶民化倾向直接相关。
时代背景
欲解析《家礼》,首先要了解其编撰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宽泛而言是宋代社会的发展变革,狭义一点来说就是宋代官僚士大夫层面以及宋代官方所呈现出来的推行礼制、教化社会的明确思想意图。而这种思想意图直接的表达即为宋代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倾向。
中国古代礼制的奠基时代是在周代,然周时已有礼不下庶人之说,且这种说法在秦汉以后诸代官方礼制中皆有明确体现。唐时颁布的《大唐开元礼》堪称中古礼仪典范,其中明确是以君主、宗亲、官僚为对象制定礼仪制度,具体分为皇帝、皇室成员、三品以上、四品五品、六品以下五个档次,庶人礼仪只是在“六品以下”档次之中略有涉及。①可以说,庶人相关礼仪杂录其中,更大意义是为了强调等级差异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庶民礼仪的修订和规范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北宋建立之后,曾专门颁行针对“士庶”或“民家”抑或“民庶”相关仪制的诏令。与此相对应,在皇帝、宗亲、品官诸礼仪等级之外,庶民百姓的礼仪规范正式成为一个详备而独立的部分存现在官方礼制中。今可看到,《宋史·礼志十八·嘉礼六》“婚礼”有:“亲王纳妃”、“诸王以下婚”、“品官婚礼”、“士庶人婚礼”几项内容。尽管其中以“士庶”为名,包括“三舍生及品官子孙”和庶人,并非单纯为针对庶民的礼仪,但是,这种分类的出现无疑已经是标志着庶民礼仪等级的发展。此外,《宋史·礼志二十八·凶礼四》中有“士庶人丧礼”与“诸臣丧礼等仪”相对应;《宋史·舆服志五》中专门列有“士庶人车服”条目,与“诸臣服”相对。士庶礼仪成为关注点,正是由宋代官方礼制中庶民礼仪的发展演进而来的。宋代庶民礼仪的发展,最明确的标志是宋徽宗颁行的官方礼典《政和五礼新仪》,其中针对庶民层面的礼仪规定已经明确而详备。例如,其书“序例·丧葬之制”中,详细规定了庶人丧葬仪制,再如,五礼仪制中列出了“庶人婚仪”、“庶人冠仪”、“庶人丧仪”等专门针对庶民百姓阶层制定的礼仪条文。这是中国古代官方礼典中第一次明确出现的专门针对庶民的礼仪条文。《政和五礼新仪》中庶民礼仪的专门规定,正是宋代官方礼制“庶民化”趋势的反映。
庶民礼仪被注重,反映的不仅是朝廷礼制内容的日趋完善,更是官僚士大夫群体以及官方推行礼制于庶民、实现社会教化的政策导向。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对推行礼制于庶民、实现礼仪教化的关注就没有庶民礼仪的修订。宋代士大夫对礼制不能下及民间、教民化俗的认识,明显比唐人更为深刻。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乐志》中曰:“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焦点正集中在礼制不为民间所知,天下之人不能被其教化。宋人不仅对推行礼制、实现教化的认识比唐代更进一步,其对官方礼典中存在的针对庶民礼仪的缺憾亦有清晰认知。宋初《开宝通礼》“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开元礼》的不及庶民的缺点,《开宝通礼》亦不能避免。宋神宗时,吕大防上奏请定婚嫁
丧祭之礼,即云:“今之公卿大夫,下逮士民,其婚丧葬祭皆无法度,唯听其为而莫之禁。”“乞诏谕礼官,先择《开宝通礼》论定而明着之,以示天下,违者有禁,断以必行。”①并云其士以上“当专用礼”,“虽未能下逮黎庶,而小人所视,足以成化”。其中已经明确官方礼典中存在的未能“下逮黎庶”缺陷。
正是以这种认知为基础,至宋哲宗元祐时,朝臣奏请中已经明确提出要修订“教民”之礼仪。右司谏朱光庭《上哲宗乞详议五礼以教民》疏中,即奏请举礼官参议“上自朝廷所行之制度,下至民庶所守之规矩”,著为一代之典,颁诸四海,以正人伦变礼俗。②太常博士颜复在上奏哲宗《乞详议五礼以教民》疏中更是直接指出:“士民之礼,踵历代之咎,未降彝制,下无矜式,使有志之士动虚名失实之叹。此甚可为治朝惜也。”认为民需教,“不教则失中,失中则流。祭享之礼不教,则流于祝襘佛齐。婚姻之礼不教,则流于委巷俚习。宾客之礼不教,则流于游衍嬉乐。师田之礼不教,则流于夷风暴俗。丧纪之礼不教,则流于道释数术”③。颜复不仅指出了制礼教民的急迫性,更对修订士民礼仪提出具体建议,亦即“会萃经史古今仪式至诸家祭法,岁荐时享、家范书仪之类可取者,高而不难,近而不迫,成士民五礼”。不必讲究古礼之冕服、礼器,不必要求古礼之币车、筵席,“就其便安”以为主。④换而言之,就是根据现世的实际情况制定“教民”的礼仪。值得注意的是,颜复对“教民”之礼的推行亦有建议,那就是颁布州县,“缓驱以令,使乐而不骇”,促使民众慢慢知晓其义,遵行其仪。总的来看,至于北宋后期,官僚士大夫层面无疑对修订和推行庶民礼仪、实现社会教化已经形成了清晰而稳妥的思路。《政和五礼新仪》专门庶民礼文的出现,显然也是这种思路和意图的体现。
对庶民礼仪的关注在南宋时期继续发展。绍熙中,礼官黄灏奏请于《政和五礼新仪》之内掇取品官、庶人冠昏丧祭礼仪,“摹印颁之郡县”,朝廷允从其奏,此即《政和冠昏丧祭礼》十五卷书。①将品官、士庶冠婚丧祭礼文专门摘录、刊印并颁发各州县地方,正是推行礼仪教化于庶民层面的重要举措。官僚士大夫们在任职地方之际,亦重视推行礼仪的实践。朱熹在泉州就曾提交《申严婚礼状》,其中有云:“仍乞备申使州,检会《政和五礼》士庶婚娶仪式行下,以凭遵守,约束施行。”②正是意在将政和礼典中个关于士庶的礼文规定专门录出颁行于地方之中,以促进庶民百姓的礼仪教化。
尽管庶民礼文的制定并不能说明礼制已经在实际上真正达于庶民生活之中,但是由开始关注修订庶民礼仪到“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遇民庶之家,有冠昏丧葬之礼,即令指受新仪”,官方礼制明确推行于庶民层面的倾向无疑是清晰的。也正是通过对庶民礼仪的修订和推行,官僚士大夫群体所主张的推行礼制、教化民众的意图才有可能更大意义上实现。需要指出的是,就宋代社会而言,官僚士大夫们对推行礼制于庶民层面的教化意图不仅表现在其敦促朝廷修订庶民礼文仪制,更表现在其自身积极修撰和遵行日趋“庶民化”的家礼的行为。二按循礼经、顺应世俗:
北宋家礼庶民化的迹象
唐宋时期,家礼的发展明确呈现出了独特的阶段性特征。唐代家礼修撰始终与世家旧族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家礼文本的著述者主要出身于世家旧族。其次,家礼修撰的事例亦主要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再次,承续礼经旧文而来的家礼修撰,与世家旧族的家学渊源和传承有着直接关系。唐代家礼的世家旧族色彩始终凸显,因此唐代家礼的行用始终有很大局限,并不具有广泛意义。与此相比,宋代家礼则呈现出了别样的面貌。北宋时代局限于世家旧族之中的全面承袭古礼仪制的家礼已基本上不复存在,由普通的科举官僚士大夫修撰并遵行的家礼,表现出了明显的远离经典旧文、参以时宜、遵从民俗的特征,其内容仪制所呈现出来了的庶民化亦日趋明显起来。换而言之,北宋家礼已经表现出了明确的下延及庶民层面的迹象。
北宋家礼的庶民化迹象,首先表现在其修撰者大多是普通的科举官僚士大夫,而其生活已经接近庶民生活层面。北宋家礼修撰和遵行引起士人的广泛关注,家礼影响日渐扩大,与社会变迁家族观念的淡化促成敬宗收族意识的兴起直接相关。然北宋家礼的影响能够超过前代,还有一点无疑不可忽视,北宋家礼修撰者多当朝之名人。据《宋史·艺文志》记载诸家礼文本撰作者,有名相贤相如杜衍、韩琦、司马光、吕大防;又有学古力行之士人宗师,如程颐、张载;其他几人虽不及杜、韩、司马之闻名于世,亦是一时翘楚、宋史有传之名臣,如吕大临、吕大钧,又如范祖禹。这些时代风标性人物修撰和积极遵行家礼,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家礼的影响。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名垂青史,但是不
能否认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科举入仕的普通官僚士大夫。宋代官学发展迅速,家学衰微,类似前代世家大族的家学渊源、礼学传承早已不再。因此,这些普通科举官僚修撰和遵行家礼,其顺应世俗、参以时宜的特点就尤为明显。
北宋家礼的庶民化迹象,还可以从具体礼文仪制规定的顺应世俗表现出来。细观北宋家礼仪制,可以发现,虽然仍有如杜衍家祭“守其家法,不迁于世俗”①这样的例子,但是“独杜氏守其家法,不迁于世俗”②的评语却恰恰表明北宋家礼整体而言与杜氏家礼明显有异,事实上诸家家礼清晰可见的正是“迁于世俗”,正是顺应世俗、参以时宜。例如,韩琦参合前代七家祭礼,撰述韩氏家祭礼十三篇,名曰《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其序中云:“采前说之可行,酌今俗之难废者,以人情断之”③,即采用前人家祭礼可行之于今者,并吸纳世俗之难以轻易废除者。正是由此,韩氏家祭式明确顺应世俗,在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废”。因其“虽出于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忘亲也”。④这种“迁于世俗”“参以时宜”的做法,在张载家礼中也有明显表露。《宋史·张载传》载“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朱熹更是明确指出张载制礼多不本诸《仪礼》,自有“独撰”。亦可知其对“世俗”“时宜”的考量和参用。⑤
司马光在家礼修撰方面卓有成就,其著述包括《书仪》《涑水祭仪》以及《居家杂仪》在内,详细规定了家族冠婚丧祭诸仪,尤其强调祭仪和居家杂仪。①今仅据《书仪》,②其沿用古礼而参以时宜、顺应今俗的特点清晰可见。《书仪》对冠婚丧祭等礼文仪式的规范,屡屡可见的是其行文之中“今从俗”、“且须从俗”、“今从便”之语。例如,“冠”中有礼宾之仪,注云:“今虑贫家不能办,故务从简易”。其实已经考虑到了士庶人家的财力有限,不能按循烦琐古礼行事。又如,“婚仪”中亲迎前一日,有“女氏使人张陈其婿之室”之仪,注云:“俗谓之铺房,古虽无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废也。”亦是顾及到了世俗民情。后人或以为司马光家礼“从俗”最显著者,在于新妇入门拜先灵(祖祢)于影堂而废“三月庙见”的古礼。司马光在此注文中云:“古无此礼,今谓之拜先灵,亦不可废也。”设影堂以祭祖是北宋官僚士大夫家族时俗,《书仪》设有专门影堂祭祀以及影堂杂仪的条目,正是顺从这一世俗而来。但是恰恰这一设置,说明《书仪》家礼规范对象主要是仍是官僚士大夫群体,而非是普通庶民百姓。由此我们在理解韩琦、张载等人家礼中的顺应世情民俗的时候,也就不能将其对普通民俗的参酌估计过甚,因为其同样是主要针对官僚士大夫家族的仪制规定。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的是,北宋家礼是在按袭古礼旧文的基础上,比唐代家礼更为明确地加入了世俗、时宜的因素,更趋从俗、从众、从简易,亦更趋接近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
北宋家礼的庶民化迹象,亦可以从居家杂仪的关注上表现出来。《宋史·艺文志》列北宋时期的10部家礼,家祭礼有8部,家礼修撰主要集中于祭礼,显然承继了唐代家礼修撰的传统,这与自古以来的祭祖为家族重事有关。韩琦、司马光等人亦正是出于对士人之家祭祀“多苟且不经”、官僚之家祭如同闾巷庶民有着清晰的认知,才关注和强调家祭礼仪的规范,但顺应世俗、不违孝子之情的做法使其家祭礼中依然表现出了接近闾巷庶民的迹象。与此8部家祭礼不同,另外两部亦即司马光所著的《书仪》和《居家杂仪》,除了规范冠婚丧祭礼诸仪之外,却表现出了对日常居家杂仪的特别强调。司马光专门撰写了单行本的《居家杂仪》,又在《书仪》一书中专列“居家杂仪”篇。《书仪》卷四“婚仪下”中列有“居家杂仪”,其名目包括凡家长御群子弟及家众、凡诸卑幼事家长、凡为子妇者事父母舅姑、凡为人子弟者事父兄宗族、凡为人子者事父母、凡子妇侍父母舅姑疾、凡为宫室、凡卑幼于尊长、凡节序及非时家宴、凡子始生即教育、凡内外仆妾事主人等等内容,涉及家族内各成员的礼仪规范、日常居家的各个方面。居家杂仪的单独提出、专门规定,是对日常居家生活礼仪的规范和特别强调,这是唐代家礼中关注尚少的内容,无疑是对家礼修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和扩充。居家杂仪的突出规定,表明了北宋家礼日趋接近普通士庶生活层面的现实。
检视家礼的发展历程可见,依据礼经旧文编撰家礼是南北朝世家大族的风习,唐代家礼修撰正是南北朝世家大族撰制家
礼风习的延续。也正是在此传承礼经旧文的趋势特征中,关注冠婚丧祭诸仪而忽视日常居家礼仪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局面,根源在于无论是南北朝的门阀士族还是唐代的世家旧族,其家学渊源、礼学传承都是非常明显的,所谓风教“整密”,垂髫换齿之时“便蒙诱诲”,习得“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①,因此居家日常行为规范并无需要特别关注。然至于宋代,世家旧族早已沦丧,不为人知,家学渊源、礼学传承更不见于私家,兴起于普通士庶层面的科举官僚士大夫们按循礼经、参以时宜、顺从世俗编撰家礼仪制之际,不仅要关注冠婚丧祭诸仪,更要专门关注家族成员的日常行为规范、居家生活的日常礼仪约束。因此,对这种居家杂仪的关注,正反映了北宋家礼日趋接近士庶民众生活层面的趋势特征。
总的来看,以《书仪》为代表的北宋家礼,在按循礼经旧文的基础上,参以时宜、顺应民俗的主旨明确,日趋接近士庶百姓的生活实际,表现出了一定的庶民化的迹象。尽管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家礼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针对自家修订的礼仪规范,因此这种“接近”依然有限,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并未能有更大程度上直白地显露和进展。然这种庶民化迹象的影响依然不可低估,作为宋代家礼庶民化的标志性成果的《朱子家礼》的修撰,正是以北宋家礼的发展演进为基础的。三变古适今、简而易行:《朱子家礼》
庶民化倾向的标识
北宋时期,由于前代世家旧族沦胥不再,崔卢李郑之流为世人所不闻,在家学渊源中断,官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古礼传承无疑已经在事实上为世人所忽视。由此科举官僚家族的家礼修撰和遵行,表露出了鲜明的参以时宜、顺应世情民俗的特点,日趋接近庶民生活实际的趋势。至于南宋时代,家礼则更进一步演化为凸显变古适今原则的普及于士庶之间的明确庶民化的仪制规范。
《宋史·艺文志三》记载南宋家礼文本有朱熹《二十家古今祭礼》二卷①、《四家礼范》五卷②、《家礼》一卷③,赵希苍《赵氏祭录》二卷、李宗思《礼范》一卷、周端朝《冠婚丧祭礼》二卷(集司马氏、程氏、吕氏礼),高闶《送终礼》一卷④等。上述家礼著述者5人,可考身世者4人。与北宋家礼修撰者类似,基本都是官僚士大夫。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宗思曾“从朱子学”①,周端朝亦曾“从朱晦庵武夷读书”②,二者作为朱熹门生,其家礼修撰显然是受到朱熹的影响。从上面所列家礼名目亦可看出,与北宋家礼修撰不同,一是家祭礼虽然依然得到关注,但不再是家礼修撰的绝对重点和主要方向,南宋家礼修撰中关注冠婚丧祭诸项礼仪规范的著述比重增大;二是重视对以往朝代家礼著述的汇总和总结,而此正表明了南宋家礼修撰中直接审视和总结前代家礼著述的倾向。正是在充分审视和总结前代家礼著述的基础上,南宋官僚士大夫们对家礼修撰顺应世俗人情的认知更加明确,徐度评价韩琦家祭礼顺应世俗民情时曾云:“其说多近人情,最为可行。”③朱熹评价司马光《书仪》亦曾云:“读者见其节文度数之详,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见习行,而已有望风退怯之意。又或见其堂室之广,给使之多,仪物之盛,而窃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书虽布,而传者徒为笥箧之藏,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④在此番评述中,朱熹指出司马光家礼对古礼仪节仪物的削减幅度还有局限,幅度还不够大,不能更大意义上接近普通士庶的生活实际,因此传布者虽众但往往不见习行,影响了推广行用。显然朱熹关注的已经是家礼能否接近普通士庶的生活实际,能够真正传布推广的问题了。因此,朱熹撰制《家礼》,与北宋家礼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是由削减古礼烦琐之仪节到直接变易、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其为普通士人、庶民修礼的意图和主张。
首先,朱熹明确阐释其修撰《家礼》的目的,欲推行礼仪规范于士人与庶民之中,既面向好礼之士人,亦针对“贫窭”的庶民层面。朱熹在《家礼·序》文中云:
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用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
按此,朱熹撰制《家礼》的出发点正是基于此前君子所撰家礼的不能行用,自己要撰制家礼欲使好礼之士能遵礼仪、贫窭庶民之家亦能及于礼。与北宋家礼修撰更多是用于自家族内相比,朱熹在修撰《家礼》之初,就明确了将《家礼》推行开来的目的,欲推行的范围从好礼之士到贫窭之家,换而言之,其不仅是欲推行于士人层面,更是要推行于庶民层面。所谓“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正彰显了朱熹意欲为士庶广泛层面制定家礼规范的主张和宗旨。而此欲广泛推行于庶民层面的做法,无疑比北宋家礼修撰有了更进一步的推进和发展。
也正是由此目的出发,朱熹在《家礼·序》中还阐释了修撰家礼的原则,亦即变古适今,所谓变古适今就是在遵行古礼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更大程度上的改变古礼以适应今世,朱熹的具体做法就是略去浮文缛节,强调礼之名分本实。谨名分、崇敬爱以为之本,略浮文而务本实。所以,有学者明确指出,《家礼》“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专用的‘贵族之礼’,而是通用于整个
社会的、更多地考虑到社会普通家庭的‘庶民’之礼”①。显然,《家礼》的庶民化倾向已经在其修撰目的、修撰原则上清晰地表露出来。
其次,《家礼》的“通礼”设置充分体现了其庶民化的倾向。朱熹在《家礼·序》文中明确提出了礼之本的观点,认为:“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者,其本也。”又言到,“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因此,《家礼》开篇第一卷即是“通礼”,“此篇所著,皆所谓有家日用之常礼,不可一日而不修者。”强调的正是日常所行之礼仪,所谓务本实也。而此篇之首要内容“祠堂”,正是其所强调的务本实的关键。朱熹曰:
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
显然,朱熹针对庙制不行而士庶层面又财力有限,提出了祠堂的建制,且祠堂相关仪制体系所用亦多为俗礼,亦正是顺应民情的做法。祠堂具体规制明确考虑士人以及庶民之行用需要,财力限制,力求符合士人及庶民的生活实际。例如,“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按其规定: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若按此规制,则祠堂之建制亦可谓繁杂,非普通庶民之力可以达到。朱熹遂又有曰:
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正寝谓前堂也。地狭,则于厅事之东亦可。
按此记述可见,朱熹在针对官僚士大夫之家或者说财力相当之家规定了较为繁复的三间式祠堂建制的同时,又考虑到了财力贫窭的庶民之家的实际情况,而阐释了一间式祠堂的建制,更甚至提出了“厅事之东”式的祠堂建制。由此言之,朱熹在撰制祠堂规制之时,具体考虑到了普通士庶层面的各种情况,使祠堂规制能够符合士人乃至庶民层面的需求。
此外,祠堂相关仪制内容,朱熹也明显考量了士庶的生活实际、风俗人情。例如,祠堂祭礼时日规定,沿承古代祭祖“正至、朔望则参”的同时,又规定了“俗节”的祭献,曰:“俗节则献以时食。”注文云:“节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阳之类。凡乡俗所尚者,食如角黍;凡节之所尚者,荐以大盘,问以蔬果。礼如正至、朔日之仪。”这一规定顺应乡俗人情,明显是迎合士庶社会层面的风俗习惯的一种举措。而祠堂“有事则告”诸仪亦同样体现了对庶民的考虑,所谓有事则告之“事”,既包括了告授官、告贬降、告追赠等官僚士人家族官品升降之事,还包括了生嫡长子、冠、婚等普通士人、庶民之家皆有的家族重事。对先祖的称呼,亦着意于既可适合官僚士人之家,亦可行用普通庶民之家,其规定“有官封谥则皆称之;无则以生时行第称号,加以府君之上。妣曰‘某氏夫人’”。除了祠堂诸制明显表露对普通庶民的考量外,“居家杂仪”列入“通礼”卷,也充分体现了其对士人、庶民之家的日常家居礼仪规范的重视和强调。
再次,《家礼》中冠婚丧祭诸仪的内容规定,也充分表露出其
庶民化的倾向。朱熹《家礼》五卷,观其篇目,与司马光《书仪》大体类同,甚至一半以上的文字语句援引了《书仪》的内容。①然细读其中冠婚丧祭诸礼之程序步骤、仪式仪物,其与《书仪》的差异明显可见,《家礼》冠婚丧祭诸礼仪式程序显然更趋简单易行。如冠礼仅存告于祠堂、戒宾、宿宾、陈冠服、三加、醮、字冠者、见尊长、礼宾等大仪节。如婚礼程序简化,将古礼之婚六礼削去其三。《书仪》婚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妇见舅姑、婿见妇之父母八项内容,前六项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是为古礼之婚礼“六礼”。《家礼》婚礼仪节包括纳采、纳币、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婿见妇之父母六项内容,明显改易了传统婚礼“六礼”为“三礼”即“纳采、纳币、亲迎”。而即使是此“纳采、纳币、亲迎”三项,其仪式记述亦非拘泥于繁文缛节、厅事仪物,只着重简述仪式过程而已。“庙见”是将古制“三月而庙见”简化为三日“以妇见于祠堂”。再如丧礼,则将《书仪》的三十七节削至二十一节。古礼丧葬甚为烦琐,《书仪》丧仪即包括从初终、复以至祔、小祥、大祥、禫祭等共计37项内容,而《家礼》丧仪却只有初终、沐浴、袭以至祔、小祥、大祥、禫等21个仪式,其对丧礼仪节步骤的变易无疑是十分明显的。较之《书仪》,《家礼》丧仪的叙述文字更趋简洁明了,“节次也更为分明”②。
《家礼》中冠婚丧祭诸仪不仅程序明显简略,行文清晰简明,更重要的是具体仪式规定也力求简单易行,注意考虑庶民之家的财力状况。例如“昏礼”中“纳币”仪节,即曰:“币用色缯,贫富随宜,少不过两,多不逾十,今人更用钗钏、羊酒、果实之属,亦可。”宋时婚礼多重烦琐,纳币聘财亦以多为尚,官僚士大夫层面更是崇尚聘财嫁资,而普通庶民之家往往不行礼仪,更无论婚礼诸节。朱熹意欲推行礼仪于庶民层面,其在尽力简化、省略婚礼仪节程序之同时,明确减少聘财之数量,以使普通庶民之家亦可能遵行简化之后的婚礼仪节。又如,“祭礼”中即明确说明:“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筋力而行之,财力可及者,自当如仪。”所谓称家之有无,实际上是对应礼器、祭品诸事而言,所谓量筋力而行之,实际上是针对施行祭礼时斋戒、省牲、涤器、具馔以及三献诸仪节而言的。此番特别说明,实质是对普通庶民而言,宣扬了一种祭祖贵诚心爱敬而非执着于礼器、祭品以及周备仪节,在能力不及的情况之下,量力而行亦是对祖宗的爱敬呈现,并非是不敬祖先。显然,朱熹的这种有力则如仪、无力则量力即可的主张,对于祭祖之礼能够为更为广泛的庶民层面接受和遵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朱子家礼》不仅彻底改变了儒家礼经旧文仪节繁缛的贵族面孔,甚至也脱离了北宋时代家礼离古不远的状态,成为充分考量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庶民婚丧嫁娶、日常居家生活的一部“庶民之礼”①。当然,庶民化的《家礼》的出现并非偶然,其与宋初以来官僚士大夫们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倾向直接联系在一起,更与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的紧密关联。换句话说,南宋时期庶民化的《家礼》的出现和推行,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
始终贯穿着重本实、轻浮文而量力行礼的主张的《朱子家礼》,正顺应了宋代官僚士大夫传布礼制以教民化俗的追求,因此其书一旦面世即引发关注,加以朱门弟子的大力刊印和注释,故很快便在社会上广泛传布开来。元代《朱子家礼》影响渐及南北,至于明代成为朝廷明确要求士庶之家遵行的礼文范本,其书更传布于日本和朝鲜,在朝鲜半岛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局面的出现,恰恰与《朱子家礼》的鲜明的庶民化倾向直接相关。
附注
①王美华、耿元骊,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
②关于此点可参见周鑫《(朱子家礼)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32—446页。
①任爽在《唐代礼制研究》中指出:《开元礼》确有以朝廷之礼为中心,重上轻下之弊(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杨志刚也谈道:庶人不是《大唐开元礼》的制礼对象,仅在为区别和强调等级差异时,才于相关条文下以附记形式,用片言只字指明庶人该行何礼(《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①《宋朝诸臣奏议》卷九六,吕大防《上神宗请定婚嫁丧祭之礼》。
②《宋朝诸臣奏议》卷九六,朱光庭《上哲宗乞详议五礼以教民》。
③《宋朝诸臣奏议》卷九六,颜复《上哲宗乞详议五礼以教民》。
④《宋朝诸臣奏议》卷九六,颜复《上哲宗乞详议五礼以教民》。
①《文献通考》卷一七八,经籍考一四。
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〇。
①《欧阳修集》卷三一《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衍)墓志铭》。
②徐度《却扫编》卷中。
③《安阳集》卷二二《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序》。
④《却扫编》卷中。
⑤《朱子语类》卷八四《论后世礼书》。
①王立军《试论司马光礼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文中认为:《书仪》这种家礼格局,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庭礼仪系统,为后世家庭礼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都学刊》,2001年3期,第47—50页)。
②《书仪》(或称《司马氏书仪》),卷一为有关表奏、公文、私书、家书格式;其后分别是卷二为冠仪,包括冠、笈、堂室房户图、深衣制度;卷三为婚仪,包括婚、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妇见舅姑、婿见妇之父母,卷四中还列居家杂仪;卷五至卷一○为丧仪的内容,其中,卷六有“五服制度”、“五服年月略”,卷九有“居丧杂仪”,卷一〇有“祭”与“影堂杂仪”。此书中,书札体式占据很小比重,除了卷一之外,只有卷九的“居丧杂仪”后附书式20则,关于讣告、吊丧、慰问以及居丧期间往来的书信体例,卷一〇的“影堂杂仪”后附书式6则,关于举行拜祭祖先礼仪仪式与家族成员之间的书信体例。可以说,司马光《书仪》一书,虽以书仪为名,但是重点是对冠、婚、丧、祭诸礼仪的修撰。因此比之前代书仪著述而言,此书虽用书仪之名,但却是家礼之实,亦被认为是北宋最著名的家礼文本(今据《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
①《颜氏家训》序致第一。
①《直斋书录解题》卷六云:《古今家祭礼》20卷,朱熹集《通典》《会要》所载以及唐本朝诸家祭礼皆在焉。
②《直斋书录解题》卷六云:《四家礼范》五卷,张栻、朱熹所集司马、程、张、吕氏诸家,而建安刘珙刻于金陵。
③《直斋书录解题》中亦载为一卷,又据《家礼·点校说明》之考证,可知《家礼》版本比较明确的有五卷本、十卷本、不分卷本和七卷本等。本文所依据为收入《朱子全书》的五卷本《家礼》。
④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载曰:“《高氏送终礼》一卷,礼部侍郎高闶抑崇撰。”而此书又有《厚终礼》之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〇二载,绍兴十四年,时高闶为礼部侍郎,患近世礼学不明,凶礼尤甚,著《厚终礼》。《延祐四明志》卷四载,高闶“又集《厚终礼》一编,行于世,朱文公定《家礼》多用之。”①(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〇载:李宗思,建安人,从朱子学。朱子称其教深好修,笃志问学,登隆兴元年进士,为蕲州教授。
②《宋史》卷四五五《杨宏中传》中有云:“端朝字子静,嘉定三年试礼部第一,终刑部侍郎兼侍讲。”未言及其他。又据《宋诗纪事》卷六一记云:周端朝字子靖,永嘉人,从朱晦庵武夷读书。登嘉定四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谥文忠。
③《却扫编》卷中。
?《晦庵集》卷八三《跋三家礼范》。
①参见《朱子全书》之《家礼·校点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58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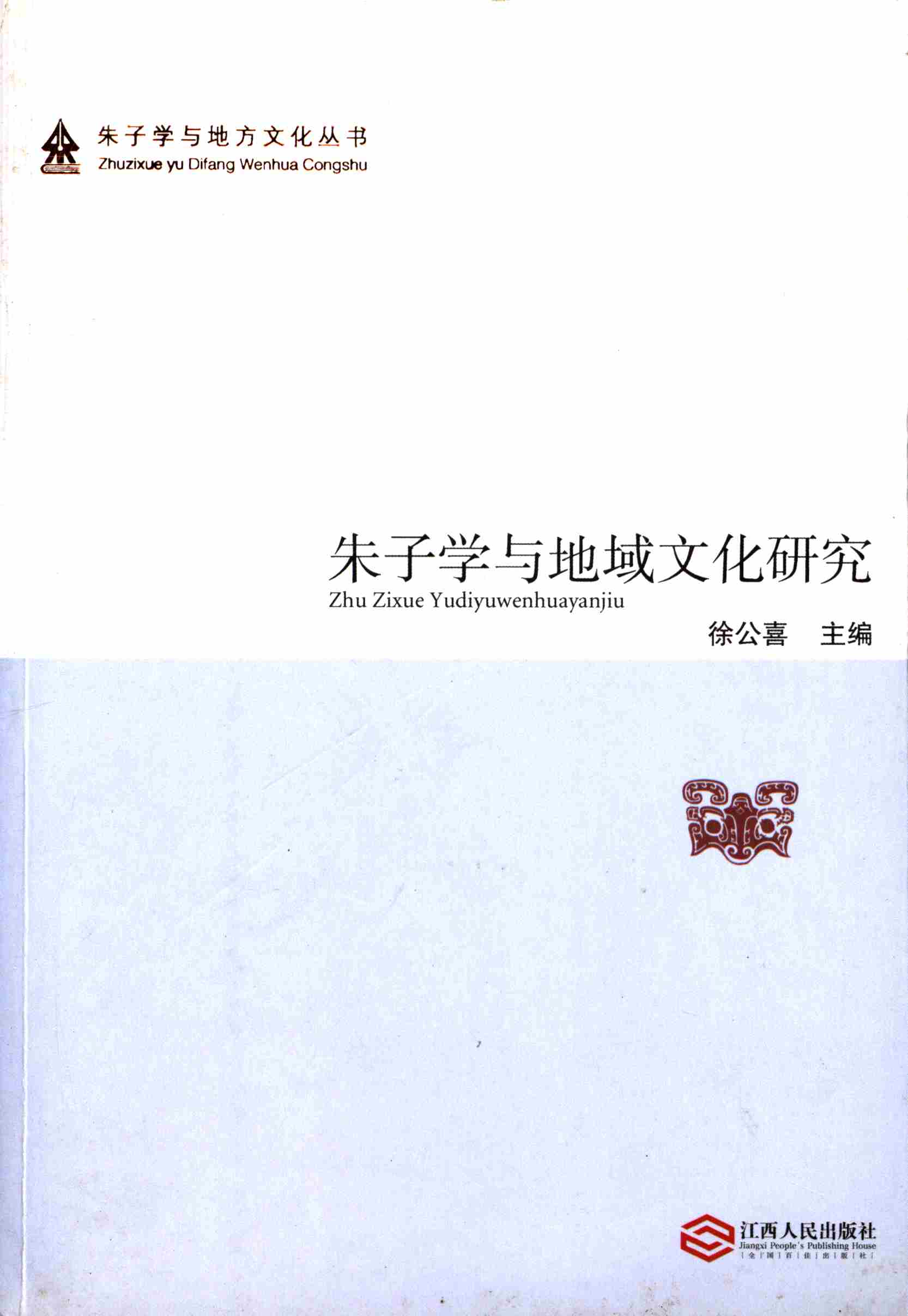
《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2013年“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研讨会的成果汇编,收录《新安理学特质》、《试论饶鲁的学术思想与心学化的双峰学派》、《朱子理学与关帝信仰》、《韩国九曲园林雏形阶段》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