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学研究的升温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6》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342 |
| 颗粒名称: | 三、经学研究的升温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4 |
| 页码: | 197-20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子经学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对各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将其著作成为后代科举考试的标准。在近年来的研究中,经学成为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焦点,特别是对《四书》的研究。朱子对《四书》进行了新的解释,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义理系统,并改变了对五经的认识。此外,朱子的注释著作《四书集注》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成为朱子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在具体章句的阐释中,特别关注《大学》的“格物致知”论以及《中庸》的诠释。此外,朱子的经学研究还涉及《尚书》、《孝经》、《易经》等经典的解释。尽管朱子经学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但仍有一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关注。 |
| 关键词: | 朱子学 文献整理 经学研究 |
内容
朱子经学是中国经学史的重要一环,他继承汉唐经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但在根本气质上与之不同。朱子基本上遍著群经,对各经都有论述。其经学著作更是成为后代科举考试的标准。清代考据学兴起,清儒虽然不同意朱子经学的阐释,但在研究上也绕不开朱子的经学著作。在以往的朱子学研究中,经学不是一个关注热点,而近些年,经学研究不断升温。
朱子所著的《四书集注》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教科书,“《四书》学”因此是朱子经学研究中的重点。
在《四书》与“五经”的关系上,陈壁生教授有《朱熹的〈四书〉与“五经”》[38]一文,他指出朱子“对《四书》的新解释,创造性地提出新的义理系统,其主旨在于求圣人之心,以提升个人道德;同时,又在此基础上改造‘经’的观念以及对五经的认识。汉唐经学求‘圣人之法’,朱熹把经视为‘圣人之心’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五经进行了内在化解读,将五经《四书》化。这样,五经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四书》总论方面,许家星教授有《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一文,指出朱子四书的形成贯穿其毕生,大致可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其间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或各书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应特别注意的是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至于《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包含丁酉年(1177)《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个不同时期、层次的著作,不可视而为一。顾宏义教授出版了《宋代〈四书〉文献论考》[40]一书,该书专为考辨两宋时期《四书》著述与相关文献而作。分为上下编,上编论及《四书》文献兴盛的社会背景、出版传播及其与程朱理学的发展等,下编则具体对宋代学人有关《四书》的著述进行逐人逐书的考证,廓清了有关《四书》记载的讹误和缺失。闫春则有“从朱子到朱子后学:元明清四书学研究(2014)”一课题,尝试将朱子及朱子后学四书义理的动态演进问题予以凸显。
在《四书》各个文本的阐释上,《大学》的“格物致知”论一直以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近些年依旧如此,前述上海学者对朱子工夫论重视即是一例。此外如杨祖汉教授《西方认识论还是儒家工夫说——谁误读了“格物致知”?》[41]一文,从中西哲学对比的角度揭示朱子“格物致知”的含义,现代学人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逻辑体系是“误读”了朱熹。在朱熹思想体系中,格物致知论并不能等同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而是关于如何实现和完成修己治人的工夫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的作用被研究者夸大了,如乐爱国教授就重视朱子的《中庸》诠释。乐爱国教授有《朱子〈中庸章句〉论“诚”及其与“三达德”“五达道”的关系》[42],从“诚”出发,尝试系统分析朱子的《中庸》解释;又有《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43],关注朱子思想背后的生态观;又有《“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44]一文,认为朱子思想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近些年,乐爱国教授特别强调《中庸》在朱子思想结构中的地位。此外,围绕朱子《四书》具体章句的义理分析的论文更是层出不穷,本文不一一列举。
在“《尚书》学”研究方面,陈来先生有《“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45]一文,指出“在经典的诠释上,朱子对‘极’的解释最早为中年时代对《太极图说》的解释;在朱陆太极之辩中朱子承继和发展了其关于‘极’的理解,形成一套有关‘极’的理论,并在讨论太极之义时论及皇极之义。在朱陆太极之辩后不久所作的《皇极辨》之中,朱熹把这一套理解运用于皇极说作为一种基础,又以君主正身修身的儒家表率说把‘建用皇极’的意义具体化,形成朱子学的皇极说。皇极说既是朱子政治思想的一个论述,也同时可以看作其哲学太极论的相关部分,在后世发挥了持续的影响”。陈先生将朱子对经典的诠释及其义理阐发之间的关系充分地展现了出来。此外,陈良中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朱子〈尚书〉学研究》[46]一书,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宋代《尚书》学背景下的朱子《尚书》学,尤其是其理学诠释特色,考察了朱子对《尚书》阐释的历史,以及解经方法和价值取向,并关注朱子阐释与蔡沈《书集传》的关系,考察了朱子《尚书》学的影响。
礼学则是朱子经学研究这几年来特别突出的一个面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朱子的礼学,尤其注意探讨“礼与理”的关系。如冯兵教授《“理”“礼”会通,承扬道统》[47]一文,认为朱子“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辩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殷慧、张卓合写的《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48]一文,则从朱子的《大学》诠释出发,认为“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两文一从朱子的思想系统出发,一从朱子的经典诠释出发,代表了理解“礼”与“理”关系的两个向度。
张凯作博士《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49]一文着重论述朱子以“理”出发的“礼”学和前代礼学的继承关系,在她看来,“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朱子对古代礼教的最主要的传承即在于他对个人心性修养之学的发扬”。
与哲学上的鬼神问题直接相关,有学者关注朱子对于祭礼的讨论,尤其是其理学思想与儒家传统祭礼之间的张力。如殷慧教授《祭之理的追索——朱熹的鬼神观与祭祀思想》[50]即认为,“朱熹从义理层面论述了祭祀与鬼神的关系:强调鬼神的本体论意义,重视其天地转化的功能;认为鬼神既是阴阳二气物质,也是二气相互作用、转化的功用与性质。朱熹的祭祀思想与实践引人注目,强调义理与礼制并举”。
在《孝经》学方面,唐文明教授有《朱子〈孝经刊误〉析论》[51]一文,他认为“《孝经刊误》表达了朱子试图将《孝经》纳入其四书学的努力,而从《孝经刊误》的后世影响来看,朱子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过,如果考虑到《孝经》本来的思想旨趣,我们不能不说,朱子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陈壁生教授《〈孝经〉学史》[52]一书第六章第一节也专门讨论了朱子的《孝经》诠释。
《易》学一直以来是朱子经学阐释的另一重镇,尤其是围绕着《周易》展开的义理诠释,以往对朱子《易学》的研究较为充分,而近些年的研究热点则不太明确。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对朱子象数易学研究得不是太多,陈睿超博士《略论朱子之先天〈横图〉》[53]则特别关注这点,文章认为“朱子在虽在易学研究方面对北宋邵雍的先天易学推崇有加,但处于其对先天学理解之核心的先天《横图》却并非对邵雍原旨的忠实继承。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横图》中两仪、四象、八卦的名称与邵雍《观物内篇》所述不同;第二,《横图》八卦卦序与《观物内篇》所述不符;第三,《横图》变换为《圆图》的过程有涉安排,不够自然;第四,依《横图》卦序对《圆图》顺逆方向的解释与邵雍本意有异。朱子对邵雍的先天学并非完全继述,而有自己的改造与发挥,不加区分地以朱子之《横图》解释邵雍易学思想的做法是不够严谨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关于朱子经学研究已经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但还是有一些不足。如《仪礼经传通解》仅在文献上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而对其义理阐发则远远不够。在《诗经》学方面,学者们主要侧重在对《诗集传》赋比兴等手法的研究以及朱子诗论与其他人的比较上,相关哲学义理性阐发则很有限。朱子虽然未注《春秋》,但其有《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传世,并对东亚产生重要影响,而关于该书也缺乏文献、义理的进一步关注。
朱子所著的《四书集注》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教科书,“《四书》学”因此是朱子经学研究中的重点。
在《四书》与“五经”的关系上,陈壁生教授有《朱熹的〈四书〉与“五经”》[38]一文,他指出朱子“对《四书》的新解释,创造性地提出新的义理系统,其主旨在于求圣人之心,以提升个人道德;同时,又在此基础上改造‘经’的观念以及对五经的认识。汉唐经学求‘圣人之法’,朱熹把经视为‘圣人之心’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五经进行了内在化解读,将五经《四书》化。这样,五经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四书》总论方面,许家星教授有《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一文,指出朱子四书的形成贯穿其毕生,大致可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其间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或各书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应特别注意的是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至于《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包含丁酉年(1177)《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个不同时期、层次的著作,不可视而为一。顾宏义教授出版了《宋代〈四书〉文献论考》[40]一书,该书专为考辨两宋时期《四书》著述与相关文献而作。分为上下编,上编论及《四书》文献兴盛的社会背景、出版传播及其与程朱理学的发展等,下编则具体对宋代学人有关《四书》的著述进行逐人逐书的考证,廓清了有关《四书》记载的讹误和缺失。闫春则有“从朱子到朱子后学:元明清四书学研究(2014)”一课题,尝试将朱子及朱子后学四书义理的动态演进问题予以凸显。
在《四书》各个文本的阐释上,《大学》的“格物致知”论一直以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近些年依旧如此,前述上海学者对朱子工夫论重视即是一例。此外如杨祖汉教授《西方认识论还是儒家工夫说——谁误读了“格物致知”?》[41]一文,从中西哲学对比的角度揭示朱子“格物致知”的含义,现代学人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逻辑体系是“误读”了朱熹。在朱熹思想体系中,格物致知论并不能等同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而是关于如何实现和完成修己治人的工夫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的作用被研究者夸大了,如乐爱国教授就重视朱子的《中庸》诠释。乐爱国教授有《朱子〈中庸章句〉论“诚”及其与“三达德”“五达道”的关系》[42],从“诚”出发,尝试系统分析朱子的《中庸》解释;又有《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43],关注朱子思想背后的生态观;又有《“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44]一文,认为朱子思想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近些年,乐爱国教授特别强调《中庸》在朱子思想结构中的地位。此外,围绕朱子《四书》具体章句的义理分析的论文更是层出不穷,本文不一一列举。
在“《尚书》学”研究方面,陈来先生有《“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45]一文,指出“在经典的诠释上,朱子对‘极’的解释最早为中年时代对《太极图说》的解释;在朱陆太极之辩中朱子承继和发展了其关于‘极’的理解,形成一套有关‘极’的理论,并在讨论太极之义时论及皇极之义。在朱陆太极之辩后不久所作的《皇极辨》之中,朱熹把这一套理解运用于皇极说作为一种基础,又以君主正身修身的儒家表率说把‘建用皇极’的意义具体化,形成朱子学的皇极说。皇极说既是朱子政治思想的一个论述,也同时可以看作其哲学太极论的相关部分,在后世发挥了持续的影响”。陈先生将朱子对经典的诠释及其义理阐发之间的关系充分地展现了出来。此外,陈良中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朱子〈尚书〉学研究》[46]一书,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宋代《尚书》学背景下的朱子《尚书》学,尤其是其理学诠释特色,考察了朱子对《尚书》阐释的历史,以及解经方法和价值取向,并关注朱子阐释与蔡沈《书集传》的关系,考察了朱子《尚书》学的影响。
礼学则是朱子经学研究这几年来特别突出的一个面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朱子的礼学,尤其注意探讨“礼与理”的关系。如冯兵教授《“理”“礼”会通,承扬道统》[47]一文,认为朱子“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辩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殷慧、张卓合写的《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48]一文,则从朱子的《大学》诠释出发,认为“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两文一从朱子的思想系统出发,一从朱子的经典诠释出发,代表了理解“礼”与“理”关系的两个向度。
张凯作博士《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49]一文着重论述朱子以“理”出发的“礼”学和前代礼学的继承关系,在她看来,“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朱子对古代礼教的最主要的传承即在于他对个人心性修养之学的发扬”。
与哲学上的鬼神问题直接相关,有学者关注朱子对于祭礼的讨论,尤其是其理学思想与儒家传统祭礼之间的张力。如殷慧教授《祭之理的追索——朱熹的鬼神观与祭祀思想》[50]即认为,“朱熹从义理层面论述了祭祀与鬼神的关系:强调鬼神的本体论意义,重视其天地转化的功能;认为鬼神既是阴阳二气物质,也是二气相互作用、转化的功用与性质。朱熹的祭祀思想与实践引人注目,强调义理与礼制并举”。
在《孝经》学方面,唐文明教授有《朱子〈孝经刊误〉析论》[51]一文,他认为“《孝经刊误》表达了朱子试图将《孝经》纳入其四书学的努力,而从《孝经刊误》的后世影响来看,朱子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过,如果考虑到《孝经》本来的思想旨趣,我们不能不说,朱子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陈壁生教授《〈孝经〉学史》[52]一书第六章第一节也专门讨论了朱子的《孝经》诠释。
《易》学一直以来是朱子经学阐释的另一重镇,尤其是围绕着《周易》展开的义理诠释,以往对朱子《易学》的研究较为充分,而近些年的研究热点则不太明确。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对朱子象数易学研究得不是太多,陈睿超博士《略论朱子之先天〈横图〉》[53]则特别关注这点,文章认为“朱子在虽在易学研究方面对北宋邵雍的先天易学推崇有加,但处于其对先天学理解之核心的先天《横图》却并非对邵雍原旨的忠实继承。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横图》中两仪、四象、八卦的名称与邵雍《观物内篇》所述不同;第二,《横图》八卦卦序与《观物内篇》所述不符;第三,《横图》变换为《圆图》的过程有涉安排,不够自然;第四,依《横图》卦序对《圆图》顺逆方向的解释与邵雍本意有异。朱子对邵雍的先天学并非完全继述,而有自己的改造与发挥,不加区分地以朱子之《横图》解释邵雍易学思想的做法是不够严谨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关于朱子经学研究已经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但还是有一些不足。如《仪礼经传通解》仅在文献上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而对其义理阐发则远远不够。在《诗经》学方面,学者们主要侧重在对《诗集传》赋比兴等手法的研究以及朱子诗论与其他人的比较上,相关哲学义理性阐发则很有限。朱子虽然未注《春秋》,但其有《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传世,并对东亚产生重要影响,而关于该书也缺乏文献、义理的进一步关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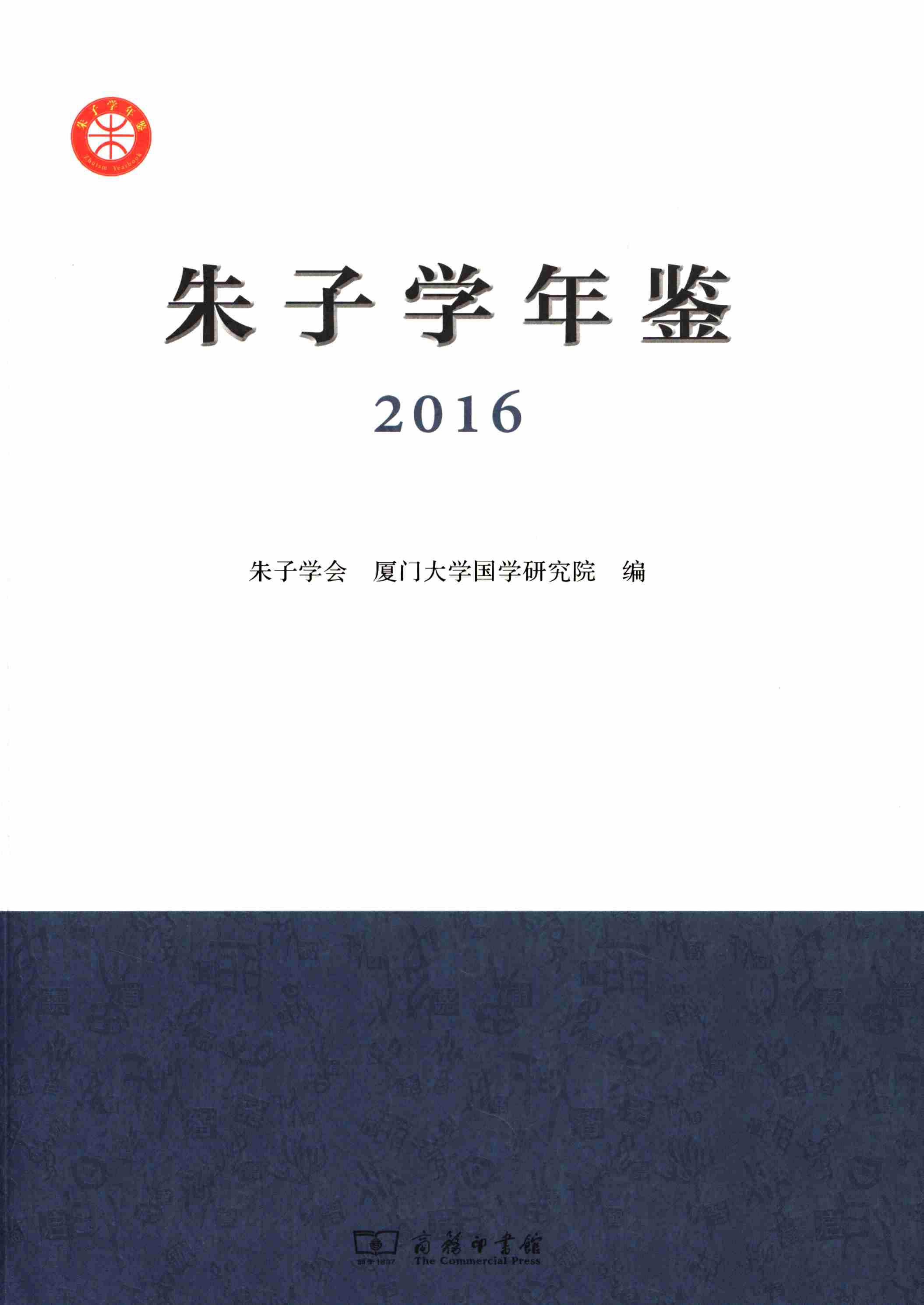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6》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年鉴内容设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9个栏目。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