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6》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320 |
| 颗粒名称: | 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1 |
| 页码: | 149-209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朝鲜朝后期实学家对朱子学的研究和发展。通过分析这些实学家在朱子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说明了朱子学在朝鲜朝后期的重要性。 |
| 关键词: | 朝鲜朝后期 实学家 朱子学 |
内容
2016年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
⊙杨得煜
笔者从台湾2016年的期刊论文当中,分别摘录数篇来进行说明[1,所摘录论文以台湾重要期刊、重要学者或对朱子义理有新意之学者为主要依据。所选择的论文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宋明理学当代诠释(心性论与工夫论)。第二,东亚朱子学。第三,比较哲学。第四,清代朱子学。
为了让读者快速掌握到这些学者之研究成果,笔者以论文问题意识、论文架构、论文摘要等三大项之方式作为架构。这样的架构分类可以帮助读者清楚掌握到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证成的程序与结论。
一、宋明理学当代诠释(心性论与工夫论)
1.黄莹暖:《再论朱子之心》,《鹅湖学志》第56期(2016年6月),第113~139页。
(1)问题意识
在朱子心性论当中,“心”之概念在当代朱子学研究当中,存在着“认知心”与“道德本心”两种解释空间。当代新儒家杨祖汉教授指出:性理能随时显于心,心对性理本有所知。从这意义来看,朱子言“心”是一具有道德自觉的能力,并非只是一“形下”意义的“认知心”。黄教授以杨祖汉教授理论为机模,尝试从“恶的产生”与“善端发露”两个进路,以对朱子“心义”提供更多的视角。
(2)论文架构
论文共有两大章节,第一节:从恶之产生与善端之发的论述看朱子之心;第二节:心之虚灵知觉的道德属性。在第一节中,分析朱子理论中,恶的产生是由心失其主所致;善的发端时私欲经常随起夹杂。第二节,则是分析《中庸章句序》中的“人心”“道心”概念。
(3)论文摘要
黄教授在论文中指出,第一,恶的产生并非由天赋气禀所决定,亦并非由气机之偶然或其障蔽所致。人之所以流为不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心的自我放失懈怠。第二,虽然朱子肯定道德自觉与动能具有内在必然性,但是气禀私欲也是具有影响力。在道德觉醒与善端萌发的历程中,同时也是气禀私欲潜入与笼罩的时机。第三,朱子言“心”并非仅仅是形下之气心或认知心,而是一道德主体、道德根源,并且具有自发不息之动力。第四,关于人心、道心问题,前者归属于形气或感官欲望;后者归属于明德之体。这两者本是同时存在,甚至可以用一体来理解。两者之间的转换之关键概念在于虚灵知觉。最后,作者指出:心之虚灵知觉证成了道心具有优位性与必然性,使得人在天理人欲之抉择当中,对于天理有必然之取向。
2.蔡家和:《朱子的孟学诠释特征》,《中正汉学研究》总第27期(2016年6月),第143~162页。
(1)问题意识
朱熹在四书诠释过程中,一方面想要从理学架构来进行四书学的建构;另一方面又会受制于四书的原文限制。蔡家和教授欲说明,从这两方面来看,当理学架构与孟子相遇后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火花出来。
(2)论文架构
论文分为五个章节。第一节,说明朱子“先知后行”理论。第二节,说明“学以复其初”的设计。第三节,说明“理气论”架构。第四节,说明“性发为情”“心统性情”理论。第五节,物性能同于人性,而有微明。
(3)论文摘要
蔡教授归纳出五种朱子诠释孟学的特征,指出朱子的孟子学是一种理气论的建构或说是一种理学的建构。在“知先行后”理论中,朱子用《大学》“知先行后”架构诠释《孟子·尽心知性章》。朱子将孟子言“知言、养气”,比配于《大学》中的“格物、诚意”。顺着《大学》主张“先格物,后诚意”,而将孟子“知言”“养气”,诠释为“先知言,后养气”。朱子以《大学》中“学以复其初”的架构诠释孟子,强调“心本具理”,因为物欲所蔽,而不能见理。格物穷理、涵养用敬的目的,都是在恢复“本具”的性理。但是,以“复其初”的架构诠释孟子,是否会对孟子言“扩充”有所冲突?蔡教授指出,两者在朱子诠释下并无冲突。理由在于:朱子对于“扩充义”有特殊的见解,即“充满其本来之量”。透过一种创造性的诠释来回避理学架构与孟子本意之冲突。在理气论架构中,朱子用理气论来诠释《孟子·生之谓性章》之人性、物性问题。在理气论架构下,人性与物性都是禀受相同之天理。两者差异在于:人能推,物不能推;并且人在气禀上是优于物。由此,人能尽性善之性,但物不能。朱子批评告子“生之谓性”是“视性为气”。在“性发为情”之体用观理论下,朱子用《中庸》“中和之说”来诠释《孟子·公都子问性章》。朱子用“心统性情”的架构,将孟子“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理解为“情感之发用”。在《孟子·人禽之辨章》言“人所以之于禽兽者,几希”,朱子则用“理一分殊”架构来进行诠释。朱子认为人与禽兽是在“气质之性”上不同,而“天命之性”则是相同。故孟子言“几希”,在朱子诠释下就会理解为“气质之性”之差异。最后,蔡教授指出朱子对于孟子的诠释,可以视为一种创造性诠释。
3.林宏星:《朱子论真知及其动机效力》,《国立台湾大学哲学论评》第52期(2016年10月),第1~26页。
(1)问题意识
林宏星教授在论文中开宗明义说明:论文的目的在于透过说明“真知必能行”所具有的动机效力,来响应休谟式的问题的诘难。林教授响应此问题的进路是讨论朱子对于真知概念的内容和结构的论述。林教授指出所谓休谟式的诘难,即是问:“如果仅仅凭着理性本身,如何可以为道德行动提出足够的动机理由?”林教授的问题意识主要是聚焦在“真知何以必能行”的动力方面。
(2)论文架构
论文共三章节:第一节,说明何谓真知?第二节,说明真知与动机效力;第三节,说明理由与动力。
(3)论文摘要
首先,林教授指出“真知”有两种特点:1)凡是直接从经验中获得的真实、正确的知识就是真知。2)真知并非要求每个人都要从经验中获得,只要是被人类在实践中所证明的知识,也可以归类为真知。其次,林教授指出,真知对于朱子而言,是站在第一人称的角度,追问自家身心上的“先天”就具有的“是非理据”。当我们对于这样的“是非理据”有了真切的反省后,便能获得一种“内在的肯信”,如此的“肯信”成为行动主体的道德行动之动力来源。由此也说明了,为何朱子提出了“真知必能行”的主张。林宏星教授指出:在朱熹真知理论中,真知与行动的关系,似乎并不存在着动力不足的问题。
4.张子立:《道德与知识的两种辩证关系:朱子格物致知说重探》,《中正汉学研究》总第27期(2016年6月),第163~190页。
(1)问题意识
朱子格物致知理论,在学界常面临一个挑战,即:在道德实践时,知识如何能促成道德实践?此亦即是问:知识如何能提供道德行为之动力?对于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阳明批评“心与里为二”;当代新儒学学者牟宗三先生,则将其定位为成德之助缘工夫。对于此问题,张教授试图从两种道德与知识之模型来回答此一问题,分别为“主从的辩证关系”与“对列的辩证关系”。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评断朱子学为逆觉体证型态之助缘,而唐君毅与刘述先,则从“主从的辩证关系”层次来立论,试图为朱子辩护;而张子立教授欲从“对列的辩证关系”之模型来重新定位朱子格物致知理论。他进一步指出,朱子的格物工夫可以处理在“强意义”下的道德两难之问题,而这正是阳明良知学所不足之处。
(2)论文架构
此篇论文主要章节为,第一节,说明道德实践与知识:朱子格物致知是否为助缘。第二节,说明道德与知识“主从的”辩证关系。第三节,说明“对列的”辩证关系:再探朱子格物致知说。
(3)论文摘要
张教授指出,阳明良知学理论特色就是类似“境遇伦理学”,只提出一形式原则,再视所处的情境决定具体行为。阳明模式的困难在于:当面临到道德两难情境时,这样模型仅仅只能处理“弱意义”下的道德两难问题。例如,舜之不告而娶。但是,一但面临“强意义”的道德两难时,这样的模型会遭遇到两个问题。第一,每一个情境都有其独特性,如果依照阳明的模式,当我们遇到强意义的道德两难问题时,都有可能会陷入手足无措的情形。第二,阳明模式缺乏“伦理知识”,而这样的伦理知识是可以主导道德判断,形成一种判断“中”的内在决定。张教授指出:如果是从“道德实践”层面看“道德与知识”的相互关系,陆王实有较正确的体认,理由在于:厘清了二者间“主从的辩证关系”;反之,如果是从“伦理知识”与“道德判断”之“对列的辩证关系”切入,则朱子格物致知工夫对于道德判断有较全面的认知,这也正是阳明理论所不及之处。
二、东亚儒学
1.杨祖汉:《朝鲜儒者田艮斋对朱子思想的理解——比较牟宗三先生的说法》,《中正汉学研究》总第27期(2016年6月),第93~116页。
(1)问题意识
杨祖汉教授此篇论文以朝鲜儒者田艮斋与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为比较进路,分析两者对于朱子哲学诠释上的不同与相同之处。杨教授指出田艮斋对于朱子诠释,主张理不活动、心是气,心与理为二,而道德实践之动力不能从理本身给出来。这样的观点和牟先生无异。但是,田艮斋认为朱子是儒家正宗;牟先生认为别子为宗。如果依照牟先生的判准,别子为宗最重要的判准根据在于:“是否为他律伦理学”。如果朱子是他律伦理学,那么艮斋就不能主张朱子与儒家本质相同。杨祖汉教授此篇论文指出:田艮斋之说具有一特殊含义,使得朱子仍可与儒家本质相同。
(2)论文架构
论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节,说明牟先生对朱子学的衡定。第二节,说明艮斋朱子学诠释的要点。第三节,引艮斋文献来证艮斋思想要点。第四节,说明艮斋与牟先生朱子诠释之比较及艮斋之说的特殊含义。
(3)论文摘要
杨祖汉教授指出,如何在心与理为二的架构下,说明朱子“不是”他律论理学?第一,艮斋在“心与理为二”架构下提出了“性师心弟”或“性尊心卑”的理论。根据这样的心性关系理论,会让心以性为尊、遵理而行。心则不敢僭越、不敢自主。第二,透过康德理论说明,在“性师心弟”或“性尊心卑”的架构下,只要越能强调“性天之尊”就会越有道德实践动力之产生,而这样的动力来自于对于道德法则产生的敬意。第三,艮斋主张,朱子《大学》所说的“明德”注语,表示了明德是“心”。“心”之所以称为“明德”是因为“具理”。虽然如此,但是真正的道德实践之根据所在仍然是性理。第四,心虽然是形下之气,但是不同于一般的形气。心具“虚灵明觉”,而可以通于性理。最后,杨教授认为,艮斋在“性师心弟”成德之教模型,可以使得朱子在主张“心与理为二”的架构下,仍然与儒家本质兼容。
2.藤井伦明:《日本崎门朱子学的智藏论探析》,《中正汉学研究》总第27期(2016年6月),第191~210页。
(1)问题意识
朱子晚年“智藏”的概念在日本崎门朱子学派中被视为重要概念。藤井教授指出在过去对于朱子“智藏”概念并未有充分的讨论、分析。有鉴于此,藤井教授欲从分析“智藏说”,来阐明崎门朱子学派智藏说的具体内容与逻辑结构。
(2)论文架构
论文章节为,第一节,说明朱熹思想中的“智藏”观与山崎暗斋的宣扬。第二节,三宅尚斋的《智藏说》以及崎门学者的“智藏”论。
(3)论文摘要
藤井教授指出,崎门朱子学派“智藏说”有诸多特色:第一,对于性理(未发之理)理解为具有双重结构,即“无迹”之“智”与“有迹”之“仁、义、礼”。第二,前者是“未发之理”的最深层之根源,未受到任何的限定。后者,则是已经具有限定、带有具体特色于其中。但,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属于“形上之理”。第三,崎门朱子学派所理解的“智”可能就是理之能量本身,亦即将其视为一块“能量体”。而此一能量体作为本体而产生各种现象、作用。第四,将这本体与其所产生的作用,用“知”概念来做整体的掌握。
三、比较哲学
1.林维杰:《朱熹理气论与莱布尼兹的自然神学》,《中正汉学研究》总第27期(2016年6月),第211~228页。
(1)问题意识
林维杰教授论文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他所要讨论的问题,即:先秦儒学中具有位格性的天、帝概念,到了宋明理学中已经逐渐转化为道德性的天、道、理等概念。然而,在这样的道德性意义之下,是否仍有宗教的意涵。林教授进一步指出,这样问题的症结在于:理则化、德性化的超越者是否仍可视为宗教要素?所参照的系统是以西方的神学论述(特别是自然神学),以莱布尼兹的自然神学作为对比来说明朱子理学的宗教性。
(2)论文架构
论文架构为:第一节,说明朱熹理论及其理气论之诸性质。第二节,说明莱布尼兹之自然神学及其对朱熹理气论上的参照意涵。
(3)论文摘要
在朱熹理学方面,林教授首先指出,朱子理气论有六种性质,分别为“理气双显”“不离不杂”“理先气后”“理在气中”“理同气异”“理静气动”。从这六种性质来检视太极与万物之关系,可以视为一种“观解形上学”的内在之规定,即:“超越的理即内在于万物之理”。朱子的理气论是从形上学角度来谈太极、理与万物之关系。另一方面,莱布尼兹对于中国自然神学所采取的观点是宗教多元主义或上帝中心主义,而并不认为中国宗教思想是属于唯物论或是处于精神论或唯物论之间的矛盾主张。同时莱布尼兹也批评龙华民对于朱熹理气论的理解。龙华民对于朱熹理的理解有二:第一,理是至善的精神体且能“生出气”。第二,“理”可能是“原初物质”。莱布尼兹反对这样的看法,主张“理”不会是“原初物质”。批评龙华民将太极与气给混淆了。但是,莱布尼兹也同意“理能生气”的观点。虽然如此,林教授也指出莱氏犯了跟龙华民一样的错误,即混淆朱子太极与元气说,以及“理生气”之意。朱熹的“理生气”并没有基督教“从无生有”的意涵。最后,林教授认为透过莱布尼兹自然神学理解朱子理气论的宗教意涵是很有意义的。林教授指出:莱布尼兹站在会通中西教理的态度上,尽可能地拉进儒学中太极、理与基督宗教中的上帝、天主之性格,而提出了自然神学式的“以理为神”观点。
四、清代朱子学
1.陈祺助:《王船山与朱子工夫论比较》,《中央大学人文学报》第62期(2016年10月),第1~48页。
(1)问题意识
陈教授指出当代对于船山与朱子比较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采取概念或范畴为进路。然而,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所做的比较研究,则为少见。以此之故,陈教授打算从“主敬存心”“知行关系”“致知格物”这三个主题上,来比较船山与朱子工夫论之说,对于两家之说详细讨论,以厘清其异同之处。
(2)论文架构
此篇论文架构分别为:第一节,论主敬存心的比较。第二节,论知行关系的比较。第三节,论致知格物的比较。
(3)论文摘要
首先,陈教授指出,对于孟子“求放心”的诠释上,船山批评朱子“文理有碍”。朱子认为如果将“求放心”理解为“一心求,操另一心”,会造成“一人有两心”的理论困境。并且在工夫论上必导致心越求越昏乱。依照朱子对于“求放心”的理解,“放心”是赘词,“求”字所表示的工夫力道太弱。船山认为,孟子言“求放心”,此“求”字是大有工夫之所在,并非如朱子所主张,如果强调“求”字就会产生主客、能所对立,形成“一人有两心”的困境。第二,对于“存心”之说,如何保证存心能有道德价值?在朱子方面,朱子透过“持敬”工夫使心气收敛凝聚,常在静默中对超越之天理,使得“中性”知觉之心得以具有道德价值内含。陈教授指出,虽然“持敬”可以此心收敛凝聚,涵养心气。但是,如果心气本“不固有”仁义之性,则虽收敛心气使其不昏昧,心仍“未必善”。反观,不同于朱熹主张“心”为“虚灵明觉”;船山主张“仁义”为“心之实”,而主敬工夫用来收敛心气,必能使心之实之仁义呈现出来。陈祺助教授指出,朱子与船山的理论差异在于:前者“存心说”并不能保证存心必能有道德价值。后者则可。第三,对于知行问题,陈教授指出,船山批评朱子“知先行后”的主张会产生与王学末流相同的困境。即,如果“凡是要求等我先知道后,再去行为活动”,会导致“先知以废行”的结果,这点正是朱子理论的困境。于此,船山则提出了“知行并进”的理论架构来补足朱子理论软点之处。
(作者单位: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
2016年韩国学者的朱子学与
韩国儒学的研究状况[1]
⊙〔韩〕姜真硕
2016年度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不但涉及的主题很广,也出现了未曾研究过的新的领域,可见朱子学及韩国儒学的研究依然活跃,成为韩国学者的主流研究之一。关于朱子学的研究方面,韩国学者探讨了心性论、工夫论、经学、书院及画幅、朱子家礼、易学、训诂学、哲学治疗、比较哲学等各种主题。其中,关于朱子哲学方面,有些韩国学者论及朱熹的心性论、《中庸》的情感论及《大学》的平天下的意义。笔者在这里介绍几篇论文,以共享其内容。
1.金基铉:《朱子学的未发概念的成立过程》,《阳明学》44号,2016年。
金基铉从湖湘学与阳明学的角度探讨了朱熹早年的心性论。他认为朱熹在中和旧说时期提出的未发为性、已发为心的主张,并非通过真正体认察识端倪而提出的,而是在短暂的思考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想法。严格来讲,朱熹在通过察识工夫体认本心方面未达到真正的理解,是因为当时他把寂然不动视为性。湖湘学派一向追求要体认天命流行的生生不已之天机的寂然不动即已发之心,然而朱熹却把已发之心误认为性的领域。金基铉认为朱熹始终把寂然不动当作未发性,因此在工夫方面无法做出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在修养工夫上必须从尽心达到成性,这是孟子说的尽心、成性、知天的次序和过程。金基铉的论文在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朱熹早年的心性论方面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他提出朱熹早年的学说未有真正的体悟,抑或由于把寂然不动视为未发之性,从而断定朱熹在修养工夫上有缺陷等说法,不是从朱子学本身思想演变的角度理解中和说,而是从阳明学的角度判断中和旧说的内容,由此产生一些解释上的分歧。
2.洪性敏:《朱子哲学中的情感的适当性与道德性》,《东方学》35号,2016年。
未发之中和已发之和是《中庸》第一章的中心概念。韩国学界一向着重于探讨“未发”部分的思想内涵。但洪性敏认为,相对来讲,关于中节之和的研究却未引起学者们广泛的注意。中节之和的研究能更丰富对未发之中的理解,也能让学者更深入地理解未发涵养的意义。中节之和的深层理解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探索能够解释道德感情论的某种新的渠道。性理学中的“情”的意义不完全是与英语的“emotion”相符,但是从《中庸》首章的理论脉络看,未发和已发确实是提到情感上的问题,也显示中节之和具有情感之中节扩大到达道的某种道德价值的意义。而且洪性敏主张朱子虽然有意识地把四端和七情看作不同的情感圈,但是就实际的情感现象方面而言,四端与七情的关系不是像纯善与有善恶那样可以划清。朱熹认为四端和七情反而都隐含着恶的危险性和善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他看来,七情与四端是可以就同质脉络上探讨的。由此可说,七情之恶是从四端之恶发生的,也可说哀惧是怵惕恻隐之深化。四端与七情不仅是从同一根源发出的,同时也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关系。
从这样的意义上看韩国儒学的李退溪和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辩,朱子本身理解的四端七情的关系,似乎更接近奇大升的说法。因此四端都有在现实生活中可发生未中节而为恶的可能性,七情也包含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发而中节为善的可能性。判断情感的道德性与否,其标准正是现实上的中节与否。朱熹认为恶的本质并不是先天的,而是现象的、后天的。这不但表示他对道德本心具有毫无动摇的信心,同时显示他把善恶问题局限于现象领域去进行思考。由此可说,四端也是如果在现实领域中不中节则可成为恶,七情也是在现实领域中发而中节则可被认为善。在此篇论文中,洪性敏特别关注“持志”这一概念。朱熹要运用持志工夫调整情感,以符合中节之标准,而且要控制因气质所产生的情感泛滥的现象。意即朱熹认为情感变为道德性需要充分的具有意志的训练工夫。笔者认为洪性敏的论文可说是现代版四端七情论。他注意“中节”概念,深入探讨了朝鲜时代“四七论辩”未提出的一些理论结构,也提出了较倾向于奇大升说法的情感道德思想。
3.徐根植:《从朱子〈大学章句〉看平天下的世界》,《东洋古典研究》63号,2016年。
徐根植专门探讨了《大学章句》第10章的内容。他认为此章的中心思想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絜矩之道,另一是节用思想。朱熹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实践絜矩之道、选拔人才、节用,平天下的理想就不是件遥远的事了。徐根植介绍了当代中国和韩国学者说的忠恕和絜矩之道思想,认为《大学》的絜矩之道实际上指的是“恕”思想,而不是指“忠恕”。《大学章句》的絜矩之道充分体现消极意义之恕,由此可探索平天下的方法。己立立人的积极意义之恕,可适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等实践领域,而在平天下的实践过程中可能更需要絜矩之道及消极意义之恕。笔者认为此篇论文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絜矩之道的视角,但是在梳理忠恕概念及探讨恕与絜矩之道的关系方面深度稍微不够,留给我们更深入研究恕与絜矩之道的关系、消极意义的恕所蕴含的深层意义等课题。
下面的两篇论文是关于朱子学传入韩国的文化特色及本土化过程的研究。一篇是叙述了朱子画像供奉于韩国书院的过程及特色,另一篇是韩国儒者吸收《朱子家礼》而后予以本土化的内容。
4.朴晶爱:《朝鲜时代朱子崇慕热与其形象的视觉化特色》,《大东文化研究》93号,2016年。
朴晶爱的论文是关于自朱子学传播至韩国以来所形成的书院和美术等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他说朱子学是高丽末期安垧(1243~1306)从中国燕京回韩国时,抄朱子书及摹写孔子和朱子画像后开始传播于韩国的。后来15世纪初《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等著作从中国传来,16世纪初《性理大全》及《朱子大全》在朝鲜刊印,而且李退溪写了《朱子书节要》、李栗谷又写了《圣学辑要》为朝鲜朱子学的广泛普及带来积极的作用。1543年周世鹏(1495~1554)模仿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建立了白云洞书院。17~18世纪在韩国所建立的书院约达903所。韩国文人特别仰慕朱熹隐居武夷山期间的生涯,不但模仿武夷九曲及创作武夷诗歌,也背诵及阅读《朱熹词》《斋居感兴诗》等作品。徐起(1523~1591)及其门人在1581年供奉朱子画像建立了孔岩书院。之后该书院因壬辰倭乱被破坏,1624年又赐额为忠贤书院。1790年重修忠贤书院时尹命泽改摹晦菴影帧。据说此影帧在1871年政府发布书院废除令之后被移安于公州乡校。1925年重建忠贤书院时,添购了新的朱子画像供奉于书院内。由此可说,朝鲜时代韩国的朱子画像与当时的忠贤书院的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朴晶爱在此篇论文中介绍了许多现存的朱子画像的照片。现在这些资料分别保存于国立中央博物馆、首尔历史博物馆、公州忠贤书院、庆州云谷书院、成均馆大学博物馆、个人收藏等地。笔者认为此篇论文提供了朱子学传播于韩国后而形成的朱子画像与书院的关系史,丰富了韩国儒学之朱子学本土化的研究。
5.崔俊夏:《〈朱子家礼〉的传播与韩国传统礼法的转变及具有现代意义的定位研究》,《人文学研究》103号,2016年。
崔俊夏的论文是韩国儒学对《朱子家礼》传承方面的研究。他说韩国学术界难以确定《朱子家礼》传播于韩国的时期。一般推论是高丽时代安珦(1243~1306)在带了许多有关性理学的书籍回国时一起带回的。朝鲜王朝成立之后,新进士大夫阶层开始积极推动了《朱子家礼》。新进士大夫为了巩固他们的阶层地位,首先施行家庙制,以终止高丽时代佛教文化习俗的弊病,另一方面宣扬祖先崇拜和孝道精神。《朱子家礼》中的三年丧制是在皇室和士大夫阶层中所施行,而一般老百姓则都守百日丧制。16世纪以后《朱子家礼》之所以能推广并普及于全国,李退溪和李栗谷的贡献很大。1592年壬辰倭乱之后,韩国儒林继承退溪和栗谷的推广精神,继续推动了《朱子家礼》的礼学。17、18世纪的《朱子家礼》成为朝鲜礼学的骨干。金长生(1548~1631)著述了世称朝鲜礼学的理论书的《家礼辑览》,还写了《典礼问答》《丧礼备要》《疑礼问解》等书。大韩民国成立之后,韩国政府趁着打破虚礼虚式传统的名分之际,1973年推行了“家庭仪礼准则”。崔俊夏详细地梳理及比较了韩国传统家礼与近代以来多次变化的现代家礼。笔者认为此篇论文不但梳理了《朱子家礼》传入韩国的演变过程,而且详细探讨韩国的传统家礼与现代伦理的异同问题,以显示韩国现代家庭伦理存在的虚实问题。
关于朝鲜性理学、退溪学、茶山学方面,韩国学者研究退溪的哲学评论、退溪的士观、茶山的修养论、当代韩国新儒家、当代朱子学家、茶山解配期的易学、茶山纪行、茶山与基督教、茶山的经世学及权衡论等主题。在笔者看来,在2016年度的研究中,值得介绍的是关于当代韩国新儒家的一些著述和思想。
6.郑圣喜:《再论民族主义倾向的韩国儒学史的叙述——以玄相允的〈朝鲜儒学史〉为主》,《儒学研究》37号,2016年。
此篇论文专门探讨了韩国学者玄相允(1893~1950)的《朝鲜儒学史》具有的意义及特色。郑圣喜首先介绍了玄相允,他出生于朝鲜的儒林家庭,接受了扎实的儒学教育,而且他12岁结婚之后,受到了岳父白彝行,即当时被称为名门民族私学的五山学校的首届校长,深厚的影响。27岁时遇到了“3·1独立运动”而身陷囹圄,以至于后来他不直接参与任何政治运动,而将自身奉献于教育活动。郑圣喜提及玄相允的儒学观与朝鲜时期韩国儒者的儒学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玄相允认为朝鲜时代的社会可类比于欧洲的中世纪。于是他主张应当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方法治疗韩国社会的弊病、革除社会中的各种弊端。他对朝鲜时代的儒学一直保持批判的态度。他虽然高度评价朝鲜时代早期赵光祖等士林派推行的王道政治思想,但认为己卯士祸发生以后韩国儒学的“实际”运动不断被瓦解,以至于只好走向“理论”路线。相反的,玄相允对反动于朱子学兴起的经济学派(实学运动)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主张由丁若镛所集大成的经济学派的主张具有爱民、考据学的学风、吸收西学等特色。
在玄相允的《朝鲜儒学史》内容中最受注目的是所谓儒学功罪论。玄相允认为朝鲜儒学之功在于君子学之勉励、人伦道德之尊崇、清廉节义之精神等三种。相反的,儒学给朝鲜社会带来的罪过则有慕华思想、党争、家族主义的弊害、阶级思想、文弱、工业能力之下降、丧名主义、复古思想等八种。他的功罪观是以浓厚的儒学节义观与民族主义作为基础的。
7.洪元植:《现代新儒学与卿辂李相殷》,《孔子学》30号,2016年。
洪元植的论文是关于当代韩国新儒家李相殷(1905~1976)的研究。李相殷的代表著作有《韩国哲学史讲义》《退溪的生涯与学问》等。李先生是从1927~1931年攻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一直任职于韩国高丽大学哲学系。他的读书与学术活动不限于韩国,经常与中华圈的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等学者交流。李先生强调仁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是具有跨越东西古今之普遍价值。人类处于急速的近代化、工业化所带来的异化及本性丧失的时代,由此他主张以儒家的人道主义治理这些问题。洪元植认为如果从中体西用类的角度看李相殷的思想,他也是一位东道主义者。他说的“东道”的核心思想是儒学,其精华是指退溪学。这与当代中华圈的新儒家以阳明学作为核心价值趋向有所区别。到了1960年,韩国儒学界逐渐重视实学思想之际,李先生发表《实学思想的形成与展开》,主张性理学与实学并不是相克关系,而是相辅关系,正视这点才能创造出高水平的学术文化。笔者认为洪元植的论文综合地梳理及探讨了当代韩国新儒家李相殷的思想。同一时期活动的玄相允(1893~1950)的思想较突出民族主义特色,李相殷的思想则一方面与当代中华圈新儒家的思想相呼应,另一方面在韩国儒学中寻找跨越东西古今之普遍思想。
8.姜卿显:《退溪对明代儒学的批判与退溪学的实践意义的特色》,《哲学论集》46号,2016年。
姜卿显的论文主要梳理及探讨李退溪对明代儒学的批判。李退溪对禅学保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他对禅学的批判直接关系到他对象山陆九渊、白沙陈献章、医闾贺钦、阳明王守仁等心学的批判。退溪批判陈白沙,说他的思想充满着禅佛教的意蕴。退溪言“陈白沙、王阳明之学皆出于象山,而以本心为宗,盖皆禅学也。然白沙犹未纯为禅,而有近于吾学。……但其悟入处终是禅家伎俩,故自谓非禅,而其言往往显是禅语。”退溪认为白沙主张读书穷理,所以不能完全视他为禅学,然而他又过度强调静坐、厌世求定,因此难免有流于禅学的嫌疑。他针对阳明学说“欲排穷理之学”。姜卿显指出阳明的知行合说把形气上的好恶与义理上的知行混为一谈,排除外面的事物,而只在人心之本位上说明知行问题,因此不能成功地做出与人伦秩序相符的实践。姜卿显特别强调退溪把自己的学问与白沙、医闾、阳明等明儒心学区别开来,乃是在他从天命之理所导出的儒学理想实践上的命令与对遵循其命令的义务之省察,而在此二者的背景下所提出的。笔者认为姜教授不但梳理了退溪对明儒之学的批判内容,同时也深入剖析退溪学本身具有的哲学含义,由此使得读者能理解在传承朱子学方面韩国儒学与明代儒学之不同。
9.沈庆昊:《丁若镛解配以后的学问及春川旅游》,《茶山学》29号,2016年。
沈教授的论文是朝鲜儒者丁若镛的文化纪行研究。丁若镛(号茶山,1762~1836)是朝鲜时代的韩国大儒。他因为各种缘由受到政治压迫,被流放于康津将近十八年。1818年,他57岁时才解配出来。这篇论文主要叙述了丁茶山解配之后的生涯及纪行。茶山的文化纪行充满着文人色彩及哲学意蕴,令人足以感受到既有激情又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风貌。沈教授介绍丁若镛解配后两次去春川旅游。茶山一生仰慕杜甫,因此他去春川时把春川附近的马迹山比作杜甫诗中的鹿头山。他始终努力体会杜甫的诗人精神及意蕴。他的学术思想随着仕宦期、流配期、解配期而发生了变化。他第二次去春川旅游时,叙述了对学问的关心、对山水大自然的钟情以及对庶民的同情。而且他主张如果朝鲜受到外国的侵略,应当把春川作为最后的防御线。
以上笔者简单地梳理了2016年度值得介绍的一些韩国学者的论文。其中,笔者认为所谓当代韩国新儒家思想及韩国儒学的本土化研究需要继续扩大且加强。事实上,韩国学者对近现代韩国朱子学或是当代韩国新儒学的研究十分不够,连其师承关系和思想系谱的研究也未得出共识,这些项目的研究还停滞于朝鲜时期的研究。当代韩国新儒家可分为留学派、民族主义派、基督教派等派别。如上述的李相殷(1905~1976)先生属于留学派,玄相允(1893~1950)先生是属于民族主义派,文中未提及的柳永摸先生(1890~1981)、咸锡宪先生(1901~1989)是属于基督教派。尚有略早于他们活动的朴殷植(1859~1925)是一位阳明学家。这些人物及派别是值得继续关注和研究的。
(作者单位: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2016年日本朱子学研究综述
⊙〔日〕板东洋介
一、日本儒教学会之成立
谈到今年日本儒教研究中最具特色的大事,首先应该提到日本儒教学会之成立。在日本代表性儒教研究者的倡议下,2016年5月14日于东洋文库(东京都文京区)举办了该学会的成立大会。东洋文库是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在日本最为重要的“东洋学”研究方面的专门图书馆,坐落在著名庭园“六义园”附近,此园由“诗有六义”(《毛诗大序》)得名。日本儒教研究能在此地迈出新的一步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成立大会首先由倡议者代表土田健次郎(早稻田大学教授)致开幕词。在其中,详尽地叙述了学会成立的趣旨之全貌。土田健次郎提及下述内容:在当今日本,没有专门研究儒教的学会,儒教问题主要由中国文化学会、日本思想史学会等学会分散研究。这是不可思议的。就亚洲的其他宗教学问即佛教、道教而言,已有印度哲学学会、日本道教学会,为何唯独儒教方面没有呢?海外的儒教研究者也曾困惑不解地指出过这一点,并且近年来不断增多并深化的与海外研究者的合作研究都仅限于以个人为单位分散性进行的小规模活动,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因此希望可以作为日本的儒教研究者固定的交流场所,并作为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基地而设立该学会。[1]土田健次郎的发言内容大致如上。
其后,恰巧来到东洋文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程永华祝了贺词。接着举行了“日本儒教研究之现状”研讨会,研究各地域、各时代儒教的权威学者们做了报告并开展了讨论。担当者如下,日本近世儒教:前田勉(爱知教育大学教授)、日本近代儒教:河野有理(首都大学东京教授)、朝鲜儒教:山内弘一(上智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儒教:渡边义浩(早稻田大学教授)、中国近世儒教:小岛毅(东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儒教:中岛隆博(东京大学教授)。通过上述担当范围,可以一目了然地得知,学会不是研究“日本儒教”的学会,而是以日本研究者为中心的“儒教学会”。尽管如此,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该学会将成为与日本思想史学会并驾齐驱的“日本儒教”的一大研究中心。在此仅就涉及日本朱子学的问题介绍一下登台发言者的报告内容。[2]首先,前田勉基于日本思想史研究中近世儒教研究的地位与数量都相对低下这一局面所带来的“一种危机感”,全面概括了丸山真男、尾藤正英、渡边浩等人研究二战后日本儒教的方法论与研究视角,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在近世后期出现的“会读”习惯,陶冶出了承担起日本近代化重任的社会精英的风貌。前田勉的讲话意味着,这一风气正显示了在日本存在着亚洲的“另一个近代”,它不同于战后日本高声提倡、积极探索的西欧近代型“主体性”。另外,河野有理介绍了田口卯吉(1855~1905)、加藤弘之(1836~1916)等近代日本著名的知识人使用“封建”“郡县”等儒教古典词汇,围绕地方分权与立宪政体所展开的时政性争论,并指出,儒教在近代日本也作为“词汇数据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其后的综合讨论中,在登坛者之间以及学会成员之间开展了活跃的讨论,给笔者(板东)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是,许多发言人都强调,其他儒教文化圈中的儒教研究热气腾腾且具有现实意义,而与此相对,日本研究者不过是作为“逝去的东西”来客观性地研究儒教,他们将这一“温差”及“与对象之间保持距离”作为日本研究者的特色予以积极的肯定。
其后在综合大会上,推选土田健次郎为首届会长,前田勉为副会长。同时任命的理事及评议员也都是日本著名的儒教研究者。正如上述土田健次郎所提倡的,设置一个日本儒教研究者的综合性交流场所具有深远意义,并且可以期待,该学会作为有关儒教的国际性合作研究之主体将发挥重大作用。
二、日本人的死生观与朱子学
人死之后去哪里?是去天国、极乐净土、地狱那样的他界,还是变为神性的存在留在现世或是如近代的“科学性”世界观所说的那样消失得无踪无迹?并且,这些对死后世界的想法与如何度过此生这一问题密切相联。这种对死与生的思考,在日本常被称为“死生观”。与日本思想文化整体类似,日本人的死生观也同样,积极地说是重叠的,消极地说是极其含糊的。例如,古代神话中包含着对死者之国(黄泉国)的恐惧、平安时代曾流行净土教派佛教等,日本人的死生观在不同时代姿态各异,而决定当今日本人典型的死生观的最重要契机,应是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强制全体国民接受佛教。由此,与日本人的死亡相关的仪式(葬礼、祭礼)都变为以佛教式举行。在幕府崩溃,信仰宗教的自由得到承认的近现代,大多数日本人的葬礼祭礼还是以佛教式进行的。问题是在德川时代以后,日本人的死生观全都染上了佛教色彩吗?其实并非如此。调查了日本人的习俗并为日本民俗学奠定了基础的柳田国男(1875~1962)[3]主张:大半的日本人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佛教式葬送礼仪,但在观念上并不认同轮回、极乐往生等佛教的一般性死后观念(《先祖の话(祖先之事)》,1946年)。柳田国男认为,日本的“常民”(在农村从事稻作耕种的普通的日本人)的死生观是死后也作为神留在现世,在他接受子孙祭祀时定期降临,永远保佑子孙。在这一想法中,死者既未轮回,也未成佛。也有人反对柳田的这一说法,他们认为,佛教对于日本人的死生观及葬礼祭礼产生了决定性影响。[4]对这一点至今未得出定论。
上述死生观在日本构成了极其现代性的问题。大家庭急速向核心家庭(一夫一妻及子女构成的小家庭)转变,长期不景气造成家庭年收入减少等使得以家庭为单位举行的葬礼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批判传统佛教式葬礼之虚伪的宗教学者岛田裕巳的《葬式は、要らない(不要葬礼)》》(幻冬舍,2010)这一轰动性著作带来了巨大反响,取代佛教式葬仪,基督教式、神道式、非宗教式等新式葬仪逐步增多起来(总体而言,薄葬倾向日益显著)。大型超市集团介入丧葬业界,全球性函购公司展开了为葬礼“派遣僧侣”的事业,这些都作为葬礼的商业化、形式化的深刻问题而受到重视。进一步而言,作为国际性问题长期受到关注的靖国神社这一设施也是建立在“作为神来祭祀殉国者”这一固定的死生观上的。这是源自于日本人传统的死生观而自然形成的,或者不过是到了近代才树立起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一直是有识之士争执不休的重要争论点之一。
那么,对于如此错综复杂并具有现实意义的日本人的死生观,朱子学施加了怎样的影响呢?如上所述,论及“日本人的死生观”之际提及的两大要素是佛教与神道(基层信仰),而不是朱子学。因此日本人的死生观与朱子学之关联问题至今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在今年,出版了一部追溯这一关联的重要著作。那就是本村昌文所著《今を生きる江户思想——十七世纪における佛教批判と死生观(活在当下的江户思想——十七世纪的佛教批判与死生观)》(ペりかん社,2016年)。
德川幕府的统治恰始于17世纪初(1603),如上所述,官方宗教政策是佛教式的,但是从设立幕府时就开始有所作为的儒者们则仿照他们所尊崇、所依据的宋学者,对佛教展开了抨击。一般认为,他们对佛教的抨击只不过是对朱熹等人排佛言论的“翻版”“照搬”,基本上缺乏独创性。可是本村昌文仔细检阅了17世纪日本儒者的著作,从中发现了日本儒者独自的思维方式及意义。该书中提到了中江藤树(1608~1648)、林罗山(1583~1657)、松永尺五(1592~1657)、清水春流(1626~?)、向井元升(1609~1677)、熊泽蕃山(1619~1691)、中村惕斋(1629~1702)等知名的与无名的儒者的专门性著作,以及被称为“假名草子”等面向一般大众的启蒙书籍(在仅限于僧侣和儒者能读懂汉文的近世前期社会,用假名写作的浅显易懂的假名草子,反而比正式的汉文儒书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本村昌文认为,在这些17世纪的儒教文献中可以看出,以1640年左右为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17世纪前半期的儒者对人类死后的问题几乎不置一词,而使用“佛教是破坏伦常道德的‘异端’教说,而树立现世人伦的儒教教说才是最好的”这一韩愈以来排佛的老套言论方式来抨击佛教。本村昌文将这种集中关注“如何活在当下”(第51页)这一点的儒教教说称为“生之教说”。可是到了17世纪中叶以后,儒者们开始抨击佛教的轮回与极乐往生之说,主张气之聚散与鬼神之来格,开始积极地基于朱子学来谈论死后世界。这被本村昌文称之为“生死之教说”。本村昌文总结说:就这样,以1640年左右为界,出现了从“生之教说”向“生死之教说”的转变。至于为何这发生在开设幕府后半世纪左右,他分析道:由于战乱终息,社会趋于稳定,一方面“教化人们不受基督教与异国宗教诱惑的意识”(第291页)在儒者们心中觉醒,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死后之事所拥有的不安与恐惧,以及未理解死生之根干这一认识”(第292页)形成起来。在重新归于稳定与和平的社会中,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死生观,以此超越由官方权力强制灌输的佛教式死生观,朱子学的教说因此重要起来。
本村昌文认为,当时的日本儒者作为朱子学死生观的根本性典据常常参照的是《朱子语类》卷三:第十九条,其中主张死后的气(魂魄)的聚散,以及继承了同一气的子孙之祭祀形成的感格。在此说日本儒者的死生观并非仅限于“照搬”朱子,是由于日本儒者们有意识地从朱子言论中摒弃了“气之散逸”,反而强调“死后灵魂不灭”这一点。受着道德约束而活过此生的人,死后也不会消亡,而作为超越性留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他的本性会被子子孙孙无穷地继承下去。之后,日本人从朱子的言论中辨别出的这一死生观与神道的词汇、概念混淆起来。本村教授在本书尾章介绍了同在17世纪中叶谈论了不同于佛教死生观的神道家吉川惟足(1616~1694)的死生观,这不是用朱子学,而是使用“神避”“长隐”“日少宫”等神道词汇来说的,同时指出:“虽然使用的概念不同,死后的灵魂回归到某处而永续这一思考框架是与本书中探讨的以17世纪中叶形成的朱子学为基础的死生观共通的”(第293页)。[5]读者或许已看出,这一死生观与柳田国男分析的日本人民俗性死生观极其相似。被视为“日本人固有的”“神道式”的死生观与朱子学的死生观之间出现的思想性交涉过程,今后或许会成为日本朱子学研究中的一大主题。
另外,本村昌文的著作主要分析了书籍上围绕死生观所记载的教说,并未言及在礼仪上如何具体实践此类死生观的问题。从本村昌文认为的教说上发生转机的1640年起,大约过了30年左右,于1670年前后儒教式死生观在礼仪上也出现了一大转机。即当时日本先进的政治家与儒者开始尝试根据《朱子家礼》实际举行儒式葬礼(其大半由于幕府的禁压而流产)。首先在宽文十二年(1672),会津藩主保科正之(1611~1672)的儒葬不顾幕府反对而进行,接着于天和二年(1682)举行了日本第一淳儒山崎暗斋(1618~1682)的儒葬,之后到了元禄十三年(1700),延请朱舜水(1600~1682)为宾师的水户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也举行了儒葬。关于这些作为礼仪的儒葬,可参见2012年笔者介绍过的田世民所著《《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礼受容の研究(近世日本的儒礼受容之研究)》(ぺりかん社,2012)。在这些礼仪方面,也能见到朱子学式的葬礼随着国粹意识之高涨,逐步被脱胎换骨为神道式葬礼[6],这一过程极其耐人寻味。
(林松涛译)
(作者单位:日本皇学馆大学)
2016年日本朱子学研究综述
〔日〕板东洋介
一、日本儒教学会の設立
本年の日本儒教研究を特徴づける出来事としては、何よりもまず、日本儒教学会の設立を挙げなくてはならない。日本を代表する儒教研究者たちが 発起人となり、2016年5月14日に東洋文庫(東京都文京区)でその創立大会が行われた。東洋文庫は世界有数、そして日本随一の「東洋学」の研究図書館であり、「詩有六義」(「毛詩大序」)から名を取った名庭園「六義園」の近傍に立地している。日本儒教研究の一つの出発を記念するのに相応しい場 所である。
設立大会ではまず、発起人代表で、ある土田健次郎(早稲田大学教授)による開会挨拶が行われた。その内容のうちに、学会設立趣旨の大概は尽くさ れていた。土田は次のような内容を述べた。すなわち、現在の日本には儒教の専門学会が存在せず、儒教の研究は主に中国文化学会•日本思想史学会な ど、諸学会で分散して行われている。これは奇妙なことである。他のアジア 発の諸教諸学、すなわち仏教や道教については印度哲学学会や日本道教学 会がすでに存在するのに、なぜ儒教についてのみ存在しないのか。この事情 は海外の儒教研究者からも驚きをもって指摘されることであり、かつ近年増加•進展している海外研究者との共同研究カヾ、個人単位の散発的で小規模のものにとどまりがちであることの要因ともなっている。そこで日本の儒教研 究者の恒常的な交流の場として、ならびに国際学術交流の基盤として、本学会を設立したい[1]。土田の発言の更概は以上であった。
その後、ちょうど東洋文庫を来訪中であった中華人民共和国の程永華•駐日大使が祝辞を述べられた。続いてシンポジウム「日本における儒教 研究の現在」が行われ、各地域各時代の儒教研究の第一人者が報告と討論を行なった。担当者は次のようである。日本近世儒教:前田勉(愛知教育大学教授)、日本近代儒教:河野有理(首都大学東京准教授)、朝鮮儒教:山内弘一(上智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儒教:渡邊義浩(早稲田大学教授)、中国近世儒教:小島毅(東京大学教授)、中国現代儒教:中島隆博(東京大学教授)。上の担当範囲に瞭然な通り、本学会は「日本の儒教」についての学会ではなく、日本の研究者を中心とする「儒教の学会」である。とはいえ、本学会は日本思想史学会と並んで「日本の儒教」の一大研究中心となってゆくことカヾ、極めて高い蓋然性をもって予想される。日本朱子学に関連する限りで登壇者たちの報告内容を紹介すると、次のようである⑵。まず前田勉は日本思想史研究の中で近世儒教研究の位置と量とが相対的に低下していることへの「一種の危機感」のもと、丸山真男•尾藤正英•渡辺浩らによる戦後の日本儒教研究の方法論や研究視角を総括し、その上で近世後期に見られる「会読」の慣習の中で日本近代を担う選良たちの気風が涵養されたことを後付けた。その気風は、これまで戦後日本で声高に提唱され、模索された西欧近代型の「主体性」とは異なるアジア的な「もう一つの近代」の所在を示していると前 田は示唆する。また河野有理は、田口卯吉(1855-1905 )や加藤弘之(1836-1916)ら近代日本の代表的な知識人たちか、、「封建」「郡県」という儒教の古典的な語彙を用いて、地方分権や立憲政体をめぐる同時代的な議論を展開していることを紹介し、近代日本においても「語彙データベース」として儒教が有為に機能し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た。またその後の総合討論においては登壇者相互、また参加した学会員たちによる活発な議論が交わされたが、報告者(板東)の印象に残ったのは、多くの発言者が、、他の儒教文化圏における儒教 研究が、もつ熱気や現代性に対して、日本人研究者はあくまで「過去のもの」 として客観的に儒教を研究しているという「温度差」や「対象との距離」を強調し、かつそれを日本の研究者の特色として肯定的に評価していた点であ った。
その後、総会にて土田健次郎が初代会長、前田勉が副会長を務めることが決議された。同時に任命された理事及び評議員には、日本の代表的な儒教研究者が名を連ねた。上記の土田の提言の通り、日本の儒教研究者の総合的な交流の場が設けられたことは極めて意義深く、かつ儒教に関する国際的な共同研究の主体としても本会が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ゆくことが期待される。
二、日本人の死生観と朱子学
人は死んだ後、どこへ行くのか。天国•極楽浄土•地獄のような他界に赴くのか、それとも神的な存在となって現世に留まるのかあるいは近代の「科学的」世界観が説く如く、消滅してそれきりなのか。そして、こうした死後の世界の構想は、この生をいかに生きるかという問いへと連動してくる。このような死と生との捉え方を、日本では多く「死生観」とよぶ・。日本の思想文化全体と同じく、日本人の死生観もまた、良くいえば重層的であり、悪くいえば極めて曖昧である。古代神話における死者の国(黄泉国)への恐れや、平安時代における浄土教系仏教の流行など、、日本人の死生観は時代ごとに極めて異なった姿を見せるが、今日の日本人の平均的な死生観を決定づけた最も重要な契機は、やはり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徳川幕府による全国民への仏教の強制である。これにより日本人の死に関する儀礼(葬・祭)は仏教式で行われることになった。幕府が瓦解し、信教の自由が認められた近現代でもなお、大多数の日本人の葬祭は仏教式である。ならば徳川時代以降、日本人の死生観は仏教一色に塗りつぶされてしまったのか。そうではない。日本人の習俗を調査し、日本民俗学の基礎を築いた柳田國男(1875~1962)⑶は、大半の日本人は形式的には仏教の葬送儀礼を受容しつつも、観念の上では輪廻や極楽往生といった仏教の一般的な死後観を承認していないと主張した(『先祖の話』1946)〇柳田によれは,、日本の「常民」(農村で稲作を営む平均的な日本人)の死生観は、死後も神として現世にとどまり、子孫の祭りに応じて定期的に来臨し、いつまでも子孫を見守り続け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ここでは死者は輪廻することも成仏することもな・い。こうした柳田の説に対しては、仏教は日本人の死生観と葬祭とに決定的な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という反論もあり⑷、充分な結論が得られていないのが現状である。
そして如上の死生観は、日本において極めて現代的な問題と化している。大家族から核家族(単婚小家族)への急速な移行や、長引く不況による世帯年収の減少は、家族単位で営まれる葬儀の形を抜本的に変えつつある。伝統的な仏式葬儀の虚飾を批判する宗教学者•島田裕巳の『葬式は、要らない』(幻冬舎、2010)というセンセーシ크ナルな書籍が大きな反響を呼び、仏式の葬儀に代わってキリスト教式•神道式•無宗教式といった新しい形式の葬儀が増加しつつある(総体的に見ると薄葬化の傾向が著しい)。大手スーパーの葬儀業界への参入や、国際的な通信販売会社による葬儀への「僧侶派遣」事業の開始も、葬儀の商業化•形式化として深刻に受け止められた。またさらに、国際問題として焦点化して久しい靖国神社も、“国に殉じた大を神として祀る”という一定の死生観にもとづいた施設であって、それが日本人の伝統的な死生観からして自然なものであるのか、それとも近代に入ってから作為されたイデオロギーに過ぎないのかという問題が、識者たちの論戦の重要な一論点を構成している。
で、は、このように錯綜し、かつアクチ그アルな日本人の死生観に対して、朱子学はどのような影響を及ぼしたのか。ここまでの概略に瞭然な通り、“日本人の死生観”を論じる際に言及される二大因子は仏教と神道(基層信仰)であって、朱子学ではな・い。それゆえ日本人の死生観と朱子学との関わりについては従来、十分な顧慮が払われていなかったのである。しかるに本年、この関わりを後付けた労作が上梓された。本村昌文『今を生きる江戸思想一十七世紀における仏教批判と死生観』(ぺりかん社、2016.9)である。徳川幕府の統治はちょうど17世紀の初頭(1603)にはじまり、前述の通り公の宗教政策としては仏教が行われたが、開幕とともに活動を開始した儒者たちは、彼らが尊崇し、依拠した宋学者たちに倣って仏教批判を展開した。彼らの仏教批判は、一般に朱熹たちの排仏言説の単なる「焼き直し」「受け売り」にすぎないといわれ、概して独創性に乏しいものとされる。しかし本村は、17世紀の日本儒者たちの著作を丁寧に検討し、そこに日本儒者独自の思惟と意義とを見出している。本著で扱われるのは、中江藤樹(1608~1648)、林羅山(1583~1657)、松永尺五(1592~1657)、清水春流(1626~?)、向井元升(1609~1677)、熊沢蕃山(1619~1691)、中村惕斎(1629~1702)といった有名無名の儒者たちの専門的な著作と、「仮名草子」とよばれる一般大衆向けの啓蒙書とである(漢文の読解能力が僧侶や儒者のみに限定されていた近世前期社会にあって、仮名で書かれ、内容も平易で通俗的な仮名草子は、かえって本格的な漢文儒書以上の社会的な影響力を有していた)。本村によると、これら十七世紀の儒教文献の中には、1640年頃を境にして、大きな変化が認められるという。すなわち、17世紀前半の儒者は、人間の死後の問題にはほとんど言及することなく、“仏教は倫常道徳を解体する「異端」の教えであり、現世の人倫を成立させる教えとしては儒教が最勝である”という、韓愈以来の排仏言説の常套形を用いて仏教を批判した。このように「いまをいかに生きるか」(p.51)という関心に集中した儒教教説を、本村は〈生の教説〉と呼ぶ。しかし十七世紀の半ば以降になると、儒者たちは仏教の輪廻や極楽往生の説を批判し、気の聚散や鬼神の来格を説いて、積極的に朱子学に基つ’く死後の世界を語り始める。これを本村は〈生死の教説〉と呼んでいる。このように1640年頃を境として、〈生の教説〉から〈生死の教説〉への移行が見られると本村は結論づけるのである。それが開幕後半世紀ほどのタイミングで生じた理由については、戦乱の終息と社会の安定の中で、一つには「キリスト教や異国の宗教に惑わぬように人びとを教化するという意識」(p.291)が儒者たちに目覚めたためであり、もう一つには「人々が死後
のことに不安や恐れを抱き、また死生の根幹を理解していないという認識」(p.292)が生じたためと分析されている。安定と平和を取り戻した社会の中 で、公権力によって強制された仏教的死生観を越えた死生観が模索され、朱子学の教説が大きな存在感をもったのである。
本村によると、当時の日本人儒者が朱子学の死生観の根本典拠として繰り返し参照したのは、死後の気/魂魄の聚散や、同一気の子孫の祭祀による感格を説く『朱子語類』巻三•第十九条である。ここで日本儒者の死生観が朱子の「受け売り」に留まらないのは、日本儒者たちが朱子の議論の中で“気の散逸”を意図的に捨象し、むしろ“死後の霊魂の不滅”を強調してゆく点である。道徳的に律された生を生きた人は、死後も消滅することなく、超越的な存在としてこの世界に留まり、とりわけその本性は子々孫々に無窮に受け継がれてゆく。朱子の議論から日本人が読み出したこうした死生観は、神道の語彙や概念と混淆してゆく。本村は本書終章で、同じく17世紀半ばに仏教とは異なる死生観を語り出した神道家•吉川惟足(1616~1694)の死生観を取り上げ、、それが朱子学ではな、く「神避」「長隠」「日少宮」など神道の語彙を用いて語られたものでありなが、ら、「使用するタームは異なるものの、死後の霊魂がどこかへ回帰し永続するという思考の枠組みは、本書で検討してきた十七世紀中葉において形成された朱子学をベースとした死生観にも共通する」(p.293)と指摘している⑶。すでに瞭然であるカヾ、こうした死生観は、柳田が分析した日本人の民俗的死生観とも極めて似通っているのである。「日本人固有」とされ、「神道的」とされる死生観と、朱子学の死生観との思想的な交渉過程については、これからの日本朱子学研究の一大テーマとなるであろう。
なお、本村の著作は死生観についての書物の上に記された教說を分析したものであり、死生観が具体的に実践される儀ネ.Lの上までは及んでいない。本村が教說の上での転機とした1640年からおよそ30年遅れて、1670年頃に、儀礼の上での儒教的死生観の転機が訪れる。日本の先進的な政治家や儒者たちによって、『朱子家礼』に基づいた実際の儒葬が試行され始めるのである(その大半は幕府の禁圧によって頓挫した)。まず寛文12(1672)年に会津藩主・保科正之(1611~1672)の儒葬が幕府の抵抗を押し切る形で斎行され、続いて天和2(1682)年には日本随一の淳儒•山崎闇斎(1618~1682)の儒葬があり、遅れて元禄13(1700)年には朱舜水(1600~1682)を賓師とした水戸藩主•徳川光囹(1628~1700)の儒葬が行われた。こうした儀礼としての儒葬については、2012年の本稿で紹介した田世民『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礼受容の研究』(ぺりかん社、2012)がある。こちらの儀礼面でもやはり、朱子学式の葬儀が次第に国粋意識の高まりとともに神道式の葬儀へと換骨奪胎されてゆく過程が見られる⑹のが極めて興味深〉ゝ。
(作者单位:日本皇学馆大学)
2016年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综述
⊙〔日〕福谷彬 廖明飞 译
2016年日本学界有关朱子及其后学思想(狭义的“朱子学”)的研究并不多,本文拟扩大范围,介绍包括朱子学研究在内的宋学研究(广义的“朱子学”)的最新进展。本文分专著、单篇论文、译著三方面做介绍,最后总结本年度的研究并展望未来的学术走向。
一、专著
1.福田殖:《宋元明時代の朱子学と陽明学》(《福田殖著作集I》),研文出版,2016年11月。
本书著者福田殖(1933~2016)为九州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师从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史讲座首任主任教授楠本正继,同时又师事九州大学教养部冈田武彦教授。福田殖先生于本书出版前一月逝世,本书也成为作者最后一部著作。
本书由作者在已发表的21篇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由四章组成:第一章“道学诗”,第二章“宋代篇”,第三章“元代篇”,第四章“明代篇”。其中,与朱子直接相关的有第一章的《朱子の道学詩について》《宋明の道学詩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两篇讨论“道学诗”的论文,以及第二章“宋代篇”中的《朱子の死生観について》《朱子の死生観について(続)》。其他论文与朱子并不直接相关,但都是讨论宋明理学的议题。第二章“宋代篇”的《范仲淹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胡安国小論(上·下)》《張南軒に関する二、三の考察》《張南軒初年の思想》探讨了范仲淹的相关问题以及胡安国、张南轩等湖南学者的思想;第三章“元代篇”《許衡について》《元代の経学者許衡ーその思想的特色》《呉澄小論》讨论素有“南吴北许”之称的许衡和吴澄的思想。第四章“明代篇”《陳白沙思想の性格》《王陽明の心学思想の構造——学三変•教三変をめぐって》等讨论陈白沙的思想特色和王阳明的思想变化。无论哪篇文章,都以该时代的代表性理学家作为讨论对象,于此也可窥见作者的学术追求和志向。
首先,本书的第一章对“道学诗”做了考察。“道学诗”乍听起来很陌生,其实就是指道学家所作之诗。道学诗乃借用诗之形式表达道学之哲理。在本章的论述中,作者将邵雍《伊川击壤集》定位为道学诗的先驱。
作者认为,朱子道学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三十七岁时创作的《斋居感兴二十首》(《文集》卷四)。朱子于该诗序文中云:“虽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于日用之实”。作者认为据此可以看出朱子于道学诗并不追求文采,而是留意有助日常修养的伦理性,并将该诗当作“道学诗”的标杆。作者指出,道学诗是阐述哲理之诗,惯用说理之言——理语,与普通诗重视表现感情和风景不同。比如,作者根据朱子《克己》(《文集》卷二)一诗的内容,认为“克己”不单是禁欲的工夫,而是伴随着开朗自在和喜悦的自我充实的意识。如此,道学诗是通过诗的形式表现道学修养实践中的心境。福田氏通过以上的考察,发掘出“道学诗”与普通诗不同的独特价值。
其次,第二章宋代篇的《朱子の死生観について》一文,分析了朱子对“鬼神”“死生”的思考。正如分别有“在天之鬼神”“在人之鬼神”“祭祀之鬼神”,鬼神是多种多样的。作者认为,朱子将鬼神的这种多样性,归因于“气”的多面性,通过阴阳二气的屈伸往来解释鬼神。对于鬼神这种本来是超自然非现实的存在,朱子尝试做出符合自然科学的、合理的解释。但是,另一方面,朱子对视鬼神与气为一的弟子说“是这气里面神灵相似”[1],可见朱子避免将鬼神等同于气。此外,关于“鬼神”,朱子又说“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处且莫要理会”[2],承认鬼神也有无法根据理推阐的一面。根据以上两点,福田氏指出,朱子的鬼神生死观本质上存在着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和通过因果律解决的方面,事实上毋宁说,正是无法由理推阐的一面成就了朱子理论的自恰完足。
过去一直将“祭祀感格”说当作朱子鬼神论的重大缺陷,在《朱子の死生観について(続)》中,福田氏对“祭祀感格”说进行了再探讨。所谓“祭祀感格”说是指,人死之后构成人体的气也随之飘散,但并非立即散尽,通过适当的祭祀,先祖之气能够感通而至(感格)。朱子从将鬼神与气相联系做出合理解释的立场出发,试图说明祭祀这一本来非合理性的儒家传统仪式的意义。针对此说,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岛田虔次质疑气如果完全散尽,也就没有必要祭祀。此一质疑揭示了朱子祭祀感格说的缺陷所在——朱子的合理主义倾向与传统儒家的非合理主义的龃龉不合。[3]
对于岛田氏的上述观点,福田氏站在拥护朱子的立场上重新探讨了祭祀感格说的内容。根据《语类》中朱子的发言,福田氏指出:朱子认为子孙的身上延续了祖先之气,通过祭祀,子孙身上的祖先之气便会伸长,而随祭祀感格的祖考之精神,存在于祭祀者自身的精神之中。即不同于过去将朱子所说“祭祀感格”理解为物理现象,福田氏将之理解为祭祀者心中的问题。于是,福田氏认为“祭祀感格”说是在可以合理认识的“知”的世界和宗教的“信”的世界并存的状态下成立的。
以上介绍了本书与朱子直接相关的论文。正如上述,本书著者福田殖师事楠本正继和冈田武彦,在具有浓郁的九州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特色的学风中形成自己的学问体系。九州大学的宋明理学研究,并不单是理论分析、文献考证,而且还有尊重体悟的传统。作者认为“道学诗”是对修养者心理状态的表现的观点,以及从祭祀者的心理问题的角度重新理解祭祀感格说等,都充分发挥了九州大学宋明理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另外,文末附载疋田启佑《福田殖先生の学問》一文,对本书各篇的内容做了扼要介绍,可参考。
与本书同时出版的《日本と朝鮮の朱子学》(《福田殖著作集Ⅱ》)分本篇和附篇。本篇讨论了李退溪等朝鲜儒者[4]和楠本硕水、楠本端山及大桥讷庵等日本儒者[5]的思想。附篇收录了作者撰写的介绍老师辈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先生之学问的文章。因为该书讨论的是关于日本朱子学研究和朝鲜朱子学研究的内容,不属于本文介绍的范围,故在此只提供书讯,请读者一并参考。
2.川原秀城[6]主编:《朝鮮朝後期の社会と思想》,勉诚出版,2015年2月。
《朱子学年鉴》设立了韩国学界的朱子学研究和日本学界的朱子学研究的项目,但关于日本学界的朝鲜朱子学研究则付诸阙如[7]。虽然本文并无义务介绍日本学界的朝鲜朱子学研究,还是深感有责任对此稍作介绍。
本书编者川原秀城,是当今日本学界朝鲜朱子学研究的第一人。本书收录九篇论文,皆由活跃于第一线的学者撰写,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角度,考察伴随1592年丰臣秀吉的入侵(“倭乱”),1627年、1636年满清的两次入侵(“胡乱”)带来巨大变动的朝鲜后期社会。其中,与朝鲜朱子学直接与关的论文有吉田光男[8 ]《士林派と士禍言説の成立》、川原秀城《宋時烈の朱子学——朝鮮朝前中期学術の集大成》。
二、论文
1.种村和史:《継承と刷新:宋代詩経学の理念と方法》,庆应义塾大学日吉纪要《中国研究》第九号,2016年3月。[9]
种村和史氏长期致力于宋代《诗经》学的研究,本《年鉴》也曾多次对其研究加以介绍。本文是种村氏对自己历年发表的21篇研究论文的总结性论述。
作者的具体考察和论证,请直接参考该文末尾所附目录揭载的论文。在此仅介绍作者关于《诗经》学研究的整体观点。
在本论开头,作者概述了自己迄今为止研究宋代《诗经》学的目的所在。
一直以来,笔者都以阐明如下问题为目标开展研究:宋代《诗经》学者继承了前代《诗经》学的哪些方面,又出现哪些新变,与此同时,他们是如何建立自身解释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又是由怎样的学问理念作为支撑,在中国古代《诗经》学史上占据怎样的位置。
种村氏对自己的研究目的做了如上说明,该文主要讨论以下三点。(与下述三章对应)
(1)经过对代表性的《诗经》注释书的分析确定宋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其与各时代《诗经》学的关系。
(2)作为《诗经》解释方法论基础的认识。
(3)儒学的道德观及时代状况在《诗经》解释中的反映。
在第一章《刷新が内包する継承、継承から生まれ出る刷新》中,种村氏总结了自己对欧阳修《诗本义》、王安石《诗经新义》、苏辙《诗集传》、程颐《诗说》等北宋《诗经》学代表性著作的研究。
首先,种村氏指出,这些著作都受到《毛诗正义》影响,并且相当重要。比如欧阳修《诗本义》经说的确立,《毛诗正义》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关于《诗经》的比喻,欧阳修认为“古之诗人取物比兴,但取其一义以喻意尔”(《诗本义》卷二《鹊巢》)、“诗人引类比物、长于譬喻”(《诗本义》卷五《破斧》)[110种村氏认为,这两点分别是在《毛诗正义》“兴者,取于一象”(《国风·周南·兔罝》),“兴必以类”(《国风·召南·击鼓》)之说的基础上加以展开的。作者更认为,欧阳修对《毛诗正义》中仅仅针对个别的解释加以融会贯通,扩大到《诗经》整体的解释中。此外,认为朱子的“淫诗说”导源于欧阳修的“准淫诗说”,而欧阳修的“准淫诗说”实际上在《毛诗正义》已有先例。过去单纯强调《毛诗正义》是宋代学者批判和超越的对象,而作者提示我们《毛诗正义》也为宋代学者的解释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可以说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其次,在第二章《宋代詩経学の解釈理念と方法》中,种村氏提出以下三个术语突显宋代《诗经》学的特征。
一是“泛论”“泛言”。将诗篇的一部分,解释为体现了全诗的整体意义或者普遍教训的内容,以“泛论”“泛言”解之。这样的方法不见于《毛诗正义》,而见于欧阳修的《诗本义》,此后在其他注释书中也有所体现。
二是“假设”“设言”。认为诗篇的一部分,并非如实记录事实,而是诗作者的虚构,以“假设”“设言”解之。这类方法不见于毛传、郑笺,而见于《毛诗正义》。朱子《诗集传》中有所使用,此后学者也经常使用。
三是“思古伤今”“陈古刺今”。这类概念本身已出现于《诗序》,自然毛传、郑笺、《毛诗正义》也继承了这一解释角度。宋代解释的特色是,譬如王安石认为,诗中歌咏勾起对古代回忆的现在的部分,和歌咏想象的古代的部分两个不同的时间层同时存在。
通过以上的考察,种村氏指出,宋代《诗经》学者的解释立足于这一前提:诗作者秉持明确的意识,综合虚构和现实、过去和现在的不同维度、层次的事件,加以组织创作。
在第三章解釈における道徳的•政治的意図と文学的意図との不可分性》中,作者指出宋代《诗经》解释中强烈反映了当时形成的道德价值观。比如,对于生逢乱世深陷不幸生活中的民众离开父母之邦移居他国的行为,汉唐《诗经》学采取有条件地认可的解释。但是在宋代,这些行为都是忌讳,因而尽量不将有关诗句解读为离开父母之邦移居他国。这是被周边强大的异民族国家所包围的宋朝的历史状况所需要的伦理观,在《诗经》解释上的反映。另外,宋朝的《诗经》解释,有排除讽刺前代君主行为——“追刺”的倾向。这一倾向反映了在宋代自由批判政治受到限制的事实。
通过以上的分析,种村氏认为,宋代《诗经》学根本上共通的学问倾向,一言以蔽之,是将阐明诗篇的构造和追究其逻辑性融合为一。
目前为止的宋代《诗经》学研究,重在阐明个别著作的特色。种村氏的研究,则是在考察各书特性的基础上,将这些特性作为理解宋代《诗经》学整体的指标,通过分析这些指标,以期勾勒宋代《诗经》学共通的特征,明确宋代《诗经》学的特色和倾向。
2.吾妻重二:《〈家礼〉の和刻本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9号,2016年3月。[11]
《朱子家礼》作为士庶人家举行冠、婚、丧、祭之礼的指南,在东亚世界有着广泛影响。日本江户时代也出版了大量的和刻本,其影响可见一斑。吾妻氏在本文中,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日本现存的和刻《朱子家礼》诸本做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根据吾妻氏的调查,《朱子家礼》的和刻本至少有以下四种:浅见䌹斋点《家礼》五卷、图一卷,《文公家礼仪节》八卷,小出永安点《新刻性理大全》家礼部分四卷,《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家礼部分二卷。该文以前三种和刻本为对象,讨论了各自的成立、特色及所据底本。以下略述吾妻氏此文的要点。
(1)浅见䌹斋点《家礼》五卷[12]
作者指出,《朱子家礼》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1)周复五卷本系统有:宋版、公善堂覆宋本、明版、《四库全书》本、郭嵩涛本;2)《性理大全》系统有:纂图互注本、《朱子成书》本、《性理大全》本、和刻本。浅见䌹斋校点本(和刻本)虽为五卷本,但从文本内容来看,属于《性理大全》本系统。然而,除了和刻本,《性理大全》本系统中并无其他版本为五卷本。此外,朝鲜本有四卷本、七卷本而无五卷本。因此,浅见校点本当是以《性理大全》本《朱子家礼》为底本,重新编辑分卷,试图复原《朱子家礼》原本五卷的形态。[13
(2)和刻《文公家礼仪节》本
明成化间邱濬从便于理解和实际行礼出发,改编《朱子家礼》,成《文公家礼仪节》八卷。《仪节》在明代非常流行,陆续出现各种重辑、重订之本。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由京都大和田九左卫门刊刻于万治二年(1659),底本并非邱濬原本,而是杨慎手定、种秀堂藏版的崇祯刊本,因而文字内容也与邱濬原本不尽相同。
(3)和刻《新刻性理大全》本(小出永安点)
胡广、杨荣等奉敕编纂的《性理大全》七十卷为永乐“三大全”之一,1415年编成后,由内府刊刻颁行天下。其中,卷十八至二十一收录《朱子家礼》。正德年间,坊刻《性理群书大全》(一题《性理群书集览》)七十卷附载玉峰道人所撰“集览”。同时,又出现附载周礼所撰“补注”之本。明中期以降,《性理大全》更出现各式各样的增注本,版本情况相当复杂。[14]
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七十卷,由京都的田中清左卫门和小嶋弥左卫门刊于承应二年(1653),小出永安为之校点。和刻本附载了《性理大全》原本没有的“集览”和“补注”。作者认为,和刻本的底本虽难以确指,但可以推测其祖本为嘉靖三十九年(1560)进贤堂刊《新刊性理大全》本(内阁文库藏本),其底本当为该系统之版本。
吾妻氏长期关注《家礼》的文献学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部分成果可参考《朱子〈家礼〉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近年,吾妻氏致力于搜集整理日本的《家礼》相关文献,以《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之名影印出版,并附《解说》。2010年出版第一辑,2016年出版至第六辑,该辑收录了以上三种和刻本。本文也是作者在第六辑《解说》的基础上增订而成。
3.松野敏之[15]:《宋代訓蒙書と朱熹〈小学〉》,《国学院杂志》第117卷第11号,2016年11月。
在朱子《小学》以前,已经出现了不少以童蒙教育为目的而编纂的训蒙书。朱子编《小学》[16]曾经参考过的就有吕本中《童蒙训》、吕祖谦《少仪外传》等。朱子的《小学》正是以此前积累下来的训蒙书为基础编纂成书的。松野氏此文,首先概述了朱子编《小学》参考过的训蒙书,其次分析朱子如何引用这些文献据以编成《小学》,从而明确《小学》的特征。
松野氏指出,《少仪外传》等《小学》以前的训蒙书,是根据所引用书的不同编排叙述,而《小学》则是立“立教”“明伦”“敬身”等门目,根据内容的不同分类叙述。与此同时,朱子也留意各个门类篇幅的平衡,务必网罗人事的方方面面。松野氏认为,以上这些编纂《小学》的考虑,与朱子把《小学》当作大学的预备阶段看待密切相关。就朱子学而论,研读以四书为代表的经书是要探索“事之理”,《小学》的目的则是提示“格物”和“敬”的对象——“事”的具体内容。
过去大多将《小学》置于朱子学的框架内理解,松野氏从“训蒙书”这一角度,通过与宋代其他训蒙书的比较,明确朱子在《小学》编纂上的思考,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察《小学》在朱子学中的意义。
三、译著
1.绪方賢一、白井顺:《朱子語類訳注》卷98~100,汲古书院,2016年12月。
日本中国学界立志通过合作共同将《朱子语类》140卷全部翻译成现代日语,并做校订、注释。2007年出版了第一册(卷1~3)译注,至2016年共出版十三册。本年出版的三卷译注,其中卷九十八、九十九为《张子之书一·二》,卷一百为《邵子之书》。
2.李退溪著、难波征男校注:《自省録》,平凡社《東洋文庫》,2015年10月。
朝鲜大儒李退溪从近200通与弟子、友人的书信中,择取22篇,编定成册,以为自省之用,故名《自省录》。本书即为《自省录》的日文译注本,卷末附难波氏所撰解说《李退渓の〈自省録〉と東アジア体認学》。
四、总结和展望
2016年狭义的朱子学的研究并不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学界的朱子学研究停滞不前,而是因为学者对宋学的关心由朱子本人扩展至与朱子有关的其他思想家。正如后附《2016年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书目》所载,有不少学者将视野聚焦于陆九渊、杨万里等与朱子同时代的思想家。在日本学界的宋学研究者中,如土田健次郎、小岛毅等并不以朱子为宋学的中心,而是将朱子相对化,认为朱子只是此一历史时期活跃的思想家之一。可以预期的是,今后在此立场上开展宋学研究或成为一种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介绍的川原秀城主編《朝鮮朝後期の社会と思想》和难波征男译注《自省录》二书皆出版于2015年,因笔者的疏忽,未能及时予以介绍,敬祈读者海涵。
(作者单位: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译者单位: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
2016年美国朱子学研究综述
⊙戚轩铭
2016年美国有关朱熹的研究成果似乎较过去数年有所逊色。尽管如此,其中亦有可兹报告者。根据笔者所收集到的文章,本文将简述美国学者对于朱熹的研究,或是在美国出版的有关朱熹的研究。
首先介绍田浩教授(Hoyt Cleveland Tillman)2016年一年的研究。笔者于2016年曾提到田浩教授曾在2015年11月到台湾政治大学做演讲,其中两场的主题都与朱子学有关。(第二场《朱熹“淫祠”祈雨文的分析及其深义》的内容与田浩教授和陈曦教授的文章重复)[1 ]讲座完结后不久,政治大学便将有关讲座内容制作成书。[2]由于笔者在2016年的报告中只十分简略地提及有关讲座的主题,故这里将对最后讲座的内容——《朱熹对“夷”的看法及其价值观的普世意义》做更详细的描述。
田浩教授这次演讲的内容大致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先对宋代道学家有关华夷之别的问题进行分析。他以2014年杨劭允博士撰写的博士论文为中心展关讨论。[3]田浩教授指出,杨劭允的论文主要批评了列文森(JosephLevenson)和他对于道学群体有关夷狄的观点。根据田浩教授的说法,杨氏认为他们太着重以“文化”来说明当时的华夷之辩。但是,杨氏认为宋人是将夷狄视为一种“不道德的、在思想上属于异端的以及不合乎礼仪的状态。”[4]田浩教授却认为杨劭允博士是以当代对于文化的标准来理解宋人的。事实上,根据田浩教授的解释,杨劭允博士上述所提到的三个标准正是朱熹和其他宋代人对于“文化”的理解。[5]由杨劭允博士的论文,田浩教授将演讲的重心转到对当代中国有关普世价值发展的讨论上。田浩教授以《朱子家训》在21世纪的发展为例,说明了中国对于普世价值态度的转变。他认为在21世纪之初,中国政府留下空间予人讨论《朱子家训》对中国国家建设的好处和普世意义。但是自2012年后,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国内开始对普世价值进行批评。宣扬普世价值变得困难,因为国内学者认为普世价值便是欧美价值。田浩教授认为如有文化自信,不必怕讨论普世价值,因为它必然会受到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学者在面对普世价值的问题时,应保持开放性,并包容各种文化。田浩教授向来都十分关注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代的影响。他在2016年12月曾到香港进行两场名为“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活动。第一场演讲的题目便是《在应对危机中不断发展单一行政权力:“9·11”之后一个美国人思考中国政治制度的皇权》。由于讲座主题与朱子学的研究关系不大,故这里不再详述。但从中我们亦可看出田浩教授的学术旨趣。
顺带一提,田浩教授于2012年与德国学者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合撰的专著《宋金元代文化权威与政治文化》(CulturalAuthorityandPoliticalCultureinChina:Exploring Lssues withthe Zhongyongand the Daotong during the Song,Jinand YuanDynasties)现正筹备翻译成中文版,有进一步消息将会在未来向各位报告。
除了田浩教授的研究外,美国著名的学术期刊《东西哲学》(PhilosophyoEastandWest)刊登了郑淑红教授一篇名为《朱熹与埃克哈特大师的智慧和意志》(LntellectandWillinZhuXi and MeisterEckhart)的文章。[6]虽然论文作者现执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由于论文发表于美国的期刊之中,故笔者在撰写这份报告时决定一并收录,供有兴趣的学者参考。郑教授的论文指出在新儒家中出现了两个门派,分别是理学和心学。同样的,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亦有方济各会(Franciscan)和道明会(Dominican)。作者因此认为比较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与作为道明会一员的埃克哈特大师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解远东和西方拉丁世界思想发展的分别的门钥。根据郑氏的分析,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人的智慧(知)往往具有最关键的作用,它一方面决定人的行为,同一时间比人的意志更为重要。有趣的是,朱熹在讨论“知”时往往是提及它的作用,而不是用它来从生理上定义人类。换言之,朱熹本人的思想与儒家强调人的道德自觉的传统是相符合的。作者认为,朱熹的目的是要突出儒家的价值并以此在三个方面:个人精神自觉(personal spiritual awareness)、社会责任(socialaccountability)以及超验的重要性(transcendent signiffcance)压倒道教和佛教在当时的影响,并因此而提到他对“理”的解释,即宇宙的本源与永恒的真理。必须申明的是,尽管朱熹认为“理”的重要性是超验的,但他不认为“理”存在于一个与现实世界分割的空间之中。同时,朱熹对于人的“知”的重视并不代表他据此认为人类的价值比其他生物高。他之所以强调“知”,是因为它可作为儒家自我修养的出发点。作者因此认为,朱熹有关“知”的论述只是为儒家的自我修养提供一个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基础。
另外,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亦出版了一部由David Edward Jones与HeJinli合编,并收录中西学界有关朱子学研究的论文集,名为《回到朱熹:太极所呈现的模式》(Returning to ZhuXi:EmergingPatterns withinthe SupremePolarity)。[7]这部论文集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对朱熹的诠释”(Interpreting with Zhu Xi)共收入四篇论文,分别为张立文的《朱熹的形而上学》(ZhuXi'S Metaphysics)、艾周思(Joseph A.Adler)的《论〈太极〉的翻译》(OnTranslatingTaiji)、陈来的《〈朱熹中庸章句〉中的儒家思想》(ZhuXi'j ConfucianThoughts onthe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fthe Zhongyong)及金永植的《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的事物:对儒家学说界线所作的定义与扩充》(ZhuXi onScientificand Occult Subjects:Definingand Extending the BoundariesofConfucianLearning)。第二部分为“通过朱熹而思”(Thinking through ZhuXi),其中收入了三篇论文。分别是Kirill O.Thompson的《朱熹思想中的对立与互补》(Oppositionand Complementarity inZhuXi's THought)、刘述先的《论朱熹心灵世界的建构》(Onthe FormationofZhuXi’s SpiritualWorld)和EihoBaba的《理作为气的呈现方式:一个非还原性的诠释》(Lias Emergent PatternsofQi:ANonreductiveLnterpretation)。第三部分“应用朱熹的思想”(ApplyingZhu Xi)则共有五篇论文。它们分别是John Berthrong的《波士顿的道学:现代对朱熹哲学思想的转化》(BostonDaoxue:AModernTranspositionoZhuXi'sPhilosophicalVision)、Stephen C.Angle的《朱熹的道德伦理与胡果·格老秀斯的挑战》(ZhuXi's Virtue Ethicsand the GrotianChallenge)、蒙培元的《如何统一所以然与所当然?一个对朱子著作的解释》(How to UniteIsand Ought:AnExplanationRegarding theWorkofMa ster Zhu)、Kwong-loi Shun的《论愤怒:儒家的道德心理学》(OnAnger:AnEssay onConfucian MoralPsychology)以及彭国翔的《心理与肉体的修炼:朱子读书法在宗教上的意义》(SpiritualandBodily Exercise:The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ZhuXi's Reading Methods)。据编者所言,朱熹作为一位“集大成”者,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部文集所收录的论文,正是希望在西方哲学世界的想象底下探讨朱熹别树一帜的思想。
在学位论文方面,Wong Pui Fong博士在2016年以《从独处到走进群体:新儒家在自我转化的问题上对归心祈祷的运用》(FromSolitude to Solidarity:ANeo-ConfucianAppropriationofCentering Prayer intheTranSformationofSelf)一文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神学院得到博士学位。8]这篇论文旨在探讨汤玛斯·基廷(Thomas Keating)有关归心祈祷的学说如何为朱熹有关静坐的学说和宇宙论所支持与扩充。她认为朱熹有关宇宙论的三个概念:气与理作为宇宙的两个基本单位;动与静是宇宙运行的方式;以及两极与中庸是维持宇宙和平与创造的基本法则启发了人们对于基督教的人论(Christian anthropology)与沉思的研究。基于Sandra Schneiders与Francis Clooney有关比较神学的理论,作者认为朱熹所提倡的“静坐”这门工夫是必需的,因为人可以通过静与终极的道产生联系。通过近代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作者认为Mindfulness(笔者并未能为这个名词提供一个准确的翻译,为免误导读者,故选择只引用英文原文)在西方社会渐渐成为达到幸福的途径。这亦间接为朱熹与汤玛斯·基廷的学说提供证据。作者期望,她这篇论文能令学界对基督教中沉思的价值和作用有更深入的认识。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走向世界与未来的朱子学研究
⊙赵金刚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致广大而尽精微”“综罗百代”,深刻影响着南宋以后的中国思想世界,对东亚世界产生了持续影响。近年来,“朱子学”一直是中国思想研究的重要领域,对朱子学的研究涉及哲学、文献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诸多学术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也不断扩展。以中华朱子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下二级分会)和朱子学会(一级学会,挂靠厦门大学)作为支撑,关于朱子学的研究稳步推进,厦门大学国学院、上饶师院等学术机构还联合成立了“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朱子学会专门设立《朱子学年鉴》编委会[1],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同时日韩欧美等学者对于朱子学也十分关注,有关朱子学的国际学术交流十分活跃,几乎每年都有关于朱子学的国际会议在全球各地召开,海外学者关于朱子学研究的著作也层出不穷,“朱子学研究的全球化早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2]。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已有学者试图以朱子学为思想资源,尝试将朱子学与中国当下具体问题以及全球化问题结合,处理具体的时代问题;还有学者从朱子学出发,努力建构新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可以说,朱子学研究一方面已经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哲学界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一个典范,而另一方面,朱子学已经走向了未来,为新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
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具体总结和分析朱子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以及新的研究趋势。
一、文献整理与出版
中国哲学研究的推进与对原始文献材料的解读息息相关,相关文献的结集与新材料的发现往往会促进某些领域的发展。朱子学的稳步发展,与朱子学文献的整理关系也十分密切。经过多年的整理,朱子著作较为全面地出现在世人面前,为学者研究朱子学提供了有力支持。这里首先要提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历时十年整理编辑了《朱子全书》[3]及《朱子全书外编》[4],基本上收录了朱熹所有的文献资料,并对相关逸文进行收集辨析,为学者研究朱子思想提供了重要支撑。除了对相关文献进行点校之外,《朱子著述宋刻集成》[5]等原始文献也影印出版,为学者探究朱子著述的原貌提供了方便。
除了集中整理朱子著作,有关朱子单个著作的整理与出版成果也较为突出,这首先体现在对《朱子语类》的进一步研究与整理上关于《朱子语类》在研究朱子思想中的作用,历史上争议较大。朱子的弟子在《语类》最早整理出版后就有分歧,如黄榦就曾说过:“语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而李心传则与黄榦的态度相反,认为朱子去世之后,如果学者审慎地使用《语类》的话,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他的思想。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清代,如王懋竑就认为《语类》中不可信的部分颇多,而同时代的朱止泉却极为重视《语类》。今天对于《语类》的作用,还有学者存在不同看法。但正如邓艾民先生指出的,如果能对《语类》分析应用,《语类》的价值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语录中有些晚年的思想,纠正他早期著作中某些意见,更可看出语录的价值。何况,语录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他的文集中有叙述简略甚至完全阙如的,语录的重要性就更明显”。[6]邓先生指出的“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理气”问题,《文集》等其他材料,在很多点上只有“孤证”,必须借助《语类》才能进一步研究。《语类》的意义不能否认,但《语类》的问题毕竟也很多,尤其是在后世传刻过程中导致了一些新的问题。“分析应用”《语类》,首先需要对《语类》的版本有细致的校勘。这一工作,可以说无论是中华书局点校本《朱子语类》还是华师大古籍所《朱子全书》本《朱子语类》,都做得不尽人意。因此对《朱子语类》展开细致的文献研究,可以说是近些年朱子学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
现存最早的《朱子语类》版本为日本九州大学所藏《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与黎靖德本《朱子语类》规模相当,分卷基本一致,仅卷一百零一、卷一百零三、卷一百三十八、卷一百三十九与卷一百四十互有错杂。然而《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中却又有许多黎靖德本《朱子语类》中没有的重要内容,如《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有而黎靖德本《朱子语类》无的朱子语录,朝鲜古写本和黎靖德本都有、而朝鲜古写本更详细的朱子语录,还有淳祐十一年(1251)吕年为《徽州刊朱子语类》所作的序,以及宝祐二年(1254)魏克愚为《徽州刊朱子语类》再校正本所作的按语、跋等。”然而中华书局以及《朱子全书》点校本均未参考这一版本。胡秀娟博士的博士论文则关注了《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研究》[7]一书,该书通过对比《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与黎靖德本《朱子语类》,辑录了大量朝鲜古写本有而黎靖德本无的《朱子语录》和朝鲜古写本详细而黎靖德本简略的《朱子语录》,还整理出朝鲜古写本和黎靖德本有所差异的字、词、句。于此前后,徐时仪、杨艳两位学者出版了《朱子语类汇校》[8]一书,以徽州本为底本,汇校成化本等诸本,将成化本无而底本有、底本有而成化本无,以及二本皆有而顺序不同者一一校出。朱杰人教授还在与胡秀娟博士合作,希望在版本校勘上更进一步,出版《〈朱子语类〉合刊本》,我们可以期待这一著作的问世。可以说,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徽州本与其他版本《朱子语类》的差异基本上已经呈现在今人面前,为对朱子思想进一步的哲学上的探究提供了较好的文本支持。
除《朱子语类》在文献上的研究获得进展外,《仪礼经传通解》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朱子晚年的学术重点之一就是编著《仪礼经传通解》,但朱子生前并未完成此书,其弟子黄榦续撰《丧礼》《祭礼》,但是《祭礼》仅写成草稿,杨复经数十年整理、编辑最终成书。经由杨复完成的《仪礼经传通解》在当时影响颇大,可惜后来失传,明清学者已不能得见。至清末陆心源复得此书,但藏本后归日本静嘉堂,静嘉堂非秘不示人,而一百年来未有学者前往阅读。桥本秀美和叶纯芳于静嘉堂阅读此书,历时三月抄写全书,并花费两年时间整理,最终出版了《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9]一书,使杨复所续编《祭礼》得以示人。不仅如此,二人后又影印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藏宋刻本《仪礼经传通解》,并用元明善本补全阙文,成《影印宋刊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10]一书,为进一步研究朱子礼学提供了版本依据。
朱子礼学另一重要著作为《朱子家礼》,然而关于此书的真伪历代聚讼纷纭,至今还有学者怀疑此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出版了《朱熹〈家礼〉实证研究》[1]一书,一方面汇集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家礼》非伪,同时从朱熹弟子著作和后世藏书家藏书目录来理清《家礼》版本的发展演变,把《家礼》版本分为原稿本、宋刻本、元刻本,揭示《家礼》宋元版本系统;一方面把朱熹《家礼》放在朱熹家礼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演变历程中加以考察,通过对《家礼》思想内容的考察,来阐释朱熹博采古今众家的礼学特点,并结合晚年的礼学著作和语录来探讨其礼学思想的变化发展。吴震先生以为,“本书研究在考证上有重要创获。我们知道,朱熹《家礼》自清代王懋竑提出‘伪作说’并得到《四库全书》编撰者的认同以来,几成‘定说’。虽然在此之前已有学者隐隐约约地表示怀疑《家礼》可能并非朱熹亲撰,如元代‘武林应氏’(经作者考证,即钱塘应本),但对此进行所谓严密考证的无疑是王懋竑。当然,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的学者对此‘伪作说’屡有质疑并提出了种种反驳,但是从文献考证上全面推翻王懋竑的‘伪作说’,认定《家礼》为朱熹亲作,唯有通过作者的本书研究才最终得以确立。因此,可以说作者的这项研究工作既具有颠覆性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作者的研究结论使得《家礼》得以名至实归——重新归入朱熹名下,而且这一研究结论亦完全有可能成为此后学界可以信从的‘定说’”[12]。
关于朱子后学的文献整理与出版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朱子后学继承朱子学术,对很多问题有重要的推进。但相比于对朱子本人的研究,对朱子后学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尤其是对比阳明后学已经研究到四代五代的情况,这一点尤为明显。文献的匮乏是朱子后学研究薄弱的一项重要原因。南昌大学承担了“朱子门人后学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旨在推进朱子后学的相关研究,而文献整理则是这一项目要做的第一步,目前黄幹、辅广、饶鲁等朱子重要门人的资料辑佚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相信这一工程势必会推动朱子后学的相关研究,对朱子学相关哲学问题有进一步的推进。
二、哲学问题的深入拓展
在中国哲学界,朱子学的研究一直以来比较活跃,每一段时期都会有新的成果产生,关注的问题域也不断扩展。朱子学的研究首先与研究典范的确立关系密切。
在大陆学界,冯友兰、张岱年等老一代学者都十分重视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学界流行“范畴”研究,对理学相关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做了细致的分析,陈来先生《朱子书信编年考》和《朱子哲学研究》二书更是确立了朱子研究的典范。《朱子书信编年考》把朱子近两千封信做了一个时间的编排,特别有助于学者从发展的观点看待朱子思想的演进,而《朱子哲学研究》则将其成果应用到具体的哲学分析上,并采取“概念分析法”系统地研究朱子哲学的基本范畴、概念与问题。陈来先生将朱子哲学总结为“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已发未发、心统性情、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主敬与涵养、格物穷理、道心人心、知行先后”等十个基本哲学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确立了方向。
在港台学界,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等先生也都十分重视朱子学。牟宗三有《心体与性体》一书,将伊川与朱子视为一系,侧重于朱子对中和问题、心性情问题、理气问题、《仁说》问题的阐释,并从早中晚三期观察朱子思想的演进。牟宗三先生的研究深刻影响了港台学界对朱子哲学的一般看法,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牟派学者基本上沿着其基本理解对朱子哲学进行阐释。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则与牟宗三的朱子学研究不甚相同,他主要类集朱子思想言论,又按数十个条目分门别类,以钱穆先生自己的观点将朱子思想构造成一个体系。《朱子新学案》不仅涉及朱子哲学思想,还旁涉经学、史学、文学,全方面评述朱子与其他思想家或思想体系的关系,可以说是关于朱子研究一个较为全面的著作。
海外朱子学开展较早,这以陈荣捷先生为代表,“1946年H.F.MacNair在柏克莱出版的英文《中国》一书中即有陈荣捷所写的‘新儒学’一章,这是战后西方叙述理学专篇之始,也是叙述朱子思想专篇之始”[113,之后陈先生发表了一系列与朱子学有关的论文。60~80岁之间,陈先生开始专注于朱子学研究,并将《近思录》(1967年)翻译成英文。陈荣捷先生的学术贡献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欧美学界关于朱子学的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一定时期内,中国与欧美的朱子学研究交流甚少,1982年陈荣捷先生在檀香山组织“国际朱熹会议”之后,大陆与其他区域的朱子学交流日益增多,最近数年则更加频繁,学者的研究能够集各方之长,诸多问题的研究实现突破,哲学问题的辨析度越来越深入,领域也由存有论逐步扩展到朱子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生态哲学等方向。下面,我们集中叙述近些年在朱子学哲学层面上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
理气论是朱子哲学存有论最基础的命题。近年来,学者在相关问题上进一步细化。2011年,藤井伦明教授出版《朱熹思想结构探索——以“理”为考察中心》[14]一书,围绕着“理”“诚”“知”“心”等概念,从朱子文本出发,详细考察朱子的思想结构。在作者看来,“朱熹思想世界之样貌,其显然并非一以外在‘静态式’之‘理’为基础而建构出的思想;而是一以内在‘动态式’之‘理’为基础而开展出的思想。也就是说,对朱熹而言,这世界的所有自然现象以及道德行为,原原本本系内在之‘理’活泼地发露、开展,而且朱熹思想的存在论、心性论、工夫论等,无一不是以此一动态式之‘理’为基础而建构出的”。这就与以往牟宗三先生将朱子的理理解为“只存有,不活动”的观点不同了。乔清举教授《论朱子的理气动静》[15]一文亦可以看作是对牟宗三先生观点的一种回应,文章区分形上之动静与形下之动静,认为朱子的理在形上层面还是“动”的,这种动与理的“兼”“有”“涵”“该贯”等说法有关,表现在理之主宰作用、理生气等层面,最终是理的自我实现。杨立华教授《体用与阴阳:朱子〈太极图说解〉的本体论建构》[16]则从《太极图说解》出发,诠释朱子思想中的理气关系,文章认为“朱子在《太极图说解》中确立的本体论架构,是他的中岁定法,之后始终没有改变。太极是理,是体,而非用。朱子有时讲太极之体用,只是理论表述上的不得已。‘阳之动’对应的是用,而‘阴之静’对应的是体。朱子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立言角度的不同。‘体用一源’从理上说,理虽是形而上者,但其中已有万象;‘显微无间’从象上说,至著之象虽然是形而下者,但理即寓于其中。‘体立而后用行’,体非独立之体,体自有象;用则是体之发用,体在其中。义智为体、仁礼为用。太极作为理,‘不离于形’,也‘不囿于形’,太极有动静。理无造作,但理必有气,气自然能凝结创造;理无动静,但既有理,便有气、有象,便有动静”。这一论断突出了《太极图说解》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丁为祥教授《从生存基础到力动之源——朱子哲学中的“气”论思想》[17]则专门讨论了朱子对气的论述,文章认为“从理气关系的角度看,气始终充当着一切存在之前提基础的作用;而从生物之具到人的生存基础,就是朱子哲学中的气在宇宙天道与人生世界中的两种不同的表现。但无论是生物之具还是生存基础抑或是宇宙发展的力动之源,气既是作为所有存在之前提基础出现的,同时也代表着人所必须超越、驾驭与主宰的对象;而从生存基础到力动之源,则充分展现了从自然到天性这一人既生存其中,同时又不得不时时面对的世界”。文章揭示出的气在朱子思想中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
鬼神观可以说是近些年朱子理气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吴震教授《鬼神以祭祀而言——关于朱子鬼神观的若干问题》[18]一文,从祭祀的角度考虑朱子的鬼神观,文章通过对朱熹“以气释鬼神”“鬼神以祭祀而言”的诠释方式以及“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等观点的深入探讨,指出对朱熹而言,鬼神问题主要是祭祀的问题而不是言说的问题、是宗教的问题而不是气学的问题。朱熹在鬼神问题上强调祭祀实践的重要性,这是朱熹宗教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朱熹对儒学鬼神论的一大理论贡献。冯兵教授《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朱熹的鬼神观辨析》[19]也关注了朱子鬼神观与礼学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鬼神‘实有’,源于理气的共同作用;出于‘正理’的鬼神‘无形与声’,而‘非理之常’的鬼怪却有可见之‘形质’;鬼神思想是构成礼学的重要部分,鬼神与礼乐有着内在相通性。朱熹对鬼神的讨论,主体上是一种哲学化的鬼神观,但十分复杂,它既有较强的理性主义精神,又受到了世俗的鬼神迷信及佛道二教的影响,从而染上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可视为传统儒家鬼神观念的一个代表,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王文娟博士《朱熹论感应》[20]一文,则关注了感应与鬼神的关系,认为“祭祀中‘感应’之理的运用既反映了民众在世俗生活中的精神诉求,又体现出一种对生命本源的敬畏感与归属感。此外,与感应相结合的劝善言论在具有政治和伦理双重导向的同时,也体现出不同于世俗功利导向的理性精神”。
在心性论上,“人心道心”问题,“明德”问题依旧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而朱子的仁学也逐渐成为这几年研究的一个重点。魏义霞博士《朱熹对仁的诠释》[21]一文,认为“通过对仁的诠释,朱熹建构了本体、道德、工夫三位一体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赖尚清博士《朱子早期仁论思想研究》[22]以《延平答问》为中心,认为“李侗和朱子师弟子之间主要从理、心、未发与已发、理一分殊等方面展开对仁的讨论,从中可以看到朱子早期仁论的特点以及之后仁论思想的各种萌芽”。此外,向世陵教授《“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23]则详细考察了朱子对“性”的论述,文章认为“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性即理’的构架不仅在说明人性即天理,同时也通过‘所谓理,性是也’的反向路径,使实理在实性的基础上真正得以落实”。吴震教授《朱子“心论”试析》[24]一文,则关注对朱子“心”的研究,认为“朱熹‘心论’的基本义有二:知觉义和主宰义。其‘心论’的基本立场是:不能承认‘心’为形上本体。由其“‘心’字只一个字母”以观,‘心’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存在,故其主宰义就不免落空;由其‘心是做工夫处’之命题来看,‘心’是工夫的对象而非工夫之主脑。总之,在朱熹哲学的系统中,‘心’不是本体论问题而是工:夫论问题”。
工夫论是近些年朱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学者们从多角度关注这一问题。如吴震教授近些年持续关注朱子的工夫论,关注朱子对“敬”的论述(《敬只是此心自作主宰处——关于朱熹“敬论”的几个问题》[25]),以及“格物致知”等问题(《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26]),而《从政治文化角度看道学工夫论之特色——有关朱熹工夫论思想的一项新了解》[27]一文则转换研究思路,“从朱熹亲身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这一独特视角出发,来尝试式了解朱熹为何强调‘吾平生所学’只有正心诚意‘四字’这一十分醒目而前人未免有所忽略的重要观点”,“当我们将审视问题的角度转向政治文化层面,却发现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在面对君主进行思想劝说之时,他们劝导君主实践的第一序工夫往往不是格物致知而恰恰是诚意正心,至于外在事功则可以随着正心诚意的完成而得以实现”。李承贵教授《对道德与知识的双重关切——朱熹“格物致知论”探微》[28]一文认为在朱子那里,“格物致知”是具有“理想性”的范畴,就是要求全面地“穷理”、全面地“普知”。朱熹观念中的“格物”与“致知”关系可以表述为:“格物”与“致知”的任务并不相同,但它们是一件事的两面,即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格物”是获得事物之“理”(知识)的过程,“致知”是将所获知识推演、应用的过程,“格物”是感性的、具体的、归纳的,“致知”是理性的、抽象的、演绎的、实践的,因而它们关系的最高境界当然是“一”。李敬峰、刘俊《朱子的格物致知:一种可能的科技理性》[29]一文则从更为现代的角度关注朱子的工夫问题,对格物致知“从诠释的转向、认知的指向和范式转换三个角度予以重新观照,认为朱子的‘格物致知’主观意愿指向人文伦理,而客观上却走向科技理性”。还须指出的是,这些年对朱子哲学很多问题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都和朱子的工夫论有关,比如杨祖汉教授所做朱子和康德的比较,前述吴震教授对“心”的研究,藤井伦明、乔清举等教授对理的诠释,这些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对朱子工夫论、道德哲学上“实践动力”来源的思考。
除上述三个领域外,其他哲学问题也得到学者们的注意,比如张立文、谢晓东、陈壁生等教授就关注朱子的政治哲学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对朱子政治哲学加以论述。苏费翔教授则在“道统”问题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其《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30]重新检索唐代文献,发现在唐代就有了“道统”一词,纠正了以往学术界的看法。
朱子和其他思想家的比较研究,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朱子与其前辈、同辈的关系研究,依旧被大家重视,与王阳明等之后的思想家的关系也进一步得到讨论。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丁为祥教授《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31]一书,该书从发生学的视野出发,依据朱子文本与相关文献,在充分吸纳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扣朱子的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展开对朱子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深入考察,尤其是该书上篇梳理了朱熹从出身、师承到学术性格及其思想谱系的形成,并通过朱熹与张栻、陆象山、吕祖谦、陈亮的理论论辩以及朱熹对《四书》的集注与具体探讨展现其思想体系,对朱子和前后思想家的关系有着细致的论述。此外,该书也关注了朱子之后的思想家,尤其是民国思想家对朱子的诠释。
同样关注民国学者对朱子诠释的还有乐爱国教授,其“百年朱子学研究”一课题,就关注近百年来学者对朱子的诠释,近些年来乐教授陆续发表了相关论文,或探讨民国时期对朱子某个问题的探讨,如理气、理生气,或探讨某个人物对朱子的研究,如谢无量、牟宗三等。
近些年,最为突出的朱子哲学研究,也最能体现朱子学“走向未来”特质的,则为用朱子学回应时代问题以及从朱子学出发建立新的哲学体系的努力。
朱子学中的很多资源,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依然有其意义,值得我们抽象地继承。特别是“理一分殊”这一命题,就可以被用来处理全球化时代普遍性与多元性、世界性与地方性的关系。黄俊杰教授有《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一文,认为“为了适应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我们可以跃入传统的巨流中,汲取新时代的灵感。在中华文化与思想传统之中,南宋大儒朱子的‘理一分殊’说有其21世纪的新意涵,但在全球化时代各地互动的新脉络中,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在21世纪各文化传统所蕴蓄的多元之‘理’互相对话的新时代中,求同存异是一条必然的道路。传统中华文化重视‘同’而忽视‘异’。古代儒家就非常强调‘同’的价值”,“就21世纪大中华文化圈及其与世界之互动而言,如何开发求‘同’而存‘异’的价值观,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32]。
陈来先生《“水流无彼此,地势有西东”——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及其意义》[33]一文则从“理—势”的构架分析全球化问题,他认为“水流无彼此,可以表示各文明与文化的共通之理,强调交流与共享;地势有西东,可表达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价值差异性,尊重差异”,“‘理—势’分析的出现,既是为了强调人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清醒认识,更是为了强调人以及人的道德理想对历史的批判改造的功能。从前人们常说‘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历史潮流就是势。势或历史潮流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不一定是全然合理的,不是不可以引导的;但不顾历史大势,反势而行,逆历史潮流而动,则必然要失败。妥当的态度应当是‘理势兼顾’‘以理导势’,这是朱子学面对全球化的问题应采取的立场”。此外,陈来先生还有《朱子学的时代价值》[34]一文,专门从六个方面分析现代人从朱子的思想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陈来先生近些年对朱子学的关注从未间断。在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上,陈来先生关注朱子对《四书》的阐释,同时还关注朱子的一体性思维。在其《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35]《朱子四德说续论》[36]两文中关注朱子对于“四德”的阐释,认为“应当承认,朱子的思想不断发展出一种论述的倾向,即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如将其看作元气流行的不同阶段。由于天人对应,于是对仁、义、礼、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贞的模式发生变化,即仁义礼智不仅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气流行的不同发作形态”。更为重要的是,陈来先生还以其对朱子学的最新理解为基础,建构了其哲学体系,《仁学本体论》[37]正是陈来先生在这一方面贡献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迎来儒学的繁荣发展,作为民族哲学的儒学应积极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调整与挑战,面对中华民族的新发展,开拓出新的辩证吸收西方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并从儒家立场对世界和人类的普遍性问题给出指引。《仁学本体论》正是这样一部著作,它是中国哲学“接着讲”的当代典范,这样一部著作的出现具有其时代必然性。陈来先生能够创作出《仁学本体论》这样的著作,与其长久扎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尤其是对朱子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该书关注“仁”在中国思想当中历史的演进,尤其注意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对“仁”的阐释,吸收朱子以生生言仁、注重生气流行等特点,充分将传统的朱子哲学的思想要素转化为时代哲学。可以说,陈来先生的这一研究,为朱子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更加有助于利用朱子学的思想资源关注当下时代的发展、关注人类未来的走向。
三、经学研究的升温
朱子经学是中国经学史的重要一环,他继承汉唐经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但在根本气质上与之不同。朱子基本上遍著群经,对各经都有论述。其经学著作更是成为后代科举考试的标准。清代考据学兴起,清儒虽然不同意朱子经学的阐释,但在研究上也绕不开朱子的经学著作。在以往的朱子学研究中,经学不是一个关注热点,而近些年,经学研究不断升温。
朱子所著的《四书集注》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教科书,“《四书》学”因此是朱子经学研究中的重点。
在《四书》与“五经”的关系上,陈壁生教授有《朱熹的〈四书〉与“五经”》[38]一文,他指出朱子“对《四书》的新解释,创造性地提出新的义理系统,其主旨在于求圣人之心,以提升个人道德;同时,又在此基础上改造‘经’的观念以及对五经的认识。汉唐经学求‘圣人之法’,朱熹把经视为‘圣人之心’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五经进行了内在化解读,将五经《四书》化。这样,五经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四书》总论方面,许家星教授有《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一文,指出朱子四书的形成贯穿其毕生,大致可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其间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或各书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应特别注意的是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至于《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包含丁酉年(1177)《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个不同时期、层次的著作,不可视而为一。顾宏义教授出版了《宋代〈四书〉文献论考》[40]一书,该书专为考辨两宋时期《四书》著述与相关文献而作。分为上下编,上编论及《四书》文献兴盛的社会背景、出版传播及其与程朱理学的发展等,下编则具体对宋代学人有关《四书》的著述进行逐人逐书的考证,廓清了有关《四书》记载的讹误和缺失。闫春则有“从朱子到朱子后学:元明清四书学研究(2014)”一课题,尝试将朱子及朱子后学四书义理的动态演进问题予以凸显。
在《四书》各个文本的阐释上,《大学》的“格物致知”论一直以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近些年依旧如此,前述上海学者对朱子工夫论重视即是一例。此外如杨祖汉教授《西方认识论还是儒家工夫说——谁误读了“格物致知”?》[41]一文,从中西哲学对比的角度揭示朱子“格物致知”的含义,现代学人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逻辑体系是“误读”了朱熹。在朱熹思想体系中,格物致知论并不能等同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而是关于如何实现和完成修己治人的工夫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的作用被研究者夸大了,如乐爱国教授就重视朱子的《中庸》诠释。乐爱国教授有《朱子〈中庸章句〉论“诚”及其与“三达德”“五达道”的关系》[42],从“诚”出发,尝试系统分析朱子的《中庸》解释;又有《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43],关注朱子思想背后的生态观;又有《“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44]一文,认为朱子思想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近些年,乐爱国教授特别强调《中庸》在朱子思想结构中的地位。此外,围绕朱子《四书》具体章句的义理分析的论文更是层出不穷,本文不一一列举。
在“《尚书》学”研究方面,陈来先生有《“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45]一文,指出“在经典的诠释上,朱子对‘极’的解释最早为中年时代对《太极图说》的解释;在朱陆太极之辩中朱子承继和发展了其关于‘极’的理解,形成一套有关‘极’的理论,并在讨论太极之义时论及皇极之义。在朱陆太极之辩后不久所作的《皇极辨》之中,朱熹把这一套理解运用于皇极说作为一种基础,又以君主正身修身的儒家表率说把‘建用皇极’的意义具体化,形成朱子学的皇极说。皇极说既是朱子政治思想的一个论述,也同时可以看作其哲学太极论的相关部分,在后世发挥了持续的影响”。陈先生将朱子对经典的诠释及其义理阐发之间的关系充分地展现了出来。此外,陈良中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朱子〈尚书〉学研究》[46]一书,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宋代《尚书》学背景下的朱子《尚书》学,尤其是其理学诠释特色,考察了朱子对《尚书》阐释的历史,以及解经方法和价值取向,并关注朱子阐释与蔡沈《书集传》的关系,考察了朱子《尚书》学的影响。
礼学则是朱子经学研究这几年来特别突出的一个面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朱子的礼学,尤其注意探讨“礼与理”的关系。如冯兵教授《“理”“礼”会通,承扬道统》[47]一文,认为朱子“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辩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殷慧、张卓合写的《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48]一文,则从朱子的《大学》诠释出发,认为“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两文一从朱子的思想系统出发,一从朱子的经典诠释出发,代表了理解“礼”与“理”关系的两个向度。
张凯作博士《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49]一文着重论述朱子以“理”出发的“礼”学和前代礼学的继承关系,在她看来,“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朱子对古代礼教的最主要的传承即在于他对个人心性修养之学的发扬”。
与哲学上的鬼神问题直接相关,有学者关注朱子对于祭礼的讨论,尤其是其理学思想与儒家传统祭礼之间的张力。如殷慧教授《祭之理的追索——朱熹的鬼神观与祭祀思想》[50]即认为,“朱熹从义理层面论述了祭祀与鬼神的关系:强调鬼神的本体论意义,重视其天地转化的功能;认为鬼神既是阴阳二气物质,也是二气相互作用、转化的功用与性质。朱熹的祭祀思想与实践引人注目,强调义理与礼制并举”。
在《孝经》学方面,唐文明教授有《朱子〈孝经刊误〉析论》[51]一文,他认为“《孝经刊误》表达了朱子试图将《孝经》纳入其四书学的努力,而从《孝经刊误》的后世影响来看,朱子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过,如果考虑到《孝经》本来的思想旨趣,我们不能不说,朱子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陈壁生教授《〈孝经〉学史》[52]一书第六章第一节也专门讨论了朱子的《孝经》诠释。
《易》学一直以来是朱子经学阐释的另一重镇,尤其是围绕着《周易》展开的义理诠释,以往对朱子《易学》的研究较为充分,而近些年的研究热点则不太明确。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对朱子象数易学研究得不是太多,陈睿超博士《略论朱子之先天〈横图〉》[53]则特别关注这点,文章认为“朱子在虽在易学研究方面对北宋邵雍的先天易学推崇有加,但处于其对先天学理解之核心的先天《横图》却并非对邵雍原旨的忠实继承。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横图》中两仪、四象、八卦的名称与邵雍《观物内篇》所述不同;第二,《横图》八卦卦序与《观物内篇》所述不符;第三,《横图》变换为《圆图》的过程有涉安排,不够自然;第四,依《横图》卦序对《圆图》顺逆方向的解释与邵雍本意有异。朱子对邵雍的先天学并非完全继述,而有自己的改造与发挥,不加区分地以朱子之《横图》解释邵雍易学思想的做法是不够严谨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关于朱子经学研究已经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但还是有一些不足。如《仪礼经传通解》仅在文献上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而对其义理阐发则远远不够。在《诗经》学方面,学者们主要侧重在对《诗集传》赋比兴等手法的研究以及朱子诗论与其他人的比较上,相关哲学义理性阐发则很有限。朱子虽然未注《春秋》,但其有《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传世,并对东亚产生重要影响,而关于该书也缺乏文献、义理的进一步关注。
四、大陆以外的朱子学研究
(一)港台
长久以来,牟宗三关于朱子学的论断在港台占有一定的统治地位。而近些年来,港台朱子学的发展,则与对牟宗三相关观点的反思有密切关系。牟宗三从康德哲学出发,认为陆王哲学是自律道德,而朱子学是他律道德,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陆王高于朱子。牟先生的一些弟子,观点已经开始与其不同。在2009年,杨祖汉教授发表了《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一文,认为朱熹之言敬是由敬“契入本心”,而恭敬亦是“道德心本有之内容”[54],从朱子的“敬”出发,就不会认为朱子的思想是他律。2014年12月4~5日,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一次“朱熹与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及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杨祖汉教授发表《朱子与康德敬论的比较》一文,顺承上文思路,认为朱子学说虽不讲心即理,但心可以知理,心依旧能够提供道德实践的动力,不必像牟先生所讲,只有心即理才能提供道德实践动力。我们可以看到,杨祖汉教授已经极大修正了牟宗三先生的论断。但我们依旧可以指出,杨祖汉教授的观点依旧在牟先生的框架当中,只不过将牟先生所认之他律修正为自律而已。
与杨祖汉教授不同,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杜保瑞教授则对牟宗三先生的理解做了更大的反思,以其对中国哲学的结构性解读重新阐释朱子学。杜保瑞教授最近一系列论文均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认为牟先生没有区分清楚朱子的论述到底是讨论存有论、宇宙论、工夫论,还是境界论,以至于混淆了朱子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对朱子思想做出了错误解读。例如杜教授在《对牟宗三诠释朱熹心性情理气论的方法论反思》[55]一文中针对牟先生《心体与性理》中的一些结论性论述,认为牟先生借明道、濂溪讲神体,朱熹之解释虽符合明道、濂溪之义,却与朱熹一向的不活动的理、神说不合,这反而是牟先生割裂存有论和本体宇宙论及本体工夫论的错误诠释;牟先生讲朱熹的心性情说,以为朱熹讲心者气之灵爽,就是连着阴阳气化的人存有处讲,不能超越至圣境,这还是把存有论当成不活动的工夫论讲的错置,于是对朱熹做了有道德性减杀、无创生义和不能由体及用的批评。杜保瑞教授的研究代表了港台朱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一方向值得大陆学者注意,对于杜教授的观点似乎可以在学界展开进一步讨论,一是杜教授对牟宗三之评价是否符合牟宗三本身的理解,二是其对朱子的结构性诠释是否符合朱子思想本身的逻辑。杜保瑞教授的研究揭示的面向具有很强的哲学史意义。
与反思牟宗三先生对朱子的解释相关的则是唐君毅研究路向的重新得到重视。在2014年香港会议上,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宗义教授发表《比论唐君毅、牟宗三对朱子哲学的诠释》一文,强调新儒家中另一重要人物唐君毅对朱子研究的意义,其朱子哲学诠释虽散见于《中国哲学原论》之《原教篇》《导论篇》《原性篇》及《原道篇(卷三)》等书中,论述之集中程度及篇幅或不及牟宗三,“然其中一些闪烁的洞见,则隐然提示了一套足可与牟氏解读相抗手的诠释体系”,他认为“通过比论唐、牟对朱子哲学的不同看法,来将唐氏提示的诠释体系做一初步的梳理、发挥与建构”。也就是说,即使在新儒家内部,也不仅有牟宗三一种思路可供选择,还有别的路向可作为研究朱子学的重要资源。
当然在港台学者内部,依旧日有学者坚持牟宗三先生对朱子的相关诠释,这方面主要以李明辉教授和李瑞全教授为代表。
港台学者对于朱子的研究也还有别的路向打开。比如说陈荣开教授就关注朱子的经典诠释,尤其是朱子对于《中庸》的阐释,细致分析朱子每章的注解。更值得注意的则是黄俊杰教授组织主持的“东亚儒学的新视野”这一项目下有关朱子学的研究。该项目将儒学放置于东亚文明的演进发展当中予以关注,黄俊杰教授以为,“近七百年来东亚各地儒者可以阐释朱子,可以批判朱子,但不能绕开朱子”,朱子可以说是东亚儒学展开的重要人物,但是东亚儒学的发展在部分研究者看来,却不能将中国视为中心,应该“去中心化”。这点也提醒我们注意,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作为前现代东亚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地位究竟如何?我们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以及今日所谓“去中心化”可能导致的思想后果。大陆学者似乎应该以新的视角解释清楚朱子学在东亚历史上的实际地位。
(二)日韩
东亚儒学圈的展开,主要是以朱子学为核心,朱子学早在前现代时期就已经走出中国,走向东亚,深刻影响着日本与韩国的政治文化,朱子学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日韩思想史内在的问题,而不是异己的文化传统。
1.韩国朱子学研究
历史上韩国朱子学主要以三大论辩为主,即四端七情论辩、湖洛论辩、心说论辩,朱子学的内在逻辑问题在韩国以独特的形式展开、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涌现出李退溪、李栗谷、宋时烈等一大批朱子学者,韩国朱子学的论辩基本上在这些思想间之间展开。韩国还有专门的退溪学会、栗谷学会,专门推动相关人物和问题的研究。而近些年来,韩国朱子学研究也主要围绕着对这些人物和问题的研究展开。
关于栗谷学派,李基镛在《栗谷学派的理气论》一文中,把《栗谷全书》中的理气关系整理为以下几种说法:一、有从理而发者(竖说):有从气而发者(横说);二、就理上求气(竖说):就气上求理(横说);三、推本之论(竖说):沿流之论(横说);四、推本其所以然或极本穷源(竖说):于物上观或以物上观(横说);五、因有形之物,而可见其理之费处也(竖说):以复卦言之,则一阳未生之前,积分之气,虽在于地中,而便是难看处也(横说)。这说明了理气之不相离和不相杂的关系,也就是栗谷所谓的“理气之妙”。[56
《朝鲜朝“朱子学”——理气心性论在韩国儒学中的发展趋势》一文,以“朱子学的理同”“栗谷学的理通”“洛学的性同”“北学派的人物均论”为中心,讨论了栗谷的“理通气局论”与湖洛论争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进而探讨了以“人物性同异论证”为中心建立的洛论界思想基础、洛学和北学的思想背景以及韩国近代韩国思想史的哲学基础和其趋势。
四端七情之辩一直以来是韩国朱子学研究的重点,也为中国学者熟知,很多中国学者也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中,研究成果最多。关于退溪学派,韩国学者还是比较关注对这一问题的阐发。郑相峰在《退溪对朱子哲学的理解与其特色》的论文中,深入探讨了退溪说过的“理之动静”“理发”“理到”的思想。[57]崔英辰教授的《关于退溪四七理气互发论之渊源的考察——以洪治的〈心学章句集注大全〉为主》一文,认为“在韩国一般学术界里,洪治与退溪的思想传承几乎不被重视,是因为洪治之著作因当时的政治士祸而消失,并且他的著作依然有后代之伪作的嫌疑。崔英成主张学者把洪治的《心学》看作伪书是没有根据的,当今学者应当以更严密和理性的态度再分析《心学》的真伪问题和意义内涵”。[58]此外,韩国学者还重点关注退溪与其辩论对手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如崔英辰教授《退溪与高峰四端七情论辩中“四端无不善”和“四端有善恶”的冲突》一文就关注了退溪与奇高峰的辩论。诸如此类文章,一直是这些年韩国儒学的研究重点。
心说论辩和湖洛论辩在之前一段时间并不被学者重视,研究得也不是太多,而这些年研究则逐渐升温。韩国的栗谷学会在2013年6月召开了“人的本性与心的根本”学术大会,学者们综合探讨了从栗谷以来形成的“湖洛论争”的主要概念及哲学含义。在2015年厦门召开的“百年东亚朱子学学术研讨会”上,宣炳三先生专门提交《洛湖论辩研究成果及展望》一文,指出21世纪以来关于洛湖论辩思想渊源的研究成果大幅增加,课题更加丰富,比较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崔英辰教授则提交《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状及展望》一文,指出韩国朱子学者试图用理气论的概念来定义人类的心性,韩国朱子学的三大论争是始于对心性情理气论的规定,而相关比较研究,尤其是中日韩关于相关问题的比较性研究,则可以进一步推进。这一点也值得中国学者注意,尤其是如何在和韩国朱子学的对比中理解朱子思想的意义以及中国朱子学的走向问题。
此外,韩国学者还对其他哲学问题有密切关注,比如关注退溪的教育思想,关注栗谷的经世思想,如栗谷学会特别重视推广栗谷的蒙学著作《击蒙要诀》并加强与中国思想界沟通来共同研究这一蒙学著作的时代意义。
2.日本朱子学研究
早在13世纪初期,朱子学就已经传入日本,进入江户时代,朱子学在日本开始兴盛,涌现出藤原惺窝、林罗山、贝原益轩等一批思想家。传统的日本朱子学研究侧重于对朱子学文献的阐释,并借由文献的解释阐发义理,关注“理气心性”等问题。而战后的日本朱子学研究则侧重于文献研究,思想研究的成果远较文献研究的成果要少,这些年情况更为明显,日本学者“形而下”的取向越来越明显,而较少关注以“理气心性”等问题为核心的“形而上”向度,这与日本近代以降重新构造其东亚叙事有密切的关系。591
日本学者擅长考证工夫,这点历来被学者重视。近年来这方面成果也较多,前述吾妻重二先生对《朱子家礼》的考辨就是一例。此外,鹤成久章有《〈四书纂疏〉所引の朱子学文献について:〈朱子语录〉を中心に》(《〈四书纂疏〉引用的朱子学文献:以〈朱子语录〉为中心》,2014)一文,考察了《四书纂疏》的成书年代以及《纂疏》所收朱熹及其后学13人文献的情况,特别注意《四书纂疏》所引《朱子语类》,指出了数量在2000条以上的《四书纂疏》所引朱子的语录的一些特征,发现《四书纂疏》所用语录与传世文献的一些差异。2014年儿玉宪明作《朱熹律吕新书序注解》一文,对朱子《律吕新书序》做校勘、日译和注释。日本学者对朱子学涉及的语言学等问题,尤其是与日语相异的语言问题,也有较多的关注。
在义理学方面,木下铁矢于2013年出版《朱子学》一书,可以说是义理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作者不赞成把朱子理解成二元论者,认为朱子力图打破理气、阴阳等二元对立,“心”的阐释可以说是朱子突破二元对立的枢纽。此外,日本学者长期以来关注对朱子鬼神问题的讨论,这一点在日本的朱子学研究上十分突出。牛尾弘孝先生在2010年曾写书评,专门回顾了日本学者对鬼神问题的相关讨论,2013年又专门作《朱熹的鬼神论的构造》一文,从“理生气”与“屈伸”两个层次,阐释朱子的鬼神观,并对祭祀问题加以讨论。
在日本朱子学方面,土田健次郎教授2014年出版的《江户的朱子学》一书可以说是近些年研究的代表。该书详细讨论了朱子学本身,以及朱子学进入日本思想史之后的问题与演进,认为日本思想史学者对朱子学理解不深,没有把握朱子学的特质,没有看到朱子学在理气论构架下做出的哲学贡献。该书还讨论了朱子思想与日本本土思想的关系,诸如“敬”与“神道”,认为朱子学已经进入到日本的“日常”当中,并从这一思路出发,详细讨论了日本反朱子学者,如伊藤仁斋对朱子学的理解与批判。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吾妻重二先生以“文化交涉学”的视角关注东亚朱子学的相关问题,勾勒了东亚儒学和东亚朱子学的多个侧面,关注“以儒教为中心的知的世界”。在吾妻重二先生看来,“朱子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进而言之,也无妨称其自身拥有着一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广度。因而,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哲学史中,还要在教育史、礼仪史乃至于人类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理解朱子学”。吾妻先生强调文化是在不同地域之间不断流动的,他本人就是在这样的理解下诠释朱子学跨地域的文化特质。
3.欧美
欧美的朱子学研究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亮点,其研究,既有针对朱子学本身的讨论研究,又有引入比较哲学的视角、进行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
英美汉学界对朱子的研究较为偏重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艾周思出版《儒家之道的重建:朱熹对周敦颐思想的运用》60]一书,从宗教实践的角度探讨朱子对周敦颐思想的发展,并对主要文献进行了翻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田浩教授可以说是美国朱子学界的代表,之前就有关于朱子和陈亮的两本专著问世。2011年田浩教授出版了《旁观朱子学》[61]一书,收录多篇其观察朱子以及南宋思想的文章。同时,田浩教授还关注朱子学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对朱子学的一些当代实践进行了思考,与其女儿田梅一起写成《礼之殊途:〈朱子家礼〉现代化与恢复古礼的践行——以当代儒家婚礼为视角的分析》一文。他还与殷慧合著《从〈五经〉到〈四书〉——以宋代礼理的突破与融合为中心》[62]一文,关注朱子思想中“礼”和“理”的关系。田浩教授对朱子学的关注可谓是多方面的。在他的推动下,2012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专门召开了朱熹经学研讨会。此外白朗诗教授的《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和南乐山的比较研究》[63]一书于2011年翻译成中文,该书从比较哲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怀特海、朱熹和南乐山那里会有创造性这一观念,以及为什么对于比较过程思想来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法国,值得关注的是戴鹤白教授专门将《戊申封事》翻译为法文[64,并写专文对朱子的封事进行讨论(《论朱熹的〈庚子应召封事〉和〈辛丑延和奏札〉》,2012年)。2012年杜杰庸、戴鹤白还合译了朱子和陆九渊的通信《太极之辩》。
德语学界则更多地关注朱子本身的哲学问题。前文提到的苏费翔教授就是德语学界研究朱子的一个新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研究了朱子的道统观,还关注朱子弟子之间的争论(《〈近思录〉〈四子〉之阶梯——陈淳与黄榦争论读书次序》,2012年),近些年还特别注意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朱子思想。苏费翔等人还一同将《朱子家训》翻译为德文(2011年)。2015年7月特里尔大学专门和华东师范大学一起主办了“朱熹与他的革新:创新、社会改革与认识论”会议,欧美汉学界与中国大陆研究朱子和宋明理学的学者齐聚一堂,探讨朱子学的相关问题。
此外,澳洲学者梅约翰主编了《理学家哲学的“道”的指南》(2010年),收录了不少关于朱子研究的成果。
有关朱子学的研究不只以上这些内容,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注意。比如说余英时教授出版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之后,学者们陆续开始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朱子学进行相关研究。此外,朱子学的世俗化进程也拓展了朱子学的当代面向,使朱子学的当代境况不同于其他中国传统哲学。自2005年开始,世界朱氏联合会与闽北朱氏宗亲会联合中国、欧美等高校,组织学者和青年学生开展“朱子之路”活动,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促进当代青年对朱子进一步了解。在世俗化方面朱杰人教授“朱子家礼之婚礼的现代实验”特别值得关注,他以实际的操作探讨求证时至今日《朱子家礼》是否仍有生命力,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婚俗是否可以对全盘西化发起一次挑战,以寻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可以说,朱子学的世俗化努力已经使朱子学走出了纯粹的书斋式的研究,促使朱子学以及儒学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以上简要总结了2011年以来朱子学的发展情况,可以说,朱子学的研究在各个领域稳步推进,朱子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属于当下的,也是属于未来的,朱子学也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朱子学的研究为中国哲学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典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杨得煜
笔者从台湾2016年的期刊论文当中,分别摘录数篇来进行说明[1,所摘录论文以台湾重要期刊、重要学者或对朱子义理有新意之学者为主要依据。所选择的论文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宋明理学当代诠释(心性论与工夫论)。第二,东亚朱子学。第三,比较哲学。第四,清代朱子学。
为了让读者快速掌握到这些学者之研究成果,笔者以论文问题意识、论文架构、论文摘要等三大项之方式作为架构。这样的架构分类可以帮助读者清楚掌握到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证成的程序与结论。
一、宋明理学当代诠释(心性论与工夫论)
1.黄莹暖:《再论朱子之心》,《鹅湖学志》第56期(2016年6月),第113~139页。
(1)问题意识
在朱子心性论当中,“心”之概念在当代朱子学研究当中,存在着“认知心”与“道德本心”两种解释空间。当代新儒家杨祖汉教授指出:性理能随时显于心,心对性理本有所知。从这意义来看,朱子言“心”是一具有道德自觉的能力,并非只是一“形下”意义的“认知心”。黄教授以杨祖汉教授理论为机模,尝试从“恶的产生”与“善端发露”两个进路,以对朱子“心义”提供更多的视角。
(2)论文架构
论文共有两大章节,第一节:从恶之产生与善端之发的论述看朱子之心;第二节:心之虚灵知觉的道德属性。在第一节中,分析朱子理论中,恶的产生是由心失其主所致;善的发端时私欲经常随起夹杂。第二节,则是分析《中庸章句序》中的“人心”“道心”概念。
(3)论文摘要
黄教授在论文中指出,第一,恶的产生并非由天赋气禀所决定,亦并非由气机之偶然或其障蔽所致。人之所以流为不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心的自我放失懈怠。第二,虽然朱子肯定道德自觉与动能具有内在必然性,但是气禀私欲也是具有影响力。在道德觉醒与善端萌发的历程中,同时也是气禀私欲潜入与笼罩的时机。第三,朱子言“心”并非仅仅是形下之气心或认知心,而是一道德主体、道德根源,并且具有自发不息之动力。第四,关于人心、道心问题,前者归属于形气或感官欲望;后者归属于明德之体。这两者本是同时存在,甚至可以用一体来理解。两者之间的转换之关键概念在于虚灵知觉。最后,作者指出:心之虚灵知觉证成了道心具有优位性与必然性,使得人在天理人欲之抉择当中,对于天理有必然之取向。
2.蔡家和:《朱子的孟学诠释特征》,《中正汉学研究》总第27期(2016年6月),第143~162页。
(1)问题意识
朱熹在四书诠释过程中,一方面想要从理学架构来进行四书学的建构;另一方面又会受制于四书的原文限制。蔡家和教授欲说明,从这两方面来看,当理学架构与孟子相遇后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火花出来。
(2)论文架构
论文分为五个章节。第一节,说明朱子“先知后行”理论。第二节,说明“学以复其初”的设计。第三节,说明“理气论”架构。第四节,说明“性发为情”“心统性情”理论。第五节,物性能同于人性,而有微明。
(3)论文摘要
蔡教授归纳出五种朱子诠释孟学的特征,指出朱子的孟子学是一种理气论的建构或说是一种理学的建构。在“知先行后”理论中,朱子用《大学》“知先行后”架构诠释《孟子·尽心知性章》。朱子将孟子言“知言、养气”,比配于《大学》中的“格物、诚意”。顺着《大学》主张“先格物,后诚意”,而将孟子“知言”“养气”,诠释为“先知言,后养气”。朱子以《大学》中“学以复其初”的架构诠释孟子,强调“心本具理”,因为物欲所蔽,而不能见理。格物穷理、涵养用敬的目的,都是在恢复“本具”的性理。但是,以“复其初”的架构诠释孟子,是否会对孟子言“扩充”有所冲突?蔡教授指出,两者在朱子诠释下并无冲突。理由在于:朱子对于“扩充义”有特殊的见解,即“充满其本来之量”。透过一种创造性的诠释来回避理学架构与孟子本意之冲突。在理气论架构中,朱子用理气论来诠释《孟子·生之谓性章》之人性、物性问题。在理气论架构下,人性与物性都是禀受相同之天理。两者差异在于:人能推,物不能推;并且人在气禀上是优于物。由此,人能尽性善之性,但物不能。朱子批评告子“生之谓性”是“视性为气”。在“性发为情”之体用观理论下,朱子用《中庸》“中和之说”来诠释《孟子·公都子问性章》。朱子用“心统性情”的架构,将孟子“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理解为“情感之发用”。在《孟子·人禽之辨章》言“人所以之于禽兽者,几希”,朱子则用“理一分殊”架构来进行诠释。朱子认为人与禽兽是在“气质之性”上不同,而“天命之性”则是相同。故孟子言“几希”,在朱子诠释下就会理解为“气质之性”之差异。最后,蔡教授指出朱子对于孟子的诠释,可以视为一种创造性诠释。
3.林宏星:《朱子论真知及其动机效力》,《国立台湾大学哲学论评》第52期(2016年10月),第1~26页。
(1)问题意识
林宏星教授在论文中开宗明义说明:论文的目的在于透过说明“真知必能行”所具有的动机效力,来响应休谟式的问题的诘难。林教授响应此问题的进路是讨论朱子对于真知概念的内容和结构的论述。林教授指出所谓休谟式的诘难,即是问:“如果仅仅凭着理性本身,如何可以为道德行动提出足够的动机理由?”林教授的问题意识主要是聚焦在“真知何以必能行”的动力方面。
(2)论文架构
论文共三章节:第一节,说明何谓真知?第二节,说明真知与动机效力;第三节,说明理由与动力。
(3)论文摘要
首先,林教授指出“真知”有两种特点:1)凡是直接从经验中获得的真实、正确的知识就是真知。2)真知并非要求每个人都要从经验中获得,只要是被人类在实践中所证明的知识,也可以归类为真知。其次,林教授指出,真知对于朱子而言,是站在第一人称的角度,追问自家身心上的“先天”就具有的“是非理据”。当我们对于这样的“是非理据”有了真切的反省后,便能获得一种“内在的肯信”,如此的“肯信”成为行动主体的道德行动之动力来源。由此也说明了,为何朱子提出了“真知必能行”的主张。林宏星教授指出:在朱熹真知理论中,真知与行动的关系,似乎并不存在着动力不足的问题。
4.张子立:《道德与知识的两种辩证关系:朱子格物致知说重探》,《中正汉学研究》总第27期(2016年6月),第163~190页。
(1)问题意识
朱子格物致知理论,在学界常面临一个挑战,即:在道德实践时,知识如何能促成道德实践?此亦即是问:知识如何能提供道德行为之动力?对于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阳明批评“心与里为二”;当代新儒学学者牟宗三先生,则将其定位为成德之助缘工夫。对于此问题,张教授试图从两种道德与知识之模型来回答此一问题,分别为“主从的辩证关系”与“对列的辩证关系”。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评断朱子学为逆觉体证型态之助缘,而唐君毅与刘述先,则从“主从的辩证关系”层次来立论,试图为朱子辩护;而张子立教授欲从“对列的辩证关系”之模型来重新定位朱子格物致知理论。他进一步指出,朱子的格物工夫可以处理在“强意义”下的道德两难之问题,而这正是阳明良知学所不足之处。
(2)论文架构
此篇论文主要章节为,第一节,说明道德实践与知识:朱子格物致知是否为助缘。第二节,说明道德与知识“主从的”辩证关系。第三节,说明“对列的”辩证关系:再探朱子格物致知说。
(3)论文摘要
张教授指出,阳明良知学理论特色就是类似“境遇伦理学”,只提出一形式原则,再视所处的情境决定具体行为。阳明模式的困难在于:当面临到道德两难情境时,这样模型仅仅只能处理“弱意义”下的道德两难问题。例如,舜之不告而娶。但是,一但面临“强意义”的道德两难时,这样的模型会遭遇到两个问题。第一,每一个情境都有其独特性,如果依照阳明的模式,当我们遇到强意义的道德两难问题时,都有可能会陷入手足无措的情形。第二,阳明模式缺乏“伦理知识”,而这样的伦理知识是可以主导道德判断,形成一种判断“中”的内在决定。张教授指出:如果是从“道德实践”层面看“道德与知识”的相互关系,陆王实有较正确的体认,理由在于:厘清了二者间“主从的辩证关系”;反之,如果是从“伦理知识”与“道德判断”之“对列的辩证关系”切入,则朱子格物致知工夫对于道德判断有较全面的认知,这也正是阳明理论所不及之处。
二、东亚儒学
1.杨祖汉:《朝鲜儒者田艮斋对朱子思想的理解——比较牟宗三先生的说法》,《中正汉学研究》总第27期(2016年6月),第93~116页。
(1)问题意识
杨祖汉教授此篇论文以朝鲜儒者田艮斋与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为比较进路,分析两者对于朱子哲学诠释上的不同与相同之处。杨教授指出田艮斋对于朱子诠释,主张理不活动、心是气,心与理为二,而道德实践之动力不能从理本身给出来。这样的观点和牟先生无异。但是,田艮斋认为朱子是儒家正宗;牟先生认为别子为宗。如果依照牟先生的判准,别子为宗最重要的判准根据在于:“是否为他律伦理学”。如果朱子是他律伦理学,那么艮斋就不能主张朱子与儒家本质相同。杨祖汉教授此篇论文指出:田艮斋之说具有一特殊含义,使得朱子仍可与儒家本质相同。
(2)论文架构
论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节,说明牟先生对朱子学的衡定。第二节,说明艮斋朱子学诠释的要点。第三节,引艮斋文献来证艮斋思想要点。第四节,说明艮斋与牟先生朱子诠释之比较及艮斋之说的特殊含义。
(3)论文摘要
杨祖汉教授指出,如何在心与理为二的架构下,说明朱子“不是”他律论理学?第一,艮斋在“心与理为二”架构下提出了“性师心弟”或“性尊心卑”的理论。根据这样的心性关系理论,会让心以性为尊、遵理而行。心则不敢僭越、不敢自主。第二,透过康德理论说明,在“性师心弟”或“性尊心卑”的架构下,只要越能强调“性天之尊”就会越有道德实践动力之产生,而这样的动力来自于对于道德法则产生的敬意。第三,艮斋主张,朱子《大学》所说的“明德”注语,表示了明德是“心”。“心”之所以称为“明德”是因为“具理”。虽然如此,但是真正的道德实践之根据所在仍然是性理。第四,心虽然是形下之气,但是不同于一般的形气。心具“虚灵明觉”,而可以通于性理。最后,杨教授认为,艮斋在“性师心弟”成德之教模型,可以使得朱子在主张“心与理为二”的架构下,仍然与儒家本质兼容。
2.藤井伦明:《日本崎门朱子学的智藏论探析》,《中正汉学研究》总第27期(2016年6月),第191~210页。
(1)问题意识
朱子晚年“智藏”的概念在日本崎门朱子学派中被视为重要概念。藤井教授指出在过去对于朱子“智藏”概念并未有充分的讨论、分析。有鉴于此,藤井教授欲从分析“智藏说”,来阐明崎门朱子学派智藏说的具体内容与逻辑结构。
(2)论文架构
论文章节为,第一节,说明朱熹思想中的“智藏”观与山崎暗斋的宣扬。第二节,三宅尚斋的《智藏说》以及崎门学者的“智藏”论。
(3)论文摘要
藤井教授指出,崎门朱子学派“智藏说”有诸多特色:第一,对于性理(未发之理)理解为具有双重结构,即“无迹”之“智”与“有迹”之“仁、义、礼”。第二,前者是“未发之理”的最深层之根源,未受到任何的限定。后者,则是已经具有限定、带有具体特色于其中。但,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属于“形上之理”。第三,崎门朱子学派所理解的“智”可能就是理之能量本身,亦即将其视为一块“能量体”。而此一能量体作为本体而产生各种现象、作用。第四,将这本体与其所产生的作用,用“知”概念来做整体的掌握。
三、比较哲学
1.林维杰:《朱熹理气论与莱布尼兹的自然神学》,《中正汉学研究》总第27期(2016年6月),第211~228页。
(1)问题意识
林维杰教授论文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他所要讨论的问题,即:先秦儒学中具有位格性的天、帝概念,到了宋明理学中已经逐渐转化为道德性的天、道、理等概念。然而,在这样的道德性意义之下,是否仍有宗教的意涵。林教授进一步指出,这样问题的症结在于:理则化、德性化的超越者是否仍可视为宗教要素?所参照的系统是以西方的神学论述(特别是自然神学),以莱布尼兹的自然神学作为对比来说明朱子理学的宗教性。
(2)论文架构
论文架构为:第一节,说明朱熹理论及其理气论之诸性质。第二节,说明莱布尼兹之自然神学及其对朱熹理气论上的参照意涵。
(3)论文摘要
在朱熹理学方面,林教授首先指出,朱子理气论有六种性质,分别为“理气双显”“不离不杂”“理先气后”“理在气中”“理同气异”“理静气动”。从这六种性质来检视太极与万物之关系,可以视为一种“观解形上学”的内在之规定,即:“超越的理即内在于万物之理”。朱子的理气论是从形上学角度来谈太极、理与万物之关系。另一方面,莱布尼兹对于中国自然神学所采取的观点是宗教多元主义或上帝中心主义,而并不认为中国宗教思想是属于唯物论或是处于精神论或唯物论之间的矛盾主张。同时莱布尼兹也批评龙华民对于朱熹理气论的理解。龙华民对于朱熹理的理解有二:第一,理是至善的精神体且能“生出气”。第二,“理”可能是“原初物质”。莱布尼兹反对这样的看法,主张“理”不会是“原初物质”。批评龙华民将太极与气给混淆了。但是,莱布尼兹也同意“理能生气”的观点。虽然如此,林教授也指出莱氏犯了跟龙华民一样的错误,即混淆朱子太极与元气说,以及“理生气”之意。朱熹的“理生气”并没有基督教“从无生有”的意涵。最后,林教授认为透过莱布尼兹自然神学理解朱子理气论的宗教意涵是很有意义的。林教授指出:莱布尼兹站在会通中西教理的态度上,尽可能地拉进儒学中太极、理与基督宗教中的上帝、天主之性格,而提出了自然神学式的“以理为神”观点。
四、清代朱子学
1.陈祺助:《王船山与朱子工夫论比较》,《中央大学人文学报》第62期(2016年10月),第1~48页。
(1)问题意识
陈教授指出当代对于船山与朱子比较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采取概念或范畴为进路。然而,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所做的比较研究,则为少见。以此之故,陈教授打算从“主敬存心”“知行关系”“致知格物”这三个主题上,来比较船山与朱子工夫论之说,对于两家之说详细讨论,以厘清其异同之处。
(2)论文架构
此篇论文架构分别为:第一节,论主敬存心的比较。第二节,论知行关系的比较。第三节,论致知格物的比较。
(3)论文摘要
首先,陈教授指出,对于孟子“求放心”的诠释上,船山批评朱子“文理有碍”。朱子认为如果将“求放心”理解为“一心求,操另一心”,会造成“一人有两心”的理论困境。并且在工夫论上必导致心越求越昏乱。依照朱子对于“求放心”的理解,“放心”是赘词,“求”字所表示的工夫力道太弱。船山认为,孟子言“求放心”,此“求”字是大有工夫之所在,并非如朱子所主张,如果强调“求”字就会产生主客、能所对立,形成“一人有两心”的困境。第二,对于“存心”之说,如何保证存心能有道德价值?在朱子方面,朱子透过“持敬”工夫使心气收敛凝聚,常在静默中对超越之天理,使得“中性”知觉之心得以具有道德价值内含。陈教授指出,虽然“持敬”可以此心收敛凝聚,涵养心气。但是,如果心气本“不固有”仁义之性,则虽收敛心气使其不昏昧,心仍“未必善”。反观,不同于朱熹主张“心”为“虚灵明觉”;船山主张“仁义”为“心之实”,而主敬工夫用来收敛心气,必能使心之实之仁义呈现出来。陈祺助教授指出,朱子与船山的理论差异在于:前者“存心说”并不能保证存心必能有道德价值。后者则可。第三,对于知行问题,陈教授指出,船山批评朱子“知先行后”的主张会产生与王学末流相同的困境。即,如果“凡是要求等我先知道后,再去行为活动”,会导致“先知以废行”的结果,这点正是朱子理论的困境。于此,船山则提出了“知行并进”的理论架构来补足朱子理论软点之处。
(作者单位: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
2016年韩国学者的朱子学与
韩国儒学的研究状况[1]
⊙〔韩〕姜真硕
2016年度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不但涉及的主题很广,也出现了未曾研究过的新的领域,可见朱子学及韩国儒学的研究依然活跃,成为韩国学者的主流研究之一。关于朱子学的研究方面,韩国学者探讨了心性论、工夫论、经学、书院及画幅、朱子家礼、易学、训诂学、哲学治疗、比较哲学等各种主题。其中,关于朱子哲学方面,有些韩国学者论及朱熹的心性论、《中庸》的情感论及《大学》的平天下的意义。笔者在这里介绍几篇论文,以共享其内容。
1.金基铉:《朱子学的未发概念的成立过程》,《阳明学》44号,2016年。
金基铉从湖湘学与阳明学的角度探讨了朱熹早年的心性论。他认为朱熹在中和旧说时期提出的未发为性、已发为心的主张,并非通过真正体认察识端倪而提出的,而是在短暂的思考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想法。严格来讲,朱熹在通过察识工夫体认本心方面未达到真正的理解,是因为当时他把寂然不动视为性。湖湘学派一向追求要体认天命流行的生生不已之天机的寂然不动即已发之心,然而朱熹却把已发之心误认为性的领域。金基铉认为朱熹始终把寂然不动当作未发性,因此在工夫方面无法做出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在修养工夫上必须从尽心达到成性,这是孟子说的尽心、成性、知天的次序和过程。金基铉的论文在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朱熹早年的心性论方面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他提出朱熹早年的学说未有真正的体悟,抑或由于把寂然不动视为未发之性,从而断定朱熹在修养工夫上有缺陷等说法,不是从朱子学本身思想演变的角度理解中和说,而是从阳明学的角度判断中和旧说的内容,由此产生一些解释上的分歧。
2.洪性敏:《朱子哲学中的情感的适当性与道德性》,《东方学》35号,2016年。
未发之中和已发之和是《中庸》第一章的中心概念。韩国学界一向着重于探讨“未发”部分的思想内涵。但洪性敏认为,相对来讲,关于中节之和的研究却未引起学者们广泛的注意。中节之和的研究能更丰富对未发之中的理解,也能让学者更深入地理解未发涵养的意义。中节之和的深层理解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探索能够解释道德感情论的某种新的渠道。性理学中的“情”的意义不完全是与英语的“emotion”相符,但是从《中庸》首章的理论脉络看,未发和已发确实是提到情感上的问题,也显示中节之和具有情感之中节扩大到达道的某种道德价值的意义。而且洪性敏主张朱子虽然有意识地把四端和七情看作不同的情感圈,但是就实际的情感现象方面而言,四端与七情的关系不是像纯善与有善恶那样可以划清。朱熹认为四端和七情反而都隐含着恶的危险性和善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他看来,七情与四端是可以就同质脉络上探讨的。由此可说,七情之恶是从四端之恶发生的,也可说哀惧是怵惕恻隐之深化。四端与七情不仅是从同一根源发出的,同时也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关系。
从这样的意义上看韩国儒学的李退溪和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辩,朱子本身理解的四端七情的关系,似乎更接近奇大升的说法。因此四端都有在现实生活中可发生未中节而为恶的可能性,七情也包含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发而中节为善的可能性。判断情感的道德性与否,其标准正是现实上的中节与否。朱熹认为恶的本质并不是先天的,而是现象的、后天的。这不但表示他对道德本心具有毫无动摇的信心,同时显示他把善恶问题局限于现象领域去进行思考。由此可说,四端也是如果在现实领域中不中节则可成为恶,七情也是在现实领域中发而中节则可被认为善。在此篇论文中,洪性敏特别关注“持志”这一概念。朱熹要运用持志工夫调整情感,以符合中节之标准,而且要控制因气质所产生的情感泛滥的现象。意即朱熹认为情感变为道德性需要充分的具有意志的训练工夫。笔者认为洪性敏的论文可说是现代版四端七情论。他注意“中节”概念,深入探讨了朝鲜时代“四七论辩”未提出的一些理论结构,也提出了较倾向于奇大升说法的情感道德思想。
3.徐根植:《从朱子〈大学章句〉看平天下的世界》,《东洋古典研究》63号,2016年。
徐根植专门探讨了《大学章句》第10章的内容。他认为此章的中心思想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絜矩之道,另一是节用思想。朱熹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实践絜矩之道、选拔人才、节用,平天下的理想就不是件遥远的事了。徐根植介绍了当代中国和韩国学者说的忠恕和絜矩之道思想,认为《大学》的絜矩之道实际上指的是“恕”思想,而不是指“忠恕”。《大学章句》的絜矩之道充分体现消极意义之恕,由此可探索平天下的方法。己立立人的积极意义之恕,可适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等实践领域,而在平天下的实践过程中可能更需要絜矩之道及消极意义之恕。笔者认为此篇论文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絜矩之道的视角,但是在梳理忠恕概念及探讨恕与絜矩之道的关系方面深度稍微不够,留给我们更深入研究恕与絜矩之道的关系、消极意义的恕所蕴含的深层意义等课题。
下面的两篇论文是关于朱子学传入韩国的文化特色及本土化过程的研究。一篇是叙述了朱子画像供奉于韩国书院的过程及特色,另一篇是韩国儒者吸收《朱子家礼》而后予以本土化的内容。
4.朴晶爱:《朝鲜时代朱子崇慕热与其形象的视觉化特色》,《大东文化研究》93号,2016年。
朴晶爱的论文是关于自朱子学传播至韩国以来所形成的书院和美术等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他说朱子学是高丽末期安垧(1243~1306)从中国燕京回韩国时,抄朱子书及摹写孔子和朱子画像后开始传播于韩国的。后来15世纪初《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等著作从中国传来,16世纪初《性理大全》及《朱子大全》在朝鲜刊印,而且李退溪写了《朱子书节要》、李栗谷又写了《圣学辑要》为朝鲜朱子学的广泛普及带来积极的作用。1543年周世鹏(1495~1554)模仿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建立了白云洞书院。17~18世纪在韩国所建立的书院约达903所。韩国文人特别仰慕朱熹隐居武夷山期间的生涯,不但模仿武夷九曲及创作武夷诗歌,也背诵及阅读《朱熹词》《斋居感兴诗》等作品。徐起(1523~1591)及其门人在1581年供奉朱子画像建立了孔岩书院。之后该书院因壬辰倭乱被破坏,1624年又赐额为忠贤书院。1790年重修忠贤书院时尹命泽改摹晦菴影帧。据说此影帧在1871年政府发布书院废除令之后被移安于公州乡校。1925年重建忠贤书院时,添购了新的朱子画像供奉于书院内。由此可说,朝鲜时代韩国的朱子画像与当时的忠贤书院的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朴晶爱在此篇论文中介绍了许多现存的朱子画像的照片。现在这些资料分别保存于国立中央博物馆、首尔历史博物馆、公州忠贤书院、庆州云谷书院、成均馆大学博物馆、个人收藏等地。笔者认为此篇论文提供了朱子学传播于韩国后而形成的朱子画像与书院的关系史,丰富了韩国儒学之朱子学本土化的研究。
5.崔俊夏:《〈朱子家礼〉的传播与韩国传统礼法的转变及具有现代意义的定位研究》,《人文学研究》103号,2016年。
崔俊夏的论文是韩国儒学对《朱子家礼》传承方面的研究。他说韩国学术界难以确定《朱子家礼》传播于韩国的时期。一般推论是高丽时代安珦(1243~1306)在带了许多有关性理学的书籍回国时一起带回的。朝鲜王朝成立之后,新进士大夫阶层开始积极推动了《朱子家礼》。新进士大夫为了巩固他们的阶层地位,首先施行家庙制,以终止高丽时代佛教文化习俗的弊病,另一方面宣扬祖先崇拜和孝道精神。《朱子家礼》中的三年丧制是在皇室和士大夫阶层中所施行,而一般老百姓则都守百日丧制。16世纪以后《朱子家礼》之所以能推广并普及于全国,李退溪和李栗谷的贡献很大。1592年壬辰倭乱之后,韩国儒林继承退溪和栗谷的推广精神,继续推动了《朱子家礼》的礼学。17、18世纪的《朱子家礼》成为朝鲜礼学的骨干。金长生(1548~1631)著述了世称朝鲜礼学的理论书的《家礼辑览》,还写了《典礼问答》《丧礼备要》《疑礼问解》等书。大韩民国成立之后,韩国政府趁着打破虚礼虚式传统的名分之际,1973年推行了“家庭仪礼准则”。崔俊夏详细地梳理及比较了韩国传统家礼与近代以来多次变化的现代家礼。笔者认为此篇论文不但梳理了《朱子家礼》传入韩国的演变过程,而且详细探讨韩国的传统家礼与现代伦理的异同问题,以显示韩国现代家庭伦理存在的虚实问题。
关于朝鲜性理学、退溪学、茶山学方面,韩国学者研究退溪的哲学评论、退溪的士观、茶山的修养论、当代韩国新儒家、当代朱子学家、茶山解配期的易学、茶山纪行、茶山与基督教、茶山的经世学及权衡论等主题。在笔者看来,在2016年度的研究中,值得介绍的是关于当代韩国新儒家的一些著述和思想。
6.郑圣喜:《再论民族主义倾向的韩国儒学史的叙述——以玄相允的〈朝鲜儒学史〉为主》,《儒学研究》37号,2016年。
此篇论文专门探讨了韩国学者玄相允(1893~1950)的《朝鲜儒学史》具有的意义及特色。郑圣喜首先介绍了玄相允,他出生于朝鲜的儒林家庭,接受了扎实的儒学教育,而且他12岁结婚之后,受到了岳父白彝行,即当时被称为名门民族私学的五山学校的首届校长,深厚的影响。27岁时遇到了“3·1独立运动”而身陷囹圄,以至于后来他不直接参与任何政治运动,而将自身奉献于教育活动。郑圣喜提及玄相允的儒学观与朝鲜时期韩国儒者的儒学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玄相允认为朝鲜时代的社会可类比于欧洲的中世纪。于是他主张应当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方法治疗韩国社会的弊病、革除社会中的各种弊端。他对朝鲜时代的儒学一直保持批判的态度。他虽然高度评价朝鲜时代早期赵光祖等士林派推行的王道政治思想,但认为己卯士祸发生以后韩国儒学的“实际”运动不断被瓦解,以至于只好走向“理论”路线。相反的,玄相允对反动于朱子学兴起的经济学派(实学运动)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主张由丁若镛所集大成的经济学派的主张具有爱民、考据学的学风、吸收西学等特色。
在玄相允的《朝鲜儒学史》内容中最受注目的是所谓儒学功罪论。玄相允认为朝鲜儒学之功在于君子学之勉励、人伦道德之尊崇、清廉节义之精神等三种。相反的,儒学给朝鲜社会带来的罪过则有慕华思想、党争、家族主义的弊害、阶级思想、文弱、工业能力之下降、丧名主义、复古思想等八种。他的功罪观是以浓厚的儒学节义观与民族主义作为基础的。
7.洪元植:《现代新儒学与卿辂李相殷》,《孔子学》30号,2016年。
洪元植的论文是关于当代韩国新儒家李相殷(1905~1976)的研究。李相殷的代表著作有《韩国哲学史讲义》《退溪的生涯与学问》等。李先生是从1927~1931年攻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一直任职于韩国高丽大学哲学系。他的读书与学术活动不限于韩国,经常与中华圈的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等学者交流。李先生强调仁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是具有跨越东西古今之普遍价值。人类处于急速的近代化、工业化所带来的异化及本性丧失的时代,由此他主张以儒家的人道主义治理这些问题。洪元植认为如果从中体西用类的角度看李相殷的思想,他也是一位东道主义者。他说的“东道”的核心思想是儒学,其精华是指退溪学。这与当代中华圈的新儒家以阳明学作为核心价值趋向有所区别。到了1960年,韩国儒学界逐渐重视实学思想之际,李先生发表《实学思想的形成与展开》,主张性理学与实学并不是相克关系,而是相辅关系,正视这点才能创造出高水平的学术文化。笔者认为洪元植的论文综合地梳理及探讨了当代韩国新儒家李相殷的思想。同一时期活动的玄相允(1893~1950)的思想较突出民族主义特色,李相殷的思想则一方面与当代中华圈新儒家的思想相呼应,另一方面在韩国儒学中寻找跨越东西古今之普遍思想。
8.姜卿显:《退溪对明代儒学的批判与退溪学的实践意义的特色》,《哲学论集》46号,2016年。
姜卿显的论文主要梳理及探讨李退溪对明代儒学的批判。李退溪对禅学保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他对禅学的批判直接关系到他对象山陆九渊、白沙陈献章、医闾贺钦、阳明王守仁等心学的批判。退溪批判陈白沙,说他的思想充满着禅佛教的意蕴。退溪言“陈白沙、王阳明之学皆出于象山,而以本心为宗,盖皆禅学也。然白沙犹未纯为禅,而有近于吾学。……但其悟入处终是禅家伎俩,故自谓非禅,而其言往往显是禅语。”退溪认为白沙主张读书穷理,所以不能完全视他为禅学,然而他又过度强调静坐、厌世求定,因此难免有流于禅学的嫌疑。他针对阳明学说“欲排穷理之学”。姜卿显指出阳明的知行合说把形气上的好恶与义理上的知行混为一谈,排除外面的事物,而只在人心之本位上说明知行问题,因此不能成功地做出与人伦秩序相符的实践。姜卿显特别强调退溪把自己的学问与白沙、医闾、阳明等明儒心学区别开来,乃是在他从天命之理所导出的儒学理想实践上的命令与对遵循其命令的义务之省察,而在此二者的背景下所提出的。笔者认为姜教授不但梳理了退溪对明儒之学的批判内容,同时也深入剖析退溪学本身具有的哲学含义,由此使得读者能理解在传承朱子学方面韩国儒学与明代儒学之不同。
9.沈庆昊:《丁若镛解配以后的学问及春川旅游》,《茶山学》29号,2016年。
沈教授的论文是朝鲜儒者丁若镛的文化纪行研究。丁若镛(号茶山,1762~1836)是朝鲜时代的韩国大儒。他因为各种缘由受到政治压迫,被流放于康津将近十八年。1818年,他57岁时才解配出来。这篇论文主要叙述了丁茶山解配之后的生涯及纪行。茶山的文化纪行充满着文人色彩及哲学意蕴,令人足以感受到既有激情又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风貌。沈教授介绍丁若镛解配后两次去春川旅游。茶山一生仰慕杜甫,因此他去春川时把春川附近的马迹山比作杜甫诗中的鹿头山。他始终努力体会杜甫的诗人精神及意蕴。他的学术思想随着仕宦期、流配期、解配期而发生了变化。他第二次去春川旅游时,叙述了对学问的关心、对山水大自然的钟情以及对庶民的同情。而且他主张如果朝鲜受到外国的侵略,应当把春川作为最后的防御线。
以上笔者简单地梳理了2016年度值得介绍的一些韩国学者的论文。其中,笔者认为所谓当代韩国新儒家思想及韩国儒学的本土化研究需要继续扩大且加强。事实上,韩国学者对近现代韩国朱子学或是当代韩国新儒学的研究十分不够,连其师承关系和思想系谱的研究也未得出共识,这些项目的研究还停滞于朝鲜时期的研究。当代韩国新儒家可分为留学派、民族主义派、基督教派等派别。如上述的李相殷(1905~1976)先生属于留学派,玄相允(1893~1950)先生是属于民族主义派,文中未提及的柳永摸先生(1890~1981)、咸锡宪先生(1901~1989)是属于基督教派。尚有略早于他们活动的朴殷植(1859~1925)是一位阳明学家。这些人物及派别是值得继续关注和研究的。
(作者单位: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2016年日本朱子学研究综述
⊙〔日〕板东洋介
一、日本儒教学会之成立
谈到今年日本儒教研究中最具特色的大事,首先应该提到日本儒教学会之成立。在日本代表性儒教研究者的倡议下,2016年5月14日于东洋文库(东京都文京区)举办了该学会的成立大会。东洋文库是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在日本最为重要的“东洋学”研究方面的专门图书馆,坐落在著名庭园“六义园”附近,此园由“诗有六义”(《毛诗大序》)得名。日本儒教研究能在此地迈出新的一步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成立大会首先由倡议者代表土田健次郎(早稻田大学教授)致开幕词。在其中,详尽地叙述了学会成立的趣旨之全貌。土田健次郎提及下述内容:在当今日本,没有专门研究儒教的学会,儒教问题主要由中国文化学会、日本思想史学会等学会分散研究。这是不可思议的。就亚洲的其他宗教学问即佛教、道教而言,已有印度哲学学会、日本道教学会,为何唯独儒教方面没有呢?海外的儒教研究者也曾困惑不解地指出过这一点,并且近年来不断增多并深化的与海外研究者的合作研究都仅限于以个人为单位分散性进行的小规模活动,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因此希望可以作为日本的儒教研究者固定的交流场所,并作为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基地而设立该学会。[1]土田健次郎的发言内容大致如上。
其后,恰巧来到东洋文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程永华祝了贺词。接着举行了“日本儒教研究之现状”研讨会,研究各地域、各时代儒教的权威学者们做了报告并开展了讨论。担当者如下,日本近世儒教:前田勉(爱知教育大学教授)、日本近代儒教:河野有理(首都大学东京教授)、朝鲜儒教:山内弘一(上智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儒教:渡边义浩(早稻田大学教授)、中国近世儒教:小岛毅(东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儒教:中岛隆博(东京大学教授)。通过上述担当范围,可以一目了然地得知,学会不是研究“日本儒教”的学会,而是以日本研究者为中心的“儒教学会”。尽管如此,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该学会将成为与日本思想史学会并驾齐驱的“日本儒教”的一大研究中心。在此仅就涉及日本朱子学的问题介绍一下登台发言者的报告内容。[2]首先,前田勉基于日本思想史研究中近世儒教研究的地位与数量都相对低下这一局面所带来的“一种危机感”,全面概括了丸山真男、尾藤正英、渡边浩等人研究二战后日本儒教的方法论与研究视角,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在近世后期出现的“会读”习惯,陶冶出了承担起日本近代化重任的社会精英的风貌。前田勉的讲话意味着,这一风气正显示了在日本存在着亚洲的“另一个近代”,它不同于战后日本高声提倡、积极探索的西欧近代型“主体性”。另外,河野有理介绍了田口卯吉(1855~1905)、加藤弘之(1836~1916)等近代日本著名的知识人使用“封建”“郡县”等儒教古典词汇,围绕地方分权与立宪政体所展开的时政性争论,并指出,儒教在近代日本也作为“词汇数据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其后的综合讨论中,在登坛者之间以及学会成员之间开展了活跃的讨论,给笔者(板东)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是,许多发言人都强调,其他儒教文化圈中的儒教研究热气腾腾且具有现实意义,而与此相对,日本研究者不过是作为“逝去的东西”来客观性地研究儒教,他们将这一“温差”及“与对象之间保持距离”作为日本研究者的特色予以积极的肯定。
其后在综合大会上,推选土田健次郎为首届会长,前田勉为副会长。同时任命的理事及评议员也都是日本著名的儒教研究者。正如上述土田健次郎所提倡的,设置一个日本儒教研究者的综合性交流场所具有深远意义,并且可以期待,该学会作为有关儒教的国际性合作研究之主体将发挥重大作用。
二、日本人的死生观与朱子学
人死之后去哪里?是去天国、极乐净土、地狱那样的他界,还是变为神性的存在留在现世或是如近代的“科学性”世界观所说的那样消失得无踪无迹?并且,这些对死后世界的想法与如何度过此生这一问题密切相联。这种对死与生的思考,在日本常被称为“死生观”。与日本思想文化整体类似,日本人的死生观也同样,积极地说是重叠的,消极地说是极其含糊的。例如,古代神话中包含着对死者之国(黄泉国)的恐惧、平安时代曾流行净土教派佛教等,日本人的死生观在不同时代姿态各异,而决定当今日本人典型的死生观的最重要契机,应是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强制全体国民接受佛教。由此,与日本人的死亡相关的仪式(葬礼、祭礼)都变为以佛教式举行。在幕府崩溃,信仰宗教的自由得到承认的近现代,大多数日本人的葬礼祭礼还是以佛教式进行的。问题是在德川时代以后,日本人的死生观全都染上了佛教色彩吗?其实并非如此。调查了日本人的习俗并为日本民俗学奠定了基础的柳田国男(1875~1962)[3]主张:大半的日本人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佛教式葬送礼仪,但在观念上并不认同轮回、极乐往生等佛教的一般性死后观念(《先祖の话(祖先之事)》,1946年)。柳田国男认为,日本的“常民”(在农村从事稻作耕种的普通的日本人)的死生观是死后也作为神留在现世,在他接受子孙祭祀时定期降临,永远保佑子孙。在这一想法中,死者既未轮回,也未成佛。也有人反对柳田的这一说法,他们认为,佛教对于日本人的死生观及葬礼祭礼产生了决定性影响。[4]对这一点至今未得出定论。
上述死生观在日本构成了极其现代性的问题。大家庭急速向核心家庭(一夫一妻及子女构成的小家庭)转变,长期不景气造成家庭年收入减少等使得以家庭为单位举行的葬礼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批判传统佛教式葬礼之虚伪的宗教学者岛田裕巳的《葬式は、要らない(不要葬礼)》》(幻冬舍,2010)这一轰动性著作带来了巨大反响,取代佛教式葬仪,基督教式、神道式、非宗教式等新式葬仪逐步增多起来(总体而言,薄葬倾向日益显著)。大型超市集团介入丧葬业界,全球性函购公司展开了为葬礼“派遣僧侣”的事业,这些都作为葬礼的商业化、形式化的深刻问题而受到重视。进一步而言,作为国际性问题长期受到关注的靖国神社这一设施也是建立在“作为神来祭祀殉国者”这一固定的死生观上的。这是源自于日本人传统的死生观而自然形成的,或者不过是到了近代才树立起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一直是有识之士争执不休的重要争论点之一。
那么,对于如此错综复杂并具有现实意义的日本人的死生观,朱子学施加了怎样的影响呢?如上所述,论及“日本人的死生观”之际提及的两大要素是佛教与神道(基层信仰),而不是朱子学。因此日本人的死生观与朱子学之关联问题至今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在今年,出版了一部追溯这一关联的重要著作。那就是本村昌文所著《今を生きる江户思想——十七世纪における佛教批判と死生观(活在当下的江户思想——十七世纪的佛教批判与死生观)》(ペりかん社,2016年)。
德川幕府的统治恰始于17世纪初(1603),如上所述,官方宗教政策是佛教式的,但是从设立幕府时就开始有所作为的儒者们则仿照他们所尊崇、所依据的宋学者,对佛教展开了抨击。一般认为,他们对佛教的抨击只不过是对朱熹等人排佛言论的“翻版”“照搬”,基本上缺乏独创性。可是本村昌文仔细检阅了17世纪日本儒者的著作,从中发现了日本儒者独自的思维方式及意义。该书中提到了中江藤树(1608~1648)、林罗山(1583~1657)、松永尺五(1592~1657)、清水春流(1626~?)、向井元升(1609~1677)、熊泽蕃山(1619~1691)、中村惕斋(1629~1702)等知名的与无名的儒者的专门性著作,以及被称为“假名草子”等面向一般大众的启蒙书籍(在仅限于僧侣和儒者能读懂汉文的近世前期社会,用假名写作的浅显易懂的假名草子,反而比正式的汉文儒书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本村昌文认为,在这些17世纪的儒教文献中可以看出,以1640年左右为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17世纪前半期的儒者对人类死后的问题几乎不置一词,而使用“佛教是破坏伦常道德的‘异端’教说,而树立现世人伦的儒教教说才是最好的”这一韩愈以来排佛的老套言论方式来抨击佛教。本村昌文将这种集中关注“如何活在当下”(第51页)这一点的儒教教说称为“生之教说”。可是到了17世纪中叶以后,儒者们开始抨击佛教的轮回与极乐往生之说,主张气之聚散与鬼神之来格,开始积极地基于朱子学来谈论死后世界。这被本村昌文称之为“生死之教说”。本村昌文总结说:就这样,以1640年左右为界,出现了从“生之教说”向“生死之教说”的转变。至于为何这发生在开设幕府后半世纪左右,他分析道:由于战乱终息,社会趋于稳定,一方面“教化人们不受基督教与异国宗教诱惑的意识”(第291页)在儒者们心中觉醒,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死后之事所拥有的不安与恐惧,以及未理解死生之根干这一认识”(第292页)形成起来。在重新归于稳定与和平的社会中,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死生观,以此超越由官方权力强制灌输的佛教式死生观,朱子学的教说因此重要起来。
本村昌文认为,当时的日本儒者作为朱子学死生观的根本性典据常常参照的是《朱子语类》卷三:第十九条,其中主张死后的气(魂魄)的聚散,以及继承了同一气的子孙之祭祀形成的感格。在此说日本儒者的死生观并非仅限于“照搬”朱子,是由于日本儒者们有意识地从朱子言论中摒弃了“气之散逸”,反而强调“死后灵魂不灭”这一点。受着道德约束而活过此生的人,死后也不会消亡,而作为超越性留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他的本性会被子子孙孙无穷地继承下去。之后,日本人从朱子的言论中辨别出的这一死生观与神道的词汇、概念混淆起来。本村教授在本书尾章介绍了同在17世纪中叶谈论了不同于佛教死生观的神道家吉川惟足(1616~1694)的死生观,这不是用朱子学,而是使用“神避”“长隐”“日少宫”等神道词汇来说的,同时指出:“虽然使用的概念不同,死后的灵魂回归到某处而永续这一思考框架是与本书中探讨的以17世纪中叶形成的朱子学为基础的死生观共通的”(第293页)。[5]读者或许已看出,这一死生观与柳田国男分析的日本人民俗性死生观极其相似。被视为“日本人固有的”“神道式”的死生观与朱子学的死生观之间出现的思想性交涉过程,今后或许会成为日本朱子学研究中的一大主题。
另外,本村昌文的著作主要分析了书籍上围绕死生观所记载的教说,并未言及在礼仪上如何具体实践此类死生观的问题。从本村昌文认为的教说上发生转机的1640年起,大约过了30年左右,于1670年前后儒教式死生观在礼仪上也出现了一大转机。即当时日本先进的政治家与儒者开始尝试根据《朱子家礼》实际举行儒式葬礼(其大半由于幕府的禁压而流产)。首先在宽文十二年(1672),会津藩主保科正之(1611~1672)的儒葬不顾幕府反对而进行,接着于天和二年(1682)举行了日本第一淳儒山崎暗斋(1618~1682)的儒葬,之后到了元禄十三年(1700),延请朱舜水(1600~1682)为宾师的水户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也举行了儒葬。关于这些作为礼仪的儒葬,可参见2012年笔者介绍过的田世民所著《《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礼受容の研究(近世日本的儒礼受容之研究)》(ぺりかん社,2012)。在这些礼仪方面,也能见到朱子学式的葬礼随着国粹意识之高涨,逐步被脱胎换骨为神道式葬礼[6],这一过程极其耐人寻味。
(林松涛译)
(作者单位:日本皇学馆大学)
2016年日本朱子学研究综述
〔日〕板东洋介
一、日本儒教学会の設立
本年の日本儒教研究を特徴づける出来事としては、何よりもまず、日本儒教学会の設立を挙げなくてはならない。日本を代表する儒教研究者たちが 発起人となり、2016年5月14日に東洋文庫(東京都文京区)でその創立大会が行われた。東洋文庫は世界有数、そして日本随一の「東洋学」の研究図書館であり、「詩有六義」(「毛詩大序」)から名を取った名庭園「六義園」の近傍に立地している。日本儒教研究の一つの出発を記念するのに相応しい場 所である。
設立大会ではまず、発起人代表で、ある土田健次郎(早稲田大学教授)による開会挨拶が行われた。その内容のうちに、学会設立趣旨の大概は尽くさ れていた。土田は次のような内容を述べた。すなわち、現在の日本には儒教の専門学会が存在せず、儒教の研究は主に中国文化学会•日本思想史学会な ど、諸学会で分散して行われている。これは奇妙なことである。他のアジア 発の諸教諸学、すなわち仏教や道教については印度哲学学会や日本道教学 会がすでに存在するのに、なぜ儒教についてのみ存在しないのか。この事情 は海外の儒教研究者からも驚きをもって指摘されることであり、かつ近年増加•進展している海外研究者との共同研究カヾ、個人単位の散発的で小規模のものにとどまりがちであることの要因ともなっている。そこで日本の儒教研 究者の恒常的な交流の場として、ならびに国際学術交流の基盤として、本学会を設立したい[1]。土田の発言の更概は以上であった。
その後、ちょうど東洋文庫を来訪中であった中華人民共和国の程永華•駐日大使が祝辞を述べられた。続いてシンポジウム「日本における儒教 研究の現在」が行われ、各地域各時代の儒教研究の第一人者が報告と討論を行なった。担当者は次のようである。日本近世儒教:前田勉(愛知教育大学教授)、日本近代儒教:河野有理(首都大学東京准教授)、朝鮮儒教:山内弘一(上智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儒教:渡邊義浩(早稲田大学教授)、中国近世儒教:小島毅(東京大学教授)、中国現代儒教:中島隆博(東京大学教授)。上の担当範囲に瞭然な通り、本学会は「日本の儒教」についての学会ではなく、日本の研究者を中心とする「儒教の学会」である。とはいえ、本学会は日本思想史学会と並んで「日本の儒教」の一大研究中心となってゆくことカヾ、極めて高い蓋然性をもって予想される。日本朱子学に関連する限りで登壇者たちの報告内容を紹介すると、次のようである⑵。まず前田勉は日本思想史研究の中で近世儒教研究の位置と量とが相対的に低下していることへの「一種の危機感」のもと、丸山真男•尾藤正英•渡辺浩らによる戦後の日本儒教研究の方法論や研究視角を総括し、その上で近世後期に見られる「会読」の慣習の中で日本近代を担う選良たちの気風が涵養されたことを後付けた。その気風は、これまで戦後日本で声高に提唱され、模索された西欧近代型の「主体性」とは異なるアジア的な「もう一つの近代」の所在を示していると前 田は示唆する。また河野有理は、田口卯吉(1855-1905 )や加藤弘之(1836-1916)ら近代日本の代表的な知識人たちか、、「封建」「郡県」という儒教の古典的な語彙を用いて、地方分権や立憲政体をめぐる同時代的な議論を展開していることを紹介し、近代日本においても「語彙データベース」として儒教が有為に機能し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た。またその後の総合討論においては登壇者相互、また参加した学会員たちによる活発な議論が交わされたが、報告者(板東)の印象に残ったのは、多くの発言者が、、他の儒教文化圏における儒教 研究が、もつ熱気や現代性に対して、日本人研究者はあくまで「過去のもの」 として客観的に儒教を研究しているという「温度差」や「対象との距離」を強調し、かつそれを日本の研究者の特色として肯定的に評価していた点であ った。
その後、総会にて土田健次郎が初代会長、前田勉が副会長を務めることが決議された。同時に任命された理事及び評議員には、日本の代表的な儒教研究者が名を連ねた。上記の土田の提言の通り、日本の儒教研究者の総合的な交流の場が設けられたことは極めて意義深く、かつ儒教に関する国際的な共同研究の主体としても本会が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ゆくことが期待される。
二、日本人の死生観と朱子学
人は死んだ後、どこへ行くのか。天国•極楽浄土•地獄のような他界に赴くのか、それとも神的な存在となって現世に留まるのかあるいは近代の「科学的」世界観が説く如く、消滅してそれきりなのか。そして、こうした死後の世界の構想は、この生をいかに生きるかという問いへと連動してくる。このような死と生との捉え方を、日本では多く「死生観」とよぶ・。日本の思想文化全体と同じく、日本人の死生観もまた、良くいえば重層的であり、悪くいえば極めて曖昧である。古代神話における死者の国(黄泉国)への恐れや、平安時代における浄土教系仏教の流行など、、日本人の死生観は時代ごとに極めて異なった姿を見せるが、今日の日本人の平均的な死生観を決定づけた最も重要な契機は、やはり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徳川幕府による全国民への仏教の強制である。これにより日本人の死に関する儀礼(葬・祭)は仏教式で行われることになった。幕府が瓦解し、信教の自由が認められた近現代でもなお、大多数の日本人の葬祭は仏教式である。ならば徳川時代以降、日本人の死生観は仏教一色に塗りつぶされてしまったのか。そうではない。日本人の習俗を調査し、日本民俗学の基礎を築いた柳田國男(1875~1962)⑶は、大半の日本人は形式的には仏教の葬送儀礼を受容しつつも、観念の上では輪廻や極楽往生といった仏教の一般的な死後観を承認していないと主張した(『先祖の話』1946)〇柳田によれは,、日本の「常民」(農村で稲作を営む平均的な日本人)の死生観は、死後も神として現世にとどまり、子孫の祭りに応じて定期的に来臨し、いつまでも子孫を見守り続け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ここでは死者は輪廻することも成仏することもな・い。こうした柳田の説に対しては、仏教は日本人の死生観と葬祭とに決定的な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という反論もあり⑷、充分な結論が得られていないのが現状である。
そして如上の死生観は、日本において極めて現代的な問題と化している。大家族から核家族(単婚小家族)への急速な移行や、長引く不況による世帯年収の減少は、家族単位で営まれる葬儀の形を抜本的に変えつつある。伝統的な仏式葬儀の虚飾を批判する宗教学者•島田裕巳の『葬式は、要らない』(幻冬舎、2010)というセンセーシ크ナルな書籍が大きな反響を呼び、仏式の葬儀に代わってキリスト教式•神道式•無宗教式といった新しい形式の葬儀が増加しつつある(総体的に見ると薄葬化の傾向が著しい)。大手スーパーの葬儀業界への参入や、国際的な通信販売会社による葬儀への「僧侶派遣」事業の開始も、葬儀の商業化•形式化として深刻に受け止められた。またさらに、国際問題として焦点化して久しい靖国神社も、“国に殉じた大を神として祀る”という一定の死生観にもとづいた施設であって、それが日本人の伝統的な死生観からして自然なものであるのか、それとも近代に入ってから作為されたイデオロギーに過ぎないのかという問題が、識者たちの論戦の重要な一論点を構成している。
で、は、このように錯綜し、かつアクチ그アルな日本人の死生観に対して、朱子学はどのような影響を及ぼしたのか。ここまでの概略に瞭然な通り、“日本人の死生観”を論じる際に言及される二大因子は仏教と神道(基層信仰)であって、朱子学ではな・い。それゆえ日本人の死生観と朱子学との関わりについては従来、十分な顧慮が払われていなかったのである。しかるに本年、この関わりを後付けた労作が上梓された。本村昌文『今を生きる江戸思想一十七世紀における仏教批判と死生観』(ぺりかん社、2016.9)である。徳川幕府の統治はちょうど17世紀の初頭(1603)にはじまり、前述の通り公の宗教政策としては仏教が行われたが、開幕とともに活動を開始した儒者たちは、彼らが尊崇し、依拠した宋学者たちに倣って仏教批判を展開した。彼らの仏教批判は、一般に朱熹たちの排仏言説の単なる「焼き直し」「受け売り」にすぎないといわれ、概して独創性に乏しいものとされる。しかし本村は、17世紀の日本儒者たちの著作を丁寧に検討し、そこに日本儒者独自の思惟と意義とを見出している。本著で扱われるのは、中江藤樹(1608~1648)、林羅山(1583~1657)、松永尺五(1592~1657)、清水春流(1626~?)、向井元升(1609~1677)、熊沢蕃山(1619~1691)、中村惕斎(1629~1702)といった有名無名の儒者たちの専門的な著作と、「仮名草子」とよばれる一般大衆向けの啓蒙書とである(漢文の読解能力が僧侶や儒者のみに限定されていた近世前期社会にあって、仮名で書かれ、内容も平易で通俗的な仮名草子は、かえって本格的な漢文儒書以上の社会的な影響力を有していた)。本村によると、これら十七世紀の儒教文献の中には、1640年頃を境にして、大きな変化が認められるという。すなわち、17世紀前半の儒者は、人間の死後の問題にはほとんど言及することなく、“仏教は倫常道徳を解体する「異端」の教えであり、現世の人倫を成立させる教えとしては儒教が最勝である”という、韓愈以来の排仏言説の常套形を用いて仏教を批判した。このように「いまをいかに生きるか」(p.51)という関心に集中した儒教教説を、本村は〈生の教説〉と呼ぶ。しかし十七世紀の半ば以降になると、儒者たちは仏教の輪廻や極楽往生の説を批判し、気の聚散や鬼神の来格を説いて、積極的に朱子学に基つ’く死後の世界を語り始める。これを本村は〈生死の教説〉と呼んでいる。このように1640年頃を境として、〈生の教説〉から〈生死の教説〉への移行が見られると本村は結論づけるのである。それが開幕後半世紀ほどのタイミングで生じた理由については、戦乱の終息と社会の安定の中で、一つには「キリスト教や異国の宗教に惑わぬように人びとを教化するという意識」(p.291)が儒者たちに目覚めたためであり、もう一つには「人々が死後
のことに不安や恐れを抱き、また死生の根幹を理解していないという認識」(p.292)が生じたためと分析されている。安定と平和を取り戻した社会の中 で、公権力によって強制された仏教的死生観を越えた死生観が模索され、朱子学の教説が大きな存在感をもったのである。
本村によると、当時の日本人儒者が朱子学の死生観の根本典拠として繰り返し参照したのは、死後の気/魂魄の聚散や、同一気の子孫の祭祀による感格を説く『朱子語類』巻三•第十九条である。ここで日本儒者の死生観が朱子の「受け売り」に留まらないのは、日本儒者たちが朱子の議論の中で“気の散逸”を意図的に捨象し、むしろ“死後の霊魂の不滅”を強調してゆく点である。道徳的に律された生を生きた人は、死後も消滅することなく、超越的な存在としてこの世界に留まり、とりわけその本性は子々孫々に無窮に受け継がれてゆく。朱子の議論から日本人が読み出したこうした死生観は、神道の語彙や概念と混淆してゆく。本村は本書終章で、同じく17世紀半ばに仏教とは異なる死生観を語り出した神道家•吉川惟足(1616~1694)の死生観を取り上げ、、それが朱子学ではな、く「神避」「長隠」「日少宮」など神道の語彙を用いて語られたものでありなが、ら、「使用するタームは異なるものの、死後の霊魂がどこかへ回帰し永続するという思考の枠組みは、本書で検討してきた十七世紀中葉において形成された朱子学をベースとした死生観にも共通する」(p.293)と指摘している⑶。すでに瞭然であるカヾ、こうした死生観は、柳田が分析した日本人の民俗的死生観とも極めて似通っているのである。「日本人固有」とされ、「神道的」とされる死生観と、朱子学の死生観との思想的な交渉過程については、これからの日本朱子学研究の一大テーマとなるであろう。
なお、本村の著作は死生観についての書物の上に記された教說を分析したものであり、死生観が具体的に実践される儀ネ.Lの上までは及んでいない。本村が教說の上での転機とした1640年からおよそ30年遅れて、1670年頃に、儀礼の上での儒教的死生観の転機が訪れる。日本の先進的な政治家や儒者たちによって、『朱子家礼』に基づいた実際の儒葬が試行され始めるのである(その大半は幕府の禁圧によって頓挫した)。まず寛文12(1672)年に会津藩主・保科正之(1611~1672)の儒葬が幕府の抵抗を押し切る形で斎行され、続いて天和2(1682)年には日本随一の淳儒•山崎闇斎(1618~1682)の儒葬があり、遅れて元禄13(1700)年には朱舜水(1600~1682)を賓師とした水戸藩主•徳川光囹(1628~1700)の儒葬が行われた。こうした儀礼としての儒葬については、2012年の本稿で紹介した田世民『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礼受容の研究』(ぺりかん社、2012)がある。こちらの儀礼面でもやはり、朱子学式の葬儀が次第に国粋意識の高まりとともに神道式の葬儀へと換骨奪胎されてゆく過程が見られる⑹のが極めて興味深〉ゝ。
(作者单位:日本皇学馆大学)
2016年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综述
⊙〔日〕福谷彬 廖明飞 译
2016年日本学界有关朱子及其后学思想(狭义的“朱子学”)的研究并不多,本文拟扩大范围,介绍包括朱子学研究在内的宋学研究(广义的“朱子学”)的最新进展。本文分专著、单篇论文、译著三方面做介绍,最后总结本年度的研究并展望未来的学术走向。
一、专著
1.福田殖:《宋元明時代の朱子学と陽明学》(《福田殖著作集I》),研文出版,2016年11月。
本书著者福田殖(1933~2016)为九州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师从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史讲座首任主任教授楠本正继,同时又师事九州大学教养部冈田武彦教授。福田殖先生于本书出版前一月逝世,本书也成为作者最后一部著作。
本书由作者在已发表的21篇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由四章组成:第一章“道学诗”,第二章“宋代篇”,第三章“元代篇”,第四章“明代篇”。其中,与朱子直接相关的有第一章的《朱子の道学詩について》《宋明の道学詩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两篇讨论“道学诗”的论文,以及第二章“宋代篇”中的《朱子の死生観について》《朱子の死生観について(続)》。其他论文与朱子并不直接相关,但都是讨论宋明理学的议题。第二章“宋代篇”的《范仲淹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胡安国小論(上·下)》《張南軒に関する二、三の考察》《張南軒初年の思想》探讨了范仲淹的相关问题以及胡安国、张南轩等湖南学者的思想;第三章“元代篇”《許衡について》《元代の経学者許衡ーその思想的特色》《呉澄小論》讨论素有“南吴北许”之称的许衡和吴澄的思想。第四章“明代篇”《陳白沙思想の性格》《王陽明の心学思想の構造——学三変•教三変をめぐって》等讨论陈白沙的思想特色和王阳明的思想变化。无论哪篇文章,都以该时代的代表性理学家作为讨论对象,于此也可窥见作者的学术追求和志向。
首先,本书的第一章对“道学诗”做了考察。“道学诗”乍听起来很陌生,其实就是指道学家所作之诗。道学诗乃借用诗之形式表达道学之哲理。在本章的论述中,作者将邵雍《伊川击壤集》定位为道学诗的先驱。
作者认为,朱子道学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三十七岁时创作的《斋居感兴二十首》(《文集》卷四)。朱子于该诗序文中云:“虽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于日用之实”。作者认为据此可以看出朱子于道学诗并不追求文采,而是留意有助日常修养的伦理性,并将该诗当作“道学诗”的标杆。作者指出,道学诗是阐述哲理之诗,惯用说理之言——理语,与普通诗重视表现感情和风景不同。比如,作者根据朱子《克己》(《文集》卷二)一诗的内容,认为“克己”不单是禁欲的工夫,而是伴随着开朗自在和喜悦的自我充实的意识。如此,道学诗是通过诗的形式表现道学修养实践中的心境。福田氏通过以上的考察,发掘出“道学诗”与普通诗不同的独特价值。
其次,第二章宋代篇的《朱子の死生観について》一文,分析了朱子对“鬼神”“死生”的思考。正如分别有“在天之鬼神”“在人之鬼神”“祭祀之鬼神”,鬼神是多种多样的。作者认为,朱子将鬼神的这种多样性,归因于“气”的多面性,通过阴阳二气的屈伸往来解释鬼神。对于鬼神这种本来是超自然非现实的存在,朱子尝试做出符合自然科学的、合理的解释。但是,另一方面,朱子对视鬼神与气为一的弟子说“是这气里面神灵相似”[1],可见朱子避免将鬼神等同于气。此外,关于“鬼神”,朱子又说“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处且莫要理会”[2],承认鬼神也有无法根据理推阐的一面。根据以上两点,福田氏指出,朱子的鬼神生死观本质上存在着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和通过因果律解决的方面,事实上毋宁说,正是无法由理推阐的一面成就了朱子理论的自恰完足。
过去一直将“祭祀感格”说当作朱子鬼神论的重大缺陷,在《朱子の死生観について(続)》中,福田氏对“祭祀感格”说进行了再探讨。所谓“祭祀感格”说是指,人死之后构成人体的气也随之飘散,但并非立即散尽,通过适当的祭祀,先祖之气能够感通而至(感格)。朱子从将鬼神与气相联系做出合理解释的立场出发,试图说明祭祀这一本来非合理性的儒家传统仪式的意义。针对此说,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岛田虔次质疑气如果完全散尽,也就没有必要祭祀。此一质疑揭示了朱子祭祀感格说的缺陷所在——朱子的合理主义倾向与传统儒家的非合理主义的龃龉不合。[3]
对于岛田氏的上述观点,福田氏站在拥护朱子的立场上重新探讨了祭祀感格说的内容。根据《语类》中朱子的发言,福田氏指出:朱子认为子孙的身上延续了祖先之气,通过祭祀,子孙身上的祖先之气便会伸长,而随祭祀感格的祖考之精神,存在于祭祀者自身的精神之中。即不同于过去将朱子所说“祭祀感格”理解为物理现象,福田氏将之理解为祭祀者心中的问题。于是,福田氏认为“祭祀感格”说是在可以合理认识的“知”的世界和宗教的“信”的世界并存的状态下成立的。
以上介绍了本书与朱子直接相关的论文。正如上述,本书著者福田殖师事楠本正继和冈田武彦,在具有浓郁的九州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特色的学风中形成自己的学问体系。九州大学的宋明理学研究,并不单是理论分析、文献考证,而且还有尊重体悟的传统。作者认为“道学诗”是对修养者心理状态的表现的观点,以及从祭祀者的心理问题的角度重新理解祭祀感格说等,都充分发挥了九州大学宋明理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另外,文末附载疋田启佑《福田殖先生の学問》一文,对本书各篇的内容做了扼要介绍,可参考。
与本书同时出版的《日本と朝鮮の朱子学》(《福田殖著作集Ⅱ》)分本篇和附篇。本篇讨论了李退溪等朝鲜儒者[4]和楠本硕水、楠本端山及大桥讷庵等日本儒者[5]的思想。附篇收录了作者撰写的介绍老师辈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先生之学问的文章。因为该书讨论的是关于日本朱子学研究和朝鲜朱子学研究的内容,不属于本文介绍的范围,故在此只提供书讯,请读者一并参考。
2.川原秀城[6]主编:《朝鮮朝後期の社会と思想》,勉诚出版,2015年2月。
《朱子学年鉴》设立了韩国学界的朱子学研究和日本学界的朱子学研究的项目,但关于日本学界的朝鲜朱子学研究则付诸阙如[7]。虽然本文并无义务介绍日本学界的朝鲜朱子学研究,还是深感有责任对此稍作介绍。
本书编者川原秀城,是当今日本学界朝鲜朱子学研究的第一人。本书收录九篇论文,皆由活跃于第一线的学者撰写,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角度,考察伴随1592年丰臣秀吉的入侵(“倭乱”),1627年、1636年满清的两次入侵(“胡乱”)带来巨大变动的朝鲜后期社会。其中,与朝鲜朱子学直接与关的论文有吉田光男[8 ]《士林派と士禍言説の成立》、川原秀城《宋時烈の朱子学——朝鮮朝前中期学術の集大成》。
二、论文
1.种村和史:《継承と刷新:宋代詩経学の理念と方法》,庆应义塾大学日吉纪要《中国研究》第九号,2016年3月。[9]
种村和史氏长期致力于宋代《诗经》学的研究,本《年鉴》也曾多次对其研究加以介绍。本文是种村氏对自己历年发表的21篇研究论文的总结性论述。
作者的具体考察和论证,请直接参考该文末尾所附目录揭载的论文。在此仅介绍作者关于《诗经》学研究的整体观点。
在本论开头,作者概述了自己迄今为止研究宋代《诗经》学的目的所在。
一直以来,笔者都以阐明如下问题为目标开展研究:宋代《诗经》学者继承了前代《诗经》学的哪些方面,又出现哪些新变,与此同时,他们是如何建立自身解释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又是由怎样的学问理念作为支撑,在中国古代《诗经》学史上占据怎样的位置。
种村氏对自己的研究目的做了如上说明,该文主要讨论以下三点。(与下述三章对应)
(1)经过对代表性的《诗经》注释书的分析确定宋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其与各时代《诗经》学的关系。
(2)作为《诗经》解释方法论基础的认识。
(3)儒学的道德观及时代状况在《诗经》解释中的反映。
在第一章《刷新が内包する継承、継承から生まれ出る刷新》中,种村氏总结了自己对欧阳修《诗本义》、王安石《诗经新义》、苏辙《诗集传》、程颐《诗说》等北宋《诗经》学代表性著作的研究。
首先,种村氏指出,这些著作都受到《毛诗正义》影响,并且相当重要。比如欧阳修《诗本义》经说的确立,《毛诗正义》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关于《诗经》的比喻,欧阳修认为“古之诗人取物比兴,但取其一义以喻意尔”(《诗本义》卷二《鹊巢》)、“诗人引类比物、长于譬喻”(《诗本义》卷五《破斧》)[110种村氏认为,这两点分别是在《毛诗正义》“兴者,取于一象”(《国风·周南·兔罝》),“兴必以类”(《国风·召南·击鼓》)之说的基础上加以展开的。作者更认为,欧阳修对《毛诗正义》中仅仅针对个别的解释加以融会贯通,扩大到《诗经》整体的解释中。此外,认为朱子的“淫诗说”导源于欧阳修的“准淫诗说”,而欧阳修的“准淫诗说”实际上在《毛诗正义》已有先例。过去单纯强调《毛诗正义》是宋代学者批判和超越的对象,而作者提示我们《毛诗正义》也为宋代学者的解释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可以说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其次,在第二章《宋代詩経学の解釈理念と方法》中,种村氏提出以下三个术语突显宋代《诗经》学的特征。
一是“泛论”“泛言”。将诗篇的一部分,解释为体现了全诗的整体意义或者普遍教训的内容,以“泛论”“泛言”解之。这样的方法不见于《毛诗正义》,而见于欧阳修的《诗本义》,此后在其他注释书中也有所体现。
二是“假设”“设言”。认为诗篇的一部分,并非如实记录事实,而是诗作者的虚构,以“假设”“设言”解之。这类方法不见于毛传、郑笺,而见于《毛诗正义》。朱子《诗集传》中有所使用,此后学者也经常使用。
三是“思古伤今”“陈古刺今”。这类概念本身已出现于《诗序》,自然毛传、郑笺、《毛诗正义》也继承了这一解释角度。宋代解释的特色是,譬如王安石认为,诗中歌咏勾起对古代回忆的现在的部分,和歌咏想象的古代的部分两个不同的时间层同时存在。
通过以上的考察,种村氏指出,宋代《诗经》学者的解释立足于这一前提:诗作者秉持明确的意识,综合虚构和现实、过去和现在的不同维度、层次的事件,加以组织创作。
在第三章解釈における道徳的•政治的意図と文学的意図との不可分性》中,作者指出宋代《诗经》解释中强烈反映了当时形成的道德价值观。比如,对于生逢乱世深陷不幸生活中的民众离开父母之邦移居他国的行为,汉唐《诗经》学采取有条件地认可的解释。但是在宋代,这些行为都是忌讳,因而尽量不将有关诗句解读为离开父母之邦移居他国。这是被周边强大的异民族国家所包围的宋朝的历史状况所需要的伦理观,在《诗经》解释上的反映。另外,宋朝的《诗经》解释,有排除讽刺前代君主行为——“追刺”的倾向。这一倾向反映了在宋代自由批判政治受到限制的事实。
通过以上的分析,种村氏认为,宋代《诗经》学根本上共通的学问倾向,一言以蔽之,是将阐明诗篇的构造和追究其逻辑性融合为一。
目前为止的宋代《诗经》学研究,重在阐明个别著作的特色。种村氏的研究,则是在考察各书特性的基础上,将这些特性作为理解宋代《诗经》学整体的指标,通过分析这些指标,以期勾勒宋代《诗经》学共通的特征,明确宋代《诗经》学的特色和倾向。
2.吾妻重二:《〈家礼〉の和刻本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9号,2016年3月。[11]
《朱子家礼》作为士庶人家举行冠、婚、丧、祭之礼的指南,在东亚世界有着广泛影响。日本江户时代也出版了大量的和刻本,其影响可见一斑。吾妻氏在本文中,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日本现存的和刻《朱子家礼》诸本做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根据吾妻氏的调查,《朱子家礼》的和刻本至少有以下四种:浅见䌹斋点《家礼》五卷、图一卷,《文公家礼仪节》八卷,小出永安点《新刻性理大全》家礼部分四卷,《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家礼部分二卷。该文以前三种和刻本为对象,讨论了各自的成立、特色及所据底本。以下略述吾妻氏此文的要点。
(1)浅见䌹斋点《家礼》五卷[12]
作者指出,《朱子家礼》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1)周复五卷本系统有:宋版、公善堂覆宋本、明版、《四库全书》本、郭嵩涛本;2)《性理大全》系统有:纂图互注本、《朱子成书》本、《性理大全》本、和刻本。浅见䌹斋校点本(和刻本)虽为五卷本,但从文本内容来看,属于《性理大全》本系统。然而,除了和刻本,《性理大全》本系统中并无其他版本为五卷本。此外,朝鲜本有四卷本、七卷本而无五卷本。因此,浅见校点本当是以《性理大全》本《朱子家礼》为底本,重新编辑分卷,试图复原《朱子家礼》原本五卷的形态。[13
(2)和刻《文公家礼仪节》本
明成化间邱濬从便于理解和实际行礼出发,改编《朱子家礼》,成《文公家礼仪节》八卷。《仪节》在明代非常流行,陆续出现各种重辑、重订之本。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由京都大和田九左卫门刊刻于万治二年(1659),底本并非邱濬原本,而是杨慎手定、种秀堂藏版的崇祯刊本,因而文字内容也与邱濬原本不尽相同。
(3)和刻《新刻性理大全》本(小出永安点)
胡广、杨荣等奉敕编纂的《性理大全》七十卷为永乐“三大全”之一,1415年编成后,由内府刊刻颁行天下。其中,卷十八至二十一收录《朱子家礼》。正德年间,坊刻《性理群书大全》(一题《性理群书集览》)七十卷附载玉峰道人所撰“集览”。同时,又出现附载周礼所撰“补注”之本。明中期以降,《性理大全》更出现各式各样的增注本,版本情况相当复杂。[14]
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七十卷,由京都的田中清左卫门和小嶋弥左卫门刊于承应二年(1653),小出永安为之校点。和刻本附载了《性理大全》原本没有的“集览”和“补注”。作者认为,和刻本的底本虽难以确指,但可以推测其祖本为嘉靖三十九年(1560)进贤堂刊《新刊性理大全》本(内阁文库藏本),其底本当为该系统之版本。
吾妻氏长期关注《家礼》的文献学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部分成果可参考《朱子〈家礼〉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近年,吾妻氏致力于搜集整理日本的《家礼》相关文献,以《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之名影印出版,并附《解说》。2010年出版第一辑,2016年出版至第六辑,该辑收录了以上三种和刻本。本文也是作者在第六辑《解说》的基础上增订而成。
3.松野敏之[15]:《宋代訓蒙書と朱熹〈小学〉》,《国学院杂志》第117卷第11号,2016年11月。
在朱子《小学》以前,已经出现了不少以童蒙教育为目的而编纂的训蒙书。朱子编《小学》[16]曾经参考过的就有吕本中《童蒙训》、吕祖谦《少仪外传》等。朱子的《小学》正是以此前积累下来的训蒙书为基础编纂成书的。松野氏此文,首先概述了朱子编《小学》参考过的训蒙书,其次分析朱子如何引用这些文献据以编成《小学》,从而明确《小学》的特征。
松野氏指出,《少仪外传》等《小学》以前的训蒙书,是根据所引用书的不同编排叙述,而《小学》则是立“立教”“明伦”“敬身”等门目,根据内容的不同分类叙述。与此同时,朱子也留意各个门类篇幅的平衡,务必网罗人事的方方面面。松野氏认为,以上这些编纂《小学》的考虑,与朱子把《小学》当作大学的预备阶段看待密切相关。就朱子学而论,研读以四书为代表的经书是要探索“事之理”,《小学》的目的则是提示“格物”和“敬”的对象——“事”的具体内容。
过去大多将《小学》置于朱子学的框架内理解,松野氏从“训蒙书”这一角度,通过与宋代其他训蒙书的比较,明确朱子在《小学》编纂上的思考,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察《小学》在朱子学中的意义。
三、译著
1.绪方賢一、白井顺:《朱子語類訳注》卷98~100,汲古书院,2016年12月。
日本中国学界立志通过合作共同将《朱子语类》140卷全部翻译成现代日语,并做校订、注释。2007年出版了第一册(卷1~3)译注,至2016年共出版十三册。本年出版的三卷译注,其中卷九十八、九十九为《张子之书一·二》,卷一百为《邵子之书》。
2.李退溪著、难波征男校注:《自省録》,平凡社《東洋文庫》,2015年10月。
朝鲜大儒李退溪从近200通与弟子、友人的书信中,择取22篇,编定成册,以为自省之用,故名《自省录》。本书即为《自省录》的日文译注本,卷末附难波氏所撰解说《李退渓の〈自省録〉と東アジア体認学》。
四、总结和展望
2016年狭义的朱子学的研究并不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学界的朱子学研究停滞不前,而是因为学者对宋学的关心由朱子本人扩展至与朱子有关的其他思想家。正如后附《2016年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书目》所载,有不少学者将视野聚焦于陆九渊、杨万里等与朱子同时代的思想家。在日本学界的宋学研究者中,如土田健次郎、小岛毅等并不以朱子为宋学的中心,而是将朱子相对化,认为朱子只是此一历史时期活跃的思想家之一。可以预期的是,今后在此立场上开展宋学研究或成为一种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介绍的川原秀城主編《朝鮮朝後期の社会と思想》和难波征男译注《自省录》二书皆出版于2015年,因笔者的疏忽,未能及时予以介绍,敬祈读者海涵。
(作者单位: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译者单位: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
2016年美国朱子学研究综述
⊙戚轩铭
2016年美国有关朱熹的研究成果似乎较过去数年有所逊色。尽管如此,其中亦有可兹报告者。根据笔者所收集到的文章,本文将简述美国学者对于朱熹的研究,或是在美国出版的有关朱熹的研究。
首先介绍田浩教授(Hoyt Cleveland Tillman)2016年一年的研究。笔者于2016年曾提到田浩教授曾在2015年11月到台湾政治大学做演讲,其中两场的主题都与朱子学有关。(第二场《朱熹“淫祠”祈雨文的分析及其深义》的内容与田浩教授和陈曦教授的文章重复)[1 ]讲座完结后不久,政治大学便将有关讲座内容制作成书。[2]由于笔者在2016年的报告中只十分简略地提及有关讲座的主题,故这里将对最后讲座的内容——《朱熹对“夷”的看法及其价值观的普世意义》做更详细的描述。
田浩教授这次演讲的内容大致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先对宋代道学家有关华夷之别的问题进行分析。他以2014年杨劭允博士撰写的博士论文为中心展关讨论。[3]田浩教授指出,杨劭允的论文主要批评了列文森(JosephLevenson)和他对于道学群体有关夷狄的观点。根据田浩教授的说法,杨氏认为他们太着重以“文化”来说明当时的华夷之辩。但是,杨氏认为宋人是将夷狄视为一种“不道德的、在思想上属于异端的以及不合乎礼仪的状态。”[4]田浩教授却认为杨劭允博士是以当代对于文化的标准来理解宋人的。事实上,根据田浩教授的解释,杨劭允博士上述所提到的三个标准正是朱熹和其他宋代人对于“文化”的理解。[5]由杨劭允博士的论文,田浩教授将演讲的重心转到对当代中国有关普世价值发展的讨论上。田浩教授以《朱子家训》在21世纪的发展为例,说明了中国对于普世价值态度的转变。他认为在21世纪之初,中国政府留下空间予人讨论《朱子家训》对中国国家建设的好处和普世意义。但是自2012年后,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国内开始对普世价值进行批评。宣扬普世价值变得困难,因为国内学者认为普世价值便是欧美价值。田浩教授认为如有文化自信,不必怕讨论普世价值,因为它必然会受到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学者在面对普世价值的问题时,应保持开放性,并包容各种文化。田浩教授向来都十分关注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代的影响。他在2016年12月曾到香港进行两场名为“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活动。第一场演讲的题目便是《在应对危机中不断发展单一行政权力:“9·11”之后一个美国人思考中国政治制度的皇权》。由于讲座主题与朱子学的研究关系不大,故这里不再详述。但从中我们亦可看出田浩教授的学术旨趣。
顺带一提,田浩教授于2012年与德国学者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合撰的专著《宋金元代文化权威与政治文化》(CulturalAuthorityandPoliticalCultureinChina:Exploring Lssues withthe Zhongyongand the Daotong during the Song,Jinand YuanDynasties)现正筹备翻译成中文版,有进一步消息将会在未来向各位报告。
除了田浩教授的研究外,美国著名的学术期刊《东西哲学》(PhilosophyoEastandWest)刊登了郑淑红教授一篇名为《朱熹与埃克哈特大师的智慧和意志》(LntellectandWillinZhuXi and MeisterEckhart)的文章。[6]虽然论文作者现执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由于论文发表于美国的期刊之中,故笔者在撰写这份报告时决定一并收录,供有兴趣的学者参考。郑教授的论文指出在新儒家中出现了两个门派,分别是理学和心学。同样的,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亦有方济各会(Franciscan)和道明会(Dominican)。作者因此认为比较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与作为道明会一员的埃克哈特大师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解远东和西方拉丁世界思想发展的分别的门钥。根据郑氏的分析,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人的智慧(知)往往具有最关键的作用,它一方面决定人的行为,同一时间比人的意志更为重要。有趣的是,朱熹在讨论“知”时往往是提及它的作用,而不是用它来从生理上定义人类。换言之,朱熹本人的思想与儒家强调人的道德自觉的传统是相符合的。作者认为,朱熹的目的是要突出儒家的价值并以此在三个方面:个人精神自觉(personal spiritual awareness)、社会责任(socialaccountability)以及超验的重要性(transcendent signiffcance)压倒道教和佛教在当时的影响,并因此而提到他对“理”的解释,即宇宙的本源与永恒的真理。必须申明的是,尽管朱熹认为“理”的重要性是超验的,但他不认为“理”存在于一个与现实世界分割的空间之中。同时,朱熹对于人的“知”的重视并不代表他据此认为人类的价值比其他生物高。他之所以强调“知”,是因为它可作为儒家自我修养的出发点。作者因此认为,朱熹有关“知”的论述只是为儒家的自我修养提供一个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基础。
另外,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亦出版了一部由David Edward Jones与HeJinli合编,并收录中西学界有关朱子学研究的论文集,名为《回到朱熹:太极所呈现的模式》(Returning to ZhuXi:EmergingPatterns withinthe SupremePolarity)。[7]这部论文集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对朱熹的诠释”(Interpreting with Zhu Xi)共收入四篇论文,分别为张立文的《朱熹的形而上学》(ZhuXi'S Metaphysics)、艾周思(Joseph A.Adler)的《论〈太极〉的翻译》(OnTranslatingTaiji)、陈来的《〈朱熹中庸章句〉中的儒家思想》(ZhuXi'j ConfucianThoughts onthe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fthe Zhongyong)及金永植的《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的事物:对儒家学说界线所作的定义与扩充》(ZhuXi onScientificand Occult Subjects:Definingand Extending the BoundariesofConfucianLearning)。第二部分为“通过朱熹而思”(Thinking through ZhuXi),其中收入了三篇论文。分别是Kirill O.Thompson的《朱熹思想中的对立与互补》(Oppositionand Complementarity inZhuXi's THought)、刘述先的《论朱熹心灵世界的建构》(Onthe FormationofZhuXi’s SpiritualWorld)和EihoBaba的《理作为气的呈现方式:一个非还原性的诠释》(Lias Emergent PatternsofQi:ANonreductiveLnterpretation)。第三部分“应用朱熹的思想”(ApplyingZhu Xi)则共有五篇论文。它们分别是John Berthrong的《波士顿的道学:现代对朱熹哲学思想的转化》(BostonDaoxue:AModernTranspositionoZhuXi'sPhilosophicalVision)、Stephen C.Angle的《朱熹的道德伦理与胡果·格老秀斯的挑战》(ZhuXi's Virtue Ethicsand the GrotianChallenge)、蒙培元的《如何统一所以然与所当然?一个对朱子著作的解释》(How to UniteIsand Ought:AnExplanationRegarding theWorkofMa ster Zhu)、Kwong-loi Shun的《论愤怒:儒家的道德心理学》(OnAnger:AnEssay onConfucian MoralPsychology)以及彭国翔的《心理与肉体的修炼:朱子读书法在宗教上的意义》(SpiritualandBodily Exercise:The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ZhuXi's Reading Methods)。据编者所言,朱熹作为一位“集大成”者,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部文集所收录的论文,正是希望在西方哲学世界的想象底下探讨朱熹别树一帜的思想。
在学位论文方面,Wong Pui Fong博士在2016年以《从独处到走进群体:新儒家在自我转化的问题上对归心祈祷的运用》(FromSolitude to Solidarity:ANeo-ConfucianAppropriationofCentering Prayer intheTranSformationofSelf)一文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神学院得到博士学位。8]这篇论文旨在探讨汤玛斯·基廷(Thomas Keating)有关归心祈祷的学说如何为朱熹有关静坐的学说和宇宙论所支持与扩充。她认为朱熹有关宇宙论的三个概念:气与理作为宇宙的两个基本单位;动与静是宇宙运行的方式;以及两极与中庸是维持宇宙和平与创造的基本法则启发了人们对于基督教的人论(Christian anthropology)与沉思的研究。基于Sandra Schneiders与Francis Clooney有关比较神学的理论,作者认为朱熹所提倡的“静坐”这门工夫是必需的,因为人可以通过静与终极的道产生联系。通过近代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作者认为Mindfulness(笔者并未能为这个名词提供一个准确的翻译,为免误导读者,故选择只引用英文原文)在西方社会渐渐成为达到幸福的途径。这亦间接为朱熹与汤玛斯·基廷的学说提供证据。作者期望,她这篇论文能令学界对基督教中沉思的价值和作用有更深入的认识。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走向世界与未来的朱子学研究
⊙赵金刚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致广大而尽精微”“综罗百代”,深刻影响着南宋以后的中国思想世界,对东亚世界产生了持续影响。近年来,“朱子学”一直是中国思想研究的重要领域,对朱子学的研究涉及哲学、文献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诸多学术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也不断扩展。以中华朱子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下二级分会)和朱子学会(一级学会,挂靠厦门大学)作为支撑,关于朱子学的研究稳步推进,厦门大学国学院、上饶师院等学术机构还联合成立了“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朱子学会专门设立《朱子学年鉴》编委会[1],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同时日韩欧美等学者对于朱子学也十分关注,有关朱子学的国际学术交流十分活跃,几乎每年都有关于朱子学的国际会议在全球各地召开,海外学者关于朱子学研究的著作也层出不穷,“朱子学研究的全球化早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2]。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已有学者试图以朱子学为思想资源,尝试将朱子学与中国当下具体问题以及全球化问题结合,处理具体的时代问题;还有学者从朱子学出发,努力建构新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可以说,朱子学研究一方面已经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哲学界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一个典范,而另一方面,朱子学已经走向了未来,为新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
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具体总结和分析朱子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以及新的研究趋势。
一、文献整理与出版
中国哲学研究的推进与对原始文献材料的解读息息相关,相关文献的结集与新材料的发现往往会促进某些领域的发展。朱子学的稳步发展,与朱子学文献的整理关系也十分密切。经过多年的整理,朱子著作较为全面地出现在世人面前,为学者研究朱子学提供了有力支持。这里首先要提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历时十年整理编辑了《朱子全书》[3]及《朱子全书外编》[4],基本上收录了朱熹所有的文献资料,并对相关逸文进行收集辨析,为学者研究朱子思想提供了重要支撑。除了对相关文献进行点校之外,《朱子著述宋刻集成》[5]等原始文献也影印出版,为学者探究朱子著述的原貌提供了方便。
除了集中整理朱子著作,有关朱子单个著作的整理与出版成果也较为突出,这首先体现在对《朱子语类》的进一步研究与整理上关于《朱子语类》在研究朱子思想中的作用,历史上争议较大。朱子的弟子在《语类》最早整理出版后就有分歧,如黄榦就曾说过:“语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而李心传则与黄榦的态度相反,认为朱子去世之后,如果学者审慎地使用《语类》的话,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他的思想。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清代,如王懋竑就认为《语类》中不可信的部分颇多,而同时代的朱止泉却极为重视《语类》。今天对于《语类》的作用,还有学者存在不同看法。但正如邓艾民先生指出的,如果能对《语类》分析应用,《语类》的价值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语录中有些晚年的思想,纠正他早期著作中某些意见,更可看出语录的价值。何况,语录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他的文集中有叙述简略甚至完全阙如的,语录的重要性就更明显”。[6]邓先生指出的“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理气”问题,《文集》等其他材料,在很多点上只有“孤证”,必须借助《语类》才能进一步研究。《语类》的意义不能否认,但《语类》的问题毕竟也很多,尤其是在后世传刻过程中导致了一些新的问题。“分析应用”《语类》,首先需要对《语类》的版本有细致的校勘。这一工作,可以说无论是中华书局点校本《朱子语类》还是华师大古籍所《朱子全书》本《朱子语类》,都做得不尽人意。因此对《朱子语类》展开细致的文献研究,可以说是近些年朱子学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
现存最早的《朱子语类》版本为日本九州大学所藏《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与黎靖德本《朱子语类》规模相当,分卷基本一致,仅卷一百零一、卷一百零三、卷一百三十八、卷一百三十九与卷一百四十互有错杂。然而《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中却又有许多黎靖德本《朱子语类》中没有的重要内容,如《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有而黎靖德本《朱子语类》无的朱子语录,朝鲜古写本和黎靖德本都有、而朝鲜古写本更详细的朱子语录,还有淳祐十一年(1251)吕年为《徽州刊朱子语类》所作的序,以及宝祐二年(1254)魏克愚为《徽州刊朱子语类》再校正本所作的按语、跋等。”然而中华书局以及《朱子全书》点校本均未参考这一版本。胡秀娟博士的博士论文则关注了《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研究》[7]一书,该书通过对比《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与黎靖德本《朱子语类》,辑录了大量朝鲜古写本有而黎靖德本无的《朱子语录》和朝鲜古写本详细而黎靖德本简略的《朱子语录》,还整理出朝鲜古写本和黎靖德本有所差异的字、词、句。于此前后,徐时仪、杨艳两位学者出版了《朱子语类汇校》[8]一书,以徽州本为底本,汇校成化本等诸本,将成化本无而底本有、底本有而成化本无,以及二本皆有而顺序不同者一一校出。朱杰人教授还在与胡秀娟博士合作,希望在版本校勘上更进一步,出版《〈朱子语类〉合刊本》,我们可以期待这一著作的问世。可以说,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徽州本与其他版本《朱子语类》的差异基本上已经呈现在今人面前,为对朱子思想进一步的哲学上的探究提供了较好的文本支持。
除《朱子语类》在文献上的研究获得进展外,《仪礼经传通解》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朱子晚年的学术重点之一就是编著《仪礼经传通解》,但朱子生前并未完成此书,其弟子黄榦续撰《丧礼》《祭礼》,但是《祭礼》仅写成草稿,杨复经数十年整理、编辑最终成书。经由杨复完成的《仪礼经传通解》在当时影响颇大,可惜后来失传,明清学者已不能得见。至清末陆心源复得此书,但藏本后归日本静嘉堂,静嘉堂非秘不示人,而一百年来未有学者前往阅读。桥本秀美和叶纯芳于静嘉堂阅读此书,历时三月抄写全书,并花费两年时间整理,最终出版了《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9]一书,使杨复所续编《祭礼》得以示人。不仅如此,二人后又影印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藏宋刻本《仪礼经传通解》,并用元明善本补全阙文,成《影印宋刊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10]一书,为进一步研究朱子礼学提供了版本依据。
朱子礼学另一重要著作为《朱子家礼》,然而关于此书的真伪历代聚讼纷纭,至今还有学者怀疑此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出版了《朱熹〈家礼〉实证研究》[1]一书,一方面汇集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家礼》非伪,同时从朱熹弟子著作和后世藏书家藏书目录来理清《家礼》版本的发展演变,把《家礼》版本分为原稿本、宋刻本、元刻本,揭示《家礼》宋元版本系统;一方面把朱熹《家礼》放在朱熹家礼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演变历程中加以考察,通过对《家礼》思想内容的考察,来阐释朱熹博采古今众家的礼学特点,并结合晚年的礼学著作和语录来探讨其礼学思想的变化发展。吴震先生以为,“本书研究在考证上有重要创获。我们知道,朱熹《家礼》自清代王懋竑提出‘伪作说’并得到《四库全书》编撰者的认同以来,几成‘定说’。虽然在此之前已有学者隐隐约约地表示怀疑《家礼》可能并非朱熹亲撰,如元代‘武林应氏’(经作者考证,即钱塘应本),但对此进行所谓严密考证的无疑是王懋竑。当然,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的学者对此‘伪作说’屡有质疑并提出了种种反驳,但是从文献考证上全面推翻王懋竑的‘伪作说’,认定《家礼》为朱熹亲作,唯有通过作者的本书研究才最终得以确立。因此,可以说作者的这项研究工作既具有颠覆性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作者的研究结论使得《家礼》得以名至实归——重新归入朱熹名下,而且这一研究结论亦完全有可能成为此后学界可以信从的‘定说’”[12]。
关于朱子后学的文献整理与出版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朱子后学继承朱子学术,对很多问题有重要的推进。但相比于对朱子本人的研究,对朱子后学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尤其是对比阳明后学已经研究到四代五代的情况,这一点尤为明显。文献的匮乏是朱子后学研究薄弱的一项重要原因。南昌大学承担了“朱子门人后学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旨在推进朱子后学的相关研究,而文献整理则是这一项目要做的第一步,目前黄幹、辅广、饶鲁等朱子重要门人的资料辑佚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相信这一工程势必会推动朱子后学的相关研究,对朱子学相关哲学问题有进一步的推进。
二、哲学问题的深入拓展
在中国哲学界,朱子学的研究一直以来比较活跃,每一段时期都会有新的成果产生,关注的问题域也不断扩展。朱子学的研究首先与研究典范的确立关系密切。
在大陆学界,冯友兰、张岱年等老一代学者都十分重视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学界流行“范畴”研究,对理学相关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做了细致的分析,陈来先生《朱子书信编年考》和《朱子哲学研究》二书更是确立了朱子研究的典范。《朱子书信编年考》把朱子近两千封信做了一个时间的编排,特别有助于学者从发展的观点看待朱子思想的演进,而《朱子哲学研究》则将其成果应用到具体的哲学分析上,并采取“概念分析法”系统地研究朱子哲学的基本范畴、概念与问题。陈来先生将朱子哲学总结为“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已发未发、心统性情、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主敬与涵养、格物穷理、道心人心、知行先后”等十个基本哲学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确立了方向。
在港台学界,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等先生也都十分重视朱子学。牟宗三有《心体与性体》一书,将伊川与朱子视为一系,侧重于朱子对中和问题、心性情问题、理气问题、《仁说》问题的阐释,并从早中晚三期观察朱子思想的演进。牟宗三先生的研究深刻影响了港台学界对朱子哲学的一般看法,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牟派学者基本上沿着其基本理解对朱子哲学进行阐释。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则与牟宗三的朱子学研究不甚相同,他主要类集朱子思想言论,又按数十个条目分门别类,以钱穆先生自己的观点将朱子思想构造成一个体系。《朱子新学案》不仅涉及朱子哲学思想,还旁涉经学、史学、文学,全方面评述朱子与其他思想家或思想体系的关系,可以说是关于朱子研究一个较为全面的著作。
海外朱子学开展较早,这以陈荣捷先生为代表,“1946年H.F.MacNair在柏克莱出版的英文《中国》一书中即有陈荣捷所写的‘新儒学’一章,这是战后西方叙述理学专篇之始,也是叙述朱子思想专篇之始”[113,之后陈先生发表了一系列与朱子学有关的论文。60~80岁之间,陈先生开始专注于朱子学研究,并将《近思录》(1967年)翻译成英文。陈荣捷先生的学术贡献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欧美学界关于朱子学的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一定时期内,中国与欧美的朱子学研究交流甚少,1982年陈荣捷先生在檀香山组织“国际朱熹会议”之后,大陆与其他区域的朱子学交流日益增多,最近数年则更加频繁,学者的研究能够集各方之长,诸多问题的研究实现突破,哲学问题的辨析度越来越深入,领域也由存有论逐步扩展到朱子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生态哲学等方向。下面,我们集中叙述近些年在朱子学哲学层面上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
理气论是朱子哲学存有论最基础的命题。近年来,学者在相关问题上进一步细化。2011年,藤井伦明教授出版《朱熹思想结构探索——以“理”为考察中心》[14]一书,围绕着“理”“诚”“知”“心”等概念,从朱子文本出发,详细考察朱子的思想结构。在作者看来,“朱熹思想世界之样貌,其显然并非一以外在‘静态式’之‘理’为基础而建构出的思想;而是一以内在‘动态式’之‘理’为基础而开展出的思想。也就是说,对朱熹而言,这世界的所有自然现象以及道德行为,原原本本系内在之‘理’活泼地发露、开展,而且朱熹思想的存在论、心性论、工夫论等,无一不是以此一动态式之‘理’为基础而建构出的”。这就与以往牟宗三先生将朱子的理理解为“只存有,不活动”的观点不同了。乔清举教授《论朱子的理气动静》[15]一文亦可以看作是对牟宗三先生观点的一种回应,文章区分形上之动静与形下之动静,认为朱子的理在形上层面还是“动”的,这种动与理的“兼”“有”“涵”“该贯”等说法有关,表现在理之主宰作用、理生气等层面,最终是理的自我实现。杨立华教授《体用与阴阳:朱子〈太极图说解〉的本体论建构》[16]则从《太极图说解》出发,诠释朱子思想中的理气关系,文章认为“朱子在《太极图说解》中确立的本体论架构,是他的中岁定法,之后始终没有改变。太极是理,是体,而非用。朱子有时讲太极之体用,只是理论表述上的不得已。‘阳之动’对应的是用,而‘阴之静’对应的是体。朱子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立言角度的不同。‘体用一源’从理上说,理虽是形而上者,但其中已有万象;‘显微无间’从象上说,至著之象虽然是形而下者,但理即寓于其中。‘体立而后用行’,体非独立之体,体自有象;用则是体之发用,体在其中。义智为体、仁礼为用。太极作为理,‘不离于形’,也‘不囿于形’,太极有动静。理无造作,但理必有气,气自然能凝结创造;理无动静,但既有理,便有气、有象,便有动静”。这一论断突出了《太极图说解》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丁为祥教授《从生存基础到力动之源——朱子哲学中的“气”论思想》[17]则专门讨论了朱子对气的论述,文章认为“从理气关系的角度看,气始终充当着一切存在之前提基础的作用;而从生物之具到人的生存基础,就是朱子哲学中的气在宇宙天道与人生世界中的两种不同的表现。但无论是生物之具还是生存基础抑或是宇宙发展的力动之源,气既是作为所有存在之前提基础出现的,同时也代表着人所必须超越、驾驭与主宰的对象;而从生存基础到力动之源,则充分展现了从自然到天性这一人既生存其中,同时又不得不时时面对的世界”。文章揭示出的气在朱子思想中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
鬼神观可以说是近些年朱子理气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吴震教授《鬼神以祭祀而言——关于朱子鬼神观的若干问题》[18]一文,从祭祀的角度考虑朱子的鬼神观,文章通过对朱熹“以气释鬼神”“鬼神以祭祀而言”的诠释方式以及“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等观点的深入探讨,指出对朱熹而言,鬼神问题主要是祭祀的问题而不是言说的问题、是宗教的问题而不是气学的问题。朱熹在鬼神问题上强调祭祀实践的重要性,这是朱熹宗教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朱熹对儒学鬼神论的一大理论贡献。冯兵教授《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朱熹的鬼神观辨析》[19]也关注了朱子鬼神观与礼学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鬼神‘实有’,源于理气的共同作用;出于‘正理’的鬼神‘无形与声’,而‘非理之常’的鬼怪却有可见之‘形质’;鬼神思想是构成礼学的重要部分,鬼神与礼乐有着内在相通性。朱熹对鬼神的讨论,主体上是一种哲学化的鬼神观,但十分复杂,它既有较强的理性主义精神,又受到了世俗的鬼神迷信及佛道二教的影响,从而染上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可视为传统儒家鬼神观念的一个代表,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王文娟博士《朱熹论感应》[20]一文,则关注了感应与鬼神的关系,认为“祭祀中‘感应’之理的运用既反映了民众在世俗生活中的精神诉求,又体现出一种对生命本源的敬畏感与归属感。此外,与感应相结合的劝善言论在具有政治和伦理双重导向的同时,也体现出不同于世俗功利导向的理性精神”。
在心性论上,“人心道心”问题,“明德”问题依旧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而朱子的仁学也逐渐成为这几年研究的一个重点。魏义霞博士《朱熹对仁的诠释》[21]一文,认为“通过对仁的诠释,朱熹建构了本体、道德、工夫三位一体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赖尚清博士《朱子早期仁论思想研究》[22]以《延平答问》为中心,认为“李侗和朱子师弟子之间主要从理、心、未发与已发、理一分殊等方面展开对仁的讨论,从中可以看到朱子早期仁论的特点以及之后仁论思想的各种萌芽”。此外,向世陵教授《“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23]则详细考察了朱子对“性”的论述,文章认为“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性即理’的构架不仅在说明人性即天理,同时也通过‘所谓理,性是也’的反向路径,使实理在实性的基础上真正得以落实”。吴震教授《朱子“心论”试析》[24]一文,则关注对朱子“心”的研究,认为“朱熹‘心论’的基本义有二:知觉义和主宰义。其‘心论’的基本立场是:不能承认‘心’为形上本体。由其“‘心’字只一个字母”以观,‘心’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存在,故其主宰义就不免落空;由其‘心是做工夫处’之命题来看,‘心’是工夫的对象而非工夫之主脑。总之,在朱熹哲学的系统中,‘心’不是本体论问题而是工:夫论问题”。
工夫论是近些年朱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学者们从多角度关注这一问题。如吴震教授近些年持续关注朱子的工夫论,关注朱子对“敬”的论述(《敬只是此心自作主宰处——关于朱熹“敬论”的几个问题》[25]),以及“格物致知”等问题(《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26]),而《从政治文化角度看道学工夫论之特色——有关朱熹工夫论思想的一项新了解》[27]一文则转换研究思路,“从朱熹亲身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这一独特视角出发,来尝试式了解朱熹为何强调‘吾平生所学’只有正心诚意‘四字’这一十分醒目而前人未免有所忽略的重要观点”,“当我们将审视问题的角度转向政治文化层面,却发现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在面对君主进行思想劝说之时,他们劝导君主实践的第一序工夫往往不是格物致知而恰恰是诚意正心,至于外在事功则可以随着正心诚意的完成而得以实现”。李承贵教授《对道德与知识的双重关切——朱熹“格物致知论”探微》[28]一文认为在朱子那里,“格物致知”是具有“理想性”的范畴,就是要求全面地“穷理”、全面地“普知”。朱熹观念中的“格物”与“致知”关系可以表述为:“格物”与“致知”的任务并不相同,但它们是一件事的两面,即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格物”是获得事物之“理”(知识)的过程,“致知”是将所获知识推演、应用的过程,“格物”是感性的、具体的、归纳的,“致知”是理性的、抽象的、演绎的、实践的,因而它们关系的最高境界当然是“一”。李敬峰、刘俊《朱子的格物致知:一种可能的科技理性》[29]一文则从更为现代的角度关注朱子的工夫问题,对格物致知“从诠释的转向、认知的指向和范式转换三个角度予以重新观照,认为朱子的‘格物致知’主观意愿指向人文伦理,而客观上却走向科技理性”。还须指出的是,这些年对朱子哲学很多问题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都和朱子的工夫论有关,比如杨祖汉教授所做朱子和康德的比较,前述吴震教授对“心”的研究,藤井伦明、乔清举等教授对理的诠释,这些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对朱子工夫论、道德哲学上“实践动力”来源的思考。
除上述三个领域外,其他哲学问题也得到学者们的注意,比如张立文、谢晓东、陈壁生等教授就关注朱子的政治哲学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对朱子政治哲学加以论述。苏费翔教授则在“道统”问题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其《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30]重新检索唐代文献,发现在唐代就有了“道统”一词,纠正了以往学术界的看法。
朱子和其他思想家的比较研究,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朱子与其前辈、同辈的关系研究,依旧被大家重视,与王阳明等之后的思想家的关系也进一步得到讨论。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丁为祥教授《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31]一书,该书从发生学的视野出发,依据朱子文本与相关文献,在充分吸纳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扣朱子的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展开对朱子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深入考察,尤其是该书上篇梳理了朱熹从出身、师承到学术性格及其思想谱系的形成,并通过朱熹与张栻、陆象山、吕祖谦、陈亮的理论论辩以及朱熹对《四书》的集注与具体探讨展现其思想体系,对朱子和前后思想家的关系有着细致的论述。此外,该书也关注了朱子之后的思想家,尤其是民国思想家对朱子的诠释。
同样关注民国学者对朱子诠释的还有乐爱国教授,其“百年朱子学研究”一课题,就关注近百年来学者对朱子的诠释,近些年来乐教授陆续发表了相关论文,或探讨民国时期对朱子某个问题的探讨,如理气、理生气,或探讨某个人物对朱子的研究,如谢无量、牟宗三等。
近些年,最为突出的朱子哲学研究,也最能体现朱子学“走向未来”特质的,则为用朱子学回应时代问题以及从朱子学出发建立新的哲学体系的努力。
朱子学中的很多资源,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依然有其意义,值得我们抽象地继承。特别是“理一分殊”这一命题,就可以被用来处理全球化时代普遍性与多元性、世界性与地方性的关系。黄俊杰教授有《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一文,认为“为了适应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我们可以跃入传统的巨流中,汲取新时代的灵感。在中华文化与思想传统之中,南宋大儒朱子的‘理一分殊’说有其21世纪的新意涵,但在全球化时代各地互动的新脉络中,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在21世纪各文化传统所蕴蓄的多元之‘理’互相对话的新时代中,求同存异是一条必然的道路。传统中华文化重视‘同’而忽视‘异’。古代儒家就非常强调‘同’的价值”,“就21世纪大中华文化圈及其与世界之互动而言,如何开发求‘同’而存‘异’的价值观,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32]。
陈来先生《“水流无彼此,地势有西东”——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及其意义》[33]一文则从“理—势”的构架分析全球化问题,他认为“水流无彼此,可以表示各文明与文化的共通之理,强调交流与共享;地势有西东,可表达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价值差异性,尊重差异”,“‘理—势’分析的出现,既是为了强调人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清醒认识,更是为了强调人以及人的道德理想对历史的批判改造的功能。从前人们常说‘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历史潮流就是势。势或历史潮流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不一定是全然合理的,不是不可以引导的;但不顾历史大势,反势而行,逆历史潮流而动,则必然要失败。妥当的态度应当是‘理势兼顾’‘以理导势’,这是朱子学面对全球化的问题应采取的立场”。此外,陈来先生还有《朱子学的时代价值》[34]一文,专门从六个方面分析现代人从朱子的思想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陈来先生近些年对朱子学的关注从未间断。在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上,陈来先生关注朱子对《四书》的阐释,同时还关注朱子的一体性思维。在其《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35]《朱子四德说续论》[36]两文中关注朱子对于“四德”的阐释,认为“应当承认,朱子的思想不断发展出一种论述的倾向,即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如将其看作元气流行的不同阶段。由于天人对应,于是对仁、义、礼、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贞的模式发生变化,即仁义礼智不仅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气流行的不同发作形态”。更为重要的是,陈来先生还以其对朱子学的最新理解为基础,建构了其哲学体系,《仁学本体论》[37]正是陈来先生在这一方面贡献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迎来儒学的繁荣发展,作为民族哲学的儒学应积极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调整与挑战,面对中华民族的新发展,开拓出新的辩证吸收西方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并从儒家立场对世界和人类的普遍性问题给出指引。《仁学本体论》正是这样一部著作,它是中国哲学“接着讲”的当代典范,这样一部著作的出现具有其时代必然性。陈来先生能够创作出《仁学本体论》这样的著作,与其长久扎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尤其是对朱子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该书关注“仁”在中国思想当中历史的演进,尤其注意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对“仁”的阐释,吸收朱子以生生言仁、注重生气流行等特点,充分将传统的朱子哲学的思想要素转化为时代哲学。可以说,陈来先生的这一研究,为朱子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更加有助于利用朱子学的思想资源关注当下时代的发展、关注人类未来的走向。
三、经学研究的升温
朱子经学是中国经学史的重要一环,他继承汉唐经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但在根本气质上与之不同。朱子基本上遍著群经,对各经都有论述。其经学著作更是成为后代科举考试的标准。清代考据学兴起,清儒虽然不同意朱子经学的阐释,但在研究上也绕不开朱子的经学著作。在以往的朱子学研究中,经学不是一个关注热点,而近些年,经学研究不断升温。
朱子所著的《四书集注》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教科书,“《四书》学”因此是朱子经学研究中的重点。
在《四书》与“五经”的关系上,陈壁生教授有《朱熹的〈四书〉与“五经”》[38]一文,他指出朱子“对《四书》的新解释,创造性地提出新的义理系统,其主旨在于求圣人之心,以提升个人道德;同时,又在此基础上改造‘经’的观念以及对五经的认识。汉唐经学求‘圣人之法’,朱熹把经视为‘圣人之心’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五经进行了内在化解读,将五经《四书》化。这样,五经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四书》总论方面,许家星教授有《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一文,指出朱子四书的形成贯穿其毕生,大致可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其间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或各书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应特别注意的是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至于《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包含丁酉年(1177)《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个不同时期、层次的著作,不可视而为一。顾宏义教授出版了《宋代〈四书〉文献论考》[40]一书,该书专为考辨两宋时期《四书》著述与相关文献而作。分为上下编,上编论及《四书》文献兴盛的社会背景、出版传播及其与程朱理学的发展等,下编则具体对宋代学人有关《四书》的著述进行逐人逐书的考证,廓清了有关《四书》记载的讹误和缺失。闫春则有“从朱子到朱子后学:元明清四书学研究(2014)”一课题,尝试将朱子及朱子后学四书义理的动态演进问题予以凸显。
在《四书》各个文本的阐释上,《大学》的“格物致知”论一直以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近些年依旧如此,前述上海学者对朱子工夫论重视即是一例。此外如杨祖汉教授《西方认识论还是儒家工夫说——谁误读了“格物致知”?》[41]一文,从中西哲学对比的角度揭示朱子“格物致知”的含义,现代学人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逻辑体系是“误读”了朱熹。在朱熹思想体系中,格物致知论并不能等同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而是关于如何实现和完成修己治人的工夫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的作用被研究者夸大了,如乐爱国教授就重视朱子的《中庸》诠释。乐爱国教授有《朱子〈中庸章句〉论“诚”及其与“三达德”“五达道”的关系》[42],从“诚”出发,尝试系统分析朱子的《中庸》解释;又有《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43],关注朱子思想背后的生态观;又有《“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44]一文,认为朱子思想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近些年,乐爱国教授特别强调《中庸》在朱子思想结构中的地位。此外,围绕朱子《四书》具体章句的义理分析的论文更是层出不穷,本文不一一列举。
在“《尚书》学”研究方面,陈来先生有《“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45]一文,指出“在经典的诠释上,朱子对‘极’的解释最早为中年时代对《太极图说》的解释;在朱陆太极之辩中朱子承继和发展了其关于‘极’的理解,形成一套有关‘极’的理论,并在讨论太极之义时论及皇极之义。在朱陆太极之辩后不久所作的《皇极辨》之中,朱熹把这一套理解运用于皇极说作为一种基础,又以君主正身修身的儒家表率说把‘建用皇极’的意义具体化,形成朱子学的皇极说。皇极说既是朱子政治思想的一个论述,也同时可以看作其哲学太极论的相关部分,在后世发挥了持续的影响”。陈先生将朱子对经典的诠释及其义理阐发之间的关系充分地展现了出来。此外,陈良中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朱子〈尚书〉学研究》[46]一书,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宋代《尚书》学背景下的朱子《尚书》学,尤其是其理学诠释特色,考察了朱子对《尚书》阐释的历史,以及解经方法和价值取向,并关注朱子阐释与蔡沈《书集传》的关系,考察了朱子《尚书》学的影响。
礼学则是朱子经学研究这几年来特别突出的一个面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朱子的礼学,尤其注意探讨“礼与理”的关系。如冯兵教授《“理”“礼”会通,承扬道统》[47]一文,认为朱子“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辩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殷慧、张卓合写的《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48]一文,则从朱子的《大学》诠释出发,认为“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两文一从朱子的思想系统出发,一从朱子的经典诠释出发,代表了理解“礼”与“理”关系的两个向度。
张凯作博士《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49]一文着重论述朱子以“理”出发的“礼”学和前代礼学的继承关系,在她看来,“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朱子对古代礼教的最主要的传承即在于他对个人心性修养之学的发扬”。
与哲学上的鬼神问题直接相关,有学者关注朱子对于祭礼的讨论,尤其是其理学思想与儒家传统祭礼之间的张力。如殷慧教授《祭之理的追索——朱熹的鬼神观与祭祀思想》[50]即认为,“朱熹从义理层面论述了祭祀与鬼神的关系:强调鬼神的本体论意义,重视其天地转化的功能;认为鬼神既是阴阳二气物质,也是二气相互作用、转化的功用与性质。朱熹的祭祀思想与实践引人注目,强调义理与礼制并举”。
在《孝经》学方面,唐文明教授有《朱子〈孝经刊误〉析论》[51]一文,他认为“《孝经刊误》表达了朱子试图将《孝经》纳入其四书学的努力,而从《孝经刊误》的后世影响来看,朱子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过,如果考虑到《孝经》本来的思想旨趣,我们不能不说,朱子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陈壁生教授《〈孝经〉学史》[52]一书第六章第一节也专门讨论了朱子的《孝经》诠释。
《易》学一直以来是朱子经学阐释的另一重镇,尤其是围绕着《周易》展开的义理诠释,以往对朱子《易学》的研究较为充分,而近些年的研究热点则不太明确。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对朱子象数易学研究得不是太多,陈睿超博士《略论朱子之先天〈横图〉》[53]则特别关注这点,文章认为“朱子在虽在易学研究方面对北宋邵雍的先天易学推崇有加,但处于其对先天学理解之核心的先天《横图》却并非对邵雍原旨的忠实继承。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横图》中两仪、四象、八卦的名称与邵雍《观物内篇》所述不同;第二,《横图》八卦卦序与《观物内篇》所述不符;第三,《横图》变换为《圆图》的过程有涉安排,不够自然;第四,依《横图》卦序对《圆图》顺逆方向的解释与邵雍本意有异。朱子对邵雍的先天学并非完全继述,而有自己的改造与发挥,不加区分地以朱子之《横图》解释邵雍易学思想的做法是不够严谨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关于朱子经学研究已经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但还是有一些不足。如《仪礼经传通解》仅在文献上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而对其义理阐发则远远不够。在《诗经》学方面,学者们主要侧重在对《诗集传》赋比兴等手法的研究以及朱子诗论与其他人的比较上,相关哲学义理性阐发则很有限。朱子虽然未注《春秋》,但其有《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传世,并对东亚产生重要影响,而关于该书也缺乏文献、义理的进一步关注。
四、大陆以外的朱子学研究
(一)港台
长久以来,牟宗三关于朱子学的论断在港台占有一定的统治地位。而近些年来,港台朱子学的发展,则与对牟宗三相关观点的反思有密切关系。牟宗三从康德哲学出发,认为陆王哲学是自律道德,而朱子学是他律道德,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陆王高于朱子。牟先生的一些弟子,观点已经开始与其不同。在2009年,杨祖汉教授发表了《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一文,认为朱熹之言敬是由敬“契入本心”,而恭敬亦是“道德心本有之内容”[54],从朱子的“敬”出发,就不会认为朱子的思想是他律。2014年12月4~5日,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一次“朱熹与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及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杨祖汉教授发表《朱子与康德敬论的比较》一文,顺承上文思路,认为朱子学说虽不讲心即理,但心可以知理,心依旧能够提供道德实践的动力,不必像牟先生所讲,只有心即理才能提供道德实践动力。我们可以看到,杨祖汉教授已经极大修正了牟宗三先生的论断。但我们依旧可以指出,杨祖汉教授的观点依旧在牟先生的框架当中,只不过将牟先生所认之他律修正为自律而已。
与杨祖汉教授不同,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杜保瑞教授则对牟宗三先生的理解做了更大的反思,以其对中国哲学的结构性解读重新阐释朱子学。杜保瑞教授最近一系列论文均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认为牟先生没有区分清楚朱子的论述到底是讨论存有论、宇宙论、工夫论,还是境界论,以至于混淆了朱子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对朱子思想做出了错误解读。例如杜教授在《对牟宗三诠释朱熹心性情理气论的方法论反思》[55]一文中针对牟先生《心体与性理》中的一些结论性论述,认为牟先生借明道、濂溪讲神体,朱熹之解释虽符合明道、濂溪之义,却与朱熹一向的不活动的理、神说不合,这反而是牟先生割裂存有论和本体宇宙论及本体工夫论的错误诠释;牟先生讲朱熹的心性情说,以为朱熹讲心者气之灵爽,就是连着阴阳气化的人存有处讲,不能超越至圣境,这还是把存有论当成不活动的工夫论讲的错置,于是对朱熹做了有道德性减杀、无创生义和不能由体及用的批评。杜保瑞教授的研究代表了港台朱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一方向值得大陆学者注意,对于杜教授的观点似乎可以在学界展开进一步讨论,一是杜教授对牟宗三之评价是否符合牟宗三本身的理解,二是其对朱子的结构性诠释是否符合朱子思想本身的逻辑。杜保瑞教授的研究揭示的面向具有很强的哲学史意义。
与反思牟宗三先生对朱子的解释相关的则是唐君毅研究路向的重新得到重视。在2014年香港会议上,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宗义教授发表《比论唐君毅、牟宗三对朱子哲学的诠释》一文,强调新儒家中另一重要人物唐君毅对朱子研究的意义,其朱子哲学诠释虽散见于《中国哲学原论》之《原教篇》《导论篇》《原性篇》及《原道篇(卷三)》等书中,论述之集中程度及篇幅或不及牟宗三,“然其中一些闪烁的洞见,则隐然提示了一套足可与牟氏解读相抗手的诠释体系”,他认为“通过比论唐、牟对朱子哲学的不同看法,来将唐氏提示的诠释体系做一初步的梳理、发挥与建构”。也就是说,即使在新儒家内部,也不仅有牟宗三一种思路可供选择,还有别的路向可作为研究朱子学的重要资源。
当然在港台学者内部,依旧日有学者坚持牟宗三先生对朱子的相关诠释,这方面主要以李明辉教授和李瑞全教授为代表。
港台学者对于朱子的研究也还有别的路向打开。比如说陈荣开教授就关注朱子的经典诠释,尤其是朱子对于《中庸》的阐释,细致分析朱子每章的注解。更值得注意的则是黄俊杰教授组织主持的“东亚儒学的新视野”这一项目下有关朱子学的研究。该项目将儒学放置于东亚文明的演进发展当中予以关注,黄俊杰教授以为,“近七百年来东亚各地儒者可以阐释朱子,可以批判朱子,但不能绕开朱子”,朱子可以说是东亚儒学展开的重要人物,但是东亚儒学的发展在部分研究者看来,却不能将中国视为中心,应该“去中心化”。这点也提醒我们注意,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作为前现代东亚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地位究竟如何?我们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以及今日所谓“去中心化”可能导致的思想后果。大陆学者似乎应该以新的视角解释清楚朱子学在东亚历史上的实际地位。
(二)日韩
东亚儒学圈的展开,主要是以朱子学为核心,朱子学早在前现代时期就已经走出中国,走向东亚,深刻影响着日本与韩国的政治文化,朱子学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日韩思想史内在的问题,而不是异己的文化传统。
1.韩国朱子学研究
历史上韩国朱子学主要以三大论辩为主,即四端七情论辩、湖洛论辩、心说论辩,朱子学的内在逻辑问题在韩国以独特的形式展开、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涌现出李退溪、李栗谷、宋时烈等一大批朱子学者,韩国朱子学的论辩基本上在这些思想间之间展开。韩国还有专门的退溪学会、栗谷学会,专门推动相关人物和问题的研究。而近些年来,韩国朱子学研究也主要围绕着对这些人物和问题的研究展开。
关于栗谷学派,李基镛在《栗谷学派的理气论》一文中,把《栗谷全书》中的理气关系整理为以下几种说法:一、有从理而发者(竖说):有从气而发者(横说);二、就理上求气(竖说):就气上求理(横说);三、推本之论(竖说):沿流之论(横说);四、推本其所以然或极本穷源(竖说):于物上观或以物上观(横说);五、因有形之物,而可见其理之费处也(竖说):以复卦言之,则一阳未生之前,积分之气,虽在于地中,而便是难看处也(横说)。这说明了理气之不相离和不相杂的关系,也就是栗谷所谓的“理气之妙”。[56
《朝鲜朝“朱子学”——理气心性论在韩国儒学中的发展趋势》一文,以“朱子学的理同”“栗谷学的理通”“洛学的性同”“北学派的人物均论”为中心,讨论了栗谷的“理通气局论”与湖洛论争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进而探讨了以“人物性同异论证”为中心建立的洛论界思想基础、洛学和北学的思想背景以及韩国近代韩国思想史的哲学基础和其趋势。
四端七情之辩一直以来是韩国朱子学研究的重点,也为中国学者熟知,很多中国学者也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中,研究成果最多。关于退溪学派,韩国学者还是比较关注对这一问题的阐发。郑相峰在《退溪对朱子哲学的理解与其特色》的论文中,深入探讨了退溪说过的“理之动静”“理发”“理到”的思想。[57]崔英辰教授的《关于退溪四七理气互发论之渊源的考察——以洪治的〈心学章句集注大全〉为主》一文,认为“在韩国一般学术界里,洪治与退溪的思想传承几乎不被重视,是因为洪治之著作因当时的政治士祸而消失,并且他的著作依然有后代之伪作的嫌疑。崔英成主张学者把洪治的《心学》看作伪书是没有根据的,当今学者应当以更严密和理性的态度再分析《心学》的真伪问题和意义内涵”。[58]此外,韩国学者还重点关注退溪与其辩论对手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如崔英辰教授《退溪与高峰四端七情论辩中“四端无不善”和“四端有善恶”的冲突》一文就关注了退溪与奇高峰的辩论。诸如此类文章,一直是这些年韩国儒学的研究重点。
心说论辩和湖洛论辩在之前一段时间并不被学者重视,研究得也不是太多,而这些年研究则逐渐升温。韩国的栗谷学会在2013年6月召开了“人的本性与心的根本”学术大会,学者们综合探讨了从栗谷以来形成的“湖洛论争”的主要概念及哲学含义。在2015年厦门召开的“百年东亚朱子学学术研讨会”上,宣炳三先生专门提交《洛湖论辩研究成果及展望》一文,指出21世纪以来关于洛湖论辩思想渊源的研究成果大幅增加,课题更加丰富,比较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崔英辰教授则提交《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状及展望》一文,指出韩国朱子学者试图用理气论的概念来定义人类的心性,韩国朱子学的三大论争是始于对心性情理气论的规定,而相关比较研究,尤其是中日韩关于相关问题的比较性研究,则可以进一步推进。这一点也值得中国学者注意,尤其是如何在和韩国朱子学的对比中理解朱子思想的意义以及中国朱子学的走向问题。
此外,韩国学者还对其他哲学问题有密切关注,比如关注退溪的教育思想,关注栗谷的经世思想,如栗谷学会特别重视推广栗谷的蒙学著作《击蒙要诀》并加强与中国思想界沟通来共同研究这一蒙学著作的时代意义。
2.日本朱子学研究
早在13世纪初期,朱子学就已经传入日本,进入江户时代,朱子学在日本开始兴盛,涌现出藤原惺窝、林罗山、贝原益轩等一批思想家。传统的日本朱子学研究侧重于对朱子学文献的阐释,并借由文献的解释阐发义理,关注“理气心性”等问题。而战后的日本朱子学研究则侧重于文献研究,思想研究的成果远较文献研究的成果要少,这些年情况更为明显,日本学者“形而下”的取向越来越明显,而较少关注以“理气心性”等问题为核心的“形而上”向度,这与日本近代以降重新构造其东亚叙事有密切的关系。591
日本学者擅长考证工夫,这点历来被学者重视。近年来这方面成果也较多,前述吾妻重二先生对《朱子家礼》的考辨就是一例。此外,鹤成久章有《〈四书纂疏〉所引の朱子学文献について:〈朱子语录〉を中心に》(《〈四书纂疏〉引用的朱子学文献:以〈朱子语录〉为中心》,2014)一文,考察了《四书纂疏》的成书年代以及《纂疏》所收朱熹及其后学13人文献的情况,特别注意《四书纂疏》所引《朱子语类》,指出了数量在2000条以上的《四书纂疏》所引朱子的语录的一些特征,发现《四书纂疏》所用语录与传世文献的一些差异。2014年儿玉宪明作《朱熹律吕新书序注解》一文,对朱子《律吕新书序》做校勘、日译和注释。日本学者对朱子学涉及的语言学等问题,尤其是与日语相异的语言问题,也有较多的关注。
在义理学方面,木下铁矢于2013年出版《朱子学》一书,可以说是义理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作者不赞成把朱子理解成二元论者,认为朱子力图打破理气、阴阳等二元对立,“心”的阐释可以说是朱子突破二元对立的枢纽。此外,日本学者长期以来关注对朱子鬼神问题的讨论,这一点在日本的朱子学研究上十分突出。牛尾弘孝先生在2010年曾写书评,专门回顾了日本学者对鬼神问题的相关讨论,2013年又专门作《朱熹的鬼神论的构造》一文,从“理生气”与“屈伸”两个层次,阐释朱子的鬼神观,并对祭祀问题加以讨论。
在日本朱子学方面,土田健次郎教授2014年出版的《江户的朱子学》一书可以说是近些年研究的代表。该书详细讨论了朱子学本身,以及朱子学进入日本思想史之后的问题与演进,认为日本思想史学者对朱子学理解不深,没有把握朱子学的特质,没有看到朱子学在理气论构架下做出的哲学贡献。该书还讨论了朱子思想与日本本土思想的关系,诸如“敬”与“神道”,认为朱子学已经进入到日本的“日常”当中,并从这一思路出发,详细讨论了日本反朱子学者,如伊藤仁斋对朱子学的理解与批判。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吾妻重二先生以“文化交涉学”的视角关注东亚朱子学的相关问题,勾勒了东亚儒学和东亚朱子学的多个侧面,关注“以儒教为中心的知的世界”。在吾妻重二先生看来,“朱子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进而言之,也无妨称其自身拥有着一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广度。因而,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哲学史中,还要在教育史、礼仪史乃至于人类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理解朱子学”。吾妻先生强调文化是在不同地域之间不断流动的,他本人就是在这样的理解下诠释朱子学跨地域的文化特质。
3.欧美
欧美的朱子学研究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亮点,其研究,既有针对朱子学本身的讨论研究,又有引入比较哲学的视角、进行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
英美汉学界对朱子的研究较为偏重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艾周思出版《儒家之道的重建:朱熹对周敦颐思想的运用》60]一书,从宗教实践的角度探讨朱子对周敦颐思想的发展,并对主要文献进行了翻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田浩教授可以说是美国朱子学界的代表,之前就有关于朱子和陈亮的两本专著问世。2011年田浩教授出版了《旁观朱子学》[61]一书,收录多篇其观察朱子以及南宋思想的文章。同时,田浩教授还关注朱子学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对朱子学的一些当代实践进行了思考,与其女儿田梅一起写成《礼之殊途:〈朱子家礼〉现代化与恢复古礼的践行——以当代儒家婚礼为视角的分析》一文。他还与殷慧合著《从〈五经〉到〈四书〉——以宋代礼理的突破与融合为中心》[62]一文,关注朱子思想中“礼”和“理”的关系。田浩教授对朱子学的关注可谓是多方面的。在他的推动下,2012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专门召开了朱熹经学研讨会。此外白朗诗教授的《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和南乐山的比较研究》[63]一书于2011年翻译成中文,该书从比较哲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怀特海、朱熹和南乐山那里会有创造性这一观念,以及为什么对于比较过程思想来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法国,值得关注的是戴鹤白教授专门将《戊申封事》翻译为法文[64,并写专文对朱子的封事进行讨论(《论朱熹的〈庚子应召封事〉和〈辛丑延和奏札〉》,2012年)。2012年杜杰庸、戴鹤白还合译了朱子和陆九渊的通信《太极之辩》。
德语学界则更多地关注朱子本身的哲学问题。前文提到的苏费翔教授就是德语学界研究朱子的一个新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研究了朱子的道统观,还关注朱子弟子之间的争论(《〈近思录〉〈四子〉之阶梯——陈淳与黄榦争论读书次序》,2012年),近些年还特别注意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朱子思想。苏费翔等人还一同将《朱子家训》翻译为德文(2011年)。2015年7月特里尔大学专门和华东师范大学一起主办了“朱熹与他的革新:创新、社会改革与认识论”会议,欧美汉学界与中国大陆研究朱子和宋明理学的学者齐聚一堂,探讨朱子学的相关问题。
此外,澳洲学者梅约翰主编了《理学家哲学的“道”的指南》(2010年),收录了不少关于朱子研究的成果。
有关朱子学的研究不只以上这些内容,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注意。比如说余英时教授出版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之后,学者们陆续开始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朱子学进行相关研究。此外,朱子学的世俗化进程也拓展了朱子学的当代面向,使朱子学的当代境况不同于其他中国传统哲学。自2005年开始,世界朱氏联合会与闽北朱氏宗亲会联合中国、欧美等高校,组织学者和青年学生开展“朱子之路”活动,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促进当代青年对朱子进一步了解。在世俗化方面朱杰人教授“朱子家礼之婚礼的现代实验”特别值得关注,他以实际的操作探讨求证时至今日《朱子家礼》是否仍有生命力,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婚俗是否可以对全盘西化发起一次挑战,以寻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可以说,朱子学的世俗化努力已经使朱子学走出了纯粹的书斋式的研究,促使朱子学以及儒学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以上简要总结了2011年以来朱子学的发展情况,可以说,朱子学的研究在各个领域稳步推进,朱子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属于当下的,也是属于未来的,朱子学也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朱子学的研究为中国哲学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典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附注
注释:
[1]为了避免因笔者的误读,而扭曲了作者的本意,故摘要之方式尽可能使用作者原有的论述说明,而不加上笔者自身的诠释于其中。
注释:
[1]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of2017.
注释:
[1]上述内容与“日本儒教学会设立旨趣”所述内容相同,“设立旨趣”在日本儒教学会的网站上可以阅览(不过仅有日文,http://nichijyu.gakkaisv.org/)。
[2]研讨会上各位登台发言者所述内容,将刊登于预订2017年2月在网上向学会成员公开的《日本儒教学会报》创刊号。
[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柳田深受近世后期激烈抨击佛教的平田笃胤(1776~1843)的国学思想之影响,对于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中佛教的比重是打了很大折扣来把握的。
[4]代表性的例子有:佐藤弘夫(东北大学教授)认为,柳田式死生观不是日本人自古而来的观念,而不过是“江户时代以后逐渐形成的观念”,他举出在退回他界,即向佛教式净土的往生受到广泛信仰的中世、公然遗弃骨骸等的古代事例,强调了日本人的死生观之多样性与重叠性(《死者のゆくえ(死者去向)》岩田书院,2008年)。
[5]不过根本而言,还需考虑吉川惟足本人是属于在朱子学的决定性的影响下形成的神道思想之一派——吉田神道的人物。自从作为吉田神道的集大成者,支配着中世后期神道界的吉田兼俱(1435~1511)以来,朱子学与神道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6]关于在近世日本从基于《文公家礼》的儒葬向神葬转移的过程,近藤启吾《儒葬え神葬(儒式葬礼与神道式葬礼)》(国书刊行会,1990年)介绍了其梗概及丰富具体的事例,开展了先驱性基础性的研究。其后,从神道学立场出发,研究进一步深化,其成果收在加藤隆久编《神葬祭大事典》(戎光祥出版,1997年)中。在该辞典的“神葬祭的进程”“神葬祭”等9个关键词中多处言及了朱子学式的葬礼祭礼。
注释:
[1]以上の内容は、ほほ、「日本儒教学会設立趣意書」と同旨であり、「趣意書」は日本儒教学会ホームページにて閲覧できる(ただし日文のみ、http:// nichijyu.gakkaisv.org/ )。
[2]シンポジウムでの各登壇者の発表内容については、2017年2月にweb上で学会員に公開予定の『日本儒教学会報』創刊号に掲載される。
[3]ただし、柳田は近世後期にイ厶教を激しく排斥した平田篤胤(1776~1843)の国学思想の影響を濃厚に受けており、日本人の精神世界におけるイ厶教の重みを相当割り引いて捉えている点には、注意が必要である。
[4]代表的なものとして、佐藤弘夫(東北大学教授)は柳田的な死生観を、日本人の古来の観念ではなく「江戸時代以降に徐々に形成された観念」に過 ぎないものと捉え、他界への退去、すなわちイ厶教的浄土への往生が広く信 じられていた中世や、平然と遺骸を遺棄していた古代など、日本人の死生観の多様性・重層性を強調している(『死者のゆくえ』岩田書院、2008 )。
[5]ただしそもそも、吉川惟足自身力ヾ、朱子学からの決定的な影響を受けて成立した神道思想の一派である吉田神道に属する人物であることも考慮し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吉田神道の大成者であり、中世後期の神道界を支配した吉田兼倶(1435~1511)以来、朱子学と神道とは不可分の関係だったの である。
[6]近世日本における『文公家礼』に基づ‘く儒葬から神葬への移行過程については、近藤啓吾『儒葬と神葬』(国書刊行会、1990)がその概要と豊富な具 体的事例とをともに載せ、先駆的かつ基礎的な研究をなした。その後、神道学の立場から研究が深められ、その成果として加藤隆久編『神葬祭大事典』(戎光祥出版、1997)が編纂された。本辞典の「神葬祭のあゆみ」「「神葬祭」九つのキーワード」のうちに、朱子学の葬祭についての多くの言及 が見られる。
注释:
[1]《朱子语类》卷三,吕焘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页。
[2]同上书,第35页。
[3]岛田虔次(1917~2000),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教授。著有《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筑摩书房,1949年初版)《朱子学と陽明学》(岩波新书,1967年初版)《中国思想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初版)等,以上三书皆有中译本。岛田虔次对朱子祭祀感格说的考察,见于氏著《大学·中庸》(朝日新闻社,1967年)的《中庸》第十六章的解说中。
[4]收录《朱子学の伝来と李退渓の朱子学の特色》《李退渓の〈自省録〉について》等。
[5]收录《李退渓と崎門学者楠本碩水》《楠本碩水》《大橋訥庵の〈闢邪小言〉について》《小笠原敬斎略伝·資料》《春日潜庵による〈叢山人譜〉〈王心斎 全集〉》等。
[6]川原秀城,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名誉教授。著有《朝鮮数学史——朱子学的な展開とその終焉》(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10月)等。
[7]此外,川原秀城氏最近又编有《高橋亨朝鮮儒学論集》(知泉书馆,2011年)。高桥亨(1878~1967)是京城帝国大学教授,也是近代日本朝鲜儒学研究先驱。以“主气派”“主理派”来分别朝鲜朱子学者的思想倾向,即出自高桥亨。本书收录的《朝鮮儒学大観》一文用简括的语言,勾勒了从高丽王朝到李氏王朝的朝鲜儒学的发展历程,《李退渓》一文则详细介绍了李退溪的生涯和思想,李朝儒学史に於ける主理派主気派の発達》一文首次提倡用“主理派”“主气派”的框架分析朝鲜朱子学,影响深广,沿用至今。以上论文皆为朝鲜朱子学研究史上极其重要的论述。
[8]吉田光男,放送大学教养学部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有《《近世ソウル都市社会研究——漢城の街と住民》(草风馆,2009年3月)等。
[9]种村和史,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教授。另,种村氏《诗经》研究的相关论文,可在此链接下载:http://koara.lib.keio.ac.jp/author-list/66-0006553.htm。
[10]《〈詩本義〉に見られる欧陽脩の比喩説:伝箋正義との比較という視座で》,《藝文研究》第87号,2004年,第104~127页。
[11]吾妻重二,关西大学文学部综合人文学科教授。著有著有《朱子学の新研究—— 近世士大夫の思想史的地平》(创文社,2004年9月)、《宋代思想の研究—— 儒教·道教·イ厶教をめぐる考察》(关西大学出版部,2009年4月)等。本文可在以下链接下载:http://kuir.jm.kansaiu.acjp/dspace/handle/101 [12]10109[12]浅见?斋(1652~1712),生于近江国(今滋贺县)。师从山崎暗斋,为“崎门三杰”之一。和刻本《朱文公文集》等众多朱子学文献的校点出版都出其手。日本刊刻中国古籍通常施加训点(这一工作也称“校点”),读者据以用日语之语法读通中国古典。
[13]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有“家礼五卷”的记载,从中可知《朱子家礼》原本为五卷。
[14]三浦秀一:《明代中期の〈性理大全〉——東北大学図書館蔵本の書誌学的意義に寄せて》,《集刊東洋学》第109号,2013年6月。
[15]松野敏之,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副教授。著有著有《王夫之思想研究——〈讀四書大全説〉における“作聖之功”議論を中心にして》,早稻田大学出版会,2010年。
[16]《小学》一书或说朱子自著,或说出自刘清之之手。松野氏认为,今本《小学》即便曾经刘清之之手,大体仍是据朱子的编纂方针编定成书。详参《朱熹〈小学〉編纂考——劉清之小学書からの改修に関してー》,《論叢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第13号,2004年12月,第1~26页。
注释:
[1]见拙文:《2015年美国朱子学研究综述》,《朱子学年鉴(2015)》,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51~153页。
[2]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主讲:《王梦鸥教授学术讲座演讲集2015》,台北: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2016年。
[3]Yang Shao-yun.“Reinventing the Barbarian:Rhe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Usesof the Yi-Di in Mid-Imperial China,600~1 300”,Ph.D.diss.University ofCalifornia,Berkeley,2014.
[4]Ibid.,PP.373.
[5]田浩主讲:《王梦鸥教授学术讲座演讲集2015》,第76页。
[6]Zheng Shuhong,“Intellect and Will in Zhu Xi and Meister Eckhart”,PhilosophyEastandWest66.4(2016):1319~1339.
[7]David Jones and Jinli He ed.,Returning to ZhuXi:EmergingPatterns withintheSupremePolari ty,New York:SUNY Press,20 1 5.
[8]Wong Pui Fong, “From Solitude to Solidarity:A Neo-Confucian Appropriation of Centering Prayer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lf”, 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20 1 6.
注释:
[1]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朱子学年鉴》相关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并对提供相关资料的各位教授尤其是朱人求教授表示感谢。
[2]朱人求:《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朱子学年鉴(2011~2012)》,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3]《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初版,2010年修订再版。
[4]《朱子全书外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5]《朱子著述宋刻集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6]邓艾民:《朱熹与〈朱子语类〉》,《朱子语类》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10页。
[7]胡秀娟:《〈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8]徐时仪、杨燕:《朱子语类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9]〔日〕桥本秀美、叶纯芳:《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1年。
[10]〔日〕桥本秀美、叶纯芳:《影印宋刊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1]〔日〕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12]吴震:《朱子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巅峰之作》,《中华读书报》,2012年8月22日第9版。
[13]陈来:《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序》,载于陈荣捷《朱子门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14]〔日〕藤井伦明:《朱熹思想结构探索——以“理”为考察中心》,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
[15]乔清举:《论朱子的理气动静》,《哲学动态》,2012年第7期。16]杨立华:《体用与阴阳:朱子〈太极图说解〉的本体论建构》,《哲学研究》2012年第10期。
[17]丁为祥:《从生存基础到力动之源——朱子哲学中的“气”论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8]吴震:《鬼神以祭祀而言——关于朱子鬼神观的若干问题》,《哲学分析》,2012年第5期。
[19]冯兵:《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朱熹的鬼神观辨析》,《学术研究》,2013年第2期。
[20]王文娟:《朱子论感应》,《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21]魏义霞:《朱熹对仁的诠释》,《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
[22]赖尚清:《朱子早期仁论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3]向世陵:《“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孔子研究》,2011年第3期
[24]吴震:《朱子“心论”试析》,《儒家文化研究》第4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
[25]吴震:《敬只是此心自作主宰处——关于朱熹“敬论”的几个问题》,《哲学门》,第1 1卷第2册。。
[26] 吴震:《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27]吴震:《从政治文化角度看道学工夫论之特色——有关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28]李承贵:《对道德与知识的双重关切——朱熹“格物致知”论探微》,《贵阳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29]李敬峰、刘俊:《朱子的格物致知——一种可能的科技理性》,《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年第3期。
[30]苏费翔:《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31]丁为祥:《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32]参看《朱子学年鉴(2011~2012)》之《朱子学研究新视野》栏目。
[33]陈来:《“水流无彼此,地势有西东”——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及其意义》,2012年,http://blog.sina.com.cn/s/blog-4a03de990l0layu2.html。
[34]陈来:《朱子学的时代价值》,《光明日报》,2015年5月14日第15版。
[35]陈来:《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
[36]陈来:《朱子四德说续论》,《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
[37]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38] 陈壁生:《朱熹的〈四书〉与“五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39]许家星:《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1期。
[40]顾弘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41]杨祖汉:《西方认识论还是儒家工夫说——谁误读了“格物致知”》,《光明日报》,2012年3月6日。
[42]乐爱国:《朱子〈中庸章句〉论“诚”及其与“三达德”“五达道”的关系》,《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韩国成均馆大学,2011年第9期。
[43]乐爱国:《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44] 乐爱国:《“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江淮论坛》,2014年第6期。
[45]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46]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47]冯兵:《“理”“礼”会通,承扬道统》,《东南学术》,2013年第1期。
[48]殷慧、张卓:《朱熹理礼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49]张凯作:《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50]殷慧:《祭之理的追索——朱熹的鬼神观与祭祀思想》,《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1]唐文明:《朱子〈孝经刊误〉析论》,《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52]陈壁生:《〈孝经〉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53]陈睿超:《略论朱子之先天〈横图〉》,厦门大学“百年东亚朱子学”学术会议,2015年。
[54]杨祖汉:《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载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55]杜保瑞:《对牟宗三诠释朱熹心性情理气论的方法论反思》,2014,http://homepage.ntu.edu.tw/~duhbauruei/4pap/5mod/26.htm。
[56]《朱子学年鉴(201 1~2012)》,第143~144页。
[57]郑相峰:《退溪对朱子哲学的理解及其特色》,《朱子学年鉴(2013)》,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58]崔英辰:《关于退溪四七理气互发论之渊源的考察——以洪治的〈心学章句集注大全〉为主》,《朱子学年鉴(2013)》,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59]板东洋介先生《2013年日本朱子学研究综述》一文第一部分《概观》专门讨论了“对日本而言,朱子学意味着什么”,这可以反映当代日本学者对朱子学在日本的定位。参见《朱子学年鉴(2013)》,第155~156页。
[60] Joseph A.Adler,Reconstructing the ConfucianDao:ZhuXisAppRopriationofZhouDunyi,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 1 4.[61]田浩:《旁观朱子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62]田浩、殷慧:《从〈五经〉到〈四书〉——以宋代礼理的突破与融合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2期。
[63] 白朗诗:《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和南乐山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64]戴鹤白:《戊申封事》,2008年出版,2013年出版汉法对照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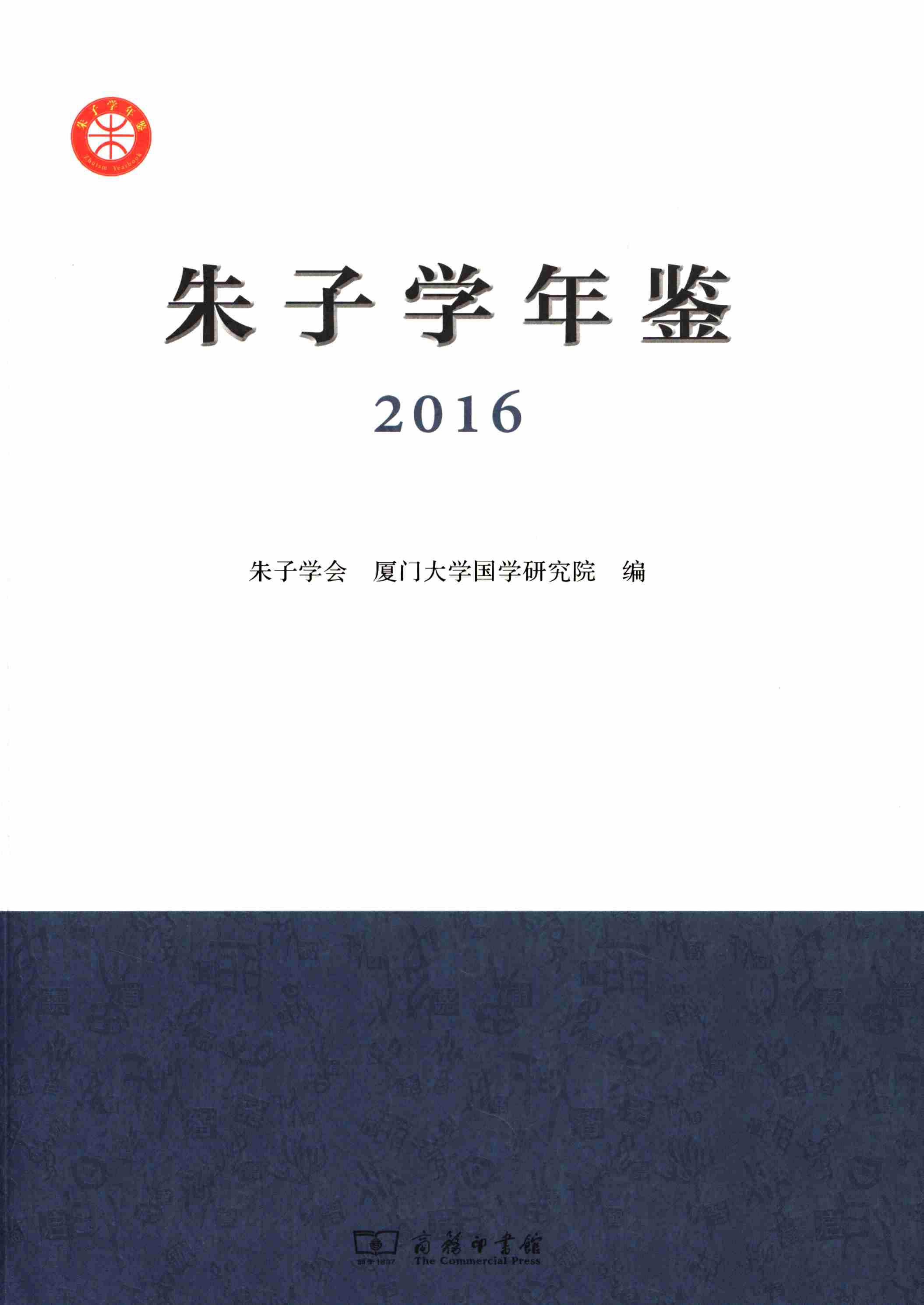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6》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年鉴内容设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9个栏目。
阅读